《说文解字》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价值
说文解字的价值和意义

《说文解字》及清代“说文”四大家10外汉一曾钰佳10260253《说文解字》简介与作者《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东汉许慎著,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
作者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献给汉安帝)。
《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
内容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540个部首,将9353字分别归入540部。
540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14大类,字典正文就按这14大类分为14篇,卷末叙目别为一篇,全书共有15篇。
《说文解字》共15卷,其中包括序目1卷。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六书。
造字法上提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所谓“六书”学说,并在《说文解字叙》里对“六书”做了全面的、权威性的解释。
从此,“六书”成为专门之学。
“六书”不能单纯的认为就是造字法,前四种象形、指示、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而转注和假借则为用字法。
体例《说文解字》的体例是先列出小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则在后面列出。
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再解释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
《说文解字》中的部首排列是按照形体相似或者意义相近的原则排列的。
《说文解字》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后世的字典大多采用这个方式,段玉裁称这部书“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
价值与意义(一)、《说文》在文字学研究中的价值1、《说文解字》是研究古文字的重要著作2、六书理论是汉子结构规律和发展规律的总结3、《说文解字》开创了以部首统率汉子的字典编排体例(二)、《说文解字》与古汉语词汇研究《说文解字》收录了上古汉语的大量词汇,保存了古义,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说文解字》和上古音研究1、《说文解字》与上古韵部研究2、《说文解字》与上古声母研究(四)、《说文解字》和古代文化研究《说文解字》的内容涉及了历史、哲学、军事、地理、天文、动物、职务、医学和人体解剖等,几乎无所不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类知识领域的各个方面,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简述《说文解字》的贡献

《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种书”。
其作者是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
《说文解字》对中国汉字的发展和研究做出了以下重要贡献:
1. 开创了部首检字法的先河: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首创了部首检字法,将 9353 个字归入 540 个部首之中。
这种检字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了汉字检索的基本方法。
2. 系统地分析了汉字的字形结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字形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将汉字分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六种类型,并对每种类型的汉字进行了举例说明。
这种分类方法对后世的汉字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考究了字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每个字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等进行了详细的考究,为后人研究汉字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4. 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化资料:《说文解字》中收录了大量的古代文化资料,包括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为后人了解古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窗口。
总之,《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对中国汉字的发展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座巍峨的丰碑”。
说文解字的意义和价值

说文解字的意义和价值《说文解字》是科学文字学和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字书,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辞书。
除此之外《说文解字》一书对于了解自然万物和汉代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面貌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1、第一,《说文解字》从上万个汉字中区别其偏旁和部首,分类归纳成五百四十个部类,开启了汉字按部首编排的汉字字典编排方法。
直至当今使用的汉语字典、词典,仍然使用部首检字法编排。
2、第二,《说文解字》在前记内容中首次阐释了“六书”的内容,横跨了六书的原则,许慎对六书分别下了定义,握了例字,后世谈六书都延用许慎的名称和定义。
3、第三,《说文解字》收录了汉字形体的多种写法,当时汉朝的篆体外,还有籀文、古文等异体写法。
这些字体大都为象形体。
这就为研究汉字提供了宝贵的古文字资料,也为推究上古文字的本义给予了较大的方便。
后世发现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简帛文字这些汉朝以前的文字,都是依据《说文解字》所收录的这些古文字字形作依据,才得以考证和认读。
所以《说文解字》是语言文字学的宝库,在文字、训诂和音韵等方面都显示出极大的价值。
《说文》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古字,同时还保存了大量的古义,它既是一部文字学经典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训诂学名著。
清儒将其奉为词义训诂的准绳,认为它在训诂学上的地位可以与《尔雅》相提并论。
段玉裁就说过:“《说文》、《尔雅》相为表里。
”直至现代,《说文》学仍然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无论是从事古汉语词义的专门研究,还是字典辞书的编纂,《说文解字》都是一部经常被援引的著作。
4、第四,《说文解字》一书留存了大量的古音资料,对于汉语语音史的研究,特别就是上古音的研究,具备关键的价值。
清儒在上古音研究方面获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就他们所依据的材料来看,主要存有两种:第一就是《诗经》等先秦文的押韵情况,第二就是《说道文》的谐声。
根据先秦韵文用韵的实际情况去概括上古韵部,所得出结论的结果虽然比较可信,但是,一方面,这样概括出的结果还须要其他方面的材料去检验,另一方面,由于上古韵文的进韵字非常有限,必须论定每个汉字的古韵部居,光凭韵文的材料还是很比较的,这就须要利用《说道文》的谐声系统去予以检验和补足。
说文解字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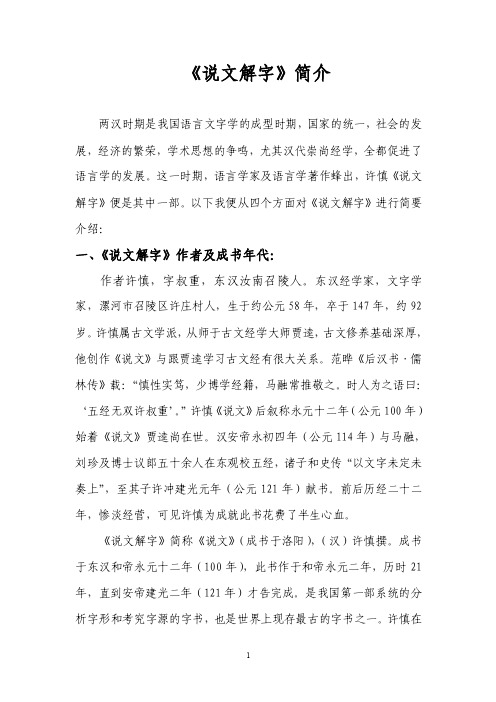
《说文解字》简介两汉时期是我国语言文字学的成型时期,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学术思想的争鸣,尤其汉代崇尚经学,全都促进了语言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语言学家及语言学著作蜂出,许慎《说文解字》便是其中一部。
以下我便从四个方面对《说文解字》进行简要介绍:一、《说文解字》作者及成书年代:作者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人。
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漯河市召陵区许庄村人,生于约公元58年,卒于147年,约92岁。
许慎属古文学派,从师于古文经学大师贾逵,古文修养基础深厚,他创作《说文》与跟贾逵学习古文经有很大关系。
范晔《后汉书〃儒林传》载:‚慎性实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
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
‛许慎《说文》后叙称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始着《说文》贾逵尚在世。
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4年)与马融,刘珍及博士议郎五十余人在东观校五经,诸子和史传‚以文字未定未奏上‛,至其子许冲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献书。
前后历经二十二年,惨淡经营,可见许慎为成就此书花费了半生心血。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成书于洛阳),(汉)许慎撰。
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此书作于和帝永元二年,历时21年,直到安帝建光二年(121年)才告完成。
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的字书之一。
许慎在病中遣其子许冲将此书献给皇帝。
二、《说文解字》的主要内容:《说文》不仅是一部古代文字学大典,而且也是一部‚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许冲《上(说文解字)表》语)的百科全书。
《说文》涉及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礼仪等,因而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史料价值极高。
它不仅有助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字的音、形、义,了解中国文字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也适合于了解和爱好中国文字学的读者阅读。
《说文》十四卷,又叙目一卷为十五卷,每卷分上、下共三十卷,收字9353,又重文1163,注文约十三万余字。
说文解字的价值

三、请你谈一谈《说文解字》的重要价值。
1、《说文》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
同时,它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文献语言学,《说文》就是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
《说文》对传统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巨大影响,后世所说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字,大体不出《说文》所涉及的范围,而《说文》本身则形成一个专门学科。
2、《说文》首次总结并阐发了六书的理论内容,并在《说文》中贯穿了六书原则,为汉字建立了理论体系。
《说文解字》是第一部系统地运用“六书”理论来全面考察汉字的开创之作,奠定了传统文字学的理论基础。
“六书”之目虽列在班书、郑汴,而最终确定“六书”理论的只有许慎一人。
因此,胡朴安在《中国文学史》中说:“六书之学说,当自《说文解字》始。
”钱大昕在《说文解字•跋》中说:“所赖以考见六书之源者,独有许叔重《说文解字》一书。
”这话十分精要地评价了许慎的历史功绩。
3、《说文》改变了周、秦到汉字书的编纂方法,将所收字编成四言、七言韵语的形式,首次从汉字系统中归纳出540部首,并创立了符合汉字自身特点的,按部首排列的汉字字典编纂法。
汉字部首,许慎独创,沿用至今,已逾1800多年,可见其生命力之旺盛。
如:江工的《古今文字》、张自烈的《正字通》、张玉书等编的《康熙字典》,都属于《说文解字》系统,可见许慎独创的部首分类对后世字典辞书影响极大。
王筠在《说文句读》中说:《说文》体例“独立千古,后世所宗”。
4、《说文》掌握并抓住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根本特点,创造了结合字义与字音分析汉字的科学方法,即先解释字义,再剖析形体构造,最后注明读音。
这种剖析字形的方法,是以前字书中没有出现过的。
许慎认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古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以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
《说文解字》正文全文十四篇每个字的下面都用简明的词语说明造字的方法,在文字发展史上他第一个回答了汉字关于形音义的根本问题,是千古未有的伟大创举。
中国传统语言文学

中国传统语言文学
中国传统语言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丰富的语言学、文学和历史等方面的内容。
在语言学方面,中国传统语言文学包括汉字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以及汉语的语法、音韵、词汇和修辞等方面的研究。
其中,《说文解字》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系统地总结了汉字的构造和含义,是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资料。
在文学方面,中国传统语言文学包括古典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多种形式。
古典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代表,如《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等作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
散文和小说也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形式,如《左传》、《史记》、《聊斋志异》等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此外,中国传统语言文学还包括对联、灯谜、谚语等民间文学形式,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等方面。
这些民间文学形式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总之,中国传统语言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它不仅是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也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书籍

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书籍
1. 《汉语语法史》(王力著):这是一本系统介绍汉语语法演变的著作,涵盖了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语法发展历程。
2. 《说文解字》(许慎著):中国最早的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种书”。
3. 《马氏文通》(马建忠著):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对汉语语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
4. 《音韵学教程》(唐作藩著):本书系统介绍了音韵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学习和研究音韵学的重要参考书。
5.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著):这是一本广泛使用的现代汉语教材,全面介绍了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知识。
6. 《古代汉语》(王力著):这是一本经典的古代汉语教材,详细介绍了古代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音韵等方面的内容。
7. 《中国语言学史》(王力著):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从先秦时期一直到现代,涵盖了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等多个领域。
8. 《汉语方言学教程》(游汝杰著):本书全面介绍了汉语方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学习和研究汉语方言学的重要参考书。
这些书籍在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深入了解汉语的历史演变、语言结构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推荐,中国语言学领域还有许多其他优秀的研究书籍,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进一步探索。
《说文解字》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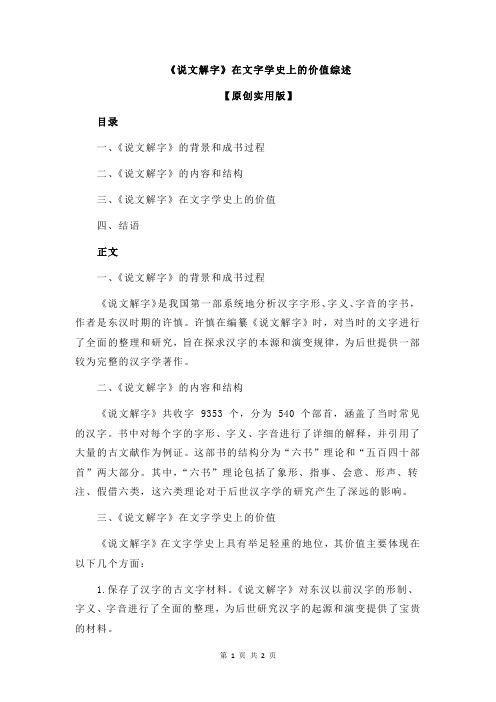
《说文解字》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综述【原创实用版】目录一、《说文解字》的背景和成书过程二、《说文解字》的内容和结构三、《说文解字》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四、结语正文一、《说文解字》的背景和成书过程《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的字书,作者是东汉时期的许慎。
许慎在编纂《说文解字》时,对当时的文字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旨在探求汉字的本源和演变规律,为后世提供一部较为完整的汉字学著作。
二、《说文解字》的内容和结构《说文解字》共收字 9353 个,分为 540 个部首,涵盖了当时常见的汉字。
书中对每个字的字形、字义、字音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并引用了大量的古文献作为例证。
这部书的结构分为“六书”理论和“五百四十部首”两大部分。
其中,“六书”理论包括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类,这六类理论对于后世汉字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说文解字》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说文解字》在文字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保存了汉字的古文字材料。
《说文解字》对东汉以前汉字的形制、字义、字音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为后世研究汉字的起源和演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2.系统地阐述了“六书”理论。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六书”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一理论对于汉字学、语言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促进了汉字规范化。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每个字的字形、字义、字音进行了规范,这一规范对于后来汉字的统一和规范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丰富了古代文化研究。
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古文献,对古代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书法视角看许慎《说文解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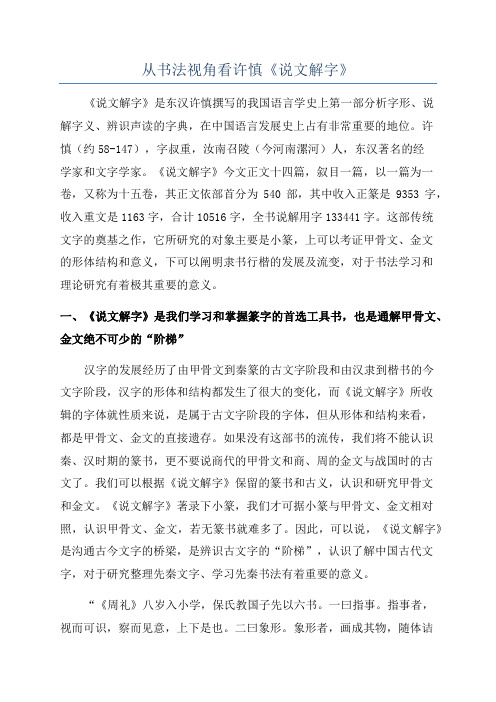
从书法视角看许慎《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撰写的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在中国语言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许慎(约58-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人,东汉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字学家。
《说文解字》今文正文十四篇,叙目一篇,以一篇为一卷,又称为十五卷,其正文依部首分为540部,其中收入正篆是9353字,收入重文是1163字,合计10516字,全书说解用字133441字。
这部传统文字的奠基之作,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小篆,上可以考证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和意义,下可以阐明隶书行楷的发展及流变,对于书法学习和理论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说文解字》是我们学习和掌握篆字的首选工具书,也是通解甲骨文、金文绝不可少的“阶梯”汉字的发展经历了由甲骨文到秦篆的古文字阶段和由汉隶到楷书的今文字阶段,汉字的形体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说文解字》所收辑的字体就性质来说,是属于古文字阶段的字体,但从形体和结构来看,都是甲骨文、金文的直接遗存。
如果没有这部书的流传,我们将不能认识秦、汉时期的篆书,更不要说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与战国时的古文了。
我们可以根据《说文解字》保留的篆书和古义,认识和研究甲骨文和金文。
《说文解字》著录下小篆,我们才可据小篆与甲骨文、金文相对照,认识甲骨文、金文,若无篆书就难多了。
因此,可以说,《说文解字》是沟通古今文字的桥梁,是辨识古文字的“阶梯”,认识了解中国古代文字,对于研究整理先秦文字、学习先秦书法有着重要的意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一曰指事。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说文解字的价值

《说文解字》的价值和不足B04中文2班学号:040701236姓名:TYM清代大儒戴震有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故曰,文字作为一切学术的基础,做学问得从掌握文字开始。
而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原文化一块瑰宝,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闪烁着绚丽的色彩。
它不仅是一部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奠基之作,而且是一部因形表义的反映原始文化的著作,是古汉字结构纷呈的原始文化的一种载体。
笔者就其价值归纳了以下内容:其一世界第一部规范字典“《说文解字》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规范字典,将永远在词典编纂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辉。
它的词典学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成书时代之‘早’,还在于它所实际达到的令人惊讶的水平。
”[①]《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也是第一部系统完备的字典。
首创540个偏旁作为部首,发明部首制度;先列小篆形体后说解,先释字义,后说形体结构的体例,系统的编排汉字;采用构形分析法,系统地进行字义、词义说明;建立收字、释字、注音、引证的编纂法体例;建立“博采通人”,“信而有征,不知盖阙”的辞书编纂法原则。
极具使用价值,保存古字、古义、古音,对于古今字和异体字的分析有很大的帮助,有助于后世研究古代文献。
同时,许慎《说文解字》收录小篆9353文,参照古籀大篆,因形释本义,诠释每个字的形、音、义,吸取前人成果,广收博采,征引时人前贤通人之说30余家,文献典籍110多种。
许慎辛辣地批驳和嘲笑了汉字凝固不变的观点。
《序》就是一部东汉以前的汉字发展史。
除体式发展之外,《序》还论及汉字内部结构的发展。
“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擎乳而浸多也。
”许慎认为,文是源,字是流。
汉字是沿着简单到复杂、文到字的擎乳浸多的方向发展的。
《序》对文字的功用的论述是明确的。
“六书”说本来是战国末年以来流行的文字学理论,班固曾转引在《汉书"艺文志》里:“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我国第一部系统字典

我国第一部系统字典《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为东汉的许慎。
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也是到目前流传最广的中文必借工具书。
此书在流传过程中屡经窜改,今本与原书颇有出入。
本书首创的部首编排法,为后世字书所沿用,对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古史学的研究作用极大。
在清代,研究《说文》成为专门的学问,给它作注的大家就有数十家。
简介许慎(约58-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人。
古文经学家、古文字学家。
他初举孝廉,后入京,官至太尉南阁祭酒。
曾从贾逵学习古文经学,博通经籍,当时洛阳儒生称其为“五经无双许叔重”。
许慎对我国文字学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许慎所处的时代,古文经与今文经的论争非常激烈。
今文经的儒生大多认为当时通行的用隶书书写的经典解说字义不严肃,谬语较多。
而古文经的儒生则认为从孔壁中发掘出来的用六国文字书写的经典是可靠的。
这场斗争对推动经学和文字学的发展是有益的。
处于这个时代的许慎,“性淳笃”且“博学经籍”,并注意研究周秦时的西土文字籀书及“孔壁古文”(又称“东土文字”),尤其着力于小篆和六书,诸如《仓颉》《博学》《凡将》《急救》《训纂》等字书无不涉猎。
由此,为他后来撰写《说文解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他才学过人,成年后即任职汝南郡功曹。
在任上,他勤于政事、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刚毅多谋、颇有政绩,因此被举为孝廉,来到了京师洛阳,补为太尉南阁祭酒。
许慎到洛阳后,尽管他“少博经籍”,颇有造诣,但仍“从逵受古学”,拜当时的儒学大师贾逵为师。
所以,他对古文经和仓颉古文、史籀大篆的研究,又有了更高的造诣。
汉代儒生研究古代文献,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两大学派。
今、古文经之争到汉章帝时代已进行了二百多年。
今、古文经之争也诱发了那些不肯墨守成规、敢于创新的有志之士的创造欲,许慎就是其中一位不断进取、锐意创新的学问家。
许慎针对古、今文经之争的根源在于使用文字的混乱,批评今文经学家牵强附会、随意解说文字,只凭笔画臆测文字起源与结构,是荒诞不经的“巧说邪辞”。
说文解字的特点和价值

说文解字的特点和价值《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的一部巨著,由东汉许慎所著。
该书以说文解字为宗旨,通过对汉字形体、读音和意义的详细分析,揭示了汉字的构形原理、历史演变和文化内涵。
《说文解字》的特点和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特点系统性:《说文解字》将汉字按照部首进行分类,使得整部字典呈现出有条不紊的体系。
这种分类方法既便于查阅,也有助于理解汉字之间的相互关系。
追溯性: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每个汉字的起源和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使得我们能够了解汉字的历史渊源。
这种追溯性不仅有助于理解汉字的本义,还能揭示汉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
创新性:《说文解字》在解释汉字时,采用了“六书”理论,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这一理论为后来的汉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提供了依据。
二、价值语言学价值:《说文解字》作为古代语言学的重要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汉字资料和语言信息。
通过对汉字的分析和解释,我们可以了解古代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从而加深对古代汉语的理解。
文化价值:《说文解字》不仅是一部语言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化史著作。
通过对汉字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文化现象,从而加深对古代文化的认识。
教育价值:《说文解字》对于汉字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汉字的起源、演变和意义的讲解,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汉字知识,提高汉字运用能力。
同时,《说文解字》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总之,《说文解字》作为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瑰宝,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通过对该书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汉字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加深对古代汉语和文化的认识。
说文解字传承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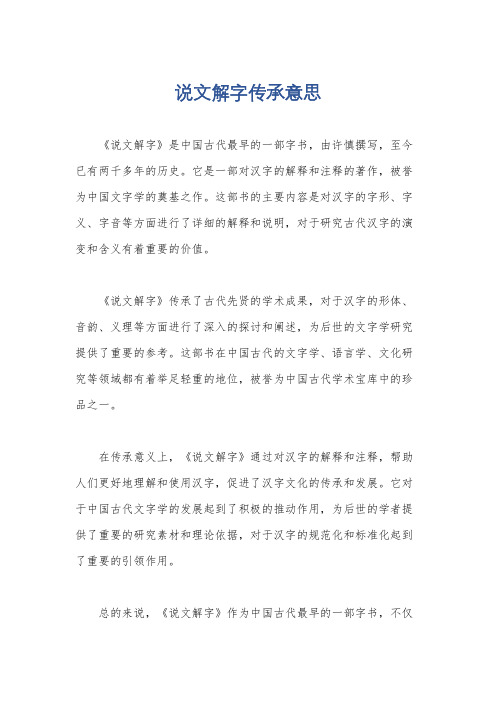
说文解字传承意思
《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字书,由许慎撰写,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它是一部对汉字的解释和注释的著作,被誉为中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
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是对汉字的字形、字义、字音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对于研究古代汉字的演变和含义有着重要的价值。
《说文解字》传承了古代先贤的学术成果,对于汉字的形体、音韵、义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述,为后世的文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这部书在中国古代的文字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领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中国古代学术宝库中的珍品之一。
在传承意义上,《说文解字》通过对汉字的解释和注释,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汉字,促进了汉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它对于中国古代文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后世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素材和理论依据,对于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总的来说,《说文解字》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字书,不仅
在学术研究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促进汉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传承意义深远而重要。
1.《说文解字》名词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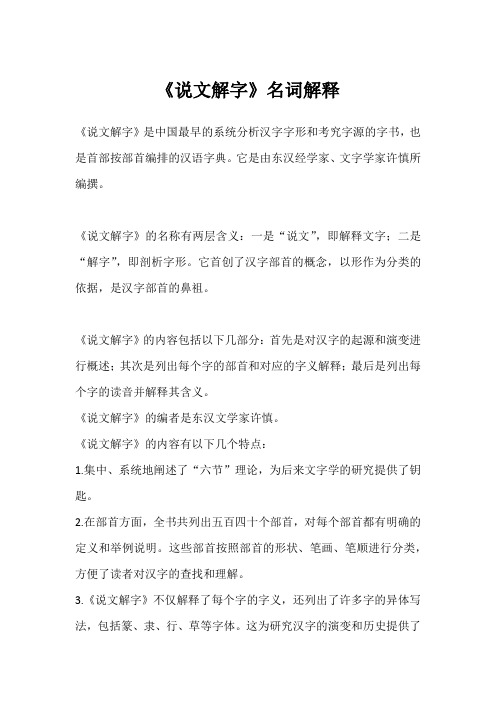
《说文解字》名词解释
《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也是首部按部首编排的汉语字典。
它是由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编撰。
《说文解字》的名称有两层含义:一是“说文”,即解释文字;二是“解字”,即剖析字形。
它首创了汉字部首的概念,以形作为分类的依据,是汉字部首的鼻祖。
《说文解字》的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首先是对汉字的起源和演变进行概述;其次是列出每个字的部首和对应的字义解释;最后是列出每个字的读音并解释其含义。
《说文解字》的编者是东汉文学家许慎。
《说文解字》的内容有以下几个特点:
1.集中、系统地阐述了“六节”理论,为后来文字学的研究提供了钥匙。
2.在部首方面,全书共列出五百四十个部首,对每个部首都有明确的定义和举例说明。
这些部首按照部首的形状、笔画、笔顺进行分类,方便了读者对汉字的查找和理解。
3.《说文解字》不仅解释了每个字的字义,还列出了许多字的异体写法,包括篆、隶、行、草等字体。
这为研究汉字的演变和历史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
4.在文字的编排上,采用部首法进行编排,使得查找汉字更为方便和有序。
5.《说文解字》中还首次阐述了“六书”的内容,贯穿了六书的原则,为后来的汉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许慎对六书分别下了定义,举了例子,后世讲六书都沿用许慎的名称和定义。
总之,《说文解字》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语言学著作,它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和结构,为研究汉字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理论框架。
谈《说文解字》的文化价值

谈《说文解字》的文化价值作者:冯艳萍来源:《美与时代·城市版》2013年第09期摘要:《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字学专著、形音义兼释的字典,它首创部首分类的编排体制,第一次把六书理论同汉字分析有机地结合。
陆宗达先生说过:“从全世界的范围考察,《说文解字》也是出现最早的、系统合于科学精神的、具有独创的民族风格的字典。
” 《说文解字》在中国语言学史和世界语言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得很多学者对它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说文解字;玉部;文化价值古今中外,语言文字皆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说文解字》总括五百四十部、九千多字,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极大的文化研究价值。
本文以《说文解字》的“玉部”为例,深入剖析其部内文化价值,探讨说文的文化意义。
一、《说文·玉部》简介《说文解字》玉部共收小篆126个,重文17个,始玉终靈。
这些以玉为成字部件的字,系统庞杂,功能各异,以六书体例进行分类,除“玉”外,其余皆为形声字。
而按其文化内涵的层次性,可大致分为:玉的种类:璙、瓘、璥、琠、瑍、璵等;玉的声、光、色:瑛、琰、瑳;玲、瑲、玎;瑑、珇等;玉的形状:璧、瑗、环、圭、璋等;玉的用途:琥、珑、瑞、瑁、珥等;类玉之石:珊、瑚、琇、玖、珋等;从以上分类,能看出当时人们已经对于玉有了较为形象且深动地认识,也可知,在当时,《说文解字》确实已经成为了一部收字非常详尽的工具书。
它不仅关注于文化实体现象,更深入研究了众多文化现象背后的潜在意义。
首先,作为玉部的构字基本部件——玉,它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总领玉部内所有字的文化内涵,《说文》中写到“玉,石之美。
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尃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橈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技,絜之方也。
象三玉之連。
其貫也。
” 玉是一种美好的文化象征。
通观玉部,玉的礼用、祭祀、丧葬、装饰、军用价值可见一斑。
二、《说文·玉部》文化剖析(一)礼用文化玉本是最光泽最美好的石头,最初由西北新疆传入黄河流域。
中国语言学史试题及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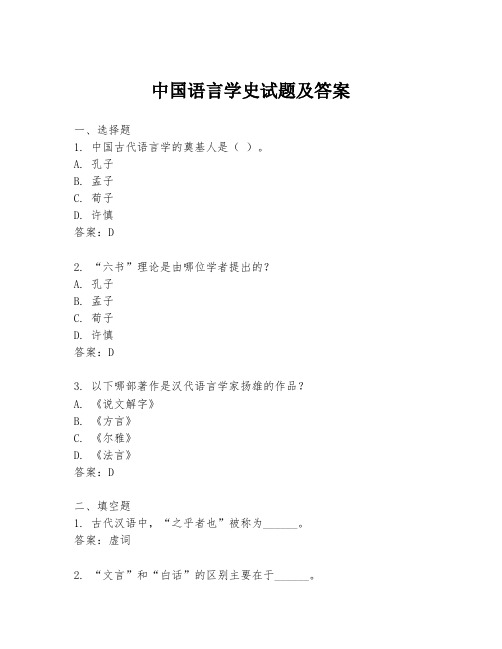
中国语言学史试题及答案一、选择题1. 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奠基人是()。
A. 孔子B. 孟子C. 荀子D. 许慎答案:D2. “六书”理论是由哪位学者提出的?A. 孔子B. 孟子C. 荀子D. 许慎答案:D3. 以下哪部著作是汉代语言学家扬雄的作品?A. 《说文解字》B. 《方言》C. 《尔雅》D. 《法言》答案:D二、填空题1. 古代汉语中,“之乎者也”被称为______。
答案:虚词2. “文言”和“白话”的区别主要在于______。
答案:语言风格3. 宋代语言学家陆游的《______》是研究古代汉语方言的重要文献。
答案:《老学庵笔记》三、简答题1. 简述《说文解字》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答案:《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字字典,对后世的汉字研究和字典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请简述“六书”理论的主要内容。
答案:六书理论是汉字构字的六种基本方法,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四、论述题1. 论述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在语法、词汇、语音方面的主要差异。
答案: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在语法上,古汉语词序较为灵活,而现代汉语词序较为固定;在词汇上,古汉语词汇较为丰富,现代汉语词汇更加简化;在语音上,古汉语声调较少,现代汉语声调较多。
五、翻译题1. 请将以下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
原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翻译:孔子说:“学习了知识之后,经常复习它,不也是很愉快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是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自己却不生气,不也是君子吗?”。
大徐本《说文解字》名词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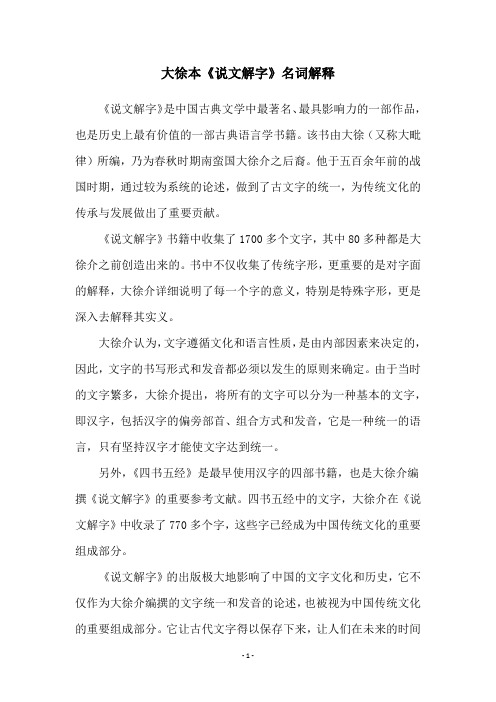
大徐本《说文解字》名词解释《说文解字》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也是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一部古典语言学书籍。
该书由大徐(又称大毗律)所编,乃为春秋时期南蛮国大徐介之后裔。
他于五百余年前的战国时期,通过较为系统的论述,做到了古文字的统一,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说文解字》书籍中收集了1700多个文字,其中80多种都是大徐介之前创造出来的。
书中不仅收集了传统字形,更重要的是对字面的解释,大徐介详细说明了每一个字的意义,特别是特殊字形,更是深入去解释其实义。
大徐介认为,文字遵循文化和语言性质,是由内部因素来决定的,因此,文字的书写形式和发音都必须以发生的原则来确定。
由于当时的文字繁多,大徐介提出,将所有的文字可以分为一种基本的文字,即汉字,包括汉字的偏旁部首、组合方式和发音,它是一种统一的语言,只有坚持汉字才能使文字达到统一。
另外,《四书五经》是最早使用汉字的四部书籍,也是大徐介编撰《说文解字》的重要参考文献。
四书五经中的文字,大徐介在《说文解字》中收录了770多个字,这些字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文解字》的出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字文化和历史,它不仅作为大徐介编撰的文字统一和发音的论述,也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让古代文字得以保存下来,让人们在未来的时间里,不断地研究古文字,对明确古人构思的语言义理做更深入的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综上所述,《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学者大徐介于战国时期所编的一部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品。
它收集了很多大徐介前的文字,并以此为基础,让古代文字得以保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当今社会,《说文解字》仍然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权威作品,是我们探究古人思想的重要参考书籍。
许慎作品地位及意义

作品地位及意义:两千年来,《说文解字》是文字学上的首创之书,也是最有权威之书,它的作者许慎的名字与他的杰作成为后人阅读古籍,探讨古代文化,研究古文必不可少的桥梁和钥匙。
《说文》问世以后,很快就引起当时学者的重视,在注释经典时常常引证《说文》。
如:郑玄注三礼,应劭、晋灼注《汉书》,都曾援引《说文》以证字义。
《到了南北朝时代,学者们对《说文》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认识。
唐代科举考试规定要考《说文》。
自唐代以后,一切字书、韵书及注释书中的字义训诂都依据《说文》。
在对《说文》研究的历朝历代中,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高峰时期。
清代研究《说文》的学者不下200人,其中称得上专家的有数十人之多。
清代《说文》之学,可分为四类:其一,是校勘和考证工作,如严可均的《说文校议》、钱坫的《说文解字斠诠》等;其二,对《说文》进行匡正,如孔广居的《说文疑疑》、俞樾的《儿笘录》等;其三,对《说文》的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句读》;其四,订补前人或同时代学者关于《说文》研究的著作,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等。
其中第三种最为重要,这四人也并称“说文四大家”。
近人丁福保持以往各家研究《说文》的专著和其他论及《说文》的著述以及甲骨文、金文的材料汇集为《说文解字诂林》,后又搜集遗逸编为《补遗》,是该书注释的总汇。
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吸取前辈的研究成果,成为一部研究汉民族语言文字的系统的专著,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不但对于后人研究语言文字学、文献学是唯一的经典著作,就是整理文化遗产也都是不可缺乏的阶段。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它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以及汉代和以前的不少文字训诂,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的面貌,比较系统地提出分析文字的理论,是我国语文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辩识声读的字典,也是1800年来唯一研究汉字的经典著作,是我们今天研究古文字和古汉语的必不可少的材料。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说文解字》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价值《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名作。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说文解字正义序》中曾说:“《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馀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
”此书推崇《说文》未免太过,但若换一角度,或许并不为过。
《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字学专著,是我国第一部形音义兼释的字典,它首创部首分类的编排体制,第一次把六书理论同汉字分析有机地结合。
正如陆宗达先生所说:“从全世界的范围考察,《说文》也是出现最早的、系统合于科学精神的、具有独创的民族风格的字典。
”[1] 《说文》在中国语言学史和世界语言学史上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它的深入研究,尤为必要,以下便是对《说文》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价值的界定。
一、标志着我国文字学的正式建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字书就已经出现。
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周宣王所作《史籀》15篇(即后代的《史籀篇》)是最早的一部字书。
在《说文》之前,《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这些文字学著作均已出现。
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字书还有《凡将篇》(司马相如作)、《急就篇》(史游作)、《元尚篇》(李长作)、《训纂篇》(扬雄作)四篇。
在众多文字学著作中,《说文》何以倍受关注且泽被深远呢?可以说这与许慎的正确文字观,尤其是与他对文字的系统性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
早期的字书,类似于近代的《千字文》和《百家姓》,都是孩童启蒙识字的教科书,被编辑成合辙押韵、朗朗上口的课本形式,便于记忆和诵读,然而其缺点亦很明显。
由于这些字书仅是罗列和堆砌单字,无顺序和规律可言,既不便于检索,又未作任何解说和阐释,因而被世人称作“杂字书”。
这种“杂字书”在文字学史上无甚价值。
许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以其系统的文字学观点克服了上述“杂字书”的诸多缺陷。
这种系统性主要体现在“六书”理论和他首创的540部分类体制上。
许慎第一次把“六书”理论与汉字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他认为所有的汉字,按其形体结构,都可以归并到“六书”中的任何一类之下,因此他解说文字是按“六书”系统进行的。
至于《说文》中的每一个字,许慎则把它们安排在他独创的540个部首之下,而540个部首的顺序,则是依照形体关系加以排列的,即所谓的“据形系联”。
把文字分部归类是许慎的首创。
这样,不仅9000多个字不再是一盘散沙,就连540个部首也是有条理的了。
可见,无论从文字的形体结构,还是从各个字在《说文》中的编排来看,许慎都是把各个汉字置于一定的类别中去的,这充分体现了许慎的系统性思想。
正是由于许慎能把其文字的系统观理论有效地用之于文字解析,加之他掌握了丰富的语言材料及其求真务实的科研态度,才使得《说文》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字学著作。
《说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字学、字典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许慎540部的创立,意义十分重大。
一方面,它较好地解决了统摄所有汉字的问题,另一方面则在于它首创部首检字法,开了文字学、字典学之先河。
部首检字法这种字典编纂体制,较之《说文》之前的《三苍》式、《尔雅》等字书的体例,有很大的优越性。
后代较为重要的字书,如晋吕忱的《字林》、梁顾野王的《玉篇》、宋司马光等的《类篇》等,基本上承袭了《说文》的编排形式。
明清以后的字书,如梅膺祚的《字汇》、张玉书等的《康熙字典》等,还有近现代的一些字书,多依据通行汉字的形体结构。
对《说文》部首有所简化、改革,字的归部也由严格依照文字学原则改为适合一般群众的检字法原则。
然而从本质上说,这种编制仍然属于部首检字法一系的,从源流上看,仍然取法于《说文》,不过是对《说文》编纂体制的继承和发展而已。
至于专门领域(如古文字)的文字字书,如今大多仍因袭许慎“据形系联”的部首格局,由此足见《说文》部首检字法编纂体制的强大生命力。
二、训诂学、词汇学价值由于《说文》分析每一个字的形体结构,这就使我们可以透过文字形体来考察文字的本义,即造字时文字所代表的词的意义。
北齐颜之推说:“大抵服其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著书往往引以为证。
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
”(《颜氏家训·书证》)的确,《说文》中的训释,其保留古义者至多,解释古籍时往往用得着它。
如1973年马王堆出土帛书竹简《医经方·十一脉灸经》第二种(甲本)中有“肩以(似)脱,臑以(似)折。
是肩脉主治”等语,说的是肩脉所主治的症状。
这个“臑”,或以为“羊豕之臂”,或以为“牲畜的前肢”,说者纷纭。
陆宗达先生引《说文》说:“臑,臂羊矢出。
”是说臂上的羊矢穴。
后来引申,也叫臂为臑。
用这种解释去读《医经方》,直接而准确。
《说文》解释的一般都是本义,所以,它又为我们从认识本义入手,进而考察其词义系统提供了依据。
我们知道,多义词的义项常有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之分。
掌握了一个词的本义,其它诸多引申义也就很容易掌握了。
这就是所谓“一领挈而全裘振,一纲举而万目张”。
以“本”为例。
《说文》:“木下曰本。
从木,一在其下。
”徐锴曰:“一,记其处也。
” “本”本指草本的根,如《国语·晋语一》:“伐木不自本,必复生。
”引申为草木记数单位,如《荀子·富国》:“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
”又引申为树木的根基、主体或原本,如《论语·学而》:“君子务本。
”《礼记·乐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以之为主,又引申为执掌,如《汉书·爰盎传》:“是时绛候为太尉,本兵柄。
”以之为原本,故又引申为根据,如《周易·乾》:“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
三、音韵学价值《说文》通过形声系统,通过读若,以及声训、假借、重文、联绵词等等,提供了大量上古语音材料。
清代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说文》所提供的语音材料。
下面我们着重对《说文》的形声系统做详细论述。
《说文》所收9353个字中,形声字占7697个之多。
对于形声字的注音,《说文》大体上采用“从某,某声”的方法。
“某声”就是一般所说的谐声偏旁(简称“谐声”),它是研究上古音的必不可少的材料。
正如李恕豪所说:“使用谐声材料研究上古韵,除了能够与利用韵文的押韵材料所归纳出来的韵部互相印证之外,还有两个明显的优点:第一,由于在上古韵文中能作韵脚的字有限,有些本属同一韵部的字就可能系联不上,通过《说文》的谐声偏旁可以重新把他们联系起来。
第二,通过《说文》的谐声偏旁可以确定那些从来没有做过韵脚的字所属的韵部。
”[2]在充分认识到《说文》音韵学价值的基础上,段玉裁把对《说文》谐声系统的分析整理同先秦的押韵情况相结合,著出《六书音韵表》,考订古韵17部,终使古韵学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其后,严可均的《说文声类》,姚文田的《说文声系》、苗夔的《说文声读表》、张惠言的《说文谐声谱》、张行孚的《说文审音》、江有诰的《二十一部谐声表》以及朱骏声、孔广森的古韵18部,章太炎的古韵23部,黄侃的28部说等,分别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另外,清代以来的古音学家,也有依靠谐声系统的双声关系来研究古汉语声类的,如钱大昕“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著名论断,章太炎的“娘日归泥”等说都在《说文》中找到了确凿的证据。
今之学者,仍然把《说文》的谐声看成是研究上古音韵价值最高的材料之一。
四、考释古文字的津梁《说文》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 [3]首先,它收录小篆9000余个,可谓是保存秦代小篆的最完整的字典。
小篆的形体上承甲金古籀,下开隶体楷体,后人要根据古隶和楷书去探讨甲金古籀,就一定要经过小篆这个桥梁。
其次,在《说文》产生的年代里,学者能见到的小篆以前的文字并不很多,而《说文》则收录并与小篆对照解释了东汉以前例代古文、籀文计700余字,这大概是历史上对小篆以前古文字的第一次大搜集、大整理。
这对考释古文字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0世纪以来,尤其是建国以后,随着殷墟甲骨文、殷周青铜器铭文以及战国简帛书、古玺等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说文》的重要作用愈发超出以往人们的估计。
现在看来,《说文》不仅系统保存了古汉字阶段许多有参考价值的字形,而且其解说与征引,为古文字考释提供了多方面的参考依据,《说文》有些字头和字说虽不见于传世文献,却见于出土古文字资料,并能够得到较好的印证,所见到的古文字原始材料和考释成果,又可以用以修正《说文》的不足与缺陷。
《说文》和古文字,二者密切结合,相得益彰,古文字学如今取得的成果,很大程度上都可看作是《说文》直接帮助和间接启发的结果。
运用《说文》帮助释读古文字,例子较多,现略举一例。
《说文》七上鼎部,“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
……籀文以鼎为贞”;三下卜部:“贞,卜问也。
……一曰鼎省声。
”此引据大徐本。
小徐本鼎下还有“古文以贞为鼎”句。
许慎认为古以贞为鼎,以鼎为贞,小篆贞字从鼎省声,都是言之有据的,可是这种说法却难在传世的典籍中得到印证。
今唯于殷墟卜辞中发现有鼎字,屡见同音假为贞卜之“贞”,西周甲骨卜辞中见有从卜鼎声的贞字,而在周代铭文材料里,这个从鼎的“贞”则又通常借为鼎字,古时贞、鼎二字的用法及其字形关系正由于《说文》之引线而得以证实。
五、规范、统一汉字的重要工具汉字的历史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演化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加以规范、趋于统一的过程。
殷商至西周时期的文字,看起来还比较统一,但到了战国时代,各国使用的文字及其书写形式,则自成系统,很不一致。
秦并六国后,文字混用现象日渐突出,据载当时的汉字有八种不同的写法。
鉴于当时文字形体不规范的情形,秦始皇推出“书同文”政策,以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
然秦只统制了十四年,而文字统一规划工作很难一蹙而蹴,这就使得这种文字书写不规范的状况一直波及到古今文字交接过渡的两汉。
如出土所见汉初的帛书简策,文字写法仍然纷呈不一,点画出入随便,书体结构或袭战国文字遗风,至于《说文》成书前后的碑刻文字,也是别体繁出,不可胜数。
这说明秦王朝的书同文,对于民间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而汉代文字使用上的混乱状况,则亟待进行统一和规范化工作。
汉代的三苍式识字书以及平帝时的未央廷讲字、汉末的《熹平石经》等受官方支持的活动,对当时汉字的规范,曾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全面地系统地整理文字、长远地对文字的统一规范产生广泛影响的,还只能是许慎的《说文》。
《说文》的字形结构分析首先规范了小篆,从此以后,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可以共同遵循的文字系统,汉字的运用才逐步纳入规范化的轨道。
而汉字隶楷形体的演变,也明显受到了《说文》的影响。
汉世以后,许多朝代都曾把《说文》作为规范、统一文字的重要工具。
唐代以后,开科取士,《说文》被列为必试科目,选举中设“明字”科,国子监又设书学博士,这些行政措施进一步加强了《说文》在实现文字统一方面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