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纯的怀旧”到“动能的怀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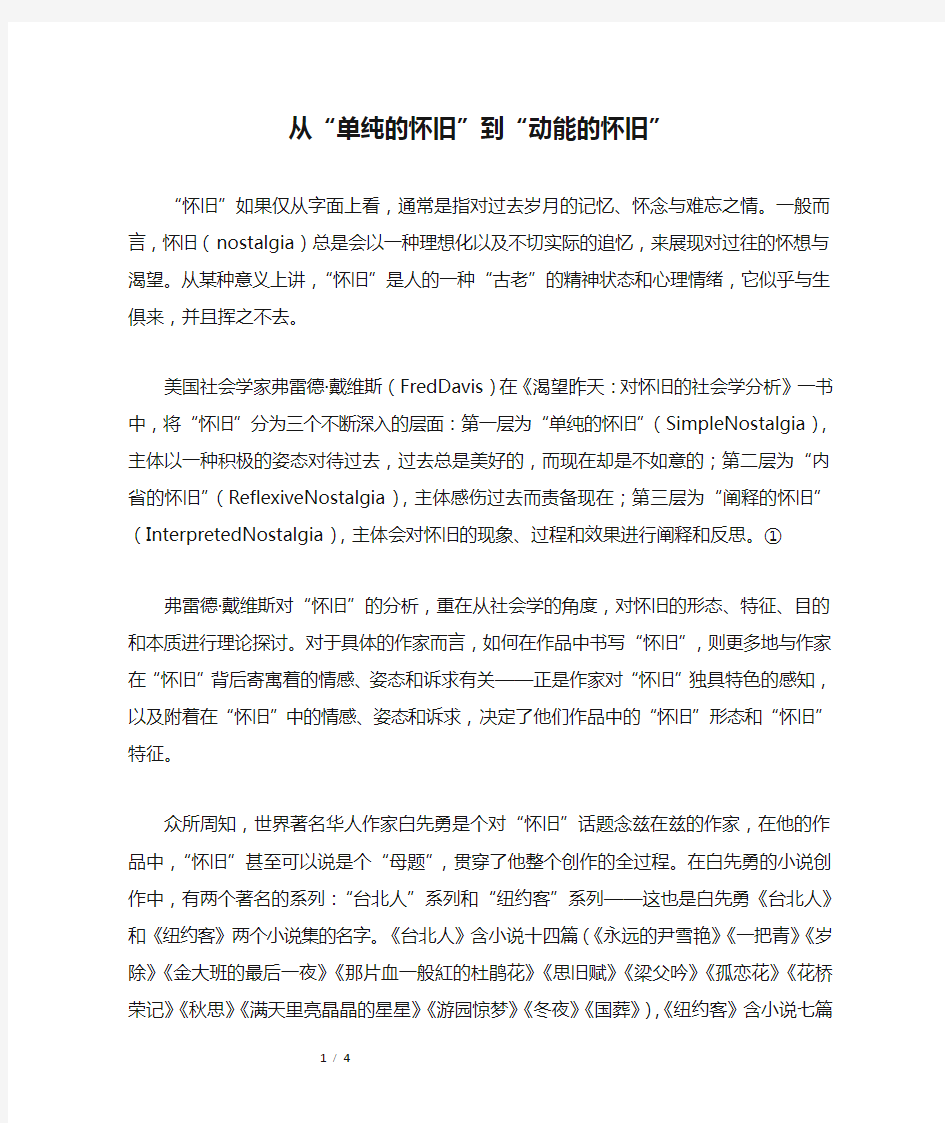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从“单纯的怀旧”到“动能的怀旧”
“怀旧”如果仅从字面上看,通常是指对过去岁月的记忆、怀念与难忘之情。一般而言,怀旧(nostalgia)总是会以一种理想化以及不切实际的追忆,来展现对过往的怀想与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讲,“怀旧”是人的一种“古老”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情绪,它似乎与生俱来,并且挥之不去。
美国社会学家弗雷德·戴维斯(FredDavis)在《渴望昨天:对怀旧的社会学分析》一书中,将“怀旧”分为三个不断深入的层面:第一层为“单纯的怀旧”(SimpleNostalgia),主体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对待过去,过去总是美好的,而现在却是不如意的;第二层为“内省的怀旧”(ReflexiveNostalgia),主体感伤过去而责备现在;第三层为“阐释的怀旧”(InterpretedNostalgia),主体会对怀旧的现象、过程和效果进行阐释和反思。①
弗雷德·戴维斯对“怀旧”的分析,重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怀旧的形态、特征、目的和本质进行理论探讨。对于具体的作家而言,如何在作品中书写“怀旧”,则更多地与作家在“怀旧”背后寄寓着的情感、姿态和诉求有关——正是作家对“怀旧”独具特色的感知,以及附着在“怀旧”中的情感、姿态和诉求,决定了他们作品中的“怀旧”形态和“怀旧”特征。
众所周知,世界著名华人作家白先勇是个对“怀旧”话题念兹在兹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怀旧”甚至可以说是个“母题”,贯穿了他整个创作的全过程。在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有两个著名的系列:“台北人”系列和“纽约客”系列——这也是白先勇《台北人》和《纽约客》两个小说集的名字。《台北人》含小说十四篇(《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岁除》《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鹃花》《思旧赋》《梁父吟》《孤恋花》《花桥荣记》《秋思》《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游园惊梦》《冬夜》《国葬》),《纽约客》含小说七篇(包括已收入《纽约客》集子的《谪仙记》《谪仙怨》《夜曲》《骨灰》《DannyBoy》
《TeaforTwo》和2015年刚刚发表的《SilentNight》)。在这两个系列二十一篇小说中,白先勇通过对不同人物形象的展示以及对他们人生轨迹的描摹,呈现出一种浓烈的“怀旧”心绪——而这种“怀旧”心绪,又与他笔下斑斓的都市色彩和复杂的身份建构密切关联。
在小说《台北人》中,白先勇对“怀旧”的表现,更多地聚焦为一种作品人物的心理形态:寻求安全感、寄托归宿感、放大美好、记忆青春——这导致了《台北人》中的众多人物,在时空错位的情形下,形成了身份确认上的非此非彼亦此亦彼。
从总体上看,《台北人》中的“怀旧”,基本上应属于“单纯的怀旧”(SimpleNostalgia)——也就是作品中的人物都是通过对过去某一(些)方面的肯定来反衬现时的不如意。“台北人”顾名思义,本来应该是“台北的市民”,可是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台北人”却是一帮生活在台北,却心系上海、南京、北京、桂林的上海人、南京人和桂林人,这群人现在叫“台北人”本来就含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因为他们其实是“被台北人”了,时空的错位和感情的偏重,导致了“怀
旧”的产生——所谓的“今昔之比”②,其实是对过去上海、南京、北京、桂林的不能忘怀,并以“昔”之标准来衡量、比照“今”之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昔”之光华记忆,已经完全控制、覆盖了“今”之生活,并因此而产生“台北人”身份的错乱。这些名为“台北人”的上海人、南京人、桂林人在过去的记忆中寻找荣耀和安慰,在过去的时光中寄托精神和心灵,在错置的时空中寻求支撑的力量,以对现实的拒绝和对过去的拥抱(怀旧)获得安全感——其实是一种躲避和自我保护。
《台北人》首篇《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不但她本人“怀旧”(她在台北的新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从来不肯把它降低
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客厅的家具是一色桃花心红木桌椅,几张老式大靠背的沙发,塞满了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而且她还成了别人“怀旧”的对象(老朋友来到台北的尹公馆,“谈谈老话,
大家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想一会儿当年,在尹雪艳面前发发牢骚,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
一班曾经在上海滩出过风头如今落魄的上海人身在台北,集聚在尹公馆这个小型公共空间,面对着尹雪艳这个“总也不老”的上海百乐门舞厅头牌,仿佛就又回到了当年繁华的上海时代。《一把青》中的朱青,虽然有南京时期和台北时期两个阶段,但她的台北时期,其实形同行尸走肉——因为她所有的精神寄托和情感世界,已经永远停留在了南京时代,对南京时代人与事的难以忘怀,使她的台北人生已经完全“空洞化”;《岁除》中的赖鸣升人生辉煌也是在大陆时期,那时的赖鸣升是个精壮军人,下级军官,能喝酒,敢碰硬,割营长“靴子”、参加台儿庄大战,人生是何等的威风壮烈,可是到了台北,不但年岁大了,女人跑了,连酒量也不行了,唯一能够自傲的就是在大陆的过去经历;此外,《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兆丽、《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思旧赋》中的罗伯娘和顺恩嫂、《梁父吟》中的朴公、《孤恋花》中的“总司令”、《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和“我”、《秋思》中的华夫人、《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的教主、《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和窦夫人、《冬夜》中的余嵚磊和吴柱国以及《国葬》中
的秦义方,几乎《台北人》中的所有主人公,都在今昔对比的结构中带有回眸的姿态和“怀旧”的意味。
从某种意义上讲,《台北人》中的众多人物,一律沉湎于旧人、旧事、旧物、旧地(上海、南京、北京、桂林);对新人、新事、新物、新地(台北)普遍感到不适应,在这种拥抱“旧”而陌生“新”的价值取向中,不难发现作者白先勇在人物身上赋予的都市观和身份认同,那就是时间上追忆过去,空间上“再造”旧地,认同上努力适应当地。在小说中,上海、南京是繁华的现代都市,北京是五四发源地,桂林是难忘的故乡,而台北则是一个全新的城市。原本是“当下”的台北,在小说描述中却往往成为衬托的“背景”,而原本是“过往”的上海、南京、北京和桂林,在小说中倒成了叙述的关注对象(“前景”)。当小说在展示和描绘“台北人”身份的时候,对于尹雪艳、朱青、赖鸣升、金兆丽、王雄、罗伯娘、顺恩嫂、朴公、“总司令”云芳老六、教主、卢先生、钱夫人、窦夫人、余嵚磊、秦义方等人而言,它们其实既是“台北人”(肉身所在)又不是“台北人”(精神、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