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张家口
汪曾祺描写美食的散文作品

汪曾祺描写美食的散文作品从个体生命的迁徙,到食材的交流运输,从烹调方法的演变,到人生命运的流转。
人和食物的匆匆脚步从来不曾停歇。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汪曾祺描写美食的散文作品,供大家欣赏。
汪曾祺描写美食的散文作品:五味山西人真能吃醋!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调羹醋。
邻座的客人直瞪眼。
有一年我到太原去,快过春节了。
别处过春节,都供应一点好酒,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
”这在山西人是大事。
山西人还爱吃酸菜,雁北尤甚。
什么都拿来酸,除了萝卜白菜,还包括杨树叶子,榆树钱儿。
有人来给姑娘说亲,当妈的先问,那家有几口酸菜缸。
酸菜缸多,说明家底子厚。
辽宁人爱吃酸菜白肉火锅。
北京人吃羊肉酸菜汤下杂面。
福建人、广西人爱吃酸笋。
我和贾平凹在南宁,不爱吃招待所的饭,到外面瞎吃。
平凹一进门,就叫:“老友面!”“老友面”者,酸笋肉丝氽汤下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做:“老友”。
傣族人也爱吃酸。
酸笋炖鸡是名菜。
延庆山里夏天爱吃酸饭。
把好好的饭焐酸了,用井拔凉水一和,呼呼地就下去了三碗。
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
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四川夹沙肉用大片肥猪肉夹了洗沙蒸,广西芋头扣肉用大片肥猪肉夹芋泥蒸,都极甜,很好吃,但我最多只能吃两片。
广东人爱吃甜食。
昆明金碧路有一家广东人开的甜品店,卖芝麻糊、绿豆沙,广东同学趋之若鹜。
“番薯糖水”即用白薯切块熬的汤,这有什么好喝的呢?广东同学曰:“好!”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
我家曾有老保姆,正定乡下人,六十多岁了。
她还有个婆婆,八十几了。
她有一次要回乡探亲,临行称了两斤白糖,说她的婆婆就爱喝个白糖水。
北京人很保守,过去不知苦瓜为何物,近年有人学会吃了。
菜农也有种的了。
农贸市场上有很好的苦瓜卖,属于“细菜”,价颇昂。
北京人过去不吃蕹菜,不吃木耳菜,近年也有人爱吃了。
汪曾祺在张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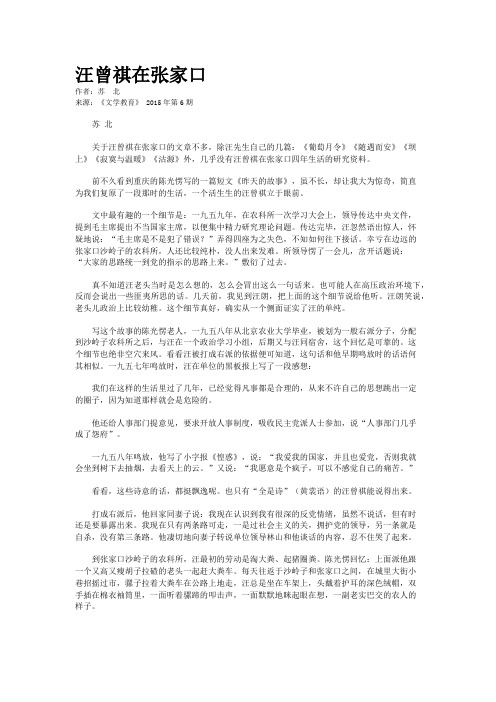
汪曾祺在张家口作者:苏北来源:《文学教育》 2015年第6期苏北关于汪曾祺在张家口的文章不多,除汪先生自己的几篇:《葡萄月令》《随遇而安》《坝上》《寂寞与温暖》《沽源》外,几乎没有汪曾祺在张家口四年生活的研究资料。
前不久看到重庆的陈光愣写的一篇短文《昨天的故事》,虽不长,却让我大为惊奇,简直为我们复原了一段那时的生活,一个活生生的汪曾祺立于眼前。
文中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一九五九年,在农科所一次学习大会上,领导传达中央文件,提到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以便集中精力研究理论问题。
传达完毕,汪忽然语出惊人,怀疑地说:“毛主席是不是犯了错误?”弄得四座为之失色,不知如何往下接话。
幸亏在边远的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人还比较纯朴,没人出来发难。
所领导愣了一会儿,岔开话题说:“大家的思路统一到党的指示的思路上来。
”敷衍了过去。
真不知道汪老头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也可能人在高压政治环境下,反而会说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话。
几天前,我见到汪朗,把上面的这个细节说给他听。
汪朗笑说,老头儿政治上比较幼稚。
这个细节真好,确实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汪的单纯。
写这个故事的陈光愣老人,一九五八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分配到沙岭子农科所之后,与汪在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后期又与汪同宿舍,这个回忆是可靠的。
这个细节也绝非空穴来风。
看看汪被打成右派的依据便可知道,这句话和他早期鸣放时的话语何其相似。
一九五七年鸣放时,汪在单位的黑板报上写了一段感想: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过了几年,已经觉得凡事都是合理的,从来不许自己的思想跳出一定的圈子,因为知道那样就会是危险的。
他还给人事部门提意见,要求开放人事制度,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说“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府”。
一九五八年鸣放,他写了小字报《惶惑》,说:“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又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看看,这些诗意的话,都挺飘逸呢。
汪曾祺生平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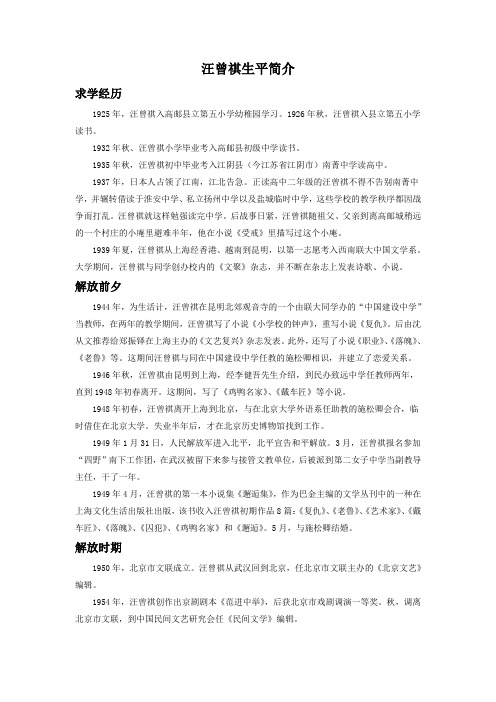
汪曾祺生平简介求学经历1925年,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
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
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
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
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解放前夕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
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
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
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
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
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
汪曾祺《菌小谱》原文及赏析

汪曾祺《菌小谱》原文及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文档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谢谢!并且,本店铺为大家提供各种类型的经典范文,如诗歌散文、原文赏析、读书笔记、经典名著、古典文学、网络文学、经典语录、童话故事、心得体会、其他范文等等,想了解不同范文格式和写法,敬请关注!Download tips: This document is carefully compiled by this editor.I hope that after you download it, it can help you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document can be customized and modified after downloading, please adjust and use it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thank you!In addition, this shop provides you with various types of classic sample essays, such as poetry and prose, original text appreciation, reading notes, classic works, classical literature, online literature, classic quotations, fairy tales, experience, other sample essays, etc.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difference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format and writing of the sample essay!汪曾祺《菌小谱》原文及赏析【导语】:菌小谱是汪曾祺写的一篇散文,来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赏析吧菌小谱南方的很多地方把冬菇叫香蕈(xùn)。
关于汪曾祺的生平

一、关于汪曾祺的生平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与张爱玲同岁),江苏高邮人。
汪家是一个士绅世家,祖父是清朝末期拔贡,开过药店,作过眼科大夫。
父亲汪菊生是一位熟读经史子集的儒生,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花鸟鱼虫无所不爱。
汪曾祺在气质、修养和情趣上较多地继承了他父亲的基因,从小受到正规的传统教育和父亲的宠爱,又聪颖过人。
不仅有一个与沈从文一样无忧无虑的小学时代,而且还有一个沈从文和张爱玲都无法相比的天真浪漫、幸福快乐的金色童年。
在家乡读完小说和初中后,考入江阴县南普中学读高中。
1939年(19岁)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接触到大量的新文学作品和国外的翻译作品。
1940年开始小说创作,最初创作的《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等,主要受到弗吉尼亚•伍尔芙、阿索林、纪德和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手法的影响,后得到当时在西南联大任中文系教授的著名小说家沈从文的亲自指导。
1943年毕业后,先后在昆明和上海当中学教师,出版有小说集《邂逅集》。
1947年(27岁)写于上海的短篇小说《鸡鸭名家》,在小说题材和创作风格等多方面都受到沈从文小说的极大影响,并显露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948年到北平,失业半年,后经沈从文推荐任职于历史博物馆。
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第四野战军工作团南下,在武汉参加文教单位的接管工作,被派到一女子中学任教。
1950年又调回北京,在北京市文联工作(1951年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到江西进贤县参加土改),1954年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
在此期间,参加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文艺刊物的编辑。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长城外张家口地区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1962年,调回北京,在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参加京剧现代戏《沙家浜》(《芦荡火种》)的改编,同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文革”中还参加了“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漫谈汪曾祺和他的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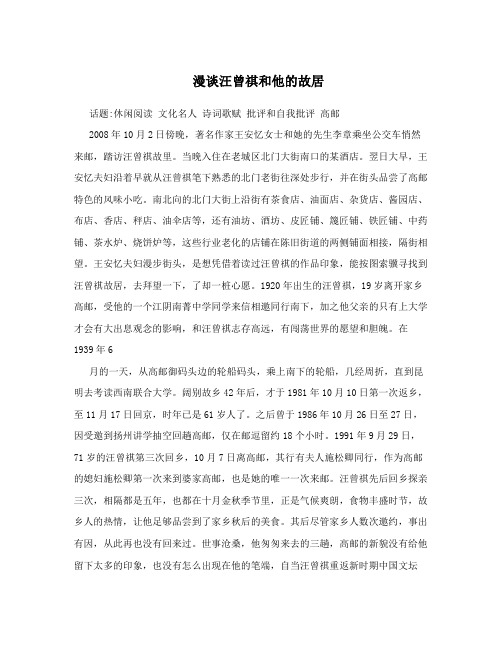
漫谈汪曾祺和他的故居话题:休闲阅读文化名人诗词歌赋批评和自我批评高邮2008年10月2日傍晚,著名作家王安忆女士和她的先生李章乘坐公交车悄然来邮,踏访汪曾祺故里。
当晚入住在老城区北门大街南口的某酒店。
翌日大早,王安忆夫妇沿着早就从汪曾祺笔下熟悉的北门老街往深处步行,并在街头品尝了高邮特色的风味小吃。
南北向的北门大街上沿街有茶食店、油面店、杂货店、酱园店、布店、香店、秤店、油伞店等,还有油坊、酒坊、皮匠铺、篾匠铺、铁匠铺、中药铺、茶水炉、烧饼炉等,这些行业老化的店铺在陈旧街道的两侧铺面相接,隔街相望。
王安忆夫妇漫步街头,是想凭借着读过汪曾祺的作品印象,能按图索骥寻找到汪曾祺故居,去拜望一下,了却一桩心愿。
1920年出生的汪曾祺,19岁离开家乡高邮,受他的一个江阴南菁中学同学来信相邀同行南下,加之他父亲的只有上大学才会有大出息观念的影响,和汪曾祺志存高远,有闯荡世界的愿望和胆魄。
在1939年6月的一天,从高邮御码头边的轮船码头,乘上南下的轮船,几经周折,直到昆明去考读西南联合大学。
阔别故乡42年后,才于1981年10月10日第一次返乡,至11月17日回京,时年已是61岁人了。
之后曾于1986年10月26日至27日,因受邀到扬州讲学抽空回趟高邮,仅在邮逗留约18个小时。
1991年9月29日,71岁的汪曾祺第三次回乡,10月7日离高邮,其行有夫人施松卿同行,作为高邮的媳妇施松卿第一次来到婆家高邮,也是她的唯一一次来邮。
汪曾祺先后回乡探亲三次,相隔都是五年,也都在十月金秋季节里,正是气候爽朗,食物丰盛时节,故乡人的热情,让他足够品尝到了家乡秋后的美食。
其后尽管家乡人数次邀约,事出有因,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世事沧桑,他匆匆来去的三趟,高邮的新貌没有给他留下太多的印象,也没有怎么出现在他的笔端,自当汪曾祺重返新时期中国文坛后,提笔写到的家乡高邮,大都还是他记忆中的高邮。
汪曾祺的《我的家》开篇写道:“我们的那个家原来是不算小的,我的家大门开在科甲巷(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巷子起了这么个名字,其实这条巷里除了我的曾祖父中过一名举人,我的祖父中过拔贡外,没有别的人家有过功名)而在西边的竺家巷有一个后门。
汪曾祺与京剧《沙家浜》的前前后后

汪曾祺与京剧《沙家浜》的前前后后作者:陆建华来源:《华人时刊》2015年第01期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
他自称是“两栖类”,写小说,也写戏剧。
在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沙家浜》的过程中,他是主要执笔者。
如今,提起《沙家浜》,人们就会自然地想到汪曾祺;对中国广大普通老百姓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可能不知道汪曾祺,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京剧《沙家浜》。
江青先后看中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1962年1月,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结束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长达三年的“流放”生活,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回到北京,调任北京京剧团专职编剧。
1963年冬,他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为现代京剧,如同林斤澜所说:“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结,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从某个角度说来,所谓“八个样板戏”,首先是源于现代京剧《红灯记》和《沙家浜》,这两个戏都是由沪剧改编而成,并且,这两个沪剧本都是由江青看中,进而于1963年先后分别推荐给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的。
江青有把握断定,把这两个戏抓好了,既肯定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也定然能推动本人政治地位的上升,为她后来成为“文艺革命旗手”积累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本。
当时,江青还不能直接发号施令,她把任务交给了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由林默涵出面具体操作。
其时,北京京剧一团刚从香港成功演出后载誉归来,接到上级交来的沪剧《芦荡火种》剧本后,从领导到演员都很高兴,下决心改编好、演出好这出戏。
首先成立了剧本的改编创作组,由四人组成,除汪曾祺外,另外三人是: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肖甲,编剧兼艺术室主任杨毓珉。
编创人员被特地安排住入颐和园龙王庙,除了写作环境宜人,生活安排上也很好。
创作人员的写作情绪也十分高涨,多年后,汪曾祺在题为《关于〈沙家浜〉》的文章中这样记述道:“我和肖甲、杨毓珉去改编,住颐和园龙王庙。
天已经冷了,颐和园游人稀少,风景萧瑟。
汪曾祺的三所大学

汪曾祺的三所大学•相关推荐汪曾祺的三所大学原标题:汪曾祺的三所大学1946年的汪曾祺。
汪曾祺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张家口(右一)除家乡外,汪曾祺一生待的最长的是三个地方:昆明、北京和张家口。
家乡给了他的童年记忆,而昆明、北京和张家口却给了他经历、见识和人生教育。
也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三所大学。
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的逝世纪念日,让我们随着这篇追忆文章,重温他的人生轨迹。
在他人生重要的节点上,他究竟汲取了怎样的暗功夫,使他成为了汪曾祺。
昆明,西南联大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这是大家都晓得的。
这是他的第一所大学。
西南联大学制四年,汪曾祺却读了五年,因为他的体育和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又留了一年。
我们知道,汪曾祺在学校是个不用功的学生。
泡茶馆,跑图书馆,可“不爱上课”(汪曾祺自语)。
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
比如朱自清的课,他就不听,他自己说:“朱自清教我们宋词。
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
一张一张地讲。
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
汪不上课,不代表不读书。
他是个夜猫子。
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
他曾写过一个历史系的同学,同他住上下铺,可一学期下来几乎没见过面。
那是一个极其正常的人,白天上课,晚上早睡早起;而汪黑白颠倒。
因此汪回来该同学上课去了。
汪泡图书馆是有名的,他说:“常不上课,但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
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
有时只有我一个人。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认识了沈从文,成了沈先生的入室弟子。
他还认识了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唐兰、陈梦家、罗常培……受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读了A·纪德、萨特、弗吉尼·伍尔芙、契诃夫、阿左林和普鲁斯特的作品。
他读了很多书,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
这是汪曾祺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他这一生要成为一个作家。
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在昆明先后待了七年。
五年读书,两年教书。
葡萄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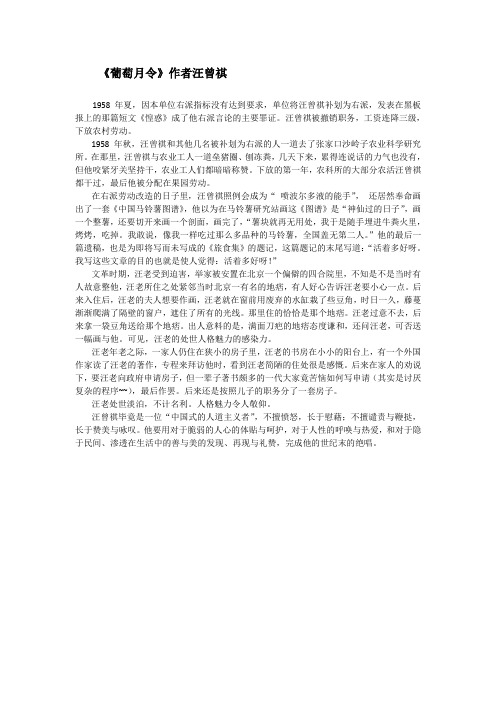
《葡萄月令》作者汪曾祺1958年夏,因本单位右派指标没有达到要求,单位将汪曾祺补划为右派,发表在黑板报上的那篇短文《惶惑》成了他右派言论的主要罪证。
汪曾祺被撤销职务,工资连降三级,下放农村劳动。
1958年秋,汪曾祺和其他几名被补划为右派的人一道去了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
在那里,汪曾祺与农业工人一道垒猪圈、刨冻粪,几天下来,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但他咬紧牙关坚持干,农业工人们都暗暗称赞。
下放的第一年,农科所的大部分农活汪曾祺都干过,最后他被分配在果园劳动。
在右派劳动改造的日子里,汪曾祺照例会成为“喷波尔多液的能手”,还居然奉命画出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以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这《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第二人。
”他的最后一篇遗稿,也是为即将写而未写成的《旅食集》的题记,这篇题记的末尾写道:“活着多好呀。
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
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
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
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
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
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
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
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曾祺笔下的坝上

两个小时 , 可以采一网兜。回来,用线
穿好 , 晾 在房 檐 下 。”
“ 我 曾经 采到一 个白蘑。一般 蘑菇
都是 ‘ 黑片 蘑 ’, 菌 盖 是 白的 ,菌摺 是紫
汪先生写道 :“ 我大概吃过 几十种
不 同 样 的 马 铃 薯 。据 我 的 品 评 ,以 ‘ 男
爵 ’为最 大 , 大的一个可达两斤 ; 以 ‘ 紫
黑色的。白蘑则Biblioteka 盖菌摺都是雪白的, 是 很 珍贵 的 , 不 易遇 到 。” 汪曾祺笔下 , 有些 风景是人们很难
看 到的 :
过许多农活。 起猪圈、 刨冻粪、跟马车送 粪等。有一段 E l 子在果园上班 , 常干的活
儿是 给 果 树喷 波 尔 多液 。 许 多人写过坝 上 , 啥 特 征 ?汪 曾 祺 两 句 话 就 写清 楚 了 : “ 所谓 坝 是 一 溜大 山, 齐齐的, 远 看 倒像 是 一 座 大坝 。坝 上坝 下 , 海 拔悬 殊 。
汪 先 生 在 散 文 随 遇 而 安
沙岭
汪先 生还说 : “ 我还 画过一 套 口蘑
化添香 ・ 书 香
j
蔓 皇
汪曾祺笔下的坝上
张文睿推荐 :
作 家 汪 曾 祺 在 张 家 口 生 活 工 作 过
四年。 子 与 沽 源 》中,回忆 了在 坝 上 画 马 铃 薯 图谱 的 那 段 日子 。笔 调平 和 、 淡然 , 如
市 场 价 :5 6 . 8 0 元 作者 :汪 曾祺 出版社 :江苏 文艺出版 社 出 版 时 间 :1 9 9 4 年1 月
图谱 , 钢笔画 。口蘑都是灰 白色, 不需要
着 色 。”
汪 先 生 以 一 种 悠 闲 、轻 松 的 笔 调 ,
“人间送小温”:汪曾祺的北京

“人间送小温”:汪曾祺的北京作者:袁满芳来源:《博览群书》2016年第10期1948年,汪曾祺初到北京,谋职于午门历史博物馆,家住在右掖门下,据说原来是锦衣卫值宿的所在。
1950 年夏天,他又在东单三条、河泊厂住过一段时间。
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四年后,汪曾祺终于回京,其间先后住进国会街五号、甘家口,将近20年。
再后来,他举家搬到北京东南角的蒲黄榆,又住了十几年。
除了江苏、云南外,北京可谓是汪曾祺的第三家乡,占据了他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光,历经了人生的起起伏伏。
汪曾祺始终在默默地静观着这座古城,书写着它的琐碎人事,记录着它的四时流转,体味着它的酸甜苦辣。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
”这位从容恬静的文人,从来都是以爱与暖的姿势,拥抱着这个世界、这座古城,以及所有人群。
午门、国会街五号和甘家口初入偌大古城,汪曾祺没找到落脚之地,心中不免茫茫然。
幸而,不久老师沈从文为他在历史博物馆觅得一职,于是翻资料、做卡片、接待游客,接触的人寥寥无几,日常工作也乏善可陈。
当时汪曾祺住在午门右掖门,一到夜晚,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上了锁,他独自站立在午门下的大石坪上,万籁俱寂,满天繁星,于是给黄永玉写信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那时候筒子河边有杂耍的,算卦的,卖艺的,形形色色的人各有其生活。
汪曾祺好奇地观察着他们,算是苦中作乐。
汪曾祺接触到一些地道北京人,历史博物馆有一位叫老董的,一天三餐凑合填肚,时常自我调侃,但内心深处却愤世嫉俗,常发泄在儿子身上。
汪曾祺从其身上感受到了京城底层市民的朴素原态和内心焦灼。
他感到,自己所熟悉的民国初期文人笔下的北平古都,那些冲淡古意的诗句,那些风云际会的场景,那些悠远从容的姿态,都在渐渐褪色。
发配到沙岭子之后,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搬到了宣武门城墙下的国会街五号,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斗室,只能摆下一张双人床和一只五斗橱。
到1962年汪曾祺回京时,全家已住进了院子里的一座木头小楼上,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套间。
汪曾祺的爱情故事

等施松卿在北平安顿下来后,远在上海的汪曾祺匆匆辞职于次年也来到了北平。由于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和住处都成了问题。他只得在北大红楼一个同学的言舍里搭了一个铺,每晚去挤着睡,吃饭则全靠施松卿接济,汪曾祺在这儿度过了半年散漫而无着落的生活。后来还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为他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在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任职员,他把铺盖搬到午门旁的一个值班室里,从此有了一个小小的窝。
汪曾祺读中文系时,曾随沈从文学写作。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还要好。由此可见他多么赏识汪曾祺。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沈从文先生给过120分。
和其他用功苦读的学生不同,汪曾祺是个“异类”。“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福建长乐是个出人才的地方,现代著名作家郑振铎、冰心
都是长乐人。施松卿的祖辈是赤贫之家,她的父亲施成灿自幼跟随我的祖父在南洋闯荡,我祖父在那里是唱戏的。她父亲后在马来亚开了一家药店,日子才逐渐安定并慢慢变得好起来。大哥深感没有文化的痛苦,下决心让弟弟一边在药店当学徒,一边上夜校。几年下来,施成灿学有长进,考上了“医士”。有了这样一个名分,找工作就容易多了。不多久,他应聘到一个小镇的诊所当上了医生,施家的日子进一步变好。又过几年,施成灿回老家福建结了婚,随后把妻子带到马来亚,不久生了大女儿施松卿。
汪曾祺散文:马铃薯

汪曾祺散文:马铃薯马铃薯的名字很多。
河北、东北叫土豆,内蒙、张家口叫山药,山西叫山药蛋,云南、四川叫洋芋,上海叫洋山芋。
除了搞农业科学的人,大概很少人叫得惯马铃薯。
我倒是叫得惯了。
我曾经画过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
这是我一生中的一部很奇怪的作品。
图谱原来是打算出版的,因故未能实现。
一九五八年,我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一九六〇年摘了“右”派分子帽子,结束了劳动,一时没有地方可去,留在所里打杂。
所里要画一套马铃薯图谱,把任务交给了我,所里有一个下属的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源。
我在张家口买了一些纸笔颜色,乘车往沽源去。
马铃薯是适于在高寒地带生长的作物。
马铃薯会退化。
在海拔较低、气候温和的地方种一二年,薯块就会变小。
因此,每年都有很多省市开车到张家口坝上来调种。
坝上成为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
沽源在坝上,海拔一千四,冬天冷到零下四十度,马铃薯研究站设在这里,很合适。
这里集中了全国的马铃薯品种,分畦种植。
正是开花的季节,真是洋洋大观。
我在沽源,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情,真是说不清。
远离了家人和故友,独自生活在荒凉的绝塞,可以谈谈心的人很少,不免有点寂寞。
另外一方面,摘掉了帽子,总有一种轻松感。
日子过得非常悠闲。
没有人管我,也不需要开会。
一早起来,到马铃薯地里(露水很重,得穿了浅靿的胶靴),掐了一把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画。
马铃薯的花是很好画的。
伞形花序,有一点像复瓣水仙。
颜色是白的,浅紫的。
紫花有的偏红,有的偏蓝。
当中一个高庄小窝头似的黄心。
叶子大都相似,奇数羽状复叶,只是有的圆一点,有的尖一点,颜色有的深一点,有的淡一点,如此而已。
我画这玩意儿又没有定额,尽可慢慢地画,不过我画得还是很用心的,尽量画得像。
我曾写过一首长诗,记述我的生活,代替书信,寄给一个老同学。
原诗已经忘了,只记得两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画画不是我的本行,但是“工作需要”,我也算起了一点作用,倒是差堪自慰的。
[舌尖上的汪曾祺阅读答案]舌尖上的汪曾祺阅读
![[舌尖上的汪曾祺阅读答案]舌尖上的汪曾祺阅读](https://img.taocdn.com/s3/m/6131ec2126fff705cd170a06.png)
[舌尖上的汪曾祺阅读答案]舌尖上的汪曾祺阅读[舌尖上的汪曾祺阅读答案]舌尖上的汪曾祺阅读汪曾祺笔下的食物都不是单独作为个体出现的,总是会与一个事件、一段回忆联系起来,看起来是在谈吃,但细细品味起来,却能感觉到一种时光的流动,从他笔下的各种吃食读者便能知道时光蹉跎了什么,但尽管世事变换,汪曾祺笔下流露出来的那种从容淡然的态度却让人不禁一叹。
舌尖上的汪曾祺余显斌1汪曾祺是个传说,生活在清风明月中。
我手头有本《汪曾祺选集》,不厚,三百多页,在今天这个动辄砖头子厚的书籍朝外砸的时候,这真叫小册子。
一本小册子,让我反复读。
我把它放在床头,晴日夜晚,午睡醒来,都会看一篇:好文章如美食,不能撑开肚皮吃,这是作贱美食,也作贱自己,我不敢。
三百多页文字如一片月光,汪老在月光里喃喃讲叙着,讲叙着生活小事,谈论着生活里的美,让人听了心里一片清净,一片空明。
2这本书封面是白纸,大半空白,氤氲着一片山气,下角则用线条淡淡勾勒出市井小巷,还有撑着伞走的人。
封面清新淡雅,和汪老文风吻合。
汪老文字很美,那种美不是溪山云谷,也不是千里大川,是一滴清亮的露珠,映着青嫩的草儿;是一声蝉唱,在柔软的柳条里流泻;是一丝雨线,划过彩虹下的天空。
读这种文字,得如古人般净手,焚香。
读这样的文字,会产生古人一样的慨叹,齿颊留香,难以忘怀。
我读《受戒》,读《大淖记事》,竟有种面对唐诗宋词的感觉,心,也在语言的细雨里幻化成一朵莲花,清新优美。
他写独守空房的寂静,用珠子零落的声音衬静,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空明洁净的语言,不沾灰尘。
他写吃的,昆明旧有卖燎鸡杂的……鸡肠子盘紧如素鸡,买时旋切片。
耐嚼,极有味,而价甚廉,为佐茶下酒妙品。
色香辣五味俱全的文字,圆溜溜如同肉丸子。
他的一支笔,能让文字活色生香。
3别人的语言美是可举例的,汪曾祺的很难,因为他的语言美是与内容美水乳交融的。
因此,其书在手,低头皆美,抬头却张口结舌无法言说。
汪曾祺谈吃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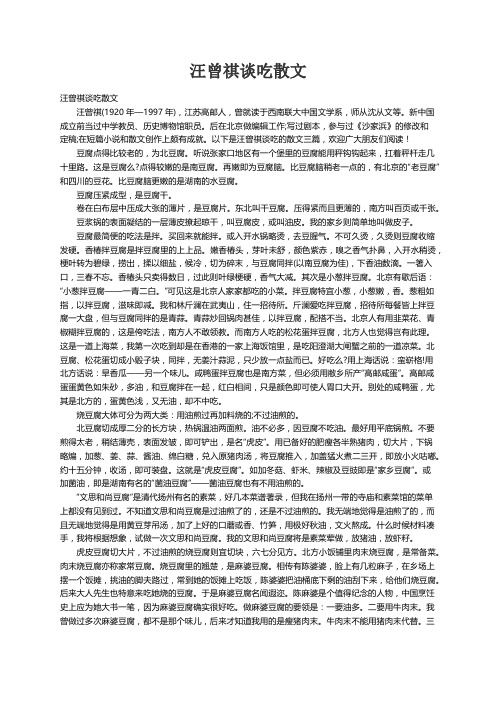
汪曾祺谈吃散文汪曾祺谈吃散文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苏高邮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
新中国成立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
后在北京做编辑工作;写过剧本,参与过《沙家浜》的修改和定稿;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
以下是汪曾祺谈吃的散文三篇,欢迎广大朋友们阅读!豆腐点得比较老的,为北豆腐。
听说张家口地区有一个堡里的豆腐能用秤钩钩起来,扛着秤杆走几十里路。
这是豆腐么?点得较嫩的是南豆腐。
再嫩即为豆腐脑。
比豆腐脑稍老一点的,有北京的“老豆腐”和四川的豆花。
比豆腐脑更嫩的是湖南的水豆腐。
豆腐压紧成型,是豆腐干。
卷在白布层中压成大张的薄片,是豆腐片。
东北叫干豆腐。
压得紧而且更薄的,南方叫百页或千张。
豆浆锅的表面凝结的一层薄皮撩起晾干,叫豆腐皮,或叫油皮。
我的家乡则简单地叫做皮子。
豆腐最简便的吃法是拌。
买回来就能拌。
或入开水锅略烫,去豆腥气。
不可久烫,久烫则豆腐收缩发硬。
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
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以南豆腐为佳),下香油数滴。
一箸入口,三春不忘。
香椿头只卖得数日,过此则叶绿梗硬,香气大减。
其次是小葱拌豆腐。
北京有歇后语:“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
”可见这是北京人家家都吃的小菜。
拌豆腐特宜小葱,小葱嫩,香。
葱粗如指,以拌豆腐,滋味即减。
我和林斤澜在武夷山,住一招待所。
斤澜爱吃拌豆腐,招待所每餐皆上拌豆腐一大盘,但与豆腐同拌的是青蒜。
青蒜炒回锅肉甚佳,以拌豆腐,配搭不当。
北京人有用韭菜花、青椒糊拌豆腐的,这是侉吃法,南方人不敢领教。
而南方人吃的松花蛋拌豆腐,北方人也觉得岂有此理。
这是一道上海菜,我第一次吃到却是在香港的一家上海饭馆里,是吃阳澄湖大闸蟹之前的一道凉菜。
北豆腐、松花蛋切成小骰子块,同拌,无姜汁蒜泥,只少放一点盐而已。
好吃么?用上海话说:蛮崭格!用北方话说:旱香瓜——另一个味儿。
汪曾祺与张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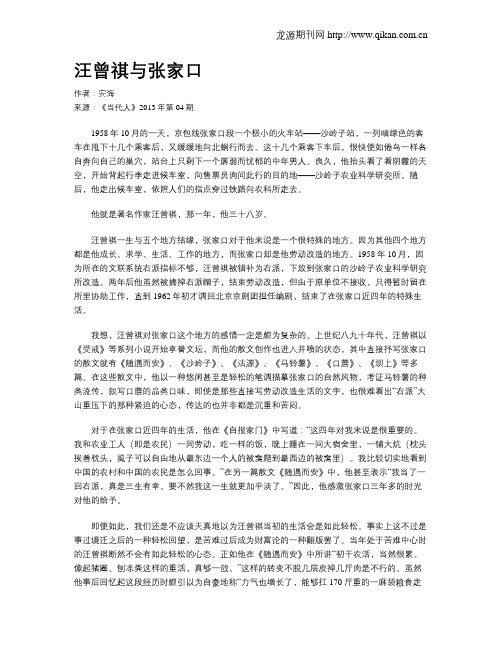
汪曾祺与张家口作者:安海来源:《当代人》2013年第04期1958年10月的一天,京包线张家口段一个极小的火车站——沙岭子站,一列暗绿色的客车在甩下十几个乘客后,又缓缓地向北蜗行而去。
这十几个乘客下车后,很快便如倦鸟一样各自奔向自己的巢穴,站台上只剩下一个孱弱而忧郁的中年男人。
良久,他抬头看了看阴霾的天空,开始背起行李走进候车室,向售票员询问此行的目的地——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
随后,他走出候车室,依照人们的指点穿过铁路向农科所走去。
他就是著名作家汪曾祺,那一年,他三十八岁。
汪曾祺一生与五个地方结缘,张家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因为其他四个地方都是他成长、求学、生活、工作的地方,而张家口却是他劳动改造的地方。
1958年10月,因为所在的文联系统右派指标不够,汪曾祺被错补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改造。
两年后他虽然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改造,但由于原单位不接收,只得暂时留在所里协助工作,直到1962年初才调回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结束了在张家口近四年的特殊生活。
我想,汪曾祺对张家口这个地方的感情一定是颇为复杂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汪曾祺以《受戒》等系列小说开始享誉文坛,而他的散文创作也进入井喷的状态,其中直接抒写张家口的散文就有《随遇而安》、《沙岭子》、《沽源》、《马铃薯》、《口蘑》、《坝上》等多篇。
在这些散文中,他以一种悠闲甚至是轻松的笔调描摹张家口的自然风物,考证马铃薯的种类流传,叙写口蘑的品类口味,即使是那些直接写劳动改造生活的文字,也很难看出“右派”大山重压下的那种紧迫的心态,传达的也并非都是沉重和苦闷。
对于在张家口近四年的生活,他在《自报家门》中写道:“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
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画土豆的大家

龙源期刊网 画土豆的大家作者:华明玥来源:《作文与考试·初中版》2019年第35期在张家口坝上草原地区,有一望无际的土豆花,白色的,浅紫的,深紫的。
这里也是当年汪曾祺下放时画土豆图谱、搞土豆品种研究的地方。
1961年春,因右派身份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改造的汪曾祺,因为态度温和,且有不错的美术才能,终于被分配到沽源马铃薯研究站,专职画画。
他真是过上了神仙一般无拘无束的日子。
这里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集中种植了全国各地上百个品种的土豆。
他每天上午蹚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漂亮的土豆花,插在玻璃杯里,然后对着花描画。
等天气渐凉,土豆成熟了,又把刨出的新土豆画在对应的花叶边上。
这些活儿对汪曾祺来说,都是专心致志的享受。
画完后,汪曾祺便把切开的土豆“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所以,老头儿曾得意地自夸:“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在这里,汪曾祺还发现坝上土豆长得好的原因之一:这是北方难得的高海拔地区,日照长,昼夜温差大,暴雨与暴晴相间,雨在盛夏下得透彻,之后又是十几天的晴天,太阳把土地都晒得龟裂。
这种酷烈的气候,反而促使土豆的根系向下延伸,让这种默默无闻的植物得到最深厚的孕育。
在这里,汪曾祺不但画成了《中国马铃薯图谱》,还暗自进行了小说格局的自由探索——当然,那都是无处发表的文字,写在笔记本上,有开头,无结尾。
最重要的是,在与土豆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汪曾祺培养出远超常人的顺应环境的能力,孕育了被外表素朴、慈蔼所掩盖的一双眼睛,一双对世间人情洞若观火的眼睛。
他静静等待了整整20年,犹如一窝塞外的薯种,等待大面积发芽的那一刻。
1980年,他的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发表。
晚熟的土豆,滋味如此鲜醇,叫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那一年,老头儿已经过了60岁。
◎萤火小语:生活是一面镜子,你若一遇到沟沟坎坎就气急败坏、抱怨心塞,那么,你看到的永远都会是一片灰暗的景象;你若从容自然、豁达阳光,生活必定回报你一个美好的明天。
汪曾祺的爱情故事

汪曾祺的爱情故事汪曾祺与施松卿的爱情故事1 马来侨领施成灿在作家汪曾祺的生平介绍中很少提到他是华侨的女婿这件事。
汪曾祺夫人施松卿,我的姑妈,是南洋长大的。
在马来亚,松姑一家的生活倒也衣食无虞。
她父亲很热心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后来成了著名侨领。
由于他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即使在日本人占领马来亚期间,到处捕杀爱国侨领,他也没有被人告发和出卖,他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而安然度过了那腥风血雨的三年八个月。
2 与汪曾祺同学的施松卿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施松卿小时候的生活很不安定。
她跟随着妈妈,福建、海外两边跑,时而在老家,时而在南洋。
她的小学、中学是在福建老家、马来亚和香港相继读完的。
1939年,施松卿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汪曾祺同一年。
她先是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同学。
不久感到功课繁重,十分吃力,加之这期间得了肺结核病,难以跟上课程,便在一年后转到了生物系,想向医学方向发展,以期有朝一日继承父业。
但生物系的课程也不轻松,而这时,她的肺病趋向严重,其时昆明的物质条件太差,无奈之下,只好休学一年到香港养病。
重回学校后,施松卿改读西语系,并一直坚持到毕业。
施松卿毕业后,因战争原因,家中无法对她给予正常的经济支持,一时又找不到工作,生活变得拮据起来。
为谋生计,她也到了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和汪曾祺成了同事。
两人在联大读书时虽不认识,却也对对方情况有所耳闻。
汪曾祺听说过,西语系有个女生,性格温和、善良,秀丽的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微笑;她长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虽有病,但那副慵慵懒懒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人称“病美人”。
相比之下,施松卿对汪曾祺的情况知道得更多一些。
她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过,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以后又不断地在报刊上读到汪曾祺的作品。
施松卿原来就爱好文学,上高中时还曾获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这就很容易对有西南联大才子之称的汪曾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她喜欢汪曾祺凭借厚实的古文基础,把精炼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他的创作之中,读来只觉得上下妥帖、顺畅,不似常见的那种诘屈聱牙。
有关汪曾祺的经典散文

有关汪曾祺的经典散文有关汪曾祺的经典散文汪曾祺经典散文1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派我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去画马铃薯图谱。
我从张家口一清早坐上长途汽车,近晌午时到沽源县城。
沽源原是一个军台。
而军台是清代在新疆和蒙古西北两路专为传递军报和文书而设置的邮驿。
官员犯了罪,就会被皇上命令发往军台效力。
我对清代官制不熟悉,不知道什么品级的官员,犯了什么样的罪名,就会受到这种处分,但总是很严厉的处分,和一般的贬谪不同。
然而据龚定庵说,发往军台效力的官员并不到任,只是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人去代为效力。
我这回来,是来画画的,不是来看驿站送情报的,但也可以说是效力来了,我后来在带来的一本《梦溪笔谈》的扉页上画了一方图章:效力军台,这只是跟自己开开玩笑而已,并无很深的感触。
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只身到塞外这地方在外长城北侧,可真正是塞外了来画山药(这一带人都把马铃薯叫作山药),想想也怪有意思。
沽源在清代一度曾叫独石口厅。
龚定庵说他北行不过独石口,在他看来,这是很北的地方了。
这地方冬天很冷。
经常到口外揽工的人说:冷不过独石口。
据说去年下了一场大雪,西门外的积雪和城墙一般高。
我看了看城墙,这城墙也实在太矮了点,像我这样的个子,一伸手就能摸到城墙顶了。
不过话说回来,一人多高的雪,真够大的。
这城真够小的。
城里只有一条大街。
从南门慢慢地遛达着,不到十分钟就出北门了。
北门外一边是一片草地,有人在套马;一边是一个水塘,有一群野鸭子自自在在地浮游。
城门口游着野鸭子,城中安静可知。
城里大街两侧隔不远种一棵树杨树,都用土墼围了高高的一圈,为的是怕牛羊啃吃,也为了遮风,但都极瘦弱,不一定能活。
在一处墙角竟发现了几丛波斯菊,这使我大为惊异了。
波斯菊昆明是很常见的。
每到夏秋之际,总是开出很多浅紫色的花。
波斯菊花瓣单薄,叶细碎如小茴香,茎细长,微风吹拂,姗姗可爱。
我原以为这种花只宜在土肥雨足的昆明生长,没想到它在这少雨多风的绝塞孤城也活下来了。
当然,花小了,更单薄了,叶子稀疏了,它,伶仃萧瑟了。
汪曾祺散文《天山行色》

汪曾祺散文《天山行色》汪曾祺散文《天山行色》我的童年的鸠声啊。
昆明似乎应该有斑鸠,然而我没有听鸠的印象。
上海没有斑鸠。
我在北京住了多年,没有听过斑鸠叫。
张家口没有斑鸠。
我在伊犁,在祖国的西北边疆,听见斑鸠叫了。
“鹁鸪鸪——咕,“鹁鸪鸪——咕……”伊犁的鸠声似乎比我的故乡的要低沉一些,苍老一些。
有鸠声处,必多雨,且多大树。
鸣鸠多藏于深树间。
伊犁多雨。
伊犁在全新疆是少有的雨多的地方。
伊犁的树很多。
我所住的伊犁宾馆,原是苏联领事馆,大树很多,青皮杨多合抱者。
伊犁很美。
洪亮吉《伊犁记事诗》云:鹁鸪啼处却春风,宛如江南气候同。
注意到伊犁的鸠声的,不是我一个人。
伊犁河人间无水不朝东,伊犁河水向西流。
河水颜色灰白,流势不甚急,不紧不慢,汤汤洄洄,似若有所依恋。
河下游,流入苏联境。
在河边小作盘桓。
使我惊喜的是河边长满我所熟悉的水乡的植物。
芦苇。
蒲草。
蒲草甚高,高过人头。
洪亮吉《天山客话》记云:“惠远城关帝庙后,颇有池台之胜,池中积蒲盈顷,游鱼百尾,蛙声间之。
”伊犁河岸之生长蒲草,是古已有之的事了。
蒲苇旁边,摇动着一串一串殷红的水蓼花,俨然江南秋色。
蹲在伊犁河边捡小石子,起身时发觉腿上脚上有几个地方奇痒,伊犁有蚊子!乌鲁木齐没有蚊子,新疆很多地方没有蚊子,伊犁有蚊子,因为伊犁水多。
水多是好事,咬两下也值得。
自来新疆,我才更深切地体会到水对于人的生活的重要性。
几乎每个人看到戈壁滩,都要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么大的地,要是有水,能长多少粮食啊!伊犁河北岸为惠远城。
这是“总统伊犁一带”的伊犁将军的驻地,也是获罪的“废员”充军的地方。
充军到伊犁,具体地说,就是到惠远。
伊犁是个大地名。
惠远有新老两座城。
老城建于乾隆二十七年,后为伊犁河水冲溃,废。
光绪八年,于旧城西北郊十五里处建新城。
我们到新城看了看。
城是土城,——新疆的城都是土城,黄土版筑而成,颇简陋,想见是草草营建的。
光绪年间,清廷的国力已经很不行了。
将军府遗址尚在,房屋已经翻盖过,但大体规模还看得出来。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汪曾祺在张家口
作者:苏北
来源:《读书》2014年第04期
关于汪曾祺在张家口的文章不多,除汪先生自己的几篇:《葡萄月令》、《随遇而安》、《坝上》、《寂寞与温暖》、《沽源》外,几乎没有汪曾祺在张家口四年生活的研究资料。
前不久看到重庆的陈光愣写的一篇短文《昨天的故事》,虽不长,却让我大为惊奇,简直为我们复原了一段那时的生活,一个活生生的汪曾祺立于眼前。
文中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一九五九年,在农科所一次学习大会上,领导传达中央文件,提到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以便集中精力研究理论问题。
传达完毕,汪忽然语出惊人,怀疑地说:“毛主席是不是犯了错误?”弄得四座为之失色,不知如何往下接话。
幸亏在边远的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人还比较纯朴,没人出来发难。
所领导愣了一会儿,岔开话题说:“大家的思路统一到党的指示的思路上来。
”敷衍了过去。
真不知道汪老头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也可能人在高压政治环境下,反而会说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话。
几天前,我见到汪朗,把上面的这个细节说给他听。
汪朗笑说,老头儿政治上比较幼稚。
这个细节真好,确实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汪的单纯。
写这个故事的陈光愣老人,一九五八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分配到沙岭子农科所之后,与汪在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后期又与汪同宿舍,这个回忆是可靠的。
这个细节也绝非空穴来风。
看看汪被打成右派的依据便可知道,这句话和他早期鸣放时的话语何其相似。
一九五七年鸣放时,汪在单位的黑板报上写了一段感想:
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过了几年,已经觉得凡事都是合理的,从来不许自己的思想跳出一定的圈子,因为知道那样就会是危险的。
他还给人事部门提意见,要求开放人事制度,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说“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府”。
一九五八年鸣放,他写了小字报《惶惑》,说:“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又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
看看,这些诗意的话,都挺飘逸呢。
也只有“全是诗”(黄裳语)的汪曾祺能说得出来。
打成右派后,他回家同妻子说:我现在认识到我有很深的反党情绪,虽然不说话,但有时还是要暴露出来。
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条就是自杀,没有第三条路。
他凄切地向妻子转说单位领导林山和他谈话的内容,忍不住哭了起来。
到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汪最初的劳动是淘大粪、起猪圈粪。
陈光愣回忆:上面派他跟一个又高又瘦胡子拉碴的老头一起赶大粪车。
每天往返于沙岭子和张家口之间,在城里大街小巷招摇过市,骡子拉着大粪车在公路上地走,汪总是坐在车架上,头戴着护耳的深色绒帽,双手插在棉衣袖筒里,一面听着骡蹄的叩击声,一面默默地眯起眼在想,一副老实巴交的农人的样子。
最锻炼人的当然是在寒冬刨冻粪了。
室外零下几十度,人畜粪冻得硬如石头,得用钢钎、铁锹才能把粪弄进粪车。
这样的劳动,汪也卖力干。
汪自己在《随遇而安》中说:“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
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
”陈光愣在《昨天的故事》中关于汪的描述是这样的:每每干得满头大汗、浑身蒸汽笼罩,背心汗渍了也不敢脱去棉袄,进入了中医所谓的“内热外寒”的状态。
在劳动之余的政治学习会上,汪畅谈劳动心得体会,说:“古人为了治病,臭粪尚可嘴尝。
现在改造思想,闻一闻臭粪又何妨?”(这是陈光愣的记述)汪自己后来则平静地说:“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
”
在劳动锻炼的后期,汪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转到果园上班,活则相对比较轻松了。
他的《果园杂记》、《关于葡萄》和《葡萄月令》就是在果园劳动的产物。
他是喷波尔多液的能手。
他自己说:“这是一个细活。
要喷得很均匀,不多,也不少。
喷多了,药水的水珠糊成一片,挂不住,流了;喷少了,不管用。
树叶的正面、反面都要喷到。
”说:“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
……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
”最后汪说:“我觉得这活比较有诗意。
”
还是归到诗上去。
在果园劳动之余,汪读了很多书。
汪自己说:“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
”陈光愣回忆说:“他的床头小桌上,堆满书籍,古籍为多。
晚上,汪多数时间是坐在小桌前读书,读的多是《诗经》。
汪有时说,如果能有那么一天的话,就去专门研究《诗经》。
”汪先生在《随遇而安》中说:“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
”在《七里茶坊》中说:“带了两本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
”汪晚年写随笔,时有提到以上的书,我想多是在张家口读书时留下的印象。
人在艰苦环境下读的书,更容易记住。
有意思的是,汪在张家口时,还到一个叫沽源的县画了一段时间马铃薯。
汪说:“去时大约是深秋,待了一两个月,天冷了,才离开。
”在沽源,他每天一早起来,就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
到马铃薯成熟时,就画薯块。
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
他在《随遇而安》中骄傲地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而且他能分出土豆的品种名称:“男爵”最大,“紫土豆”味道最好,还有一种类似鸡蛋大小的,很甜,可当水果吃。
(这个老汪,真是个好吃精!)—最近有人到沽源考察,还有一种叫“黑美人”,是黑瓤的(土豆多为黄瓤白瓤)!这一款,汪先生并没提到!
关于汪画马铃薯图谱,黄永玉后来在回忆中这样说:他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在那里好几年,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他就来一封信,需要什么就要我帮忙买好寄去。
他在那里画画,画马铃薯,要我寄纸和颜料。
汪自己在《随遇而安》里也说:“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
”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
眸子炯如虎。
这个朋友大约是黄永玉了。
那一册《中国马铃薯图谱》丢失了太可惜。
汪后来提到过多次,可他毫无惋惜之意。
倒是他自得地说:“薯块更好画了,想画得不像都不大容易。
”
近些年,有人到张家口寻访汪曾祺的足迹。
多数人不记得当年那个黑瘦的中年人了。
去到旧地,见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已物是人非,倒是有几排旧房子,门前一棵大榆树,屋后一块空地,说曾是储藏马铃薯的大窖。
有一个叫赵喜珍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人瘦瘦的,性格温和。
只待了几个月。
冬天没有得画了,就走了。
汪先生在张家口待了四年,但这四年对汪意义非凡。
他自己说,我和农民一道干活,一起吃住,晚上被窝挨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
是的,汪小时候虽在高邮县城,可家里富裕,他没有真正接触农民、了解农民,在昆明、上海、北京,则更不可能。
其实张家口是给汪补上了这一课,虽然是不得已的。
关于张家口,汪后来写了九个短篇小说,十三篇散文,有十多万文字,可以出一本《汪曾祺文学地理之张家口》,这也是汪的收获。
汪后来写文章和接受采访时说:“我三生有幸,当了一回右派,否则我这一生更平淡了。
”虽是自嘲,但也是实情。
汪在生活中总是能看到美,不管在何种境遇下。
他自己说,我认为生活是美的,生活中是有诗的。
我愿意把它写下来,让我的读者,感到美,感到生活中的诗意。
关于张家口,也是一样的。
他写了《萝卜》(其中一节专门写张家口的心里美萝卜)、《坝上》、《果园杂记》、《葡萄月令》、《寂寞与温暖》等名篇,都写得很美。
比如在《坝上》,他写到口蘑,写了多种口蘑的品种,并说他曾采到一个口蘑,晾干带回北京,做了一碗汤,一家人喝了,“都说鲜极了!”写到关外的百灵鸟,到北京得经过一段训练,否则有关外口音:“咦,鸟还有乡音呀!”—这就是汪曾祺。
当然,他的《葡萄月令》,更是文学名篇了。
看来,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美、热爱文学的人,到哪里都能发现生活之中的美,生活之中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