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性灵说的形成
袁枚的“性灵说

关于[袁枚的“性灵说”(上)]的字幕:∙我们现在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第十三讲,袁枚的“性灵说”清代袁枚的“性灵说”。
袁枚是清代乾隆皇帝时代的江南才子,也是著名的一个文学评论家。
他的诗话代表作就是《随园诗话》,这是很有名的。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字子才,号随园老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乾隆时候的进士,曾任江宁等地的知县,然后他辞官后就居住在江宁,就是现在南京附近的江宁。
他在小仓山修了一个园林,号随园。
∙他后来写的一些书都是以随园命名,像《随园诗话》等。
他的书信颇具特色,他的诗歌,多抒发其闲情逸致。
所以袁枚在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有才学,有才华的一个文人。
∙他的文学批评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性灵说”,“性灵说”他的文学批评的思想继承了晚明思想解放者的观点,特别是公安三袁和李贽、汤显祖等人的思想。
在学术思想上,袁枚反对盲目地崇拜圣人经典,他对当时的乾嘉考据学,就是乾隆年代的汉学考据也表示不满,∙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因为他认为宋学空谈性理,固然不好,像程朱理学。
但汉学就是从汉代,因为乾嘉考据学主张就是继承两汉的学术,他认为两汉的学术更有弊,为什么呢?两汉的学术引导读书人钻牛角尖,在考据当中讨生活。
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袁枚的思想是比较解放的。
下面我们来谈袁枚性灵说的第一个问题,一“性灵说”什么是性灵?什么是袁枚的性灵说?袁枚性灵说的真髓,就是对于性灵的倡导。
明代公安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公安三袁当中的老二袁宏道,在《序小修诗》当中,∙曾经称赞他的弟弟袁中道的诗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以最早的性灵说是从公安三袁来的。
袁枚谈性灵也是继承了公安派的性灵说,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袁枚的性灵说又和公安三袁有所不同,他有明显地针对性,∙这就是反对乾隆皇帝的沈德潜的诗教说与格调说。
沈德潜是乾隆时候的一个著名的诗歌批评家,他写过五格诗的别栽,也就是《唐诗别裁》、《宋诗别裁》、《元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还编过《古诗源》。
清诗概述48性灵说之袁枚

清诗概述48性灵说之袁枚清诗概述48——清史札记之四十四我楚狂人四、清诗流派184.性灵说1清朝乾隆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
他对清代以来的各种诗歌理论观点予以全面排斥。
他的这种反传统、求创新的特点,是对于清代以来道统文学观的强大权威的挑战。
性灵派的成就主要为诗歌,其中七绝和七律尤佳。
如《春日杂诗》于恬淡宁静中透出轻松活泼的生活气息,十分舒畅自然;《马嵬》命意新颖,感情倾向也发生了根本转变。
性灵说可说是明代公安派的余绪,其代表人物袁枚,前文在“清代散文”中已经说过,这里先说袁枚的诗歌。
(1)袁枚与他的诗1袁枚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主张的“性灵说”在当时独树一帜。
“性灵说”对流行于当时诗坛的各种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和扫荡,一改清诗风貌,影响深远。
袁枚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以情为本,主张“诗写性情”,即从诗歌的创作内容出发,要求诗歌创作主体抒发真情实感,以真情去充盈诗作的内容。
这是其诗论的核心部分。
在他看来,诗人唯有抒发真情,才能体现出诗歌自身的抒情本质,才能表现出自然清新、生动活泼、风趣别致的艺术魅力。
他不仅把抒发真情作为采集和鉴赏诗歌的标准,而且以身作则,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一以贯之,创作出很多富有真情的诗文作品。
袁枚除了要求诗歌创作主体要抒发真实情感之外,还对诗人要具备一定的诗才天分道出了自己的见解。
袁枚认识到因为每个人的诗才禀赋各有所异,就会呈现出“笔性灵”和“笔性笨”的情况,于是就生发出禀赋灵性与创作灵感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诗才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他甚至用夸张、过分的语言把天分的作用提升到一个绝对的地位。
其实,袁枚在认识到“才”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学识的重要性。
他清晰地认识到每个人的性情各异,所以诗歌创作要情出于己,体现出“著我”的精神,强调“作诗,不可以无我”,激烈反对一切束缚诗歌抒发真情的制约因素,高呼“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
浅论袁枚的“性灵说”

浅论袁枚“性灵说”“性灵说”是古代试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
清代袁枚的倡导最力。
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未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要直接抒发诗人的真实情感,是对人自然心声的流露。
基于源远流长得历史,袁枚的“性灵说”主要是在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下的产物。
它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反对对理学的束缚,批判当时文坛复古模拟风气。
从诗歌创作的主体出发,从真情、个性、诗才三个方面论证了诗人应率真地表达感情,表现个性,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破除雕章琢句、堆砌典故、以学问为诗。
关键词:性灵、真情、诗才、个性、反格调一.“性灵说”的渊源古典文论中首先采用“性灵”一词的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
《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
其后南朝钟嵘在其《诗品》中则直接以“性灵”论诗的本质。
他曾评论阮籍《咏怀》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
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基于此,他还提倡抒发感情的“直寻”、抨击“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等,这些都直影响了后来袁枚性灵说的核心内容。
唐代诗文中“性灵”一词更为普遍。
一是沿用南北朝“性灵”的含义,如皎然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诗式》);二是对其的发展与开拓,如高适《答候少府》中“性灵出石象,风骨超常伦。
”等将“性灵”与“才”相联系。
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剽袭模拟,“掉书袋”的习气,主张“风趣专写性灵”,推崇“天分”,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与后来袁枚的性灵说的内涵十分接近。
明代李贽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强调要用“赤子之心”作文,反对假人假事,认为“天下之至文”都是“童心”的体现,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性灵”,反对儒家礼义的约束。
同一时期的公安三袁反对明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的思想,提出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如袁宏道在《识张幼于箴铭后》中:“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
袁枚的性灵说及其诗歌创作

伪 险恶 , 指出了封 建制度 的不合理 。袁枚 在诗歌 中直 接抨击封建制度 , 这不仅需要超卓识见和过人胆量 , 而
且 也 正 是 其 真 性 情 的 自然 流 露 。 2 以平等、 . 民主 的 态 度 尊 重 下 层 人 民 。 虽 然 身 在
袁枚 巨大的影 响。他宣扬性情至上 , 肯定情欲合理 , 强 调情是其诗 论 的核 心 , 女 是真情 的 本源 。他 在《 男 遣
兴》 诗 中说 :郑 孔 门前 不 掉 头 , 朱 席 上 懒 勾 留 。 明 一 “ 程 ” 确表示对孑 子 以来 的儒学特别是 程颐 、 熹 的理 学 的 L 朱 反叛 。他还认 为“ 宋学 有 弊, 汉学更 有 弊” 进 而 质疑 , “ 六经 ”公开宣称“ 经虽读不全信” 并借庄子的话抨 , 六 , 击“ 六经尽糟 粕” 《 然 作》 。他 的言 行 可谓 大胆 出 (偶 ) 格、 惊世骇俗 。他对虚伪 的假道学深恶痛绝 , 常常借机 加 以嘲讽抨击 , 表现 出封建社会 末期个性 解放思 想的 再次苏醒。 这些思想体现在文学理论 上, 就是 他的“ 性灵说” 。 袁 枚 的 “ 灵 说 ” 在 内 容 上 包 括性 情 、 性 和 诗 才 性 , 个 三个要素 。袁枚认 为“ 情 以外本无 诗” “ 性 ,若夫 诗者 , 心之声也 , 性情所 流露者也 ” “ ,天性多 情句 自工 ” 。就 是说诗生于性情 , 性情 是诗 的本 源和灵魂 。他所说 的 性情 , 就是真情。诗人 内心 要有真情 实感才 有创作 构 思的可能性 , 诗歌 中的景 物形象归根 结底也是 为 了体 现“ 的。而这种性情要表现出诗人的独特个性 。因 情” 此, 袁枚又认为“ 诗 , 可 以无我 ” “ 作 不 ,有人 无我 , 是傀 儡也” 。就是说没有个性 的诗人所作 的诗就 如同受人 摆布的“ 傀儡” 缺乏真正的生命力 。没有个性 , 就丧 , 也 失了真性情 。他在 《 续诗 品》 中专辟“ 著我 ” 品 , 一 就是 明确提倡创写 “ 有我” 旨。这是性灵说 审美价值 的核 之 心 。袁枚还进一步认为 , 仅有性 情 、 个性是 不够 的 , 还 应具备表现这一切 的诗才 。“ 诗人无才 , 不能役典籍运 心灵 ”有诗才 的人在 进行艺术构 思时才会 产生 灵机 , , 善 于把握灵机 , 易于成篇 。这里所说的灵机 , 就是今人 所谓灵感。艺术构思 中的灵机与才 气 、 分与 学识要 天 结合并重 。 这 三 个 方 面 的 有 机 结 合 , 成 了 完 整 的 诗 歌 理 论 构 体 系, 是晚明公 安派文学 主张 的隔代复兴 , 为清诗开创 新 的局 面打下 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
袁枚的研究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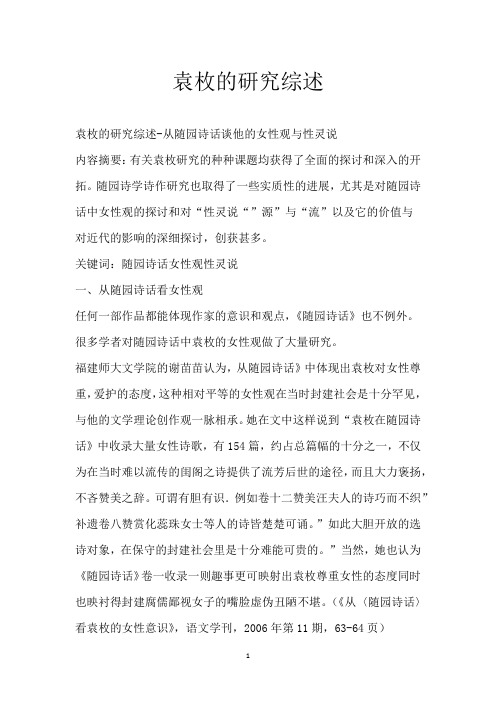
袁枚的研究综述袁枚的研究综述-从随园诗话谈他的女性观与性灵说内容摘要:有关袁枚研究的种种课题均获得了全面的探讨和深入的开拓。
随园诗学诗作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对随园诗话中女性观的探讨和对“性灵说“”源”与“流”以及它的价值与对近代的影响的深细探讨,创获甚多。
关键词:随园诗话女性观性灵说一、从随园诗话看女性观任何一部作品都能体现作家的意识和观点,《随园诗话》也不例外。
很多学者对随园诗话中袁枚的女性观做了大量研究。
福建师大文学院的谢苗苗认为,从随园诗话》中体现出袁枚对女性尊重,爱护的态度,这种相对平等的女性观在当时封建社会是十分罕见,与他的文学理论创作观一脉相承。
她在文中这样说到“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收录大量女性诗歌,有154篇,约占总篇幅的十分之一,不仅为在当时难以流传的闺阁之诗提供了流芳后世的途径,而且大力褒扬,不吝赞美之辞。
可谓有胆有识.例如卷十二赞美汪夫人的诗巧而不织”补遗卷八赞赏化蕊珠女士等人的诗皆楚楚可诵。
”如此大胆开放的选诗对象,在保守的封建社会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当然,她也认为《随园诗话》卷一收录一则趣事更可映射出袁枚尊重女性的态度同时也映衬得封建腐儒鄙视女子的嘴脸虚伪丑陋不堪。
(《从〈随园诗话〉看袁枚的女性意识》,语文学刊,2006年第11期,63-64页)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李祥林是这样认为的:“这个率意行事又骨节峥峥的袁先生,竟然拿身份低贱的青楼女子跟权势赫赫的当朝尚书作比,一番话把道貌岸然的对方顶撞得下不了台。
”由此窥豹,可知他潜意识中对小女子地位的认识,早已跟传统男尊女卑的两性观拉开了距离。
”,“他同情妇女,赞赏女子之才,收了许多女弟子,与旧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相异,却又以尚无子嗣为由,先后娶了数位小妾,而且还喜欢追求美妓,颇为人所诟病。
一代旷世才子的袁枚,就是这样一位思想、行事从常情常理的眼光看难以说他是伟大还是庸俗的人物,只能采用简单的二分法,说他是既伟大,又庸俗。
袁枚《性灵说》

古代文论袁枚与性灵说教师:马建智学生:李越专业:文新学院汉语言文学084班学号:200830401137袁枚与性灵说“性灵”一词是由“性”与“灵”两个字组成。
“性”的本意是人类本性,论语中有“人之初,性本善”;“性”也指人的性情,即人的秉性气质。
灵的本意甚多,与性灵美学相关的涵义有:人的主观精神:人的聪明灵活。
“性灵”一词出现较迟,不会早于南北朝时期。
首先采用“性灵”一词的文论著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
其中《原道》篇说:“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
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
”唯有人具有灵智的天性,才能产生文章。
后来南北朝的钟嵘、宋代的杨万里、明代的李赞、公安三袁等人都对“性灵”加以丰富与发展。
袁枚总结先人经验,吸收历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精华,完善并进一步发展了性灵说。
使之成为“清代四派重要诗论中最有活力,也最有革新精神的一个诗派,在诗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1性灵说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
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给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使诗文普遍陷入了模拟蹈袭的死胡同。
李贽在《童心说》中就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问题,认为只要写出了“童心”即是好作品,这是对复古主义文艺思想的有力的抨击。
公安派正是进一步发挥了李贽这个思想,提出了一个“变”字,指出每个时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具有独创性,才是好作品。
性灵派的代表人物袁枚主要活动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这个时期,复古主义已不象明代那么猖獗。
前期乾隆有王士镇鼓吹神韵说, 片面倡导清远、冲淡、含蓄之作。
翁方纲推崇的肌理说刚刚出现,主张以考据为诗。
左右诗坛的主要是沈德潜标榜的格调说,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复古主义的风气。
这些诗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 使清诗面临着僵化的危机。
为此, 袁枚独辟蹊径, 从历代诗歌理论中吸取关于诗歌吟咏情性、抒写性灵的观点,加以丰富发展, 再次树起性灵说大旗, 与上述诗学观相抗衡, 以开创诗坛的新局面。
从“言志”到“言己”:袁枚“性灵说”与乾隆后期自利性话语的传播

从“言志”到“言己”:袁枚“性灵说”与乾隆后期自利性话语的传播本文作者郑宇丹教授摘要“性灵说”始于南朝,经由刘勰的《文心雕龙》回归“诗言志”的传统。
清乾隆年间的袁枚试图以“真性情”消解礼教的束缚,将诗学的重心由“言志”转向“言情”。
在此过程中,随园给予袁枚对外交往的空间,诗话给予袁枚臧否文坛的权力,一个用“温和—生产—利润”原则扩散话语权力的模式得以建立,“言己”成为此模式的重要表征。
在文网密布的乾隆朝,“性灵说”的存活是“去政治化”的结果,也意味着士人阶层价值取向的异化,从以“言志”为核心的精神传统,逐渐走向重利轻义的一面。
这种文化的下行加剧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危机。
关键词袁枚;性灵说;乾隆时期;诗言志;文化传播;话语;价值观乾隆一朝,恰如其年号所寓意的,曾出现“天道昌隆”的局面。
其时,清朝疆域空前辽阔,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人口从乾隆六年(1741)的1.43亿激增至乾隆六十年的2.97亿,国库存银达7 300万两以上;文化方面亦取得卓越成就,完成了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编撰。
然而,盛中藏衰,尤其在乾隆后期,看似枝繁叶茂的帝国已面临深刻危机——土地兼并愈发严重,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社会风气骄奢靡费,各级官吏贪腐无度。
最令人诟病的是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总计135起,占清朝全部文祸的80%左右。
乾隆帝像在这样一个动辄因文获罪的年代,却有一人“以诗、古文主东南坛坫,海内争颂其集”,桐城派领袖姚鼐为此称叹:“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
”不仅如此,他还因文致富,广收弟子,放情声色,得享82寿岁。
此人便是袁枚,曾获“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的美誉。
因名气与大学士纪昀不相上下,更有“南袁北纪”之说。
然而,与历代正统文人所获“清誉”不同,有关袁枚的评价“毁誉参半”。
既有乾嘉时期的文学家洪亮吉将袁枚与白居易相提并论,赞其“性灵句实逼香山”;又有同期史学大家章学诚贬其“乃人伦之蟊贼,名教所必诛”。
天真自是一家言_袁枚_性灵_说简论

探询主观性真理的意义叩问方向, 而且对个体心性和人的存 在的勘探, 抵达了理性不能照亮的“黑夜”。
参考文献; [1]赵 毅 衡 . 神 性 的 证 明 : 面 对 史 铁 生 . 开 放 时 代 , 2001 年 7月. [2]林 舟.生 命 的 摆 渡— ——中 国 当 代 作 家 访 谈 录.海 天 出 版 社, 1998年.第175页.
“笔 性 灵 ”不 仅 指 灵 犀 ( 天 分 ) , 还 指 灵 机 , 意 思 同 灵 感 近 似 。 就 是 说 , 诗 人 应 该 在 兴 会 淋 漓 、灵 感 爆 发 时 赶 紧 捕 捉 诗 意, 才能妙手偶得, 写出自然天成的“天籁”之诗。“凡有著作, 特 寡 思 功 , 须 其 自 来 , 不 以 力 构 。 ”(《诗 话 》卷 四 ) 写 诗 要 等 待 灵感到来, 这是创作的最佳时刻。此时, 诗人对外物的感受力 最强, 突然意象契合, 思如泉涌, 运笔挥洒自如, 得心应手。灵 感 不 来 , 诗 思 枯 竭 , 勉 强 写 作 , 肯 定 写 不 出 好 诗 。《续 诗 品 》又 云:“混元运物, 流而不住。迎之未来, 揽之已去。诗如化工, 即 景成趣。逝者如斯, 有新无故。因物赋形, 随影换步。彼胶柱 者, 将朝认暮。”灵感有骤来骤去、来去匆匆的特点。如不及时 捕捉, 去之可惜, 难以为继。“作诗火急追亡逋, 情景即失难再 摹 。 ”( 苏 轼 语 )“好 诗 须 在 一 刹 那 上 揽 取 , 迟 则 失 之 。 ”( 徐 增 语) 这是符合形象思维实际的。以上三点, 便是袁枚“性灵”说 的基本内容。约而言之, 写诗要抒发性情, 要抒发独具的个 性, 写出个性化的诗, 这就必须具备天分。光有天分还不行,
第三, 天分。“性灵”既指性情、个性, 又包括“笔性灵”的含 义。袁枚说:“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 笔性笨虽写闺房 儿女亦少风情。”(《补遗》卷二) 灵, 就是灵犀、灵机。“但肯寻诗 便有诗, 灵犀一点是吾师。斜阳芳草寻常物, 解用都为绝妙 词。”(《遣兴》) 寻常之物写入诗中, 变为绝妙之词, 这便需要一 种不寻常的才能, 需要天分, 袁枚力主写诗的天分。他认为: “诗文之道, 全关天分, 聪颖之人, 一指便悟。”(《诗话》卷十四) “用笔构思, 全凭天分。”(《诗话》卷十五) 天分就是“聪颖”,“聪 颖”的表现就是“一指便悟”, 悟, 就是严羽说的“妙悟”, 妙悟就 是对诗歌艺术特殊的心领神会、融会贯通。是对诗的理解能 力, 也是捕捉诗意、描绘诗境的能力。“鸟啼花落, 皆与神通。人 不能悟, 付之飘风。惟我诗人, 众妙扶智。”(《续诗品》) 一切景 语皆情语, 情景交融、思与境偕, 全靠妙悟。
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精神

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精神袁枚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和文化名人,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他所提出的“性灵说”对于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美的本质、美感、审美标准乃至文艺创作的哲学思考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探讨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精神。
一、袁枚“性灵说”的提出与发展二、“性灵说”对于美的本质的观照三、“性灵说”对于美感的理解与表达四、“性灵说”对于审美标准的建构与塑造五、“性灵说”对于文艺创作的启示与借鉴六、袁枚的美学思想与当代美学的联系与发展七、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精神对于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八、袁枚“性灵说”的局限性及其对于美学思想的挑战九、对于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精神的借鉴与思考综上所述,袁枚“性灵说”是一种独特而深刻的美学思想,其内涵专注于对于“性灵”的探索与研究,旨在揭示美的本质、美感、审美标准以及文艺创作的哲学思考,对于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与当代美学的联系及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然而,“性灵说”在应用方面存在局限性,需要面临一系列挑战,这也提醒我们要深入思考并借鉴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精神,推进美学理论的发展。
1. 袁枚“性灵说”的提出与发展本部分将介绍袁枚“性灵说”的概念、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相关内容,探究“性灵说”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和过程,为后续对“性灵说”美学精神的探讨做铺垫。
2. “性灵说”对于美的本质的观照美学的起点是美的本质问题,本部分将探究袁枚“性灵说”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和阐述,分析“性灵”这一概念在美学中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探讨“性灵说”对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观照。
3. “性灵说”对于美感的理解与表达美感是感知美的一种心理体验,本部分将探究袁枚“性灵说”在美感理解和表达方面的贡献,分析它对于美感体验、感性认识与意蕴表达等美学问题的影响和贡献。
4. “性灵说”对于审美标准的建构与塑造审美标准是衡量美的尺度和标准,准确的审美标准对于判断和欣赏美的价值至关重要。
本部分将探究袁枚“性灵说”对于审美标准的建构和塑造,分析其对于审美标准的形成和树立的贡献和价值。
试论袁枚“性灵说”的基本内涵

试论袁枚“性灵说”的基本内涵人文学院陈勇指导老师张晚林摘要:“性灵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审美理论。
“性灵”一词最早出现于南朝刘宋。
范泰、谢灵运、何尚之、颜延之率先使用。
明代,经李贽和“公安三袁”等人的不懈努力,到清代的袁枚时,发展成为一套理论性强、又适合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内涵丰富的审美理论。
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形成了一套包括真情,个性,诗才三个方面的比较完整的诗论体系。
本文梳理了“性灵说”的历史渊源,并着重论述袁枚“性灵说”的基本内涵。
关键词:袁枚;性灵;真情;个性;诗才Simple analyse the basic intension on“TheTheory of Native Sensibility” of Yuan MeiSchool of humanism and socialism :Chen Y ong Director: Zhang wanlinAbstract:" the theory of native sensibility ”, it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aesthetic theory in the theory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the native sensibility”appear o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Song Liu first. Fan Tai , Xie Linyun , He Shangzhi, whom face prolong take the lead in using. Ming Dynasty, pass gift presented to a senior at one's first visit as a mark of esteem Li Zhi and "Gong An Three Y uan " untiring efforts of people, Y uan Mei,in Qing Dynasty, develop into a theory strong , meaningful aesthetic theory suitable for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reating again. It and the theory of romantic charm , the theory of style , the theory of skin texture to be and one of the theory groups of four major poems of earlier stage of Q ing Dynasty, having formed a suit of true feelings of including, individual character , just more intact poem of three respects talks about the system in the poem. This text comb historical origin of " the theory of native sensibility ", expound the fact basic intension that " the theory of native sensibility " of Y uan Mei emphatically.Key Words:Y uan Mei; the native sensibility ; True feelings ; Individual character ; talent and learning一、“性灵说”的发展“性灵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理论。
从作品中探析袁枚的“性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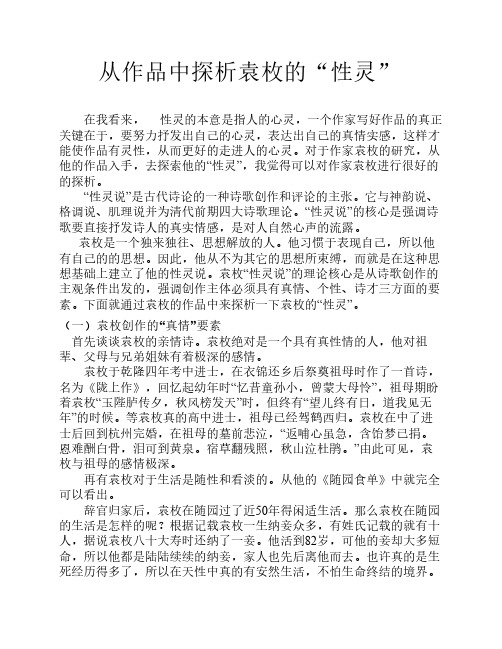
从作品中探析袁枚的“性灵”在我看来,性灵的本意是指人的心灵,一个作家写好作品的真正关键在于,要努力抒发出自己的心灵,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样才能使作品有灵性,从而更好的走进人的心灵。
对于作家袁枚的研究,从他的作品入手,去探索他的“性灵”,我觉得可以对作家袁枚进行很好的的探析。
“性灵说”是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
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要直接抒发诗人的真实情感,是对人自然心声的流露。
袁枚是一个独来独往、思想解放的人。
他习惯于表现自己,所以他有自己的的思想。
因此,他从不为其它的思想所束缚,而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性灵说。
袁枚“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的,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的要素。
下面就通过袁枚的作品中来探析一下袁枚的“性灵”。
(一)袁枚创作的“真情”要素首先谈谈袁枚的亲情诗。
袁枚绝对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人,他对祖辈、父母与兄弟姐妹有着极深的感情。
袁枚于乾隆四年考中进士,在衣锦还乡后祭奠祖母时作了一首诗,名为《陇上作》,回忆起幼年时“忆昔童孙小,曾蒙大母怜”,祖母期盼着袁枚“玉陛胪传夕,秋风榜发天”时,但终有“望儿终有日,道我见无年”的时候。
等袁枚真的高中进士,祖母已经驾鹤西归。
袁枚在中了进士后回到杭州完婚,在祖母的墓前悲泣,“返哺心虽急,含饴梦已捐。
恩难酬白骨,泪可到黄泉。
宿草翻残照,秋山泣杜鹃。
”由此可见,袁枚与祖母的感情极深。
再有袁枚对于生活是随性和看淡的。
从他的《随园食单》中就完全可以看出。
辞官归家后,袁枚在随园过了近50年得闲适生活。
那么袁枚在随园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根据记载袁枚一生纳妾众多,有姓氏记载的就有十人,据说袁枚八十大寿时还纳了一妾。
他活到82岁,可他的妾却大多短命,所以他都是陆陆续续的纳妾,家人也先后离他而去。
也许真的是生死经历得多了,所以在天性中真的有安然生活,不怕生命终结的境界。
性灵派研究——袁枚性灵思想成因浅析

摘要:同众多思潮的产生一样,性灵派的形成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及人文背景。
性灵说在清袁枚时期渐趋顶峰,既有前人的积淀,也包含有清一代特殊的环境以及个人因素,我们可以从社会历史因素以及袁枚独特的成长经历解析性灵派的成因。
关键词:性灵派;袁枚;社会历史环境;个人禀赋王英志在其《性灵派研究》中说:“在清代众多诗派中力量最强大、成绩最卓著、影响最深远,并最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是性灵派,性灵派亦是中国古代自觉型文学流派中名声最著者之一。
”从宋杨万里到明李贽“童心说”、公安三袁“不拘格调,独抒性灵”,到清袁枚性灵学说发展到高峰,形成主盟一时文坛的性灵派。
性灵学说至袁枚臻于成熟,成因诸多;从时代、社会以及个人成长历程切入分析性灵派和袁枚,对其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一、双目自将秋水洗袁枚一生主要活动于雍、乾两朝。
此期正处康乾盛世,经济文化繁荣,各种文化思潮异彩纷呈;统治阶级为稳定政权,对思想钳制力度加大。
此期出现的崇理学与反理学的论争、汉学的兴盛以及性灵思潮的发展对袁枚性灵思想形成起到很大的推助作用。
(一)反理学:情所最先,莫如男女清初政府在康熙帝时大力推崇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圣主仁皇帝圣训》卷十二曰:“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
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訾议。
朕以为孔、孟之后,有稗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
”“盛世最高统治者推崇理学,维护理学的正统地位,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言论,目的在于愚弄百姓,以汉学引导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巩固其一统之势。
1、对理学的反叛康乾时期,政局稳定,经济恢复发展,一度销声匿迹的启蒙思潮逐渐兴起。
反理学理论的盛行是这一表现。
其中最突出的是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颜李学派。
针对程朱学派提出理善气恶之说,颜元主张“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 ,强调理气本为一体,而气质本善并不恶。
袁枚性灵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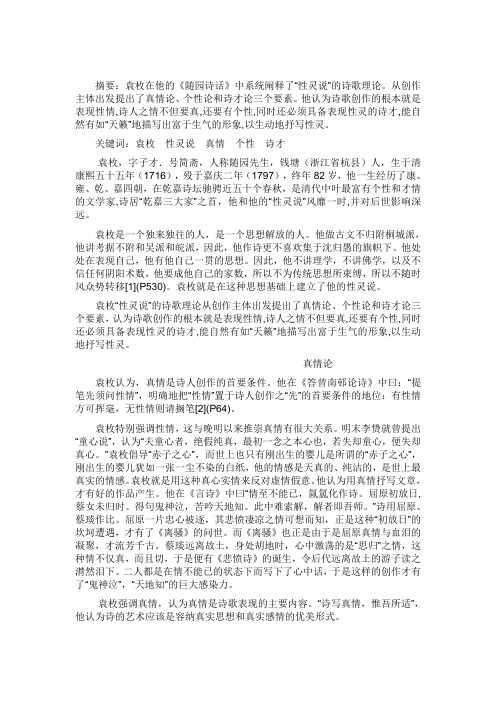
摘要: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系统阐释了“性灵说”的诗歌理论。
从创作主体出发提出了真情论、个性论和诗才论三个要素。
他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就是表现性情,诗人之情不但要真,还要有个性,同时还必须具备表现性灵的诗才,能自然有如“天籁”地描写出富于生气的形象,以生动地抒写性灵。
关键词:袁枚性灵说真情个性诗才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人称随园先生,钱塘(浙江省杭县)人,生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殁于嘉庆二年(1797),终年82岁,他一生经历了康、雍、乾、嘉四朝,在乾嘉诗坛驰骋近五十个春秋,是清代中叶最富有个性和才情的文学家,诗居“乾嘉三大家”之首,他和他的“性灵说”风靡一时,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袁枚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
他做古文不归附桐城派,他讲考据不附和吴派和皖派,因此,他作诗更不喜欢集于沈归愚的旗帜下。
他处处在表现自己,他有他自己一贯的思想。
因此,他不讲理学,不讲佛学,以及不信任何阴阳术数,他要成他自己的家数,所以不为传统思想所束缚,所以不随时风众势转移[1](P530)。
袁枚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性灵说。
袁枚“性灵说”的诗歌理论从创作主体出发提出了真情论、个性论和诗才论三个要素,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就是表现性情,诗人之情不但要真,还要有个性,同时还必须具备表现性灵的诗才,能自然有如“天籁”地描写出富于生气的形象,以生动地抒写性灵。
真情论袁枚认为,真情是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
他在《答曾南邨论诗》中曰:“提笔先须问性情”,明确地把“性情”置于诗人创作之“先”的首要条件的地位:有性情方可挥毫,无性情则请搁笔[2](P64)。
袁枚特别强调性情,这与晚明以来推崇真情有很大关系。
明末李贽就曾提出“童心说”,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
”袁枚倡导“赤子之心”,而世上也只有刚出生的婴儿是所谓的“赤子之心”,刚出生的婴儿犹如一张一尘不染的白纸,他的情感是天真的、纯洁的,是世上最真实的情感。
简论袁枚的“性灵说

简论袁枚的“性灵说袁枚〔1761—1797〕,字子才,号简斋,杭州钱塘人,34岁于**任上辞官,隐居于**小**的随园,世称随园先生,自号**居士,随园老人等。
著有《小**房集》、《随园诗话》和笔记体小说《子不语》等。
他与**翼、蒋士铨并称为“乾隆三大家”,而历来被公认为三家之首。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更是一位杰出的诗论家。
他说倡导的“性灵说”独树一帜,在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一诗学史中的“性灵”,并非袁枚首创,但他在继承前人思想理论的根底上,经过创造性的发挥,丰富和开展了性灵说,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诗学流派。
性灵说的提出,虽有历史继承性,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现实针对性,它反对沈德潜、翁方纲的风格说和肌理说,具有较高的审美理论价值。
袁枚的性灵说是一种较为完备的、系统的文学创作理论,阐述了诗歌创作的某些艺术规律。
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题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个方面的要素。
1、性情是诗歌的第一要素,是诗歌的根源和灵魂。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实情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诗人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真挚、坦诚,不矫饰,不隐匿。
袁枚所说的“性灵”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性情”同意。
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
”“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
”〔《随园诗话》〕,又说:“诗者,心之声也,行情所流露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认为诗是由情所生的,性情的真实流露才是“诗之本旨”。
因为袁枚认为具有真情是诗人创作的先决条件,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这和李贽的“童心说”是一脉相承的,强调诗人应具备纯真的感情。
真情又是诗歌表现的主要内容,因此袁枚一改传统上关于“诗言志”的解释,把真实的性情作为诗歌表现的内容,揭示了诗歌以表情为主、专主性情的根本特点。
他宣称“提笔须先问性情”,这种性情必须是真诚的、真实的,才能使诗歌具有生动的艺术感染力。
两性性灵诗说的“和而不同”

两性性灵诗说的“和而不同”作者:聂欣晗来源:《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18期性灵诗说是清代四大诗说之一。
现在学界大都从袁枚的诗学观来认识性灵说的内涵、价值与意义。
事实上,清代女性对性灵说也作出了一定贡献,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性别差异,应成为性灵诗说的一部分。
所以,要客观全面识评性灵说,应从双性视野出发。
两性性灵诗说的同声相应。
袁枚“性灵”论一出,“从游者若鹜若蚁”①,形成“袁枚现象”②,继王士禛后独领文坛风骚。
在大量追随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约60人的随园女弟子身影,紧承其后的碧城闺秀诗群规模相当,相继形成一个在声气相通、唱酬角胜中走向繁荣的两性诗学网络,女诗人也当之无愧为性灵生力军。
现代学界对袁枚“性灵”的诠释不尽相同,还原当时语境去了解应属捷径。
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
”确定性情是诗歌的本源与灵魂。
第二,主张独创性,如《答兰垞论诗书》曰:“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
”作诗须体现独特的“这一个”,无须执著于宗唐、宗宋。
第三,创作时强调有“才”与“灵机”。
如《蒋心余蕺园诗序》有曰:“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
”第四,语言自然简洁。
“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
”综上,性灵诗论应包含率真的性情、鲜明的个性、奇妙的灵感与本色的语言。
大部分女诗人以性灵为指导,并在创作中呼应此说。
如被袁枚誉为“诗冠本朝”的席佩兰《长真阁集》中的十数首论诗,揭橥的正是性灵诗说:“始知绝妙传神句,不在辞华在性灵”③;金逸的“格律何如主性灵”也以性灵为旨归。
汪端、沈善宝、归懋仪、宗粲、吴静、刘琬怀等一致赞同诗歌内容要真实:“诗本天籁,情真景真皆为佳作。
”④吴静《自题集后》云:“一瓣清香何所得,敢夸真率不夸奇。
”创作个性上,沈善宝《名媛诗话》中女诗人屡屡认同“未经人道语”的新颖而自然之作为好诗,如“(郭)笙愉诗皆性灵结撰,无堆砌斧凿之痕,为可贵也”。
对即便不合格律而秀韵天成之作也充分肯定:“安邱李婉遇幼而敏慧,性耽吟咏,虽不甚讲求格律,而往往出口成章,自然秀逸。
袁枚性灵说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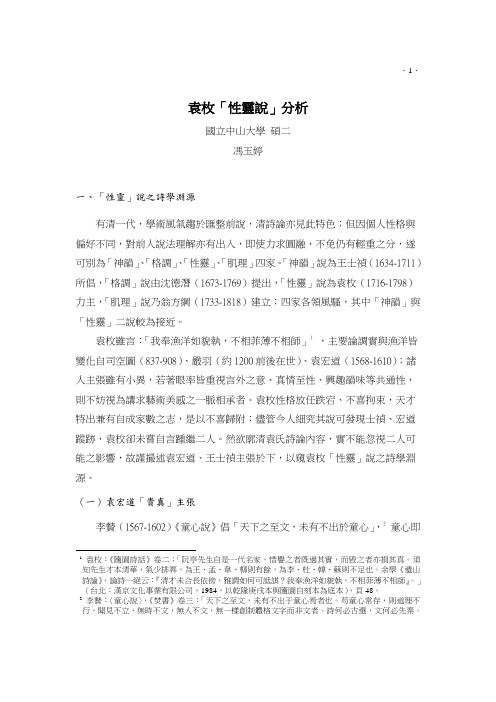
.1.袁枚「性靈說」分析國立中山大學碩二馮玉婷一、「性靈」說之詩學淵源有清一代,學術風氣趨於匯整前說,清詩論亦見此特色;但因個人性格與偏好不同,對前人說法理解亦有出入,即使力求圓融,不免仍有輕重之分,遂可別為「神韻」、「格調」、「性靈」、「肌理」四家。
「神韻」說為王士禎(1634-1711)所倡,「格調」說由沈德潛(1673-1769)提出,「性靈」說為袁枚(1716-1798)力主,「肌理」說乃翁方綱(1733-1818)建立;四家各領風騷,其中「神韻」與「性靈」二說較為接近。
袁枚雖言:「我奉漁洋如貌執,不相菲薄不相師」1,主要論調實與漁洋皆變化自司空圖(837-908)、嚴羽(約1200前後在世)、袁宏道(1568-1610);諸人主張雖有小異,若著眼率皆重視言外之意、真情至性、興趣韻味等共通性,則不妨視為講求藝術美感之一脈相承者。
袁枚性格放任跌宕、不喜拘束,天才特出兼有自成家數之志,是以不喜歸附;儘管今人細究其說可發現士禎、宏道蹤跡,袁枚卻未嘗自言踵繼二人。
然欲廓清袁氏詩論內容,實不能忽視二人可能之影響,故謹撮述袁宏道、王士禎主張於下,以窺袁枚「性靈」說之詩學淵源。
1袁枚:《隨園詩話》卷二:「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譽之者既過其實,而毀之者亦損其真。
須知先生才本清華,氣少排奡,為王、孟、韋、柳則有餘,為李、杜、韓、蘇則不足也。
余學《遺山詩論》,論詩一絕云:『清才未合長依傍,雅調如何可詆諆?我奉漁洋如貌執,不相菲薄不相師』。
」(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以乾隆庚戌本與隨園自刻本為底本),頁48。
.2.第六屆南區五校中國文學系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一)袁宏道「貴真」主張李贄(1567-1602)《童心說》倡「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2童心即真心,是文學創作的根本,其說為公安三袁所繼承;公安派基本主張重視個性與自然,袁宏道為代表人物。
袁氏貴「真」,以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化,一人有一人之情感,唯「變」方能存「真」,二者相輔相成而後有韻趣。
袁枚性灵说的形成

袁枚“性灵说”的形成在我们着手讨论袁枚“性灵说”之前,似乎有必要对它产生的基础、根源等问题先进行一番调查。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类喜欢追根溯源的良好品德使然;一方面则因为我们长期养成的思维定性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到了清代时已是历经数迁了,各种形态的诗论结晶有着相当丰厚的历史积淀,不管在研究领域、方式方法,还是理论体系上,都使传统的文学研究达到了成熟的状态。
在这种大坏境之下,袁枚竟然还能蝉蜕于传统模式的躯壳,提出具有个性解放色彩的“性灵说”,开一代诗风,不能不令人钦佩。
究其原因,“性灵说”的形成不仅得益于前代进步的哲学思想,还与袁枚自身的现实际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一节哲学理论渊源从理论建构上看,袁枚虽未形成自己自立自足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但其诗论中所彰显的对传统的反叛精神却有力地阐说着其思想的进步性,这与前人的进步哲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袁枚“性灵说”的思想基础,可以从近因和远因两方面来理解。
哲学方面的近因,指的是晚明时期泰州学派和康熙时期颜元、戴震等人的影响。
泰州学派又称“王学左派”,他继承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坚持自我,保留个性,努力将自身生命价值把握在自己手中,引领了当时的思想解放的潮流。
嵇文甫先生曾评价道:“泰州学派是王学的极左派,王学的自由解放精神,王学的狂者精神,到泰州学派才发挥尽致”。
[1]袁枚的思想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极为明显,突出地表现为,他汲取了其“狂者精神”,于个性气质上表现出一种“狂”气来,其诗论中也难免也会外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个性思想。
他在《邛州知州杨君笠湖传》中自我剖析道:君与余为总角交,性情绝不相似。
余狂,君狷;余疏俊,君笃诚。
[2]这里的“性情”与个性之义相通,袁枚毫不隐晦自己“狂”、“疏俊”的性格特征,自由地表达出不受礼教牵绊的独立意识,不可不谓之狂人。
公开以“异端”自居的泰州学派成员李贽,其“童心说”也对袁枚思想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李贽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应该有一种单纯朴素的心地,即为“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袁枚“性灵说”的形成在我们着手讨论袁枚“性灵说”之前,似乎有必要对它产生的基础、根源等问题先进行一番调查。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类喜欢追根溯源的良好品德使然;一方面则因为我们长期养成的思维定性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到了清代时已是历经数迁了,各种形态的诗论结晶有着相当丰厚的历史积淀,不管在研究领域、方式方法,还是理论体系上,都使传统的文学研究达到了成熟的状态。
在这种大坏境之下,袁枚竟然还能蝉蜕于传统模式的躯壳,提出具有个性解放色彩的“性灵说”,开一代诗风,不能不令人钦佩。
究其原因,“性灵说”的形成不仅得益于前代进步的哲学思想,还与袁枚自身的现实际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一节哲学理论渊源从理论建构上看,袁枚虽未形成自己自立自足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但其诗论中所彰显的对传统的反叛精神却有力地阐说着其思想的进步性,这与前人的进步哲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袁枚“性灵说”的思想基础,可以从近因和远因两方面来理解。
哲学方面的近因,指的是晚明时期泰州学派和康熙时期颜元、戴震等人的影响。
泰州学派又称“王学左派”,他继承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坚持自我,保留个性,努力将自身生命价值把握在自己手中,引领了当时的思想解放的潮流。
嵇文甫先生曾评价道:“泰州学派是王学的极左派,王学的自由解放精神,王学的狂者精神,到泰州学派才发挥尽致”。
[1]袁枚的思想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极为明显,突出地表现为,他汲取了其“狂者精神”,于个性气质上表现出一种“狂”气来,其诗论中也难免也会外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个性思想。
他在《邛州知州杨君笠湖传》中自我剖析道:君与余为总角交,性情绝不相似。
余狂,君狷;余疏俊,君笃诚。
[2]这里的“性情”与个性之义相通,袁枚毫不隐晦自己“狂”、“疏俊”的性格特征,自由地表达出不受礼教牵绊的独立意识,不可不谓之狂人。
公开以“异端”自居的泰州学派成员李贽,其“童心说”也对袁枚思想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李贽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应该有一种单纯朴素的心地,即为“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
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3]失去童心,便是失去了真心,失去真心,真人便不复存在了。
李贽看来,这种没有受到后天的纲常污染的自然质朴的天赋心理,才是人类本真的情感,才有利于创作出真作品来。
因此,他在创作上主张的对情性自由倾吐的文学观,反对一切虚饰矫情。
李贽论道: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
[4]在他看来,一切文艺皆源于自然流露出来的情感,“牵合矫强”难以至,真正的“礼义”其实内在于“情性”,随“情性”而定。
他的这种对自然纯真感情的要求以及“赤子之心”的观点对袁枚诗论影响亦为不小。
袁枚吸收了他这种思想,曾于《随园诗话》卷三中说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5]此外,康熙时期的戴震、颜元、陈廷祚等人也是在哲学思想上影响袁枚的先导者,提出诸如“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6],“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7]等进步观点,锐意批判当时的程朱理学,扫除当时的禁欲主义,显示出一些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锋芒。
袁枚在《宋儒论》中曾肯定了“我朝有颜、李者”,[8]对他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提出“宋儒分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大谬。
”[9]显示出批判封建礼教的民主主义精神。
至于袁枚“性灵说”哲学思想的远因,其诗作《山居绝句》有明确的说明,云:问我归心向何处,三分周孔二分庄。
[10]这里袁枚明确地指出了其思想与周公、孔子、庄子的关系。
可从袁枚诗论中的论述中看来,孔孟远远要比周孔出现的次数多,可见,袁枚的思想基础应是“三分孔孟二分庄”才对。
在他的著作里,可以经常看到其尊孔崇孟的印记。
他认为:“古今来尊之而不虞其过者,孔子一人而已”。
[11]“孔子之道大而博”,[12]且“‘六经’中,惟《论语》、《周易》可信”,[13]因此,他吸收了孔子的某些观点,譬如说对“才”的认识:孔子论成人,以勇艺居先,而以思义受命者次之。
论士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居先,而以称孝称弟者次之,曰:“高阳氏有才子八人。
”曰:“才难。
”曰:“如有周公才之美。
”若是乎,才之重也!降之战国,纵横便诈,以为才之为祸尤烈。
故孟子起而辩之曰:“若夫为不善,非其才之罪也。
”孟子之意,以为能视者,目之才也;虽察秋毫,不足为目病。
而非礼之视,非其才之罪也。
能食者,口之才也;虽辩淄渑,不足为口病。
而非礼之食,非其才之罪也。
若因其视非礼而必矐目而盲之,食非礼而必钳口儿噎之;是则罪才贱才之说,非孔、孟意矣。
[14]庄子虽未像孔孟那样对袁枚的思想占三分影响,但也是不容小觑的。
庄子的自然之道,逍遥之旨,形成了独特的哲学观念,而袁枚的个性张扬论恐怕与此有关。
其真情论从庄子思想中亦可发现原型。
如袁枚的“伪笑佯哀,吾其忧也”[15],“情在理先”[16]与庄子的“真者,精诚之至也。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17]“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18]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节现实际遇影响袁枚身处的清朝时期,对于文人来说并非一个乐观的理想时代:这个朝代有太多的清规戒律束之左右,有太强的文化压制围绕其间,现实的冷漠与精神的压抑也时时考验着人们脆弱的神经。
范文澜先生曾这样概述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满清入关获得明朝统治阶级的拥护,同时也继承了明朝的全部制度。
它是少数的落后的外来民族,对人口众多文化程度较高的汉族(包括汉族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始终怀着疑忌歧视的心情。
不能不在旧制度上增加怀柔镇压的新成分,建立阶级的民族的双重压迫的制度。
”[19]文字狱便是最典型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
在这种高压统治的社会环境下,为避祸端,很多文人承袭了先前学者们所运用的考据方法,并且转向致力于专门汉学;这样,学者们既可以脱离社会现实,又可以回避开学术上的理论原则。
.而袁枚在此时打出“性灵”的口号,主张反传统,尊情,求变,倡导思想解放,这与他自身的现实际遇也有着很大关系。
幼年时期家庭环境浓郁亲情的沐浴,催生了袁枚的“情真”萌芽。
少年时期良好教育的熏陶,也逐渐培养了袁枚的诗歌审美能力,从而为形成诗学“性灵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袁枚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幕僚之家,父亲袁滨和叔叔袁鸿皆因生活拮据而游食四方,靠作人幕府为生。
因此,幼年的袁枚受到了祖母的悉心照顾和通文墨的姑母的谆谆教诲,浓郁的亲情氛围使袁枚初步认识到真“情”之重,对以后的情真论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影响。
后来,当其祖母柴氏去世后,他写下了泣血之作《陇上作》,记录了祖母一直对他如“掌珠真护惜,轩鹤望腾骞”般的爱护,表达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之情:反哺心虽急,舍饴梦已捐。
恩难酬白骨,泪可到黄泉。
宿草翻残照,秋山泣杜鹃。
今宵华表月,莫向陇头圆![20]寥寥数语,就把他对亲情的珍视表达得淋漓尽致。
他还在《秋夜杂诗》其八中描述道:我年甫五岁,祖母爱家珍,抱置老人怀,弱冠如闺人。
其时有孀姑,亦加鞠育恩,授经为解义,嘘背为馀温。
[21]正是在姑母娓娓不倦地讲解下,“授经为解义”,使得袁枚在五岁时就知晓汉、魏、唐、宋的国号与人物,学会了朗读《盘庚》、《大诰》,培养了对文史知识的浓厚兴趣;在七岁时,就开始了正式教育的历程。
九岁之前的他“除了《四书》《五经》外,不知诗为何物”,[22]偶然一次机会,他看到了恩师老友的《古诗选》,开始对诗歌产生兴趣,并时时“吟咏而蓦仿之”,[23]打下了诗歌功底。
他回忆道:九岁读《离骚》,嗜古有馀幕。
学为四子文,聪明逐陈腐。
犹复篝残火,偷习词与赋。
[24]可见袁枚对诗赋也算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
他从小就对八股文有种抵触心理,认为八股文“陈腐”,如再点燃的残火一般,没有持久的生命力,对封建礼教的一些不合理性也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对郭巨的假道学在十四岁时所作的《郭巨埋儿论》中就加以了猛烈抨击。
青年时期,由于家庭教育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袁枚也逐渐接受了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25]的价值观,在其二十一岁时,便以探望叔父袁鸿为名以期得到金鉷(袁鸿于金鉷幕中)的赏识。
因此,当他们初次见面时,袁枚便即兴作了《铜鼓赋》,使得金鉷对其才华大为赞赏,随后极力奏疏举荐,使袁枚搭上了博学鸿词科考试的末班车。
遗憾的是,最终的结果却不尽人意,最终名落孙山,使颇为自信的他倍受打击。
为了应付下一次的科考,他苦练八股文,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二十三岁时终于考中举人,次年又中进士,于悲喜交加之间,作《举京兆》:信当喜极翻愁误,物到难求得尚疑。
一日性命举京兆,十年涕泪桂花知。
[26]可见此时的袁枚还无意规避官场,对仕途仍抱有理想主义的憧憬。
乾隆十二年时的尹继善荐其补邮洲刺史,吏部议审时未能通过,这次的仕途挫折让袁枚对官场的黑暗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最终成为其辞官归隐的导火索。
三载翰林,七年县令,颇有政绩却难以升迁,再加上为官的事务琐碎而且多出于无奈,日日忙碌却不过只是无聊的应酬,这对钟情于文学创作的袁枚来说无异于是一种折磨。
诸此种种,促使个性本来极强的他终于在乾隆十九年完成了其追求自由精神的另类表达——辞官。
这在世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对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亦是重重一击。
当然,也正是袁枚的这段不尽人意的入仕经历,才使他对封建社会的各种弊端认识得更为透彻,从而加入到了批判封建正统下的程朱理学的行列之中。
同时,他也更加确信个体自身生命价值的重要性,为“性灵说”个性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