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隐喻与象征——简评南翔《老桂家的鱼》(于爱成)
桃花流水鳜鱼肥阅读理解【桃花流水鳜鱼肥】

从臭鳜鱼看徽州文化这,是一道名菜,初见的人不敢下筷,那似有似无,似臭非臭的气味,真的叫人有点担心。
其实,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似臭非臭”正是这道菜独有的风味。
轻轻的浅尝,你会惊讶地发现,色泽红亮的外表下,它所呈现出外酥内嫩的味道竟是那样鲜美。
它,就是徽菜代表——臭鳜鱼。
相传古时,沿江一带的鱼贩每年入冬时将长江名贵水产鳜鱼,用木桶装运至徽州山区出售(当时有“桶鱼”之称),途中为防止鲜鱼变质,采用一层鱼洒一层淡盐水的办法。
如此七八天抵达屯溪等地时,鱼鳃仍是红色,鳞不脱,质未变,只是表皮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特殊气味,但是洗净后经热油稍煎,细火烹调后,非但无臭味,反而鲜香无比,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肴。
怎么会有臭鳜鱼这道菜?这还要从古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说起。
古徽州,即古歙州,今安徽歙县一代。
古时徽州山清水秀,恍如世外桃园。
汤显祖有诗云“欲识金银气,须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可见徽州山水之斑斓。
但因古时徽州地域山多地少,人多地稀,路窄弯多,所谓“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生存环境非常严峻。
虽有群山环抱,风景如画,但交通极不便利,彼时更无保温车、冰袋保鲜,想要品尝新鲜的外地时令佳肴更是异常困难,于是才有“桶鱼”的诞生,于是才有了臭鳜鱼的鲜香美味,于是,催生出这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徽派菜系。
众所周知,徽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起源于黄山麓下的歙县,发端于唐宋,兴盛于明清。
徽菜的产生完全依傍徽州的人文及地理环境。
其特点,一是就地取材,以鲜制胜。
徽地盛产山珍野味河鲜家禽,就地取材使菜肴地方特色突出并保证鲜活;二是善用火候,火功独到。
根据不同原料的质地特点、成品菜的风味要求,分别采用大火、中火、小火烹调;三是娴于烧炖,浓淡相宜。
除爆、炒、熘、炸、烩、煮、烤、焐等技法各有千秋外,尤以烧、炖及熏、蒸菜品而闻名;四是注重天然,以食养身,讲究食补,这是徽菜的一大特色。
一个菜系的形成是经济与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
金鱼赋第一段赏析【清代】高景芳骈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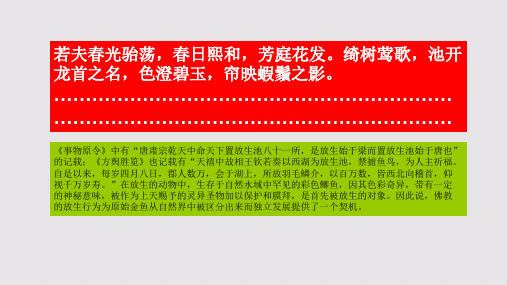
……………………………………………………… பைடு நூலகம்……………………………………………………
《事物原令》中有“唐肃宗乾天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是放生始于梁而置放生池始于唐也” 的记载;《方舆胜览》也记载有“天禧中故相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 自是以来,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放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皆西北向稽首,仰 视千万岁寿。”在放生的动物中,生存于自然水域中罕见的彩色鲫鱼,因其色彩奇异,带有一定 的神秘意味,被作为上天赐予的灵异圣物加以保护和膜拜,是首先被放生的对象。因此说,佛教 的放生行为为原始金鱼从自然界中被区分出来而独立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国学 骈体文
金鱼赋
第一段
清代 高景芳
作品赏析
• 在中国汉字中,金鱼的“鱼”与“余”同音,因此,金鱼就有金余的口彩。人们为了寓意年年有余,吉 庆有余,经常将有金鱼形象的饰物带入家中。在颐和园的长廊彩绘中,皖南民居的砖雕石刻上,苏州园 林的屏风窗格里,金鱼的形象无处不在。过年时,在窗户上贴上金鱼剪纸的窗花,墙上挂上杨柳青的金 鱼年画,桌上养一缸锦鳞闪闪的金鱼——元宝红,大门上再贴上一幅大红对联,写着:“岁岁进元宝,年 年有金余”。金鱼又与金玉谐音,金在古语中常代指女儿,玉一般代指儿子,所以金鱼满塘就是金玉满 堂,象征子孙满堂,人丁兴旺。
图片欣赏
作者简介
• 高景芳(1681―?),字远芬,汉军正红旗人,归张宗仁。《红雪 轩稿》张宗仁序曰:“余年十九,即受知于今大司空武原陈夫 子……越二年,就婚渤海……戊戌(1718年)秋,病初起,沦茗相 对,忽以汇成之稿六卷示余。且谓余曰:‘二十年绣余病后之绪言, 具在于是。’”由此上推,则其应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成婚。 景芳《七思》提到“承欢十八年”、“笄年归侯门”,可以推断她 应是18岁出阁,生年为康熙二十年(1681年)。其诗文集刊刻于康 熙五十八年(1719年),弟钦于同年所作序跋中均未提到其姊亡故, 可知景芳的卒年应在此后。
汪曾祺我的家乡赏析

汪曾祺我的家乡赏析汪曾祺是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汪曾祺我的家乡赏析,欢迎参考阅读!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游。
我小时候常常到运河堤上去玩。
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底下的街道房屋。
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
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颤悠悠的风筝在我们脚下飘着。
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过来,绕过去,我们看到的是鸽子青*的背。
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
看打鱼。
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
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
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
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
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劈劈**地纷纷跃进水里。
只见它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工夫,有的就叼了一条鳜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鳜鱼。
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把鳜鱼扔进船里,奖给它一条小鱼,它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转身又跳进水里去了。
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鳜鱼上来,鳜鱼还在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
这条鳜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
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
倒是打渔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
有时候我们到西堤去玩,坐小船两蒿子就到了。
西堤外就是高邮湖,我们那里的人都叫它西湖,湖很大,一眼望不到边。
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
这样一片打水,浩浩渺渺(湖上常常没有一只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
黄昏了。
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很深很深的紫*。
这种紫*使人深深感动,我闻到一阵阵炊*的香味,那是停泊在御码头一带的船上正在烧饭。
只听见一个女人高亮而悠长的声音:“二丫头……回家吃晚饭来……”像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常爱说的那样,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
作者赞美他的家乡(也是我的故乡)是“圣境”。
“圣境”者,人间仙境也。
先登上那“悬河”大堤向村内俯瞰,顿生“巡天遥看一千河”之感:风筝,在脚下飘,鸽子飞过来,绕过去,让你只能看到它青*的背。
年年有鱼王成祥阅读答案

年年有鱼王成祥阅读答案【原文】阅读短文,完成练习。
年年有鱼王成祥①古往今来,“鱼”与春节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春节“鱼”文化,情趣盎然。
②民间有“无鱼不成席”之说,尤其是年夜饭,家家户户少不了一条鱼。
因“鱼”与“余”谐音,寓意“年年有余”,象征新的一年里,丰盛有余。
③_____________:有的地方用鲤鱼,象征“鲤鱼跳龙门”;有的地方用鲢(lián)鱼,以示“连年有鱼”;有的地方用鳜(guì)鱼,寄寓“富贵有余”。
④在辞旧迎新的新春佳节,人们正是用这种“讨口彩”的方式,表达着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1、结合上下文,解释下面词语的意思。
无鱼不成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辞旧迎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如果在第③自然段的横线处给这一段话加上一个中心句,你认为下列哪句话最合适?()A、在鱼的选择上,各地不尽相同。
B、在鱼的做法上,各地不尽相同。
C、鱼这种食材因为物美价廉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
D、鱼是年夜饭上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
3、第④自然段中的“讨口彩”指的是利用语言的谐音和一些事物的特性,人为地加以创意获得新的寓意,来寄托人们的某些美好的心理愿望。
除了“有鱼”和“有余”的谐音之外,文中还有两处谐音,请用“_____”画出来。
你还知道哪些“讨口彩”的方式?请写在下面的横线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答案】1、“无鱼不成席”是一种传统习俗,意思就是民间在节日、婚寿喜庆等隆重的宴席上,绝对少不了鱼这道菜。
鱼不仅是美食,还蕴含着年年有余的意义,寓意着吉祥、富贵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其十分独特的鱼文化,流传千古、千姿百态。
汪曾祺《钓鱼的医生》全文赏析

钓鱼的医生汪曾祺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这个医生几乎每天钓鱼。
他家挨着一条河。
出门走几步,就到了河边。
这条河不宽。
会打水撇子(有的地方叫打水漂,有的地方叫打水片)的孩子,捡一片薄薄的破瓦,一扬手忒忒忒忒,打出二十多个,瓦片贴水飘过河面,还能蹦到对面的岸上。
这条河下游淤塞了,水几乎是不流动的。
河里没有船。
也很少有孩子到这里来游水,因为河里淹死过人,都说有水鬼。
这条河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水不流,也没有人挑来吃。
只有南岸的种菜园的每天挑了浇菜。
再就是有人家把鸭子赶到河里来放。
河南岸都是大柳树。
有的欹侧着,柳叶都拖到了水里。
河里鱼不少,是个钓鱼的好地方。
你大概没有见过这样的钓鱼的。
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
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
他钓鱼很有经验。
钓竿很短,鱼线也不长,而且不用漂子,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看到线头动了,提起来就是一条。
都是三四寸长的鲫鱼。
——这条河里的鱼以白条子和鲫鱼为多。
白条子他是不钓的,他这种钓法,是钓鲫鱼的。
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
不大一会,鱼就熟了。
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
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叫做“起水鲜”。
到听见女儿在门口喊:“爸——!”知道是有人来看病了,就把火盖上,把鱼竿插在岸边湿泥里,起身往家里走。
不一会,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
这位老兄姓王,字谈人。
中国以淡人为字的好像特别多,而且多半姓王。
他们大都是阴历九月生的,大名里一定还带一个菊字。
古人的一句“人淡如菊”的诗,造就了多少人的名字。
王淡人的家很好认。
门口倒没有特别的标志。
211125872_浅析苏童小说中的“鱼”意象

026《名家名作》·评论[摘 要] 南方是苏童笔下重要的文学坐标,在他意象交叠的文学南方世界中,“鱼”意象反复出现,意蕴深刻。
旨在探讨苏童小说中“鱼”意象的表现形式,剖析“鱼”意象在苏童小说中蕴含的挣扎与血性、漂泊与回归、异化与退化的象征意蕴,并结合苏童几十年间的作品,以历时性角度观察“鱼”意象在苏童小说中的变化,以此更好地了解苏童小说,领略他别样的才情与哲思。
[关 键 词] 苏童;“鱼”意象;象征浅析苏童小说中的“鱼”意象韩 影苏童生于南方,江南水乡滋养着他的才情,也成为他笔下重要的文学坐标。
他创造的以“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为核心场域的文学南方引人入胜,其“意象主义写作”也备受赞誉。
“苏童小说叙事,除语言、结构之外最为重要的元素就是意象”①,作者因物所感,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物象传递情思体悟,意象由此而来。
苏童的文学南方意象交叠,江南多水,下有江河湖,上有雨雪雾,共同构成水汽氤氲的南方图景。
有水自然就离不开鱼,无数沾染着鱼的气息、与鱼形神相似的人和物出现在他“文学南方”的世界中,“鱼”意象凝聚着他对世界的观望与思索。
一、“鱼”意象的表现形式在他的中长篇小说中,明确涉及“鱼”意象的有《1934年的逃亡》《外乡人父子》《罂粟之家》《十九间房》《米》《菩萨蛮》《群众来信》《城北地带》《红粉》《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黄雀记》《驯子记》《三盏灯》等,短篇小说中“鱼”意象也层出不穷,可以说,对“鱼”的描绘贯穿苏童几十年的创作生涯。
众多作品中,“鱼”意象的表现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以鱼喻物苏童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精准捕捉本体与喻体间的相似点,创作出不少令人印象深刻、极具画面感的作品。
以鱼的流动性特征为连接点,苏童在《外乡人父子》中将老冬爷扔在河流中的竹器比作美丽的鱼类,在《十九间房》中写“萧萧的风声像鱼一样在村庄里游荡回旋”②,在《菩萨蛮》中写“阳光是活的,它们像一群鱼,从窗外的河水里纷纷跳到我家的窗台上、门板上,跳到孩子们的床上,跳到脸盆里,跳到锅里。
沈从文小说中的鱼意象

、
鱼在 沈从 文小说 中随处 可见 ,大多 情况 下较 笼统地 写成 鱼 ,不 具体 到鱼 的品种 。具名 的 主要有鳜 鱼 、鲫鱼 、鲤 鱼 、鳝 鱼和金 鱼等 。 沈从文 对水 边 的生 活十分 了解 ,所 以对 鱼 的品种也 很熟悉 。鳜 鱼 、鲫 鱼 、鲤鱼 ,是作 家笔 下最常
见 的鱼 。鳜 鱼味 道特美 ,也是 沈从 文作 品 中的人物 喜欢 吃 的一 种 鱼。 《 上 岸上 》 中 , “ ” 与 叔远 船 我
在街上向老妇人Βιβλιοθήκη 梨子 ,梨子十分可口,但是知道吃饭有鳜鱼,所以才忍住没有吃梨子;《 黎明》 中
叔远 在船上 回忆 家乡 的时候 ,最 乐 于对 “ ”谈 的便 是在 碾 堰 坝上 钓 鱼 ,大 多 数是 鲫 鱼 和鲤 鱼 。鲤 我
天来 了 ,金 鱼都憔 悴 了 。城 市 中的女子 和鱼 缸 中的金鱼 一样缺 少生 命 的活力 。金鱼 也偶然 出现在在沈
从文 湘西题 材小 说 中 ,如 《 伍 》 中的金鱼 是 “ ” 和 莲姑 纯真友 情 的见证 。 卒 我
( ) 捕鱼 之术 二
沈从 文在水 边长 大 ,在水 的教育下 ,不 仅认 识多种 多样 的鱼 ,还见 识 了多种 多样 的捕鱼 方法 。
[ 收稿 日期 ]2 1 一D D 0 1 5一 3 [ 修回 日期]2 1 — 6—1 01 0 5 [ 作者简介 ]胡斌 ( 96一) 17 ,男 ,副教授 ,硕士 ,从事 中国现 当代文学研究。E m i tig@yhocr c — a :nbno ao.o . n l n
第 2期
胡斌 ,等 :沈 从 文 小 说 中 的鱼 意 象
・0 19・
最 常见 的捕 鱼 之术 是 钓鱼 ,这 也是 沈从 文 幼时 最为 喜爱 的游 戏 之一 。在 《 私塾 》 我 的教育 》 在 、《
汪曾祺《鳜鱼》原文及赏析

汪曾祺《鳜鱼》原文及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文档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谢谢!并且,本店铺为大家提供各种类型的经典范文,如诗歌散文、原文赏析、读书笔记、经典名著、古典文学、网络文学、经典语录、童话故事、心得体会、其他范文等等,想了解不同范文格式和写法,敬请关注!Download tips: This document is carefully compiled by this editor.I hope that after you download it, it can help you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document can be customized and modified after downloading, please adjust and use it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thank you!In addition, this shop provides you with various types of classic sample essays, such as poetry and prose, original text appreciation, reading notes, classic works, classical literature, online literature, classic quotations, fairy tales, experience, other sample essays, etc.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difference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format and writing of the sample essay!汪曾祺《鳜鱼》原文及赏析【导语】:鳜鱼是汪曾祺写的一篇散文,来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赏析吧鳜鱼读《徐文长佚草》,有一首《双鱼》:如鳜鱼如鲋栉,鬐张腮呷跳纵横。
杜桂兰的鱼之乐

鱼,因其灵动、优雅的形象,悠远的意境和寓意成为中国画中重要的意象,周东卿、八大山人、齐白石等人笔下游弋的鱼儿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关于鱼,同样著名的还有庄子在《秋水》中描绘的那个场景:庄子与惠子同游于濠梁之上,庄子见游鱼从容,不禁啧啧赞叹鱼之乐,惠子反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灿然笑曰:“子非吾,安知吾不知鱼之乐?”画家杜桂兰也是一位深知鱼之乐的人。
每当拿起画笔,在宣纸上左右纵横、前后进退中,她如同自己笔下跃动的鱼儿,游于江海而自得其乐。
“鱼,形态优美,既有富贵的象征,又有和谐招财之意,自古人人皆爱。
我从小就喜欢它们气质非凡的美。
”由是,家中鱼缸中的金鱼、公园池塘里的锦鲤、乡下河沟里的黑鲤鱼等都成为杜桂兰的好玩伴。
她亲近它们,仔细观察它们。
20世纪90年代末,杜桂兰调入济南工作,有机会拜著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张鹤云先生为师,专攻画鱼。
幸运的是,杜桂兰得到张鹤云先生的悉心教导。
边学、边练、边创作,杜桂兰把自己的岁月浸润到了绘画艺术中。
画鱼很简单。
鱼,人人可见,寥寥数笔就可勾勒出其轮廓,因此,它们常常被收录于启蒙孩童艺术智力的简笔画中;画鱼也很难。
难在一个“活”上,若表现不好,就显得呆板俗气,只有下狠功夫才能把鱼画活,才能得其神韵。
在画鱼上,杜桂兰下了狠功夫。
为了画鱼,她专门购买了一个大鱼缸摆在家中,里面养了很多鲤鱼。
一有空闲,她就坐在鱼缸前仔细观察鱼的动态和习性,因此,星期天和节假日常常伴着一缸鱼度过。
同时,一有机会她还经常跑到渔场,细心观察鲤鱼的生活习性,向渔民请教有关鲤鱼的知识。
每画一阶段,总是不忘拿给老师指导,请老师提意见。
这样一天复一天的和鲤鱼打交道,勤耕不辍,杜桂兰把鲤鱼画活了,达到了逼真的境地。
据说有一次,她画了一幅鲤鱼,被家中花猫看见,扑咚一声扑到纸上抓“鱼”,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其功力可见一斑。
勤奋、苦练、下狠功夫,再加上“一丁点儿天赋”,让杜桂兰笔下的鱼“活”了起来。
鱼儿或是游弋于水中悠然自得,或是跃水搏浪奋勇向前。
魏柏林《鳜鱼》阅读答案(1篇)

魏柏林《鳜鱼》阅读答案(1篇)魏柏林《鳜鱼》阅读答案 1《鳜鱼》阅读:对你来说,这个夜晚注定难以成眠。
明天就是请客的日子,计划中的宴席还有一道主菜未能备齐,确切地说,还差六条鳜鱼。
鳜鱼谐音“桂遇”,含有蟾宫折桂的意思。
露水湖也因此有了一个习俗:只要孩子考上大学,请客设宴便少不了鳜鱼这道菜。
这个秋天,你儿子不仅考上了头榜,还拿了考区状元。
儿子争得了脸面,做父亲的哪能不请客呢?请客又哪能不用鳜鱼?今夜,就剩今夜了。
老实说,你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对捕鱼者来说,夜幕下的露水湖并没有那么黑暗,虽然这还是个没有星月的晚上,你照样能脚踩月牙划盆,逐浪湖面,将渔网一一下到有效的水域。
以往下完渔网,你会在岸边拴了划盆,倚靠在盆里,或以手枕头,聆听水面鱼儿游动、林岸虫鸣;或遥望苍穹,依着星月移行的方位,估算着昼夜更替的大致时光;再不就想儿子,想他成年后的身高长相,想他毕业后的工作;或抽完三五支劣质香烟,窝在划盆里惬意地眯一会儿。
可今夜,你没有在岸边拴划盆,而是依然荡着划盆,游曳在寂寥如梦的湖面。
不知不觉,你已接近村主任家的网箱。
这儿囤养着清一色的鳜鱼。
你知道,村主任在湖边设了哨棚,也常来哨棚过夜,但有时也难免上演“空城计”。
此刻,你望着黝黑静谧的哨棚,不由耳热心跳起来,兀自疑问:又是空城计吗?这种疑问,与其说是猜测,不如说是希望。
而更可笑的`是,你却还在心里暗暗祈祷:村主任,你可别给我机会啊!谁能想到,你的祈祷竟有了神奇的呼应,哨棚里及时地响起了手机彩铃声,当然是村主任的。
你先是吓了一跳,继而抚了抚胸口,又轻嘘了一口气,说不清是庆幸还是失望。
村主任接听了电话。
从他的话中,你知道了大致内容:是镇长要村主任连夜去镇里,接待一位露水湖的开发商。
村主任临走时,打着手电,从网箱里捞了好几条活蹦乱跳的鳜鱼,然后才匆匆离去。
嗅着那鲜腥的鳜鱼味儿,你羡慕得直咽口水:多么可爱的家伙,是拿去讨好开发商的吧?村主任走了,哨棚空了,正所谓天赐良机!可你却坐在划盆里发呆,这太巧合了,巧合得难以置信。
游鱼老树依湖的寓意和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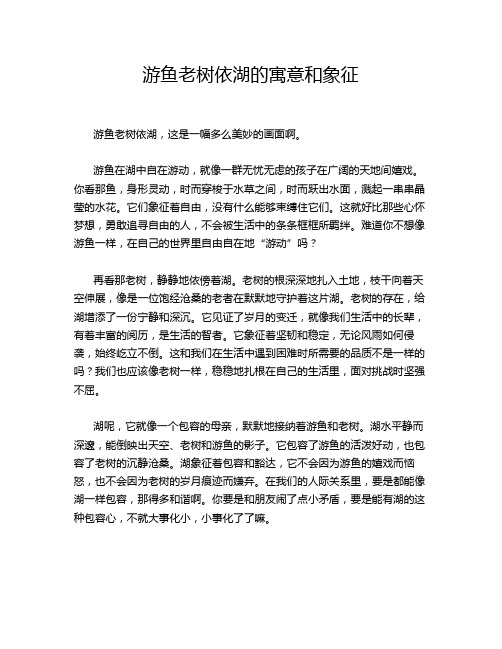
游鱼老树依湖的寓意和象征游鱼老树依湖,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面啊。
游鱼在湖中自在游动,就像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在广阔的天地间嬉戏。
你看那鱼,身形灵动,时而穿梭于水草之间,时而跃出水面,溅起一串串晶莹的水花。
它们象征着自由,没有什么能够束缚住它们。
这就好比那些心怀梦想,勇敢追寻自由的人,不会被生活中的条条框框所羁绊。
难道你不想像游鱼一样,在自己的世界里自由自在地“游动”吗?再看那老树,静静地依傍着湖。
老树的根深深地扎入土地,枝干向着天空伸展,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在默默地守护着这片湖。
老树的存在,给湖增添了一份宁静和深沉。
它见证了岁月的变迁,就像我们生活中的长辈,有着丰富的阅历,是生活的智者。
它象征着坚韧和稳定,无论风雨如何侵袭,始终屹立不倒。
这和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所需要的品质不是一样的吗?我们也应该像老树一样,稳稳地扎根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对挑战时坚强不屈。
湖呢,它就像一个包容的母亲,默默地接纳着游鱼和老树。
湖水平静而深邃,能倒映出天空、老树和游鱼的影子。
它包容了游鱼的活泼好动,也包容了老树的沉静沧桑。
湖象征着包容和豁达,它不会因为游鱼的嬉戏而恼怒,也不会因为老树的岁月痕迹而嫌弃。
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要是都能像湖一样包容,那得多和谐啊。
你要是和朋友闹了点小矛盾,要是能有湖的这种包容心,不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嘛。
游鱼、老树和湖三者构成的画面,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游鱼离不开湖的滋养,老树离不开湖的滋润,而湖因为有了游鱼和老树,也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这就像我们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大家相互依存,相互成就。
比如说,工人生产出各种商品,商家负责销售,消费者购买商品,这其中每个环节都不可或缺。
有时候,游鱼在湖中的游动会引起一圈圈的涟漪,这些涟漪会扩散到老树的根部。
这就好像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个小举动,可能会对周围的人或者事物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也许你不经意间的一个微笑,就能给别人带来一天的好心情,就像游鱼的游动给老树带来了微微的波动一样。
银鳞戏水知年早,“鱼”传统文化中极具寓意的符号

银鳞戏水知年早,“鱼”传统文化中极具寓意的符号鱼是中国文化当中一个寓意极为丰富的符号。
赵少俨作品《富贵有余》尽管在民间,鱼作为丰足的象征、情爱的具象而受到广泛喜爱,但是在古代文人们的作品中,鱼的形象却呈现出了许多有别于民间的文化色彩。
由于古代文人社会地位的不确定性,文人们对于鱼有着极为特殊的情感,他们将鱼视为与自己同命运的生物,因而由鱼生发出了种种生命感喟。
文人们是熟悉民间鱼文化的,然而他们不满足于用自己的才华去简单地继承和传播先民们的鱼文化而是更注重通过对于鱼的描绘来抒发那些属于自己的情志,创造出带有本阶层特色的鱼文化。
《富贵有余》创作过程在他们的笔下,鱼不仅是富足的象征,更具有高贵脱俗的意蕴; 它既是文人自身的形象代言,也是文人们所渴望的悠游生活的具象。
可以说,鱼既是文人观照自我、表现自我的工具,也是他们进行哲学思辨的依凭。
较之于民间文学中的鱼文化,中国古代文人作品中的“鱼”的形象有着更为丰富的哲学与美学内涵。
一、丰足与尊贵的象征物(一)“鱼”作为丰足的象征物《富贵有余》创作过程在鱼文化发展的较早时期,受物质生活水平的制约,文人作品中鱼文化的始生导向较为明显。
如,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们与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劳动者们一样将鱼视为丰足的象征。
(二)“鱼”作为尊贵的象征物由于鱼肉味鲜美并且不易捕获,所以它常常被文人们视为珍贵之物的代表。
二、古代文人形象的代言赵少俨作品《富贵有余》局部(一)文人与“鱼”的相似命运鱼与文人,似乎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
然而在我国古代,两者却有着很程度的相似。
文人阶层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极其特殊的阶层。
他们拥有文化知识,具备机敏头脑,既可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而跃居社会上流,犹如越过龙门一步登天的鲤鱼; 也可能因怀才不遇而比一般的劳动者更为潦倒,恰如那些跃龙门而不过反致伤残的点额鱼。
赵少俨作品《富贵有余》局部(二)文人们借以自喻的“鱼”正是由于现实中文人的命运与传说中鱼的命运极其相似,所以文人们往往将自身与鱼联系起来,借鱼言志。
桃花流水鳜鱼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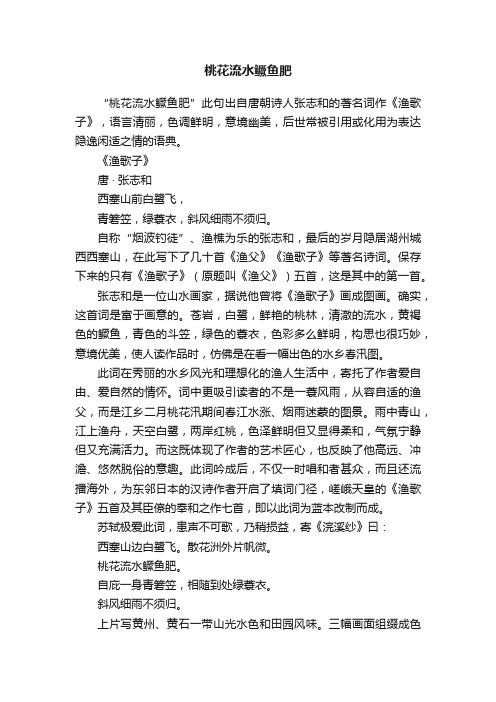
桃花流水鳜鱼肥“桃花流水鳜鱼肥”此句出自唐朝诗人张志和的著名词作《渔歌子》,语言清丽,色调鲜明,意境幽美,后世常被引用或化用为表达隐逸闲适之情的语典。
《渔歌子》唐· 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自称“烟波钓徒”、渔樵为乐的张志和,最后的岁月隐居湖州城西西塞山,在此写下了几十首《渔父》《渔歌子》等著名诗词。
保存下来的只有《渔歌子》(原题叫《渔父》)五首,这是其中的第一首。
张志和是一位山水画家,据说他曾将《渔歌子》画成图画。
确实,这首词是富于画意的。
苍岩,白鹭,鲜艳的桃林,清澈的流水,黄褐色的鳜鱼,青色的斗笠,绿色的蓑衣,色彩多么鲜明,构思也很巧妙,意境优美,使人读作品时,仿佛是在看一幅出色的水乡春汛图。
此词在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作者爱自由、爱自然的情怀。
词中更吸引读者的不是一蓑风雨,从容自适的渔父,而是江乡二月桃花汛期间春江水涨、烟雨迷蒙的图景。
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两岸红桃,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
而这既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也反映了他高远、冲澹、悠然脱俗的意趣。
此词吟成后,不仅一时唱和者甚众,而且还流播海外,为东邻日本的汉诗作者开启了填词门径,嵯峨天皇的《渔歌子》五首及其臣僚的奉和之作七首,即以此词为蓝本改制而成。
苏轼极爱此词,患声不可歌,乃稍损益,寄《浣溪纱》曰:西塞山边白鹭飞。
散花洲外片帆微。
桃花流水鳜鱼肥。
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上片写黄州、黄石一带山光水色和田园风味。
三幅画面组缀成色彩斑斓的乡村长卷。
下片写效法张志和,追求“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答李端叔书》)的超然自由的隐士生活。
全词虽属隐括词,但写出了新意。
所表现的不是一般自然景物,而是黄州、黄石特有的自然风光。
所表现的不是一般的隐士生活情调,而是属于苏轼此时此地特有的幽居生活乐趣。
全词的辞句与韵律十分和谐,演唱起来,声情并茂,富有音乐感。
“中国画鲤第一高手”—朱贵成工笔鱼作品

“中国画鲤第一高手”—朱贵成工笔鱼作品朱贵成,笔名阿贵,金陵画鱼人,1957年出生于南京,现为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理事、南京亚东书画院秘书长。
自幼酷爱绘画,刻苦自学,攻研山水、花鸟,尤擅长画工笔鲤鱼。
近年作品常被印成挂历、邮票或刊于报纸、杂志。
1991年至今分别在江苏省美术馆及南昌、常州、扬州、美国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级展览并获奖,江苏电视台、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等亦作专题介绍。
画鲤高手朱贵成文/苏子龙朱贵成又称“金陵画鱼人”。
因为鱼尤其是鲤鱼画得好,被称为“中国画鲤第一高手”,享有盛誉。
朱贵成个头不高,微胖,大眼睛,脑后扎着个小辫子,上身常常穿一件深色或紫红色中装,足下有时登一双圆口布鞋,高雅而不失淳朴,很让人接近。
鱼,尤其是鲤鱼,向来被民间视为吉祥之物。
“鲤鱼跳龙门”“年年有余(鱼)”,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意喻,也是画家笔下不尽的题材。
阿贵的鱼,有金鱼、鲶鱼、鳜鱼等;但画得最多也是最精彩的是鲤鱼。
在他的鲤鱼画中,有的一跃而起,如腾空展“翅”之状;有的成群嬉游,似举行盛大联欢。
画面中少者一二条,伸手可触;多则上百尾,姿态各异。
再辅以水花、水浪、水草、睡莲、荷花,以及岸边紫藤、垂柳、迎春花等等,愈显得生动鲜活,美不胜收。
阿贵画鱼,讲究逼真,一片鳞一片鳍一笔不乱,一只眼一根须一丝不苟。
因此他笔下的鱼,无论大鱼还是小鱼,条条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充满灵性。
更难得的是,阿贵还擅画群鱼,动辄八九条十数条集于一纸。
《乐哉》和《百乐图》,上百条鲤鱼齐聚嬉戏,大大小小、虚虚实实、争先恐后、千姿百态,搅得水草浮动、浪花飞溅。
阿贵的画集工笔和写意于一身,构图疏密有致,笔法细腻传神,尽融工笔和写意之妙,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十分难能可贵。
朱贵成是自学成才。
他的岳父迟明是安徽著名画家,称“江南渔翁”。
阿贵潜心学习,终于有成,又彰显了自己的个性,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的画作多次入选省及全国性展览,被国内外一些美术馆、展览馆、纪念馆及个人收藏,并在国画市场上行情看好。
海鱼文言文

海鱼文言文先秦时期,中国的文化繁荣,文人雅士们对于自然界的观察和思考形成了丰富的文学作品。
其中,海鱼作为大自然中的一份子,在文言文中被赋予了独特的意境和寓意。
本文将深入探讨海鱼在文言文中的描写以及所传达的思想和情感。
一、海鱼的描写文言文中常常使用形象生动的描写手法来展示海鱼的形态和特点。
例如:“冯唐公画出金目公鱼图,不是坊间俗物。
画鱼下品,上作鲤鱼,更有雨亭鱼。
” ——韩白《续画舫记》这段文字中,用“金目公鱼”、“鲤鱼”和“雨亭鱼”来描述了不同种类的海鱼,揭示了它们的身姿和外貌。
另外,也有文言文将海鱼比喻为宝石、珍宝等,形象描绘了它们的美丽和高贵。
二、海鱼的象征海鱼在文言文中往往象征着富贵、吉祥和成功等美好的品质。
这源于对于鱼儿的特性和行为的观察。
比如:“使之可入饭碗者最好,但比金钱世界更像水晶世界,溪水给它润泽,阳光、晴朗的天空给亮丽的光泽。
” ——钱钟书《管锥编》这段文字中,通过描写鱼在水中游动的场景,凸显了鱼的纯洁和高贵。
同时,将鱼与金钱进行对比,突显了鱼的珍贵和价值。
这种象征意义的描述常常被运用在祝福寿星长寿、商家生意兴隆等吉祥场合中。
三、海鱼的哲思文言文中的海鱼还经常被用作忧患意识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于生活和命运的思考。
例如:“鱼为古之耐寒者…退而“寒鳞静悲,不惧死而后怀既逝’之心。
” ——郦道元《饮冰室诗选评注》这段文字中,借鱼的耐寒能力,表达了人们应当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
鱼不畏寒冷,即使失去生命也要怀着对逝去的美好的执念,这种思想意蕴令人深思。
四、海鱼的寓意海鱼在文言文中除了对于形态和特点的描写,还寓意着和谐、自由和生命力的象征。
比如:“海鱼与空气和水源以浑沌为多,并无避隐藏之处,和他们相适应,随时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中。
” ——雅克布朗《鱼鳖学说》这段文字揭示了鱼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鱼无拘无束地活动于空气和水源之中,传达出一种自由自在、生命力旺盛的意象。
这种寓意常常被运用在表达人们对于自由、开放的向往和追求的场合中。
汪曾祺作品的阅读赏析

汪曾祺作品的阅读赏析汪曾祺作品的阅读赏析导语:朴素、平淡、韵味,是汪曾祺作品的主要风格。
他的作品以白描见长,语言轻盈质朴,平中显奇,淡而有味。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汪曾祺作品的阅读赏析,欢迎大家阅读!(一)小说赏析晚饭花①李小龙的家在李家巷。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巷子,相当宽,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
但是不长,巷子里只有几户人家。
西边的北口一家姓陈。
这家好像特别的潮湿,门口总飘出一股湿布的气味,人的身上也带着这种气味。
陈家往南,直到巷子的南口,都是李家的房子。
东边,靠北是一个油坊的堆栈;靠南一家姓夏。
在油坊堆栈和夏家之间,是王玉英的家。
王家人很少,一共三口。
王玉英的父亲在县政府当录事,每天一早便提着一个蓝布笔袋,一个铜墨盒去上班。
王玉英的弟弟上小学。
王玉英整天一个人在家。
她老是在她家的门道里做针线。
王玉英家进门有一个狭长的门道。
三面是墙:一面是油坊堆栈的墙,一面是夏家的墙,一面是她家房子的山墙。
南墙尽头有一个小房门,里面才是她家的房屋。
从外面是看不见她家的房屋的。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一年四季,照不进太阳。
夏天很凉快,上面是高高的蓝天,正面的山墙脚下密密地长了一排晚饭花。
王玉英就坐在这个狭长的天井里,坐在晚饭花前面做针线。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
他都看见王玉英。
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
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
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这是李小龙的黄昏。
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其为黄昏了。
李小龙很喜欢看王玉英,因为王玉英好看。
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
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
红花、绿叶、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这是李小龙天天看的一张画。
王玉英一边做针线,一边等着她的父亲。
她已经焖好饭了,等父亲一进门就好炒菜。
王玉英已经许了人家。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丰富的隐喻与象征——对南翔短篇小说《老桂家的鱼》的一种阐释于爱成从短篇小说的基本要求看,南翔短篇小说《老桂家的鱼》深具意味。
“鱼”作为贯穿全篇的“穿缀物”紧紧抓住了“人生横断面”和故事关键点,并贯穿始终。
正如经典短篇小说往往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作家的发现力和创作智慧一样,这个作品“浓缩人生悲剧”,在信守篇幅的同时,努力把触角伸展到更加广阔的意义层面,从而在“意味”的有无上同故事以及传统小说有了区分,在严格的空间里寻找到了最大的爆发力。
作品写出了三重象征。
也许有人说短篇小说不宜采取象征写法,因为篇幅太短。
如布鲁姆所说,“我们必须小心提防所谓的象征,因为在技艺精湛的短篇小说中,往往是没有象征而不是有象征”、“象征对短篇小说来说是危险的,因为长篇小说有足够的世界和时间来自然而然地遮掩象征,但短篇小说必须是较突如其来的,因而处理象征很难不显得唐突”。
可见短篇小说里使用象征但又不显得唐突不是容易的事情,却也是难得的事情,不易做到的事情。
象征使用的得当,其实反而能够“构成一种根本性的形式”(博尔赫斯语)——所有伟大的短篇小说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形式,不管是契诃夫式的还是卡夫卡式的。
像爱伦坡、霍桑、梅尔维尔等美国传奇小说家,就特别强调写出小说中的象征性和诗意叙事。
因为象征性和寓言性的人物事件不需要连篇累牍地描述,反而可以使得写得更简。
就《老桂家的鱼》来说,象征和隐喻的使用,第一重,老桂是当代都市的被抛弃者,现代社会的疍民——想上岸而不得;第二重,老桂家打上来翘嘴巴鱼恰恰也正是老桂式健康生命终归被现实榨干成为鱼干的象征,但他却是有尊严的——想自由体面生存而不得;第三重,潘家婶婶是当代都市中的隐士——想做隐士而不得。
三重象征,隐喻的正是当代城市底层民众的命运!在城市化和资本挤压下,无望的底层的悲苦人生。
这是作品的批判性所在。
作品中的老桂,像是一个提线木偶,被命运之手拨弄,在四大即将耗尽散掉之际,在业风中左右摇摆,踉踉跄跄,溃不成军,拿不成个。
这是一具病体,是一堆即将熄灭的余烬,但却又是一个清醒的观察者,叙事者,参与了作者的叙事。
老桂是沉默的,通篇没有一句话,只是用表情、动作、眼神、手势来表达感情。
作者提醒读者,是因为老桂过于虚弱,而无力说话。
其实,这正也是作者的策略,让老桂不发一言,用沉默的苦涩和忧伤,来强化底层的悲哀,当然也是底层的坚强。
这个病体正是作者采用的的隐喻,疍民也是隐喻——老桂一家,本来并不是传统水边居民意义上的疍民,不是广东地区传统意义上不被允许上岸而饱受挤压和欺凌的边缘族群的疍民,老桂一家如果说是疍民,其实只是疍民特征的自觉选择水上生活的边缘人,或者可以称之为新疍民。
老桂的悲剧,隐喻了一个群体的共同的悲剧和境遇。
这个群体甚至很大,无依无靠,自食其力,自生自灭,艰难时世。
最终的结局也如老桂,如老桂的家庭。
正如老桂家的鱼所象征的。
这条翘嘴巴鱼,其实是作品的文眼,是高度集中化的象征物,是作品的核心穿缀物。
叙述者对这条鱼,极具耐心地描写,甚至忍不住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跳出来,以诗意抒情哲人的语言进行评论。
作品写老桂的一天,连带出了饱满的现实生活背景,繁复的社会形态,绵延的历史脉络,写出了宽阔度、丰富性和历史感,写出了老桂等人的苦难、无力、无奈和悲伤——如果说这是老桂的遣悲怀,何尝不也是作者的遣悲怀呢?先是,打鱼收网的过程,像是老人与海的壮观奇诡;打上来后,鱼的凶猛反抗把老桂家击倒在地,扫掉牙齿,而老桂对鱼惺惺相惜,不舍得拿剪刀割伤它的身体;这条鱼像是一个尤物,一个精灵,作者不厌其烦地描述它的惊艳:“身材修长,宛如一枚无限放大的丰腴的柳叶,银亮平直的头部锋利如刀如戟,浅棕色的背部是一道起伏的峰峦,一张鲜红的突吻,娇艳滴滴,哪里就是一只网中之物哇!”鱼的形象,其实正是象征了老桂自己。
打上这条鱼的兆头,未必是好兆头,完全是恶兆。
借民间的说法,打上来的应该就是老桂的元神了!元神出窍,所以鱼后来莫名失踪,所以老桂终至不治。
鱼和人,在此互成隐喻,互为镜像。
所以,作者魂不附体地吟诵出这样的话:“如此这般的翘嘴巴鱼,是雄与雌,阴与阳的结合,讲是壮美却柔婉,到底旷放还忧伤。
”老桂死了,因为无钱看病。
病不起,只能死。
鱼象征了老桂的尊严和不屈。
这是象征的一层。
还有一层。
即疍民的所指,实则也是底层民众、打工阶层、都市边缘人生,如何在城市更有尊严扎根落脚的一个隐喻。
没有房子,买不起房子,没有技能,不能靠手艺体面生活,所以成为逐水而居靠江河捕鱼吃饭的疍民。
而那些住在贫民区、城中村、棚户区、桥底涵洞中的人,房子岂不也是他们的梦想,他们回到人群、世间的依托吗?疍民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实为无奈之举。
而河流和渔船,哪里又有什么浪漫和超脱?这种底层悲歌和道德义愤,正是作品的出发点。
其实,潘家婶婶何尝不也是一种象征?潘家婶婶这个人也像是当代的陶渊明,城市中的隐士。
心远地自偏,自得其乐,自我拯救,但到了最后,城市整治到了她的“东篱”——桥底的菜地,终至做隐士而不得。
体制化的力量,城市化刚性设计的无孔不入,必然要消灭土地,哪怕一点点残留的被忽略的空地。
城市也必然消灭最后的疍民!无论真疍民还是类似疍民,无论是遁世者还是边缘人,只要你在城市中。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层面,形而下的层面。
更广泛的意义上,如果说鱼所在的江湖,实在的江湖告急,鱼处处受困被捉,反映了一种绝境;那么,社会的江湖,人间的江湖,普通人置身其中的江湖,处境何尝不是如此!鱼逃不过网,而人逃不过命运,这命运之网的编织者,除了冥冥中的天意,更多是类似鲁迅先生《故乡》中所说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的社会挤压。
老桂被网住了,所以赴了死地;等待老桂家的,仍是同样的命运。
江湖和鱼,在此就具有整体性的象征意味了。
作者是个道德家,或者说道德倾向比较鲜明。
无论他早期的作品《南方的爱》、《大学轶事》、《前尘——民国遗事》、《女人的葵花》,还是晚近的作品《绿皮车》、《哭泣的白鹳》、《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都是如此。
而这个作品显然还远远溢出了这个道德和伦理的层次,更有形而上的深意在。
一个人的生与死,尊严的生与死。
老桂和鱼,都活出了他们的尊严,对命运的抗争,并不祈求怜悯。
还有潘家婶婶。
说道影响的焦虑,老桂倒有点像《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了,只不过中国的这个老人,肉体被病击倒了,无法成为不倒下的勇士。
但他的意志并没有倒下,仍然倔强而顽强,执拗而勇猛。
鱼也像《老人与海》中的大马哈鱼,不过这条鱼不像大马哈鱼所象征的命运,还多了慑人的精气和魂魄,作为老人的灵魂对应物出现——它选择跳出水槽,风干而死,而不像大马哈鱼被鲨鱼蚕食式的成为他者的口中餐。
这是一部不合时宜的小说,不与时俱进的小说,不时髦的小说。
不是吗?快时代的慢文本,小时代的大叙事,软时代的硬情感,碎时代的全信息。
总之,这是一部看得痛、看得累的小说。
作品采用的是作者一贯拿手的书面语描述,也就是执拗的知识分子叙事。
叙述推进的节奏显得凝重,似乎刻意不追求行云流水之势,而处处显出粘滞,粘滞的现实,粘滞的生存,粘滞的历史,粘滞的情绪。
而粘滞的状态中,主人公老桂是清醒的,叙述者即作者是清醒的。
作品叙事娴熟,手法精道,采取了第三人称叙述的选择性全知视角,叙述者仅仅透视主人公老桂的内心,仅仅了解主人公的内心,对老桂老伴、潘家婶婶等其他人物只是“外察”。
同时,作者作为叙述者,又采用了主人公老桂的意识和感知,来替代自己的意识和感知进行聚焦,主人公老桂的感知构成叙事角度,这又构成人物的有限视角。
这两种限知模式,在《老桂家的鱼》中却有时出现了交互使用,全知叙述者和故事主人公交替充当起了“观察之眼”,谁看、谁说出现了交集。
这种独具匠心的结构安排和文体选择,为表达主题意义和增强审美效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利于深化作品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
总体来看,作品的叙事是把真实作者的视角和老桂的视角合为一体,以行将死去的老桂的清醒的眼光,凝视着这不多的时日,主要是在一天中发生的事情。
在老桂的凝视下,或者说在这个大病缠身行将就木之人苦涩的视角下,这粘滞的现实在我们面前敞开,文本在我们面前呈现历史与现实的繁复,呈现人物的命运感。
作品通篇描写的是老桂的所见所感所思所为,他的自语式叙事。
在他的眼中,一切都像是重病之人、将亡之人的疾病叙事。
老伴小气,寡情,粗鄙,宁愿老桂病死也不舍得花钱治病,但她却能干、坚韧、不屈不挠;潘家婶婶有情有义,仗义无私,朴素的爱的精神在她身上和在阿珍身上都有体现,底层并没有完全陷落!其实,老桂家对老桂的死活不管不顾,其实未尝不是当代中国部分人群的现实,穷困之家的现实。
病在穷人眼里,在广大的农村那里,迄今大抵仍然不是休养的理由。
只要能动,就要做活,能治则治,治不起就等死。
其实何尝农村如此,穷人如此,城里人何尝不也大批人的人群如此?病不起,是当代中国的病。
但真实作者这个全知叙述人,有时候却又站出来,独立于主人公感知之外,做几句评说。
像“工作服三个字,几多熨帖,几多念想。
三四十年前,做了回乡知青的年月,多么想去城里当工人,那时节,穿工作服就是一生的盼头,无上的荣光”“如此这般的翘嘴巴鱼,是雄与雌,阴与阳的结合,讲是壮美却柔婉,到底旷放还忧伤”等这类语言,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叙述者的感叹,哪些是老桂的声音了。
甚至在文本当中,作者还化身为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向老师,对疍民的由来进行历史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解说。
当然,这不是作者越轨,而是有其不得不然的理由,是作者知识分子立场的独有动力所致。
作家采用的是典型的书面语言,知识分子话语体系。
像上来的第一句话:“入冬以后,老桂知晓自己病了,或许,病得不轻。
”这话中的“入冬”、“知晓”、“或许”之类,都是典型书面语。
而仅就后面的三段而言,又有“跃然而上”、“趋前”、“蔫没声响”、“沁人心脾”、“飘逸”、“分辨与捕捉”、“冷峻”、“氤氲”等相对文雅的词,看得出,这是作者一以贯之的知识分子写作了。
何为知识分子写作?首先是一种立场,即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写作就是写那些无人敢写之事,讲那些无人敢言之语,这就意味着要反一般人之常态”,是永远的不认同者,追求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写作,一种烛照良心的灯塔式写作。
这种写作,更接近于伟大的俄罗斯传统,托尔斯泰式的、果戈里式的,索尔仁尼琴式的,准确的说,更像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以及纳博科夫的结合,不仅仅是外观的,还有内视的,内省的。
就当代中国文学来讲,则与鲁迅、钱钟书、韩少功、李锐的同一个谱系。
知识分子写作在叙事上,也更多采取文雅的一脉,讲究的书面语的一面。
当然,不排除口语的进入,但文气贯通始终,终究不是汪洋恣肆的民间话语系统,例如莫言、阎连科等的话语体系。
慢,也正是南翔式知识分子叙事有意为之的慢节奏。
作品上来写到老桂的病态,作家不厌其烦地写老桂从小船上大船的缓慢笨拙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