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自觉说
魏晋文学自觉之说的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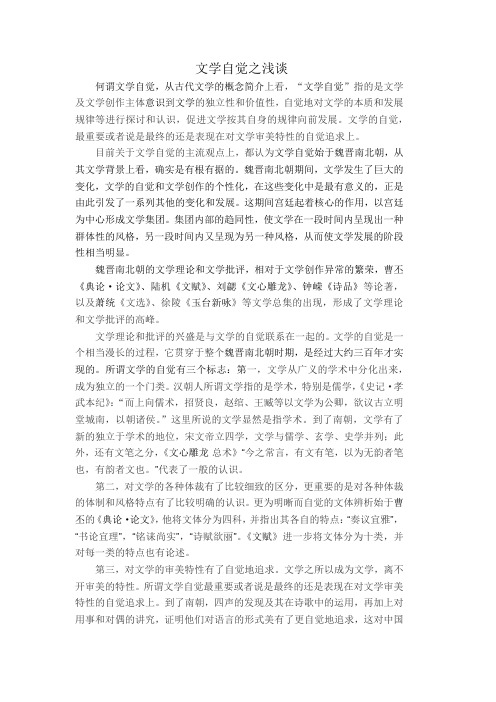
文学自觉之浅谈何谓文学自觉,从古代文学的概念简介上看,“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
文学的自觉,最重要或者说是最终的还是表现在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目前关于文学自觉的主流观点上,都认为文学自觉始于魏晋南北朝,从其文学背景上看,确实是有根有据的。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
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
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内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的繁荣,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论著,以及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
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
”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
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列;此外,还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代表了一般的认识。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其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1)“魏晋文学自觉说”评介

视“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最 早来自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叔孙豹的“三不朽” (见《春秋左传集解· 襄公二十四年》)。司马 迁《报任安书》的“发愤著书”是对此的继承; 扬雄亦然,班固《扬雄传赞》:“(扬雄)实好 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二人所 求不朽并非专指论说文,亦包括诗赋。曹丕不但 没有超越反倒落后。曹丕言及不朽,所举例子是 文王、周公:“西伯幽而演《周易》,周旦显而 治礼。”
詹福瑞《从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 觉》:从汉人的屈原批评看,文学已渐趋独立, 文学观念也渐近自觉。
李炳海《黄钟大吕之音———古代辞赋的文本阐 释》:“辞赋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场变革, 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种新的文学尝试,更重要的它 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标志。”
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的总结:
(二)“诗赋欲丽”观点不是曹丕原创。
追求华丽辞藻是汉赋写作的基本特征,“丽” 是汉文特有的审美要求。《西京杂记》中司马相 如:“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班固 《汉书· 艺文志》:“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 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汉宣帝:“辞赋大 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
总之,“文章不朽说”和“诗赋欲丽说”既 非曹丕首创,更无理论建树,却被铃木、鲁迅、 李泽厚等人吹捧抬高,是否因其身分特殊,人著 言重?
三、《典论· 论文》的本义与地位
(一)“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是指 诗赋为代表的“文学”而是“文章”。 “文章”范围远甚“文学”。曹丕所列八种 文体,属于标准“文学”的诗赋排在最末,可见 他对“文学”的真实态度。在其眼中,真正不朽 者并非诗赋文学,而是论说文。对建安七子,他 不认为《七哀诗》、《登楼赋》的作者王粲会不 朽,却认为写《中论》的徐干将不朽。把这句话 看成对“文学”的重视,是对《典论· 论文》的某 种误读。
浅论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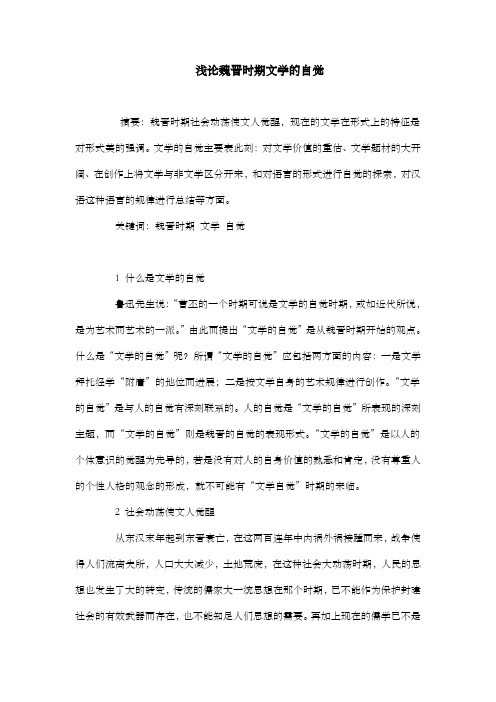
浅论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摘要: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使文人觉醒,现在的文学在形式上的特征是对形式美的强调。
文学的自觉主要表此刻:对文学价值的重估、文学题材的大开阔、在创作上将文学与非文学区分开来,和对语言的形式进行自觉的探索,对汉语这种语言的规律进行总结等方面。
关键词:魏晋时期文学自觉1 什么是文学的自觉鲁迅先生说:“曹丕的一个时期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期,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由此而提出“文学的自觉”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观点。
什么是“文学的自觉”呢?所谓“文学的自觉”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拜托经学“附庸”的地位而进展;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
“文学的自觉”是与人的自觉有深刻联系的。
人的自觉是“文学的自觉”所表现的深刻主题,而“文学的自觉”则是魏晋的自觉的表现形式。
“文学的自觉”是以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若是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熟悉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期的来临。
2 社会动荡使文人觉醒从东汉末年起到东晋衰亡,在这两百连年中内祸外祸接踵而来,战争使得人们流离失所,人口大大减少,土地荒废,在这种社会大动荡时期,人民的思想也发生了大的转变,传统的儒家大一统思想在那个时期,已不能作为保护封建社会的有效武器而存在,也不能知足人们思想的需要。
再加上现在的儒学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学了,因为汉武帝时期起来的儒学,虽然顶着孔子的招牌,但其学说的本质,已并非孔子的真面目。
儒学中加进去了许多阴阳五行的学说,因此那时的儒学,就带有了浓厚的术士之气,哲学也就成了迷信的宗教。
那时的帝王、权贵却极爱这种哲学,这种哲学成了他们的护身符,但这种哲学对平民老百姓却无丝毫有利和受用的地方,因此当政治动荡、政权四分五裂之时,如此的儒学也就随着衰亡了。
而在动荡之时,人们思想往往更需要一种寄托,无论是知识分子阶级仍是平民阶级,都有酿成新信仰、新宗教的需求,老庄玄学、道佛宗教便应运而生了。
如何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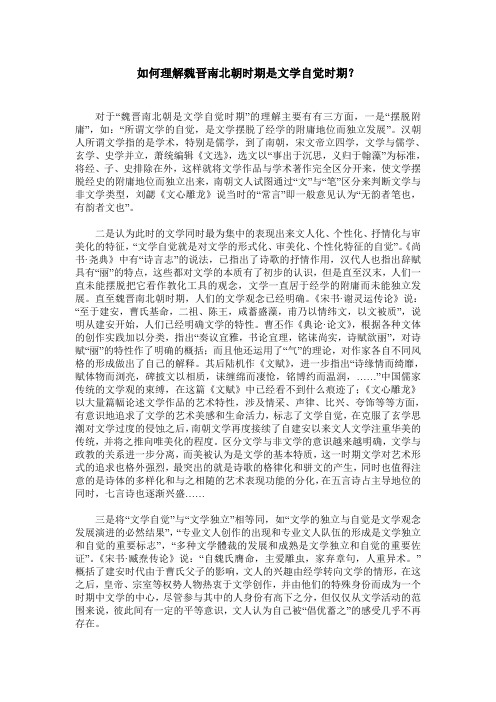
如何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时期?对于“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的理解主要有有三方面,一是“摆脱附庸”,如:“所谓文学的自觉,是文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发展”。
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萧统编辑《文选》,选文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为标准,将经、子、史排除在外,这样就将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完全区分开来,使文学摆脱经史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出来,南朝文人试图通过“文”与“笔”区分来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类型,刘勰《文心雕龙》说当时的“常言”即一般意见认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二是认为此时的文学同时最为集中的表现出来文人化、个性化、抒情化与审美化的特征,“文学自觉就是对文学的形式化、审美化、个性化特征的自觉”。
《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的说法,已指出了诗歌的抒情作用,汉代人也指出辞赋具有“丽”的特点,这些都对文学的本质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直至汉末,人们一直未能摆脱把它看作教化工具的观念,文学一直居于经学的附庸而未能独立发展。
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文学观念已经明确。
《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说明从建安开始,人们已经明确文学的特性。
曹丕作《典论·论文》,根据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加以分类,指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对诗赋“丽”的特性作了明确的概括;而且他还运用了“气”的理论,对作家各自不同风格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其后陆机作《文赋》,进一步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中国儒家传统的文学观的束缚,在这篇《文赋》中已经看不到什么痕迹了;《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涉及情采、声律、比兴、夸饰等等方面,有意识地追求了文学的艺术美感和生命活力,标志了文学自觉,在克服了玄学思潮对文学过度的侵蚀之后,南朝文学再度接续了自建安以来文人文学注重华美的传统,并将之推向唯美化的程度。
以《文赋》为例浅析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

关键词 : 文赋 ; 文学 自觉 ; 具体表现
宗 白华说 : “ 汉末魏晋六 朝是 中国政治上最混 乱 ,社会 上最
苦痛 的时代 , 然 而却是精神史 上极 自由、 极解放 , 最 富于智慧 、 最 浓于 热情 的一个 时代 。 因此也 就是 最 富有艺 术 精神 的一个 时 代 。” e r ( P 1 7 7 ) 文学在这样 宽松的大背景下逐 渐进入 了 自觉时期 。 而这种 自觉 的具体表 现主要有以下 四个方面 。
陆机的文赋第一次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对六朝文学理论批判发展影响极大不仅文心雕龙是对他的全面继承和发展挚虞李充的文体论沈约等人的声律论萧统的文选中的文学观念都是在陆机思想影响下从某一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2 0 1 4年 4月
文 学 研 究
谚掰
以《 文赋》 为例 浅 析魏 晋 时期 的文学 自觉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个独立 的存在。这是魏晋时期文学 自觉 的第一个 表现。 二、 文体辨析风炽 如果 魏晋时期人们 仅仅意识 到文体 的独 立而不 了解文体 的
曹丕 的《 典论论文 》 是在文 艺思想发展 和文 学理论批判方 面 具有 重大转折意义 的一篇纲领性 文献 。陆机 的《 文赋》 第一次 系
统全面地研究 了文学创作 的基 本理论 ,对六 朝文学理论批判发
张瑞瑞
河南大学文学 院 河南 摘 开封 4 7 5 0 0 1
要: 魏晋“ 文 学 自觉” 这一 问题 首先 由 日本 汉学家铃 木虎雄提 出, 鲁迅在其 著名演讲 《 魏晋 风度及文章 与药及酒之 关 系》 中将
铃 木 氏的观 点用文学家的热情进一步进行 了阐发并得到 学术界 的积极 响应 。本 文主要 以陆机的《 文赋 》 为例 , 探讨 了魏晋 时期文化 自
高中阅读理解及答案解析——“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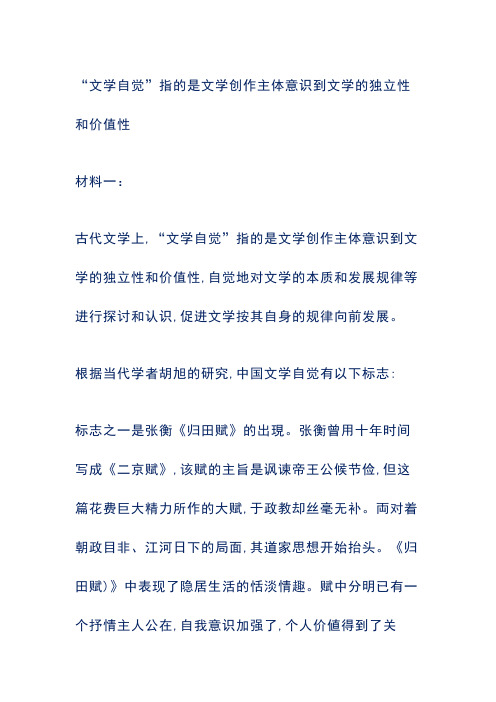
“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材料一:古代文学上,“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
根据当代学者胡旭的研究,中国文学自觉有以下标志: 标志之一是张衡《归田赋》的出現。
张衡曾用十年时间写成《二京赋》,该赋的主旨是讽谏帝王公候节俭,但这篇花费巨大精力所作的大赋,于政教却丝毫无补。
両对着朝政目非、江河日下的局面,其道家思想开始抬头。
《归田赋)》中表现了隐居生活的恬淡情趣。
赋中分明已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在,自我意识加强了,个人价値得到了关注。
此后,抒情小赋不断出现,辞赋成了文人抒情写意的工具,实现了文学的自觉。
标志之二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現。
大约在桓、灵之世,出现了一批文人五言诗,其代表就是选录于《昭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
古诗在内容上表现了“人的自党”。
“十九首”的内容不外游子之歌和思妇之词两个方面,诗人们慨叹人生的短促和前途的渺茫,抒写了羁旅愁怀和离别相思,情调是悲哀而深沉的,这些慨叹正是对人生的执着与重视。
“古诗十九首”的抒情十分真实强烈,作者们对自己的种种情感,毫不怖,一寄之于诗。
这说明古诗的作者们不再把文学作政教的附庸,而是为满足自己的抒情需要进行创作;人的主题鲜明了,文学成了表现人生、人的命运、人的心灵的文学。
标志之三是散文创作方画新西貌的出现。
首先是各体散文的长足发展。
以文体而言,碑、铭、诔、箴、书、笺、楸、策、令、议、记、嘲、谒文、连珠等,种类繁多。
其次,东汉中后期散文逐渐趋向整齐华美。
一是在向式、音节、辞藻、用典等方面做文章,着カ创造出一种形式美;二是讲究散文风神的飘逸与灵动。
(摘编自“百度百科”,有删改) 材料二: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朝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这一讽喻时事、有感而发的观点竟在传播中异化,“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界影响愈加广泛。
“文学自觉魏晋说”再探讨

“文学自觉魏晋说”再探讨首先,魏晋时期的文人具有对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文人们深感时代的变幻和不安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们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对时局的关切和思考。
他们深入反思自己的身份和角色,意识到自身的文学才能和责任。
例如王羲之认为:“书者有以记名姓者,有以发缛心思者。
”他将书写视为一种表达自己内心思想的方式,通过文字来传递情感和思考。
其次,魏晋时期的文人对文学的自觉追求体现在他们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探索。
他们意识到文学不仅是一种表达情感的工具,也是思想的载体。
因此,他们对文学形式进行了创新和改变。
例如陶渊明追求自然写实的文字表达,通过描绘自然景色、个体生活和人性的复杂性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观点;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以独特的写作手法和角度展现了对世态和人性的深入探究。
他们对文学内容进行了丰富多样的探索,关注社会伦理和道德,通过对历史、政治、人性等方面的思考来展现自己对时代的理解和反思。
而魏晋时期的文人的自觉追求还体现在对文学评价和创作规范的思考。
魏晋时期,文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创作需要一种标准和规范。
他们开始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和批判,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学批评标准。
例如陶渊明在《陶渊明集序》中提出了“公正、宽容、审美、理性”的文学四原则,要求文学作品既要有审美价值,又要有思想内涵。
这种对文学评价的追求,体现了魏晋时期文人对自己创作的自觉和自省,也促进了魏晋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总之,“文学自觉魏晋说”是一种对魏晋文学特点的观点,它认为魏晋时期的文人对自身的文学创作有一种自觉的认知和追求。
从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探索、对文学评价和创作规范的思考,以及对时代的关切和反思等方面来看,魏晋文人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自觉和自省。
他们通过文学的表达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通过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来丰富文学的内涵和价值,通过对文学评价和创作规范的思考来推动文学的发展和进步。
“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文档 (3)解读

文学遗产“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作者:雷恩海《光明日报》(2015年12月31日15版)鲁迅论“魏晋文学自觉”,指出其关键乃世情的变化促使思想的新变,遂引起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其优点是自尊、自我觉醒,其缺点则是消极避世。
曹操提倡通脱,打破东汉经学之桎梏以及党锢清流末派的固执,嵇康、阮籍之“师心”“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特色。
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
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
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
”显然,鲁迅认为世情思想的演变、人之觉醒,乃文学自觉的动因。
正因为关切世事,文学所承载的乃是世情、思想和个人情性及其生命体验:“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
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
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探源溯本,极为精当。
事实上,思想之活跃、人之价值之重视、精神之摆脱束缚而趋于自由,乃文学自觉之前提。
人有性灵,自古而然,但此前往往湮灭于社会群体的状态之中,至此则超越社会群体的束缚而日趋独立、觉醒,重视个体生命意识。
时世动荡,战乱相仍,人命危浅,被时代所裹挟,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与命运,直面惨淡的人生,也将目光内视,追求精神与心灵的自由与自足,乃使士人认识到个体生命的可贵、处于动荡时世的艰危与无奈。
因觉醒、自尊而使生命过得精彩,服食求长生乃虚妄,纵情享乐为荒诞,如何超越限制而自致不朽?立德、立功,皆须依凭机遇和位势,非由自我所能掌控,唯有立言则可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获致,遂为人所青睐。
因而,觉醒的个体生命意识,必然借助于文学艺术来表达。
文学自觉乃一个渐进的进程。
以文字记述事件,表达思想与情性,进而描摹物象,传神写照,娱情悦性,经历了漫长的演进,日益积累了创作的经验与体会。
魏晋文学自觉名词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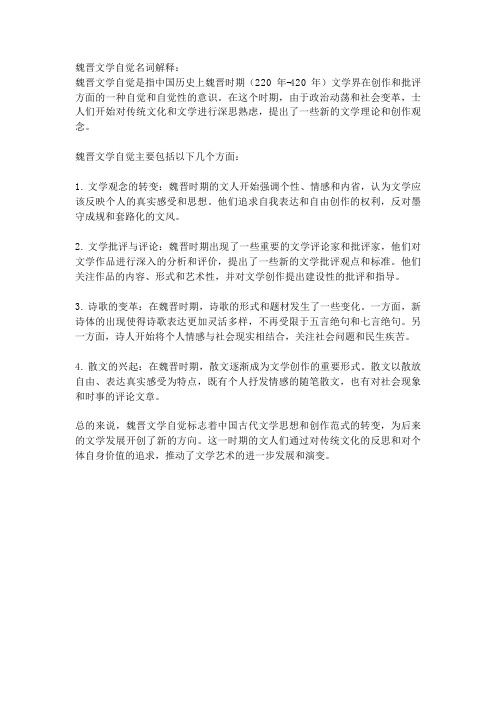
魏晋文学自觉名词解释:
魏晋文学自觉是指中国历史上魏晋时期(220年-420年)文学界在创作和批评方面的一种自觉和自觉性的意识。
在这个时期,由于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士人们开始对传统文化和文学进行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和创作观念。
魏晋文学自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学观念的转变:魏晋时期的文人开始强调个性、情感和内省,认为文学应该反映个人的真实感受和思想。
他们追求自我表达和自由创作的权利,反对墨守成规和套路化的文风。
2. 文学批评与评论:魏晋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和批评家,他们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价,提出了一些新的文学批评观点和标准。
他们关注作品的内容、形式和艺术性,并对文学创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指导。
3. 诗歌的变革:在魏晋时期,诗歌的形式和题材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新诗体的出现使得诗歌表达更加灵活多样,不再受限于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
另一方面,诗人开始将个人情感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关注社会问题和民生疾苦。
4. 散文的兴起:在魏晋时期,散文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形式。
散文以散放自由、表达真实感受为特点,既有个人抒发情感的随笔散文,也有对社会现象和时事的评论文章。
总的来说,魏晋文学自觉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和创作范式的转变,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开创了新的方向。
这一时期的文人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个体自身价值的追求,推动了文学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一、概述“魏晋文学自觉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指的是在魏晋时期,文学开始从经史之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意识。
这一说法自上世纪初由王国维等人提出以来,对于理解魏晋文学的独特价值和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反思也逐渐兴起。
本文旨在通过对该说法的梳理和反思,重新审视魏晋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以期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在具体反思过程中,本文将首先回顾“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背景及其主要内涵,分析其在学术史上的影响和意义。
通过考察魏晋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创作实践以及文学理论批评等方面的情况,探讨“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尝试提出新的视角和方法,以重新审视魏晋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1. 简要介绍“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意义。
“魏晋文学自觉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指的是在魏晋时期(大约公元220年至04年2),文学创作开始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和独立性,与之前的文学形式相比,更加注重个体情感的表达和审美追求。
这一说法的历史背景与学术意义,不仅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在于它为我们理解古代文人心态和文学创作动机提供了重要视角。
历史背景方面,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士人阶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惑,这种压力与困惑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形成了对个体情感、生命哲理的深刻思考。
同时,由于佛教、道教等思想的传入和融合,也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灵感和视角。
学术意义方面,“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探究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揭示了魏晋时期文学创作的独特面貌,也为我们理解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通过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研究,我们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和创作动机,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和魅力。
(1)“魏晋文学自觉说”评介PPT课件

真问题还是伪命题
1
一、“魏晋文学自觉说”缘起
日本铃木虎雄1920年《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 首次提出。主要证据是曹丕《典论·论文》的观 点:第一,开始评论作家;第二,提出文章是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附庸转为主流; 第三,提出诗赋欲丽;第四,提出“文以气为 主”。
鲁迅1927年《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袭用铃木的观点。
2
李泽厚上世纪80年代初《美的历程》发挥其说, “人的觉醒”、“文的自觉”遂在其后20多年风 行天下。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文学的自觉”贯 穿整个魏晋南北朝,历时约三百年。三个标志: 第一,文学脱离广义学术,成为独立门类;第二, 细致区分文学体裁,明确认识各体的体制和风格; 第三,自觉追求文学的审美特性。
观点的泛泛总结而已。
7
(3)汉人自觉追求文学的审美艺术效果。司 马相如专论作赋之道,其他赋家莫不如是。扬雄 《解嘲》:“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 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 也。”张衡作《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投入精力如此之大,求文而已。
如果以袁行霈“文学自觉说”的三个标准来 衡量,汉代文学已经完全“达标”;如果说中国 文学有一个“自觉时代”,起点应该在汉代而不 在魏晋。
8
三、《典论·论文》的本义与地位
(一)“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是指 诗赋为代表的“文学”而是“文章”。
“文章”范围远甚“文学”。曹丕所列八种 文体,属于标准“文学”的诗赋排在最末,可见 他对“文学”的真实态度。在其眼中,真正不朽 者并非诗赋文学,而是论说文。对建安七子,他 不认为《七哀诗》、《登楼赋》的作者王粲会不 朽,却认为写《中论》的徐干将不朽。把这句话 看成对“文学”的重视,是对《典论·论文》的某 种误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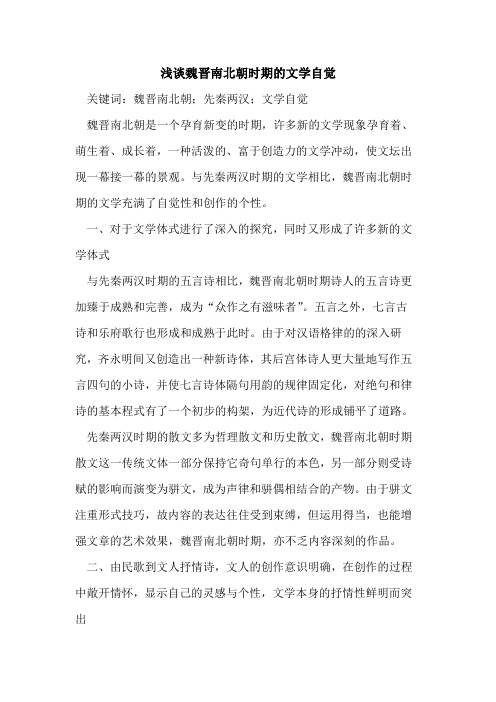
浅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先秦两汉;文学自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孕育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一种活泼的、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的景观。
与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充满了自觉性和创作的个性。
一、对于文学体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同时又形成了许多新的文学体式与先秦两汉时期的五言诗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的五言诗更加臻于成熟和完善,成为“众作之有滋味者”。
五言之外,七言古诗和乐府歌行也形成和成熟于此时。
由于对汉语格律的的深入研究,齐永明间又创造出一种新诗体,其后宫体诗人更大量地写作五言四句的小诗,并使七言诗体隔句用韵的规律固定化,对绝句和律诗的基本程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架,为近代诗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多为哲理散文和历史散文,魏晋南北朝时期散文这一传统文体一部分保持它奇句单行的本色,另一部分则受诗赋的影响而演变为骈文,成为声律和骈偶相结合的产物。
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内容的表达往住受到束缚,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期,亦不乏内容深刻的作品。
二、由民歌到文人抒情诗,文人的创作意识明确,在创作的过程中敞开情怀,显示自己的灵感与个性,文学本身的抒情性鲜明而突出在先秦两汉,主要的文学形式是诗赋。
先秦的《诗经》奠定了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道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诗经》是中国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但是《诗经》内容多是劳动人民集体口头创作的民歌,反映的是劳动人民的生活。
由此可以概括,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文学的形式主要为民歌,尚未能显示作家的性灵和特色。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抒情文学开始涌现。
建安时期由于时代的现实基础不同,文人对传统思想有了很大的突破,故眼界和心胸得以开阔。
此时的文人作家均能敞开胸怀、无拘无束地抒写自己的性灵和个性,具有较高的文学抒情性。
三、开掘了许多新的文学题材,文学作品内容丰富,使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内容方面显得多姿多彩这一时期的文学的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后世盛行的各类题材几乎都在此时滥觞或发展盛行。
浅谈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

浅谈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作者:刘秀红来源:《文学教育》2009年第03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中国文坛无论是文学创作,理论评价,还是文学史的重新审视,都体现了开放、兼容、客观、理性的当代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中过多的政治意味日渐消退,学术研究的氛围则日益浓重,很多过去与时代主流意识相左的作品和评论又以本真面目在文学史中展现出来。
本文主要从当代“人”与“文”的角度,来谈一谈自己对魏晋文学的一点看法。
一、乱世文学深化了文人对个体生命的体认中华民族传统美学观念中讲求一个和字,而且用运动变化的的理论来突显和的重要,所以我们总能看到盛世王朝的大书特书之史笔,对于乱世、分裂、专制“则更多地从离乱、凋零的角度去阐述人民罹受的种种苦难,正史上也就常常出现带有主流意识评判的“黑暗、战争、独尊”等字眼,而从哲学角度来看“福祸相依”、“否极泰来”、“黑暗寓示着新的黎明”世界万事万物都处在相互转化中,恰恰是有缺憾的魏晋乱世衍生了自觉的魏晋文学。
战乱频繁,文人们的报国梦破灭了。
他们的目光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向个人自我,面对死神暴虐,性命如蚁的残酷现实,他们更惊骇地意识到人生之短促,生命之脆弱。
因此,魏晋文人形成一种忧生惧死、依恋人生的凝重凄哀的自然生命意识。
作家们更多地在诗歌中流露出感叹生死的情感。
如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操的《短歌行》,陶渊明的《拟挽歌辞》,江淹的《恨赋》。
这种“年过何可攀援”、“人生如朝露”、“托体同山阿”的人生慨叹,使人更多地从生命过程和质量去强调生命的意义,从感官上去享受“朝夕生命”的快乐。
“天地无穷,人命有终。
立功扬名,行之在躬。
”(曹睿《月重轮行》)“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
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陈琳《游览》)即使汲汲于功名,其基点也不完全是献身帝业、忠君报国,而是追逐个人荣耀,借建功以扬名,实现个人自我的价值,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无限的存在。
立足点显然已转移到以个体生命意味为本位的基础之上。
魏晋时期的“文学的自觉”,正是孕生于这种充满个体生命意识的时代气氛之中。
浅谈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

浅谈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中国文坛无论是文学创作,理论评价,还是文学史的重新审视,都体现了开放、兼容、客观、理性的当代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中过多的政治意味日渐消退,学术研究的氛围则日益浓重,很多过去与时代主流意识相左的作品和评论又以本真面目在文学史中展现出来。
本文主要从当代“人”与“文”的角度,来谈一谈自己对魏晋文学的一点看法。
一、乱世文学深化了文人对个体生命的体认中华民族传统美学观念中讲求一个和字,而且用运动变化的的理论来突显和的重要,所以我们总能看到盛世王朝的大书特书之史笔,对于乱世、分裂、专制“则更多地从离乱、凋零的角度去阐述人民罹受的种种苦难,正史上也就常常出现带有主流意识评判的“黑暗、战争、独尊”等字眼,而从哲学角度来看“福祸相依”、“否极泰来”、“黑暗寓示着新的黎明”世界万事万物都处在相互转化中,恰恰是有缺憾的魏晋乱世衍生了自觉的魏晋文学。
战乱频繁,文人们的报国梦破灭了。
他们的目光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向个人自我,面对死神暴虐,性命如蚁的残酷现实,他们更惊骇地意识到人生之短促,生命之脆弱。
因此,魏晋文人形成一种忧生惧死、依恋人生的凝重凄哀的自然生命意识。
作家们更多地在诗歌中流露出感叹生死的情感。
如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操的《短歌行》,陶渊明的《拟挽歌辞》,江淹的《恨赋》。
这种“年过何可攀援”、“人生如朝露”、“托体同山阿”的人生慨叹,使人更多地从生命过程和质量去强调生命的意义,从感官上去享受“朝夕生命”的快乐。
“天地无穷,人命有终。
立功扬名,行之在躬。
”(曹睿《月重轮行》)“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
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陈琳《游览》)即使汲汲于功名,其基点也不完全是献身帝业、忠君报国,而是追逐个人荣耀,借建功以扬名,实现个人自我的价值,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无限的存在。
立足点显然已转移到以个体生命意味为本位的基础之上。
魏晋时期的“文学的自觉”,正是孕生于这种充满个体生命意识的时代气氛之中。
论魏晋文学的自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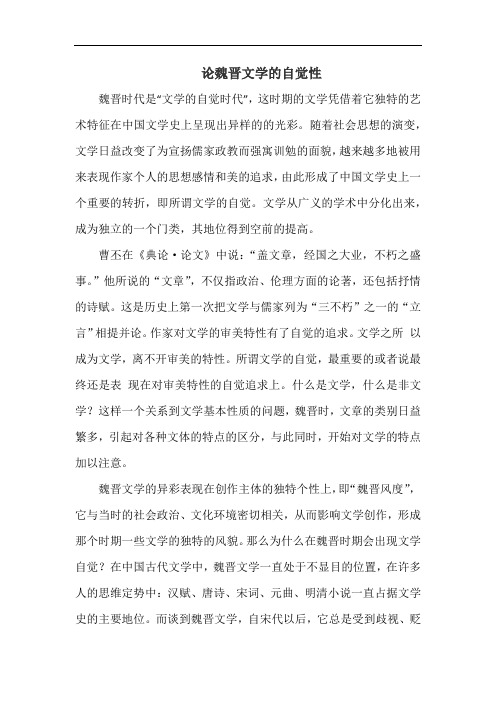
论魏晋文学的自觉性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时期的文学凭借着它独特的艺术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呈现出异样的的光彩。
随着社会思想的演变,文学日益改变了为宣扬儒家政教而强寓训勉的面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美的追求,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即所谓文学的自觉。
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其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他所说的“文章”,不仅指政治、伦理方面的论著,还包括抒情的诗赋。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文学与儒家列为“三不朽”之一的“立言”相提并论。
作家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
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这样一个关系到文学基本性质的问题,魏晋时,文章的类别日益繁多,引起对各种文体的特点的区分,与此同时,开始对文学的特点加以注意。
魏晋文学的异彩表现在创作主体的独特个性上,即“魏晋风度”,它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从而影响文学创作,形成那个时期一些文学的独特的风貌。
那么为什么在魏晋时期会出现文学自觉?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魏晋文学一直处于不显目的位置,在许多人的思维定势中: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占据文学史的主要地位。
而谈到魏晋文学,自宋代以后,它总是受到歧视、贬斥,甚至受到人们的忽视。
其实,魏晋文学的魅力之所在,正在于文学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产生了突破和超越的伟大意义,更在于魏晋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的纷繁驳杂、陆离怪诞多少令许多人难以从惯常的思维去得到清晰的解读,它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更令诸多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敬而远之,也许,这就是魏晋文学一直处于被冷落和疏远地位的原因之一。
若换一种眼光来看,一种文化色彩鲜明、魅力非凡、不同凡响又受到人们的冷遇,不能不说是文化的缺憾。
浅谈“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

浅谈“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介绍建安文学时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以说是‘文学自觉地时代’。
”这一“文学自觉”的看法成为后世中国文学史发展认识的一个基本的共识。
标签:魏晋;文学一、文学自觉的转变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文学一直作为政治目的和历史记录的附庸而存在。
最开始的文学——神话,起源于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和想象,是在人们劳动生产的过程中的产物。
大量用牲畜的现象出现在甲骨上。
殷代时,事無巨细,必须请示鬼神,作为一切行动(尤其是农业劳动)的指南,并且有专门的巫和史来从事这种占卜预测吉凶祸福活动的专职人员,这也是文学发生的雏形。
到了周代,有专门的机构采集民歌,与宫廷乐曲,祭祀颂歌等,一并集成《诗经》;将文化礼仪等典章制度记录下来,即《尚书》;东周时期,社会大变革催生了史官。
春秋时期出现了各种史书和散文;新的诗歌体裁,《楚辞》中的“骚体”,也是由楚国民歌而来。
到了两汉,赋开始风靡一时,或是针砭时弊,或是高歌颂德;其余的或抒政见(如《盐铁论》),或成为倡优博弈的娱乐品(如王褒的《洞箫赋》),或干脆就以欺骗人民、束缚士人的谶纬迷信之词,都出于非文学的目的;而《史记》、《汉书》等著作的产生,单纯的站在历史的角度,没有考虑文学目的。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墨客在文章之中表情达意。
汉末建安七子和曹氏父子,显露出天下一统的愿望;同时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文学批评由此出现,文学自觉性诞生,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等。
之后的正始文学,表达了阮籍等人以老庄的“自然”为旨来否定现实、韬晦遗世,抒发个人的苦闷思想与不满。
两晋的玄言诗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的恬静心境,寄情山水,成为山水诗的开端;陶渊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辞官还乡,归隐田园;《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中,多是代表人民意识和夙愿的志怪小说。
南北朝时,佛经的传人使音韵学有了发展,将发现的“四声说”应用在诗歌上就创造了永明体,诗歌在形式上有了重要的突破;出于对形式美追求风气的影响下,骈文的发展也迎来一个高潮;此时还出现了“文笔之辨”,对文学的界限进行争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文学批评巨著应运而生。
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

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王晓丹(无锡机电高职)摘要:魏晋南北朝以前,没有独立的文学范畴㊂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从广阔的学术领域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㊂关键词:文学自觉;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图分类号:G4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文章编号:(2020)01-01-02㊀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㊂最重要的是文学自觉㊂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文学是继文学自觉之后的文学㊂文学自觉是一个贯穿魏晋南北朝的漫长过程㊂这种自觉有三种迹象㊂本文就从以下三方面来粗浅的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现象㊂一㊁文学从广阔的学术领域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先秦文学不是具有现代功能的文学㊂先秦时期的文学形式一方面是文学㊁历史㊁哲学的结合,另一方面是诗㊁乐㊁舞的结合㊂生动多彩是文学的萌芽阶段㊂汉代以后,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一个典型的动荡时期的文学㊂文学创作形成了一些共同的主题,如生死主题㊁游仙主题㊁隐逸主题等,这一时期的文学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㊂先秦散文没有纯文学散文㊂散文创作常与历史㊁哲学相融合,但仍有一定的文学性㊂先秦诗歌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从宗教颂扬和祷祝诗到政治叙事诗,再到抒情诗㊂魏晋南北朝诗歌注重抒情性㊂先秦没有赋这种文体㊂汉赋是继承‘诗经“赋颂传统,仿效楚辞,吸收战国文学的铺张恣意以及先秦文人作品的相关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新文体㊂魏晋南北朝时期,词赋表现出抒情性和小品性,文学性得到加强㊂先秦小说是神话和寓言的故事㊂汉代小说没有文学形式,到了魏晋南北朝小说才逐渐成为一种新型文体㊂二㊁不同的文学体裁之间有更详细的区别㊂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系和风格特点有了清晰的认识先秦时期,不同的文体㊁文学㊁历史㊁哲学㊁诗歌㊁舞蹈没有明显的区别㊂不同风格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㊂到了汉代,风格看似有所不同,但风格掺杂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大多数文体都形成了自己的写作要求和基本文体特征㊂魏晋南北朝时期,学者们开始重视文体的辨析,文体差异更加明显㊂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体明确的分为了 四科八体 ㊂关于文学体裁分类的著作很多,这说明了作家们开始关注体裁的特点,并且有自己的风格㊂三㊁文人对文学的审美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因其审美特征而被称为文学㊂文学自觉最终还是表现为对审美特征的自觉追求㊂(1)散文先秦散文不分文学㊁历史和哲学㊂诸子百家的说理散文呈现了相当高的文学性㊂汉代散文的文学性与先秦相比并没有很大的提高,反而有所下降㊂西汉散文成就较高的是政论散文,其中贾谊的‘过秦论“就是这种代表.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辩文创作出现了高潮,题材广泛,名家众多㊂嵇康的论辩文最为突出㊂他的纹章析道缜密,辞喻丰博,兼几家之长,将论辩文推到新的高度㊂比如他的‘养生论“就阐释了形神互育的原则㊂魏晋南北朝时期,散文逐渐发展为骈化,作家开始提倡追求优美的散文,骈散逐渐合一,散文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㊂作家开始自觉地追求文章的审美特征㊂这一时期,散文的要求不断变化,体现了文人自觉意识的增强,文章美感的增强,审美特征的增强㊂(二)赋先秦时期没有赋这种文体㊂赋出现于西汉,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㊂在汉代,骚体赋首先出现,并逐渐形成了以 九体 为代表的独特格局的体系㊂骚体赋体系固定,题材相近㊂魏晋南北朝时期,辞赋的创作深受时代的影响㊂人们开始讲究对偶㊁声律㊁藻饰之美㊂文章的句子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骈化影响很大㊂魏晋时期,词赋变得抒情㊁小品化㊁个性化,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表达主要是抒情性的增强㊂王粲的‘登楼赋“表达了他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㊂这一时期,大赋开始抒发作者的情感,不再拘泥于政治,如潘岳的‘西征赋“㊁谢灵运的‘山居赋“㊂由于永明声律说的兴起,赋的创作也受到影响,出现了抒情赋的创作㊂比如江淹的‘恨赋“不仅充分发挥了赋体空间结构的优势,而且以情感为主线贯穿其中,造成气势起伏,藻饰也是恰到好处,是南朝著名的抒情小赋㊂诗体赋是魏晋南北朝齐梁文章新变的产物,是对赋的进一步抒情化尝试㊂赋的变化是魏晋南北朝文化自觉的充分体现㊂(三)诗歌先秦诗歌主要是‘诗经“和‘楚辞“㊂‘诗经“中的大部分诗都是抒情诗,为后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㊂魏晋时期很多人借用了‘诗经“的技法㊂‘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㊂‘古诗十九首“采用的抒情策略也多种多样,后世许多学者以此为例,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的生成㊂魏晋南北朝建安时期,中国诗歌开创了新局面, 建安风骨 成为诗歌美学的典范㊂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五言诗,每一首都有自己的特点㊂如曹植的‘白马篇“抒发了自己对前途的信心㊂曹操对乐府诗进行了改造,使之脱离了民歌成为一种独立文体㊂至此,诗人开始自觉追求审美特性㊂西晋诗歌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㊂陆机的‘拟古诗“藻饰华丽,‘猛虎行“诗风繁复,‘赴洛道中作“句式骈偶,这种诗风的有简单向繁缛的转化时文化自觉的明显表现㊂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而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㊂谢灵运作山水诗,鲍照善边塞诗,梁陈出现宫体诗,诗歌类型多样化,个性化㊂齐梁陈的 永明体 讲究声律和对偶,四声的发现和运用,推动了 永明体 的成熟,使古体诗向近体诗发展㊂诗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巨大转变可以说是文人对文学审美自觉追求的成果㊂(四)小说先秦时期的各种神话是小说的源头,但这些神话还不能算作小说㊂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才真正出现㊂魏晋南北朝小说可以分为志怪和志人两类㊂志怪小说主要记述神仙方术㊁鬼魅妖怪㊁殊方异物㊁佛法灵异㊂最具代表性的是‘搜神记“,曲折地反映社会现实㊁表达人民的爱憎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㊂志人小说记述人物的逸闻铁事㊁言谈举止,成就和影响最大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㊂‘世说新语“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言谈描写使人物生动形象,对故事进行一定的提炼㊂‘世说新语“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机智和幽默㊂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无论在文学门类㊁体裁风格还是审美特性上都有其 自觉性 ,各项文学体裁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自觉时期,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㊂2522020年第1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女报㊃家庭素质教育。
试论“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不可靠性

学眼光看来。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 ‘ 文学的 自觉时代’ 或如近代 。 所说是 为 艺术 而艺术 的一 派 。 以 曹丕做 的 诗赋很 好 。 因为他 以 所 更 ‘ ’ 气 为主 , 于华 丽 以外 , 上壮 大。⑤值得注 意 的是 , 故 加 ” 鲁迅关 于魏 晋时代是“ 文学的 自觉时代” 的学术观点有自己独定的前提 。他强 调的是此说应在“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 也就是说仪仅限于近代 ,
社会, 表达作 者的思想情感 、 喜怒哀乐, 可以较少约束地表达某一 阶层或某一利益集团对社会时改的看法 ,较为自由地 述作家想 己
3前人对论证依据 的误读 与现代人对前人说法 的误解
曹丕在《 典论 ・ 论文》 里所说“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 不是指 以诗赋为主的“ 文学”而是“ , 文章” 。在曹丕所列出的八种文体 中, 今天我们看来真正属于“ 文学” 的诗赋两类被 排在了最后。把曹丕 的“ 文章. 经国之 大业, 不朽之盛事” 之说看成是对“ 文学” 自身价值 的重视显 然是一种误读。 其次 “ 诗赋欲丽” 的 点 并非曹丕首先提 出。 追求华丽的辞藻是汉赋写作的基本特征, 这一点, 龚克 昌先生有
一
个 伪命题 , 不起推 究。 经 关键 词 : 晋 : 学 : 魏 文 自觉说
中图分类号 :27 I0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6 3 2 1 (0 20 - 1 00 17— 1 12 1)6 0 7 - 2
至魏晋南北朝间 , 遂较两汉更进一步, 于同样 的美而动人的文 章中间更有“ “ 之分。也即是, 文”笔” 该时期所谓的“ 文学” 目 贝 当于 两汉的文章之义, 即近人所指的广义的文学 , 它包括“ 与“ , 文” 笔” 也即是近人所说的“ 纯文学” 杂文学” 与“ 。纯文学 : 和雅文学 、 严肃 文学概念榴近 , 与通俗文学相对而言。除此之外 , 纯文学还有两种 含义, 一是表明文学 的特征和独立性 。 凡是以艺术形象为手段反映 生活 , 表现情感的语言艺术 , 包括诗歌 、 小说 、 戏剧 、 散文等 . 称为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在近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魏晋文学自觉说”是最有影响的一种说法,它甚至成为许多人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常识性判断。
但是,“魏晋文学自觉”的这种提法合适吗?它能很好地揭示中国文学史现象吗?近年来,陆续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有力反驳。
但总的来说,“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术界的影响仍然巨大。
我以为,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这一说法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却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
这样做的结果会影响我们对汉魏六朝文学的全面认识,也有碍于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全过程和中国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因此需要我们对这一说法进行深入系统的讨论。
一、“魏晋文学自觉说”简述“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源于日本人铃木虎雄1920年在日本《艺文》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名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后收入他的《中国诗论史》。
铃木认为,汉末以前中国人都没有离开过道德论的文学观,按此路线发展,就不可能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倾向。
他由此得出结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作为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证据,就是他对曹丕的《典论·论文》的分析。
铃木强调了四点:第一,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开始了对于作家的评论;第二,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所谓“经国”,恐非对道德的直接宣扬,而可以说是以文学为经纶国事之根基。
这是从道德论的文艺观转向的重要标志;第三,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观点,“这是根据不同的文体说明其归趋之异”;第四,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
可见,关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主要根据,铃木当时基本上都已经说到了。
但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讲,最直接接受的还是鲁迅的观点。
1927年9月,鲁迅应邀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
他不仅沿用了铃木“文学的自觉”的说法,而且同样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主要论证根据,包括对于曹植的分析,都与铃木的说法大致相同。
以后,“魏晋文学自觉说”逐渐在一些人的论述中开始出现,但是由于都没有对鲁迅的观点作更多的展开,因而它的影响并不大。
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如郭绍虞就指出:“(曹丕的)这种论调,虽则肯定了文章的价值,但是依旧不脱离儒家的见地。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过李泽厚的特别推重,以鲁迅为代表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术界迅速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有“风靡天下”之势。
其后,学者们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具体内容也做了比较多的概括与补充,并在时间上也各有修正。
最有代表性的是袁行霈的说法。
他说:“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的自觉”,他认为:“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
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袁行霈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这种概括,比起李泽厚的论述更有条理性和系统性,也更为坚实地立足于文学本身,其论述随着由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作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校文科教材的大量发行,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挑战“魏晋文学自觉说”虽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自鲁迅以来对于“文学自觉”的具体内涵解释的并不清楚,而当代学者对于什么是“文学自觉”本身就存在着理解上的歧义,所以,近年来逐渐有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不是从魏晋时代开始,而是从汉代就开始了。
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龚克昌。
早在1981年,在《论汉赋》一文中,他就认为应该把文学自觉的时代,“提前到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身上”。
后来,他又专门就此问题发表了题为《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的文章,认为从两个方面可以证明汉赋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一是“文学意识的强烈涌动,文学特点的强烈表露”,二是“提出新的比较系统的文艺理论”。
张少康在这方面论述得最为系统。
他说:“文学的自觉和独立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和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各种文学体裁的成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直接相联系的。
”以此而进行综合考察,“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初露端倪,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逐步发展过程,到西汉中期就已经很明确了,这个过程的完成,我以为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作为标志。
”詹福瑞也坚持汉代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开始的观点。
他认为,“两汉时期,文士的兴起和经生的文士化倾向,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自觉”。
李炳海同样以汉赋创作实践的大量事实说明:“辞赋的出现……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标志。
”如果进入现代学术界关于“文学自觉”的讨论范围的话,在以上两种观点中,我本人是赞成“汉代文学自觉说”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按袁行霈所说的三个标志来衡量,凡是“魏晋文学自觉说”所提出的诸多理论和事实佐证,在汉代我们都可以找到明显的存在。
首先,汉代的文学已经“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诗赋单列一类,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而由刘向所编辑的楚辞,所收只限于屈原作品和汉人摹仿《离骚》、《九章》之作,说明当时人对于文体的区分已经非常细致。
其次,汉人不仅“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在这方面,扬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班固在《扬雄传赞》中说:“(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
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仿依而驰骋云。
”可见,扬雄对于“易”、“传”、“史”、“箴”、“赋”等文体及其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并有意识地去进行仿作。
张衡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
他曾经写过多种文学作品,也体现了比较明显的文体区分意识。
同时,从《后汉书·文苑列传》可知,汉代文人使用的文体不仅有诗与赋,还有书、铭、诔、吊、赞、颂、连珠、碑、策、箴、论、笺、奏、书、令、檄、谒文等等多种,每种都有明确的体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末蔡邕的《独断》里,不仅把天子号令群臣与群臣上奏天子之文各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和“章”、“奏”、“表”、“驳”四类,而且对上述文体的性质以及基本写作要求都做了细致的说明。
可见,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并不是他的提倡和发明,不过是对汉人各种文章体裁风格与创作实践认识的一般性的简要总结而已。
其三,汉人已经“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这一点,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司马相如关于作赋的论述外,其他赋家的创作也莫不如是,如扬雄在《解嘲》中自言“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
”史称张衡作《二京赋》就是“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可见,即便是以袁行霈关于文学自觉说的三个标志来衡量,汉代文学也已经完全达到“自觉”了。
如果说中国文学有一个自觉时代的起点,这个起点也应该是在汉代,而不应该是在魏晋。
三、对曹丕《典论·论文》的重新理解与评价考察“魏晋文学自觉说”的缘起,总是与人们对于曹丕的《典论·论文》的理解相关。
铃木、鲁迅、李泽厚等人之所以把它看作是魏晋文学自觉的标志,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曹丕在这里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说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重文学的价值;第二,曹丕又说过“诗赋欲丽”的话,说明魏晋人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文体区分意识和对文学审美特点的认识。
下面我们就在重读文本的基础上,分别讨论这两句话的意义。
(一)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所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指以诗赋为主的“文学”吗?不是,而是“文章”。
在曹丕所列出的八种文体中,在今天我们看来真正属于“文学”的诗赋两类,被曹丕排在了最后,可见他对“文学”的真正态度。
在曹丕的眼中,真正能够让人不朽的是可以“成一家之言”的论说文。
他在对建安七子进行评价时,没有认为在我们今天看来写出了《七哀诗》和《登楼赋》这样高水平的文学作品的王粲不朽,而是认为只有写出了《中论》的徐干才会不朽。
由此看来,把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看成是他对“文学”自身价值的重视,显然是对曹丕《典论·论文》的一种误读。
其实,把“文章”看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由来已久,这句话最早来自于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叔孙豹的“三不朽”之说。
它是春秋以来士大夫人生价值观的基本追求,并被汉人继承了下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就是对叔孙豹“三不朽”观点的继承,也是司马迁追求立言不朽的最好说明。
扬雄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观点。
曹丕的《典论·论文》基本继承了司马迁和扬雄的思想,而且,司马迁、扬雄所说的文章不朽都不是专指论说之文,而是指包括诗赋在内的广义的文章。
在这一点上,曹丕的观点不但没有比司马迁、扬雄二人进步,反倒有些落后。
(二)“诗赋欲丽”的观点是曹丕首先提出来的吗?也不是。
鲁迅说:“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
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又说:“华丽即曹丕的主张”。
鲁迅把“华丽”看成是曹丕的提倡,这是错误的,当今的研究者已经从汉赋的研究中作了很好的证明。
追求华丽的辞藻是汉赋写作的基本特征。
我们看汉人对于诗赋的评价,基本上都要提到“丽”字。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说:“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喻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关于汉赋的“丽”的特征,连当时的皇帝汉宣帝也看出来了,他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
”由此可见,鲁迅说汉文华丽是曹丕的提倡,显然是错误的。
由此可见,把曹丕的《典论·论文》看成是“魏晋文学自觉”的标志是不妥的。
四、“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的关系“魏晋文学自觉说”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从魏晋开始,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在魏晋以前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基本都是功利主义的,而魏晋以后则开始追求艺术自身的美。
功利主义真的与艺术审美不相兼容吗?我们从两方面展开讨论。
(一)如何看待先秦两汉时期功利主义文学观的问题很明显,站在“魏晋文学自觉说”的立场上,从铃木虎雄到李泽厚,对于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或者说经学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它们影响或者阻碍了中国文学自觉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