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与东方学
《东方学绪论》

二
我的出发点乃下面这样一种假定: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它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正如西方也并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一样。我们必须对维柯(6)的精彩观点——人的历史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他所知的是他已做的——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且将其扩展到地理的领域: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因此,这两个地理实体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对方的。
东方学的含义一直摇摆于其学术含义与上述或多或少出自想像的含义二者之间,18世纪晚期以来,这两种含义之间存正着明显的、小心翼翼的——也许甚至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交合。接下来我要谈的是东方学的第三个含义,与前面两个含义相比,这一含义更多地是从历史的和物质的角度进行界定的。如果将18世纪晚期作为对其进行粗略界定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我发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和《规约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中所描述的话语(discourse)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像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而且,由于东方学占据着如此权威的位置,我相信没有哪个书写、思考或实际影响东方的人可以不考虑东方学对其思想和行动的制约。简言之,正是由于东方学,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这并不是说东方学单方面地决定着有关东方的话语,而是说每当“东方”这一特殊的实体出现问题时,与其发生牵连的整个关系网络都不可避免地会被激活。本书力图显明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同时也力图表明,欧洲文化是如何从作为一种替代物甚至是一种潜在自我的东方获得其力量和自我身份的。
东方主义名词解释

东方主义名词解释东方主义则是东方学研究的概念衍生,20世纪以来,用东方主义形容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有负面意思的,大意是指该研究者抱着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态度来理解东方世界,又指外来人,主要是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及人文带有偏见的理解。
简言之就是,东方主义是指西方人在研究过程中对东方文化的偏见性的思维方式。
“对于欧洲而言,东方既不是欧洲的纯粹虚构或幻想,也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种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漫长历史积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
”这一对萨义德观点的总结,恰如其分地表述了东方主义的实质内容。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方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
并且,这种建构及论述,与那些国家的真实面貌几乎毫无关系。
这就是说,西方人自己自我构建了一个面目全非的、甚至本来可能不存在的东方,用来区别自我与他者。
关于东西方的分界线的争议一直存在,众说纷纭从来没有定论。
有人简单地认为欧亚分界线就是东西方的分界线,有的人认为铁幕是东西方分界线,还有的人认为阿富汗以西是西方,有人认为伊朗以西是西方,欧洲更有人认为希腊是东方。
国人一般觉得日本是西方的一部分。
有些国家自己也陷入了糊涂,俄罗斯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东还是西,搞出了不伦不类的“欧亚主义”,土耳其、高加索三国等处于欧亚交界线上的国家无一不对这一身份认同无比纠结,成为无所适从、两面不讨好的国家,德国内部甚至产生了“国内边界”,一个国家分属两个阵营长达数十年之久。
究竟什么是东方?什么是西方?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不太明白。
只是当国际矛盾风起云涌,各国纷纷选边站队时,大家才能明显地感受到:东西方确实存在,而且存在矛盾,只是边界不甚清晰。
那么如果一定要分出来,恐怕只有西方有较为明确的边界,至少可以让西方人自己确定自己的边界,西方人从心底里愿意认同谁,谁就是西方,反之就不是。
东方来自于西方人的自我构建,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整体,西方人说谁是东方谁就必须是东方,落后国家没有选择西方确实存在,美国、加拿大是西方,英国毫无疑问是西方,英国的邻国,法国、荷兰、北欧各国,也应该属于西方。
东方主义 PPT课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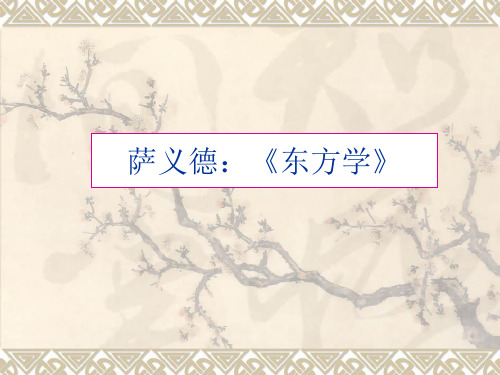
东方主义是西方社会人为建构起来的一套强势
符号体系,这套符号体系成为一种过滤框架,东方 即通过此框架被过滤后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
这套符号体系的基本信条有:A、理性、发达、 人道、高级的西方,与离经叛道、不发达、低级的 东方之间绝对的、系统的差异。B、对东方的抽象 概括,特别是那些以代表着“古典东方”文明的文 本为基础的概括,总是比来自现代东方社会的直接 经验更有效。C、东方永恒如一,始终不变,没有 能力界定自己;因此人们假定,一套从西方的角度 描述东方的高度概括和系统的词汇必不可少,甚至 有着科学的“客观性”。D、归根到底,东方要么 是给西方带来威胁,要么是为西方所控制。
《无间道风云》
香港拍的《无间道》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当年可算 是席卷整个东亚,由于出色的剧情和成功的演绎, 吸引的好莱坞的目光。时代华纳斥资170万美元将 《无间道》的版权买断,翻拍成了《无间道风云》
剧情大体上没什么改变,就是韩琛和泰国老板交易 白粉的那段有所改变。竟然是中国政府和当地黑社 会勾结,准备为解放军购买美国被盗的电子芯片, 这些芯片会被用于攻打台湾的导弹上
美国女特工在山西挖煤 |
2013年10月22日 11:11财讯.COM
/wkp/20131022-CX03c6t1.html
微博认证为“环球网美国记者站”的微博截图爆料, 美剧《神盾局特工》第一季第四集上演雷人桥段, 一位西装革履的调查人员,正在向一位黑人女子询 问着什么,女子说:“醒来时在什么伤员验伤分类 处,然后自己在一个铜矿下面的牢房里过了四 年……”那位调查人员马上试探着问,“有消息说你 被带去了山西省”。该微博调侃,“有一女特工任 务失手结果神秘失踪了很多年,经过组织调查原来 是被抓到山西挖矿了……美帝的编剧你们够 了!!!”还有网友继续接力调侃,“其实她原来 是个白人,挖了四年煤染黑了。”
东方学

基于《东方学》理论的阐述和探索——萨义德方法论和思想论的探讨【摘要】: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中重新审视了西方在处理和对待东方问题时所依仗和运用的经验主义方式,以一种特殊的、偏离事实但又成为系统的方法协调东方事物的内容在西方世界里的呈现角度,他把这一系列理论概括为东方学(Orientalism,或译作东方主义)。
本文基于这本理论著作,试图将其理论系统化整合,探索萨义德的理论思想和具体的理论实践方法。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话语一、概念的确立对于Orientalism的具体含义,萨义德本身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
”1从这一点表述上我们不难发现,Orientalism首先是一个介于方法论范畴的用语,是一种欧洲人在表述东方、描绘东方时既存的先见。
萨义德显然对此定义仍然不满意,因为根据既有的事实表明,Orientalism并不能简简单单地被概念化,因为它至少含有多重角度被解读发挥的可能性,而这一点在整部理论著作中将会随着语境和运用的需要不停地发生更迭。
它可以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的含义”2。
在西方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体系中,东方被列为能够被普遍认识的客观实存,作为一种知识存在。
在19世纪的西方学科建制中,东方学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一起被列入社会科学的范畴,成为了被了解、被表述、被认识的对象。
这里所能透露出的信息有三点:Orientalism作为被描述的学术研究对象存在;西方世界在表述,东方世界在被表述;话语的权柄在西方。
这似乎为萨义德之后的理论展开和辩驳提供了素材,同样的,这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确立的基础。
Orientalism也可以是“一种思维方式”3,或者更为确凿地去限定,它是一种西方人、欧洲人的思维方式。
不止于民众,包括“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行政官员”在“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说”将Orientalism作为他们的出发点和基准点,并且用以作为评判的方式和依据。
萨义德“东方主义”的理论来源及其不足

思想理论研究萨义德"东方主##的理论来源及其不足郑大伟张孟雪(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南232001)摘要:爱德华・W•萨义德是近几十年来世界上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是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
他于1978年出版《东方主义》,这本书被视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开山之作,成为风靡文学批评界的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发e之作。
本文从萨义德生平简介、“东方主义”吸收的理论、“东方主义”的研究内容与意义和不足之处四个层面,对《东方主义》进行解读,正确认识西方眼中的“东方”,同时进行东方反省,以寻求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和求同存异之道。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萨义德“东方主义”一、萨义德及其“东方主义”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Said)是二十世纪著名的文学、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他出生于巴勒斯坦,身上带有浓厚的巴勒斯坦文化传统。
他早年在开罗的西方殖民学校接受英国式教育,后又到美国一流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1963年入职哥伦比亚大学后,职称快速提升,最终成为在多个领域都享有声望的教授,学术生涯可谓一,成:著。
,萨义德是一有名的,他在国上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持续发声,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民的和解放事业,巴勒斯坦的&萨义德的出生——巴勒斯坦的,1922年于英国的殖民统&1947年,国巴勒斯坦一为二,&1947年年,巴勒斯坦内部的和武装冲突迫使萨义德一家他,移民开罗&1948年国对英国的授权终止,国,的是年,成上万的巴勒斯坦地区&西方国大,家园的,但巴勒斯坦称为“事件”&在萨义德的生,为一个出生于第世,成、成名在第一世的,家受的和他国的教育与培养造了他“流亡者”的身份和精神落差感,他深深验到了东西方间的复杂关系&,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生活给予他“跨”研究的储备和思维视角,种复杂的身份使他可用边缘话语面心权力话语,创了大量超出学院派范围的文化批判品&因此,《东方主义》(或称《东方学》)品面世之后能够在东西方学术界和其他领域引起大的关注,萨义德的生贡献了基础的思维和研究视角&二、“东方主义”的基本内容萨义德认为一种话语系统,实际上就是一种紧密结合的系统和力系统&在《东方主义》中,他指明了东方主义的三层含义:东方主义是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理论出发点是假定东方这一概念是为构的,东方主义是一种被为创造出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是西方对东方及当代命运的表述,东方(the Orient)是与西方(the Occident)相对而言的&萨义德认为,这种所谓的“东方主义”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的,是和“国语”的理论基础&他“话语一权力”结构到了主国、、文化念边缘国文化明的二元,种虚构出了一个西方眼的“东方”,用东西方之间的比彰显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先,是“东方主义”作为西方东方设定出的的意义&,东方主义第一层含义是东方主义其他学科一是一门学科、一学,是西方关于东方和东方的一学科和学&是最表层的学术层面的含义,含西方学者于这一域的和;第二层含义是是一种思维方式,是西方东方思、认、判的思维方式,话语东西方开来&东方在“东方主义”里并不是现实,只是西方人的建构——“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的"(萨义德,1999)-与前两种含义比,第三种含义最能东方主义的,东方主义为一种力话语或文化,西方此优话语和用实文化,出力的在隐秘关系&层含义可出,东方主义了西方东方的有认,是一种构出的了西方和优越感的话语,是东方主义的&另外,东方主义的层含义,萨义德一方面了东方的,了东方主义的,一方面东方主义为东方主义和隐性东方主义个方面,其有了深入的研究&发展来看,东方主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十世纪到第一世大,在一,业命后,英成为世上个最强大的西方国家&为了的利益,他们在世界各地扩展殖民地,几乎控制了大半个地球。
从“东方”到《东方学》

从“东方”到《东方学》萨义德的《东方学》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开山之作。
该书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东方学研究方法,而是另辟蹊径,将东方学作为一种殖民话语进行批判式的分析,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开启了一种新的文化研究领域,确立了一种新的话语系统。
可以说,《东方学》这本书是萨义德对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一次最有力的批判。
仔细阅读和研究本书,不仅可以对东方学研究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清晰的认识,也可以为当今后殖民主义时期的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找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标签:萨义德;《东方学》;后殖民主义;比较文学60年代末,新左派运动骤然兴起,萨义德所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这场论战中首当其冲。
随后的70年代,萨义德带头在美国比较文学界推进知识考古,并以一部《东方学》大爆冷门,树立起后殖民批评典范①。
分析他之所以成功的原因,离不开他所运用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欧洲左派的批判思想。
通过这种方式,他将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文化历史现象处理为一种与现实的人的活动内在相关的东西,从而将文化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话语系统。
一、引言:萨义德眼中的“东方”与《东方学》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英文名为Edward Waefie Said,1935年11月1日~2003年9月24日),生于耶路撒冷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英国圣公会)家庭。
家境优越,他的童年在埃及开罗度过,儿时就读于西方人办的学校接受西式教育。
195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学位,1960年和1964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自1963年以后,一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为该校英文和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Parr Professor),也曾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
萨义德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阿拉伯语和法语。
他还是一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音乐的造诣非浅。
萨义德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主要包括《康拉德和传记小说》(1966)、《东方学》(1979)、《巴勒斯坦问题》(1979)、《关于伊斯兰》(1981)、《世界、文本和批评家》(1983)、《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等。
浅析萨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是如何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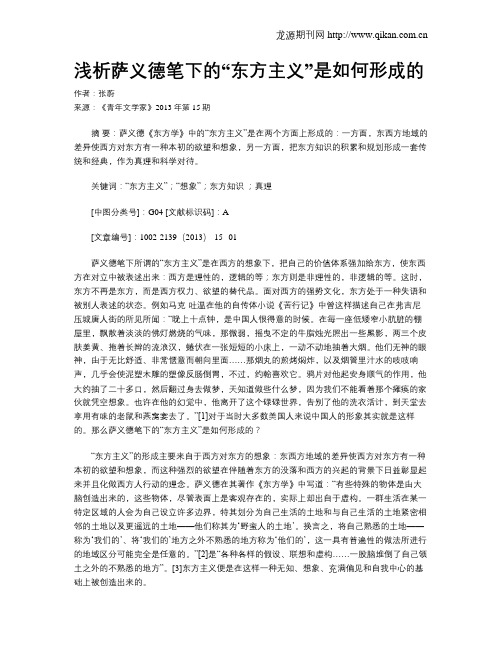
浅析萨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是如何形成的作者:张蔚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15期摘要:萨义德《东方学》中的“东方主义”是在两个方面上形成的:一方面,东西方地域的差异使西方对东方有一种本初的欲望和想象,另一方面,把东方知识的积累和规划形成一套传统和经典,作为真理和科学对待。
关键词:“东方主义”;“想象”;东方知识;真理[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5--01萨义德笔下所谓的“东方主义”是在西方的想象下,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给东方,使东西方在对立中被表述出来:西方是理性的,逻辑的等;东方则是非理性的,非逻辑的等。
这时,东方不再是东方,而是西方权力、欲望的替代品。
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东方处于一种失语和被别人表述的状态。
例如马克·吐温在他的自传体小说《苦行记》中曾这样描述自己在弗吉尼压城唐人街的所见所闻:“晚上十点钟,是中国人很得意的时候。
在每一座低矮窄小肮脏的棚屋里,飘散着淡淡的佛灯燃烧的气味,那微弱,摇曳不定的牛脂烛光照出一些黑影,两三个皮肤姜黄、拖着长辫的流浪汉,蜷伏在一张短短的小床上,一动不动地抽着大烟。
他们无神的眼神,由于无比舒适、非常惬意而朝向里面……那烟丸的煎烤焖炸,以及烟管里汁水的吱吱响声,几乎会使泥塑木雕的塑像反肠倒胃,不过,约翰喜欢它。
鸦片对他起安身顺气的作用,他大约抽了二十多口,然后翻过身去做梦,天知道做些什么梦,因为我们不能看着那个瘫痪的家伙就凭空想象。
也许在他的幻觉中,他离开了这个碌碌世界,告别了他的洗衣活计,到天堂去享用有味的老鼠和燕窝宴去了。
”[1]对于当时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中国人的形象其实就是这样的。
那么萨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是如何形成的?“东方主义”的形成主要来自于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东西方地域的差异使西方对东方有一种本初的欲望和想象,而这种强烈的欲望在伴随着东方的没落和西方的兴起的背景下日益彰显起来并且化做西方人行动的理念。
萨义德_东方学_的文化启示意义

萨义德_东方学_的文化启示意义萨义德《东方学》的文化启示意义摘要:爱德华?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对东方主义予以阐释、批判和观照,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
在萨义德看来,东方主义不仅是一门学科研究、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霸权话语垄断,最终成为西方列强和文化霸权主义行动的理论借口。
他通过《东方学》阐释了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东方及东方主义概念。
他的理论洞见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文化启示意义。
真正的东方文化,是东方民族创造的,必须由东方人来言说、来表达,我们应创立客观的真实的新东方主义。
中国论文网/doc/3517184713.html/7/view-2248875.htm关键词:萨义德;东方学;东方主义;文化特征;他者;美学意义萨义德(1935-2003),美籍巴勒斯坦人。
早年在耶路撒冷和开罗的法文和英文学校接受教育,1954年赴美,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获博士学位。
他通晓九种语言,虽然接受西方精英教育,却念念不忘东方文明,他还是巴解组织的盟友。
萨义德身有阿拉伯血统却为基督教徙,身为巴勒斯坦人却持美国护照,他始终拿不定自己的母语是阿拉伯语还是英语,这一切都让他无论置身何处,均有格格不入之感,是个永远的局外人。
20世纪70年代他潜心研究福柯,1978年出版了《东方学》,引起极大反响,是70年代末美国左倾文化批评的代表。
一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对作为后殖民理论的一个主要批判对象和观照客体的东方主义予以批判和观照,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
在萨义德看来,东方主义不仅是一门学科研究、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霸权话语垄断,最终成为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存在的理论借口。
在中国学界,“Orientalism”一词以往习惯上译为“东方主义”。
在萨义德的阐述中,“Orientalism”有其三个方面(学术研究学科、思维方式、权力话语方式)的含义,“东方主义”是其三种含义之一,是从作为学术研究学科的“东方学”中引申出来的含义。
萨义德《东方学》之争与中国的“理论东方学”

萨义德《东方学》之争与中国的“理论东方学”萨义德《东方学》之争与中国的“理论东方学”摘要:中国学界曾就萨义德的《Orientalism》究竟应该译为《东方学》《东方主义》还是《东方观》做过探讨与论争,译名之争集中反映了对这部书的内容与性质的理解,触及了“理论东方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问题。
中国学者指出萨义德以中东代“东方”,论题与中国颇有违和,由此涉及到“东方”的范围、东西方文化身份与两种“东方主义”的问题;另有学者受其学术方法的启发,认为西方汉学作为“东方学”之组成部分同样具有“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并提出“汉学主义”概念来评价西方汉学,又引发一些学者从“国外汉学”学科价值论的角度提出反驳。
从“理论东方学”的角度看,这场持续了30多年的探讨与论争,作为中国学术史仅有的一次关于“东方学”学科范围、性质、价值判断等理论问题的论辩,具有一定的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萨义德;东方学;东方观;汉学主义;理论东方学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XX)01-0098-08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发轫于20世纪初,如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但学者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而对东方学的学科理论,即“理论东方学”问题不甚措意。
对于东方学是一门什么学问,学科的由来,学科对象与学术方法是什么,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是什么等问题,还未能做系统深入的思考。
而且,即便是西方和日本,较之研究实践而言,东方学学科理论建构也一直较为薄弱。
直到1990年代中期,當欧美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被译介到中国,特别是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萨义德(一译“赛义德”)的《Orientalism》翻译出版后,关于“东方学”学科理论问题才由此引起学界讨论。
萨义德的这部书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著作,学者们看法不同。
研究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者,主要把它看做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著作;研究国家政治的人,主要把它视为国际政治学著作。
文本虚构与历史解构:东方主义系谱学分析——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中心

后殖 民主义① 是后 现 代 主义 之 后 , 方 兴起 又 西
一
解 构 的关 联 。
通 过历 史 的文本化 , 后殖 民主 义对历 史学 进行釜 底 抽 薪 的批判 。 那 么 , 殖 民主义 主 要 在 哪些 方 面 ④ 后 对 历史 学进 行批 判 性反 思 呢?最 终 能 否实 现 东 西
柯对系谱学是这样定义 : 即福柯——引者注 ) 谓 的系谱学既是 那些作 我( 所 为事件 的话语 的理 由也是 目标 , 我所试 图显示 的是 那些论述 事件如何 以一
种特定 的方式规定 了构成我们现在的东西 , 规定 了构成我们 自己( 包括我们
的知识 , 我们的实 践, 我们 的理性 类型 , 我们 与我 们 自己 、 与他 人 的关 系 ) 系谱学是分析 的最终结果 。
… …
③ 参见王岳川著 《 后殖 民主义与新历史 主义文论 》 山东教 育出版社 , 19 年 出版 , 16页 。作者指出 : 史主义诞 生以后 , 99 第 5 新历 彻底颠 覆了关 于 “ 历史与人” 的一些古老的命题 ……在“ 文本 的历史性 ” 历 史 的文本 性” 与“ 上受到了当代文化 的关注 。 ④ 虽然后现代 主义也是借鉴福柯知识 与权 力关系理论来 否定历史事
文本 虚构 与历史本质
历 史是什 么 ?这 是 古往 今 来 历 史 学家 孜 孜 以 求 的问题 。卡 尔 曾说 : 历 史 学 家在 不 断地 问 ‘ “ 为 什么 ’ 这个 问题 , 且 只 要 他 一 直 希 望 得 到 答 案 , 而 他便 不能 休 息 。 _对 于历 史 的定 义 , 学 家 们 的 ”2 史 见解也 不 甚 相 同 。关 于 “ 史 是 什 么? 的论 著 也 历 ”
东方主义介绍2010.4.1

东方主义是西方对近、中及远东社会文化、语言及人文的研究。
它亦可意为西方作家、设计师及艺术家对东方的模仿及描以东方主义形容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有负面意思的,在“西方”的知识、制度和政治/经济政策中,长期积累的那种将“东方”假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思维。
在一些激进作品中,东方甚至被认为是西方的对立面;即将所谓的“他们”(They)表现们”(Us)的反面。
对东方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莫过于爱德华·萨义德[1],他用福柯的话语概念考察了东方主义,并试图阐明权通过话语起作用、权利如何产生认识,以及关于“东方”的认识本身如何表现了社会权利关系。
近古以前欧洲人所说的东方主义中的东方,指亚洲等地,包括欧洲人所指的近东、中东、远东地区,甚至包括俄罗斯和原来的东罗马中国称东方文化圈则指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圈。
而在当代英语中,东方(Oriental)一词狭义上也主要指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区,不包括印度、西亚等地区,比以前所指的范围小。
持偏见态度的人被认为是时常有意无意地抱着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态度来理解东方世界,又或对东方文化及人文的旧式及带有偏见的理解。
东方主义的描述性表达无一例外地将地中海以东各国家社会的多种生活进行了对象化、本质化和刻板印象的方式处理。
对立化的表现有:1.敌视(the xenophobic):专注于他者的威胁性和可憎性(如暴君、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等,东方男性成为堕落无耻且被妖魔化的对象)。
2.异域(the xenophilic):关注他者具有吸引力的一面(如闺房、面纱、艺妓等,东方女性被描绘成为放荡、被动且颇具异域风情)。
萨义德与东方主义萨义德于1978年在他富争议的名著《东方主义》里清晰表达并宣扬了这个观点,批评这种学术传统以及一些现代学者,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Bernard Lewis教授,和文明冲突论学者,耶鲁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博士。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而在法国和英国要让东方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埃及、印度成为殖民地的时候,这种思想形态便在政治上有利用价值。
东方学ppt

Orientalism
发展阶段: 1、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16 世纪末~18世纪是 东方学的酝酿阶段。欧洲商人、传教士和探险的人 员编写的关于东方各国的记载。《马可波罗行纪》 2、 19世纪是东方学的确立时期。标志——各国东 方学研究组织的建立和国际东方学会议的召开。 3、20世纪繁荣时期。东方国家的学者加入东方学的 研究队伍,以有别于西方的东方学视角来描述东方。
东方的东方学
Orientalism
西方的东方学是伴随着西方对东方 的殖民而产生的,为殖民统治服务。 “Orientalism” 本质性的含义是西方 人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
Orientalism
Orientalism
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 为东西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 西方文化的优越性。
他们认为的中国美女
东方学视角下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
——以《喜福会》为例 《谍中谍3》
东方学家对东方的本质论观念通过种族类型 学表达自身,并走向种族主义、 霸权主义、 欧洲中心主义
东方主义的核心就是欧洲中心主义
傅满洲——曾经的中国形象代言人
傅满洲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 罗默创 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 傅满洲是一个又高又瘦,面容 如同 撒旦,穿着清朝官服的邪恶博士,号称 世上最邪恶的角色。他也应该是文艺作 品中第一个”邪恶科学家”。他对抗的 是像福尔摩斯一样的白人警探 Denis Smith。在作品里,警探和傅满洲的对 抗通常靠的都是意志而不是智慧。他创 造了很多酷刑来对抗警探。作者要塑造 一种黄种人如此聪明而且邪恶,善良单 纯的白人只能用最痛苦的方法和他们对 抗的感觉。 傅满洲的系列在1920年代的美国取 得很大成功,后来有超多的文学影视作 品都以傅满洲为原本进行人物创作。
萨义德《东方主义》思想探析

萨义德《东方主义》思想探析马元雄【摘要】摘要:东方学蕴含着丰富的沉积了几个世纪的物质层面的内涵。
东方概念是一个源于语言,经过历史演绎而逐渐复杂化的建构物。
东方主义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学科,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是通过与政治、文化、道德、知识等权力的交换而形成的话语方式。
【期刊名称】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00)013【总页数】3【关键词】东方主义;权力话语;建构《东方主义》(或译为《东方学》)直接开创了一个新的即关于后殖民研究的领域,在后殖民研究领域处于中心地位,取得了很高的认可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了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也被看作是当代帝国研究的标志性著作。
《东方主义》运用新理论,即与某些类型的法国“高雅理论”有关的批评方法协调所得之理论,并将新理论的主要原理用于对西方文化和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来论证萨义德称为“权力的政治、考虑、地位和战略”的污染深深的存在于所有西方系统的文化描述中。
它关注的是诸如人类学、语文学等现代学科和知识体系与欧洲帝国——大英帝国以及法国的殖民扩张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东方主义》的观点和成就瓦莱丽·肯尼迪在他的著作《萨义德》中对《东方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
作为一名后殖民理论研究学者,他认为《东方主义》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不仅以新政治化和新历史化解读个体文本的形式变革了英语和比较文学研究,而且开启了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先河”。
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这两位后殖民研究的主将亦承认在萨义德《东方主义》中获益良深。
巴巴在“后殖民批评”一文中说:“《东方主义》开创了后殖民领域。
”斯皮瓦克同样用热情洋溢的词句称这本书是“我们学科的基藏读本”。
她认为,《东方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源泉”通过它“边缘性”本身从而在西方学术界获得了一个学科的地位:“对于殖民话语的研究灌溉了一个花园,在这个花园中边缘的话语可以言说被言说或为之而言说。
东方主义

一、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 一个国家运用政治与经济权力,通过 文化输出的方式对另一国进行文化侵蚀 , 使自己的文化在输入地占据主导地位,而 当地的文化被迫逐渐消失,进而更容易地 获取经济、政治利益。是一国以文化方式 达到从根本上消灭另一国文化、淡化民族 意识,从而达到更根本的政治、经济侵略 的目的。 情人节与七夕 学外语
二、《东方学》的简介 1、东方主义的含义 东方主义原文 orientalism,萨义德赋予它三个 含义: 一个学科——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 东方的人所做的事情就是东方主义,也叫东方学。 一种思维方式——将东西方进行区分,并以此 为出发点来建构有关东方的各种理论。 一种权力话语方式——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 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 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 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主义视为西方用以控制、 重建和掌握东方的一种方式。
美国女特工在山西挖煤 |
2013年10月22日 11:11财讯.COM /wkp/20131022-CX03c6t1.html
微博认证为“环球网美国记者站”的微博截图爆料, 美剧《神盾局特工》第一季第四集上演雷人桥段, 一位西装革履的调查人员,正在向一位黑人女子询 问着什么,女子说:“醒来时在什么伤员验伤分类 处,然后自己在一个铜矿下面的牢房里过了四 年……”那位调查人员马上试探着问,“有消息说你 被带去了山西省”。该微博调侃,“有一女特工任 务失手结果神秘失踪了很多年,经过组织调查原来 是被抓到山西挖矿了……美帝的编剧你们够 了!!!”还有网友继续接力调侃,“其实她原来 是个白人,挖了四年煤染黑了。”
电影:《古墓丽影2》
2003年夏天,一部好莱坞商业大片《古墓丽影
为什么总感觉西方凭空想象我们?看看萨义德“东方主义就明白了

为什么总感觉西方凭空想象我们?看看萨义德“东方主义就明白了萨义德,作了后殖民主义的奠基者,是一位美藉巴勒斯坦人,成年后接受的主要是西方教育,他对当代文化研究起到了深远影响,最为著名的便是'东方主义'理论以及与文化与帝国主义的相关论述。
中国一直饱受西方的误解与歧视,在萨义德身上,我们可以寻到那么几分真相。
话语建构的东方——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萨义德所谓的'东方'指的主要是中东地区的国家。
东方学本是西方专门研究东方、阐述东方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萨义德重新梳理了东方学的发展历史,发现了东方学者研究中的'误区',这些误区深入到西方的文化内涵之中,成为一种潜意识中的认定。
他指出所谓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界线完全是东方学者想象出来的,'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
'在《东方主义再思考》一文中,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强调:'东方和西方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事实……如果一来没有东方学家,二来没有东方人,也就不会有东方主义。
'东方本来是一个拥有着众多的民族国家代表着多样的差异化的民族文化的地区,却完全被想象为一个固定不变的他者形象,是相对于先进的文明的优越的西方而言的相反的固定模式里面。
在这个模式中,东方是落后的、粗野的、不变的、劣等的的形象,完全成为殖民体系话语的一种建构,一个只存在于西方印象中的幻影。
'东方'被'西方'创造并且被强行带入了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西方语境之中,全凭西方话语进行任意的曲解式的定义,这种行为毫无疑问带着强烈的政治性和殖民主义色彩。
'东方'被'东方化',东方的男性是软弱的女性化的,然而又对白人女性构成威胁;东方女性则是奴性的,自愿受到统治,甘受压迫而不反抗然而又与众不同,风姿奇异的形象。
东方文学参考资料

东方、东方精神、东方主义、东方学东方:方位的概念,地理概念(立足点);政治概念;文化概念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研究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历史,哲学,宗教,文学,政治,语言,经济以及其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东方精神: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敬畏与驯服);思维方式的内顺化和直觉化;人际关系的伦理化,等级化(角色意识);生活方式的克俭无争。
东方:所谓“东方”,是一个内涵丰富、可作多种诠释的复杂概念,它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东方”这个名称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亚、非两大洲的合称,它不再是狭隘的民族中心论,也突破了“东方学”中“东方”概念的凝固性和西方霸权主义,而成为世界性的共识,是在单纯的、相对的地理概念基础上,融入了历史的、政治的因素,尤其还有统一性的文化的因素,并与“西方”相对而言所作的一种划分和概括。
“东方精神”: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造成了东方人根深蒂固的王权崇拜、家长崇拜意识,还有权威主义、“官本位”思想。
“东方精神”的核心部分是强烈的宗教伦理道德观念。
东方文学:“东方文学”是“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方学”是19世纪初由欧洲人建立起来,继而在欧美获得了大的发展。
它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包括考古、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
按照国内通行的概念,东方文学是指古今亚洲和非洲文学的总体,其中埃及、巴比伦、希伯来、印度、中国、日本、波斯、阿拉伯以及朝鲜等国的文学是有代表性的东方文学。
东方文学的特质:①悠久古老的文学历史与文学传统。
②形成与发展的多源性。
③浓郁的宗教与伦理道德色彩。
④鲜明的民间文学特色。
《亡灵书》:《亡灵书》是宗教诗篇的庞大总集,其中汇编了大量的歌谣、祈祷文、颂神诗、咒语诗神话诗等,是古埃及神话传说的宝库。
它即是一部具有文学遗产价值的诗歌总集,又是一部保存了重要生活习俗的历史文献,它是宗教观念、冥事崇拜和来世思想的产物,《亡灵书》是埃及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诗歌总集之一。
萨义德《东方学》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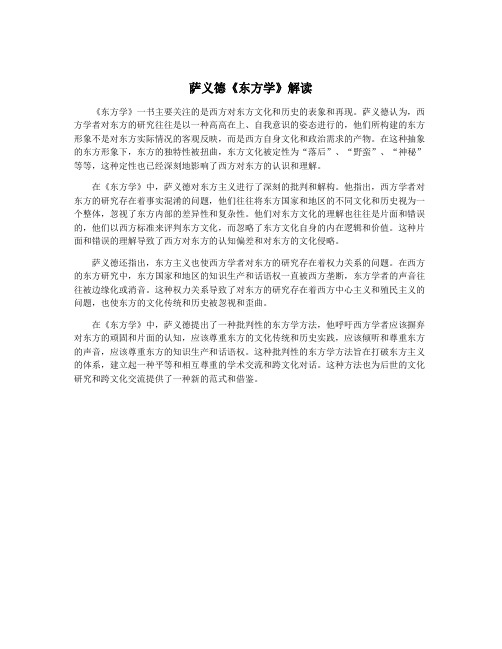
萨义德《东方学》解读
《东方学》一书主要关注的是西方对东方文化和历史的表象和再现。
萨义德认为,西方学者对东方的研究往往是以一种高高在上、自我意识的姿态进行的,他们所构建的东方形象不是对东方实际情况的客观反映,而是西方自身文化和政治需求的产物。
在这种抽象的东方形象下,东方的独特性被扭曲,东方文化被定性为“落后”、“野蛮”、“神秘”等等,这种定性也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和理解。
在《东方学》中,萨义德对东方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解构。
他指出,西方学者对东方的研究存在着事实混淆的问题,他们往往将东方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和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忽视了东方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他们对东方文化的理解也往往是片面和错误的,他们以西方标准来评判东方文化,而忽略了东方文化自身的内在逻辑和价值。
这种片面和错误的理解导致了西方对东方的认知偏差和对东方的文化侵略。
萨义德还指出,东方主义也使西方学者对东方的研究存在着权力关系的问题。
在西方的东方研究中,东方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生产和话语权一直被西方垄断,东方学者的声音往往被边缘化或消音。
这种权力关系导致了对东方的研究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也使东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被忽视和歪曲。
在《东方学》中,萨义德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东方学方法,他呼吁西方学者应该摒弃对东方的顽固和片面的认知,应该尊重东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实践,应该倾听和尊重东方的声音,应该尊重东方的知识生产和话语权。
这种批判性的东方学方法旨在打破东方主义的体系,建立起一种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学术交流和跨文化对话。
这种方法也为后世的文化研究和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和借鉴。
《东方学》演讲提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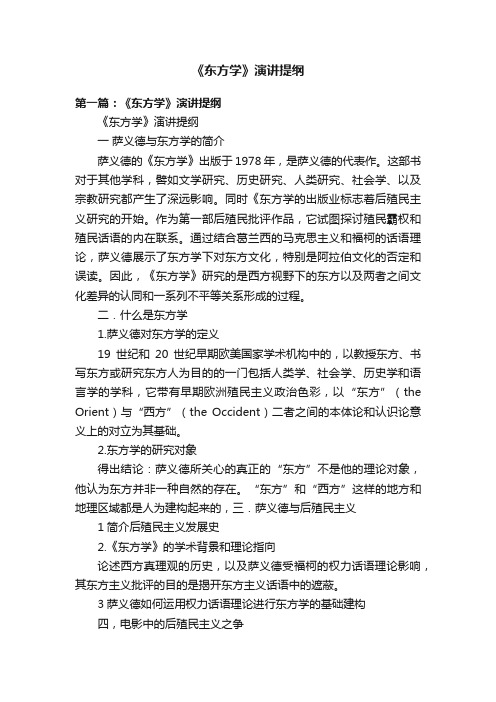
《东方学》演讲提纲第一篇:《东方学》演讲提纲《东方学》演讲提纲一萨义德与东方学的简介萨义德的《东方学》出版于1978年,是萨义德的代表作。
这部书对于其他学科,譬如文学研究、历史研究、人类研究、社会学、以及宗教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东方学的出版业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开始。
作为第一部后殖民批评作品,它试图探讨殖民霸权和殖民话语的内在联系。
通过结合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和福柯的话语理论,萨义德展示了东方学下对东方文化,特别是阿拉伯文化的否定和误读。
因此,《东方学》研究的是西方视野下的东方以及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认同和一系列不平等关系形成的过程。
二.什么是东方学1.萨义德对东方学的定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美国家学术机构中的,以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人为目的的一门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科,它带有早期欧洲殖民主义政治色彩,以“东方”(the Orient)与“西方”(the Occident)二者之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对立为其基础。
2.东方学的研究对象得出结论:萨义德所关心的真正的“东方”不是他的理论对象,他认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
“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三.萨义德与后殖民主义1简介后殖民主义发展史2.《东方学》的学术背景和理论指向论述西方真理观的历史,以及萨义德受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影响,其东方主义批评的目的是揭开东方主义话语中的遮蔽。
3萨义德如何运用权力话语理论进行东方学的基础建构四,电影中的后殖民主义之争后殖民主义认为张艺谋等人的电影为迎合西方中心主义,塑造了一个贫困荒蛮的图景,以其满足西方观众的审美期待,认同并为西方观众学者构建了一个“东方他者”的形象。
但是我认为,不能简单的用东方主义理论将这类电影贬低,因为这批电影代表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对自我文化身份和历史的一种反思和自省,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电影所匮乏的。
第二篇:东方学读后感读《东方学》内容摘要:西方和东方(更准确的说是伊斯兰东方),在地理位置上有着明显的界限,同时也有着不同的政治和历史文化传统。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编者按]本文讨论了萨义德Orientalism一书的汉译名(《东方主义》/《东方学》?)问题,所反映出的史学视野与开放性的研究思路,无疑值得研究现当代东方文学者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萨义德之书以及罗氏本文值得推荐!“东方主义”与“东方学”罗厚立民国初年曾访华并引起轰动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当时说,他眼望旗帜上飘动之流苏,便悬想到中国人的浪漫特性,进而企慕中国人的浪漫生活。
但曾经编辑《国故学讨论集》的中国人许啸天却以为,浪漫性其实“并不是什么好名词”,反是“可以叫人嘲骂、叫人鄙弃的劣等人种的贱性!”因为,“生在如今科学精神极发达的时候,一天不发明,便一天得不到进步;你若不进步,便只好坐待着别人拿物质的实力来亡你的国、灭你的种。
到那时候,且问你浪漫不浪漫?”许氏此语恐怕代表了民初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甚至包括康有为)的观念:“浪漫”与“科学精神”固然有些对立的意谓,更重要的是,没有“物质的实力”,浪漫即由奢侈变为低劣的代称,带有挖苦的意思了。
不管泰戈尔悬想的中国人的特性和生活是否符合实际,他的原意当然是说好话;又不论他是真有此想,还是特意找出点什么来礼节性地奉承,其出于善意应无疑问。
然而许啸天却读出了嘲骂和鄙弃的言外之意。
这真有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意味。
“反求诸己”固然是清季以还许多中国士人的共相,许氏的联想仍不免体现出一种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因而也提供了探讨“东方主义”之微妙复杂的例证。
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最重要的核心观念即剖析建立在东西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人我之别(Other &/vs Self),但“东方”’和“西方”对不同的具体对象其实可以有许多层次的含义,这是萨义德所不曾讨论的中国情形给我们的启发。
对民初的多数中国读书人来说,他其实是作为“西方象征”或“西方代表”而来到中国的(若是亡国代表断无“资格”挖苦中国人);这很有点类似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勒斯坦裔教授萨义德,他自己觉得在美国社会中仍是个“他人’(the other),如今却以西学正宗的“东方主义”观念风靡了中国士林(若从一般市井之见看,能做常春藤大学的讲座教授,绝对已融入美国社会主流,但萨义德所重却不止此,这是许多称引他的言论者所可注意的)。
本来“东方主义”是揭露和批判西方帝国主义者用他们的眼光加诸被侵略和被殖民地区之人民,但近代中国从梁启超起的许多趋新学者却正好相反,他们并不认为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历史文化是错的,反而认为用西方眼光或学习西人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甚或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中国问题都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他们自觉并反复强调其胜过昔人之处。
近代中国当然也有将西方“他人化”的西方主义倾向存在(我们本有夷夏之辨这一本土思想武器),但中国士人主动投入西方“文化霸权’之下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仍极为明显,且更居主流、持续得更长久。
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许多学者都毫不犹豫地标举自己研究问题的“新眼光”,虽名之以带普世性的“科学”却并不讳言是西来的。
这个问题拟另文专论,下面仅稍作简述。
前些年许多号称继承“五四”精神的学人说要将传统“创造转化”,不知“五四”人正要将传统送进博物院,不许其在新时代里延续。
顾颉刚晚年论其古史研究的意义说:“我们现在的革命工作,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
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
换句话说,我要把家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
”此文写在“文革”结束后不久,虽有点特意从“革命工作”的角度诠释古史辨的时代特征,但基本观念是符合他的一贯思想的。
强调“现代”与“古代”的根本不相容的确是“五四”人的学术观念,毛子水在一九一九年强调“我们是我们——是现在时候的人,古人是古人——是古代的人”。
他明确提出学术研究的“正当”与“合法”问题说:“要达到究竟的真理,须照着正当的轨道;但是中国过去的学者,就全体讲起来,还没有走入这个正当的轨道。
”毛以为,现在“研究学术,应当研究合法的学术。
因为研究学术的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广义的科学——就是合法的学术。
因此,我们现在要研究学术,便应当从研究现代的科学入手。
”而中国的国故则“不是研究学术的最正当的法门”,因其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所以“不能算得合法的学术”。
正因为如此,毛子水不能同意“国故和‘欧化’(欧洲现代的学术思想)为对等的名词”,甚至不承认其为“世界上学术界里争霸争王的两个东西”(这正凸显了对待“国故”的态度其实与清季人开始关注的中西“学战”相关)。
盖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看,“国故是过去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知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
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
”他进而提出“国新”即“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学术思想”这一概念;并明确指出:如果“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学术思想的程度同欧洲人的一样,这个‘国新’就和欧化一样。
这个和欧化一样的‘国新’,无论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或从欧化里面吸收来的,都是正当的。
”因为“学术思想并不是欧洲人专有的,所以‘国新’不妨和欧化雷同”。
最后一点颇有深意,毛子水虽然先存“欧化”才“正当”的观念,却又秉持“学术是天下古今的公器”这样一种超人超国的观念。
“天下”是旧词,时人说得更顺口的是“世界”。
这样,新文化人就通过引入一个新的范畴“世界”而赋予传统与现代的两分以新的含义,他们对“世界”的定位与今日是不甚相同的:世界代表“新”的未来,而中国则象征着“旧”员(其实内心自己不认为平等,故中国仍要全面向西方学习)。
与此相应的是“世界观”一词的出现,那时“世界观”的意义并非关于世界的全局观念,实际上更多是时人所说的“人生观”的同义词或至少是近义词,这最足表现“世界”并非地理意义或全人类意义的。
美国学者李文森注意到,梁启超已开始引进新旧之分来(部分地)取代中西对立,但梁本人基本上未从中国人的立场上移位,这就是李文森所说的历史与价值之间的诡论性冲突和紧张。
这个说法曾引起不少海外华裔学者的不满,其实身为美国社会中的犹太人,李文森在这一点上的体会对理解近代中国人的心态极具启发性(巴勒斯坦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与犹太人相去太远,所以萨义德的“他人”感要强烈得多)。
在引入新概念取代中西之分这一点上,新文化人不过是继承梁启超的取向,但与梁根本不同的是,他们自动移位到“世界人”的一面,希望在“世界人”的认同范畴里尽量容纳“中国人”,在“世界学术”的范畴里包容“中国学术”(实即占一席之地)。
故对他们来说,李文森所说的历史与价值的冲突被进一步推向潜意识的层面,不那么显著;他们站在世界人的立场来批判中国传统也就更加理直气壮而更少犹豫。
当然,从中/西到新/旧再到世界/中国的传承性是明显的,但也的确越来越具有超人超国的特性。
故至少在意识层面,今日讨论得非常热闹的“人我之别”对民初读书人意义不大;他们当然也感受到来自西方的“东方主义”,但由于“世界”这一超人超国范畴的存在,他们可以(实际上也经常)站在常规意义上他人(Other)的立场来批判自我(Self)。
从晚清开始,中西二元对立观念本越来越得到强调(这里当然有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2“东方主义”的合力作用);但由于中国在此二元观念中处于精神和物质皆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存在一种试图摆脱这一对立的长期努力。
对清季民初的中国士人来说,“世界”概念的引入意味着中西二元对立观念的突破,而前者的确立更提示着后者的部分解体。
此后中西对立的二元观念仍然强有力,并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但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多元思维也始终存在,而且同样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述,与二元思维竞争。
马尔库塞曾批判过“单向度”(one dimensional)思维并提出“解放想像力”的口号,许多人因而倾向于“双向度”的思维(我这样讨论“向度”未必马氏原意,此仅借喻而已)。
其实如果进一步“解放想像力”,“三向度”甚而“多向度”的思维也是可以而且应该尝试的。
近来西人所谓“第三”的言说逐渐流入中国,如关于“第三文化”(《读书》一九九八年五期)和“第三条道路”(《读书》一九九九年四期)的讨论便是。
不过一般的“第三”多是在既存的二元“道路”或“文化”之外再增加一元,还不是充分的多元(已有人提出“第三”可以有许多,其实多就多,似不必一定保留或强调这个“第三”);更有将其与所谓“中间道路”相提并论者,若“中间”则仍是在二元思维模式之内了。
但不管怎么说。
这都体现出一种从二元思维模式走向多元思维的倾向。
想像力一旦得到“解放”,对许多事物便可以从多元角度理解;那些今天仍在提倡“启蒙”的读书人表面上似乎过分尊西,也正式把中国传统作为批判对象;但在他们的认知中,其思想武器“启蒙”却是“世界”的而非“西方”的。
正是第三个“向度”的世界给了他们“自我批判”(在物质人层面,民族国家这一日益受到质疑的分类系统仍然得到确认,“世界人”毕竟是一个想像的范畴,至少仍是努力实现中的范畴)的勇气和力量。
同样有意思的是,那些以“全球化”为思想武器的学人,其近日提出的关于国家民族的思考甚至具体措施上的建言反相对更倾向于“民族主义”。
这类看似“矛盾”的现象正体现出思维的多元化,因而可以从“多向度”去认识和理解,实际上这些现象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传统”以新的形式表述出来吧。
从史学的视角看,正因为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这样一种多元思维或隐或显的存在,正因为中国读书人长期具有超人超国的愿望,所以如今正在红火的“人我之别”说对近代中国特别、什么“东方主义”(以及与之对立的“西方主义”)开始盛行于国中时,我们切勿只是跟着喊口号,恐怕还是要回到以实证为基础的取向,看看时人心目的“他人”和“自我”到底如何。
这当然决非否认“东方主义”对我们的启发。
其实,跳出当年士人至为关注的中西新旧之分而从人我之别的新视角考察历史现象,的确可以带来一些前所忽略的新认识。
不过,这仍然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若将人我之别的研究思路与新文化人已有的多元思路结合起来,则对我们的研究可以有更大的启发,相信还会有更进一步也更宽阔的认识。
对后之研究者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等于开辟了一个超二元的多元分析框架。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增加一元而成三元,而是可以进一步开放的,其他因素也可引入这一分析框架之中。
最简单的一点,当女性(应当不止是“先进”的女性)的声音被认真引入我们的史学言说时,我们也许会发现,昔年读书人看重的或者不仅是妇女解放,在男性掌握“话语权势”的时空里引入女性的“话语”,是否意味着在中西、新旧等等的(男性)二元对立中出现了第三种声音,从而也就打破了二元思维而导向一种多元思维呢?从这一视角看“五四”后期提出的“模拉尔小姐”的口号,不论提倡者的初衷何在,多少总体现了一种欲与德、赛二“先生”有所区别的愿望(女性主义者甚至可能会说这一口号之所以未能流行,正因男性“话语权势”的控制力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