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是触及根源性的一种前瞻精神
【中华文化要略】第六章 道家精神

矛盾的双方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 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 相随,恒也。”(《第二章》) 矛盾双方都以其对立面为自己存 在的前提。如“曲则全,枉则直, 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 惑。”(《第22章》)
道家精神
②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 老子说:“物或损之而益,或 益之而损。”(《第42章》)楚庄 王欲封孙叔敖(《淮南子》)。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 伏。”(第58章)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 夺之,必固与之。”(第36章)
道家精神
5、至德之世
——庄子的理想国 “夫至德之世,同一禽兽居,族 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 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 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马蹄》) 比老子的“小国寡民”还倒退。
道家精神
老子是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提出了“道”作为最高的实体范畴, 用以标志世界万物产生的总根源及 其变化规律,扬弃了“天命”“以 天为宗”的世界观,提出了“反者 道之动”的辩证思想,创立了“道 法自然”的思想理论。
道家精神
崂山老君峰下的太清宫 武当山金殿 华山 青城山 泰山 都有道观宫观。
道家精神
道家精神
道家精神
三、教义
根源于道家学说。 基本教义:道、 德、玄、无为、 清静、寡欲、不 争等。
道家精神
四、儒道思想的互补
道家精神
道家精神
(第48章)。提出认识上的两种方 式。 4、小国寡民
——理想的社会形态 老子的时代,大国争霸,小国朝 不保夕。对现实失望,就向往初民 的淳厚的社会状态。
道家精神
《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有什 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 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 死,不相往来”(《第18章》)。 无为社会。原始状态与文明状 态最理想的结合。
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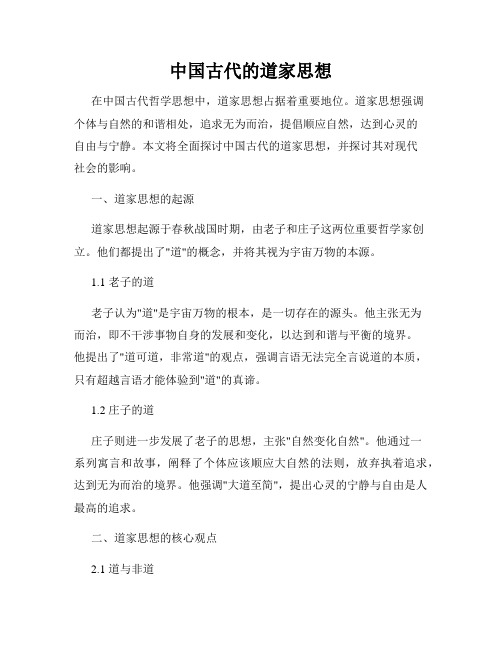
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道家思想占据着重要地位。
道家思想强调个体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无为而治,提倡顺应自然,达到心灵的自由与宁静。
本文将全面探讨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并探讨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一、道家思想的起源道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由老子和庄子这两位重要哲学家创立。
他们都提出了"道"的概念,并将其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
1.1 老子的道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是一切存在的源头。
他主张无为而治,即不干涉事物自身的发展和变化,以达到和谐与平衡的境界。
他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的观点,强调言语无法完全言说道的本质,只有超越言语才能体验到"道"的真谛。
1.2 庄子的道庄子则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主张"自然变化自然"。
他通过一系列寓言和故事,阐释了个体应该顺应大自然的法则,放弃执着追求,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他强调"大道至简",提出心灵的宁静与自由是人最高的追求。
二、道家思想的核心观点2.1 道与非道道家思想中,"道"通常是指宇宙的原则与规律,代表了一种超越言语和理性的境界。
"非道"则是指失去与违背了"道"的状态。
道家哲学强调逆境与对立统一的观点,认为"道"与"非道"、"有"与"无"互为存在。
2.2 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的重要观点之一。
它主张个体应当顺其自然,不过分干预外界,并以无为的态度去面对世界。
通过此种境界,个体可以达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实现心灵的自由。
2.3 非欲无为道家思想主张超越欲望的束缚,将个体的欲望放低到最低限度,以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它认为欲望是人类痛苦的根源,通过超越欲望可以获得内心的自由。
三、道家思想的现代影响道家思想虽然源远流长,但其思想观点对现代社会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道家思想及应用

道家思想及应用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之一,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代表者为老子和庄子。
道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道”,它代表着宇宙的本源和统一原理,是一种普遍而无束缚的力量。
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对中国社会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道家思想强调“无为而治”。
道家认为,宇宙万物都遵循自然规律,而人类的行为也应该尊重和顺应自然。
因此,庄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即人们应该摒弃过分追求权力和物质财富的欲望,放下执着和欲望,顺其自然,以达到心灵的平静和内在的和谐。
这一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应用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生活的满足,导致精神空虚和环境破坏。
倡导“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可以引导人们追求内在的平静和和谐,从而使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找到心灵的依靠。
其次,道家思想强调“自由自在”。
在道家看来,自由自在是人们真正追求的目标,在人们内在的本性中存在着一种自由和无限的潜力。
道家主张精神的自由,要求人们解放思想、开拓视野、突破束缚,以达到真正的自由状态。
这一思想对于个人的应用意义非常重要。
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在物质追求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忽略了精神自由的重要性。
倡导“自由自在”的道家思想可以帮助人们意识到内在的潜能和追求,从而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
第三,道家思想强调“无欲无求”。
道家认为,人们的欲望和追求会使人们的心灵受到束缚和煎熬,因此提出了“无欲无求”的思想。
庄子认为,心灵的平静和内在的和谐只有通过摒弃欲望和追求,放下执着的心态才能实现。
这一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过分追求物质财富和欲望的满足,经常处于追逐和焦虑的状态。
倡导“无欲无求”的道家思想可以帮助人们从物质追求中解脱出来,实现心灵的平静和幸福。
第四,道家思想强调“大同”。
道家认为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上的共通性,即“大道”。
这种共通性使得个体与世界、自然与人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通性和一体性。
道家思想相关知识点总结

道家思想相关知识点总结一、道家思想的起源和发展道家思想起源于中国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时期,由老子和莫子等人创立并发展。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奠基人,其主要著作是《道德经》,莫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著作是《莫子》。
道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家思想逐渐与儒家、墨家等其他学派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多元化和丰富性。
道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对后世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道家思想的核心理念道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道”,主张“道法自然”,强调无为而治,提倡顺应自然、追求自由、尊重自然规律。
在《道德经》中,老子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等经典论断,阐述了道家思想的主要理念。
道家思想的主要特点是返璞归真、无为而治、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等,这些理念都体现了道家思想对自然、宇宙和人性的深刻探索,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道家思想的主要观点1. 无为而治: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认为“无为而治”是一种最高的治理原则。
这并不是指不做任何事,而是指顺应自然、遵循道的规律,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
它是一种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治国理政的理念。
2. 自然无为:道家思想主张自然无为,认为“自然无为”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状态。
这并不是指自然界没有任何作为,而是指自然界运行的规律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人为干预。
它是一种让事物自然发生、顺其自然的状态。
3. 道法自然:道家思想主张道法自然,认为“道法自然”是一种至理真理。
它强调宇宙万物存在的道是一个无形的规律,顺应这个规律是追求智慧和幸福的最高理念。
4. 无为而治: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认为“无为而治”是一种最高的治理原则。
这并不是指不做任何事,而是指顺应自然、遵循道的规律,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
它是一种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治国理政的理念。
道家思想的利与弊

道家思想的利与弊 This manuscript was revised on November 28, 2020道家思想的利与弊摘要:道家思想源远流长,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思想作为百家争鸣的一支重要学派演绎自身的传奇,同时对我们后世社会发展也有很大作用。
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在历史的洪流中,统治者一般会采取儒家和法家的治国思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外儒内法”,而道家思想一直被放在若即若离的位置,在现实生活中道家的作用也被大家忽略了。
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源之一的道家文化虽然有其时代的固有弊端,但是在很多方面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
在道家学派看来,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最理想的状态,因此道家把道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
道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独立于物质世界,是物质世界的本原。
道可以用于区分自然界万物的良否和判断人类社会生活的善恶,认识了道就可以认识世界万物。
道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有着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曾经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思想家,比如说老子、关尹、列御寇、庄周。
学习道家的思想有利于我们了解道家思想的利与弊,从而我们可以吸取其中的精华,应用到实践中去。
在政治理想方面,道家的思想家们把小国寡民作为理想社会,把“道”或“至德”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境界,把原始、蒙昧、与自然为一的状态作为社会理想。
他们用倒退的观念理解人类历史,带有浓重的复古倾向,否定了人类社会生活的群体性特征,轻视人类社会的伦理原则和价值标准,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相违背,但是他们的观点体现了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揭示了人与人质之间利害冲突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敢于批判敢于否定,勇敢批判现实,改变现实。
在政治主张方面,道家提倡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不尚贤使民不争;第二,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第三,绝圣齐贤,绝仁弃义;第四,慎征罚。
道家认为如果不尚贤就可以制止社会纷争,他们虽然想制止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但是他们错误的理解了尚贤与争之间的关系,尚贤并不是社会纷争的根源,不尚贤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社会纷争。
道家的基本思想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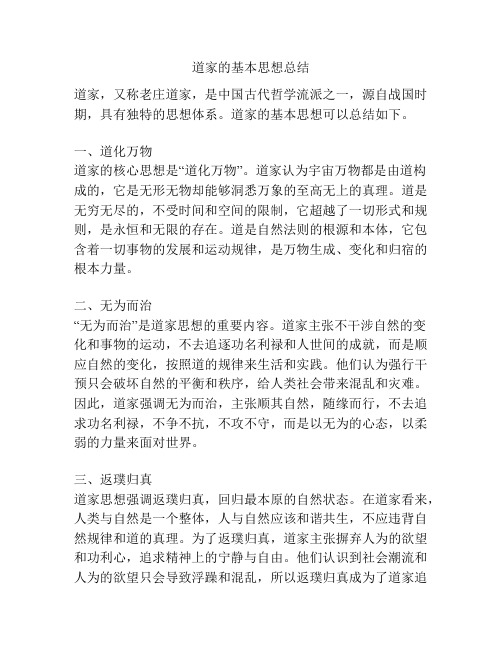
道家的基本思想总结道家,又称老庄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之一,源自战国时期,具有独特的思想体系。
道家的基本思想可以总结如下。
一、道化万物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化万物”。
道家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道构成的,它是无形无物却能够洞悉万象的至高无上的真理。
道是无穷无尽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超越了一切形式和规则,是永恒和无限的存在。
道是自然法则的根源和本体,它包含着一切事物的发展和运动规律,是万物生成、变化和归宿的根本力量。
二、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道家主张不干涉自然的变化和事物的运动,不去追逐功名利禄和人世间的成就,而是顺应自然的变化,按照道的规律来生活和实践。
他们认为强行干预只会破坏自然的平衡和秩序,给人类社会带来混乱和灾难。
因此,道家强调无为而治,主张顺其自然,随缘而行,不去追求功名利禄,不争不抗,不攻不守,而是以无为的心态,以柔弱的力量来面对世界。
三、返璞归真道家思想强调返璞归真,回归最本原的自然状态。
在道家看来,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生,不应违背自然规律和道的真理。
为了返璞归真,道家主张摒弃人为的欲望和功利心,追求精神上的宁静与自由。
他们认识到社会潮流和人为的欲望只会导致浮躁和混乱,所以返璞归真成为了道家追求心灵自由和真理的重要路径。
四、道德修养道家提倡道德修养,认为道德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和目标。
在道家看来,道德的根本在于追求和谐、宽容、无私和非攻的生活方式。
人们应该修养自身的品德和操守,摒弃功利主义和自我中心的行为,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保持节制和自律的生活态度。
道家认为,只有通过修身养性,塑造道德意识,人才能进一步接近道,达到真正的境界。
五、反对人为创造和干预道家反对人为创造和干预。
他们强调自然本然的力量和规律,主张自然的发展和变化。
道家认为如果人们过度干预和干扰自然,就会破坏自然的平衡和秩序,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和痛苦。
因此,他们主张顺应自然、随缘而行,不去干涉自然的进程,同时也提醒人们要保护自然,不要过度开发和破坏自然资源。
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

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道家思想大概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哲学体系。
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道教的起源和基本思想道教起源于汉代,是一种中国民间宗教。
道家思想对道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在道教的发展和传承中,道家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道家思想的基本思想是道和德的关系。
道代表着万物的原则和本源,是自然之道,是宇宙万物之中最高的一种法则。
而德则代表着人的品德和行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是实践道的具体形式。
道教的基本思想就是要人们通过实践德的行为,追求归于自然之道。
二、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道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道家思想促进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
它的思想深奥,意蕴丰富,培育了一系列伟大的思想家、文化人、哲学家和艺术家。
其次,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学和艺术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精神,包括诗歌、小说、戏剧、艺术等方面,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核心。
再次,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医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的治疗原则和方法都与道家思想密不可分。
中医不仅要治疗疾病,还要通过调整身体的阴阳平衡,使人体能恢复自然平衡。
最后,道家思想对中国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家思想强调自然、平和、自由和维护人类尊严等方面的思想已成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
同时,道家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行为准则和社会习惯。
例如,中国人重视和平、信任、道德规范和自尊,并遵循谦虚、自我节制和人文关怀等道家思想的价值观。
三、道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今天,道家思想仍然对现代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环保方面,道教思想提倡顺应自然,和谐共处,反对毁灭自然和滥用自然资源。
道家辩证法-概述说明以及解释

道家辩证法-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道家辩证法是道家学派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其起源可追溯到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道家辩证法是在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认识和思考中逐渐形成的,它强调对事物的整体性、变化性和相互关系的认识,通过分析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律,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
道家辩证法的核心思想是以“道”为中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
它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而不是孤立存在的。
在道家的观念中,万物皆为道的表现,道既是万物的根源,也是宇宙间的规律和道德准则。
道家辩证法的应用范围广泛,不仅适用于个人修养和人际关系的拓展,还可延伸到政治、经济、科学等各个领域。
它通过分析事物的矛盾和变化,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结来说,道家辩证法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以整体性和变化性为基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通过分析矛盾和变化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个人修养和社会发展中,道家辩证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未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道家辩证法的研究,探索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做出更大的贡献。
1.2 文章结构本文将围绕着道家辩证法展开深入探讨。
文章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引言、正文和结论。
在引言部分,我们将首先概述本文的主题,简要介绍道家辩证法的背景和基本概念。
接着,我们将详细说明文章的结构,以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本文的组织框架和内容安排。
最后,我们将明确本文的目的,以揭示我们撰写此文的原因和意义。
接下来是正文部分,本文将从三个方面阐述道家辩证法。
首先,我们将追溯道家辩证法的起源,探讨其发展历程和形成背景。
其次,我们将深入剖析道家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包括对于事物的观察和认识方式,以及其独特的辩证思维方式。
最后,我们将探讨道家辩证法的应用领域,包括其在个人修养、人际关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实际运用。
最后是结论部分,我们将对道家辩证法的重要性进行总结,强调其在个人修养和社会进步中的价值。
道家思想顺应自然的智慧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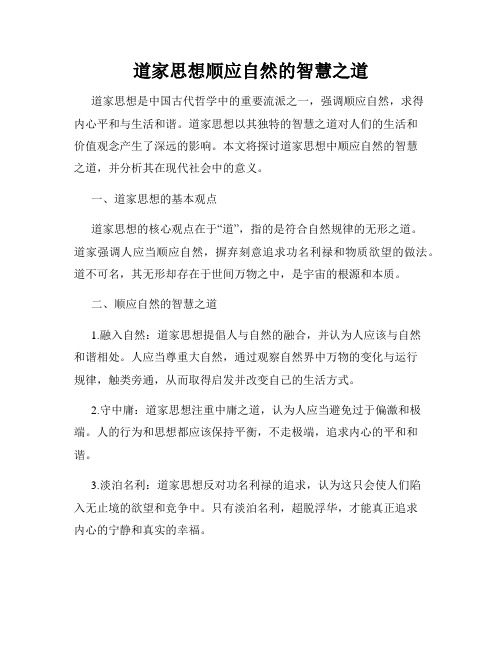
道家思想顺应自然的智慧之道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流派之一,强调顺应自然,求得内心平和与生活和谐。
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智慧之道对人们的生活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道家思想中顺应自然的智慧之道,并分析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
一、道家思想的基本观点道家思想的核心观点在于“道”,指的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无形之道。
道家强调人应当顺应自然,摒弃刻意追求功名利禄和物质欲望的做法。
道不可名,其无形却存在于世间万物之中,是宇宙的根源和本质。
二、顺应自然的智慧之道1.融入自然:道家思想提倡人与自然的融合,并认为人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应当尊重大自然,通过观察自然界中万物的变化与运行规律,触类旁通,从而取得启发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2.守中庸:道家思想注重中庸之道,认为人应当避免过于偏激和极端。
人的行为和思想都应该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追求内心的平和和谐。
3.淡泊名利:道家思想反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认为这只会使人们陷入无止境的欲望和竞争中。
只有淡泊名利,超脱浮华,才能真正追求内心的宁静和真实的幸福。
4.自我约束:道家思想倡导人们自我约束,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
通过反省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找到内心的平静。
三、道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意义1.生活方式:现代社会充斥着物质欲望和竞争压力,道家思想提醒人们要追求内心的平和与生活的简单。
人们可以通过顺应自然的智慧之道,舍弃浮华虚荣,选择简单而独立的生活方式,追求内心真正的幸福。
2.环保意识:道家思想中的顺应自然,对于当代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人们应该意识到自身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提倡绿色生活和可持续消费,积极保护环境资源。
3.心灵健康: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使许多人感到压力重重,道家思想强调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通过修炼道家思想中的智慧之道,人们可以更好地处理自己的情绪,保持心理健康。
4.和谐社会:道家思想倡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以和平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可以使人们享受更好的生活。
道教的思想渊源和基本精神讲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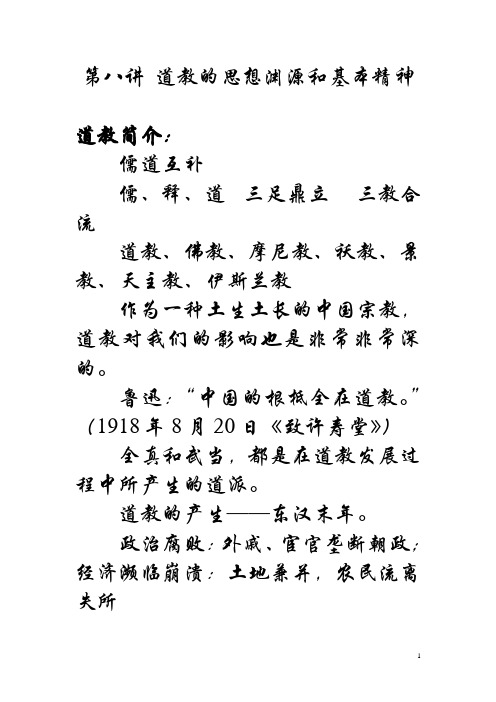
第八讲道教的思想渊源和基本精神道教简介:儒道互补儒、释、道三足鼎立三教合流道教、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道教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的。
鲁迅:“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堂》)全真和武当,都是在道教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道派。
道教的产生——东汉末年。
政治腐败:外戚、宦官垄断朝政;经济濒临崩溃: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文化危机:儒家经学僵化,谶纬神学道教产生和发展“太平道”《太平经》,黄巾起义,张角“五斗米道”巴蜀地区张陵宣称太上老君授予张陵以“天师”的称号,并传授所谓的“正一盟威之道”。
魏晋以来,这个道派被称为“天师道”或“正一道”。
张陵也被称为“张天师”。
在天师道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很多新的宗派:魏晋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在江苏茅山创立茅山宗、陆修静创立灵宝派、梁堪在陕西终南山上的楼观台创立楼观道。
唐初统治者奉老子为李家的祖先,道家道教也因此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宋辽金元时期,道派林立,如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等等。
王重阳及其弟子创立全真道。
“全真七子”在重阳祖师去世后各立门户,如马钰创立遇山派、丘处机创立龙门派、郝大通创立华山派,等等。
大东门的长春观属于全真道龙门派,丘处机的道号“长春真人”,长春观因此而得名。
元朝以后,全真道成为道教最大的道派之一,与正一道并驾齐驱。
一、思想渊源道教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鬼神信仰】第二,【神仙信仰】《山海经》中关于“不死之山”、“不死之国”、“不死之药”的传说。
《老子》第59章:“治人事天,莫若啬。
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之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
是谓根深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庄子〃逍遥游》关于神人的记载:“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大宗师》女禹魏晋南北朝道士葛洪《神仙传》。
道家观念的基本价值观

道家观念的基本价值观引言道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观念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本文旨在探讨道家观念的基本价值观,以期为现代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道家观念的核心理念道家观念的核心理念是“道”,它代表着宇宙间最根本的规律。
道家认为,人类社会和个体生活都应该顺应自然规律,遵循“道”的原则。
二、道家观念的自然观道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张“无为而治”。
在道家看来,自然界是有机的整体,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因此,人们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道家观念的人生观道家认为,人生的真谛在于追求内心的平静与自由。
个体应当摒弃物欲和名利,关注内心的修养,实现精神上的自由与解脱。
四、道家观念的道德观道家道德观的核心是“无为”与“道德”。
道家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和谐共处的基石。
通过修身养性,人们可以培养出高尚的道德品质,实现个人与社会的高度和谐。
五、道家观念的社会观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最好的社会治理方式是让民众自发地遵循道德规范,实现自我管理。
政府的作用应当是引导而非干预,让市场和社会自主调节,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六、结论道家观念的基本价值观为现代社会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在环境问题、人生追求、道德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道家观念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应该深入研究道家思想,汲取其中的智慧,为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希望这份文档能满足您的需求。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修改,请随时告诉我。
七年级下册道法知识点第四

七年级下册道法知识点第四章:道家思想道家始创于先秦时期,其代表人物为老子和庄子。
道家强调“道”这一概念,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源,宇宙的本体,是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
以下是七年级下册道法知识点第四章:道家思想的详细介绍。
一、道道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最重要的概念。
道被认为是一种超越人类认知能力的最高境界,可以概括为真、善、美的总和。
道家的观念认为只有通过摆脱一切形式的束缚,才能进入道的境界。
只有开启心智,自由自在地融入大自然,才能通向道。
二、无为而治在道家思想中,“无为而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它是指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应该遵循自然之道,让事情自然地运行,不要过度干预。
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和平。
同时,也表现了一种对于权力的节制和克制。
三、环境与自然道家思想主张人类应该尊重自然和环境,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保持和自然的和谐并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在其思想中,强调“天人合一”,告诉人们与自然相处的方法。
四、道家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道家思想是一种永恒的思想,直到今天都有着很深的影响。
其提出的重要观点,如道、无为而治等,不仅对于现代人的生活有着启示,也对于当代的管理理论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在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工作压力等。
道家思想提出的环境保护、人际关系处理、抗压能力等重要观点,对于解决这些问题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用道家思想的方法去看待这些问题,并且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或者在对待事物时采取适当的无为而治策略,就能化解这些问题并创造更美好的社会。
五、总结道家思想从根本上呼唤人们要敬畏大自然、爱惜环境,要追求与自然的和谐与联动。
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借鉴道家思想,强调自然和人类的和谐相处,推崇人文主义与生态文明,才能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社会。
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及其影响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重要的一种思想流派,它的理论内涵深厚,其对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精神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道家思想的概念、历史背景、基本观点以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来一一探讨。
一、道家思想的概念道家思想是指以道为核心观念的哲学思想体系,表现为“道”的存在、本质及其中所包含的一系列理论。
其核心观念是“道”,即“大道至简,天下为公”,希望通过对人性、自然、理性等方面的探讨,发现大道的存在及其本质。
在道家思想中,道被看作是一种根本的存在方式,一种无形无物的虚实统一的存在,是存在的本质和地位的标志,也是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的精神追求。
二、道家思想的历史背景道家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
这个时期,各国之间的战争剧烈,民众生活迷茫,因此出现了各种民间思想,其中就包括了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的主要创始人是老子和庄子。
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的思想,即人与自然、社会本应一体而不是有隔别。
庄子则提出“自由自在”、“无为而治”的思想,认为人类自由自在的发展才是最完美的状态。
三、道家思想的基本观点1. 大道至简“大道至简”是道家思想的核心思想之一,其主张人类应当追求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摆脱繁琐而不必要的物质,以追求心灵的宁静和内心的自由。
2. 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观点。
它主张在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不该过多地规定和干涉,而应该让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发展。
他们认为越是用规矩管理,越会加剧人类的困惑和不安。
3. 神秘主义道家思想中的“神秘主义”也是一种思想观念。
主张人类应该摆脱迷信、盲从,以一种客观观察的方式去看待事物。
道家认为,非理性的思考方式往往会带给人类更多的困惑和焦虑。
四、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以至于这种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之一。
它主张“天下为公”,强调个体人性和社会伦理的平等性,鼓励人类追求人生的理想和追求。
浅谈对道家思想的认识

从古代到当今社会各个领域,道家思想还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
并产生重要的影响。
例如,西汉初年经济的恢复,兵法上的辩证法的成功运用,当代城市的合理规划。
以及对规律的正确运用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道家的思想文化并非空洞,而是有着重要的实用性,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
一、道家的起源与本质论述道家的源头之一是以坤卦为首卦的《归藏》。
道家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一个思想学派。
以“道”为本主张无为,消极避世。
到了西汉初年,统治者用道家思想统治国家,养精蓄锐,积聚实力,使人民从秦朝暴政的摧残和长期的战乱中得以休养生息,过上安稳的日子。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至汉武帝时期,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在思想领域一直处于正统地位。
尽管道家未被统治者采纳,但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思想领域。
佛教的某些教义也受到道家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佛教依附于道家得以发展,佛教的心性本体论路向的确立,就是以道家为主要载体的实体主义理路。
魏晋玄学也是揉合了道家思想形成和发展。
宋明理学在某些方面也受道家影响,例如把认知问题与身心超越及其交身立命联系起来,道家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是多欲,多欲才导致乱折腾。
因此道家提出“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这对理学的禁欲思想影响颇深。
道家地位虽不及儒家崇高,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上呈现出重要的实用价值与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著名的思想家鲁迅曾说:“道家是中国文化的根,阐述中国文化的本体概念”。
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道家所主张的“道”,指万物的本质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
天地万物皆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天地万物的本源就是道,道就是应该遵守的基本法则。
因此,道家把道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
道家思想包括道教的历史景点、人物生平等诸多方面。
道家思想文化包含道教各个方面的内容,虽然内容多样,但教义始终如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道家思想承前启后,在对道家信仰的稳定中传承了下来。
总结一下道家思想

总结一下道家思想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主要思想核心是“道”和“无为”,强调顺应自然、追求无为而治的理念。
道家思想对中国的哲学、政治、文化和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道家思想的起源、主要观点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详细的探讨和总结。
道家思想起源于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老子和庄子,他们对人类存在和宇宙运行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与传统儒家思想相对立的观点。
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它具有无形无相、无处不在、永恒无终的特点,被认为是宇宙的本源和万物的根源。
道家认为,人类追求真理和幸福的关键在于顺应自然,追求人性的本真和内心的宁静。
道家思想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强调“无为而治”。
道家认为,人为的干预会扰乱宇宙的自然运行,最好的方式是顺应自然,不要过度干预。
他们主张无为而治,即以无为之道为准则,不以人力为主,而是顺应自然,任其自然发展。
他们认为,只有遵循自然的规律和节奏,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是追求无欲无求。
道家思想主张人们应该舍弃追求身外之物的欲望,追求内心的宁静与平和,以达到真正的幸福。
他们认为欲望与功利是人们痛苦和困扰的根源,而无欲无求则是实现内心自由的关键。
此外,道家强调“自然自发”。
他们认为,人们应该按照自己内心的本真去生活,不受规则与框架的束缚。
他们主张天人合一,即人应该与自然融为一体,顺应自然的变化,追求内外和谐。
道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道家注重个体的修养和情感的宣泄,倡导平和宁静的生活方式,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
道家思想的影响使人们更加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和人性的追求。
其次,道家的政治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强调“以德治国”,反对过度干预和用人的规定。
这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政治体制产生了积极的倡导,尤其是在秦朝的统一帝制和唐朝的盛世时期,道家思想对政治制度形成和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家真经道家思想玄学追求思维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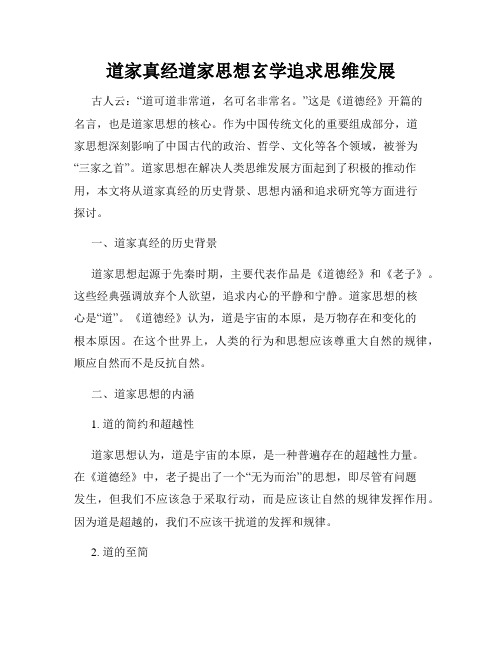
道家真经道家思想玄学追求思维发展古人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是《道德经》开篇的名言,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被誉为“三家之首”。
道家思想在解决人类思维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将从道家真经的历史背景、思想内涵和追求研究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道家真经的历史背景道家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主要代表作品是《道德经》和《老子》。
这些经典强调放弃个人欲望,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宁静。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
《道德经》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是万物存在和变化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行为和思想应该尊重大自然的规律,顺应自然而不是反抗自然。
二、道家思想的内涵1. 道的简约和超越性道家思想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超越性力量。
在《道德经》中,老子提出了一个“无为而治”的思想,即尽管有问题发生,但我们不应该急于采取行动,而是应该让自然的规律发挥作用。
因为道是超越的,我们不应该干扰道的发挥和规律。
2. 道的至简道家思想是关于自然界和人性的基本思想。
鲁迅曾经说过:“《道德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出色的智慧之一。
”道家思想有着至简的思想,通过极简的表达方式,展现了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
3. 道的平衡道家思想的核心是对平衡的追求。
在宇宙中,所有事物都是以平衡为基础存在的。
在人类社会中,道家思想也注重平衡的追求,强调尽可能避免极端行为和情绪,保持内心的平衡和宁静。
三、道家思想的追求研究道家历来被认为是一种玄学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是道家的信奉者,如庄子、列子和酉阳子等。
在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思想和信仰,道家思想仍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许多人都认为这种思想在解决现代社会中的问题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追求研究方面,道家思想也有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
道家思想中的“语言哲学”被许多学者看作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学派,可以用来解释许多重要的概念和思想。
道家思想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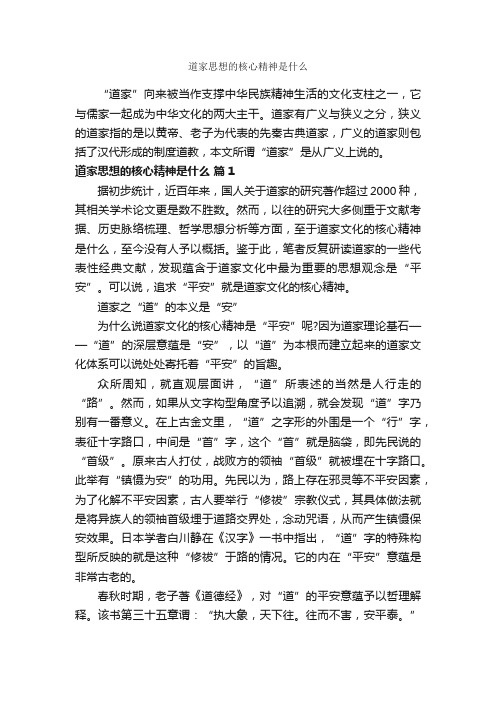
道家思想的核心精神是什么“道家”向来被当作支撑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文化支柱之一,它与儒家一起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主干。
道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道家指的是以黄帝、老子为代表的先秦古典道家,广义的道家则包括了汉代形成的制度道教,本文所谓“道家”是从广义上说的。
道家思想的核心精神是什么篇1据初步统计,近百年来,国人关于道家的研究著作超过2000种,其相关学术论文更是数不胜数。
然而,以往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文献考据、历史脉络梳理、哲学思想分析等方面,至于道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么,至今没有人予以概括。
鉴于此,笔者反复研读道家的一些代表性经典文献,发现蕴含于道家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观念是“平安”。
可以说,追求“平安”就是道家文化的核心精神。
道家之“道”的本义是“安”为什么说道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平安”呢?因为道家理论基石——“道”的深层意蕴是“安”,以“道”为本根而建立起来的道家文化体系可以说处处寄托着“平安”的旨趣。
众所周知,就直观层面讲,“道”所表述的当然是人行走的“路”。
然而,如果从文字构型角度予以追溯,就会发现“道”字乃别有一番意义。
在上古金文里,“道”之字形的外围是一个“行”字,表征十字路口,中间是“首”字,这个“首”就是脑袋,即先民说的“首级”。
原来古人打仗,战败方的领袖“首级”就被埋在十字路口。
此举有“镇慑为安”的功用。
先民以为,路上存在邪灵等不平安因素,为了化解不平安因素,古人要举行“修祓”宗教仪式,其具体做法就是将异族人的领袖首级埋于道路交界处,念动咒语,从而产生镇慑保安效果。
日本学者白川静在《汉字》一书中指出,“道”字的特殊构型所反映的就是这种“修祓”于路的情况。
它的内在“平安”意蕴是非常古老的。
春秋时期,老子著《道德经》,对“道”的平安意蕴予以哲理解释。
该书第三十五章谓:“执大象,天下往。
往而不害,安平泰。
”老子所谓“大象”即“道”,而“执大象”就是信仰大道、奉行大道、固守大道。
“天下往”是说圣人奉行大道,天下万物都归向大道。
daosishi

daosishi
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之一,它的精神追求在于通过内在的心
灵自然找到理论上的解释,修行者无需外部的束缚而获得自我的成长、最终的觉悟。
它的思想主要围绕着“道”的概念,历史上众多著名的
道家学派如:《老子》、《庄子》、《莲花经》等,都以“道”为基
础建立起理论体系。
道家的核心概念是道、气、合一等概念,意思是整体与其组成部
分间的协调,只有达成气、道、合一的统一,才能够真正的发掘人的
潜力,同时也能展示出正确的实践路径。
另一方面,道家士也有着普
世的道德准则,即“仁义礼智”。
道家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道家士们是传承中
国传统哲学文化的使者,他们在国家的建设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般来说,道家士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追求心态
的清新、行动的端庄平衡,这也是道家士教导修行者的目标。
道家士传统上以武器礼仪、心灵法术、神秘审美、及细腻的议论
等技能来表现自己的精神。
他们格外注重心灵、思想的修养,并以此
为基础养成一套自己的礼仪、习俗、及规范,以尊重他人的意见,保
留自身的尊严为宗旨。
道教精神本原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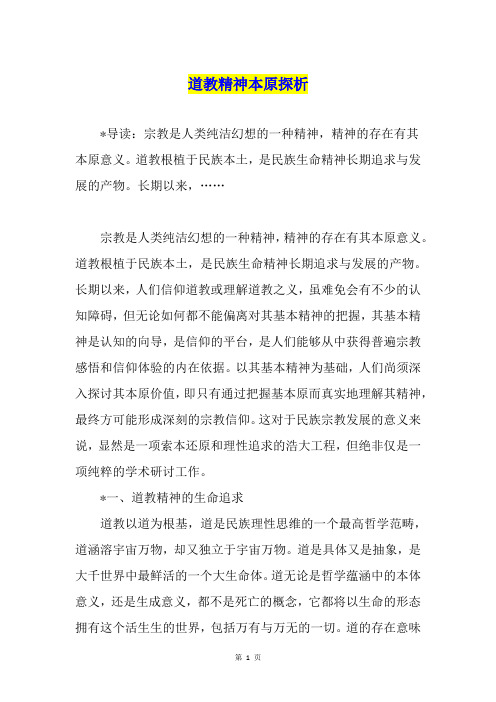
道教精神本原探析*导读:宗教是人类纯洁幻想的一种精神,精神的存在有其本原意义。
道教根植于民族本土,是民族生命精神长期追求与发展的产物。
长期以来,……宗教是人类纯洁幻想的一种精神,精神的存在有其本原意义。
道教根植于民族本土,是民族生命精神长期追求与发展的产物。
长期以来,人们信仰道教或理解道教之义,虽难免会有不少的认知障碍,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偏离对其基本精神的把握,其基本精神是认知的向导,是信仰的平台,是人们能够从中获得普遍宗教感悟和信仰体验的内在依据。
以其基本精神为基础,人们尚须深入探讨其本原价值,即只有通过把握基本原而真实地理解其精神,最终方可能形成深刻的宗教信仰。
这对于民族宗教发展的意义来说,显然是一项索本还原和理性追求的浩大工程,但绝非仅是一项纯粹的学术研讨工作。
*一、道教精神的生命追求道教以道为根基,道是民族理性思维的一个最高哲学范畴,道涵溶宇宙万物,却又独立于宇宙万物。
道是具体又是抽象,是大千世界中最鲜活的一个大生命体。
道无论是哲学蕴涵中的本体意义,还是生成意义,都不是死亡的概念,它都将以生命的形态拥有这个活生生的世界,包括万有与万无的一切。
道的存在意味着生命的永恒,生命是道最本质的意义。
道无论是以无,以水,以玄,以谷神,以玄牝,以天根,以万物之母,以众妙之门等均是不死之生命体而绵绵若存。
道之不死之生命,一是缘其无具体生命之象,无血脉生机与腐败的过程;二是缘其覆盖众形之巨,是万有生命之神髓;三是缘其超迈时空,无生命长短宽厚之界域;四是缘其造万物而生生不息之母体,从创生之无始至终结之未了,是一个永恒的生成体。
道的基本精神蕴涵着生命的本质意义,不朽之生命是道生与成的内在源泉及其外在表现的基本形态。
道教以道为宗,继承了道的生命意义,道之大生命以宗教形式为世人所信仰,由是,追求道之大生命遂成了道教信仰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道教是生的宗教,始终界定在生命存在的层面上,而不以生命消亡之后的超度为功力。
道家思想与士人的精神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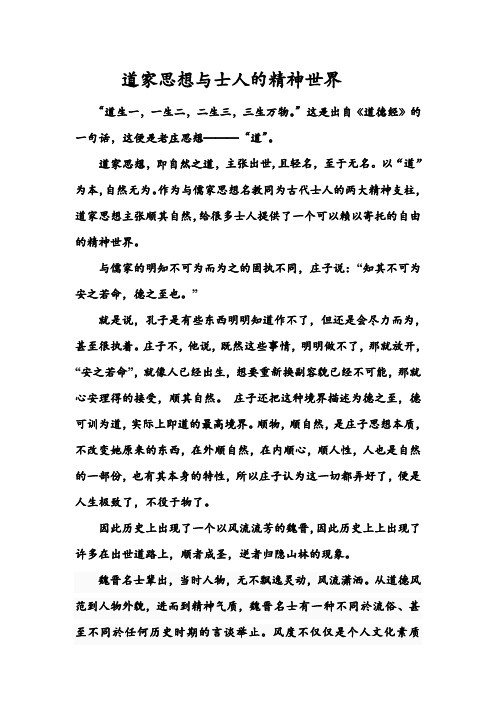
道家思想与士人的精神世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是出自《道德经》的一句话,这便是老庄思想———“道”。
道家思想,即自然之道,主张出世,且轻名,至于无名。
以“道”为本,自然无为。
作为与儒家思想名教同为古代士人的两大精神支柱,道家思想主张顺其自然,给很多士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赖以寄托的自由的精神世界。
与儒家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固执不同,庄子说:“知其不可为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就是说,孔子是有些东西明明知道作不了,但还是会尽力而为,甚至很执着。
庄子不,他说,既然这些事情,明明做不了,那就放开,“安之若命”,就像人已经出生,想要重新换副容貌已经不可能,那就心安理得的接受,顺其自然。
庄子还把这种境界描述为德之至,德可训为道,实际上即道的最高境界。
顺物,顺自然,是庄子思想本质,不改变她原来的东西,在外顺自然,在内顺心,顺人性,人也是自然的一部份,也有其本身的特性,所以庄子认为这一切都弄好了,便是人生极致了,不役于物了。
因此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以风流流芳的魏晋,因此历史上上出现了许多在出世道路上,顺者成圣,逆者归隐山林的现象。
魏晋名士辈出,当时人物,无不飘逸灵动,风流潇洒。
从道德风范到人物外貌,进而到精神气质,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於流俗、甚至不同於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
风度不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应,对於一定的社会阶层来说,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集中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形象。
这种风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
而晋朝成立,道家思想便进入了这个国家的核心意识部分。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
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
“竹林七贤”的酣饮醉谈,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和梦里那个桃花源,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携领着他们飞蛾扑火般的旅程?魏晋的名士都注重精神世界的纯净,无视功名利禄和富贵,内心旷达,形迹放浪,这就反映了整个时代对传统礼教的挑战,对腐朽文化的不满。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道家思想是触及根源性的一种前瞻精神”2006-12-29 作者:河西——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叶维廉教授访谈道家精神最终是要去语障、解心囚,恢复活泼泼的整体的生命世界……——叶维廉■河西/采访整理叶维廉是个喜欢“脚踏两只船”的人。
他站在灵动神思的东方诗学和严谨修辞的西方诗学之间,左顾右盼,指东打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停地换位”。
生处乱世有时候也不能说一点好处都没有,至少在叶维廉身上是这样。
从广东中山迁往香港是他第一次背井离乡,这个他尚未认知的城市让他感到“渗透到所有器官”的恐惧;然后是去台北念书,对中国文化的犹疑焦虑和重建中国文化的努力交织在一起,这是混乱的时期,叶维廉觉得自己深陷在“生死存亡的处境”中,有点迷惘,但更多的是中国文化救亡图存的青春期冲动:“既承受着五四以来文化虚位之痛,复伤情于无力把眼前渺无实质支离破碎的空间凝合为一种有意义的整体。
”此后,从台北赴美留学成为了叶维廉思想变局三部曲中的终曲,在这里,他系统学习比较文学理论的结果则是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更为切实的认识。
美国诗人罗登堡说叶维廉是个游子,这只是行动层面上考量的结果,在文化层面上,叶维廉的“双重国籍”从未动摇他对中国本体的坚持和信仰。
近日,他的成名作《中国诗学》(增订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叶维廉先生欣然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河西:您认为在现代的语境中,以道家美学为核心的中国古典诗学是否还有发展的土壤?一个悖论是,您虽然极力推崇恬淡冥无的道家和禅宗诗学观,可是您对于中国现代的诗坛诸家,也不避讳去选一些感情浓烈的诗作(包括穆旦的《我》),这是否有矛盾?而您在序中也承认,自己的创作在70年代之前也是“如此浓烈”,这是否可以看作道家美学并不能时时压过爱国热情的一种迹象?叶维廉:你这里有一个预设,把道家看成一种被动的,甚且是逃避主义者的思域。
让我先澄清关于道家的一些成见。
把它看成一种消极的行为/哲学,这,实在是因为内在化了几千年得势的思想(儒家)的偏见所致,我想趁此机会唤起读者一种被沉淹已久的觉识,那就是,当我们把一些现象视为“异于常态”时,我们所依据的所谓“常”,或者我们已经内在化的仿佛不用思索便知道的“常”,其实不是绝对的,而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些所谓“常”往往只是以前因某种政治利益或社会效应的主观执见而建构出来的一种运作准据,多是以偏概全的,是一种器囚,尤其是在某些社会的运作下,僵固偏狭,反而宰制了我们思维的活动空间,而看不见这些强势的“常”如何遮盖了宇宙与人性更大的胸怀。
道家精神最终是要去语障、解心囚,恢复活泼泼的整体的生命世界,是另一种积极的运作。
一旦了解了这些特权的分封,尊卑关系的订定,不同礼教的设立,如所谓“天子”受命于天而有绝对的权威,如君臣、父子、夫妇的尊卑关系(臣不能质疑君,子不能质疑父,妻不能质疑夫)如男尊女卑等等,完全是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发明,是一种语言的建构,至于每个人生下来作为自然体的存在的本能本样,都受到偏限与歪曲。
道家对语言的质疑,对语言与权力关系的重新考虑,完全是出自这种人性危机的警觉。
所以说,道家精神的投向,既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
政治上,他们要破解封建制度下圈定的“道”(王道、天道)和名制下种种不同的语言建构,好让被压抑、逐离、隔绝的自然体(天赋的本能本样)的其它记忆复苏,引向全面人性、整体生命的收复。
我们可以看见,从一开始,道家语言的运作,大多时候是在语言争战磁场上发生,其出手仿佛比武时的“招数”或对弈时的“着数”,时虚时实,似真仍假,似假复真,使对方在惑与不惑目眩未定之际,得个正着,跳脱常语的语规而一闪见朴。
道家思想是触及根源性的一种前瞻精神,最能发挥英文字radical 的双重意义,其一是激发根源问题的思索从而打开物物无碍的境界,其二是提供激进前卫的颠覆性的语言策略。
关于后者,熟识老庄论述的读者,不难注意到其间经常出现的攻人未防的惊人的话语和故事,特异的逻辑和戏谑性的语调,这里还包括矛盾语法、模棱多义的词字以及“以惑作解”。
发展到玄学时期,进而以行动来调侃现行的囚制生活和禅宗公案、棒喝等。
这些策略早已预示、预演了西方达达主义以来前卫艺术常用的Disturb(惊骇、扰乱)、Dislocate(错位、错序)和Destroy(打破旧有因袭)的三个步骤。
但道家在用颠覆性语言策略这三个步骤的同时要重现自由无碍、物我物物互参互补互认互显的圆融世界。
达达式的前卫艺术往往只停留在惊世骇俗的层面而未能在解框后提供万物圆融的精神投向。
现代中国文学、现代诗的语境,我曾这样描述:是本源感性与外来意识形态争战协商下极其复杂的共生,借生物学的一个名词,可以称之为Antagonistic Symbiosis (异质分子处于斗争状态下的共生),指的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霸权利用船坚炮利、企图把中国殖民化所引起的异质文化与本源文化的争战。
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一开始便是在帝国主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辩证下的蜕变与转化。
以上的情结和文化异质的争战其实不只发生在创作上,也发生在东西比较文学里文化、文学的论述上,从一开始便面对方法论上必然产生的争战,我1974年提出的模子的应用,就是对西方的文化模子、理论架构、美学据点的质疑。
道家在语言争战、解框(尤其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内在化了的西方的框限的破解)后提供万物圆融的精神投向正可以为西方和内在化的西方的语境解困,引向(在创作上在思域的呈现上)弓张弦紧的对话。
我们在位的精英分子仿佛对现代化、全球化有高度的内在化,没有多大批判性的反思,譬如现在中国不少学者(包括比较文学学者和全球化的论述者)往往对西方流行的理论话语、术语未经反思地全面拥抱,没有经历文化异质争战内在的衍化,许多对传统中国文化里的解困能力甚至没有什么认识,把后现代全球化的走向奉为圭璋,乐不思蜀。
西方霸权的成功,其中最大的关键之一,是依存第三世界统治阶级中精英分子对西方后启蒙思想,包括开发理论的内在化,对西方生产模式所带动的杀伤性的文化工业视而不见。
真正的独立必须是经济与文化同时的独立。
这必须要期待中介的精英分子---受过外来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反思。
而且这个反思又必须要认识到外来思想体系里根源性问题与困境,以及自己传统中根源性的解困能力。
在这个为新文化努力的阶段中,为了整体生命情境的完成,不应该接受宰制者现存系统的模式,也不应该没有反思地回归过去的传统,而是要对异质文化、文学争战共生过程中两种宰制性和创造性文化的交参纠缠深探和思索,在相争相持的文化对话火光一闪中见出自我解放和超越内在化情结的可能,而中国的自然观,譬如道家对语言、概念的框限行为根源性的思索和质疑正可以帮我们突围而出。
河西:又有一个悖论,您说中国古典诗歌是很难翻译成英文的,一旦翻译就可能得不偿失,可是您又是怎么将这些古典诗介绍给美国的同行的呢?叶维廉:关于翻译上的诸种问题,是我的专长,我的《Ezra Pound’s Cathay》(1969),是一本通过翻译、翻译理论的讨论进入语言哲学、美学策略的比较文学的书,因为这本书和1976年用实践及理论向西方语言策略挑战的《Chinese Poetry:Major Modes and Genres》[中国古典诗(由诗经到元曲)举要的译本]使得美国最重要的诗人罗登堡称我为“The linking figure between American modernism(in-the-line-of-Pound)and Chinese traditionsand practices”(美国庞德系列的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的汇通者”)。
《Ezra Pound’s Cathay》(1969)之后,还有《比较诗学》(1982),《Diffusion of Distances: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1993),本书和其他有关道家美学的文章里都是有关中西语言哲学、观物感悟形态、表意策略的基本差异更深层的寻索。
关于我的翻译理论,除了这些书之外,我还有一篇文章《破信达雅:翻译后起的生命》,说明“重建作者的原意”“客观的诠释”“意义可复制性”和“理想读者”(所谓信)是一种迷思。
一篇作品的意义,不是一个封闭、圈定、可以“载”、可以“剥取”的东西,是文辞美学空间开放的交流、参化、衍变、生长的活动。
我翻译中国古典诗是挑战式地与诗人读者对话,分原文、逐字解读,和用把定向限义元素,也就是英文语法中的限指元素减到最低的创意的灵活的英文提供翻译文本三个步骤,因为读者在我的序文中有了有关中国灵活语法所提供的有异于西方的美学向度和庞德通过中国诗的接触引发回响着中国灵活语法的创新与试探,以及引带后起美国诗人大幅度的实践这个事实的认识,都很乐意在逐字解读和我提供的文本之间做出开放、交流、参化的再创造的阅读。
有识的读者会明白,语法切断在英文里,并不是随便切断就可以,译者必须掌握字组语群发射的能量和互玩所构成的气象,也就是说译者必须是一个诗人,在这里讲的是掌握英语潜能的诗人。
河西:您对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异质文化的错位”,用亨廷顿的话似乎也可以说成是“文明的冲突”,在这一次错位或冲突的过程中,道家美学在主流文化中是被完全的打败了,除了国家兴亡的民族大义的原因之外,道家美学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是否也是非常脆弱的信仰?叶维廉:你在这里简化了我的原意,我的用语是“异质文化争战的共生”。
事实上,道家美学在现代的西方诗里在前卫艺术里,有非常大的开展,我的《Chinese Poetry:Major Modes and Genres》受到相当多的美国现代诗人喜爱也不是偶然的。
你也可以参看前面提到的《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的第二章,论及John Cage与Allan Kaprow涉道家美学之深。
你问:“道家美学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是否也是非常脆弱的信仰”,其基本原因,是五四以来的被边缘化的过程,其中我在上面提到的“内在化了几千年得势的思想(儒家)的偏见”损害最大。
最主要的是五四以后许多丰富语言和哲思的契机被动荡的政治环境扼杀了。
我之前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不妨用来回答你的问题:第一,要了解我们白话建立以来的瘦弱病变的缘由。
第二,“文字的雕塑”一直是我们传统诗里的骄傲,“诗眼”、“警句”、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我们在那里找到什么可以与现代接轨的地方呢?后者就是我后来作为学者要重建的努力(由我的《比较诗学》到《中国诗学》到《道家美学》)。
关于第一点,首先,白话里内涵的演绎性。
在白话被应用为诗的表达媒介之前,主要是三言到大型古典小说的表达媒介,在古典小说里的诗都是文言诗,在叙述过程中需要加入诗的浓度的瞬间时,说书人/小说家都借助中国古典诗,而从来没有设法把白话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