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话”的前世今生——关于贵州方言与贵州文化的访谈
读书贵阳话

读书贵阳话(最新版)目录1.贵阳话的概述2.贵阳话的特点3.贵阳话与普通话的差异4.学习贵阳话的方法5.读书与贵阳话的关系正文【贵阳话的概述】贵阳话,也被称为贵阳方言,是一种属于汉语方言的贵州话。
它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贵阳市及周边地区,是当地居民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
贵阳话的历史悠久,起源于古代西南地区的夷语,后来受到汉语的影响逐渐演变成现今的贵阳话。
【贵阳话的特点】贵阳话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声调丰富:贵阳话拥有 5 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这使得贵阳话听起来韵律感十足。
2.儿化音:贵阳话中有许多儿化音,即在词尾加上“儿”音,如“花儿”、“瓜儿”等,这种发音方式使得贵阳话听起来富有地方特色。
3.口音浓厚:贵阳话的口音与普通话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在声母、韵母和声调方面。
这使得贵阳话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和独特性。
【贵阳话与普通话的差异】贵阳话与普通话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声母方面:贵阳话的声母较多,一些普通话中没有的声母在贵阳话中出现,如“ng”、“ny”等。
2.韵母方面:贵阳话的韵母发音与普通话有一定差异,部分韵母发音较长,如“i”、“u”等。
3.声调方面:贵阳话有 5 个声调,而普通话只有 4 个声调。
这意味着同样的词汇在不同的声调下有不同的意义。
【学习贵阳话的方法】想要学习贵阳话,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听:多听贵阳话,熟悉贵阳话的发音、语调和韵律。
2.说:尽量多与贵阳话母语者交流,模仿他们的发音和语言表达。
3.读:阅读贵阳话的相关书籍和文章,了解贵阳话的语言特点和文化背景。
4.写:尝试用贵阳话进行写作,通过写作来巩固所学的贵阳话知识。
【读书与贵阳话的关系】读书是学习贵阳话的重要途径之一。
通过阅读贵阳话的书籍和文章,不仅可以了解贵阳话的语言特点和文化背景,还可以提高自己的贵阳话阅读和写作能力。
贵阳土话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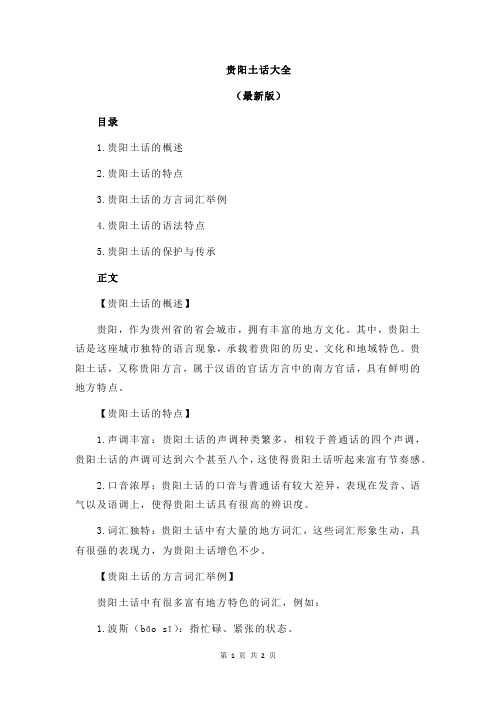
贵阳土话大全(最新版)目录1.贵阳土话的概述2.贵阳土话的特点3.贵阳土话的方言词汇举例4.贵阳土话的语法特点5.贵阳土话的保护与传承正文【贵阳土话的概述】贵阳,作为贵州省的省会城市,拥有丰富的地方文化。
其中,贵阳土话是这座城市独特的语言现象,承载着贵阳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
贵阳土话,又称贵阳方言,属于汉语的官话方言中的南方官话,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
【贵阳土话的特点】1.声调丰富:贵阳土话的声调种类繁多,相较于普通话的四个声调,贵阳土话的声调可达到六个甚至八个,这使得贵阳土话听起来富有节奏感。
2.口音浓厚:贵阳土话的口音与普通话有较大差异,表现在发音、语气以及语调上,使得贵阳土话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3.词汇独特:贵阳土话中有大量的地方词汇,这些词汇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为贵阳土话增色不少。
【贵阳土话的方言词汇举例】贵阳土话中有很多富有地方特色的词汇,例如:1.波斯(bāo sī):指忙碌、紧张的状态。
2.鬼头刀:指一种昆虫,学名为蝉。
3.麻怪:指青蛙。
4.叶噶:指翅膀。
这些词汇形象生动,充分体现了贵阳土话的独特魅力。
【贵阳土话的语法特点】贵阳土话的语法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语序变化:贵阳土话中,动词一般放在名词前,这与普通话的语序有所不同。
2.助词使用:贵阳土话中助词使用较为频繁,如“得”、“勒”、“些”等。
3.量词搭配:贵阳土话中的量词搭配与普通话有所区别,如“一碗饭”、“一匹瓦”等。
【贵阳土话的保护与传承】作为一种地方方言,贵阳土话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然而,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贵阳土话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传承面临着一定的压力。
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贵阳土话的保护和传承,让这一独特的地方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贵州方言节目存在的价值—大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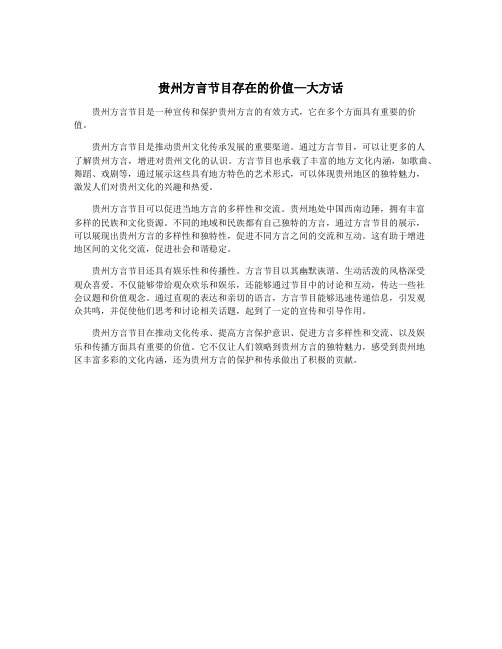
贵州方言节目存在的价值—大方话
贵州方言节目是一种宣传和保护贵州方言的有效方式,它在多个方面具有重要的价
值。
贵州方言节目是推动贵州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渠道。
通过方言节目,可以让更多的人
了解贵州方言,增进对贵州文化的认识。
方言节目也承载了丰富的地方文化内涵,如歌曲、舞蹈、戏剧等,通过展示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可以体现贵州地区的独特魅力,
激发人们对贵州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贵州方言节目可以促进当地方言的多样性和交流。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拥有丰富
多样的民族和文化资源。
不同的地域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方言,通过方言节目的展示,
可以展现出贵州方言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促进不同方言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这有助于增进
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贵州方言节目还具有娱乐性和传播性。
方言节目以其幽默诙谐、生动活泼的风格深受
观众喜爱。
不仅能够带给观众欢乐和娱乐,还能够通过节目中的讨论和互动,传达一些社
会议题和价值观念。
通过直观的表达和亲切的语言,方言节目能够迅速传递信息,引发观
众共鸣,并促使他们思考和讨论相关话题,起到了一定的宣传和引导作用。
贵州方言节目在推动文化传承、提高方言保护意识、促进方言多样性和交流、以及娱
乐和传播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它不仅让人们领略到贵州方言的独特魅力,感受到贵州地
区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还为贵州方言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贵州方言节目存在的价值—大方话

贵州方言节目存在的价值—大方话
贵州方言节目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承和保护方式,它在多个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贵州方言节目是贵州地方文化的一部分,它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传承贵州的地
域文化。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有着丰富的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
贵州方言节目
可以通过语言、歌曲、舞蹈等形式,将贵州的地域文化展现给观众,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
解贵州的传统和乡土风情。
贵州方言节目是贵州方言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
方言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它有着
自己独特的词汇、语法和语音特点。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方言的使用逐渐减少,正在逐
渐面临消失的危险。
贵州方言节目通过将方言运用到表演中,使人们重新关注和使用方言,促进方言的传承和保护。
贵州方言节目还有着丰富的娱乐和文化内涵。
方言表演可以将地方特色和幽默感融入
到节目中,给观众带来欢乐和娱乐。
方言节目还可以通过舞台表演、音乐和戏剧等形式,
传达文化信息和情感,提供观众流连忘返的艺术享受。
贵州方言节目还具有促进交流和认同感的作用。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方
言节目可以促使观众更加了解贵州的人文风情,增进不同乡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方
言节目也可以促进贵州人对家乡方言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加深对地域文化的认同。
贵州方言节目在文化传承、方言保护、娱乐文化和社会认同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我们应该重视和支持贵州方言节目的发展,传承和保护好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
花了一年时间,对贵州家乡方言(贵州话)记录研究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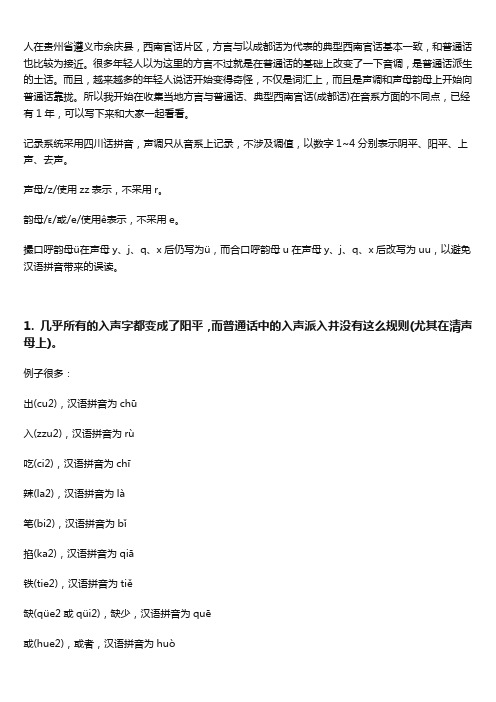
人在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西南官话片区,方言与以成都话为代表的典型西南官话基本一致,和普通话也比较为接近。
很多年轻人以为这里的方言不过就是在普通话的基础上改变了一下音调,是普通话派生的土话。
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话开始变得奇怪,不仅是词汇上,而且是声调和声母韵母上开始向普通话靠拢。
所以我开始在收集当地方言与普通话、典型西南官话(成都话)在音系方面的不同点,已经有1年,可以写下来和大家一起看看。
记录系统采用四川话拼音,声调只从音系上记录,不涉及调值,以数字1~4分别表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声母/z/使用zz表示,不采用r。
韵母/ᴇ/或/e/使用ê表示,不采用e。
撮口呼韵母ü在声母y、j、q、x后仍写为ü,而合口呼韵母u在声母y、j、q、x后改写为uu,以避免汉语拼音带来的误读。
1. 几乎所有的入声字都变成了阳平,而普通话中的入声派入并没有这么规则(尤其在清声母上)。
例子很多:出(cu2),汉语拼音为chū入(zzu2),汉语拼音为rù吃(ci2),汉语拼音为chī辣(la2),汉语拼音为là笔(bi2),汉语拼音为bǐ掐(ka2),汉语拼音为qiā铁(tie2),汉语拼音为tiě缺(qüe2或qüi2),缺少,汉语拼音为quē或(hue2),或者,汉语拼音为huò屋(və2),屋头,汉语拼音为wū括(gua2或kua2),括号,汉语拼音为kuò笛(di2),笛子,汉语拼音为dí还有一些数字(一六七八十百)、否定词(不莫)等等等等只有几个例外:给(gei3),汉语拼音为gěi没(mei1),汉语拼音为méi,否定词喝(ho1),汉语拼音为hē但存在其他的西南官话片区的人把喝说成ho2(比如武汉)武汉人、部分四川人还把吃念作七(qi2)我猜西南官话的前身可能是一种有独立入声声调的的方言,后来该声调和阳平发生了合并,于是产生了如今的局面。
贵阳土话大全

贵阳土话大全贵阳,位于我国西南部,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城市。
在这座城市里,流传着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贵阳土话。
贵阳土话作为地方方言,既有与其他方言相似的地方,又有其独特之处。
本文将从贵阳土话的简介、分类以及学习与传承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贵阳土话简介1.地理位置背景贵阳,位于贵州省中部,是贵州省的省会。
贵阳土话主要分布在贵阳市及周边地区,使用人口约500万。
2.贵阳土话的特点贵阳土话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
语音方面,贵阳土话的声调丰富,具有独特的音韵特点;词汇方面,贵阳土话具有大量的地方特色词汇,富含生活气息;语法方面,贵阳土话的结构较为简单,易于掌握。
二、贵阳土话分类1.生活用语(1)日常问候在贵阳,人们见面时会用“吃了吗?”、“今天忙啥子?”等土话问候对方。
这种问候方式充满了亲切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2)道谢与道歉贵阳土话中表示道谢的词汇有“谢谢”、“辛苦了”等,道歉的词汇有“对不起”、“不好意思”等。
(3)情感表达贵阳土话中有很多表达情感的词汇,如“安逸”(舒服)、“巴适”(很好)、“哦豁”(糟糕)等。
2.饮食文化(1)特色美食贵阳土话中有很多与美食相关的词汇,如“豆花”(豆腐脑)、“老干妈”(一种辣椒酱)等。
(2)饮食习俗贵阳土话中的饮食习俗词汇有“吃饭”(吃米饭)、“喝汤”(喝粥)等。
3.休闲娱乐(1)传统活动贵阳土话中有许多与传统活动相关的词汇,如“划龙船”(端午节划龙舟)、“舞龙舞狮”(春节期间舞龙舞狮)等。
(2)流行语贵阳土话中的流行语不断更新,如“高大上”(形容事物高端、上档次)、“网红”(指网络红人)等。
三、贵阳土话的学习与传承1.学习途径(1)家庭传承在家庭中,长辈们可以用贵阳土话与晚辈交流,使土话得到传承。
(2)学校教育在学校里,可以通过语文、地理等课程学习贵阳土话的相关知识。
(3)社会资源社会上有很多关于贵阳土话的学习资源,如图书、音频、视频等。
贵州方言文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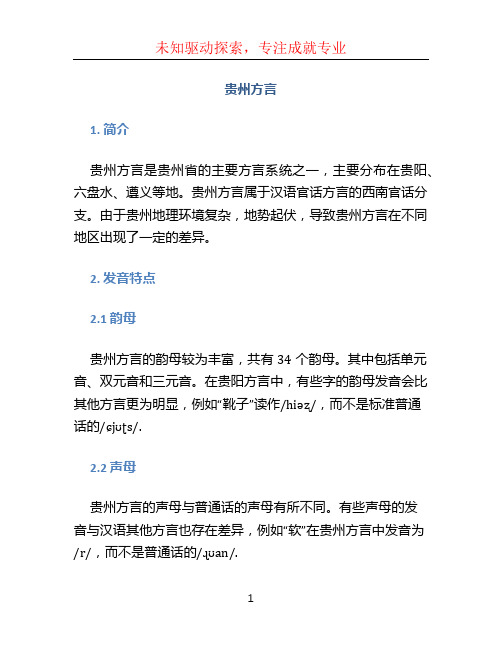
贵州方言1. 简介贵州方言是贵州省的主要方言系统之一,主要分布在贵阳、六盘水、遵义等地。
贵州方言属于汉语官话方言的西南官话分支。
由于贵州地理环境复杂,地势起伏,导致贵州方言在不同地区出现了一定的差异。
2. 发音特点2.1 韵母贵州方言的韵母较为丰富,共有34个韵母。
其中包括单元音、双元音和三元音。
在贵阳方言中,有些字的韵母发音会比其他方言更为明显,例如“靴子”读作/hiəʐ/,而不是标准普通话的/ɕjʊʈs/.2.2 声母贵州方言的声母与普通话的声母有所不同。
有些声母的发音与汉语其他方言也存在差异,例如“软”在贵州方言中发音为/r/,而不是普通话的/ɻʊan/.2.3 声调贵州方言的声调较多,通常分为六个声调。
贵阳方言中的声调变化比较明显,且具有一定的特色。
例如,贵阳方言中的第二声较普通话要重一些。
3. 词汇特点3.1 俚语和口头语的使用贵州方言中广泛使用俚语和口头语,这些词汇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
例如,“土豆”在贵州方言中被称为“朽土”;“牛肉”在贵州方言中被称为“羊头肉”。
3.2 特色词汇贵州方言中还有一些特色词汇,这些词汇在普通话中并不常见。
例如,“火锅底料”在贵州方言中被称为“麻辣”。
4. 语法特点贵州方言的语法也有一些特点。
4.1 主谓宾语的顺序贵州方言中,主谓宾语的顺序与普通话有所不同。
在普通话中,宾语通常放在谓语动词之后,而在贵州方言中,宾语通常放在谓语动词之前。
4.2 复句的连接词在贵州方言中,复句的连接词常常省略。
例如,“我去买菜,你去做饭”在贵州方言中可以简化为“我去买菜,你做饭”。
5. 方言变异由于贵州省地域辽阔,贵州方言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
例如,贵阳方言和遵义方言的发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
6. 方言保护与传承方言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贵州方言也面临着濒危的情况。
为了保护贵州方言,相关部门和机构加大了方言传承的力度。
通过开设课程、组织方言比赛和活动等方式,致力于贵州方言的传承和发展。
贵州方言话大全句子

贵州方言,又称黔语,是汉语方言之一,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及周边地区。
由于地域广大,方言内部存在许多差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贵州方言句子:
1. 你这人真有意思,我好喜欢和你聊天。
2. 别怕,有我在呢。
3. 今天的天气真好,我们去爬山吧。
4. 你吃饭了吗?
5. 这个问题我不会,你能教我吗?
6.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家?
7. 这个地方真美,我想多待一会儿。
8. 你的作业做得怎么样了?
9.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10. 这个菜真好吃,你做的吗?
11. 你别担心,我会帮你的。
12. 你怎么这么瘦啊?
13. 今天的比赛真精彩,你觉得呢?
14. 我们一起去吧,人多热闹。
15. 你喜欢吃辣的吗?
16. 这个地方真吵,我们换个地方吧。
17. 你今天穿的衣服真好看。
18. 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
19. 我们一起去看日出吧。
20. 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
这些句子只是贵州方言中的一部分,实际上贵州方言非常丰富多样。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贵州方言的知识,可以查阅相关的书籍或者请教当地的贵州朋友。
贵州方言节目存在的价值—大方话

贵州方言节目存在的价值—大方话
贵州方言节目有助于保护传承方言。
方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语言遗产。
在现代社会的大环境下,方言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和侵蚀。
贵州是中国方言区域的重要一部分,承载着丰厚的方言文化。
方言节目可以通过呈现方言的生动形象和艺术表现形式,促进了方言的传播和传承,激发了民众对方言的兴趣和关注,为方言的保存和传承提供了有力的保护。
贵州方言节目有助于促进地方文化的发展。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
方言节目不仅包含了方言的语言特色,还融入了独特的音乐、舞蹈、戏曲等表演形式,展现了贵州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魅力。
这样的节目不仅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有助于推动贵州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地方经济增添了新的动力。
贵州方言节目有助于增强地方认同感。
方言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共同语言,是人们的情感纽带。
方言节目通过表演和传播方言,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方言所承载的地方文化和历史。
观众们在欣赏方言节目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自己与这个地方的联系和归属感,从而增强了对贵州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这种认同感和自豪感不仅有助于塑造乡土精神,还对地方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有着重要意义。
贵州方言节目还具有文化交流和交流的价值。
作为方言区的重要一部分,贵州拥有着独特的方言和文化特色。
方言节目可以通过表演和传播方言,让外地观众更好地了解和感受贵州的方言文化和民俗风情,促进了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和交流。
方言节目也为贵州的文化产业走出去提供了契机,扩大了贵州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贵州方言

贵州方言- 相关介绍西南官话又称上江官话。
分布在中国西南的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北几乎全部汉语地区、以及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广西北部和湖南西北部、南部(与土话并用)。
于西藏军分区隶属于成都军区,大多数官兵来源于云贵川渝,同时由于地缘因素,西藏人民同西南人接触最多,他们在非课堂中学习的汉语也是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由于内部一致性较高(主要是声调调形的同一性较高),彼此都能接受对方的口音,所以通用贵州方言性较广。
西南官话是中国除了普通话之外覆盖人口最多、占地面积最广的方言,据统计使用西南官话的人口约2亿,占全国人口的1/5,整个官话人口的1/3,并且相当于湘语、粤语、闽语人口的总和。
民国初年曾以一票之差落选于北平官话,差点成为中国国语。
当时候选的3个方言是西南官话、北平官话、广东话。
广东话是最接近古代的,因为孙中山自己是广东人,为了利于联合北方政府,他排除了广东话成为国语的可能,而西南官话以一票之差败于北平官话。
编辑本段回目录贵州方言- 发音特点大部分字发音和普通话一样,只是调稍微变变。
由于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现在贵州话有被普通话同化的倾向。
很多人讲的贵州话中,好多韵母发音逐渐普通话化,地方特色的土话辞藻也正逐渐消失。
你只要把普通话的1、2、3、4声按1、3、4、2声来读基本上你通行云贵川了。
贵州话四川话云南话虽然差不多,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一般非西南地区人分不出。
最明显的就是四川话吐字清楚,一个字一个字都咬的清楚,而贵州话连读比较多(例:你家[li-a]、哪样[la-ang]、这个[zi-o])。
还有一个词:什么。
在四川叫啥子[sa:'zi],在贵州和广西北部叫朗子[la-ang'zi](哪样子),在湖北和湖南西部叫么子[mo:'zi]。
声调也是4声部,不过是把普通话的二声读得有点象三声,没有转弯,后面婉转的部分省略了;三声读得有点象四声,但不完全类似;四声读得有点象二声,几乎没差异。
贵州方言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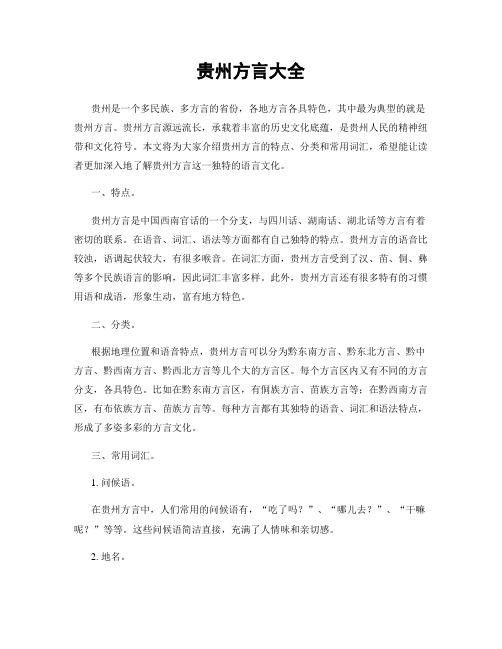
贵州方言大全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省份,各地方言各具特色,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贵州方言。
贵州方言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是贵州人民的精神纽带和文化符号。
本文将为大家介绍贵州方言的特点、分类和常用词汇,希望能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贵州方言这一独特的语言文化。
一、特点。
贵州方言是中国西南官话的一个分支,与四川话、湖南话、湖北话等方言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贵州方言的语音比较浊,语调起伏较大,有很多喉音。
在词汇方面,贵州方言受到了汉、苗、侗、彝等多个民族语言的影响,因此词汇丰富多样。
此外,贵州方言还有很多特有的习惯用语和成语,形象生动,富有地方特色。
二、分类。
根据地理位置和语音特点,贵州方言可以分为黔东南方言、黔东北方言、黔中方言、黔西南方言、黔西北方言等几个大的方言区。
每个方言区内又有不同的方言分支,各具特色。
比如在黔东南方言区,有侗族方言、苗族方言等;在黔西南方言区,有布依族方言、苗族方言等。
每种方言都有其独特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方言文化。
三、常用词汇。
1. 问候语。
在贵州方言中,人们常用的问候语有,“吃了吗?”、“哪儿去?”、“干嘛呢?”等等。
这些问候语简洁直接,充满了人情味和亲切感。
2. 地名。
贵州方言中的地名常常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比如“都匀”(读作du1 yun2)、“凯里”(读作kai3 li3)等。
这些地名的发音和普通话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贵州方言的独特之处。
3. 食物。
在贵州方言中,食物的名称也有很多特色,比如“酸汤鱼”(读作suan1 tang1 yu2)、“酸汤米粉”(读作suan1 tang1 mi3 fen3)等。
这些食物的名称生动形象,让人忍不住垂涎三尺。
四、结语。
贵州方言作为贵州特有的语言文化,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是贵州人民的精神家园。
通过本文的介绍,相信读者对贵州方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和传承贵州方言这一宝贵的语言文化遗产。
外地人不可不知的贵州土话

外地人不可不知的贵州土话1、在贵州,有一种拳法叫一定子!2、在贵州,有一种流话叫小丝儿!3、在贵州,有一种问法叫克不克!4、在贵州,有一种街头小吃叫洋芋陀陀5、在贵州,有一种情绪叫老火。
6、在贵州,有一种惊讶叫妈也。
7、在贵州,有一种台阶叫坎坎。
8、在贵州,有一种蛮不讲理叫横得很。
9、在贵州,有一种回忆叫啊些年生。
10、在贵州,有一种人叫砍脑壳的。
11、在贵州,有一种未来叫二天。
12、在贵州,有一种丢失叫“打落了”。
13、在贵州,有一种形容叫怪迷日眼。
14、在贵州,有一种加油叫斩劲点。
15、在贵州,有一种欺骗叫你喝我。
16、在贵州,有一种武功叫一窝脚。
17、在贵州,有一种丑陋叫鬼头刀霸!18、在贵州,有一种等待叫等一哈儿。
19、在贵州,有一种部位叫手倒拐。
20、在贵州,有一种悲剧叫拐了。
21、在贵州,有一种开心叫把老子笑惨了。
22、在贵州,有一种死亡叫“翘脚”。
23、在贵州,有一种野味叫八一瓜。
24、在贵州,有一种糊涂叫脑壳头进水了。
25、在贵州,有一种傻瓜叫哈批。
26、在贵州,有一种AA制叫打平伙。
27、在贵州,有一种气愤叫鬼火戳。
28、在贵州,有一种闭嘴叫阴倒起。
29、在贵州,有一种过去叫江江儿。
30、在贵州,有一种蟑螂叫偷油婆。
31、在贵州,有一种食品叫糟海椒。
32、在贵州,有一种糯米饼叫油炸巴。
33、在贵州,有一种鬼怪叫麻猫。
34、在贵州,有一种不要叫稀奇。
35、在贵州,有一种错误叫哦喝。
贵州的文化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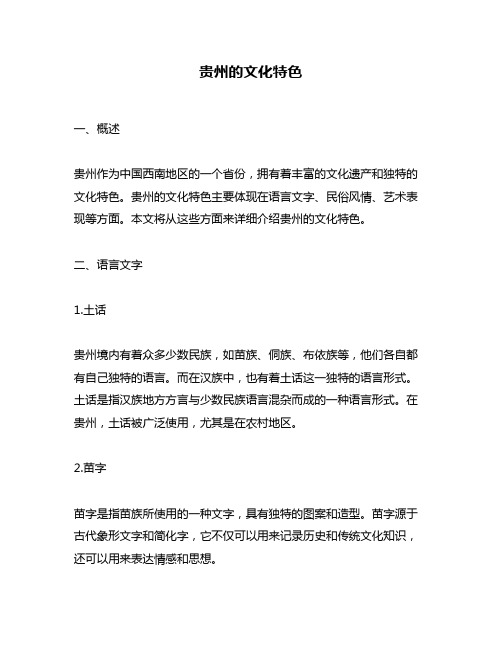
贵州的文化特色一、概述贵州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省份,拥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文化特色。
贵州的文化特色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字、民俗风情、艺术表现等方面。
本文将从这些方面来详细介绍贵州的文化特色。
二、语言文字1.土话贵州境内有着众多少数民族,如苗族、侗族、布依族等,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
而在汉族中,也有着土话这一独特的语言形式。
土话是指汉族地方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混杂而成的一种语言形式。
在贵州,土话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2.苗字苗字是指苗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具有独特的图案和造型。
苗字源于古代象形文字和简化字,它不仅可以用来记录历史和传统文化知识,还可以用来表达情感和思想。
三、民俗风情1.节日庆典贵州拥有着众多节日庆典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花灯节”和“苗族三月三”。
花灯节是贵州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举行。
届时,各地民众都会制作各种形状的花灯,进行游行和展览。
而苗族三月三则是苗族人民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通常在农历三月初三举行。
届时,人们会穿上盛装,进行舞蹈、歌唱、打鼓等各种活动。
2.服饰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非常独特,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例如苗族女子的服装上常常绣有各种图案和花纹,而侗族女子则喜欢在头发上插入银质首饰。
四、艺术表现1.音乐舞蹈贵州地区的音乐舞蹈非常多样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苗族舞蹈和侗族歌舞。
苗族舞蹈以跳高脚为主要特色,跳起来轻盈优美;而侗族歌舞则以婉转悠扬为主要特色。
2.手工艺品贵州地区的手工艺品也非常有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苗绣和侗银。
苗绣是苗族女子的传统手工艺,以其精湛的技艺和丰富多彩的图案而闻名于世;而侗银则是侗族人民传统的银饰制作工艺,以其华丽精致而著称。
五、结语贵州地区拥有着独特的文化特色,这些特色不仅体现了当地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成为了中华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了解贵州的文化特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多样性,并进一步推动各个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和融合。
论贵州汉语“标志性方言”的阙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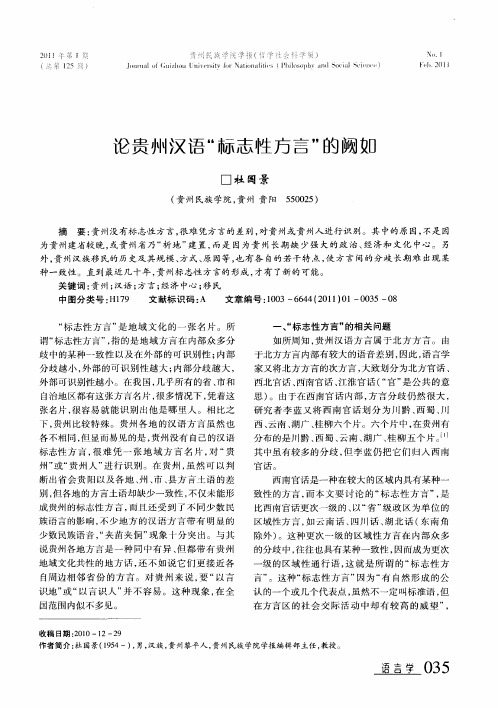
一
、
如 所周 知 , 州 汉语 方 言 属 于北 方 方 言 。 由 贵 于北方 方 言 内部 有较 大 的语 音差别 , 因此 , 言 学 语 家 又将 北方 方言 的次 方 言 , 致划 分 为北方 官话 、 大 西北 官 话 、 南官 话 、 西 江淮 官 话 ( 官 ” 公 共 的 意 “ 是 思) 。由于在 西南 官 话 内部 , 言 分歧 仍 然 很 大 , 方 研 究 者 李 蓝 又 将 西 南 官话 划 分 为 川 黔 、 蜀 、 西 川 西、 云南 、 广 、 柳六 个 片 。六 个 片 中 , 湖 桂 在贵 州有 分布 的是 川黔 、 蜀 、 南 、 广 、 柳 五 个 片 。 西 云 湖 桂 … 其 中虽有 较 多 的分 歧 , 李 蓝 仍 把 它 们 归人 西 南 但
2 l f l≯ 0 l 尊
鼍 譬 擘 学 缸 ( 掌 ■0 拿 ) 0
j1 d o ( I f( l ol l vri r st v Nai n l i s f ' i s t I “ o t a “ tl ol o C t lo e } Ⅲt ( S ‘ )
Nl.1 1
( 警 l5 垮) 2 j
} }2 、J. O1 f
论 贵 州 汉 语 “ 志 性 方 言 " 阙如 标 的
口 杜 国 景
( 州 民族 学 院 , 州 贵 阳 5 0 2 ) 贵 1 贵 5 0 5
摘
要 : 州没有标 志性方 言 , 难 凭方 言的 差别 , 贵 很 对贵 州或 贵 州人进 行识 别 。其 中的原 因 , 不是 因
为 贵 州建省较 晚 , 或贵 州省 乃 “ 地 ” 置 , 析 建 而是 因为 贵 州长 期 缺 少强 大 的政 治、 济 和 文化 中心。 另 经 外 , 州汉族移 民的历 史及 其规模 、 贵 方式 、 因等 , 有 各 自的若 干特 点 , 方 言 间 的分 歧 长 期难 出现 某 原 也 使
贵州方言节目存在的价值—大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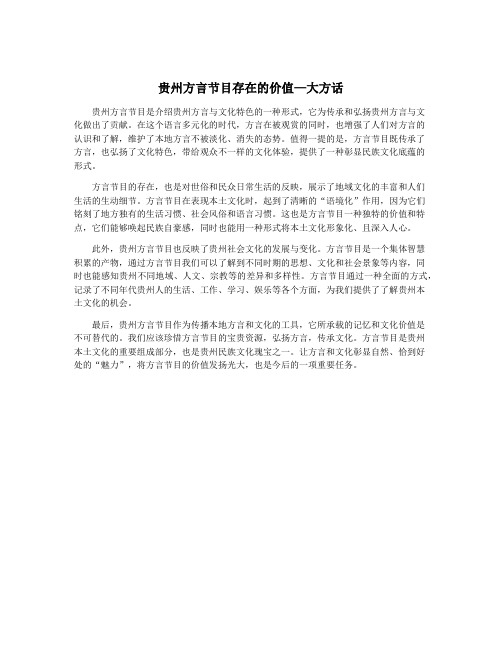
贵州方言节目存在的价值—大方话
贵州方言节目是介绍贵州方言与文化特色的一种形式,它为传承和弘扬贵州方言与文
化做出了贡献。
在这个语言多元化的时代,方言在被观赏的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方言的
认识和了解,维护了本地方言不被淡化、消失的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方言节目既传承了
方言,也弘扬了文化特色,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文化体验,提供了一种彰显民族文化底蕴的
形式。
方言节目的存在,也是对世俗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反映,展示了地域文化的丰富和人们
生活的生动细节。
方言节目在表现本土文化时,起到了清晰的“语境化”作用,因为它们
铭刻了地方独有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和语言习惯。
这也是方言节目一种独特的价值和特点,它们能够唤起民族自豪感,同时也能用一种形式将本土文化形象化、且深入人心。
此外,贵州方言节目也反映了贵州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方言节目是一个集体智慧
积累的产物,通过方言节目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景象等内容,同
时也能感知贵州不同地域、人文、宗教等的差异和多样性。
方言节目通过一种全面的方式,记录了不同年代贵州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等各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贵州本
土文化的机会。
最后,贵州方言节目作为传播本地方言和文化的工具,它所承载的记忆和文化价值是
不可替代的。
我们应该珍惜方言节目的宝贵资源,弘扬方言,传承文化。
方言节目是贵州
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贵州民族文化瑰宝之一。
让方言和文化彰显自然、恰到好
处的“魅力”,将方言节目的价值发扬光大,也是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_贵州话_的前世今生_王小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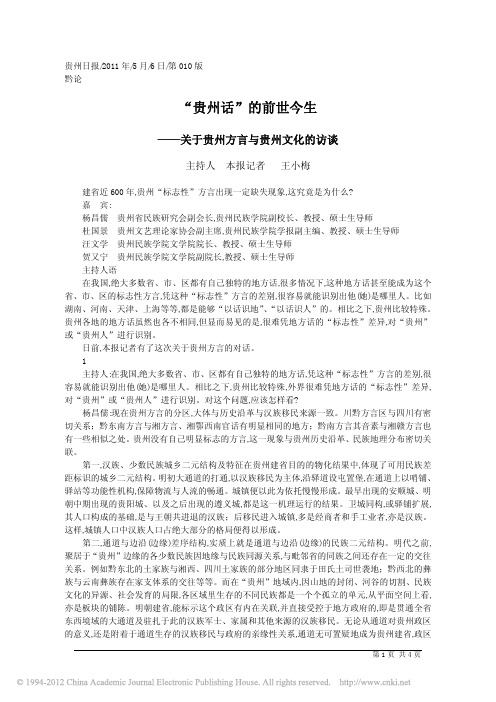
贵州日报/2011年/5月/6日/第010版黔论“贵州话”的前世今生——关于贵州方言与贵州文化的访谈主持人本报记者王小梅建省近600年,贵州“标志性”方言出现一定缺失现象,这究竟是为什么?嘉 宾:杨昌儒 贵州省民族研究会副会长,贵州民族学院副校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杜国景 贵州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副主编、教授、硕士生导师汪文学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贺又宁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人语在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话,很多情况下,这种地方话甚至能成为这个省、市、区的标志性方言,凭这种“标志性”方言的差别,很容易就能识别出他(她)是哪里人。
比如湖南、河南、天津、上海等等,都是能够“以话识地”、“以话识人”的。
相比之下,贵州比较特殊。
贵州各地的地方话虽然也各不相同,但显而易见的是,很难凭地方话的“标志性”差异,对“贵州”或“贵州人”进行识别。
日前,本报记者有了这次关于贵州方言的对话。
1主持人:在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话,凭这种“标志性”方言的差别,很容易就能识别出他(她)是哪里人。
相比之下,贵州比较特殊,外界很难凭地方话的“标志性”差异,对“贵州”或“贵州人”进行识别。
对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看?杨昌儒:现在贵州方言的分区,大体与历史沿革与汉族移民来源一致。
川黔方言区与四川有密切关系;黔东南方言与湘方言、湘鄂西南官话有明显相同的地方;黔南方言其音素与湘赣方言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贵州没有自己明显标志的方言,这一现象与贵州历史沿革、民族地理分布密切关联。
第一,汉族、少数民族城乡二元结构及特征在贵州建省目的的物化结果中,体现了可用民族差距标识的城乡二元结构。
明初大通道的打通,以汉族移民为主体,沿驿道设屯置堡,在通道上以哨铺、驿站等功能性机构,保障物流与人流的畅通。
城镇便以此为依托慢慢形成。
最早出现的安顺城、明朝中期出现的贵阳城、以及之后出现的遵义城,都是这一机理运行的结果。
贵州方言节目存在的价值—大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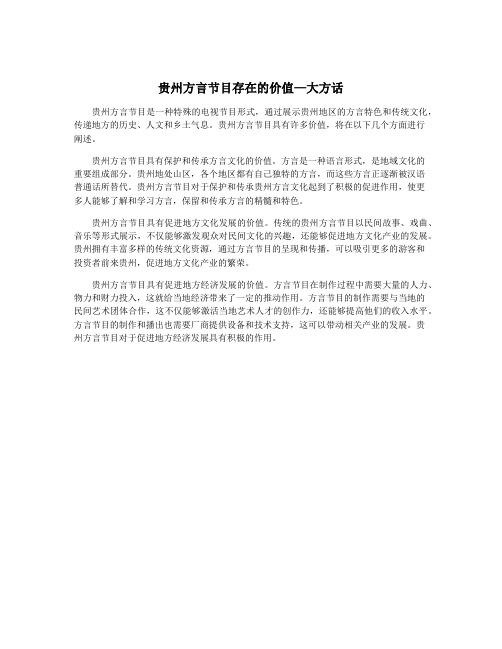
贵州方言节目存在的价值—大方话
贵州方言节目是一种特殊的电视节目形式,通过展示贵州地区的方言特色和传统文化,传递地方的历史、人文和乡土气息。
贵州方言节目具有许多价值,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阐述。
贵州方言节目具有保护和传承方言文化的价值。
方言是一种语言形式,是地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贵州地处山区,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言,而这些方言正逐渐被汉语
普通话所替代。
贵州方言节目对于保护和传承贵州方言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使更
多人能够了解和学习方言,保留和传承方言的精髓和特色。
贵州方言节目具有促进地方文化发展的价值。
传统的贵州方言节目以民间故事、戏曲、音乐等形式展示,不仅能够激发观众对民间文化的兴趣,还能够促进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
贵州拥有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方言节目的呈现和传播,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和
投资者前来贵州,促进地方文化产业的繁荣。
贵州方言节目具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价值。
方言节目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这就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方言节目的制作需要与当地的
民间艺术团体合作,这不仅能够激活当地艺术人才的创作力,还能够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方言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也需要厂商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这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贵
州方言节目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贵港文化遗产之100贵县话

贵港文化遗产之100贵县话贵港文化遗产之100 贵县话贵县话:粤语的一朵奇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方性语言是千百年来地域文化点点滴滴积累沉淀的结晶。
贵县话,即贵县土话,就是在今天贵港这片土地上贵港先人祖祖辈辈的繁衍生息的文化之根。
贵县话,属于号称我国最古老语言的活化石——粤语中的一个分支,属于粤语的范畴,但却又跟粤语的标准音——广州话相差巨大,从南宁到广州的西江沿岸操粤语的诸多城镇中,以贵县话最为独特,可以这样讲,贵县话源自粤语,却又独自发展成具有浓郁特色腔调的地域性方言,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粤方言中的一朵奇葩。
这朵粤方言的奇葩,跟贵港的历史、地理、文化密切相关。
贵县话,民间分为“街里话”和“村里话”,所谓的“街里话”,是指原来贵县县城的县东街(县前街、仁东街合并)、西五街(西街、五长巷合并)、棉新街、永明街、榕兴街这几条老城区街道、以及三合、登龙桥、震塘、南平、南斗、小江、南江等附城四厢的居民所讲贵县话为代表,又称“贵县街话”,使用人口约10万人。
所谓的“村里话”是指除城区外其他乡镇,包括郁江沿岸诸乡镇,南岸片区诸乡镇居民所讲的贵县话,使用人口尚无准确数据,根据市辖三区190万户籍人口,按贵港三大语言贵县话、客家话、壮话“三分贵县”的比例推算,操“村里话”的贵县话人口约有40-50万人。
尽管如此,使用人数占多数的“村里话”并没有成为贵县话的标准音,恰恰是使用人数不占优势“街里话”成为贵县话的代表,即平时人们所说的“贵县话”是与“贵县街话”划等号的。
关于贵县话的研究与探讨,许多语言学者达人都有专文论述。
现简单汇集各家的观点:一是古典性,贵县话既属于粤语一支,即存在与古汉语的共通性,像古文“凭栏处,怒发冲冠”,贵县话“勿要凭我膊头喂,咖喱难睇”,其中的“凭”、“膊”、“睇”都是古文字,其古义与今意仍共通,体现了贵县话的古汉语遗存。
二是地域性,贵县话与其他粤方言支系一样,都具有其独特的一面,如“苏甲”,即意为“有盔甲的害虫”,形象的描述与恐龙同时代并生存至今的蟑螂;如“蚊零”、“蚊默”,用来形容体形极细小的蚊虫类。
贵州方言节目存在的价值—大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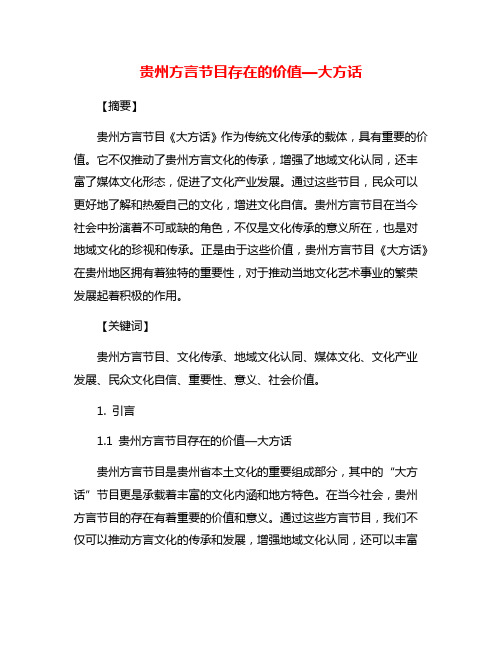
贵州方言节目存在的价值—大方话【摘要】贵州方言节目《大方话》作为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具有重要的价值。
它不仅推动了贵州方言文化的传承,增强了地域文化认同,还丰富了媒体文化形态,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
通过这些节目,民众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热爱自己的文化,增进文化自信。
贵州方言节目在当今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意义所在,也是对地域文化的珍视和传承。
正是由于这些价值,贵州方言节目《大方话》在贵州地区拥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对于推动当地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贵州方言节目、文化传承、地域文化认同、媒体文化、文化产业发展、民众文化自信、重要性、意义、社会价值。
1. 引言1.1 贵州方言节目存在的价值—大方话贵州方言节目是贵州省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大方话”节目更是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
在当今社会,贵州方言节目的存在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这些方言节目,我们不仅可以推动方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增强地域文化认同,还可以丰富媒体文化形态,促进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能增进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
“大方话”节目作为贵州方言节目的代表,不仅在语言和音调上展现了浓厚的地方特色,更将当地的民俗风情、传统文化等内容融入为观众呈现出一幅生动的贵州乡土画卷。
通过这些节目,不仅让年轻一代了解和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更多人了解贵州这片土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
贵州方言节目的存在对于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激发人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同时也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到文化传承和保护的行列中来。
2. 正文2.1 推动方言文化传承推动方言文化传承是贵州方言节目存在的重要价值之一。
通过这些节目,贵州本地方言得以传播和保留,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方言,增进对方言的热爱和认同。
方言节目也为广大方言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通过节目内容的丰富多样性,大家可以更好地体验和感受贵州方言的魅力,促进方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贵州八条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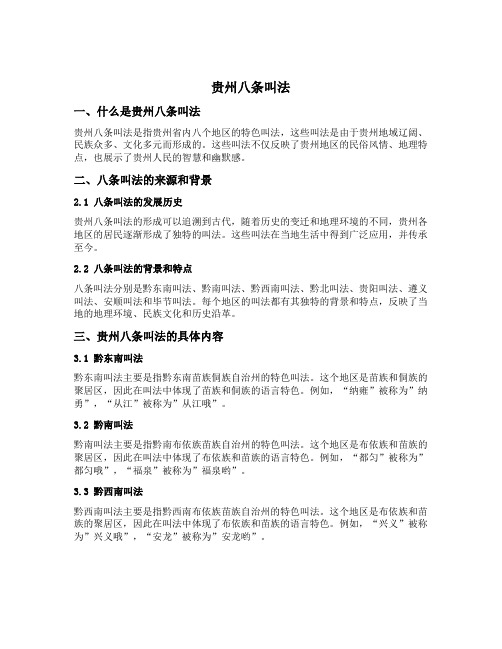
贵州八条叫法一、什么是贵州八条叫法贵州八条叫法是指贵州省内八个地区的特色叫法,这些叫法是由于贵州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而形成的。
这些叫法不仅反映了贵州地区的民俗风情、地理特点,也展示了贵州人民的智慧和幽默感。
二、八条叫法的来源和背景2.1 八条叫法的发展历史贵州八条叫法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古代,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贵州各地区的居民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叫法。
这些叫法在当地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并传承至今。
2.2 八条叫法的背景和特点八条叫法分别是黔东南叫法、黔南叫法、黔西南叫法、黔北叫法、贵阳叫法、遵义叫法、安顺叫法和毕节叫法。
每个地区的叫法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特点,反映了当地的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和历史沿革。
三、贵州八条叫法的具体内容3.1 黔东南叫法黔东南叫法主要是指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特色叫法。
这个地区是苗族和侗族的聚居区,因此在叫法中体现了苗族和侗族的语言特色。
例如,“纳雍”被称为”纳勇”,“从江”被称为”从江哦”。
3.2 黔南叫法黔南叫法主要是指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特色叫法。
这个地区是布依族和苗族的聚居区,因此在叫法中体现了布依族和苗族的语言特色。
例如,“都匀”被称为”都匀哦”,“福泉”被称为”福泉哟”。
3.3 黔西南叫法黔西南叫法主要是指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特色叫法。
这个地区是布依族和苗族的聚居区,因此在叫法中体现了布依族和苗族的语言特色。
例如,“兴义”被称为”兴义哦”,“安龙”被称为”安龙哟”。
3.4 黔北叫法黔北叫法主要是指黔北地区的特色叫法。
这个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因此在叫法中体现了多民族的语言特色。
例如,“赤水”被称为”赤水哦”,“仁怀”被称为”仁怀哟”。
3.5 贵阳叫法贵阳叫法主要是指贵阳市的特色叫法。
作为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叫法体现了贵州省的汉族文化和地理特点。
例如,“花溪”被称为”花溪哦”,“观山湖”被称为”观山湖哟”。
3.6 遵义叫法遵义叫法主要是指遵义市的特色叫法。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贵州话”的前世今生——关于贵州方言与贵州文化的访谈主持人:贵州日报记者王小梅嘉宾:杨昌儒贵州省民族研究会副会长,贵州民族学院副校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杜国景贵州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副主编、教授、硕士生导师汪文学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贺又宁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绘图/陈柏融主持人语在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话,很多情况下,这种地方话甚至能成为这个省、市、区的标志性方言,凭这种“标志性”方言的差别,很容易就能识别出他(她)是哪里人。
比如湖南、河南、天津、上海等等,都是能够“以话识地”、“以话识人”的。
相比之下,贵州比较特殊。
贵州各地的地方话虽然也各不相同,但显而易见的是,很难凭地方话的“标志性”差异,对“贵州”或“贵州人”进行识别。
日前,本报记者有了这次关于贵州方言的对话。
杨昌儒(绘图/陈柏融)1主持人:在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话,凭这种“标志性”方言的差别,很容易就能识别出他(她)是哪里人。
相比之下,贵州比较特殊,外界很难凭地方话的“标志性”差异,对“贵州”或“贵州人”进行识别。
对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看?杨昌儒:现在贵州方言的分区,大体与历史沿革与汉族移民来源一致。
川黔方言区与四川有密切关系;黔东南方言与湘方言、湘鄂西南官话有明显相同的地方;黔南方言其音素与湘赣方言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贵州没有自己明显标志的方言,这一现象与贵州历史沿革、民族地理分布密切关联。
第一,汉族、少数民族城乡二元结构及特征在贵州建省目的的物化结果中,体现了可用民族差距标识的城乡二元结构。
明初大通道的打通,以汉族移民为主体,沿驿道设屯置堡,在通道上以哨铺、驿站等功能性机构,保障物流与人流的畅通。
城镇便以此为依托慢慢形成。
最早出现的安顺城、明朝中期出现的贵阳城、以及之后出现的遵义城,都是这一机理运行的结果。
卫城同构,或驿铺扩展,其人口构成的基础,是与王朝共进退的汉族;后移民进入城镇,多是经商者和手工业者,亦是汉族。
这样,城镇人口中汉族人口占绝大部分的格局便得以形成。
第二,通道与边沿(边缘)差序结构,实质上就是通道与边沿(边缘)的民族二元结构。
明代之前,聚居于“贵州”边缘的各少数民族因地缘与民族同源关系,与毗邻省的同族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交往关系。
例如黔东北的土家族与湘西、四川土家族的部分地区同隶于田氏土司世袭地;黔西北的彝族与云南彝族存在家支体系的交往等等。
而在“贵州”地域内,因山地的封闭、河谷的切割、民族文化的异源、社会发育的局限,各区域里生存的不同民族都是一个个孤立的单元,从平面空间上看,亦是板块的铺陈。
明朝建省,能标示这个政区有内在关联,并直接受控于地方政府的,即是贯通全省东西境域的大通道及驻扎于此的汉族军士、家属和其他来源的汉族移民。
无论从通道对贵州政区的意义,还是附着于通道生存的汉族移民与政府的亲缘性关系,通道无可置疑地成为贵州建省,政区功能实现的载体,其轴心线的性质与汉族移民的民族性便以地域、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强势安排,将板块拼凑的各少数民族沿中轴线再切一刀,使之在原有自我封闭的空间中更加碎片化、边缘化,以更小单元的弱势,附着在通道中轴线的边沿。
第三,民族分布区域自然环境差异性结构。
例如,黔西北建省前以彝族为主要民族的区域特征,到清末时已经变为汉夷杂处、以汉为主的民族区域性特征。
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虽在明清500年变迁中民族主体未变,但其经济活动方式已经从建省前单一型农耕变为林粮兼种的立体型开发。
黔中地区建省前是多个少数民族杂居相处,在不同海拔高度的土地上粗放耕作,清末以降,黔中地区则变为汉族作为主要民族,商贸也逐渐发展,成为西南重要商品集散地之一。
杜国景:贵州“标志性”地方方言缺失的后面,值得关注的问题太多。
夸张一点说,贵州“标志性”地方话的缺失,对民族学、人类学、方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学科而言,恰恰凸显了一种“活化石”的“标志性”价值。
因为任何一种“标志性”的地方方言的形成,总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总会蕴含着太多的、超乎语言史意义的信息,而在贵州,建省近600年,这种“标志性”地方话居然没有形成,这究竟是为什么?一种“标志性”地方话的形成,除了语言自身和文化因素,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如,一个地区性行政中心的建立,对一种“标志性”地方话的形成究竟能产生怎样的作用?这种“标志性”地方话一旦形成,又将给予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怎样的影响?语言(方言)是独立于社会,还是服务于社会?总之,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值得去研究的,这是“贵州建省六百年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
对贵州“标志性”地方方言缺失的研究,大致属于社会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范畴。
它所关注的主要不是句子或篇章,不是语言本体,而是要通过语言来解释社会文化。
尤其在建省较晚的贵州。
在贵州不同文化的碰撞里,在移民社会的语言渗透里,在语言不平等和政治权力大小的关系里,在多民族地区的交往用语里,或许都能为一种“标志性”地方方言的形成亦或缺失寻到某种答案,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杜国景(绘图/陈柏融)2主持人:贵州方言和贵州人的文化身份有什么关系?杜国景:毫无疑问,贵州“标志性”方言的缺失,会给贵州人的文化身份带来一点尴尬,最起码会导致文化自信的缺失。
这是因为,方言总是忠实地反映着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积淀。
或者说,方言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本身即可被看作一种文化载体,具很强的文化凝聚力。
所谓强势方言与弱势方言之区分,除了使用人数多寡,传播与分布范围大小外,它本身所反映的经济文化成就,也是一个不可忽略因素。
一段时间以来,“粤语”行情看涨,就是与珠三角地区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分不开的。
相比之下,弱势方言心理凝聚力与文化整合力则比较有限。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贵州方言与贵州人的文化身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民族想象关系,由于没有“标志性”或“代表性”地方方言的整合,贵州各地的方言往往自成体系,且发展不平衡,很多时候,这些方言是在受着不同的民族语言的改造和整合,这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只是如此一来,“标志性”方言的缺失也就不可避免了。
贺又宁(绘图/陈柏融)3主持人:贵州方言的特点是什么?有什么区别于四川、云南方言的现象和例子?贺又宁:在我国八大方言的划分中,贵州、四川、云南都属“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区。
贵州、云南、四川话过去都叫“西南官话”,也叫“上江官话”。
“上江”是长江上游的意思,“官话”则指官方标准话,也含有文雅、正式、通行或流行的意思,所以古代官话又被称为雅言、雅音、通语、正音。
明清以后才称官话,清代、民国称为国语,1956年改称普通话。
除了贵州、四川、云南,西南官话还分布在湖北、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广西北部和湖南西北部、南部。
西南官话由于内部一致性较高(主要是声调调形的同一性较高),彼此都能接受对方的口音,所以通用性较广。
贵州方言可以分为三个次方言:川黔方言、黔东南方言和黔南方言。
川黔方言分布最广,覆盖贵州省北部、西北部、西部、西南部、中部以及东北部。
贵阳、遵义、安顺、毕节、六盘水、兴义等,以贵阳话为代表;黔东南方言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州大部分地区和铜仁部分地区,以凯里话为代表;黔南方言主要分布在黔南州大部分地区和黔东南小部分地区,以都匀话为代表。
除此之外,贵州境内还有几个所谓的“方言岛”:安顺二铺一带的“屯堡话”,黔东南天柱的“酸汤话”,黔西南晴隆、普安的喇叭话,它们在特征上比较接近湘、赣方言。
贵州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以贵阳话、凯里话、都匀话为例:贵阳话的主要语音特征是声母不分平翘舌、边鼻音,前后鼻韵母有部分混淆等,如贵阳话中,周/邹、吃/词、诗人/私人、女客/旅客、鲇鱼/鲢鱼。
贵阳话还有一系列“方言土词”,从而形成自己的词语特征。
例如:悄悄咪咪勒,我走哦!就呛我悄悄咪咪嘞来!我轻轻地甩哈衣袖,不带走一坨云!语法方面,贵阳话的特征是有特殊的重叠词、有特殊的“把字句”,如:瓢瓢,碗碗,盒盒,杯杯。
他把来哦。
玻璃把烂哦。
凯里话:主要语音特征是除了同样不分平翘舌,鼻、边音有混淆,前后鼻韵母有部分不分之外,典型的特征有“h”、“f”在某些词语发音中混淆。
例如:地方/地荒、发红/花红、凡是/环视、花费/花卉。
都匀话:在语音上突出的特征在于有“腭化辅音”,没有“an”类韵母等。
贵州方言与四川、云南等方言在语法上区别不明显,在语音上“声调”较为一致,“声母”区别也不很突出,韵母的区别相对明显一点。
如,“an——ang”:贵阳话区分很清楚,四川、云南方言不是很清晰,再如,四川方言有“儿化”,贵州大部分地区没有。
贵州方言与四川、云南方言区别最明显的应该是“词汇”,三地方言均存在特色土语。
这些特色土语,正是它们的标志。
汪文学(绘图/陈柏融)4主持人:看来,地方方言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息息相关。
汪文学:一个文化自我认同意识比较强的民族或群体,当他们谈及自己的文化时,必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或者说,文化的自我认同意识与文化上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是成正比关系的。
老实说,长期以来,贵州人对贵州文化是缺乏自觉意识的,因此其文化上的自我认同意识也是比较淡薄的,这主要在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心。
钱理群先生在《贵州读本》“前言”中说:“鲁迅当年曾经谈到,近代以来,中国常常处于‘被描写’的地位,这是一个弱势民族、弱势文化在与强势民族、强势文化遭遇时经常面对的尴尬。
而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中,贵州文化也是一种弱势文化,也会面对‘被描写’或根本被忽视的问题。
这正是许多贵州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人们对贵州岂止是陌生,更有许多误会与成见,并形成了有形无形的心理压力;而黔人的‘自我陌生’则造成了文化凝聚力的不足,更是贵州开发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是每一位思考贵州文化发展的贵州人都应当认真面对和反思的问题。
加强贵州文化建设,重塑贵州文化形象,彰显贵州文化的优势和特色,建立贵州人对贵州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认同,这是当代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杜国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广大观众对赵本山的小品和《乡村爱情》等电视连续剧的追捧,“东北话”行情看涨,各地方言剧一时热闹起来,这其中就有同属西南官话次方言区的四川、重庆的影视剧,李伯清的散打评书,昆明的方言动画片《小米喳》等。
也许正是受着这股潮流的推动,贵州的一些媒体也相继陆续推出了一批大致是“以贵州中部语音为标准音、以贵阳话为基础方言”的频道、栏目、电视剧、影视配音、音频或视频广告,欲打造“贵州方言”品牌,如早期的《天天摆故事》,后来的《蓝色档案》,2010年的中天城投杯多彩贵州小品大赛中的“黔味小品”等,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化自觉”的信号,表面看它与“推广普通话”是矛盾的,但它所传达的那种贵州人的文化自信,还是让人精神一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