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致许广平的情书
名人写的书信

名人写的书信读着鲁迅的书信,就仿佛穿越时空,与这位文学巨匠进行了一场奇妙的对话。
我记得有一次在旧书摊淘宝,在那一堆泛黄的书籍里,我偶然翻到了一本收录鲁迅书信的集子。
当时只是好奇地翻开,没想到这一翻就陷了进去。
其中有一封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那字里行间满是深情与关切。
我仿佛看到鲁迅坐在那有些昏暗的书桌前,手中握着笔,眉头时而微微皱起,像是在斟酌用词。
他在信里提到生活中的琐事,说自己近日身体有些不适,去看了医生,那医生的模样和说的话他都细细地写了下来,“那大夫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透着一股严肃,把了脉,便摇头晃脑地说需得好好调养,不可再过度劳累。
我听了只是笑笑,这忙碌的世间,哪能轻易停歇。
”从这些文字里,我能感受到他的疲惫,也能感受到许广平在他心中的特殊地位,他愿意把自己的脆弱与日常分享给她。
还有他写给友人的信,谈论着当时的文学界。
他对一些不良现象的批判毫不留情,“那些个文人,为了些许名利,便写出些无病呻吟的文字,就如同那没有根基的浮萍,看似繁茂,实则一戳就破。
”我似乎能看到他写信时的义愤填膺,手中的笔力透纸背。
他在信里也会推荐一些好书,讲述自己阅读时的感悟,“近日读了一本古籍,其中的智慧深邃得如同那无尽的夜空,每翻一页都有新的思索。
”这一封封信,就像一扇扇通往过去的窗。
让我看到了鲁迅在文学创作之外的生活、情感与思想。
他不仅仅是那个在文章里犀利无比的战士,也是一个会生病、会有烦恼、会对友人倾诉的普通人。
这些书信让他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也让我深深着迷于那个时代的故事与情感。
我想,这就是名人书信的魅力吧,它能让岁月的尘埃散去,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民国最美的情书句子

民国最美的情书句子1、沈从文致张兆和我一辈子走过很多地方的路,行过很多地方的桥,看过很多样子的云,喝过很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值最好年龄的人。
2、鲁迅致许广平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爱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
3、朱湘致刘霓君妹妹,你的信我都好好收起,注明号码。
哪封是哪天发的,哪天到,我都写得明明白白,好带回家去。
我们肩并着肩的从头细看,细数这五年的离情别意。
4、徐志摩致陆小曼我爱你朴实,不爱你奢华。
你穿上一件蓝布袍,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荣,我看了心里就觉着无可名状的高兴。
朴实是真的名贵。
你穿戴整齐的时候当然是好看,但那好看是寻常的,人人都认得的。
素服时的美,有我独到的领会。
5、朱生豪致宋清如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肯定很可爱。
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
6、丁玲致胡也频有你一切都好,有你爱我,我真美好,我会写文章的。
而且我确定安心等到暑假再和你相聚,照我们的`打算去做,而且也决心,也宣誓以后再不离开了。
7、胡兰成致张爱玲梦醒来,我身在忘川,立在属于我的那块三生石旁,三生石上只有爱玲的名字,可是我看不到爱玲你在哪儿,原是今生今世已惘然,山河岁月空惆怅,而我,终将是要等着你的。
8、朱自清致陈竹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糊涂起来,我更喜爱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感谢你给我力气。
9、白薇致杨骚你来!我们同游奇山,去洗温泉不好么?早晚一块儿往群芳竞放的原野,在黄茑回啭的密林下漫步不好么?无论如何请来吧!我在等你。
10、闻一多致高孝贤妹:今日早晨起来拔了半天草,心里想到等你回来看着兴奋,荷花也放了苞,也许也要等你回来开,一切都是为你。
11、郁达夫致王映霞你所盼望我的,规劝我的话,我以后肯定牢牢的记着。
假使我将来若有一点成就的时候,那么我的这一点成就的荣耀,情愿全部归赠给你。
鲁迅在情书中向许广平发誓不看漂亮女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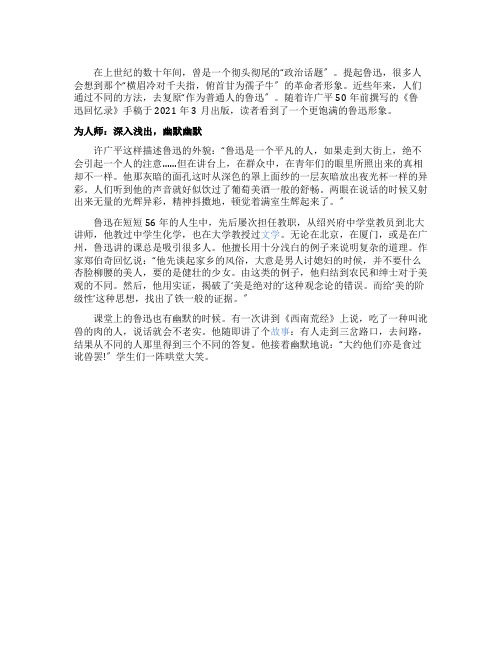
在上世纪的数十年间,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话题〞。
提起鲁迅,很多人会想到那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者形象。
近些年来,人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去复原“作为普通人的鲁迅〞。
随着许广平50年前撰写的《鲁迅回忆录》手稿于2021年3月出版,读者看到了一个更饱满的鲁迅形象。
为人师:深入浅出,幽默幽默许广平这样描述鲁迅的外貌:“鲁迅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绝不会引起一个人的注意……但在讲台上,在群众中,在青年们的眼里所照出来的真相却不一样。
他那灰暗的面孔这时从深色的罩上面纱的一层灰暗放出夜光杯一样的异彩。
人们听到他的声音就好似饮过了葡萄美酒一般的舒畅。
两眼在说话的时候又射出来无量的光辉异彩,精神抖擞地,顿觉着满室生辉起来了。
〞鲁迅在短短56年的人生中,先后屡次担任教职,从绍兴府中学堂教员到北大讲师,他教过中学生化学,也在大学教授过文学。
无论在北京,在厦门,或是在广州,鲁迅讲的课总是吸引很多人。
他擅长用十分浅白的例子来说明复杂的道理。
作家郑伯奇回忆说:“他先谈起家乡的风俗,大意是男人讨媳妇的时候,并不要什么杏脸柳腰的美人,要的是健壮的少女。
由这类的例子,他归结到农民和绅士对于美观的不同。
然后,他用实证,揭破了‘美是绝对的’这种观念论的错误。
而给‘美的阶级性’这种思想,找出了铁一般的证据。
〞课堂上的鲁迅也有幽默的时候。
有一次讲到《西南荒经》上说,吃了一种叫讹兽的肉的人,说话就会不老实。
他随即讲了个故事:有人走到三岔路口,去问路,结果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三个不同的答复。
他接着幽默地说:“大约他们亦是食过讹兽罢!〞学生们一阵哄堂大笑。
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的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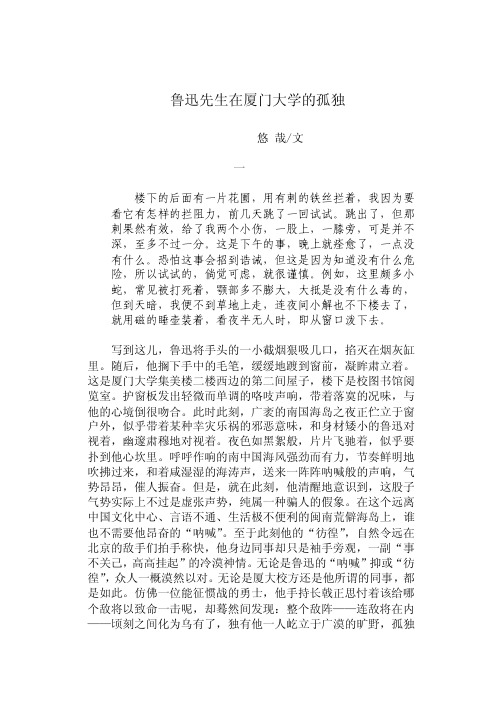
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的孤独悠哉/文一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
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给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可是并不深,至多不过一分。
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痊愈了,一点没有什么。
恐怕这事会招到诰诫,但这是因为知道没有什么危险,所以试试的,倘觉可虑,就很谨慎。
例如,这里颇多小蛇,常见被打死着,颚部多不膨大,大抵是没有什么毒的,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磁的睡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
写到这儿,鲁迅将手头的一小截烟狠吸几口,掐灭在烟灰缸里。
随后,他搁下手中的毛笔,缓缓地踱到窗前,凝眸肃立着。
这是厦门大学集美楼二楼西边的第二间屋子,楼下是校图书馆阅览室。
护窗板发出轻微而单调的咯吱声响,带着落寞的况味,与他的心境倒很吻合。
此时此刻,广袤的南国海岛之夜正伫立于窗户外,似乎带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邪恶意味,和身材矮小的鲁迅对视着,幽邃肃穆地对视着。
夜色如黑絮般,片片飞驰着,似乎要扑到他心坎里。
呼呼作响的南中国海风强劲而有力,节奏鲜明地吹拂过来,和着咸湿湿的海涛声,送来一阵阵呐喊般的声响,气势昂昂,催人振奋。
但是,就在此刻,他清醒地意识到,这股子气势实际上不过是虚张声势,纯属一种骗人的假象。
在这个远离中国文化中心、言语不通、生活极不便利的闽南荒僻海岛上,谁也不需要他昂奋的“呐喊”。
至于此刻他的“彷徨”,自然令远在北京的敌手们拍手称快,他身边同事却只是袖手旁观,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神情。
无论是鲁迅的“呐喊”抑或“彷徨”,众人一概漠然以对。
无论是厦大校方还是他所谓的同事,都是如此。
仿佛一位能征惯战的勇士,他手持长戟正思忖着该给哪个敌将以致命一击呢,却蓦然间发现:整个敌阵——连敌将在内——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了,独有他一人屹立于广漠的旷野,孤独且傲岸。
于是,他高举的手臂因举得过久而渐渐酸疼,最终不得不尴尬地垂落下来。
那些年中外作家写过的情书

那些年中外作家写过的情书我先前偶⼀想到爱,总⽴刻⾃⼰惭愧,怕不配,因⽽也不敢爱某⼀个⼈,但看清了他们的⾔⾏的内幕,便使我⾃信我绝不是必须⾃⼰贬抑到那样的⼈了,我可以爱。
1、沈从⽂沈从⽂是作家、历史⽂物研究家、京派⼩说代表⼈物。
14岁时,他投⾝⾏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
1924年开始⽂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说。
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本事1930年7⽉张兆和与沈从⽂在胡适的办公室第⼀次见⾯,刚见⾯时,胡校长⼤夸沈从⽂是天才,是中国⼩说家中最有希望的。
张兆和却不以为然,沈从⽂对张兆和的爱恋来得默然,却是⼀发不可收拾,写给她的情书⼀封接⼀封,延绵不绝地表达着⼼中的倾慕。
在1931年6⽉的⼀封信中,他以做张兆和的奴⾪为已任。
他说,多数⼈愿意仆伏在君王的脚下做奴⾪,但他只愿做张兆和的奴⾪。
最终打动了张兆和,于1933年9⽉9⽇在北京中央公园成婚。
情书⼀个⽩⽇带⾛了⼀点青春,⽇⼦虽不能毁坏我印象⾥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
⼀个⼥⼦在诗⼈的诗中,永远不会⽼去,但诗⼈他⾃⼰却⽼去了。
我想到这些,我⼗分犹豫了。
⽣命是太脆薄的⼀种东西,并不⽐⼀株花更经得住年⽉风⾬,⽤对⾃然倾⼼的眼,反观⼈⽣。
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看重⼈与⼈凑巧的藤葛。
在同⼀⼈事上,第⼆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
我⽣平只看过⼀回满⽉。
我也安慰⾃⼰过,我说:“我⾏过许多地⽅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个正当最好年龄的⼈。
2、鲁迅本事1923年秋天,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到北京⼥⼦⾼等师范学校讲课,就在这⾥认识了⼩他17岁的许⼴平。
这样的师⽣关系延续了⼀年多,直到1925年3⽉,由于许⼴平写信向鲁迅求教,他们之间才有了进⼀步的接触,原本疏远的师⽣关系才有了突破。
这些信件就是《两地书》。
起初的通信的确不带恋情,⽽是师⽣间关于社会⼈⽣诸问题的请益与教导。
来看看那些文学家是怎样表白的

来看看那些文学家是怎样表白的“我这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1930年7月,沈从文初见张兆和。
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恋一发不可收,写给她的情书一封接一封,延绵不绝地表达着心中的倾慕。
沈从文在情书中写道:“三三,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
我的自卑,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美丽。
”沈从文毫不掩饰,他近乎卑微地爱着张兆和,把她当做女神。
1933年,两人结婚。
鲁迅致许广平:“我现在只望乖姑要乖,保养自己,我也当心平气和,度过豫定的时光,不使小刺猬担忧。
”▲1923年,鲁迅与许广平相识。
简单的师生关系延续了一年多,1925年3月,许广平写信向鲁迅求教,他们之间有了进一步的接触。
从1925年到1927年,鲁迅与许广平通了135封信,亲密关系一路升温。
起初,他在信里称“广平兄”。
后来称呼慢慢变了。
先后有“乖姑”、“小刺猬”、“小莲蓬”。
许广平怀孕后,鲁迅更称他为“我的有莲子的小莲蓬”。
在另一封信里,鲁迅写道:“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
女生共五人。
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
”徐志摩致陆小曼:“你的眉目间有一种特异的光彩,我看了心里就觉着不可名状的欢喜。
……我口里低呼一声我的爱,我的心为你多跳了一下。
”▲徐志摩停妻再娶,陆小曼离婚再嫁,皆是有违封建礼教的,然而他们坚贞不移,用郁达夫的话说:“志摩热情如火,小曼温柔如棉,两人碰在一起,自然会烧成一团,哪里还顾得了伦教钢常,更无视于宗法家风。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为了赶上林徽因那天晚上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讲演,迫不及待地搭乘了一架邮政机飞往北京。
登机之前,他给陆小曼发了一封短信,信上说:“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准备返沪。
”但最终他还是走了。
因大雾影响,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徐志摩身亡。
两地书六则

《两地书》是鲁迅先生写给许广平的书信集,其中包含了鲁迅先生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经历。
以下是其中的六则:
1. “我不愿意你将来受苦,所以我现在吃苦,将来我们可以同享幸福。
”
2. “我的生命,是为了你而存在的。
”
3. “我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
4. “我的心,永远属于你。
”
5. “我爱你,不仅仅是因为你是你,而是因为我和你在一起时,我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
6. “我们的爱情,是纯洁而美好的,它像一朵花,需要我们用心去呵护和灌溉。
”
这些话语充满了鲁迅先生对许广平的真挚感情和深深爱意,也展现了他对爱情和家庭的珍视和重视。
这些话语也成为了经典的爱情名言,被人们传颂至今。
鲁迅谈冰心:一个原创性的话题

刘廷芳这首诗是1921年8月7日在庐山牯岭写的,发表之后惹怒了1919年即已登上文坛的冰心。她当日便写出了一篇短文,含蓄而愤怒地对诗作者进行谴责,题为《蓄道德能文章》,刊登于9月6日的同一报纸。紧接着,冰心所在的燕京大学一些学生以全体同学名义致函《晨报》,说同人中虽有别名冰心者,而并未收到刘廷芳的赠诗,所以这首诗的被赠者应该是另外一个同名的“冰心”,希望《晨报》予以澄清。后一情况据鲁迅原信转述,而鲁迅的消息估计来自《晨报》第七版的编者孙伏园。我在《晨报》上并未查到该项声明。
鲁迅谈冰心:一个原创性的话题.txt等余震的心情,就像初恋的少女等情人,既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 听说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回想起来,我竟然七手八脚地裸奔了二十多年!今天心情不好,我只有四句话想说,包括这句和前面的两句,我的话说完了!“鲁迅谈冰心”,这绝对是一个原创性的话题。鲁迅虽然评论过很多中国现代作家,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还没有正面谈论过冰心。但新版《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打破了这种局面。这条注释出自1921年9月11日鲁迅致周作人信。原信中有一段稀奇古怪的话,看后如读天书,不知所云:“コホソコ·コ之蓄道德云云,即指庐山叙旧而发,闻晨报社又收到该大学全体署名一信,言敝周作人中虽有别名‘ピンシン’者而未曾收到该项诗歌,然则被赠者当系别一ピンシン云云,大约不为之登出矣。夫被赠无罪,而如此龈龈,殊可笑,与女人因被调戏而上吊正无异,诚哉如柏拉图所言,‘不完全则宁无’也。”
首先破译这段“神秘密码”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社长、著名作家楼适夷。他熟悉文坛掌故,又精通日语。他发现,“コホソコ”是“冰心”二字的日语意译,而“ピンシン”是“冰心”二字的日语音译,因此这段文字肯定跟冰心有关。循着这一线索,该社的老编辑王永昌专程去北京图书馆查阅《晨报》,在当年9月4日的《晨报》第七版找到了署名刘廷芳的一首短诗:《寄冰心》。
鲁迅和爱人的信件

鲁迅和爱人的信件
鲁迅和他的爱人许广平之间有过多封情书往来。
这些信件记录了他们的感情历程和相互关怀。
以下是其中一封鲁迅写给许广平的情书:“广平兄,
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
我总喜欢挨到将近下班的时候,等你回信快来了,我跑到邮局里去看,看过还没有来,就仍跑回家。
如是者数四,信仍不来,于是死心塌地了,去看书。
过一些时候,再跑去一看——已经来了。
这欢喜,正如小儿得到糖果一样,是要跳着舞跑回家去的。
可是那一天要收到很多信,就不能常常去看,而且去看的时候,如果来了我的信,而同时有你的信呢,那也只得先看你一个人的,而且看得及看到那最后的一行,又要去等别的信了。
回来的时候又有多少信呢?便拿着饭粒黏着它们,但这些信总要一个跟着一个走,而跳来跳去的却总是别的信。
等到看着了你的信,心里好高兴,去看饭粒,却不知黏在什么地方了。
邮票也撕破了一点。
”
这封鲁迅写给许广平的情书表达了鲁迅对许广平的深深爱意和
期待。
通过描述等信的急切心情和看到来信的高兴,鲁迅展示了他对许广平的思念和关注。
这些信件是鲁迅和许广平感情的见证,也是鲁迅文学创作中温馨的一面。
民国情侣书信范文见字如晤

民国情侣书信范文见字如晤一说到情书,就会想起流行书信的年代。
那时候,没有便捷的交通,更没有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表达爱意也只能靠鸿雁传情,但在这样“落伍”的方式里,承载着满满的真情和感动。
民国时期的文人和他们的爱情故事总是为人们津津乐道,他们写给爱人的情书,更是广为流传,让人感动。
最缠绵:徐志摩致陆小曼书我爱你朴素,不爱你奢华。
你穿上一件蓝布袍,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彩,我看了心里就觉着不可名状的欢喜。
朴素是真的高贵。
你穿戴齐整的时候当然是好看,但那好看是寻常的,人人都认得的,素服时的眉,有我独到的领略。
眉,我写日记的时候我的意绪益发蚕丝似的绕着你;我笔下多写一个眉字,我口里低呼一声我的爱,我的心为你多跳了一下。
你从前给我写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形我知道,因此我益发盼望你继续你的日记,也使我多得一点欢喜,多添几分安慰。
当风流诗人徐志摩遇上一代名媛陆小曼,注定要把浪漫进行到极致。
为了博美人一笑,徐志摩用尽了毕生的才华。
即使别人都不理解,他也不在乎,只顾把炽烈的爱情化为浓烈的情话,看得小曼脸红心跳,沉醉不已,最后以身相许。
最庄重:鲁迅致许广平书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我十三日所发的明信片既然已经收到,我惟有希望十四日所发的信也接着收到。
我惟有以你现在一定已经收到了我的几封信的事,聊自慰解而已。
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
女生共五人。
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
鲁迅写杂文时都是横眉冷对,写起情书时却柔情似水。
在厦门大学任教时,他对许广平的思念与日俱增,有时甚至一天一张明信片,有什么芝麻小事都想和她分享,还主动发誓:除了你,我再也不会正眼看别的女人!。
看《鲁迅全集》---《两地书》

看《鲁迅全集》---《两地书》看《鲁迅全集》时的胡思乱想--661--《两地书》之《序言》原文节选:中国的衙门是谁都知道只要一碰着,就有多么的可怕。
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遇到横祸,大家决不另眼相看,但若坐过牢监,到过战场,则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人们也总看得特别一点。
有一同过事的同事,傲,那是没说的了,狂,那也是没说的了。
对于与他不甚友好的领导,他常常私下说,熬也熬死他。
这话在正常情况下,不假,因为自然规律就是这样,领导大他几十岁,一般是熬不过他的。
前天看一个新闻,亲孙女也对其爷爷说,熬也熬得过他,只是没有说出那个死字。
但后来,同过事的同事,却因犯事进了班房。
出来后,总结出一条,没有进过监狱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
这话说得好像完整,也好像不完整,如果把进监狱当作人生的必备一环,那么,不进监狱,的确不完整。
但如果说,什么事情都是人生必备一环,那么,谁又敢说自己的人生是完整的呢。
比如,工农商学兵这几行,是不是都干过,再扩开了说,三百六十行,是不是行行都干过,如果抬个杠,说干完三百六十行就是完整人生的话,那么,三百六十行的各个岗位是否都待过。
再抬个杠,就是都待过,那么,全世界各地的三百六十行呢?月球上呢?火星上呢?等不到我说的这些你一天干一样,恐怕到闭眼也干不完。
所以,如此所说,人生没有完整的,人生也没有完美的,人生都是有缺憾的,反过来,有缺憾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
是不是有点儿哲学的味道了。
原文节选:这一本书,在我们自己,一时是有意思的,但对于别人,却并不如此,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辞呢,我们都未曾研究过“尺牍精华”或“书信作法”,只是信笔写来,大背文律,活该进“文章病院”的居多。
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这样平凡的东西,别人大概是不会有,即有也未必存留的,而我们不然,这就只好谓之也是一种特色。
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则旧作也即飞升,连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
那些曾经动人心的经典老情书

但这次计划并未实现。接下来的 5 年, 钱学森一直被美国当局拘禁, 住所被 监视, 甚至电话也被监听。 那时, 钱学森只 能在学校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 蒋英则
在家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 那是一段屈辱
鲁迅致许广平 此刻是半夜, 却很静, 和上海 大不同。我不知乖姑( 鲁迅对许广 平的昵称) 睡了没有 , 我觉得她一 定还未睡着, 以为我正在大谈三年 的经历了. . 其实并未大谈, 我现在
的滋味… ” 圃
样长久的
梁实秋致韩菁清
凤凰5 l 火自焚, 然后有一个新 生, 、 我也是 自己捡起柴木, 煽动火
( 摘 自时代文艺出版社《 你好吗? 我
பைடு நூலகம்
很想你——许 多许 多年前的老情
书》 一书) ( 实习编辑 其偌)
, , /, >= A
只望乖姑要乖, 保养 自己, 我也当
平 心和气 , 度过 预 定的时 光 . 不使
封条
奏。 晚年的钱学森不禁感慨 : “ 每当听到蒋
英的歌声,就能感受到一种美好的赐予,
小刺猬( 鲁迅对许广平的另一个昵
称) 忧虑。 沈从文致张兆和
徐志摩与陆小曼 有人告诉我鱼的记忆只有 7 秒, 7 秒之后它就不记得过去的事
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 女子怕
做过的事, 都可以烟消云散 、 可我
不是鱼, 无法忘记我爱的人 , 无法 忘记牵挂的苦.无法忘记相思的
做错事, 男 子却并不在做过的错事
上有所遁避 所以, 如果我爱的是
你的不幸, 那你这不幸是同我生命
一
痛 如果一开始你就不要出现在我 面前, 那么 我也许就不会知道幸福
新中国, 参加祖国的建设, 他预订了 7月 2 7日回国的机票。而女儿钱永真 6 月2 6 日才出生, 这意味着女儿一满月, 蒋英就
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故事

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故事第一篇嗨,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咱们来聊聊鲁迅和许广平那浪漫又动人的爱情故事。
你们知道吗?鲁迅一开始可是个严肃又深沉的大先生。
但许广平的出现,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的世界。
许广平啊,那可是个勇敢又有才华的女子。
她对鲁迅充满了敬仰和爱慕,一点都不害怕世俗的眼光,大胆地向鲁迅表达自己的心意。
还记得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吗?那一封封的信,字里行间都是真情实意。
许广平的活泼、热情,慢慢融化了鲁迅那颗看似冰冷的心。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有很多温馨的小瞬间。
比如一起讨论文学,一起为了理想奋斗。
许广平总是默默地支持着鲁迅,给他力量。
而且啊,鲁迅在生活中也会有温柔的一面,对许广平关怀备至。
虽然他们的爱情没有那么多花前月下,但在平淡中却有着最真挚的情感。
他们的爱情,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而是细水长流,相互陪伴,相互成就。
真的太让人感动啦!第二篇嘿,朋友们!今天咱们讲讲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哟!鲁迅,这位文学巨匠,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好像很难接近。
但爱情这东西就是神奇,许广平出现后,一切都变啦。
许广平那姑娘,有想法,有勇气,就认准了鲁迅。
不管别人咋说,她都坚定地走向鲁迅。
他们在相处中,越来越发现彼此的好。
鲁迅的深刻思想吸引着许广平,许广平的活力也感染着鲁迅。
记得有一次,鲁迅工作累了,许广平就贴心地给他泡杯热茶,陪在他身边。
这种小小的举动,充满了爱。
而且他们一起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从不退缩。
许广平理解鲁迅的抱负,鲁迅也珍惜许广平的陪伴。
虽说他们的爱情没有太多浪漫的约会,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为有对方而变得特别。
他们的爱情就像一杯暖暖的茶,越品越有味。
真的是太美好啦,是不是?。
鲁迅许广平的爱情故事

鲁迅许广平的爱情故事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有一段爱情如星子般在黑暗的天幕上闪烁着独特的光芒,这便是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
鲁迅,那可是文学界的一座巍峨大山啊。
他犀利的文字就像一把把手术刀,精准地剖析着旧中国的弊病。
而许广平呢,一个勇敢的新女性,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向往。
他们的相遇就像是两颗流星在浩瀚宇宙中的邂逅,注定要擦出绚烂的火花。
想当年,许广平还是鲁迅的学生呢。
课堂上,鲁迅那渊博的知识就像一个无尽的宝藏,每一句话都仿佛带着魔力,深深地吸引着许广平。
许广平心里啊,肯定在想:“这个先生可真是与众不同,他的思想就像一阵狂风,能把我心中那点懵懂的想法吹得更开阔。
”而鲁迅呢,或许也注意到了这个眼神里透着机灵劲儿的女学生。
你说巧不巧,后来啊,许广平就开始给鲁迅写信了。
那信里可都是她的所思所想,对社会的看法,对文学的见解。
这信就像一只只小鸽子,在他们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鲁迅收到信后,心里肯定是有触动的。
他或许会想:“这个年轻女子,竟有如此深刻的想法。
”然后啊,他就认真地回信。
一来二去,两人的感情就在这信件的往来中慢慢地生根发芽了。
他们的爱情可不是那种风花雪月的小情小爱。
你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多恶劣啊,封建礼教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想要把人们都束缚住。
可鲁迅和许广平不怕,他们就像两只并肩作战的大雁,互相鼓励,互相支持。
他们的爱情中有着对自由的共同追求,有着对旧传统的强烈反抗。
有一次,许广平可能对鲁迅说:“先生,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像勇士一样,冲破这重重的枷锁。
”鲁迅也许会笑着回答:“广平,你说得对,我们要做那黑暗中的灯塔,照亮更多的人。
”他们的对话里充满着力量,就像两把燃烧的火炬,越烧越旺。
他们在一起后的生活也充满了故事。
鲁迅继续他那伟大的文学创作,许广平则在一旁默默地支持他。
她照顾着鲁迅的生活起居,让鲁迅能安心地在文学的战场上厮杀。
鲁迅的笔下流淌出的文字,也像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他写的那些文章,里面或许也有着许广平带给他的灵感呢。
民国时期的唯美情书合集 经典情书汇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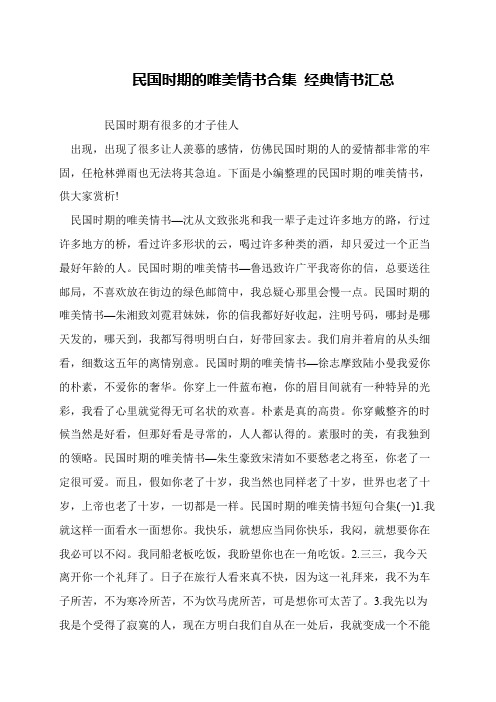
民国时期的唯美情书合集经典情书汇总 民国时期有很多的才子佳人 出现,出现了很多让人羡慕的感情,仿佛民国时期的人的爱情都非常的牢固,任枪林弹雨也无法将其急迫。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民国时期的唯美情书,供大家赏析! 民国时期的唯美情书—沈从文致张兆和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民国时期的唯美情书—鲁迅致许广平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
民国时期的唯美情书—朱湘致刘霓君妹妹,你的信我都好好收起,注明号码,哪封是哪天发的,哪天到,我都写得明明白白,好带回家去。
我们肩并着肩的从头细看,细数这五年的离情别意。
民国时期的唯美情书—徐志摩致陆小曼我爱你的朴素,不爱你的奢华。
你穿上一件蓝布袍,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彩,我看了心里就觉得无可名状的欢喜。
朴素是真的高贵。
你穿戴整齐的时候当然是好看,但那好看是寻常的,人人都认得的。
素服时的美,有我独到的领略。
民国时期的唯美情书—朱生豪致宋清如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
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
民国时期的唯美情书短句合集(一)1.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
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
我同船老板吃饭,我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
2.三三,我今天离开你一个礼拜了。
日子在旅行人看来真不快,因为这一礼拜来,我不为车子所苦,不为寒冷所苦,不为饮马虎所苦,可是想你可太苦了。
3.我先以为我是个受得了寂寞的人,现在方明白我们自从在一处后,我就变成一个不能。
鲁迅先生最经典的情书:《两地书》,总是如此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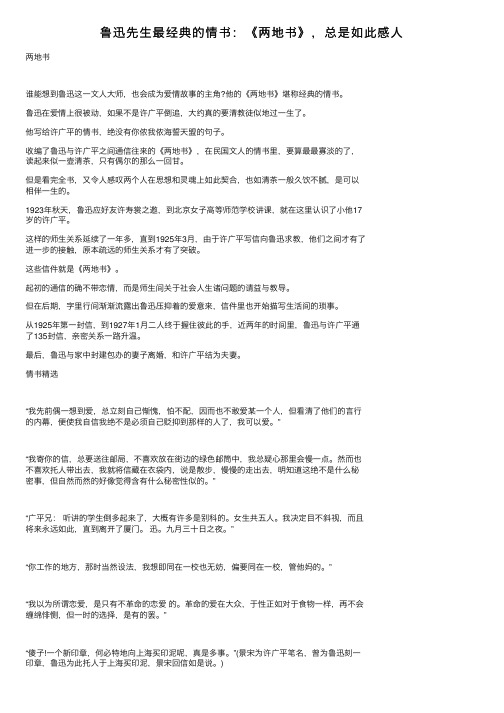
鲁迅先⽣最经典的情书:《两地书》,总是如此感⼈两地书谁能想到鲁迅这⼀⽂⼈⼤师,也会成为爱情故事的主⾓?他的《两地书》堪称经典的情书。
鲁迅在爱情上很被动,如果不是许⼴平倒追,⼤约真的要清教徒似地过⼀⽣了。
他写给许⼴平的情书,绝没有你侬我侬海誓天盟的句⼦。
收编了鲁迅与许⼴平之间通信往来的《两地书》,在民国⽂⼈的情书⾥,要算最最寡淡的了,读起来似⼀壶清茶,只有偶尔的那么⼀回⽢。
但是看完全书,⼜令⼈感叹两个⼈在思想和灵魂上如此契合,也如清茶⼀般久饮不腻,是可以相伴⼀⽣的。
1923年秋天,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到北京⼥⼦⾼等师范学校讲课,就在这⾥认识了⼩他17岁的许⼴平。
这样的师⽣关系延续了⼀年多,直到1925年3⽉,由于许⼴平写信向鲁迅求教,他们之间才有了进⼀步的接触,原本疏远的师⽣关系才有了突破。
这些信件就是《两地书》。
起初的通信的确不带恋情,⽽是师⽣间关于社会⼈⽣诸问题的请益与教导。
但在后期,字⾥⾏间渐渐流露出鲁迅压抑着的爱意来,信件⾥也开始描写⽣活间的琐事。
从1925年第⼀封信,到1927年1⽉⼆⼈终于握住彼此的⼿,近两年的时间⾥,鲁迅与许⼴平通了135封信,亲密关系⼀路升温。
最后,鲁迅与家中封建包办的妻⼦离婚,和许⼴平结为夫妻。
情书精选“我先前偶⼀想到爱,总⽴刻⾃⼰惭愧,怕不配,因⽽也不敢爱某⼀个⼈,但看清了他们的⾔⾏的内幕,便使我⾃信我绝不是必须⾃⼰贬抑到那样的⼈了,我可以爱。
”“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邮筒中,我总疑⼼那⾥会慢⼀点。
然⽽也不喜欢托⼈带出去,我就将信藏在⾐袋内,说是散步,慢慢的⾛出去,明知道这绝不是什么秘密事,但⾃然⽽然的好像觉得含有什么秘密性似的。
”“⼴平兄:听讲的学⽣倒多起来了,⼤概有许多是别科的。
⼥⽣共五⼈。
我决定⽬不斜视,⽽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
迅。
九⽉三⼗⽇之夜。
”“你⼯作的地⽅,那时当然设法,我想即同在⼀校也⽆妨,偏要同在⼀校,管他妈的。
鲁迅先生情书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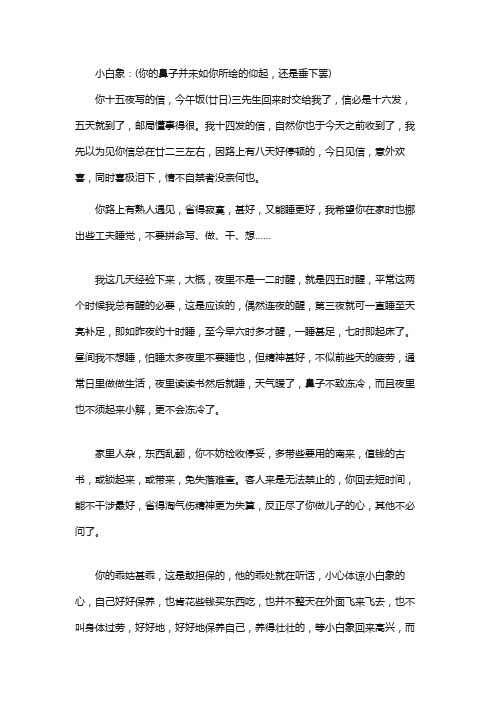
小白象:(你的鼻子并未如你所绘的仰起,还是垂下罢)你十五夜写的信,今午饭(廿日)三先生回来时交给我了,信必是十六发,五天就到了,邮局懂事得很。
我十四发的信,自然你也于今天之前收到了,我先以为见你信总在廿二三左右,因路上有八天好停顿的,今日见信,意外欢喜,同时喜极泪下,情不自禁者没奈何也。
你路上有熟人遇见,省得寂寞,甚好,又能睡更好,我希望你在家时也挪出些工夫睡觉,不要拼命写、做、干、想……我这几天经验下来,大概,夜里不是一二时醒,就是四五时醒,平常这两个时候我总有醒的必要,这是应该的,偶然连夜的醒,第三夜就可一直睡至天亮补足,即如昨夜约十时睡,至今早六时多才醒,一睡甚足,七时即起床了。
昼间我不想睡,怕睡太多夜里不要睡也,但精神甚好,不似前些天的疲劳,通常日里做做生活,夜里读读书然后就睡,天气暖了,鼻子不致冻冷,而且夜里也不须起来小解,更不会冻冷了。
家里人杂,东西乱翻,你不妨检收停妥,多带些要用的南来,值钱的古书,或锁起来,或带来,免失落难查。
客人来是无法禁止的,你回去短时间,能不干涉最好,省得淘气伤精神更为失算,反正尽了你做儿子的心,其他不必问了。
你的乖姑甚乖,这是敢担保的,他的乖处就在听话,小心体谅小白象的心,自己好好保养,也肯花些钱买东西吃,也并不整天在外面飞来飞去,也不叫身体过劳,好好地,好好地保养自己,养得壮壮的,等小白象回来高兴,而且更有精神陪他。
他一定也要好好保养自己,平心和气,渡〔度〕过豫〔预〕定的时光,切不可越加瘦损,已经来往跋涉,路途辛苦,再劳心苦虑,病起来怎样得了!三先生吃饭见面时总找些时事和我谈谈,王也格外照应,小孩有时候在楼下翻翻东西,但不久也为大人制止,还算好的。
我写给你的信,把生活状况一一说了,务求其详,但大体是好的。
即如少睡些,也是照常,并非例外,困起来就更多睡了,你切不可言外推测,如来信所云,我十二时尚未睡,其实我十二时总在熟睡中的,今日接北平常妹信,说那面可穿单衣,你也可少穿些了。
鲁迅致许广平的情书

鲁迅致许广平的情书鲁迅致许广平的情书细细翻阅那些文人的情书,令人感动。
那些温暖人心的文字,足以温暖红尘中孤寂的心灵。
以下关于鲁迅致许广平的情书,仅供参考。
人物简介: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
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许广平(1898年—1968年),中国现代女作家,祖籍福建。
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曾是鲁迅的学生,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终于和鲁迅走到了一起。
鲁迅致许广平的情书(一)广平:5日与7日的两函,今天(11)上午一同收到了。
这封挂号信,却并无要事,不过我因为想发几句议论,倘被遗失,未免可惜,所以宁可做得稳当些。
这里的风潮似乎还在蔓延,但结果是决不会好的。
有几个人已在想利用这机会高升,或则向学生方面讨好,或则向校长方面讨好,真令人看得可叹。
我的事情大致已了,本可以动身了,今天有一只船,来不及坐,其次,只有星期六有船,所以于15日才能走。
这封信大约要和我同船到粤,但姑且先行发出。
我大概15日上船,也许要到16日才开,则到广州当在19或20日。
我拟先住广泰来栈,待和学校接洽之后,便暂且搬入学校,房子是大钟楼,据伏园来信说,他所住的一间就留给我。
助教是伏园出力,中大聘请的,俺何敢“自以为给”呢?至于其余等等,则“爆发”也好,发爆也好,我就是这么干,横竖种种谨慎,也还是重重逼迫,好像是负罪无穷。
现在我就来自画招供,自卸甲胄,看看他们的第二拳是怎样的打法。
我对于“来者”,先是抱着博施于众的心情,但现在我不,独于其一,抱了独自求得的心情了。
(这一段也许我误解了原意,但已经写下,不再改了。
)这即使是对头,是敌手,是枭蛇鬼怪,我都不问:要推我下来,我即甘心跌下来,我何尝高兴站在台上?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作“朋友”。
谁有什么法子呢?但现在之所以还只(!)说了有限的消息者:一,为己,总还想到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借我已成之地位,而作改革运动。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鲁迅致许广平的情书细细翻阅那些文人的情书,令人感动。
那些温暖人心的文字,足以温暖红尘中孤寂的心灵。
以下关于鲁迅致许广平的情书,仅供参考。
人物简介: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
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许广平(1898年—1968年),中国现代女作家,祖籍福建。
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曾是鲁迅的学生,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终于和鲁迅走到了一起。
鲁迅致许广平的情书(一)广平:5日与7日的两函,今天(11)上午一同收到了。
这封挂号信,却并无要事,不过我因为想发几句议论,倘被遗失,未免可惜,所以宁可做得稳当些。
这里的风潮似乎还在蔓延,但结果是决不会好的。
有几个人已在想利用这机会高升,或则向学生方面讨好,或则向校长方面讨好,真令人看得可叹。
我的事情大致已了,本可以动身了,今天有一只船,来不及坐,其次,只有星期六有船,所以于15日才能走。
这封信大约要和我同船到粤,但姑且先行发出。
我大概15日上船,也许要到16日才开,则到广州当在19或20日。
我拟先住广泰来栈,待和学校接洽之后,便暂且搬入学校,房子是大钟楼,据伏园来信说,他所住的一间就留给我。
助教是伏园出力,中大聘请的,俺何敢“自以为给”呢?至于其余等等,则“爆发”也好,发爆也好,我就是这么干,横竖种种谨慎,也还是重重逼迫,好像是负罪无穷。
现在我就来自画招供,自卸甲胄,看看他们的第二拳是怎样的打法。
我对于“来者”,先是抱着博施于众的心情,但现在我不,独于其一,抱了独自求得的心情了。
(这一段也许我误解了原意,但已经写下,不再改了。
)这即使是对头,是敌手,是枭蛇鬼怪,我都不问:要推我下来,我即甘心跌下来,我何尝高兴站在台上?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作“朋友”。
谁有什么法子呢?但现在之所以还只(!)说了有限的消息者:一,为己,总还想到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借我已成之地位,而作改革运动。
但我要兢兢业业,专为这两事牺牲,是不行了。
我牺牲得不少了,而享受者还不够,必要我奉献全部的性命。
我现不肯了,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
这是你知道的,单在这三四年,我对于熟识的和初初相识的文学青年是怎样,只要有可以尽力之处就尽力,并没有什么坏心思。
然而男的呢,他们自己之间也掩不住嫉妒,到底争起来了,一方面于心不满足,就想打杀我,给那方面也失了助力。
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
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
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
如果我再隐忍,退让,他们更要得步进步,不会完的。
我蔑视他们了。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那流言,是直到去年11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
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飚》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
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
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
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
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什么诗,也低能得很。
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
那时我又写信去打听孤灵,才知道这种流言,早已有之,传播的是品青、伏园、亥情、微风、宴太。
有些人又说我将她带到厦门去了,这大约伏园不在内,是送我上车的人所流布的。
白果从北京接家眷来此,又将这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
在送别会上,田千顷且故意当众发表,意图中伤。
不料完全无效,风潮并不稍减,因为此次风潮,根柢甚深,并非由我一人而起,而他们还要玩些这样的小巧,真可谓“至死不悟”了。
现在是夜二时,校中暗暗的熄了电灯、贴出放假布告,当即被学生发现,撕掉了。
此后怕风潮还要扩大一点。
我现在真自笑我说话往往刻薄,而对人则太厚道,我竟从不疑及亥情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探我,虽然他的目光如鼠,各处乱翻,我有时也有些觉得讨厌。
并且今天才知道我有时请他们在客厅里坐,他们也不高兴,说我房里藏了月亮,不容他们进去了。
你看这是多么难以侍奉的大人先生呵。
我托令弟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很可惜,有些不高兴,而宴太即大放谣诼,说我在纵容着学生虐待她。
为求清宁,偏多滓秽,我早先说,呜呼老家,能否复返,是一问题,实非神经过敏之谈也。
但这些都由它去,我自走我的路。
不过这次厦大风潮之后,许多学生,或要同我到广州或想转学到武昌去。
为他们计,在这一年半载之中,是否还应该暂留几片铁甲在身上,此刻却还不能聚然决定。
这只好于见到时再商量。
不过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同事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中了流言家的诡计了。
鲁迅致许广平的情书(二)广平: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
学风如何,我以为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
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校和社会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
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在都市,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其苦恼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
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
教育界的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
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者,大概即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花费的必要之故罢。
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所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取巧,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
可是这不独女界,男人也都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
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问,倘若闯入深坑,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
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历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
”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解释。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
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不大好。
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
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者,大概即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花费的必要之故罢。
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所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取巧,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
可是这不独女界,男人也都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
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问,倘若闯入深坑,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
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历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
”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解释。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
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不大好。
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
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者,大概即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花费的必要之故罢。
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所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取巧,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
可是这不独女界,男人也都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
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问,倘若闯入深坑,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
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历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
”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解释。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
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不大好。
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