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电影”评电影《国家公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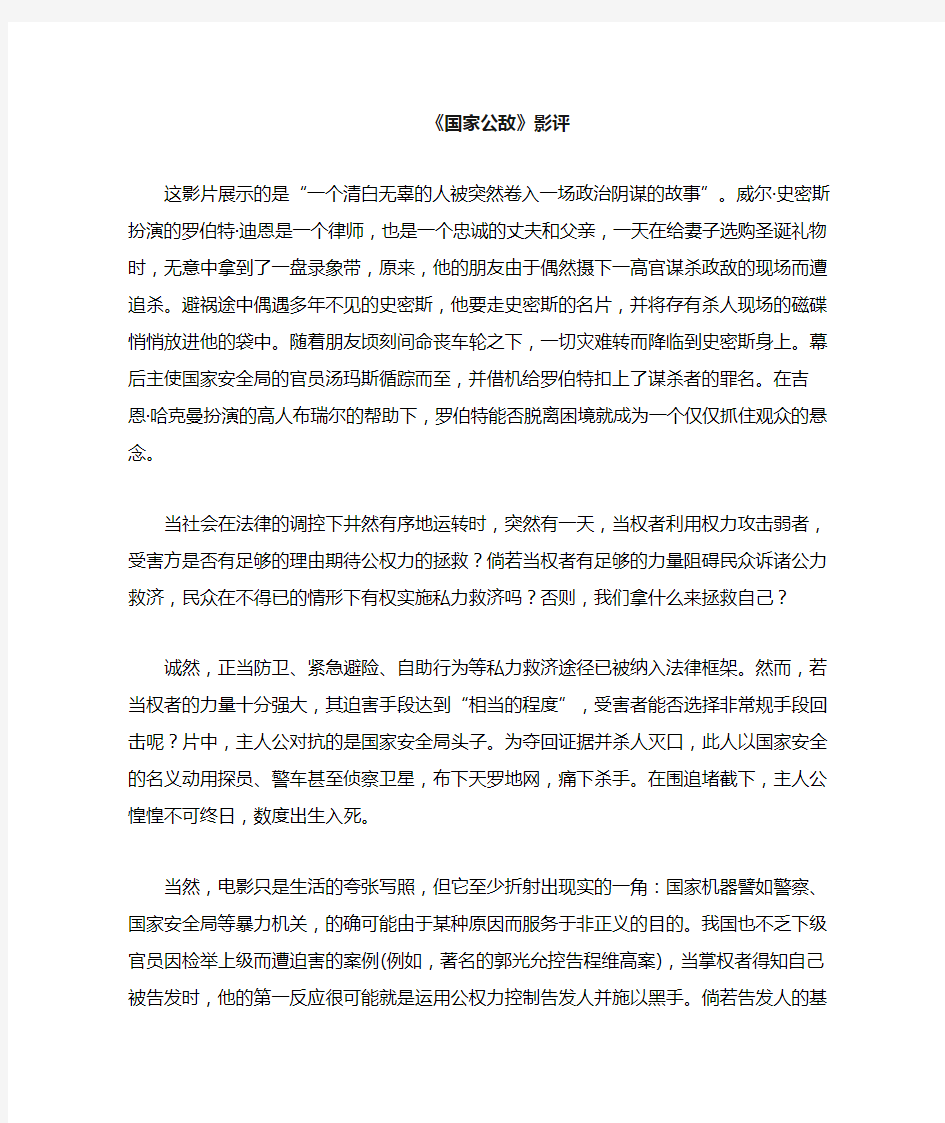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国家公敌》影评
这影片展示的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被突然卷入一场政治阴谋的故事”。威尔·史密斯扮演的罗伯特·迪恩是一个律师,也是一个忠诚的丈夫和父亲,一天在给妻子选购圣诞礼物时,无意中拿到了一盘录象带,原来,他的朋友由于偶然摄下一高官谋杀政敌的现场而遭追杀。避祸途中偶遇多年不见的史密斯,他要走史密斯的名片,并将存有杀人现场的磁碟悄悄放进他的袋中。随着朋友顷刻间命丧车轮之下,一切灾难转而降临到史密斯身上。幕后主使国家安全局的官员汤玛斯循踪而至,并借机给罗伯特扣上了谋杀者的罪名。在吉恩·哈克曼扮演的高人布瑞尔的帮助下,罗伯特能否脱离困境就成为一个仅仅抓住观众的悬念。
当社会在法律的调控下井然有序地运转时,突然有一天,当权者利用权力攻击弱者,受害方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期待公权力的拯救?倘若当权者有足够的力量阻碍民众诉诸公力救济,民众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有权实施私力救济吗?否则,我们拿什么来拯救自己?
诚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私力救济途径已被纳入法律框架。然而,若当权者的力量十分强大,其迫害手段达到“相当的程度”,受害者能否选择非常规手段回击呢?片中,主人公对抗的是国家安全局头子。为夺回证据并杀人灭口,此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动用探员、警车甚至侦察卫星,布下天罗地网,痛下杀手。在围追堵截下,主人公惶惶不可终日,数度出生入死。
当然,电影只是生活的夸张写照,但它至少折射出现实的一角:国家机器譬如警察、国家安全局等暴力机关,的确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服务于非正义的目的。我国也不乏下级官员因检举上级而遭迫害的案例(例如,著名的郭光允控告程维高案),当掌权者得知自己被告发时,他的第一反应很可能就是运用公权力控制告发人并施以黑手。倘若告发人的基本人权都被残酷剥夺,他难道没有权利去争取生存的资格吗?在不得已的时候,他是否有权以恶抗恶呢?
对此问题,德国法学家耶林的一句话大可作答:对以蔑视自己人格践踏权利的行为,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加以回击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义务。仅仅是话中蕴含的情感就足以令人震撼:捍卫权利,无需理由!正如影片的主人公起初只是东躲西藏,但当罪恶之手开始殃及亲
友、危及生命时,他毅然选择了奋起反击,以一人之力与庞大的集团力量抗争!
现实毕竟不是电影。面对实力强大的公力,个人或许只有两种选择:以合法的形式抗争,艰难等待,一如郭光允的八年长跑;或以恶抗恶,奋起反抗。但后者结果难料,可能引发极其恶劣的影响,难免牢狱之灾,也可能荡尽乌云,得见天日。但当我们投入的一封封检举信泥牛入海时,黑手伸向我们的速度将远甚于正义的来临。
当正义姗姗而来,法绳套向贪官的脖子时,他们将因为戕害检举人而罪加一等;当人们为其落马拍手称快时,法律的惩罚性与威慑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揭发者在等待正义的漫长过程中所承受的苦难由谁来拯救?倘若告发人在其间不堪迫害,忍无可忍去拼个鱼死网破,即使能得到大众的同情,也很难为法律所宽容!
正义的维护者们难道只能如殉道般与强大的恶势力斗争?法律的保护体现在哪里?一再出现的悲剧英雄是恢恢法网难以遮盖的尴尬。颂扬愿为权利牺牲的斗士,绝非颂扬牺牲本身;影片随着迫害的升级而愈趋紧张,你死我活的正邪较量正在上演。
但《国家公敌》的主人公是以律师身份出现的,注定了本片不同于《蝙蝠侠》之类的个人英雄主义。尽管我们一次次为主人公惊心动魄的逃脱而喝彩,但影片并没有为私力救济高唱赞歌。且看,主人公以磁碟为饵引高官到一辆车内,先是假意谈判,制造冲突,请驾驶座上的伙伴(装作局外人)全程录音,以举报的方式将录音带呈给有关机构;然后将一干人等骗至伪称的藏物地点并挑起枪战,让枪声吸引警察前来将当事人全部控制——若我们走进银幕以法官的角度审视,主人公寻求救济的每一个环节皆尽可能贴近法律的正当程序。主人公并未如我先前所料去寻求原始的报复性正义,而只是以私力救济为手段去寻求公力救济,重新拾起被公力迫害者抛弃的法律武器。
至此勉强可以回答开头的问题了:迫不得已时人们有权实施私力救济,以恶抗恶,捍卫权利,但权利的实现须尽可能诉诸法律。然而,这个答案的现实意义却十分单薄。史密斯一开始东躲西藏,直到确信对方目的既是抢磁碟又是夺命时才奋起反击。为什么他没有一开始就采取以恶制恶的非常规方式呢?这正是因为主人公的律师身份:既然尚未认定对方意图害命,若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手中的物件,则过
当的防卫就意味着于法无据,同时也会导致对方犯罪成本增加或犯罪
手段升级,反使自己的生命安全遭受更严重的威胁。
所以,他在当时的最佳选择是乖乖交出录像带,然后去寻求公力来补救——这恰好是先前那句耶林名言的前提:“只有当主张所有权的义务与维持生命这一更高层次义务相冲突,才使放弃所有权成为合理的。”——就个人的利益而言,任何权利都不值得以生命作为交换,我们需要审慎和冷静;但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如银幕英雄般敏锐果敢,能够准确地判断局势,快速地把握时机。相反,在人们确认迫害已危及其基本权利时也许已经失去了自我拯救的机会;更让人难以把握的是,在掌权者滥用公力进行迫害,逐步升级的过程中,何种程度才可界定为受害者“迫不得已”呢?衡量标准难道只有“受害者的恐惧感”这个无比模糊的“尺度”吗?而从公益角度看,以恶制恶行为潜藏着不可预知的社会危害,谁敢将它贸然纳入法律规定?
看完《国家公敌》,不禁想,许多时候,人们自救的权利是否无奈地成了一张空头支票呢?为免除社会公益的受损,我们只能等待迟来的正义;只要公力侵害没成为社会通病,就没有私力救济的伸展余
地。
谁给我们拯救自己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