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小说修辞艺术片论
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_毕飞宇论

右捡, 难得达标。 典型论是打不倒的, 街上有塑像不朽, 有
目共睹。它后来叫人厌烦, 也叫自己颓废, 只 因定做惟一, 惟我独革也。
典型的选择之难, 也是不倒之理。文学大 街周边, 决不只典型一路, 多有里弄胡同, 或 宽或窄, 或平坦或曲折, 都与大街相通相连。 通连之处, 必有选择栅栏, 也必是各有各的标 尺, 或重理性或重感性, 或向外或向内, 或求 真或求美。如无标尺, 何以选择, 如无选择, 何 可通连。塑像不倒, 选择不废, 因为老太太都
· ·升·为·一·种·语 ·言, 一种参与 世界的方式, 一种 美。”而“现实主义”在他眼中也与我们的经典 理解迥然不同: “现实主义应当从哲学意义和 语言学意义上分别对待之。现实主义其实是 语言对‘在’的一种走势与趋使, 是语言对‘生 存’的一种近 亲企图, 离开了这个, 先谈‘人 物’, ‘细节’, 又能说出什么呢? 现成的例子 是, 《水浒》也许比《西游》更浪漫, 《红楼》也许 比《百年孤独》更魔幻。语言近亲此岸的, 无论 花样如何, 都是现实主义 的, 语言近亲 彼岸 的, 无论形态多么质朴, 都是非现实主义 的。”¹ 而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而言, 毕飞宇 小说的此种风格在他的艺术世界内又集中体 现为作家对“错位情境”的出色塑造。在他的 小说中, “·错·位·情·境”是多维立体的, 也是寓含 丰富复杂的。它是世俗的, 又是哲学的、形而 上的; 它 可以指涉个体的 生存状态、心 理状 态、人性状态与命运状态, 又可以整体性地指 涉某种对历史或现实的寓言化理解; 它可以 是一种真切、具体的“实在”, 也可以是一种隐 喻、抽象的象征, 或一种虚幻的精神氛围; 它 可以是背景, 是手段, 又可以是目的, 是主体, 是对象……我觉得, “错位情境”既是毕飞宇 呈现他审美理想的艺术载体, 又是他能够把 感性经验融入抽象叙事的艺术桥梁, 对它的 有效阐释, 将是我们理解毕飞宇及其小说的 前提。
23562635_毕飞宇的三个美学时刻——以中短篇小说为例

毕飞宇的三个美学时刻以中短篇小说为例方岩一1991年,毕飞宇的中篇小说《孤岛》在《花城》发表,这是他的处女作。
这个由权谋、情欲、暴力交织而成的权力更迭的故事,在情节反转之前,更像是中国王朝统治及其更替历史的重新叙述,只是晚近的两次权力更迭改变了故事的走向及其意蕴———外来者依靠秘而不宣的武器/科技实现了掌权。
如果再考虑到这个故事发生的时空是某种孤悬海外的封闭状态,如同晚清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和形象,那么,这个故事便成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变局的隐喻。
当毕飞宇在结尾处写到“科学的最初意义变成了一种新宗教,它顺利地完成了又一次权力演变”①时,便知故事远没有结束。
当科技及其相关的器物和制度被神秘化、被垄断时,即将发生的历史依然如同迷雾中的孤岛。
毕飞宇重新想象历史的野心在此可见一斑。
从这个角度来看,《孤岛》无疑是先锋的,彼时的毕飞宇无疑也是先锋的,用毕飞宇自己的话来说:“一九九一年,中国的文学依然先锋,而我也在先锋。
”②确实,从《孤岛》发表到1995年前后,毕飞宇写下了大量的先锋文学作品。
这是毕飞宇的先锋写作时期。
但是,毕飞宇自我定位的先锋并非仅仅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的自然延续。
于是,如何理解毕飞宇的“先锋”便成了一个问题。
曾有一些文献将毕飞宇这代作家命名为“晚生代”,这其实暗含着某种暧昧的判断:他们是迟到者,是站在先锋文学名人堂大门之外焦灼等待的人,他们的起点天然地位于经典序列之外。
面对刚刚消失的文学史的黄金时代,他们永远无法分享先锋文学的历史荣耀。
至于他们的写作是否已经足够卓越、足够先锋,倒成了退而求其次的问题。
这批作家以两个人为代表:南方的毕飞宇和北方的李洱。
类似的判断同样隐含在一些影响力巨大的文学史著作中。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均出版于1999年,这两本文学史教材中的诸多判断构成了认知当代文学的基本常识,有些常识至今未被重新辨析。
他们在提及“先锋文学”时,均指向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批作家作品,前者罗列了马原、洪峰、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苏童、余华、北村③这些名字,而后者则指认了马原、洪峰、余华、86DOI院10.16551/ki.1002-1809.2021.01.010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①②③毕飞宇:《孤岛》,《花城》1991年第1期。
从_玉米_看毕飞宇小说的语言艺术

高粱》里那一片令人眩目的高粱地,给人以强烈的色彩质 一起,手拉手,共建美好幸福的小家庭吗”,而是“你愿意
感。随后又将镜头拉近,直到能看到“每一颗麦粒上都立着 和我一起,手拉手,和帝修反做斗争吗”。这违悖了我们头
一根麦芒”,这些都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作者用农民收 脑中的常情常理,出乎我们的意料。但在一个特定的时代, 33
34 望和理性的把持。
(6).
XIANDAI YUWEN
Modern chinese
现
这样的比喻还有很多,如玉米接到彭国梁来信时:“玉
代
语
文 2007.05
(魏 娜,河南师范大学来了,尽管是正面像, 帝修反做斗争吗?
还是能看出拱嘴。
例(1)“辩证法”“内因”“外因”本是哲学术语,有
(3)麦子们大片大片地黄在地里,金光灿烂的,每一颗 其自身的科学性和严肃性,而王连方成功地把他们运用到生
麦粒上都立着一根麦芒,这一来每一只麦穗都光芒四射,呈 男孩生女孩的问题上,令人啼笑皆非。科学的认识论与“不
毕飞宇小说中的比喻设置,大胆而又独特,显示了作家
回天了,他王连方随便撒一泡尿其实就是一天的雨了。
非凡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些个性化比喻的运用,在表现人物
(3)女孩子的心里一旦有了心上人,眼睛就成了卷尺, 形象,暗示人物命运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目光一拉出去就能量,量完了呼拉一下又能自动收进来。
不同的作家具有不同的语言欲望和语言感觉,并由此形
2.华语自觉地建立自己的标准规范,成为与普通话平行 的华人通语。
3.处于第1与第2之间,无论是趋同的过程中或在建立自
默”,用轻松、随意、常常带有玩笑、谐谑的幽默笔调来书 米在大腿上一正一反擦了两遍手,接过来,十个指头象长上
论毕飞字新作《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叙事艺术

8 2 论 毕飞 宇 新作《 苏北 少年“ 堂吉诃 德” 》 的叙 事艺 术 宋 雯
●语 言 ・文 学
论毕飞宇新作《 苏北少年“ 堂吉诃德 ’ ’ 》
的 叙 事 艺 术
宋 雯
( 华 中科 技 大学人 文 学院 , 湖北 武 汉 4 3 0 0 7 0 )
摘
要: 《 苏 北 少年 “ 堂 吉诃 德 ” 》 是 毕 飞 宇 的 第一 本 自传 性 作 品 , 由几 十 篇 记 录 了作 者 童 年 往 事 的 小 短 文 组 成 。 它 具 有 以 下 几
A b s t r a c t : T h e y o u n g D o n Q u i x o t e i n N o r t h e r n J i a n g s u i s B i f e i y u ’ S f i r s t a u t o b i o g r a p h y , w h i c h i s c o mp o s e d o f d o z e n s
Ke y wo r d s : B i F e i y u ; he T y o u n g D o n Q u i x o t e i n N o r t h e r n J i a n g s u ; a u t o b i o g r a p h y ; n a r r a t i v e f e a t u r e s
毕飞宇小说语言浅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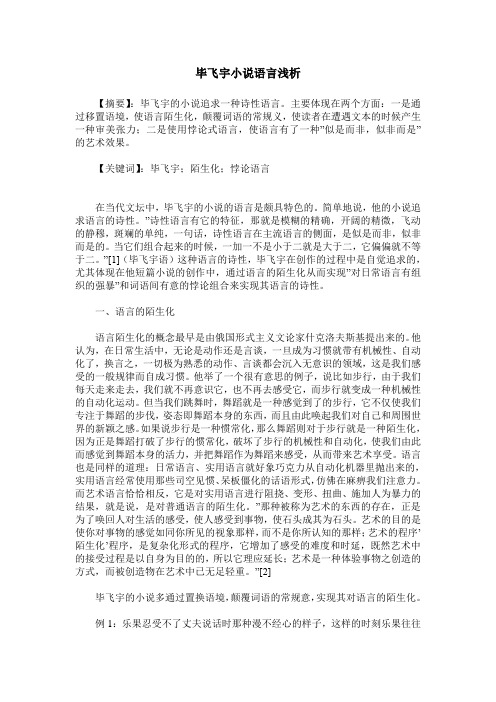
毕飞宇小说语言浅析【摘要】:毕飞宇的小说追求一种诗性语言。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移置语境,使语言陌生化,颠覆词语的常规义,使读者在遭遇文本的时候产生一种审美张力;二是使用悖论式语言,使语言有了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毕飞宇;陌生化;悖论语言在当代文坛中,毕飞宇的小说的语言是颇具特色的。
简单地说,他的小说追求语言的诗性。
”诗性语言有它的特征,那就是模糊的精确,开阔的精微,飞动的静穆,斑斓的单纯,一句话,诗性语言在主流语言的侧面,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
当它们组合起来的时候,一加一不是小于二就是大于二,它偏偏就不等于二。
”[1](毕飞宇语)这种语言的诗性,毕飞宇在创作的过程中是自觉追求的,尤其体现在他短篇小说的创作中,通过语言的陌生化从而实现”对日常语言有组织的强暴”和词语间有意的悖论组合来实现其语言的诗性。
一、语言的陌生化语言陌生化的概念最早是由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来的。
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动作还是言谈,一旦成为习惯就带有机械性、自动化了,换言之,一切极为熟悉的动作、言谈都会沉入无意识的领域,这是我们感受的一般规律而自成习惯。
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说比如步行,由于我们每天走来走去,我们就不再意识它,也不再去感受它,而步行就变成一种机械性的自动化运动。
但当我们跳舞时,舞蹈就是一种感觉到了的步行,它不仅使我们专注于舞蹈的步伐,姿态即舞蹈本身的东西,而且由此唤起我们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新颖之感。
如果说步行是一种惯常化,那么舞蹈则对于步行就是一种陌生化,因为正是舞蹈打破了步行的惯常化,破坏了步行的机械性和自动化,使我们由此而感觉到舞蹈本身的活力,并把舞蹈作为舞蹈来感受,从而带来艺术享受。
语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日常语言、实用语言就好象巧克力从自动化机器里抛出来的,实用语言经常使用那些司空见惯、呆板僵化的话语形式,仿佛在麻痹我们注意力。
而艺术语言恰恰相反,它是对实用语言进行阻挠、变形、扭曲、施加人为暴力的结果,就是说,是对普通语言的陌生化。
浅谈毕飞宇小说语言艺术

浅谈毕飞宇小说语言艺术作者:陈子谦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27期摘要:毕飞宇的小说看似文风质朴,实其自有风韵。
微妙的利用意识形态性话语赋予文本全新的语义,自然而娴熟的赋予谙熟的公众话语新鲜的活力,在小说文本中对其个人价值进行了充分的宣叙,同时建立起了自身话语伦理的体系。
本文从高中生角度出发分析了毕飞宇小说的语言艺术,以供参考。
关键词:毕飞宇;小说;语言艺术[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7-0-01从传统意义上讲,小说是语言的艺术。
而追求语言的艺术可以说是毕飞宇小说创作的显著特征,他对文字有近乎天赋的敏感。
毕飞宇对小说语言艺术的追求在语言风格上自有高度。
这对于高中生的阅读以及学习是非常好的课外教材。
一、公众话语的个人解释在最初命名事物时,人们习惯接受传统意义上的话语规则,即公众话语。
公众话语因有其成规而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毕飞宇则打破了这约定俗成的规则,以其独特的语言视角给小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毕飞宇利用意识形态性话语,赋予文本全新的语义,生动地解释被概念化的语言,使僵化的语言重新复活,赋予了话语反讽的力量,这些同时也正是构成毕飞宇小说语言张力最为关键的因素。
例如“樂果忍受不了丈夫说话时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吵到这个份上,苟泉就会摔着门出去,以不说话这种方式与小市民进行斗争。
当然,农民最终是要向小市民投降的。
农村包围了城市,农民也只能靠拢市民。
”而类似“农村包围城市”之类的政治话语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但毕飞宇此文此句的移用,则使我们感觉另有一番天地。
别致的移用,看似质朴实而掷地有声的语句,却是毕飞宇语言的一大特点。
毕飞宇就像是他笔下的一地玉米田,“长势喜人,郁郁葱葱”。
《玉米》的发表对毕飞宇而言似乎是预示着其写作的高潮,而在批评界看来,这未尝又不是个新开端。
人们逐渐发现毕飞宇的作品提供了“多价”的小说文本,他时常使用意识形态性话语,使得其语言叙事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质。
逸出主题域的唯美叙事_以毕飞宇为例谈小说无意义叙事

毕飞宇小说中的无意义叙事,可能是他从先锋文学那里继承过来并加以创造的一种叙事方式。
我们已经说过,对于毕飞宇而言,虽然在先锋时期受着先锋的影响,但他绝不甘于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后来者。
不愿作为一个文化上的后来者,决定了他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文化“弑父者”的角色———他必定是在继承的同时改造,在改造的时候创新。
事实上,在一段时间里,有人将前期的毕飞宇划为先锋作家。
在有关场合,毕飞宇也称自己受先锋小说影响较大。
“我不回避我的写作是从先锋小说起步的,我写小说起步晚,最早从先锋作家们的身上学到了叙事、小说修辞,我感谢他们,他们使我有了一个高起点。
当然了,他们也是从翻译小说学来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对中国的小说有根本性的意义。
”与《祖宗》相比,《充满瓷器的时代》可能更像一篇先锋小说(《充满瓷器的时代》曾被收录进《夜晚的语言———当代先锋小说精品》)。
诡吊的人物关系、诡秘的小说情节、黑色的小说背景、尖锐锋利而又绚烂的语言面貌,使这篇小说完美地呈现出一种先锋小说的特点。
正是从这一篇小说开始,毕飞宇小说叙事中的另一个特点浮出水面,那就是无意义叙事。
关于无意义叙事,很多论者在论及先锋小说的时候,并没有谈到这一点。
这也许是笔者臆想出来的一个评论语词或者概念,但我们认为,它恰到好处地概括了一种小说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恰到好处地彰显了小说的一种美学品质———小说叙事的作用,有时候是以“无用之用”显示出来的。
无意义叙事,更多的意义便在于它的“无用之用”的美学韵味。
它的存在是使小说更像小说,或者是使小说显示出一种美学风格的重要元素。
无意义叙事,是指叙事作品不以意义表达为主旨,或者在叙事角度上追求一种唯美的无意义的表达———以一种纯粹的唯美主义的品质结构小说、吸引读者。
无意义叙事,也许是最接近小说叙事品质的一种叙事手段或方式。
不以意义表达为主旨,可以理解为叙事没有中心思想方面的诉求,这是就叙事主体而言的;也可以是在一个主题的框架之中,叙事却逸出了主题的边界,在另一个主题域里信马由缰。
反讽_毕飞宇_小说理想_的实现方式

摘要英美“新批评”派的布鲁克斯曾说:“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
”[1]简言之,反讽就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所言非所指。
反讽作为一种具有张力的语言技巧,曾得到古今中外众多作家的青睐,毕飞宇也不例外。
反讽性语言在毕飞宇的小说中广泛地存在着,它依托作家的反思质疑精神而产生,为实现毕飞宇“轻盈而凝重”的小说理想而服务。
下面以毕飞宇1998年以后的作品为例,进一步探析其小说中反讽性语言的基本类型及其功能。
关键词反讽毕飞宇“小说理想”1广泛运用“反语”(1)耿长喜一听到“鲜花插在牛粪上”就喜上眉梢,他就是牛粪,他就喜欢别人说他牛粪,这可不是一般的牛粪,这是插着鲜花的牛粪、幸福的牛粪、伟大的牛粪。
有鲜花插着,牛粪越臭就越是非同一般,就越是值得开心与值得自豪。
能耐是假,福气是真,你就做不成这样的牛粪!———《那个夏季那个秋天》(2)用“敌敌畏”杀死自己,是企图寻死的乡村女人或乡下姑娘们最新的创造。
比起投河来,比起上吊、跳井、撞墙、剪气管、抹脖子来,喝农药利索多了,也科学多了,一句话,省事多了。
是时代的一个进步。
———《平原》反语包括“以正当反”和“以反当正”两种基本类型。
赵毅衡认为,“正话反说”是“反讽格局最清楚的表现方式”[2]。
赵毅衡所说的“正话反说”类似于反语中的“以反当正”,而上述两例则属于“以正当反”式的小说语言,即反话正说。
柏格森曾说:“用高尚的语言表达不道德的思想,用严格的体面的词汇去描写猥亵的场面、低微的职业、卑劣的行为,一般地都是滑稽的。
”[3]柏格森这番描述与“以正当反”的反语在修辞效果上是一致的。
例(1)中“牛粪”的这一番“心灵告白”不幸正被柏格森言中,因为毕飞宇以反话正说的方式巧妙地从“鲜花插在牛粪上”这句俗语演绎出一段关于“牛粪”的“千古绝唱”,而耿长喜这个乡村无赖卑劣无耻的本性与得逞后得意忘形的丑恶嘴脸也如水落石出般暴露无遗。
例(2)中“最新的创造”、“科学”、“进步”等词语在用法上也属于反话正说,同样产生了柏格森所说的滑稽效果。
诗性的语言与飞扬之累_毕飞宇小说的语言成就及其局限

184
科技信息
○高校讲坛○
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
2008 年 第 13 期
史与民族历史的交织、语 言 问 题 、哲 学 问 题 、少 年 成 长 史 、现 代 爱 情 与 婚姻、婚姻与物欲 等 等 一 系 列 此 后 毕 飞 宇 关 注 的 各 个 题 材 侧 面 , 而 一 直备受争议的有关语言问题的几个场景描写, 则代表了文化的隔阂这 样的主题, 而这种隔阂在《马家父子》中是妙趣横生的父子代沟, 在《楚 水 》、《明 天 遥 遥 无 期 》中 则 是 民 族 矛 盾 的 一 个 侧 面 。
哲学家斯贝尔斯认为, 艺术的真正使命不在于满足大众一时的好 奇心与娱乐目的, 而在于通过它, 使人认识真正的人性本相, 使人通过 艺术倾听到超越存在的声音。可能是基于同样的认识, 无论是从文学 的观念层面, 还是从文学的实践层面, 毕飞宇带给我们的就是他对世 界 、人 生 和 人 性 本 相 的 独 特 把 握 和 在 形 而 上 意 义 上 的 精 神 超 越 。 毕 飞 宇的小说在平平常常的叙事中总夹杂进预言与寓言般的话语, 微言大 义或指此道彼, 既体现了作者的才智, 又使小说充满思想与理性, 耐人 寻味, 有些作品则体现了明显的哲学趣味。评论家汪政就把《叙事》视 为语言哲学小说, 《楚 水 》是 文 化 哲 学 小 说 , 《雨 天 里 的 棉 花 糖 》是 精 神 分析小说。具体而言, 毕飞宇对深度哲学思考的追求在语言风格上有 时 会 直 接 表 现 在 小 说 中 叙 述 人 的 设 置 和 叙 述 语 式 上 。他 小 说 的 叙 述 人 大都是一 些 喜 欢 沉 思 冥 想 、追 根 问 底 的 学 者 型 知 识 分 子 , 他 们 总 是 会 在小说中不时 跳 出 故 事 之 外 , 直 接 表 达 对 于 世 界 、人 生 、历 史 、时 间 等 等的“哲学化思想”。因此, 他的文本中, 这样的文字很常见:
逸出主题域的唯美叙事_以毕飞宇为例谈小说无意义叙事

毕飞宇小说中的无意义叙事,可能是他从先锋文学那里继承过来并加以创造的一种叙事方式。
我们已经说过,对于毕飞宇而言,虽然在先锋时期受着先锋的影响,但他绝不甘于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后来者。
不愿作为一个文化上的后来者,决定了他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文化“弑父者”的角色———他必定是在继承的同时改造,在改造的时候创新。
事实上,在一段时间里,有人将前期的毕飞宇划为先锋作家。
在有关场合,毕飞宇也称自己受先锋小说影响较大。
“我不回避我的写作是从先锋小说起步的,我写小说起步晚,最早从先锋作家们的身上学到了叙事、小说修辞,我感谢他们,他们使我有了一个高起点。
当然了,他们也是从翻译小说学来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对中国的小说有根本性的意义。
”与《祖宗》相比,《充满瓷器的时代》可能更像一篇先锋小说(《充满瓷器的时代》曾被收录进《夜晚的语言———当代先锋小说精品》)。
诡吊的人物关系、诡秘的小说情节、黑色的小说背景、尖锐锋利而又绚烂的语言面貌,使这篇小说完美地呈现出一种先锋小说的特点。
正是从这一篇小说开始,毕飞宇小说叙事中的另一个特点浮出水面,那就是无意义叙事。
关于无意义叙事,很多论者在论及先锋小说的时候,并没有谈到这一点。
这也许是笔者臆想出来的一个评论语词或者概念,但我们认为,它恰到好处地概括了一种小说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恰到好处地彰显了小说的一种美学品质———小说叙事的作用,有时候是以“无用之用”显示出来的。
无意义叙事,更多的意义便在于它的“无用之用”的美学韵味。
它的存在是使小说更像小说,或者是使小说显示出一种美学风格的重要元素。
无意义叙事,是指叙事作品不以意义表达为主旨,或者在叙事角度上追求一种唯美的无意义的表达———以一种纯粹的唯美主义的品质结构小说、吸引读者。
无意义叙事,也许是最接近小说叙事品质的一种叙事手段或方式。
不以意义表达为主旨,可以理解为叙事没有中心思想方面的诉求,这是就叙事主体而言的;也可以是在一个主题的框架之中,叙事却逸出了主题的边界,在另一个主题域里信马由缰。
毕飞宇作品语言的陌生化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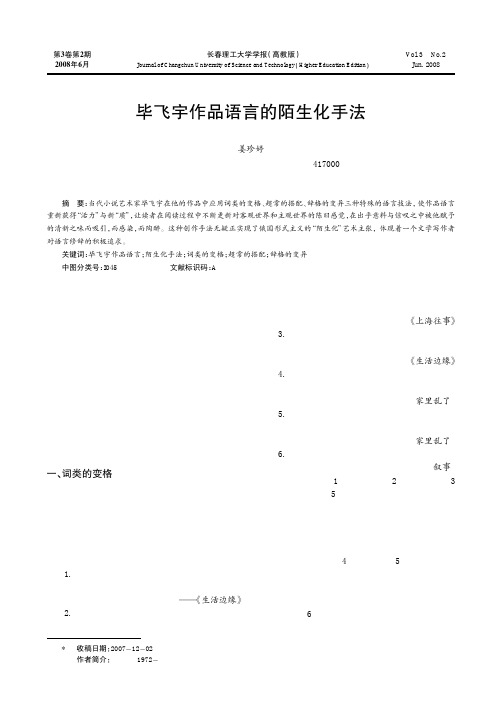
毕飞宇作品语言的陌生化手法姜珍婷(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湖南娄底,417000)摘要:当代小说艺术家毕飞宇在他的作品中应用词类的变格、超常的搭配、辞格的变异三种特殊的语言技法,使作品语言重新获得“活力”与新“质”,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更新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陈旧感觉,在出乎意料与惊叹之中被他赋予的清新之味而吸引,而感染,而陶醉。
这种创作手法无疑正实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艺术主张,体现着一个文学写作者对语言修辞的积极追求。
关键词:毕飞宇作品语言;陌生化手法;词类的变格;超常的搭配;辞格的变异中图分类号:I045文献标识码:A文学创作总是要求新颖、独特,这样作品才具有艺术生命力,才能不流入媚俗的行列。
作为小说艺术家的毕飞宇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他卓绝的审美力,在他的作品中,他运用多种特殊的语言技法,使作品语言重新获得“活力”与新“质”,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更新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陈旧感觉,在出乎意料与惊叹之中被他赋予的清新之味而吸引,而感染,而陶醉。
这种创作手法无疑正实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艺术主张,体现着一个文学写作者对语言修辞的积极追求。
词类的变格、超常的搭配、修辞格的变异是毕飞宇在作品中常用的三种陌生化手法。
一、词类的变格汉语的每一个词,都归属于一定的词类。
兼类的现象虽有,但很少,基本上符合语法规律的要求的是为“常格”。
而“陌生化”语言,出于某种情境的需要,则完全可以冲破语法的樊篱,是为“变格”。
为了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毕飞宇在他的作品中应用了不少的变格语词:1.她就把失望和希望全放在眼睛里头,和暮色一起冲着汪老板苍茫过去。
——《生活边缘》2.我把衣裤团在地上,翘着屁股泡进了热水,不规则的乳色热气在脖子四周袅娜并升腾。
——《上海往事》3.耿师傅很开心地摸着小铃铛的腮,小铃铛的双手撑在门框上,一对黑眼珠对着两个生人伶牙俐齿——《生活边缘》4.星期五的生意很好。
阿森说,生意都“啤”了。
毕飞宇小说语言浅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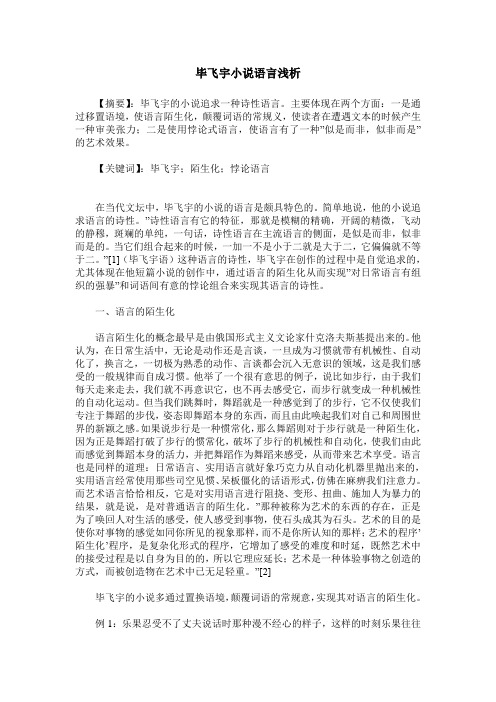
毕飞宇小说语言浅析【摘要】:毕飞宇的小说追求一种诗性语言。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移置语境,使语言陌生化,颠覆词语的常规义,使读者在遭遇文本的时候产生一种审美张力;二是使用悖论式语言,使语言有了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毕飞宇;陌生化;悖论语言在当代文坛中,毕飞宇的小说的语言是颇具特色的。
简单地说,他的小说追求语言的诗性。
”诗性语言有它的特征,那就是模糊的精确,开阔的精微,飞动的静穆,斑斓的单纯,一句话,诗性语言在主流语言的侧面,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
当它们组合起来的时候,一加一不是小于二就是大于二,它偏偏就不等于二。
”[1](毕飞宇语)这种语言的诗性,毕飞宇在创作的过程中是自觉追求的,尤其体现在他短篇小说的创作中,通过语言的陌生化从而实现”对日常语言有组织的强暴”和词语间有意的悖论组合来实现其语言的诗性。
一、语言的陌生化语言陌生化的概念最早是由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来的。
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动作还是言谈,一旦成为习惯就带有机械性、自动化了,换言之,一切极为熟悉的动作、言谈都会沉入无意识的领域,这是我们感受的一般规律而自成习惯。
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说比如步行,由于我们每天走来走去,我们就不再意识它,也不再去感受它,而步行就变成一种机械性的自动化运动。
但当我们跳舞时,舞蹈就是一种感觉到了的步行,它不仅使我们专注于舞蹈的步伐,姿态即舞蹈本身的东西,而且由此唤起我们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新颖之感。
如果说步行是一种惯常化,那么舞蹈则对于步行就是一种陌生化,因为正是舞蹈打破了步行的惯常化,破坏了步行的机械性和自动化,使我们由此而感觉到舞蹈本身的活力,并把舞蹈作为舞蹈来感受,从而带来艺术享受。
语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日常语言、实用语言就好象巧克力从自动化机器里抛出来的,实用语言经常使用那些司空见惯、呆板僵化的话语形式,仿佛在麻痹我们注意力。
而艺术语言恰恰相反,它是对实用语言进行阻挠、变形、扭曲、施加人为暴力的结果,就是说,是对普通语言的陌生化。
倾心营造小说的形而上世界——毕飞宇的小说理论与创作

倾心营造小说的形而上世界毕飞宇的小说理论与创作段崇轩 2017年毕飞宇出版课堂讲稿集《小说课》,让人们看到了一位思想丰沛、直觉敏锐的小说理论家形象。
此前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既有现代派精神又有现实主义功底的新潮小说家形象。
他穿越在理论与创作之间,令二者水乳交融、出神入化,在小说上进入一种自由之境。
在当代文坛上,不乏既有创作实绩、又有理论建树的优秀作家。
但像毕飞宇这样,能够真正深入小说“王国”,把握住其中的深层规律和艺术真谛,并化为自己的理论思考和具体创作,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小说理论乃至小说美学的,似乎还不多见。
作为起步于1990年代的“60后”作家,他的人生、创作与理论,具有“标本”的意义。
我们从中可以窥见,“60后”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探索轨迹,多元化文学时期小说创作遭遇的困境与突围,以及未来小说发展的路径选择。
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文学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作家与思想理论的关系。
有的作家专注于小说创作,没兴趣甚至不屑于招惹理论,也写出了独树一帜的优秀作品;有的作家兼顾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以两种形象展示给人们,同样写出了引领潮流的杰出之作。
创作与理论,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活动,有人只能“单挑”,有人可以兼顾;但一般说来,善于兼顾的作家,更容易写出新颖、丰厚的作品,更富有创作生命力。
当代文学史上作家的理论建树,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新时期”文学以降,作家在思想理论特别是小说理论方面的建设才真正开始,涌现了一大批创作与理论并驾齐驱的重要作家。
老一代作家中的王蒙、汪曾祺、林斤澜,中青年作家中的韩少功、王安忆、残雪、马原、格非、毕飞宇等,他们或发表创作谈文章,或与评论家进行对话,或解读经典作家作品,或出版讲座、课堂讲稿集辑,不仅促进和提升了作家自身的小说创作,同时也推动和深化了小说文体的发展。
毕飞宇是一位兼有艺术才华和理论思维的作家。
他在一次访谈中低调地说:“我没有什么理论素养,我能知道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小说要把不可言说的东西推向极致——《飞渡火烈鸟》讨论纪实

Y O U T H小说要把不可言说的东西推向极致张永禄(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这是我们上海大学第二次做小说沙龙,前些年毕飞宇老师亲自到上海大学来指导创意写作专业一个博士生的小说,让我们很受启发,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写作热情、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
我觉得小说沙龙是个非常好的形式,随着创意写作教育的不断深入,我们的探索也不断成熟,与刊物的联动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迈出的很重要的一步。
应该说,上海大学中文系这些年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能够不断地探索,且产生一些影响力,要得益于著名批评家和重要刊物的支持和关心,我们很荣幸地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希望我们能够共同把创意写作、把中国的创作事业往前推进一步。
谢尚发(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副主任):首先这篇小说写得还是相当可以的,整体上来说它的优点有三个。
一是小说的感觉比较好,对人的行为、心理、意识的把控比较准确。
二是它的——《飞渡火烈鸟》讨论纪实毕飞宇工作室上海大学文学院《青春》杂志社本期主办本文为毕飞宇工作室第35期小说沙龙讨论纪实。
本期活动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张永禄、汪雨萌主持,汪政、来颖燕、项静、走走、晏杰雄、谢尚发等作家、评论家以及三名学生代表围绕卜书典的短篇小说《飞渡火烈鸟》,从小说的故事结构、语言、主题等多个维度进行解读与点评。
作者在现场听完讨论,就大家的点评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对作品进行修改。
编者按毕飞宇工作室·小说沙龙细节描写非常到位,尤其是来自女性的、对生活的细腻的感知。
三是这篇小说的语言非常有自己的个性,将学生创作的语言格调做了一次集中的展示。
我给这次的发言起了个标题叫《小说的腔调》。
所谓“小说的腔调”,它不仅是语言的修辞或风格,还是属于小说的气韵和格调,它是一种综合性的、主题性的感觉。
这篇小说的腔调前后并不是非常完美统一,有时候会跑偏,比如小说人物的对话跟整个文章的气韵就未能嵌到一起。
这篇小说集中地凸显了校园青春写作的内容,或者说它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所以怎么样把小说的腔调转为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恐怕还需要再进行一些改变。
论毕飞宇小说的幽默——以插入语和排比句为例

论毕飞宇小说的幽默———以插入语和排比句为例施 龙 在1990年代中期,毕飞宇抛开先锋实验的走板荒腔,开始探究生活“最基础、最根本、最恒常、最原始的那个部分”,①而直到2000年发表《青衣》,毕飞宇小说的叙述者从“严肃的教师”变成“高明的说书人”,②这一追求才算真正落到实处。
单就叙述论,毕飞宇小说的句法也有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变,从前期较多使用插入语变成后期较多使用排比句,而这一点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和毕飞宇小说的审美风格相关。
毕飞宇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国外许多书评人和记者都认为他是一个幽默的作家,但幽默“离不开夸张”,而他却“不夸张”③,言下之意,他的小说就算不得幽默。
其实,国外读者跨语境的共同认知凸显了一个简单事实,那就是毕飞宇小说最鲜明、同时也就是最根本的风格,正是“幽默”。
柏格森认为最常见的对比发生在“现在是怎样”的“现实”和“应该是怎样”的“理想”之间:当“人们说的是应该是怎样,却装出相信现在就是这样的样子”时,是反语,而当“人们把现实的事情详详细细、小心翼翼地描写出来,却假装那是事情应该有的模样”之时,就是幽默;二者“都是讽刺的形式”。
④据此而论,毕飞宇小说最基础的风格的确是幽默,只是国人如我者常是见到反讽。
因此,需要追问的是,毕飞宇小说的幽默或反讽的具体技巧是什么?国人和他者之间的见仁见智,由何原因造成?讽刺在毕飞宇的创作中居何地位,又会对其今后的创作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须从毕飞宇小说独特的语言风格谈起。
一、插入语:从反讽到幽默如果说毕飞宇小说之树是叙述,那么语言则是树上的枝叶。
语言“在隐秘之中贯串了人的来龙去脉,笼罩了人的沟沟坎坎与枝枝杈杈”,⑤而“枝叶怎么长都是正确的,都是好看的”。
⑥在这些婆娑的语言枝叶间,最为醒目的当属插入语。
小说中的插入语,从中041DOI院10.16551/ki.1002-1809.2016.06.015当代作家评论 2016年第6期①②③④⑤⑥毕飞宇:《自序》,《轮子是圆的》,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4。
毕飞宇散文作品中的幽默手法探析-各体文学论文-文学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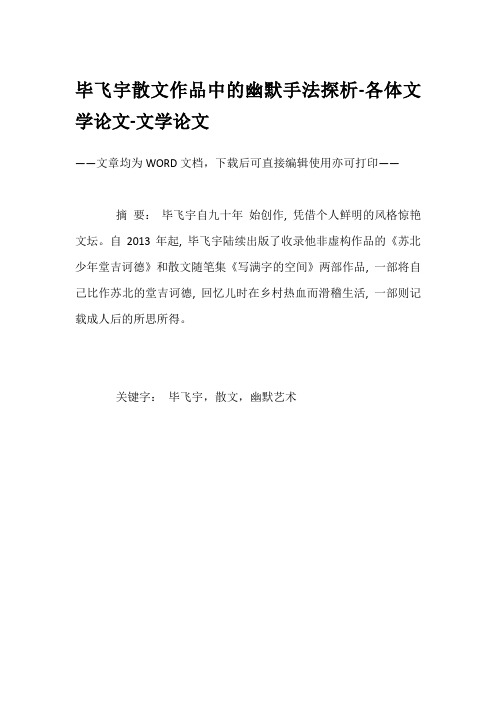
毕飞宇散文作品中的幽默手法探析-各体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摘要:毕飞宇自九十年始创作, 凭借个人鲜明的风格惊艳文坛。
自2013年起, 毕飞宇陆续出版了收录他非虚构作品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和散文随笔集《写满字的空间》两部作品, 一部将自己比作苏北的堂吉诃德, 回忆儿时在乡村热血而滑稽生活, 一部则记载成人后的所思所得。
关键字:毕飞宇,散文,幽默艺术在散文作品中, 毕飞宇把他真切地袒露在我们面前, 既不掩饰自己儿时的贫穷与孤独, 也不矫饰成人之后依然存在的尴尬与窘迫。
毕飞宇的散文作品虽数量不大, 但依然保持了他鲜明强烈的个人风格, 其特征的呈现, 较之小说甚至更为典型和酣畅。
其中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幽默特质, 在散文创作中更是被放大, 在研读其散文的过程中很难不被注意。
毕飞宇散文个人化风格的彰显, 与其娴熟自如的幽默手法的运用密不可分。
本文即尝试从这一角度, 深入毕飞宇的散文世界, 探讨其幽默艺术基本的表现方式、深层的形成因素, 并进一步在当代散文创作的总体趋势下对其艺术价值进行简要评述。
一、毕飞宇散文中幽默艺术的表现幽默首先是一种语言, 以文字的形式直观地传递给受众。
语言是幽默艺术的载体, 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文字可以变成一种游戏, 而修辞手法等语言表现技巧的介入, 更是丰富了给语言增加幽默性的策略。
毕飞宇在散文表达中擅长运用比喻、戏仿手法, 在语气上能够巧妙地以轻驭重, 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用语风格, 常有奇语, 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幽默的踪影。
毕飞宇向来注重语句的观赏性与字里行间的耐人寻味, 追求语言的新颖奇特, 喜用修辞手法, 尤擅长使用比喻。
他能够做到朱自清所说的多远取喻, 即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看出同来。
例如他在《歌唱生涯》中写道, 音乐系的琴房离我并不遥远, 不时传来一两句歌声。
那些歌声像飞镖一样, 嗖嗖的, 全部落在了我的身上。
论毕飞宇短篇小说_段崇轩

毕飞宇的短篇小说, 追求的是一种如诗词那样的境界、 形态、 韵味, 是一种诗化的短篇小说。它的所指是最 日常的世态人情, 实在的事和人, 但却可以涵 盖广大的世界和人生。而作家所关注的、 感兴趣的现 实中的人的情感世界, 就成为这种小说最恰当的表现 对象。因为情感就是一种抽象的、 朦胧的、 “不及物” 的东西。
(3)
是说, 作家的创作素材, 来源于现实事件背后人的情 感反应, 这种情感是虚幻的、 变化的, 但它同样具有真 实性、 现实性。它在作家的创作中成为表现的重心。 而作家的创作动机, 也往往来自主体的情感触发, 这 种情感包含了作家的的人生经验、 生活愿望和人文情 怀等。毕飞宇坚持了现代派文学注重个人体验、 直觉 把握的精神, 又融合了现实主义文学关注当下、 直面
(8) 篇这东西天生就具有东方美学的特征。 ” 这就是说,
毕飞宇生在乡下, 长在 “文革” 时期。这样一个特殊的 家庭和身份, 在贫困、 动荡的农村, 在荒谬、 畸形的时 代,幼年的毕飞宇能感受到什么呢?自然会有父母、 老师的关爱, 也会有 “广阔天地” 的自由, 但更多的却 是时代的邪恶, 人与人的斗争, 为官者的强权, 乡村的 封闭、 愚昧, 以及在这种环境中滋生的恐惧感、 孤独感、 无爱感等等。而毕飞宇又恰恰是一个敏感、 内向、 耽 思的人, 这种心灵创伤便像伤疤一样留在了记忆里。 抒发心灵的创伤, 寻觅精神的慰藉, 就成为他日后创 作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在毕飞宇带有自传色彩的童年生活小说中, 弱小 者的孤独感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主题。早期作品 《那个 男孩是我》 , 以散文笔法, 描述了 “我” 寄住城里的婶婶 家养病的经历。婶婶虽然和善, 但忙于上班无暇照护 “我” , 表姐泼辣、 刁钻不喜欢 “我” 。 “我” 关在冷清的 屋子里寂寞难耐, 是隔壁院子里的钢琴声和排戏声吸
公众话语的个人化解释_论毕飞宇小说语言艺术

直很勤快地写作 ! 所以他也就一茬一茬地收获着他的庄 稼 " 对于毕飞宇来说 ! # 玉米 $ 的发表似乎预示着一次高 潮 % 对于批评界来说 ! 这同时又是一个开端 ! 之后所有关 于毕飞宇的批评话题开始呈现出一个日趋热闹的景象 ! 也许 ! 是毕飞宇作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个 & 富有歧义 的 ! 多价的 ! 也是抵制终级阐释的小说文本 ’ " 这种对
!
命 * 人其实是没有生命的 ! 生命只不过是家的辅助 物 ! 家的性腺 , 家的唾液 ,家的末枝与细节 * ## # % 家里乱了 & ’ 对 于 书 写 者 来 说 !建 立 独 立 叙 事 模 式 !就 是 寻 找 一种个人化的价值准则 ! 以及这种个人 价 值 的 充 分 宣 叙 ! 并在书写中建立起自身的知识谱系和话语伦理 * 这 种独立叙事还将成为更精确的身份标志 ! 也即在公共空 间里保持着个人身份和个人话语特征 * ( " 在毕飞宇的 叙述文字中 ! 我们可以随意看到这种独立的叙事 ! 不 仅 是对上述’ 艺术 ( 与’ 家 ( 的概念注入了个人话语特征 ! 小说家还对所谓爱情 , 城市 , 农村 , 权力 , 国家等我们耳 熟能详的意识形态性公众话语都有过贴合语 境 与 人 物 内心的重新解释与定义 ! 这使毕飞宇小说轻易显示出一 种独有的话语伦理 * 评论家汪政认为 !’ 权力以及对极权的反思 ! 在毕 飞宇小说中最成功的表现方式是将其日常生活化 ( * 这 句话反过来看也成立 ! 那就是毕飞宇同样擅长将日常生 活赋予权力争夺的气息 * % 玉米 & 里玉米的母亲施桂芳生孩子’ 生伤了 ( ! 连 持家的权利都不要了 * 这种情况下 ! ’ 玉米倒没有抱怨 母亲 ! 相反 ! 很愿意 * 玉米愿意这样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 玉穗 , 玉秀 , 玉英 , 玉叶 , 玉苗 , 玉秧 ! 平时虽说喊她姐姐 ! 究竟不服她 * 关键是老三玉秀 * 玉秀仗着自己聪明 !又会 笼络人心 !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村子上 ! 势力已经 有 一 些了 ( * 这样 !毕飞宇就把’ 玉米的第一次掌权 ( 放在了 ’ 中午的饭桌上 ( # ## 玉米并没有持家的权利 ! 但是 ! 权利就是这样 ! 你只要把它握在手上 ! 捏出汗 来 ! 权 利 会 长 出 五 根 手指 ! 一用劲就是一只拳头 * 父亲到公社开会了 !玉 米选择这样的 时 机 应 当 说 很 有 眼 光 了 00 玉 米 决 定效仿母亲 !一切从饭桌上开始 * 00 玉米要的其实只是听话 * 听了一次 ! 就有 两次 ! 有了两次 ! 就有三次 * 三次以后 ! 她也就习惯 了 ! 自然了 * 所以第一次听话是最最要紧的 * 权利就 是在别人听话的时候产生的 ! 又通过要求别人听话 而显示出来 * 放倒了玉秀 ! 玉米意识到自己开始持 家了 ! 洗碗的时候就有一点喜上心头 ! 当然 ! 绝不会 喜上眉梢的 * 心里的事发展到了脸上 ! 那就不好了 * # ##% 玉米 & " 玉米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 正是做梦的 年龄 ! 这样一个孩子却在梦里都浸透了关于权利的全部 欲望 ! 她的争权运动竟是从饭桌这样一个原本应该充满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毕飞宇小说修辞艺术片论王彬彬内容提要 这里的“修辞”不是一个狭义的与“语法”相对应的语言学概念,而指那种广义的文学性表达的手段、方法、技巧,也就是美国文学批评家布斯在小说理论名著《小说修辞学》中所说的“修辞”。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把体现在一部小说中的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各种关系,视作是一种修辞性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则是作者通过种种修辞性的考量、选择、经营所构造的。
本文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谈论毕飞宇小说的修辞艺术的。
1996年,毕飞宇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引起广泛注意,收获了如潮的好评。
于是,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广为人知,《哺乳期的女人》也被视作是毕飞宇的“成名作”。
但在此之前,毕飞宇已有很优秀的作品发表。
1993年同样发表于《作家》杂志的短篇小说《那个男孩是我》,已是相当精美和富有意味的。
它与《哺乳期的女人》某种意义上属同一类型,都写了孩子的难以被大人所理解的心事,写了孩子的孤独、寂寞和忧伤,写了孩子的尊严被大人残酷地蹂躏,写了孩子心中神圣的东西被大人们所误解、所亵渎。
或者说,这两个短篇,都写了孩子精神上的“孤苦无告”。
而较之《哺乳期的女人》,《那个男孩是我》的内涵似乎更丰富些。
就我来说,更愿意把《那个男孩是我》看作是毕飞宇的“成名作”,尽管他并未因此而成名。
1994年,毕飞宇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了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
这部作品也是颇为独特和圆熟的。
个体生命与社会意识的紧张关系在小说中有着撼人心魄的表现。
1995年,毕飞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说话》,十分机智地表达了对历史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神秘性的理解,而且通过对几次“偷情”的描写,让历史的神秘性与人生的神秘性形成某种对照,很是耐人寻味。
《那个男孩是我》、《雨天的棉花糖》、《是谁在深夜说话》,都有资格成为毕飞宇的“成名作”。
但实际上它们问世之初都悄无声息。
直到《哺乳期的女人》出现,人们才知道,在写小说的人中,多了一个叫毕飞宇的年轻人。
大体可以200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青衣》为界,将毕飞宇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分为两个阶段。
在修辞方式上,前后两阶段的差别是很明显的。
前期小说的叙述语言,一般说来典雅整饬而又不失清纯流丽,叙述语调则总是那么庄严端重,是一种“书生气”很重的话语方式。
在写小说之前,毕飞宇曾迷恋于诗歌。
在前期小说中,偶尔有些句子还让人想到他从诗人到小说家的“身份转型”。
例如,“我站在大街上,路灯一拳头把我的影子撂倒在水泥地面”(《叙事》)。
这样的句子让人觉得它像是从哪首诗中开了小差,混进了小说里,于是便如一碗绿豆中的一粒红豆,过于显眼。
毕飞字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被称作“先锋作家”的那个群体,正在文坛上大红大紫,毕飞宇多多少少地、有意无意地,有着对他们的模仿,即便在叙述语言上,也能隐约看出其时的所谓“先锋小说”的影响。
《青衣》在修辞方式上有点突变的意味。
较之此前的作品,《青衣》的故事性明显增强了,人物形象也更加具有立体感。
叙述语言则向粗实豪放转变,口语的色彩大大加强,并且时有苦心经营的凌乱和芜杂。
如果说,在前期小说中,叙述者基本上只有一种很“书生气”的声调,那从《青衣》开始,叙述者的声调变得多样化了:时而一本正经,时而插科打诨;时而温文尔雅,时而夹枪带棒、捉鸡骂狗。
如果说前期小说中的叙述者像一个严肃的教师,总用一种规范而考究的语言说话,那从《青衣》开始,叙述者变成了一个高明的说书艺人,他的语言随着叙述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着,说曹操不同于说刘备,说关公不同于说张飞。
修辞方式的这种变化,无疑意味着作者创作观念的变化,意味着作者对文学与现实之关系的重新认识。
通过修辞方式的大幅度调整,毕飞宇大幅度地调整了与现实的关系,从而也大幅度地调整了与读者的关系。
当然,反过来说也许更易理解:首先是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大幅度地调整了自身与现实的关系,然后是大幅度地调整了小说的修辞方式,而修辞方式的大幅度调整,便使得毕飞宇与读者的关系也被大幅度地调整了。
《青衣》以后的小说,引入注目的变化之一,是具有了一种幽默的品格。
说到幽默,其实应是小说的一种重要品格。
昆德拉甚至说:“小说的智慧跟哲学的智慧截然不同。
小说的母亲不是穷尽理性,而是幽默。
”①昆德拉的小说,的确具有强烈的幽默感,他惯以幽默的方式展示着极权政治下人性的种种表现。
以幽默的方式表现悲剧,往往比涕泪交加的控诉更具有艺术效果。
昆德拉之所以为昆德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种“昆德拉式的幽默”。
幽默,在毕飞宇《青衣》以前的作品中,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的确不很多见。
要举例的话,可举发表于1998年的《男人还剩下什么》。
这个短篇中的有些叙述,是颇为幽默的:“住在办公室没有什么不好。
惟一不适应的只是一些生理反应,我想刚离婚的男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适应,一到晚上体内会平白无故地蹿出一些火苗,蓝花花的,舌头一样这儿舔一下,那儿舔一下。
我曾经打算‘亲手解决’这些火苗,还是忍住了。
我决定戒,就像戒烟那样,往死里忍。
像我们这些犯过生活错误的人,对自己就不能心太软。
就应该狠。
”主人公“我”一再煞有介事地说自己“犯过生活错误”,而我们知道,他的全部“错误”不过是与一个大学时代的女同学有过一次短暂的拥抱。
他实际所做的事,与他自认为所做的事之间,有了一种距离,幽默由此而生。
我们在品味着这幽默的同时,不禁对主人公的遭遇有了更深的同情。
这种艺术效果的取得,当然与修辞上的幽默有关。
从《青衣》开始,这种修辞上的幽默明显增多。
到了2001年的《玉米》和《玉秀》,幽默性的叙述甚至成为一种基调。
《玉米》和《玉秀》的故事背景是“文革”时期的农村。
那是一个政治全能的时代,政治性话语满天飞。
而毕飞宇往往通过对那时代所流行的政治性话语的戏仿和挪用,使叙述幽默化。
《玉米》在说到支部书记王连方利用权力公然奸淫村里的许多有夫之妇时,有这样的叙述:“关于王连方的斗争历史,这里头还有一个外部因素不能不涉及。
十几年来,王连方的老婆施桂芳一直在怀孕,她一怀孕王连方只能‘不了’。
施桂芳动不动就要站在一棵树的下面,一手扶着树干,一手捂着腹部,把她不知好歹的干呕声传遍全村。
施桂芳十几年都这样,王连芳听都听烦了。
施桂芳呕得很丑,她干呕的声音是那样的空洞,没有观点,没有立场,咋咋呼呼,肆无忌惮,每一次都那样,所以有了八股腔。
这是王连方极其不喜欢的。
她的任务是赶紧生下一个儿子,又生不出来。
光喊不干,扯他娘的淡。
王连芳不喜欢听施桂芳的干呕,她一呕王连芳就要批评她:‘又来作报告了。
’”把王连方对村中妇女的奸淫说成是“斗争”,把施桂芳的干呕说成是“没有观点,没有立场”的“八股腔”,把王连方对老婆的讥讽说成是“批评”,通过王连方的口把施桂芳的干呕说成是“作报告”,这都是在用那时所流行的庄严的政治性话语来说明奸淫和妊娠反应一类的生理现象,让人忍俊不禁。
《玉秀》这样叙说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的儿子郭左:“郭家兴玉米他们一下班,郭左又沉默了。
像他的老子一样,一脸的方针,一脸的政策,一脸的组织性、纪律性,一脸的会议精神,难得开一次口。
”用“方针”、“政策”、“组织性、纪律性”、“会议精神”等来形容郭左的表情,也让人哑然失笑。
这种对那时代流行性政治话语的巧妙“挪用”,在产生幽默感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
毕飞宇小说在运用这类政治话语时,语气里有着明显的调侃。
毕飞宇以对那个时代流行性政治话语的妙用,调侃了那个时代的得势者,更以对那个时代流行性政治话语的妙用,调侃了那个时代。
毕飞宇小说修辞艺术片论毕飞宇小说在修辞上的幽默,不仅体现在语言选择上,也体现在情节设计上,或者说,也有着一种情节性的幽默。
《玉米》中的王连方,因为“破坏军婚”而被开除党籍、撤消职务,沦为“一介草民”。
他决定外出学漆匠。
离开家乡前,仗着酒劲,他想与有庆的老婆再鬼混一次,遭到拒绝。
王连方这时的表现,大出读者意料,却又让人击节叹赏: 王连方一直听不到动静,只好提着裤子,到堂屋里找。
有庆家的早已经不在了。
王连方再也没有料到这样的结果,两只手拎着裤带,酒也消了,心里滚过的却是世态炎凉。
王连方想,你还在我这里立牌坊,早不立,晚不立,偏偏在这个时候立,你行。
王连方一阵冷笑,自语说:“妈个巴子的!”回到西厢房,再一次扒光了,王连方重新爬进被窝,突然扯开了嗓子。
王连方睡在床上,一个人扮演起阿庆嫂、胡传魁和刁德一。
他的嗓门那么大,那么粗,而他在扮演阿庆嫂的时候嗓子居然捏得那么尖,那么细,直到很高的高音,实在爬不上去了,又恢复到胡传魁的嗓音。
王连方的演唱响遍了全村,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好像谁也没有听见。
王连方把《智斗》这场戏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有庆的床上,一字不差,一句不漏。
唱完了,王连方用嘴巴敲了一阵锣鼓,穿好衣裳,走人。
王连方的举动令人发笑,同时又令人发指,或者说,正因为令人发笑,所以令人发指。
这个情节因其具有幽默性,所以具有极大的表现力。
一场《沙家浜》唱下来,王连方把自己作为一个乡村地痞的无赖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地痞,自古是中国乡村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
历史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从江洋大盗到帝王将相,原都是乡村地痞出身。
对近代中国极为熟悉的美国人明恩溥(阿瑟・史密斯),在其所著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专题性地探讨过中国的“乡村地痞”。
他说:“可以说,不充分了解乡村地痞的地位,就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国人的生活。
换句话说,准确了解了中国地痞的特点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中国社会。
”“地痞一般都是穷人,他没有什么可损失的。
这是十分有用但不一定是必要的条件”②。
毕飞宇的一些小说,写到过这类乡村地痞。
长篇新作《平原》中的佩全、大路、国乐和红旗这一群人,实际上就是地痞这种古老的“种属”在“文革”时期的延续。
发表于1998年的短篇小说《白夜》中的李狠、张蛮、王二等,由于年龄尚小,只能称为乡村中的“不良少年”,但再大几岁,他们就是《平原》中的佩全、大路、国乐和红旗。
而从王连方遭有庆家的拒绝后出人意料的表现,我们就能断定,他原本也是这一类人。
毕飞宇对作为大队书记的王连方的刻画,令我想到赵树理的一些作品。
赵树理曾经敏锐而又深刻地指出:“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
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容易和贫农相混。
……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方面也可以。
”③赵树理的不少小说,写到了这类在“土改”中执掌了乡村基层政权的流氓地痞。
对此,“文革”后的周扬有这样的评价:“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恶霸地主,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与勇敢。
”④而毕飞宇《玉米》中当了二十年大队书记的王连方,正是在“土改”中“混入党内”、执掌了乡村基层政权的。
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不妨把《玉米》看作是赵树理那一类小说的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