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儒家的知识论传统与扬雄的重智思想

儒家的知识论传统与扬雄的重智思想
发表时间:2008-10-09T14:03:01.560Z 来源:《阳明学刊》第一辑 作者: 王青 [导读] 在先秦诸派中,存在着重智与反智两条线索;而在儒家内部,则有重仁与重智之不同侧重,它们各自代表了孔子思想的一个侧面。 由子思及其门徒,到荀子,再到董仲舒、扬雄,其重智思想构成了儒家知识论中一个一脉相承的传统。论文重点分析了扬雄的知识论,指 出扬雄在知识的对象、知识的价值、知识的来源、知识获取的可能性、知识的目的及其真理的标准等问题上,均有丰富独到的论述,是值 得我们重视的思想资源。
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圣与智戚矣,仁与义戚矣,忠与信戚[3]。
《五行》篇云:
闻君子道而不智(知),其君子道也,谓之不圣。见贤人而不智(知)其有德也,谓之不智。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
也。明明,智也;虩虩,圣也[4]。
可见在子思学派中,一直存在着将高度的智慧视之是成圣的必要条件这种观念。这一派的学说显然在汉朝还有着巨大的影响。马王 堆出土的帛书中有《五行》一篇,与简书《五行》大致相同。又有《四行》篇,其云:
然而,仅仅是对具体事物的知识尚还不是智者的最高目标:在扬雄看来,知识的重要程度是有高下之别的。从认识上来说,扬雄注重事物 的根本性规律,认为这是小知与大知的区别。
或问:“小每知之,可谓师乎?”曰:“是何师与?是何师与?天下小事为不少矣,每知之,是谓师乎?师之贵也,知大知也,小知之 师,亦贱矣。”(《法言·问明》)
“先知其几于神乎!敢问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视,忽、眇、绵作昞。”(《法言·先知》)
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政教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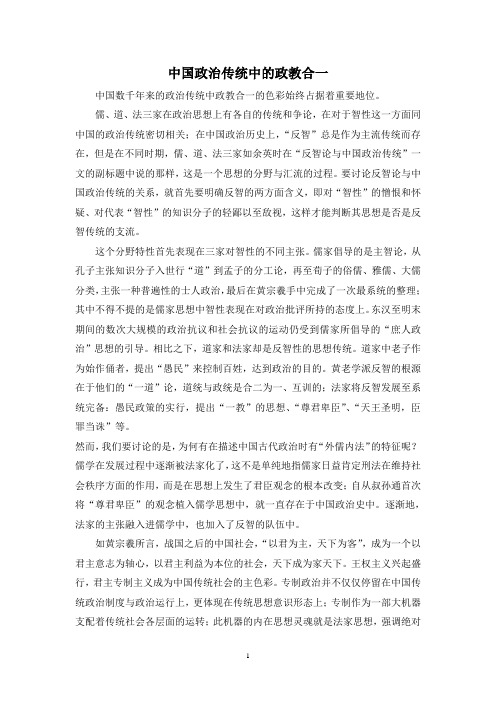
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政教合一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传统中政教合一的色彩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
儒、道、法三家在政治思想上有各自的传统和争论,在对于智性这一方面同中国的政治传统密切相关;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反智”总是作为主流传统而存在,但是在不同时期,儒、道、法三家如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的副标题中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思想的分野与汇流的过程。
要讨论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的关系,就首先要明确反智的两方面含义,即对“智性”的憎恨和怀疑、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的轻鄙以至敌视,这样才能判断其思想是否是反智传统的支流。
这个分野特性首先表现在三家对智性的不同主张。
儒家倡导的是主智论,从孔子主张知识分子入世行“道”到孟子的分工论,再至荀子的俗儒、雅儒、大儒分类,主张一种普遍性的士人政治,最后在黄宗羲手中完成了一次最系统的整理;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儒家思想中智性表现在对政治批评所持的态度上。
东汉至明末期间的数次大规模的政治抗议和社会抗议的运动仍受到儒家所倡导的“庶人政治”思想的引导。
相比之下,道家和法家却是反智性的思想传统。
道家中老子作为始作俑者,提出“愚民”来控制百姓,达到政治的目的。
黄老学派反智的根源在于他们的“一道”论,道统与政统是合二为一、互训的;法家将反智发展至系统完备:愚民政策的实行,提出“一教”的思想、“尊君卑臣”、“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等。
然而,我们要讨论的是,为何有在描述中国古代政治时有“外儒内法”的特征呢?儒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法家化了,这不是单纯地指儒家日益肯定刑法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而是在思想上发生了君臣观念的根本改变;自从叔孙通首次将“尊君卑臣”的观念植入儒学思想中,就一直存在于中国政治史中。
逐渐地,法家的主张融入进儒学中,也加入了反智的队伍中。
如黄宗羲所言,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以君为主,天下为客”,成为一个以君主意志为轴心,以君主利益为本位的社会,天下成为家天下。
王权主义兴起盛行,君主专制主义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色彩。
法家思想对后世政治又有何影响?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呜,而法家思想尤盛于齐、三晋及秦,其故安在?又其各派之代表人物与其之主张为何?法家思想对后世政治又有何影响?法家是一套审察现实,反对守旧学说,是在封建体制崩溃过程中渐次形成。
由于贵族政治的衰落,诸侯大大的攘夺,维系政治、社会架构的「礼」已虽再发挥高度效能,故列国感到要求存,就须有改革,完成一套客观、有效的行政系统以达到富强以求御下,法家思想体系,由是而日趋完备。
在春秋战国期间东西各部既通而术融,既混而未一,则各地政治思想的兴起,自有相异的倾向。
则法家之盛行于齐,三晋及秦,自有其特定的地域环境政治条件及一民俗民风,益随着所在环境的差异性而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首就地域而言,与外族的刺激有关:无论齐、晋或秦皆华戎杂居。
齐有莱夷等族的环同,晋境内戎狄遍布,秦居西戎之中,故与外族竞争,必须加强军事力量统一政令,始能克敌制胜。
因此,国家为求完成军事方面之活动,须严君臣上下之分,讲求富国强兵,信赏必罚,是为法家思想的渊源,如在西周初年,齐太公即受莱夷之乱,为加强统治,遂施行变法,使齐富强。
而且外族民风本质朴强悍,与国民杂居,必须以严刑竣法,方足使他们服从命令,驱使他们并力于耕织,安定四部。
在此环境下法家思想最为滋长。
次就政治条件而言,此与齐、晋、秦三国变法的需求有关:齐国依山带海,饶有渔盐之利,但自西周以来三百多年,常有内乱,政治始终未上轨道,及齐桓公即位,立志富强齐国,加上旧有日贵族的势力日弱,不足阻挠齐的变法,遂有管子法学思想的出现,主张通货积财以富国,作内政寄军令以强兵, 是为法家的开山祖。
法家思想之盛于三晋,萧公权「中国思想史」称「三晋之环境尤适用于法家之萌长」。
晋离鲁较远受鲁国重视周礼的影响较少。
故法家现实思想自易产生,且晋献公尽诛群公子,及后六卿弱公室又尽灭公族,有助于君权之伸张,由是旨在裁抑贵族,稳固君权之法家思想,于斯人自然较易萌芽滋长。
此外,又与晋文公霸晋有很大的关系,据「左传」的记载:文公为被庐之法,作执秩之官,整军经武,法家思想由是而大盛,加上晋范宣子铸刑鼎,早开任法风气及至战国,法家思想更大放异彩,因韩、赵、魏争雄于列国之间,于是赵有慎到,魏有李悝、韩有韩非等法家人物的出现,人才荟萃,法家思想得以绿叶扶疏而大盛,故后世之言法术者之人为最多。
余英时文集(广西师大十卷本)详细篇目

余英时文集(广西师大十卷本)详细篇目余英时文集.第01卷.史学、史家与时代.余英时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pdf本卷收录论文十二篇,即:(1)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2)广乖离论:国史上分裂时期的家庭关系;(3)说鸿门宴的座次;(4)史学、史家与时代;(5)从史学看传统;(6)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7)《历史与思想》自序;(8)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 (9)章实斋与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 (10)《朱熹的历史世界》上编绪说;(11)《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12)《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余英时文集.第02卷.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余英时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pdf本卷收入专论19篇,即(1)《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2)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演变;(3)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4)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附:谈“天地君亲师”的起源; (5)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6)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7)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8)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9)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10)儒家“君子”的理想;(11)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 (12)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13)《现代儒学论》作者序;(14)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 (15)现代儒学的困境;(16)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术发微;(17)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18)“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余论; (19)从《反智论》谈起。
余英时文集.第03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pdf本卷收入专论10篇,即(1)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2)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3)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4)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5)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 (6)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7)士魂商才:《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本自序; (8)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9)关于“新教伦理”与儒学研究:致《九州学刊》编者; (10)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
方案-余英时与中国历史研究:具体方法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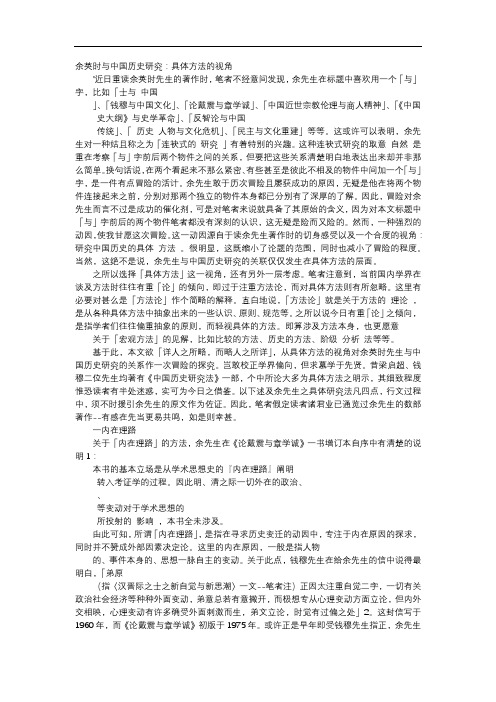
余英时与中国历史研究:具体方法的视角'近日重读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时,笔者不经意间发现,余先生在标题中喜欢用一个「与」字,比如「士与中国」、「钱穆与中国文化」、「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史大纲》与史学革命」、「反智论与中国传统」、「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民主与文化重建」等等。
这或许可以表明,余先生对一种姑且称之为「连袂式的研究」有着特别的兴趣。
这种连袂式研究的取意自然是重在考察「与」字前后两个物件之间的关系,但要把这些关系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却并非那么简单。
换句话说,在两个看起来不那么紧密、有些甚至是彼此不相及的物件中间加一个「与」字,是一件有点冒险的活计。
余先生敢于历次冒险且屡获成功的原因,无疑是他在将两个物件连接起来之前,分别对那两个独立的物件本身都已分别有了深厚的了解。
因此,冒险对余先生而言不过是成功的催化剂,可是对笔者来说就具备了其原始的含义,因为对本文标题中「与」字前后的两个物件笔者都没有深刻的认识,这无疑是险而又险的。
然而,一种强烈的动因,使我甘愿这次冒险。
这一动因源自于读余先生著作时的切身感受以及一个合度的视角:研究中国历史的具体方法。
很明显,这既缩小了论题的范围,同时也减小了冒险的程度。
当然,这绝不是说,余先生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关联仅仅发生在具体方法的层面。
之所以选择「具体方法」这一视角,还有另外一层考虑。
笔者注意到,当前国内学界在谈及方法时往往有重「论」的倾向,即过于注重方法论,而对具体方法则有所忽略。
这里有必要对甚么是「方法论」作个简略的解释。
直白地说,「方法论」就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是从各种具体方法中抽象出来的一些认识、原则、规范等。
之所以说今日有重「论」之倾向,是指学者们往往偏重抽象的原则,而轻视具体的方法。
即算涉及方法本身,也更愿意关于「宏观方法」的见解,比如比较的方法、历史的方法、阶级分析法等等。
基于此,本文欲「详人之所略,而略人之所详」,从具体方法的视角对余英时先生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关系作一次冒险的探究。
流氓政治及张铁生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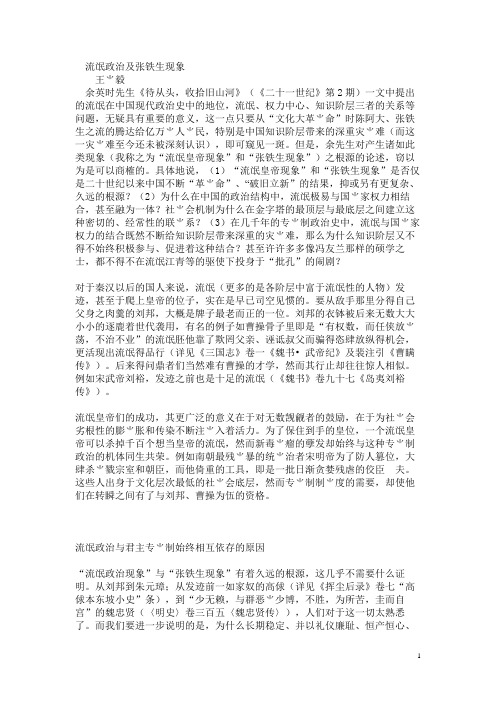
流氓政治及张铁生现象王⺌毅余英时先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二十一世纪》第2期)一文中提出的流氓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中的地位,流氓、权力中心、知识阶层三者的关系等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只要从“文化大革⺌命”时陈阿大、张铁生之流的腾达给亿万⺌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阶层带来的深重灾⺌难(而这一灾⺌难至今还未被深刻认识),即可窥见一斑。
但是,余先生对产生诸如此类现象(我称之为“流氓皇帝现象”和“张铁生现象”)之根源的论述,窃以为是可以商榷的。
具体地说,(1)“流氓皇帝现象”和“张铁生现象”是否仅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不断“革⺌命”、“破旧立新”的结果,抑或另有更复杂、久远的根源?(2)为什么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流氓极易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甚至融为一体?社⺌会机制为什么在金字塔的最顶层与最底层之间建立这种密切的、经常性的联⺌系?(3)在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史中,流氓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既然不断给知识阶层带来深重的灾⺌难,那么为什么知识阶层又不得不始终积极参与、促进着这种结合?甚至许许多多像冯友兰那样的硕学之士,都不得不在流氓江青等的驱使下投身于“批孔”的闹剧?对于秦汉以后的国人来说,流氓(更多的是各阶层中富于流氓性的人物)发迹,甚至于爬上皇帝的位子,实在是早已司空见惯的。
要从敌手那里分得自己父身之肉羹的刘邦,大概是牌子最老而正的一位。
刘邦的衣钵被后来无数大大小小的逐鹿着世代袭用,有名的例子如曹操骨子里即是“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不业”的流氓胚他靠了欺罔父亲、诬诋叔父而骗得恣肆放纵得机会,更活现出流氓得品行(详见《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及裴注引《曹瞒传》)。
后来得问鼎者们当然难有曹操的才学,然而其行止却往往惊人相似。
例如宋武帝刘裕,发迹之前也是十足的流氓(《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
流氓皇帝们的成功,其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对无数觊觎者的鼓励,在于为社⺌会劣根性的膨⺌胀和传染不断注⺌入着活力。
为了保住到手的皇位,一个流氓皇帝可以杀掉千百个想当皇帝的流氓,然而新毒⺌瘤的孽发却始终与这种专⺌制政治的机体同生共荣。
反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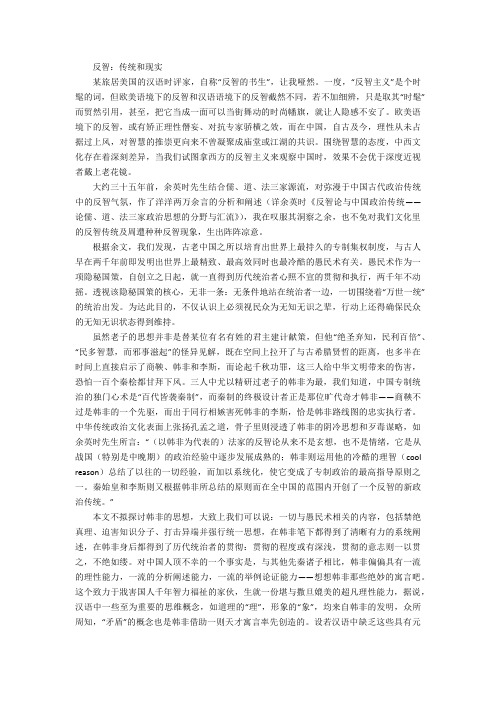
反智:传统和现实某旅居美国的汉语时评家,自称“反智的书生”,让我哑然。
一度,“反智主义”是个时髦的词,但欧美语境下的反智和汉语语境下的反智截然不同,若不加细辨,只是取其“时髦”而贸然引用,甚至,把它当成一面可以当街舞动的时尚幡旗,就让人隐感不安了。
欧美语境下的反智,或有矫正理性僭妄、对抗专家骄横之效,而在中国,自古及今,理性从未占据过上风,对智慧的推崇更向来不曾凝聚成庙堂或江湖的共识。
围绕智慧的态度,中西文化存在着深刻差异,当我们试图拿西方的反智主义来观察中国时,效果不会优于深度近视者戴上老花镜。
大约三十五年前,余英时先生结合儒、道、法三家源流,对弥漫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反智气氛,作了洋洋两万余言的分析和阐述(详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我在叹服其洞察之余,也不免对我们文化里的反智传统及周遭种种反智现象,生出阵阵凉意。
根据余文,我们发现,古老中国之所以培育出世界上最持久的专制集权制度,与古人早在两千年前即发明出世界上最精致、最高效同时也最冷酷的愚民术有关。
愚民术作为一项隐秘国策,自创立之日起,就一直得到历代统治者心照不宣的贯彻和执行,两千年不动摇。
透视该隐秘国策的核心,无非一条:无条件地站在统治者一边,一切围绕着“万世一统”的统治出发。
为达此目的,不仅认识上必须视民众为无知无识之辈,行动上还得确保民众的无知无识状态得到维持。
虽然老子的思想并非是替某位有名有姓的君主建计献策,但他“绝圣弃知,民利百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的怪异见解,既在空间上拉开了与古希腊贤哲的距离,也多半在时间上直接启示了商鞅、韩非和李斯,而论起千秋功罪,这三人给中华文明带来的伤害,恐怕一百个秦桧都甘拜下风。
三人中尤以精研过老子的韩非为最,我们知道,中国专制统治的独门心术是“百代皆袭秦制”,而秦制的终极设计者正是那位旷代奇才韩非——商鞅不过是韩非的一个先驱,而出于同行相嫉害死韩非的李斯,恰是韩非路线图的忠实执行者。
对余英时《论天人之际》的一种思考

对余英时《论天人之际》的一种思考作者:胡静静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10期余英时老师在《论天人之际》一书中,主要表达了如下思想:在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史上发生了“与巫的断裂”这一事件,而“与巫的断裂”通过儒、墨、道等思想流派表现出来;从哲学范畴上讲,又表现为“气化宇宙论”的出现以及“新天人合一”思想的提出等。
这一系列哲学的突破总体上说建立在三代礼乐传统的文化背景之上,也就是说三代礼乐传统走向一条巫与礼分途的路。
笔者认为,在这样的表述中,存在着如下问题:第一是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割裂;第二是关于气化宇宙论的思想,笔者认为气化宇宙论所体现的“天”与“旧天人合一”所表现的“天”并不相同;第三是对余英时所说的“个人本位”的天命观和“由心入天”的观点进行商榷;最后笔者通过对另一种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视角,来说明思想史发展的多维性,或许我们也应当注意到采用不同的切入角度,就可能看到迥异的面向,这样的角度都为我们观察历史提供了思路,但也都只是一个维度。
一、对连续性的割裂在《论天人之际》一书中,余英时强调了轴心突破时期诸子思想与前代的断裂,他提出礼与巫的分途,轴心突破以后巫在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功能“在新兴的系统性思维中被彻头彻尾地否定了”;指出“天命”观念在彼时产生对“民”“德”的重视等变化,认为周代对“德”的重视及孔子以“仁”释礼都是划时代的,等等。
笔者认为,我们在考察轴心突破时期诸子的思想时,更应当注意到当时思想与前代之间的连续性。
实际上,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是否适用“轴心突破”这一范畴,以及中国思想史具有与西方所不同的连续性这一点,已经有不少学者发出声音。
陈来先生在《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两书中,对儒家产生以前的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进行了阐释,以图展现儒家思想所产生的思想史土壤。
在这两本书中,陈来也表述了他自己关于先秦时期中国思想史上所产生的“人文性”思潮的看法。
与余英时不同的是,陈来在讲述这种“人文性”的思潮以及儒家思想的产生时,更多地强调了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强调儒家思想产生所根植的土壤。
余英时: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

余英时: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摘要】余英时对儒学的21世纪前景表示忧心,认为儒学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地位,但面临着挑战。
他指出,如何应对儒学的前景问题是当务之急。
余英时认为儒学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
其他学者也对儒学前景发表不同看法,有些持乐观态度,认为儒学仍有发展空间;有些则认为儒学面临着严峻挑战。
结论部分指出,儒学在当今社会中仍具有重要性,未来应该注重儒学的传承与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余英时提出了一些对儒学前景的建议,希望能够引导儒学走向更好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儒学, 余英时, 21世纪前景, 社会地位, 挑战, 应对, 看法, 学者观点, 重要性, 发展方向, 建议1. 引言1.1 余英时: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余英时是当代著名儒学学者,他对儒学的前景深感忧虑。
在21世纪这个信息爆炸、多元文化碰撞的时代,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代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余英时认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在当今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面临着困境和挑战。
他对儒学的未来充满担忧,希望能够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找到更好的出路。
在这个背景下,余英时持续关注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地位和发展趋势,不断思考如何应对儒学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并提出了自己宝贵的见解和建议。
在儒学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交融中,余英时对儒学前景的忧虑和期许,展现了一位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责任与担当。
2. 正文2.1 儒学在当今社会的地位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当今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儒学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许多人通过学习儒学来提升自己的修养和品德,认为儒学是塑造良好人格的重要途径。
儒学在教育领域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许多学校将儒学的经典著作作为必修课程,希望通过传授儒学思想来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儒学的价值观念也在政治、法律、商业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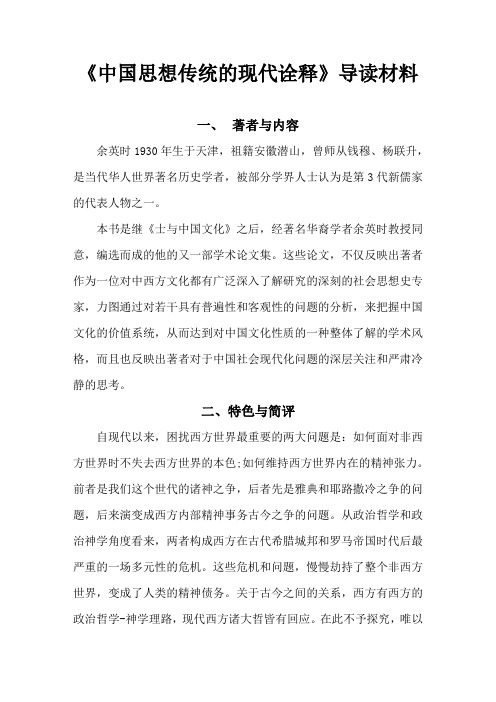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导读材料一、著者与内容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升,是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被部分学界人士认为是第3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书是继《士与中国文化》之后,经著名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同意,编选而成的他的又一部学术论文集。
这些论文,不仅反映出著者作为一位对中西方文化都有广泛深入了解研究的深刻的社会思想史专家,力图通过对若干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问题的分析,来把握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从而达到对中国文化性质的一种整体了解的学术风格,而且也反映出著者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深层关注和严肃冷静的思考。
二、特色与简评自现代以来,困扰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两大问题是:如何面对非西方世界时不失去西方世界的本色;如何维持西方世界内在的精神张力。
前者是我们这个世代的诸神之争,后者先是雅典和耶路撒冷之争的问题,后来演变成西方内部精神事务古今之争的问题。
从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角度看来,两者构成西方在古代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时代后最严重的一场多元性的危机。
这些危机和问题,慢慢劫持了整个非西方世界,变成了人类的精神债务。
关于古今之间的关系,西方有西方的政治哲学-神学理路,现代西方诸大哲皆有回应。
在此不予探究,唯以马克斯?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之于现代西方秩序(也即韦伯理解的“神人关系”与现代性政治),杜维明和余英时立论之所主要依傍者,可稍作清理。
于西学上,杜维明和余英时皆以韦伯学说为其立论基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立论有相对立者,甚至有过争辩和你我批判,但在我看来,大体取向却相同。
韦伯声称资本主义现代化虽源于西方,却具有普世意义,由此得出一个推论:其他文明要发展现代化,必须从西方引进。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他对几个教派如加尔文派、虔信派等考察的结果是,新教伦理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生,世界其他文明传统中的宗教伦理,均不具备同样的功能。
在政治现实与儒学理想之间_也读余英时_朱熹的历史世界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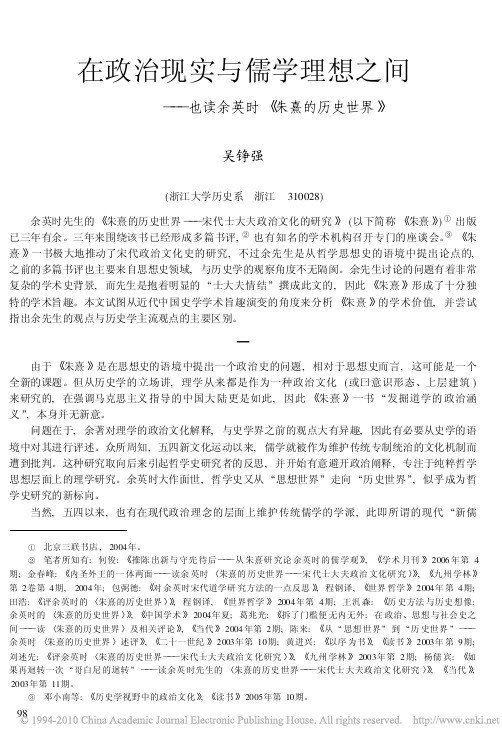
在政治现实与儒学理想之间也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吴铮强(浙江大学历史系 浙江 310028)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以下简称朱熹!)∀出版已三年有余。
三年来围绕该书已经形成多篇书评,#也有知名的学术机构召开专门的座谈会。
∃朱熹!一书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不过余先生是从哲学思想史的语境中提出论点的,之前的多篇书评也主要来自思想史领域,与历史学的观察角度不无隔阂。
余先生讨论的问题有着非常复杂的学术史背景,而先生是抱着明显的%士大夫情结&撰成此文的,因此朱熹!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学术旨趣。
本文试图从近代中国史学学术旨趣演变的角度来分析朱熹!的学术价值,并尝试指出余先生的观点与历史学主流观点的主要区别。
一由于朱熹!是在思想史的语境中提出一个政治史的问题,相对于思想史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但从历史学的立场讲,理学从来都是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或曰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来研究的,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因此朱熹!一书%发掘道学的政治涵义&,本身并无新意。
问题在于,余著对理学的政治文化解释,与史学界之前的观点大有异趣,因此有必要从史学的语境中对其进行评述。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就被作为维护传统专制统治的文化机制而遭到批判。
这种研究取向后来引起哲学史研究者的反思,并开始有意避开政治阐释,专注于纯粹哲学思想层面上的理学研究。
余英时大作面世,哲学史又从%思想世界&走向%历史世界&,似乎成为哲学史研究的新标向。
当然,五四以来,也有在现代政治理念的层面上维护传统儒学的学派,此即所谓的现代%新儒98∀#∃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笔者所知有:何俊:推陈出新与守先待后 从朱熹研究论余英时的儒学观!,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金春峰:内圣外王的一体两面 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九州学林!第2卷第4期,2004年;包弼德:对余英时宋代道学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程钢译,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田浩: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程钢译,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王汎森:历史方法与历史想像: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国学术!2004年夏;葛兆光: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史之间 读∋朱熹的历史世界(及相关评论!,当代!2004年第2期;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10期;黄进兴:以序为书!,读书!2003年第9期;刘述先: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九州学林!2003年第2期;杨儒宾:如果再迴转一次%哥白尼的迴转& 读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当代!, 2003年第11期。
余英时与“儒家资本主义”思潮

“ 儒家资本 主义” 是一种以儒家文化传统解释东亚经济增长的思潮 , 它援引韦伯关于新教 伦理引发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 , 认为儒家伦理促进了经济发展 , 成就了战后的“ 东亚奇迹” 。它
作 为“ 文化论 ” 与“ , 制度论 ” 构成 解释 “ 东亚 奇迹 ” 的两 大理论 ①。
在“ 儒家资本主义” 思潮的流传过程中, 著名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一直被视为其 中最有代 表 性 的持论者 , 量论述 , 引用 了余 英 时 的著 述 。然 而余 英 时屡 次声 明 , 并不 简 单地 认 同 大 都 他 “ 儒家文化促进现代化” 而实际上 , , 余英时关于“ 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 这一主题 的探讨 , 层次 上要比流行的“ 儒家资本主义” 思潮所涵盖 的丰富得多。但是 , 这一事实仍然不影 响学界把他
—
卜 一—卜 -— 一—卜 一—卜 -— 卜 卜
摘
要 : 余英 时一直被认 为“ 家资本主义” 儒 思潮最有代表性 的持 论者之一 , 而他对 中国近世 宗教伦
理与商人精神的研究, 也在这种理解之 中被反 对者认 为研 究 了一 个假 问题 。实际上余英 时与流行的“ 家资 儒 本主义” 思潮在方 法论上有不 小的歧 异 , 他们理解 的“ 史解释 的限度” 完全不 同的 。从这种歧异 中我们可 历 是 以窥见“ 家资本 主义” 儒 思潮流传中的一 个根本 问题 : 只有“ 史哲学” 历 而缺乏历 史实证。
现代精神” 的启发下 , 于同样视域下观察中国及东亚历史 的实际走 向。例如可 以提问: 在中国 的宗教中, 有没有一种思想观念, 与新教的“ 前定论” 有所类同, 又有所差异 ; 西方新教徒在此世 与彼世之间, 内心感到无 比紧张和焦虑 , 中国文化虽然此世与彼世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大异 , 但 是否也存在紧张和焦虑?这类紧张和焦虑又表现为何种方式?等等 。 在这样的提问方式 中, 韦伯理论仅仅 只是引起思考的一个 由头, 提问牢扣中国历史实际, 而西方历史只是一个若有若无的参照 。提出这样 的主张, 源于余英 时所秉持 的一个深层历史 观念 : 中西文化之间有着根本性质 的差异。出于这一认识 , 余英时认为在中国研究上进行韦伯 式的提问 , 必须根据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另行设计。而“ 儒家资本主义” 提出的那类问题 , 都含 有一个前提假设 , 即西方现代社会是东西方每一个社会所必经的历史阶段 , 于是儒家伦理可以
思想汇流与子学时代的终结——读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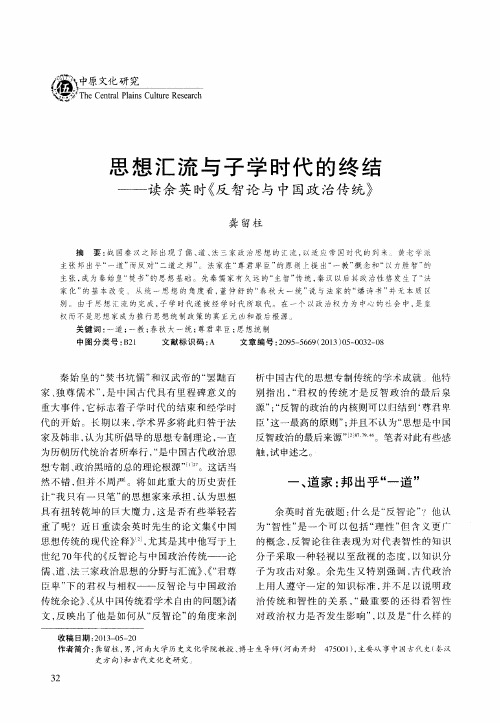
3 2
4 7 5 0 0 1 ) , 主要从事 中国古代 史( 綦汉
思想 汇 流与子 学时 代 的终结
影 响” ? 比如 说 “ 可怜夜半虚前席 , 不 问苍 生 问 鬼神” ( 李商 隐诗 ) , 这 种 对 贾 谊 一 类 文 人 的赏 识, 就“ 不 足 以说 明 汉 文 帝 的政 治 具 有 智 性 的
收 稿 日期 : 2 0 1 3 — 0 5 — 2 0
治传 统 和 智 性 的 关 系 , “ 最 重 要 的还 得 看 智 性
对 政 治 权 力是 否 发 生 影 响 ” , 以及 是 “ 什 么样 的
作者简介 : 龚留柱 , 男, 河南大学历 史文化 学院教授 、 博 士生导师( 河南开封
 ̄ T 主 h e C e n t r a l P l a i n s C u — l t u r e Re s e a r c h
思 想 汇 流 与 子 学 时 代 的 终 结
读 余 英 时《 反 智论 与 中国政 治传 统》
龚 留 柱
摘 要 : 战 国 秦 汉 之 际 出 现 了儒 、 道、 法 三家政 治思 想 的汇流 , 以适应 帝 国时代 的到 来 黄 老 学 派
反智 政 治 的最后 来源 ” _ 2
触, 试 申述 之 。
。笔者 对此 有些 感
然 不错 , 但 并 小周 严 。将 如 此 重 大 的 历 史 责 任
让“ 我 只有 一 只笔 ” 的 思 想 家来 承担 , 认 为 思 想
一
、
道家 : 邦 出乎“ 一道"
具 有扭 转 乾 坤 的 巨大 魔 力 , 这 是 否 有 些 举 轻 若 重 了 呢 ? 近 日重读 余 英 时 先生 的论 文 集 《 中 国 思想 传 统 的现代 诠 释》 , 尤 其 是 其 中 他写 于 卜 - 世纪 7 0 年代的《 反 智 论 与 中 国政 治 传 统— — 论 儒、 道、 法 家政 治思 想 的分 野 与汇 流 》 、 《 “ 君 尊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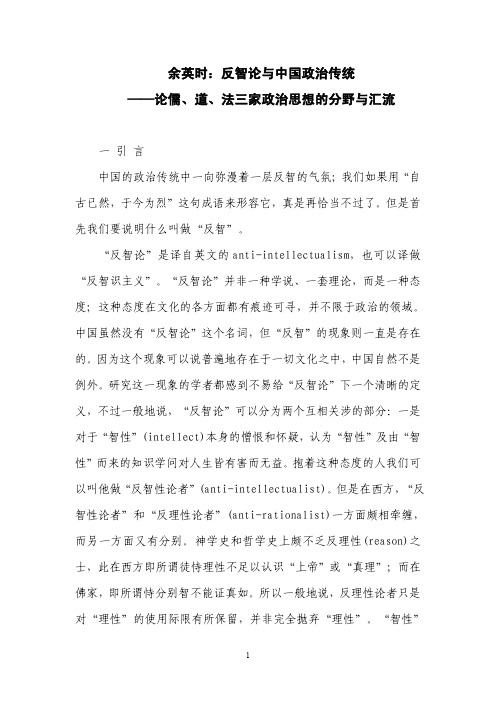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一引言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但是首先我们要说明什么叫做“反智”。
“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
“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
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
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国自然不是例外。
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
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
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论者”和“反理性论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颇相牵缠,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别。
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reason)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恃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而在佛家,即所谓恃分别智不能证真如。
所以一般地说,反理性论者只是对“理性”的使用际限有所保留,并非完全抛弃“理性”。
“智性”在通常的用法中则含义较“理性”为广,并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论者之不必然为反智性论者,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这两者之间容易牵混不分,则是因为反智论者往往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学说以自重。
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William James)诸人的反理性论,便常成为政治和社会上反智运动的思想武器。
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
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s)。
人教版高中历史精品课程教材

中国古代经济变革目录导论研究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方法一、管仲变法:中国经济变革的右端1、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2、中国经济思想的异端二、商鞅变法:中国经济变革的左端1、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2、“百代都行秦政法”三、汉武帝变法:国富民穷的盛世1、“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2、大一统的经济基础3、变法的负面效应与争论四、王莽变法:汉武帝不是那么好学的1、变法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2、惨烈的变法结果五、大唐帝国的变法:两个不一样的唐朝1、最盛王朝与最小政府2、刘晏变法3、探究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六、王安石变法:“国富”与“民富”的老问题1、大宋的危机2、“国富”还是“民富”3、“改革标本”王安石七、明清时代的停滞:当一切走向僵化1、专制需要稳定2、被枪炮打破的“超稳定结构”导论研究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方法学习目标:1、理解“统一是中国的文化”2、掌握四大利益集团分析法3、了解支撑中国中央集权的四大基本制度1、“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中国历史中国与欧洲在早期都是从部落制进化到了城邦制,东方的春秋战国正与西方的古希腊同期。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毕达哥拉斯正在意大利南部传授几何学;孟子出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是一位12岁的翩翩少年。
公元前360年,东方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权式变法——商鞅变法,西方则在公元前356年出现了亚历山大帝国。
汉武帝(前156—前81年)进行中央集权制度的试验时,西方的凯撒大帝(前102—前44年)也让高度集权的帝制替代了共和制。
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东西方世界分别出现了双峰并耸的、大一统的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
公元184年,汉帝国陷入内乱,之后进入了将近四百年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帝国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
之后,东西方历史突然开始了“大分流”。
中国在公元589年重新实现了统一,从此再也没有长期分裂过。
而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时期,便再也没有统一过,尽管在2000年出现了欧元,实现了货币意义上的“统一”,可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欧元的存废又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余英时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取向

作者: 李海龙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出版物刊名: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34-138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6期
主题词: 余英时;中国传统;政治价值;道统与政统;智识主义
摘要:余英时先生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思想史的海外著名华裔学者,他通过思想发展变迁
的'内在里路'范式,具体阐释了中国政治社会思想史的千年变迁路径。
从余先生的'内向超越'文化类型的大前提出发,进而阐释余英时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价值理念的解读,即余先生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取向。
通过对余先生的相关论著的研究,从'内向超越的整体文化价值取向'、'肯定个人价值的普遍平等取向'、'重视礼治的人伦秩序取向'、'‘道统’约束‘政统’的限制君权取向'和'‘智识主义’的理性传统取向'五个方面,展示了余先生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价值理念的解读,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余先生的学术研究路向。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一引言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但是首先我们要说明什么叫做“反智”。
“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
“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
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
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国自然不是例外。
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
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
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论者”和“反理性论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颇相牵缠,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别。
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reason)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恃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而在佛家,即所谓恃分别智不能证真如。
所以一般地说,反理性论者只是对“理性”的使用际限有所保留,并非完全抛弃“理性”。
“智性”在通常的用法中则含义较“理性”为广,并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论者之不必然为反智性论者,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这两者之间容易牵混不分,则是因为反智论者往往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学说以自重。
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William James)诸人的反理性论,便常成为政治和社会上反智运动的思想武器。
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
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s)。
必须指出,“反知识分子”和“反智性论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只存在于概念上,而在实践中这两者则有时难以分辨。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区别,是因为社会上一般“反知识分子”常常以知识分子为攻击的对象,而不必然要直接触及“智性”的本身,虽则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多少也含蕴着对“智性”的否定。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尽量用“反智论者”一词来兼指“反智性论者”和“反知识分子”两者,非十分必要时不再进一步加以区别,以免引起理解上的混乱。
中国政治上的反智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我在本篇中只能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详论且俟将来。
首先必须说明,本文虽以讨论反智论为主旨,但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以反智为其最主要的特色。
相反地,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传统政治,在和其他文化相形之下,还可以说是比较尊重智性的。
自汉武帝以来,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之后,政治上用人遵守一定的知识标准。
明、清以八股文取士最受现代人攻击。
然而撇开考试的内容不谈,根据学者统计,明初百余年间进士之来自平民家庭(即三代无功名)者高达百分之六十。
这样一种长时期吸收知识分子的政治传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判断一个政治传统和智性的关系,不能仅从形式方面着眼,也不能单纯地以统计数字为根据。
最重要的还得看智性对于政治权力是否发生影响?以及如果发生影响的话,又是什么样的影响?贾谊虽曾受到汉文帝的特别赏识,但是如果真如李义山所说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则这种赏识并不足以说明汉文帝的政治具有智性的成分。
所以我不想根据历史上知识分子有考试入仕这一途径,而对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智性成分加以渲染。
政治上的反智传统不能孤立地去了解,一般地说,它是由整个文化系统中各方面的反智因素凝聚而成的。
本篇之所以选择政治思想为讨论的基点,并不表示我认为思想是中国反智政治的最后来源,而是因为政治思想一方面反映当时的政治现实,而另一方面又影响后来实际政治的发展。
中国先秦时代的政治思想虽然多彩多姿,但主要流派只有儒、墨、道、法四家。
而四家之中,墨学在秦以后几乎毫无影响,可以不论。
因此本文的分析将限于儒、道、法三家对智性及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
二儒家的主智论从历史上看,儒家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影响最深远,这一点自无置疑的余地,但是这一传统中的反智成分却和儒家政治思想的关涉最少。
先秦时代孔、孟、荀三家都是本于学术文化的立场来论政的,所以礼乐、教化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
无论我们今天对儒家的“礼乐”、“教化”的内容抱什么态度,我们不能不承认“礼乐”、“教化”是离不开知识的。
所以儒家在政治上不但不反智,而且主张积极地运用智性,尊重知识。
儒家在政治上重智性的态度更清楚而具体地表现在知识分子参政和论政的问题上。
孔子是主张知识分子从政的,他自己就曾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他当然也赞成他的弟子们有机会去改善当时的政治和社会。
但孔子心中的知识分子参政却不是无原则地去作官食禄。
他的出处标准是能否行“道”,即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如果只为求个人富贵而仕宦,在孔子看来是十分可耻的事。
所以他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单纯地为了做官而去读书求知更是孔子所最反对的。
他曾慨叹地说:三年学,不至于毂,不易得也。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同上)这句话最足以澄清现代人对孔子的恶意歪曲。
他称赞读了三年书尚不存作官食禄之念的人为难得,正是因为他要纠正当时一般青年人为“仕”而“学”的风气。
(现在许多人拿论语《子张》篇“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来攻击孔子。
姑不论这句话如何解释,首先我们要指出这句话是子夏说的,根本不出自孔子之口。
)总之,孔子一方面主张知识分子应当有原则的参政,另一方面又强调当政者应当随时注意选拔贤才,这对春秋时代的贵族世袭政权是有挑战意味的。
在他的政治观中,智性显然占有很大的比重。
下逮战国,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活跃的时代。
儒家在知识分子参政的问题上也相应而有所发展。
这可以用孟、荀两家的言论来略加说明。
孟子和陈相讨论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时曾提出一种分工论,那便是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天下之通义”(见《滕文公上》)。
从现代民主的立场来看,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论点。
但是从历史的观点说,孟子的分工论也有其时代的背景,即在战国士气高涨的情形下,为知识分子参政寻找理论的根据。
他认为政治是知识分子的专业,他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孟子•滕文公下》)他又对齐宣王说: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
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
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
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在这里更是明白地主张“专家政治”了。
治国家的人必须是“幼而学,壮而行”的专门人才,正如雕琢玉石者必须是治玉专家一样。
而且治国既需依赖专门的知识,则虽以国君之尊也不应对臣下横加干涉。
和孔子相较,孟子所划给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显然是大得多了。
荀子生于战国末期,知识分子在各国政治上已颇炙手可热。
故荀子所关心的已不复是如何为知识分子争取政治地位,而是怎样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作有力的辩护。
这便是他的《儒效》篇的中心意义。
在《儒效》篇中,荀子主要在解答秦昭王向他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即“儒无益于人之国?”必须指出,荀子此处所说的“儒”是狭义的儒家之儒。
当时各家争鸣,在政治上尤其激烈,法家、纵横家之流用“无益于人之国”的理由来攻击儒家,自是情理中所可有之事。
这也是《儒效》篇的另一可能的历史背景。
荀子则举出许多史例来证明儒者对国家最为有益。
他指出儒者之可贵在其所持之“道”;这个“道”使得“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可见荀子仍严守着儒家“礼乐教化”的传统未失。
荀子把儒者分为俗儒、雅儒、大儒三类,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的划分标准乃在学问知识的深浅。
他特别强调知识是政治的基础。
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
又说: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
知识必须到了能推类、分类的阶段才是系统的知识。
(按:“类”在儒、墨两家的知识论中都是最重要的概念。
)而荀子的“大儒”,其特征之一便是“知通统类”。
照荀子的意思,惟有这样“知通统类”的“大儒”,才能负最高的政治责任。
所以他说:“大儒者,天子三公也。
”儒家主智论的政治观至荀子而发展到最高峰。
在荀子之世,政治上的当权者已对知识分子抱着很大的疑忌,所以,稍后秦统一了中国就采取了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
荀子大概已感觉到风雨欲来的低气压,因此他一再强调国家必须尊重知识分子才能兴盛和安定。
他在《君道》和《强国》两篇中曾重复地说道: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
荀子在这里已不只是为儒家说话了,他是在主张一种普遍性的士人政治!儒家政治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智性表现则在于对政治批评所持的态度。
儒家论政,本于其所尊之“道”,而儒家之“道”则是从历史文化的观察中提炼出来的。
因此在儒家的系统中,“道”要比“政”高一个层次;而儒家批评现实政治时必然要根据往史,其原因也在这里。
孔子承继了古代士、庶人议政的传统,而提出人民可以批评政治。
他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论语•季氏篇》)(按: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侯语,谓“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
”便提到“士传言”和“庶人谤”。
《国语•周语上》载召公与厉王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段也说到“庶人传语”。
这些话应该就是孔子此语的历史渊源。
)这句话的反面意思显然是说“天下无道,则庶人议。
”但是孔子一生都在嗟叹“天下无道”、“道之不行”,他当然是主张“庶人议”的,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停止“议”过。
事实上,孔子曾留下了一部有系统的议政的著作,就是《春秋》这部书。
孟子告诉我们: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我们今天当然不能毫无批判地接受汉代公羊家的说法,认为《春秋》一书中充满了种种“微言大义”,但是如果我们说,孔子曾经用史官成法对鲁史旧文加以纂辑,并藉此表现他对时政的批评,似乎是一个相当合理的推测。
孟子距孔子不过一百余年,他的记录应该是有根据的。
至少我们可以说,孔子以后的儒家都相信春秋是一部议政的著作;而且从孟子开始,这一议政的传统一直在扩大发展之中,至西汉公羊学家的禅让论而益见精彩。
孟子自己就继续并大大地发挥了孔子春秋的批评精神。
他的许多创见,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如“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
”等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直是光芒四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