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陌生化
张爱玲散文语言陌生化探析

一
就得多花钱在时装店里” 如果 你不调戏女人 ,她说你不是一 ;“ 个 男人 ;如果 你调戏 她 ,她 说你不是—个上等人 ” ;“ 若是女 人信 口编 了故事之 后就可 以被抽 版税 ,所有 的女人全 都发财 了”( 谈 女人 》 ;“ 《 ) 谁都说上海人坏 ,可是坏g - S- ”“ 人  ̄f - ) 寸 好 爱昕坏 人的 故事 ,坏 人可不 爱昕 好人 的故事 ”( 到底 是上海 《
个诸 葛亮 ”( 炎樱语录 》 ;“ 《 ) 二鸟在林 中不如 一鸟在手 ”( 谈 《
吃与 画饼充饥 》 )的 中西方谚 语 以及 “ 小狗 ,走一走 ,咬 一 小 口”( 私语 》 ;“ 《 ) 香又 香来糯 又糯”( 道 路 以目》 《 )的歌谣 ;也 有 “ 兄弟如手足 ,妻子 如衣服 ”( 更衣记 》 ;“ 《 ) 洗手净指 甲 ,
人 》 ;“ ) 不知道钱的坏处 ,只知道钱的好处 ”( 童言无忌 》 ; 《 )
、
熟 悉 的陌 生
具体说来 , 张爱玲 散文语言的陌生化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
是把语 言还原到它的原生状态 中, 利用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 口语 、
“ 文明人要原始也原始不 了 :他们对野蛮没有恐怖 ,也没有尊 敬 ”( 谈跳 舞 》 ;“ 《 ) 世俗所 供的观音不过 是古装美女赤 了脚 , 半裸的高大肥硕 的希腊石像不 过是女运动家 ,金发的圣母不 过 是个俏 奶妈 ,当众喂 了一千余年的奶 。 《 ”( 谈女人 》 这样充 ) 满 了机 警和智慧 的俏皮话 ,在 张爱玲的散 文 中也随处可见 。 这些文字充 分展 示了张爱玲的智慧和才 华 , 也昭示了她的 独树一帜 的驾驭 语言的能力 ,让读 者在 忍俊不禁中拍 案叫绝 ,
张爱玲“太阳”意象的陌生化建构

张爱玲 “ 阳" 象的 陌生化建构 太 意
林 莺
摘 要 : 阳本 是 宇 宙 中重 要 的 天 体 , 作 为 一 种 意 象 应 用 于 文 本 之 中 。 温 暖 和 光 明 的 象 征 的 太 太 后
阳, 却在 张爱玲的笔下演绎 出隔世 、 生和 凄凉 , 陌 幻化 为吞噬 生命 的预 兆。张爱玲 作 品中将太 阳进 行
“ 陌生化 ” D fm l r ai ) ( e ia zt n 理论 是 2 a ii o 0世纪 初 由俄罗 斯 文 艺理 论 家 维 克多 ・ 什克 洛 夫斯
基 在《 为技 巧 的艺术 》 书 中提 出 的 , 谓 “ 生 化 ” 是 “ 使 之 陌生 ’ 使对 象 形 式 变 得 困 作 一 所 陌 就 ‘ ,
张爱玲主 动设置 的 “ 阳 ” 象 是 以 自身 做基 础 的对 人 世 的 旁 观 , 文 本 中 一 个 “ 照 太 意 是 关 体 ” 以太 阳的陌生化塑 造为手段 , 面建构她 的时代 的人物 众生 。“ 阳 ” , 全 太 在张 爱玲 的设 置下 是有 “ ” 的 , 者 可 以说 张 爱 玲 就 是 这个 旁观 者 , 是 这 种 旁 观 者 的设 置 可 以使 张 爱 玲 人 性 或 正
立 足点 。
“ 隔世 的太 阳” 可能会令 人觉得 意象 突兀 , , 却是 其 笔下 人物 人生 观 的彰显 , 是张 爱玲 叙 也 述 的基调 。张爱玲笔 下常有 “ 世 的太 阳” 隔 的诉说 : 连古 代 的太 阳都 落上 了灰尘 。 ⑤( 小 团 “ ” 《 圆》 “ ) 野外 的 日光照在 碎花椅 套上 , 梦一样 的荒凉 ” ( 谈 画》 。 《 ) “ 隔世 的太 阳 ” 打破 了 自动化 感 受 的定 势 , “ 冲破 审 美惯 性 , 主 体 用 惊 奇 的眼 光 关 注对 使 象, 让钝 化 的审美复活 , 在创造 “ 复杂化 ” “ 化 ” 和 难 的过 程 中 , 加 感觉 的难 度 , 长感 觉 的过 增 延
近二十年来国内关于张爱玲小说语言艺术研究综述

近二十年来国内关于张爱玲小说语言艺术研究综述作者:祖雪妍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8年第06期内容摘要:近二十年来,国内关于张爱玲小说语言艺术的研究一直不断进行,主要侧重如下四个方向:一侧重语言修辞手法的研究,二侧重语言特色的研究,三侧重语言风格的研究,四侧重语言陌生化效果的研究。
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对于天才作家张爱玲小说语言艺术的理解,成就显著。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语言艺术研究综述作家叶兆言曾说:“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
”传奇女子张爱玲留给我们太多唏嘘,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栩栩如生,仿佛走进人心里。
同样,她的种种表达就像她本人的照片一样让人过目不忘,难以释怀。
研究张爱玲小说语言艺术对探究张爱玲小说无疑是重要的一环。
近二十年来,关于张爱玲小说语言艺术的研究一直在扩宽及深入,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张爱玲小说的色彩语言、修辞手法、语言风格以及语言陌生化效果。
本文将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与分析,希望为后来人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一.关于张爱玲小说语言修辞手法研究张爱玲小说中使用的修辞手法别具一格,让人眼界大开。
近二十年来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反讽、隐喻以及比喻三种手法。
龚敏律认为“在反讽中,张爱玲使人性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人性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冲突碰撞,或以冷静、或无奈、或居高临下、或超脱、或夸张的心态,呈现出酸甜苦辣的人生百相。
”复旦大学林莺从张爱玲的作品中总结了自然万象、人体、性别人生观、性格映照、感官体验五类隐喻,“遗”、“世”、“独”、“立”四个范畴,并以语言学视角概括出张爱玲“在矛盾中寻求对立”的范畴内隐喻的独特风格。
邬远峰的《素朴中的粉饰——张爱玲小说写作中的比喻技巧》、杨峰的《论张爱玲作品的比喻艺术》两篇专文主要从喻体的选择,比喻与其它修辞的交叉以及比喻的修辞效果展开,其他研究者的思路大致相同,张晓平的文章则凸显了张爱玲小说比喻手法的现代性特征。
二.关于张爱玲小说语言特色研究近二十年来关于研究张爱玲小说的语言特色研究主要以色彩美和音乐美两个角度切入。
论张爱玲小说的语言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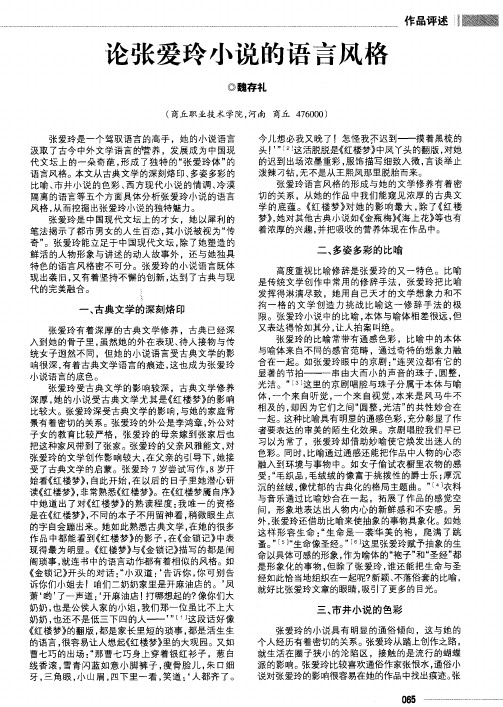
今儿想必 我又晚 了 !怎怪 我不迟到——摸 着黑梳 的 头! ” ’ E z ] 这活脱 脱是《 红楼梦》 中凤 丫头的翻版 , 对她 的迟到 出场浓 墨重彩 , 服饰 描写细致入微 , 言谈举止 泼辣 刁钻 , 无不是从王 熙凤 那里脱胎 而来 。 张爱玲语言风 格的形成 与她的文学修 养有着密 切的关系 ,从她 的作品 中我们能 窥见浓厚 的古典文 学 的底蕴 。《 红 楼 梦》 对 她 的影 响最 大 , 除了《 红楼 梦》 , 她对其他古典 小说 如《 金瓶梅》 《 海 上花》 等也有 着浓厚的兴趣 , 并把 吸收 的营养体现在作 品中。
二、 多姿多彩的比喻
高度重视 比喻修 辞是张爱玲 的又一特色 。比喻 是传统文学创作 中常用 的修辞手 法 ,张爱玲 把比喻 发挥得淋漓尽致 ,她 用 自己天 才的文学想 象力和不 拘一 格 的文 学创 造力 挑 战比 喻这 一修 辞 手 法 的极 限。张爱玲小说 中的比喻 , 本体 与喻体相 差很远 , 但 又表达 得恰 如其分 , 让人拍案 叫绝。 张爱玲 的比喻 常带有通感色彩 ,比喻 中的本体 与喻体 来 自不 同的感官范畴 ,通过奇 特的想象 力融 合在一起。如张爱玲 眼中的京剧 : “ 连哭泣都有 它的 显 著的节拍——一 串由大而小的声音 的珠 子 , 圆整 , 光洁。” E 3 这里 的京剧唱腔 与珠 子分 属于 本体 与喻 体, 一个来 自听觉 , 一个来 自视觉 , 本 来是风 马 牛不 相 及的 , 却因为它们之 间“ 圆整 , 光洁” 的共性妙 合在 起 。这种 比喻具有 明显 的通感色彩 , 充分 彰显了作 者 要表达的审美 的陌生化效果 。京剧 唱腔我们 早已 习以为常 了,张爱玲却借 助妙喻使 它焕 发 出迷人 的 色彩 。同时, 比喻通过通感还 能把作品中人 物的心 态 融入 到环境与事物 中。如女子偷试衣 橱里衣物 的感 受: “ 毛织品 , 毛绒 绒的像 富于挑 拨性的 爵士乐 ; 厚沉 沉 的丝绒 , 像 忧郁的古典化的格 局主题曲。” E 衣料 与音 乐通过比喻妙合在 一起 ,拓展 了作品的感 觉空 间 ,形 象地 表达 出人物 内心 的新鲜感 和不安感 。另 外, 张爱玲还借助比喻来使 抽象的事物具象化。如她 这 样形 容 生命 : “ 生命 是一 袭 华美 的袍 ,爬满 了跳 蚤。 ” E 5 ] I ‘ 生命像 圣经。 ” E e 这里张爱玲 赋予抽象的生 命 以具体可感的形象 , 作为喻体 的“ 袍子 ” 和“ 圣经 ” 都 是形 象化的事物 , 但 除了张 爱玲 , 谁还 能把生命 与圣 经如此恰 当地组织在 一起 呢? 新颖 、 不落俗套 的比喻 , 就好比张爱玲文章的眼睛 , 吸引了更 多的 目光。
浅析文学作品中的“陌生化”现象

浅析文学作品中的“陌生化”现象刘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内容提要:“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者奉献给文艺学界的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基本概念,它既是一种艺术手段,又是一种艺术效果。
陌生化理论的成立有其内在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
文学作品中陌生化氛围的营构主要体现在陌生化的语言、陌生化的形象、陌生化的意蕴三个层面。
从审美现代性来看,陌生化就是通过文学技巧和形式因素的强调恢复审美感受的真实性,追求文学的本真存在状态。
关键词:陌生化陌生化氛围熟悉的陌生化本真状态“陌生化”一词由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他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被人们称为艺术的东西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要重新去体验生活,感觉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的。
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一种幻象的事物的感觉,而不是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反常化”程序及增加了感觉的难度与范围的高难形式的程序,这就是艺术的程序,因为艺术中的接受过程是具有自我目的的,而且必须被强化;艺术是一种体验人造物的方式,而在艺术里所完成的东西是不重要的。
①这里提到的“反常化”也就是所说的“陌生化”,只是翻译略有不同。
什克洛夫斯基创造性地提出这一理论,并将其上升为艺术的总原则,随后“陌生化”理论日渐引起文学理论界的关注。
正如荷兰学者佛克马所说“欧洲文论家几乎每一个新派别都从这‘形式主义’传统得到启发。
”②陌生化概念应用于文学理论预示着现代主义思想的艺术潮流正从俄国形式主义这里孕育,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文艺理论在西方由作者本体论到作品本体论的历史发展恰恰肇始于此。
因此,陌生化理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范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理论价值,应结合中国文论发展现状予以深入地探讨。
“陌生化”一词是什克洛夫斯基按照俄文构词法生造的一个新词。
这个词是由副词“ctpahho”变成的动名词,含有“使之陌生、惊奇、不寻常”等涵义。
③什克洛夫斯基将其界定为“使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难度和时间的方法。
《金锁记》的陌生化翻译研究

第 49 卷 第 3 期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
ou
r
na
lo
fI
nne
rMongo
l
i
aNo
rma
lUn
i
ve
r
s
i
t
Ph
i
l
o
s
ophy & So
c
i
a
lSc
i
enc
e)
y(
May2020
Vo
l.
49No.
3
« 金锁记 » 的陌生化翻译研究
游 晟1,武海燕2
者.1943 年,她的中篇小说«金锁记»载 于«杂 志»月
刊,好评不断,被誉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1]9-10 .
张爱玲也借 此 蜚 声 上 海,大 放 异 彩.1955 年,张 爱
玲远赴美国,计 划 以 英 语 写 作 打 入 主 流 市 场,无 奈
The Ri
c
e Spr
ou
t Song 销 路 不 佳,The Nak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G
7623(
2020)
03
G
0111
G
G
06
DOI:
10.
3969/
i
s
sn.
1001-7623.
2020.
03.
015
j.
张爱 玲 是 中 国 近 代 文 学 史 上 著 名 的 作 家 和 译
题,张爱玲在英译«金 锁 记»的 过 程 中 究 竟 采 用 了 什
浅谈文学语言的陌生化

浅谈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作者:张艳玲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上旬刊》 2012年第3期张艳玲陌生化理论是由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陌生化”这个词语最早是1914年什克洛夫斯基在其纲领性的宣言《词的复活》中提出的。
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重要成员之一的什克洛夫斯基,是从克服人的感觉自动化这一角度提出陌生化问题的。
他认为,动作一旦成为习惯就会带有机械性,对于多次感受过的事物,人们在开始的时候会用“感受”来接受它,但渐渐地就会对它习以为常,最后成为一种习惯的、自动的动作。
当我们所有的习惯都变得机械、僵硬,退回到无意识和自动的环境中,我们往往就会对摆在我们眼前的事物视而不见,感受不到它的独特性。
这就是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感觉“自动化”。
而“陌生化”能够使人打破“自动化”的束缚,摆脱日常感受的惯常化,它会刺激人们已经麻木的神经,重新唤起人对事物、对世界的新奇感受。
“陌生化”理论开始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的。
而艺术的目的就在于使人恢复对于事物的感觉,“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感觉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存在着一种名为艺术的东西。
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视觉而不是作为识别的事物的感觉;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的手法,是使形式艰深化,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的手法,因为艺术中的感觉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应该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的制作的方法,而‘制作’成功的东西对艺术来说是无关重要的”。
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也能够打破“自动化”,实现“陌生化”,主要表现为语言的新奇与变异。
“艺术家永远是挑起事物暴动的祸首。
事物抛弃自己的旧名字,以新名字展现新颜,便在诗人那里暴动起来。
诗人使用的是多种形象—譬喻、对比…以此实现语义学的发展,他把概念从它所寓的意义系列中抽取出来,并借助于词(比喻)把它掺杂到另一个意义系列中去,使我们的耳目为之一新。
”什克洛夫斯基在提出陌生化理论时,主要是以诗歌语言为依据的。
他指出诗歌语言的特点“是为使感觉摆脱自动性而有意识的创造的;它的视觉表示创作者的目的,并且是人为构成的,为的是使感觉停留在视觉上,并使感觉的力量和时间达到最大的限度。
张爱玲小说陌生化手法及意境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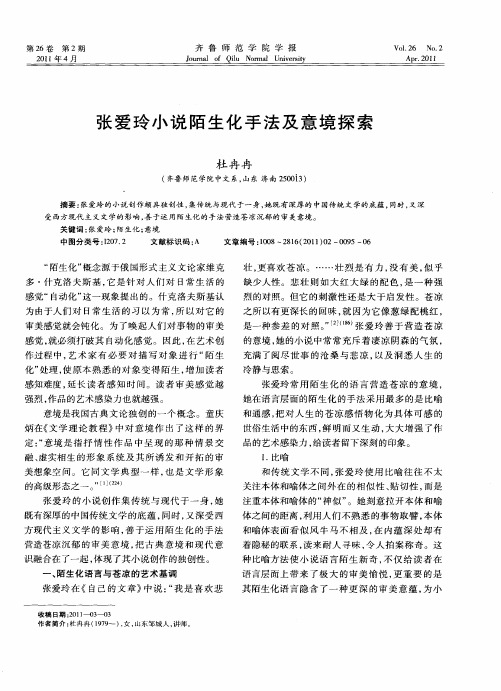
张爱玲 常 用 陌 生 化 的语 言 营 造 苍 凉 的 意 境 , 她在语 言层 面 的 陌生 化 的手 法 采 用 最 多 的 是 比喻
强烈 , 品 的艺术感 染力 也 就越强 。 作
意境 是我 国古 典 文 论 独创 的一 个 概 念 。童 庆
和通感 , 对 人 生 的 苍 凉 感 悟 物 化 为 具 体 可 感 的 把
壮, 更喜 欢 苍 凉 。 …… 壮 烈 是 有 力 , 有 美 , 乎 没 似
缺少 人性 。悲 壮 则 如 大 红 大 绿 的 配 色 , 一 种 强 是
多 ・ 克 洛 夫 斯 基 , 是 针 对 人 们 对 日常 生 活 的 什 它
感觉“ 自动 化 ” 这一 现 象提 出的 。什 克 洛夫 斯 基认
三十年 前 的月 亮 。年轻 的 人想 着 三 十前 的月亮 该
是铜钱 大 的一 个 红 黄 的湿 晕 , 朵 云轩 信 笺 上 落 像
了一滴 泪珠 , 旧 而 迷 糊 。老 年 人 回忆 中 的三 十 陈
一
张 爱 玲 还 善 于运 用 通 感 的修 辞 方 法 , 即是 用 种感觉 写 另 一 种 感 觉 , 善 于 把 日常 生 活 中庸 她 常 的感觉 如视觉 、 听觉 、 触觉 等 采 用一 种 新颖 的方
杜 冉 冉
( 齐鲁 师 范 学 院 中 文 系 , 东 济 南 2 0 i ) 山 50 3
摘 要 : 爱玲 的 小说 创 作 颇 具 独 创性 , 传 统 与现 代 于 一 身 , 既 有 深 厚 的 中 国传 统 文 学 的底 蕴 , 时 , 深 张 集 她 同 又 受 西方 现 代 主 义 文 学 的影 响 , 于 运 用 陌 生 化 的 手 法 营 造 苍 凉 沉 郁 的 审 美意 境 。 善
浅谈文学语言的陌生化

浅谈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作者:张艳玲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2年第03期陌生化理论是由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陌生化”这个词语最早是1914年什克洛夫斯基在其纲领性的宣言《词的复活》中提出的。
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重要成员之一的什克洛夫斯基,是从克服人的感觉自动化这一角度提出陌生化问题的。
他认为,动作一旦成为习惯就会带有机械性,对于多次感受过的事物,人们在开始的时候会用“感受”来接受它,但渐渐地就会对它习以为常,最后成为一种习惯的、自动的动作。
当我们所有的习惯都变得机械、僵硬,退回到无意识和自动的环境中,我们往往就会对摆在我们眼前的事物视而不见,感受不到它的独特性。
这就是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感觉“自动化”。
而“陌生化”能够使人打破“自动化”的束缚,摆脱日常感受的惯常化,它会刺激人们已经麻木的神经,重新唤起人对事物、对世界的新奇感受。
“陌生化”理论开始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的。
而艺术的目的就在于使人恢复对于事物的感觉,“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感觉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存在着一种名为艺术的东西。
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视觉而不是作为识别的事物的感觉;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的手法,是使形式艰深化,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的手法,因为艺术中的感觉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应该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的制作的方法,而…制作‟成功的东西对艺术来说是无关重要的”。
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也能够打破“自动化”,实现“陌生化”,主要表现为语言的新奇与变异。
“艺术家永远是挑起事物暴动的祸首。
事物抛弃自己的旧名字,以新名字展现新颜,便在诗人那里暴动起来。
诗人使用的是多种形象—譬喻、对比…以此实现语义学的发展,他把概念从它所寓的意义系列中抽取出来,并借助于词(比喻)把它掺杂到另一个意义系列中去,使我们的耳目为之一新。
”什克洛夫斯基在提出陌生化理论时,主要是以诗歌语言为依据的。
他指出诗歌语言的特点“是为使感觉摆脱自动性而有意识的创造的;它的视觉表示创作者的目的,并且是人为构成的,为的是使感觉停留在视觉上,并使感觉的力量和时间达到最大的限度。
视觉的狂欢——语言陌生化在小说和诗歌中的一种体现

烈 的 个 性 的 体 现 张 爱 玲 存 《 自己 的 文 章 》 门 己 的爱 憎 暴 露 无 将 遗 : 我 不 喜 欢 壮 烈 我 是 喜 欢 悲 壮 , 喜 欢 苍 凉 。壮 烈 只 有 力 , “ 、 更 没 有荚 , 似乎 缺 少 人性 。悲 剧 则 如 大红 大绿 的配 乜 . 一种 强 烈 的对 是 照 、 它 的 刺 激 性 还 足 大 于 启 发性 。 凉之 所 以有 哩深 长 的 昧 , 但 苍
贺 的许 多作 品 都 体 现 出 了语 言 的 强烈 视 觉 化 . 、 关键 词 : 言 : 生化 : 觉化 : 性 语 陌 视 个 中 图分 类 号 : 8 H0 文献 标 识 码 : A
文 章 编 号 :6 3 2 1 ( ( 0) 9 0 31 0 1 7 — l 1 2) 0 — 0 — 2 1
文 学 弄 。 学存 裔 文
视 觉 的狂欢
— —
语 言 陌 生化 在 小说和 诗歌 中的一 种体现
董 鸣 鹤
( 川 大 学 文 学 与新 闻学 院 , 川 成 郜 610 4) 四 四 06
摘 要 :艺 术 陌 生 化 的 前 提 是 语 言 陌 生 化 。 符 合 指 向条 件 … … 这 样 我 们 就可 以把 诗 歌 确 诗 正
定 为受 阻 碍 的 、 曲 的 语言 。 ” 扭
张 爱 玲 存 《 玫 瑰 与 门攻 瑰 l 埘 “ 攻 瑰 ” 红 I 1 红 王娇 蕊 作 _精 荚 『 绝 伦 的描 述 : 她 穿 着 的 一 件 曳 地 的 长 袍 .是 最 鲜 辣 的 潮 湿 的绿 “ 色, 沾着 什么 就 染 绿 她 略 略 移 动 了 步 , 佛 她 刚 才 昕 占 有 的 空 仿 、 , 边 进 开 一 寸 半 的 了 I j = 对 气 上 便 留着 个 绿 迹 子 农 服 似 做 的
浅析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数女性角色 的人格和心灵都是被扭 曲的 , 都 是一些深受 中国封建
文化传统 营销 的平庸 小角色。她用 独到的人 生领悟和非凡 的艺术
在张爱玲 的文学作 品中, 随处可见优美的文字表达 , 新颖别致
细致入微 的心理刻 画以及生动传神的人 物描写 。 张爱玲文 表现力 刻画 出女 人在 旧式 家庭 中 的沉 浮 , 既挖 掘 出来女性 在历史 的比喻 ,
技巧 以及奇巧 的修辞运用 吸引着广大读者。 关键词 : 张爱玲; 悲剧色彩 ; 语言巧 ; 艺术特色
张爱玲 从小接受 着 中西文化 冲突下 的教 育 , 这样 的家庭 环境
和文化氛围导致她形成 了一种 中西杂糅 的人格 品性 和怪异 自立 的
二、 浓郁的市井气 息和华丽 的人生渴望
张爱玲的文学作 品带有 浓郁的市井气 息和华丽的 人生 渴望 。
色・ 戒》 , 其 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王佳芝为 面意象 的营造新颖 以及 比喻和对 比的巧妙运用 都发展到 了顶峰 。 华丽 的布景。例如其作 品《
不惜 以身犯险去勾引汉奸易先生 , 可是后来刺杀工作还没 张爱玲塑造 了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 ,她的作 品表现 了决绝 的生活 了革命 , 她身边 的人都开始渐渐地疏离她 , 她还发现 自己爱 态 度和苍凉的视野 , 带领读者走进苍凉惨淡 的小说世界 。 其 文学 作 有完成的时候 ,
人生态度 ,她 的作 品也带有三 、四十年代 中国社会 所特有 的苍凉 张爱 玲从不讳言 自己身上 的小市 民色彩 ,她的文学 作品里也没有
只有一些世俗里 的生活细节 , 她 感 。张爱玲 以其第一篇小说《 沉香 屑 ・ 第一炉香》 一举成名 , 她的代 惊天 动地或者轰轰烈烈的大事件 , 都有着各种各 样 表作有 《 金锁记》 《 红玫瑰 与白玫瑰 》 《 倾城之恋》 《 传奇 》 《 流言》 《 同 所刻画 的人物形象 也都是一些地地道 道的俗人 , 而不是像 电影里面拥有迷人身材和漂亮脸蛋的俊男美女 , 学少年都不贱》 等。 纵观张爱玲 的作 品, 我们可 以发 现 , 在题材方面 的俗欲 ;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消磨 它们 大都取材于 沦陷前后 的香 港和上海 , 描写 的多是男女 之间 的 他们 在喧嚣 嘈杂 的俗世里只求安生立命 , 例如其作 品《 等》 , 就描述了一群无聊 的男男女女在候诊 时的 恋爱婚姻关 系; 在结 构方 面它们总体结 构都 十分独特 , 尤其 是开头 日子 。 她笔下 的每个人物形象都长着 一副猥琐 的嘴脸 , 尤其是 和结尾 引人人胜 , 张爱玲作 品 的一大 特色就是采用 倒叙 的手法 来 家长里短 , 真 的是极尽嘲讽 之能事 。 叙 述故事 ;在写作 目的方面它们的 内容往往都是揭示那个 没落年 描写那群长相丑陋的男 子时 , 代 的人 物生存状态 ; 在语 言风格方 面 , 一是古典借用造成 陌生化效 虽然 张爱 玲笔下 的人物都是 一些俗不可 耐的小市民 , 但是在 她还是 渴望大舞台 , 需要 果, 二是追求 中西方 文化 与旧现代小说 之间的调 和 ; 在艺术 手法方 她 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 华丽的人生渴望 ,
张爱玲作品分析

张爱玲作品分析张爱玲从小接受着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教育,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导致她形成了一种中西杂糅的人格品性和怪异自立的人生态度,她的作品也带有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所特有的苍凉感。
张爱玲以其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她的代表作有《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同学少年都不贱》等。
纵观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题材方面它们大都取材于沦陷前后的香港和上海,描写的多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婚姻关系;在结构方面它们总体结构都十分独特,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引人入胜,张爱玲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采用倒叙的手法来叙述故事;在写作目的方面它们的内容往往都是揭示那个没落年代的人物生存状态;在语言风格方面,一是古典借用造成陌生化效果,二是追求中西方文化与旧现代小说之间的调和;在艺术手法方面意象的营造新颖以及比喻和对比的巧妙运用都发展到了顶峰。
张爱玲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她的作品表现了决绝的生活态度和苍凉的视野,带领读者走进苍凉惨淡的小说世界。
其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畸形的时代背景下造就了女性生存的悲剧。
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大多数女性角色的人格和心灵都是被扭曲的,都是一些深受中国封建文化传统营销的平庸小角色。
她用独到的人生领悟和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刻画出女人在旧式家庭中的沉浮,既挖掘出来女性在历史中所遭受的文化和精神的扭曲,也指出女性生存的困境和情感心理。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深陷封建意识的影响,无法摆脱命运的束缚,大多数女性都表现出对生活的困窘和不安,展现出了女性的全部弱点以及生存的困境,其目的在于揭示那个年代背景下的女性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心理。
以张爱玲刻画女性悲剧命运的经典之作《金锁记》为例,其中的人物形象曹七巧出生于小户人家,为了攀龙附凤,嫁入姜家做了二少奶奶,却得不到爱与尊重,导致了她的婚姻悲剧。
体会张爱玲独特的人生视角

的名言引用和阅读提示) (见p43的名言引用和阅读提示) 的名言引用和阅读提示
快速阅读一遍课文, 快速阅读一遍课文,找出小说的三要素
环境: 环境:被“封锁”的电车里 封锁” 人物:乘客(主要——吕宗桢、吴翠远) 吕宗桢、 人物:乘客(主要 吕宗桢 吴翠远) 情节:开端——电车被“封锁” 电车被“ 情节:开端 电车被 封锁” 发展——车上人的不同表现 发展 车上人的不同表现 高潮——吕、吴二人的交谈及心理活动 高潮 吕 结局——“封锁”开放,大家都回到自己生活的常态 封锁” 结局 封锁 开放, 思考书上p43的思考题和 的思考题和p51探究题㈠㈡㈢ 探究题㈠㈡㈢ 思考书上 的思考题和 探究题 每人从文中摘抄5句自己最感兴趣的话,说出理由。 每人从文中摘抄5句自己最感兴趣的话,说出理由。
陌生化不仅表现在语言层面上,也表现在叙事技巧上 小 陌生化不仅表现在语言层面上 也表现在叙事技巧上.小 也表现在叙事技巧上 说具有独特的叙事视角,其独特性在于人物有限叙事视角的采 说具有独特的叙事视角 其独特性在于人物有限叙事视角的采 使描写对象陌生化,即使读者习以为常的事物或事件经过 用,使描写对象陌生化 即使读者习以为常的事物或事件经过 艺术处理,或放大或变形 由审美的自在之物转变成审美对象,唤 或放大或变形,由审美的自在之物转变成审美对象 艺术处理 或放大或变形 由审美的自在之物转变成审美对象 唤 回了读者对生活的原初感受,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事物 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事物,进而获 回了读者对生活的原初感受 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事物 进而获 得新鲜的审美感受.例如鲁迅笔下 狂人”的倾诉、 例如鲁迅笔下“ 得新鲜的审美感受 例如鲁迅笔下“狂人”的倾诉、卡夫卡笔 甲壳虫”的内心独白、荒诞剧《等待戈多》 下“甲壳虫”的内心独白、荒诞剧《等待戈多》……
论《倾城之恋》的语言特点

乱世倾城与子成悦——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语言特点文学1106班徐雨萌 22 在中国现代文坛中,张爱玲的小说如同一枝繁花绽放着奇异的光彩。
作为张爱玲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的《倾城之恋》被许许多多文学爱好者反复品读,不仅仅因为它的故事情节波荡起伏、感人至深,更是因为它的语言别具特色、奇秀精当。
一、迥然的城市和恰当的氛围——形象之美故事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发生的。
文章充满了浓郁的地方气息:一边是“胡琴咿咿呀呀拉着”,京戏一板一眼的唱着,外强中干、人多为患又相互算计的上海白公馆;一边是灯红酒绿、“栽个跟头也要比别处痛些”的欲望都市,才子配佳人、有着欧仆服侍的浅水湾饭店。
作者刻意把一段看似普通的爱情拉锯战安排在这两个城市之间,用生活化的语言、多种叙述手段、多角度的描写巧妙的营造气氛,使社会大背景的形象美生动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深含的意蕴和道理的暗示——意蕴之美使人难忘的语言往往是含有道理的。
和其他的爱情小说不同的是,《倾城之恋》中许多语言有深度、耐人寻味。
“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等等,这些语言经得起仔细考究,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在文章特定的环境下直接道出了读者的心声。
并且,它在不同时间段品读起来就会有不一样的体味。
三、多变的句式和纷繁的词句——节律之美小说多个文段有长短句、叠词、成语、俗语等的使用,使语言有节律美,轻快有张力。
平白的叙述也不显得死板,读起来上口,有吸引力。
例如:“从小时候起,她的世界就嫌过于拥挤。
推着,挤着,踩着,背着,抱着,驮着,老的小的,全是人”;“她的声音灰暗而轻飘,像断断续续的尘灰吊子。
她仿佛做梦似的,满头满脸都挂着尘灰吊子,迷迷糊糊向前一扑,自己以为是枕住了她母亲的膝盖,呜呜咽咽哭了”。
四、华美的语言和缤纷的意象——手法之美个性化语言是“张体”小说一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别具一格的色彩描绘。
“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那整个的房间像暗黄的画框,镶着窗子里一幅大画。
现当代文学专题研修之张爱玲篇

现当代文学专题研修之张爱玲篇本文为文研青年专题研习、讨论计划,感谢文研青年冲刺群成员夏同学搜集整理并授权发布(内容有删改)。
因系讨论稿,难免有所疏漏,敬请谅解。
一、真题链接2023年武大试题:张爱玲作品在1980中期前后评价有很大差异,谈谈你对这种现象的看法。
二、背景介绍1、张爱玲其人:张爱玲(1920-1995年),原名张瑛,河北丰润人,中国现代作家。
张出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宦官之家,祖父张佩纶,外祖父李鸿章,后随家迁居上海。
张爱玲一生经历了优裕而忧郁的童年、立志发奋的少年、成名而求爱的青年、漂泊而执着的中年,孤寂而怪癖的晚年。
关于张的生活地理位置,大致可以分为早年的上海,青年时期的香港(张于中学毕业后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后香港沦陷,未及毕业,归至上海,后于1952年移居香港),晚年的海外(美国)。
2、张爱玲文学成就简述:张爱玲是沦陷区文学的代表作家,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不带偏见的尝试过鸳鸯蝴蝶派、章回体、“文艺新腔”等多种文体。
她是将中国古代文人小说精华与现代小说技巧结合的最好的现代作家之一、既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等西方先进思潮的影响,也受中国传统小说如《红楼梦》的影响。
因此,她可以创造出熔古典小说、现代小说于一炉,古今杂错,华洋杂错的小说文体。
这些小说历来被人称为“新鸳蝴体”等,雅俗共赏。
其笔下人物的人性深度和美学意蕴,高于一般现代作家的作品。
同时,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张又能以其独到体验和叙事方式体现出女性在现代社会的处境。
三、张爱玲小说总体上说:1、张小说的背景:张的小说总体上以沪港为背景2、张小说的人物:①以民间社会的小人物以及都市民间社会中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处于新旧交替的大家族社会中的人物生存状态为创作题材进行创作。
②女性人物:多为旧式家庭的“怨妇”、“怨女”,不同于五四以来的许多女作家,不写冰心式的理想的“淑女”,不同于丁玲的“叛女”,也不同于萧红笔下的“愚女”。
3、张小说的思想内容: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是“苍凉”,比如她文章中经常提到的一句话“人生是个苍凉的手势”以及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个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的陌生化手法

在封锁的突然发生,封闭的环境中,原 本陌生的宗桢和翠远在短时间内将日常 压抑的情感迸发出来,老实枯燥的宗桢 成立单纯多情的郎君,保守内向的翠远 变成的娇羞可爱的少女。他们从陌生中 第一次发现对方和自己的激情,虽然这 激情极其短暂,但这陌生中突然产生的 情感,还是别具魅力,体现了陌生化的 文学效果。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抽长 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 短了,……
这一段属于哪一个 方面?
词语重复看似啰嗦而笨拙的 句子,其实是揭示了人们最根本的 生活,周而复始。封锁成为了与日 常生活失去关联的,突然凸显出来 的真空状态,打破了日常生活紧密 的时空组,创设了一个“陌生化” 的故事场景。
“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 ,每一个“玲”字是冷冷 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 条虚线,切断时间与空间 。
《第七天》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的思绪借助身体的行走穿越了很
多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的情景之后 ,终于来到了这一天。”
余华在这里想要说明的其实就是“我” 终于回想起了这一天发生的事,但他却 花费了许多笔墨描写。思维是借助身体 行走的、情景像纷纷扬扬的雪花一样纷 繁复杂,余华在这里借助了这些“陌生 化”的描写加大了读者对熟知的事物的 认知难度。
2、“葱绿配桃红”,本是中国绘画审美 中犯忌的色彩搭配,但是对古典绘画颇 有研究的张爱玲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目 的在于用这种格外扎眼,格外夸张的色 彩,更有效地揭穿人物心灵的激越、矛 盾和不安。
《金锁记》
“冷盘撤了下去,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 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 着光站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 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 捧着大红热水袋,身边夹峙着两个高大 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 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 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
张爱玲散文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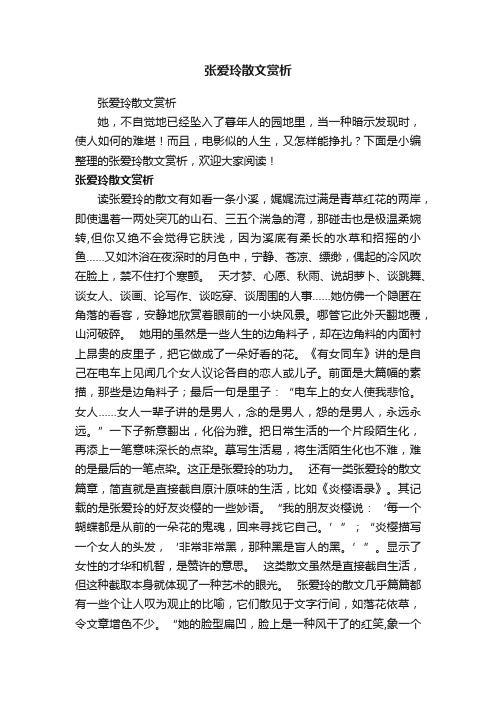
张爱玲散文赏析张爱玲散文赏析她,不自觉地已经坠入了暮年人的园地里,当一种暗示发现时,使人如何的难堪!而且,电影似的人生,又怎样能挣扎?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张爱玲散文赏析,欢迎大家阅读!张爱玲散文赏析读张爱玲的散文有如看一条小溪,娓娓流过满是青草红花的两岸,即使遇着一两处突兀的山石、三五个湍急的湾,那碰击也是极温柔婉转,但你又绝不会觉得它肤浅,因为溪底有柔长的水草和招摇的小鱼……又如沐浴在夜深时的月色中,宁静、苍凉、缥缈,偶起的冷风吹在脸上,禁不住打个寒颤。
天才梦、心愿、秋雨、说胡萝卜、谈跳舞、谈女人、谈画、论写作、谈吃穿、谈周围的人事……她仿佛一个隐匿在角落的看客,安静地欣赏着眼前的一小块风景。
哪管它此外天翻地覆,山河破碎。
她用的虽然是一些人生的边角料子,却在边角料的内面衬上昂贵的皮里子,把它做成了一朵好看的花。
《有女同车》讲的是自己在电车上见闻几个女人议论各自的恋人或儿子。
前面是大篇幅的素描,那些是边角料子;最后一句是里子:“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
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一下子新意翻出,化俗为雅。
把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段陌生化,再添上一笔意味深长的点染。
摹写生活易,将生活陌生化也不难,难的是最后的一笔点染。
这正是张爱玲的功力。
还有一类张爱玲的散文篇章,简直就是直接截自原汁原味的生活,比如《炎樱语录》。
其记载的是张爱玲的好友炎樱的一些妙语。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
显示了女性的才华和机智,是赞许的意思。
这类散文虽然是直接截自生活,但这种截取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艺术的眼光。
张爱玲的散文几乎篇篇都有一些个让人叹为观止的比喻,它们散见于文字行间,如落花依草,令文章增色不少。
“她的脸型扁凹,脸上是一种风干了的红笑,象一个小姑娘羞涩的笑容放在烈日底下晒干了的。
”(《华丽缘》)这是写一个老妇人的笑。
浅析《封锁》的叙事空间及其象征意蕴

张爱玲小说叙事空间大都是公馆、公寓或者车厢,小说人物似乎总被拘束在一个封闭性的空间中,欲挣脱而不得。
在其众多小说中,《封锁》可以说是较为成熟也较为别致的一篇。
小说向我们讲述了一对都市男女,在战争年代空袭封锁期间的电车里的一场梦幻般的罗曼史。
一、全知视角下的线性叙事结构小说大致可划分为三部分:封锁发生前,封锁发生时,封锁解除后。
开篇伊始,叙述者便把读者带入一个别样的叙事空间一辆因封锁而停滞不前的电车,切断了时间和空间,空间的封锁阻碍了电车内部人物行动。
叙述者的视点首先落在电车外部的环境: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开始奔跑。
封锁引发了骚乱,但随着时间推移周边的一切又重归于寂静。
作者将封锁期间电车的静态与周边环境的动态对照,使上海这座城市由喧闹嘈杂进入到沉寂安静的过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展示了上海这个繁华都市的另一面。
人声逐渐渺茫,像睡梦里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窸窣声&&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
叙述者以一个车厢乘客的听觉臆想,导引读者体验一种预设的梦幻的生存状态。
叙述焦点由外部环境转移到车内人物,先是两个打破静默的乞丐,接着是电车司机,再到公务员、中年夫妇。
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居高临下地俯瞰芸芸众生,不断游走的视线最终落到了男主人公华茂银行的会计师吕宗桢身上。
他是一个老实人。
这是吕宗桢的自我评价,由叙述者转述后当即充满了讽刺嘲弄的意味。
短暂的停留后,视线再次转移,终于,女主人公吴翠远进入了视线。
显而易见,文本中描绘女主人公吴翠远的笔墨远多于吕宗桢。
作者运用陌生化的语言刻画出这样一位新式知识女性: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但却不爱张扬的好女儿、好学生。
深蓝与白是她的主色调,她的美是那种淡淡的模棱两可的美,但她身上却依旧具有那种典型的上海小姐脾气。
叙述者的焦点在吴翠远的身上停留许久后,又再次转向,奶妈、小孩、医科学生各式各样的人逐一展示在读者眼前。
这时,小说里仅余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董培芝,出现了。
他可以说是男女主人公产生交集的直接原因。
封锁读后感

封锁读后感封锁读后感(一)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是中国现代着名作家之一。
这是一位迷一样的作家,既善于将生活艺术化,又满怀着近乎浪漫的悲剧情感,她是名门之后,但是她以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而自豪;她既悲天悯人,但时时刻刻又能洞见芸芸众生之可怜可笑。
只有她才能同时享受万众瞩目的喧闹和形单影只的落寞。
这本身,就足以成就一段悲壮的传奇…………在传奇的人生中写出了一部特别的短篇小说——《封锁》。
《封锁》是张爱玲一篇独具匠心的短篇小说,全篇主要写的是男女主脚在公车封锁的情况下与常态不同的行为,他们在公车上恋爱了,可是下车后就自然而然地分手了,一个看似荒唐的事在小说中发生了。
《封锁》的不同之处在于看似随意的笔调下隐藏着巨大的张力!它通过电车被封锁,描写出两个在平淡、疲乏无聊的都市生活中的世俗男女,而在某一短暂而特定的环境允许的情势之下,表现出对各自常规生活的不至于引起后果的瞬间反叛。
这是一种平常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反逆。
反映出的是一种人的“本我”状态,包括人类本能的驱动力和被压抑的无意识倾向,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会展现出本我。
正如陈奕迅《红玫瑰》的歌词唱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疼爱的都有恃无恐。
在一切有序的生活轨道上,人与人都保持着恰如其分的“位置”,这个位置是社会要求并规定的位置,于生命深处也许有着种种的遗憾,那是对自己没有得到的一切,所怀有的那一些不甘心在心里骚动着而在平常的生活中不会表露出来。
而电车上的“封锁”环境是人性的一个出逃机会,这是一个暂时与外界隔绝的空间,在这里他们没有了在现实社会中原有的身份、地位和责任,没有了平时的那些种种顾虑,人们会暂时的抛离原本存在的那个自己,一个单纯的自己,一个真正的自己,这也是一场试验,它引发了人心蓄积已久的燥动,让人从常规脱缰而出,然而“封锁”终究是短暂的,而这种短暂又意味着“安全”,让“封锁”中的男女有了现实中的退路最终破蛹而出的本我。
《封锁》中的男女主人公从电车上相遇再到相爱再到最后的分手,其实正好是对内心一直隐藏的那个“自己”的展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谈张爱玲小说中的“陌生化”“陌生化”是由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核心概念。
这个理论强调的是在内容与形式上违反人们习见的常情、常理、常事,同时在艺术上超越常境。
陌生化的基本构成原则是表面互不相关而内里存在联系的诸种因素的对立和冲突,正是这种对立和冲突造成了“陌生化”的表象,给人以感官的刺激或情感的震动。
其实所谓陌生化,就是将对象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移出,通过施展创造性手段,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觉,从而扩大认知的难度和广度,不断给读者以新鲜感的创作方式。
通俗地说,就是将文章写“新”,把故事讲“奇”。
陌生化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观照生活的新的视点,并使我们在文学中不是印证熟识的生活而是发现新奇的生活,改善和改变我们世俗的、常态的生活感觉,进而改善和改变我们的生命活动方式,与我们面对的生活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陌生化并非是脱离现实生活情况,而是对一个故事以另外一种视角进行重述,使其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语言的陌生化是文学新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的小说之所以赢得不同时代读者的喜爱,不仅因为她小说反映的平凡人生故事多么“传奇”,更重要的一点是她作品语言的匠心独运。
陌生化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其价值在于能否营构陌生化的艺术氛围。
文学创作主体借助于陌生化手段引导接受主体在一种奇异新鲜的陌生化效果中感受到事物的本真状态。
陌生化使事物变得陌生,使感知重新变得敏锐和深刻,因而营构陌生化的艺术氛围异常重要。
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其最基本的形态是文字的。
(一)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张爱玲在小说语言上,始终下着极深的功夫。
她的小说之所以刺激读者的眼球,就在于语言的强烈视觉化,而将这种感觉发挥到至极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色彩语言的运用。
与张爱玲同时代的上海女作家苏青形容她的小说语言是: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
她的小说色彩语不只是停留在对客观物象的复制和感觉的捕捉上,更重要的是饱含着色外之“色”的审美意蕴。
环境特征往往是人物情绪的外射,通过色彩语言的描绘,往往会放大和渲染人物的心理感受。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主人公葛薇龙想留在香港继续求学,希望得到姑妈的资助,只身一人来到梁家,却受到无法忍受的奚落,此时,看到屋子里的装饰是:“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瓷盘里一棵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叶子,四下里探着头,象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
”“宝蓝、苍绿、青、红”的色彩固然鲜艳,但是这种夺目的色彩并没有调制出一丝和谐温馨的家庭气氛,反而让人感到恐怖,像是潜伏着静静的杀机,暗示出姑妈具有杀伤力的语言对薇龙未来人生的茫茫威胁,是薇龙将置身命运陷阱的信息转递。
“葱绿配桃红”,本是中国绘画审美中犯忌的色彩搭配,但是对古典绘画颇有研究的张爱玲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目的在于用这种格外扎眼,格外夸张的色彩,更有效地揭穿人物心灵的激越、矛盾和不安。
“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
”(《倾城之恋》)油画般的色彩勾勒出一幅独特的香港市景图:光怪陆离,繁华喧闹,充满现代商业文明的刺激。
然而,男女主人公的恋爱故事,要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可以想见,他们的恋情怎能有温馨、宁静的幸福感?事实上是,男女主人公彼此的内心世界恰如这犯冲的色彩,时刻在角斗、在厮杀。
“三轮车夫披着方格子绒毯,缩着颈子唏溜溜浠溜溜在行人道上乱转,象是忍着一泡尿。
红棕色的洋梧桐,有两棵还有叶子,清晰异常的焦红小点,一点一点,整个的树显得很玲珑轻巧起来。
冬天的马路,干净之极的样子,淡黄灰的地,淡得发白,头上的天却是白中发黑,黑沉沉的,虽然不过下午两三点钟时分。
一辆电车驶过,里面搭客挤得歪歪斜斜,三等车窗里却戳出来一大捆白杨花——花贩叫做白杨花的,一种银白的小绒咕嘟,远望着,象枯枝上的残雪。
”(《创世纪》)街上片断零碎的景物,一经色彩的涂抹,总算泛出生命的活气。
但是不顾祖父干涉的潆珠,决定出来找活谋生时的心情,是凄冷、孤寂和荒凉的。
这些环境描写的色彩词语,颇具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营造特点,因而富有诗意美。
张爱玲小说语言中,对冷暖色调的调配,尤为醒目。
代表作《金锁记》中就有这样一段:“冷盘撤了下去,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
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站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边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
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
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子——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眼中,长安家是一个由“青灰色”、“昏黄”和“湖绿”等色彩所构筑成的灰暗世界,突然掺入一点“大红”,使灰暗的色彩注入了亮色,这种强烈的对照,把曹七巧阴森恐怖的变态心理活脱脱映衬出来,让人直觉感到“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二)文学形象的陌生化文学是通过语言来塑造形象的艺术,读者在语言的感染下经过联想和想象,便可在头脑中唤起相应的文学形象,从而构成一个动人心弦的艺术世界。
比如一个时期,在我国文坛上有这样一类作品:只要作品中出现一个贼头贼脑、尖嘴猴腮的人物,人们大致会料到这是个阶级敌人,以下便有投毒、放火、盗窃之类的破坏活动,最后必然会被心明眼亮的人民群众发现。
《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中内蕴最为丰厚的作品,她消解了普通的母亲形象,刻画了一个阴狠毒辣的母亲形象——曹七巧,把金钱异化人性的力量叙述的惊心动魄。
《金锁记》写出了人性的扭曲与变态,颠覆母爱,解构母亲神话。
由于曹七巧在畸形的夫妻关系禁锢下从未享受沟生命的真正快乐,长期的性压抑刺激了她的心理,满腹怨气变成尖刻歹毒的人。
七巧在潜意识中是把儿子当作一个真正的男人来看待的,既然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让别人得到。
她让儿子通宵达旦的陪她烧烟泡,追根究底的盘问媳妇的情况,次日便在牌桌上添油加醋的加以公布,长白的一妻一妾先后在七巧的精神折磨下丧命。
如果说对媳妇的折磨是为发泄同性的嫉妒,变相占有儿子,那么对女儿婚事的破坏则是为了满足其施虐欲。
女儿长安同留学生童世舫的新式恋爱带来的精神变化与七巧的不幸形成强烈的反差,她把对生活的怨恨发泄到女儿身上,虚设圈套在漫不经心中用一句话断送了女儿的婚事。
七巧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结束了人性大毁灭的悲剧,也把传统的母亲形象完全消解了。
张爱玲小说对人物的描写常常从外形穿着打扮着墨,有评论者认为她的小说人物出场往往是一堆衣服的叠砌,但是透过华丽的服饰表面,显露出的是一种凄切、苍凉的人生状态,所以她的视觉化色彩语有着强烈的内趋性。
“她穿着的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
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
衣服似乎做的太小了,两边迸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
那过份刺眼的色调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也只有她能够若无其事地穿着这样的衣服。
”(《红玫瑰与白玫瑰》)绿色代表着朝气和活力,但是王娇蕊衣服的颜色鲜艳得含有了另一层用意:即生命是如此放恣,以至于有一种游戏人生之嫌。
“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手帕,下身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
”(《金锁记》)七巧相当村俗和极端张扬的打扮,映衬出她性格的泼辣、诡谲、阴鸷特点,同时还能感觉到长期蜗居封建大家庭,旧式环境对其生命的碾磨。
“……吴翠远,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但是还没有结婚。
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
她携着一把蓝白格子小遮阳伞。
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
”(《封锁》)翠远的外在特征显示,这是一个出身于正统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乖女孩,但是过于严肃、纪律化的装束又见出其生命的平淡、乏味和了无机趣。
《心经》中许峰仪在屋子里见到女儿小寒时的情景:“隔着玻璃,峰仪的手按在小寒的胳膊上——象牙黄的圆圆的手臂,袍子是幻丽的花洋纱,朱漆似的红底子,上面印着青头白脸的孩子,无数的孩子在他的指头缝里蠕动。
小寒——那可爱的大孩子,有着丰泽的,象牙黄的肉体的大孩子……”这不是一般父亲眼中的女儿,而是充满欲望、躁动、恐惧等各种复杂心理的坠入“父女恋”畸形池沼中的父亲特殊视角中的女儿。
在有限的句子中嵌入“象牙黄,幻丽的,青头白脸”等充满奇幻怪异色彩的词语,就把一个陷入情爱死胡同的“父女恋”的原罪意识最大限度地突现出来。
张爱玲笔下的色彩语言不是“壹加壹”式的简单文字符号排列,而是通过背景渲染,人物肖像刻画,意在透视人物内心世界。
她在作品中极尽色彩渲染之能事,发挥人物的视觉功能,强化语言的感受力,以此达到诗化的审美表现。
“陌生化”理论总是从全新的视角观察问题,不断更新着文学世界的感知方式。
究其实质,陌生化理论就是要破除日常经验的遮蔽性和欺骗性,是要破除思维方式的机械性和习惯性。
“在狭义上说,我们将把那种被特殊程序创造出来的事物称为艺术作品,而所谓特殊的目的在于,要使这些事物尽可能地被人们称为艺术品来感受。
”陌生化也是一种写作和阅读策略,凭借陌生化理论,创作者不但制造惊奇和新鲜的感受,而且还可以不必在乎时局的禁锢和牵连,尽可能展示真实内心感觉;接受者也以同样的方式读懂作者的真实内心。
因而,恢复感受和激发感受,让人重新回到富有情趣味和发现意味的现实生活中去,是陌生化理论的主要目的。
陌生化理论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洞见,它不但肯定接受者的“求奇趋新”的心理规律,为艺术的独创性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同时陌生化理论将研究深入到艺术文本与接受者两个维度,为后来现代主义诸理论的发展提供契机。
陌生化作为构筑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基石,永远闪耀着理性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