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案例——弗洛伊德_创伤
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

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位心理学巨匠对心理创伤的理解。
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著名的心理防御机制和梦的理论,对心理创伤的形成和治疗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而荣格,作为分析心理学的先驱,他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和对心理创伤的诠释,为理解个体心理与社会文化背景的互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通过比较和分析这两位心理学家的理论,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心理创伤的本质、成因及其对个人心理发展的深远影响。
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基本理论,然后重点探讨他们对心理创伤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最后对两者的观点进行比较和整合,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心理创伤的框架。
二、弗洛伊德对心理创伤的理解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对心理创伤的理解深刻且独到。
他坚信心理创伤不仅仅是外在事件造成的身体伤害,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心理体验。
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创伤往往源于童年时期的经历,这些经历由于种种原因被压抑在个体的无意识之中,但却在日后的生活中不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影响个体的行为和情感。
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心理创伤与“防御机制”紧密相连。
当个体遭遇无法承受的心理压力或冲突时,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会无意识地采用各种防御机制,如否认、投射、升华等。
这些防御机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帮助个体逃避痛苦,但长期而言,它们可能会阻碍个体对创伤的真实感受和认识,从而导致心理问题的产生。
弗洛伊德还特别强调了性心理发展在心理创伤形成中的重要性。
他认为,儿童在性心理发展的不同阶段,如果遭遇到不良的刺激或压抑,就可能导致心理创伤的产生。
这些创伤不仅会影响个体的性心理健康,还可能对个体的整体人格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心理创伤的治疗关键在于“回忆”和“宣泄”。
通过引导个体回忆并表达那些被压抑的创伤记忆,可以帮助他们重新面对并处理这些创伤,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
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如自由联想、梦境分析等,都是基于这一理念而设计的。
【名人故事】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

【名人故事】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出生于1856年5月6日,是奥地利的心理学家、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被认为是现代心理学之父和精神分析学之父。
他提出了诸多有影响力的理论,例如无意识、童年体验在成年人行为中的重要性、性本能等。
“之父”这个称号也因此名正言顺。
弗洛伊德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名毛皮商人。
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神经学和医学,在医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他也曾在巴黎学习神经解剖学和病理学。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的研究生时代其实就已经开始探讨心灵和行为间的关系,并且经常借鉴自己的病人与痴呆症患者的案例,在精神诊断领域上取得重大发现。
1885年,弗洛伊德开始实践催眠疗法,并在之后的实践中,他逐渐发现了人类某些行为的真正原因不是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指导,而是人类内心潜在的一些感受和欲望在起作用。
1895年,他正式提出了心理学领域内最为基础和重要的理论——“无意识”。
弗洛伊德深入研究了儿童时期和童年经验对成年人的影响,并提出了童年性感受的理论,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观和行为常常是由于童年不良体验在成年人的人格上暗中起作用的。
这个理论成为了弗洛伊德的另一个心理学理论的基础,即儿童心理学。
弗洛伊德还提出了人的性本能理论。
他认为性是人类恒久的生理需求之一,并且性主要包括本能驱动、身体机能和了解自己的欲望。
这个理论引发了当代社会的许多争议和批评,但它在其时代里仍然是颇为受欢迎的理论之一。
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期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健康专家之一,并且他的理论引领了更多人对于心理健康的认识和理解。
在1913年,他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成为了研究、教学和实践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组织。
他开创了精神治疗的实践方法,人称“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治疗”。
除了他的心理学理论之外,弗洛伊德也发表了许多关于文学、文化、宗教和哲学等其他领域的作品。
尽管弗洛伊德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亦受到许多批评和争议,但他的学说仍然大大地影响到了现代心理学和其他领域的人们。
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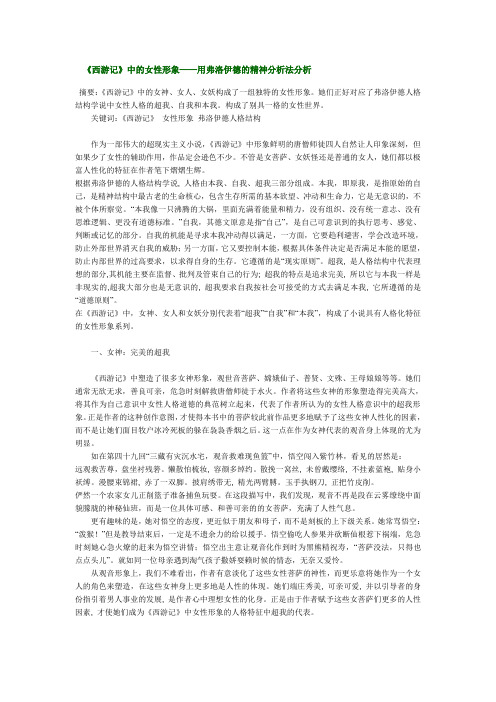
《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分析摘要:《西游记》中的女神、女人、女妖构成了一组独特的女性形象。
她们正好对应了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学说中女性人格的超我、自我和本我。
构成了别具一格的女性世界。
关键词:《西游记》女性形象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作为一部伟大的超现实主义小说,《西游记》中形象鲜明的唐僧师徒四人自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如果少了女性的辅助作用,作品定会逊色不少。
不管是女菩萨、女妖怪还是普通的女人,她们都以极富人性化的特征在作者笔下熠熠生辉。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学说, 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
本我,即原我,是指原始的自己,是精神结构中最古老的生命核心,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它是无意识的,不被个体所察觉。
“本我像一只沸腾的大锅,里面充满着能量和精力,没有组织、没有统一意志、没有思维逻辑、更没有道德标准。
”自我,其德文原意是指“自己”,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
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一方面,它要趋利避害,学会改造环境,防止外部世界消灭自我的威胁;另一方面,它又要控制本能,根据具体条件决定是否满足本能的愿望,防止内部世界的过高要求,以求得自身的生存。
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
超我, 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 超我的特点是追求完美, 所以它与本我一样是非现实的,超我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 超我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 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
在《西游记》中,女神、女人和女妖分别代表着“超我”“自我”和“本我”,构成了小说具有人格化特征的女性形象系列。
一、女神:完美的超我《西游记》中塑造了很多女神形象,观世音菩萨、嫦娥仙子、普贤、文殊、王母娘娘等等。
她们通常无欲无求,善良可亲,危急时刻解救唐僧师徒于水火。
作者将这些女神的形象塑造得完美高大,将其作为自己意识中女性人格道德的典范树立起来,代表了作者所认为的女性人格意识中的超我形象。
【最新文档】佛洛依德案例-精选word文档 (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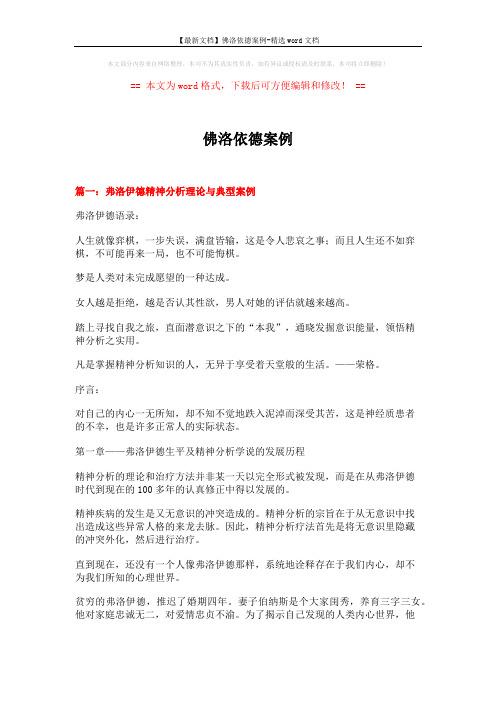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佛洛依德案例篇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典型案例弗洛伊德语录:人生就像弈棋,一步失误,满盘皆输,这是令人悲哀之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可能悔棋。
梦是人类对未完成愿望的一种达成。
女人越是拒绝,越是否认其性欲,男人对她的评估就越来越高。
踏上寻找自我之旅,直面潜意识之下的“本我”,通晓发掘意识能量,领悟精神分析之实用。
凡是掌握精神分析知识的人,无异于享受着天堂般的生活。
——荣格。
序言:对自己的内心一无所知,却不知不觉地跌入泥淖而深受其苦,这是神经质患者的不幸,也是许多正常人的实际状态。
第一章——弗洛伊德生平及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历程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并非某一天以完全形式被发现,而是在从弗洛伊德时代到现在的100多年的认真修正中得以发展的。
精神疾病的发生是又无意识的冲突造成的。
精神分析的宗旨在于从无意识中找出造成这些异常人格的来龙去脉。
因此,精神分析疗法首先是将无意识里隐藏的冲突外化,然后进行治疗。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像弗洛伊德那样,系统地诠释存在于我们内心,却不为我们所知的心理世界。
贫穷的弗洛伊德,推迟了婚期四年。
妻子伯纳斯是个大家闺秀,养育三字三女。
他对家庭忠诚无二,对爱情忠贞不渝。
为了揭示自己发现的人类内心世界,他不惜公开自己的隐私和生活。
除了在16岁时有过一次单恋,他一生只爱一个女人,玛莎·伯纳斯。
第一阶段:1856出生到1897年年,为情感创伤论阶段。
母亲19岁时与39岁的父亲结婚,弗洛伊德和同父异母哥哥的儿子年龄相仿,而同父异母的哥哥与母亲年龄相仿。
兄妹7人,5个妹妹和一个小弟弟。
3岁时,母亲生的第二个男孩6个月夭亡,弗洛伊德认为弟弟的死因自己而生。
10岁,父亲作为犹太人而遭受侮辱,弗洛伊德喜欢汉尼拔将军的动机如此有关。
社会工作精神分析理论案例-HELLO,弗洛伊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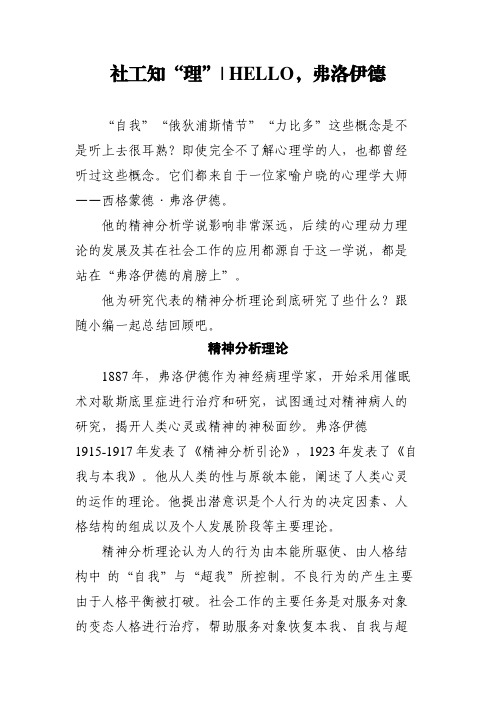
社工知“理”| HELLO,弗洛伊德“自我”“俄狄浦斯情节”“力比多”这些概念是不是听上去很耳熟?即使完全不了解心理学的人,也都曾经听过这些概念。
它们都来自于一位家喻户晓的心理学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影响非常深远,后续的心理动力理论的发展及其在社会工作的应用都源自于这一学说,都是站在“弗洛伊德的肩膀上”。
他为研究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到底研究了些什么?跟随小编一起总结回顾吧。
精神分析理论1887年,弗洛伊德作为神经病理学家,开始采用催眠术对歇斯底里症进行治疗和研究,试图通过对精神病人的研究,揭开人类心灵或精神的神秘面纱。
弗洛伊德1915-1917年发表了《精神分析引论》,1923年发表了《自我与本我》。
他从人类的性与原欲本能,阐述了人类心灵的运作的理论。
他提出潜意识是个人行为的决定因素、人格结构的组成以及个人发展阶段等主要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的行为由本能所驱使、由人格结构中的“自我”与“超我”所控制。
不良行为的产生主要由于人格平衡被打破。
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服务对象的变态人格进行治疗,帮助服务对象恢复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平衡。
主要观点1、意识层次理论通过对病人的一系列临床观察,弗洛伊德提出了无意识存在的理论。
他认为“无意识是一个巨大的水库,储存着那些通常不为他人接受,自己也经常难以忍受的思想、感受、愿望和记忆。
”人的精神活动,包括欲望、冲动、思维、幻想、判断、决定、情感等,会在不同的意识层次里发生和进行。
不同的意识层次包括意识、前意识和潜(无)意识三个层次。
该理论核心观点是,人的任何精神活动都是存在其根源的,并非偶然。
他认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根源就是潜意识,它对人行为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因此要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就必须探寻潜意识的意义。
方法是通过解释梦和自由联想,在人无意识的表达中发现潜意识的意义,对造成病态的潜意识给予诠释,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2、人格结构理论弗洛伊德将人格划分成了三个相互作用的部分:本我、自我、超我。
弗洛伊德五大心理治疗案例

弗洛伊德是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对现代心理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弗洛伊德五大心理治疗案例:
1. 安娜·奥: 安娜是弗洛伊德的第一个患者,她在一次催眠治疗中回忆起了童年受虐经历,这引发了弗洛伊德对于潜意识、情感冲突和人格结构等方面的研究,也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的开始。
2. 沃尔夫人: 沃尔夫人是一位患有强迫症的病人,她在弗洛伊德的心理治疗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弗洛伊德通过对沃尔夫人的治疗,提出了精神防御机制和转移情感的重要性。
3. 德尔大夫: 德尔大夫是弗洛伊德的另一位心理治疗患者,他的治疗过程中展示了“自由联想”的概念,即通过无目的地的思考和表达,患者可以自发地表达出潜意识中的情绪和冲突。
4. 小汉斯: 小汉斯是一位患有恐惧症的孩子,他害怕马和黑暗,但在弗洛伊德的治疗下成功克服了恐惧症。
弗洛伊德通过对小汉斯的治疗,提出了儿童心理学的重要性和精神分析学在儿童治疗中的应用。
5. 索菲·缪勒: 索菲是弗洛伊德的一位患者,她的治疗案例展示了“反移情”现象的重要性。
弗洛伊德通过对索菲的治疗,提出了治疗师与患者关系中的难以避免的情感冲突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些情感冲突的方法。
总之,弗洛伊德的心理治疗案例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创伤性离开:弗洛伊德中的幸存和历史

2020年4期(第4卷) 批评理论 No.4 2020 ( Vol.4 ) ·文论前沿·创伤性离开:弗洛伊德中的幸存和历史批评理论·文论前沿——发生了什么事?——发生?——是的。
——我没死。
《典当行》近年来,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和神经生物学越来越多地坚持外部暴力对精神障碍的直接影响。
这一趋势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相关研究中达到高峰。
创伤后应激障碍描述了突发事件或灾难性事件的压倒性经历,在这种经历下,对事件的回应经常以幻觉和其他侵入现象不受控制的、重复的出现的方式发生。
bq01正如今天普遍理解的那样,创伤后应激障碍反映了恐怖事件不可避免的现实性(reality)对精神(mind)的直接强加,即无法被精神控制的事件在心理层面和神经生物学层面上接管了精神。
因此,创伤后应激障碍似乎是心理暴力和外部暴力之间最直接的联系,也是最有毁灭性的心理障碍。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将论证,创伤不仅仅是一种毁灭的效果,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幸存(survival)bq02之谜。
bq03只有认识到创伤经历是毁灭和幸存bq01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1980年)中给出的名称,在19世纪和20世纪不同时期,它曾被称为“炮弹休克”(shell shock)、“战斗神经症”(combat neurosis)或“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c neurosis)以及其他被使用过的名称。
第三版、第三版修订版和第四版《手册》中的定义包括了弗洛伊德后来关于创伤的著作中所描述的同样的基本症状,包括他所谓的“积极症状”(闪回和幻觉)和“消极症状”(麻木、健忘和避免触发刺激)。
虽然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定义存在争议——是否应将引发性事件(causative event)视为超出人类通常经验的范围;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否基本上是由交替的闪回和麻木组成的双相式的反应,或如特伦斯·基恩所建议的那样,创伤的核心是一种无法改变的麻木,被更具治疗可能性的闪回打断——对创伤经历的基本描述在临床和理论叙述以及幸存者故事中都保持着明显的稳定性。
弗洛伊德的几个早期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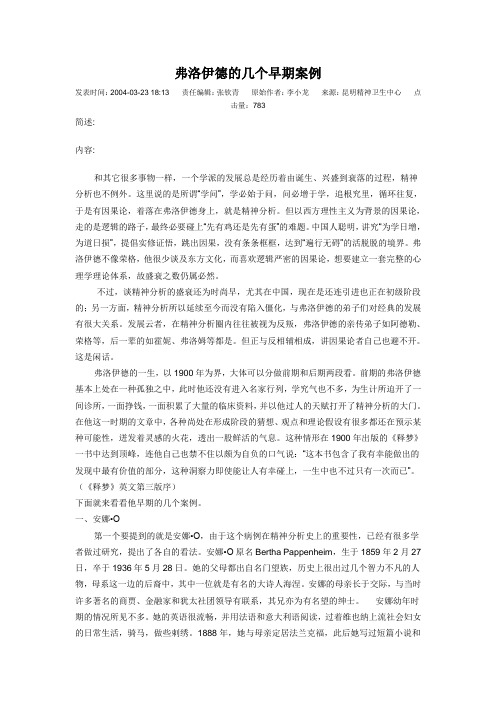
弗洛伊德的几个早期案例发表时间:2004-03-23 18:13 责任编辑:张钦青原始作者:李小龙来源:昆明精神卫生中心点击量:783简述:内容:和其它很多事物一样,一个学派的发展总是经历着由诞生、兴盛到衰落的过程,精神分析也不例外。
这里说的是所谓“学问”,学必始于问,问必增于学,追根究里,循环往复,于是有因果论,着落在弗洛伊德身上,就是精神分析。
但以西方理性主义为背景的因果论,走的是逻辑的路子,最终必要碰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
中国人聪明,讲究“为学日增,为道日损”,提倡实修证悟,跳出因果,没有条条框框,达到“遍行无碍”的活脱脱的境界。
弗洛伊德不像荣格,他很少谈及东方文化,而喜欢逻辑严密的因果论,想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心理学理论体系,故盛衰之数仍属必然。
不过,谈精神分析的盛衰还为时尚早,尤其在中国,现在是还连引进也正在初级阶段的;另一方面,精神分析所以延续至今而没有陷入僵化,与弗洛伊德的弟子们对经典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发展云者,在精神分析圈内往往被视为反叛,弗洛伊德的亲传弟子如阿德勒、荣格等,后一辈的如霍妮、弗洛姆等都是。
但正与反相辅相成,讲因果论者自己也避不开。
这是闲话。
弗洛伊德的一生,以1900年为界,大体可以分做前期和后期两段看。
前期的弗洛伊德基本上处在一种孤独之中,此时他还没有进入名家行列,学究气也不多,为生计所迫开了一间诊所,一面挣钱,一面积累了大量的临床资料,并以他过人的天赋打开了精神分析的大门。
在他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各种尚处在形成阶段的猜想、观点和理论假设有很多都还在预示某种可能性,迸发着灵感的火花,透出一股鲜活的气息。
这种情形在1900年出版的《释梦》一书中达到顶峰,连他自己也禁不住以颇为自负的口气说:“这本书包含了我有幸能做出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种洞察力即使能让人有幸碰上,一生中也不过只有一次而已”。
(《释梦》英文第三版序)下面就来看看他早期的几个案例。
一、安娜•O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安娜•O,由于这个病例在精神分析史上的重要性,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卡鲁斯与创伤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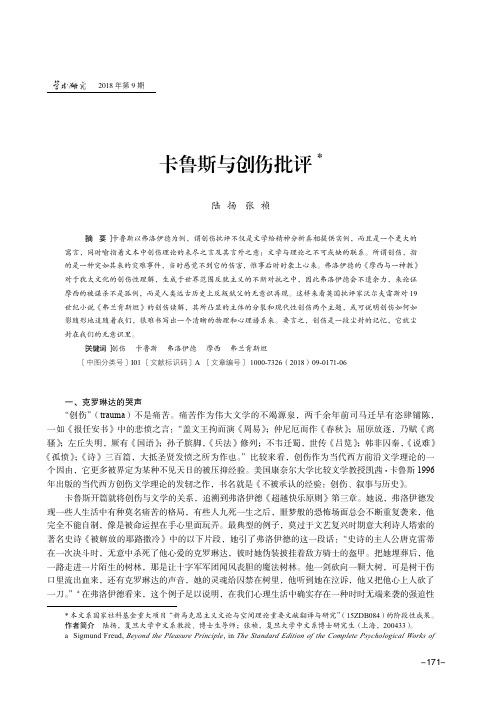
一、克罗琳达的哭声“创伤”(trauma )不是痛苦。
痛苦作为伟大文学的不竭源泉,两千余年前司马迁早有恣肆铺陈,一如《报任安书》中的悲愤之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比较来看,创伤作为当代西方前沿文学理论的一个因由,它更多被界定为某种不见天日的被压抑经验。
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凯茜•卡鲁斯1996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创伤文学理论的发轫之作,书名就是《不被承认的经验:创伤、叙事与历史》。
卡鲁斯开篇就将创伤与文学的关系,追溯到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第三章。
她说,弗洛伊德发现一些人生活中有种莫名痛苦的格局,有些人九死一生之后,噩梦般的恐怖场面总会不断重复袭来,他完全不能自制,像是被命运捏在手心里面玩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著名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以下片段,她引了弗洛伊德的这一段话:“史诗的主人公唐克雷蒂在一次决斗时,无意中杀死了他心爱的克罗琳达,彼时她伪装披挂着敌方骑士的盔甲。
把她埋葬后,他一路走进一片陌生的树林,那是让十字军军团闻风丧胆的魔法树林。
他一剑砍向一颗大树,可是树干伤口里流出血来,还有克罗琳达的声音,她的灵魂给囚禁在树里,他听到她在泣诉,他又把他心上人砍了一刀。
”a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在我们心理生活中确实存在一种时时无端来袭的强迫性*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与研究”(15ZDB08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陆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祯,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a Sigmund Freu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 in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2018年第9期卡鲁斯与创伤批评*陆 扬 张 祯[摘 要] 卡鲁斯以弗洛伊德为例,谓创伤批评不仅是文学给精神分析真相提供实例,而且是一个更大的寓言,同时喻指着文本中创伤理论的未尽之言及其言外之意:文学与理论之不可或缺的联系。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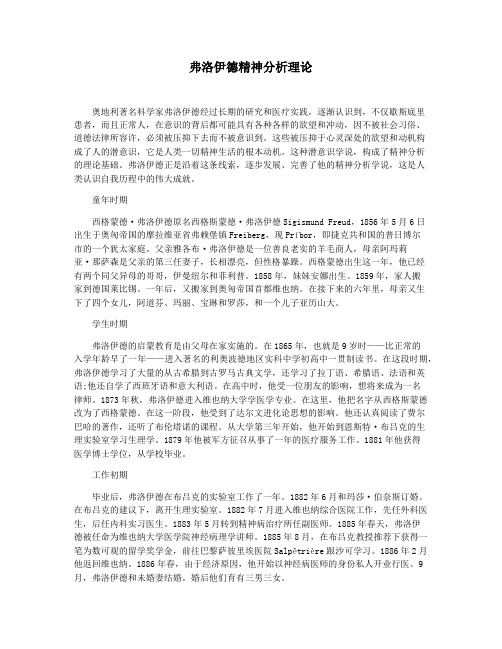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奥地利著名科学家弗洛伊德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医疗实践,逐渐认识到,不仅歇斯底里患者,而且正常人,在意识的背后都可能具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和冲动,因不被社会习俗、道德法律所容许,必须被压抑下去而不被意识到。
这些被压抑于心灵深处的欲望和动机构成了人的潜意识,它是人类一切精神生活的根本动机。
这种潜意识学说,构成了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
弗洛伊德正是沿着这条线索,逐步发展、完善了他的精神分析学说,这是人类认识自我历程中的伟大成就。
童年时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原名西格斯蒙德·弗洛伊德Sigis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省弗赖堡镇Freiberg,现Príbor,即捷克共和国的普日博尔市的一个犹太家庭。
父亲雅各布·弗洛伊德是一位善良老实的羊毛商人,母亲阿玛莉亚·那萨森是父亲的第三任妻子,长相漂亮,但性格暴躁。
西格蒙德出生这一年,他已经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伊曼纽尔和菲利普。
1858年,妹妹安娜出生。
1859年,家人搬家到德国莱比锡。
一年后,又搬家到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母亲又生下了四个女儿,阿道芬、玛丽、宝琳和罗莎,和一个儿子亚历山大。
学生时期弗洛伊德的启蒙教育是由父母在家实施的。
在1865年,也就是9岁时——比正常的入学年龄早了一年——进入著名的利奥波德地区实科中学初高中一贯制读书。
在这段时期,弗洛伊德学习了大量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古典文学,还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英语;他还自学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在高中时,他受一位朋友的影响,想将来成为一名律师。
1873年秋,弗洛伊德进入维也纳大学学医学专业。
在这里,他把名字从西格斯蒙德改为了西格蒙德。
在这一阶段,他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他还认真阅读了费尔巴哈的著作,还听了布伦塔诺的课程。
从大学第三年开始,他开始到恩斯特·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学习生理学。
弗洛伊德童年创伤理论

弗洛伊德童年创伤理论
弗洛伊德童年创伤理论是由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提出的,他认为,童年创伤是一种心理疾病,它可能导致一些严重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如焦虑、自卑、抑郁等。
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童年创伤的根源在于父母的有意或无意的行为,他们可能是负面的、放任的或者抑制的。
例如,有的父母可能会对孩子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必须做到某些事情,而不考虑孩子的情感或意愿。
这种压力可能会使孩子感到羞耻和无助,而这种痛苦会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心理,从而影响他们今后的人生。
另一方面,有的父母可能会不小心伤害孩子,比如言语上的伤害或肢体上的伤害,这类伤害往往会让孩子感到无助和脆弱,久而久之,这种伤害会对孩子的自尊心产生严重的影响。
弗洛伊德童年创伤理论也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无爱或不关心可能也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孩子若没有父母的关爱和支持,可能会感到孤独和无助,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影响孩子今后的人生。
弗洛伊德童年创伤理论认为,童年创伤不仅会对孩子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也可能影响孩子今后的人生。
因此,父母应该加强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护,尽量减少对孩子的压力和伤害,以避免孩子受到童年创伤的影响。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典型案例

弗洛伊德语录:人生就像弈棋,一步失误,满盘皆输,这是令人悲哀之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可能悔棋。
梦是人类对未完成愿望的一种达成。
女人越是拒绝,越是否认其性欲,男人对她的评估就越来越高。
踏上寻找自我之旅,直面潜意识之下的“本我”,通晓发掘意识能量,领悟精神分析之实用。
凡是掌握精神分析知识的人,无异于享受着天堂般的生活。
——荣格。
序言:对自己的内心一无所知,却不知不觉地跌入泥淖而深受其苦,这是神经质患者的不幸,也是许多正常人的实际状态。
第一章——弗洛伊德生平及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历程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并非某一天以完全形式被发现,而是在从弗洛伊德时代到现在的100多年的认真修正中得以发展的。
精神疾病的发生是又无意识的冲突造成的。
精神分析的宗旨在于从无意识中找出造成这些异常人格的来龙去脉。
因此,精神分析疗法首先是将无意识里隐藏的冲突外化,然后进行治疗。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像弗洛伊德那样,系统地诠释存在于我们内心,却不为我们所知的心理世界。
贫穷的弗洛伊德,推迟了婚期四年。
妻子伯纳斯是个大家闺秀,养育三字三女。
他对家庭忠诚无二,对爱情忠贞不渝。
为了揭示自己发现的人类内心世界,他不惜公开自己的隐私和生活。
除了在16岁时有过一次单恋,他一生只爱一个女人,玛莎·伯纳斯。
第一阶段:1856出生到1897年年,为情感创伤论阶段。
母亲19岁时与39岁的父亲结婚,弗洛伊德和同父异母哥哥的儿子年龄相仿,而同父异母的哥哥与母亲年龄相仿。
兄妹7人,5个妹妹和一个小弟弟。
3岁时,母亲生的第二个男孩6个月夭亡,弗洛伊德认为弟弟的死因自己而生。
10岁,父亲作为犹太人而遭受侮辱,弗洛伊德喜欢汉尼拔将军的动机如此有关。
汉尼拔将军也是犹太人,曾进军罗马。
弗洛伊德在thumsee疗养所曾一个人击退了反犹太主义的进攻,与父亲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弗洛伊德对基础医学十分重视,为此推迟毕业两年。
1880到1882,他遇到了人生中的重要人物布罗伊尔,比他大14岁。
创伤概念的变革——从沙可、让内到弗洛伊德

创伤概念的变革——从沙可、让内到弗洛伊德李浩然【摘要】“创伤”一词在当下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具有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属性.生理性的“创伤”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古老概念,而“创伤”一词的心理属性其实仅仅是近百年来的新创.“创伤”的英文词汇先后由traumatism发展到trauma,而创伤概念本身,经由沙可、让内和弗洛伊德三位在创伤理论学术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学者的相继探讨,则经历了内涵与本质由身体到心理再到潜意识的重要变革,而创伤主体也在这种变革之中变得逐渐分裂,trauma开始逐渐成为“创伤”的对应词,具有时间、认同解离性的“心理创伤”才真正诞生.【期刊名称】《医学与哲学》【年(卷),期】2019(040)007【总页数】4页(P21-24)【关键词】创伤;解离;精神分析【作者】李浩然【作者单位】四川文理学院教务处四川达州 635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02自1980年“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正式列入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颁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Ⅲ,DSM-3)开始,创伤理论(trauma theory)开始越来越多的得到学术界的关注。
这样的关注已经突破了学科的界限,深深地影响到了文学、史学等诸多人文学科。
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等为标签的研究,涉足政治问题、文学批评、历史研究等不同方面,俨然成为了人文领域中的新研究“范式”。
对创伤理论自身进行的历时性梳理也在国内外学界展示出了显著的成果。
然而,创伤理论如何在身心二元结构中由身体维度游离到精神维度,又如何超越统一自我而直面心灵的解构,却成为了各项研究中遗憾缺失的一环。
创伤的必然与复原的限度——对心理创伤进行复原的思考

摘要:创伤是弗洛伊德借自医学的概念。
他保留了创伤原有的基本含义,但将其作用面转至精神层面。
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中,弗洛伊德强调了精神创伤的两个特性:创伤总是事后的;幻想带来创伤。
弗洛伊德在理论后期,不再将创伤理论局限于神经症的形成问题上,而将之归结为新生儿的无助状态,因而个体创伤具有必然性。
温尼柯特也认为人生之初的情境与创伤紧紧相连。
幼儿的成长必然暴露在创伤的产生机制中,是否是病理性的创伤,只在于环境中的冲击是否过度。
拉康认为主体与镜像我之间存在着冲突,幻想在于调和冲突,幻想不能完成的结果即是创伤。
而这种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也说明创伤是必然的。
创伤复原的限度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复原是有限的,其有限性要求主体接受自己的境地;另一方面,复原是超越限度的,复原不是回归过去,而是穿越幻想,打破冲动的重复,进入创造的可能。
关键词: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温尼柯特;拉康;创伤;复原;从2019年底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临床心理学界又重新将目光投向“创伤”的理论。
本文对弗洛伊德、温尼科特和拉康三位精神分析家创立的心理创伤理论进行了梳理,希望能帮助我们对后疫情时代的心理创伤进行理解和复原。
一、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创伤创伤一词是弗洛伊德从医学中借用来讨论精神事件的术语,他保留了创伤在医学上的三个基本含义:具有剧烈的冲击、形成穿透性破坏、对整体组织造成后果,但是将创伤的作用面从生理层面转到了精神层面。
精神分析早期对心理创伤的治疗也类似于对生理创伤的处理,只是这时所用的工具是言语。
在《癔症研究》中,弗洛伊德说:“当我们能使患者把激发的事件及其所伴发的情感清楚地回忆起来,并且患者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个事件,而且能用言语表达这种感情时,则每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即和永久地消失。
”这是宣泄疗法的工作原理。
那时的弗洛伊德认为,只要来访者带有情感地详细讲述遭遇到的创伤事件,症状就会消失。
但是,临床的进一步发现告诉弗洛伊德,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弗洛伊德分析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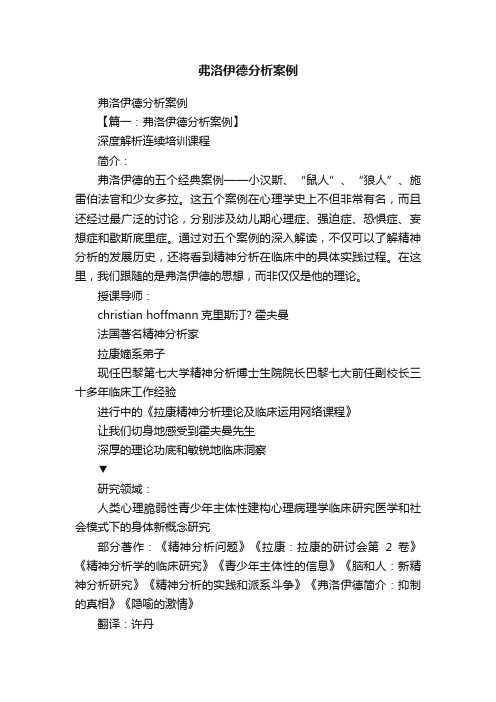
弗洛伊德分析案例弗洛伊德分析案例【篇一:弗洛伊德分析案例】深度解析连续培训课程简介:弗洛伊德的五个经典案例——小汉斯、“鼠人”、“狼人”、施雷伯法官和少女多拉。
这五个案例在心理学史上不但非常有名,而且还经过最广泛的讨论,分别涉及幼儿期心理症、强迫症、恐惧症、妄想症和歇斯底里症。
通过对五个案例的深入解读,不仅可以了解精神分析的发展历史,还将看到精神分析在临床中的具体实践过程。
在这里,我们跟随的是弗洛伊德的思想,而非仅仅是他的理论。
授课导师:christian hoffmann克里斯汀? 霍夫曼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拉康嫡系弟子现任巴黎第七大学精神分析博士生院院长巴黎七大前任副校长三十多年临床工作经验进行中的《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及临床运用网络课程》让我们切身地感受到霍夫曼先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敏锐地临床洞察▼研究领域:人类心理脆弱性青少年主体性建构心理病理学临床研究医学和社会模式下的身体新概念研究部分著作:《精神分析问题》《拉康:拉康的研讨会第2卷》《精神分析学的临床研究》《青少年主体性的信息》《脑和人:新精神分析研究》《精神分析的实践和派系斗争》《弗洛伊德简介:抑制的真相》《隐喻的激情》翻译:许丹精神分析家;法国国家临床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执照;法国心理学博士;临床心理学中法双硕士;巴黎第七大学精神分析、医学和社会学实验室特邀研究员;巴黎第七大学精神分析研究博士学院讲师;具有多年在法国精神病院和机构的实践经验,活跃于精神分析中法国际学术交流,及国内心理咨询师的培训。
回到弗洛伊德100多年前,弗洛伊德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流派他的临床工作遵循一条最朴素的道路:看病人 ? 看自己 ? 构架理论今天,我们有太多的学派、理论、技术当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我们却迷失在深深的无力中这是因为我们被引向了另一条道路:看理论 ? 看自己 ? 看病人理论代替了我们的洞察力和创造性我们成了理论的奴隶现在,我们要重新回到弗洛伊德追根溯源真正领悟精神分析的本质与起源……▼让我们从《鼠人》开始用10堂视频网络课程带你完整学习强迫症的理论和临床实践授课形式这10次网课采取在线视频授课的方式,同时结合qq群里预先阅读讨论。
运用精神分析疗法的心理咨询案例

运用精神分析疗法的心理咨询案例精神分析心理疗法是一种以改变作为心理障碍基础的潜意识层面的人格为目标的心理障碍根治疗法。
它建立在这样人的一切行为、情感、思维以及心理障碍的基础上。
以下是店铺分享给大家的关于运用精神分析疗法的心理咨询案例,欢迎大家前来阅读!运用精神分析疗法的心理咨询案例篇1X夫人,通过电话要求心理治疗。
她说她是位教师,且多年前曾收受过一次精神分析治疗。
X夫人60岁,有着一头金黄纤细的卷发,妆容精致,看起来很年轻。
和我在电话里对她的印象很一致。
她表现得很不安,坐在椅上也显得安宁不下来,在椅上扭来转去,似乎身上哪里有痛的样子,有时站起来象个哮喘的人大喘气。
开始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明白了她处于恐慌的情绪下:我可以直接感觉到她的焦虑,这种焦虑让她十分痛苦、难以忍受且饱受折磨。
从她牙逢里挤出几个词都要等上一段时间。
她说让我多包涵,她十分不舒服,胸口就象被胸衣死死箍住的感觉。
她看起来确实是胸口很不舒服的样子。
她说全科医师给她开了些精神方面的药物,服药后她感觉有些好转,但是她这样难受的状态还是没改变。
渐渐地,她平静下来,告诉我在婚姻持续了25年的时候,她与丈夫分居了。
几个星期以前,丈夫和新女友同居了。
她实在不能忍受孤独!X夫人说,她这种状况可能与她幼年经历有关。
在她出生后6周时,比她大2岁的姐姐患猩红热死了,母亲由于姐姐的去世很长时间内都情绪抑郁。
以前接受精神分析时她做过一个梦。
梦里她掉入了深渊,或粉身碎骨。
现在她有自杀冲动—以前她从来没体验过想自杀的感觉!她的想法主要围绕下面的内容:丈夫为什么要离开她?她有2个孩子没和她一起住,她又没有知心的要好朋友,她在今后的日子里是不是会更孤单?我和她预约了心理治疗,每周一次,但我对她说,她任何时间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是必须的她就可以打电话给我,而且紧急时状态时也可能可以安排紧急访谈。
我感觉患者需要坚定有力的支持。
类似她这样处在强烈且直接可见的焦虑状态的患者,我很少遇到过。
精神分析理论生活例子

精神分析理论生活例子在精神分析的治疗案例中,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安娜·O。
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是在1884年与布洛伊尔合作期间产生的,他们合作治疗一名叫安娜·O的21岁癔症患者。
弗洛伊德从布洛伊尔那里学习到宣泄疗法,又师从沙可学习催眠术,继而提出自由联想疗法,1897年创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精神分析法。
尽管安娜并不是弗洛伊德亲自治疗的病人,但这个病例在精神分析史上的重要性是极其显著的。
安娜·O原名伯莎·帕彭海姆,生于1859年2月27日,死于1936年5月28日。
安娜的父母都出自名门望族,历史上出现过几个智力不凡的人物,母系这一支中,其中一位就是有名的大诗人海涅。
她的母亲擅长交际,与当时许多著名的商贾、金融家和犹太社团领导有联系,其兄亦为有名望的绅士。
安娜的英语很流畅,并用法语和意大利语阅读,过着维也纳上流社会妇女的日常生活,骑马,做些刺绣。
1880年布洛伊尔治疗安娜时,她是一个20刚出头的知识女性,有着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歇斯底里症状:右侧、左侧会在不同的时间里出现瘫痪和麻痹;有持续性的神经性咳嗽;会出现视觉和听觉障碍;会有古怪的饮食习惯(如,在几个星期里全靠桔子过活);会一度失去说德语的能力,而仍然能说英语;并且会体验到她称之为“缺席”的解离状态。
按照布洛伊尔的描述,安娜一直很健康,成长期并无神经症迹象。
她非常聪明,对事物的领会迅速,有十分敏锐的直觉,智力极强,有很高的诗歌禀赋和想象力,但受到严厉的和带有批判性的抑制。
她意志力坚强,有时显得固执,情绪上总是倾向于轻微的夸张,像是很高兴而又有些忧郁,因而有时易受心境支配,在性方面发育很差。
布洛伊尔将她描绘成一位“洋溢着充沛智力”的女子。
1880年,安娜21岁。
这年7月,她深爱着的父亲患了胸膜周围脓肿。
安娜竭尽全力照顾父亲,不到一个月,她自己也出现了诸多症状,如虚弱、贫血、厌食、睡眠紊乱、内斜视等。
按布洛伊尔的说法,“这段时间安娜和她的母亲共同分担着护理父亲的责任。
基于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的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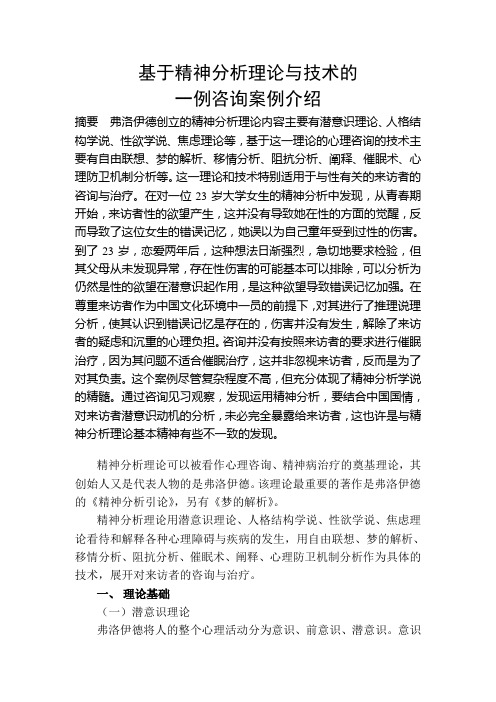
基于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的一例咨询案例介绍摘要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内容主要有潜意识理论、人格结构学说、性欲学说、焦虑理论等,基于这一理论的心理咨询的技术主要有自由联想、梦的解析、移情分析、阻抗分析、阐释、催眠术、心理防卫机制分析等。
这一理论和技术特别适用于与性有关的来访者的咨询与治疗。
在对一位23岁大学女生的精神分析中发现,从青春期开始,来访者性的欲望产生,这并没有导致她在性的方面的觉醒,反而导致了这位女生的错误记忆,她误以为自己童年受到过性的伤害。
到了23岁,恋爱两年后,这种想法日渐强烈,急切地要求检验,但其父母从未发现异常,存在性伤害的可能基本可以排除,可以分析为仍然是性的欲望在潜意识起作用,是这种欲望导致错误记忆加强。
在尊重来访者作为中国文化环境中一员的前提下,对其进行了推理说理分析,使其认识到错误记忆是存在的,伤害并没有发生,解除了来访者的疑虑和沉重的心理负担。
咨询并没有按照来访者的要求进行催眠治疗,因为其问题不适合催眠治疗,这并非忽视来访者,反而是为了对其负责。
这个案例尽管复杂程度不高,但充分体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精髓。
通过咨询见习观察,发现运用精神分析,要结合中国国情,对来访者潜意识动机的分析,未必完全暴露给来访者,这也许是与精神分析理论基本精神有些不一致的发现。
精神分析理论可以被看作心理咨询、精神病治疗的奠基理论,其创始人又是代表人物的是弗洛伊德。
该理论最重要的著作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另有《梦的解析》。
精神分析理论用潜意识理论、人格结构学说、性欲学说、焦虑理论看待和解释各种心理障碍与疾病的发生,用自由联想、梦的解析、移情分析、阻抗分析、催眠术、阐释、心理防卫机制分析作为具体的技术,展开对来访者的咨询与治疗。
一、理论基础(一)潜意识理论弗洛伊德将人的整个心理活动分为意识、前意识、潜意识。
意识是人能够知觉到的精神活动;前意识是平时意识不到,但经过集中注意思考能回忆起来的经验;潜意识则是人不能知觉的精神活动,它由原始冲动、本能欲望、出生后的许多欲望等构成,这些欲望被社会道德所不允许,是受到压抑的部分,它们会积极活动,力图冲入到意识中,获得满足。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创伤——一例精神分析治疗案例报告摘自弗洛伊德、布洛伊尔《痍症研究》奇怪的布丁味1892年底,我熟悉的一位同事转诊给我一个他正在治疗的病人。
这是一个有慢性再发化脓性鼻炎的年轻女士,我称她为露西小姐,30岁。
后来才弄清,她顽固存在的疾病是由于筛骨溃疡的缘故。
近来,她主诉的一些症状使见识渊博的医生再也不能视为局部感染了。
她完全丧失嗅觉,而且持续受到一两种主观嗅觉的纠缠,她感到这是最令她痛苦的。
另外,她感到精力差和疲劳,头有沉重感,食欲不振,办事效率低。
露西小姐在维也纳郊区一家工厂总经理的家里做家庭教师。
她经常在我诊疗时间来就诊。
她是个英国妇女,身体纤巧,皮肤上有色素沉着,除鼻部受感染之外,她显得很健康。
她最初的陈述与那位医生告诉我的一样,她感到抑郁和疲劳,并遭受主观嗅觉的折磨。
我初步认为,她患的是歇斯底里症,并表现出相当明显的一般痛觉丧失,但未丧失触觉感,大致的检查(用手)没有显示有视野的局限。
她鼻腔内完全缺乏痛觉,也没有反射。
虽然触压敏感,但作为感觉器官,她对特殊的刺激和其他刺激(如氨或醋酸)没有适当的感觉。
那时她的化脓性鼻炎正处于好转时期。
要想弄清这个疾病,就必须解释她的主观性嗅觉感,因为反复的幻觉是慢性歇斯底里的症状。
她的抑郁可能受到创伤的影响,我应当有可能发现主观嗅觉出现的一个客观经历。
这个经历也许就是个创伤,使她记忆中出现象征性的反复嗅觉感。
我认为可能反复出现的嗅觉上的幻觉与伴随着的抑郁一起引发了一次歇斯底里发作,而反复出现的幻觉性质与其在慢性症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称的。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在这个病人身上表现出来,因为对这个病人的治疗才刚刚开始。
然而,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嗅觉的主观感觉以应假设为有一个特定的来源,是来自某些非常特殊的真正对象。
这个预见很快得到验证。
当我问她什么样的嗅觉一直使其烦恼时,她答道:“一种烧焦的布丁味。
”因此,我只需要假设烧焦的布丁味实际上在她的经历中发生过,且这起着一种创伤的作用。
把嗅觉选作创伤记忆的象征物是不同寻常的,但对这种选择的解释并不困难。
该病人患化脓性鼻炎后,她的注意力特别集中在鼻子的感觉上。
我知道这个病人的生活环境局限于她照看着的两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身上,她们的母亲在多年前死于一种急病。
因此,我决定把烧焦的布丁味做为分析的出发点,我将详细的描述这个分析过程。
实际上,本来应该是一次诊治的时间却分成几次进行,因为病人只能在我的诊疗时间来,我也只能花较短的时间对她进行治疗。
而且,由于她的职责不允许她经常从很远的工厂到我这里来,因此一次单独的讨论常常需要拖延一个多星期,我们常常在短时间内中止谈话,下次再接着讨论。
当我对她尝试催眠术时,露西小姐没有进入催眠状态,因此我只是在她处于与平常稍稍不同的状态下对她做全面分析的。
小插曲我将对这个技术做详细的阐述。
在1889年,当我参观在南锡的一家诊所时,我听到一位研究催眠术的老前辈里埃波说:“如果我们能使每一个病人都进入催眠状态,那么催眠治疗将是最有效的。
”在伯恩海姆的门诊中,似乎这一技术确实存在,而且也有可能从伯恩海姆那里学到这样的技术。
但当我试图对自己的病人实施这一技术时,我发现自己的能力有很大的局限性,况且如果我对一个病人三次实施催眠而不成功的话,我就没有诱导催眠的招术了。
在我的经验中,催眠成功的百分率远低于伯恩海姆报道的。
因此,我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放弃对大多数病例可能适合的宣泄方法,要么冒险尝试这种无催眠梦游症的方法,即催眠作用很轻,甚至可能不存在。
我并不在意这种非催眠梦游状态所达到的催眠程度(用量表测量来表明的),就我们所知,对不同病人应使用不同的暗示方式,而僵硬性昏厥、自动性运动等均不是我所要治疗的,也就是说我应当用在比较容易唤醒记忆所遗忘的病人中。
不久我就放弃了用各种测验来测量病人达到的催眠程度,因为这样做引起许多病人的抵抗,并动摇他们对我的信任,而这恰恰是进一步心理治疗所必须的。
况且我很快就厌烦了发号施令,诸如“你想睡觉了!……睡觉吧!”厌烦听到病人对我的抗议(经常发生在催眠程度很轻时):“但是,医生,我并不困啊。
”也厌烦了其后对病人所作的解释:“我并不是指正常的睡觉,我指的是催眠,正如你所见的,你在被催眠,你不能睁开你的眼睛,等等。
”我确信其他许多做心理治疗的医生比起我来能够用更多的技术克服困难。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可能采用一些有别于我采用的技术。
然而,我认为如果一个人预料到在使用一个特殊的词汇而使自己经常处于一种窘迫的情境的话,那么他主动避免这一词汇和困境将是明智的。
因此,当我的第一次尝试既没有导致催眠,也没有因一定程度的催眠而发生明显的生理改变时,我就放弃了催眠术,而只是要求病人“集中”。
我让病人躺下,有意闭起眼睛,作为达到“集中”的一种方法。
可能用这种方法,我只要稍稍努力,就能使一个特殊的病人达到最大程度的催眠。
但在使用这种技术中,我发现病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致病因素。
我记起我亲眼所见到伯恩海姆所作的,即在催眠期间的记忆时间却在清醒状态下明显的被遗忘了,而用手轻压可使其再现,这一事件的回忆使我避免了这种新的窘境。
例如,他给一位妇女实施催眠术后,她的不良幻觉不复存在,然后他试着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她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他没有成功。
把她唤醒后,他要求病人告诉他,当她进入催眠状态后,他对她做了什么,她回答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但他不接受这个回答,他坚持认为她能记起任何事,他把他的手放在病人的前额上,帮她回忆。
你瞧!她果真描述了在催眠中显然没有觉察到的和在清醒状态下也明显回忆不起来的每件事。
这个令人惊奇的实验就作为我的模式。
我决定从这个设想开始,即我的病人知道任何具有治病意义的事情,问题是要让他们讲出来。
当我在问病人一些这样的问题“这个症状有多久了?”或“什么原因?”之后,我会碰到这样的回答“我确实不知道”,这时我就用下面的方法,我把一只手放在病人的前额,或者用两只手把住她的头说:“你在我的手的压力下会想出来的。
当我放松我的手时,你将会在你的面前见到某些事,或者某些事会进入你的头脑中,抓住它,它们就是我要找的,好,现在你看到了什么或发生了什么?”在我第一次使用这个方法时(不是用在露西小姐身上),我惊奇地发现它产生了我需要的那种精确的结果。
我可以肯定的说,从那以后我很少失败。
正如已表明的那样,这个分析方法应当被采纳,它能使我在没有催眠术的情况下把每一个这样的分析进行到底。
因此,我的自信心增强了,如果病人回答我“我看不到什么”或“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会消除顾虑,将其视为不可能,并使他们相信,他们肯定会知道我想要知道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他们拒绝相信或抵制的。
我告诉他们,只要他们喜欢,我就重复使用这种方法,每次他们都会看到同样的事情。
病人在尚未学会缓解危机的本领之前,他们否认脑中曾经有过的记忆或想法,认为这些记忆或想法是无用的,而且是一种干扰。
当他们把这些记忆和想法告诉我之后,实际上就是我需要的信息。
偶然情况下,经过三至四次轻压后,终于引出了信息,病人会这样回答:“其实我第一次就知道了,但我就是不想说”,或者“我不希望情况是那样的”。
这种假设意识受限制的治疗是费力的,至少比催眠术要费力得多。
然而它使我受催眠术的支配,使我洞察了常常造成病人记忆遗忘的动机。
我能肯定这种遗忘常常是故意的、期望的。
我发现更令人惊奇的是,用这种方法可引出表面上已遗忘很久的数字和日期,从而揭示了病人的精确记忆是多么的令人难以置信。
在搜寻数字和日期时,我们能从熟悉的失语症理论上得到帮助,它认为再认比回忆容易,因此当一个病人不能回忆起一个特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时,我们可以向他重复可能有关的年份,12个月份的名称和月份中的31天的日子,当他感觉是正确的数字时,他将睁开双眼。
实际上大多数病人是根据特殊的日期做出决定的。
例如,病人把注意力放在“从头至尾计数”的方法而说出其日期后,她会说“哎呀,那是我父亲的生日!”并补充到,“肯定是的,因为我们正说道期待他过生日这件事。
”这里,我只是附带地说到这个话题。
从所有这些观察中得到的结论是,引起重要治病因素的体验及其所有次要的伴随事件,均正确的保存在似乎已遗忘的病人的记忆中(当时他不能在头脑中回忆起来)。
表面上的胜利——第一个创伤情景在这长长的而又不可避免的离题后,我再回到露西小姐这个病例来。
正如我所说的,我对她实施催眠术的意图不是产生催眠梦游症。
她的眼睛始终闭着,面容有些僵硬,手脚不动,我问她是否能记起第一次闻到烧焦的布丁味的情形。
“哦,是的,我完全知道。
大约两个月以前,在我生日那两天,我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上烹饪课。
正好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我从邮戳及其笔迹看出是来自格拉斯哥我母亲那里。
我正想打开看,孩子们冲到我面前,从我手中抢去了信并叫嚷到:‘不,你现在不能看信,你必须在生日那天才能看,我们为你保存着。
’这时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气味,是她们做的布丁变焦了。
从那以后,我总是被这种气味纠缠着,整天存在,当我不安时气味更强烈。
”“你很清楚地看到你眼前的情景吗?”“和真的一样,就好像我正在经历着。
”“什么事使你如此不安?”“因为孩子们对我这么有感情,我很感动。
”“她们不是总这样吧?”“是的,但在我收到母亲的信时是这样的。
”“我不理解为什么孩子们的感情和你母亲的信之间存在对立,你认为似乎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回到母亲那里,但想到要离开可爱的孩子,我感到很悲伤。
”“你的母亲有什么事吗?她是否感到孤独而叫你回去?或者她生病了,或者你正期待着她的消息?”“不,她不是很健壮但也没有生病,她的一个朋友和她住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非得离开孩子?”“我不能再在这所房子呆下去了,房主、厨师和法国女教师似乎都认为我把自己放在高于我的位置上了,他们联合起来跟我捣鬼,向孩子的祖父说我的坏话。
当我向孩子的父亲和祖父抱怨时,我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我期望的支持。
因此我通知总经理(孩子的父亲)我要辞职,他很友善的劝我在作决定前,最好再考虑一段时间。
那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我应该离开这所房子,但我现在还呆在这里。
”“除了你依恋孩子以及孩子们喜欢你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事吗?”“是的,孩子们的母亲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亲戚。
我在她死前保证过,我将会竭尽全力照顾两个孩子,我不会离开她们,我将代替她们母亲的位置。
但是我的通知却毁了这一保证。
”这似乎已完成了对病人主观嗅觉的分析,我们已弄清原先有一个客观的感觉,这个感觉与一个经历中的小场景密切的结合起来,而这两种对立的情感在相互冲突着:即她后悔要离开孩子们和促使她下决心离开的一种轻视。
她母亲的信并没有让她离开,而是她自己打算离开这里,与母亲呆在一起。
两种情感的冲突在信来到时上升为一种心理创伤,而气味的感觉与这种创伤联系起来,保留下来成为其象征物。
我们仍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场景涉及的全部感知觉中,她只是选择了气味作为一种象征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