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福建移民对台湾的影响
清代客家移民与台湾社会

第17卷第1期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2月Vol.17 No.1JOURNAL OF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Feb.2017清代各豕移民与台湾社会赵巍u(1.福建师范大学,福州350002 ;2.福建博物院,福州350001)摘要: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台湾也是一个移民社会。
在早期移民 中,客家人作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族群,不仅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台湾社会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从清代台湾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播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进一步论证 了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并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
关键词:客家;移民;台湾社会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 -0297(2017)01 -0029 -06台湾自古就是一'个移民社会,在众多移民群 体之中有一个重要的族群——客家人。
就目前而 言,对“客家人”这一概念尚有不同看法。
有学者 认为客家人是指“唐宋以来为躲避战乱或横征暴 敛,或因经商、垦殖等因素而陆续迁居闽粤赣山区 的中原汉人,经过长期与土著居民互动融合后形 成的一个汉族族群”[1]。
清代从大陆向台湾移民的客家人来源比较复 杂,不仅包括福建的汀州,还有福建的漳州及广东 的潮汕地区。
其中,“汀州本是客家中心区域之一,汀属各县都是纯客家县份,来自汀州的移民是 地地道道的客家人,这是毫无疑问的”[2]。
除此之 外,漳州及粤东地区的移民虽然是客家人的重要 来源,但是并不能据此将漳州籍或粤籍的移民简 单等同于客家人。
这些从祖国大陆移向台湾的客家人,在早期 “水恶土瘠,烟瘴房,易生疾病”[3]的条件下不畏艰 难,历经险阻,冒死渡台,不仅体现了客家人吃苦 耐劳、勇于探索的精神品质,也为台湾的经济开发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且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 中,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古代对台湾的管理措施(一)

我国古代对台湾的管理措施(一)我国古代对台湾的管理背景自古以来,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明清两代,中国政府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台湾实施管理。
行政机构明代时期,设立福建巡抚衙门,对福建沿海及福建海外地区进行管辖,包括台湾。
清代规定了台湾设立福建台湾府。
随后,又在台湾设立县级行政单位,如台湾省、台湾府、台湾道等,分别对台湾的行政管理进行管理。
政策措施政策倡导明代时期,明朝政府推行了开疆拓土的政策,鼓励民众南下开拓福建沿海及福建海外地区,包括台湾。
清朝时期,允许福建沿海居民或东南沿海跨海逃亡者在台湾落户,裁撤苏澳等县,将原住民土地分配给闽南移民。
经济发展为了促进台湾经济发展,明代末年福建巡抚金声桓先后下令开垦种植糖蔗、茶叶等,奖励明朝军人与移民定居台湾,发展渔业、盐业等经济活动。
清朝时期,台湾成为中国糖业的重要产地,而中国又成为世界上糖的主要出口国之一。
安定稳定明清两代,台湾内部曾经发生多起叛乱事件,政府采取了一定措施进行镇压。
明朝时期下令让民众自卫,清代时期则设立“蹴鞠衙门”,由法官负责维护社会安全和治安管理。
管理成效明清时期,虽然台湾仍然存在叛乱事件,但随着政府的力量逐渐加强,台湾社会逐渐趋于稳定。
经济上,台湾成为糖业和盐业的重要产地,促进了福建地区及中国的经济发展。
政治上,台湾成为了中国政治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中国政治提供了更广泛和深入的参考。
结论明清两代对台湾管理不仅显现出中国政府的统治能力和管理智慧,也为台湾提供了良好的治理体系和社会基础,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的台湾,也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和地位,秉持着为中国和两岸发展做出贡献的精神,与大陆一起实现和平、稳定、繁荣的共同目标。
后续影响明清两代对台湾的管理,可以说是为后来的统治者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初期,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实行了殖民统治,但同时也继承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情。
1945年日本战败后,台湾被归还给中国政府,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清朝管理台湾的措施

清朝管理台湾的措施
清朝管理台湾的措施可以总结如下:
1. 行政机构:清朝在台湾设立了福建、台湾两个行省,设立巡抚、布政使、道台等官职来管理台湾事务。
清朝还在台湾设立了地方官府和县级机构,对台湾进行地方行政管理。
2. 经济管理:清朝通过改良土地制度、收税、推行洋务运动等措施,加强对台湾的经济管理。
清朝还鼓励台湾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提高台湾的经济水平。
3. 移民政策:清朝实行了一系列移民政策,鼓励汉族移民台湾。
清朝还引进了来自福建、广东等地的移民,以加强对台湾的控制和发展。
4. 文化教育:清朝在台湾推行官修教育,设立学堂、书院等教育机构,推广汉文化,并且入籍台湾的汉族积极参与了清朝的科举考试。
5. 安抚台湾原住民:清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设立保甲制度、普渡制度等,来安抚和控制台湾原住民,并稳定台湾社会。
总体来说,清朝通过行政管理、经济政策、移民政策、文化教育和安抚原住民等措施,加强对台湾的管理和控制,推动台湾的发展和稳定。
略论清代台湾移民政策与移垦社会的定型

孙尔凖的建议得到清政府批准。
海丰港 (五条港)、乌石港增设正口之后,加上原有鹿耳门、鹿仔港、八里坌三口,台湾对福
建通航增加到五口,与福建之厦门、蚶江、五虎门三口,共同构成台海两岸商民往来交流的网络。
这些正口也是大陆移民领照前往台湾的正规通道。
二、禁止携眷政策与无照偷渡
在大陆移民不断涌向台湾的过程中,清政府在实行严格的给照渡台制度的同时,也曾实行过
彰化之间的海丰港 (五条港) 则因溪水汇注,冲刷甚为深广,日渐兴盛起来,可因势利导,把海
丰港 (五条港) 增设为正口,仍归鹿港同知经理。二是噶玛兰地处台湾后山,盛产米谷,日用货
物不足,福州、泉州等地商民载日用货物,经乌石港前往易米而归,两相裨益,如果严禁,则商
贩不通,不如增设正口,以利民生。乌石港出入商民船只由噶玛兰厅头围县丞查验,严禁偷渡。
广东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2 期
略论清代台湾移民政策与移垦社会的定型*
李细珠
[摘
要] 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大陆对台移民的管理,曾经实行严格的给照渡台与两岸对渡制度,以
及严厉的禁止携眷政策,并严禁无照偷渡。在这样严苛的制度与政策规定之下,大陆移民仍然源源不
断地前赴台湾,为开发台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正是在清政府实行与内地一体化政策推动下,清代台
收管。如此不但本人有所顾忌而不敢轻为非法,并一切逃仆、逃厮与内地无籍奸棍,假客渡海之
计,亦无处躲闪矣。
”④此即清政府给照渡台之制的原初动议。
从上述陈瑸的建议看来,清政府实行给照渡台之制最早应在康熙四十一年 (1702 年) 之后。
但不久就出现“无照偷渡”现象,大量福建、广东无业游民以“偷渡”的方式涌进台湾,引起台
内,仍开明回籍限期。此外,凡文武衙门非奉公差遣,不许滥给照票,仍照现行之例,俱由厦门
清朝对台湾土著社会的政策与统治

清朝对台湾土著社会的政策与统治随着明朝的灭亡,清朝在17世纪初统一中国大陆后,开始对周边地区的统治。
其中台湾的征服与治理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本文将探讨清朝对台湾土著社会的政策与统治。
一、征服与置地政策在明朝的后期,台湾逐渐成为了多个势力争夺的焦点,其中包括荷兰殖民者和明朝朝廷。
在1661年,明朝名将施琅和郑成功率军攻占了荷兰人在台湾的据点,结束了荷兰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
然后,郑成功建立了台湾明郑王朝。
然而,当时正在北方统一中原的清朝并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独立国家,于是派兵多次进攻台湾。
最终,在1683年,清朝成功征服了台湾,将其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
清朝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巩固对台湾的控制。
二、统治政策与土地制度清朝对台湾所采取的统治政策相对温和。
一方面,清朝尊重了台湾的土著社会,保留了一部分原本的土地制度和习俗。
另一方面,清朝也在政府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清朝将台湾划入福建省,设立了台湾府来行使行政管理权力。
而在人口管理方面,清朝实行“定居制”,即统治者将大批的中国内地人定居在台湾,以填补人口空缺。
在土地制度方面,清朝采取了“白话地与乡”制度,土地归清朝官员或寺庙、士绅、贫民和农民等四类人所有。
这种制度的实施导致了一部分贫民的土地被收回,为清朝官员和寺庙所占有,而土地制度的改变也对台湾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文化与宗教政策清朝在统治台湾时,对于台湾的文化和宗教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清朝鼓励汉族移民台湾,同时也保护了原住民的文化传统。
清朝对台湾的土著社会并没有强行施加汉文化或中国传统价值观,而是尊重和包容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在宗教方面,清朝没有强制土著社会改信道教、儒教或佛教,而是保护土著社会自由信仰。
这种政策背后的考虑是希望通过宗教让土著社会更好地融入清朝的统治,并减少潜在的反抗或不满情绪。
四、军事与经济发展清朝对台湾的统治也有着军事和经济发展的考虑。
为了巩固对台湾的控制,清朝加强了台湾的军事力量,建立了海军基地,加强了对海上贸易的管控。
台湾的福建移民与台湾的农业垦殖

农村经济与科技2010年第21卷第06期(总第247期)农村经管鉴别,是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要尽快改变我国农产品质量检测手段落后的状况,采用技术引进和自我技术创新的办法,用现代化的农产品检测手段武装检测队伍,使农产品质量检测更快捷、更准确。
其四,大力普及农业标准化知识。
没有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农业标准化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和海市蜃楼。
现在,在基层搞农技推广的科技人员,经常感到农民标准化知识缺乏,接受能力差,是加快农业标准化的一大瓶颈。
因此,要通过广播电视、书报刊物等多种媒体,通过会议、科技讲座、现场会、明白纸等形式,向农民宣传加快农业标准化的意义和紧迫性,特别要讲清楚农业标准化对农民增收的益处,提高他们参与农业标准化的积极性。
同时,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班,提高广大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掌握实用的农业标准化知识。
其五,通过多种渠道发展土地规模经营。
实践证明,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着力扶持龙头企业,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
近几年,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较快,一大批龙头企业的崛起,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小农户与大市场接轨的难题,而且也为农业标准化的实施奠定了组织基础。
还要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协会、合作社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标准化中的组织优势。
此外,有条件的地方,要稳妥地促进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使有限的耕地适度向种养大户集中,形成规模化种植、养殖加工业。
其六,充分发挥政府在农业标准化中的作用。
加快农业标准化,离不开政府的正确领导。
但是,农业标准化不能建立在行政命令的基础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领导方式也应该转变,领导就是服务,基层政府在领导农业标准化的工作中,一定要把提高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作为工作重点和立足点,这也是三个代表的要求。
只有这样,农业标准化工作才能真正变成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农业标准化工作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才能使农业标准化成为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一是可以通过建立农业标准化示范园区,做给农民看,引导农民干;二是可以把农业标准化与扶持龙头企业结合起来进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过渡期的农业支持政策,大力扶持龙头企业;三是把农业标准化与实施农业名牌战略结合起来进行,让农民从中得到实惠;四是把农业标准化与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结合起来。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闽台历史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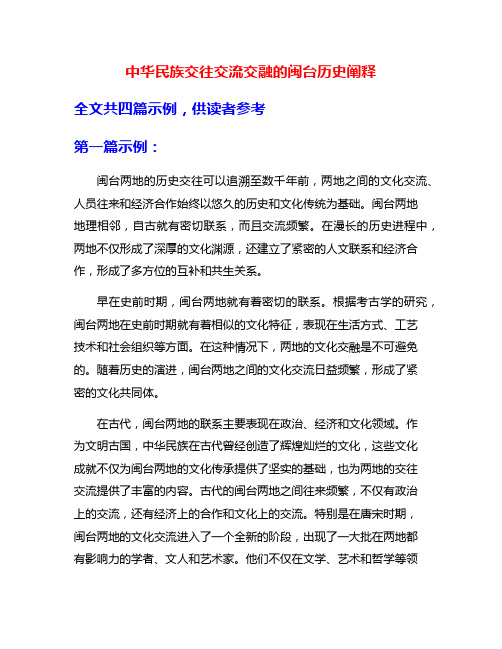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闽台历史阐释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闽台两地的历史交往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人员往来和经济合作始终以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为基础。
闽台两地地理相邻,自古就有密切联系,而且交流频繁。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地不仅形成了深厚的文化渊源,还建立了紧密的人文联系和经济合作,形成了多方位的互补和共生关系。
早在史前时期,闽台两地就有着密切的联系。
根据考古学的研究,闽台两地在史前时期就有着相似的文化特征,表现在生活方式、工艺技术和社会组织等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两地的文化交融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历史的演进,闽台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形成了紧密的文化共同体。
在古代,闽台两地的联系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
作为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古代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成就不仅为闽台两地的文化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两地的交往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古代的闽台两地之间往来频繁,不仅有政治上的交流,还有经济上的合作和文化上的交流。
特别是在唐宋时期,闽台两地的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出现了一大批在两地都有影响力的学者、文人和艺术家。
他们不仅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还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人才的涌现为闽台两地的文化交融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的闽台两地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动下,闽台两地之间的经济合作日益深入,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也不断增强。
特别是台湾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实体,为两地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
与此两地在旅游、教育、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也日益活跃,为两地的文化交流和共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闽台两地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交流、人员往来和经济合作始终是两地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闽台两地应该进一步深化交流,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两地的文化传承和发展。
明清时期泉州商人对台湾的影响

泉州是福建省东南部的文化古城,与台湾有着一衣带水的关系。
早在公元607年泉州古港便开始了与台湾的通商往来,以后泉州与台湾更是开始了自发的、零散的移民,明代著名学者、晋江人何乔远在其著作《闽书》“方域志”中,征引已佚的宋淳祐《清源志》云:“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人民侨寓其上,苫矛为舍,惟年大者长之。
不畜妻女,耕渔为业,雅宜放牧。
魁然巨羊,散食山谷间,各厉耳记。
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
府外贸易,岁数十艘,为泉外府。
其人人夜不敢举火,以为近琉球,恐其望烟而来作乱。
王忠文为守时,请添屯永宁寨水军守御。
”这段文字表明,至迟到南宋年间,澎湖岛上已有汉人定居,并有永宁寨水军协助守御。
此时澎湖已成为连结大陆与台湾经济来往的重要纽带。
而到了明清时期,闽台两地经济交往急剧增长,福建沿海漳、泉商人“往来通贩,以为常事”。
这一时期,泉州对台湾的大量移民主要有着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并呈现出其独特的特点,泉州人民与当时的台湾人民共同努力,推进了台湾的开发与社会的发展。
一、泉州人移民台湾的条件与原因(一)先天的地缘关系隔海相望的闽、台两地,属东亚大陆板块,在远古时代即连成一体,后来因剧烈的地壳运动,才出现横亘于福建与台湾之间的台湾海峡。
海峡最近处仅135公里,这个地点就在泉州惠安县崇武半岛的突出部。
崇武港渡台的地理优势,还有更重要的方面。
早年两地人民的交往,使用的是木帆船,靠潮流及风力航行。
“朝发夕至”是早年木帆船渡台的基本要求,而由崇武启航最顺。
据台湾《彰化县志》载:“彰邑与泉州府遥对,鹿港为泉、厦二郊商船贸易要地。
内地来鹿者……北风以崇武为最,獭窟次之。
故北风时渡船来鹿必至崇武,獭窟放洋……鹿泉、厦郊船户再欲上北者……必仍回内地各本澳,然后沿海北上,由崇武至莆田、湄洲、平海……”1这样就使泉州与台湾的经济往来有了先天的良好优势。
“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早在先秦时期泉州就得以与台湾开始了贸易。
在属于台湾新石器文化晚期和青铜时代文化早期的圆山文化中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与同时期的泉州出土的有段石锛十分相似,说明这个时期两地人民的经济交往渐趋密切。
清朝对台湾地区的管理措施(一)

清朝对台湾地区的管理措施(一)清朝对台湾地区的管理概述清朝对台湾地区的管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详细说明清朝对台湾地区的管理措施,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变化。
开放港口1.1683年,清朝攻占台湾后,开始实行对外贸易政策。
2.清朝开放了兵站港、淡水港等港口,促进了台湾与外界的联系。
重建行政机构1.1684年,清朝在台湾设立了台湾府,作为行政机构。
2.台湾府下设台湾道、官厅、县等机构,实行地方政权。
双重税制1.清朝对台湾实行了双重税制,即土地税和额外的关税。
2.这使得农民和商人负担沉重,引发了不满和抗议。
禁止移民1.清朝对外来移民实行限制政策,限制非官员及其家属迁居台湾。
2.这导致台湾的人口增长缓慢,限制了台湾的发展。
加强军事防御1.清朝在台湾加强了军事防御,设置了关隘、炮台等设施。
2.清朝还在台湾驻军,维护边疆稳定和安全。
促进农业发展1.清朝鼓励农业生产,对农民实行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
2.清朝还引进糖业和茶叶等新兴产业,推动台湾经济发展。
教育与文化1.清朝在台湾设立了学堂、书院等教育机构,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2.清朝还鼓励汉文化的传播,推广汉族传统文化。
政策调整1.19世纪末,清朝面临外患和国内动荡,对台湾的管理政策发生了调整。
2.清朝采取了开放对外贸易、加强军事防御等措施,应对现实挑战。
结语清朝对台湾地区的管理措施涵盖了经济、军事、教育等多个领域,虽然政策存在一些限制和问题,但也为台湾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这些政策和调整,对后来台湾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济开放与发展•清朝实施了开放对外贸易政策,并建立了兵站港、淡水港等港口,促进了台湾与外界的贸易往来。
•清朝引进了糖业和茶叶等新兴产业,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
•清朝鼓励农业生产,对农民实行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行政机构改革•清朝在台湾设立了台湾府,作为行政机构。
•台湾府下设台湾道、官厅、县等机构,实行地方政权。
台湾的人文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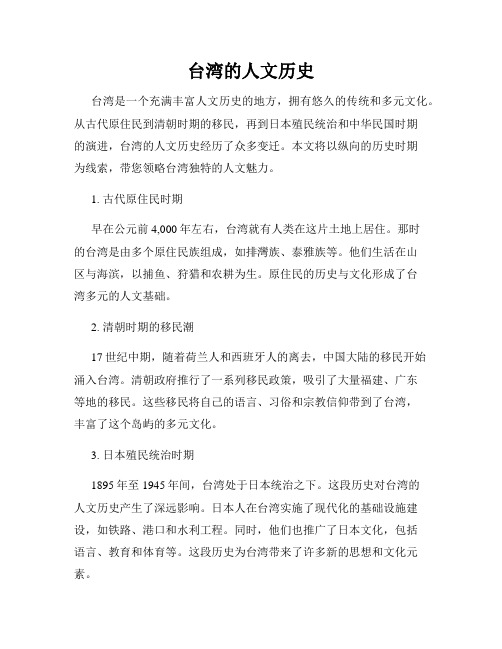
台湾的人文历史台湾是一个充满丰富人文历史的地方,拥有悠久的传统和多元文化。
从古代原住民到清朝时期的移民,再到日本殖民统治和中华民国时期的演进,台湾的人文历史经历了众多变迁。
本文将以纵向的历史时期为线索,带您领略台湾独特的人文魅力。
1. 古代原住民时期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台湾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居住。
那时的台湾是由多个原住民族组成,如排灣族、泰雅族等。
他们生活在山区与海滨,以捕鱼、狩猎和农耕为生。
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形成了台湾多元的人文基础。
2. 清朝时期的移民潮17世纪中期,随着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离去,中国大陆的移民开始涌入台湾。
清朝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移民政策,吸引了大量福建、广东等地的移民。
这些移民将自己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带到了台湾,丰富了这个岛屿的多元文化。
3.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895年至1945年间,台湾处于日本统治之下。
这段历史对台湾的人文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人在台湾实施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港口和水利工程。
同时,他们也推广了日本文化,包括语言、教育和体育等。
这段历史为台湾带来了许多新的思想和文化元素。
4. 中华民国时期的演进1945年,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接管了台湾。
这个时期,台湾经历了从军事统治到民主化的转变。
台湾人民重新恢复了言论和出版自由,并且追求了民主和人权的理念。
同时,多元文化和民族认同也成为了台湾社会的重要议题。
总结:台湾的人文历史丰富多样,各个时期的文化都对台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古代原住民时期的多元文化,清朝时期的移民潮,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华民国时期的民主转型,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台湾独特的人文魅力。
如今的台湾保留了这些历史遗迹,并且在当代社会中继续传承与发展。
无论是古老的庙宇,还是现代的艺术表演,都体现了台湾人文历史的丰富内涵。
前往台湾,您将有机会亲身感受这个宝岛上不同文化交融的魅力,探寻那些隐藏在历史长河中的珍宝。
略论明清时期福建人对台湾的开发和经营

略论明清时期福建人对台湾的开发和经营──以晋江东石人为例何振良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唇齿相依,两地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
目前所知,从宋代开始,泉州一带就不断有人移居台湾,明末以来直至有清一代,大陆多次掀起移民台湾的高潮,泉州人始终在台湾的移民中占居多数。
他们筚路蓝缕,流血流汗,开荒拓地,为开发台湾立下了丰功伟绩。
晋江市东石镇,地处泉州港围头湾内,与安海镇、南安市石井镇互为犄角,它“得鳌山之钟秀,摄东海之雄威,据山川之险峻,占水陆之优势”,自古为军事要塞和商业富埠。
翻开地图册,东石与台湾在方寸之间隔水相依,两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郑成功抗清时,曾于东石建寨,并屯兵于附近的白沙城。
东石人民大力支援过郑成功,有的还跟随郑氏大军收复台湾,成为开发台湾的先驱。
本文拟从有关东石几家族谱资料对明末清初东石人对台湾的开发和经营略作探讨。
一一衣带水两东石地名是社会文化遗产,是历史组成部分,表达人民群众的愿望。
台湾许多地名包含大陆移民史的内容,闽台血缘关系从中可见。
台湾有许多贯姓和贯籍地名,正是闽、台“血缘”(贯姓)与“地缘”(贯籍)密切关系的体现。
据调查,台湾此类地名共有200多个(贯姓地名100多个,贯籍地名80多个),主要源自泉州、漳州地区移民的姓氏、地籍,是明末清初泉州一带大批移民往台聚族而居所形成的。
当移民们离开家乡,来到这鸿蒙未开、遍地瘴烟的海岛时,为了不数典忘祖,往往以其姓氏或籍贯地来命名所居住的村落,因而在台湾出现了许多贯姓或贯籍地名。
翻阅东石各姓氏的族谱,他们先人在台湾奋斗的脚印布及布袋嘴、新塭、郭岑、虎尾寮、笨港、东港、白沙、麦园、型厝和嘉义、彰化、台南、高雄等沿海地区。
而郭岑、白沙、麦园、型厝,如同东石镇、东石乡、东石里、东石寨一样,都是沿用故乡的原地名。
①兹举有关谱牒,证明如下:如东石镇白沙村,以周姓为主,郡号是“汝南衍派”,“濂溪衍派”,堂号立有“爱莲堂”、“理学传芳”。
关于明末清初福建人移民台湾问题概述

关于明末清初福建人移民台湾问题概述下面是关于明末清初福建人移民台湾问题概述,欢迎阅读借鉴,希望你喜欢。
移民是台湾社会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移民史也是台湾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篇章。
故而,研究台湾历史,移民历史的梳理至关重要。
如今的台湾地区是一个以汉族移民为主体的移民社会。
在这些汉族移民中,福建籍、广东籍的移民数量占绝大多数,其中福建籍移民又以漳州和泉州最具代表性。
根据1926年《台湾在籍汉民乡贯别调查》结果表明,全台湾375万汉人中,有311.5万人祖籍为福建,约占83%。
福建人中,漳泉府籍者共约300万人,约占闽省籍人的90%。
故笔者试图以漳州、泉州为例,概括分析明末清初时期福建人移民台湾的主要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
一、荷兰统治台湾时期(明天启四年至清顺治十七年)自北宋以来,以“八山一水一分田”著称的福建地区,伴随着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宋金战争愈演愈烈,北方移民也蜂拥而来。
早在唐元和年间(806年至820年)之时,福建仅有74467户,但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年至983年),即已增至467815户,增长率为528%。
福建地区海拔两百米以下的平原仅占总面积的12.47%,适宜耕作的土地面积极其狭小。
故而,伴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人地矛盾日渐突出,粮食产量难以满足人口需求。
宋初“土地迫狭,生籍繁狄,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值贵”。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福建人口约为391万,耕地面积约为146259顷,万历六年(1578年),福建人口突破500万,耕地面积反而下降至134226顷。
人口快速增长,耕地面积不升反降,人地矛盾更趋尖锐。
土地对于中国农民而言,有着特殊而深刻的意义,“农民各种生活所需,直接、间接都要从土地上获得,这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
”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徭役、赋税负担沉重,福建百姓苦不堪言。
人祸未尽,天灾又至,遂成雪上加霜之势。
清末,此地先后成为清军与南明、台湾郑氏、三藩势力的交战之地。
为了生存,民众纷纷背井离乡,加紧移民台湾。
明清之际福建士绅的海岛移民及其生活样态

明清之际福建士绅的海岛移民及其生活样态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境内河流众多,山川秀丽,是一个物产丰富、地理优势明显的省份。
然而,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福建人不满足于家乡的土地,而开始踏上远航之路。
他们先是在福建省沿海,尤其是闽南地区一带,逐渐成立自己的航运公司和商业帝国。
之后,他们向南走向海上交通枢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又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华人城市”,为海外华人传播福建文化、发展经济、增进贸易、开拓市场做出了巨大贡献。
尤其是明代末年,在福建东南沿海和台湾海峡一带,由于政治、经济、民族等因素的影响,一批福建士绅选择到海岛上居住、开垦、经商,以寻求更好的生存条件。
这些海岛,有的是中国的领土,有的是归类为“蕃地”的地区,比如台湾、琉球等。
他们将北上广等地遗留下来的遗骸和信仰,与传统的岛屿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福建特色的生活样态。
他们的生活方式,以耕种、渔猎、商贸为主。
在海岛上建造的房屋有长条宅和板屋,依据岛上地形、气候、风水等条件而异。
屋子里铺设竹签地,放置土钟、香炉、宿仇碾等神龛,寓意着保佑家宅平安。
居民以传统的福建话交流,男人扛起一把竹伞,穿起透气的葛布衫,从早到晚在田头劳作,或是摆摊卖货,获得生计。
而女人则负责家务,从种菜、做饭,到织布、缝褂,无不追求最高的实用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岛民们擅长吃海产,用绿竹叶、芦苇制成的绸箩更是成了他们储藏海味佳肴的标志之一。
福建士绅的海岛移民,充分展示了岛屿生态环境和文化传承的独特魅力。
他们不仅留下了“福建十三行”商业帝国的伟大历史,更给我们带来了一份与海洋亲密接触的幸福感。
这些历史人物,犹如一道道流光溢彩的月亮,指引我们永葆初心,勇攀科技高峰,共迎美好未来。
台湾的福建移民与台湾的农业垦殖

其六 , 充分发挥政府 在农 业标准化 中的作用 。加快农业标
准 化 , 不 开 政府 的 正 确 领 导 。但是 , 业标 准化 不 能 建立 在 行 离 农
等 物 , “ 元 通 宝 ” 判 断 出该 遗 址 当 属 盛 唐 时 期 。另 据 文 献 从 开 可 史料载录 , 明末 曾 游 历 台 湾 岛 的普 陀 山 僧 人 华佑 说 , 在 刘 ( 他 即
里 脑 , 宜 兰县 冬 山 乡 补 城 村 ) 过 唐 碑 , 书 “ 元 ” 字 分 明 今 见 上 开 二
周 口店 “ 山顶 洞 人 ” 时代 大 体 相 同 , 的 同属 晚 期 智 人 。 “ 镇 人 ” 左 就是从 大陆经 由福建长途跋 涉 , 居 台湾的 , 以“ 镇人 ” 移 所 左 也
被 称 为 “ 陆 开 发 台湾 第 一 人 ” 大 。 早 在 黄 龙 二 年 ( 元 2 0 ) , 国孙 权 派 遣 将 军 卫 温 和 公 3年 春 吴
过 几 次 高潮 . 以致 台 湾的 人 口大 量 增 加 。 随 着 福 建 移 民的 迁 入 , 湾的 土 地 得 到 大 量 垦 殖 , 动 了 台湾 农 业 的发 展 。 台 推 [ 键词 】 关 台湾 ; 民 ; 殖 移 垦 台湾 在 历 史 上 属 移 民 社会 , 民 主 要 来 自闽 地 。明清 时期 , 移 随 着 福 建 移 民 的 大量 迁 居 台 湾 ,台 湾 的 土 地 得 到 大 量 垦 殖 , 农
代 遗 址 . 土 了 大 量 的 钱 币 、 银 器 皿 、 器 、 璃 饰 物 及 玉 环 出 金 铁 玻
明清的福建和台湾开发

初中学好副科的学习方法有哪些话说,“习惯成自然”,良好的学习习惯对学习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所以学生在学习上养成良好的习惯以及学习方法是很有必要得。
以下是店铺分享给大家的初中学好副科的方法的资料,希望可以帮到你!初中学好副科的方法1抓住课堂四十五分钟,学会听课听课也有不少学问。
学会听课,对初中生的学习进步至关重要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课堂学习是学习的最主要环节,四十五分钟课堂学习效益的高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
也许有的家长和学生会想,每个人都有一双耳朵,听课谁不会呀。
其实不然,听课也有不少学问。
学会听课,对初中生的学习进步至关重要。
首先,要集中注意力听。
心理学研究表明:注意能够帮助我们从周围环境所提供的大量信息中,选择对当前活动最有意义的信息;同时,使心理活动维持在所选择的对象上,还能使心理活动根据当前活动的需要作适当的分配和调整。
所以,注意力对于学习尤为重要。
集中注意力、专心致志才能学有所得;心不在焉、心猿意马往往一无所获。
其次,要带着问题、开动脑子听。
有些同学听课不善于开动脑子,不去积极思维,看似目不转睛,但一堂课下来心中却不留痕迹。
俗话说:“学贵有疑”,“疑是一切学习的开始”。
带着问题听课,就能使听课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和重点,增强听课的针对性,从而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带着问题听课,还能促使自己积极动脑,紧跟老师的教学节奏,及时理解和消化教学内容。
再次,要积极举手发言。
教与学应是双向交流,是双边活动,是互相促进的。
学生上初中后,尤其是上了初二,变得不举手、不发言了。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开始在意周围同学与老师对他的评价了,不愿意发言是怕说错了丢面子,其实这样想是错误的。
家长应该引导学生,让学生在课堂中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
积极举手发言就是一种参与,它既能较好的促使自己专心听课、动脑思维,还能锻炼语言表达能力。
再有,要认真做好笔记。
俗语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些都是说边学习边动笔的好处。
清代福建平定台湾的策略与成果

清代福建平定台湾的策略与成果作为一个岛屿国家,台湾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清代,台湾曾发生多次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清军对台湾的平定战争。
而在这场战争中,福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福建在清代平定台湾的角色入手,探讨福建在这场战争中的策略与成果。
福建在清代平定台湾的角色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福建在清代平定台湾战争中的地位。
在这场战争中,福建不仅是主力军之一,同时也是主要的后勤支援基地。
之所以福建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福建与台湾非常接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福建在清代是一个兵源地。
福建与台湾之间隔着一条海峡,只有约160公里的距离。
因此,福建是清军攻占台湾的最佳出发点。
此外,福建境内有多条通往台湾的海上航线,这些航线在这场战争中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福建还有许多港口,为清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
虽然福建在清代人口不算多,但它在清军中的兵源地位毋庸置疑。
当时的福建是一个贫穷的地区,许多人都要出去打工。
因此,福建民众很愿意加入军队,为清朝效命。
这些福建士兵都很勇敢,素有“福建贼、水师良”之称。
他们凭借着出色的战斗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清军取得了胜利。
福建的战略福建在清代平定台湾战争中的策略可以概括为“水陆攻防并举”。
这一策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水力进攻台湾,二是以陆军固守福建海疆。
福建在整个战争中都对水力的运用非常重视。
福建军队的主要战斗力来自于水师。
福建水师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和优秀的指挥官,曾多次打败荷兰和英国的海上侵略。
在进攻台湾时,福建水师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661年陈璘进攻台湾到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福建水师共派遣了数十万精兵,投入了近百次大规模的海战。
通过水力进攻,福建在台湾的沿海地区建立了牢固的阵地,使台湾沿岸一度成为清军的天下。
而在福建陆地的防御方面,福建军队同样表现出色。
福建的地形非常适合作为陆地防线。
山岭起伏,弯弓横斗,多河川,地形复杂。
冒籍:清代台湾的科举移民

冒籍:清代台湾的科举移民
李祖基
【期刊名称】《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00)001
【摘要】清代前期,闽粤移民冒籍赴台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相当普遍,台湾地方官员对此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闽省官员和巡台御史曾对其进行查禁和清理,但成效不彰.科举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改善了台湾这一边陲地区人口的文化结构.有的科举移民及其后裔还参与台湾的土地开发和文教设施建设,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繁荣和发展地方文教事业中作出贡献.清代前期台湾的科举移民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这一现象表明,海峡两岸人民之间除了地缘、血缘的关系外,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总页数】8页(P62-69)
【作者】李祖基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福建,厦门,3610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95.58
【相关文献】
1.清代顺天科举考试中的冒籍问题——一种关于“考试移民”的历史追溯 [J], 刘希伟
2.一部科举学研究的佳作--评刘希伟著《清代科举冒籍研究》 [J], 冯建民
3.清代台湾开发初期汉移民的聚居形态——兼评尹章义先生的“多籍杂处论” [J], 肖通;
4.清代台湾科举中的\"粤籍\"与\"粤籍举人\"述论 [J], 蔡正道
5.清代台湾开发初期汉移民的聚居形态——兼评尹章义先生的“多籍杂处论” [J], 肖通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清代的闽台对渡及其影响

清代的闽台对渡及其影响
戴清泉
【期刊名称】《大连海运学院学报》
【年(卷),期】1993(019)003
【摘要】阐述了清廷对台政策的转变与闽台对渡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演变过程,详细介绍了闽台对渡的管理。
闽台对渡的实施,对台湾的经济繁荣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总页数】6页(P284-289)
【作者】戴清泉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512.9
【相关文献】
1.试析清代前期的闽台对渡政策 [J], 苏惠苹
2.论清代前期的闽台对渡贸易政策(上) [J], 黄国盛
3.试析清代前期的闽台对渡政策 [J], 苏惠苹;
4.商人群体与区域经济互动研究——以清代闽台对渡时期郊商为例 [J], 杨文娟; 孟秀娟
5.商人群体与区域经济互动研究——以清代闽台对渡时期郊商为例 [J], 杨文娟; 孟秀娟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满清的沿海迁界,致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数十万人死于非命,却被《康熙王朝》美化为仁政

满清的沿海迁界,致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数十万人死于非命,却被《康熙王朝》美化为仁政康熙年间,清政府为让台湾得不到大陆的物资,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
总之,让对于台湾郑氏海军朝发夕至的福建沿海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
坚壁清野以削弱台湾郑氏海军的作战能力。
这即是所谓的“沿海迁界”。
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
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
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这段话的意思并不难理解,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
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内迁,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
可以想象,就算是现代,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
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不得不说,沿海迁界就是一场赤裸裸的暴政,是对沿海地区的人民的一种犯罪行为。
对于当时的清廷来说,做出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他们手上的血债太多了,从辽东大屠杀、济南屠城,再到扬州十日、剃发易服、广州、大同、四川全省……,满清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令人发指!但是,在某些满遗眼里,那可得想办法洗白了,虽然扬州十日、剃发易服这些罪行洗不了,因为洗了也没人信,但是“沿海迁界”这回事,大多数国人都不熟悉,那还是有必要洗一下的。
于是到了电视剧《康熙王朝》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剧情:电视剧康熙王朝里,郑氏要和荷兰殖民者平分台湾,以抗拒统一。
然而现实是,清朝为了剿灭明郑,与荷兰组成联军,并承诺与荷兰人共治台湾。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清代福建移民对台湾的影响大陆汉人移民台湾岛定居开发始于明代中后期,清代统一台湾后,设置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管辖,闽粤沿海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移民入台垦殖热潮,台湾由烟瘴之地一跃而成为清代的米糖生产基地。
大陆移民进入台湾后,必然会和分布在岛内各地的土著居民发生交流与冲突。
移民一开始在台湾的锐意垦拓受到了土著居民的抵抗,汉番矛盾比较尖锐,后来在汉族移民的不断强力开垦下,原先居住于西部沿海平地的平埔族最先逐渐汉化,一部分“生番”逐渐汉化转变为熟番,另一部分则退守内山,仍保持原有生活习惯。
汉族移民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关系说明,清代边疆国土资源的开发是各民族在长期交流往来的基础上共同完成的,移民与少数民族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
一、台湾地处东南沿海,是祖国边疆地区最重要的海岛,自明代开始,大陆与台湾的往来已十分密切,此时文献称台湾为“东番”。
清代对台湾土著居民的称谓除沿用明代“东番”名称外,在官私文献中还有“番族”、“土番”的称谓。
对居住于平地并已逐渐汉化者的土著居民称为“熟番”、“化番”或“平埔番”,即平埔族,对居住于山区尚未汉化者的土著居民则称为“生番”、“野番”或“高山番”,即高山族。
生番与熟番只名称已成为清代官府对台湾土著居民共通使用的一种行政性用语。
对其划分问题,主要以归化为依据,雍正六年(1728)九月,台湾总兵王郡奏称:“台湾自我朝开辟以来,则有生、熟二番。
其向西一带山脚服役纳课者为熟番;而分散居山不入教化者为生番。
……各种生番,其每社多则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性虽嗜杀俱皆不识不知,而所怯者惟枪与炮耳。
”王郡奏折说明,清代对生番、熟番的界定颇为明显,生番是指不服从官府统治、不服役纳课者,而熟番则是指服役纳课、服从官府统治之人。
随着汉人移民与熟番的垦殖不断深入,生番与汉人及熟番的矛盾愈益激烈,生番杀害汉人的“番害”、“番乱”事件层出不穷,雍正年间最为频繁。
正因为生番不断杀害汉民,清朝改行生番隔离政策,对之采取的措施就是“惟枪与炮耳”的武力镇压。
与此同时,为了减少番汉间的冲突,清朝划定汉番界线,阻止汉人与生番的接触,在番界上设立界石,派兵驻守。
事实上,汉番界线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更,也就是说,随着汉人对生番土地的不断越界侵垦,政府往往都承认其垦殖事实,番汉界线就不得不重新划定。
自清初至日据时代,汉番界线一直在变动之中,汉人垦殖的区域越来越大,而生番的生活区域反而愈加窄小,汉族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发生冲突势成必然。
台湾移民与土著居民关系的紧张引起了官府的高度注意,乾隆中期以前,台湾西部海岸平原的平埔族原有土地在汉族不断垦殖下,已几乎流失殆尽,随后清廷重新配置平埔族土地于西部平原东侧沿山附近生番边界一带,加以保护,并利用平埔族“熟番”防守“生番”的出草杀人及镇压汉人在台湾的动乱;对高山族的“生番”则实行消极的隔离封禁政策,直到晚清才对番地进行积极的保护开发。
清代对台湾土著居民的管理,往往根据其教化程度,对熟番设官管理,“台湾僻处海外,向为土番聚居。
自归版图后,遂有生、熟之别。
生番远住内山,近亦渐服教化,熟番则纳粮应差,等于齐民。
凡社中皆择公所为舍,环堵编竹蔽其前,曰公廨(即社寮),通事居之,以办差遣。
土官之设,系众番公举,大社四、五人,小社二、三人,给以牌照,各为约束。
”所谓“内山”大约是指汉人绝少进入之地,“凡山之绵缈阻绝、人迹不到者,统称内山”。
而这些内山大多居住着“生番”,他们与汉人接触不多。
史实表明,台湾土著居民的汉化并非由清朝官府直接推动汉番融合的结果,主要是汉族移民一开始不断向熟番占垦租赁土地耕种,与平埔族发生冲突、交流到逐渐融合,然后又逐步与“生番”发生往来,从而导致台湾土著居民的汉化出现多个层面的现象,形成熟番、半熟生番和生番的格局。
熟番已基本汉化,半熟生番则处于向汉化转变的阶段,生番则基本保持原有的生存状态。
半生熟番正是一部分生番在与汉人和熟番的不断交流往来中,一步一步地向熟番转化,他们开始改变原先以“捕鱼猎兽而食”及“不知耕作”的游牧生活逐渐向半生熟番“亦知耕种”的农耕生活转变,但又不时发生杀人行为。
还有一部分生番则仍然固守着原有的生活传统,保持着“凶悍”的习性。
官府在早期是尽量阻止汉番来往,即使后来容许汉人开垦番地,也更多的是对汉人已开发的既成事实之肯定。
二清代台湾在移民社会形成之前,理论上讲,台湾的土地均属于当地土著居民所有。
汉族移民入台实际上是分享与占有了土著居民的土地和生活资源。
随着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土著居民土地被汉族侵垦不断增加,汉番冲突日趋激烈。
清代移民在台湾土地开发基本上是循着从台湾西部海岸的南部地区,不断向北部和中部地区挺进,因此,早期汉人与台湾土著居民的接触与冲突主要是平埔族。
清前期,平埔族约有150余社,分布在台湾西部平原及丘陵地域,在汉族入台之前,凡海拔在500米以下的土地,均可视为平埔族的原居地。
至道光初年,在移民不断占垦土地压力下,平埔族被迫放弃故居地,举族迁移,向埔里盆地、宜兰平原迁徙,并将原居住的“埔眉番”(泰雅人与布农人)逐进山中。
而平埔族因与汉人长期的杂居共处,其社会经济已过渡到以农耕为主、狩猎为辅的状态,其种植的旱稻颇有名气,光绪《台阳见闻录》卷下《番部·饮食》记载:“熟番种植,多于园地。
所种悉旱稻、白豆、绿豆、番薯。
又有香米,形倍长大,味甘气馥,每岁所种止供自食,价虽数倍不售也。
”是书《番部·香米》又载:“熟番多于园中旱地种稻,粒圆而味香,名曰香米,又名大头婆,甚为珍重”。
土著对稻作农耕十分重视,乾隆时巡台给事中六十七著《番社采风图考》记载:“郡邑附近番社,亦三、四月插秧。
先日猎生酹酒祝空中,占鸟音吉,然后男女偕往插种,亲党饟黍往馌焉”。
平埔族农耕种植业的普及,与汉族移民不无关系,乾隆十年(1745)范咸纂修的《重修台湾府志》卷22《艺文·记》载有陈梦林的“游北香湖记”称,此时汉番已联合修建水利工程,发展灌溉农业,北香湖“自台斗坑凡数折,而汇县治之众流,黛蓄膏渟,广可三、四亩,修如其广数十倍,汉人与土番合筑为陂。
其下,西出北社尾,灌田凡数百顷。
”汉番的交流,也逐渐改变了土著居民的某些习俗,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番俗·服饰》记载:“土番初以鹿皮为衣,夏月结麻枲缕缕挂于下体,后乃渐易幅布。
”数年来,新港、萧垄、麻豆、目加溜湾“诸番衣裤,半如汉人”。
台湾移民开垦土地,除了自然环境恶劣外,移民还要面对与汉人交往过少的土著居民挑战。
清代台湾“生番”主要以狩猎为主,狩猎又叫“出草”,狩猎武器较简单,主要是标枪和弓箭,因此,狩猎时需集体围捕猎物,康雍时的《台海使槎录》卷8《番俗杂记·捕鹿》载:“鹿场多荒草,高丈余,一望不知其极。
逐鹿因风所向,三面纵火焚烧,前留一面,各番负弓矢、持镖槊,俟其奔逸,围绕擒杀。
”随着汉人向山区的不断进发,“出草”习俗发展为猎人首,据光绪《新竹县志初稿》卷5《风俗考·番俗》载:“内山生番或数十家为一社,或百十家为一社;各社皆有土官、有壮丁。
除妇女而外,其壮丁皆备鸟铳,听土官呼召,兼习强弩短刀。
凡有出草(杀人曰出草) 及战斗,长于埋伏掩袭,不知步伐止齐之法,出没茂林丰树中。
”这则史料出处较晚,但却明白说明“杀人曰出草”的事实。
而生番杀人由来已久,乾隆时范咸纂《重修台湾府志》卷16《风俗·番社通考》记载:“生番素喜为乱……其俗尚杀人,以为武勇。
所屠人头,挖去皮肉、煮去脂膏,涂以金色,藏诸高阁,以多较胜,称为豪杰”。
蓝鼎元在《东征集》卷4《复吕抚军论生番书》也谓:“生番杀人,台中常事”。
而移民遭生番杀害的增多,恰恰是由移民开垦的深入逼近生番造成,“内山生番野性难驯,焚庐杀人,视为故常。
其实启衅多由汉人,如业主、管事辈利在开垦,不论生番、熟番越界侵占,不夺不餍;复勾引伙党入山搭寮,见番弋取鹿麂,往往窃为己有,以故多遭杀戮。
又或小民深入内山抽藤锯板,为其所害者亦有之。
”客家人《渡台悲歌》也对此有记录,“抽藤做料当壮民,自家头颅送入山,遇到生番铳一响,燃时死在树林边;走前来到头斩去,无头鬼魅落阴间”。
一些地方因接近生番,即使已初有开发,但在生番的抵抗进攻下,汉人只好撤退,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1《封域》载,罗汉门附近“沃衍平畴,极目数十里”,汉人在此建立了外埔、中埔、内埔三个村庄,汉番杂处,“继以远社生番乘间杀人,委而去之。
今则茀草不可除矣。
”雍正时期,生番杀人不断增多,官府不得不出面干涉,史载:“水沙连,旧为输饷熟番。
朱逆乱后,遂不供赋。
其番目骨宗等自恃山溪险阻,屡出杀人。
逮雍正四年,复潜踪出没,恣杀无忌”。
官方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擒获骨宗父子三人,搜出藏贮头颅八十五颗”。
直到光绪年间,恒春县的尖山、水坑一带,“仍有凶番屡出杀人,割去头颅无虑数十,并杀高仕佛汛官林武兴及防兵一名,焚毁汛房”。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生番杀人,有时又与汉人中的“番割”引导有关,据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140《宦绩》载:“番割者,汉人通番语,窜内山娶番妇,时引生番劫掠平民”。
清前期,台湾的民番之争大多因移民垦拓土地而起,而台湾的垦殖往往是大户出资向官府申请垦照,然后招佃开垦。
所以,乾隆九年(1744),朝廷下令禁止赴台文武官员乘机设立庄田招佃开垦,“朕闻台湾地方,从前地广人稀、土泉丰足,彼处镇将大员无不创立庄产,召佃开垦以为己业,且有客民侵占番地,彼此争竞,遂投献武员,因而据为己有者。
……是以民番互控之案,络绎不休。
若非彻底清查,严行禁绝,终非宁辑番民之道。
”他下令严查且永行禁止。
实际上,这一禁令并没有被认真贯彻执行,地方官上报朝廷时对侵界垦殖多有意回避,乾隆十七年(1752)彰化县发生“生番骚扰村庄、杀死兵民”事件,乾隆下令调查原因,结论为:“细察此次凶番残杀兵民,其为因奸民占种番地,熟番逞凶焚杀,已无疑义”。
但此前“该郡文武禀报犹以事出生番为言,与提臣查覆情形迥异;始终欲以生番焚杀掩其致衅之由,且听信通事张达京诡言嫁祸,粉饰欺朦。
参请严办,以重海疆”。
而文武官员禀报的内容,之所以与提臣调查事实不符,极有可能官员本身就设有庄田。
随着清代汉人移民的不断入台,土著居民由原来的主体族群,逐渐在大规模的移民压力下,成为非主流群体,汉人则上升为台湾主体民族。
土著居民身份地位的变化,尤其是汉人的土地开发日益接近“生番”境界,汉番之间矛盾更为突出,雍正年间,浙闽总督高其倬上奏称:“番人焚杀一节,此事情节中有数种:一则开垦之民侵入番界及抽藤吊鹿,故为番人所杀;一则番社俱有通事,通事刻剥,番人愤怨之极,遂肆杀害,波及邻住之人;一则社番杀人数次,遂自恃强梁,频行此事,杀人取首,夸耀逞雄。
”汉人强入番界以及通事的刻剥引发了“生番”对汉人的仇杀,以致汉人有“自来番性嗜杀”之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