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

2、文学之根虽在文化,但却并不等同于 全部的民族传统文化。
李杭育在《理一理我们的“根”》中说:“中国 的文化形态以儒家为本。儒家的哲学浅薄、平庸, 却非常实用。”
3、对民族文化应该作出新的判断和认 识
寻根文学试图通过对民族本土文化沉积的 发掘,“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 势”,建立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学品格。
六.寻根小说的历史变革作用
局限: 对于‚根‛的理解的静止性和非历史性, 导致了一些作家一味的沉迷于古、俗、粗、 野之中,表现出贵远贱近、向虚背实的倾 向。
80年代小说
寻根小说
王安忆的《小鲍庄》
以平实朴素的语言,非线 型散点透视的叙述方法, 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浸透着 传统文化几近封闭状态的 村庄和一群农民的生存状 态。表现上看,这里民风 古朴,讲究仁义,敬老爱 幼,其实贫穷、落后、愚 昧,甚至人性被扭曲。
3、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价值选择
作家们在对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糟粕进行否定的同 时,也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价值选择。 在寻根文学中,被认为最能显示传统文化精神的 是阿城的小说。他以《棋王》、《树王》、《孩 子王》奠定了他在寻根文学中的坚实地位,以他 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道家文化的追寻成为最 有特色的寻根小说代表人物。
寻根小说
一.“寻根文学”概念
1983年前后,一些作家 把目光投向了民族文化,尝试 以现代意识去关照民族文化 传统以及民族心理深层的文 化积淀,从文学与文化的关 系中去寻求民族文化的根。 主要代表作家:莫言、韩少 功、王安忆。
二 、文化寻根思潮形成的历史背景
寻根文学是指80年代中期出现在当代文 坛上的以“文化寻根”为思想艺术追求 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种类。85年,韩少功、 阿城、郑义、李杭育等青年作家发表文 章,正式提出“文化寻根”的口号,意 欲对民族文化精神返本求源,挖掘民族 性格中的民族文化素质。主要代表作有: 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 庄》、阿城的《棋王》等。
论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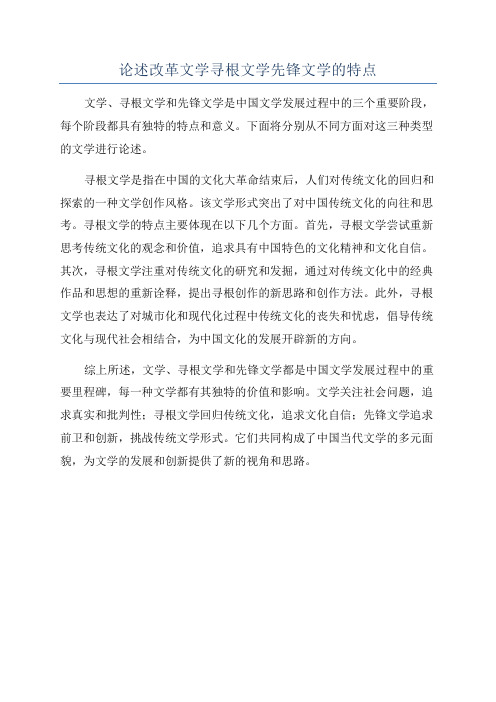
论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特点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重要阶段,每个阶段都具有独特的特点和意义。
下面将分别从不同方面对这三种类型的文学进行论述。
寻根文学是指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探索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
该文学形式突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和思考。
寻根文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寻根文学尝试重新思考传统文化的观念和价值,追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自信。
其次,寻根文学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发掘,通过对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作品和思想的重新诠释,提出寻根创作的新思路和创作方法。
此外,寻根文学也表达了对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丧失和忧虑,倡导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新的方向。
综上所述,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都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每一种文学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影响。
文学关注社会问题,追求真实和批判性;寻根文学回归传统文化,追求文化自信;先锋文学追求前卫和创新,挑战传统文学形式。
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元面貌,为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第十二讲+寻根文学

• 三、描绘出个体生命、种族生命以至 人类整体的生命存在之间的关系,探 索生命的起源、生存的艰难及生命存 在的方式和意义。
1、王一生的人物形象: 呆、痴、淡
庄禅的人生境界:悠闲、淡泊、宁 静、平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 传达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尤其是 道家文化的自觉认同,呈现出一种 文化的人格魅力。
2、“吃”与“下棋” ——文化命题
“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 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于其中,终 于还不太像人。”小说通过吃与下 棋来表现人物的两种追求(生存本 能和精神追求)和人生哲学,从而 达到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揭示。
“吃”——生存本能
• 寄寓着人生和社会的丰富内涵: • 写王一生对“饿”与“馋”的区别,
折射出社会历史的某些可悲侧面; • 写王一生对于“吃”的高度重视,暗
示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无论在任何 逆境之中,均不必怨天尤人,只有执 着于生存,才能有所发展
下棋——进取意识
• 从“生存”到“思想”的生命升华和大彻 大悟似的超脱:
• 韩少功《文学的“根”》:“文学有根, 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 中”。
•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化是一个 绝大的命题。”
• 郑万隆《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 的“根”》
• 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 开掘”之中,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
3、代表作家和类型
• A、对民族文化资源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 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阿城《棋 王》)
寻根文学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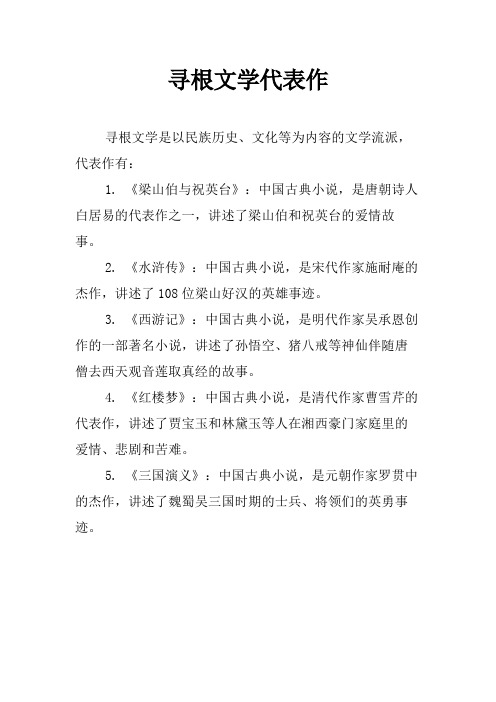
寻根文学代表作
寻根文学是以民族历史、文化等为内容的文学流派,代表作有:
1. 《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国古典小说,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故事。
2. 《水浒传》:中国古典小说,是宋代作家施耐庵的杰作,讲述了108位梁山好汉的英雄事迹。
3. 《西游记》:中国古典小说,是明代作家吴承恩创作的一部著名小说,讲述了孙悟空、猪八戒等神仙伴随唐僧去西天观音莲取真经的故事。
4. 《红楼梦》:中国古典小说,是清代作家曹雪芹的代表作,讲述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等人在湘西豪门家庭里的爱情、悲剧和苦难。
5. 《三国演义》:中国古典小说,是元朝作家罗贯中的杰作,讲述了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士兵、将领们的英勇事迹。
第六章 寻根文学

作品主旨
• 1、对健康、自然的生命、生活的赞颂。
• 作品赞美了小锡匠十一子和织席姑娘巧云 之间的发乎本性合乎自然的爱情。同时也 表现了下层穷苦人们承受苦难和反抗压迫 时的乐观、情义和坚强。
• 2、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质疑和对民间道德观 念的讴歌和向往。 • 作者从真正的下层民间生活出发,来衡量 和质疑统治阶级强加于人们的传统道德意 识,或者是知识分子新文化道德意识的合 理性,热情讴歌了真正来自民间生活的道 德立场,包括巧云接受强暴的态度、小锡 匠对待爱情的忠贞不渝、底层人们仗义反 抗压迫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3、韩少功
• 作者简介:韩少功,(1953—),笔名少功、艄 公等。湖南长沙人。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 早期 创作知青作品《月兰》、《风吹唢呐声》、《西 望茅草地》、《回声》等;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 发表《文学的根》,提出“寻根”的口号,并以 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代表作有《爸爸 爸》、《女女女》、《归去来》、《蓝盖子》等。 1986年与妹妹韩刚合作翻译出版米兰· 昆德拉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 说《马桥词典》引起各方争论。2002年发表长篇 小说《暗示》,2006年出版散文集《山南水北》 等。
《黑骏马》(1982)
• 主要内容: 《黑骏马》以流传久远的蒙古民歌 《钢嘎· 哈拉》——《黑骏马》古朴的歌词,和低 回、悲怆、激越的旋律作为小说的结构框架,叙 述了一个名叫白音宝力格的青年和蒙古草原姑娘 索米娅的爱情故事。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两人在 老奶奶额吉的养育下,一起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和 少年,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但索米娅在白音宝 力格外出学习时,被草原流氓恶棍希拉强奸并怀 孕,白音宝力格备受刺激,弃走他乡,到大城市 进了畜牧学院。
三、主要作家作品
国外寻根文学理论的研究

国外寻根文学理论的研究
寻根文学理论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文学和民族文学的理论流派,它探讨了作家在创作中寻找自身根源和文化传统的问题。
虽然寻根文学理论起源于中国,但它在国外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和研究。
在国外,学者们对寻根文学理论进行了不同的研究和评论。
他们通过对西方文学与寻根文学之间的对比和对话,扩展了对寻根文学理论的理解。
一些研究聚焦于寻根文学理论对于少数族裔文学和移民文学的应用,探讨了作家如何通过对自己文化背景的探索,拓宽了文学的边界。
此外,国外研究者还从文化认同、后殖民理论以及文学流派的角度对寻根文学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他们考察了寻根文学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总之,国外学者对于寻根文学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通过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对话,拓展了对于该理论的理解和应用。
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寻根文学理论本身,也为国际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什么是“寻根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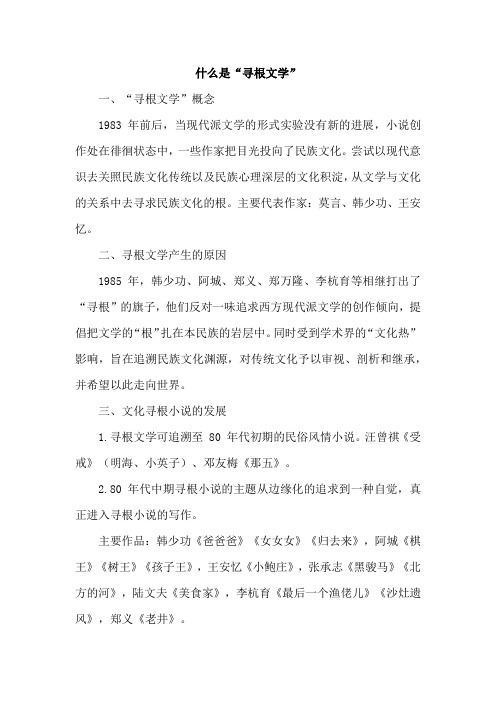
什么是“寻根文学”一、“寻根文学”概念1983 年前后,当现代派文学的形式实验没有新的进展,小说创作处在徘徊状态中,一些作家把目光投向了民族文化。
尝试以现代意识去关照民族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心理深层的文化积淀,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中去寻求民族文化的根。
主要代表作家:莫言、韩少功、王安忆。
二、寻根文学产生的原因1985 年,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相继打出了“寻根”的旗子,他们反对一味追求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倾向,提倡把文学的“根”扎在本民族的岩层中。
同时受到学术界的“文化热”影响,旨在追溯民族文化渊源,对传统文化予以审视、剖析和继承,并希望以此走向世界。
三、文化寻根小说的发展1.寻根文学可追溯至 80 年代初期的民俗风情小说。
汪曾祺《受戒》(明海、小英子)、邓友梅《那五》。
2.80 年代中期寻根小说的主题从边缘化的追求到一种自觉,真正进入寻根小说的写作。
主要作品:韩少功《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王安忆《小鲍庄》,张承志《黑骏马》《北方的河》,陆文夫《美食家》,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郑义《老井》。
3.1987 年左右是文化寻根思潮转型和终结的时期。
以莫言《红高粱》、张炜《古船》为标志。
四、寻根文学的显著特点1.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
2.具有现代意识。
以现代意识关注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
3.创作手法上传统和现代相融合。
五、文化寻根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1.文化批判型。
对传统文化持审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
2.文化认同型。
对传统文化持一种理解、认同、肯定的态度。
阿城《棋王》,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郑义《老井》。
3.原始生命型。
莫言《红高粱》、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如《老棒子酒馆》、扎西达娃《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六、寻根小说的历史变革作用1.它导致了小说由以往所关注的社会领域向文化领域的变革,使小说由当代社会生活的仆从成为广阔的文化与人性领域的探索者。
寻根文学

主要经历 十六岁时父亲因历史问题被 捕(父亲毕业于哈佛商学院, 与张学良等有过从), 十八岁时因父亲问题被学校开除,二十岁因发表 诗歌《大风歌》成为“右派”,后来“以书写反 动笔记的罪名被叛三年管制,在社教劳动中,又 以‘右派翻案’的罪名被叛三年劳教,劳教期间 回到农场,正遇上‘文化大革命’,我升级为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群专起来。1970年, 我被投进农场私设的监狱”,1979年平反,时年 四十三岁。1992年9月22日抵押全部资产在贺兰山 下镇北堡建立影视城。
代表作家作品
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 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 日郎》、《西藏》、《敦煌》和稍后模拟《易经》思维结 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等,这些作品或者在对历 史遗迹的吟赞中探询历史的深层内涵,或者借用民俗题材 歌颂远古文明的生命力,或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想象来构 筑人生和宇宙融为一体的理念世界。在小说领域里,则是 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年到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 说,虽然作家不过是描写了个人的一段生活经历,但其对 新疆各族民风以及伊斯兰文化的关注,对生活的实录手法 以及对历史所持的宽容态度,都为后来的寻根文学开了先 河。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 《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 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 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 一文学潮流的主体。主要作品如汪曾祺的《受戒》、邓友 梅的《那五》,
产生的原因
1)、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直 接反映。 2)、世界文学“寻根”潮流的影响。
前苏联一些民族作家(如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等) 对异族民风的描写、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如马尔克斯、 阿斯图里亚思等)关于印第安古老文化的阐扬以及日本川 端康成的具有东方风味的现代小说,对中国年轻一代作家 是深有启发的。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在表现出浓厚的民族 文化特征和民族审美方式同时,又分明渗透了现代意识的 精神,既富有民族文化独特性,又融合了现代感的创作倾 向,为主张“文化寻根”的中国作家提供了现成的经验和 有效的鼓励。
寻根文学

产生的原因
1)、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直 接反映。 2)、世界文学“寻根”潮流的影响。
前苏联一些民族作家(如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等) 对异族民风的描写、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如马尔克斯、 阿斯图里亚思等)关于印第安古老文化的阐扬以及日本川 端康成的具有东方风味的现代小说,对中国年轻一代作家 是深有启发的。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在表现出浓厚的民族 文化特征和民族审美方式同时,又分明渗透了现代意识的 精神,既富有民族文化独特性,又融合了现代感的创作倾 向,为主张“文化寻根”的中国作家提供了现成的经验和 有效的鼓励。
郑义的《远村》、《老井》,韩少功的《爸爸
爸》、《女女女》,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王 安忆的《小鲍庄》,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 的魂》,以至于张承志、史铁生、陆文夫、邓友 梅、冯骥才等的一些小说。在这期间,有的批评 文章不限于“文学寻根”这一用以说明潮流的说 法,而使用“寻根文学”(“寻根小说”)、“寻根 作家”的概念。但是,被指认的作家作品的面貌 是否可以这样概括?而作家本人也大多不能认可这 一归类,因而,“寻根文学”和“寻根作家”的 说法并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 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
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他的小说《黑骏马》、 《北方的河》、《残月》、《九座宫殿》等,描 绘北方的草原、戈壁、雪峰、江河,吟唱着古老 的民族歌谣,刻画出彩陶碎片的美丽、清真寺的 庄严……,在他笔下那种富有生命激情的人生境 界中,民族文化精神与大自然的博大宽广、北方 游牧民族的狞厉粗放的生存状态融化在一起,使 人感悟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强大 的人格力量。 三、文化批判型: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 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 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
关于寻根文学的文化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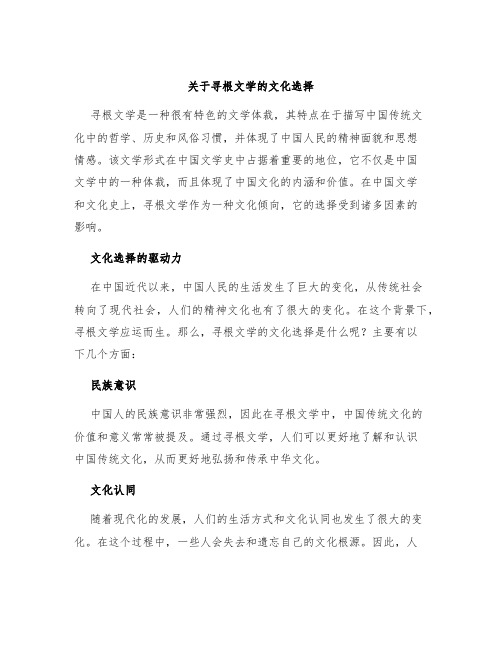
关于寻根文学的文化选择寻根文学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文学体裁,其特点在于描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历史和风俗习惯,并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情感。
该文学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中国文学中的一种体裁,而且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寻根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倾向,它的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文化选择的驱动力在中国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传统社会转向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个背景下,寻根文学应运而生。
那么,寻根文学的文化选择是什么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民族意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非常强烈,因此在寻根文学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常常被提及。
通过寻根文学,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更好地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
文化认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会失去和遗忘自己的文化根源。
因此,人们需要通过寻根文学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和认同感。
在这个过程中,寻根文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文化传承寻根文学是中华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描写中华文化、中华传统美德等文化元素,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从而更好地实现文化传承。
并且,通过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可以不断地强化中国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文化选择的策略由于文化选择有多重影响因素,因此确定寻根文学的文化选择需要下一些策略。
多元选择在寻根文学的文化选择方面,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方面或一个文化元素,而需要多元化选择。
这样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寻根文学所体现的文化价值和内涵。
清晰的价值观在确定寻根文学的文化选择时,需要清晰的价值观来进行指导。
这样可以更好地把握寻根文学的创作方向,使其更符合中华文化和中国人民的价值观。
明确读者群体寻根文学需要具有在特定读者群体中传播的能力,因此在制定寻根文学文化选择方案时,需要明确自己的读者群体。
这样可以更好地把握读者的需求和期望,使其更具吸引力和传播力。
探析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寻根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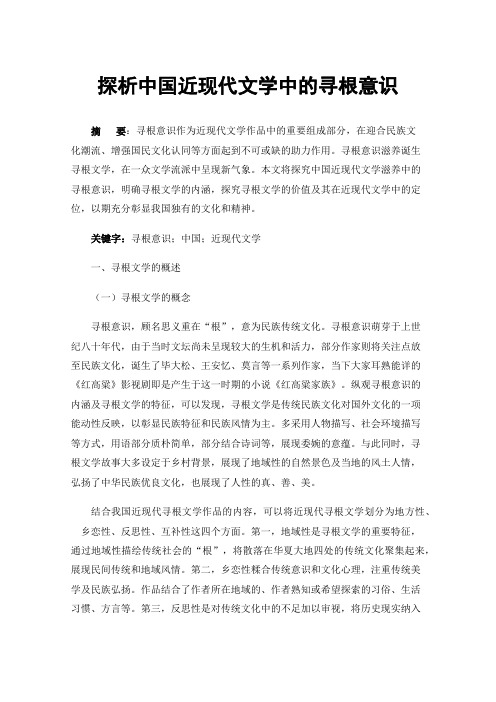
探析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寻根意识摘要:寻根意识作为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迎合民族文化潮流、增强国民文化认同等方面起到不可或缺的助力作用。
寻根意识滋养诞生寻根文学,在一众文学流派中呈现新气象。
本文将探究中国近现代文学滋养中的寻根意识,明确寻根文学的内涵,探究寻根文学的价值及其在近现代文学中的定位,以期充分彰显我国独有的文化和精神。
关键字:寻根意识;中国;近现代文学一、寻根文学的概述(一)寻根文学的概念寻根意识,顾名思义重在“根”,意为民族传统文化。
寻根意识萌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当时文坛尚未呈现较大的生机和活力,部分作家则将关注点放至民族文化,诞生了毕大松、王安忆、莫言等一系列作家,当下大家耳熟能详的《红高粱》影视剧即是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小说《红高粱家族》。
纵观寻根意识的内涵及寻根文学的特征,可以发现,寻根文学是传统民族文化对国外文化的一项能动性反映,以彰显民族特征和民族风情为主。
多采用人物描写、社会环境描写等方式,用语部分质朴简单,部分结合诗词等,展现委婉的意蕴。
与此同时,寻根文学故事大多设定于乡村背景,展现了地域性的自然景色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弘扬了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也展现了人性的真、善、美。
结合我国近现代寻根文学作品的内容,可以将近现代寻根文学划分为地方性、 乡恋性、反思性、互补性这四个方面。
第一,地域性是寻根文学的重要特征,通过地域性描绘传统社会的“根”,将散落在华夏大地四处的传统文化聚集起来,展现民间传统和地域风情。
第二,乡恋性糅合传统意识和文化心理,注重传统美学及民族弘扬。
作品结合了作者所在地域的、作者熟知或希望探索的习俗、生活习惯、方言等。
第三,反思性是对传统文化中的不足加以审视,将历史现实纳入现代视角加以评判,思考传统意识和文化是否存在有待改进之处。
第四,互补性没有明确范畴,该类寻根文学大多结合多样化的类型文学。
(二)寻根文学的价值寻根文学结合地域特色,彰显对现实问题或人性议题的反思,寄托作者希望表达的事物或主题。
从莫言《红高粱》看“寻根文学”

从莫言《红高粱》看“寻根文学”从莫言《红高粱》看“寻根文学”80年代中后期,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寻根文学悄然出现,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这批作家的典型代表就是韩少功,他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
"“寻根文学”当中的乡野文化寻根是其典型的流派,如汪曾祺表现"桃花源"式的传统生活的《大淖记事》、张承志表现蒙古草原人民生活的《黑骏马》、路遥关于城乡交叉地带的描写、莫言关于高密东北乡自己祖辈的生活秘史的讲述,如《红高粱》系列作品。
对我感触最深的当属《红高粱》,就以《红高粱》举例,在分析其人物形象和民族内涵同时,同时结合作者人物性格背景,谈谈我自己的感受。
莫言曾经说过:“这时我是强烈地感受到,20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虽然我身处闹市,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灵魂寄托在故乡的回忆里,失去的时间突然又以充满声色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认为,这段话不是简单的空谈,而是他对乡村灵魂的把握,对乡村自我精神的抒发。
在人物形象方面,《红高粱》在人物塑造上竭力表现民间状态的草莽英雄,抛弃了沉重的意识形态内容,这样就使人物变得鲜活生动,充满人性张力。
例如,文中“我爷爷”余占鳌在开篇一出场便显示了土匪头子兼抗日英雄的双重身份,“杀人越货”又除暴安良,作者始终让人物停留在未曾雕琢过的原始的农民心理上。
而奶奶戴凤莲的形象更是突破了中国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造型,热情果敢,充满情欲野性,可求人性自由与本能的满足。
在追求的过程中反抗传统封建礼教,张扬具有反抗色彩的生命意识。
在细节描写上,高粱地里火焰般的野合,一手掌管烧酒坊的魄力以及奔向天国之际的那段生命的宣誓,桩桩件件都是浓烈感人,激情奔放。
第六章 寻根文学剖析

三、主要作家作品
主要作品有: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 河》、李杭育的表现吴越文化的“葛川江小说” 系列、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 《孩子王》)、《遍地风流》、韩少功的《爸爸 爸》、《女女女》等、郑万隆的《异乡异闻》、 郑义的《远村》、《老井》、王安忆的《小鲍 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莫言的“红高粱 系列”、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 魂》、《西藏:隐秘岁月》、东北鄂温克族作家 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 火》等。
Hale Waihona Puke 品主旨• 1、对健康、自然的生命、生活的赞颂。 • 作品赞美了小锡匠十一子和织席姑娘巧云
之间的发乎本性合乎自然的爱情。同时也 表现了下层穷苦人们承受苦难和反抗压迫 时的乐观、情义和坚强。
• 2、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质疑和对民间道德观 念的讴歌和向往。
• 作者从真正的下层民间生活出发,来衡量 和质疑统治阶级强加于人们的传统道德意 识,或者是知识分子新文化道德意识的合 理性,热情讴歌了真正来自民间生活的道 德立场,包括巧云接受强暴的态度、小锡 匠对待爱情的忠贞不渝、底层人们仗义反 抗压迫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作品主题
• 这部作品表面上写的是明海和小英子之间 的纯真之爱,但真正内容却是作者以诗一 般的语言,写出了一个“桃花源”式的世 俗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恬静优美,风俗 淳厚;生活在里面的人,率性本真,自然 纯朴,充溢着田园诗趣和生命欢乐。作者 由衷地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向往与热爱, 从而表明了汪曾祺的人生态度,寄托了他 的生活理想。
第六章 寻根文学
一、寻根文学概念
• 寻根文学是1985年正式出现的一个文学思 潮。一些年轻的知青作家希望通过对民族 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再审视,来为当时陷于 困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开辟新路。
寻根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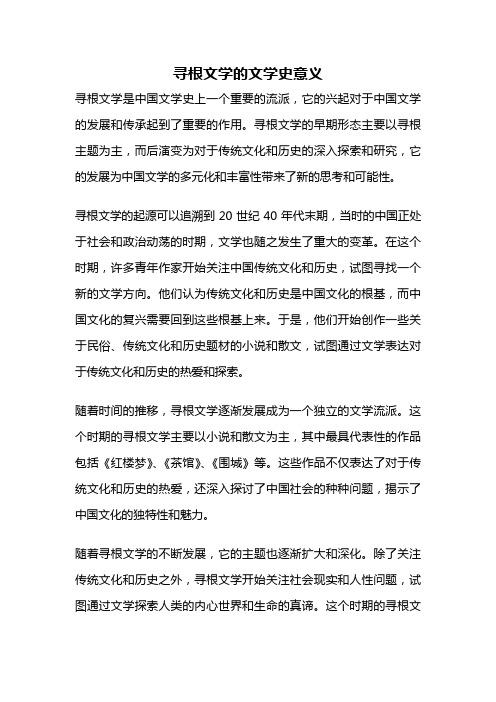
寻根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寻根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它的兴起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寻根文学的早期形态主要以寻根主题为主,而后演变为对于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深入探索和研究,它的发展为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和丰富性带来了新的思考和可能性。
寻根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期,文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在这个时期,许多青年作家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试图寻找一个新的文学方向。
他们认为传统文化和历史是中国文化的根基,而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回到这些根基上来。
于是,他们开始创作一些关于民俗、传统文化和历史题材的小说和散文,试图通过文学表达对于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热爱和探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根文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流派。
这个时期的寻根文学主要以小说和散文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红楼梦》、《茶馆》、《围城》等。
这些作品不仅表达了对于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热爱,还深入探讨了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
随着寻根文学的不断发展,它的主题也逐渐扩大和深化。
除了关注传统文化和历史之外,寻根文学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性问题,试图通过文学探索人类的内心世界和生命的真谛。
这个时期的寻根文学作品涉及面更加广泛,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鲁迅的《阿Q正传》、贾平凹的《废都》、余华的《活着》等。
寻根文学的兴起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它重新审视了传统文化和历史,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它也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和人性的种种问题,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
同时,寻根文学的多元化和丰富性也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动力。
寻根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它的兴起和发展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寻根文学通过对于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深入探索和研究,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的局限
文学摆脱了作为政治工具的命运,又担当起了文 化工具的使命,并陷入“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 模式。
不少作家对“文化”的理解是以偏概全的,对 “民族”的理解也是狭隘的。
一些作家缺乏理性批判精神,一味好古泥俗嗜怪 爱丑,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缺乏应有的理性思 辩态度。
寻,在1984年首次发表文学作品,处女作就是被誉为 “寻根文学”扛鼎之作的中篇小说《棋王》。这部作品和阿城随后一气写下 的《孩子王》、《树王》皆取材于他本人亲历的知青生活,但无论在主题意 旨还是表现形式上都与通常的知青小说有很大不同。阿城无意去描绘一种悲 剧性的历史遭遇和个人经验,也避免了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风 格模式,他在日常化的平和叙说中,传达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 《棋王》的主要魅力来自于主人公王一生。这是一个在历史旋涡中具有独 立生活方式和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他的整个人格中投射着久远的、富有无限 生机的文化精神,这使他虽以一己的单薄存在,却显现出了无可比拟的顽强 精神和文化魅力。小说中写王一生天性柔弱,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 中,像他这种小人物好比狂风中的沙粒,要在不能自主的命运中获得意义和 价值,唯一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内心,寻求自身精神的平衡和充实。小说从知 青离城的送别写起,首先就以“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之句来映衬王一生独 坐一旁的内心宁静,而后通过写他对于“吃”的高度重视,暗示了对生命价 值的尊重,在他那种处世不惊、怡然自得的性格刻画中,已经悄悄拉开了这 个人物与时代规范下的知青形象的距离,成为知青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 典型。
寻根作家对“根”的态度
一是持肯定态度,如阿城《棋王》(肯定道家学说)、 邓友梅《烟壶》《那五》(肯定传统文化的拯救力量) 等。
二是持否定态度,如韩少功《爸爸爸》(丙崽)、王 安忆《小鲍庄》(捞渣的死为他的家乡与家人换得利 益:家乡受表彰,鲍仁文成名,其兄弟进厂)。 三是持历史主义态度,如冯骥才《神鞭》(对传统文 化辩证看待)。
寻根小说

六.寻根小说的历史变革作用
局限: 对于“根”的理解的静止性和非历史性,导 致了一些作家一味的沉迷于古、俗、粗、野 之中,表现出贵远贱近、向虚背实的倾向。
80年代小说
寻根小说
三.文化寻根小说的发展
3.1987年左右是文化寻根思潮转型和终结的时 期。以莫言《红高粱》、张炜《古船》为标 志。
四.寻根文学的显著特点
(1)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 风俗意识。 (2)具有现代意识。以现代意 识关注历史,反思传统文化, 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 化重建的可能性。
(3)创作手法上传统和现代相 融合。
五.文化寻根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3)原始生命型。
莫言《红高粱》--- 对祖辈豪爽自 由生命力的张扬。
余占鳌和戴凤莲 : 高密东北乡人高粱 1)它导致了小说由以往所关注的社会领 域向文化领域的变革,使小说由当代社会 生活的仆从成为广阔的文化与人性领域的 探索者。 (2)在小说的艺术层面上,寻根运动使小 说摆脱了一个遵照生活逻辑与客观时空逻 辑进行写作的时代,也摆脱了一个社会政 治的话语时代,而开启了超验的和“虚构” 的时代。
二.寻根文学产生的原因
(1)从社会历史原因来看,国门敞开后, 导致了中西方文化的大碰撞、大融汇,思 想艺术界再次掀起了文化大讨论的热潮。
(2)从文学自身演变发展来说,这又是一 次文学寻找自我的浪潮。 一是寻找民族文学之根 二是寻找作家的个性自我
三.文化寻根小说的发展
1.寻根文学可追溯至80年代 初期的民俗风情小说。汪曾 祺《受戒》(明海、小英 子)、邓友梅《那五》。 2.80年代中期寻根小说的主 题从边缘化的追求到一种自 觉,真正进入寻根小说的写 作。
寻根文学及代表作家

❖ 鸡头寨人自称是刑天的后代。为了生存, 他 们的祖先从东方的海边迁徙而来。他们的 历史悠久。他们以宗亲为纽带, 以祠堂为社 会组织形式。沿着他们祖先的耕作习惯, “一年一道犁, 不开水圳也不铲倒不堪力 ” 地靠农业为生。他们的生命是顺其自然的。 他们没有宗教信仰, 最敬仰他们的祖宗神灵, 迷信自然界中的鬼神。小说以峻冷的笔调 通过对鸡头寨人的风俗、习惯、乡规、土 语、迷信、传说、历史、信仰、祭祀、服 饰、食品以及其他生存状态的描述, 描绘出 鸡头寨人的文化概貌。
❖ 文学寻根的目的就是为了深刻地揭示我们 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状态, “从而使人们看 到我们民族(文化)的优根和劣根, 看到我 们民族所赖以生存的精神品性和背上的因 袭的精神重担” 。这大概就是韩少功等寻 根作家努力探寻的民族文化的一种劣根。
❖ 深山老林使鸡头寨与世隔绝。在这里一个 玻璃瓶子, 一盏破马灯, 一条能长能短的松 紧带, 一张旧报纸或一张小照片, 一双皮鞋 都是那么新鲜的玩意儿。这些“玩意儿” 还能使仁宝这个后生“更有新派人物的气 象”, 使他的身份和身价与众不同。但大自 然给人生存条件是造成鸡头寨人贫困、愚 昧、落后的外在原因。
❖ 素的思考。”——樊篱
❖ 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个遥远不知所在的山寨" 鸡头寨"及其自称刑天后裔的居民们蒙昧而
充满神秘色彩的生存状态。小说以一个痴 呆儿"丙崽"为中心人物, 描述鸡头寨奇异的 风俗、来历, 鸡头寨百姓与正常世界的隔绝, 他们与鸡尾寨的"打冤"及战败后遗弃老人和 孩子举族迁徙的经过。
❖ 生存环境:
❖ 祠堂是这群人的文化核心。祠堂不仅凝聚着他们祖先的神 灵, 而且还象征着他们祖先的信念, 象征着类似今天法律的 他们族规的威严。这里深藏着他们族人文化的根。所以, 祭祀、占卜吉凶、打冤盟誓、重大的部落集会等都在祠堂 举行。
寻根文学 (1)

60—80年代,拉丁美洲出现了好几位诺贝尔文学得主。
拉丁美洲文学的巨大成功,大大启发和刺激了中国作家。 《百年孤独》 加西亚·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拉美文学的成功,直接震惊了中国的年青作家们。 (1)经济强国有文化优势。 拉丁美洲经济、政治与中国差不多,居然也出现好几位 诺贝尔奖得主。
(2)作品内容和创作特点让人震惊。
村寨不知来自何处。有的说来自陕西,有的说来自广东,说 不太清楚。
如果塞里有红白喜事,或是逢年过节,那么照规矩,大家 就得唱“简”,即唱古,唱死去的人。从父亲唱到祖父, 从祖父唱到曾祖父,一直唱到姜凉。姜凉是我们的祖先, 但姜凉没有府方生得早,府方又没有火牛生得早,火牛又 没有优耐生得早。优耐是他爹妈生的,谁生下优耐他爹呢? 那就是刑天——也许就是陶潜诗中那个“猛志固常在”的 刑天吧。
他生下来时,闭着眼睛睡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一个死人相,把亲人 们吓坏了,直到第三天才哇地哭出一声来。能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时候, 就被寨子里的人逗来逗去,学着怎样做人。很快学会了两句话,一是 “爸爸”,二是“X妈妈”。后一句粗野,但出自儿童,并无实在意 义,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符号,比方当作“X吗吗”也是可以的。 三、五年过去了,七、八年也过去了,他还是只能说这两句话,而且 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很大,象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以 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吃炮了的时候,他嘴角沾着一两颗残 饭,胸前油水光光的一片,摇摇晃晃地四处访问,见人不分男女老幼, 亲切地喊一声“爸爸”。要是你冲他瞪一眼,他也懂,朝你头顶上的 某个位置眼皮一轮,翻上一个慢腾腾的白眼,咕噜一声“X吗吗”, 调头颠颠地跑开去。他轮眼皮是很费力的,似乎要靠胸腹和颈脖的充 分准备,才能翻上一个白眼。调头也很费力,软软的颈脖上,脑袋象 个胡椒碾捶晃来晃去,须沿着一个大大的弧度,才能成功地把头稳稳 地旋过去。跑起来更费力,深一脚浅一脚找不到重心,靠头和上身尽 量前倾才能划开步子,目光扛着眉毛尽量往上顶,才能看清方向。
文化寻根文学名词解释

文化寻根文学名词解释
文化寻根是指通过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的研究和传承,挖掘和弘扬本民族文化精髓,培育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和认同。
文学是文化寻根中的重要领域,它可以通过创作和研究传统文学,描绘民族历史,反映社会生活,塑造民族精神。
常见的文学名词如下:
1.传统文学:民间流传的经典文学作品,如唐诗宋词、民间传说等。
2.现代文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西方文学思潮传入中国,国人开始进行现代文学创作。
3.文化遗产:指被誉为民族文化瑰宝、历史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物品。
4.民族精神:是指一种集体心理,对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等认同感和民族意识。
5.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分析、解读的过程。
6.文艺复兴:源于意大利文艺浪漫主义运动,指文化艺术领域的大规模创新和变革。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寻根文学、文化保守主义与山野精神摘要:寻根文学与文化保守主义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思维方式上,它们都主张向传统复归,认同民间文化;致思途径上,都采取“向后看”的视角,礼赞农业文明的闲适和平和,批判现代文明的喧嚣和躁动。
正因为此,我们在寻根文学中不仅能看到自然山水的影姿,也能感受到作家回归大地、融入山野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寻根文学;文化保守主义;山野精神一寻根文学与文化保守主义新时期之初,文学密切关注社会,参与思想解放,较之“现实”来说,“传统”还处于一种边缘的状态。
“反传统”和“现代化”互为表里,共同将启蒙这个“五四”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话题推到了文学思潮的中心地带。
人们大多以一种向前看的眼光憧憬着未来,想象着现代化带来的舒适与便利。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作家在对现代化表示由衷赞赏的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前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化既具体又实在,但面对现代化已经显露出来的理性膨胀和人性危机,又对此产生一种警惕、排斥心态。
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的语境下,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人举起“寻根文学”大旗,批判技术理性,缅怀农业文明宁静、平和的生活方式,试图在乡土、山野中寻找一种精神安慰。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急需现代化的国家,寻根作家更多的是理性上主张现代化,情感上依恋传统,不与现代化正面冲突,而是以一种审美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情感,寄托他们的理想。
寻根作家的复杂心态可以从罗兰·巴特那里得到说明。
生活在高度现代化、工业化的巴黎,呼吸着后现代气息的罗兰·巴特说,他很向往这样一种写作氛围———“在远离城市的村庄,在听不到城市一切喧嚣的地方,在昏暗的油灯下,让神思在心灵与宇宙之间自由地穿梭”。
其实,从韩少功、阿城、郑义等人把传统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来开掘并希图从中寻求一种价值支撑之时起,寻根文学就与国内正在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不期而遇,并迅速达成默契。
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向“传统”复归,在过去与当下的比较中礼赞过去牧歌式的理想生活。
寻根作家认为“规范文化”之根大都已经枯死,文学之根应深植在那些未受现代文明熏染的远村、山寨里,这些“不规范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
从李杭育对“最后一个渔佬儿”充满深情的抒写来看,他在为吴越民间文化吟唱挽歌的同时,情感的天平明显偏向以天人和谐为生存准则的农业文明。
《沙灶遗风》、《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的主人公施耀鑫、福奎对现代文明的看法可谓典型,“照着钟点上班下班,螺蛳壳里做道场。
哪比得上打鱼自由自在。
”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传统农业文明保持了固有的自信与镇定。
然而,自信与镇定的同时,李杭育也表现出不安与彷徨,施耀鑫平静地躺在床上,让自家的小洋楼立了起来,福奎也不无羡慕地看着对岸的灯光,不由自主地慨叹城里那帮照着钟点干活的孱头还真有点能耐”。
不过,短暂的认同过后,施耀鑫虽承认小洋楼既时髦又实惠,临走之前仍不忘朝它吐一口唾沫,福奎则更顽固,即使穷得连裤头也要从相好那里拿,仍坚持打渔持家的生活方式。
就这样,小说始终笼罩在一种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氛围中。
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分析日尔曼及东欧的文化保守主义时说:“日尔曼及东欧的反现代化思想家一致地认为中古时代为社会理想状态的范式,也一致地仇视于社会实际所朝向的改变方向———布尔乔亚文化。
就在其运用中古与乡民社会为社会至善的试金石这一点上,我首次见出将反现代化者对现代化反应的性质在概念上加以体系化的方式。
”[1]91与日尔曼及东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将“中古时代”作为社会理想典范一样,寻根作家在作品中也有意无意地将传统不规范文化及乡土社会加以美化,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没有对社会变革持“仇视”态度,而是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怀旧与惆怅情绪。
寻根作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韩少功,在其寻根宣言《文学的根》中曾信誓旦旦地提议:“释放现代观念的热情,来自铸和镀亮民族自我”。
在《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中又说,“东方文化自然有很落后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
要对地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
”这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论颇有相似之处。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的是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说明现代文化中的许多理念在传统中早已包含,现代化不过是传统的“转化”而已。
当韩少功带着“重造”传统的寻根理想进行创作时,却遇到了寻根文学的一个“死结”:传统之“根”并非想象中美好,在现代文明的烛照下,传统根系甚至是很丑陋、很猥琐。
既然传统之根已经腐朽,“重造”、“镀亮”初衷就失去了价值依托。
于是,韩少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境地,《爸爸爸》中,无论是作为“原始楚文化”传承人的丙崽,还是作为“现代文明”代表人的仁宝,都令人极度失望。
在韩少功笔下,丙崽成了一个怪物,有人称其为“封建原始愚昧生活方式的象征”,有人称其为“民族劣根性的活化石”。
在这样一个被鸡头寨人奉为神明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愚昧、蛮荒、保守、僵化,全然没有楚文化的自强不息、古道热肠。
另一个反对保守、倡导维新,“穿皮鞋壳子”、“行帽檐礼”的走出鸡头寨见过世面的人物———仁宝,也不过是一个淫邪、浮浪、怯弱、卑劣的无赖之徒,他虽然打破了鸡头寨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固执封闭、陈旧保守,却又陷入更为人们不齿的贪婪淫恶、矫饰浮浪。
可以说,丙崽式的传统文化不能给人们带来希望,仁宝式的现代文明也不能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
接下来的《女女女》中,韩少功延续了这一困惑,一生勤俭助人克己奉公的幺姑,到了晚年突然变得自私贪婪,就连她的身体也在萎缩颓败下去,将要变成一条鱼,幺姑的蜕变似乎在向人们昭示:人类正在向原始形态的复归。
联系韩少功在一篇题为《海念》的散文里的一段话,“人是从海里爬上岸的鱼,迟早应该回到海里去。
”我们可以将幺姑的“返祖归鱼”行为看作是现代人类对理想社会的一次“想象”———既然未来让人们看不见拯救希望,不如去集体缅怀过去的传统文明。
显然,《女女女》中,韩少功的精神困惑消除了不少,虚无的情绪有所节制,但文化保守主义气息却渐趋浓厚。
在他后来的一系列随笔、散文中,这种向传统复归的保守主义倾向愈加直白,他赞同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论断,“西方文明已经衰落,古老沉睡的东方文明有可能在外来文明的挑战下隐而复出,光照整个地球”;他推崇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认为他们都是以“东方文化传统为依托”,尽管发表了一些反现代化的言论,颇有落伍者之嫌,“却仍然是日本精神现代化的一部分,是现代日本国民的骄傲”。
从汤因比到川端康成、东山魁夷,韩少功一再表现出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赞美20世纪30年代,作家沈从文多次表白自己是“乡下人”,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乡下人”,他带着一种文化守成心态,创作了《边城》、《月下小景》等原野牧歌式作品。
无独有偶,同为湖南老乡的韩少功也喜欢说:“我是个乡下人”。
在他看来,乡村才是生命之所在,是文学根系发达的地方,他甚至还不无偏见地说,乡村才是丰富多彩的,都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多少有点缺乏个性”,如果说乡村是天然杂陈、人文荟萃的渊薮,那么城市是什么呢?他不无调侃地说:“那只是从太阳那金灿灿的肛门里排出的一堆晒出硬壳的粪便。
”[2]较之韩少功小说价值观念的模糊游弋,他散文的保守主义情绪表现得更为直接和外露。
二寻根文学与山野精神除了价值标准的趋同之外,寻根文学与文化保守主义在对“民间”的认同上也是一拍即合,它们都认为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下,传统文明几乎丧失殆尽,遗留下来的部分也主要保存民间。
现代文明是钢筋、水泥、混凝土……传统文明则是俚语、笑料、性爱方式、风俗习惯……要追寻传统,民间是一个不应忽视也不容忽视的资源宝库。
寻根作家李杭育在把文化截然二分为范与不规范之后,公然指出“规范文化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他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
就具体的创作文本来看,贾平凹之于商州文化,韩少功之于湘楚文化,莫言之于高密文化,张炜之于胶东文化,张承志之于伊斯兰教文化,郑义之于晋文化……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地域文化的眷恋。
谈及“红高粱系列”,莫言在创作谈中曾说:“小说就是带着淡淡的忧愁寻找自己失落的家园。
”在致张志忠的信里他又解释说,“所谓小说带着淡淡的乡愁寻找失落的家园或精神故乡之说,并不是我的发明,好像一个哲学家说哲学如是。
我不过挺受感触,便移植过来了,此种说法貌似深刻,但含义其实十分模糊。
说穿了,文学是一种情绪,一种忧伤的情绪,向过去看,到童年里去寻找……”莫言以一种忧伤的情绪向过去看,向高密东北乡这片长满高粱的土地寻觅,在莫言的笔下,乡民的强悍、民风的朴实、高粱地的殷红、“我爷爷”、“我奶奶”的自由不拘等这些原初文化跃然纸上。
可以这样说,对生命强力的追寻,对乡民自然本性的描写,是莫言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民间”追求,艾恺说:“对乡村社会、乡民和中世纪(常常包括宗教在内)等的加以提升和歌颂,在浪漫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几乎是无处不见的主题。
”[1]91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乡村社会因为其偏远落后,反倒能更多地保留一种原始、纯真的文化生态,因而对于乡村社会、农业文明的歌颂往往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心话题。
在寻根作家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中,我们看到,大地、田园是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诗性意象,大地、田园等民间质素在小说中交互出现,成为其精神世界的强大支持。
张炜曾说,“对于我们而言,山脉土地是万年不曾更移的背景,我们正被一种永恒所衬托。
”“世界上究竟有哪里可以与土地比拟?这里处于大地的中央,这里与母亲心理上的距离最近。
在这里,你尽可以诉说昨日的流浪……同样只是大地母亲平等照料的孩子,饮用同样的乳汁,散发着相似的奶腥。
”[3]张炜于1992年推出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有关“大地”的诗篇。
小村里发生的故事是大地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是大地上的人物。
当小村的人们从“传说”中走来并落脚于此地时,他们就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土地上生长出的地瓜,成为村民们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主食,村民的劳作与喘息、奔跑与停止所寻求的就是“地瓜”对于人们的滋养。
年轻人被地瓜激起的力量无处发泄,便在夜晚的街道和田野里自由自在地奔跑、嬉戏,结婚的男人和女人便在黑夜的炕上无休止地撕咬,痛苦与兴奋使他们精神饱满。
正是如此,夜晚的大地神秘而优美,有着一种奇特的美,令人激动,让人痴迷。
小说中,大量类似“昏沉沉的大地啊,铅一样的大地啊,像吃了长睡不醒的药一样的大地啊”这样的排比句式将山野诗意渲染得浓郁而美妙。
大地不仅供给村民们衣食住房,而且与他们交互感应,提供庇护和福祗。
“那个秋天,红色的地瓜一堆堆掘出,摆在泥土上,谁都能看出它们像熊熊燃着的炭火。
人们像要熔化成一条火烫的河流,冲撞涤荡到很远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