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理论分析沟通规划与场所塑造
新制度主义理论观点评析-2019年精选文档

新制度主义理论观点评析在政治学领域,正迅速兴起的新制度主义是相对于旧制度主义而言的,其首要关注的问题是制度的概念、性质以及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和塑造。
即在界定制度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制度是如何构成个人行为,如何在行动者之间分配权力,及如何塑造个人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
由于关于制度的广泛性的内涵而使新制度主义学者认为,新制度主义不仅涉及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而且触及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多方面,甚至可以用之解释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和行为。
目前,新制度主义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这不禁使我们要追根问源,新制度主义源何兴起?一、新制度主义的渊源制度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政治学研究对象发生了重大转变。
受科学主义和量化分析的影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主流理论,制度研究被排除在外。
在研究对象上,行为主义以政治行为和行为互动代替传统的政策和制度;在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借助于各种科学技术手段,采用量化和实证分析来研究政治现象;在研究起点上,行为主义采取的是个人主义,认为个体的真正偏好只有通过一定的行为才能具体地表现出来,而集体现象是个体行为的聚集,个人的偏好只有通过利益聚集机制才能带来最佳的效果。
然而,到了70年代,世界环境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西方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它经济学派诸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纷纷借机登场,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
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并且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
正是经济学家这种向政治领域的挺进,引起了政治学界对于制度研究的重新关注。
尤其是在美国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越南战争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上,行为主义无法对其加以理论解释,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理论家的反思和批判,并产生了变革现代政治学的要求,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新制度主义。
制度主义名词解释

制度主义名词解释
制度主义指由凡伯伦和康芒斯等人在20世纪早期倡导的一种政治学流派,认为个人的社会行为、获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本身的产物,但面对制度性的约束因素,社会成员也不是完全被动的。
它会在制度范围内或某些制度边缘,采用某些非正式的运作手段来获取社会资源的一种政治学流派。
在制度主义中,影响较大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规范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既是当代西方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也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的一个重要流派。
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继承和改造了政治科学中的旧制度主义,而且还在对行为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承接了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分析视角,同时吸纳了历史社会学的有关理论资源。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
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通过新范式的建立而架起了政治科学各分支的沟通桥梁,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新空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
行为主义是美国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对西方心理学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
行为主义的发展可以被区分为早期行为主义,新行为主义和新的新行为主义。
早期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以华生为首,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则为斯金纳等,新的新行为主义则以班杜拉为代表。
制度分析模型

制度分析模型(P318)界定:康芒斯: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为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标准。
科斯:制度就是指一系列关于产权安排、调整的规则,制度就是“规则”或组织形式。
诺斯: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和本人效益最大化中的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
1、旧制度主义:旧制度主义关注的更多的是制度的属性,以及制度如何使个人的行为变得更好。
主旨和目标:如何使个人行为朝向有利于集体目标的方向。
重点:制度的规范性导向,以及制度对社会的影响。
诟病所在:旧制度主义的目标是规范性的,它致力于在限定的政治系统中追求好的制度,相当程度上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其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形成,它侧重于对立法、行政、司法等制度和机构进行相对机械的研究。
评价:旧制度主义更多的是以国家为导向,侧重于对宏观层面的制度进行研究,对运作中的制度及其操作规则缺乏一种动态的视觉进行考察,抹杀了个人行为和人类活动的能动性。
2、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制度沿用旧制度主义的一些假设,但在研究工具和理论关注上吸收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分析的要素,从而丰富了旧制度主义的研究内涵。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制度主义中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倾向。
新制度主义着力对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进行探讨,把制度当成一个变量,并着重探讨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是如何的不同。
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区分了操作、集体选择与立宪选择三个相互作用的层次或领域。
多制度的中心安排:主张让大、中、小幅规模的政府和非政府的企业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
新制度主义事实上是旧制度主义与理性主义、行为主义互相影响和渗透而发展形成的新的研究途径。
精英分析模型(P321)核心观点:公共政策是统治精英的偏好和价值体现,大众在相当程度上是被精英所操纵的核心观点:公共政策是统治精英的偏好和价值体现,大众在相当程度上是被精英所操纵的1、理论代表人物及主张:帕累托:任何社会都可以分为三个群体:人数较少的统治精英集团、非统治的精英集团和普通大众或非精英集团。
制度理论

4.多层次、多方位的对策理论研究
如前所述,该中心的学术研究或者说制度 分析的学术方法在于多层次、多方位的理 论分析和研究。这一方法在该中心的对策 理论研究方面十分明显,现已形成基本的 理论构架。有关管理制度方面的对策研究, 在我国已有较早的学术渊源,如古代田忌 赛马的故事,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对策研 究案例。 欧美学者把这些案例加以规范化、 理论化,从而形成欧美政治、经济类研究 生的一门必修课,即对策理论。这理论所 强调的就是运用一定范畴和原则,提出最 佳对策、选择与决策。
二、制度分析理论的前沿: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 策分析中心 (全称为,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中心)
1.产生
由著名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组建于1973年,两年后即成 为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该中心 围绕大型研究计划--比较制度分析与发展,并在亚洲、非 洲、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等地建立起学术分支机构,从而 使这一中心的影响越来越大。
一、制度分析理论的形成
1.定义 所谓制度分析,就其字面而言,及是对各种类型的政治与行政管理 制度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进而言之,这种理论着力 于运用当代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成果,以及经济学的方法,对政府和 行政管理制度进行分析,并形成一种特定的研究和分析方法,以及 相对确定的研究范畴与对象,既注意宏观理论研究又强调微观政策 分析,从而试图揭示人类社会及其相关制度的发展模式和方式。
2.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和科研工作者也开始注意对这 一学术思潮进行分析和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翻译出 版的《制度分析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的《公共选择理论导论》,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翻译 出版的《美国行政管理危机》以及散见于有关报刊杂志 的一些制度分析论文,已表明我国一些科研工作者对此 所引起的注意。值得指出的是,不少当代制度分析理论 的知名学者对我国的传统学术理论以及当代经济和行政 管理改革和开放事业抱有浓厚兴趣。当然,对于这一学 术思潮的理解和认识,像对待其他西方学术思潮一样, 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和探讨,以期有益于我 国行政科学研究的发展。
新制度主义理论略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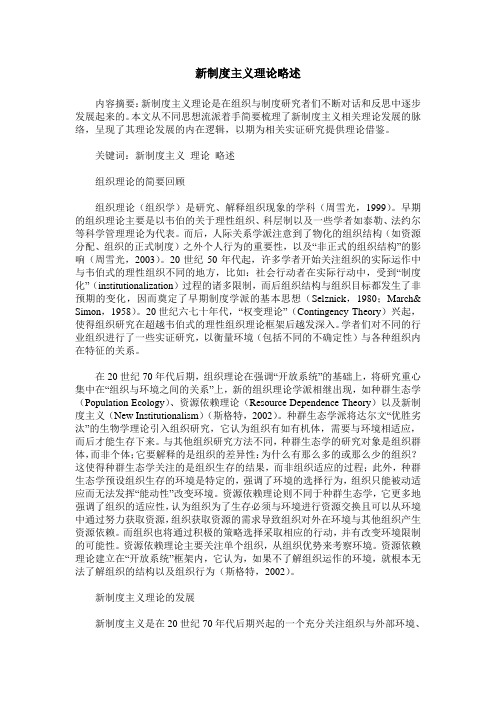
新制度主义理论略述内容摘要:新制度主义理论是在组织与制度研究者们不断对话和反思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本文从不同思想流派着手简要梳理了新制度主义相关理论发展的脉络,呈现了其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期为相关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理论略述组织理论的简要回顾组织理论(组织学)是研究、解释组织现象的学科(周雪光,1999)。
早期的组织理论主要是以韦伯的关于理性组织、科层制以及一些学者如泰勒、法约尔等科学管理理论为代表。
而后,人际关系学派注意到了物化的组织结构(如资源分配、组织的正式制度)之外个人行为的重要性,以及“非正式的组织结构”的影响(周雪光,2003)。
20世纪50年代起,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组织的实际运作中与韦伯式的理性组织不同的地方,比如:社会行动者在实际行动中,受到“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的诸多限制,而后组织结构与组织目标都发生了非预期的变化,因而奠定了早期制度学派的基本思想(Selznick,1980;March& Simon,1958)。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兴起,使得组织研究在超越韦伯式的理性组织理论框架后越发深入。
学者们对不同的行业组织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以衡量环境(包括不同的不确定性)与各种组织内在特征的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组织理论在强调“开放系统”的基础上,将研究重心集中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上,新的组织理论学派相继出现,如种群生态学(Population Ecology)、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以及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斯格特,2002)。
种群生态学派将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生物学理论引入组织研究,它认为组织有如有机体,需要与环境相适应,而后才能生存下来。
与其他组织研究方法不同,种群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群体,而非个体;它要解释的是组织的差异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或那么少的组织?这使得种群生态学关注的是组织生存的结果,而非组织适应的过程;此外,种群生态学预设组织生存的环境是特定的,强调了环境的选择行为,组织只能被动适应而无法发挥“能动性”改变环境。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分析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分析【摘要】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政治学理论,旨在通过制度分析来解释政治行为和政治变革。
本文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核心观点、研究方法、实践应用、与其他政治学理论的比较以及局限性等方面展开分析。
通过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深入探讨,可以揭示现代政治制度变革的规律及其对政治实践的影响。
本文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启示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为我们理解政治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政治改革和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忽略了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理论的结合,以完善政治分析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分析、背景、研究目的、意义、核心观点、研究方法、实践应用、比较、局限性分析、启示、未来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1. 引言1.1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分析的背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政治学理论,它主要关注政治制度在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政治学的批判和挑战,其背景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制度化理论和制度主义思潮。
传统政治学主要关注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则强调政治制度对政治行为的制约和塑造作用,并强调政治制度对政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政治体制和制度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分析正逐渐受到政治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出现和发展,可以说是对传统政治学理论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完善,为我们深入理解和分析当下政治现实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通过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和分析,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政治学视角,为政治现实的解读和理解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框架。
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背景、观点及评论

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背景、观点及评论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领域的背景、主要观点及其引发的广泛评论。
新制度主义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崭露头角,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发展壮大,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首先将对新制度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背景进行简要介绍,然后详细阐述其核心观点和理论框架,最后对现有研究进行评论,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解。
在背景部分,本文将回顾新制度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包括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传统政治理论的局限性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等。
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新制度主义的诞生,为政治学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工具。
在观点部分,本文将详细介绍新制度主义的核心观点,包括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机制、制度对个体和集体行为的影响等。
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政治现象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制度是政治行为的重要约束和动力,对政治发展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响。
在评论部分,本文将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分析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领域的贡献和不足。
一方面,新制度主义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推动了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进步;另一方面,新制度主义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过度强调制度而忽视其他因素、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力不够充分等。
通过对这些评论的分析,本文旨在为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新制度主义理解。
二、新制度主义背景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流派,其背景复杂且多元,反映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转向和现实世界的变化。
新制度主义在批判传统行为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强调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制度不仅是政治行为的框架,也是政治结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理论背景上,新制度主义受到了结构功能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等多种理论的影响。
规范制度主义理论评析

制 度 主义 者 的研究 体现 在政 治制 度 中的规 范与价 值 如 何影 响个 体 的行 为 。 ” _ 2 j 5 。
由 以上 可 以看 出 , 规 范 制度 主义 作 为一 种 思 想
理论 , 主要 强调 组织 规范 与价 值对 人 的行 为 的影 响 ,
2 0 1 4年 7月
胜利 油 田党校 学报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P a r t y S c h o o l o f S h e n g l i Oi l i f e l d
J u l y . 2 0 1 4
Vo l _ 2 7 NO . 4
治 学的 研 究成 果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形成 了对 旧制 度 主 义 的 复 归与 超 越 。
【 关 键 词】 规 范 制度 主 义 ; 旧制 度 主 义 ; 复 归 与超 越 ; 评 析
【 中 图 分 类 号1 B 5 0 6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 0 0 9 —4 3 2 6 ( 2 0 1 4 ) 0 4 —0 0 4 7 —0 5
什( D a v i d . Ma r s h ) 与格里 ・ 斯托克 ( Ge r r y . S t o k e r ) 编著 的《 政治 科学 的理论 与方 法 》 一书中, 也将 马奇 与奥 尔森 的理 论称 为规 范制 度 主义 , 并 且指 出“ 规 范
詹姆 斯 ・ G・ 马奇 ( J a me s G. Ma r c h ) 和 约 翰 ・P・ 奥尔 森 ( J o h a n P . Ol s e n ) 发表的《 新 制度主义: 政 治 生活 中的组织 因素 》 一文 , 他 们 提 出用“ 新 制度 主 义” 观点来 看 待政 治生 活 , 使 政 治学 回归 原 来 的学 术 本 源, 重 新复 兴制 度 分 析 的作 用 。关 于新 制 度 主 义 的
制度主义理论

制度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Institutionalism)是一种关注社会制度和组织的学说,认为社会行为和社会变革是由社会制度和组织所决定的。
制度主义理论强调社会制度和组织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是影响个人行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社会制度和组织的性质和规则对于个人和社会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组织会对个体的行为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制度主义者认为,改变社会制度和组织的性质和规则可以促进社会变革和个人发展。
制度主义理论主张,社会制度和组织的性质和规则是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产物。
社会制度和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们反映了社会利益的权衡和社会权力的分配。
制度主义者认为,社会制度和组织的变革应该基于对社会历史和社会条件的深入理解,并遵循合理的理论和方法。
制度主义理论强调社会制度和组织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
社会制度和组织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
制度主义者认为,要理解社会行为和社会变革,必须分析社会制度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制度主义理论也强调社会制度和组织的改革和创新。
制度主义者认为,社会制度和组织的改革和创新是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关键。
制度主义者主张,在社会制度和组织的改革和创新过程中,应该尊重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特点,以及个体和群体的权益和利益。
制度主义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它被运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以解释社会行为和社会变革的原因和机制。
制度主义者通过研究和分析社会制度和组织的性质和规则,揭示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变革的深层次动因。
总的来说,制度主义理论强调社会制度和组织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是影响个人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
它提供了一种理论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改变社会制度和组织,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
制度主义的发展不仅对于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组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对于提高人们的社会认识和社会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重大工程组织场域的结构化与变迁——以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工程为例

重大工程组织场域的结构化与变迁——以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工程为例谢琳琳;褚海涛;韩婷;乐云【摘要】从制度理论出发,分析整合组织种群间关系、制度逻辑系统、组织原型和集体行为等核心要素,尝试构建出重大工程组织场域的理论模型,基于模型探究了制度环境与组织间关系、组织行为的交互影响;并以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工程为例实证分析了组织场域结构化和变迁过程.指出重大工程组织场域的动态变迁多,需要场域中各组织种群协同发挥能动作用,降低风险,提高绩效水平,实现重大工程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结论也为项目组合和项目群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期刊名称】《工程管理学报》【年(卷),期】2018(032)006【总页数】6页(P92-97)【关键词】重大工程;组织场域;制度环境;结构化;变迁【作者】谢琳琳;褚海涛;韩婷;乐云【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9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TU17就建设目的、交付要求、复杂程度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而言,重大工程完全不同于普通工程项目[1],由于项目背景复杂,涉及各个层次的利益相关者,重大工程建造甚至起着改变社会的作用[2]。
因此,对重大工程组织的分析不能只关注组织架构形式和建设目标,还应将其依赖的项目及社会背景容纳进来,重视多元主体在制度环境、关系结构下的协同治理。
在重大工程组织的研究中,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最为广泛,建设工程管理的学者强调有效的利益相关者管理能够消除利益冲突、化解矛盾,实现重大工程效益最大化[3]。
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交互影响和行为模式等问题,无法考虑“重大工程组织环境”作为行为背景的制约作用。
组织场域将重大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置于关系和制度的背景环境中,以更高层次的组织集合为研究单位关注组织的演进过程。
经济社会学-05_理论模式二:制度主义

大学课件
1
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模式(2)
制度主义
制度主义的两种类型 制度主义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应用 简短的评论
制度主义的两种类型(1)
1. 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
“制度主义”的界定
Institution theory presents a paradox. Institutional analysis is as old as Emile Durkheim’s exhortation to study “social facts as things”, yet sufficiently novel to be preceded by new in much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stitutionalism purportedly represents a distinc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henomena; yet it is often easier to gain agreement about what it is not than what it is.
大学课件 14
制度主义的两种类型(14)
制度理论论文总结范文

摘要:制度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对理解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以及政策制定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制度理论的概述、主要观点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应用进行梳理,旨在总结制度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对制度理论在实践中的反思进行探讨。
一、制度理论的概述制度理论起源于20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
该理论认为,制度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和准则,包括正式制度(如法律、政策)和非正式制度(如习俗、信仰)。
制度理论强调制度在资源配置、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二、制度理论的主要观点1. 制度与经济发展:制度理论认为,良好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落后的制度则会阻碍经济发展。
诺思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2. 制度与政治:制度理论认为,政治制度是维护国家稳定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
威廉姆森强调,政治制度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3. 制度与社会变迁:制度理论认为,社会变迁是制度不断调整和变革的过程。
科斯认为,制度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4. 制度与市场:制度理论认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依赖于良好的制度环境。
威廉姆森强调,制度对市场效率具有显著影响。
三、制度理论在当代社会中的应用1. 经济发展:制度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通过完善法律、政策等制度,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
2. 政策制定:制度理论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政策制定者依据制度理论,调整和完善政策,以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
3. 社会治理:制度理论为我国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
通过建立健全制度,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促进社会和谐。
4. 国际关系:制度理论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各国通过制定国际规则,维护国际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四、制度理论的反思1. 制度与人的关系:制度理论过于强调制度的作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制度实践中,应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使制度与人的发展相互促进。
2. 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
制度理论_精品文档

Selznick最初的意图是研究韦伯的理性组织(科层
组织)的实际运作问题,按照韦伯的理性组织模式,
组织应该有明确的目标,高度形式化,排除了个
性因素的干扰,仅奉行法律程序和公务原则,具
有精确性、纪律性和严谨性等特点。
2021/10/10
12
但是,Selznick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个工程表面看来是 个大众参与的工程,在实际运作中却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利 益集团,地方势力和全国性利益组织都参与进来了,例如 美国农业部、农场联合会、当地政界、工商界头目都卷入 了这一工程。这些利益集团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工程,他们 派自己的人把持、占据了各个大的工程部门,控制很多政 策制定。结果是很多项目的实施与当时设计的组织目标背 道而驰。这一项目的初衷是帮助穷人,但是执行的结果是 富人从中得到了利益和服务。这一结果显然与韦伯的理性 组织模式不一致。
不同于前两个视角,开放系统视角把组织看作是一个开放 的系统,与外面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能量、信息、资源 的交换,这种交换关系是组织存活的关键。这种视角虽然 出现最晚,但它传播的非常快,并且对组织理论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组织内部特征的研究开始 让位于对外部事件和过程的研究,围绕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70年代密集产生了多个具有重大影响的至今仍然是学术研 究主流的理论学派。
Selznick对研究发现进行了提炼,他承认组织是被合理设 计以完成特定目标的工具。但他认为,这些组织在实际运 作中却“不能控制组织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原因有两 个:一是个体,他们加入组织,但并不仅仅按照组织给他 们设定的角色行动;二是组织结构,既包括正式结构也包 括非正式结构,组织结构将组织成员与组织之外的人联系 起来,组织受环境因素的影响,环境会危及组织的既定目 标。
规范制度主义理论评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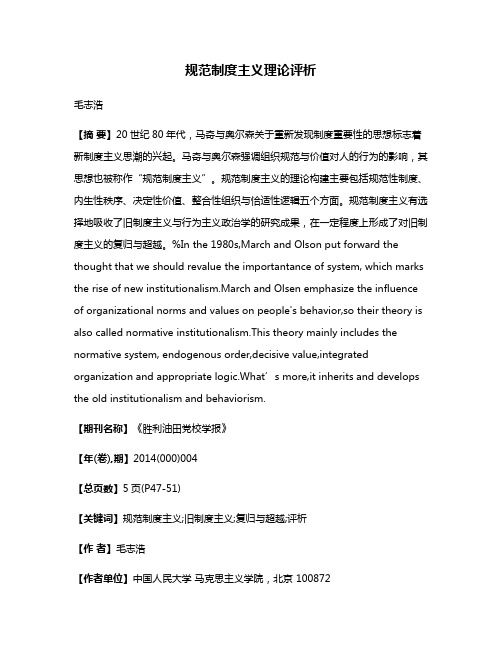
规范制度主义理论评析毛志浩【摘要】20世纪80年代,马奇与奥尔森关于重新发现制度重要性的思想标志着新制度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奇与奥尔森强调组织规范与价值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其思想也被称作“规范制度主义”。
规范制度主义的理论构建主要包括规范性制度、内生性秩序、决定性价值、整合性组织与恰适性逻辑五个方面。
规范制度主义有选择地吸收了旧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旧制度主义的复归与超越。
%In the 1980s,March and Olson put forward the thought that we should revalue the importantance of system, which marks the rise of new institutionalism.March and Olsen emphasize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norms and values on people's behavior,so their theory is also called normative institutionalism.This theory mainly includes the normative system, endogenous order,decisive value,integrated organization and appropriate logic.What’s more,it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old institutionalism and behaviorism.【期刊名称】《胜利油田党校学报》【年(卷),期】2014(000)004【总页数】5页(P47-51)【关键词】规范制度主义;旧制度主义;复归与超越;评析【作者】毛志浩【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506规范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它关注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础,强调制度因素的解释性权力。
制度主义理论

制度主义理论从本质上讲,行为主义政治学是对传统政治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革新。
在研究对象上,行为主义以政治行为和行为互动代替传统的政策和制度;在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借助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量化和实证分析。
行为主义认为,个体的真正偏好只有通过一定的行为才能具体地表现出来;集体现象是个体行为的聚集,个人的偏好只有通过利益聚集机制才能带来最佳的效果。
但是,行为主义的研究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味地强调价值中立和研究手段的科学化,使政治科学远离了现实政治生活;而从现实来看,主流学者无法应用行为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复杂的变化,他们对60、7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越南战争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无能为力。
这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理论家的反思和批判。
1984年,马奇和奥尔森发表了《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他们指出,由于行为主义的影响,作为政治生活基本因素的组织被忽略了,而实际上,组织和法律制度则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者。
个体“表现出来的”偏好与真正的偏好是存在距离的,集体决策不是个体偏好聚集的结果,而是决策规则影响的产物,而且集体决策无法还原为个体偏好。
他们提出用“新制度主义”观点来看待政治生活,重新复兴制度分析的作用。
在政治学领域中,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与对行为主义理论的批判是分不开的。
新制度主义者认为放弃对制度的研究是行为主义的一个主要缺陷。
“新制度主义强烈反对把行为确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要素;他们不相信行为能够为解释‘所有政府现象’提供足够的基矗因为,行为发生在制度环境中,因此,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必须考虑制度因素。
”[1]而在经济学领域中,主导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实践的主流思潮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它们使西方国家经历了战后长时期的经济繁荣。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停滞,失业问题困扰着各国的决策者。
这种状况引起了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反思,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宏观问题,政府作用、政府职能等问题进入了经济学领域。
4制度理论

14
合法性机制
合法性:制度学派使用的合法性(Legitimacy )主要是强调 在社会认可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权威。周雪光p78.
合法性机制:指那些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制度的力量。 合法性机制基础:超越个人的私利,为大家所承认并接受,合
乎情理和社会期待。周雪光p82. 合法性机制既约束组织行为,又帮助组织提高社会地位,得到
8
新制度理论产生背景
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与效率规则表明:
组织结构等取决于组织的具体目标、任务、技术和规模等。 由于每个组织内部的这些情况不同,所以他们的机构、规则、
行为、活动等也应该不同。
但是现实中出现了组织趋同现象。 以往的理论解释不了类似问题,这使得一些学者需求
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即按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周雪光p72. 制度环境要求组织要服从“合法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
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周雪光p73. 制度环境强调的是组织遵从理性规范、符合正确的实施程序、存在恰
当的结构位置。斯格特《组织理论》p128. 总之:技术环境要求组织遵从效率机制,制度环境要求组织遵从合法
6
新制度理论
制度理论的“新”、“旧”之分标志是:1977 年约翰·梅
耶(John W Meyer)和布莱恩·罗恩(Brian Rowan)在 《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Sociology )上 发表的论文《制度化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见鲍威尔与张永宏的书
保罗·迪马鸠(Paul J.DiMaggio)和沃尔特·鲍威尔(Walter W.Powell)1983年在《美 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发表的论文《重访铁笼:组织域 中的制度同形和集体理性》(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该论文对新制度理论学派的发展起到了非 常重要推进作用。 ——见鲍威尔与张永宏的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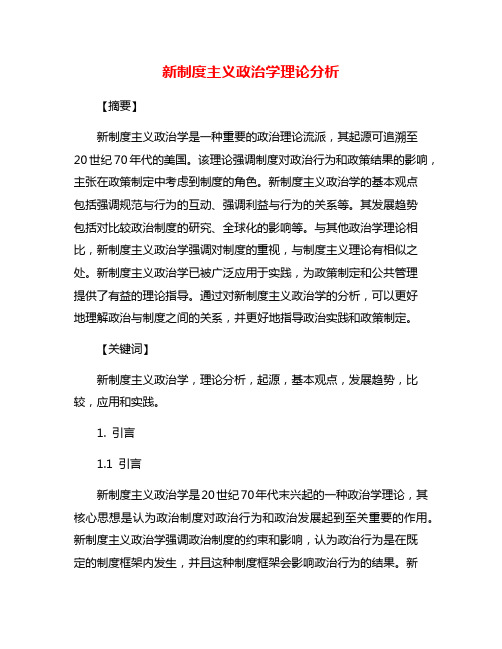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分析【摘要】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理论流派,其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该理论强调制度对政治行为和政策结果的影响,主张在政策制定中考虑到制度的角色。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包括强调规范与行为的互动、强调利益与行为的关系等。
其发展趋势包括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全球化的影响等。
与其他政治学理论相比,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强调对制度的重视,与制度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已被广泛应用于实践,为政策制定和公共管理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
通过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政治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并更好地指导政治实践和政策制定。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分析,起源,基本观点,发展趋势,比较,应用和实践。
1. 引言1.1 引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一种政治学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认为政治制度对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强调政治制度的约束和影响,认为政治行为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并且这种制度框架会影响政治行为的结果。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分析的出现,使政治学研究的视野得到了拓展,为理解当代政治现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将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起源、基本观点、发展趋势、与其他政治学理论的比较以及应用和实践等方面,旨在全面了解这一重要的政治学理论,并对其在当代政治研究中的价值进行评估。
2. 正文2.1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分析的起源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传统政治理论的挑战和批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开始崭露头角。
其起源主要可以归因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政治科学家对于现有政治体制和制度的失效感和不满,二是对传统政治学理论的反思和批判。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的起源与政治科学家对现有政治体制和制度的不满有着密切关系。
传统政治学往往关注政治制度的形式,而忽视了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行和效果。
剖析制度分析整体主义法涵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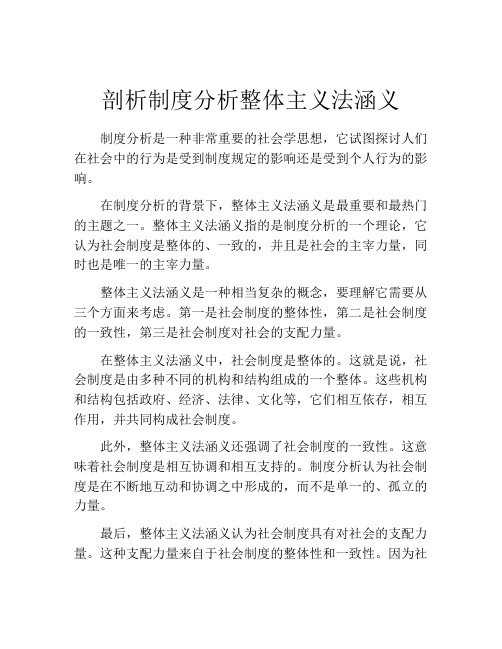
剖析制度分析整体主义法涵义制度分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学思想,它试图探讨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是受到制度规定的影响还是受到个人行为的影响。
在制度分析的背景下,整体主义法涵义是最重要和最热门的主题之一。
整体主义法涵义指的是制度分析的一个理论,它认为社会制度是整体的、一致的,并且是社会的主宰力量,同时也是唯一的主宰力量。
整体主义法涵义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概念,要理解它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是社会制度的整体性,第二是社会制度的一致性,第三是社会制度对社会的支配力量。
在整体主义法涵义中,社会制度是整体的。
这就是说,社会制度是由多种不同的机构和结构组成的一个整体。
这些机构和结构包括政府、经济、法律、文化等,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并共同构成社会制度。
此外,整体主义法涵义还强调了社会制度的一致性。
这意味着社会制度是相互协调和相互支持的。
制度分析认为社会制度是在不断地互动和协调之中形成的,而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力量。
最后,整体主义法涵义认为社会制度具有对社会的支配力量。
这种支配力量来自于社会制度的整体性和一致性。
因为社会制度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使得社会制度能够统一和协调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对社会产生影响和控制力。
总的来说,整体主义法涵义是指社会制度是整体性、一致性和支配力量的体现。
它认为社会制度是社会最重要的支配力量,是社会的主宰力量,并且只有通过社会制度才能对社会产生控制力和影响力。
然而,也有学者对整体主义法涵义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整体主义法涵义过度强调了社会制度作为统一力量的作用,而忽略了个人、群体等社会其他力量的作用。
他们强调了社会制度和其他力量之间的互动和影响,认为社会制度不是唯一的支配力量。
总之,整体主义法涵义是制度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试图揭示社会制度的整体性、一致性和支配力量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
但是,在理解整体主义法涵义时,需要同时考虑社会制度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和影响,以达到更加全面的认识。
【07】【张 靓】:《社会学制度主义简析》

社会学制度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研究路径, 近年来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增强了其理论说 服力,但是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而且还带来许多新问题。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的由来及演变 本文所说的社会学制度主义最初源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 的分析路径,其直接源头是对涂尔干的结构和马克斯·韦伯的官 僚组织理论的反思。以涂尔干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组织理论认为" 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组织结构;每项制度、每种宗教、每条法律、每 类家庭组织的作用均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延续和发展。"①即社会 的发展是因为其制定的有效组织结构,为达到组织目标而采取高 效的内在理性和效率来完成其承担的社会任务。它是一种典型的 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仅从资源分配的效率这一角度来看组织的 存在,把组织中的人看成是理性人,没有看到他们在组织中的某些 活动是出于他们的特定责任和义务。并且,古典组织理论根本无 法解释社会中无效率组织存在的现象。因此,社会学制度主义可 以被认为是在继承社会学传统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适应性逻辑 适应性逻辑的提出有三个背景:首先是对古典组织理论的反 思,韦伯认为官僚组织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使其在执行任务时具 有高度的理性和效率,但他却忽视了在组织运作过程中,外在文化 和价值因素对组织成员的作用。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组织追求 的不仅是效率,还有价值目标;组织也不仅按理性设计的要求运作, 它还受到外界环境、价值和观念的影响。其次,组织具有趋同现象, 尽管组织面临的环境、社会规范、价值等因素具有不同的特点,可 是组织并没有像权变理论所语言的那样有不同的形式。最后,制 度一直是理论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以韦伯、涂尔干、帕森斯为代表 的社会学家主要关注静态的宏观结构而忽视了微观行为结构;经 济学家制度主义关注微观的个人选择行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但 却很难解释在制度形成、运作、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微观--宏观联络 问题,即不能有效解决集体困境问题。因此,社会学制度主义根据 其独特的理论资源和解释传统,发展出了适应性逻辑。 所谓的适应性逻辑是指"在个人行为与制度之间确立了一个 价值标准,人们所处的制度环境包括正式规则、习俗、典礼和惯例 等为人的行动提供了意义框架和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 等。"②即人们总是根据他们所共享的规则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使 自己的行为尽可能适合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规则。这样,制度相关 人通过适应性逻辑将特定的行为与特定的情境联系起来,并且在 相关人对制度的认知和适应性过程中,选择接受制度或者改变制 度。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研究的主要问题 ㈠广泛的制度定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界定显得更为广泛。他们从几个方 面理解和界定制度的涵义,首先,社会学制度主义没有在制度与组 织之间做出清晰的区分。道格拉斯·斯诺认为,制度为其相关人 承担着行动的框架、信息、激励等功能;而组织虽然和制度有着密 切的关系,但组织作为一个能动的、追求着自身目标的个体是作为 行动者出现在制度之中的。马奇和奥尔森的理论认为"政治制度 是政治行动者",并且认为"制度具有整体性和自主性",因此制度和 组织在某种情况下是同一的。其次,社会学制度主义倾向于从宏 观角度界定制度。社会学制度主义的适应性逻辑揭示了制度相关 人的选择偏好受到制度的影响,而且制度作为相关人的认知模板 为相关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的选择提供了认知标准。因此,社 会学制度主义必须对制度作宏观上的界定,只有这样才能具有解 释能力。最后,在个体行动者的行动与制度的关系上,社会学制度 主义理论强调制度的认知模板作用。认为制度不仅是影响个体行 动者的策略性行为,而且还影响其基本偏好、认知模式以及身份认
试论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

试论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试论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一、引言制度分析是一种研究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方法。
在本论文中,我们将探讨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这种方法将整体性和系统性作为研究的基本框架,通过考虑制度因素的相互关系和综合影响,深入剖析其影响经济的机制和路径,以期提高我们的研究能力和预测准确性。
二、整体主义方法的基本理念整体主义方法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它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并试图理解事物的内部相互关系,从而获得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在制度分析中,整体主义方法的基本理念如下:1.注重制度因素的内部关系和相互作用。
制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和相互作用关系。
因此,在分析制度问题时,我们必须关注不同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部逻辑。
2. 强调制度的演化和动态变化。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但制度不是静态存在的,它随着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
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制度的演化和动态变化,以期深入理解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3.重视制度结构和制度环境的影响。
制度结构和制度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它们不仅决定着经济行为的规则,而且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态度。
因此,在制度分析中,我们应该重视制度结构和制度环境的影响。
4.注重经济和制度问题的综合研究。
经济问题和制度问题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影响,经济问题的发生通常都与制度因素相关。
因此,在制度分析中,我们应该注重经济和制度问题的综合研究,以期深入理解其相互关系。
5.采用系统性分析方法。
整体主义方法是一种系统性分析方法,因此,在制度分析中,我们也应该采用系统性分析方法,强调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综合影响。
三、制度分析中的整体主义方法在制度分析中,整体主义方法具体应用的基本步骤如下:1.识别制度因素。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在制度分析中,我们首先需要识别出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
2.确定制度因素之间的关系。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制度主义理论分析、沟通规划与场所塑造地方特性(qualities of places )的塑造在西方社会,传统的规划活动一直侧重于对不同层次的场所进行管理,从邻里、住区到城市、区域和整体景观。
这种规划形式不可避免地反映并塑造了次级国家管治(governance )的组织结构以及有关的主流观念,即场所(places )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们应该是什么。
20世纪下半叶,综合规划(comprehensive plans )、总体规划(master plans )以及物质空间发展规划(physical development plans )反映了整合城市系统的概念,表现了为寻求平衡关系而产生的特殊城市形态。
当时的规划任务是促进发展,对有关变化进行控制以利于减缓与这种关系的背离,纠正市场的错误,以及维持秩序对抗混乱的威胁。
这些概念现在已经被放弃,它们被认为是代表了有关地方特性(place qualities )的“现代主义”思想和“国家经济统制论”(statist ),代表了政府在控制空间变化方面的角色是“命令与控制”的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规划活动一直与我们现在要试图摆脱的过去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并不足为奇。
此结论得到后现代文化倡导者的支持,也得到市场自由倡导者的拥戴,其论点基于许多不同的主张。
有些观点认为,与经济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社会动力相比,地方特性无关紧要。
这一论点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们认为新的信息社会使人们从对地方的依赖中解放了出来。
另一些人则通过强调概念化和控制未来方向的不可能性,从而使规划概念塑造未来的野心遭到幻灭。
在许多管治语境下,这种争论已经使得部门政策共同体(sectoral policy communities )发展成孤立的堡垒,这些部门政策共同体往往关注于特定的职责或议题(如经济发展、住房、医疗卫生、教育、交通、农业、旅游等等)。
每一个政策共同体都与商业集团和压力集团之间有着独特的关系,很少关注其自身政策与经济组织、社会生活、生物圈系统等现实之间的交互作用。
这种交互作用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方,并且涉及到对地方特性的理解。
由于摒弃了场所曾经是什么、可以发展成什么的战略概念以及地方内部系统关联的模式,地方特性在西方许多公共政策中已经淹没于项目设计和评估中。
同时,在20世纪中期为空间规划和土地使用管理建立的政策系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Communicative Planning, and Shaping Places帕齐·希利 著 邢晓春 译摘要:本文回顾了社会科学中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沿革及其与沟通规划理论的关系,并强调了它与有关实践任务的关联,这种实践任务回应了公共政策演变中对更多地方意识的需求。
作者追溯了对于公民社会的多种诉求和社会生活能够做出更多回应的管治形式的演变,并且讨论了社会建构主义关于制度的概念、参与者和网络的重要性、结构和能动作用的内在联系,以及社会网络的文化维度。
作者还探究了管治能力或制度能力发展的意义。
在回顾沟通规划理论时,作者论述了哈贝马斯对于交往行为的研究方法可能被引入制度主义理论的观点中或者被改写。
最后,作者探讨了这些进展如何能够增进理解并形成相应的战略,用更加包容的方法推动关注地方的、整合性的公共政策发展。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communicative planning theory,with emphasis on the relevance to the practical task of responding to demands for a more place-conscious evolution in public policy. I trace the evolution of forms of governance that are more responsive to the multiple claims and social worlds of civil society and include discussion of the social-constructionist conception of institutions, the significance of actors and networks,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agency,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social networks. Th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governance capability or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re also explored. In reviewing comnmunicative planning theory, I discuss how Habermas ’s approach to communicative action may be reworked or positioned in a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Finally, I explore how these developments can be used to develop understanding and strategies for evolving more inclusionary approaches to integrated, place-focused public policy.“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Communicative Planning, and Shaping places ”原载于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999, 19, 111-122;Sage 出版集团授权作者在我刊发表中译文。
作者:帕齐·希利(Patsy Healey ),参见第4页作者简介。
patsyhealey@译者:邢晓春。
jane2109@帕齐·希利① 英国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neo-institutionalism, Rhodes 1995)尽管对有关管治制度下行动者的工作做出了有价值的经验主义研究,但是与本文探讨的理论发展联系甚微。
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抨击,它们被称为现代主义者和福利国家组织结构的残羹冷炙。
随着规模庞大的国家经济规划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一种说法,认为规划的时代已经走到尽头。
在公共政策中这种无视地方的演变,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如英国)非常明显,并且正在面临区域经济分析研究、环境科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带来的强大挑战。
把公司体系的生产关系和增值链与公司及其人员所在地方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使用了“社会经济学”、“进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多种名称的这一学科,首先被纳入在这一框架下(Amin 和Thrift, 1994; Amin 和Hausner, 1997)。
这导致出现了大量关于“工业区”和“知识园区”特征的研究工作(Asheim, 1996; Belussi, 1996)。
第二种学科的发展受到环境保护论者的启发,吸收和利用了有关概念,正在探求以整合系统的模式来表达在地方可以发现的复杂关系。
这些研究工作不仅将经济和社会系统相联系,而且将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联系在一起。
与新制度经济学一样,这些在建立整合环境模式方面的成就是从某个场所的一种现象(例如废弃物产生和处理的循环系统或水文系统)中延伸和扩展,并且试图将对这一系统起作用的其他关系视为影响因素。
最后,关于文化地理学、女权论日常生活体验以及当代社会的社会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已将重点集中于身份认同的政治学(identity politics )以及社会分异和边缘化的过程。
这些研究正在将地方特性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和生存体验质量的方式揭示出来。
在这种工作中,场所是一种物质和社会的空间,代表着一种生存习性,被赋予了意义和内涵,并且有多种关系交织于其中,通过这些关系可以形成并改变特定的“文化资本”(Bourdieu, 1977)。
所有这些发展都正在对分析议程和政治议程进行着重构,重新强调地方特性在公共政策中的位置。
在欧洲背景下,无论是从总体上对公共政策的关注,还是对次级国家管治组织机构的关注,都有越来越多的政策辞令提倡政策区域之间更多的整合,并且更加强调以战略方式对于地方、城市、边缘地区、有价值的景观地区和大都市系统中地方特性的变化进行管理(CSD, 1997)。
在这些压力的背后,部分是由于上述知识和思辨的发展导致了变化。
但是,由于经历了政策执行中的困难、追逐效益(通过整合如何少做多得),以及面对日益碎片化的管治来寻找途径以减少它所带来的问题等等原因,这些发展正在被推向歧路。
在很多情形下,还有一种关注与协作议程(coordination agenda )共同发挥作用,将政策设计概念从已经确立的政策共同体的观点,转变为与工商界和市民的当前关注更为相关的形式(Harding, 1997)。
克服民主的缺失,使管治议程及其传递和扩散的节点与市民更加相关,再加上提供对经济发展的支持,这一切都需要具有对具体情况加以理解和回应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对于免除某一特定管治能动作用的回应。
目前,在当代公共政策中使用的隐喻(如伙伴关系、整合、整体的、一站式),反映了对于减少政府机构破碎化的关注,至少在英国是这样。
这些关注在区域和地方层面都促进了管治能力的发展,能够将地方发生的不同方面的事务相互联系在一起,至少是建立起战略联系,即那些看上去具有重大意义的联系(Mawson, 1997;DETR, 1998)。
所有这些转变,无论是在分析还是在政策关注上,都导致了次级国家管治有关战略和场所意识(place-conscious )进行变化的需求。
这既需要思维模式的转变,以明确在伙伴关系和整合中所强调的意义,另外也需要行为模式的转变,以使不同的政策共同体、不同类型的专业技能之间建立联系,在民主缺失的情形下,建立起管治、市民和工商界之间更为互动的新型关系。
规划队伍作为一个专家团队,具有战略性的、关注地方关系的智力传承,也有面对政策整合挑战的日常工作实践,可以为管治的重新设计做出诸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