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一)
山海经中的名词研究报告

《山海经》中的名词研究摘要:《山海经》是中国先时代的重要古籍,书中收录了大量的地理知识,包括了山川,民族,物产,药物等,同时又保存了诸如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这使其具有了非凡的文献价值,研究其中收录的名词,对研究先语言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本论文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
主要介绍的是本论文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其研究现况和研究意义第二章《山海经》中名词的特点及分类。
主要阐述《山海经》中名词的特点并对《山海经》中动植物名词按草木虫鱼鸟兽进行简单分类和统计第三章《山海经》中名词的文化涵。
选取了几个《山海经》中所记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神话事件等,对《山海经》中所承载的文化涵进行分析第四章结语。
对全文做出总结,指出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及不足之处,并对《山海经》可以进行的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关键词:《山海经》名词特点分类第一章绪论一、《山海经》概述《山海经》是一部奇书,它涉及到神话,社会文化,地理等多个方面。
对于该书作者,前人有认为是禹,伯益,经西汉向,歆校编,方才形成传世书籍,而现代学者大多认为其成书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单基本可确定成书非一人一时。
《山海经》版本颇为复杂,现可见的最早版本为晋郭璞《山海经传》,而《山海经》的书名在《史记》中便有提及,《史记·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已,至《禹本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史记引述了很多书藉的容,但无一例外,都是堪称经典的书籍,在司马迁论述西域的时候虽然形式上是对《山海经》提出了质疑,实质上是证明了《山海经》无比高贵的身份和正统地位,在他眼里《山海经》是和《禹本纪》相提并论的。
由此亦可见《山海经》在先典籍中的重要地位。
《山海经》是一本囊括了极为丰富类容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性质的典籍,其全书虽只有三万一千多字,但却涉及到了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历史,地理,天文,气象,民俗,,动物,植物,矿物,医药等各个方面,包罗万象。
论《山海经》的时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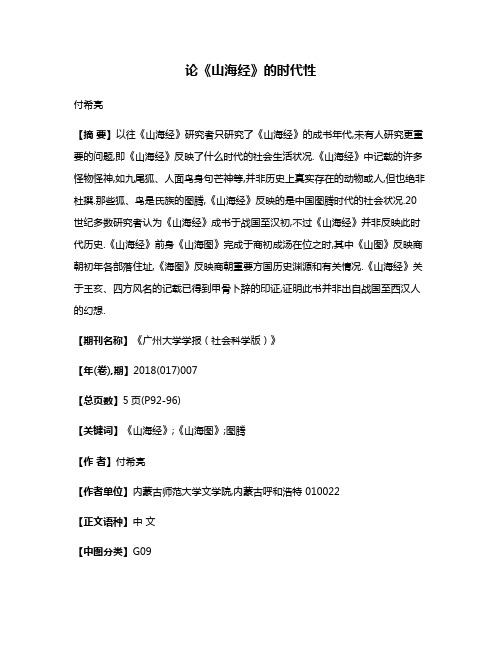
论《山海经》的时代性付希亮【摘要】以往《山海经》研究者只研究了《山海经》的成书年代,未有人研究更重要的问题,即《山海经》反映了什么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山海经》中记载的许多怪物怪神,如九尾狐、人面鸟身句芒神等,并非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动物或人,但也绝非杜撰.那些狐、鸟是氏族的图腾,《山海经》反映的是中国图腾时代的社会状况.20世纪多数研究者认为《山海经》成书于战国至汉初,不过《山海经》并非反映此时代历史.《山海经》前身《山海图》完成于商初成汤在位之时,其中《山图》反映商朝初年各部落住址,《海图》反映商朝重要方国历史渊源和有关情况.《山海经》关于王亥、四方风名的记载已得到甲骨卜辞的印证,证明此书并非出自战国至西汉人的幻想.【期刊名称】《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8(017)007【总页数】5页(P92-96)【关键词】《山海经》;《山海图》;图腾【作者】付希亮【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09一、《山海经》研究述评《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神话宝藏和地理方志之祖。
20世纪以来,有众多学者对《山海经》进行了研究。
关于《山海经》的作者,徐显之认同两汉人的观念,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
[1]何观洲提出《山海经》中《五藏山经》是战国邹衍所著,《海外经》以下为秦汉以后伪经。
[2]卫聚贤提出为战国墨子弟子随巢子所作。
[3]这些观点都禁不起推敲。
《山海经》中记载了许多绝非大禹和伯益所能见到的夏代的事情,有夏启、夏桀、后羿、武罗、孟涂、王亥等,说明此书绝非大禹和伯益所著。
邹衍是战国阴阳五行学派的代表,史料上记载的是他的五德终始说和大小九州岛说,没有志怪的东西,显然没有根据证明邹衍是《山海经》的作者。
墨子弟子随巢子来自印度的说法更没有根据,《山海经》所记载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圣贤都是华夏族的祖先,跟印度没有关系。
学术界多数人认为《山海经》非一人一时所作。
《山海经》研究成果概述

《山海经》研究成果概述作者:张国平来源:《丝绸之路》2009年第20期[摘要]《山海经》是我国先秦典籍中一部具有独特风貌的作品,自古被称为奇书。
学者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山海经》的研究:《山海经》的作者是谁,《山海经》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山海经》是怎样成书的,它对后世文学有着怎样的影响等,这些都是历代学者研究的重点。
本文主要对前人研究《山海经》的成果做一概述。
[关键词]《山海经》;神话传说;文学典籍一、《山海经》的性质《山海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籍,因其内容广博,自汉至今,未有定论,总括诸家之言,如下具有代表性观点:地理类:西汉刘秀(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认为该书“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
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
因此,判定为地理类书籍。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都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
数术类:《汉书•艺文志》把《山海经》列入数术略刑法家之首,与《相人》、《相六畜》之类的巫卜星象之书混在一起,《宋史•艺文志》亦将之列入五行类。
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把《山海经》列在子部小说家类。
《提要》述改列的理由云:“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
故“道藏”收入太玄部兢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
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
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
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其他观点:清代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将《山海经》看作历史著作,列入古史类。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它为巫书,“记海内外山川神祗异物及祭祀所宜……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
袁珂先生认为,“《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亦乃神话之渊府”。
而李剑国又认为《山海经》是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是志怪小说发展的源头之一。
甚至有人提出,“《山海经》涉及面广泛,诸如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医药、疾病、气象、占验、神灵、祀神的仪式和祭品、帝王的世系及葬地、器物的发明制作,以至绝域遐方,南山北地,异闻奇见,都兼收并录,无所不包,可说是一部名物方志之书,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类书”。
山海经学研究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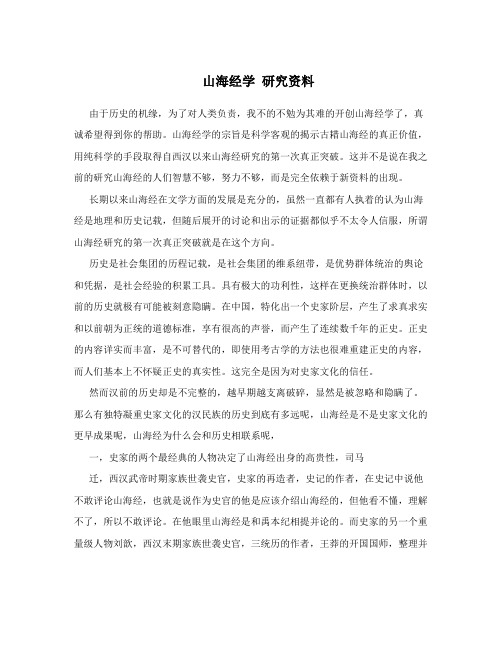
山海经学研究资料由于历史的机缘,为了对人类负责,我不的不勉为其难的开创山海经学了,真诚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山海经学的宗旨是科学客观的揭示古耤山海经的真正价值,用纯科学的手段取得自西汉以来山海经研究的第一次真正突破。
这并不是说在我之前的研究山海经的人们智慧不够,努力不够,而是完全依赖于新资料的出现。
长期以来山海经在文学方面的发展是充分的,虽然一直都有人执着的认为山海经是地理和历史记载,但随后展开的讨论和出示的证据都似乎不太令人信服,所谓山海经研究的第一次真正突破就是在这个方向。
历史是社会集团的历程记载,是社会集团的维系纽带,是优势群体统治的舆论和凭据,是社会经验的积累工具。
具有极大的功利性,这样在更换统治群体时,以前的历史就极有可能被刻意隐瞒。
在中国,特化出一个史家阶层,产生了求真求实和以前朝为正统的道德标准,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产生了连续数千年的正史。
正史的内容详实而丰富,是不可替代的,即使用考古学的方法也很难重建正史的内容,而人们基本上不怀疑正史的真实性。
这完全是因为对史家文化的信任。
然而汉前的历史却是不完整的,越早期越支离破碎,显然是被忽略和隐瞒了。
那么有独特凝重史家文化的汉民族的历史到底有多远呢,山海经是不是史家文化的更早成果呢,山海经为什么会和历史相联系呢,一,史家的两个最经典的人物决定了山海经出身的高贵性,司马迁,西汉武帝时期家族世袭史官,史家的再造者,史记的作者,在史记中说他不敢评论山海经,也就是说作为史官的他是应该介绍山海经的,但他看不懂,理解不了,所以不敢评论。
在他眼里山海经是和禹本纪相提并论的。
而史家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刘歆,西汉末期家族世袭史官,三统历的作者,王莽的开国国师,整理并极力向皇帝推荐山海经说是唐虞历史。
这二位史家人物做事的份量已经一再被证明,不容轻视。
二,山海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广泛,无处不在,任何一本中华典籍中都能看到山海经的影子。
三,在以拘谨而著称的中华文化中,山海经这部莫名其妙的书一直被顽固的留在了核心地位。
从山海经中看中国神话

从山海经中看中国神话中国神话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其中《山海经》作为中国神话的重要文献,记录了众多神祇的故事和传说。
本文从《山海经》中分析中国神话,试图揭示中国神话的起源和发展。
一、《山海经》中的神话形象《山海经》是我国古代神话文献的重要代表,其中的神话形象涉及天地、神鬼、妖怪、禽兽等众多生灵。
在《山海经》中,神话形象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形象丰富多彩,神秘而神圣,既有人类化的形态,也有独特的形象特征。
比如,《山海经》中记录了众多神鬼形象,如夜叉、鬼面、蛇身人面等;还有一些禽兽神话形象,比如岳麓白鹿、穆天子之雕等。
这些形象都有着神话传统特征,既拥有人类形态,同时也拥有独特的超自然能力和形象特征。
二、中国神话的起源从《山海经》所记录的历史和传说可以看出,中国神话起源于人类对自然及自然界中一些神秘现象、奇特事物的研究和创造。
久而久之,这些神秘的现象逐渐被人们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形成了人们心中的神灵、神话。
中国神话更多地是在人类的追求和理解自然中逐渐形成的。
同时,中国神话也受到了中国古代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影响。
例如太极图、阴阳五行、道德经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神话的创作和发展。
三、中国神话的演变《山海经》中所记录的神话故事,是中国神话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神话文化的重要代表。
此后,中国神话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了自己的发展和变化。
在汉代,由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神话逐渐出现了与宗教、哲学思想融合的趋势。
唐代以后,随着佛教与道教的影响,中国神话的发展也深受其影响。
现代中国神话则更多地与文学、艺术等领域相结合,形成了许多新型神话,如《三体》中的三体文明等。
四、结语中国神话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山海经》作为中国神话的重要文献,记录了众多神秘的生灵和传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神话文化。
通过对中国神话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掘中华民族的灵魂,同时也可以拓宽我们的文化视野。
浅评《山海经》

《山海经》的神话思维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山海经》的文学价值是丰富多样的,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探究。
我们至少可以从神话思维(即原始思维)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原始逻辑的表述方式、人文关怀中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实用主义的审美判断等视角对《山海经》的文学价值予以解读和探究。
本文仅试从第一个视角从三个方面来解读和探究其文学价值,争取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以引起学界对《山海经》文学价值更多的关注和进一步探索。
《山海经》中包含着丰富的神话思维,它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深入地研究神话思维并揭示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从源头上来探讨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形成的深层次影响因素,而且对于弄清各种文学现象形成和发展的规律都有很大帮助。
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神话思维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1.丰富的直观想象力和巨大的想象空问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创作的影响;2.包含丰富神话思维的神话传说常常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素材;3、神话思维的原始生命观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
一、丰富的直观想象力和巨大的想象空间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创作的影响神话思维在许多方面如丰富的直观想象力和巨大的想象空间等都与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和基本特色相契合,神话思维的主要文化成果——神话传说从内容到形式,从表现手法到创作手法都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着重表现作者个人主观世界对事物的感受,这些作品表现出来的丰富的主观想象和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与神话思维是一脉相承的。
如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作品中无不充满奇幻瑰丽的想象。
在《离骚》中诗人在现实叙述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和幻想。
诗人忽而到了天国的门前,忽而到了世界的屋顶,忽而又到了西极的天边,上天下地去追求他的理想。
两次远逝中都有十分壮丽而浪漫的场景: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山海经神话探源的文献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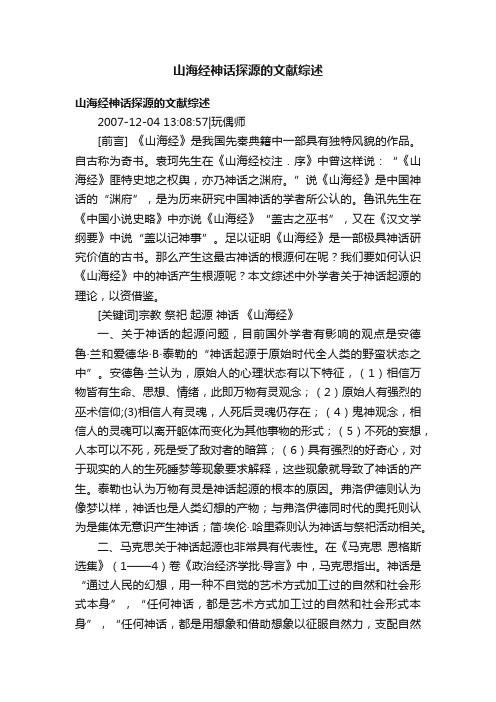
山海经神话探源的文献综述山海经神话探源的文献综述2007-12-04 13:08:57|玩偶师[前言] 《山海经》是我国先秦典籍中一部具有独特风貌的作品。
自古称为奇书。
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序》中曾这样说:“《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亦乃神话之渊府。
”说《山海经》是中国神话的“渊府”,是为历来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所公认的。
鲁讯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亦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又在《汉文学纲要》中说“盖以记神事”。
足以证明《山海经》是一部极具神话研究价值的古书。
那么产生这最古神话的根源何在呢?我们要如何认识《山海经》中的神话产生根源呢?本文综述中外学者关于神话起源的理论,以资借鉴。
[关键词]宗教祭祀起源神话《山海经》一、关于神话的起源问题,目前国外学者有影响的观点是安德鲁·兰和爱德华·B·泰勒的“神话起源于原始时代全人类的野蛮状态之中”。
安德鲁·兰认为,原始人的心理状态有以下特征,(1)相信万物皆有生命、思想、情绪,此即万物有灵观念;(2)原始人有强烈的巫术信仰;(3)相信人有灵魂,人死后灵魂仍存在;(4)鬼神观念,相信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而变化为其他事物的形式;(5)不死的妄想,人本可以不死,死是受了敌对者的暗算;(6)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于现实的人的生死睡梦等现象要求解释,这些现象就导致了神话的产生。
泰勒也认为万物有灵是神话起源的根本的原因。
弗洛伊德则认为像梦以样,神话也是人类幻想的产物;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奥托则认为是集体无意识产生神话;简·埃伦·.哈里森则认为神话与祭祀活动相关。
二、马克思关于神话起源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政治经济学批·导言》中,马克思指出。
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任何神话,都是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20世纪上半世纪关于国学书目的争论

20世纪上半世纪关于国学书目的争论“国学研究”论争综述(二)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国学热潮中,《清华周刊》记者最早邀请知名学者开列国学书目,考虑到中国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提出了只需列出最低书目的要求,由于这些书目皆出自名家之手,又广为刊发,对国学研究影响甚大。
但是,正是这些书目却反映出确定国学内涵的难度,国学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成了未解的难题,一直留到了今天。
一、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开列的《国学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来收入其《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论语》、《孟子》、《易经》、《礼记》、《老子》、《墨子》、《庄子》、《荀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论衡》、《抱朴子》、《列子》、《近思录》、《传习录》、《明儒学案》/黄宗羲、《宋元学案》/黄宗羲、《日知录》、《亭林文集》/顾炎武、《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思问录》/王夫之、《颜氏学记》/戴望编、《东原集》/戴震、《雕菰楼集》/焦循、《文史通义》/章学诚、《大同书》/康有为、《国故论衡》/章炳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胡适、《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周礼》、《考信录》/崔述、《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毕沅、《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通志二十略》、《二十四史》、《廿二史札记》/赵翼、《圣武记》/ 魏源、《国朝先正事略》/李元度、《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史通》/ 刘知几、《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
丙、韵文书类《诗经》、《楚辞》、《文选》、《乐府诗集》/郭茂倩编、《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右丞集》、《孟襄阳集》、《韦苏州集》、《高常侍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李义山集》、《王临川集》、《苏东坡集》、《元遗山集》、《陆放翁集》、《唐百家诗选》/王安石选、《宋诗钞》/吕留良钞、《清真词》/周美成、《醉翁琴趣》/欧阳修、《东坡乐府》/苏轼、《屯田集》/柳永、《淮海词》/秦观、《樵歌》/朱敦儒、《稼轩词》/辛弃疾、《后村词》/刘克庄、《石道人歌曲》/姜夔、《碧山词》/王沂孙、《梦窗词》/吴文英、《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
中国_山海经_研究述略_胡远鹏

第3期收稿日期:2005-10-13作者简介:胡远鹏(1947-)男,湖北武汉人,教授。
一《山海经》研究的历史和所达到的学科水平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山海经》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自古号称“奇书”。
全书仅3万1千余字,一般认为,它却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历法、气象、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考古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等方面的诸多内容,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一部上古世界大观。
由于它保存有上古社会丰富的历史资料,因此,它是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
但是,《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内容,还有很多不为后世读者(包括今天的研究者)所理解,常被斥为怪诞不经,连司马迁也叹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班固在《汉书・张骞传》赞语中,就更加上“放哉”(荒唐)的判断词。
王充在《论衡・谈天》中也说:“《山海经》、《禹纪》,虚妄之言。
”“《禹纪》、《山经》、《淮南・地形》,未可信也。
”在儒家的排斥下,《山海经》一直不被人们所重视,也少有人过问。
说《山海经》具有“独特风格”,别的且不论,仅从其性质和类属看,古来即众说纷纭。
汉代刘秀(歆)在其《上<山海经>表》中,最早认定它是一部地理书。
刘秀曾指出:《山海经》“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
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
”《隋书・经籍志》以后不少史书,也把它列入地理类。
《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数术类刑法家之首,与《相人》,《相六畜》之类的巫卜星相之书混在一起,《宋史・艺文志》亦将之列入五行类。
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称它为专讲神怪之书,即“古之语怪之祖”。
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它是最古的小说,云:“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
……诸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
核实定名,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论现阶段《山海经》研究

论现阶段《山海经》研究胡远鹏《山海经》研究有年矣。
自晋郭璞注《山海经》以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千余年间,《山海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只限于浅表层次上,正如袁珂先生所言,“山而在山川古今异同”。
现阶段的《山海经》研究,从地理范围上说扩展到世界圈,从内容上说则提出了“信史”说,从研究方法上说则与其他学科开始接轨。
以上三方面,则构成了现阶段《山海经》研究的特征和重点内容《山海经》,特征,世界圈,信史,接轨论现阶段《山海经》研究胡远鹏摘要《山海经》研究有年矣。
自晋郭璞注《山海经》以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千余年间,《山海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只限于浅表层次上,正如袁珂先生所言,“山而在山川古今异同”。
现阶段的《山海经》研究,从地理范围上说扩展到世界圈,从内容上说则提出了“信史”说,从研究方法上说则与其他学科开始接轨。
以上三方面,则构成了现阶段《山海经》研究的特征和重点内容。
关键词《山海经》特征世界圈信史接轨中图法分类号K203近年来,《山海经》这一有重要价值的中华文化瑰宝,日益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当前,这一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加上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等学科都出现了一些新成果,逐渐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合力,为跨学科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今天,揭开它的奥秘成为有志于发掘它的学者的重要课题,而且,其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现在,这些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征和内容主要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一)冲破了原有的地理范围,从中国圈、亚洲圈,进而扩展到世界圈。
《山海经》记载的地理范围究竟有多大?换言之,《山海经》记载的究竟是中国文化圈、亚洲文化圈抑或世界文化圈?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古今中外学者都没有能够予以彻底解决的问题,堪称“世界难题”。
但是,有这样几种基本观点。
《山海经》特别是其中的《山经》记载的主要是中国本土上的事物,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持此说,而吴承志则认为超越了现今国界到达了朝鲜、日本、前苏联、蒙古、阿富汗等邻国,法国学者维宁则更进一步认为到达了北美洲、中美洲。
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一)

20 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一)【内容纲要】 20 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队伍不断扩大,门派特点逐渐光亮且形成合力,不但在《山海经》的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年代、《山海经》的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方面获取一些打破,而且在《山海经》科学价值、《山海经》经文破译等新论题方面也获取重要成就。
【要点词】 20 世纪 / 《山海经》 / 研究 / 回顾【正文】《山海经》堪称天下奇书。
它是一部拥有独到风格的中华古代典籍,今后书内容波及之广泛,文化聚积之深邃,历代学者研究成就之丰富,以及此刻《山海经》影响之不断扩大等方面进行察看,能够说,把《山海经》称之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之瑰玉是当之无愧的。
一 20 年纪以来,从事《山海经》研究的学者逐渐增添,成就迭出。
据不完好统计,本世纪(截止各正式学刊公布论题含有“山海经”或其篇目名的学术论文就有 172 篇,其中外国学者 6 篇。
至于论题未直接注明书名而波及《山海经》研究的则更多。
专着的推出标志住《山海经》研究的深入。
1980 年和 1985 年,袁珂《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先后由上海古籍初版社初版, 90年代初版的《山海经》研究专着则有徐显之《山海经探原》(武汉初版社1991 年初版)和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初版社 1992 年初版)。
《山海经校注》包括《山海经山经柬释》和《山海经海经新释》两部份,后附“《山海经》叙录”,全录汉刘歆(秀)《上〈山海经〉表》、晋敦璞《注〈山海经〉叙》、旧本《山海经》目录和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另附“所据版本及诸家旧经书目”与“引用书目”,书后还有《山海经》索引,由张明华编。
袁珂《山海经校注》的主体部分是《山经柬释》和《海经新释》,后者完成于 1963 年,“重视对神话传说部分的说明,搜罗丰富,征引详博,很有发明,其他部分也作了诠解和校勘” (注:《〈山海经〉校注》初版说明,上海古籍初版社 1980 年版。
)。
《山经柬释》完成于 80 年代。
叶舒宪_山海经_研究综述_唐启翠 (1)

第29卷 第2期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 129N o 122006年04月Journal o fY angtze U n i versity(Soc i a l Sc i ences)A pr 2006收稿日期:20050928作者简介:唐启翠(1975)),女,湖北襄樊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民间文学与古典文学研究;胡滔雄(1983-),男,湖南娄底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学生。
叶舒宪5山海经6研究综述唐启翠 胡滔雄(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海南海口570228)摘 要:对于5山海经6的研究,已经有了两千余年的历史。
在众多的研究者当中,叶舒宪先生立足于文化人类学大视野,运用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5山海经6进行了知识考古性的思想发掘与现代性的意义诠释,为5山海经6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关键词:叶舒宪;5山海经6;神话政治地理学;跨文化阐释分类号:I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06)02-0019-05人们大多以实证方法去考证5山海经6。
这种/纯粹实证0的研究方式,不仅未能证实5山海经6的真实面貌,反而把5山海经6研究引入无限纷争之中。
在众多的研究者当中,文化人类学家叶舒宪先生是一位特别引人注目的学者,他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把5山海经6研究推向了一个新境界。
一、叶舒宪5山海经6研究的主要内容1.5山海经6是奇书中的奇书叶舒宪先生说:/我们若想在奇书中寻奇,那么就非5山海经6莫属。
0[1]首先,它充满被儒家拒斥的/怪力乱神0,却能从上古保留至今;其次,5山海经6奇特到带有正统思想的大史家如司马迁都/不敢问津0,不敢言说的地步;再次,5山海经6之奇,使最渊博、最聪明、最有/考据癖0的学者都望而生畏,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上古典籍中注解诠释得最少,而疑问和难题又最多的一本书;最后,由于它的奇僻荒奥,这个书名本身也成了/奇谈怪论0或/子虚乌有0的同义语,成了/真实可信0的对立面,就跟5天方夜谭6这部书名从专有名词变成泛称一样,连近世淹雅博识君子如梁启超,也疑心5山海经6不是中国人写的书,而是古时外国地理著作的/汉译本0。
关于《山海经》研究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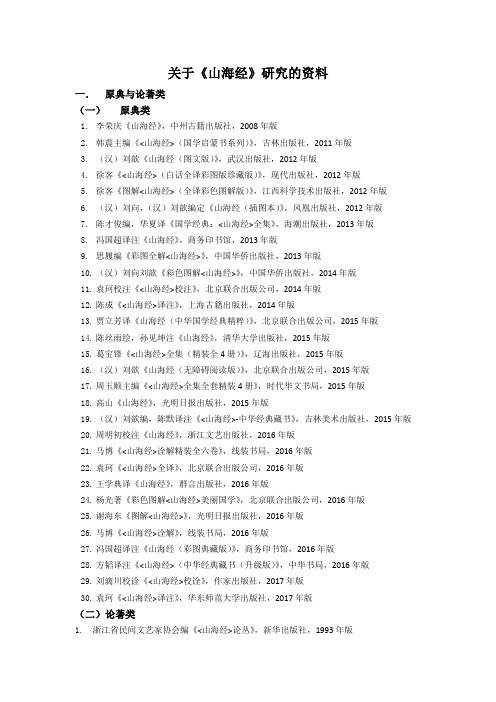
关于《山海经》研究的资料一.原典与论著类(一)原典类1.李荣庆《山海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2.韩震主编《<山海经>(国学启蒙书系列)》,吉林出版社,2011年版3.(汉)刘歆《山海经(图文版)》,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4.徐客《<山海经>(白话全译彩图版珍藏版)》,现代出版社,2012年版5.徐客《图解<山海经>(全译彩色图解版)》,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6.(汉)刘向,(汉)刘歆编定《山海经(插图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7.陈才俊编,华夏译《国学经典:<山海经>全集》,海潮出版社,2013年版8.冯国超译注《山海经》,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9.思履编《彩图全解<山海经>》,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10.(汉)刘向刘歆《彩色图解<山海经>》,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11.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12.陈成《<山海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13.贾立芳译《山海经(中华国学经典精粹)》,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14.陈丝雨绘,孙见坤注《山海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15.葛宝锋《<山海经>全集(精装全4册)》,辽海出版社,2015年版16.(汉)刘歆《山海经(无障碍阅读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17.周玉顺主编《<山海经>全集全套精装4册》,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版18.高山《山海经》,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19.(汉)刘歆编,陈默译注《<山海经>-中华经典藏书》,吉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20.周明初校注《山海经》,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21.马博《<山海经>诠解精装全六卷》,线装书局,2016年版22.袁珂《<山海经>全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23.王学典译《山海经》,群言出版社,2016年版24.杨光著《彩色图解<山海经>美丽国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25.谢海东《图解<山海经>》,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26.马博《<山海经>诠解》,线装书局,2016年版27.冯国超译注《山海经(彩图典藏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28.方韬译注《<山海经>(中华经典藏书(升级版)》,中华书局,2016年版29.刘滴川校诠《<山海经>校诠》,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30.袁珂《<山海经>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二)论著类1.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山海经>论丛》,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2.宫玉海,杜宇主编《<山海经>与华夏文明论集》,大禹及夏商周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版3.张春生著《<山海经>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4.阿菩《<山海经>密码》,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5.阿菩《<山海经>密码2》,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6.陈连山《<山海经>学术史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7.和兴文化编《青少年品读国学精粹<山海经>》,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8.杨靖,李昆仑编《品读国学经典<山海经>》,敦煌文艺出版社9.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10.刘瑞明,作著《<山海经>新注新论》,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二.论文类(一)关于《山海经》神怪的研究1.毛文志《<山海经>的神祗形象》,《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2.陈连山《神怪内容对于<山海经>评价的影响》,《民俗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3.宋志玛《谈<山海经>中的蛇形象》,《衡水学院院报》,2009年第2期4.陈飞《<山海经>神话形象与当代中国网络玄幻小说研究》,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5.王晶《从“蛇巫形象”探源<山海经>的原属文化系统》,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6.陈富元《谈<山海经>神话物象的类型》,《群文天地》,2011年第9期7.杨建芳《古代玉雕中的神怪世界与<山海经>中的神怪对照》,《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期8.陈帅《<山海经>神怪形象流变研究》,延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9.李婧《<山海经>女性鬼神形象研究与思考》,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10.吕先琼《<山海经>神怪形象的生命意识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11.郑松《浅析<山海经>中的“动物形象”和“人性化”》,《现代交际》,2014年第4期12.马昕露《浅析<山海经>中的神怪形象及神话思维》,《金田》,2014年第7期13.李鹏《<山海经>异兽形象设计》,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14.张帆《<山海经>与《怪奇鸟兽图卷》中的异兽形象对比研究.》,北京服装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15.宋志玛《<山海经>之形象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16.段丽《<山海经>兽形形象变形叙事类型探幽》,《大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17.靳希《<山海经>兽形“神”探析》,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18.柏兰兰《<山海经>神话形象背后的文化内涵》,《科教导刊:电子版》,2015年第20期19.王子龙《基于<山海经>中神怪形象的插画研究与创作》,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20.高洋《<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列析》,《中国民族博览》,2016年第10期(二)关于《山海经》文学价值与特色的研究1.赵沛霖《中国神话的分类与<山海经>的文献价值》,《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2.杨琳《<山海经>“浴日”“浴月”神话的文化底蕴》,《民族艺术》,2002年第3期3.方牧《<山海经>与海洋文化》,《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4.詹子庆《<山海经>和夏史》,《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5.田畦耘《<山海经>中变形神话的文化内涵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6.沈士军《谈<山海经>的信仰民俗及其文学价值》,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7.沈士军《谈<山海经>的神话思维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8.史玉凤,赵新生《<山海经>的海洋小说“母题原型”及其海洋文化特质》,《淮海工学院学报》,2010年8期9.徐非《<山海经>神话分类及其文化意蕴探析》,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10.吴豫娟《中国古代小说史视野下的<山海经>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11.叶舒宪《<山海经>与失落的文化大传统》,《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12.郭立军《<山海经>的地理博物志怪小说特色》,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13.王永,王玲《<山海经>的山水游记特色》,《临沂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14.卢烈炎《初探<山海经>中共工氏与红山文化间的关系》,《青春岁月》,2013年第5期15.梁奇《<山海经>中人猪组合的神人形象及其文化意义》,《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1期16.王玲《<山海经>的山水游记文学特色与审美意蕴》,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17.张永圣《<山海经>中的东夷古史与传说》,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18.金广芸《<山海经>的神话思维》,《鸭绿江月刊》,2015年第12期19.周恬逸《<山海经>文图关系研究》,南京大学,201520.王水香《论<山海经>医药的神话特质及文学意义》,《闽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21.贾子璇《浅论<山海经>的思维特征》,《北方文学旬刊》,2015年第11期22.郭静《<山海经>神话的母题分类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23.徐佳威《文化诗学视域下的<山海经>》,《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24.刘森《<山海经>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山海经》,2016年第4期25.刘园婧《从文化背景看<山海经>性质转变的动因》,《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26.荣华《浅论<山海经>的文学特色》,《未来英才》,2016年第10期27.薛正英《论<山海经>神话英雄形象及文化精神》,《现代交际》,2016年第3期28.张岩,张晔《<山海经>独特审美视角论析》,《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院报》,2016年第7期29.王艳玲《<山海经>中神话所表达的思想》,《山西青年》,2017年第3期(三)关于《山海经》地理文化的研究1.顾颉刚《<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2.翁银陶《<山海经>产于楚地七证》,《江汉论坛》,1984年第2期3.张箭《从自然地理学辨<山海经>的地域范围》,《大自然探索》,1996年第3期4.张步天《<山海经>“南西北东”顺序辨》,《湖南城市学院学报》,1998第3期5.刘付靖《<山海经>若干地名新解》,《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6.张步天《20世纪<山海经>地域范围的讨论》,《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7.张步天《从<山海经>看青海海东地区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青海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8.刘树人《<山海经>中的“东山”区位地理考古研究》,《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04年第1期9.金荣权《<山海经>作者应为巴蜀人》,《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10.杨平,韦东《<山海经>地域之谜》,《故事世界》,2005年第9期11.丁振宗《<山海经>地貌应属的年代》,《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6年3月12.李小波,吴晓《中国<山海经>里的蜀山密码》,《中国西部》,2012年第26期13.任玉贵《<山海经>与青海地域文化的新信息新诠释》,《柴达木开发研究》,2014年第1期14.任玉贵《<山海经>与青海地域文化的新发现》,《中国土族》,2014年第4期15.黄亮亮《浅析神话<山海经>的地域性》,《青春岁月》,2015年第12期(四)关于《山海经》对其他事物影响的研究1.刘恭德《试论<山海经>与中国远古气候学史关系的若干问题》,《大自然探索》,1993年第4期2.宁稼雨《<山海经>与中国奇幻思维》,《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3.刘宗迪《<山海经>与上古历法制度》,《民族艺术》,2002年第2期4.蒋南华《<山海经>天文历法浅说》,《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5.刘琴《<山海经>对镜花缘的影响》,《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闫德亮《<山海经>与屈赋关系考》,《中州学刊》,2005年第4期7.李杨《论<山海经>与屈赋中的神话》,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8.陈富元《试论<山海经>二元对应神话思维模式与明清神魔小说》,《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0期9.陈富元《浅析<山海经>的叙事模式和情节解构模式对神魔小说的影响》,《群文天地》,2010年第10期10.陈飞《<山海经>神话形象与当代中国网络玄幻小说研究》,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11.相鲁闽《<山海经>及其对先秦医学的影响》,《河南中医》,2012年第2期12.练晓琪,纪晓建《<山海经>对古代中医学著作影响管窥》,《内蒙古中医药》,2012年第9期13.李姝,刘莎《从<山海经>看白蛇的性恶之源及其最初流变》,《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14.王焕然《试论<山海经>对谶纬的影响》,《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15.叶舒宪《<山海经>与白玉崇拜的起源》,《民族艺术》,2014年第6期16.李雨涵《<山海经>对汉赋的影响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17.胡宸《<山海经>对汉大赋自然环境描写的影响及原因》,《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18.孟瑀《<山海经>对汉画像中“昆仑”山脉的影响》,《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第2期19.朱丽卉《<山海经>中神话英雄永续生存意识及其影响研究》,云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20.刘宗迪《<山海经>与古代朝鲜的世界观》,《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6期21.郑凯歌《<山海经>对诛仙的影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22.罗茜《<山海经>与原始宗教关系再探究》,《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32期23.陈红梅《<山海经>涉药内容分类思想与编纂体例探讨》,《中医文献杂志》,2016年第3期(五)关于《山海经》的背景的研究1.苏茂德《论<山海经>的历史背景》,《西安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2.叶舒宪《<山海经>大荒经的观念背景》,《现代中文学刊》,2000年第4期3.陈连山《从文化背景谈<山海经>学史上的一个问题》,《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4.徐佳俐《生态批评视野下的<山海经>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刘园婧《从文化背景看<山海经>性质转变的动因》,《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六)关于《山海经》作者的研究1.孙致中《<山海经>的作者及著作时代》,《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2.李行之《<山海经>作者考》,《求索》,1989年第6期3.杨兴华《从祖先崇拜和楚俗看<山海经>作者的族别》,《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4.王红旗《<山海经>作者之谜》,《中学语文:教师版》,2000年第12期5.张步天《20世纪<山海经>作者和成书经过的讨论》,《益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22期6.唐世贵《<山海经>作者及时地再探讨》,《江汉学术》,2003年第6期7.唐世贵《<山海经>成书时代及作者新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4期8.杨兴慧,罗大和《<山海经>之作者析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0期。
《山海经》神话研究综述

《山海经》神话研究综述摘要:20世纪初西方“神话”概念的传入真正使《山海经》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其后老一辈学者们运用人类学等新的学术理论为《山海经》的神话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其七八十年代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近年来结合考古材料尤其是汉画像石进行《山海经》的神话研究越来越成为热点,考古材料文化解释的不确定性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大挑战。
关键词:山海经;神话;综述;考古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209-03《山海经》全书仅3万1千余字,却涉及神话、地理、历史、方物、民族、民俗、天文、历法、宗教诸方面,被称为中国上古典籍中的“奇书”。
但以前《山海经》因其内容怪诞不经,多被当作“虚妄之言”。
历史上最早提到《山海经》的是司马迁,因他对其可信性表示了明确怀疑,这对《山海经》在华夏文明传统中的地位产生了根本影响,自汉刘秀整理作《上〈山海经〉表》、晋郭璞首次为注后,一千年间问津者寥寥,直到明清时才再次有学者进行校注释义。
其后如蒙文通、王国维、胡厚宣、顾颉刚诸先生的研究则开始使学界重新定位山海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地位。
至于《山海经》的研究方向,如郦道元、自隋唐至宋各史志、清毕沅等都视其为地理书,一直也有很多学者热衷于其地理考证。
但是尽管《山海经》的地理学价值不可否认,其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仍存在局限性,而且或多或少地回避了地理描述中夹杂的大量神怪内容。
真正使《山海经》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却是20世纪初西方“神话”概念的传入以及人类学、神话学等现代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山海经》中的大量神怪内容不再遭到史学家的诟病反而成为当代学者所从事的“中国神话”或“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基石。
一、20世纪初到70年代的《山海经》神话研究关于20世纪开始以来我国神话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参考1994年出版的马昌仪的《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作为包含中国“原始神话”最多的古代典籍《山海经》,正是神话研究的重要部分。
山海经神话研究综述

各种鬼魂和妖怪,如女鬼、夜叉等。
精怪
幻兽
自然界的精灵和妖怪,如山精、水怪等。
具有神奇力量的幻想生物存
神灵和怪物在某些情况下相互依存,如一些神灵需要怪物作 为守护神或者助手。
对立冲突
神灵和怪物有时也会产生对立和冲突,因为怪物会威胁到神 灵的权威和秩序。
04
这些神话故事不仅是古代中国 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传承和 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研究山海经神话有助于深入了 解中国古老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
供重要支持。
研究目的与方法
研究目的
通过对山海经神话的深入研究,探讨其文化价值和影响,为 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研究方法
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和专家访谈等多种手段,对山海经神话进 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山海经神话传说的文化内涵
自然崇拜与原始宗教
自然崇拜
山海经神话中存在着大量的自然神祇,如日神、月神、风神等,这些神祇在 自然力量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因此人们便创造了这些神祇,以表达对自然力 量的敬畏和崇拜。
原始宗教
山海经神话中的许多神祇都具有宗教色彩,如西王母、东王公等,这些神祇 被视为能够保佑人们平安、健康的神灵,人们通过祭祀、朝拜等方式与这些 神祇建立联系,以期获得庇护和保佑。
研究内容与范围
研究内容
通过对山海经神话的起源、发展和影响进行研究,重点探讨山海经神话所蕴 含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研究范围
研究范围涉及山海经神话的各个方面,包括神话的起源、发展和传承,以及 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等。
02
山海经神话的起源与流变
起源与形成
古代先民的原始信仰
在原始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不足,产生了各种神秘的信 仰和神话。这些信仰和神话在《山海经》中得到了反映。
【2016年】《山海经》的神话地理【古代文学论文】

古代文学论文-《山海经》的神话地理一.引言《山海经》既是一部挑战性的古书,又是我们民族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的渊薮。
在古代,它以异端邪说之渊薮的性质对"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统思想方式提出挑战,对通行的经史子集图书分类法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在现代,它又给既定的学科划分和专业界限造成很大的麻烦。
无论是中国古时候的知识分类还是现代国际通行的学科体制,都无法使它对号入座。
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方志学家,科学史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文学批评家,乃至思想史家均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但谁也无法将它据为己有。
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科,却又同时属于所有学科。
一般说来,20世纪以前,国人较多地把《山海经》视为地理著作(《辞海》"地理学"条目下云:"地理学一词始见于我国《易经.系辞》和古希腊埃拉托色尼《地理学》,我国最古的地理书籍有《禹贡》,《山海经》。
")而自1903年西方的"神话"概念假道日本传入中国,人们较为普遍的把它看成是上古的神话著述。
还可以再进一步追问:如果神话是幻想的产物,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又是怎样和作为科学理性产物的地理学统一呢?《山海经》的构成,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它之所以出现,和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
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神话政治地理书。
更确切的讲,它以山川地理志的外观表现着现实世界与神话时空交织的内容,而这种虚实相间,半真半假的空间图式之实质,则是服务于功利目的的宗教政治想象图景。
只要从祭政合一(或政教合一)的远古社会的政治特色着眼,《山海经》的巫书性质和功能便容易理解了。
那就是为走向一统的文化权力话语提供神权政治的空间证明,通过对各地山神祭祀权的局部认识和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的远近山河实施一种法术性的全盘控制。
二.地理与政治之缘地理学作为人类对现实生存空间的理性认识结果,在西方学术体系中一直占有着重要位置。
《山海经》之当代揭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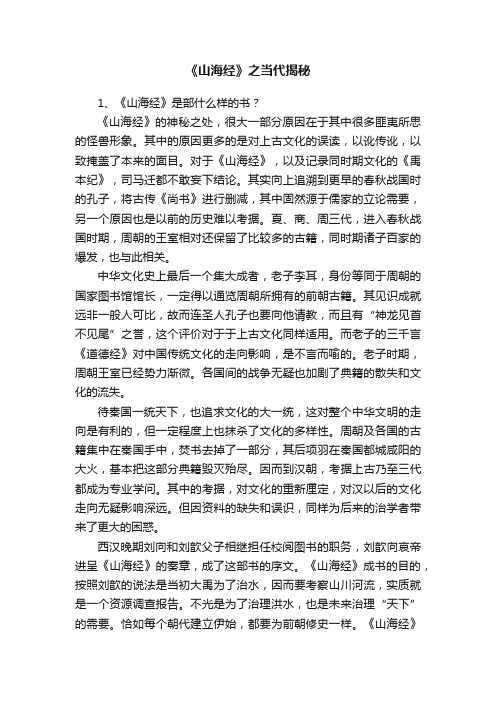
《山海经》之当代揭秘1、《山海经》是部什么样的书?《山海经》的神秘之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中很多匪夷所思的怪兽形象。
其中的原因更多的是对上古文化的误读,以讹传讹,以致掩盖了本来的面目。
对于《山海经》,以及记录同时期文化的《禹本纪》,司马迁都不敢妄下结论。
其实向上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战国时的孔子,将古传《尚书》进行删减,其中固然源于儒家的立论需要,另一个原因也是以前的历史难以考据。
夏、商、周三代,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的王室相对还保留了比较多的古籍,同时期诸子百家的爆发,也与此相关。
中华文化史上最后一个集大成者,老子李耳,身份等同于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一定得以通览周朝所拥有的前朝古籍。
其见识成就远非一般人可比,故而连圣人孔子也要向他请教,而且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誉,这个评价对于于上古文化同样适用。
而老子的三千言《道德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老子时期,周朝王室已经势力渐微。
各国间的战争无疑也加剧了典籍的散失和文化的流失。
待秦国一统天下,也追求文化的大一统,这对整个中华文明的走向是有利的,但一定程度上也抹杀了文化的多样性。
周朝及各国的古籍集中在秦国手中,焚书去掉了一部分,其后项羽在秦国都城咸阳的大火,基本把这部分典籍毁灭殆尽。
因而到汉朝,考据上古乃至三代都成为专业学问。
其中的考据,对文化的重新厘定,对汉以后的文化走向无疑影响深远。
但因资料的缺失和误识,同样为后来的治学者带来了更大的困惑。
西汉晚期刘向和刘歆父子相继担任校阅图书的职务,刘歆向哀帝进呈《山海经》的奏章,成了这部书的序文。
《山海经》成书的目的,按照刘歆的说法是当初大禹为了治水,因而要考察山川河流,实质就是一个资源调查报告。
不光是为了治理洪水,也是未来治理“天下”的需要。
恰如每个朝代建立伊始,都要为前朝修史一样。
《山海经》这个资源报告,同样地起到了历史记载的作用。
《五藏山经》记载的是黄帝到尧、舜、禹时期,以中原为中心的山川河流以及风土人情等。
远古第一部国土资源调查报告:《山海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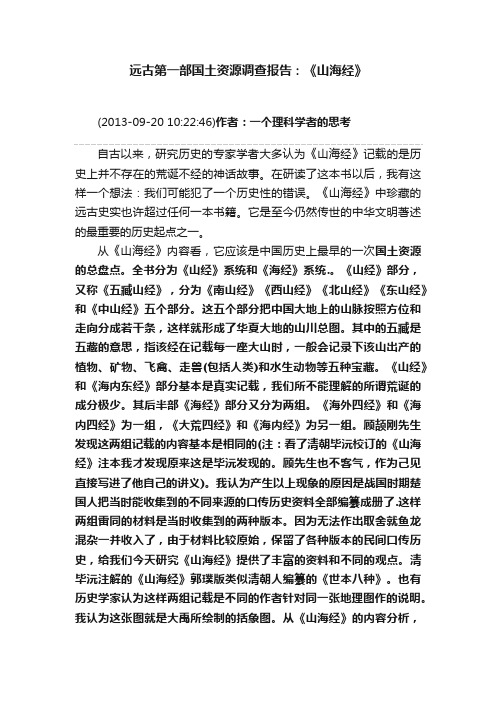
远古第一部国土资源调查报告:《山海经》(2013-09-20 10:22:46)作者:一个理科学者的思考自古以来,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大多认为《山海经》记载的是历史上并不存在的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
在研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可能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山海经》中珍藏的远古史实也许超过任何一本书籍。
它是至今仍然传世的中华文明著述的最重要的历史起点之一。
从《山海经》内容看,它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国土资源的总盘点。
全书分为《山经》系统和《海经》系统.。
《山经》部分,又称《五臧山经》,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五个部分。
这五个部分把中国大地上的山脉按照方位和走向分成若干条,这样就形成了华夏大地的山川总图。
其中的五臧是五藏的意思,指该经在记载每一座大山时,一般会记录下该山出产的植物、矿物、飞禽、走兽(包括人类)和水生动物等五种宝藏。
《山经》和《海内东经》部分基本是真实记载,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所谓荒诞的成分极少。
其后半部《海经》部分又分为两组。
《海外四经》和《海内四经》为一组,《大荒四经》和《海内经》为另一组。
顾颉刚先生发现这两组记载的内容基本是相同的(注:看了清朝毕沅校订的《山海经》注本我才发现原来这是毕沅发现的。
顾先生也不客气,作为己见直接写进了他自己的讲义)。
我认为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是战国时期楚国人把当时能收集到的不同来源的口传历史资料全部编纂成册了.这样两组雷同的材料是当时收集到的两种版本。
因为无法作出取舍就鱼龙混杂一并收入了,由于材料比较原始,保留了各种版本的民间口传历史,给我们今天研究《山海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不同的观点。
清毕沅注解的《山海经》郭璞版类似清朝人编纂的《世本八种》。
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样两组记载是不同的作者针对同一张地理图作的说明。
我认为这张图就是大禹所绘制的括象图。
从《山海经》的内容分析,这种可能性极大。
虽然括象图今天失传了,但是依据《山海经》的叙述我们可以复原这张图。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一)【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流派特征逐渐明朗且形成合力,不仅在《山海经》的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年代、《山海经》的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方面取得一些突破,而且在《山海经》科学价值、《山海经》经文破译等新论题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
【关键词】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正文】《山海经》堪称天下奇书。
它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华古代典籍,从此书内容涉及之广泛,文化沉积之深厚,历代学者研究成果之丰硕,以及当今《山海经》影响之不断扩大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说,把《山海经》称之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之瑰玉是当之无愧的。
一20年纪以来,从事《山海经》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成果迭出。
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截至各正式学刊发表论题含有“山海经”或其篇目名的学术论文就有172篇,其中外国学者6篇。
至于论题未直接标明书名而涉及《山海经》研究的则更多。
专着的推出标志着《山海经》研究的深化。
1980年和1985年,袁珂《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出版的《山海经》研究专着则有徐显之《山海经探原》(武汉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山海经校注》包括《山海经山经柬释》和《山海经海经新释》两部份,后附“《山海经》叙录”,全录汉刘歆(秀)《上〈山海经〉表》、晋敦璞《注〈山海经〉叙》、旧本《山海经》目录和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另附“所据版本及诸家旧经书目”与“引用书目”,书后另有《山海经》索引,由张明华编。
袁珂《山海经校注》的主体部分是《山经柬释》和《海经新释》,后者完成于1963年,“着重对神话传说部分的注释,搜罗丰富,征引详博,颇有发明,其它部分也作了诠解和校勘”(注:《〈山海经〉校注》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
《山经柬释》完成于80年代。
袁氏在序中指出的“《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注:《〈山海经〉校注》序。
)是对《山海经》一书内容的概括,很有见地。
《山海经校译》的最大成果在于校勘方面。
作者认为“须首先整理出一个《山海经》的新校本来”(注:《〈山海经〉校译》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
该书校勘是从十个方面着手的,即错、脱、衍、倒、经文入注、注入经文、脱简和错简、它书窜入、篡改、其它。
在校勘的基础上,此书按郭璞注《山海经》18卷顺序作了全译。
《山海经》研究的地理学派、历史学派和文学神话派发端甚早。
地理学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主要记述地理事物的著作,历史学派认为《山海经》是反映中国上古时代的史籍,文学神话派认为此书是神话汇集。
本世纪中,由于不同学者对《山海经》性质的认定和研究侧面各有不同,各学派的流派特征逐渐明朗。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从事自然科技史研究的学者也参加治《山海经》学人队伍,他们的研究侧重于《山海经》科学价值和经文破译。
近年来,各学派已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共识,形成了研究合力。
为适应《山海经》研究发展形势,1983年12月在成都举办了“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有10多个省区的60多位学者参加。
这是第一次《山海经》专题研究会议,标志着《山海经》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后,1986年1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山海经新探》,该论文集共收论文27篇,“大致依照地理、民族、神话、科技、综论的顺序进行编排”,“各篇论文均从不同角度对《山海经》及其所反映的中国古史诸问题进行了探索,对于研究和了解我国上古的社会和自然状况均有参考意义”(注:《〈山海经〉新探》前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
二20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在本书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年代、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上取得很大进展。
关于《山海经》的性质,学者的论点很不一致。
30年代前,几个主要论点先后提出。
廖平《〈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载《地学杂志》14卷第3期、第4期,1923年)认为《山海经》是《诗经》之传注,这大概是本世纪最早涉足《山海经》性质讨论的论文。
著名的《山海经》研究日本学者小川琢治重提史地书说,他在《〈山海经〉的考证及补遗》(《支那历史地理研究》,1928年)一文中指出:“《山海经》一书远比一向认为金科玉律之地理书《禹贡》为可靠,其于中国历史及地理之研究为唯一重要之典籍”。
鲁迅则提出巫书说,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
80年代以后,《山海经》性质的讨论更为活跃。
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学者主张《山海经》是一部“侧重反映上古历史的珍贵古籍,虽有许多神话传说,但应与史实区分开来,通过此书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由原始蒙昧向高级阶段渐次前进的发展总过程”(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
)。
胡钦甫《从〈山海经〉的神话中所得到的古史观》(《中国文学季刊》1928年8月)、朱希祖《〈山海经〉内大荒海内二经古代帝世系传说》(《民俗》第116期—118期,1933年5月)、邓慕维《〈山海经〉古史考》(《励学(山东大学)》第4期,1934年)和80年代发表的常征《〈山海经〉及其史料价值》(《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等文都倾向于认定《山海经》为历史书。
侧重于探讨《山海经》地理价值或认定其为地理书的学者仍占多数。
主要论文有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史学论丛》第1期,1934年)、徐旭生《〈山海经〉的地理意义》(《地理知识》1955年第8期)、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等。
刘起釪认为,“保存了丰富的地理素材而附丽以高度神话的《山海经》,它开了幻想的一派”,但“不能把这一派这些著作认真当作严肃的地理书看待”(注:《〈禹贡〉作者》,《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
近年一些探讨《山海经》地域范围的学者大多也主张地理书说。
支持《山海经》巫书说的学者也不少,在1983年成都学术会议上,有些学者又提出了这一主张。
仅1985年一年就发表了三篇明确主张巫书说的论文:翁银陶《〈山海经〉性质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孙致中《〈山海经〉的性质》(《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第3期)。
关于《山海经》篇目与版本讨论的论文也很多,主要有蒋经三《〈山海经〉篇目考》(《语历所周刊百期纪念号》,1929年)、贺次君《〈山海经〉之版本及关于〈山海经〉之著述》(《禹贡》第1卷第10期,1934年)、周士琦《论元代曹善抄本〈山海经〉》(《历史文献集刊》第1集,1980年9月)等文,袁珂《〈山海经〉产生地域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也讨论了《山海经》篇目。
通过讨论,目前对《山海经》篇目的认定已接近取得共识,至于《山海经》版本学探讨尚处于初始阶段。
关于《山海经》作者,论者的分歧很大。
何观洲主张邹衍县《山海经》的作者(《〈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顾颉刚等主张非一人之所作,作者为秦人(如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
”)袁珂等主张《山海经》作者为楚人或楚地人(如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吕子方、蒙文通等认为有巴蜀人的手笔(如吕子方《山海经杂记》等)。
另外,卫聚贤主张“战国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进而推演为墨子弟子随巢子写定;李行之认为《山海经》作者是楚国南部一位少数民族士人,其籍贯之地望为今湖南省常宁县(《〈山海经〉作者考》,《求索》1989年第6期);还有人主张《山海经》有北方齐国、燕国人的手笔。
讨论《山海经》成书时代的论文很多,主要有何定生《〈山海经〉成书时代》(《语历所周刊》第2卷第20期,1928年)、陆侃如《论〈山海经〉著作年代》(《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翁银陶《〈山海经〉作于楚怀王末年考》(《求索》1987年第5期)。
通过论讨,大多数学者认定的《山海经》成书时间在东周至汉代之间。
不过,也有人认为“本书成书年代可上溯至夏商。
”有的认为“《山海经》的相对年代以儒家所说尧舜时期较为准确,即夏代建立以前,约在公元前21世纪”(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
)。
《山海经》地理范围的讨论十分活跃,众说迭起且相差惊人。
大致说来,本世纪发表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传统的华夏说,二是局部小区说,三是世界圈说。
传统的华夏说认为,《五藏山经》的地理范围,“从所提到的山名来看,东边达到东海之滨的会稽山,西边提到了新疆的天山;从所描述的地理环境来看,北边似乎越过了蒙古高原,到了西伯利亚,南边似乎到了江南”(注:赫维人:《浅谈〈五藏山经〉》,《云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
《海经》描述的地理范围则可远及朝鲜、日本、中南半岛和阿富汗、俄罗斯等邻国。
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对《山海经》的地理内容作了详细的考订,如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卫挺生《南山经地理考释》等五篇(载《东方杂志》1969年至1973年)等就是如此。
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域范围很小,只及中国境内某一局部地域。
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认为《海经》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东省中南部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域。
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一书认为,《山海经》记述的是云南西部东经101度以西,北纬23度以北纵谷地区的地理,书中的古昆仑山即今云南纳溪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云县县城以北、高黎贡山以东、金沙江以南横断山脉地区。
作者还利用地图比例,换算出《山海经》里距为今日华里的3.4%左右(注: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和局部小区说相反,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理事物远及非洲、欧洲、大洋洲和美洲,不少国外学者也持这一观点。
国人《山海经》地理范围世界圈说可能发端于梁启超、苏雪林的中亚西亚说,本世纪7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认定《山海经》某些部分相当准确地描写了北美大陆,以及近年来在南美洲等地发现中华古文化遗物从而推论中国人最早到达美洲,这些事实支持并推动了世界圈说的提出。
梁启超很早就曾提出“此经盖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注: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教与中国文学》,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
)。
苏雪林认为《山海经》所述海内外的海实际指黑海、里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山海经》“是两河流域的地理书”,在战国时由波斯学者携来中国(注:《屈原与〈九歌〉》,《屈原评传》1978年版第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