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其昌山水画“南北宗论”
董其昌“南北宗说”论

董其昌“南北宗说”论作者:梁少膺来源:《美术界》2015年第11期【摘要】中国山水画学到了明董其昌时代,出现了以禅喻画的“南北宗”之说。
董其昌以唐之禅分两宗比拟当时的青绿、水墨两派画系,可谓开中国画学流派分析之先河。
北宗重渐悟,南宗重顿悟。
北宗画家(以李思训为始)画法谨细,风格粗硬;南宗画家(以王维为始)画法清逸,风格淳秀。
北刚南柔,是董其昌对山水画分宗立派的标准。
董其昌这一理论的另一创见,是旨在发扬南宗画(文人画)天然淡雅、逸笔草草的风格。
故南宗笔墨成为了中国画学之核心,使它的表现最大限度地挣脱了写物的束缚,树立了绘画作品中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
因此,董其昌的南北宗说,即使到了今天,于当代中国山水画的创作乃至当代艺术的发展仍具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禅宗;董其昌;南北宗;文人画;笔墨一、“南北宗说”的提出中国的山水画学,到了明代,出现了“南北宗”之说。
董其昌《容台别集·画旨》(亦见于《画禅室随笔》):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
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
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四大家”。
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
这是以禅家的宗法来比喻画家的宗派,此说又见于莫是龙的《画说》与陈继儒的《偃曝余谈》。
董其昌和莫是龙、陈继儒都是华亭人,彼此相互往来,故他们的画学观念、理论建树与审美趣味基本相同。
明代晚期,董其昌属画坛影响最大的一位领袖人物,因而他的这一理论成为了“南北宗说”的代表。
二、董其昌的禅学思想与“南北宗说”的构建“南北宗”原是禅家的宗派。
禅是梵文“禅那”的略语,意译为“思维修”,即静坐息虑之意。
禅本是佛教的一宗,相传开始是一脉相承的,到了五祖弘忍时分为两宗。
五祖弟子神秀潜心于佛教经典,后随弘忍习禅。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有如下一段话: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
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
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驌,以至马、夏辈。
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躁、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马祖道一)、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
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 (王)维也无间然。
知言哉。
在这段话中,董其昌提出了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影响深远的南北宗的绘画理论,他认为南宗属于文人画的范畴,北宗则以匠人画或行家画为尚,并且崇南抑北。
仙山楼阁图南宋赵伯驹董其昌区分南北宗并不是按照地域上的南北,而是根据画家的身份、画法、风格为标准的。
北宗画家多为皇家宗室或宫廷画家,其绘画多以着色山水、界画为主。
技法上北宗方刚谨严,体势尚奇峭突兀,多块面结构,多用泼墨法,笔墨运行则往往需要发力且迅走疾行。
北宗适合表现多石且石质坚硬顽重的山体,皴法多为斧劈皴或其变体。
万壑松风图南宋李唐南宗的画家多具有文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绘画多以水墨为主,不拘于常法。
技法上多为线型结构,平淡混穆,圆柔疏散,自如随意,皴法多为披麻皴及其变体,适合表现多土且植被较丰厚的山体。
天池山壁图元代黄公望南北宗论是有很大的理论缺陷的,其崇南抑北的思想也是值得商榷的,但其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
与南宗山水相比,北宗山水较多地受到理性精神的制约,自律性的特征比较突出,画家受到各种技法规范的强力约束。
北宗山水的技术难度是古代画家所公认的。
由于北宗山水画家的职业化特征所决定,他们很难像文人画家那样对创作实践进行理论的总结,也很难对自己的审美追求加以阐说和辩解,只好一任他人的否弃、贬低或冷落,使许多精华也被当成糟粕。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
华山图册明代王履近现代以来,徐悲鸿等人对南北宗论的过分贬低也是不可取的。
董其昌“南北宗”画论的理论价值及其影响

3 “ 南宗 ” 与“ 北宗” 艺 术 特 色 的 区别
“ 南 北宗 ” 论 更 能 突 出“ 南宗” 与“ 北宗” 的特 征 , 在 笔 墨 线 条表 现上 , 主要 以“ 淡柔” 与“ 刚硬 ” 来 区分
“ 南宗” 与“ 北宗 ” [ 3 ] 。 根 据 董其 昌的论述 可知 , “ 南宗” 以 王维 为 主 , 另
杨 城
安徽 师 范大 学美 术 学院 , 安徽 芜 湖 , 2 4 1 0 0 0
摘要 : 为探讨董其 昌“ 南北宗” 画论 的理 论 价 值 及 其 影 响 , 简要 分 析 了“ 南北宗” 划 分 的 两 大 因 素 —— 宗教 和 时 代 背 景; 并 采 用 比较 的方 法 , 从 两 派 不 同的 绘 画特 色、 “ 南北宗” 论 的 价 值 与 影 响 等 方 面 阐述 了董 其 昌 的 这 一 国 画 理 论 。 “ 南北宗” 的提 出. 虽然是大师们的观点 , 但 人 们 还 应 该 客 观 地 去 看待 , 并 结 合 当代 实 际辩 证 地 去 继承 和发 扬 。 关键词 : 董其昌 ; 南北 宗论 ; 书画 美学; 南宗 ; 北 宗 中 图分 类 号 : J O 5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l 6 7 3 —2 0 0 6 ( 2 0 1 5 ) 0 3 -O O 8 2 —0 3
时始 分 。画之 南 北 二 宗 , 亦 唐 时 分也 …… 而 北 宗 微
矣! ” [
传 统 的再认 识 。董其 昌将 中国山水 画划 分 为南北 两 派—— “ 南北 宗 ” , 即 以王 维 为 首 的 “ 南宗” 和 以李 思
训为 首 的“ 北宗 ” 。董 其 昌提 出 的“ 南北 宗 ” 山水 画理 论, 是对 明 以前 绘 画的一 大 总结 , 遂成 为对 明以后 中
艺术论丨董其昌之“南北宗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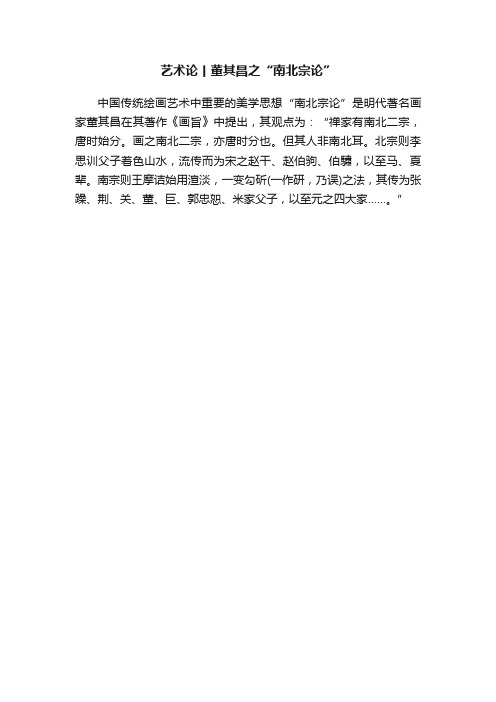
艺术论丨董其昌之“南北宗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重要的美学思想“南北宗论”是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在其著作《画旨》中提出,其观点为:“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
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
但其人非南北耳。
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驌,以至马、夏辈。
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一作研,乃误)之法,其传为张躁、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
”李思训《江帆楼阁图》101.9 x 54.7cm 绢本青绿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李昭道《明皇幸蜀图》55.9 x 81cm 绢本青绿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借助禅家的南北宗,对于唐代以来的绘画进行了解读、总结;以禅家的“南顿”和“北渐”的思想理念,在其绘画美学里将“文人画”归属于“南宗”,其主张顿悟;而将“画青绿的画家”归属于“北宗”其主张渐悟;实际是将唐以来的画家通过他们的身世经历、绘画时的笔墨技法以及绘画风格等等,分为了文人画家和职业画家两个不同的体系。
赵伯驹宋代《九成宫图》66 × 36cm镜心绢本设色王维唐代《雪溪图》36.6 × 30cm绢本墨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在董其昌的“南北宗”观点里:北宗的主要画家是“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驌,以至马、夏辈。
”而南宗“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一作研,乃误)之法,其传为张躁、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
南宗画始用渲淡,以淡雅的画风见长,而北宗画重着色、重青绿。
王维唐代《江干雪霁图卷》28.4 x 171.5cm日本京都小川家族藏荆浩五代《匡庐图》185.8 x 106.8 cm 绢本水墨“南北宗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山水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清代的画家影响深远,比如清初的“四王”深受董其昌摹古绘画理念的影响。
董源五代《夏景山口待渡图卷》50 × 320cm 绢本淡设色辽宁省博物馆藏米友仁宋《云山墨戏图》21.4 x 195.8cm 纸本北京故宫博物院巨然五代《秋山问道图》156.2 x 77.2cm 绢本水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但“南北分宗论”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董其昌是明代著名的士大夫画家,在其“南北宗论”中带着明显的崇南而抑北的思想,推崇南宗文人画而贬低北宗职业画家,进而造成了后来的一些画家苦于宗派之争,在一定成度上局限了绘画的创作。
论董其昌绘画美学思想——以南北宗论为例

【美术理论研究】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而其本身的绘画美学思想也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从根本上来说,是当时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绘画思想的有机结合。
从董其昌所处的时代来看,明末清初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绘画本身具有极强的表现性和写意性,画家可以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因此,绘画才有了极为丰富的风格和形式。
而董其昌的绘画美学思想与他的南北宗论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分析南北宗论,可以从侧面看出董其昌的绘画美学思想。
因此,本文从创作美学、艺术美学、人格美学三方面对董其昌的美学思想进行分析,为后世的绘画艺术创作提供一些借鉴。
一、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及其渊源董其昌在他的《画禅室随笔》中曾经写道:“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
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
”由此可见,董其昌认为南北宗论早在唐朝就有所区分。
而《画禅室随笔》也是他的南北宗论的正式出处。
绘画分为南宗和北宗两个宗派,南宗的宗师是王维,后来还有张璪、郭忠恕、李成、王晋卿、赵大年、米家父子、文征明、董其昌等;北宗以李思训为宗师,后有李昭道、赵干、李唐、刘松年、马远、仇英、夏圭等人,这是董其昌南北宗论的主要内容论述。
董其昌曾考中进士,甚至官拜礼部尚书,再加上他本身就在书法和绘画方面颇有造诣,所以他提出的山水画南北宗论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影响很深,不仅中国绘画的发展,就连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也因此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
”由此可见,他的南北宗论与禅家有着莫大的关系。
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禅宗中的禅学主要流行于北方,而南方则以般若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禅学与般若学成为佛教的两大学派,这便是禅家有南北二宗说法的缘由。
《辞海》中关于禅家南北二宗的说法是,禅宗因一条偈语而引发继承人的变化,后来又因此导致禅宗分立门户,即渐修渐悟的北宗和顿悟渐修的南宗。
董其昌便因此将中国历史上的山水画分成南北宗两派,由此可见,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与佛教的南北宗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董其昌画学南北宗论为文人画学经典辨体

2020/06 No.220论 坛明中期以后,文人画领域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仿古现象:吴门画家沈周在跋文中明确出现了仿古代某家笔法、拟古代某家笔意等说法;至清初,仿古模式成为画家群体重要的学习和创作方法。
所谓画学仿古模式,是指模仿古代画学经典的笔墨、造型、意境等进行学习和创作的程式化手法。
其核心是经典意识[1],而确定画学经典、为经典辨体,则是重要的理论基础。
因此,在个体的画学仿古方法到群体的画学仿古模式转变过程中,董其昌以南北宗论为书画辨体的行为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董其昌画学南北宗论的辨体依据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借鉴前人的书画理论成果,结合自身的书画实践经验和鉴赏心得[2],提出了著名的画学南北宗论。
在董其昌的书画跋文、诗文集中,直接论及南北分宗理论者,有以下三条: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
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
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
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
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
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
”知言哉。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王维)始。
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
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
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
[3]41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
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钱舜举(钱选)是已。
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仇英),在昔文太史(文征明)亟相推服。
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故非以赏誉增价也。
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骈阗之声,如隔壁钗钏戒,顾其术亦近苦矣。
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画殊不可习,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
董其昌南北宗论内容及历史意义

董其昌南北宗论内容及历史意义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可真是一桩有趣的事儿!想当年,董其昌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把中国的绘画分成了南宗和北宗。
南宗,那可是代表着文人画,讲究的是心境、情感,像一杯清茶,淡淡的却回味无穷。
北宗呢,强调的是工笔、写实,犹如一块精致的点心,样子美味,技术扎实。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董其昌就像个“调解员”,他在这两者之间搭起了桥梁。
他认为南宗画更符合文人的气质,更能表达他们的情感。
你想啊,那些文人墨客,心里有那么多想法,怎么能只是拘泥于技艺呢?董其昌可谓是深得其妙。
他的观点在当时的文化圈里引起了不少争议,许多人觉得南宗太过“飘”,而北宗则显得“死板”。
哎,这就像一场好莱坞大片,争论不断,精彩纷呈。
在历史意义上,董其昌的南北宗论真是为中国绘画史开辟了新的天地。
他不仅仅是把南北宗划分开来,更是将绘画的理念、审美、情感都提上了台面。
你看,艺术本来就是一种表达,如果只停留在技术层面,那真是大煞风景。
董其昌告诉我们,绘画可以是情感的宣泄,是内心世界的流露,这种思想可是深深影响了后来的艺术家们。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还让大家对艺术有了新的思考。
传统的艺术标准是不是就一定对呢?不一定哦!南宗和北宗的辩论,让我们明白了,艺术没有绝对的对错,有的只是不同的表达方式。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谁也不能说哪个更好。
是不是听起来很有道理?再说,董其昌的主张也影响了后来的文人画。
他的理论为文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空间,鼓励大家追求个性化的艺术。
许多文人画家都开始探索自己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语言,真是热闹非凡。
艺术圈内外,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创作,大家都在尝试“自我”,仿佛每个人都变成了艺术家,真让人惊叹不已。
董其昌也不是没遇到反对声。
有些人认为他的理论太过主观,忽略了技术的重要性。
你说这也能理解,毕竟在当时,传统的工笔画占据了很大的份额。
有人觉得南宗太“飘”,缺乏扎实的基础。
可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啊!不同的声音碰撞出火花,才让这个领域更加丰富多彩。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

《【婉娈草堂图】
【 江 干 三 树 图 】
【 秋 兴 八 景 】
董其昌的书法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 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 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 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 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 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 。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 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 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 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 长段跋语加以赞美:
南北宗论原文出处:
《画禅室随笔》卷二:“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 。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 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驌 (sù) ,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 斫(一作研,乃误)之法,其传为张躁、荆、关、董、巨、 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 驹(马祖道一)、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 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 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 (王)维也无 间然。知言哉。”
谢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观赏
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
(1)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 品比较常见; (2)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 较少见。 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 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 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 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 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 ,在 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 ,融会于绘画的皴(cūn )、擦、点划之中,因而 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 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 ,清隽雅逸。他 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
再释董其昌之南北宗论

再 释 美术学院O 级加研 究生 河南新 乡 8 4 30 507
摘要 :董其昌,明晚期绘 画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的画重在 笔墨的变化 ,有雅逸天真之趣 ,画风有枯 笔水墨 、没骨或浅绛两 种倾向 ,在雅 拙、简淡中带有 宁静 、 自然的文人之 恩,同时禅宗对董其 昌也有重要的影响 ,禅 宗的 明心见性 、摆脱形迹的思想 与文人画的适求 自然之性 的清高气息是一致 的。其 中,他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 的就是 “ 南北 宗论” ,他通过禅的义理 ,大致把 唐代 以来 山水画家按 南宗( 即文人 画) 北宗 (即院体 画 )两大体 系划分 ,南宗以王维 为始祖 ,董 源、 巨然为实际领袖 ;北 宗以 与 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始祖 ,马远 、夏 圭为旗 下干将 ,这一言论几乎 占据 了以后三 百年 画坛 的主流 ,并影响到其后绘画的发展
一
“ ”反 “ ”的思潮 ,以徐 渭、汤显祖 、三袁 ( 情 理 袁宗道 、 袁宏 道 、袁 中道 )为代表 ,文学 界则有 反 复古主 义的公安 派 、竟陵派 ,主张独抒性灵 。思想文化领域 冲破程朱理学 和 封建文化束缚所 呈现的诸家争 鸣和生机篷勃局面 也给绘 画界 以有利 的影 响,于是 “ 南北宗论 ”应运而生 。而南北宗论 的 创立者董其 昌正是想通过对从 唐至明近千年 的山水 画的分 析 总结 ,用艺术风格 分流派并加 以褒贬 ,以建立绘 画的新风格
、
笔势的运动做意象的组合 。各种传统 图像 ,经过董其 昌富有创 意才是最高境界 ,而这种禅意在 王维的画 中已初露端倪 。王 造性的糅合 、改造和重建 ,使得观者在 目睹熟悉的材料被重新 维的画一变勾斫 为渲淡 ,渐近 自 、意境幽深 、颇有天趣 , 然 米友仁 组合和编织之时 ,既体会到具有特殊背景知识的阅读愉悦 ,又 故把他列 为南宗 之祖。此后 ,在董 源 、巨然 、米芾 、 黄公望 、王蒙 、吴镇 、倪 有一种新鲜感 。同时董其 昌特别 强调布局中的势,笔墨的虚与 的画 中逐渐发展 ,到元季四大 家 ( 实,追求画面 “ 暗”的含蓄性 ,发展 了前人墨法。他在笔墨上 瓒 )画 中遂达 到了最 高峰 。所 谓 的禅意 、禅 境就是 以简代 也有很高的造诣和动人 的艺术魅力,可 以说明代真正推重笔墨 繁 ,以拙代 巧 ,以虚 代实 ,以少胜 多等手 法表 现 出含蓄 、 闲远清 的应是董其 昌,他曾言 : “ 以境 之奇怪论 , 画不如山水 ;以 则 宁静 、空疏 、平 远的 境界 。用 萤其 昌的话 说就 是 “ 天真幽淡 ”、 “ 古淡天然 ” 、 “ 脱尽廉纤刻画和纵 行墨之精妙论 ,则山水决不如画。” (《 旨》) 画 董其昌提倡 润” 、 “ “ 元四家 ”, 轻视 “ 门画派”, 吴 极力鼓吹纯 “ 画”。他的 文人 画风有两种倾向, 是枯笔水墨, 一 一是没骨或浅绛 。董其 昌的画 重在笔墨的变化 , 在师承各家的基础上 ,以书法的笔墨修养 , 融人于绘画的皴、擦 、点 、划之中,因而他的山水树石、烟云 流涧 ,柔 中有骨力,转折灵变 ,墨色干湿浓淡 ,层次分明,且 拙 中带秀,有雅逸天真之趣。他的画富有清润温雅 、平和怡然 的趣味 , 稚拙 、简淡 中带有宁静、 自 然的文人 之思 。董其昌的 枯笔水墨取法宋、元水墨一路 , 喜用干笔浓、淡之墨 ,多次勾 皴点擦 , 最后再以淡墨晕染 ,浑厚秀润 ,似与元人画法相近 。 如前所说, 昌很重视笔墨 , 董其 他把笔墨的作用提升到 了 前所未 有的高度 ,他的作品已脱略了山水形似 ,只讲究笔墨韵味。 横之气” 。以李思 训开创 的青绿 山水 画法和南宋院体画传统 影响的浙派 山水被 董其昌等人认 为是 “ 廉纤刻画”和有 “ 纵 横之气” ,故无禅 意被 列为北宗 。南 北宗论是文人画思潮的 种反映 ,所 以一 经建立便得 到文人画家的赞 同。此论树立 了温和文雅 , “ 精气内含”的作用, 定了文人 画在绘画史 上 奠
传统与超越——董其昌山水画论之“南北宗论"的研究

吴 画 派 髂 行 于 明 朝 中 期 ,但 南 于 明 朝 后 期 的 政 治 昏 席 无 望 , 朝 廷 官 员 腐 败 , 导 致 经 济 萧 条 ,使 得 文 人 大 夫 渐 渐 隐 退 , 虽 对 朝 廷 无 望 , 但 仍 有 难 舍 庙 之 高 远 之 意 。 这 时 出 现 以 董 其 吕 为 代 表 的 画家 ,} 停崇 绘 画 的 最 高 境 界 是 禅 宗 禅 意 , 董 其 禺 绘 画 书 法 以 及 佛 学 方 面 都 有 着 非 常 高 的 造 诣 , 而 日他 几 乎 是 对 上 下 千 余 年 的 中 国 书 画 卷 轴 都 过 H 了 一 遍 , 存 当 时 这 种 阅 历 很 少 有 人 企 及 , 他 经 常 入 朝 廷 于 I J I l 野 之 间 ,精神 理 念 与禅 宗 高 僧 比 更 足 不 相 上 下 , 并 且 其 对 于 当 时 社 会 精 神 而 貌 了解 也 比较 深刻 , 《 画 禅 室 随 笔 》中 的 “ 南北 宗 论” 运 而 生 ,其 对 唐 朝 至 今 的 庙 堂 与
源 、 巨然 、李 成 为 代 表 ,其 精 华 于 南 宗 1 I I 水 画 作 给 人 的 感 觉 是 恬 淡 、浦 幽 、 典 雅 , 与 “ 阴 柔之 美 ” 相 比 更 是 清 灵 之 美 。 把 南 方 那 种 水 灵 静 柔 以 诗 画 同 体 的 形 式 与 水 墨 替 代 渲 染 的 手 法 进 行 体 现 出 来 温 润 、 淡 泊 、秀 逸 、 文 雅 的 气 氛 。 ,李 思 训 为 “ 北 宗 ” 之 首 ,李 昭 道 、 马 远 、 赵 继 承 师
竹: 上 响 深 远 。
二 、董其 昌 “ 南北 宗论 ”与 当今 创作启 示
董 其 昌的 “ 南 北 宗 论 ” 近 百 年 柴 对 于 中 国 人 文 思 想具 有 十分 深 刻 的影 响 , 于 他 的 理 论 . 山
中西方画论董其昌南北宗论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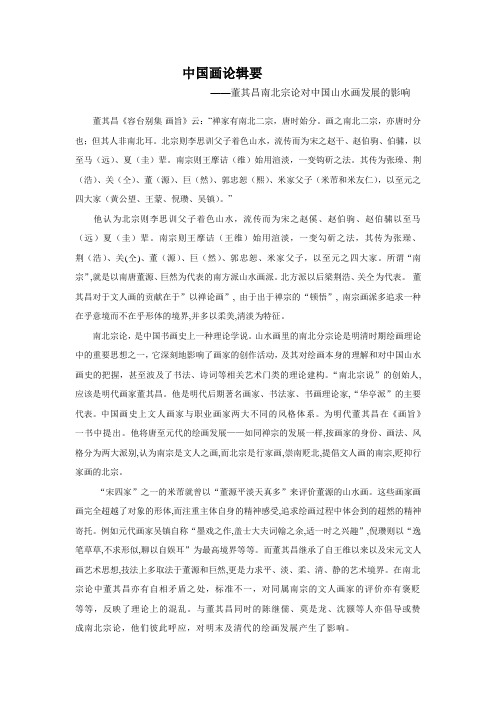
中国画论辑要——董其昌南北宗论对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影响董其昌《容台别集·画旨》云:“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
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
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远)、夏(圭)辈。
南宗则王摩诘(维)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
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熙)、米家父子(米芾和米友仁),以至元之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
”他认为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傒、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远)夏(圭)辈。
南宗则王摩诘(王维)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
所谓“南宗”,就是以南唐董源、巨然为代表的南方派山水画派。
北方派以后梁荆浩、关仝为代表。
董其昌对于文人画的贡献在于”以禅论画”, 由于出于禅宗的“顿悟”, 南宗画派多追求一种在乎意境而不在乎形体的境界,并多以柔美,清淡为特征。
南北宗论,是中国书画史上一种理论学说。
山水画里的南北分宗论是明清时期绘画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画家的创作活动,及其对绘画本身的理解和对中国山水画史的把握,甚至波及了书法、诗词等相关艺术门类的理论建构。
“南北宗说”的创始人,应该是明代画家董其昌。
他是明代后期著名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华亭派”的主要代表。
中国画史上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两大不同的风格体系。
为明代董其昌在《画旨》一书中提出。
他将唐至元代的绘画发展——如同禅宗的发展一样,按画家的身份、画法、风格分为两大派别,认为南宗是文人之画,而北宗是行家画,崇南贬北,提倡文人画的南宗,贬抑行家画的北宗。
“宋四家”之一的米芾就曾以“董源平淡天真多”来评价董源的山水画。
这些画家画画完全超越了对象的形体,而注重主体自身的精神感受,追求绘画过程中体会到的超然的精神寄托。
例如元代画家吴镇自称“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倪瓒则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为最高境界等等。
试论述董其昌的南北宗论

试论述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董其昌的南北宗论,真是个有趣的话题,咱们来聊聊吧!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明朝的画坛大咖。
他提出来的南北宗,哎呀,简直让人耳目一新。
南宗主张写意,强调情感和意境,仿佛在对你耳语,带你走进那梦幻的世界。
而北宗呢,则更注重写实,力求形似,像是个老实巴交的朋友,把所有的细节都呈现给你,简直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董其昌认为,南宗的艺术更具灵性,像是那无形的风,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
而北宗呢,就像是扎根大地的树,给人一种踏实感,能让你心里暖暖的。
他特别强调南宗的画要表达个性,像是在与观众进行心灵的对话。
他觉得,艺术不应该只是模仿自然,而要升华出一种独特的情感。
这种看法简直让人觉得耳边一亮,仿佛被打开了一扇窗,透进来清新的空气。
再说说北宗,董其昌认为它的价值也不容小觑。
他觉得,北宗能让人明白,什么叫做扎实。
北宗的画风,就像那无数的细节拼凑而成的画卷,精致得让人不由得赞叹。
想想那些北宗的大家,真是个个都是能工巧匠,技艺高超,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可是,董其昌又指出,北宗的画往往陷入一种死板,缺少了那种灵动感,像是块石头,难以融入生活的点滴。
董其昌在南北宗的辩论中,像个调皮的孩子,把这两种风格都摆上了桌,任你挑选。
他希望大家能从中感受到不同的美,能在这艺术的海洋里畅游。
他特别提到,画家要有自我意识,创作不能随波逐流,要敢于挑战传统,才能找到那属于自己的风格。
这种理念就像是在告诉我们,做事不要拘泥于规矩,要勇于尝试。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不光是在说绘画,实际上它反映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思考。
他用自己的方式,传达出一种生活的态度,真是深得人心。
艺术不止于形式,而在于内心的感受,这种思想让人感到特别贴近生活,仿佛随时都能用上。
无论你喜欢哪种风格,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条路,让自己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
所以,董其昌的南北宗论,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琢磨。
他用幽默风趣的方式,将艺术和生活结合在一起,让人不仅能欣赏到美,更能在美中找到快乐。
董其昌“南北宗论”刍议

董其昌“南北宗论”刍议作者:王丽欣来源:《美与时代·下》2024年第02期摘要: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是中国古典绘画理论重要的理论之一。
南北宗究其根本并不是流派的划分,而是对中国山水画两种不同绘画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划分。
董其昌肯定“南宗”绘画风格,并提出以“淡”为宗的审美理想和“不求形似,以画为乐”的文人画精神,对后世文人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通过对“南北宗论”主要内容的解读来探寻其真正精神内涵以及董其昌对待“南北宗”的真实态度。
关键词:南北宗论;文人画精神;淡;董其昌董其昌是著名的书画理论家,他所处的明代后期,社会动荡不安,文人之间盛行隐匿遁世之风,文化上佛禅、玄学盛行。
董其昌一方面受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受佛、道思想影响,研习禅学。
他提出著名的画学理论“南北宗论”,并且这一理论引发诸多争议。
他回顾中国山水画史,根据不同的笔墨技法、绘画风格、审美理想,分派出代表文人画派的“南宗”与代表画工画派的“北宗”,在中国画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南北宗论”主要内容《画旨》中,董其昌有关“南北宗论”最著名的论断如下: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
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
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伯骕,以至马(远)、夏(圭)辈。
南宗则王摩诘(维)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同)、董(元)、巨(然)、郭忠恕、米家父子(米芾、米友仁),以至元之四大家(黄公望子久、王蒙叔明、倪瓒元镇、吴镇仲圭)。
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马祖道一)云门、临济(云门、临济两宗)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
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
东坡赞吴道子王维壁画,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
”知言哉。
[1]37开篇“南北宗论”借禅宗“南北”喻画之“南北”。
何谓“南顿北渐”?这是说菩提达摩传给五祖之后,他的两个徒弟分南北二宗,“南宗”为“慧能”、“北宗”为“神秀”,两者得道方法不同,“南宗”重“顿悟”,也就是“天才”,而“北宗”重“渐修”是重“功力”。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

董其昌“南北宗论”董其昌(1555—1636)明代末期书画家。
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
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祖籍山东莱阳,祖父以军功封苏州卫。
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
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
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
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
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
存世作品有《岩居图》《秋兴八景图》《昼锦堂图》等。
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等,刻有《戏鸿堂帖》。
董其昌不仅是绘画大家,还是位重要的绘画理论家。
他提出了“南北宗论”,并得到许多人的赞成,流行数百年,影响国内外。
董其昌受社会风气熏染,既接受儒家的教养,又接受道、佛思想的影响,尤好禅理,喜欢以禅论艺学。
以禅家宗派来譬喻历代山水画风格的分野,将唐以来画家分为南北两大派系,唐朝王维、张璪,五代北宋的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李公麟、米芾父子,以及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明朝沈周、文徵明等历代画家被划归“南宗”,而唐朝的李思训父子,宋朝赵伯驹兄弟、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以及明朝的戴进、吴伟等历代画家被划为“北宗”,扬“南”而抑“北”。
北宗画家多为皇家画院所供养,所以又被成为“院体画”,由于它十分讲究技巧,又被贬称为“工匠画”。
而南宗画由于讲究文学修养,往往是士大夫词翰之余随性抒发,所以又被成为“士夫画”或“士人画”、“文人画”。
判断画家南北宗的依据:一是据其气息修养,二是依据所绘山水的南北地貌特色及其画法。
北方崇山峻岭,南方浅屿平峦,因而形成山水画中斧劈皴和披麻皴两大刚柔相异派系。
北宗山水多用斧劈皴,笔墨刚劲外露而具阳刚之美,尤以气胜;南派山水多用披麻皴,气息蕴藉儒雅而具阴柔之美,故以韵胜。
笔墨气息差距是南北宗文野精神分离之关键。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弘扬了北宋以来的文人画思想,要求画家在绘画中摆脱工匠气,追求主观表现的韵味,体现了近代绘画的思想意识,对于近现代中国文人画的发展影响深远。
简述南北宗论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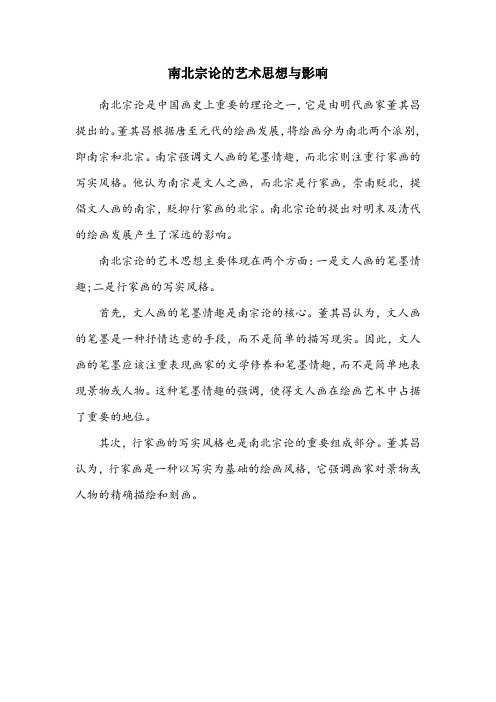
南北宗论的艺术思想与影响
南北宗论是中国画史上重要的理论之一,它是由明代画家董其昌提出的。
董其昌根据唐至元代的绘画发展,将绘画分为南北两个派别,即南宗和北宗。
南宗强调文人画的笔墨情趣,而北宗则注重行家画的写实风格。
他认为南宗是文人之画,而北宗是行家画,崇南贬北,提倡文人画的南宗,贬抑行家画的北宗。
南北宗论的提出对明末及清代的绘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北宗论的艺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人画的笔墨情趣;二是行家画的写实风格。
首先,文人画的笔墨情趣是南宗论的核心。
董其昌认为,文人画的笔墨是一种抒情达意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描写现实。
因此,文人画的笔墨应该注重表现画家的文学修养和笔墨情趣,而不是简单地表现景物或人物。
这种笔墨情趣的强调,使得文人画在绘画艺术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其次,行家画的写实风格也是南北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其昌认为,行家画是一种以写实为基础的绘画风格,它强调画家对景物或人物的精确描绘和刻画。
南北宗论

“南北宗”论
定义:董其昌《画旨》中提出山水画派分南北两宗的观点。
借禅宗南北二派“顿、渐”的修行方式,把我国唐以来的山水画中的文人画、水墨画和院体画两大体系划出了一个轮廓。
文人画体系似禅之南宗,院体画似禅之北宗。
北宗是注重功力的,犹如神秀的渐修,南宗是注重天趣的,犹如慧能的顿悟。
在董其昌看来,山水画中必须有禅意才是最高境界,而这种禅意在王维的画中已露端倪。
用董其昌的话说就是“闲远清润”、“天真平淡”、“古淡天然”,“脱尽廉纤刻画和纵横之气”。
北宗代表人物:李思训。
开创的青绿山水画法和。
代表作:《江帆楼阁图》
南宋院体画传统影响的浙派山水被董其昌等人认为是“廉纤刻画”和有“纵横之气”,故无禅意,被列为北宗。
李思训父子著色山水,流传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啸,以致马(远):马一角,《踏歌图》《寒江独钓》《西园雅集图》、夏(硅):下半边,泥里拔丁皴。
拖泥带水皴《山水四段图》辈
南宗代表人物:王维水墨山水画,被视为“文人画”派的鼻
祖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
其传为张躁、荆(浩)、关(同)《关山行旅图》笔墨皴擦加渍染、董(源)《潇湘图》、巨(然)《万壑松风图》披麻皴、郭忠恕、米家父子(米芾、米友仁)创造了“米点山水画”。
开启元明写意山水画的道路。
代表作:米友仁《潇湘奇观图》,以至元四家。
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
董其昌南北宗论对后世的影响(精图)

董其昌南北宗论对后世的影响(精图)董其昌南北宗论对后世的影响(精图)松江派始祖董其昌>>南北宗论│作品精选│娄东画派>>百家董其昌南北宗论对后世的影响 - 潮河边⼈ - 潮河边⼈博客董其昌画选故宫藏作品精选南北宗论故宫⼭⽔画册故宫仿古⼭⽔册⽴轴画精选仿宋元⼈缩本画⼤都会藏⼭⽔册仿⼤师⼭⽔册【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南北宗论”是董其昌对中国古代⼭⽔画派所持的⼀种理论。
董⽒的这⼀理论可归纳为以下三层含义:其⼀,从唐代开始,绘画领域就出现了两⼤派系,⼀派是以唐代画家王维为代表的南宗派系,包括五代的董源、巨然,北宋的⽶芾、⽶友仁⽗⼦及元代的“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等,另⼀派是以唐代画家李思训为代表的北宗派系,包括宋代的马远、夏圭、赵伯驹、赵伯骕等。
这两个画派是与禅学的两⼤宗派同时产⽣的。
其⼆,绘画中的南宗派系和北宗派系在艺术风格上(如“精⼯”与“⼠⽓”、“⼯”与“雅”)和艺术技法上(如“渲染”与“着⾊”、“勾斫之法”)是根本不同的,这与禅学的南北⼆宗在达到“涅槃”佛境所采取的不同途径和⽅法是相通和类似的。
其三,董其昌本⼈推崇的是绘画的南宗派系(即⽂⼈之画),认为这⼀派系的画家“皆其正传”。
⽽对北宗派系(即⾏家画)则加以贬斥。
这种推崇与贬斥与禅学的南宗派系兴盛和北宗派系衰落的状况极其相似,故称之为“南北宗论”。
董其昌被称为⼀代宗师不仅仅在于他的书法风⾏天下,也不仅仅在于他改变了明中期“吴门画派”的画风,更重要的是他旁通禅学,以禅论画,在中国历史上第⼀次以绘画发展过程为脉络,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画派的理论——“南北宗论”。
他把唐宋以来千⽀百派、纷纭万绪的⼭⽔画,通过对画家的⾝份和画家的笔墨、皴法、构图等因素的综合⽐较,借⽤禅宗派系,将⼭⽔画划分为南北⼆宗,⼒图全⾯⽽系统地梳理出⼀条⼭⽔画师承、流派的脉络。
其概括虽不准确、科学,但对研究中国⼭⽔画的发展,以及对艺术风格美学价值的思考,都有着积极的启迪意义。
董其昌的绘画南北宗论

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浅谈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学院:艺术学院班级: 2009级美本三班姓名:***指导教师:陈俊堂职称:讲师完成日期: 2012年 5 月 8 日目录一董其昌简介 ······························································ (错误!未定义书签。
) (一)董其昌生平 ···················································· (错误!未定义书签。
) 二董其昌的“南北宗”论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论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思想根源

艺术论坛+TEXT/魏庆春论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思想根源引言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画有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一种是以董源、巨然、“元四家”为主要代表人物,画风“平淡”、“柔润”。
这一路画风在南宋以后成了山水画的主流形式。
另一种画风是以“南宋四家”为主要代表人物,画风“雄强”、“刚硬”。
这种画风在南宋后逐渐地衰微下去。
这两种艺术风格代表了中国山水画发展过程中的两种美学思想。
在中国当代山水画的发展过程中,深入地研究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艺术风格与美学思想,有助于当代山水画家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理解和认识。
一、董其昌与“南北宗论”董其昌(1555—1636),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等。
华亭(上海松江)人。
卒于明毅宗崇祯九年,终年八十二岁。
董其昌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
他是明代晚期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
董其昌的艺术思想与美学观,主要表现在他的《容台集》之中,《容台集》是由《容台诗集》《容台文集》与《容台别集》组成。
“南北宗论”在《容台别集》和《画禅室随笔》中都有论述。
他在“南北宗论”论中说:“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
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
但其人非南北耳。
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赵白骕,已至马、夏辈。
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马祖道一)、云门、临济,儿孙之盛。
而北宗微矣。
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王)维也无间然。
知言哉。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具有“崇南贬北”的美学思想,他推崇南宗山水画“柔润”、“平淡”的艺术风格,反对北宗山水画“强硬”、“锋芒外露”的艺术风格。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对明代晚期以来的中国山水画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此,北宗山水画派更加的衰败,发展到了几乎无人问津的地步。
二、“南北宗论”的思想根源1、禅宗思想的重大影响佛教禅宗在唐代的神秀与慧能之时就逐渐地分化为北宗禅与南宗禅两大宗派,北宗禅在唐代以后就逐渐地衰微。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论董其昌的山水画与“南北宗论”摘要:作为明清之际文人画家的典型,董其昌的山水画艺术及其艺术理论既有它的代表性,也有其局限性。
对于董其昌的艺术及其艺术理论的认识与批评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对于我们全面地理解传统文化艺术,拓展当代中国画发展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董其昌;禅宗;南北宗论中图分类号:j2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002-03董其昌(1555-1636),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
字玄宰,号思白、思翁,别号香光。
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
谥文敏,因称董文敏。
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举进士,历任编修,湖广副使、太常寺卿,礼部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
董其昌不仅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他的书法、绘画、书画理论在明清之际也备受统治阶级以及士大夫们的推崇,俨然占据明末至清初近三百年的正统地位,他的艺术及理念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四王以及八大山人和龚贤等艺术大家。
同时,董其昌又是中国美术史上最具争议的一位画家,围绕着他的绘画、书法到书画理论乃至人品,都一直存有争议。
五四期间,董其昌与他的继承者四王曾经遭到了强烈的批判。
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在美术史上的地位,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艺术的重新关注,董其昌的艺术再次吸引了海内外学界的目光,诸多学者对董其昌的艺术和艺术理论给予了热烈的关注与极高的评价,当然同时围绕他的争论也从未间断。
笔者认为,对董其昌的艺术的追捧代表了部分艺术家与学者们对传统艺术重新认识的一个现象,但是,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新旧观念交替,信息与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与艺术的时候,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视角看待传统以怎样的观念解读传统?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是顶礼膜拜是全盘否定还是批判地继承或者温和地改良?以今天的眼光,客观地来看,董其昌的艺术及其艺术理论既有代表性,但也有明显之局限性。
作为明清之际的文人画的代表人物之一,董其昌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对他的艺术及其艺术理论的认识与批评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关系到我们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乃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理解。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董其昌的艺术及其艺术理论,清醒客观地看待他的艺术与理念,以期进一步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拓展当代中国画发展思路。
关于董其昌的山水画董其昌的绘画以山水见长,注重摹古,主要师法董源、巨然、米南宫、元四家等大家。
董其昌精于鉴赏,富于收藏,由于他的身份和地位,使得他有条件能够亲睹并收藏到大量前人名家真迹,这也使得他能够对前人艺术有很好的理解与把握。
他深厚的学养对他的绘画格调的提升也有很大帮助。
他的山水画笔墨秀润,设色古雅,极具性灵和书卷气。
毋庸置疑,董其昌作品的气格是高于同时代一般画家的。
而他的作品的这种气格的形成,除了其个人禀性以外,笔者认为还和他本人的禅宗信仰不无关系。
《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六.文苑四》中对董其昌有一段这样的描述:“(董其昌)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
人拟之米芾、赵孟頫云……”。
董其昌的好友陈继儒也在《容台别集叙》中说他:“独好参曹洞禅,批阅永明《宗镜录》一百卷,大有奇怪。
”董其昌信奉佛教禅宗,曾经与当时的高僧莲池大师等过从甚密,并且认真研读过宋代永明延寿禅师的著作《宗镜录》,可见他参禅是下过工夫的。
以禅入书画,是董其昌艺术的一大特色,也是董其昌作品之所以格调高于其他艺术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个人以为,董其昌的山水画艺术的成就在主要体现以下几点:第一,董其昌山水画作品所营造的古雅秀润、平淡天真的艺术境界代表了明清之际一批文人画家的艺术理念与追求;第二,笔墨形式语言的运用开启了后世山水画的抽象表现意识;第三,把禅宗理论应用到绘画实践当中,提升了中国画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然而另一方面,今天看来,董其昌的绘画并没有达到理想的高度,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技术的缺失和绘画实践的不足。
董其昌在绘画上只重临摹不重写生,致使它的作品缺少了生活的源泉,作品题材有些单一,形象也显得空洞、概念化。
在造型、构图、空间感的表现等方面,董其昌的山水画略显有些稚弱。
想来也不奇怪,董其昌的一生中,踏上仕途之前主要精力要用来应付科举,为官之后政治生涯里大部分时间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政务以及应付官场的种种斗争与应酬,能专门腾出出来作画的时间毕竟有限,因此他不可能像一些专业画家那样有大量的时间专门去写生以及推敲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启功先生曾经在《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一文谈到:“董其昌以显宦负书画重名,功力本来有限……”,“平心而论,董其昌在书画道中,自有他的特识。
以功力言,书深画浅。
……”然而董其昌的确是一个天分很高的画家,很懂得扬长短。
他发挥自己书法与笔墨的优势,回避了造型上一些丰富的变化,巧妙形成了自己的面貌。
同时,在理论方面,董其昌也很善于替自己辩解,提出了“尚率真,轻功力,崇士气,斥画工,重笔墨,轻丘壑,尊变化,轻刻画”等主张。
今天来看,董其昌的绘画确有抽象语言的显露,其绘画的抽象表现意识对后世是有启迪的。
但是很显然,这种抽象意识还处于萌芽状态,其中不排除部分是由于技术欠缺造成的将错就错,这与经历提炼后的抽象变形(例如八大山人的绘画作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潘天寿先生曾说过:“画事须有天资、功力、学养、品德四者兼备,不可有高低先后。
画事须有高尚之品德,宏远之抱负,超越之识见,厚重渊博之学问,广阔深入之生活,然后能登峰造极。
岂仅如董华亭所谓‘但读万卷书,但行万里路’而已哉?”在这里潘天寿先生对董其昌的艺术理念提出了批评,认为仅仅重视学养与阅历,是根本不够的,同时他提出了攀登艺术顶峰所须具备的四个条件“天资、功力、学养、品德”,并认为缺一不可,其中“品德”这一项由于带上了伦理色彩,一些学者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暂且不做讨论,但绝不可否认,一个成功的画家,至少起码应具备“天资、学养、功力”这三个基本条件。
这里的“功力”,是种长期积累的艺术素养。
它包含了画家对造型与色彩的敏锐觉察、对笔墨技巧的娴熟运用,对构图的驾驭以及对画面整体氛围的把握等能力。
随着画家的天资的高低不同,而掌握这些能力所需要的时间长短也不同,但无论天资高低,都只有通过后天的练习才能不断提高。
作为一流的艺术大师,“功力”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绘画上,董其昌试图走一条捷径,禅宗的理论固然玄奥,但艺术的学习既有主观体验也有其客观规律,它和禅宗的修正也并不完全相同。
换言之,禅宗可以不假修持当下顿悟,而绘画的造型、笔墨等技术层面问题不经过长期的锤炼却是难以经营好的。
观历代艺术大师们的创作经验无一验证了这一真理,郑板桥画竹经历了从“胸有成竹”到“胸无成竹”的过程;八大山人的鸟、齐白石的虾、这些看似随意的艺术形象,也都经过了反复的尝试与探索。
另外,在官本位意识浓重的明清社会,董其昌之所以能在书画领域得享盛名,除了自身的艺术造诣外,也和他的政治地位以及清初统治者的推崇不无关系。
对于董其昌的艺术的贡献与局限,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一分为二地看待,一味地褒扬,或者轻率地否定,实际上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传统与发展创新都是不利的。
关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董其昌的艺术理论颇为引人注目,也是历来引发争议最多的。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荣台集》、《荣台别集》等著作中阐释了他对绘画、书法中的诸多见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南北宗论”。
关于“南北宗论”,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的评议,在这里我想主要从禅宗与绘画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从以下几方面谈谈个人的理解:首先,我们应当肯定,“南北宗论”是很有创意的艺术理论,他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宗教体验与艺术创作历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把禅与绘画相结合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董其昌强调绘画的思想性、随意性,自发性与愉悦性,对当时院体和浙派刻板雕琢的绘画时流有矫正作用,把禅宗理论引入绘画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画的思想性,在当时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二,正如学界共识的,“南北宗论”是美学观念,是画家本人的创作理念,但作为对画史的概括却不是很准确。
董其昌所划分的山水画的“南宗”与“北宗”,总体来看只不过是艺术风格不同罢了,所谓“南宗”与“北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究竟哪些画家当属于南宗,哪些当属于北宗,也都是依据董其昌的个人主观论断。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被董其昌划入北宗的画家与被划入南宗的画家的绘画风格有些并没有太大差别,而被划入“北宗”的画家其艺术格调也未必都不如“南宗”的画家。
强行把某些画家划入“南宗”、某些划入“北宗”,显然失之于武断了。
其三,绘画与禅虽然相通,但仍然是不同的两个领域,用佛学来说一个是“世间法”一个是“出世间法”。
作为“出世间法”的禅主张“无修无证”,而作为“世间法”的绘画技艺要靠长期实践并且反复总结经验才能提高。
所谓“佛法不离世间法”,是说佛法可以通过世间法去体悟。
绘画可以作为禅者参禅悟道的一种方式,但绘画本身有其规律,可以说,任何一个画家艺术风格的成熟过程都是遵循“渐悟”这一规律的。
了解禅宗的人都知道,禅宗在唐代以前虽然有南北宗之分,实际上北宗自唐以后就失去了正统地位。
慧能的南宗一派持“顿悟”的观点,他们主张“无修无证”,主张放弃一切主观的追求,认为只有“无相、无住、无念”方能契入本心。
在禅师们看来,“五蕴本空,六尘非有”,“本来圆成,不假修添”,“当下即是,动念即乖”。
只有放下一切目的和求索,觉悟才有可能不期而至。
否则只要一有“修行”的念头就已经错了。
正如六祖慧能的弟子永嘉玄觉禅师在《证道歌》中所说的:“绝学无为闲道人。
不除妄想不求真。
无明实性即佛性。
幻化空身即法身……”,在南宗禅师心目中是没有次第的。
而神秀一派的北宗则主张要通过刻苦的修行来逐渐达到觉悟,由于北宗有主观修行的想法,因而在南宗祖师们看来是落入了“法执”与“我执”,是要遭到呵斥的。
因此神秀一派从来不被视为禅门正脉。
另外,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有这样一段理论:“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
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
黄子久、沈石田、文征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赵吴兴止六十余。
仇与赵,品格虽不同,皆习着之流。
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
”董其昌的艺术观是“以画为乐”,也就是把绘画当作消遣,这是典型的文人作画的心态,这种思想的源头应该上溯到庄子的哲学,这种思想在文人画家中有很大市场,但同时它也有其积极与消极的两面,它强调了艺术创作的愉悦感和超功利性——这种心态作画的确很放松,但对艺术创作来说,恐怕难以创作出有震撼力的作品来。
“以画为乐”的创作态度作为个人艺术追求本无可厚非,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些通过艰辛劳动创作出的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不一定非要表现闲情逸致,艺术创作的过程可以是热情洋溢的、激情饱满的,也可以是悲愤的、焦虑的甚至痛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