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
张爱玲笔下之上海与今日之上海对比

新潮的上海文化形象。
2.配饰
翡翠耳坠、翡翠手镯、红宝石簪子
张爱玲小书中的配饰纷乱繁多,红金绿玉,每一件都是极为精致的, 极能体现当时上海女性对精致的追求。
在她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翡翠耳坠、红宝石簪子、翠玉手镯等极具 中国古典风格的首饰。
如《金锁记》中长安相亲那天“耳朵上 戴了二寸来长的玻璃翡翠宝塔坠子,又换 上了苹果绿乔琪纱旗袍,高领圈,荷叶边 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
《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就是那个病态的、毫无生气的生活方 式结出的一枚苦涩的果实;《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的罗杰;《年青 的时候》中的潘汝良,作为时代的失落者,他们被旧的时代所封闭 着,不管如何挣扎也逃不出时代的梦魇,明知挣扎无益,也不再徒 劳了。
张爱玲笔下丰富多彩的男性形象,无论是 封建遗老遗少、庸俗的都市男性还是洋场 社会的风流绅士,大都崇尚金钱、玩弄女 性,庸俗卑琐,很少有好男人的形象。这 也就是张爱玲对男性的基本评价和基本视 角。
也有自己的精神追求。
二、上海男性的对比
(一)张爱玲笔下的上海男性:
1、卑琐自私的遗老遗少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一群没落的世家子弟,曾经靠祖上的遗产 度日,不务正业,抽鸦片,逛窑子,捧戏子,可是旧的安逸的生存环 境突然发生变故,他们在新的环境下无所适从,因此始终被一种无法 驱除的危机感所笼罩,整日惶恐不安,又从惶恐走向自私 。比如: 《倾城之恋》中白公馆里的白三爷、白四爷。
3、旧式家庭中为自己放手一搏的女性。
以 《 倾城之恋 》 中的白流苏、 《 沉香屑 ·第一炉香 》 中的葛薇龙为代表;
她们在现代都市生活与旧式家庭中的地位与长安、川嫦类似,不同的是,当她们
被现实逼迫到绝境时,其自我意识终于觉醒,或主动出击抢夺本不属于自己的机
白先勇与张爱玲中短篇小说的结尾艺术比较

她惯于在小说的开头 , 出故事化叙事 的姿 态 , 摆 象古代 的说书人那样 , 一段 开场白 , 来 故事末尾又有一段饱含 苍凉意味的结束语 。如《 金锁记》 她立足 当下 , , 以现代 体验抒写关于过去的往事 , 咀嚼随着 时间流逝 , 人物生 命和 良知也消磨得一千二净的挥之不尽 的悲凉感 。说是就 主人公在 进行 叙述 。他 时 而称赞 主 不 人公 ; 时而批评主人公 ; 总之他可 以 自由地对主人公评
头 品足 。 ”
特征的可有可无 的配角 。她对主人公 多从 正 面描写 , 但在导入和结尾之初 都作 了突出叙 述者 的技术 处理 。
白先勇在小说结 尾上更是突 出了这种最适合作者
三 十年 前 的 月亮 早 已沉 了下 去 , 三十 年前 的人
也死 了。 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 充一 完不了。 小说在一 片朦胧 的月光下开 始, 也在月光中结束 , 整篇
评价人物和感情 的作 用。其 中《 丈青》 一 采用师娘的视 角, 以第一人称写 成 , 了使 故事 显得 较有亲 切感 , 除 还
通过师娘和朱青 问的对 比烘托 出朱青 的悲剧 性 , 结尾 写到师娘看见麻将桌 上 的朱青 已经成 了大赢 家 , 她不 停地笑 , 嘴里 翻来 滚去 哼着她常爱唱 的那首《 山一把 东
维普资讯
陈子欣
结尾 , 和开头一样 , 对一篇文 章来 说是一个 非常重 述 , 结尾里《 山一把青 》 东 的歌 曲听起来就 不会 那么讽 要的问题 。元 朝杨 载《 诗法 家数》 :诗 结尤难 , 好 、刺 了 。 云 “ 无 - 结句 , 可见其人终无成 也。 不仅是诗 , ” 所有文体 的文 章 又如《 片血一般 红的杜鹃花》 那 的结尾 : 都应该特别重 视结尾 , 尾并 不是 独立 、 结 简单 的技巧 , 当我 走到 因子里 的时候 , 赫然 看见 那百 多 却 而是 整体艺术 构思 中融 合作 者意 图的一 种有 利形式 , 株杜 鹃花 , 一球堆着一球 , 一片卷起一 片, 全部爆放 同时它 又是 自然 、 得体 地合 乎情节 和人 物性格 发展 规 开 了。好 象一腔按撩 不住 的鲜血 , 猛地 喷 了出来, 律的, 能给人 以深刻 的印象 和美的启示 。 洒得一 因子斑斑点点都是血红血红的 , 我从 来没看 综观 白先 勇、 张爱玲 的 中短篇 小说 , 无一 不用 “ 曲 见杜鹃花开得 那样放肆 , 那样愤怒过 。丽儿正和一 群女孩子在 因子 里捉迷藏 , 她们在 那片血一般红的 尽音绕梁 ” 式结尾 ( 与之 相对的是 “ 章显 其志” ) 它 卒 式 , 以含蓄蕴藉 的文字 来暗示 文 章主 旨, 读者 必须通 过作 杜 鹃花丛 中穿来穿去。女 孩子们尖锐 清脆 的嬉 笑 者给定的意境 , 系全 文 , 真 体味 咀 嚼才 能得其 真 联 认 声, 在春 日的晴空里 , 一阵紧似一阵的荡漾着。 意, 余音绕梁 , 意生 畜外 , 发人 深思 , 耐人寻 味 , 大地 正是叙述者 “ 那懵然不知 的语气 , 极 我” 不存心 、 不在 意的 调动读者的兴味 , 从而 提升表 达 的实 际效果 。此 为它 客观描述使读者可 以处处 拾得“ 本 人没 感觉 到 、 我” 没 们 的一大共同点 , 是它 们所 运用 的写作手 法却有 所 认识到的含义 , 听到作者 白先 勇的 弦外 之 音 :花 之 但 并 “ 差异 . 面, 下 就分而述之 。 ‘ 盛开 ’ 正是 ‘ 落 ’ 凋 之前奏 ……故事叙 述者 , 次见 到 首 花园时 , 鹃花还 只在 ‘ 杜 打苞 ’ 。丽儿 的童稚 纯真 , 时 那 叙述者 角 度 ‘ 白先勇的小说多 以第一 人称出现的次要人物作为 还有一段前 途。但两三 年后的今 日,全 部爆 放开 了 ’ 所 就只是枯萎的开始。正如园里女 观 察者进 行叙述。这在 技法 上相 当于里安 ・ 沙梅里 昂 的花朵 , 能预期 的, ‘ 紧到极点 , 所说 的“ 要人 物 的叙 述 ” 次 。里 安 ・ 沙梅 里 昂如 是说 : 孩 子们尖 锐清脆 的嬉笑声 ,一阵紧似一阵 ’ ” “ 次要人物为观察者 时 , 在 主人公便 可以就 自己进行 通 必将绷 裂。 相反, 张爱玲的作 品里 几乎没有 以“ ” 我 为叙 述者 常 难 于为 之 的 客 观 描 写 。 … … 之 所 以 如 此 , 非 是 因 无 次要人物在张爱 玲笔下 都是些没 有 明显 性格 为他所 承担 的角色 比重 不大 , 与其说 是就 自己进行 的例子 , 他
双城记:张爱玲与白先勇小说的沪港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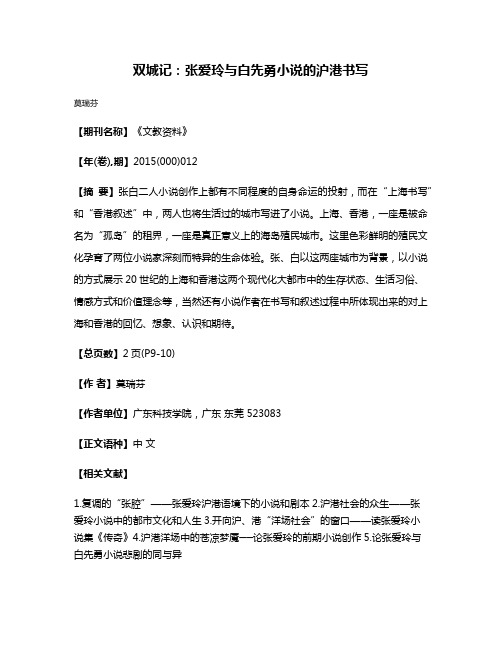
双城记:张爱玲与白先勇小说的沪港书写
莫瑞芬
【期刊名称】《文教资料》
【年(卷),期】2015(000)012
【摘要】张白二人小说创作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自身命运的投射,而在“上海书写”和“香港叙述”中,两人也将生活过的城市写进了小说。
上海、香港,一座是被命名为“孤岛”的租界,一座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岛殖民城市。
这里色彩鲜明的殖民文化孕育了两位小说家深刻而特异的生命体验。
张、白以这两座城市为背景,以小说的方式展示20世纪的上海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存状态、生活习俗、情感方式和价值理念等,当然还有小说作者在书写和叙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上海和香港的回忆、想象、认识和期待。
【总页数】2页(P9-10)
【作者】莫瑞芬
【作者单位】广东科技学院,广东东莞 523083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复调的“张腔”——张爱玲沪港语境下的小说和剧本
2.沪港社会的众生——张
爱玲小说中的都市文化和人生3.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
说集《传奇》4.沪港洋场中的苍凉梦魇──论张爱玲的前期小说创作5.论张爱玲与
白先勇小说悲剧的同与异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_传奇_的上海书写_论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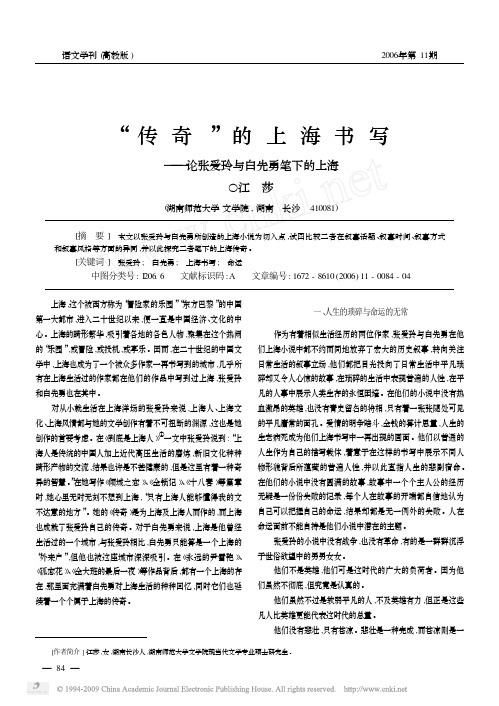
[作者简介]江莎,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传奇”的上海书写———论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江 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摘 要] 本文以张爱玲与白先勇所创造的上海小说为切入点,试图比较二者在叙事话题、叙事时间、叙事方式和叙事风格等方面的异同,并以此探究二者笔下的上海传奇。
[关键词] 张爱玲; 白先勇; 上海书写; 命运中图分类号: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06)11-0084-04 上海,这个被西方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的中国第一大都市,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便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
上海的畸形繁华,吸引着各地的各色人物,聚集在这个热闹的“乐园”,或冒险,或投机,或享乐。
因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上海也成为了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到的城市,几乎所有在上海生活过的作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写到过上海,张爱玲和白先勇也在其中。
对从小就生活在上海洋场的张爱玲来说,上海人、上海文化、上海风情都与她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扭断的渊源,这也是她创作的首要考虑。
在《到底是上海人》①一文中张爱玲说到:“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着一种奇异的智慧。
”在她写作《倾城之恋》、《金锁记》、《十八春》等篇章时,她心里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她的《传奇》是为上海及上海人而作的,而上海也成就了张爱玲自己的传奇。
对于白先勇来说,上海是他曾经生活过的一个城市,与张爱玲相比,白先勇只能算是一个上海的“外来户”,但他也被这座城市深深吸引。
在《永远的尹雪艳》、《孤恋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作品背后,都有一个上海的存在,那里面充满着白先勇对上海生活的种种回忆,同时它们也延续着一个个属于上海的传奇。
一、人生的琐碎与命运的无常作为有着相似生活经历的两位作家,张爱玲与白先勇在他们上海小说中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关注日常生活的叙事立场,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中平凡琐碎却又令人心惊的故事,在琐碎的生活中表现普遍的人性,在平凡的人事中展示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
异曲同工的悲歌_张爱玲与白先勇悲剧意识的比较

差的对照。”4 这句话表明了张爱玲笔下的悲剧不像 的生活的丧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有过一个显
传统意义上的悲剧强调力和崇高、英雄和壮烈等强 赫、辉煌的“过去”,《梁父吟》中的总司令王孟养早年
烈的对比,而是“参差的对照”;不是悲壮,是一种苍 投身辛亥革命,勇往直前、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早在
凉的意味。张爱玲将这种苍凉看得极为真切,褪去层 那个时候就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岁除》 中的四川老
一部短篇小说集《传奇》代表了张爱玲小说创 作的主要成就。《传奇》中长短不一的 16 篇小说写出 了张爱玲对于人性深处隐秘角落的敏感透视、对于 人生的悲剧透视。《传奇》初版的扉页上写道:“书名 叫传奇,目的是奇。”1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小说的着 眼点在对人及人生的书写。他要在琐碎而平凡的世 俗生活中传达出人世沧桑的种种慨叹,来表现自己 对无常人生的悲剧体验和阐释。
层浮华外表的生命,天地间仅剩一盘陈旧而迷蒙的 兵赖鸣升也是一个穿越民国历史战场的叱咤风云的
月亮,断瓦残垣中一堵冷而粗糙的墙。他们寓示着天 英雄、功勋卓著的忠臣。可以说“台北人”们大都经历
荒地老,更述说着人生无尽的苍凉。“总而言之,对永 过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并在那个时代里做过威风
恒人生、普遍人性的深刻体悟使张爱玲拥有了深刻 八面的历史创造者,甚至连旧贵族阶层的依附者
剧—— —“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桂 无法也无力改变现状中,白先勇痛感人生如梦、万事
花蒸·阿小悲秋》展示了一个乡下到上海谋生的女佣 皆空的虚无情绪。一种诸事无常之感时常侵袭困扰
人丁阿小普通一天的日常生活,却让人从中感受到 着他。他深感到人对于自己命运的无法控制,这使得
日子的无奈与酸楚。《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 感伤忧郁之感沦落为彻底的悲观主义。因此,弥漫在
浅谈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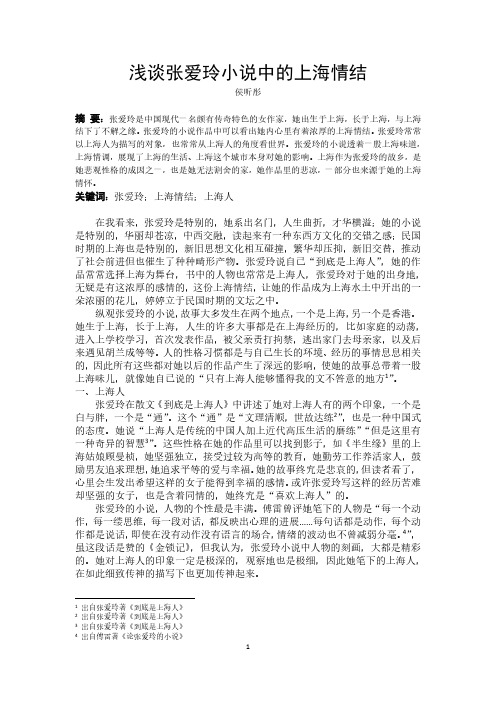
浅谈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情结侯昕彤摘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一名颇有传奇特色的女作家,她出生于上海,长于上海,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可以看出她内心里有着浓厚的上海情结。
张爱玲常常以上海人为描写的对象,也常常从上海人的角度看世界。
张爱玲的小说透着一股上海味道,上海情调,展现了上海的生活、上海这个城市本身对她的影响。
上海作为张爱玲的故乡,是她悲观性格的成因之一,也是她无法割舍的家,她作品里的悲凉,一部分也来源于她的上海情怀。
关键词:张爱玲;上海情结;上海人在我看来,张爱玲是特别的,她系出名门,人生曲折,才华横溢;她的小说是特别的,华丽却苍凉,中西交融,读起来有一种东西方文化的交错之感;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是特别的,新旧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繁华却压抑,新旧交替,推动了社会前进但也催生了种种畸形产物。
张爱玲说自己“到底是上海人”,她的作品常常选择上海为舞台,书中的人物也常常是上海人,张爱玲对于她的出身地,无疑是有这浓厚的感情的,这份上海情结,让她的作品成为上海水土中开出的一朵浓丽的花儿,婷婷立于民国时期的文坛之中。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故事大多发生在两个地点,一个是上海,另一个是香港。
她生于上海,长于上海,人生的许多大事都是在上海经历的,比如家庭的动荡,进入上学校学习,首次发表作品,被父亲责打拘禁,逃出家门去母亲家,以及后来遇见胡兰成等等。
人的性格习惯都是与自己生长的环境、经历的事情息息相关的,因此所有这些都对她以后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她的故事总带着一股上海味儿,就像她自己说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答意的地方1”。
一、上海人张爱玲在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中讲述了她对上海人有的两个印象,一个是白与胖,一个是“通”。
这个“通”是“文理清顺,世故达练2”,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态度。
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3”。
这些性格在她的作品里可以找到影子,如《半生缘》里的上海姑娘顾曼桢,她坚强独立,接受过较为高等的教育,她勤劳工作养活家人,鼓励男友追求理想,她追求平等的爱与幸福。
浅论文学创作中的“上海女性”与“上海书写”——以张爱玲、白先勇、程乃珊为例

浅论文学创作中的“上海女性”与“上海书写”———以张爱玲、白先勇、程乃珊为例■毛梦杰 乔子路/江苏大学摘 要:出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引人瞩目,涌现出一系列关注上海城市文化或以上海为题材的作家。
其中,以张爱玲、白先勇、程乃珊为代表的作家笔下的“上海女性”颇具传奇色彩。
本文以三位作家创作的“上海书写”小说为例,试图探究笔下女性形象及上海传奇。
关键词:“上海书写” “上海女性” 张爱玲 白先勇 程乃珊二十世纪开始,话语叙述对中国的强力推广和开发,使上海成为了被众多作者一再书写的城市,形成了独特的“上海书写”风貌。
而“所谓上海书写,是指以上海为表现背景,展示了20世纪中国人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上海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
”[1]即在“上海题材”的基础上,融入进书写者对上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
其中,作为上海繁华历史的见证者张爱玲,曾居住过上海的“外来户”白先勇,及通过搜集资料和访谈为基础进行创作的程乃珊。
这三位关注“传奇”的作家不仅爱好“上海书写”,还十分擅长对上海女性的刻画。
本文希望以三位作家的不同视角来观摩上海及上海女性,揭开上海神秘而魅力的面纱。
一、张爱玲———无力的苍凉从小生活在上海的张爱玲,其文学创作多与上海及上海风情有关。
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着一种奇异的智慧。
”[2]可见她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有一种高贵的孤傲感,而她所写的传奇故事也往往充满了美丽而悲哀的浮华。
《倾城之恋》中,女主角流苏为保障生存以婚姻作筹码,男主角柳原以“物质”为诱饵来满足空虚的情欲。
两人棋逢对手,机关算尽,只为获得欲望的满足。
流苏如履薄冰地跨过了情妇生涯,终于得到了一桩可靠的婚姻,却透着无尽的感伤;《金锁记》中,曹七巧为摆脱穷困低贱的人生,用青春换得姜家二奶奶的身份。
从白先勇小说谈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影视化塑造

从 白先勇
影视作品中女性形
孙 嘉 ( 江 苏师范 大学传 媒 与影视 学院 江 苏徐 州 2 2 1 0 0 0 )
摘要 :近 几年 来 ,随 着 《 青春 版牡 丹亭 》的推 出,对 白先 勇先 中 的金大 班 有情 有 义 的背 后是 在 为 自己 的利益 而考 虑 ,她 有着 舞
历 史 文化 的解 读 。 而这 种环 境 结合 历 史 的研 究方 法 让一 部分 研 究 者 把 张爱 玲 与 白先 勇联 系 在 了一起 。他们 有 着 一样 显赫 的家 世 , 对 上 海十 里 洋场 文 化有 着 独特 的感 情 , 同样 放逐 在 了海 外 ,半 身 沉 浮 ,用 文 字诉 说 着他 们 对那 段 历 史的怀 念 与解 读 。李 爽 的 《 张 爱 玲 与 白先 勇 的 人 生记 忆 与 文 学 创 作 的相 似 性 分 析 》2 江 莎 的 《“ 传奇 ”的上海 书 写— — 论张 爱玲 与 白先 勇笔 下 的上海 》3 王桂荣 的 《 白先 勇 与 张 爱玲 笔 下 女 性 命运 的沉 浮 》 4 李沁 园的 《 试 析 张爱 玲 与 白先 勇小 说 中 的命运 和 人性 》 ,拓 展 了原 有 的研 究 角 度 ,从 两 者共 有 的上 海文 化 入 手 ,着眼 于 小说 人物 的命运 与 人 性 发展 ,深 入解 读 文化 底蕴 。 近几 年 , 随着 大 陆社 会 的开 放 与发 展 ,影 视产 业 茁壮 成 长 , 大 陆 的 一 些 编 剧 、 导 演 也 看 到 了 白先 勇 小说 的卖 点 ,相 继 改编 了 一 些 电 影 电 视 作 品 。 如 黄 以 功 导 演 的 电视 剧 《 玉卿 嫂 》 、鞠 觉 亮 导 演 的 电视剧 《 金大 班 》等 。这些 电视 剧 虽然 是 根据 白先勇 的 同名 小 说改 编而 来 ,但 不 是 由原 著作 者 改编 ,根据 播放 的需求 编 导在 原 有 的基础 上 做 了很 多 的修 改 ,特 别是 由于原 著 是短 片 小 说 ,所 以必然 要对 作 品进 行 大 修改 ,而 这 种修 改 是否 需 要尊 重 原 著 的 旨意 ,这 就取 决 于 编剧 对 作 品的解 读 ,对 市 场 需求 的分 析 。 编剧 《 金 大班 》在 原 著 的基 础 上给 金 兆丽 设计 了一个 扑 朔迷 离 的 身 世 ,暂 且不 论 这种 设 计是 否 符合 原 著 的精神 ,但 是从 可观 性 来 看 ,确 是 满足 了观众 的 观赏 需 要 , 曲折 的身世 、善 良的品行 、为 爱 牺 牲 的精 神 、可 悲 可 叹 的命 运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异 于 寻 常 的舞 女 ,观 众 爱上 了这个 女 性形 象 。这 个 比现 实 中 的 自己 ( 女性 )更 坎 坷 的银 幕 女性 ,让 众 多女 性 观众 更 加乐 于追 剧 。人更 乐于 接 受 喜 剧式 的结尾 ,乐 于看 到善 良纯洁 的人性 , 容易 被 比 自己更 惨 的 人 物吸 引,而 不 乐 于见 到别 人 比 自己更幸 福 ,编 剧 正是 出于 对 这 种 原则 的理解 ,让 我们 在银 幕 上看 到 了一 个 孤独 的 身影 在大 上海 灯 红酒 绿 中迷 茫 、选 择 。改编 的 女性 形象 与 原著 截 然不 同,原 著
古典的悲天悯人与现代的人性解剖——白先勇与张爱玲悲剧艺术的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年第期古典的悲天悯人与现代的人性解剖——白先勇与张爱玲悲剧艺术的审美比较吴凡安徽大学中文系合肥摘要白先勇和张爱玲同为中国世纪优秀小说家二人都具备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悲剧文化心理都深受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其作品总体上都呈现出“苍凉”的审美境界。
但是他们的悲剧艺术却形成鲜明的对比白先勇体现的是悲天悯人张爱玲则是恐惧冷酷白先勇割舍不掉文化乡愁情结张爱玲则显示出对文化的超然态度白先勇在中西交融中倾向民族感伤的古典美张爱玲则显示出对世界性存在思考的知性美。
关键词白先勇张爱玲悲剧艺术审美比较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白先勇和张爱玲均是中国世纪杰出的小说家一个是悲天悯人、具有浓厚文化乡愁意识的“昆曲的终身义工”一个是“异数”、“残酷的天才”。
然而掠过二者表面上的歧异他们在深层次上又有相通之处他们身世相似都出生于曾经显赫的名门继而家道式微童年时都有一段孤寂的生命体验白七八岁时患肺病曾像囚鸟一样独居四年多张幼年父母离异所受双亲之爱甚少他们都受到中西文化的浸染在作品中可以咀嚼出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双重硬度并且都十分推崇《红楼梦》深受其影响而创作都非常关注人类的生存悲剧和人性的孤独。
这些相似性导致了二者的作品都透露出挥之不去的“苍凉”、“悲观”的美学风格和悲剧余味。
虽然同为悲剧小说家白先勇和张爱玲却表达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态度。
前者揭示了那些失去了青春、荣耀、爱人和家国的失落者内心的悲痛或表现了因特殊情感特征同性恋而导致的无言创痛表达了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浓郁的文化乡愁情结和感伤的悲悯情怀。
后者多采写那些不是身体病了就是心理病了或者身体心理都病了的遗老遗少们的悲剧故事反讽之余近乎冷酷地解剖人性的卑陋和扭曲充满了孤独漂浮感和虚无幻灭感。
一、悲天悯人与恐惧冷酷白先勇和张爱玲都从两性关系与婚姻关系方面来挖掘人性的病态因为“在世界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是爱。
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
蚍白先勇早期代表作《玉卿嫂》写一个叫玉卿嫂的年轻寡妇杀死情人后自戕的悲剧。
有一种情怀叫上海――从文学作品中看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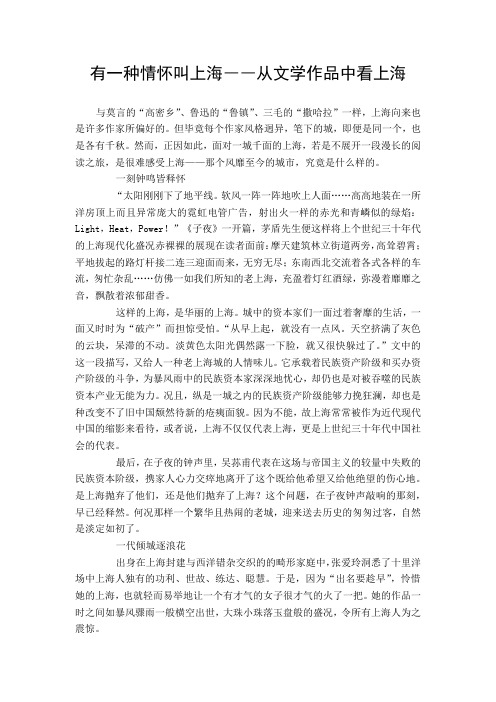
有一种情怀叫上海――从文学作品中看上海与莫言的“高密乡”、鲁迅的“鲁镇”、三毛的“撒哈拉”一样,上海向来也是许多作家所偏好的。
但毕竟每个作家风格迥异,笔下的城,即便是同一个,也是各有千秋。
然而,正因如此,面对一城千面的上海,若是不展开一段漫长的阅读之旅,是很难感受上海——那个风靡至今的城市,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刻钟鸣皆释怀“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
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嶙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子夜》一开篇,茅盾先生便这样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现代化盛况赤裸裸的展现在读者面前:摩天建筑林立街道两旁,高耸碧霄;平地拔起的路灯杆接二连三迎面而来,无穷无尽;东南西北交流着各式各样的车流,匆忙杂乱……仿佛一如我们所知的老上海,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飘散着浓郁甜香。
这样的上海,是华丽的上海。
城中的资本家们一面过着奢靡的生活,一面又时时为“破产”而担惊受怕。
“从早上起,就没有一点风。
天空挤满了灰色的云块,呆滞的不动。
淡黄色太阳光偶然露一下脸,就又很快躲过了。
”文中的这一段描写,又给人一种老上海城的人情味儿。
它承载着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为暴风雨中的民族资本家深深地忧心,却仍也是对被吞噬的民族资本产业无能为力。
况且,纵是一城之内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力挽狂澜,却也是种改变不了旧中国颓然待新的疮痍面貌。
因为不能,故上海常常被作为近代现代中国的缩影来看待,或者说,上海不仅仅代表上海,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代表。
最后,在子夜的钟声里,吴荪甫代表在这场与帝国主义的较量中失败的民族资本阶级,携家人心力交瘁地离开了这个既给他希望又给他绝望的伤心地。
是上海抛弃了他们,还是他们抛弃了上海?这个问题,在子夜钟声敲响的那刻,早已经释然。
何况那样一个繁华且热闹的老城,迎来送去历史的匆匆过客,自然是淡定如初了。
一代倾城逐浪花出身在上海封建与西洋错杂交织的的畸形家庭中,张爱玲洞悉了十里洋场中上海人独有的功利、世故、练达、聪慧。
海外张爱玲研究述评

海外张爱玲研究述评刘维荣 回首张爱玲1952年出走香港至今,海外研究她的学术进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57~1984年,以旅美学者夏志清,台港的水晶、林以亮等为代表,在文学史或专论中,较中肯地评述了张爱玲的创作实绩,但高估了她的才华和技巧,溢美之辞随处可见,几近认定张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这未免有吹捧过度之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于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分析,张氏小说的特色在于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对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在人生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无人可比。
水晶对其小说中玻璃与镜子的意象暗喻的把握觉颇有新意,同时采用比较文学、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分析《倾城之恋》和《沉香屑・第一炉香》及《秧歌》的多重变调复合结构、《半生缘》中的“潜我”和“他我”的文本解读,都对打破40年代迅雨(傅雷)、谭正璧、胡兰成的研究思路进行了尝试性的拓宽。
以台湾学者唐文标、林柏燕、王拓等为代表的学者,往往以偏狭的眼光,尖锐地指出她小说中流露出的一味追求技巧、格调不高、情趣卑俗的倾向。
在这一时间,公认为张氏小说的核心文本《金锁记》被提到不同的位置,或褒或贬,研究的笔力最为集中,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她小说的美丑感特征,具体层面或集中于主题、或意象、或受西洋文学的影响。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以夏志清和唐文标最有代表性,他们都发现张氏小说对普通人生苍凉的感悟,因是开风气之先,故在具体操作上是需要有超人的勇气和胆识的;但在论断的精辟和准确上均有不少失之公允的地方,也有不少见解为后来学者所诟嘲,但毕竟提供了不少理论上的依据可供参考。
如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中提出:张氏是去矗立一个旧的死的世界,趣味主义地描写她所熟悉的腐朽、衰败、垂死、荒凉,而没有加以道德的批判。
还详尽分析《传奇》,为她笔下的遗老遗少家庭画像、制表、写族谱。
尽管唐为编《张爱玲资料大全集》付出了不少心血,但他一味责难张氏抓不到时代进步的方向,分析方法未免过于机械功利,有的学者如傅禺、董千里,总试图置张氏早年的申辩不顾,而强行将她与汉奸文人联系,以诋毁其人格,未免有点太过庸俗无聊了。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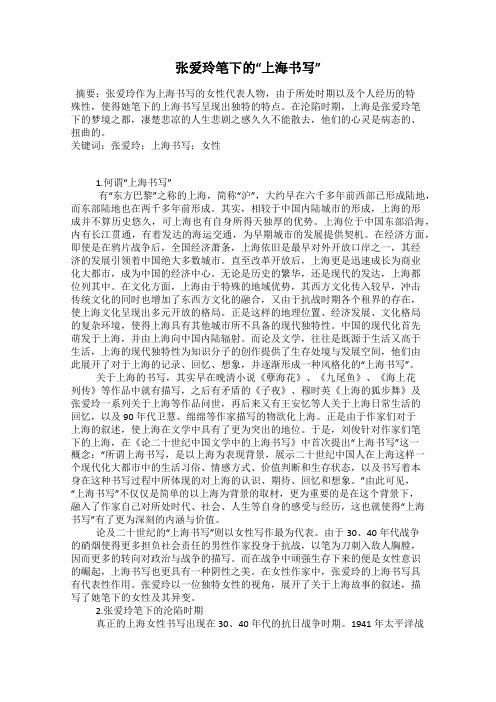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书写”摘要:张爱玲作为上海书写的女性代表人物,由于所处时期以及个人经历的特殊性,使得她笔下的上海书写呈现出独特的特点。
在沦陷时期,上海是张爱玲笔下的梦境之都,凄楚悲凉的人生悲剧之感久久不能散去,他们的心灵是病态的、扭曲的。
关键词:张爱玲;上海书写;女性1.何谓“上海书写”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简称“沪”,大约早在六千多年前西部已形成陆地,而东部陆地也在两千多年前形成。
其实,相较于中国内陆城市的形成,上海的形成并不算历史悠久,可上海也有自身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上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内有长江贯通,有着发达的海运交通,为早期城市的发展提供契机。
在经济方面,即使是在鸦片战争后,全国经济萧条,上海依旧是最早对外开放口岸之一,其经济的发展引领着中国绝大多数城市。
直至改革开放后,上海更是迅速成长为商业化大都市,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无论是历史的繁华,还是现代的发达,上海都位列其中。
在文化方面,上海由于特殊的地域优势,其西方文化传入较早,冲击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增加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又由于抗战时期各个租界的存在,使上海文化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格局。
正是这样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文化格局的复杂环境,使得上海具有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现代独特性。
中国的现代化首先萌发于上海,并由上海向中国内陆辐射。
而论及文学,往往是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上海的现代独特性为知识分子的创作提供了生存处境与发展空间,他们由此展开了对于上海的记录、回忆、想象,并逐渐形成一种风格化的“上海书写”。
关于上海的书写,其实早在晚清小说《孽海花》、《九尾鱼》、《海上花列传》等作品中就有描写,之后有矛盾的《子夜》、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及张爱玲一系列关于上海等作品问世,再后来又有王安忆等人关于上海日常生活的回忆,以及90年代卫慧、绵绵等作家描写的物欲化上海。
正是由于作家们对于上海的叙述,使上海在文学中具有了更为突出的地位。
于是,刘俊针对作家们笔下的上海,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中首次提出“上海书写”这一概念:“所谓上海书写,是以上海为表现背景,展示二十世纪中国人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状态,以及书写着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的对上海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
论张爱玲小说的文学成就及影响

论张爱玲小说的文学成就及影响论张爱玲小说的文学成就及影响摘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并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
其小说创作是现代文学的巨大收获。
其文学成就表现为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一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文学成就文学影响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其小说无论是选材、立意,还是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语言技巧无不显现出个人的特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女性文学像一条小溪流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若断若续地流淌着。
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掀起了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高潮,也给女性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冰心、庐隐、丁玲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脱颖而出。
她们冲破了传统文化禁忌,以女性视角观察女人、写女人,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女性形象。
冰心等作家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慈祥的母亲和贤惠的妻子,其道德审美观念仍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
丁玲等作家的作品中则塑造了一些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走出封建家庭,投身革命的女性,虽然表面上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待遇,实际上却放弃了自我。
与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相比,张爱玲的小说具有更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
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远离抗日救国的主流话语,把眼光投向了“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1]。
其小说集《传奇》刻画了一大群真实地生存于男权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
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一样,从女性本体出发,怀着对经济和精神上缺乏独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孜孜于女性悲惨命运的写作。
通过对一系列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描写,既揭示了男权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及习俗对女性的摧残,更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从女人原罪意识出发,对女性自身的人格弱点进行了思索与批判,开启女性批判立场。
一座“伤城”的两种感伤——张爱玲和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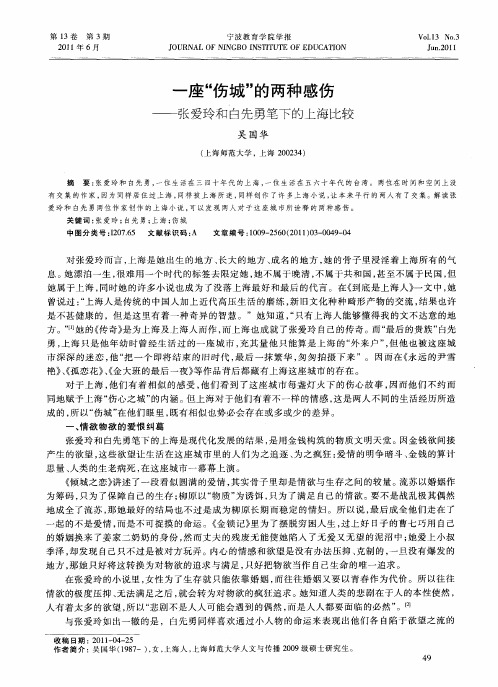
同地 赋予 上海 “ 心之城 ” 内涵 。但上 海对 于他 们有 着不 一样 的情 感 , 是两 人不 同的生活 经历所 造 伤 的 这 成 的 , 以“ 所 伤城 ” 他们 眼里 , 在 既有 相似 也势 必会 存在 或 多或少 的差 异 。
一
、
情 欲物 欲 的爱恨 纠葛
张爱玲 和 白先 勇笔下 的上 海是 现代 化发 展 的结果 , 是用 金钱 构筑 的物 质文 明天 堂 。因金钱 欲 间接 产生 的欲望 , 些欲 望让 生活 在这 座城 市里 的人们 为之 追 逐 、 这 为之 疯狂 : 情 的 明争 暗 斗 、 钱 的算计 爱 金 思量、 人类 的生 老病死 , 这座 城市 一幕 幕上 演 。 在
勇 , 海 只是 他 年幼 时 曾经 生 活过 的一座 城 市 , 上 充其 量 他 只能 算 是上 海 的 “ 外来 户 ” 但 他 也被 这 座城 ,
市 深深 的 迷恋 , “ 一个 即将 结 束 的 旧时代 , 后 一 抹繁 华 , 匆拍 摄 下 来 ”。 因 而在 《 远 的尹 雪 他 把 最 匆 永 艳 》 《 恋花 》 《 大班 的最 后一 夜》 、孤 、金 等作 品背后 都藏 有 上海这 座城 市 的存在 。
4 9
宁 波 教 育 学 院学 报
第 l 3卷
第 3期
宁 波 教 育 学 院 学报
J RNAL OF NI 0U NGB0 I T TU E 0 NS l T F EDUC 【 AT 0N
Vo |3 l No 3 1 .
21 0 1年 6月
J n2 u .01 1
论白先勇笔下的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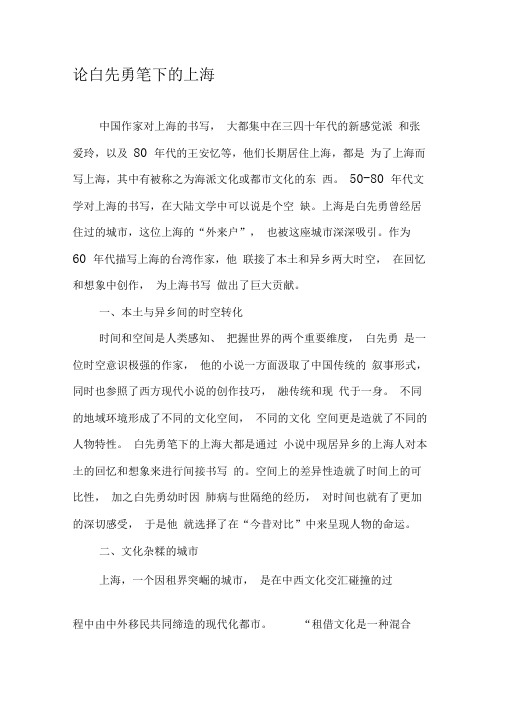
论白先勇笔下的上海中国作家对上海的书写,大都集中在三四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和张爱玲,以及80 年代的王安忆等,他们长期居住上海,都是为了上海而写上海,其中有被称之为海派文化或都市文化的东西。
50-80 年代文学对上海的书写,在大陆文学中可以说是个空缺。
上海是白先勇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这位上海的“外来户”,也被这座城市深深吸引。
作为60 年代描写上海的台湾作家,他联接了本土和异乡两大时空,在回忆和想象中创作,为上海书写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本土与异乡间的时空转化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感知、把握世界的两个重要维度,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极强的作家,他的小说一方面汲取了中国传统的叙事形式,同时也参照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融传统和现代于一身。
不同的地域环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空间,不同的文化空间更是造就了不同的人物特性。
白先勇笔下的上海大都是通过小说中现居异乡的上海人对本土的回忆和想象来进行间接书写的。
空间上的差异性造就了时间上的可比性,加之白先勇幼时因肺病与世隔绝的经历,对时间也就有了更加的深切感受,于是他就选择了在“今昔对比”中来呈现人物的命运。
二、文化杂糅的城市上海,一个因租界突崛的城市,是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过程中由中外移民共同缔造的现代化都市。
“租借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且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其浅薄粗陋不但引起中西社会的共同轻视而且常令身在其中的自觉者自卑。
这两难格局造就了一种复杂心态,一方面这种杂凑的不中不西的新兴文化强而有力富有诱惑,另一方面内内外外的人都嫌弃它而久久不愿认同于它。
”白先勇小说中的人物大都处于前一种心态,他们都因受到了新文化的诱惑,开始对西方文化表示盲目崇拜,并且迫切希望尽快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对自身的束缚。
首先,白先勇极力展示了租借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
他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就有论及,小说故事发生在上海虹桥镇,全篇采用孩子的叙述视角。
金大奶奶原本是个有钱的寡妇,之后遇到了有模有样,并对她百般体贴的金大先生,但是金大先生在骗取了金大奶奶的的钱财之后就开始虐待殴打她,最后他娶了位在上海唱戏的女人,新婚当天,金大奶奶服毒自尽。
《台北人》中的上海书写

,
苏 师范大 学 学生
汉语 言 文学 ( 师范 )
却 也不 仅仅 是 台 北
在 对 台北 生活 的 细致
,
勾勒 出 一 代人 的繁 华逝 去 参考文献
,
,
处 处透 着 白先 勇 对大 陆 的眷 恋
,
这 种 眷恋
浸 润在 过 去 纸醉 金 迷 的生 活里 非 的 沧桑 里 事实 上
,
浸润 在 如今 物 是人
上海
,
代 则 更加 的广 阔
着 一 个上 海情 结
虽然 有 所不 同
,
,
但 这 些作 家都 有
`
这 个 充 满 各种 故 事 的 大都 市
,
,
一直在
花样百 出
。
”
于是
,
白先 勇对 上海 的 记忆便 是儿 童
,
浓 缩 了 不 同 年化 魔都 ( 作 者单 位
:
”
的梦
。
许 多作 家 笔 下保持 着蓬 勃 的生 命 力
,
y n
,
o n
’`
g
Sha
g hai o r
in T a iP e i p e o Pl e i s m
o
直到 四八 年 的深 秋 离开
,
象 铸 就 了 他在 《台 北人 》 当 中的 上海 书 写
生 于 上海
、
张 爱玲
腼
ut
i伯 l m o e r g la m
K即
o
u s
,
对 我 一生
,
都 意 义 非凡 …
。
如果 说白先勇 笔下 的上 海是繁华的 上 海
是
【 ] 古 大勇 练 修 从 1
张爱玲与白先勇小说艺术观比较——以《传奇》和《台北人》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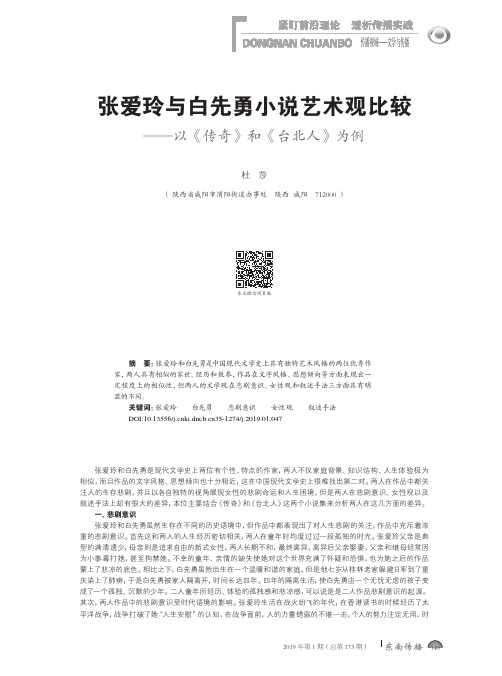
东南传播2019年第1期(总第173期)140张爱玲与白先勇小说艺术观比较——以《传奇》和《台北人》为例杜 莎( 陕西省咸阳市渭阳街道办事处 陕西 咸阳 712000 )张爱玲和白先勇是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有个性、特点的作家,两人不仅家庭背景、知识结构、人生体验极为相似,而且作品的文字风格、思想倾向也十分相近,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难找出第二对。
两人在作品中都关注人的生存悲剧,并且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展现女性的悲剧命运和人生困境,但是两人在悲剧意识、女性观以及叙述手法上却有很大的差异,本位主要结合《传奇》和《台北人》这两个小说集来分析两人在这几方面的差异。
一、悲剧意识张爱玲和白先勇虽然生存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但作品中都表现出了对人生悲剧的关注,作品中充斥着浓重的悲剧意识。
首先这和两人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两人在童年时均度过过一段孤独的时光。
张爱玲父亲是典型的满清遗少,母亲则是追求自由的新式女性,两人长期不和,最终离异,离异后父亲娶妻,父亲和继母经常因为小事毒打她,甚至拘禁她。
不幸的童年、亲情的缺失使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怀疑和恐惧,也为她之后的作品蒙上了悲凉的底色。
相比之下,白先勇虽然出生在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但是他七岁从桂林老家躲避日军到了重庆染上了肺痨,于是白先勇被家人隔离开,时间长达四年。
四年的隔离生活,使白先勇由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孤独、沉默的少年。
二人童年所经历、体验的孤独感和悲凉感,可以说是是二人作品悲剧意识的起源。
其次,两人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受时代语境的影响。
张爱玲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香港读书的时候经历了太平洋战争,战争打破了她“人生安慰”的认知,在战争面前,人的力量错弱的不堪一击,个人的努力注定无用,时摘 要:张爱玲和白先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两位优秀作家,两人具有相似的家世、经历和教养,作品在文字风格、思想倾向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但两人的文学观在悲剧意识、女性观和叙述手法三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一、对上海城市的情感张爱玲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是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她致力于描写这逐渐下沉的时代里平凡人中的传奇。
可以说张爱玲对上海的欣赏、喜爱、眷恋贯穿她始终的创作生涯。
张爱玲是都市生活的拥护者,她钟情热闹的都市生存经验,她在散文中曾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①即使她在去美国后,仍然时时“睹景思情”:“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
”②以上皆是张爱玲散文中的自述,足以见得她本人对于上海都市生活的热爱与怀念。
对比张爱玲,白先勇对上海的情感,则显得浅白且立足于城市繁华景象的追忆、想象与建构。
白先勇随家人来到上海定居时才九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时间,上海给白先勇留下了强烈的、惊艳而深刻的印象。
白先勇首先记取的仍然是这座城市的华丽外表。
他在《上海童年》一文中片段式地展示了记忆中“大世界”的哈哈镜、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等标志性场景,“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
” ③梳理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这些匆匆的影像在其创作的重要阶段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步入文坛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是以幼年初到上海近郊的经历为背景;他的小说集《台北人》的首篇《永远的尹雪艳》,以上海人的众生相作为大陆人流亡台北之生存写照的开场;在他另一部小说集《纽约客》中,同样以上海人为主角的《谪仙记》和《谪仙怨》也占据了较多篇幅,并以显著的地域个性凸显出来。
以白先勇较成熟的小说集《台北人》为例,这部小说集共有14篇,除去已指出的《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是描写上海交际女尹雪艳和金大班外,《孤恋花》的主人公以前是上海舞女,《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主人公朱焰和姜青的原型是上海名演员朱飞和白云。
④《游园惊梦》中的宴席上的鱼翅是从上海请来的厨师所烹,表示水准之高。
涉及上海人或事的竟有5篇之多,要知道白先勇先后随全家迁移经过桂林、四川、南京、上海、香港,定居台湾后又留学美国,在上海不过两年,却写了这么多关于上海的小说,刻画了如此多的上海人形象。
对此,白先勇自言:“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渐酝酿发酵。
” ⑤无独有偶,当白先勇接受林怀民的采访时自言,想家想得厉害,那“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是“所有关于中国记忆的总和”,陆士清指出,白先勇的“‘家’的意识附着点在上海”。
⑥白先勇也曾直言在上海有很深厚的感情,常将上海与父母姐姐等亲人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本质意义上,上海就是他心中的家的所在地。
二、对上海人及上海文化的价值判断张爱玲不止对上海这个城市素有好感,上海人,包括上海文化,也是她所赞赏的。
白先勇在描写上海人的同时,也对上海文化有所表达。
他注意到了上海文化内部的流变,看到了旧上海世俗文化对人的毁灭作用,上海新兴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龃龉。
(一)张爱玲对上海文化的赞赏在《到底是上海人》一文中,张爱玲直指“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且到处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这是对上海整体浓厚的文化氛围、实用的文化交流的赞许。
张爱玲对上海文化的赞扬体现在她运用“上海人的观点”创作小说,同时在小说中点出上海的文化吸引力和上海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1.运用“上海人的观点”。
张爱玲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
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⑦,此“上海人的观点”至少包含了道德口味、异国情调和都市意象三个层次。
⑧第一层次,“上海人的道德口味”,是比较市侩实用,但又不失原则的。
如《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哥儿达先生,他吝啬,宁愿把炒饭放馊了也不送给佣人阿小。
他多情,一边玩弄痴情的李小姐,一边与不同的女性交往。
他虽然坏,却也不是十恶不赦,夜晚他看见阿小在厨房睡觉,丝毫没有冒犯的想法,因为他觉得和女佣调情会降低佣人的服务品质,“好的佣人难得,而女人要多少有多少。
”⑨哥儿达完全符合张爱玲对上海人的定义:“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
”⑩第二层次便是异国情调。
当时的上海是比香港更发达更现代化的大都市,所以这里的“异国情调”并不是西洋景观或摩天大楼的氛围,而是奇特的中西混杂、华洋结合的文化混杂。
在上海女孩葛薇龙眼里,梁太太的别墅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却盖上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⑪,处处充满着不和谐。
豪华的客厅布置亦中亦西,更有梁太太的园会的布置,一派英国作风夹雜着晚清中国的元素,西方人可以在其中找到“伪东方”,上海人可以看到“伪西方”。
第三层都市意象。
张爱玲喜欢用人工世界形容自然世界且可以混淆两者界线,既体现她本人对室内物品的细致持久的特别兴趣,也显示了她对都市环境城市情调的美学理解。
⑫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月亮才上来,黄黄的,像玉带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
” ⑬张爱玲在小说的意象中常将人工的产物作为本体,自然的景物作为喻体,这种手法将自然人工化,暗含了一种哲思:现实生活也是真伪难辨的。
所有这些张爱玲式的独特意象,不仅要在灯红酒绿的背景里才能创造,而且也要在嘈杂市声的氛围里才能欣赏。
2.点出上海人的自我认同感。
有趣的是,张爱玲也在小说中点出上海人的优越感,或者是外乡人面对上海人的自卑感。
在《半生缘》中,叔惠笑道:“‘小城里的大小姐’,南京可不能算是个小城呀。
”世钧笑道:“我是冲着你们上海人的心理说的。
在上海人看来,内地反正不是乡下就是小城,是不是有这种心理的?”⑭世钧问叔惠,也许是他平时接触到的上海人大多自带一种优越感,或是他在生活中受到上海都市文化与文明的吸引,都让读者对上海人和上海的市民阶层有了模糊的感知。
事实上,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人是对自身的城市归属感到自豪的。
在上海,到处充斥着矛盾:时髦与老旧、前卫与保守、繁华与衰败、向死而生与向生而死……正是各种矛盾的张力的凸显,集中了这座城市及其治下的人民的发展无限的可能性。
学者赵园曾说,“矛盾,渗透在小说创造的整个艺术世界,由人物的生活情调,趣味,以至服饰,到精神生活,到婚姻关系。
”⑮上海不知不觉吸纳了大批外乡人来此经商、卖文,反过来更兴盛了上海的经济、政治、文化、时尚等领域。
(二)白先勇对上海文化流变的隐喻式诠释白先勇敏锐地道出了旧有上海世俗文化美且美,却包含着与生俱来的毁灭性。
换句话说,即使红色的时代浪潮没有改写世界主义的上海,她自己也可能走向灭亡。
⑯1.旧上海世俗文化的毁灭性。
这种毁灭力不仅指向对象,还指向自身。
前者如死神般的尹雪艳,她是无情的不老的死神,她的座上宾都一个个走上窮途末路甚至死亡的绝境;再如玉菩萨金兆丽,她在上海百乐门时做了不少伤风败德的事,害了不少的人。
后者有如李彤和黄凤仪。
李彤的形象是暗合上海这座躁动的城市的,她的命运就好比上海由于自身的狂躁达到极致反噬自身一般。
黄凤仪本来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却在纽约街头做妓女,是肉身的沉沦,也是精神的毁灭导致的。
这种毁灭是双向的,沉迷感官的愉悦、腐朽堕落的享乐可以腐蚀世道人心,旧世俗文化也可以毁灭一个人的精神,继而是肉体。
2.上海新兴文化与传统文化。
上海新兴的现代文化,成熟壮大,希冀打败并取代传统文化。
《金大奶奶》的故事就内隐了此寓意。
故事背景是在上海的农村,主人公金大奶奶原来是一个富有的寡妇,后来嫁给了追求她比她小很多的金大先生,最后被抛弃虐待,被迫服毒自杀。
金大奶奶其实就是传统文化的化身,她性格软弱,在强势的新兴文化面前丧失战斗力,必定处于劣势。
金大先生“刚从上海读了点儿书回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相人,他在上海徐家汇一带有些黑势力”。
作家反复提到“金大先生不像个坏人嘛!”“镇上系领带的只有他一个人呢!”⑰金大奶奶斑白短发、缠着小脚、走路跛行、涂厚厚的雪花膏、一对假眉一高一低,代表的是传统文化曾经的辉煌与现今的不合时宜、没落。
相比较而言,金大先生风度翩翩是一个美男子,强势而有手段,可见金大先生代表的是一股新兴的文化势力,所以现代文化取代传统文化成为历史的必然,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着现代文明的先进性,传统文明才败退的。
三、张爱玲与白先勇描写上海的原因如前所述,张爱玲喜爱都市和都市生活方式。
她在上海出生成长,混迹多年,对上海人和上海整体文化氛围很认同,且深受其影响,要为其“立言”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张爱玲的笔下,上海的一切似乎都是好的。
上海街道干净整洁,就算是拥挤的弄堂,市民生活起来却很便利、经济。
沿街叫卖的小贩的食物也比别地的精致美味,公寓中开电梯的职员,总是穿着体面,等等。
除此之外,也有商业因素的考量。
上海传媒出版业发达,市民读者众多。
张爱玲说道:“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难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而且大众是抽象的。
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⑱可见,张爱玲认同在上海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文人,不单是能够自足,也是一件很体面的事。
又如张爱玲评价苏青时也说过:“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⑲张爱玲从不避讳自己对于金钱的追求,上海的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可以给她带来体面的生活和文人的尊荣。
白先勇笔下的上海以自己的记忆为原型,因为他在上海时间很短,童年记忆也很久远,他向往的记忆中的老上海,是繁华、鼎盛、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不夜城,是新奇的万花筒。
他用现代主义笔触想要重塑回忆中老上海的辉煌。
他在上海的时期,是国民党党运高昂的时期,他的个人体验,与当时的“家国运”联系在一起的,即上海还是那个上海,由于作者将自身的情感投射到对象上去,所以上海从那时就在作者的心里留下了特殊的烙印,一直影响作者许多年的文学创作,就像鲁迅的《社戏》结尾时那样,“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在上海已然成为国民党失掉的好江山的缩影,是一个权利转移的象征后,许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上层阶级在小说中颇有种“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的悲戚怀旧之感,念念不忘上海的蟹汤包、上海的厨师做的鱼翅宴、大陆的花雕酒。
身为一代军阀之子,白先勇应该从小就接触到这些人,无意中熏染了他们的怀旧之情,更为自己早年留存的上海记忆增添神秘、迷人的意味。
迁居到台北的人上海人如此众多,台北俨然成为一个“小上海”,过去上海的舞女,仍旧在台北的“上海”舞厅中莺歌,上海的夫人们怀念上海的时髦衣料、精美的饭食。
写上海和上海人,可以切合白先勇小说的“老上海、新台北——今、昔之比”的主题。
其实白先勇反复写上海是很有些“风险”的。
他的“上海资源”本也不会很多,他不像张爱玲在上海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他的“上海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否则容易流入“炒冷饭”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