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神性的交融
神性与人性

神性与人性的变奏——艺术史演变的精神之维摘要:西方哲学有着强烈的人性特征,同时又具有浓厚的神性特点,人性与神性的并存形成了西方哲学的传统。
研究人性与神性的关系,对西方古代哲学中神性与人性的历史演进、矛盾运动进行分析、梳理,有助于对其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传承脉络关系,以及西方哲学思考方式的深层理解与把握。
关键词哲学;神性;人性由古希腊哲学所奠定的西方哲学的人性和神性的特征,构成了西方哲学的深厚的传统。
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各种哲学几乎都包容了人性和神性, 但近代从文艺复兴开始,尤其是20 世纪以来,在反传统思潮中,西方哲学家赋予人性以新的含义,批判并力图清除哲学的神性,成为西方哲学新的表现形态和发展趋势。
因而对神性与人性的追问,就成为了言述西方哲学的两种不可或缺的维度。
对西方古代哲学(从公元前5 世纪到公元后15 世纪,包括古罗马和中世纪两个时期) 大约两千年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学习西方文化,理解其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传承脉络关系,把握西方文化的思考方式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试图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就这一论题的历史演化作一梳理。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神性与人性的交融作为西方文化史之源的古希腊哲学诞生于城邦制的奴隶社会。
在从原始宗教之中脱颖而出的时候, 古希腊哲学首先表现为自然哲学的形态,这使它同时具有人性和神性的特征。
因为,那种自然哲学可以说是广义的人学,并包含着严格意义上的人学的萌芽。
正如黑格尔说的,自然界乃是与人“不同质”但又与人“牵连在一起”的人的另一半。
在古代哲学中,始基和宇宙本原的性质,决定了人的属性。
人类为了认识自已,首先必须认识自然界,所以认识自然界也就是间接地认识人自身。
当智者派把哲学变得通俗,即直接着手“认识自己”并通过人自身去看世界的时候,普罗塔戈拉率先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题。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1 ] (P187) 在他看来,世界万物都必须接受人的感觉的标准和评价,要由现实的人的喜怒哀乐来决定真假、善恶和美丑。
思辨“人性”与“神性”的抗争

思辨“人性”与“神性”的抗争梁铎(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南昌330000)摘要: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而在西方宗教的禁欲主义压制下,爱情每每带有悲剧色彩。
在西方文学作品关于神职人员的爱情的描写中,便有了“人性”与“神性”的抗争。
本文试从三部作品诠释西方宗教下的爱情悲剧。
关键词:爱情;人性;神性;抗争;悲剧爱情,永远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情感之一。
爱情与“谈爱色变”的禁欲主义一直在作着努力的抗争,即“人性”与“神性”的抗争。
尽管这种碰撞都带有悲剧色彩。
文章试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巴黎圣母院》、《红字》、《荆棘鸟》中笼罩在宗教统治下的爱情悲剧。
1人性悲剧:扭曲、变态的爱情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副主教克洛德一直被看作邪恶势力的代表,但如果认真考察他的内心世界及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就不难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牧师的虚伪,也有着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
纵观14世纪后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抨击了中世纪的教会的精神独裁和禁欲主义,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已成为普遍现象。
克洛德一直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
直到见到了在巴黎街头跳舞的艾斯美拉达,人的意识才觉醒了。
他被这种强烈的爱折磨着。
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这可谓是大逆不道。
但是副主教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感情、欲望和爱。
然而,他所要求的这种爱是他所代表的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表现出来的方式便是扭曲的,变形的。
他一方面憎恨宗教的非人性,一方面又在心里激起了对自己人性要求的憎恨,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法解脱的疯狂的人。
于是在他爱而不得中,他设置了一系列阴谋,劫持爱斯美拉达,诬陷她,直到把她送上绞刑架,处在“人性”与“神性”双重压迫下的克洛德,最终也在自己布下的宗教网中毁灭了。
2处境悲剧:内疚、自责的爱情与克洛德的悲剧不同的是,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红字》中则描写了海丝特·白兰与神职人员亚瑟·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悲剧。
二、从神性到人性,文

《创造亚当》是整个天顶画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这一幕没有直接画上帝塑造亚当,而是画出神圣的火花即 将触及亚当这一瞬间:从天飞来的上帝,将手指伸向亚当,正要像接通电源一样将灵魂传递给亚当。这一戏 剧性的瞬间,将人与上帝奇妙地并列起来,触发我们的无限敬畏感,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是达·芬奇为佛罗伦萨商人吉奥贡达的妻子 所作的肖像,先后用时四年。
《阿尔诺芬尼夫妇像》扬·凡·爱克
此前,画家们只是用鸡蛋清来调和颜料, 而扬·凡·爱克发现可以用松脂、亚麻油 或者核桃油来做调和剂,这样能够使颜料 更加易于调和,运笔也更自如,而且挥发 得快,等一层干了以后还可以反复描画, 这样就为描绘细节提供了许多便利,画出 画来颜色也格外鲜亮。直到今天,扬·凡 ·爱克的作品仍然完好如初。
二、从神性到人性,文艺 复兴改变了什么
思考: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原因
经 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阶 级: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 思 想:教会和神学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文化传统:意大利较多的保留了希腊、罗马
的古典文化
现实因素:黑死病在欧洲流行,促使人们反省
文艺复兴的实质、指导思想及其方式
实 质:文艺复兴是一场反对教会“神权至上”和提倡人文主义 的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
• 思想的解放 •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是以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謇挑战神学教育为开端的
。他们大力兴办世俗学校,打破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局面。 • 倡导人性教育,反对神性教育,从而将教育从神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这种解放是有限
的,囿于时代的局限。
课后练习:选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谈谈你对这幅绘画艺术的个人见解。
• 在左角的速写稿中,他想让圣婴一面回头仰望着他的母 亲,一面走开。他试画了母亲头部的几个不同姿势,以 便跟圣婴的活动相呼应。然后,他决定让圣婴转个方向 ,仰望着母亲。他又试验另一种方式,这一次加上了小 圣约翰,但是让圣婴的脸转向画外,而不去看他。后来 他又作了另一次尝试,并且显然急躁起来,用好几个不 同的姿势试画圣婴的头部,在他的速写簿中这样的画页 有好几张,他反复探索怎样平衡这三个人物最好。
“神性”的解构与“人性”的回归

“神性”的解构与“人性”的回归作者:王宏慧沈红梅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14期摘要: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内容包罗万象,文化内涵丰富。
对于西方宗教神权的颠覆就是其内涵之一。
小说中,圣人丑陋滑稽,圣殿污秽不堪,牧师猥琐淫邪,经典荒诞可笑。
这一切都旨在解构“神性”,进而回归“人性”。
也只有摒弃西方的意识形态,延续我们自己民族狂野的生命力才能抵制“种的退化”和“力的衰竭”。
关键词:莫言;《丰乳肥臀》;宗教;神性;人性作者简介:王宏慧,男,1974年10月2日生,吉林磐石人。
吉林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沈红梅,女,1976年11月27日生,黑龙江绥化人,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4-0-02《丰乳肥臀》以一个家庭为中心讲述了近百年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内容包罗万象。
依照作者本人说法,在这部小说中他“写了历史,写了战争,写了政治,写了饥饿,写了宗教,写了爱情”。
①然而,关于其他几个主题批评界早有见仁见智,唯独宗教鲜有论及。
笔者认为,宗教与其他几个主题一样贯穿小说始终,其重要性绝不逊色。
而作家对其大肆戏谑嘲讽,目的是解构“神性”回归“人性”。
这一意图在小说的开篇就体现出来。
整个故事是从瑞典籍牧师马洛亚和他的教堂开始的。
通过牧师的视角,破败的教堂里的一幅画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小说中第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意象。
圣母“粉红色的乳房”和圣子“肉嘟嘟的脸”与油画上“焦黄的水渍”和母子“木呆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②圣母的乳房是生命力的象征,圣子是圣母生命力的延续。
而本来应该有的庄严肃穆却成了木讷呆板。
作者似乎在小说的开篇就暗示了故事关于宗教的主题,即唯有生命力的延续才是救世的良方,而宗教的救赎力所不及。
换言之,只有解构颠覆“神性”,进而回归到“人性”,才能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
后来,在马洛亚牧师给上官家的金童玉女洗礼时,还有这样一段对于教堂的描写:“墙上悬挂着一些因年久而丧失了色彩的油画,画上画着一些光屁股的小孩,他们都生着肉翅膀,胖得像红皮大地瓜,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名字叫天使。
《圣经神话故事》读后感神性与人性的交织

《圣经神话故事》读后感神性与人性的交织在阅读《圣经神话故事》这本书时,我深深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神性与人性的交织,这让我对世界和人类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圣经中的故事充满了神秘、超自然的元素,如创世记中上帝创造世界的壮丽景象,以及大洪水中挽救诺亚一家的奇迹般情节。
这些故事给人带来一种无法言喻的敬畏与敬仰之情,让人感受到神性的存在和能量。
在这些故事中,上帝被描绘成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存在,引导人类前行,惩罚罪恶,赐予恩典。
这种神性的力量超越了人类的理解,使人们对宇宙、生命及人类的存在产生了更深刻的思考。
然而,与神性并存的是人性的脆弱和复杂。
圣经中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人性的多面性,他们有善有恶、有信有疑、有虔诚有背弃。
例如,亚当和夏娃背叛了上帝,导致了人类被赶出伊甸园;亚伯和该隐之间的兄弟仇恨;罗得的贪婪和妻子的背叛。
这些故事展现了人类面对诱惑、忠诚、背叛等各种挑战时的选择和后果,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和复杂性。
神性与人性的交织在圣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神性赋予了人类尊严和使命,引导人们追求善良、正义和真理;而人性的脆弱和复杂则提醒着人们自省、警惕和改变。
这种神性与人性的对话,让人更深切地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和伟大,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通过阅读《圣经神话故事》,我感受到了神性与人性的交织,这让我更加敬畏和珍惜生命,关怀和体谅他人,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和谐。
这些故事不仅是历史的记载,更是对人类经验和智慧的探索,引导着我们走向更加光明和美好的未来。
愿我们在神性与人性的交织中,找到自己的信念和力量,成为更加完整和善良的人。
以上是我对《圣经神话故事》的一些读后感,希望能够启发更多人思考神性与人性的关系,探索内心的奥秘和智慧,走向更真实、更美好的生活。
神性和人性的交织——从黑天形象演变看印度神话中的神人世界

神性和人性的交织——从黑天形象演变看印度神话中的神人世界文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张弛学号:**********【摘要】印度以其独特的宗教文化而闻名世界,印度教的教义成为印度人长久以来伦理道德的评判准则,他们崇尚天神,但是却将神的形象寓于普通人类,形成对人性化神的一种独特崇拜即巴克蒂崇拜。
从早期通过将三界中的种种自然现象加以人格化和神格化,创造诸诸神诸,诸诸来诸诸诸天诸为诸诸诸诸神化诸的形象诸诸人诸,印度人的神性诸诸是诸诸着人性和神性。
本文主要通过对印度早期神话、史诗《摩诃婆罗诸》以及中世纪《牧童歌》、《苏尔诗海》中诸天形象演变过程的研究,反映神话中的神人世界及印度人的神性诸。
【关键词】诸天神话神性人性交织【教师点评】印度文明从印度河文明开始,便显示出其特有的宗教传统和特点。
印度宗教信仰普遍存在,人民自觉地继承、坚持和表现它,并且将印度正统宗教(印度教)与诸为社会基本组织形式的种姓制度高度融诸起来,使其得诸不断发展。
在印度文学史上,文学诸品往往成为宗教和社会诸念的宣传方式和表现手法,具体表现为神人形象和说教成分的诸量涌现,诸品表现神、颂神,却不直接描写神。
本文通过对印度早期神话传说、史诗《摩诃婆罗诸》以及中世纪《牧童歌》、《苏尔诗海》中诸天形象演变过程的研究,反映印度人民神性和人性交织、诸诸的神性诸。
(点评教师:郁龙余教授)前言印度文明从印度河文明时代开始,便显示出其特有的宗教传统和特点。
直至公元纪年前后,婆罗门——印度教时代的确立,开启了印度教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明确“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等三大宗教纲领的基础上,强化了对印度教三大主神的崇拜,对整个印度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印度,文学与宗教、社会观念的联系十分紧密,文学往往成为一种宗教思想、教义的宣传方式和表现手法,文学作品与宗教典籍相互交融。
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大量涌现出神人形象和说教成分,对人物的刻画方面也将神性与人性很好地交织、揉合为一体,共同体现人物性格特征。
在神性与人性之间——解读古希腊悲剧时代

而与此相反,在城邦祭祀之外 ,还有一些秘教社团,比 如伊流欣努 秘仪 、 俄尔 甫斯教和狄俄尼索斯崇拜等,他们处 于社会共同体的边缘 ,“ 致力于开辟一条通 向希腊 神秘主 义 ’的道路 ,这种神秘主义 的特点是追求与诸神更直接、更 紧密、更个人的接触 。 6 ”【虽然这些秘教社 团的 目的是使其 J 成员享 受与神直接沟通的特权 , 但是 , 这种对神性 的追求乃 是一种纯粹 的精神追求 , 是一种基于个人 自由选择一 即对 该社 团的参与与否纯 由 自己决定——的宗教信仰 。 因此,这 些秘密传授的 “ ”只是人们各 自心 中信仰的神 ,它与在城 神 邦 中那个支配着所有公 民的、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必然 性 的公 共 之 “ ”全 然 没 有 关 系 。 神 “ 认识你 自己”这句特 尔斐神 谕透露 出 了这 两种对于 “ 神”的认识的差别 : 对于特尔斐神谕来说 ,‘ “ 认识你 自己’ 就意味着 ‘ 知道你不是神,也不要犯声称要成为神的那种错 误’ 。柏拉 图转述的苏格 拉底从 自己的角度重提 这个 公式 , 它要说的是 :认识那在你之 中,就是你 自己的神。在可能的 情况下 ,使 自己尽量与神接近 ( 着重符号为引者所加) 阴 。 前者乃是城邦的 “ 正义 ” 神,它 高高在人性之上 ,人们无 之 法企及 , 却又不得不受它支配 ; 后者则反映了那些秘教杜团 的追求 ,向往与神接近 ,甚至与神一体 ,因为那神就是他 自 己! 这种个人意志摆脱 必然性束缚的企图, 这种追求个人从 公共 的城邦生活领域解放 出来的企图, 为古希腊悲剧意识的 诞生提供 了原始的宗教起源 。“ 因此,哲学在起源时 ( 就)
在神性与人性之问
— —
解读古希腊悲剧 时代
万 远新
( 兰州理工 大学 ,甘 肃
神性与人性的精彩变奏

法朗士的获奖评语是:“他辉煌的文学成就,在于他高尚的文体……以及一个真正法国性情所形成的特质。
”神性与人性的精彩变奏译名:阿纳托尔·法朗士生卒年月:1844、4——1924、10国籍:法国代表作品:《泰伊丝》获奖评语:他辉煌的文学成就,在于他高尚的文体……以及一个真正法国性情所形成的特质。
192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一位法国左派人士,他的名字叫阿纳托尔·法朗士。
法朗士于1844年出生在巴黎一个书商家庭,他的童年是在书香熏陶下度过的,上学以后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其它方面的著作,极大地丰富了知识面,并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他热爱文学,信奉人文主义,同情社会底层人士,对社会现实十分不满,这些都构成他文学走向的朦胧标识。
1873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金色诗集》,由此受到文学界的注目,并成为“当代巴那斯”的骨干分子。
“当代巴那斯”是十九世纪末法国的一个诗歌团体,代表人物有普鲁多姆、邦维勒等,他们主张诗歌应不问政治、脱离社会现实,强调为艺术而艺术,是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前驱,作品情调悲观颓废。
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法朗士逐渐认识到“当代巴那斯”的主张与自己的所思所想裂痕渐大,后来他毅然脱离了“当代巴那斯”,开始小说创作,1881年出版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从此名声鹊起。
小说的主人公波纳尔是一位博学多才,充满善心的人,后因搭救一位孤女而犯了“拐骗罪”,孤女长大后,波纳尔又因从自己送给孤女的嫁妆里抽回几本书,犯了“盗窃罪”。
小说通过主人公的种种遭遇,表现出作者对社会的怀疑和愤懑。
接着,他又创作了《泰伊丝》、《佩克多女王的烤肉店》、《现代史话》、《在白石上》、《企鹅岛》等多部作品。
其中,《泰伊丝》是法郎士的代表作。
小说讲述了贵族子弟巴福尼斯皈依基督教,隐居在尼罗河畔的沙漠里修行了10年。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从前在亚历山大剧场见过的一个美丽放荡的女演员泰伊丝,他决心把她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希腊神话中的神性与人

希腊神话中的神性与人性姓名:***学号:**********提交日期:28-05-2014希腊神话中的神性与人性纵观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其实他们在每件事上都体现着他们的神性与人性,品味他们的人性时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他们时而冷酷无情,叫诈多变,嫉妒成性,背信弃义,不负责任。
同时他们也对人类有所爱护有加。
谈及他们的神性时我们也能找到他们与我们芸芸众生的不同,比如:他们有非凡的法力和永生的权利,他们是异能的是强大的。
他们能遇见未来,能随心所欲的变形,能驾云或乘车自由遨游天宇,这些都是常人所不及的。
那么就让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希腊神话中诸神们的神性与人性吧。
希腊诸神在性格和行为上均与凡人无异。
他们七情六欲俱在,所作所为均受情欲驱使,具有人类的种种弱点,绝非道德之圣贤。
他们与世人维持互惠关系,对虔诚者,引为所爱,赐以福祉,对怠慢犯者,引为所恨,必施以诅咒和报复。
特洛伊神话战争中,诸神因对交战双方各有恩怨而非常两派,各自支持一方。
神灵处处庇佑着自己钟爱的英雄,对凡间生育的子女更是爱护有加,充满人类亲情。
宙斯忍看爱子萨尔珀葬身沙场,竟流下伤心地泪水,忒提斯女神对阿基里斯的母爱更是真挚感人。
诸神对冒犯者必施以严厉报复,阿波罗因希腊人侮辱其祭司而在军营散播了九天瘟疫,小艾阿斯因在雅典娜女神庙内强奸特洛伊公主卡桑德拉,结果在返乡途中船尽人亡,忒拜王后尼俄柏嘲笑勒托女神子女少,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为母雪耻,将其六子六女尽射杀,嫉妒成性的赫拉无情的迫害情敌,宙斯则残酷折磨人类的恩主普罗米修斯。
神为实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阿芙洛狄忒为报答帕里斯,不惜拆散他人家庭,挑起战争。
希腊神祗从来都不是道德的化身,战神阿瑞斯是嗜血成性的战争魔王,赫尔墨斯为盗贼之主,阿芙洛狄忒则是娼妓的护身,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学家丹纳写了一本书叫《艺术哲学》,在这本书中他说:“希腊人竭力以美丽的人体为模范,结果竟奉为偶像,在地上颂之为英雄,在天上敬之如神明。
”因此,无论是希腊神话中的神明,还是希腊传说中的英雄,都具有人的形体,甚至比人更像人。
从《圣经神话故事》看神性与人性的和谐共生

从《圣经神话故事》看神性与人性的和谐共生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圣经》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经典之一,承载了丰富的神话故事和教义。
其中描绘的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神性和人性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
本文将从《圣经神话故事》中选取若干故事,通过分析其中所蕴含的神性与人性关系,探讨神性与人性如何在故事中展现出和谐共生之美。
1. 亚当与夏娃的创世故事《圣经》中的创世故事讲述了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天地万物,以及创造了第一个人类——亚当和第一个女性——夏娃。
亚当和夏娃作为人类的始祖,代表着人性的纯洁和神性的创造。
他们在伊甸园中生活,与上帝和谐共处,展示了神性与人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尽管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犯了原罪,但上帝的怜悯与宽恕也彰显了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和谐共生。
2. 摩西领导以色列人民出埃及《圣经》中也记载了摩西领导以色列人民出埃及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摩西作为一个受上帝启示的先知和领袖,展现了神性的力量和智慧。
他带领以色列人民跨越红海,逃离埃及的奴役,并颁布十诫,指引人民生活。
这个故事中神性与人性之间的互动,体现了神性的慈爱与人性的顺服,共同谱写了一曲和谐共生的乐章。
3. 耶稣的生平故事耶稣作为《圣经》中的主角之一,他的生平故事展示了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
耶稣具有神性的智慧和神迹,同时也体现出丰富的人性情感和同理心。
他以无私的奉献和宽恕的胸怀感染着人们,教导人们爱与宽恕。
耶稣的生平故事让人们感受到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和谐共生之美,引领人们走上正义和仁爱之路。
4. 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圣经》中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展示了神性与人性之间的战斗与智慧。
大卫虽然是个年轻的牧羊人,但他凭借着忠诚和勇气,打败了巨人歌利亚,展示了神性的力量与人性的勇气。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神性与人性的和谐共生并不意味着没有挑战和困难,而是通过信仰和智慧共同克服困难,展现出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
总之,《圣经神话故事》中蕴含着丰富的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关系,这些故事展现了神性与人性的和谐共生之美。
希腊神话中的神性与人

希腊神话中的神性与人性姓名:***学号:**********提交日期:28-05-2014希腊神话中的神性与人性纵观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其实他们在每件事上都体现着他们的神性与人性,品味他们的人性时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他们时而冷酷无情,叫诈多变,嫉妒成性,背信弃义,不负责任。
同时他们也对人类有所爱护有加。
谈及他们的神性时我们也能找到他们与我们芸芸众生的不同,比如:他们有非凡的法力和永生的权利,他们是异能的是强大的。
他们能遇见未来,能随心所欲的变形,能驾云或乘车自由遨游天宇,这些都是常人所不及的。
那么就让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希腊神话中诸神们的神性与人性吧。
希腊诸神在性格和行为上均与凡人无异。
他们七情六欲俱在,所作所为均受情欲驱使,具有人类的种种弱点,绝非道德之圣贤。
他们与世人维持互惠关系,对虔诚者,引为所爱,赐以福祉,对怠慢犯者,引为所恨,必施以诅咒和报复。
特洛伊神话战争中,诸神因对交战双方各有恩怨而非常两派,各自支持一方。
神灵处处庇佑着自己钟爱的英雄,对凡间生育的子女更是爱护有加,充满人类亲情。
宙斯忍看爱子萨尔珀葬身沙场,竟流下伤心地泪水,忒提斯女神对阿基里斯的母爱更是真挚感人。
诸神对冒犯者必施以严厉报复,阿波罗因希腊人侮辱其祭司而在军营散播了九天瘟疫,小艾阿斯因在雅典娜女神庙内强奸特洛伊公主卡桑德拉,结果在返乡途中船尽人亡,忒拜王后尼俄柏嘲笑勒托女神子女少,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为母雪耻,将其六子六女尽射杀,嫉妒成性的赫拉无情的迫害情敌,宙斯则残酷折磨人类的恩主普罗米修斯。
神为实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阿芙洛狄忒为报答帕里斯,不惜拆散他人家庭,挑起战争。
希腊神祗从来都不是道德的化身,战神阿瑞斯是嗜血成性的战争魔王,赫尔墨斯为盗贼之主,阿芙洛狄忒则是娼妓的护身,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学家丹纳写了一本书叫《艺术哲学》,在这本书中他说:“希腊人竭力以美丽的人体为模范,结果竟奉为偶像,在地上颂之为英雄,在天上敬之如神明。
”因此,无论是希腊神话中的神明,还是希腊传说中的英雄,都具有人的形体,甚至比人更像人。
神性与人性_论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道德主题

第8卷 第1期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l.8,N o.12009年2月Journal of Dalian Maritime U 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09文章编号:167127041(2009)01201222043收稿日期:2008211209作者简介:尹翎鸥(1971-),女,山东掖县人,副教授;E 2m ail :Y LOSeagull @神性与人性———论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道德主题3尹翎鸥(大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28)摘要:从伦理道德角度对莎士比亚文学作品进行考察。
以文化为参照,以人为基点,以道德主题嬗变的整理讨论为指归,透析文艺复兴“人”的道德图式。
文艺复兴是神性回归并参与人性建设的时代,其成为莎士比亚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
他完成了后期人文主义对“人”的诠释:享受现世节制的自然之爱,同时以上帝之爱消弭邪恶。
莎士比亚文学作品道德主题体现为神性超拔人性、人文终极的图式。
关键词:莎士比亚;文艺复兴;道德;人文主义;神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Divine and hum an nature———M orality subject in Shakespeare ’s literary w orksYI N Ling 2ou(C ollege of F oreign Languages ,Dalian Jiaotong Univ.,Dalian 116028,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nvestigated Shakespeare ’s literary w orks in terms of ethics.T aking the culture as the reference and humans as the basis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changes in m oral m otifs and ana 2lyzed people ’s m orality during the Renaissance.The Renaissance is the era that the divine nature returns and participates in the human nature construction ,which features Shakespeare ’s w orks.He ac 2com plished the later stage humanism annotation to “pers on ”:to en 2joy life ’s natural love m oderately ;to eliminate evil with the love of G od.Shakespeare ’s literary w orks embodies the m orality subject that the divine nature prom otes the human nature ,and the ultimate scheme of humanism.K ey w ords :Shakespeare ;the Renaissance ;m orality ;humanism ;G od 一、引 言瑞士著名史学家、文化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称文艺复兴为“人”的发现时代。
从“神坛”跌落“人间”

从“神坛”跌落“人间”【摘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曾有许多神话故事描述了神明从“神坛”跌落至“人间”的情形。
这种跌落象征着神灵与人类世界的联系,也意味着神性与人性的交融。
正文中,我们看到了神灵的落幕,人间的挑战和磨砺,信仰的失落与迷茫,以及心灵的得以净化,人性的升华与超越。
这些过程让我们重新审视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以及重新审视人类的本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或许会找到一种更加接近真实的自我,重新认识并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
神灵的跌落并非是堕落,而是一种必然的进化,是为了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人性的喜怒哀乐,从而达到更高的境界。
神与人,原本就是一个整体,而每一次跌落都是为了更完整地体悟这个整体的意义。
【关键词】引言、神坛、人间、神灵、落幕、挑战、磨砺、信仰、失落、迷茫、心灵、净化、人性、升华、超越、关系、人生、意义、价值、本质、审视。
1. 引言1.1 从“神坛”跌落“人间”从“神坛”跌落“人间”是一个古老而又深刻的主题,它涉及到人类意识中神秘和现实的交汇点,探讨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在世间的角色与使命。
在这个主题下,我们将探索着神灵的落幕,人间的挑战和磨砺,信仰的失落与迷茫,心灵的得以净化,以及人性的升华与超越。
这些方面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揭示了人类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探索与挑战。
通过对“神坛”与“人间”的跌落进行思考和探讨,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人类的信仰与观念,重新审视人类的本质与使命,以及重新审视人类个体在宇宙中的位置和作用。
这个深刻而又迷人的主题,将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深刻的思考和探索之路。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或许会发现,神并不遥不可及,人间并非无足轻重,而是一个复杂而又美丽的整体,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和领悟。
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以及人类的本质与真实,将在这个主题下得到更加丰富和深刻的阐释和揭示。
2. 正文2.1 神灵的落幕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刻,神灵从“神坛”跌落至“人间”,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融入人类世界之中。
钟馗形象的人性与神性转换

2016.06一、凶狠残暴的神“钟馗”形象的形成自有其演变过程,最初的钟馗也完全不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与外在形象的人物。
敦煌写本《太上洞渊神咒经》中记载着有关于钟馗的内容,其《斩鬼第七》记载:今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得,便付之辟邪。
在这段记录中并没有关于钟馗外貌与性格的具体描写,记叙的也相对简单,可以看出的是,当时钟馗唯一的一个作用就是“杀”鬼,孔子和武王负责“执刀”、“缚之”,从文本中可以看出,此时的钟馗不仅没有一个生动具体的外在形象,也没有任何性格上的特征,而且在捉鬼杀鬼的行动中,地位和作用低于孔子和武王二位圣人,类似于辅助的作用。
这是钟馗故事的萌芽期,而在敦煌文书伯2569记载,适从远来至宫门,正见鬼子一郡郡。
就中有个黑论敦,条身直上舍头存。
眈气袋,戴火盆。
眼赫赤,着非裈。
青云烈,碧温存。
……唤中馗,兰着门。
弃头上,放气薰。
慑肋折,抽却筋。
拔出舌,割却唇。
正南直须千里外,正北远去亦须论。
可以想见此时钟馗的残暴、凶狠和野蛮。
从这也可以看出,在远古时代,人们对于害人的恶鬼没有一个明确可行的驱逐方法,只能单纯的“以恶制恶”来遏制鬼怪。
此时钟馗所展现出来的是单纯的“恶”形象,在文本也侧重的描写钟馗是如何处置和对待鬼魅的,手段相对残忍。
如敦煌写本伯3522中,呪愿太夫人,敕封李郡君……鱼膏柄龙烛,魍魉敢随人?中夔并白宅,扫障尽妖纷。
……适从远来至宫宅,正见鬼子笑嚇嚇。
偎墙下,傍篱栅。
头朋僧,眼隔搦。
骑野狐,遶项胍。
捉却他,项底揢。
塞却口,面上摑。
磨里磨,磑里侧。
镬汤烂,煎豆。
放火烧,以枪擭。
刀子割,脔脔擗。
因今驱傩除魍魉,纳庆先祥无灾厄。
钟馗的最初的“恶”形象与远古人简单质朴的鬼神观念有关,在他们眼中鬼怪是无恶不作凶狠残暴的,唯有更强更凶狠残暴的人或物才能够制服这些鬼怪,也唯有残酷的手段才能够让这些鬼怪害怕、敬畏。
残忍的驱鬼手段和仪式不仅表达了人们心中对鬼怪的憎恶和愤怒,同时这也是一种表演给鬼怪看的仪式,产生一种震慑的作用。
神的“人性”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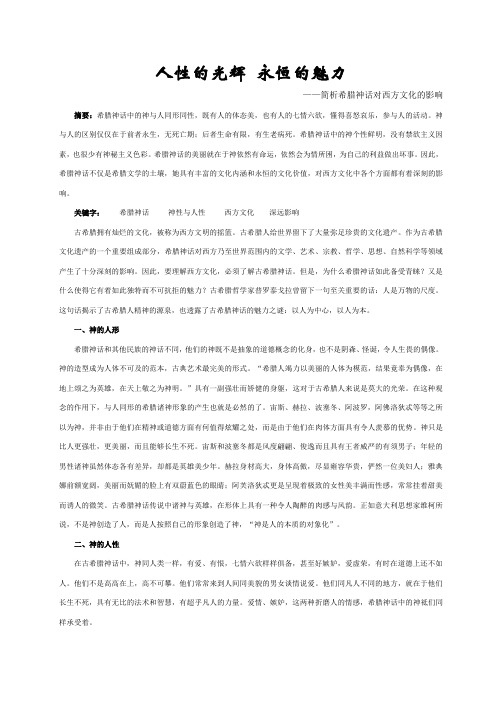
人性的光辉永恒的魅力——简析希腊神话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摘要: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人同形同性,既有人的体态美,也有人的七情六欲,懂得喜怒哀乐,参与人的活动。
神与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永生,无死亡期;后者生命有限,有生老病死。
希腊神话中的神个性鲜明,没有禁欲主义因素,也很少有神秘主义色彩。
希腊神话的美丽就在于神依然有命运,依然会为情所困,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坏事。
因此,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文学的土壤,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永恒的文化价值,对西方文化中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字:希腊神话神性与人性西方文化深远影响古希腊拥有灿烂的文化,被称为西方文明的摇篮。
古希腊人给世界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作为古希腊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腊神话对西方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思想、自然科学等领域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因此,要理解西方文化,必须了解古希腊神话。
但是,为什么希腊神话如此备受青睐?又是什么使得它有着如此独特而不可抗拒的魅力?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曾留下一句至关重要的话: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句话揭示了古希腊人精神的源泉,也透露了古希腊神话的魅力之谜: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
一、神的人形希腊神话和其他民族的神话不同,他们的神既不是抽象的道德概念的化身,也不是阴森、怪诞,令人生畏的偶像。
神的造型成为人体不可及的范本,古典艺术最完美的形式。
“希腊人竭力以美丽的人体为模范,结果竟奉为偶像,在地上颂之为英雄,在天上敬之为神明。
”具有一副强壮而矫健的身躯,这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是莫大的光荣。
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与人同形的希腊诸神形象的产生也就是必然的了。
宙斯、赫拉、波塞冬、阿波罗,阿佛洛狄忒等等之所以为神,并非由于他们在精神或道德方面有何值得炫耀之处,而是由于他们在肉体方面具有令人羡慕的优势。
神只是比人更强壮,更美丽,而且能够长生不死。
宙斯和波塞冬都是风度翩翩、俊逸而且具有王者威严的有须男子;年轻的男性诸神虽然体态各有差异,却都是英雄美少年。
神性与人性的变奏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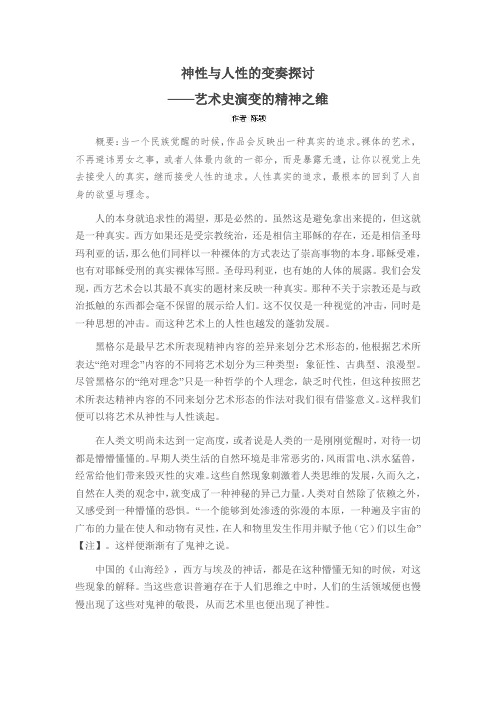
神性与人性的变奏探讨——艺术史演变的精神之维概要:当一个民族觉醒的时候,作品会反映出一种真实的追求。
裸体的艺术,不再避讳男女之事,或者人体最内敛的一部分,而是暴露无遗,让你以视觉上先去接受人的真实,继而接受人性的追求。
人性真实的追求,最根本的回到了人自身的欲望与理念。
人的本身就追求性的渴望,那是必然的。
虽然这是避免拿出来提的,但这就是一种真实。
西方如果还是受宗教统治,还是相信主耶稣的存在,还是相信圣母玛利亚的话,那么他们同样以一种裸体的方式表达了崇高事物的本身。
耶稣受难,也有对耶稣受刑的真实裸体写照。
圣母玛利亚,也有她的人体的展露。
我们会发现,西方艺术会以其最不真实的题材来反映一种真实。
那种不关于宗教还是与政治抵触的东西都会毫不保留的展示给人们。
这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冲击,同时是一种思想的冲击。
而这种艺术上的人性也越发的蓬勃发展。
黑格尔是最早艺术所表现精神内容的差异来划分艺术形态的,他根据艺术所表达“绝对理念”内容的不同将艺术划分为三种类型:象征性、古典型、浪漫型。
尽管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只是一种哲学的个人理念,缺乏时代性,但这种按照艺术所表达精神内容的不同来划分艺术形态的作法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
这样我们便可以将艺术从神性与人性谈起。
在人类文明尚未达到一定高度,或者说是人类的一是刚刚觉醒时,对待一切都是懵懵懂懂的。
早期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是非常恶劣的,风雨雷电、洪水猛兽,经常给他们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这些自然现象刺激着人类思维的发展,久而久之,自然在人类的观念中,就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异己力量。
人类对自然除了依赖之外,又感受到一种懵懂的恐惧。
“一个能够到处渗透的弥漫的本原,一种遍及宇宙的广布的力量在使人和动物有灵性,在人和物里发生作用并赋予他(它)们以生命”【注】。
这样便渐渐有了鬼神之说。
中国的《山海经》,西方与埃及的神话,都是在这种懵懂无知的时候,对这些现象的解释。
当这些意识普遍存在于人们思维之中时,人们的生活领域便也慢慢出现了这些对鬼神的敬畏,从而艺术里也便出现了神性。
从《圣经神话故事》看神性与人性的交织与碰撞

从《圣经神话故事》看神性与人性的交织与碰撞一、引言《圣经神话故事》作为古老的文化遗产,承载着对神性与人性的思考和描绘。
在这些叙述中,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交织着情感、信仰与人性的复杂情感。
本文将通过分析《圣经神话故事》中的神话叙事,探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故事中交织与碰撞,展现出神性与人性的复杂关系。
二、神性与人性的对立与融合神性在《圣经神话故事》中往往呈现出超越人类的力量与智慧,是人类的信仰对象。
然而,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对立也体现在神话故事中。
举例来说,在《创世纪》中,神创造了亚当与夏娃并将他们放置于伊甸园,却因为他们食用了禁果而遭到谴责与惩罚。
这种隐喻表达了人性的叛逆与神性的正义之间的矛盾。
虽然神性与人性之间存在着对立,但在某些叙事情节中,二者却得到了和谐的融合。
例如,在《出埃及记》中,上帝为以色列人民带来了奇迹,引领他们脱离埃及的压迫。
在这一叙事中,神性与人性的力量交汇,共同构成了一个英雄的故事,展现出人性的顽强与神性的慈爱并存的形象。
三、神性与人性的交织与相互影响在《圣经神话故事》中,神性与人性并非完全分离,而是在相互影响中共同塑造了故事的深度和魅力。
神话叙事中的神性形象往往承载着人类的理想与信仰,同时也反映出人性的复杂与矛盾。
例如,《约伯记》中描述了约伯经历磨难与信仰的考验,揭示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人生的苦难中交织与碰撞。
而在《以赛亚书》中,神的光辉与人类的罪恶同样呈现出了神性与人性的对比。
神性的慈爱与人性的罪恶在这一叙事中交织出了复杂的冲突,引发了人类对道德与信仰的思考与探索。
四、结语通过对《圣经神话故事》中神性与人性的交织与碰撞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文化中对神与人关系的思考与表达,也可以从中深刻体会到人性的复杂性与神性的崇高。
神性与人性的交织与碰撞不仅展现了古代文化的智慧,也启示着人类对自身存在与信仰的永恒探索。
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我们或许仍可以借鉴《圣经神话故事》中神性与人性的对话与碰撞,深刻审视人类的内心世界,探求信仰与道德的坚守。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人性与神性的交融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灵史》与《荆棘鸟》,在现实之此岸世界与宗教之彼岸世界的交叉地带,以其对于人性、人类命运的深切洞察以及对于宗教信仰和人的精神追求的深邃揭示,实现了人性和神性的交融,展示了作家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
标签:人性;神性;苦难;宗教;世俗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文学始终注重对人的心灵状态的追踪与描述。
自古以来,人们就能从文学的世界里,观照到人类自身关于人生、命运、爱情、生死等重大命题的体验和思考。
而且,优秀的文学作品还往往能以其对人类命运、人生价值的深切透视与终极关怀,走进人类的精神生活,成为嘈杂纷扰的现实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养料,从而凭借它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构成人类在现实人生之外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境界。
宗教之于人类也是如此。
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指出,“宗教是整个人类精神的底层”,它所关注的不是对由本能所支配的现实人生的种种欲望,而是“一种对生命的意义,对人的自我实现,对完成生命向我们提出的任务的终极关注”。
文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传达人类的情感理想。
缘于文学与宗教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今中外的文学家,都把人性与神性、现实之此岸世界与宗教之彼岸世界的交叉地带,作为文学作品的永恒题材来观照。
本文试图将中外两部以宗教生活为观照视域和艺术轴心的长篇小说,即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心灵史》和澳大利亚当代作家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作一比较。
这两部作品均产生于20世纪后半期,且都以其对人性与神性、现实与精神的深切关注,吸引着众多论者的目光。
笔者希望通过对它们的比较,来探究和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位作家关于宗教与人生、人性关系的思考,来考察宗教与人类精神生活的融通与背离之处,并由此透视出两位作家博大深邃的人文精神。
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佳构作为不同国度的文学作品,《心灵史》和《荆棘鸟》形成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自然各不相同,作者的文化建构、文学观念及审美理想也各具特征。
张承志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他的红卫兵生涯、知青生涯结束之后。
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同代作家一样,张承志力图用文学的形式,来总结和反思这段历史。
草原的游牧文化对张承志产生了脱胎换骨的重要影响,铸就了他生命的底色和精神气质中最本质的特征,成为他人生旅途上最为厚重的一次铺垫。
而且正是这次铺垫,成为他虽九死而不悔地追求人生理想的强大动因。
同时,张承志是一个回族作家。
缘于种族的血脉,他自幼受到母亲——名虔诚的穆斯林的感染。
当他在1980年代后期浪游于西北腹地时,他既感受着甘、宁、青黄土高原的贫瘠与荒凉,同时也体验到了回族捍卫内心信仰的刚烈品格。
回回人在贫苦苍凉的环境、艰窘而深受压抑的处境中所体现出的崇高而悲壮的生存品格,使张承志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感到由衷的惊喜。
他觉得自己从中发现了自我母族人生生不息的秘密,看到并深切地感受到了信仰的伟大和力量!他以这种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民族的危机感,构成其文本立意和内在结构的基础。
这种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促使张承志决意“以笔为旗”,做一番孤独的抗争,张扬他“清洁的精神”、“无援的思想”,在“落日时分的中国”做一个文化的抵抗和捍卫者。
同时,在经历过一次次心灵的净化和宗教洗礼后。
张承志终于在1990年代初期,义无反顾地皈依了自己母族的信仰,成了一名自觉而坚定的伊斯兰教信徒,实现了自己人生道路上一次信仰的“终旅”。
这样,在张承志的文学视野里,“回民的黄土高原”就成为一片最神圣最庄严的净土。
他用自己的全部热望和激情,描写着这个部族在苦难与死亡中追求信仰以求得精神人格升华与永恒的生命图景与历史画卷。
从他的前期中短篇小说《残月》、《黄泥小屋》,到晚期以长篇小说《心灵史》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均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出版子1991年的《心灵史》,正是建构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下的寓意深邃的文本。
有人说它是一部宗教史,有人则认为是一部哲学著作。
实际上,《心灵史》可看做是一部诗化的小说,小说化的教派史。
小说着重描述了被他概括为“束海达依主义”的哲合忍耶精神。
作品共分七门,即七章,每一门叙述了一代圣徒,一共叙述了七代圣徒从创教到护教,直到使教派复兴的几起几落的悲壮历史。
剥开笼罩在作品叙述中的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面纱,可以说,《心灵史》的精神内核,实际上是在讴歌理想主义的一种极致性的表现形式,即哲合忍耶人那种为了心灵的自由,为了理想中的“净土”,不惜甚至渴求殉命,渴盼“提着血衣甩手进天堂”的精神。
澳大利亚作家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则产生于另一种异质的文化环境中。
澳大利亚原本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大陆,移民的到来使这个相对孤寂的大陆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但问题是当一个人不远万里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大陆时,不免产生对祖籍地的眷恋以及那种经常不期而至的“人在旅途”的漂泊感。
宗教无疑是人们沟通与交流的重要纽带。
宗教信仰给予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它比任何物质上的帮助更具有持久和实质性的效力。
“宗教纽带具有将人和超人联系起来的力量,因此也是一种社会纽带。
人和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经常的相互联系,永久的相互作用。
宗教是规范这些社会作用及反作用的规则总体。
很自然,这些规则就会被认为是控制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培养了新老移民之间的情感以及对祖籍地的眷恋。
正是由于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及其不断的变更,才使得宗教以一种新的丰富多彩的姿态走入人们的生活。
随着二战以来澳大利亚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迅猛发展,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意识和信仰发生了变化。
澳大利亚人本来就缺乏坚定的信仰,加之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导致原有的薄弱的信念也开始动摇了。
信仰的动摇,导致对旧有的道德规范的大胆突破。
而社会生活的变化、道德规范的突破及由此带来的生命个体人生轨迹的变化,则给当时的思想家、文学家提供了思想和创作的肥沃的土壤。
于是,澳大利亚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开始思考,开始探究生命的价值及意义,探究人的内心,探究人类痛苦的原因以及上帝是否应对此负责任等深刻而令人痛苦的问题。
他们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学形式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把其触角伸向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反映当今澳大利亚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现实。
著名作家考琳·麦卡洛。
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着、思考着和追问着。
考琳·麦卡洛的创作活动起步于1974年发表的《蒂姆》,迄今为止已出版了13部小说。
她曾耗费13年心血潜心研究罗马帝国的衰败史,写出了《罗马第一人》(1990)、《草冕》(1991)、《命运的宠儿》(1993)、《恺撒的女人》(1996)、《特洛伊之歌》(1998)、《恺撒》(1997)等六部历史题材的作品,除了小说,她还写传记、散文、杂文,甚至写音乐剧,而其作品中最负盛誉的,则是问世于1977年的长篇小说《荆棘鸟》。
这部作品问世以后,不仅畅销国内,而且风靡全球,成为国际畅销小说。
根据小说改编的音乐剧、电视剧,艺术魅力也经久不衰。
《荆棘鸟》讲述的是克利里家族传奇式的家世史。
这部小说围绕着内地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女主人公梅吉和罗马天主教大主教拉尔夫之间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传统伦理道德和渴望爱情自由的矛盾心理,揭示了信仰的束缚与个性自由之间存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作者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将人世间方方面面的重大内涵,都浓缩进了这部作品之中。
作家试图通过克利里家的沧桑巨变和情感历程,在人性与神性的冲突、痛苦与极乐的交响中,揭示这样一个道理:真正的爱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需要以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的。
虽然《心灵史》和《荆棘鸟》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但在人性、人类精神信仰方面它们存在着很多相通之处。
二、穿越苦难的人性光辉痛苦与快乐是人生命体验的两极,在《心灵史》和《荆棘鸟》中,作者都关注这生命的两极,都不回避经历苦难而追寻一种至美,都有一种面对命运不屈不挠的意志品格。
与命运抗争,使无比深沉的苦难转化为无与伦比的极乐,不同之处在于《心灵史》显示的是殉教的欢乐,《荆棘鸟》表示的是殉情的极痛所激发的极乐体验。
一切有深度的幸福体验都必须以痛苦和坚韧为激素,必须以生命为代价才能换取信念的永恒。
这一点正是两部作品中体现出的苦乐观的共同之处,其中所显示的,则是两位作家观照世事与人生的深刻的辩证眼光,以及对于人类命运形态的深切把握。
张承志认为,中国底层不畏牺牲坚守心灵的人民中,蕴蓄着强烈的生存意志和殉难精神。
哲合忍耶被称作是“血脖子教”,提倡“束海达依”精神,他们祖祖辈辈“举红旗”,“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就是这种意志和精神的体现。
在荒凉贫瘠的西海固,这支坚忍的民族活得艰难,死得无畏,他们可以为心中的“念想”坦然殉教。
《心灵史》堪称是一部向读者诉说苦难的奇书。
尽管作品的议论与抒情不时流露出作者的偏激和暴躁,但对哲合忍耶民族苦难历史的叙述,则显得沉实而丰厚。
作品中充溢于那苦难民族的精神之海中的充实与畅达,足以激活当代人已经麻痹了的心脏和神经。
在作品中张承志通过对苦难的述说,赞美了存在于底层民间的真正的人道、理想、信仰和生命的意义。
而这也正是人类在自身内部所能够唤起的抗拒苦难、征服苦难的希望和根据。
张承志在《心灵史》中用自己全部的热望和激情,描写了一幅黄土高原上生生不息的流民图,“抒写了一个关于苦难与超越、贫困与信仰、死亡与永生的神话,一个靠着精神乌托邦所支撑起来的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和一部悲壮的英雄史诗”。
张承志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引人注目的硬汉形象,他们都具有尼采所推崇的“超人”意志。
张承志作品中男性的声音总是那么高亢,女性只是成功男人的参照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宣称抵抗儒家文化的张承志其在思想上的某种困惑与矛盾。
《荆棘鸟》中的教士拉尔夫完全不同于《心灵史》中虔诚刚烈的教徒,他以虔诚的教士形象出现,最终以红衣主教的身份控诉了宗教的非人性,这就使拉尔夫成为不同于《心灵史》中的虔诚的教徒,而是一种反教会文学和被宗教异化的教士形象。
《荆棘鸟》从宗教对神职人员本身所造成的痛苦方面,集中深刻地揭示了人性被宗教异化后的悲剧,作品的侧重点已经不在信仰本身了。
这正是两部作品通过人物形象显示出的内蕴和作者观照视野的最大差别之处。
《荆棘鸟》透射出与张承志女性观截然不同的女性意识,在作品中,女性们都有着鲜活的生活和大胆的追求,都具有独立的人格,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
麦卡洛以鞭辟入里的笔法,挖掘着女性内心深处丰富而美丽的忧伤,从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独立意识。
《心灵史》中作者用自己全部的心灵去体验大西北贫瘠、残酷、血腥与死亡的巨大生存苦难,《荆棘鸟》的作者则把笔墨全部放在了一个令人回肠荡气的爱情悲剧的营构上。
表面看来似乎前者是关于精神信仰的,后者则是关于世俗人生的,但细读两部作品不难发现两者均以对人生、人性的深刻透视关注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同样记录了人类的生命之旅、心灵轨迹及其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