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_布莱希特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影响
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影响

论西方文艺思潮对廿世纪中国戏剧的影响摘要:戏剧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活跃的文学形式之一。
话剧,作为一种西方戏剧形式,从19世纪末开始大量传人中国,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起着主导作用。
从最初的“新剧”和“文明戏”对“旧剧”的改良尝试,大大促进了话剧的引进,到“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成熟、浪漫主义戏剧创作的展开。
两个时期对于西方文艺思想、理论的大量引进与学习,促进了中国戏剧现代性的形成和不断完善。
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浅要探讨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对现代话剧的影响。
关键词:戏剧;话剧;现实主义二十世纪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十分繁荣,名家辈出,流派众多。
学着们将这些各不相同的流派都归结为一类——现代派。
这个现代派了包括现代文学,也包括后现代文学。
现代派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后半叶象征主义的诞生,之后历经发展,出现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等流派,也出现了如卡夫卡、萨特、等大批名家名作,这在文艺复兴以后当属头一次集体式爆发,而且前赴后继。
中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先后两次对西方文学经典和其他如哲学经典的大批引进、探讨、研究,对中国文学乃至文人学者们的思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戏剧也是如此[1]。
曾孝谷、李息霜等1906年在日本东京成立春柳社,旨在“研究旧戏曲,冀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并制定《春柳社演艺部》专章;次年2月组织出演法国亚历山大.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三幕;1907年6月有欧阳玉倩、陆镜若等加盟的春柳社在东京演出了曾孝谷改编自美国著名作家斯陀夫人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黑奴吁天录》。
这些话剧的上演反应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对现实主义的渴望与推崇。
同时,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历史性转折,是中国戏剧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发展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2]为话剧的引进进行了一次深入探索。
1912年陆镜若在上海组织新剧同志会,加之王钟声领导的春阳社、任天知领导的进化团演出《孽海花》等剧,以及南、北的学生剧演,尤其是南开新剧团的剧演活动,形成了20世纪初年的新剧(又称文明戏)演出景观。
布莱希特与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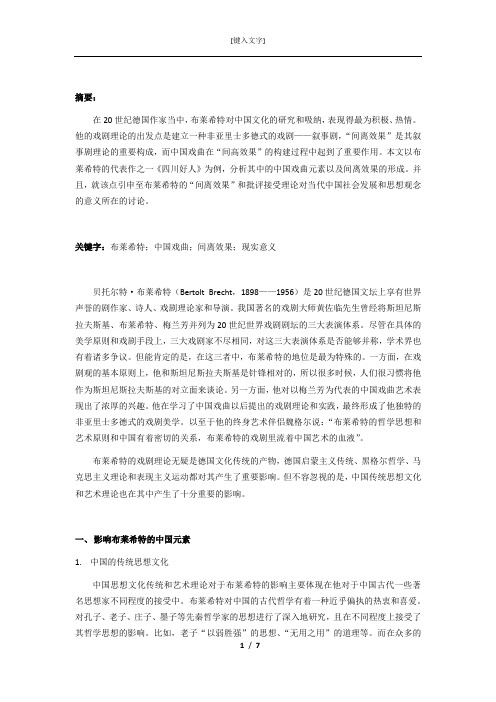
摘要:在20世纪德国作家当中,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吸纳,表现得最为积极、热情。
他的戏剧理论的出发点是建立一种非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叙事剧,“间离效果”是其叙事剧理论的重要构成,而中国戏曲在“间高效果”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以布莱希特的代表作之一《四川好人》为例,分析其中的中国戏曲元素以及间离效果的形成。
并且,就该点引申至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和批评接受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思想观念的意义所在的讨论。
关键字:布莱希特;中国戏曲;间离效果;现实意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是20世纪德国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剧作家、诗人、戏剧理论家和导演。
我国著名的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曾经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并列为20世纪世界戏剧剧坛的三大表演体系。
尽管在具体的美学原则和戏剧手段上,三大戏剧家不尽相同,对这三大表演体系是否能够并称,学术界也有着诸多争议。
但能肯定的是,在这三者中,布莱希特的地位是最为特殊的。
一方面,在戏剧观的基本原则上,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针锋相对的,所以很多时候,人们很习惯将他作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对立面来谈论。
另一方面,他对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他在学习了中国戏曲以后提出的戏剧理论和实践,最终形成了他独特的非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美学。
以至于他的终身艺术伴侣魏格尔说:“布莱希特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原则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布莱希特的戏剧里流着中国艺术的血液”。
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无疑是德国文化传统的产物,德国启蒙主义传统、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表现主义运动都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艺术理论也在其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影响布莱希特的中国元素1.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和艺术理论对于布莱希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对于中国古代一些著名思想家不同程度的接受中。
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从“间离效果”“打破第四堵墙”看东方戏剧美学对西方的影响

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从“间离效果”“打破第四堵墙”看东方戏剧美学对西方的影响陈伟【期刊名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01(30)5【摘要】表现主义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核心理论是“间离效果”、“打破第四堵墙”。
他的理论直接来源于对中国戏曲实践的认识,是中国(东方)的戏曲美学观对西方戏剧模式的重大影响。
布莱希特的理论不是照搬中国戏曲的表现方式,而是将中国戏曲表现方式的精华融入西方戏剧的表现方式中,再造出一种全新的表现方式,这种改造和创新展示了世界戏剧发展的方向。
布莱希特接受中国戏曲美学的影响主要在用新的编剧观念创作剧本、改革结构编排、借鉴中国戏曲的表现手法和舞台布景的改进等方面,通过这些改进调整了演剧中演员与角色、演员与观众的关系。
【总页数】8页(P104-111)【关键词】戏剧理论;中国;戏曲;布莱希特;演员;角色;观众;表现主义;间离效果;东方戏剧美学【作者】陈伟【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J801【相关文献】1.运用"间离效果"描绘精神图画——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对官厚生版画艺术的影响[J], 胡晶2.从“间离效果”到“连接效果”——布莱希特理论与中国戏曲的跨文化实验 [J], 孙惠柱3.浅谈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理论核心——"间离效果" [J], 张睦龄4.打破第四堵墙,让“白人”观众站到舞台上来——《美景镇》 (《fairview》)间离手法分析 [J], 赵雅倩5.《情人的衣服》戏剧间离效果分析彼得·布鲁克与布莱希特关于“间离效果”的对话 [J], 徐熳;赵琳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布莱希特与中国戏剧

就
接 触 中 国 文化艺 术 对 中 国 艺 术 发 生 浓 厚 兴 趣
,
1935年
是 布 莱 希特 在 看了 梅兰 芳的 演出之 后 在 艺术 中的 间 离 方法 》 一 文 中 首 次提 出 的 说
: “
。 。
,
《中 国
戏 曲表演
布 莱 希 特 流 亡 苏 联 期 间 在 莫斯 科观 看 了 梅 兰 芳 的 精 彩 表 演 中 国 戏 曲 独 特 的 美 学 精 神 和 表 演 方式
,
论 文 的 形 式 逐步 完善了 他 的 史 诗 剧 理 论
,
,
1
9
48
年 写的 《 戏
19 30年
,
中 国 京 剧表 演 艺术 大
,
、 、
剧 小 工 具 篇 》 则 是 他对 史 诗 剧 进 行 理论 思 考的 集 大 成 有
“
师梅 兰 芳历 时 半年 多 的 访 美演 出 轰 动 了 大 西 洋 彼 岸 赢得 了 像 美 国 著名 评论 家斯 达克
德
、
以广阔 的 视野
,
把 中 国 戏 曲 的 演 剧方 法 和欧 洲
, 、
观众 三 者的 关 系 而这 正 是 他 追求 的 目 标
。
,
,
中 国戏
戏居 」 的 演 剧 方 法 加 以 比 较 研究 从 演 员 与 角 色 的 关 系
曲 使他 看 到 了 一 个 新 的 戏 剧 境界 德 国 戏 剧 学家 莱 因 霍 尔
界 性影 响 中
,
,
故可 以
怀 念他 这 不仅 因 为 布 莱希 特 是 中 国 人 民 真挚 的 朋 友
, :
说
,
布莱希特的戏剧功能论

布莱希特的戏剧功能论### 都伯勒·布莱希特的戏剧功能论一、都伯勒·布莱希特的研究1、概述都伯勒·布莱希特是一位位于英国的戏剧学者,他主要研究戏剧分析、戏剧理论和舞台美学,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戏剧诗学,也就是戏剧功能论,指出戏剧可以分析和理解人类永恒的作品。
2、理论根据都伯勒·布莱希特的戏剧功能论,戏剧的主要功能有四种,分别是娱乐、惊险、教育和文学。
1)娱乐:戏剧给观众带来乐趣和快乐,戏剧演员依照剧本表演,以激发观众的兴奋情绪;2)惊险:戏剧会向观众呈现一些突发事件和惊慌失措的场面,用来预防自身恐惧;3)教育:戏剧者可以利用剧本中的内容来教育观众,进而激发观众的思考及批判性思维;4)文学:戏剧者可以运用文学让剧本的内容表达的更加深刻,给观众带来更强烈的**情感体验**性等一些新的功能内涵。
二、都伯勒·布莱希特的戏剧功能论的影响1、给新成熟的戏剧活动带来新的内容都伯勒·布莱希特的戏剧功能论影响了当代新成熟的戏剧活动,在他的戏剧功能论的观照下,戏剧开始的剧本的审美性、文学性及社会性意义揭露得更加完整,对戏剧活动带来新的内涵。
2、给戏剧活动提供很好的演出理念都伯勒·布莱希特的戏剧功能论不但丰富了戏剧内容,也很好的帮助了演出团队把握和彰显戏剧的演出理念,突出戏剧在观众身上发挥的作用,让戏剧更具有人文魅力。
三、戏剧功能论在当下的教学研究1、新成熟的功能论对戏剧教学的启迪戏剧功能论的提出使戏剧教学有了新的启迪,激励学生思考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情感和情绪把握能力,更有效的把握观众的气氛,更好的理解戏剧活动所能发挥的作用。
2、构建新型的戏剧教学模式将戏剧功能论的理论应用到戏剧教学中,不仅能够引导学生明确自己的教学目标,更能够构建出新的教学模式,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让课堂教学更加有趣生动。
四、小结都伯勒·布莱希特的戏剧功能论在当代文学研究和戏剧教学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布莱希特陌生化戏剧美学方法探究

布莱希特陌生化戏剧美学方法探究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意大利剧作家和理论家罗伯托布莱希特(Roberto Brice)开创了一种新的戏剧美学理论“陌生化”,改变了当时传统的戏剧美学理论,也鼓励了当时许多剧作家和从业者开展了许多关于陌生化的实践和研究。
然而,尽管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在当时颇受欢迎,但它在近代依然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追捧,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那么,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戏剧美学方法到底又是如何运作的呢?本文将探讨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戏剧美学方法,以及它在近代剧作、剧本分析中的应用。
首先,让我们来聚焦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戏剧美学方法。
布莱希特认为,戏剧是一种“体验”,而不仅仅是一种表演。
他有三个关于如何创造这种体验的原则:(1)以陌生化来塑造角色,(2)以自发性和随机性来实现意义,(3)以悬念来提升预期度。
他认为,角色的陌生化会激发观众的想象,并使角色的表演更加具有真实性,从而更好地抓住观众。
此外,布莱希特认为,角色的行动应当即兴而又随机,以便令观众产生未知的悬念。
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建议剧作者应当创造可以由实际行动来表现角色情感的情景,而不是由语言来表现的情景,以便激发观众的想象。
此外,他还建议,剧作者应该能够让实际行动表达出角色的意图,并且应当强调在同一场景中,角色应当采取不同行动,以此来添加悬念。
最后,布莱希特建议,在设计情景时,应当有意选择技法,设计出能够激起观众兴趣的情节,以便增强其参与感。
布莱希特建议,剧作者应当通过提出问题,引导观众参与其中,以使他们对角色的行动产生兴趣,同时,也能够激发观众的思考,令他们对剧情发展起兴趣,从而使他们更容易投入进来。
以上就是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戏剧美学方法,它主要侧重于鼓励剧作者创造可以激发观众想象的陌生化角色、即兴表演和悬念。
尽管这一理论出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它在近代仍然在许多剧作和剧本分析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第一,许多当代剧作家将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应用于他们的剧作当中,从而令角色表现更加具有真实性、更能引发观众的兴趣,使剧作有更深沉的内涵。
论布莱希特的寓意剧《四川一好人》

论布莱希特的寓意剧《四川一好人》
陈晓红
【期刊名称】《枣庄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4(021)004
【摘要】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在创作中十分注重借鉴吸收中国戏曲艺术的营养成分.<四川-好人>以寓意剧的形式传达了一个好人究竟能否生存的这一哲理,同时鲜明地体现了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理论.
【总页数】2页(P35-36)
【作者】陈晓红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山东,曲阜,27316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516.073
【相关文献】
1.好女人坏女人(取材于德国作家布莱希特譬喻剧《四川好人》) [J], 魏明伦
2.布莱希特叙事剧《四川好人》艺术特色探略 [J], 朱新颖
3.论布莱希特《四川好人》中“好”的倒置 [J], 姚晴晴
4.从《四川好人》与《圣经》的互文浅析布莱希特的反宗教理念 [J], 李慕晗;张世胜
5.布莱希特的"中国榜样"与《四川好人》的侨易之旅 [J], 谭渊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论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对世界戏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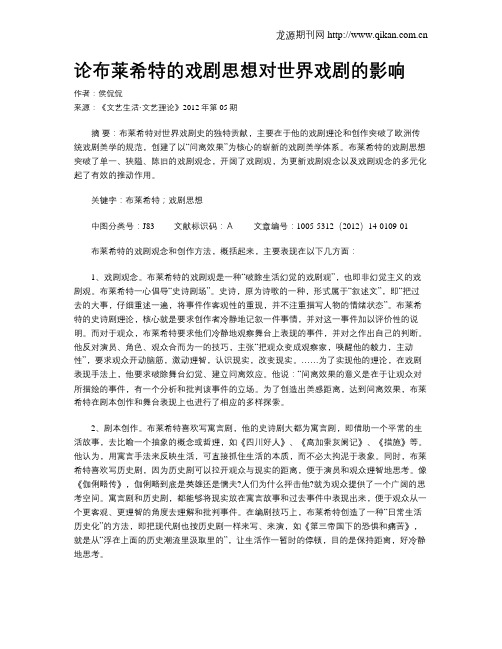
论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对世界戏剧的影响作者:侯侃侃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2年第05期摘要:布莱希特对世界戏剧史的独特贡献,主要在于他的戏剧理论和创作突破了欧洲传统戏剧美学的规范,创建了以“问离效果”为核心的崭新的戏剧美学体系。
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突破了单一、狭隘、陈旧的戏剧观念,开阔了戏剧观,为更新戏剧观念以及戏剧观念的多元化起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关键字:布莱希特;戏剧思想中图分类号:J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4-0109-01布莱希特的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戏剧观念。
布莱希特的戏剧观是一种“破除生活幻觉的戏剧观”,也即非幻觉主义的戏剧观。
布莱希特一心倡导“史诗剧场”。
史诗,原为诗歌的一种,形式属于“叙述文”,即“把过去的大事,仔细重述一遍,将事件作客观性的重现,并不注重描写人物的情绪状态”。
布莱希特的史诗剧理论,核心就是要求创作者冷静地记叙一件事情,并对这一事件加以评价性的说明。
而对于观众,布莱希特要求他们冷静地观察舞台上表现的事件,并对之作出自己的判断。
他反对演员、角色、观众合而为一的技巧,主张“把观众变成观察家,唤醒他的毅力,主动性”,要求观众开动脑筋,激动理智,认识现实,改变现实。
……为了实现他的理论,在戏剧表现手法上,他要求破除舞台幻觉、建立问离效应。
他说:“间离效果的意义是在于让观众对所描绘的事件,有一个分析和批判该事件的立场。
为了创造出美感距离,达到间离效果,布莱希特在剧本创作和舞台表现上也进行了相应的多样探索。
2、剧本创作。
布莱希特喜欢写寓言剧,他的史诗剧大都为寓言剧,即借助一个平常的生活故事,去比喻一个抽象的概念或哲理,如《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措施》等。
他认为,用寓言手法来反映生活,可直接抓住生活的本质,而不必太拘泥于表象。
同时,布莱希特喜欢写历史剧,因为历史剧可以拉开观众与现实的距离,便于演员和观众理智地思考。
试论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

试论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作者:陈风来源:《艺术科技》2014年第11期摘要:布莱希特对戏剧的创新就是提出了“叙述体戏剧”这样的一个理论,该理论与此前延续了2000多年的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性戏剧”传统有着鲜明的对抗,戏剧理论的核心范畴就是“间离说”。
本文主要是对“间离说”的浅入的分析,而来就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进行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布莱希特;间离说;戏剧布莱希特在创作新的戏剧理论时,进行了一个新的定位:就是非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而将其定位命名为“叙述体戏剧”,而来与亚里士多德式的“表演性戏剧”相区别,其戏剧中最为常用的表达方式就是叙述,最为常用的典型表现方式就是表演。
个人认为,相比于“叙述体戏剧”和“辩证戏剧”,后者更适合对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及创作进行描述,后者是他在50年代末提出的,为何这么说?那就需要在从其理论的核心“间离”的概述中来寻找答案。
1 “间离”理论的概述若想就“间离说”的深刻意义进行深入的了解,那就得需要我们以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著名定义来看:“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亚里士多德以Katharsis来定义悲剧的目的,其主要的路径希望通过情节对观众的激发出恐惧与怜悯之情,能够让观众能够从剧中人或事中生发出情感的共鸣,而最终达到情感的净化。
观众会因为戏剧中的情感而产生共鸣,进而会陷身于戏剧中无法自拔,但是对于认识和改造社会来说,情感的净化对其是没有作用的,这是布莱希特的看法。
情节的强调,戏剧性的过于突出是“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的最大特点,这一戏剧的优点是可以最大化的引人入胜,但缺点却是剥夺观众思考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处于艺术的幻觉之中。
“间离”主要是利用剧作者、演员(导演)、观众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叙述的表达方式将完整的情节打散,以此来避免引起情感共鸣,从而实现间离感情。
布莱希特戏剧与中国戏剧的比较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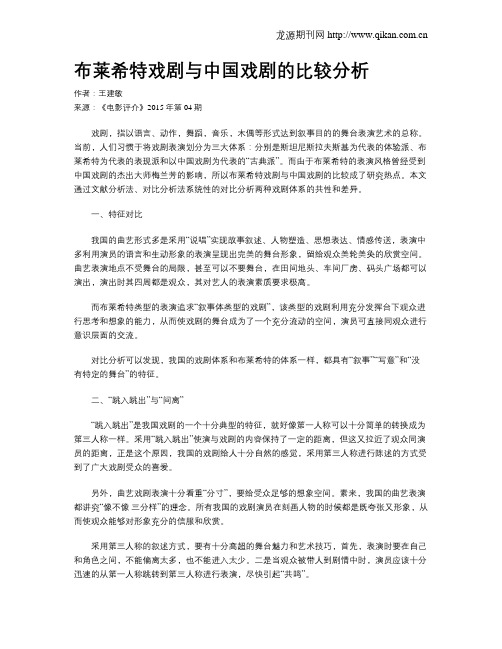
布莱希特戏剧与中国戏剧的比较分析作者:王建敏来源:《电影评介》2015年第04期戏剧,指以语言、动作,舞蹈,音乐,木偶等形式达到叙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艺术的总称。
当前,人们习惯于将戏剧表演划分为三大体系:分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代表的体验派、布莱希特为代表的表现派和以中国戏剧为代表的“古典派”。
而由于布莱希特的表演风格曾经受到中国戏剧的杰出大师梅兰芳的影响,所以布莱希特戏剧与中国戏剧的比较成了研究热点。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系统性的对比分析两种戏剧体系的共性和差异。
一、特征对比我国的曲艺形式多是采用“说唱”实现故事叙述、人物塑造、思想表达、情感传送,表演中多利用演员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表演呈现出完美的舞台形象,留给观众美轮美奂的欣赏空间。
曲艺表演地点不受舞台的局限,甚至可以不要舞台,在田间地头、车间厂房、码头广场都可以演出,演出时其四周都是观众,其对艺人的表演素质要求极高。
而布莱希特类型的表演追求“叙事体类型的戏剧”,该类型的戏剧利用充分发挥台下观众进行思考和想象的能力,从而使戏剧的舞台成为了一个充分流动的空间,演员可直接同观众进行意识层面的交流。
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戏剧体系和布莱希特的体系一样,都具有“叙事”“写意”和“没有特定的舞台”的特征。
二、“跳入跳出”与“间离”“跳入跳出”是我国戏剧的一个十分典型的特征,就好像第一人称可以十分简单的转换成为第三人称一样。
采用“跳入跳出”使演与戏剧的内容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这又拉近了观众同演员的距离,正是这个原因,我国的戏剧给人十分自然的感觉,采用第三人称进行陈述的方式受到了广大戏剧受众的喜爱。
另外,曲艺戏剧表演十分看重“分寸”,要给受众足够的想象空间。
素来,我国的曲艺表演都讲究“像不像三分样”的理念。
所有我国的戏剧演员在刻画人物的时候都是既夸张又形象,从而使观众能够对形象充分的信服和欣赏。
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要有十分高超的舞台魅力和艺术技巧,首先,表演时要在自己和角色之间,不能偏离太多,也不能进入太少。
布莱希特在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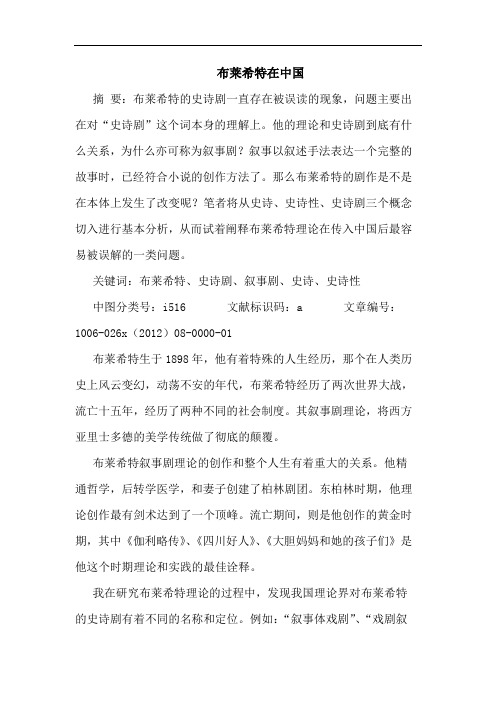
布莱希特在中国摘要:布莱希特的史诗剧一直存在被误读的现象,问题主要出在对“史诗剧”这个词本身的理解上。
他的理论和史诗剧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亦可称为叙事剧?叙事以叙述手法表达一个完整的故事时,已经符合小说的创作方法了。
那么布莱希特的剧作是不是在本体上发生了改变呢?笔者将从史诗、史诗性、史诗剧三个概念切入进行基本分析,从而试着阐释布莱希特理论在传入中国后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类问题。
关键词:布莱希特、史诗剧、叙事剧、史诗、史诗性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1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他有着特殊的人生经历,那个在人类历史上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年代,布莱希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流亡十五年,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其叙事剧理论,将西方亚里士多德的美学传统做了彻底的颠覆。
布莱希特叙事剧理论的创作和整个人生有着重大的关系。
他精通哲学,后转学医学,和妻子创建了柏林剧团。
东柏林时期,他理论创作最有剑术达到了一个顶峰。
流亡期间,则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其中《伽利略传》、《四川好人》、《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是他这个时期理论和实践的最佳诠释。
我在研究布莱希特理论的过程中,发现我国理论界对布莱希特的史诗剧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定位。
例如:“叙事体戏剧”、“戏剧叙事学”、“辩证戏剧”、“戏剧体戏剧”等等,到底什么样的名称更加能体现布莱希特理论的精髓?我曾想过,称呼概念尚无所谓,对内容的理解若出现偏差,那布莱希特的理论在中国戏剧界必然出现严重的误读的现象。
想要梳理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对“史诗剧”、“史诗性”、“史诗”这三个概念做全面的横向比较。
建国后五十年代,我国文化部长田汉接见了日本千田,千田在访问中问及布莱希特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当时只有少量几所大学的德语系对布莱希特有初步浅显的了解。
千田嘲讽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竟然不知道和自己有着同样精神信仰的布莱希特。
1956年~1957年,北大西语系冯至教授,翻译了布莱希特最初的作品。
先锋戏剧知识点范文

先锋戏剧知识点范文先锋戏剧是指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戏剧形式,它以对传统戏剧形式和观念的否定和挑战为特征,注重对社会现实、自我内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度探索,在形式、语言、主题上都极具创新性。
下面是关于先锋戏剧的知识点,详细介绍。
一.先锋戏剧的起源1.先锋戏剧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欧洲。
2.这一时期,戏剧艺术家开始对传统戏剧形式和观念进行反思和否定,试图以新的方式表达现代社会的现实。
二.先锋戏剧的特征1.对传统戏剧形式的挑战:先锋戏剧摒弃了传统戏剧的班底、剧情,以及剧目的古典和历史的主题,而是追求形式的创新与自由。
2.实验性质:先锋戏剧追求创新和实验,不拘泥于传统的剧种和表演方式,尝试新的剧目、演出方式、道具,甚至是观众与演员的互动等。
3.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先锋戏剧关注社会现实,特别是对社会不平等、性别角色、政治权力等问题的思考,并试图通过艺术表达来带动社会变革。
三.先锋戏剧的代表作品及代表性人物1.彼得·布鲁克:他是先锋戏剧运动的重要代表,其作品《空灵夏夜梦》等作品以其对舞台空间的革新贡献巨大。
2.布莱希特:他也是先锋戏剧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威鹤斯》等作品注重对社会政治意义的探索和对传统戏剧形式的挑战。
3.塞缪尔·贝克特:他的作品《等待戈多》等以其独特的语言和意象艺术的风格成为先锋戏剧重要的代表。
4.安东尼·纳尼:他的作品《盖汉佐》等融合了现代音乐与戏剧的元素,以其独特的音乐语言风格闻名。
四.先锋戏剧对当代戏剧的影响1.先锋戏剧的出现对传统戏剧形式和观念进行了颠覆和挑战,它开创了现代戏剧的新纪元。
2.先锋戏剧提倡艺术自由和创新,使戏剧艺术家能够更加自由地创作和表达,同时也激发了观众对戏剧的新的认识和期待。
3.先锋戏剧注重对社会现实、自我内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度探索,使得当代戏剧更加关注现实世界,追求表达和思考社会问题的力量。
布莱希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_布莱希特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影响_周宪

主题词外国戏剧家研究 布莱希特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布莱希特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影响周 宪一 在影响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西方戏剧家中,有三个人物影响深远。
首先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西方话剧东渐伊始,就开始了他那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戏剧界的好几代人都是在易卜生的影响下成长的,这对造就中国现代戏剧的现实主义潮流具有决定作用;其次是俄国戏剧表演艺术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作为“体验派”的一代宗师,他的影响进一步从表演和导演方面强化了易卜生式的现实主义戏剧潮流;第三个必须提及的人物则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如果说易卜生对中国现代戏剧的现实主义潮流起到了奠基作用,斯坦尼则起了促进和强化作用,那么,布莱希特在中国戏剧文化中,则是作为一种与前者相对抗的力量出现的,因此,其影响不可小觑。
本文就是对布莱希特在中国当代戏剧发展中的复杂影响的一种尝试性分析。
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有必要作两个工作性的界说。
第一,要讨论布莱希特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影响,首先必须把握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
只有把握了这种语境,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布莱希特的戏剧作用一种话语,是如何被谈论和运用的,以及这种话语的特别意味。
在我看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文化的主要矛盾始终体现为三个方面:传统-发展-社会主义。
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和转变,都体现为这三极的不同关系。
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者的关系处于迥然异趣的状态。
布莱希特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戏剧界的热门话题,与中国文化的这种三极关系密切相关。
比如,布莱希特是一个重要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西方戏剧家,这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就获得了某种被谈论的“合法性”;再比如,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的赞赏和褒奖,以及他的最重要的戏剧理论“间离效果”和中国传统戏曲的关系等,使得他成为在现代西方戏剧家中难得的对中国戏剧界有亲和力和认同感的人物,他无疑是一个与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有复杂联系的西方戏剧家【1】;再者,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作为西方现代戏剧潮流中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尝试,虽然在西方现代戏剧史上并不是作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其中所包含的某种新的戏剧观,在中国特定的戏剧文化背景中,却被当作28打破偏狭的现实主义戏剧的强有力武器。
布莱希特:误读与被误读

布莱希特:误读与被误读
邹琰
【期刊名称】《四川戏剧》
【年(卷),期】2008(000)006
【摘要】国著名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作为“非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的创立者.他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同中国古代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在他对中国古典戏剧的借鉴过程中有意对其进行了选择与误读.但他对于中国的当代戏剧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国对布莱希特的研究,从1929年赵景深的《最近德国剧坛》开始,历经了两次高潮:一次在1950年代.一次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
而这两次高潮的兴起有着惊人相似的历史背景:充满巨大变革激情与期望的特定历史时期.百废待兴。
【总页数】3页(P53-55)
【作者】邹琰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8
【相关文献】
1.不能以误读纠正"百年误读"--与《"克己复礼"的百年误读与思想真谛》的作者商
榷 [J], 萧作永
2.误读视阈下布莱希特对中国戏曲的接受 [J], 邵志华
3.文化差异、文化误读与误读的创造性价值——兼析动画片《花木兰》与《功夫熊猫》的中美文化差异与误读现象 [J], 华静
4.从“误读”走向创新--以接受美学理论分析布莱希特和京剧的关系 [J], 闵志荣
5.还有多少误读在继续——从《扁鹊见蔡桓公》误读现象看教师阅读的现状 [J], 黄丹芳; 张秋玲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浅谈布莱希特“间离效果”在戏剧中的运用

众 和 演 员能 理 性 地 看待 现 实 。无 论 是 国 内还 是 国外 ,布 人 们 去认 识 它 。 ”布 莱 希 特 为 了制 造 “ 陌生 化 ”效 果 , 莱希特 “ 间离 方法 ”理 论 的影 响都 是 巨 大 的 。在不 同 的 他 反 对西 方 戏 剧传 统 的共 鸣效 果 ,他倡 导 观众 应 该 在 理
情 况 那 样 ,在 观 众 的下 意 识 范 围 内达 到 。演 员 在 进 行 演
布莱 希 特 的 间离 效 果 的 主要 目的是 为 了推 倒 在舞 台
出时 的 自我反 省 与观 察是 一 种艺术 化 的 自我疏 远 的行 动 , 上的 “ 第 四堵 墙 ” ,让演 员 通过 “ 间离 ”的方法 来演 出 ,
作 为 世 界 著名 表 演 体 系之 一 的布 莱 希特 体 系 ,其所 人 们 彼此 的立 场 ,要 让 观 众 感 到惊 异 。人 们 必 须 赞 同 , 倡 导 的 演剧 方 法 即 “ 间离 方 法 ” 。这种 方 法 通 过 间 离效 许 多 事件 在 一 定 程度 上 令 人感 到惊 讶 。要 是 人 们不 同意 果 使 演 员 与角 色 、观众 与 角 色之 间保 持距 离 ,从 而使 观 这 点 ,我 们 的演 员 就 要 设法 将 事 件 当做 令 人 诧 异 的而 让
布莱希特对中国戏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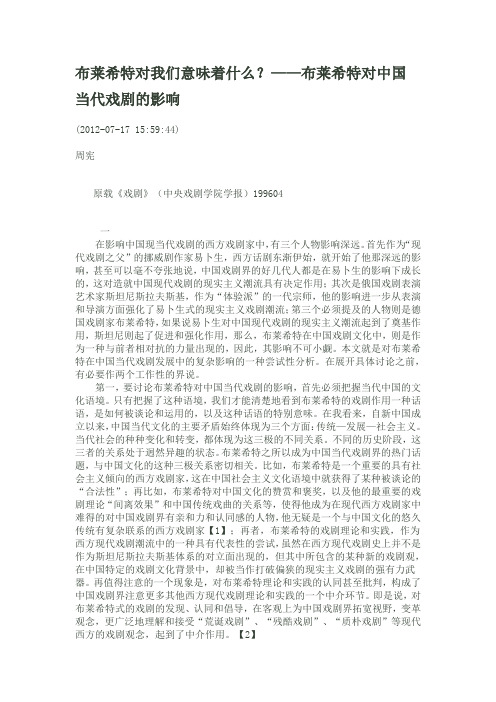
布莱希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布莱希特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影响(2012-07-17 15:59:44)周宪原载《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199604一在影响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西方戏剧家中,有三个人物影响深远。
首先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西方话剧东渐伊始,就开始了他那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戏剧界的好几代人都是在易卜生的影响下成长的,这对造就中国现代戏剧的现实主义潮流具有决定作用;其次是俄国戏剧表演艺术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作为“体验派”的一代宗师,他的影响进一步从表演和导演方面强化了易卜生式的现实主义戏剧潮流;第三个必须提及的人物则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如果说易卜生对中国现代戏剧的现实主义潮流起到了奠基作用,斯坦尼则起了促进和强化作用,那么,布莱希特在中国戏剧文化中,则是作为一种与前者相对抗的力量出现的,因此,其影响不可小觑。
本文就是对布莱希特在中国当代戏剧发展中的复杂影响的一种尝试性分析。
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有必要作两个工作性的界说。
第一,要讨论布莱希特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影响,首先必须把握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
只有把握了这种语境,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布莱希特的戏剧作用一种话语,是如何被谈论和运用的,以及这种话语的特别意味。
在我看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文化的主要矛盾始终体现为三个方面:传统—发展—社会主义。
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和转变,都体现为这三极的不同关系。
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者的关系处于迥然异趣的状态。
布莱希特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戏剧界的热门话题,与中国文化的这种三极关系密切相关。
比如,布莱希特是一个重要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西方戏剧家,这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就获得了某种被谈论的“合法性”;再比如,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的赞赏和褒奖,以及他的最重要的戏剧理论“间离效果”和中国传统戏曲的关系等,使得他成为在现代西方戏剧家中难得的对中国戏剧界有亲和力和认同感的人物,他无疑是一个与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有复杂联系的西方戏剧家【1】;再者,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作为西方现代戏剧潮流中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尝试,虽然在西方现代戏剧史上并不是作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其中所包含的某种新的戏剧观,在中国特定的戏剧文化背景中,却被当作打破偏狭的现实主义戏剧的强有力武器。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主题词外国戏剧家研究 布莱希特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布莱希特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影响周 宪一 在影响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西方戏剧家中,有三个人物影响深远。
首先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西方话剧东渐伊始,就开始了他那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戏剧界的好几代人都是在易卜生的影响下成长的,这对造就中国现代戏剧的现实主义潮流具有决定作用;其次是俄国戏剧表演艺术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作为“体验派”的一代宗师,他的影响进一步从表演和导演方面强化了易卜生式的现实主义戏剧潮流;第三个必须提及的人物则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如果说易卜生对中国现代戏剧的现实主义潮流起到了奠基作用,斯坦尼则起了促进和强化作用,那么,布莱希特在中国戏剧文化中,则是作为一种与前者相对抗的力量出现的,因此,其影响不可小觑。
本文就是对布莱希特在中国当代戏剧发展中的复杂影响的一种尝试性分析。
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有必要作两个工作性的界说。
第一,要讨论布莱希特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影响,首先必须把握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
只有把握了这种语境,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布莱希特的戏剧作用一种话语,是如何被谈论和运用的,以及这种话语的特别意味。
在我看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文化的主要矛盾始终体现为三个方面:传统-发展-社会主义。
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和转变,都体现为这三极的不同关系。
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者的关系处于迥然异趣的状态。
布莱希特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戏剧界的热门话题,与中国文化的这种三极关系密切相关。
比如,布莱希特是一个重要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西方戏剧家,这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就获得了某种被谈论的“合法性”;再比如,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的赞赏和褒奖,以及他的最重要的戏剧理论“间离效果”和中国传统戏曲的关系等,使得他成为在现代西方戏剧家中难得的对中国戏剧界有亲和力和认同感的人物,他无疑是一个与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有复杂联系的西方戏剧家【1】;再者,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作为西方现代戏剧潮流中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尝试,虽然在西方现代戏剧史上并不是作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其中所包含的某种新的戏剧观,在中国特定的戏剧文化背景中,却被当作28打破偏狭的现实主义戏剧的强有力武器。
再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对布莱希特理论和实践的认同甚至批判,构成了中国戏剧界注意更多其他西方现代戏剧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中介环节。
即是说,对布莱希特式的戏剧的发现、认同和倡导,在客观上为中国戏剧界拓宽视野,变革观念,更广泛地理解和接受“荒诞戏剧”、“残酷戏剧”、“质朴戏剧”等现代西方的戏剧观念,起到了中介作用。
【2】第二,中国当代戏剧的发展,除了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外部原因以外,还有内部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概括成中国当代“戏剧共同体”。
这里,我是借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说法,他认为,科学的进步有赖于科学共同体,所谓共同体是指经过严格科学训练的有相似或相同观念的科学家群体,他们中构成了一定的科学范式,而科学的革命实际上就是这种范式的革命。
显而易见,中国当代戏剧发展的内部动力是这样的戏剧共同体,即戏剧界各种从事戏剧工作的人,包括剧作家,导演,演员,舞美,批评家等。
相当于社会学上所说的“内集团”。
更进一步,中国当代戏剧的发展演变,事实上是戏剧共同体的戏剧观念(戏剧本体论等)发展演变的过程,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每当一种知识体系被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一致接受时,在共同体中便形成了一种“收敛思维”,这样的思维倾向导致了该共同体保守性的形成。
换言之,一种知识的“精神定势”(库恩语)构成了。
这时,一方面需要变革,但另一方面变革又是相当困难的,在一些情况下,某种外部力量常常是实现变革重要因素。
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布莱希特正是充当了这样的外部因素,作为特定意识形态环境中具有被谈论“合法性”的少数西方戏剧家,布莱希特令人意外地作为与易卜生和斯坦尼相对立的戏剧思潮出现了。
布莱希特的理论和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戏剧家(共同体),从而导致了中国戏剧舞台上“范式”的巨大转变。
布莱希特作为一个尖利的矛,打破了由狭隘的沉闷的甚至教条化的“现实主义”戏剧观一统天下的局面,对构成新时期戏剧蔚为大观的缤纷景观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本文的分析将集中在中国当代戏剧共同体的戏剧“范式”转变上。
二中国戏剧界译介布莱希特始于三十年代,【3】但系统地介绍和翻译甚至上演布莱希特的剧目则显然是建国以后的事,而布莱希特对中国戏剧界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在新时期。
针对这个事实,我们有理由把布莱希特的影响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建国到文革的17年,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以及后新时期)。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阶段。
如前所述,中国当代文化始终处在社会主义、发展和传统三者的复杂关系中。
在从建国到文革的第一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始终处于不可动摇的首要核心地位,发展则相对说来处于第二地位,而且不停地受到前者的制约和干扰,至于传统则显然被排斥在边缘地位,被曲解成封建糟粕的代名词。
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巨大变革激情和期望的特定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和教条化,使得极左政治-文化路线的逐步形成,导致了一个越来越具有封闭和排他特征的文化,发展遇到了巨大的阻碍,而传统变成了一个必须谨慎谈论的话题。
在这种文化语境里,说什么和怎么说是有特定限制的。
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布莱希特现象作为戏剧话语出现了。
1951年黄佐临编导了具有布莱希特风格的《抗美援朝大活报》,也许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第一次对布莱希特戏剧模式的尝试。
但直到1959年,戏剧界谈论他的文章著作才较多出现,而布莱希特的理论和戏剧甚至诗歌著作开始在中国出版,如剧本《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布莱希特选集》等。
特别是这一年在中国戏剧舞台上,上演了布莱希特的代表作《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我们知道,解放以来,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下,前苏联的戏剧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话剧,这其中最具影响力29的当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斯氏的表演体系作为一种“制造幻觉”(布莱希特语)的理论,与半世纪以来的中国戏剧的现实主义的主流是一脉相承的。
这无疑强化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易卜生式的现实主义戏剧模式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的主导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话剧逐渐走上了一条越来越狭窄的道路,尽管人们不时还称之为“现实主义”,当然这种“现实主义”实际上已与斯坦尼的精髓相去甚远了。
我们注意到,在17年里,真正的现实主义也许根本不存在,盛行的倒是带有这样那样“浪漫主义”特征的戏剧,而且这种戏剧不可避免地趋向于政治、道德性的说教。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戏剧倒在某些方面是和布莱希特式的戏剧接近的,特别是他的戏剧观中那些强烈的革命思想,改造社会和人们的理想,以及教育民众,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张等,实际上是和中国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相当合拍的。
换言之,这段时期应该是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最容易发生作用的时期。
但历史的复杂性恰恰表现在这里。
在中国戏剧共同体最容易接受布莱希特戏剧主张的时候,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与布莱希特的世界观一致的情况下,布莱希特实际上反倒没有发生什么深刻的影响。
中国戏剧共同体在这种语境中至少在理论上是选择是斯坦尼而不是布莱希特。
当然,以斯坦尼为楷模的并不意味着一丝不苟地照搬斯坦尼,中国文化从来都是在一种复杂的变形状态中来造就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
对斯坦尼体系的曲解和实用主义态度,加上各种政治上的压力和作用,名义上追求斯坦尼式的戏剧,实际上却是非斯坦尼的。
在一定程度上看,这种倾向到是与布莱希特式的戏剧有些接近,但却又不是在布莱希特的影响下形成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性的“错位”,这种“错位”不但表现在17年中,而且还进一步体现在新时期的戏剧实践中(详后)。
17年中,中国戏剧的道路越走越窄,越来越片面化、极端化和贫困化,越来越服务于某种非戏剧的政治的或伦理的目标,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作为一个在有限条件下可以谈论的话语,在中国这个特殊的“舞台”上的出现。
它的出现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它不是一般的外来戏剧思潮的翻译介绍,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进入中国戏剧舞台,意义是重大的。
其次,在与斯坦尼体系相比较的意义上说,当时中国的戏剧实践和倾向,应该说是和布莱希特而不是斯坦尼更接近,但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布莱希特的理论一俟进入中国戏剧共同体的视野,就是作为一种和斯坦尼体系相对立的批判力量。
换言之,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在中国这个特定的舞台上,被演变成为一种用以抗拒带有自身特征的一种戏剧思潮,尽管名义上是被戏剧共同体当做一种用以对抗偏狭的“现实主义教条”的有力武器,一种改变当时戏剧现状的外来力量。
这不防看作是布莱希特的戏剧话语在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中;历史性“错位”的另一含义。
在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有代表性的现象,可以称之为“黄佐临现象”。
黄先生属于中国现代话剧的前辈,早年留洋,熟悉西方戏剧的各种流派,同时对中国古典戏曲也有较深入的理解。
在这17年间,大力宣传倡导布莱希特戏剧的莫过于黄佐临了。
对他来说,倡导布莱希特的戏剧观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突破当时已经变得越来越教条的话剧模式。
照他看来,中国戏剧民族化的努力很容易转向传统戏曲的直接借鉴和挪用;而斯坦尼的影响又极易导致自然主义的倾向,所以,中国戏剧共同体需要一种新的观念,在这种条件下,布莱希特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黄佐临在五十年代末就提出了“向布莱希特吸取什么?”的问题。
在他看来,斯坦尼和梅兰芳是对立的两极:“一个讲究内心体验,生活化,一个讲究程式化;而布莱希特似乎站在两者的中间。
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果学不到家,可能产生自然主义倾向(对生活化误解);学习民族戏曲传统倘只发展加锣鼓点、说韵白,再好也好不过传统戏曲,这使我想到布莱希特,从他这里是否可能得到启发”【4】到了62年广州“全国话30剧歌剧创作座谈会”时,黄佐临关于戏剧观的发言,明确提出了:“中国话剧创作好象还受到这个戏剧观(指狭隘的现实主义的戏剧观——引者按)的残余所约束,认为这是话剧唯一的表现方法,突破一下我们狭隘的戏剧观,从我们祖国‘江山如此多娇’的澎湃气势出发,放胆尝试多种多样的戏剧手段,创造民族的演剧体系,该是繁荣话剧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5】从表面上看,这篇发言旨在比较斯坦尼、梅兰芳和布莱希特“三大体系”的区别,但文章的主旨则显然在于倡导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并以这种“破除生活幻觉的”“写意的戏剧观”来冲击一下已日渐僵化的“造成生活幻觉的”“写实的戏剧观”。
值得注意的是,在黄佐临的这个发言中,布莱希特理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同中国戏曲,特别是作为民族艺术瑰宝的梅兰芳表演艺术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