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春秋笔法”述论
孔子修《春秋》之“笔法”变革考论

孔子修《春秋》之“笔法”变革考论孙董霞(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 大连 116024)提要: 孔子是否作《春秋》,是学界公案,争议颇多。
但说孔子曾经修订《春秋》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提倡述而不作的孔子之“作”《春秋》,即是在鲁《春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笔削。
从先秦文献来看,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史官皆从自己国家的角度出发记录历史事件,号称“百国春秋”。
而孔子修订《春秋》的笔法也应当与春秋早期史官们的笔法不同。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使史官的书史笔法面临挑战和种种问题。
史官只书制度,不见人文的书史笔法存在着“文”过之弊,面临着“礼”与“理”的矛盾,而王官失守,史官流散再加上社会变乱,难免出现记录失宜的情形。
孔子修《春秋》对春秋史官笔法进行了改革,救“文”之弊,运用微言大义,将“义法”与“情理”结合,变“外文”为“内文”,因而更具威慑力。
关键词: 孔子;《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变革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20)06-0148-09 关于孔子是否修《春秋》,唐前人基本持肯定态度,自唐代以后,学者遂多有孔子不修《春秋》论者。
当代学者中以杨伯峻先生为代表,杨先生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有“孔子未修《春秋》”的专门论述。
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并对其中的一些佐证材料进行了辩驳[1]。
我们认为,孔子应当是修订过《春秋》的。
提倡述而不作的孔子之“作”《春秋》,即是在鲁《春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笔削。
千百年来流传的孔子“作”《春秋》说,这个“作”字就体现在孔子对春秋史官笔法的改革上。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许学夷《诗源辩体》:“盖谓东迁之后,风雅美刺之诗既亡,而《春秋》褒贬之书始作也。
吕成公言:‘指笔削《春秋》之时,非谓《春秋》之所始。
’”[2]“《春秋》作”非谓《春秋》之所始,而是笔削《春秋》,这是很精到的见解。
一、“史法旧章”与“《春秋》变例”我国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书史笔法随着时代而变化,春秋时期的史官笔法有别于西周,也有别于孔子修订后的《春秋》笔法。
左传中的春秋笔法

左传中的春秋笔法孔子作《春秋》,常以一字一语寓褒贬之义。
故后世称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寓「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的特点是暗含褒贬,微言大义、一字寓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
桓谭《新论•正经》:“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
《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左传》中“传文”所直接提到的春秋书法(杜预所谓凡例)如下,熟悉这些即可对所谓春秋笔法有个初步的了解:《左传》凡例50汇总:1: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
2: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
平地尺为大雪。
3: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
师出臧否,亦如之。
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
4:凡平原出水为大水。
5: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
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
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
6: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
7: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
过则书。
8: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
9: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10: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俊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
11:凡天灾,有币无牲。
非日月之眚,不鼓。
12: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
夫人归宁曰如某,出曰归于某。
13: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邑曰筑,都曰城。
14: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15: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
16:凡物不为灾不书。
17: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
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
18: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
中国则否。
诸侯不相遗俘。
19: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
“春秋笔法”研究——以《史记》为例

“春秋笔法”研究——以《史记》为例摘要:“春秋笔法”相传孔子修《春秋》,一字含褒贬。
后来称文章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写作手法。
这与历代学者及文学理论家们的理论说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历史学家们也成功地、有意识地使用了它。
历史写作练习重要质量原因。
而《史记》就是“春秋笔法”能够传承后世的重要载体。
本文主要对“春秋笔法”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了《史记》中的“春秋笔法”以及《史记》中的“春秋笔法”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
关键字:“春秋笔法” 《史记》史学“春秋笔法”,这是一种用毛笔字或使用语言的技术,是孔子开辟的写作方式,不是用论辩的语言表现,而是在文章的叙述上体现出作者的意识形态倾向。
孔子在以露茜为基础撰写《春秋》时,对当时重要而非决定性的历史事实采取了避讳和忌惮的态度。
也就是说,我记不清那问题。
我只用几句话就快速提醒起来,使读者能感觉到它。
有时它涉及赞扬和批评,但文本不直接涉及观点。
对人物和事件的详尽描述,运用修辞手法或材料委婉而精妙地表达他的观点。
一、对于“春秋笔法”的典故分析1.1《春秋》,鲁国史书。
据传孔子修葺了。
儒家学者认为其中的每一个词都应该受到“褒贬”,然后扭曲,所以把表示褒贬的词称为“春秋笔”。
在历史上,左秋明是第一个进行了微妙探索并精确总结了这篇文章的人。
邪恶说服之善。
非智者能培之乎?(译:《春秋》的故事细致而富有表现力,它记载了史实,深刻而机智而有逻辑,彻底而不失真,警示和嘉丑恶,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1.2比如,吴国和越国的君主都敢称王,然而孔子却在《春秋》里把他们贬称为“子”;践土之盟,其实是晋文公叫周王去的,但孔子却为周王掩饰,说“天子到河阳去打猎”。
后来的学者们将孔子的这种手法称之为“春秋笔法”,或称“微言大义”,比喻文笔曲折隐晦却又含有褒贬意思的写作风格。
1.3“不言出奔,难之也。
”《左传》指出,段不像兄弟,所以他不说“兄弟”;兄弟之间的竞争就像两个君主之间的竞争一样,因此称之为“克”;称庄公为“郑伯”是讽刺他缺乏教育。
孔子春秋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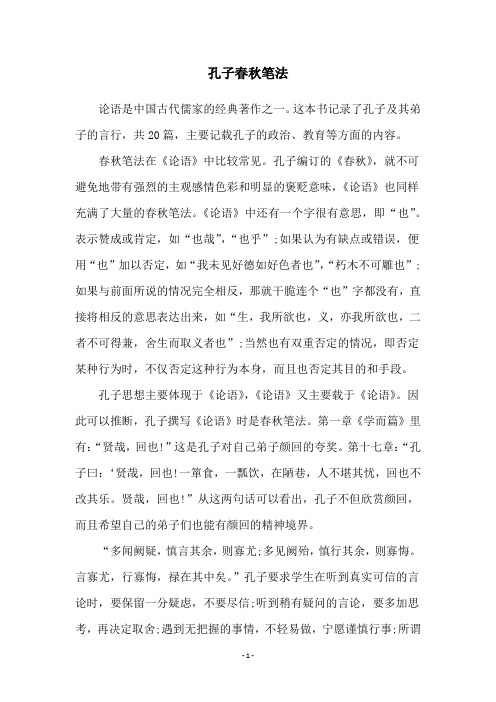
孔子春秋笔法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
这本书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共20篇,主要记载孔子的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春秋笔法在《论语》中比较常见。
孔子编订的《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和明显的褒贬意味,《论语》也同样充满了大量的春秋笔法。
《论语》中还有一个字很有意思,即“也”。
表示赞成或肯定,如“也哉”,“也乎”;如果认为有缺点或错误,便用“也”加以否定,如“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朽木不可雕也”;如果与前面所说的情况完全相反,那就干脆连个“也”字都没有,直接将相反的意思表达出来,如“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当然也有双重否定的情况,即否定某种行为时,不仅否定这种行为本身,而且也否定其目的和手段。
孔子思想主要体现于《论语》,《论语》又主要载于《论语》。
因此可以推断,孔子撰写《论语》时是春秋笔法。
第一章《学而篇》里有:“贤哉,回也!”这是孔子对自己弟子颜回的夸奖。
第十七章:“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孔子不但欣赏颜回,而且希望自己的弟子们也能有颜回的精神境界。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孔子要求学生在听到真实可信的言论时,要保留一分疑虑,不要尽信;听到稍有疑问的言论,要多加思考,再决定取舍;遇到无把握的事情,不轻易做,宁愿谨慎行事;所谓“说话少,错误就少,办事少,过失就少”。
可见孔子也深谙“春秋笔法”之妙。
第二章《为政篇》里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此处“恕”即恕道,是为人处世应当遵守的道理,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中引用此语,意在勉励学生,应当心胸宽广,待人友善,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不要以自己的好恶来推断别人。
第三章《雍也篇》里有:“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春秋笔法”集释

“春秋笔法”集释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
【背景】孔子用春秋笔法来写史书主要目的在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孔夫子写书的目的,本是要把那些他看不惯的人的行为,记入青史的;但是人总是有缺点的,连孔夫子所尊敬的人和他的亲人、贤者也不例外,竟也有使人看不惯的行为出现,如果孔夫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些看不惯的行为,一古脑儿写进去了,那么人家一看到,对“所尊敬的人”、对“亲人”和“贤者”的敬意,也就大打了折扣。
所以,孔夫子呀,宁愿说谎。
这种在历史上说谎,有一个专名词,叫做“曲笔”。
“曲笔”就是该直着说的话,要把它歪曲了来说。
相反的,有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做法,也有一个专名词,叫做“直笔”,就是正直的笔。
孔夫子写《春秋》,本来是要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可见写“直笔”是多么不容易!春秋笔法其实是一种妥协,是一种无奈!这种办法写出的史书开创了写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全书文字简略,叙事注重结果,一般不铺叙过程,写法很象今天的标题新闻。
使这本书卓立千古,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首先是因为它具有高超的表现技巧,即“春秋笔法”。
历史上,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译文:《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
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见《左传•成十四》。
)遗憾的是,限于体例,左丘明没有充分的展开,我们只能看到他思考问题的结果,而看不到他思考问题的过程,因而“春秋笔法”这个时期还显得有些朦胧。
到了西汉,一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一个结合《春秋》实例解说了这种笔法。
这是一大进步。
通过这样演绎,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治措施的推行,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条件。
春秋笔法出华章

春秋笔法出华章[小引]什么是春秋笔法?相传孔子修订史书《春秋》,注意笔削褒贬,含有“微言大义”。
后来称文章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写作手法为春秋笔法。
[解说]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杜预对“春秋笔法”作了如下的解说:“一曰微而显。
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
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
梁亡。
城缘陵是也。
”即不直接说出含意,借助“微言”而显“大义”,落笔于此而义在彼,在具体的语境中,其意自明。
“二曰志而晦。
约言示志,推以知例。
参会不地,与谋日及之类是也。
”即运用简洁的文字来表达隐晦的意思。
根据用词的不同,举一反三,以了解更多的内容。
“三曰婉而成章。
曲从义训,以示大顺。
诸所讳避,璧借许田之类是也。
”即运用“委婉”“曲笔”“避讳”,而不直接表意。
“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
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
”即如实照搬事实,不加任何的掩饰,让读者根据客观事实作出准确地判断。
“五曰惩恶而劝善。
求名而仁,欲盖而彰,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即恶人就要受到惩处,以“惩恶扬善”。
好人就要名垂青史,以给人激励。
鲁迅先生写文章很喜欢运用春秋笔法。
我们在高中教材中学到的《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是运用春秋笔法的典范之作。
如,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先生为了让人们看清“三"一八惨案”的真相,他极力描绘了刘和珍、杨德群被虐杀的经过:“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
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
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以上描写中的“其一是手枪”,“从背部入,斜穿心肺”。
事实客观、准确,毋庸质疑,反动派也无法否认、狡辩。
根据这些事实,读者也在阅读时对“三"一八惨案”就作出判断: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偷袭性质的大屠杀。
论春秋笔法及其在古代文化中的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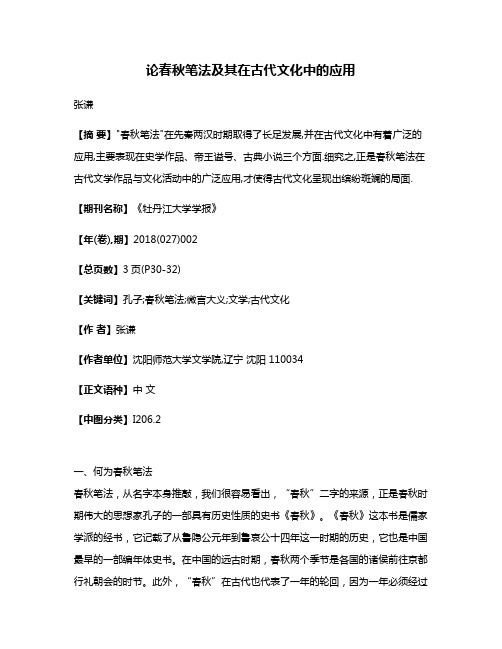
论春秋笔法及其在古代文化中的应用张谦【摘要】"春秋笔法"在先秦两汉时期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在古代文化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史学作品、帝王谥号、古典小说三个方面.细究之,正是春秋笔法在古代文学作品与文化活动中的广泛应用,才使得古代文化呈现出缤纷斑斓的局面.【期刊名称】《牡丹江大学学报》【年(卷),期】2018(027)002【总页数】3页(P30-32)【关键词】孔子;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文学;古代文化【作者】张谦【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一、何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从名字本身推敲,我们很容易看出,“春秋”二字的来源,正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一部具有历史性质的史书《春秋》。
《春秋》这本书是儒家学派的经书,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这一时期的历史,它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在中国的远古时期,春秋两个季节是各国的诸侯前往京都行礼朝会的时节。
此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了一年的轮回,因为一年必须经过春秋两季。
而史书记载的都是国家一年或者几年发生的历史事件,因此“春秋”两字便成了史书的一个专有的代名词。
春秋各个国家之中,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便被称作《春秋》。
按照传统的看法,古今很多学者推定《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是鲁国所有史官的集体智慧结晶,毕竟从当时的人力、物力来看,一个人完成一部史书的工作完全超过了当时的客观现实,并且史书的记载是编年体性质的,这就意味着史料和记载是连续不间断的,这也侧面证明了《春秋》一书是不同时期史官智慧的总体结晶。
根据史料我们能够考证,《春秋》这本书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发生后,就已经失传,而现在比较流行的各种版本,大部分是由《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这三部史书拼接融合而成的。
据《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周匡王六年,晋灵公昏庸无道,想要杀死当时的正卿赵盾,赵盾的族人赵穿便因为这件事去杀了晋灵公,晋国太史董狐便认为责任在赵盾,于是公开直书:“赵盾弑其君。
论《聊斋志异》中的春秋笔法

论《聊斋志异》中的春秋笔法高 强“春秋笔法”也被称为“曲笔”,因这种叙事手法始于孔子作《春秋》,故而得名,晋代杜预在总结这种笔法的精要时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也即刘勰所谓之“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
大略言之,“春秋笔法”的要点有二,一是作者在叙述事件、描写人物时,表面上不表达爱憎好恶,而是将其真实感情和评价寄托于行文之中,让读者自己去感受;二是作者一般用一两个重要的字,让读者结合背景知识,来理解作者的深意和价值评判,此即“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一字之贬,辱甚斧钺之诛”。
在古代文学中,这种笔法一般用于涉及帝王将相等显贵人物,或者与作者关系密切的师长亲友等有关的叙事中,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不过,这种“讳”并不是改变或歪曲事实,而是如同上文所述,作者表面上不直书好恶臧否,而是将真情实感隐藏于文字之中,让读者自己理解。
在《聊斋志异》中,春秋笔法得到了应用,这种笔法主要应用于和明末清初真实人物事件有关的篇目中,其目的主要分为褒扬和贬斥两种,以后者为主,以贬斥为目的的篇目也可细分为半晦半显和完全隐晦两类。
该笔法也用于非与真实历史相关的篇目中,以表达作者对权贵和社会丑恶现象的抨击、对人物的褒贬。
春秋笔法的采用很大程度上是蒲松龄在清初文字狱高压下的无奈之举,同时也展现了作者文字功底的精湛和行文技巧的高超,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传播性。
一、与真实历史有关篇目之春秋笔法(一)褒扬此类篇目涉及真实存在且在蒲松龄生活时代的语境中颇为敏感的人物,作者内心对其持褒扬态度,但碍于许多原因不便或不能公开表达,于是采用平实且表面看来不着态度的叙事方式,将其情感寓于行文之中。
比如《黄将军》篇,文字甚短,记录了“黄将军”黄得功微贱时的事迹,作者叙述平实,从行文表面很难看出其尊贬情感,但作者的真实态度隐藏于两个字之中——靖南。
黄得功,字虎山,祖籍合肥,后在辽阳投军,因其作战勇敢,积功逐步由亲军、游击、参将升为总兵官,崇祯末年率兵抵御农民军,并讨伐叛将,被明廷封为“靖南伯”,甲申之变后南明政权建立,黄得功位列拱卫南京的“江北四镇”之一,被封为“靖南候”,驻扎于滁州、和州地区。
春秋孔子文章写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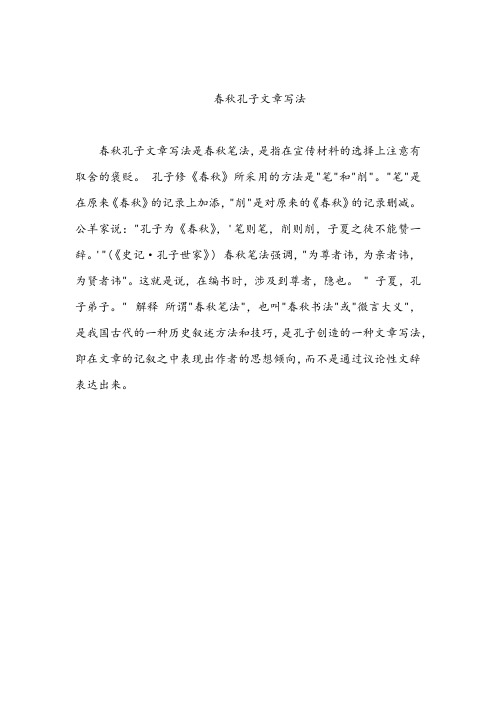
春秋孔子文章写法
春秋孔子文章写法是春秋笔法,是指在宣传材料的选择上注意有取舍的褒贬。
孔子修《春秋》所采用的方法是"笔"和"削"。
"笔"是在原来《春秋》的记录上加添,"削"是对原来的《春秋》的记录删减。
公羊家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史记·孔子世家》) 春秋笔法强调,"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这就是说,在编书时,涉及到尊者,隐也。
" 子夏,孔子弟子。
" 解释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法和技巧,是孔子创造的一种文章写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
儒家春秋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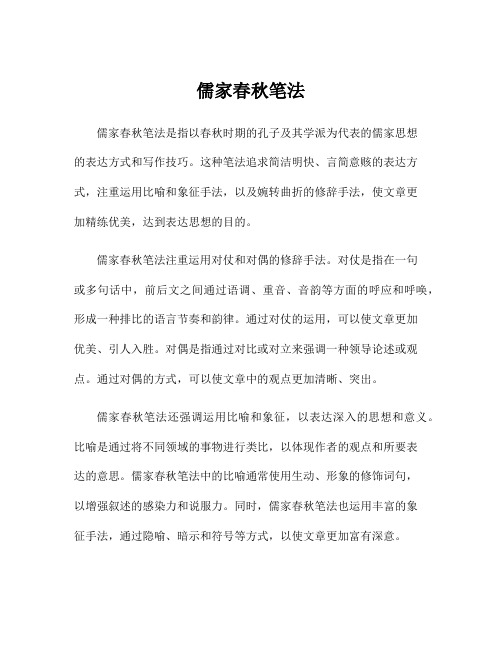
儒家春秋笔法儒家春秋笔法是指以春秋时期的孔子及其学派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写作技巧。
这种笔法追求简洁明快、言简意赅的表达方式,注重运用比喻和象征手法,以及婉转曲折的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加精练优美,达到表达思想的目的。
儒家春秋笔法注重运用对仗和对偶的修辞手法。
对仗是指在一句或多句话中,前后文之间通过语调、重音、音韵等方面的呼应和呼唤,形成一种排比的语言节奏和韵律。
通过对仗的运用,可以使文章更加优美、引人入胜。
对偶是指通过对比或对立来强调一种领导论述或观点。
通过对偶的方式,可以使文章中的观点更加清晰、突出。
儒家春秋笔法还强调运用比喻和象征,以表达深入的思想和意义。
比喻是通过将不同领域的事物进行类比,以体现作者的观点和所要表达的意思。
儒家春秋笔法中的比喻通常使用生动、形象的修饰词句,以增强叙述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同时,儒家春秋笔法也运用丰富的象征手法,通过隐喻、暗示和符号等方式,以使文章更加富有深意。
在儒家春秋笔法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法叫做喻深意远。
这种手法通过简短的文字或者故事来寓意深远的道理。
喻深意远的修辞手法不仅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而且能够使读者产生思考和领悟。
喻深意远的修辞手法在儒家经典《论语》中尤为常见,它以简短的对话和故事,将孔子的思想和哲理深入浅出地呈现给读者。
在运用儒家春秋笔法时,还应注意修饰词的运用。
修饰词可以增强句子的表达力,使句子更加生动有力。
儒家春秋笔法中常见的修饰词包括形容词、副词和比喻等,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句子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在应用儒家春秋笔法时,还需注意语言的典雅和文化内涵的体现。
在儒家春秋笔法中,语言的使用应该雅致、含蓄,体现了儒家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和追求。
同时,儒家春秋笔法中还融入了传统的文化符号和象征,这些符号和象征通过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和理解,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表达儒家思想。
总之,儒家春秋笔法以简练、明快、韵律美为特点,注重对仗、对偶、比喻和象征的运用。
孔子“春秋笔法”述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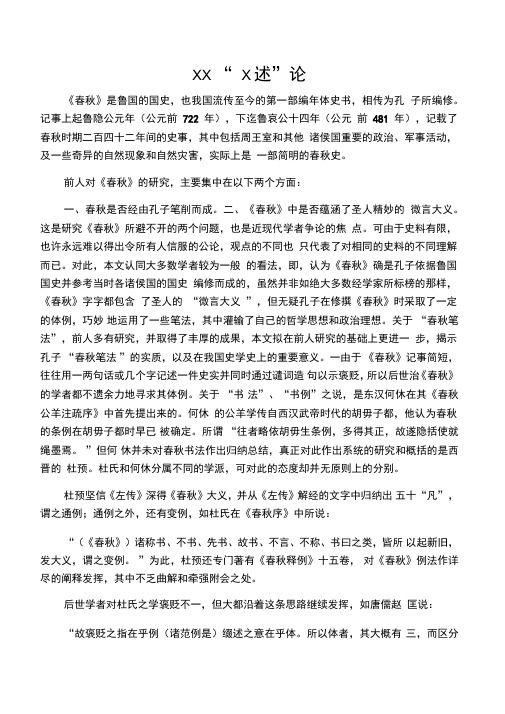
XX “ X述”论《春秋》是鲁国的国史,也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所编修。
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 年),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其中包括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及一些奇异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一部简明的春秋史。
前人对《春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春秋是否经由孔子笔削而成。
二、《春秋》中是否蕴涵了圣人精妙的微言大义。
这是研究《春秋》所避不开的两个问题,也是近现代学者争论的焦点。
可由于史料有限,也许永远难以得出令所有人信服的公论,观点的不同也只代表了对相同的史料的不同理解而已。
对此,本文认同大多数学者较为一般的看法,即,认为《春秋》确是孔子依据鲁国国史并参考当时各诸侯国的国史编修而成的,虽然并非如绝大多数经学家所标榜的那样,《春秋》字字都包含了圣人的“微言大义”,但无疑孔子在修撰《春秋》时采取了一定的体例,巧妙地运用了一些笔法,其中灌输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想。
关于“春秋笔法”,前人多有研究,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揭示孔子“春秋笔法”的实质,以及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一由于《春秋》记事简短,往往用一两句话或几个字记述一件史实并同时通过谴词造句以示褒贬,所以后世治《春秋》的学者都不遗余力地寻求其体例。
关于“书法”、“书例”之说,是东汉何休在其《春秋公羊注疏序》中首先提出来的。
何休的公羊学传自西汉武帝时代的胡毋子都,他认为春秋的条例在胡毋子都时早已被确定。
所谓“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
”但何休并未对春秋书法作出归纳总结,真正对此作出系统的研究和概括的是西晋的杜预。
杜氏和何休分属不同的学派,可对此的态度却并无原则上的分别。
杜预坚信《左传》深得《春秋》大义,并从《左传》解经的文字中归纳出五十“凡”,谓之通例;通例之外,还有变例,如杜氏在《春秋序》中所说:“(《春秋》)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
《史记》中的“春秋笔法”

《史记》中的“春秋笔法”发布时间:2022-03-02T04:33:00.864Z 来源:《教育研究》2021年12月下36期作者:白雪梅[导读] 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和初创的时期,其独有的魅力和文风艺术昭示着中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
在历史意识空前发展的周代,“史官文化”因为史官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肩负对现实的责任而成熟,以《春秋》为例,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传说孔子写《春秋》的目的是要原始察终,惩恶扬善,拨乱反正,是“礼义之大宗”,维护周礼,为达此目的,孔子在写作时非常讲究遣词造句,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出他的爱憎,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被誉为“春秋笔法”,影响着后代史传文学作品。
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白雪梅摘要: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和初创的时期,其独有的魅力和文风艺术昭示着中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
在历史意识空前发展的周代,“史官文化”因为史官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肩负对现实的责任而成熟,以《春秋》为例,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传说孔子写《春秋》的目的是要原始察终,惩恶扬善,拨乱反正,是“礼义之大宗”,维护周礼,为达此目的,孔子在写作时非常讲究遣词造句,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出他的爱憎,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被誉为“春秋笔法”,影响着后代史传文学作品。
关键词:春秋笔法;《史记》;继承;发展1.1“春秋笔法”在《春秋》中的运用1.1.1 “微而显”首先,“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出处??)指文辞简约但意义显豁。
成公“十有四年……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
”(春秋、左传、史记的引文都需要标注出处,后文同)此处,叔孙氏是氏族名,因侨如奉君命出使,为了尊重君命,所以侨如前冠上了氏族“叔孙”的称谓,即叔孙侨如前往齐国迎亲。
后一句称侨如,而不是叔孙侨如,是因为侨如迎接夫人归来,为了显示对夫人的尊重,而只称侨如。
从《春秋》一书探究“春秋笔法”

从《春秋》一书探究“春秋笔法”《吕氏春秋·先识》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之法,执而泣。
夏桀迷惑,暴乱愈甚。
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
”夏太史终古手执竹简乘车远去的背影,应是中国史官的最早印象,只是当时所成典籍只能叫记载之法,而不能称为史学。
公元前5世纪,孔子“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以成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春秋》一书,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其中共计大小战争230次,灾异122,亡国52,弑君36,却仅用一万六千余字便囊括其中,可谓语词简练,文约事丰。
不过“春秋笔法”这个概念并不是随着《春秋》的诞生而立即出现的,是在《春秋》广泛流传和后人对《春秋》的不断解读和研究中逐渐被提炼出来的。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末句可谓是关于“春秋笔法”的最佳解释,即不直接在文中以议论性的文字表明态度,而是将褒贬蕴于文章的记叙之中,相当于给文章糊上了一层“窗户纸”,能不能看透其中深意就要看诸家眼力。
言语之间看似平淡,实则字字珠玑,用意深刻,后来人多用“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来形容“春秋笔法”的苛刻与严厉。
通常认为“春秋笔法”的主要表现有以下三点:1.常事不书“常事不书”一词出于《公羊传》,多被认为是“春秋笔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体例,就是说《春秋》不记录平常之事,书里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都有其特殊含义。
而这样的书例据《公羊传》统计达54条之多,从一些自然界的灾役、奇怪之事到人事社会中的一些不同寻常或是不合理的礼仪祭祀活动,皆有所记。
如《春秋·桓公十四年》载:“春,正月,公会郑伯于曹。
无冰。
”《公羊传》曰:“何以书?记异也。
”史官对在酷寒的正月河流竟没有结冰一事感觉奇怪,便将此事记录了下来。
说说春秋笔法的“一字含褒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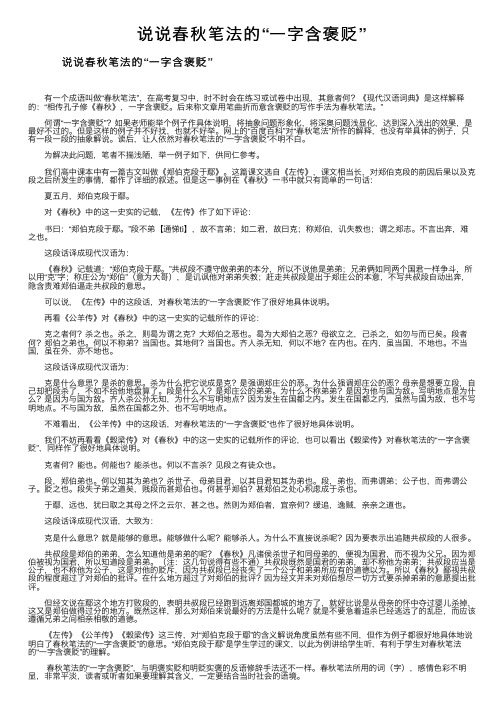
说说春秋笔法的“⼀字含褒贬”说说春秋笔法的“⼀字含褒贬”有⼀个成语叫做“春秋笔法”,在⾼考复习中,时不时会在练习或试卷中出现,其意者何?《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相传孔⼦修《春秋》,⼀字含褒贬。
后来称⽂章⽤笔曲折⽽意含褒贬的写作⼿法为春秋笔法。
”何谓“⼀字含褒贬”?如果⽼师能举个例⼦作具体说明,将抽象问题形象化,将深奥问题浅显化,达到深⼊浅出的效果,是最好不过的。
但是这样的例⼦并不好找,也就不好举。
⽹上的“百度百科”对“春秋笔法”所作的解释,也没有举具体的例⼦,只有⼀段⼀段的抽象解说。
读后,让⼈依然对春秋笔法的“⼀字含褒贬”不明不⽩。
为解决此问题,笔者不揣浅陋,举⼀例⼦如下,供同仁参考。
我们⾼中课本中有⼀篇古⽂叫做《郑伯克段于鄢》。
这篇课⽂选⾃《左传》,课⽂相当长,对郑伯克段的前因后果以及克段之后所发⽣的事情,都作了详细的叙述。
但是这⼀事例在《春秋》⼀书中就只有简单的⼀句话:夏五⽉,郑伯克段于鄢。
对《春秋》中的这⼀史实的记载,《左传》作了如下评论:书⽈:“郑伯克段于鄢。
”段不弟【通悌tì】,故不⾔弟;如⼆君,故⽈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
不⾔出奔,难之也。
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为:《春秋》记载道:“郑伯克段于鄢。
”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说他是弟弟;兄弟俩如同两个国君⼀样争⽃,所以⽤“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意为⼤哥),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赶⾛共叔段是出于郑庄公的本意,不写共叔段⾃动出奔,隐含责难郑伯逼⾛共叔段的意思。
可以说,《左传》中的这段话,对春秋笔法的“⼀字含褒贬”作了很好地具体说明。
再看《公⽺传》对《春秋》中的这⼀史实的记载所作的评论:克之者何?杀之也。
杀之,则曷为谓之克?⼤郑伯之恶也。
曷为⼤郑伯之恶?母欲⽴之,⼰杀之,如勿与⽽已矣。
段者何?郑伯之弟也。
何以不称弟?当国也。
其地何?当国也。
齐⼈杀⽆知,何以不地?在内也。
在内,虽当国,不地也。
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春秋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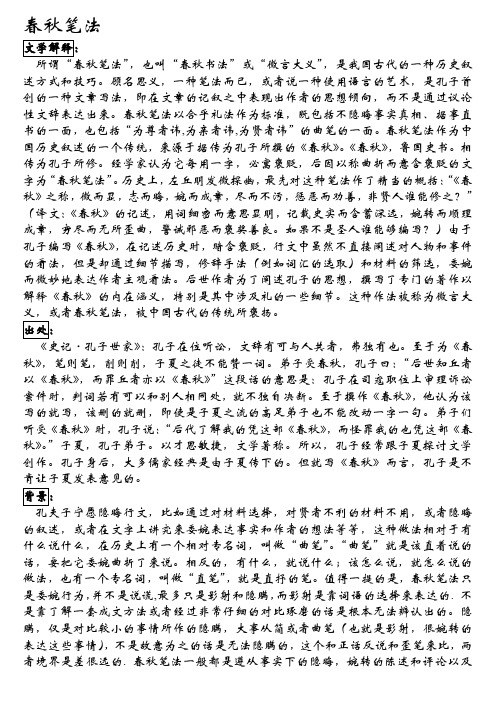
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
顾名思义,一种笔法而已,或者说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是孔子首创的一种文章写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
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既包括不隐晦事实真相、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曲笔的一面。
春秋笔法作为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传统,来源于据传为孔子所撰的《春秋》。
《春秋》,鲁国史书。
相传为孔子所修。
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后因以称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
历史上,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译文:《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
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由于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
后世作者为了阐述孔子的思想,撰写了专门的著作以解释《春秋》的内在涵义,特别是其中涉及礼的一些细节。
这种作法被称为微言大义,或者春秋笔法,被中国古代的传统所褒扬。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
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在司寇职位上审理诉讼案件时,判词若有可以和别人相同处,就不独自决断。
至于撰作《春秋》,他认为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即使是子夏之流的高足弟子也不能改动一字一句。
弟子们听受《春秋》时,孔子说:“后代了解我的凭这部《春秋》,而怪罪我的也凭这部《春秋》。
”子夏,孔子弟子。
以才思敏捷,文学著称。
所以,孔子经常跟子夏探讨文学创作。
什么是春秋笔法?都有哪些运用春秋笔法的文学作品实例?

什么是春秋笔法?都有哪些运用春秋笔法的文学作品实例?谢邀!春秋笔法,是孔子首创的描述写法,现多称文章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写作手法。
委婉地表达作者的倾向,不直接表明态度,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让人知道。
也指一字置褒贬,简练而含蓄地点评人事,亦称'微言大义'。
春秋笔法作为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传统,来源于据传《春秋》。
《春秋》,鲁国史书。
相传为孔子所修。
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贬。
历史上,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译文:《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
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春秋笔法例析】一、欲说还休,以少引多作品中所渲染、抒写的人物逐渐接近主旨时,作者忽然收笔,即“欲说还休”,不把话说尽,要留有让读者思考的余地。
由于世界观,生活经验和艺术修养的不同,读者得出的主旨与作者的主旨可能迥异,各个读者得出的主旨也可能不同,但人们又不会因此去追求,这类语言正是在这种猜度、体察、品味之中显示出语言的“不露山水”之美。
例如《红楼梦、第九十八回中写林黛五弥留之际:“……猛听寞王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心冷汗,不做声了。
” 有人试图为黛玉这“好……”字后面难言之隐语填空,但无法填出,也无须填出,因为黛玉临终前,哀恨交集,至情倾泄,“闲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
”二、不著一字,以无胜有.春秋笔法犹似画龙,见首不见其尾,方是神龙。
“露其要处而藏其全”,才能显示其潜涵的魅力。
春秋笔法又如乐曲,戛然而止,则余音缭绕,韵味无穷。
倘若倾箱倒箧,一泄无余,则使人索然乏味。
文中的直观形象仅是作者表情达意的凭藉形式,其真实意图不著一字,但读者只要作穿透性深究,就会无中悟有,“尽得风流”。
春秋笔法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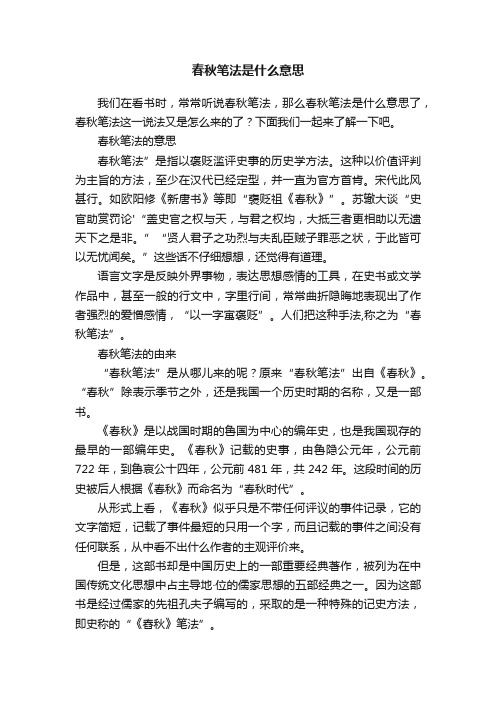
春秋笔法是什么意思我们在看书时,常常听说春秋笔法,那么春秋笔法是什么意思了,春秋笔法这一说法又是怎么来的了?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春秋笔法的意思春秋笔法”是指以褒贬滥评史事的历史学方法。
这种以价值评判为主旨的方法,至少在汉代已经定型,并一直为官方首肯。
宋代此风甚行。
如欧阳修《新唐书》等即“襃贬祖《春秋》”。
苏辙大谈“史官助赏罚论'“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
”“贤人君子之功烈与夫乱臣贼子罪恶之状,于此皆可以无忧闻矣。
”这些话不仔细想想,还觉得有道理。
语言文字是反映外界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在史书或文学作品中,甚至一般的行文中,字里行间,常常曲折隐晦地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以一字寓褒贬”。
人们把这种手法,称之为“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的由来“春秋笔法”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春秋笔法”出自《春秋》。
“春秋”除表示季节之外,还是我国一个历史时期的名称,又是一部书。
《春秋》是以战国时期的鲁国为中心的编年史,也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编年史。
《春秋》记载的史事,由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
这段时间的历史被后人根据《春秋》而命名为“春秋时代”。
从形式上看,《春秋》似乎只是不带任何评议的事件记录,它的文字简短,记载了事件最短的只用一个字,而且记载的事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从中看不出什么作者的主观评价来。
但是,这部书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重要经典著作,被列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五部经典之一。
因为这部书是经过儒家的先祖孔夫子编写的,釆取的是一种特殊的记史方法,即史称的“《舂秋》笔法”。
孔夫子修史,并没有遵守记录历史的起码守则,尊重历史事实去秉笔直书,而是依据他“使乱臣賊子惧”的主观想法去“损益”历史而书的。
凡遇到“尊者”、“亲者Z和“贤者”的过失和恶行,他都要运用曲笔,为他们掩饰。
《公羊传》总结孔夫子的修史方法为“《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春秋笔法的名词解释出处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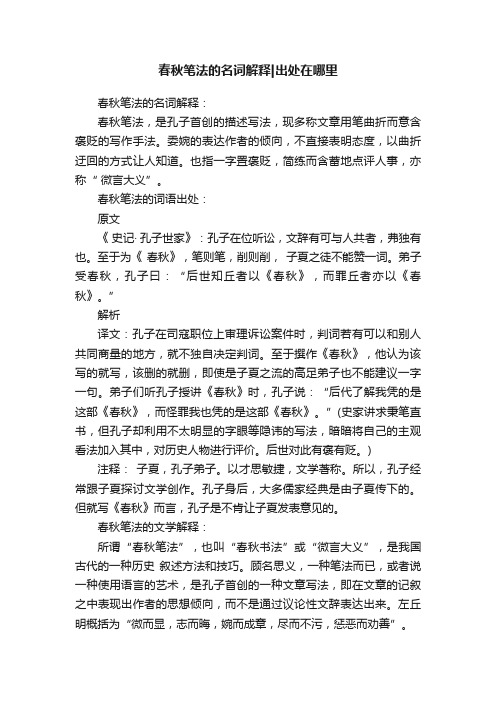
春秋笔法的名词解释|出处在哪里春秋笔法的名词解释:春秋笔法,是孔子首创的描述写法,现多称文章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写作手法。
委婉的表达作者的倾向,不直接表明态度,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让人知道。
也指一字置褒贬,简练而含蓄地点评人事,亦称“ 微言大义”。
春秋笔法的词语出处:原文《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
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解析译文:孔子在司寇职位上审理诉讼案件时,判词若有可以和别人共同商量的地方,就不独自决定判词。
至于撰作《春秋》,他认为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即使是子夏之流的高足弟子也不能建议一字一句。
弟子们听孔子授讲《春秋》时,孔子说:“后代了解我凭的是这部《春秋》,而怪罪我也凭的是这部《春秋》。
”(史家讲求秉笔直书,但孔子却利用不太明显的字眼等隐讳的写法,暗暗将自己的主观看法加入其中,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
后世对此有褒有贬。
) 注释:子夏,孔子弟子。
以才思敏捷,文学著称。
所以,孔子经常跟子夏探讨文学创作。
孔子身后,大多儒家经典是由子夏传下的。
但就写《春秋》而言,孔子是不肯让子夏发表意见的。
春秋笔法的文学解释: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法和技巧。
顾名思义,一种笔法而已,或者说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是孔子首创的一种文章写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
左丘明概括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春秋笔法作为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传统,来源于据传《春秋》。
《春秋》,鲁国史书。
相传为孔子所修。
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贬。
历史上,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译文:《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
论孔子的“春秋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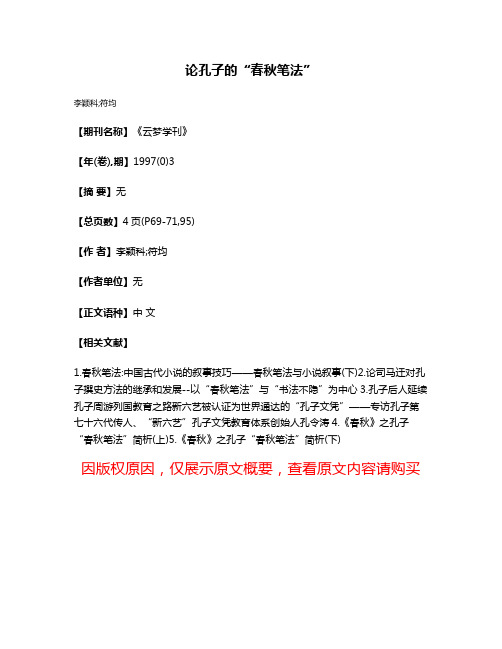
论孔子的“春秋笔法”
李颖科;符均
【期刊名称】《云梦学刊》
【年(卷),期】1997(0)3
【摘要】无
【总页数】4页(P69-71,95)
【作者】李颖科;符均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春秋笔法: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技巧——春秋笔法与小说叙事(下)
2.论司马迁对孔子撰史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以“春秋笔法”与“书法不隐”为中心
3.孔子后人延续孔子周游列国教育之路新六艺被认证为世界通达的“孔子文凭”——专访孔子第七十六代传人、“新六艺”孔子文凭教育体系创始人孔令涛
4.《春秋》之孔子“春秋笔法”简析(上)
5.《春秋》之孔子“春秋笔法”简析(下)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孔子“春秋笔法”述论《春秋》是鲁国的国史,也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所编修。
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其中包括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及一些奇异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一部简明的春秋史。
前人对《春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春秋是否经由孔子笔削而成。
二、《春秋》中是否蕴涵了圣人精妙的微言大义。
这是研究《春秋》所避不开的两个问题,也是近现代学者争论的焦点。
可由于史料有限,也许永远难以得出令所有人信服的公论,观点的不同也只代表了对相同的史料的不同理解而已。
对此,本文认同大多数学者较为一般的看法,即,认为《春秋》确是孔子依据鲁国国史并参考当时各诸侯国的国史编修而成的,虽然并非如绝大多数经学家所标榜的那样,《春秋》字字都包含了圣人的“微言大义”,但无疑孔子在修撰《春秋》时采取了一定的体例,巧妙地运用了一些笔法,其中灌输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想。
关于“春秋笔法”,前人多有研究,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揭示孔子“春秋笔法”的实质,以及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一由于《春秋》记事简短,往往用一两句话或几个字记述一件史实并同时通过谴词造句以示褒贬,所以后世治《春秋》的学者都不遗余力地寻求其体例。
关于“书法”、“书例”之说,是东汉何休在其《春秋公羊注疏序》中首先提出来的。
何休的公羊学传自西汉武帝时代的胡毋子都,他认为春秋的条例在胡毋子都时早已被确定。
所谓“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
”但何休并未对春秋书法作出归纳总结,真正对此作出系统的研究和概括的是西晋的杜预。
杜氏和何休分属不同的学派,可对此的态度却并无原则上的分别。
杜预坚信《左传》深得《春秋》大义,并从《左传》解经的文字中归纳出五十“凡”,谓之通例;通例之外,还有变例,如杜氏在《春秋序》中所说:“(《春秋》)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
”为此,杜预还专门著有《春秋释例》十五卷,对《春秋》例法作详尽的阐释发挥,其中不乏曲解和牵强附会之处。
后世学者对杜氏之学褒贬不一,但大都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发挥,如唐儒赵匡说:“故褒贬之指在乎例(诸范例是)缀述之意在乎体。
所以体者,其大概有三,而区分有十。
所谓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会,此常典,所当载也,故悉书之,随其邪正而加褒贬,此其一也。
祭祀、婚姻、赋税、军旅、蒐狩、皆国之大事,亦所当载也。
其合礼者,夫子修经时悉皆不取,故公、谷云:常事不书,是也。
其非者及合于变之正者,乃取书之,而增损其文,以寄褒贬之意,此其二也。
庆瑞灾异,及君被杀被执,及奔放逃叛,归如纳立,如此并非常之事,以史策所当载,夫子则因之而加褒贬焉,此其三也。
此述作大凡也。
”参照今本《春秋》,这种解释犹显僵硬,但比三传有更多合理之处。
清人顾栋高走得更远,他在《读春秋偶笔》中论曰:“春秋书初,书犹,书遂,俱圣笔颊上添毫处;书‘初献六羽’,以明前此之儧;书‘初税亩’,以志横征之始;‘犹绎’,‘犹三望’,是认其可已而不已;‘犹朝于庙’,是幸其礼之未尽废;‘遂伐楚,次于泾’,‘遂伐许’,‘遂围许’,是志其赴机之捷;‘遂灭赖’,‘遂灭逼汤’,‘遂伐曹,入其郛’,是志其兵威之暴;‘遂及齐侯宋公盟’,是志其国事之擅。
他如:曰‘诱杀’,曰‘以归’,曰‘取师’,曰‘大去’,曰‘弃师’,曰‘逃归’,曰‘歼’,曰‘戕’,曰‘用’,皆圣人用意下字,此其显然者。
”如此刻意探求一字之微言大义,显然求之过深。
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离“圣意”益远。
实际上,幻想从春秋中概括出一套严密的天衣无缝的体例是不可能的,就连汉儒董仲舒也认为“春秋无达诂。
”但两千多年的春秋学研究大体就是沿着这条轨迹摇摇摆摆地前行,虽然其中偶有真知灼见(如前文所引唐儒赵匡所论),但更多的是穿凿附会和冥思曲解。
所谓阐明圣人的微言大义,说到底是借以发挥自己的“大义”。
这使得《春秋》为层层幻光迷雾所笼罩,让人难以理解。
诚如宋人富弼所言:“《春秋》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有疏之,尚未能尽;以之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论议,至千余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彻晓了。
”[1]前人研究《春秋》“书法”、“书例”,并非仅仅把它作为史书的记事体例,而是刻意探求蕴涵在其中的褒贬,即“微言大义”。
从语源上考察,“微言大义”一词当出于东汉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所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
但几乎历来的研究家都认为《春秋》微言大义之说肇始于孟子。
《孟子•腾文公下》篇说:“世衰道危,邪说暴行有作。
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又据《孟子•离娄下》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檮杌》,一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由此可见,孟子认为经由孔子编修过的《春秋》同原来的史书最大的不同正在于春秋之“义”,孔子为挽救当时时势,防止“邪说暴行”,才通过《春秋》以褒贬当世,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也。
”后世的经学家便以《孟子》为依据,认为《春秋》字字都蕴涵了圣人的微言大义,美刺褒贬。
如范宁《谷梁传序》云:“(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著劝戒,拯颓纲以继三五,鼓芳风以扇游尘,一字之褒,宠踰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
”深受今文学影响的司马迁也认为:“(孔子)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
……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直到近代,仍有学者坚持《春秋》一字褒贬之说。
如皮锡瑞氏在《经学通论•论春秋一字褒贬之义宅心恕而立法严》中说:“春秋大义,在讨乱贼,则春秋必褒忠义。
”但关于《春秋》微言大义之论,后世学者多疑之。
唐刘知己《史通》有《惑经》篇,从“直笔”的标准出发,对《春秋》经文提出“未喻”者十二,“虚美”者五。
认为《春秋》“多是古史旧文”,“孔子之所修者,但因其行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
”孟子所说的“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乃乌有之谈。
北宋王安石则径直将《春秋》讥为“断烂朝报”。
南宋郑樵也说:“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此之谓欺人之学。
”[2]就连理学家朱熹也不满学者过分探求一字之间的褒贬,他说:“若欲推求一字之间。
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
”[3]认为:“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
”[4]有清一代,历史考据学兴起,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为代表的考据史家将“据实直书”、“实事求是”作为史学的根本任务,主张如实记录和审慎考求史实,反对史家追求“褒贬义例”,以既定的价值观来裁断和评论史实。
因此,他们虽然不敢直接否定《春秋》的微言大义、褒贬义例,也只是认为《春秋》仅仅直书其事,使之善恶自现。
如钱大昕氏云:“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矣。
”[5]并对孟子言“《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进行了怀疑和批判,认为孟子实夸大其辞。
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也认为:“若谓《春秋》之道,但在明法氐罪,以惧乱臣贼子,则已死之乱臣贼子,何由知惧?见在之乱臣贼子,大利当前,又何恤于口诛笔伐哉?”[6]总之,前人虽然对“春秋笔法”多有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大多都过于专精,而割裂穿凿。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春秋》著作本身太过简短难明外,还有政治上的因素。
由于孔子和《春秋》在我国历史上特殊的地位,再加上自汉代以来经史分途,就更加导致了学者们认识上的局限和混乱。
研究者大多囿于门户之见,各据一端,或以经绳之,或以史绳之,终难得其要旨。
例如清人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中还振振有辞地说:“经史分别甚明,读经者不得以史法绳《春秋》,修史者亦不当以《春秋》书法为史法。
”当代学者吕绍纲先生也认为:“(《春秋》)看来是史书,实为一部政治书。
”[7]而近世力倡“新史学”的梁启超,则标榜史学的最高目的是“使恰如其本来”,对我国传统史学提出了猛烈地抨击,其锋芒所向,首指孔子。
他认为我国传统史学“从不肯为历史而历史,而必移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的刍狗而已,岂结果必至强史就我……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
”[8]并进而讥《春秋》为“秽史”,所谓“盖春秋而果为史者,则岂惟如王安石所讥之‘断烂朝报’,恐其秽乃不减魏收矣。
”[9]其观点之偏颇,可见一斑。
二春秋笔法,主要是指《春秋》独特的记事体例。
所谓“体”,就是孔子修《春秋》时用以选材和立意的一般标准。
“例”,则是指对各类问题分别使用不同书法的具体标准。
如果我们放弃这种幻想从《春秋》中得出一套完美体例的不切实际的想法,《春秋》还是有一定体例可寻的,并非只是“断烂朝报”。
例如,一个人被杀,运用的笔法不同,表示的褒贬就不同,《春秋》隐公四年记:“卫人杀州吁于濮。
”《公羊传》解曰:“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
”《谷梁传》解曰:“称人以杀,杀有罪也。
”《春秋》僖公七年记:“郑杀其大夫申侯。
”《谷梁传》解释曰:“称国以杀大夫,杀无罪也”。
可见,称人称国只有一字之差,却有有罪无罪质的差别。
说卫国人杀州吁,意思是卫国人都主张杀州吁,表示州吁有罪该杀。
说郑国杀其大夫申侯,则只是说郑国国君个人杀了申侯,申侯则不一定有罪。
至于国君被杀,称人称国都表示国君无道,只有指出某人弑其君时才表示杀君者有罪而君无罪。
如《春秋》文公十八年记:“莒弑其君庶其。
”《公羊传》解释说:“称国以弑君者,众弑君之辞。
”《春秋》成公十八年记:“晋弑其君州蒲。
”《谷梁传》解释说:“称国以弑君者,君恶甚矣。
”又如,春秋同是记战争,有伐、侵、战、围、救、取、执、溃、败、等不同的写法。
当代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虽认为“春秋为鲁史所书”,并未经孔子编修,但仍承认:“(《春秋》)亦当有例”。
[10]“故从《春秋》中推出些例来,不足为奇。
”白寿彝先生以“《春秋经》校鲁史佚文”,认为《春秋》“有袭用旧史者,有修改旧史者,有删繁就简者,有削而不采者”。
[11]当为公允之论。
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鳞,约其文辞,去其繁重,以制义法。
”杜预《春秋序》亦云:“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
”可见,孔子参阅旧史编修《春秋》的过程也是他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理解的过程。
因此,所谓“书法”,“义例”实际上代表了孔子对史实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孔子历史思想的集中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