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时期1958一个村庄的食堂记忆 (1)
困难时期:1958:一个村庄的食堂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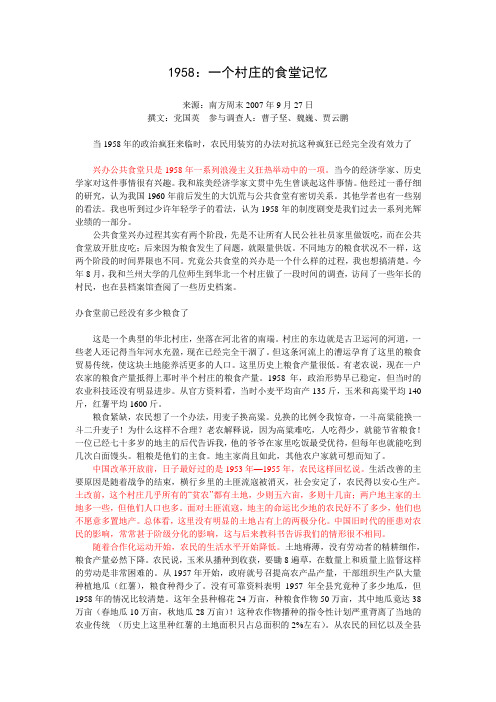
1958:一个村庄的食堂记忆来源:南方周末2007年9月27日撰文:党国英参与调查人:曹子坚、魏巍、贾云鹏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
当今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
我和旅美经济学家文贯中先生曾谈起这件事情。
他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认为我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与公共食堂有密切关系。
其他学者也有一些别的看法。
我也听到过少许年轻学子的看法,认为1958年的制度剧变是我们过去一系列光辉业绩的一部分。
公共食堂兴办过程其实有两个阶段,先是不让所有人民公社社员家里做饭吃,而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后来因为粮食发生了问题,就限量供饭。
不同地方的粮食状况不一样,这两个阶段的时间界限也不同。
究竟公共食堂的兴办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也想搞清楚。
今年8月,我和兰州大学的几位师生到华北一个村庄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访问了一些年长的村民,也在县档案馆查阅了一些历史档案。
办食堂前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北村庄,坐落在河北省的南端。
村庄的东边就是古卫运河的河道,一些老人还记得当年河水充盈,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了。
但这条河流上的漕运孕育了这里的粮食贸易传统,使这块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这里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
有老农说,现在一户农家的粮食产量抵得上那时半个村庄的粮食产量。
1958年,政治形势早已稳定,但当时的农业科技还没有明显进步。
从官方资料看,当时小麦平均亩产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红薯平均1600斤。
粮食紧缺,农民想了一个办法,用麦子换高粱。
兑换的比例令我惊奇,一斗高粱能换一斗二升麦子!为什么这样不合理?老农解释说,因为高粱难吃,人吃得少,就能节省粮食!一位已经七十多岁的地主的后代告诉我,他的爷爷在家里吃饭最受优待,但每年也就能吃到几次白面馒头。
粗粮是他们的主食。
地主家尚且如此,其他农户家就可想而知了。
我的回忆:低标准,瓜菜代

我的回忆:“低标准,瓜菜代”。
1958年,在“反右派”运动后期,人们怕再被划为右派分子,就出现了一种极左思潮。
只说好,不说坏,只说大,不说小。
宁“左”勿右。
甚至搞浮夸,说假话。
认为搞啥都要大、要快。
不管有没有条件,领导说了算。
所以,急速的、人为的、强迫性的、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说什么: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
毛主席已经肯定了。
谁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毛主席!这样谁也不敢搞慢了。
不长时间全省就公社化了。
大部分是一个乡一个公社,大的是一个县一个公社。
说什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抓住桥梁往上上,快马加鞭到天堂。
有的县一夜就宣布公社化了。
公社化后为了加强管理,公社实行了“七统一”(领导、研究、规划、部署、汇报、检查、评比)、“四反对”(本位主义、分散主义、脱离生产、脱离中心)、“三结合”(中心和部门工作结合、干部与群众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七大办”(粮食、钢铁、水利、工业、教育、文化、卫生)、“八深入”(宣传教育、卫生医疗、文化娱乐、邮电投递、商业网点、机械修理、信贷活动、党团活动)、“四个化”(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思想革命化)。
学校教育也实行了“四集体”(吃、住、校、学大集中)。
这样从形式上看确实是“一大二公”了,但人们的思想并没有“一大二公”,仍然停留在小农经济、个体户、私有制的思想基础上。
所以生产劳动积极性不高,大轰大嗡,出勤不出力,磨洋工,干活时间没有歇的时间长。
粮食产量不高,农民收入低下。
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只七、八分钱。
加之全民大办钢铁,男女老少齐上阵。
军事化行动,大兵团作战。
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
东奔西走。
“一平二调”之风大刮。
到哪住哪,走哪吃哪。
吃罢饭嘴一抹就走了。
这就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到1959年,在农村,各公社为解决农民生活问题,各地都办起了公共食堂。
规定男女老少一律在食堂吃饭,不准群众在家做饭吃。
吃食堂的岁月

听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吃食堂的岁月傍晚,和爷爷一起在院中乘凉,美好的月光下凉风习习,我惬意地闭上双眼,陶醉在月光之中。
爷爷看着眼前美好的景象,不知不觉地讲起了过去的吃食堂岁月。
“1958年的秋天,是个热闹的季节。
当时胶县农村各公社在一夜间办起了食堂。
‘1959年更是个跃进年,人人思想插红旗,干劲胜过五八年……’这首歌还是我在读初中时由一位姓周的老师教唱的。
可见,从1958年开始,全国上下都在搞大跃进。
我当时只是初中生,虽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精彩,但是胶县城早已热火朝天。
游行的队伍不分白天和夜晚,一群接着一群,有时绵延几公里,大家举着小红旗,扯着嗓子喊口号,踏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
”“接着就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县局以上的机关团体和中等学校相继停工、停课,办起了钢铁厂,竖起了一个连一个的土高炉,大量农村壮劳力一批批被调进城里或到青岛,拉风箱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整个县城的夜空被熊熊炉火映得通红。
与此同时,基层公社又抽调了一批劳力到处进行‘砍树炼碳’运动。
”“留下来的老老少少和妇女们,由村干部领着在农田里搞‘大跃进’。
为了表示将食堂办到底的决心和不让社员在自己家中烧饭吃,村干部带人人挖掉了各家各户的灶台,查封了所有用于磨面的石磨,动员社员把锅全部砸破卖给国家支援大炼钢铁。
每到吃饭时使用饭票打饭,到1958年年底,基本还能吃饱。
1959年,粮食按上级统一规定:每人每月三十斤定粮。
到了1960年的春天,粮食短缺从农村波及城市,饥饿是每天的事。
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是这么一件事:一位18岁的小伙子走到一块玉米地时,饥饿难耐,就摘了一个生玉米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这时,被村里的干部看见了,追着他打,谁知他失足掉进了井里,打来出来时手里还握着一小块生玉米。
”“真是可怜啊!”我说。
爷爷接着说:“当时家家户户都勒紧了裤腰带度日,饥饿的恐慌威胁着每一个晓事的人。
直到1960年冬天,历经了两年多的大食堂终于解散了。
““大跃进”时,能吃饱肚子,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一件新衣服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1958年农村公共食堂是怎样兴起的

1958年下半年起,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全都拥至新开办的公共食堂就餐。
至是年底,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国达到了345万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5亿中国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为这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那么,这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如何兴起的?“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中国农民早就有农忙时集体做饭吃的习惯。
农村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后,由于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要求增加更多的劳动力投人生产。
加之农业合作社实行集体劳动,在农忙季节人手紧张时,有的农业社便开始全社集体做饭,然后统一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或在做饭的地点集体就餐,由此产。
,。
这,该社的彭德),110亩田地,颇感人手不够。
于是有人提议说,要是集体吃饭,就能出工整齐,可以多干活。
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于是,借了社员刘青芝家的一间房子,集资买了一口锅,其他社员凑了一些刀、筷、碗、瓢,办起了食堂。
这个食堂办了两季,即夏收一季,秋收一季,农忙过后,还是回各家起火。
农忙食堂是临时性的,长的个把月,短的几天、十几天。
也有少数的农忙食堂办起来后一直坚持下来变成常年食堂,湖北省京山县八区合作乡,荆门县东平乡、马平乡,都有从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办起,并一直坚持下来的食堂。
荆门县的高店乡1957年曾办起了240个农忙食堂,该乡的茶新社还办了5个常年食堂。
从合伙做饭到农忙食堂,由农忙食堂到少数常年食堂表明,农村公共食堂早在人民公社建立前就已产生,当时的确是出于群众自愿而办起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
不过,这种群众自觉自愿办起的食堂,其实质只不过是合伙做饭的相对固定化,与后来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食堂是有根本区别的。
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
不能忘却的饥荒年代

不能忘却的饥荒年代父亲说,1959年村里食堂的“大锅饭”果真越来越稀,农历九月,食堂干脆断了火。
吴永宽后来觉得,如果母亲藏的那些粮食留下来,父亲后来或许就不会死。
但村里也有人因为抗交粮食,挨打、挨斗,“最后还是个死”。
“那个时代,谁跟你讲理?”吴永宽说。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食堂关门后,农民被禁止私自开火。
谁家要被发现冒了炊烟,连锅都给端走。
直到再也搜不到粮食,村干才不再管开火的事了。
那时所谓“开火”,不过是把糠皮用石磨磨碎,弄成饽饽,填填肚子,“兑个命”。
“那东西吃下去,拉不出大便,只能用棍往外捅。
”吴围孜的一位老人说。
榆树皮也成了好东西。
村里的老榆树被一棵棵扒光了皮,树皮晒干了磨成面,“吃起来特别黏、扎嘴,有一股'青’(涩)气”。
除此之外就是野草。
在吴永宽的记忆里,村里第一个饿死的人是吴德刚,按辈分算他的堂伯父。
“他五十多岁,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放现在算是'五保户’,即使死了也无人过问。
”堂伯父死后,是几个小孩,接着是更多的男人、女人,有时候一天能死几个。
死的人多了,也就不算回事儿了,“没准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对于死亡,吴永宽总是轻描淡写。
他亲眼看到村里的孩子,坐在屋里,嘴里流“水”,身子歪着,翻个白眼,“很简单地”死了。
那时候,饿死的人已经“不像个人”,但吴永宽也不怕了。
即便轮到他的亲人,也是如此。
家中第一个饿死的,是三叔吴德才。
因为饥荒,他从湖北逃回吴围孜,却发现村里同样没得吃。
农历九月底的一天早上,吴永宽从饥饿中醒来,发现睡在身边的三叔“不动弹了”,一摸,人已经凉透了。
人人都知道村里饿死人,但没人敢往外说。
直到农历十月下旬,村里的副队长吴永冠饿极了,和一个姓李的社员一起杀了生产队的牛。
牛肉没吃多少,两人就被生产队抓住。
吴永冠被扣上“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的大帽子,又被生产队队长吴永寿带人在会议室一顿殴打。
村民们不知道剩下的牛肉被收到哪里去了,反正谁也没吃到。
1958!吃大食堂的日子!

1958!吃大食堂的日子!
回忆过去,只是要珍惜现在。
也要看到老一辈为了美好未来。
进行的大胆探索和尝试!
五八年夏秋之际,各地如火如荼,跑步前进。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只争朝夕,胜利似乎唾手可得。
那时,农村各地陆续办起了大食堂。
就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办食堂。
家里不做饭,食堂集中做饭。
社员一天三顿饭,都到食堂吃饭。
社员们家家的炊具大锅都拿去大炼钢铁了。
把自己家的粮食都交到生产队。
生产队有专门的炊事员负责做饭。
每到开饭时间,生产队的院子里,男女老少,人声鼎沸,摩肩接踵。
那时,人们的初衷是,集体做饭,可以让更多的家庭主妇,离开锅台,参加劳动。
还可以节约大量的柴草。
5
但,实际,家家各自做饭,都是用边角零碎的柴草。
而集中大锅做饭,那些零碎的就不好用了。
所以只能去大河边及山上砍树。
加上大炼钢铁,不少百年大树都被砍光了。
另外,集体办伙,人们就不再那么节约了。
浪费很严重。
另外,食堂里也出现了管理人员和做饭师傅多吃多占的问题。
开始时,因为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假象?人们放开肚皮吃。
但很快就捉襟见肘了。
最后,就开始定量了,不随便吃了,有的地方还发了大食堂票。
坚持了两三多月,粮食就没多少了。
大约秋末吧,食堂就解散了。
人们就都仍然回到自己家做饭了。
消失的记忆:1958人民公社食堂的宣传画

消失的记忆:1958人民公社食堂的宣传画
公社食堂强,饭菜做得香。
吃着心如意,生产志气扬。
以前是一家几口自家做饭吃,现在大家伙儿做到一块儿吃饭,图中一位大叔笑得很开心。
这种大锅饭虽然粗糙一些,气氛可是很愉悦的。
组织起来无限好,集体生活幸福多。
对于人民公社,估计多数人都不陌生,一些影视剧里时常提到,余华小说中也有涉及。
基本上都是一个村子里集体生活,集体劳作。
社员之家:食堂办得好,生产干劲强
人民公社好
青白菜大地瓜,俺社丰产人人夸,
今天担起食堂送,炊事员见了笑哈哈。
食堂办得好,社员干劲高-1960年
食堂办得好,生产干劲强
阿姨的好帮手
办好公共食堂,
保证所有的社员吃得饱、
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
办好公共食堂,讲究集体卫生
帮助公社办好食堂
必须算了再吃,决不能吃了再算
剥蚕豆
人民公社食堂餐票
吃饭不要钱,老少齐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
1958年10月江苏国画院
钱松岩、余彤甫、魏紫熙、宋文治、
吴俊发、徐天敏、张文俊、叶巨吾、亚明、傅抱石集体作画。
新中国最早单干村

新中国最早单干村:困难时期有余粮没饿死一人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2年3月1日第1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湖南一村庄秘密单干比小岗村早17年在“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都搞农业集体化,湖南隆回县羊古坳乡雷锋七队却一直在秘密分田单干,比号称最早开始实行单干的安徽凤阳小岗村早了17年。
冒批斗危险秘密单干1958年初,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不久国家号召大办公共食堂。
隆回县所有的村民都加入了人民公社,进了公共食堂。
可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就坐吃山空了。
到1960年冬,隆回县羊古坳乡雷锋七队的公共食堂已无米下锅,全队社员饿得几乎丧失了劳动力。
这让从部队转业回乡的刘湘庭特别痛心,他苦苦思索解决办法,认为要想走出眼前困境,只有端掉“大锅饭”。
1961年春,刘湘庭约了几个负责人召开秘密会议,准备分田到户。
这在全国都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万一暴露,就会受到批斗,甚至有坐牢的危险。
他们一家家登门逐个做工作,刘湘庭表态:“大家不要怕,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承担。
”社员们吃下定心丸,全都同意分田到户,并推选刘湘庭当生产队长。
户户有余粮没露半点破绽分田到户后,大家都是给自己干活,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为了应付公社、大队的检查,雷锋七队有自己的套路:一是有时也集体出工,互帮互助;二是收获季节,统一收割;三是照样决算报表;四是征粮统购,率先完成。
唯一与以前不同的,大家白天把自己的谷物放进集体仓库,晚上又各自挑回自家。
刘湘庭的这些谋划,恰到好处,没有露出半点分田单干的破绽。
由于全队最早完成了征粮统购任务,还受到了大队和公社的表扬。
当时,全国各地因为饥饿而死了不少人,可雷锋七队却户户有余粮,社员们的亲戚都拖儿带女上门借粮。
这一消息传出,连外地讨米度日的人都朝这里涌来。
社员们走亲戚都不拿其它礼物,只拿几升米、几斗薯米或包谷,亲戚们喜笑颜开。
1958:一个村庄的公共食堂记忆

1958:一个村庄的公共食堂记忆
党国英
【期刊名称】《《农村·农业·农民A》》
【年(卷),期】2012(000)012
【摘要】这段历史,大人物可以叫它做“一段弯路”,哲学家可以叫它做“能变好事的坏事”,但在当事农民那里,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总页数】3页(P53-55)
【作者】党国英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Q427
【相关文献】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下1958年农村公共食堂探析 [J], 郑海洋
2.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下1958年农村公共食堂探析 [J], 郑海洋;
3.一个村庄的红色记忆——记青海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双树村党支部 [J], 王冬燕;
4.一个红旗食堂——江苏吳县望亭人民公社民兵团第四营第五連公共食堂調查报告[J], 无
5.1958—1961:大办农村公共食堂始末 [J], 李春峰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食堂难忘的记忆

郁忠不 _ r带 上 一 罐炒 咸 菜 ,J j I 5 可是 自己一 周 的 晚 饭 佐餐 的佳 品 ( 每个住 校 生郁 是那 样 ,淮都带 成菜 . 有时 只是 种类不 同罢 了) 。那 时 在学 校吃 食堂 的 饭 比 家 里强 多 了 ,早 上 是 一 毛钱 的 伙 食 :两个 馒 头 ,…
建 在 吃 药 ,忌 油腻 。他 们 哪里 知 道 ,我 一 天 的饭 钱
只有 5毛 钱 ,如 果早 上奢 侈 了 ,晚 上 就 没 得 吃 了 ,
就 意 味着挨饿 ! 斗 转 星移 ,高 中三 年 很快 结 束 了 ,我 有 幸 考 上
了 中学教 师 ( 北京市在 1 9 8 5年 特 招 了一批 高 中生 ,
管 后勤 工 作 ,其 中包
好食 堂 的饭 菜 ,我 们 花 高薪 从 社 会 上聘 请 了 3名 高 级厨 师 。从 此 以后 ,老 师们 在 七 点 以前 就 能 吃 上丰 富 多彩 的早 点 ,吃 上 可 口的午 饭 。 目前 ,我 们 的食 堂 的 伙食 可 以 不 吹 牛 的 说 是 全 区教 育 系统 最 好 的 , 那 简直 是 五 星 级食 堂 ,大 师傅 们 之 所 以做 得 好 ,还 得益 于我 们 改革 开 放 以后 国 家 富裕 了 ,物 质 产 品 极
碗 米 面 粥 。我 发 明 了将 馒 头 掰 成小 块 放 到 粥 池 着 吃 的方 法 ,一 口馒 头 沾粥 , 一口炒 的咸菜 ,很 足
农村 也不 知 道哪来 那 么多 的 白薯 ,我 们 天 天吃 白薯 ,
早 、巾 、晚 顿饭 ,顿 顿 是 白薯 ,偶 尔 吃顿 玉 米 面
填。
难忘童年的酱油饭1958年喝羊汤

龙源期刊网 难忘童年的酱油饭/1958年喝羊汤作者:来源:《饮食与健康·下旬刊》2013年第06期难忘童年的酱油饭文/杨黎明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开车,家里就靠母亲一人拉扯着我们兄妹三人,还要耕种六亩多地。
为了糊口,母亲刚生完小妹就得下地干活,那时候我和大妹也正蹒跚学步。
记得妈妈每次下地干活前,都是先将我们兄妹三人送到村口的衍宗奶奶家。
由于我们家每天早饭吃得晚,因此等到中午母亲接我们回家吃午饭时也不觉得饿。
可每到夕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总是饿得慌,因此每到下午四五点钟时,衍宗奶奶总会给我们拌好酱油饭,一人一碗,吃得饱饱的。
许多年过去了,由于工作关系走南闯北,也可谓是吃遍山珍海味。
可我对酱油饭依然是情有独钟。
吃酱油饭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扎根在心底的情结。
就像一个离家的牧民对羊肉串的留恋,对草原的思念。
与其说那是—种情结,倒不如说那是一种烙印,一种烙在心坎上关于亲人、关于爱、关于家的烙印。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那就是衍宗奶奶凭什么会对我们几个无亲无故,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孩子那么好呢?思来想去,觉得只有—种解释,那就是源自她骨子里一种难能可贵的“善”的天性。
我们常常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能力报答帮助过我们的人,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也有能力付出举手之劳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哪怕只是一点点,也是对“善”的传承,对“爱”的播撒。
这也许就是对帮助过我们、爱过我们的人最好的报答,也是最美、最真诚的感恩!1958年喝羊汤文/孙方友1958年,举国上下大跃进,上千人一个大食堂,大笼蒸馍,大锅熬汤,每到开饭时候,人多为患,乱得如同一窝蜂。
那一年,我虚岁8岁,父亲在人民公社工作,分到很远的一个地方驻队。
母亲在一个社办里当工人,夜里12点才能下班。
家里只有我和弟弟。
元旦节,我们那里称为“阳历年”。
节前的时候,上头就声称要杀猪宰羊,吃好“共产主义的”第一顿饭。
因久不吃肉,我自然很盼节日快快来临。
记忆中的村办集体食堂

记忆中的村办集体食堂在我孩童时的记忆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令人心酸的大锅饭——嘻嘻嘻村办集体食堂。
1958年大炼钢铁,谁家有寸铁就是“藏个美国鬼子”,谁家烟囱冒烟就割谁的“资本主义尾巴”,村民很不情愿的把鏊子、铁锅献出来炼铁。
各家各户的粮食、炊具凑起来,吃起了大锅饭。
嘻嘻嘻村当时468口人,办了两个村集体食堂,我家吃第二食堂,在宁姓的四合院里,1958年10月合灶,1959年底散伙,村办集体食堂办了一年零两个月。
吃集体食堂,按照村里的规定,年老的,生病的,干活的,上学的,可到食堂吃饭,但只准吃不准拿。
1959年春,我在村小读一年级,放学后,我挎个草筐给生产队割草,路过食堂门口,就进去了。
当时我娘和七八个婶子大娘正在摊煎饼,我二婶揭了两张煎饼,一叠递给我让我快走。
我拿了煎饼,刚到食堂门口,同食堂管理员嘻嘻嘻碰了个正着。
“好小子,偷煎饼,放下”!我拔腿就跑,聂爷爷紧追不舍,跑出老远,眼看追上抓我,我把草筐一扔撒腿直跑,哪知草筐在聂爷爷腿下打了转儿,聂爷爷摔倒了,两个膝盖磕破了,鲜血顺着腿淌。
我站在远处大声气聂爷爷:“老头头,活该,活该,活该。
”聂爷爷没说什么,一瘸一瘸回到了食堂。
偷社会主义的煎饼,那还了得,吓得我晚上没去食堂吃饭,没想到聂爷爷对谁也没说,第二天早饭,我没敢去食堂,聂爷爷亲自去我家叫我去食堂吃了饭。
如今,聂爷爷已过世多年,在此,我向九泉之下的聂爷爷说声对不起。
236口人吃饭,十几个做饭的紧忙活。
人多无好饭,菜是少油无盐的大锅菜,饭是煮地瓜、地瓜面煎饼和地瓜面窝窝,至于玉米吗,当细粮,很少吃,十天半月喝顿糊糊就挺知足了。
吃煎饼得磨糊子,那年代没有磨糊机,天天用牛拉磨磨糊。
俺队喂了16头牛,最老实的是那头花母牛,它温顺,不骄不傲,不踢不叫,从早到晚,拉着磨一圈一圈的转啊转,累的满身是汗,眼里噙着泪,鼻孔喘着粗气。
那年,四月的一天,它倒在了磨道里,再也没起来,消息传出,像塌了天,全队人都来了,挤满了院子,那年代牛是农民的宝贝,宰杀耕牛是要坐牢的,我爷爷是饲养员,他哭了,心疼的说:“吃柿子专挑软的捏,蹄跳溜猴的谁也不愿意牵,谁也不敢使,16头牛就数花母牛老实顺当,这不,累死了,你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
过往轶事(二十)1958年,经历了集体大食堂

过往轶事(二十)1958年,经历了集体大食堂1958年夏天,公共集体食堂席卷中国大地。
大办公共食堂,是对“吃饭不要钱”这一共产主义新的生产生活模式向往。
这是一种集体生活模式,是共产主义分配的性质。
要求社员“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话集体化”。
就是社员们大家在指定的范围内吃饭。
也是吃“大锅饭”,食堂有专职人员管理,有炊事班。
我们自然村的实施公共食堂化,是在58年9月,村子人口数约二百人,五十来户左右。
食堂的选择地点,位于村子中心,一幢五集房和一幢三集房。
三名房屋主人将房子腾空,搬往邻居家居住。
房子搬空清理后,大队干部指挥各家各户搬来类似八仙桌的三十多条桌子进行摆放。
大食堂的厨房和管理仑库也安排在紧邻的农户家中。
很快,大食堂开张,人们齐聚食堂,心里都充满着喜悦。
妇女们感到再也不用为吃饭、柴米油盐忧愁,可以一心一意出工搞生产。
大队通知所有社员将自留地收归集体,把社员家庭的粮食蔬菜收归大食堂。
大食堂就在此一片浓浓的喜悦激情中开始运行。
大食堂时期,也是大炼钢铁时期,笔者正在读初一,学校距家中约30里,每逢星期六下午从校步行返回,这次回到家中,已是吃大食堂了,变化之快,令人吃惊。
食堂实行军事化管理,到点敲钟吃饭、上工、收工。
此钟非钟,为一尺多长的旧钢轨。
到开饭时间,男女老少,人声鼎沸,大食堂甚是热闹,大嗓门,小孩的叫喊嬉戏,闹哄哄的一片。
人口多的家庭刚好坐一桌,人口少的两户合一桌。
到点开饭的钟声一敲,人们从四面八方争先恐后赶来,晚了就只剩残羹剩饭了。
这就造成了没干完的活儿,那怕是余下一丁点事没干完,也会丢下先吃饭去。
食堂常发生早吃的吃饱了走了,后到的嚷嚷着没吃饱,食堂只得重新做。
58年,浮夸风盛行,虚报多报粮食产量,造成粮食丰余假像,刚开始,人们尽量吃,但几个月后,就捉襟见肘了。
59年,粮食紧张开始显现。
大队干部决定分饭吃,按人口多少分给一定的数量。
这种大食堂的管理模式,成了坐吃山空,越办越穷,难以为继,连日常的开支也难以调集。
向农民致敬——农民之苦系列纪实(6):吃饭琐忆

向农民致敬——农民之苦系列纪实(6):吃饭琐忆我和共和国同龄,能记事起印象最深的就是吃饭,毕竟民以食为天!1958年农民大食堂开办起来了,一开始大人小孩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从此家家户户不用做饭,只要时辰一到,人人可去大食堂。
大食堂围墙上写着鲜红的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开始,吃饭是免费的,管饱,餐厅的墙壁上,写着:''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子吃饱饭''。
但我因人小,当时生产的劲鼓得怎么样不清楚,只记得很多农民伯伯叔叔被抽去大炼钢铁,还不时传来某地粮食产量突破万斤甚至十万斤的好消息,墙上宣传画上的猪,背上能坐好几个农民,他们种出的南瓜,大得一车只能装一个。
学校教我们唱起''星期六,乘火箭,大卫星飞上天,跃进跃进再跃进,共产主义万万年''的歌。
我们情绪高昂地唱着,可食堂的饭却慢慢地不能放开肚子吃了。
先是早晚改成了吃粥,且粥越来越稀,中午饭也越来越软(为提高米的成饭率多加了水)。
再后来,开始对每个人发饭票定量供应了。
由于定量很低,一段时间后饥饿开始惩罚起了人们,餐厅内吵架声不断,食堂掌勺者打饭时勺子的满浅,菜汤的多少,往往成了纠纷的导火索。
为解决这一问题,不久后上面规定食堂一律采用定量陶罐(老秤十六两制),分四两的、六两的、八两的三种。
再后来,食堂里的主粮食物也越来越少,每个人的饭票,只有一半能买到主粮食物,另一半只能买到红薯、青菜,……那时我亲眼看到过老师在上午最后一节课,饿得扶着讲台吐黄水。
而我们一放学,就一窝蜂冲向食堂,叫着:冲、冲、冲,读书装头疼,吃饭打先锋!当年我虽是小孩,但母亲因要下田劳动,吃饭的时间与我们放学不一致,因此把十天的饭票,都提前由我自己保管,那时的小孩,因久饿而营养不良,都精瘦精瘦的,印象中也没有啤酒肚的大人。
饿极了的我,老秤的四量饭只拳头大一块,还没吃出味就已下肚了,实在嘴馋,忍不住就寅吃卯粮起来,最后两天没饭票了,就瞒着大人上山吃野果。
我所亲历的农村“食堂化”

我所亲历的农村“食堂化”王贵堂一、“食堂化” 的兴起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国陆续出现前所未有的新鲜事,掀起了“食堂化”高潮。
食堂化旨在打破千年来一家一户各自为炊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而变革为一个生产队、几个生产队、抑或一个自然村建立一个食堂,以达到解放每户家庭妇女做饭,全部投入生产劳动及“一大二公”的目的。
食堂化这一新生事物刚一露头就象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次第出现。
当时我村不到400口人就有4个食堂,每个小队一个,先后在福保、双明、虎儿家院以及圪垯院都扎过食堂,最后只留一个食堂时是在旗杆院。
每到开饭时间,男女老幼都到食堂去进餐,饭后拿着碗筷回家去,连锅都不用刷洗,确实令人悠悠自乐。
1958年我6岁,刚懵懂记事。
当年风调雨顺,粮食大获丰收,只知道多数社员投入到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和农业机械化中,入冬时很多粮食都被埋在雪地里,有坛镇中学的学生前来帮助秋收。
食堂开始几个月还可以,吃饭不定量,来客不记账。
但进入1959年各村均感到库存空虚,粮食不足,于是不得不改弦易辙,变不定量为按人定量,变顿顿吃干为有稀有干,并实行小粮票制度。
每月初按人定量,发给各户一个月的小粮票,每日凭票打饭,吃多吃少自己掌握。
每到开饭时,社员们端盆拎罐,到食堂去打饭,有的在食堂院里吃,有的拿回家里吃。
社员们由于没有自留地,既无淹菜,又无干菜,只能吃从食堂领回的熟饭,尽管每日人均能吃到一斤粗粮,却仍然难以吃饱吃好,遂不免产生了饥饿的感觉。
后来总因粮食缺乏,以致不少社员家仅半个月就用完一个月的小粮票。
粮票紧张,群众饥饿,干部们就想了各种办法,红薯就是这个时候大力推广栽种的。
1959年,农业生产虽然减产不很严重,但因各级虚报产量导至多交了公粮,粮食难以成为公共食堂的坚强后盾。
跨入1960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干旱,社员口粮每日仅能吃到五六两,形势愈加严峻。
二、千方百计寻找食物食堂化时社员家中是不允许存放粮食的,晚上看见谁家烟囱冒烟就去看是否在做饭,紧接着村干部就来检查了。
1958年中国贫困生活的描写

1958年中国贫困生活的描写
我的老家在浙江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到大我常常听父亲讲50年代尾至60年代饥荒年的事,他说野菜、树皮、米糠……他都吃过。
还讲了什么东西难以下咽,什么东西勉强能吃。
我各举两个例子,父亲说米糠饼难以下咽,有时卡的喉咙很痛,那时农村没机器碾米的,米糠可能粗一点,吃了屎都拉不出来。
还有洋槐树的叶子特别难吃,难以下咽。
他说那时芭蕉芋一身都是宝,它的根、叶、花、结的芋都可以吃,容易下咽。
还有苎麻的叶子也容易下咽。
父亲说那时附近的草根挖得都没有了,要挖也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挖。
那时我们村饿死了好多个人。
他说有的地方不要吃草根,有米和番薯吃,我们村里有的人就去那个地方要饭。
这些事情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不相信,特别是年轻人。
每当想起父亲跟我说饥荒年的事,我就感到很心酸,唏嘘不已。
跟老一辈比,我们现在的生活多幸福!多美满和安稳!特别是年轻人,一定要好好珍惜美好的生活,努力工作。
五九年吃食堂

五九年吃食堂五九年吃食堂时,我仅七岁,但记忆深刻,印象鲜明。
食堂设在生产队的队部大院里,是没收地主的宅院。
原来的五间西厢房被改造成了厨房,一间炒菜,一间蒸饭,一间烧汤,余下两间是储藏室。
厨房里有十几个妇女在里面操作,领头兼掌菜勺的是生产队长的老婆。
当时农村不用煤炭,全靠烧柴禾。
麦稭、高梁秆,杂草火势弱,全靠烧木头,队长就领着一帮人到各家各户搜集,没有就把人家的杌子、凳子劈了当柴烧,再后来就砍伐各户的树。
主食先是大人一顿四两、小孩一顿二两(当时一斤是十六两)白面卷子,后来换成粗面的,再后来变成地瓜面黑窝窝头,再再后来就变成了煮地瓜,煮胡萝卜,煮双瓜,炒棉种。
菜一开始有肉炒辣椒,或肉烩白菜、萝卜,后来就光有开水煮白菜、萝卜、苤蓝,再后来就光有咸菜条,再再后来就没有什么菜了,也没有什么汤了。
吃饭都是排队,领完饭再去排队打菜,再排队打面汤水,为了节省时间,我家三口人,分三个地方排队,母亲打汤,妹妹领主食,我端着个黢黑的大瓷碗领菜。
队长老婆掌菜勺,每次队长老婆给我打菜,有肉时专拣青菜舀,没肉时就少给。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跟她吵起来,老娘踹了我一脚,慌忙给队长老婆陪礼。
回家后,老娘给我擦去脸上的泪水,安慰我说:“傻孩子,你爸在外地工作,队长老婆是欺负咱是妇女小孩,少吃点饿不死。
”后来没有了粮,没有了菜,连烧火的木柴也没有了,食堂就只得散伙,各回各家,各吃各的。
吃大食堂吃大食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未的事,现在还有印象。
记得当时强调一大二公,走集体化道路,为了把妇女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从事集体劳动和公务活动,便成立了公共食堂。
在王家大院南侧的几间房子里,一帮人合伙做饭,有男有女,蒸窝窝头,烧菜汤,有时也有炒菜。
人们从家里拿着篮子、盆罐去食堂打饭菜,带回家一起吃。
开始伙食还可以,慢慢就不行了,饭菜质量也越来越差。
主要是没有主粮,也没有备菜,存下的东西都吃光了。
一九五八年确实是丰产年,但实际收成并不好,那年种的地瓜多,也长得好,但收获时用犁耕收,地皮上的捡了起来,土中的就大都不管了,浪费了不少。
“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始末

“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始末
沈家善
【期刊名称】《档案与社会》
【年(卷),期】2007(000)001
【摘要】普遍兴办农村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产物,是
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左”倾思想不断发展的结果。
1957年底、1958年春,由于党内不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使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的思想开始滋长。
在农业战线上,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当时片面地认为高级社的规模已不适应大办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
党中央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
【总页数】2页(P12-13)
【作者】沈家善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323.8
【相关文献】
1."大跃进"时期河北公共食堂始末 [J], 李春峰
2."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兴衰之历史考察 [J], 陈仁涛;陈仙君
3.试析"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兴起——以徐水县为例 [J], 李海滨;刘长亮
4."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研究综述 [J], 高寒
5."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兴衰之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J], 陈仁涛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1958:一个村庄的食堂记忆来源:南方周末2007年9月27日撰文:党国英参与调查人:曹子坚、魏巍、贾云鹏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
当今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
我和旅美经济学家文贯中先生曾谈起这件事情。
他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认为我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与公共食堂有密切关系。
其他学者也有一些别的看法。
我也听到过少许年轻学子的看法,认为1958年的制度剧变是我们过去一系列光辉业绩的一部分。
公共食堂兴办过程其实有两个阶段,先是不让所有人民公社社员家里做饭吃,而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后来因为粮食发生了问题,就限量供饭。
不同地方的粮食状况不一样,这两个阶段的时间界限也不同。
究竟公共食堂的兴办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也想搞清楚。
今年8月,我和兰州大学的几位师生到华北一个村庄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访问了一些年长的村民,也在县档案馆查阅了一些历史档案。
办食堂前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北村庄,坐落在河北省的南端。
村庄的东边就是古卫运河的河道,一些老人还记得当年河水充盈,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了。
但这条河流上的漕运孕育了这里的粮食贸易传统,使这块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这里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
有老农说,现在一户农家的粮食产量抵得上那时半个村庄的粮食产量。
1958年,政治形势早已稳定,但当时的农业科技还没有明显进步。
从官方资料看,当时小麦平均亩产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红薯平均1600斤。
粮食紧缺,农民想了一个办法,用麦子换高粱。
兑换的比例令我惊奇,一斗高粱能换一斗二升麦子!为什么这样不合理?老农解释说,因为高粱难吃,人吃得少,就能节省粮食!一位已经七十多岁的地主的后代告诉我,他的爷爷在家里吃饭最受优待,但每年也就能吃到几次白面馒头。
粗粮是他们的主食。
地主家尚且如此,其他农户家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改革开放前,日子最好过的是1953年—1955年,农民这样回忆说。
生活改善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横行乡里的土匪流寇被消灭,社会安定了,农民得以安心生产。
土改前,这个村庄几乎所有的“贫农”都有土地,少则五六亩,多则十几亩;两户地主家的土地多一些,但他们人口也多。
面对土匪流寇,地主的命运比少地的农民好不了多少,他们也不愿意多置地产。
总体看,这里没有明显的土地占有上的两极分化。
中国旧时代的匪患对农民的影响,常常甚于阶级分化的影响,这与后来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情形很不相同。
随着合作化运动开始,农民的生活水平开始降低。
土地瘠薄,没有劳动者的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必然下降。
农民说,玉米从播种到收获,要锄8遍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监督这样的劳动是非常困难的。
从1957年开始,政府就号召提高农产品产量,干部组织生产队大量种植地瓜(红薯),粮食种得少了。
没有可靠资料表明1957年全县究竟种了多少地瓜,但1958年的情况比较清楚。
这年全县种棉花24万亩,种粮食作物50万亩,其中地瓜竟达38万亩(春地瓜10万亩,秋地瓜28万亩)!这种农作物播种的指令性计划严重背离了当地的农业传统(历史上这里种红薯的土地面积只占总面积的2%左右)。
从农民的回忆以及全县的一般情况推断,这个村大部分土地也种了红薯。
1958年春天,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开始执行。
先做的事情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
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30斤左右的粮食。
多的也不过二三百斤,这样的户数有三四户,所以收到的粮食吃不了多久。
当时的会计现在七十多岁了,他回忆,干部从他家里拿走十几斤黄豆,七八斤带皮谷子,还有红薯干三四十斤,黑南瓜二百多斤。
他还说,1957年的时候,农民每家每天也就吃3两粮食。
成人吃稀的,学生和老人吃稠的公共食堂刚开始办的时候,是放开肚皮吃,但因为粮食很少,也就不敢精米精面地吃。
成人吃的饭是粮食与地瓜干混合煮的饭,比较稀。
儿童在幼儿园有专人看管,是为了让妇女有更多的时间下地干活。
干部们做了一个决策,给儿童、小学生和老人吃稠一点的饭,大家都没有意见。
很快,粮食就吃完了。
年长村民们的记忆也不太清楚,有的说放开肚皮吃的时间有一个月,还有的说只有大约20天。
再后来地瓜干也没有多少了,就开始吃夏天地里新产出的东西,主要是胡萝卜。
这种没有热量的东西不顶饱,大家都很能吃,于是也就不敢放开肚皮吃了。
全村办了四个食堂,后来合为两个。
每个食堂又分成几口锅,全村13口锅,分别支在不同的农户家里。
所有农家大体分成13份,被分配到每口锅上吃饭。
食堂设有事务长,每天将做饭的原料分给每一口锅上做饭的妇女。
我问村民:食物这样短缺,事务长和锅上的炊事员会不会多吃多占?村民说,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
那时,一碗饭和生死联系在一起,谁也没有那个胆量多吃多占。
公共食堂到底办了多长时间?几位年老的村民也记不准确了。
他们大体记得,到1959年春节,村里给每一家分了一点面粉过年,村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年饭。
过完年后又继续吃食堂,实在没有吃的了,时间不长就散伙了。
公共食堂的这种情形,自然不能为村民提供起码的营养水平。
会不会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回答这个问题颇让村民们犯难。
体弱多病的人加上营养不良,自然容易死亡,但很难说他们是饿死的。
为什么躲不过1958年?大多数村民不喜欢在公共食堂吃饭。
干部们有两个办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
第一个办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粮食悉数收走。
也有胆子大的农民偷藏粮食,但这种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经常召开的斗争会上,村民对私藏粮食的人拳打脚踢,没有多少人能扛得住。
有老人回忆,有的村民私藏粮食后又害怕起来,便半夜三更把粮食偷偷地倒在野地里,以免干部们再来家里搜出粮食。
命之所系的粮食就这样被糟蹋了。
第二个办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铁锅,让农民在家里不能做饭。
1958年,这里也搞“大炼钢铁”,每家农户的铁锅都被收走,成了炼钢的原料。
办了公共食堂,铁锅还有什么用!这是收走铁锅的理由。
可是,胆大的村民还要在家里做饭吃,或者吃自家私藏的粮食,或者偷集体地里的地瓜、萝卜吃。
没有铁锅怎么办?用沙锅来代替。
那时沙锅卖得好了。
家里做饭要烧火,但不能冒烟,以免被干部发现。
有点钱的人可以用木炭解决问题,穷人就在晚上做饭,还要防止烟气跑到户外。
饥饿难耐,敢不敢跑出村外要饭吃?一般不敢。
人民公社运动是全国性的,跑出去要饭很容易被逮着,还会被看作抗拒社会主义的懒汉,要接受斗争。
但据我了解,这样对农民的紧密控制并不是全国性的。
至少在陕北,这种控制并不紧密。
在乡里乡亲之间,干部们执行大家所厌恶的政策,能下得了手么?农民们不能集体抗拒么?当代人也许对此很难理解。
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代人能做的是解释它,而不是否认它。
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受村民欢迎的好人,他从战争年代就开始做党的基层领导。
1958年他吃了一个大亏。
这年,上级政府号召提高播种密度,用三条腿的耧来播种,但这位书记不相信这个办法能增产,坚持用传统的两腿耧播种。
就这样一件事情,他遭到了“拔白旗”的命运,上了斗争会的板凳,并被斗争者踢下了板凳。
干部不听话尚且会遭受严厉处罚,其他农民自然会害怕的。
不过,换个角度看,农民们也是比较“自觉”的。
政府要办公共食堂,大家也就办了;多数农民也乖乖地交出了粮食。
政府又允许停办公共食堂,大家就回家吃饭去了。
华北的农民自古以来就饱受战争的蹂躏,学会了在忍辱负重中生存的本领。
日本人侵占华北,但真正面对老百姓的是“皇协军”,日本人忙着对国共军队作战。
“皇协军”也想让地方秩序安定下来,偶尔会敲打一下地方恶势力,但总体上那是一个官匪勾结、民不聊生的时代。
土匪喜欢华北平原。
在这里,家家总有一些粮食,小农户也没有武装手段对抗土匪。
而土匪在平原地区又有很好的机动性。
农民对付匪患的一个办法是“装穷”。
他们本来就穷,但要装得更穷。
哪家农民的生活如果稍显富裕,立刻就有村里的“地勾子”报告给土匪,这家人就要遭殃了。
敢于多购置土地当地主的农户必然是人丁兴旺的农户,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对抗土匪,人均占有土地也不多,实际生活水平也不高。
即使如此,地主家的人还有可能做土匪的人质。
在这块土地上,并没有很大的地主,地权分配比较平均。
按我们的调查,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不到1%。
有人拿西北山区农民和华北平原的农民做了一个比较,发现西北山区农民从房屋建造到室内中堂布置,都显示出某种文化气息,而华北平原的农民则似乎过着一种没有任何文化含量的生活,全部生活围绕一个字——吃。
原来这是农民的一种十分无奈的生活方式选择。
农民靠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贫穷与琐屑,换得了活命的机会。
当人只顾得活命的时候,就只能与所谓文化相揖别。
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
在这里,有一种掠夺性的制度在农民内部建立起来了。
农户家家都可能做“地勾子”,于是就没有谁敢在家里藏粮食。
当大家都希望从别人家里掏出更多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时,就都逃不过饥饿的命运了。
大家都真正穷了,就不用装穷了。
而每一个人都穷了以后,人们也就不用再和谁去对抗了,因为对抗已经不能换来任何利益。
这个制度的好坏实际上是一个“皇帝新衣”的故事,它的始作俑者和实施者都知道这个制度必须终结。
但制度的惯性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历史事变,使这个制度的直接危害竟延续数年之久。
这段历史,大人物可以叫它做“一段弯路”,哲学家可以叫它做“能变好事的坏事”,但在当事农民那里,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