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中的虞姬看女性之存在-2019年精选文档
《史记》中的女性形象

《史记》中的女性形象引言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书籍中,《史记》被视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史书。
编纂者司马迁以其卓越的才华和严谨的史学方法,将中国历史分为了一百三十篇,记录了从黄帝到西汉武帝刘彻时期的历史。
然而,《史记》中的主要角色几乎都是男性,女性形象往往只有若干次的提及。
本文将探讨《史记》中的女性形象,探索其中的原因和影响。
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古代社会的男尊女卑观念古代中国社会深受男尊女卑的观念影响,这种观念认为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具有更高的地位和权力,而女性则应处于从属地位。
这种观念从晚周时期开始逐渐形成,不仅在家庭关系中存在,也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
《史记》中的男尊女卑观念这种男尊女卑观念也在《史记》中得到体现。
许多文章中,女性被描绘成软弱、贤良和顺从的形象,而男性则被赞扬为英勇、智慧和有能力领导的形象。
这种偏见在《史记》中反映出了古代社会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
《史记》中的典型女性形象贤妻良母的形象在《史记》中,女性形象主要被描述为贤妻良母。
例如,司马迁在记载项羽和虞姬的故事时,虽然虞姬被描绘成了一个聪明美丽的女人,但她最终还是屈从于爱情,选择了自杀。
这种描写强调了女性在古代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即她们的命运和幸福完全取决于男性。
聪明智慧的女性形象然而,《史记》中也存在一些聪明智慧的女性形象。
例如,文姜和吕不韦是两个在政治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女性角色。
她们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机智,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争取了利益。
这些女性形象展示了女性在古代社会中也能发挥积极作用的一面,但她们的形象仍然是少数。
女性形象缺失的可能原因男性史学家和史书编写者的视角《史记》的编写者是司马迁,一个男性史学家。
从他的角度来看,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主要是男性。
因此,女性在《史记》中的形象往往被忽略或较少被提及。
同时,古代中国的编写史书的传统是由男性主导的,这也导致了女性形象的缺失。
社会地位的限制古代中国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她们的社会角色主要是贤妻良母。
试论《史记》中的女性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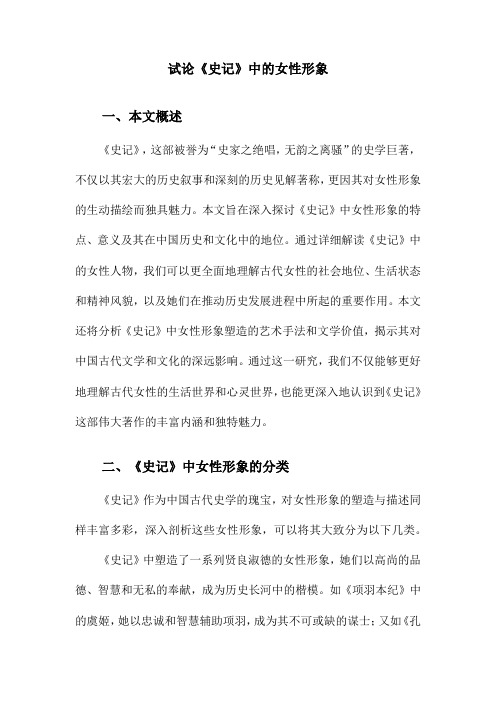
试论《史记》中的女性形象一、本文概述《史记》,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不仅以其宏大的历史叙事和深刻的历史见解著称,更因其对女性形象的生动描绘而独具魅力。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史记》中女性形象的特点、意义及其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
通过详细解读《史记》中的女性人物,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以及她们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本文还将分析《史记》中女性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法和文学价值,揭示其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深远影响。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女性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也能更深入地认识到《史记》这部伟大著作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
二、《史记》中女性形象的分类《史记》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瑰宝,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与描述同样丰富多彩,深入剖析这些女性形象,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史记》中塑造了一系列贤良淑德的女性形象,她们以高尚的品德、智慧和无私的奉献,成为历史长河中的楷模。
如《项羽本纪》中的虞姬,她以忠诚和智慧辅助项羽,成为其不可或缺的谋士;又如《孔子世家》中的南子,她以其高尚的品德和睿智的见解,为孔子的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在《史记》中,也有许多英勇善战的女性形象,她们在战场上展现出与男性同样甚至更为出色的战斗能力。
如《淮阴侯列传》中的吕后,她以果断和勇敢的军事决策,为汉朝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又如《田单列传》中的田单之母,她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带领家族抵御外敌,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
《史记》中还塑造了一些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命运多舛,遭遇种种不幸,但却以坚韧和勇敢面对困境,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敬意。
如《孝武本纪》中的钩弋夫人,她因政治斗争而被迫自尽,留下了悲惨的结局;又如《刺客列传》中的豫让之妻,她在丈夫离世后独自承担家庭重担,展现出了女性的坚强和勇敢。
在《史记》中,也有一些被描绘为妖艳惑众的女性形象,她们或因美貌而引发纷争,或因权谋而扰乱朝纲。
历史趣谈:历史上的虞姬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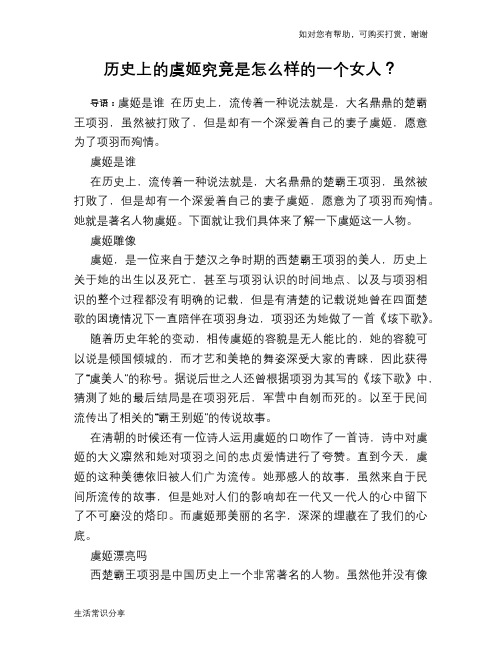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历史上的虞姬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
导语:虞姬是谁在历史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大名鼎鼎的楚霸王项羽,虽然被打败了,但是却有一个深爱着自己的妻子虞姬,愿意为了项羽而殉情。
虞姬是谁
在历史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大名鼎鼎的楚霸王项羽,虽然被打败了,但是却有一个深爱着自己的妻子虞姬,愿意为了项羽而殉情。
她就是著名人物虞姬。
下面就让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虞姬这一人物。
虞姬雕像
虞姬,是一位来自于楚汉之争时期的西楚霸王项羽的美人,历史上关于她的出生以及死亡,甚至与项羽认识的时间地点、以及与项羽相识的整个过程都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有清楚的记载说她曾在四面楚歌的困境情况下一直陪伴在项羽身边,项羽还为她做了一首《垓下歌》。
随着历史年轮的变动,相传虞姬的容貌是无人能比的,她的容貌可以说是倾国倾城的,而才艺和美艳的舞姿深受大家的青睐,因此获得了“虞美人”的称号。
据说后世之人还曾根据项羽为其写的《垓下歌》中,猜测了她的最后结局是在项羽死后,军营中自刎而死的。
以至于民间流传出了相关的“霸王别姬”的传说故事。
在清朝的时候还有一位诗人运用虞姬的口吻作了一首诗,诗中对虞姬的大义凛然和她对项羽之间的忠贞爱情进行了夸赞。
直到今天,虞姬的这种美德依旧被人们广为流传。
她那感人的故事,虽然来自于民间所流传的故事,但是她对人们的影响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没的烙印。
而虞姬那美丽的名字,深深的埋藏在了我们的心底。
虞姬漂亮吗
生活常识分享。
史记女性故事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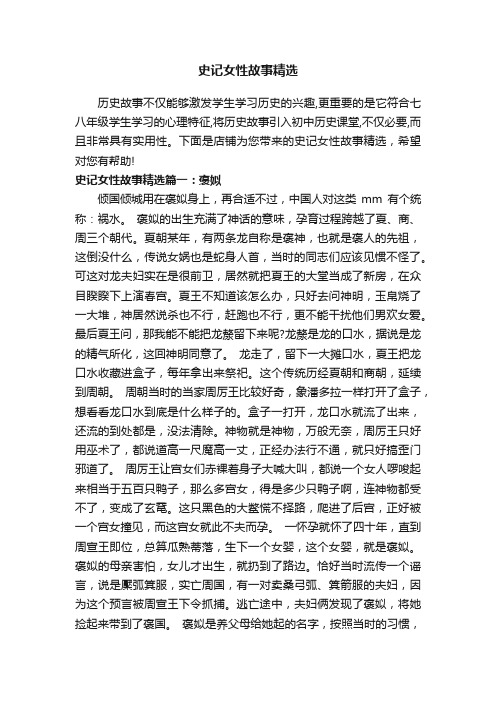
史记女性故事精选历史故事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它符合七八年级学生学习的心理特征,将历史故事引入初中历史课堂,不仅必要,而且非常具有实用性。
下面是店铺为您带来的史记女性故事精选,希望对您有帮助!史记女性故事精选篇一:褒姒倾国倾城用在褒姒身上,再合适不过,中国人对这类mm有个统称:祸水。
褒姒的出生充满了神话的意味,孕育过程跨越了夏、商、周三个朝代。
夏朝某年,有两条龙自称是褒神,也就是褒人的先祖,这倒没什么,传说女娲也是蛇身人首,当时的同志们应该见惯不怪了。
可这对龙夫妇实在是很前卫,居然就把夏王的大堂当成了新房,在众目睽睽下上演春宫。
夏王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去问神明,玉帛烧了一大堆,神居然说杀也不行,赶跑也不行,更不能干扰他们男欢女爱。
最后夏王问,那我能不能把龙漦留下来呢?龙漦是龙的口水,据说是龙的精气所化,这回神明同意了。
龙走了,留下一大摊口水,夏王把龙口水收藏进盒子,每年拿出来祭祀。
这个传统历经夏朝和商朝,延续到周朝。
周朝当时的当家周厉王比较好奇,象潘多拉一样打开了盒子,想看看龙口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盒子一打开,龙口水就流了出来,还流的到处都是,没法清除。
神物就是神物,万般无奈,周厉王只好用巫术了,都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经办法行不通,就只好搞歪门邪道了。
周厉王让宫女们赤裸着身子大喊大叫,都说一个女人啰唆起来相当于五百只鸭子,那么多宫女,得是多少只鸭子啊,连神物都受不了,变成了玄鼋。
这只黑色的大鳖慌不择路,爬进了后宫,正好被一个宫女撞见,而这宫女就此不夫而孕。
一怀孕就怀了四十年,直到周宣王即位,总算瓜熟蒂落,生下一个女婴,这个女婴,就是褒姒。
褒姒的母亲害怕,女儿才出生,就扔到了路边。
恰好当时流传一个谣言,说是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有一对卖桑弓弧、箕箭服的夫妇,因为这个预言被周宣王下令抓捕。
逃亡途中,夫妇俩发现了褒姒,将她捡起来带到了褒国。
褒姒是养父母给她起的名字,按照当时的习惯,不是姓褒名姒,而是姓姒名褒。
《史记》十二本纪中女性形象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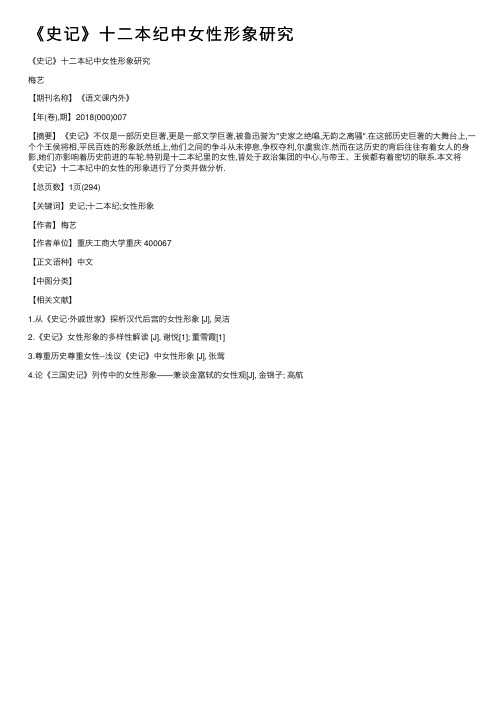
《史记》⼗⼆本纪中⼥性形象研究
《史记》⼗⼆本纪中⼥性形象研究
梅艺
【期刊名称】《语⽂课内外》
【年(卷),期】2018(000)007
【摘要】《史记》不仅是⼀部历史巨著,更是⼀部⽂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韵之离骚".在这部历史巨著的⼤舞台上,⼀个个王侯将相,平民百姓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之间的争⽃从未停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然⽽在这历史的背后往往有着⼥⼈的⾝影,她们亦影响着历史前进的车轮.特别是⼗⼆本纪⾥的⼥性,皆处于政治集团的中⼼,与帝王、王侯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本⽂将《史记》⼗⼆本纪中的⼥性的形象进⾏了分类并做分析.
【总页数】1页(294)
【关键词】史记;⼗⼆本纪;⼥性形象
【作者】梅艺
【作者单位】重庆⼯商⼤学重庆 400067
【正⽂语种】中⽂
【中图分类】
【相关⽂献】
1.从《史记·外戚世家》探析汉代后宫的⼥性形象 [J], 吴洁
2.《史记》⼥性形象的多样性解读 [J], 谢悦[1]; 董雪霞[1]
3.尊重历史尊重⼥性--浅议《史记》中⼥性形象 [J], 张莺
4.论《三国史记》列传中的⼥性形象——兼谈⾦富轼的⼥性观[J], ⾦锦⼦; ⾼航。
《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解析

《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解析《史记》是中国少数传世的史学著作,也是具有传统家风和传统历史观念的典籍之一。
作为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史记》所记述的是大量有关古代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历史现象的内容,其中包括叙述传统社会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和社会地位。
本文以《史记》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从历史、文化、家庭、仪式等角度,对古代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地位进行深入研究和解析,力图从历史角度出发,更深刻地理解并批判性思考古代女性的角色和社会地位。
首先,《史记》中的女性形象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
在古代,妇女的地位无疑低于男性,从封建社会开始,妇女便被视为家庭的“实际拥有权”,被期待成为一个贞洁、懂家务和可靠的妻子和母亲。
而《史记》中的女性形象也体现了这一点,如《贞观开元年间》中的成吉思汗与李元吉的妻子马袁氏,她在家中负责管家的事情,虽然勇敢可喜,但无法脱离贤德夫人的角色定位。
除此之外,《史记》中的女性形象也体现了古代女性的文化视野。
随着社会的发展,部分女性的心智有了发展,变得更有自立能力,如嫁给陆续仗着的小公主蔡侍御,尽管她拥有智慧和勤勉,但仍受到家庭礼仪和家庭规矩的约束。
此外,《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还反映了古代女性在宗教和仪式方面的地位。
在古代,女性被期望参与宗教活动,参加祭礼,台阶和战斗。
《史记》中便有大量关于女性参与仪式活动的内容,如《陈涉世家》中的丝带,描述了一位聪明勤勉的女士参加礼祭,给左慈大一个礼物,成就了一个重大的仪式。
此外,《史记》中还有大量关于贤德夫人受尊敬的内容,说明了古代女性在宗教、仪式和战争方面也有所作为。
最后,《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还可以反映出古代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
古代家庭男性主导,妇女有被动的角色定位,从婚姻的概念中也可以看出,妇女有被动的角色定位,即女性有责任遵守丈夫的家庭规矩,保护家庭次序不受破坏,并听从丈夫命令。
而《史记》中的女性形象也彰显了这一点,例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的妻子陈王氏,她一直被项羽的言行控制,没有自主的空间,无法改变被动的角色定位。
【荐精品文】历史上的虞姬

【荐精品文】历史上的虞姬
虞姬,秦朝末年的著名女性人物之一,人称“虞美人”。
今沭阳县(沭阳,隶属江苏省宿迁市,因位于沭河之阳而得名)颜集乡人,一说绍兴县漓渚镇塔石村人。
据《江西吉安庐陵项氏家谱》记载:虞后生时五凤鸣于宅,异香闻于庭,生于丁丑(公元前224年)卒己亥(公元前202年),葬彭城。
嫁与项羽
按《史记》、《资治通鉴》载,项梁杀人避祸携项羽由下相奔吴中,即今日苏州地。
虞氏为会稽郡(秦末置春秋吴、越地域为会稽郡,以吴(今苏州)为郡治)吴中望族。
项梁叔侄在此结交江东子弟。
虞姬,吴中虞氏美女(估计也是当地贵族)慕项羽英名,嫁与项羽为妻,陪伴左右。
抑或可以说是项羽有幸淂识虞姬,得此佳人,共谱华章。
随项羽出征
虞姬常随项羽出征。
楚汉相争后期,项羽趋于败局,于公元前202年,被汉军围困垓下兵少粮尽,夜闻四面楚歌,哀大势已去,面对虞姬,在营帐中酌酒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词苍凉悲壮,情思缱绻悱恻,史称《垓下歌》。
断项羽后顾之私情
此际,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竟也流露出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哀叹。
随侍在侧的虞姬,怆然拔剑起舞,并以歌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歌罢自刎,以断项羽后顾之私情,激项羽奋战之斗志,希冀胜利突围。
死后葬于垓下.。
古代著名美女虞姬生平简介

古代著名美女虞姬生平简介虞姬是楚汉时期霸王项羽的爱妾,古代有名的美女之一。
下面是店铺为你收集整理的虞姬生平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虞姬生平简介虞姬,西楚霸王项羽的姬妾,其生卒年、出生地以及她的结局都没有文史详细记载。
但相传虞姬容姿绝色,舞姿美艳,才艺双全,深得项羽的宠爱,有“虞美人”之称。
项羽与刘邦历时四年的楚汉之争,最终趋于失败,垓下之战中,项羽因后方补给不足,又四面楚歌,而陷入困境。
项羽知自己大势已去,唯有放不下虞姬,悲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此歌名曰《垓下歌》。
虞姬随侍在旁,听后拔剑起舞,和道:“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此歌后称《和垓下歌》,虞姬唱完后提剑自刎。
虞姬的结局在史书上并没有详细记载,在楚营中自刎也只是后人根据《垓下歌》与《和垓下歌》臆想出来的,但“霸王别姬”的故事还是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来。
虞姬故里作为一个传奇般的女子,虞姬不仅容貌惊为天人,而且拥有美妙的歌声和轻盈灵动的舞姿,这样堪称完美的女子怪不得能得到西楚霸王项羽的宠爱和怜惜,才会让项羽无论在人生的巅峰还是谷底都带在身边。
当然虞姬对项羽的钦慕之情也是令人动容,在项羽被刘邦的大军团团包围之时,为了不让自己成为项羽的拖累,虞姬毅然选择了拔剑自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情之真,其性之烈让人不禁对她肃然起敬。
虽然有关虞姬的传说和故事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不但传颂和议论,但是在正史中对于她的记录却很少。
不仅她的真名没有记载,连她的生卒年月,何时开始跟随项羽等这些信息都没有记载。
只在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句“有美人名虞”,便再无踪迹。
而关于她的出生地,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她的故乡应是现在的江苏省沭阳县颜集镇。
在颜集镇上,流传着许多有关虞姬的故事和典故。
甚至还有一条以她名字命名的虞姬沟,在沟的两侧有胭脂井,霸王桥和九龙口等历史古迹。
清代的诗人袁枚还在离任沭阳县令之后特地返回此地,写下了一首凭吊虞姬的诗词。
从虞姬看古代女性地位

名人故事:虞姬

名人故事:虞姬名人故事:虞姬楚汉之争时期西楚霸王项羽的爱妻,姓虞(在《汉书·项籍传》中有有美人姓虞的记载)。
一说名虞(在《史记·项羽本经》中有有美人名虞的记载),小名为妙弋。
生卒年不详,华夏族,出生地不详(一说今常熟虞山脚下虞溪村,一说今沭阳县颜集乡,一说今绍兴县漓渚镇塔石村)。
相传容颜倾城,才艺并重,舞姿美艳,并有虞美人之称。
曾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下一直陪伴在项羽身边,后人也因此根据项羽所作的《垓下歌》推断出她在楚营内自刎,由此流传了一段关于霸王别姬的佳话。
身世之谜史书中对虞姬的记载的较少,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在《史记·项羽本纪》里记载道:有美人名虞。
因此后来就出现了两种说法:一是有人推测虞是美人的名;二则虞是美人的姓,《辞源》备有此说。
而虞姬则是后人对其的称呼,关于姬这个字,也有一定的说法,体上有两个含义:一是姬就是她的姓;二则是姬是古代妇女的美称。
虞姬的姬可以归为第二义,即美称。
总而言之,人们只能得知虞姬的姓名与虞字有关,而她的真实姓名,却成为了一个谜。
相传,项梁杀人避祸携项羽由下相奔吴中,即今日苏州地。
虞氏为会稽郡(秦末置春秋吴、越地域为会稽郡,以吴(今苏州)为郡治)吴中望族。
项梁叔侄在此结交江东子弟。
虞姬,慕项羽英名,嫁与项羽为妻,陪伴左右。
抑或可以说是项羽有幸得识虞姬,得此佳人,共谱华章。
虞姬究竟是什么人?她的绝世容貌如何?早已消失在历史帷幕的深处。
在现代,梅兰芳等艺术家,一直借题发挥,扮演《霸王别姬》,让她到台前且歌且舞,亦悲亦泣,把幽恨二字张扬到了美学的境界。
虞姬形象如何,我们都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她至少拥有美貌、才艺与风情三大优势(林黛玉笔下的五美,包括她自己,都是色、艺、情三者兼而有之,所以林妹妹才如此地惺惺相惜),这就让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王像《金瓶梅》开篇里说的:只因撞着虞姬豪杰都休。
从历史和政治上来说,项羽是败军之将,刘邦是开国之勋。
[历史上有虞姬这个人吗]历史上的虞姬真实身份:是美人但非项羽之妻
![[历史上有虞姬这个人吗]历史上的虞姬真实身份:是美人但非项羽之妻](https://img.taocdn.com/s3/m/58a1601d7fd5360cba1adb68.png)
[历史上有虞姬这个人吗]历史上的虞姬真实身份:是美人但非项羽之妻近日热播的古装大剧《王的女人》毁誉参半,成为近期观众和网友讨论的热门话题。
其中备受争议的是将项羽、刘邦、虞姬、吕雉4人的故事进行重新编写。
对于观众的质疑,编剧于正颇为不满,称虞姬这个人物《汉书》里面根本就没有,是京剧里虚构出来的,既然是虚构的,为什么不可以改编,为什么她就一定要和楚霸王在一起?难道史书里真的没有虞姬这样一个真实人物吗?虞姬和项羽的关系究竟怎样呢?历史上的虞姬确有其人网络配图北国网、辽沈晚报记者采访了百家讲坛主讲王立群,王立群告诉记者:“在文学史上虞姬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
在《史记·项羽本纪》里曾经记载:‘有美人名虞。
’由于‘姬’是对古代妇女的美称,所以后人冠以‘虞姬’之名。
”史书中对虞姬的记载只有寥寥数笔,但是作为艺术形象,对虞姬的刻画是非常丰满的,王立群说:“虞姬作为艺术形象最早出现在元代戏曲里,在元明杂剧和传奇中,虞姬一直是作为道德符号出现,但缺乏完整的艺术形象,直到京剧《霸王别姬》,虞姬彻底转变为情感实体,成为舞台上的美丽女性形象之一。
”项羽妻子另有其人曾有传说:虞姬是吴中虞氏美女。
项羽初随伯父项梁起事,转战到吴中。
那一年项羽24岁,正值青春年少,血气方刚。
虞姬是项羽军中一员战将虞子期的妹妹,美丽而好武,虞姬十分爱慕年轻勇猛的项羽,自愿嫁给他为妾。
王立群称,《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
”由此可判断虞姬是伴随项羽左右的。
但从其他史料中可判断项羽的妻子另有其人,可并无记载其妻的真实姓名。
由于项羽生性多疑,手下团队多任用项姓将领和其妻子的娘家人,所以推断虞姬并非项羽的妻子,她并没有任何封号,只能称其为“王的女人”。
网络配图后虞姬死于四面楚歌声中,张爱玲曾感叹:“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将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庄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的确,就算楚霸王当了皇帝,虞姬也不过是成千上万的贵妃中的一个而已。
史记中的女性地位反映观察

史记中的女性地位反映观察史记是中国古代史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由司马迁所著,记载了从夏、商、周到秦朝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
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学者,我对史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中女性地位的反映观察。
通过对史记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古代中国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和地位。
首先,史记中女性地位的反映可以从女性角色的数量上观察。
在史记中,女性角色的数量相对较少,大部分记载都是男性的事迹和政治事件。
这一现象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男权制度,女性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的参与度较低。
然而,史记中仍然有一些女性角色的记载,她们或是君主的母亲、妻子,或是有特殊才能的女性,如女儿李陵、女画师齐横等。
这些女性形象的出现,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反映了古代社会对于女性才能和智慧的认可。
其次,史记中女性地位的反映还可以从女性角色的形象塑造上观察。
在史记中,女性角色的形象多样且丰富。
有的女性形象被塑造成聪明睿智、有远见的女性,如秦国太后赵姬、汉武帝的母亲吕雉等。
她们在政治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国家大事有着深刻的见解和决策能力。
另一方面,史记中也有一些女性角色被塑造成柔弱、依从的形象,如虞姬、吕后等。
这些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女性温柔、贤淑的期望,同时也暗示了古代社会对女性地位的限制。
再次,史记中女性地位的反映还可以从女性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上观察。
史记中有一些女性角色在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
例如,史记中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的外戚权臣王政吕后,她通过巧妙的手段掌握了政权,对国家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外,史记中还记载了一些女性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如虞姬为保护秦王子婴而舍身殉国的故事。
这些女性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女性勇敢、忠诚的认可。
最后,史记中女性地位的反映也可以从女性在文化传承中的角色上观察。
在古代中国,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传承家族文化和价值观的责任。
史记中记载了一些女性通过教育子女、传承家族文化等方式对后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著名美女虞姬的介绍

著名美女虞姬的介绍关于著名美女虞姬的介绍虞姬是楚汉之争时期西楚霸王项羽的美人,相传虞姬容颜倾城,才艺并重,舞姿美艳,并有“虞美人”之称。
以下是店铺精心整理的虞姬的介绍,希望能帮到大家了解!虞姬的介绍“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这句话正是来自于虞姬的口中,而当时她在唱这句歌词正是虞姬在自刎殉情前吟诵的一首诗,从这之后,这首歌词就成为了这位绝代佳人的千古绝唱。
下面就让我们了解下虞姬的简介。
关于虞姬简介,她是楚汉之争时期著名人物西楚霸王项羽的一位美人,对于她是什么时候出生,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唯一记载并留给后世的就是她与西楚霸王项羽之间的忠贞爱情。
从历史资料的相关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虞姬面容可以说是倾国倾城的,再加上她的才艺和那美艳的舞姿,就可想而知为什么项羽会给虞姬封为“虞美人”了。
记得她曾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下一直陪伴在项羽身边,后来为了不让项羽牵挂自己,于是在楚营帐内舞剑自杀了,而这一个桥段就是之后我们所熟知的“霸王别姬”这个典故。
自时间流逝以来,在人们的心中这一桥段足以证明虞姬和项羽两个人之间感天动地的爱情。
此外,从虞姬所长唱的《和垓下歌》中更能够感受到虞姬此时此刻处于生死之际的复杂感情。
“楚霸王英雄末路,虞姬自刎殉情”,这样动容的悲情瞬间,早已定格在中国文学中以及戏曲的舞台上,成为中国古典爱情中最经典,最荡气回肠的千古传奇。
虞姬为什么要自杀有关于虞姬这个传奇般的女子的传说和典故数不胜数,讲述她和西楚霸王项羽之间的凄美的故事的影视剧也有很多。
而其中流传最广也是最让人对虞姬感到钦佩不已的`一定是她为了不拖累项羽而选择用剑自刎而死的壮烈结局。
这一举动不仅让人看到了她对于项羽的一片深情,也体现了她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
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这个故事打动而流下热泪过。
不可否认,一个女子可以为了自己深爱的人选择自杀无论如何都应该获得所有人的尊敬和称颂。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是太让人悲痛,我们才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表示质疑。
《史记》中的女性

视点25提到古代女人,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她们的标签是古板、无趣、可怜,还是被两千年沉甸甸的封建枷锁压得抬不起头的苦难者?应该说,中国女人的地位上下浮动很大,她们经过了一个渐次由上坠下,又自下而上,争取“能顶一片天”的漫长革命。
这个女性地位的“至上”时代,《史记》最有发言权。
如果把《史记》看作一个宇宙,最亮眼的一定是帝王、将相、贤者、隐士、侠客等男性明星。
但太史公并未遗忘那些与男性共同组成完整社会的女性,在《史记》浩瀚篇幅中,专属帝王的《本纪》里有女性的单独篇章,王侯《世家》里也有为女性辟出的一篇《外戚世家》,其他平民女性,则像满天星,也许能见度低,着墨不多,却独树一帜映照在《史记》的整个宇宙系统里。
女儿、妻子、母亲,大义女性古代女人的社会身份,首先分为女儿、妻子和母亲三种进阶,《史记》中的三则事例,便为这三种身份选出了三个代表,大义的代表。
女儿代表如缇萦。
这是一出广为流传的故事,说缇萦的父亲淳于意是西汉齐国管太仓的长官,被尊称为太仓公。
太仓公年轻的时候还有个副业是当医生,由于精通业务,太仓公名气响彻齐鲁,不少人登门求医,但他是个旅游爱好者,经常出门交游各诸侯国之间,让患者无处寻觅。
而且,太仓公极具神医的古怪脾气,给来求医的人设置了不少门槛,因此让不少病人吃了闭门羹,结果也招致了很多仇怨。
医患关系,自古以来就是紧张的。
有记仇者愤愤不平,把太仓公私自越境巡游的事举报给了朝廷,按规矩,朝廷召他进京接受肉刑。
临行前,五个女儿跟着囚车哭哭啼啼,太仓公越看越生气,重男轻女思想油然而生,要是有个儿子,也有人为自己挺身而出一下,奈何自己只生了女儿,便没好气地骂女儿们:“生娃儿不生男孩,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小女儿缇萦听到爹爹这么说既伤感又羞愧,当下决定,随父亲一起到长安做点什么。
到了长安,缇萦以平民身份给汉文帝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申辩父亲的廉洁,然后并不打算破坏朝廷律法,而是声明支持“坐法当刑”,转而又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说到罪人改过自新的层面。
初中语文文学讨论(美文荐读)谈《史记》中的几个女性形象

谈《史记》中的几个女性形象《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文学史上,她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人物描写与刻画。
司马迁在写人时,又严格遵循着“实录”的原则。
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又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读《史记》,我们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庙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跃动在各自“历史舞台”上有血有肉、有灵有感的活生生的人。
且不论帝王将相、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几个女性形象也很出色。
女性,是人类永远不衰竭的话题。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历来处于从属的卑微地位。
从《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开始,女性大多被定位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倾国倾城的祸水。
尤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更是造就了不少关于女性的历史谎言。
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女性的描写还是比较公正的。
不论是《殷本纪》中“洗澡时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简狄,还是《周本纪》中外出见巨人脚印因心爱踩之而生弃的姜原,虽然有些离奇,但那是本着“契”和“弃”都是奉天意而诞生的这个意图而引用《诗经》上的传说罢了;不论是《周本纪》中”奔密康公“的三个女子,还是《吴太伯世家》中为争抢采摘桑叶而使楚吴相互攻杀的少女们;不论是《秦本纪》中释放三囚的文嬴,还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嫔们……总之,司马迁对她们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平的。
尽管对她们的描写着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记名,但在这众多的女性中却有几个个性鲜明、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
一是在《吕太后本纪》中的吕后,司马迁用本纪的体例,成功地塑造出她残忍刻毒、权欲熏心的乱政后妃的形象。
这个历史上著名的野心家,她处心积虑地培植吕氏势力,其表现是“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泣:眼泪)。
等丞相陈平听从侍中张辟强的办法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掌握南北军权,诸吕入宫,居中用事时,则“太后悦;其哭乃哀。
”同样是哭,前面的干哭与后面的痛哭两相对照,其用心可知。
《史记》楚汉战争中虞姬与吕后描写的深层心理阐释

《史记》楚汉战争中虞姬与吕后描写的深层心理阐释王晓红【摘要】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和<史记·高祖本纪>关于"楚汉战争"中与战争双方重要当事人紧密相关的两位女性:虞姬与吕后采用了迥异的描写方式,从创作目的、作者生平遭际、读者接受三个维度拟或可探及其表现的深层心理因素.【期刊名称】《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1(026)001【总页数】3页(P14-16)【关键词】《史记》;虞姬;吕后;深层心理【作者】王晓红【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陕西,渭南,714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司马迁关于“楚汉战争”本事记载主要见诸于《史记·项羽本纪》和《史记·高祖本纪》。
与战争双方重要当事人紧密相关的两位女性:虞姬与吕后自然而然被卷入其中。
本文着重探及司马迁描写楚汉战争中虞姬与吕后迥异的笔法以及表现的深层心理因素。
首先将《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楚汉战争中对虞姬与吕后描写抽取出来,进行比照。
关于吕后的记载:楚汉双方战端初起,彭城一战,刘邦大败,吕后被楚军俘虏,“项王常置军中”,扣留她作为人质,一直到楚汉订盟,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项羽乃“归汉王父母妻子”,吕后才回到了刘邦的身边。
从时间来推算,吕后在项王军营中度过了两年多的失却自由的生活。
关于虞姬的记载:楚汉争霸,项羽困于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
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羽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披衣而起,独饮帐中。
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
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
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史记》具有科学性和文学性的双重性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史记》肯定是“对历史文本摹仿的产物”[1]94。
这种摹仿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历史事实、历史本质、活跃其间的历史人物等等。
高二作文美人名虞

高二作文美人名虞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西楚霸王项羽在四周楚歌之歌,我们已不能看到霸王的悲愤,更不能赏到两千年前虞姬的那只绝世之舞。
但我们仍可以从历史的长河中嗅到美人虞姬的一世绝华。
本纪为列代君主帝王的传记,霸王项羽不属帝王却在本纪中熠熠生辉,而本纪所记载霸王的一生中高潮部分---四周楚歌之时,有一位女子生生的立在了那历史之巅,她便是美人虞姬。
虞姬在史记中如同一只凤尾蝶,扑闪了一下又急急飞走追逐自己的宿命,留下身后一抹芳香。
虞姬的一生还没来的及开头,便如被人堪堪折去双翅的蝶,凌乱的落入了无尽的虚空。
她因项羽而起也因项羽而灭,惜字如金的史学家司马迁用“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开头,又用“歌数阕,美人和之”来结束虞姬的传奇。
两千年后,花开花落。
硝烟落定归为尘土,千年前的故事也只有墨端的痕迹才能记住。
美人和之,司马迁留给世人太多余地来给虞姬一个适合她的结局,“霸王别姬”便是其中最为精彩的一种。
但虞姬给人带来的震撼却不止如此年京剧大师梅兰芳用自己精湛的演技叙述了这一秦末奇女子的壮烈情怀,
而观众在看完虞姬自刎后潸然泪下,以为表演已经结束便满怀感动的离开了戏场,以至于其后由武生泰斗杨小楼扮演的霸王项羽血洒乌江一幕未曾开演。
从这以后,将近百年,“霸王别姬”这一场戏至虞姬自刎便华丽结束了。
每一场都带给现代人以无比的震撼,试问在这糜烂的世界中,还有谁还保持着如古人那般的心智呢?。
《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解析

《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解析
《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解析
王美玲
【期刊名称】《现代交际》
【年(卷),期】2011(000)012
【摘要】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一鄙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巨著。
司马迁不仅刻画了帝王、将相、商人、医生等众多人物形象,还描写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
这些女性人物或人性扭曲,或以坚强睿智流芳,或具有传奇的色彩。
司马迁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尊重了女性,将自己进步的人格观融入《史记》之中,不同性格特征的女性人物脱颖而出。
【总页数】2页(97-97,96)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女性形象
【作者】王美玲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相关文献】
1.司马迁对女性的赋形--浅论《史记》中的女性形象意义 [J], 蒋建梅
2.《史记》女性形象述评 [J], 陈功文
3.论《史记》中的女性形象 [J], 董继伟
4.《史记》中的政治女性形象分析 [J], 邓燕
5.《史记》中的女性形象对《红楼梦》人物塑造的影响 [J], 张萍。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从《史记》中的虞姬看女性之存在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在以项羽为核心的描述下,提到了美人虞,其中这样描写:“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
於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
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
陆贾《新语楚汉春秋佚文》中记有“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尽管有人认为此和歌为伪作,是后世人所作。
在这里关于其真实性,我们不做考究。
总的来说,寥寥数笔记述的故事反映了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是,霸王和美人在垓下面临十面埋伏的震惊与决断;另一个则是在死亡来临之际二人写下的不朽的爱情传奇,而后者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书本中,无论是在寄恨抒愤的文人眼里还是在功成名就的达官贵人的心中,都被定格成中国古典爱情中最荡气回肠最灿烂不朽的篇章。
司马迁以受宫刑侮辱之躯写《史记》,其中自然也包含着个人的愤怒与怨恨。
他把未正式称帝的项羽放在了专记皇帝的传记本纪中且位置在西汉开国之主汉高祖之前从这里其个人的郁愤
可见一斑。
然而终归是以男性的角度去描述历史事件,即在历史的进程中,女性所处的地位如尘土。
虞姬最初的雏形司马迁以极简短的
话做了描述“有美人名虞,常幸从”,而后“美人和之”虞姬的形象就结束了。
在这段描写中,突出的不是虞姬,而是霸王项羽英雄气短,建构的也是在重重包围之中项羽所显现出来的霸气中情义,从而升华了项羽的有情有义。
美人虞在这里只是一个美人的代称,若允许假设猜想不妨做这样的想象:美人不是美人,即把“美”作为该女性的特征中抹去,是否项羽还会这样重情重义呢?历史不能假设,但不论有美无美的女人在面临充分握有“宠幸”这一对女性身体和意识占有极高话语权的男性时,女性的地位和女人之作为女人的种种意识、权利成为了一句空话,女性也就只不过成了尸留气亡的存在符号,这种存在,与个人本身无关,与历史更无关,甚至与与之相关的男人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但根据“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这个并列句式,即可看出女人在此书或者说在历史的进程中的地位。
在“霸王别姬”这一历史母题的雏形中项羽和美人虞是处于两个
不同的地位,项羽居于绝对的主体地位,拥有着本体话语权和对女性的完全归属权。
而美人虞只是霸王项羽这一英雄人物的陪衬,是极端失衡的一极,只能与乌骓马相提并论:乌骓马是项羽的坐下骑,即作战工具,“常骑之”;而美人虞自然就是项羽的妃妾,即暖床之人、性欲的对象,“常幸之”,即宠幸男性的绝对权威显露无疑。
更何况乌骓马的性命都强如虞姬:项羽“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
’”项羽对伴随五年的乌骓马有“不忍”之
心,但却对伴随身边的女人无“不忍”之心,项王之“泣”应该大多泣自己“力拔山兮”却“时不利兮”,即“天之亡我,非战之罪”。
虽然,司马迁的《史记》与《楚汉春秋》为交代虞姬的最终结局,但“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分明是项羽对美人虞的追问,在十面埋伏之中,在宗法制度的框架里,在英雄气短的项羽层层追问下,美人虞作为项羽宠幸的对象会有什么结果呢,而又该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个让我联想到了与她有相似命运的绿珠。
《晋书》列传之三载曰:“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
孙秀使人求之。
……崇竟不许。
秀怒,乃劝伦诛崇、建。
……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
'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
”因自投于楼下而死。
'”因富显赫半世的石崇与力能扛鼎驰骋半生的项羽具有相似性,与绿珠在石崇前坠楼的命运相比,作为“败寇”之妾的虞姬来说,命运又能比绿珠好到哪里去呢?后世传在垓下之地附近有虞姬草和虞美人花,而不论花与草,其传说都是建立在美人自刎的结局上。
自刎可以说是最现实也最接近真实的结局
总体来说,《史记》中未有对虞姬做任何正面的描写,也未把虞姬作为一个人的“性”即与男性相对立的另一性女性去描写和叙述,而只是把她作为男性的附属品甚至命不如马这样一种符号去探讨。
而纵观《史记》,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眼中,不论何种帝王将相,不论圣贤才子,更不论鸡鸣狗盗游侠商贾之士,女性在此书
中所占篇幅仅止于吕后一人一卷九《吕太后本纪》,而这唯一的以女性为主体的篇章却并没有突出她对西汉建国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她政治上的才能和眼光,而是大部分记录了高祖刘邦死前后吕后为维护个人利益而做的残杀无辜滥用大权把持朝政等一系列让人憎恶的事情。
概括说来,以虞姬为代表的女性对于历史来说虽有着真实的存在却失去了女性所拥有的本体话语权,女性本身也不具有独立的人格特征,而只是男性意识与男性话语的被动实践者与操纵者,从而最终成为男性所操纵的历史话语和男性主体意识覆盖、淹没之下的无语的存在者。
被誉为西方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她的《第二性》里通过对生物学、弗洛伊德等精神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学说进行对比,认为在历史长河中,女性总是处于附属地位,居于依附地位,这也就造成了女性完全沦落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和男性性欲的对象,女性丧失了主体性,被异化为客体。
波伏娃引用了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观点,指出要改变这种存在则女性必须由“自在的存在”变成“自为的存在”。
鲁迅曾说:“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
似的。
”正是由于这几个烈女的存在,为历史的壮烈装点了一抹温柔之色,但这抹温柔却也只是因为忠贞因为刚烈因为她们的死成就了后世的夸耀与祭奠。
最后,我以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的诗《过虞沟游虞姬庙》为结:
为欠虞姬一首诗,白头重到古灵祠。
三军已散佳人在,六国空亡烈女谁?
死竟成神重桑梓,魂犹舞草湿胭脂。
座旁合塑乌骓像,好访君王月下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