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以耶释佛英译_大乘起信论_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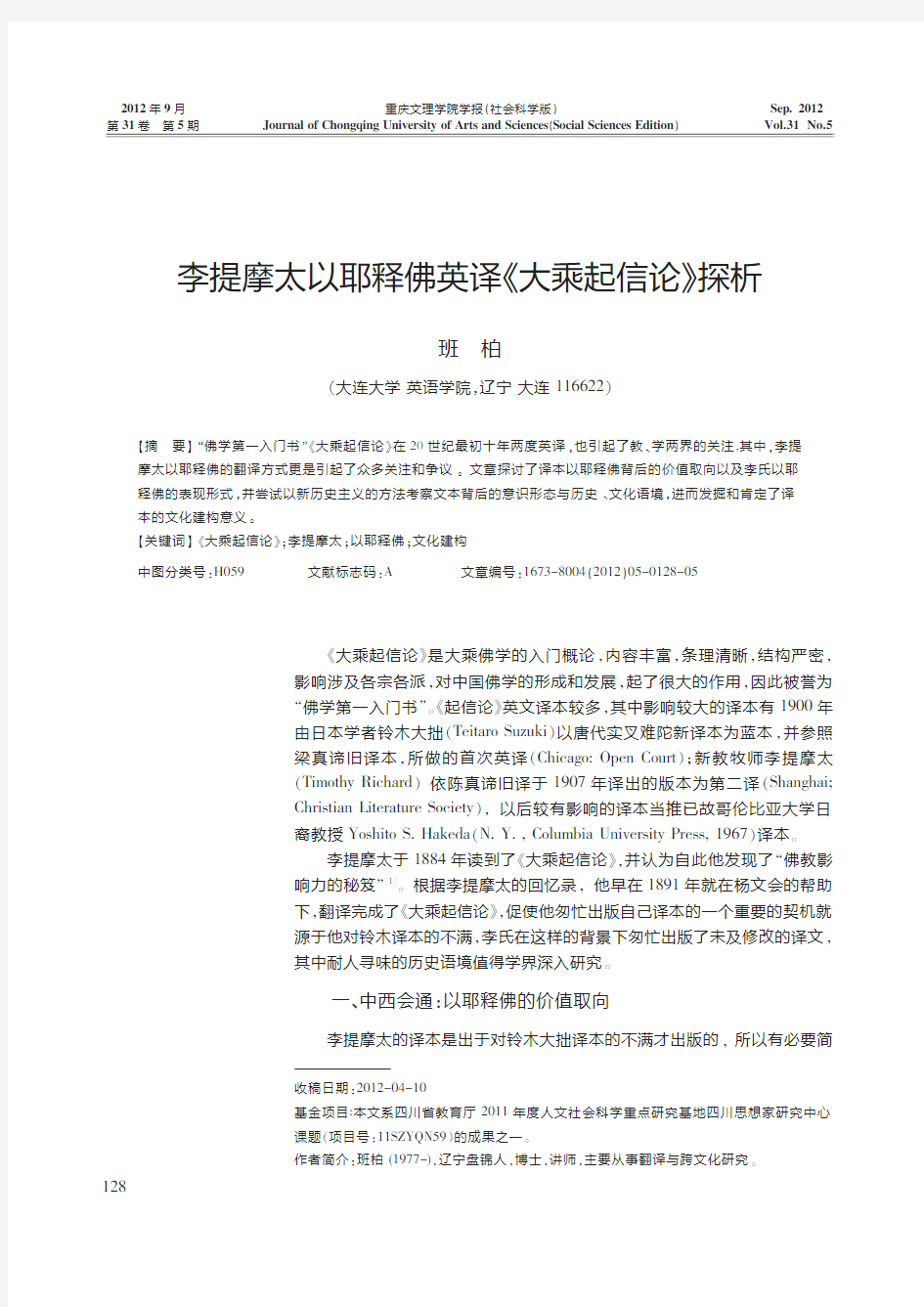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李提摩太以耶释佛英译《大乘起信论》探析
班
柏
(大连大学英语学院,辽宁大连116622)
【摘要】“佛学第一入门书”《大乘起信论》在20世纪最初十年两度英译,也引起了教、学两界的关注,其中,李提
摩太以耶释佛的翻译方式更是引起了众多关注和争议。文章探讨了译本以耶释佛背后的价值取向以及李氏以耶释佛的表现形式,并尝试以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考察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语境,进而发掘和肯定了译本的文化建构意义。
【关键词】《大乘起信论》;李提摩太;以耶释佛;文化建构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04(2012)05-0128-05
收稿日期:2012-04-1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2011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课题(项目号:11SZYQN59)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班柏(1977-),辽宁盘锦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大乘起信论》是大乘佛学的入门概论,内容丰富,条理清晰,结构严密,影响涉及各宗各派,对中国佛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被誉为“佛学第一入门书”。《起信论》英文译本较多,其中影响较大的译本有1900年由日本学者铃木大拙(Teitaro Suzuki )以唐代实叉难陀新译本为蓝本,并参照梁真谛旧译本,所做的首次英译(Chicago:Open Court );新教牧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依陈真谛旧译于1907年译出的版本为第二译(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以后较有影响的译本当推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日
裔教授Yoshito S.Hakeda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译本。
李提摩太于1884年读到了《大乘起信论》,并认为自此他发现了“佛教影响力的秘笈”[1]。根据李提摩太的回忆录,他早在1891年就在杨文会的帮助下,翻译完成了《大乘起信论》,促使他匆忙出版自己译本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源于他对铃木译本的不满,李氏在这样的背景下匆忙出版了未及修改的译文,其中耐人寻味的历史语境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一、中西会通:以耶释佛的价值取向
李提摩太的译本是出于对铃木大拙译本的不满才出版的,所以有必要简
Vol.31No.5
2012年9月第31卷第5期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Sep.2012128
单阐述一下铃木译本价值取向,“他(铃木大拙)挑选《起信论》出来向西方译介,显然是想在19世纪西方以印度佛学为中心的氛围下,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大乘佛教争得一席之地。”[2]关于这一价值取向,龚隽教授还特别佐之以“铃木大拙的禅学书写中充满了民族主义的修辞”[2]阐释,因此,铃木“坚持从东亚佛教立场出发,不惜大量笔墨为《起信论》所代表的东亚佛教传统辩护,这里面含有重要的政治论述”[2]。与铃木译本的浓厚政治意味相比,李提摩太译本则渲染了浓厚的“传教”意味,这固然与其传教士的身份密不可分,但学界尚缺乏对其译本文化观的考察。而恰恰是其文化观,或是其文化价值取向,为其翻译题材的选择和其独特翻译策略的运用提供了最佳的解释。李提摩太提出“学者何必学于古,非也。何必学于今,亦非也。盖学无论古今,学其有益于人者而已”;“中国旧学阅数千年,决不可废。今既与万国来往,则各国通行之新学亦不可不知”[3]。在李提摩太看来,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建立融汇古今中外文化可取之处的“新学”,以耶释佛英译《大乘起信论》就是这种融会贯通的价值体现。
李提摩太为“新学”提出一个“横、竖、普、专”的知识框架。所谓“横”,是指学择其善者而从之,“我国所重之要学学之,即各国所重之要学亦学之”;“竖”,即;“一国要学中有当损益者知之,即自古至今历代之因何而损,因何而益者,一毕知之”[4];“普”则意味着兼容并包,广泛吸收;“专”则指专精一学,触类旁通。这种“中西会通”的文化价值导向,促使李提摩太将汉传佛教同基督教义比较、融通,从而选择将《大乘起信论》作为佛耶对话的平台,思索宗教融合的可能。李氏这样的做法受到了教、学两界的排斥,但就其文化传播意义来说,其东学西渐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也正是基于文化会通的思路,一部英国三流历史学著作《十九世纪史》(李译《泰西新史揽要》)经由李氏的翻译,变成了一部晚清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西方历史学译作,并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和思想启蒙。据此看来,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巨大作用实在是被遗忘的研究湮没了。
李提摩太的文化价值取向使其并没像早期来华传教士那样排斥中国佛教,而是认真思考佛教在中国扎根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思索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最终使其看到了基督教和佛教的联系。在李提摩太看来,马鸣所创的这部大乘佛典是“高级形式的佛教”,是基督福音书的“亚洲形式”[5]。以耶释佛、佛耶对话正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最好平台和选择。
李提摩太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当时比较宗教学勃兴的背景也是不可分的,不难看到,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研究,是同之前的艾约瑟等人的研究一脉相承的。艾约瑟在其《中国佛教:历史,叙述和批判》一书前言中指出,北传大乘曾经受到基督教等思想的影响,从而才有了来世和不朽的观念[6]。李提摩太翻译佛教经典并考察佛教文化正是为基督教在中国扎根寻找学术理据和现实基础。
二、“洋格义”:以耶释佛的三种表现
正是基于“中西会通”的文化价值取向,李提摩太出版了《大乘起信论》英译本(1907年,上海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译本一出,教、学两界哗然,纷纷谴责“穿凿附会”。
李氏“以耶释佛”的翻译实践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运作的,这是学界少有讨论的。首先体现在术语翻译上,如“如来”(Tathagata)、“菩萨”(Bodhisattva)已有定译,李氏却将其译成Ju Lai、Pusa/Pusa Saints,故意破坏原有的佛教术语体系,以适应其“以耶释佛”的目的,这样的做法是大胆的,以致于在1960年University Books(Hyde Park,N.Y.)出版的译本中,校订者不得不为此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订,使其同其他的大乘佛典译本保持一致。该修订版对“如来藏”的核心思想“真如”的翻译也不满意。李提摩太将真如(Chen-jǔ)译成True Form, True Likeness,True Reality,Archetype,True Mod-el。修订者认为,铃木大拙将其译成suchness,更为合理。有几处,修订者干脆用true form,true model将true reality替换掉(“Occasionally,True Reality has been substituted for Richard's True Form or True Model,etc.”)[7]。修订者甚至还提供了其他的几个备选项:如Thusness,The Cosmic Order,the sum-total of all factors which shape the universe,the norm of existence,the womb in which all things take their shape and from whence they are born[7],均与李提摩太的译法不同。
其次,李氏对义理的阐释也是“私见穿凿”。以
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