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活着意象的意义
探究余华先锋小说《存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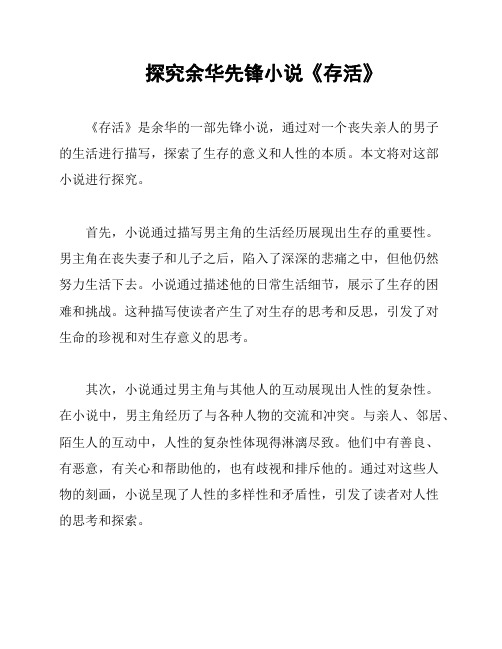
探究余华先锋小说《存活》《存活》是余华的一部先锋小说,通过对一个丧失亲人的男子的生活进行描写,探索了生存的意义和人性的本质。
本文将对这部小说进行探究。
首先,小说通过描写男主角的生活经历展现出生存的重要性。
男主角在丧失妻子和儿子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但他仍然努力生活下去。
小说通过描述他的日常生活细节,展示了生存的困难和挑战。
这种描写使读者产生了对生存的思考和反思,引发了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生存意义的思考。
其次,小说通过男主角与其他人的互动展现出人性的复杂性。
在小说中,男主角经历了与各种人物的交流和冲突。
与亲人、邻居、陌生人的互动中,人性的复杂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中有善良、有恶意,有关心和帮助他的,也有歧视和排斥他的。
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小说呈现了人性的多样性和矛盾性,引发了读者对人性的思考和探索。
此外,小说还通过男主角的思考与支撑他生活的展现了人的精神面貌。
男主角在丧失亲人后经历了失落和绝望,但他仍然寻找着生活的意义。
他尝试通过回忆和思考,寻找自己与亲人相处的意义,也反思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这种积极面对生活的精神,使他能够在悲痛中继续前行。
小说通过展现男主角的内心世界,呈现了人在面对困境时的坚韧和勇敢,给予读者一种鼓舞和启示。
综上所述,余华的先锋小说《存活》通过对一个丧失亲人的男子的生活进行描写,探索了生存的意义和人性的本质。
这部小说通过描绘生活的困难和挑战、展示人性的复杂性以及展现人的精神面貌,引发了读者对生存和人性的思考和探索。
它呈现了余华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深刻的社会观察能力,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学作品。
解读《活着》中活着的意义

解读《活着》中活着的意义《解读〈活着〉中活着的意义》余华的《活着》是一部令人深思的作品,它以朴实无华的文字描绘了在大时代背景下,主人公福贵饱经沧桑的一生。
这部作品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华丽的词藻,却能深深触动读者的心灵,引发我们对于“活着”这一简单而又深奥的命题的思考。
福贵,原本是一个富家公子,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
然而,命运的转折让他在短时间内失去了一切,从富贵跌入贫困。
他经历了家庭的变故、社会的动荡,身边的亲人一个接一个地离世:先是父亲离世,家道中落;接着母亲病逝,他在去为母亲抓药的途中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历经战火纷飞,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女儿凤霞却因一场大病变成了哑巴;儿子有庆为救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而死;女儿凤霞产后大出血去世;妻子家珍也因病离开了他;女婿二喜在工作中意外身亡;就连唯一的外孙苦根,也因吃豆子被撑死。
命运似乎对福贵充满了恶意,将无尽的苦难加诸在他身上。
然而,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福贵却没有选择放弃生命,而是坚强地“活着”。
那么,在福贵的一生中,“活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活着”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在福贵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常。
每一次亲人的离世都是对他心灵的一次重创,但他依然选择继续活下去。
这并非是对命运的屈服,而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他明白,生命是宝贵的,即使充满了苦难,也值得去珍惜和坚守。
每一个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无论遭遇多少挫折,都不能轻易放弃。
这种对生命的尊重,让福贵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展现出生命的顽强与坚韧。
其次,“活着”是一种承受苦难的勇气。
福贵的一生充满了苦难,但他却以一种平静而又坚定的态度去面对。
他没有被苦难击倒,而是在苦难中学会了承受。
这种承受并非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种积极的应对。
他接受了命运给予的一切,不抱怨,不逃避,用自己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担。
在承受苦难的过程中,福贵的内心逐渐变得强大,他的精神世界也得到了升华。
解读余华《活着》的生命意义

解读余华《活着》的生命意义余华是80 年代崛起的先锋小说家,余华的作品充满了大量的暴力、死亡和苦难。
《活着》是一部关注人生苦难及苦难中生命个体生存意义和态度的作品。
小说主人公富贵经历了坎坷的一生。
他的亲人一个又一个的离他而去,他以平淡的语调叙述了一个又一个亲人们的悲惨命运。
看似无所谓,实则内心承载着巨大的痛楚。
他在承受了亲人们远去后的悲伤中隐忍的生活着,并且还可以真切地回忆起亲人们的死亡过程,表现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顽强而执着的生活态度。
一.活着就要学会承受余华长篇小说《活着》中的所谓“活着”,实际上是在苦难中挣扎,是痛苦地生存,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平平淡淡的承受一生中的不易。
突发的、毫无预见的灾难与苦痛只能学会承受。
活着不仅要学会承受生命旅程中的愉快与幸福。
也要学会承受艰难与苦难。
小说主人公福贵的生命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世界的残酷,人生的悲剧完全理解、认识了以后,以一种不惊不喜的平常态度、宁静心情来对待生活。
主人公富贵看似戏剧性的人生实则充满着很强的真实性。
余华在这里警示人们要珍视生命,要包容生命出现的一切苦难,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 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二.活着就要学会隐忍主人公富贵在抗战爆发后,输光了家产00 亩田地,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
父亲在痛骂儿子一顿后,变卖了家产,还清了儿子的赌债,但也因此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念,掉入粪缸死了。
不久,母亲重病,福贵在为母亲进城请医的半路上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
两年后回到家中时,得知母亲早已病故。
医生为了救县长的女人,儿子有庆在献血时因超量抽血而丧失生命。
女儿凤霞虽然脑筋不好使,但是勤劳、心底善良,嫁给了城里搬运工的二喜,生活平淡而踏实,但不久却死于难产。
不久富贵的妻子家珍也离开他。
女婿二喜时常到家里帮忙干活,日子还算清闲,只是好景不长,二喜在工作时意外死亡。
而与他最后唯一能相依为命的外孙苦根却因吃豆子太多被活活撑死。
《活着》:生命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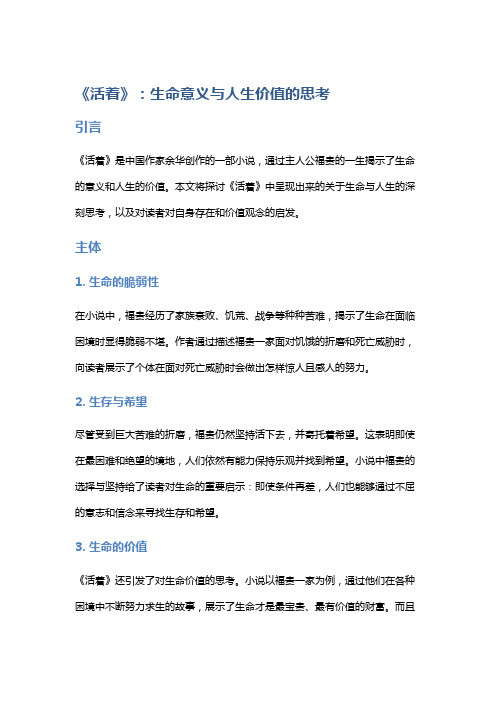
《活着》:生命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思考引言《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创作的一部小说,通过主人公福贵的一生揭示了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本文将探讨《活着》中呈现出来的关于生命与人生的深刻思考,以及对读者对自身存在和价值观念的启发。
主体1. 生命的脆弱性在小说中,福贵经历了家族衰败、饥荒、战争等种种苦难,揭示了生命在面临困境时显得脆弱不堪。
作者通过描述福贵一家面对饥饿的折磨和死亡威胁时,向读者展示了个体在面对死亡威胁时会做出怎样惊人且感人的努力。
2. 生存与希望尽管受到巨大苦难的折磨,福贵仍然坚持活下去,并寄托着希望。
这表明即使在最困难和绝望的境地,人们依然有能力保持乐观并找到希望。
小说中福贵的选择与坚持给了读者对生命的重要启示:即使条件再差,人们也能够通过不屈的意志和信念来寻找生存和希望。
3. 生命的价值《活着》还引发了对生命价值的思考。
小说以福贵一家为例,通过他们在各种困境中不断努力求生的故事,展示了生命才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财富。
而且从整个社会环境来看,作者通过揭示福贵一家成为剥削对象、受尽苦难的过程,强调了人类应该尊重并珍惜每一个生命。
4. 自我反思与内心追求小说通过福贵一家在遭受苦难时对自身价值观念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引导读者深入思考自己对生活和人生目标的态度。
通过描述主人公经历种种痛苦后忠诚于亲情、友情以及追求光明与正义等原则,读者被激励着认真审视并探索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愿望和理想。
结论《活着》是一部令人深思的作品,通过揭示生命的脆弱性、生存与希望、生命的价值以及自我反思与内心追求等主题,引发了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深刻思考。
读者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和启示,认识到生命的珍贵,并对自己的存在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调整。
通过福贵一家的故事,我们被提醒要以敬畏之心看待每一个生命,感悟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并积极寻求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人生目标。
余华《活着》的现实意义(五篇)

余华《活着》的现实意义(五篇)第一篇:余华《活着》的现实意义在这个无比缤纷的世界里,有什么值得我们生存及快乐的活下去?读完余华先生的名作《活着》后,这样的问题立即在强大的精神血液中游刃而解。
余先生以回忆的口吻描述了近代中国农民平常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其巧妙的小说写作方法,犹如电视剧广告式的巧妙穿插都为小说带来不少色泽,内容更是关注了当时也是现在越来越被多数人忽视的农民群体。
那么,农民的命运到底如何?就象作者说的那样,“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显然,余先生费劲了心思来探索中国农民的命运,点燃他们面对苦难生活的勇气。
仅有这点,小说就已扎根于高层次的文学花园。
因为基于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全球哲学意识下,关心基层人群的疼痛、喜乐、忧愁、隐忍、寻觅等要远远高于奢侈生活的群体。
在一个已经有了结果的生活状态下,或许我们认为活着就压根毫无意义,就象一场足球赛,前九十分钟已被对手踢进八个球了,除了奇迹再也无法挽回即将涣散的局面。
然而小说的主人公徐富贵却不认同,反而更沉醉于朴实生活中的快乐。
面对陌生人,内心没有丁点虚伪,太多的压力也让他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变得诚实、素朴、愚钝的最典型中国农民的形象。
我们且不多议中国农民命运究竟如何,只是肤浅的、一个普通农民能够在心灵遭受到极大创伤后还能为着理想发奋图强,在巨大的苦难下生活继续“活着”,足以证明小说的文学精神魅力,激扬着生命中最震撼的基因。
文学到底是什么?巴金先生曾这样定义: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
(1)生存在今天日益竞争的社会里,或许还有很多象小说主人公徐富贵那样遇到过很多令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的人。
经历过生死浩劫后难免会问为什么要活着抑或生活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
徐富贵父亲临死前说“徐家的老祖宗不过养了一只小鸡,鸡养大后变成了鹅,鹅养大后变成了羊,再把羊养大了,养就变成了牛,我们徐家就是这样发起来的”,他在经受种种折磨后重新定量生活俨然把父亲的遗言作为这生最大理想继续生存下去,一生地追求也只不过是买只牛而已,小说的结尾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论《活着》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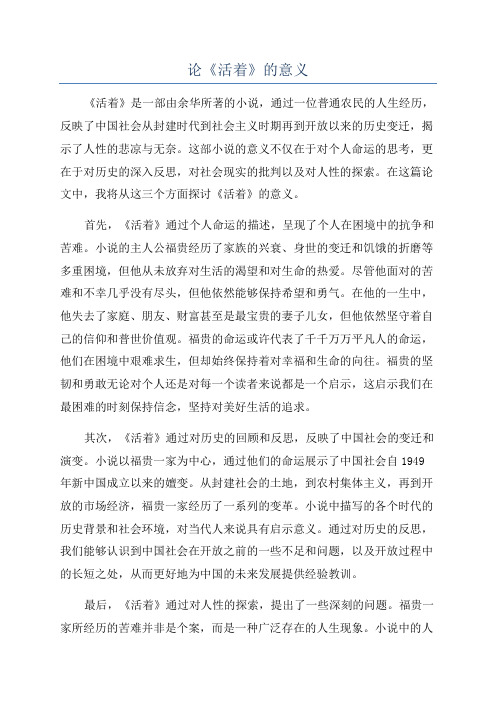
论《活着》的意义《活着》是一部由余华所著的小说,通过一位普通农民的人生经历,反映了中国社会从封建时代到社会主义时期再到开放以来的历史变迁,揭示了人性的悲凉与无奈。
这部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个人命运的思考,更在于对历史的深入反思,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对人性的探索。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从这三个方面探讨《活着》的意义。
首先,《活着》通过个人命运的描述,呈现了个人在困境中的抗争和苦难。
小说的主人公福贵经历了家族的兴衰、身世的变迁和饥饿的折磨等多重困境,但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渴望和对生命的热爱。
尽管他面对的苦难和不幸几乎没有尽头,但他依然能够保持希望和勇气。
在他的一生中,他失去了家庭、朋友、财富甚至是最宝贵的妻子儿女,但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普世价值观。
福贵的命运或许代表了千千万万平凡人的命运,他们在困境中艰难求生,但却始终保持着对幸福和生命的向往。
福贵的坚韧和勇敢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每一个读者来说都是一个启示,这启示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刻保持信念,坚持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其次,《活着》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演变。
小说以福贵一家为中心,通过他们的命运展示了中国社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嬗变。
从封建社会的土地,到农村集体主义,再到开放的市场经济,福贵一家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
小说中描写的各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对当代人来说具有启示意义。
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我们能够认识到中国社会在开放之前的一些不足和问题,以及开放过程中的长短之处,从而更好地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经验教训。
最后,《活着》通过对人性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问题。
福贵一家所经历的苦难并非是个案,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人生现象。
小说中的人物们在面对困难和选择时,展现了人性的善恶、智慧和迷茫。
比如,在生活陷入困境时,福贵选择继续活着的勇气和决心,而他的女儿敏敏则选择自杀,这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
小说通过对人性的揭示,提醒我们要对人性的普遍性保持警觉,追求善良和人文关怀。
如何评价余华的《活着》

《活着》——余华笔下的生活真谛余华的《活着》是一部深入人心的作品,它以简洁明了的文字,讲述了主人公福贵的一生。
这部小说以其独特的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思考人生的价值。
首先,余华通过福贵的人生经历,向我们展示了生活的残酷与真实。
福贵从富有的地主少爷到一贫如洗的农民,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挫折。
然而,他并没有被生活的困境所打败,而是坚韧地活下去,用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
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其次,余华在《活着》中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和珍视。
福贵的一生中,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但他从未放弃对生命的执着。
他坚信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种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态度,学会更加珍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再者,余华通过《活着》展示了人性的光辉。
在福贵的生命中,虽然充满了苦难和挫折,但他始终保持着善良和宽容。
他对待身边的人充满爱心,对待生活充满热情。
这种人性之美,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伟大和善良,也让我们更加坚信人性的力量。
最后,我认为《活着》是一部值得一读再读的经典之作。
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残酷和真实,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美好。
它教会我们要珍惜生命,珍爱身边的人和事,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善良的人性。
总之,《活着》是一部值得我们深思的作品。
它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思考人生的价值。
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获得文学上的享受,更能够从中汲取生活的智慧和勇气。
因此,我强烈推荐大家阅读余华的《活着》,相信它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思考和感悟。
浅谈余华《活着》的生命观及“活着”的现实意义

内容提要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是一部用死亡讲述活着、以死亡肯定生命意义的故事,旨在使人勇敢地面对生与死的挑战。
作者以冷峻而貌似“残忍”的笔触向我们讲述了福贵一家人的苦难史与主人公福贵命运多舛的一生:从大富大贵到穷困潦倒,从饱尝生活艰辛到身不由己卷入战争洪流,从接受他的亲人一个个走在他的前头到最后与一头叫做“福贵”的老牛在阳光下回忆生活。
在厄运弥漫、磨难接踵而至的日子里,与福贵相关的人相继谢幕,唯有福贵在唱着主角之歌,始终乐观生活,超然面世,生命的张力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从而绽放出永不凋落的生命之花。
《活着》虽然接二连三地发生死亡,但作者不再沉溺于死亡的阴影中不能自拔,而将目光转向探求“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生命无常中人们彼此关爱相携,使人感受了生命的意义。
[1]“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2]‘活着’是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3]本文试以《活着》为研究对象,探析《活着》的生命观与“活着”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余华;活着;生命观;忍耐;现实意义绪论人,作为自然界生命的主体,其物质、精神生活、价值观也随着历史的更迭而发生变化。
摆在人们面前一个最普通也最原始的话题变得日益突出了,即我们应该抱着什么心态活着,怎样活着才更有意义?余华的《活着》将触角探伸到一个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历史氛围,将全部的不幸集中浓缩于主人公福贵一家身上,把对人生的痛苦加以延伸与夸张,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既真实可信又辛酸冷酷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笔下,福贵不单单是福贵了,而是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缩影。
作者有意淡化了“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背景,转而向我们讲述普通老百姓如何在悲惨的生活遭遇下,努力挣扎着生存,好好活着。
余华活着解读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一)

余华活着解读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一)《活着》是一部余华先生创作的小说,也是其代表作之一。
本文旨在对《活着》的人物形象、意象、叙事技巧等方面进行分析,旨在展示余华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深刻思想。
一、人物形象余华的小说中人物形象鲜明,具有强烈的个性和独特性格。
其中,主人公福贵充满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货车夫三兄弟的形象则充满了荒诞和反叛,这些形象是作者对时代裂痕和人性扭曲的反映,充分展示了作者对生命的关怀和呼吁。
二、意象余华小说的意象是一种特有的符号,其独特的象征意义是小说意义和思想含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在《活着》中雪糕象征着青春与浪漫;烟囱象征着人类的劳动、污染和压迫,这些意象无不是余华对现代文明与人性的剖析与思考。
三、叙事技巧余华小说的叙事技巧新颖独特,创新性强。
其小说叙事多采用回忆、夹叙等技巧,作品按照一系列逻辑线索展开,每一个情节相互关联,小说犹如一条无声的影子,在夜幕下徘徊。
这种夹叙、回忆、随机的结构技巧全方位地展现出人物形象和意象。
四、文学价值通过对余华小说《活着》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余华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示了人性、生命、时间、历史等方面的问题,表达了对于生命的珍惜和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思考。
同时,作品中的诸多人物和情节也从一个侧面闪耀出中国人的精神特征和生存智慧。
故《活着》不仅具有文学艺术的价值,还有着强烈的社会实践意义,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五、总结在现实主义的文学背景下,《活着》以其独特的情节和意象、独到的人物刻画、叙事技巧,展现了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历程,诠释了人性和人生的真谛。
故该小说不仅为文学奖赏所崇尚,更是为学术研究所接受,作为一种思想和理念的载体已经落地生根。
论余华的《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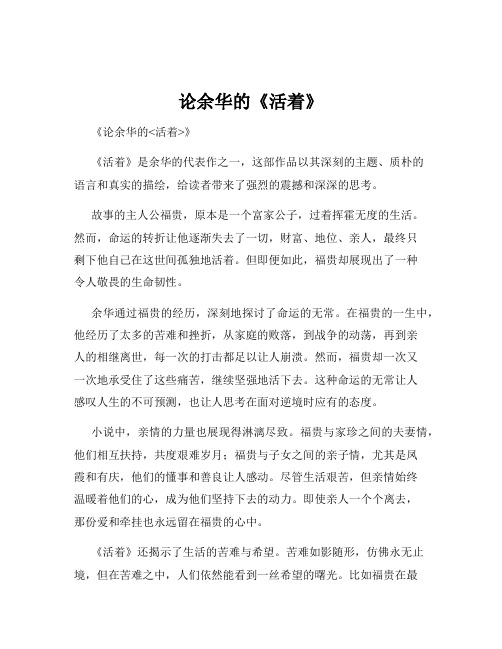
论余华的《活着》《论余华的<活着>》《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以其深刻的主题、质朴的语言和真实的描绘,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思考。
故事的主人公福贵,原本是一个富家公子,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
然而,命运的转折让他逐渐失去了一切,财富、地位、亲人,最终只剩下他自己在这世间孤独地活着。
但即便如此,福贵却展现出了一种令人敬畏的生命韧性。
余华通过福贵的经历,深刻地探讨了命运的无常。
在福贵的一生中,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挫折,从家庭的败落,到战争的动荡,再到亲人的相继离世,每一次的打击都足以让人崩溃。
然而,福贵却一次又一次地承受住了这些痛苦,继续坚强地活下去。
这种命运的无常让人感叹人生的不可预测,也让人思考在面对逆境时应有的态度。
小说中,亲情的力量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福贵与家珍之间的夫妻情,他们相互扶持,共度艰难岁月;福贵与子女之间的亲子情,尤其是凤霞和有庆,他们的懂事和善良让人感动。
尽管生活艰苦,但亲情始终温暖着他们的心,成为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即使亲人一个个离去,那份爱和牵挂也永远留在福贵的心中。
《活着》还揭示了生活的苦难与希望。
苦难如影随形,仿佛永无止境,但在苦难之中,人们依然能看到一丝希望的曙光。
比如福贵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能从田间的劳作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满足。
这种在苦难中寻找希望的精神,让我们明白,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不能放弃对未来的期待。
余华的写作手法在《活着》中也独具特色。
他以平实的语言,讲述着一个又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没有过多的修饰和渲染,却能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
他善于通过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亲眼目睹了福贵的一生。
此外,小说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
在福贵的回忆中,过去与现在交织,让读者既能感受到岁月的沧桑,又能体会到生命的延续。
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增加了故事的层次感,也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了福贵的内心世界。
《活着》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对人性的真实写照。
浅析《活着》的死亡重复意象

浅析《活着》的死亡重复意象《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是他由先锋作家向写实主义转型的标志性作品。
书中讲诉了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地遭受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故事。
余华因这部小说于2004年3月荣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在《活着》这本书中,余华不断地在重复死亡这个意象。
《活着》的死亡叙述形式,即重复。
重复是先锋小说作家惯用的一种叙述手段。
它反映了作者的语言功力、集中读者的注意力、也能拥有更强的叙述力、拥有更强大的艺术冲击力。
《活着》是余华将重复叙事运用到了极致的一部经典之作。
在叙事结构上,死亡情节重复、单纯。
死亡叙述在重复中推动情节发展,叙事节奏随着事件的发展成线形推进式人物,沿着非常单纯的“生——死”这一主线发展。
书中共写了十处死亡意象,死的人都是和福贵有关系,自己的亲人、爹娘、妻子家珍、女儿凤霞、儿子有庆,女婿二喜、外孙苦根、还有龙二、及患难与共的老全、春生,都因各种原因失去生命。
尽管死亡的脚步一刻也未曾离开过福贵,但最后,他仍然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好好地“活着”。
书中所写到的死亡意象,皆是自然状态。
仔细研究,这些人的死亡状态几乎大部分都是歪着头,人的死亡,没有人为的痕迹。
如书中写道“我爹嘿嘿笑了几下,笑完后闭上了眼睛,脖子一歪,脑袋顺着粪缸滑到了地上”“我离家两个月多一点,我娘就死了”“凤霞生下了孩子后大出血,天黑前断了气”。
事件的语言表述自然,却带领读者领略人生的悲怆,表现人类无边的苦难与艰难的生存困境。
作者书中描述的死亡意象是以否定的手法来肯定活着的意义。
福贵不断地失去亲人,这个过程是苦难的过程,实际上面对的是同一种威胁。
死亡意象写出了人生的痛苦和灾难,并通过这痛苦灾难的人生,以否定的形式来达到肯定活着的意义。
死亡描述使读者在情感的更高层次上获得一种美的再生的享受,更理解生与死的冲突:生命一方面抗拒着死亡,另一方面又不能拒绝死亡。
(完整word版)余华小说《活着》的象征意味

马健内容摘要:余华的小说《活着》语言简单直白、单纯质朴,由此却衍生出多重的象征意味.作品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抗争不止,在命运承受中包含着对生命执着追求的精神,以及儒道释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关键词:《活着》象征民族意识小说《活着》是20世纪文坛颇有影响的作家余华的代表作品。
余华评价这部小说时称:“我感到我写下了高尚的作品.”这部作品运用简洁、朴素的语言,讲述了福贵命运多舛的一生,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体现了作者对人生中关于生命意义,生存本质真谛的寻求与感悟,揭示了中国文化下的民族意识与生存哲学。
一.平实中的深邃意味《活着》中余华摒弃了先锋小说典雅诡秘、艰深难懂的语言,以简单直白、单纯质朴的语言取而代之,是余华重建日常语言秩序的界碑。
作家运用简洁朴素的语言文字,让读者去感受、猜测和想象潜藏在“冰山”下的巨大部分.作品中,作者叙述故事通过简洁的人物对话和细节行动,将人物的内心情感隐藏在文字的意象之下,让读者自己通过文字语言去慢慢体悟人物内心.句式上多用短句,不论人物对话还是其他语言,都很短促,从而通俗易懂。
如写有庆死的时候,对抽血、报丧、打医生,见到春生等情节没有大段的描写,而是用简朴的语言,平静的叙述。
通过简短的对话快节奏地展现一个个尖锐冲突的场景。
福贵的语言完全符合农民本色,是一种简单质朴的语言,同时质朴中见真理,如“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比喻的运用又是质朴语言的一大特色,比如“我知道他不会和我拼命了,可他说的话就像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脖子,脖子掉不下来,倒是疼得死去活来。
"小说运用独特的民间话语,彰显出浓郁的民间意味。
福贵一家的名字,“福贵、家珍、有庆、凤霞、二喜",无不寄托着作者对这些人美好的人生希望,然而,除福贵苦难地活着外,其他人无一不悲惨死去,这是反讽性叙述。
小说中还运用了大量的民间歌谣。
老年福贵在劳作中以粗哑的嗓音唱着“皇帝叫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
《活着》:思考人生与生存的意义

活着:思考人生与生存的意义概述《活着》是由中国作家余华创作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福贵的苦难人生经历。
小说通过描写福贵在逆境中求生存、寻找希望和思考人生意义的过程,深刻触动了读者。
本文将探讨《活着》这本书所呈现出来的人性、命运和生命意义等主题,以及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启示。
1. 人类在逆境中的顽强求生能力福贵面对各种残酷的环境和灾难,展现了人类在逆境中保持希望和勇气的能力。
他虽然失去了家庭、父母、妻子和孩子,但他仍然坚持活下去。
这揭示了人们的顽强求生本能以及对未来的渴望。
2. 生活中非物质价值远胜于物质财富福贵曾是一个富裕农户,但随着时光流转和政治变革,他失去了所有物质财富。
小说通过描写福贵在贫困中的生活,提出了对物质财富与幸福感的反思。
在逆境中,他发现身边最重要的是亲情、友情和人性的关怀。
3. 生命的意义探索小说通过福贵的经历,引发了读者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
人们常常迷失于物欲和功利之中,而在面临死亡时才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
《活着》提醒我们应该珍惜眼前拥有并认真思考存在的意义。
4. 觉醒与自我救赎小说中,福贵经历了一系列残酷事件后逐渐觉醒,并试图救赎自己过去所犯下的错误。
这给读者带来关于责任、罪恶和个人成长等方面的思考。
5. 社会与历史背景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活着》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下对普通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
政治革命、自然灾害和文化变革等因素深度影响了福贵和其他角色的命运。
•结论:《活着》通过揭示农民福贵的遭遇和求生之旅,启发人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观。
它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珍惜当下,关注非物质层面的价值,并思考自己在逆境中能否保持勇气和希望。
这本小说引发了读者对于生命、爱、幸福与痛苦等重要议题的深入思考。
以上就是关于《活着》:思考人生与生存的意义的内容编写。
通过描述小说中主角福贵所经历的艰辛与挣扎,探讨了人类在困境中探寻生活意义和追求自我救赎的主题。
对《活着》的深度解读

对《活着》的深度解读《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创作的一部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和个人命运的悲剧。
本文将对《活着》进行深度解读。
1. 主题与意义《活着》的主题是生命与命运。
通过讲述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小说揭示了个人在历史与社会环境下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残酷命运。
福贵在政治运动、自然灾害和家庭悲剧中屡遭打击,但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执着和对家人的爱。
小说通过福贵的命运反映了个人在社会变革中的无奈和力量的微弱。
《活着》的意义在于警示人们珍惜生命、关注社会变革对个人的影响,并思考人与命运的关系。
小说通过福贵的生活经历向读者传递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命运的思考,引发了人们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深思。
2. 文学手法与情感表达《活着》采用了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让读者能够直接感受到主人公的命运和情感。
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对比和象征手法,通过对福贵的痛苦经历和社会变革的描绘,传递了深刻的情感和思考。
作者还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细节的把握,使读者对福贵的遭遇和内心感受产生共鸣。
福贵的坚韧、爱与希望成为了读者情感上的触动点,引发了对生命的思考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3. 社会背景与历史意义《活着》发生在中国历史上动荡的时期,包括农民起义、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
小说通过福贵的命运展示了个体在这些大时代中所承受的痛苦和无奈。
福贵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经历了政治运动导致的家庭破碎、自然灾害带来的贫困和社会变革中的挣扎。
《活着》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意义在于揭示了个体在大时代中所遭受的苦难和困境。
小说通过反映福贵的命运,呼唤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历史的反思,以期引发人们对社会进步和个人命运的思考。
4. 人物形象与命运论述小说中的福贵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坚强的人物形象。
他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对生活和家人充满爱和责任感。
福贵的命运论述了个人对命运的无力和社会变革对个体的巨大影响。
福贵的命运也代表了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命运,通过他的故事,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个人在大时代中所承受的压力和困境,以及个人的力量和坚持。
余华小说《活着》的象征意味

现原先难 以表达 的对时代 真相 的
认 识 。 这 种 民 间 立 场 的 出 现 并 没
有 削 弱 知 识 分 子 批 判 立 场 的 深 刻
性 , 只 要 表 达 得 更 加 含 蓄 更 加 宽
阔 …… ” 余华从 民 间视 点叙述 了
福贵 经历 的各 个时代 主流 ,从 中
表现 了普通百姓 对待苦 难 的命 运
意 特点 的小 说 ,具 有 象 征 意 义 。作
品 的 开 头 ,作 者 写 “我 ”是 一 个 乡
下 采 风 的文 人 ,与 老 年 福 贵 相 遇 ,
从 而 引 Leabharlann 老 人 一 生 的 故 事 ,这 被
赋 予 了象 征 ,“用 ‘叙 述 一 个 老 百
姓 的故事 ’的认 识世界 态度 ,来表
溢 着 作 者 的 悲 悯 情 怀 ,使 读 者 情
不 自禁 地 被 感 动 。
余 华在 《虚 伪 的作 品 》中说 :
“
一
切 真 正 的 小 说 应 该 无 处 不 洋
溢着 象征 ,即我们寓 居世界 的方
式 的象征 ,我们理解 世界并 不与
世 界 打 交 道 的方 式 的象 征 。”…《活
学教 育
余华小说《活着》的象征 意 味
圃 马 健
内容摘要 :余华的小说《活着》语言简单直 白、单纯质朴,由此却衍生 出多重的象征意味。作 品体现 了中华 民 族在苦难 中抗 争不止 ,在命运承受 中包含着对 生命执着追求 的精神 ,以及儒道释 思想对 中国人的影响。
关 键 词 :《活 着》 象 征 民族 意 识
小 说 《活 着 》是 20世 纪 文 坛 颇 有 影 响 的作 家余华 的代 表作 品 。 余华 评价这部小 说 时称 :“我感到 我写 下 了 高 尚 的作 品 。”这 部 作 品 运 用 简 洁 、朴 素 的 语 言 ,讲 述 了福 贵 命 运 多 舛 的一 生 ,象 征 手 法 的 运 用 使 作 品 具 有 独 特 的 艺 术 魅 力 ,体现 了作者 对人生 中关于生 命 意义,生存 本质真谛的寻求 与感 悟 ,揭 示 了 中 国 文 化 下 的 民 族 意 识 与 生 存 哲 学 。
浅谈余华《活着》的生命观及“活着”的现实意义

内容提要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是一部用死亡讲述活着、以死亡肯定生命意义的故事,旨在使人勇敢地面对生与死的挑战。
作者以冷峻而貌似“残忍”的笔触向我们讲述了福贵一家人的苦难史与主人公福贵命运多舛的一生:从大富大贵到穷困潦倒,从饱尝生活艰辛到身不由己卷入战争洪流,从接受他的亲人一个个走在他的前头到最后与一头叫做“福贵”的老牛在阳光下回忆生活。
在厄运弥漫、磨难接踵而至的日子里,与福贵相关的人相继谢幕,唯有福贵在唱着主角之歌,始终乐观生活,超然面世,生命的张力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从而绽放出永不凋落的生命之花。
《活着》虽然接二连三地发生死亡,但作者不再沉溺于死亡的阴影中不能自拔,而将目光转向探求“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生命无常中人们彼此关爱相携,使人感受了生命的意义。
[1]“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2]‘活着’是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3]本文试以《活着》为研究对象,探析《活着》的生命观与“活着”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余华;活着;生命观;忍耐;现实意义绪论人,作为自然界生命的主体,其物质、精神生活、价值观也随着历史的更迭而发生变化。
摆在人们面前一个最普通也最原始的话题变得日益突出了,即我们应该抱着什么心态活着,怎样活着才更有意义?余华的《活着》将触角探伸到一个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历史氛围,将全部的不幸集中浓缩于主人公福贵一家身上,把对人生的痛苦加以延伸与夸张,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既真实可信又辛酸冷酷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笔下,福贵不单单是福贵了,而是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缩影。
作者有意淡化了“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背景,转而向我们讲述普通老百姓如何在悲惨的生活遭遇下,努力挣扎着生存,好好活着。
浅析余华长篇小说《活着》蕴含的人生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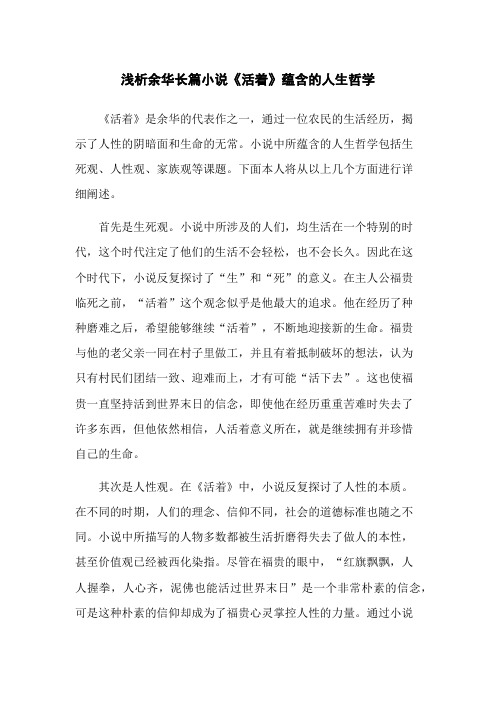
浅析余华长篇小说《活着》蕴含的人生哲学《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通过一位农民的生活经历,揭示了人性的阴暗面和生命的无常。
小说中所蕴含的人生哲学包括生死观、人性观、家族观等课题。
下面本人将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首先是生死观。
小说中所涉及的人们,均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这个时代注定了他们的生活不会轻松,也不会长久。
因此在这个时代下,小说反复探讨了“生”和“死”的意义。
在主人公福贵临死之前,“活着”这个观念似乎是他最大的追求。
他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希望能够继续“活着”,不断地迎接新的生命。
福贵与他的老父亲一同在村子里做工,并且有着抵制破坏的想法,认为只有村民们团结一致、迎难而上,才有可能“活下去”。
这也使福贵一直坚持活到世界末日的信念,即使他在经历重重苦难时失去了许多东西,但他依然相信,人活着意义所在,就是继续拥有并珍惜自己的生命。
其次是人性观。
在《活着》中,小说反复探讨了人性的本质。
在不同的时期,人们的理念、信仰不同,社会的道德标准也随之不同。
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多数都被生活折磨得失去了做人的本性,甚至价值观已经被西化染指。
尽管在福贵的眼中,“红旗飘飘,人人握拳,人心齐,泥佛也能活过世界末日”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信念,可是这种朴素的信仰却成为了福贵心灵掌控人性的力量。
通过小说中人物走出自己的世界,对外界世界的认识,对生命的重新认识和对人性的敬畏,来探讨人性的本质,由此影射出当代人性存在的不少问题。
生死之交、爱恨情仇,甚至家庭矛盾等,都在小说人物的行为中得到了多方位的呈现。
这其中,包含了人性深层次的探讨和社会文化深层次的剖析。
再次是家族观。
《活着》中,家族观成为了整个小说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在这种大背景下,人们充满了家族观。
无论是福贵的父亲,还是福贵本人,尽管事情的发展都是逆着他们跑的,但他们对家族的责任感和之间的情感,却从始至终得到了表达。
在贵福的心中,靠着老父亲和祖传宗教的心灵支撑,小小的家庭成为了他心中最坚强的防火墙。
小说解读活着中的人生哲理与社会批判

小说解读活着中的人生哲理与社会批判《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的经典小说之一,通过讲述主人公福贵的一生经历,深刻揭示了人生的哲理和对社会的批判。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解读《活着》中所体现的人生哲理和社会批判,并探究其对读者的启示与反思。
一、生命的可贵和坚韧的意志力《活着》以福贵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展现了生命的宝贵与坚韧的意志力在面对困境中的重要性。
小说中,福贵虽然经历了家族的衰落、妻子的离世、儿女的去世等一系列不幸,但他能够在亲人离世的痛苦中坚持生活下去。
在这过程中,福贵通过努力种地和坚持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福贵的坚韧意志和对生命的珍视告诉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不懈、不屈不挠,才能克服困难,活出自己的价值。
二、人性的复杂性与善恶之间的矛盾《活着》中还聚焦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善恶之间的矛盾。
小说中的福贵经历了贫穷、疾病和人生的不完整,他在生活的压力下,在敌对环境的侵害下,逐渐变得冷酷和无情。
但同时,福贵还保持着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牵挂。
在他走出生活的低谷后,他发现生命中的善良和爱彼此交织,不可分割。
通过这样的角度,小说告诉我们人性是复杂的,人们常常在复杂的生存环境中面对善恶之间的抉择。
因此,我们应该在善良和爱的引导下,坚持正确的价值观,避免内心的扭曲和堕落。
三、社会制度的残酷性和人性的虚伪《活着》对社会制度的残酷性和人性的虚伪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封建制度下的农民,在生活的底层挣扎求生,被剥削和压迫。
福贵的家族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下逐渐衰败,而不少人失去生命。
而在面对这种悲剧的同时,小说也揭示了人性的虚伪。
当时政治斗争激烈的年代里,人们的善恶行为常常被政治压力所左右。
无论是地主、豪绅,还是平民百姓,都被迫为了生存选择出卖良心、背叛朋友。
小说透过这些细节,提醒我们社会制度的残酷性和人性的虚伪,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现实社会中的不公和人性的堕落。
四、珍惜现实生活,追求心灵的自由《活着》最后让读者明白,生命的经历既是困苦的,也是悲壮的。
论《活着》的意义

《活着》如此艰难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我们品味社会品味人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余华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语言风格独树一帜。
《活着》是我在大一时读的,不可说记忆深刻,不管余华给富贵什么不幸,但是却深深地触动了活着的人。
《活着》却不是用如何克服困难、战胜生命的坚强活着,而是用“死亡”这一主题给我们讲述了人生要如何活着如何不死。
透过《活着》,我们得以透视到人生的许多问题。
“活着”意味着什么?如何在苦难中找到支撑点?作品《活着》以其独特的方式——死亡,来告诉人们什么是“活着”。
读这部作品,从进入故事到体验其中生活再到体会人生意义,相当于完成了一次人生经历。
《活着》以福贵身边的亲人不断死亡的事件来构架全文。
福贵曾是一个家有良田百亩的地主少爷,同时也是一个浪荡子、败家子。
他将田产和房屋全部输在牌桌上,将父亲活活气死。
当他洗心革面准备重新生活时却被抓了壮丁一去数年。
在这期间母亲撒手西去。
归家后他与家人安心活命,虽苦亦其乐融融。
但变故接二连三:妻子家珍患了软骨病卧床不起,儿子有庆为校长献血被过度抽血致死,家珍受不住这沉重打击凄然离世。
女儿凤霞因病致哑,她好不容易找了个贴心丈夫,却死于难产。
女婿二喜在上班时又死于意外事故。
爷孙俩艰难度日,孙子苦根又因吃多了豆子被撑死。
到头来,福贵孑然一人,形影相吊,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小说除了中途一次时空转换(由福贵作为叙述人回到“我”作为叙述人)外,没有什么可用来缓释这些犀利的非正常死亡给人造成的沉重压抑。
福贵的一生就是一部灾难与苦痛的历史,他命运多舛经历种种世事变迁,心中伤痕历历在目,但外在的死亡体验不断重复,他内心的死亡感受却越来越轻飘空灵,直至进入一种淡泊宁静的境地。
论余华小说活着意象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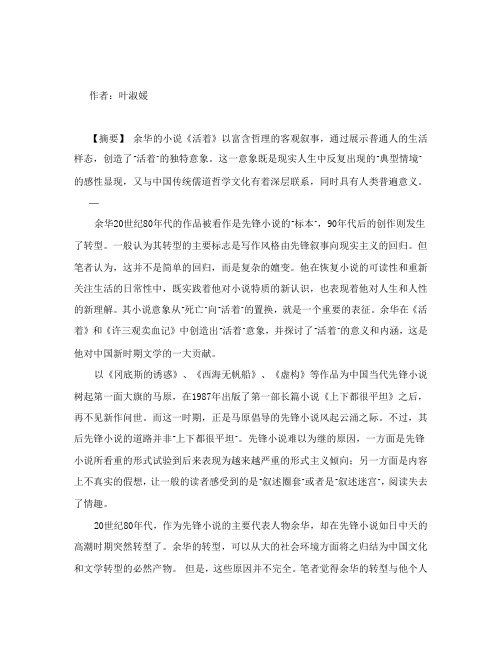
作者:叶淑媛【摘要】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富含哲理的客观叙事,通过展示普通人的生活样态,创造了“活着”的独特意象。
这一意象既是现实人生中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的感性显现,又与中国传统儒道哲学文化有着深层联系,同时具有人类普遍意义。
—余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被看作是先锋小说的“标本”,90年代后的创作则发生了转型。
一般认为其转型的主要标志是写作风格由先锋叙事向现实主义的回归。
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复杂的嬗变。
他在恢复小说的可读性和重新关注生活的日常性中,既实践着他对小说特质的新认识,也表现着他对人生和人性的新理解。
其小说意象从“死亡”向“活着”的置换,就是一个重要的表征。
余华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创造出“活着”意象,并探讨了“活着”的意义和内涵,这是他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大贡献。
以《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等作品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树起第一面大旗的马原,在1987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之后,再不见新作问世。
而这一时期,正是马原倡导的先锋小说风起云涌之际。
不过,其后先锋小说的道路并非“上下都很平坦”。
先锋小说难以为继的原因,一方面是先锋小说所看重的形式试验到后来表现为越来越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是内容上不真实的假想,让一般的读者感受到的是“叙述圈套”或者是“叙述迷宫”,阅读失去了情趣。
20世纪80年代,作为先锋小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余华,却在先锋小说如日中天的高潮时期突然转型了。
余华的转型,可以从大的社会环境方面将之归结为中国文化和文学转型的必然产物。
但是,这些原因并不完全。
笔者觉得余华的转型与他个人的成长、成熟的关系更大。
他的先锋小说《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等作品中血腥的“暴力写作”和残酷的“死亡叙述”是少年不成熟的心态对社会的不信任,对现实的激愤,因此他着力于探讨死亡,营造了整体“死亡”意象,表达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关怀。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作者:叶淑媛【摘要】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富含哲理的客观叙事,通过展示普通人的生活样态,创造了“活着”的独特意象。
这一意象既是现实人生中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的感性显现,又与中国传统儒道哲学文化有着深层联系,同时具有人类普遍意义。
—余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被看作是先锋小说的“标本”,90年代后的创作则发生了转型。
一般认为其转型的主要标志是写作风格由先锋叙事向现实主义的回归。
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复杂的嬗变。
他在恢复小说的可读性和重新关注生活的日常性中,既实践着他对小说特质的新认识,也表现着他对人生和人性的新理解。
其小说意象从“死亡”向“活着”的置换,就是一个重要的表征。
余华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创造出“活着”意象,并探讨了“活着”的意义和内涵,这是他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大贡献。
以《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等作品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树起第一面大旗的马原,在1987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之后,再不见新作问世。
而这一时期,正是马原倡导的先锋小说风起云涌之际。
不过,其后先锋小说的道路并非“上下都很平坦”。
先锋小说难以为继的原因,一方面是先锋小说所看重的形式试验到后来表现为越来越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是内容上不真实的假想,让一般的读者感受到的是“叙述圈套”或者是“叙述迷宫”,阅读失去了情趣。
20世纪80年代,作为先锋小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余华,却在先锋小说如日中天的高潮时期突然转型了。
余华的转型,可以从大的社会环境方面将之归结为中国文化和文学转型的必然产物。
但是,这些原因并不完全。
笔者觉得余华的转型与他个人的成长、成熟的关系更大。
他的先锋小说《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等作品中血腥的“暴力写作”和残酷的“死亡叙述”是少年不成熟的心态对社会的不信任,对现实的激愤,因此他着力于探讨死亡,营造了整体“死亡”意象,表达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关怀。
当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侧重于从死亡角度探讨生死母题的特色,对特别喜欢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罗伯一格里耶等人的余华来说,对他的创作影响十分深远。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余华那少年的反叛和冲动逐渐平息,目光中多了一些温情,相应地在创作中得到表现。
1991年发表的《呼喊与细雨》虽然抒发的主要还是无奈的“绝望”情怀,但多少已经有了些温情。
一般认为这部作品是余华写作转型的标志。
其后,余华“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时”,发现生活的真谛不是其他,而是活着。
于是,“活着”成为余华《活着》(1992年)和《许三观卖血记》(1995年)这两部作品的核心哲学,也是这两部作品的哲学意象。
而且,当余华进一步审视“活着”的内在力量时,他不自觉地从西方死亡哲学回归到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精神;从建构“死亡”意象转向“活着”意象内蕴的探讨;写作风格从“先锋”向“写实”回归。
因此,余华的写作转向是一种从形式到内容的复杂嬗变,是一种必然,这其中有余华对文学的重新理解。
在这样的转变中,余华为自己的创作找到了新的文化根基——回归民族精神。
“……90年代先锋小说走向民族精神史,回归故事,从自恋情结走向社会民族历史,这无疑是成熟和进步的迹象。
”余华的独特和贡献则是在民族精神史的回归中提出了“活着”意象,以此来思考民族、甚至人类的生存意义。
二余华由“先锋”转向“写实”,写下《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作品时,内心才真正地敞开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自己置身于发现之中,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灵感这时候才会突然来到。
”余华所说的“发现”就是“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因此而呈现出一种坚毅的具有民族精神史性质的“活着”的内在力量,充满了温情的舒展和对小人物苦难命运的悲悯与同情。
《活着》的主人公叫福贵,年轻时家道殷实,但他吃喝嫖赌,输光了家产,父亲气闷而死。
不久,母亲操劳成疾,福贵去县城给母亲抓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差点送了命。
回到家时,母亲已经离世。
十几年后,儿子有庆抽血过量而死,又聋又哑的女儿凤霞结婚一年难产身亡,妻子家珍故去,女婿二喜意外致死,七岁的外孙苦根多吃了豆子胀死,老来的福贵只有和那头也叫“福贵”的老牛作伴。
《活着》充满了中国道家庄周文化生命哲学的意味。
庄子将人生际遇中个人不能抗拒的遭遇,统称为“命”。
他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无也,人之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庄子·大宗师》)“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庄子·达生》)“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庄子·德充符》)《活着》中,福贵的亲人一个个死去,以赌博赢走了福贵家产的龙二被人民政府杀了头,作为人民政府县长的春生却也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死,被迫害而死去。
在福贵看来,这一切都是命,是不可把握、不可抗拒的。
福贵虽然也有过痛苦,但最终将一切的苦难和悲痛化解在忍耐和对“命”的顺从之中,表现出一种义无反顾的生活、尽其可能的生活的忍耐和勇气。
这种忍耐和顺从,就是庄子所说的“县解”。
《庄子·养生主》讲了一个故事:老聃死了,他的朋友秦失来吊唁,哭了三声就出来了,有人怪他对朋友没有感情,秦失说:我看见有些人在那里哭得很悲痛,这是“遁天倍情,忘其所爱,古者谓之遁天之刑。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
”意思是说,一个人的生,是由于偶然的机会,他的死,是顺遂自然的规律。
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对于死有过分的悲痛,这种悲痛,来源于要逃避自然规律,因此要受一种刑罚。
这种刑罚叫遁天之刑。
其内容就是那个“悲痛”。
遵循生死的自然规律,没有过度的悲愤,也没有过度的狂喜,就可以不受这种刑罚,从这种刑罚中解放出来,称为“县解”,“县”就是那种刑罚。
人在世界上活着,是一个过程,“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福贵经历的苦难足以让他失去活着的勇气和意志,但是福贵没有放弃生命,他以“县解”超越了苦难,培育了活着的乐观、平和与豁达,到了晚年再一次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中。
“在这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活了似地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
他赶着名字也是“福贵”的老牛犁地,自鸣得意地唱着“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的歌谣,直到炊烟袅袅升起时,在霞光四射中唱着歌归去。
这种超然物外的状态,几乎达到了庄子所说的“齐生死”(生与死没什么区别)的境界。
福贵的“活着”告诫人们清醒地面对命运,不要因为现实的残酷就弃世,而是顺遂自然。
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县解”,对死亡的抗争和嘲弄,而且也是热爱生命,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对人自身的重视。
《活着》的深刻之处还在于用福贵的“活着”反思了乡土中国民间普遍的生存状态。
《活着》开头说:“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回归民间的叙述立场。
“我”见到的乡间生活弥漫着生命的自然状态。
在这样的乡间,“我”碰见了福贵赶着牛耕地。
在与福贵的攀谈中,“我”看到了乡间真正的生存图景,那就是历尽苦难之后的一种逍遥自在:“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只牛不耕田”的自然生命状态。
作为这幅生存图景中的主角一“福贵们”这样的民间小人物可能不知道庄子为何人,有什么思想,但是在民间的自在状态中,顺从自然,消解了苦难,不自觉地实践着一种“活着”状态一与大道自然合为一体,悠然自得于天地万物之间,保持生命的至真至纯,也不去刻意追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而是在“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的坚韧中,显示出生命的精神重量。
实际上,福贵不是一个人的形象,他应该是成千上万忍受苦难、最终随顺自然的中国农民的形象,他的“活着”状态也是乡土中国“活着”状态的写照。
所以,作者说“当我望着到处都充满绿色的土地时,我进一步明白庄稼为何长得如此旺盛。
”这个隐喻是对民间原始、纯朴、自然以及永恒不灭的生命力的赞美。
可以说,“这部只有十二万字的长篇并不追求浓墨重彩的史诗性展示,还反其道行之而刻意突出了个人命运和细碎生活:就刻画了福贵等几个民间人物,就描述了一些凡俗生活。
但于平凡中达到奇妙效果,几近写出了一种民族苦难史和民族生命力。
”《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转型后的另一部杰作,同样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求生的乐观态度和“活着”的坚韧与力量。
不同之处是《活着》更多地以人对苦难的忍受和超越来表达生命的坚忍,活着的精神重量,《许三观卖血记》则更多地表现了人对苦难的承受和化解,以及“爱人”的精神光辉。
许三观这个丝厂茧工一生共有12次卖血的经历,从最初学会卖血到老年之后卖血未果,他有9次卖血是为了“活着”。
为娶妻成家,为缓解遭人耻笑的精神痛苦而荒唐地报复,为赔偿方铁匠儿子的医疗费,为在全民大饥荒的时期全家度过难关,为儿子的生活和工作,为给儿子治病……许三观只有以卖血解除一次次苦难,来实现生存困境中的自我救赎。
许三观活得那么艰难,特别在那荒谬的年代,他承受的煎熬和蹂躏更为残酷,让人有太多的哀痛和悲悯。
但让人更加动心的是许三观对于苦难的担当,以及自损而救人及自救去化解苦难的行动中闪现出的“仁”的光辉,这让他朴质忠厚、甚至近乎麻木的生命体现出一种神圣和崇高。
“仁”最简单的表述是:爱人。
这是儒家人际交往、处理家族内和家族间关系的准则,也是种种人际关系的调节器。
仁学精神哺育了中国民众的人性自觉和人道情感的本体追求。
许三观作为一个小人物,从来没有在理论上系统地接受过仁学思想的教育,却在具体的实践中把“仁”作为“活着”的信条和价值。
他关爱周围的每个人:让他受到羞辱做了“乌龟”的妻子,三个儿子(即使大儿子一乐不是自己亲生,他一面为此耿耿于怀,一面却因为一乐卖了6次血,其中后4次是“一路卖血去上海”救一乐的命,却差点搭上了自己的命),情人林芬芳(为了报复妻子与其有一次私情,许三观用卖血来报答),甚至情敌何小勇(为了能挽救他的性命,许三观不计前嫌让一乐给何小勇“喊魂”)……当他年老卖血卖不出去时,他哭着说:“我老了,我以后不能再卖血了,我的血没人要了,以后家里遇上灾祸怎么办……”这是一种失去了化解生活灾难的能力以及“爱人”的能力衰弱的失落和悲叹。
有了“仁爱”的支撑,许三观才没有在生存压力下垮塌。
他以卖血来对抗强大的历史、生活的暴力和苦难,这是何其惨烈的抗争?特别是他一路卖血去上海救一乐,又是多么惊人心魄的壮举。
生命要承受许许多多的苦难,人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怎样活着?许三观告诉我们:那就是以执著和坚忍化解苦难,实现个体生存的自救,以“爱人”作为活着的价值。
在中国民间,有许多“许三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