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史概述 中世纪的音乐
浅谈西方音乐史中世俗音乐的发展

浅谈西方音乐史中世俗音乐的发展中世纪是西方音乐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世俗音乐发展的关键阶段。
在中世纪,世俗音乐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多样化和丰富多彩的特点。
本文将从中世纪世俗音乐的起源、发展和特点等方面进行浅谈。
中世纪世俗音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
在古希腊,有雅典时代的抒情歌曲、琴曲以及巴瑟琴音乐等等。
而在罗马,有庆祝活动中所演奏的乐曲,其中包括世俗乐曲。
这些古代音乐的影响,为中世纪世俗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世俗音乐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民间音乐和宫廷音乐两个方面。
民间音乐是中世纪世俗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由普通民众创作和演唱的音乐形式,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情感和信仰等。
在中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民间音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些宗教节庆和民间传统活动中的吟唱和歌舞,成为了民间音乐的重要表现形式。
一些民间艺人如吟游诗人和民间乐师,也为民间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们通过吟唱和演奏,将人们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转化为音乐作品,使民间音乐逐渐取得了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宫廷音乐是中世纪世俗音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它是由贵族和统治者委派演奏和表演的音乐形式,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难度。
宫廷音乐在中世纪欧洲的宫廷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推广。
尤其是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国家,宫廷音乐达到了鼎盛时期。
宫廷音乐通常是由合唱团和乐队演奏,内容包括舞曲、歌曲和器乐等。
这些音乐作品既有宗教题材,也有爱情、战争和骑士精神等世俗题材。
宫廷音乐的发展,不仅反映了贵族阶层的审美情趣,也推动了西方音乐艺术的演进。
中世纪世俗音乐注重旋律的优美和流畅。
由于中世纪时期音乐制度的限制,旋律成为了世俗音乐中最重要的要素。
旋律优美、动人,成为了中世纪世俗音乐的鲜明特点。
中世纪世俗音乐注重节奏的鲜明和多样化。
中世纪时期,音乐节奏的变化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世俗音乐中,鼓点和舞曲的节奏变化较大,为音乐增添了活力和动感。
中世纪音乐史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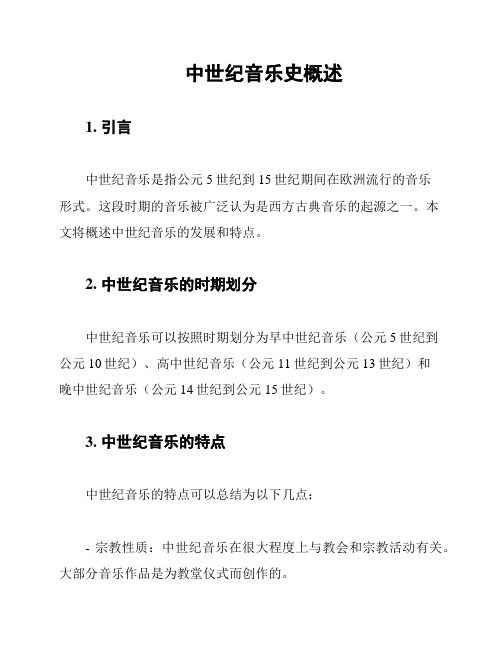
中世纪音乐史概述1. 引言中世纪音乐是指公元5世纪到15世纪期间在欧洲流行的音乐形式。
这段时期的音乐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古典音乐的起源之一。
本文将概述中世纪音乐的发展和特点。
2. 中世纪音乐的时期划分中世纪音乐可以按照时期划分为早中世纪音乐(公元5世纪到公元10世纪)、高中世纪音乐(公元11世纪到公元13世纪)和晚中世纪音乐(公元14世纪到公元15世纪)。
3. 中世纪音乐的特点中世纪音乐的特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宗教性质:中世纪音乐在很大程度上与教会和宗教活动有关。
大部分音乐作品是为教堂仪式而创作的。
- 口传传播:在中世纪,音乐主要是通过口头传统而不是书面传承来传播的。
这使得音乐的保存和传承变得更具挑战性。
- 旋律简单:中世纪音乐的旋律通常相对简单,以单声部演唱为主。
和声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得到广泛使用。
- 节奏规律:中世纪音乐的节奏规律通常是规则和重复的,以适应宗教仪式的需要。
- 音色和乐器:中世纪音乐主要使用人声来演唱,或者伴以一些简单的乐器如长笛、竖琴等。
4. 中世纪音乐的类型中世纪音乐涵盖了许多不同的类型,其中最重要的几个类型包括:- 圣歌:宗教性质的歌曲,用于教堂仪式和庆典活动。
- 民歌:民间流行的歌曲,通常由普通人创作和演唱。
- 舞曲:用于欢庆和社交活动的歌曲和舞蹈音乐。
5. 中世纪音乐的影响中世纪音乐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为西方古典音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影响了现代流行音乐的发展。
结论中世纪音乐是一个丰富多样且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音乐时期。
它不仅是西方古典音乐的起源,而且对整个音乐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应该珍视和研究这段宝贵的音乐史。
西方音乐史各时期音乐风格

西方音乐史各时期音乐风格西方音乐史各时期音乐风格古希腊和古罗马音乐风格: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音乐主要用于宗教仪式和战争激励。
古希腊音乐注重旋律与节奏的结合,使用了各种乐器,如独奏乐器、吹奏乐器和弹拨乐器。
而古罗马音乐受古希腊音乐的影响,但更加注重音乐的表演和娱乐性。
中世纪音乐风格:中世纪音乐主要是宗教音乐,以教会颂歌为主要形式。
教会颂歌分为声乐和无伴奏合唱两种形式,以拉丁文演唱。
此外,也有民间音乐形式,如吟唱诗歌和舞曲。
文艺复兴音乐风格: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注重和声的发展,以多声部合唱音乐为主。
器乐音乐也开始兴起,多使用键盘乐器和弦乐器。
此时期的音乐作品有较为复杂的结构和和声,代表作品有多声部合唱作品。
巴洛克音乐风格:巴洛克音乐追求华丽、夸张的表现形式,注重音乐的装饰性和复杂性。
巴洛克音乐中经常使用富有装饰性的滑音和急速的音乐变化。
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代表作品有巴赫的管风琴曲和手风琴协奏曲。
古典音乐风格:古典音乐注重音乐的平衡和对称,强调清晰的结构和简洁的表达。
古典音乐中常见的形式有奏鸣曲、交响曲和协奏曲等。
此时期的音乐作品被认为是西方音乐的经典之作,代表作家有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等。
浪漫音乐风格:浪漫音乐强调情感表达和个人创作,注重音乐的主观性和个性化。
浪漫音乐中常见的形式有交响诗、室内乐和歌曲等。
浪漫音乐时期的代表作曲家有舒曼、肖邦和柴可夫斯基等。
现代音乐风格:现代音乐追求创新和实验,注重音乐的表现力和自由性。
现代音乐中常见的形式有序列音乐、电子音乐和即兴音乐等。
现代音乐代表作家有斯特拉文斯基、韦伯恩和斯托克豪森等。
本文档涉及附件:1. 《古希腊音乐样例》2. 《中世纪音乐合集》3. 《文艺复兴音乐选集》4. 《巴洛克音乐精选》5. 《古典音乐经典作品集》6. 《浪漫音乐世纪盛宴》7. 《现代音乐创新之旅》本文涉及的法律名词及注释:1. 著作权法:保护音乐作品的创作权和表演权。
2. 版权:音乐作品的独占权,包括原创作品和改编作品。
高中一年级音乐教案西方音乐史概述

高中一年级音乐教案西方音乐史概述一、引言西方音乐史是音乐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了解西方音乐史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音乐的发展脉络,提高音乐鉴赏能力。
本教案将概述西方音乐史的主要时期和代表性作曲家,为学生打下音乐历史的基础。
二、古希腊罗马时期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音乐史的起源。
古希腊和罗马人对音乐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古希腊的音乐主要是合唱和器乐,而罗马则更加注重音乐的宫廷艺术性和娱乐性。
三、中世纪音乐中世纪音乐是指公元5世纪至公元15世纪的音乐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的音乐主要是教会音乐,宗教赋予了音乐非常重要的地位。
著名的中世纪音乐包括格里高利圣咏、祈祷赞歌等。
这些音乐风格简单,以宗教性质为主。
四、文艺复兴时期音乐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音乐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音乐开始与人文主义运动相结合。
作曲家们开始尝试创作各种声乐作品,如宗教合唱、歌剧、马德里哲理剧等。
著名的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有帕勒斯特里纳、蒙台威奇等。
五、巴洛克时期音乐巴洛克时期是西方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音乐以庄重和华丽为特点。
巴洛克音乐注重音乐和故事的结合,强调曲式和对位法的运用。
著名的巴洛克时期作曲家有巴赫、亨德尔等。
六、古典时期音乐古典时期是西方音乐史上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的音乐更加注重对称与平衡的构思,节奏更加统一。
古典时期作曲家们创作的音乐通常具有旋律优美、曲式清晰的特点。
著名的古典时期作曲家有莫扎特、贝多芬等。
七、浪漫时期音乐浪漫时期音乐在古典时期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注重情感表达和音乐故事的叙述。
这个时期的音乐更加富于创造力和个性化,使用的乐器也更加多样化。
著名的浪漫时期作曲家有肖邦、舒伯特等。
八、现代音乐现代音乐是指20世纪初至今的音乐发展阶段。
现代音乐以多样性和实验性为特点,包括了各种流派和风格,如爵士乐、摇滚乐、电子音乐等。
著名的现代音乐作曲家有斯特拉文斯基、科布郎等。
九、总结通过对西方音乐史的概述,我们可以了解到音乐发展的脉络和不同时期的特点。
浅谈西方音乐史中世俗音乐的发展

浅谈西方音乐史中世俗音乐的发展中世纪是西方音乐史中一个关键的时期,它标志着音乐从教堂圣诗逐渐走向了世俗化。
在这个时期,音乐的地位和功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本文将通过对中世纪西方音乐史中世俗音乐的发展进行浅谈,以揭示这一时期音乐的特点和影响。
从时间上来看,中世纪西方音乐史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早期中世纪(公元5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中世纪(公元11世纪至公元13世纪)和后期中世纪(公元14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三个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中,中世俗音乐逐渐从教堂音乐中独立出来,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并且在音乐形式、曲调和演奏风格上都有了自己的特点。
早期中世纪是基督教在西方传播初期,音乐主要是在教堂中演奏。
这个时期的音乐主要是由教士和修道院的修道士演奏,用来赞美上帝和进行宗教仪式。
早期中世纪的教堂音乐以圣咏为主,曲调简单,节奏慢悠扬,多为单音旋律,没有和声伴奏。
这种音乐形式反映了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具有严肃、庄重的特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中期中世纪的音乐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这个时期,贵族和王室开始在宫廷和卡佩拉等场合中进行大型的音乐演奏活动。
这些演奏活动包括吟唱、舞蹈和乐器演奏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中期中世纪的世俗音乐开始有了独立的发展方向,逐渐走出教堂,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
在这个时期,世俗音乐的曲调更加复杂多变,节奏更加活泼欢快,多为多声部合唱,并且开始出现了和声伴奏。
这种音乐形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丰富,具有欢乐、放松的特点。
中世纪西方音乐史中世俗音乐的发展不仅在音乐形式上有所变化,还在音乐功能和影响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世世俗音乐的发展使得音乐逐渐独立出教堂,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
它也促进了社交和娱乐活动的进行,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俗音乐的发展还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现代音乐的诞生埋下了种子。
中世纪西方音乐史中世俗音乐的发展标志着音乐从教堂走向了世俗化。
大学音乐易考知识点西方古典音乐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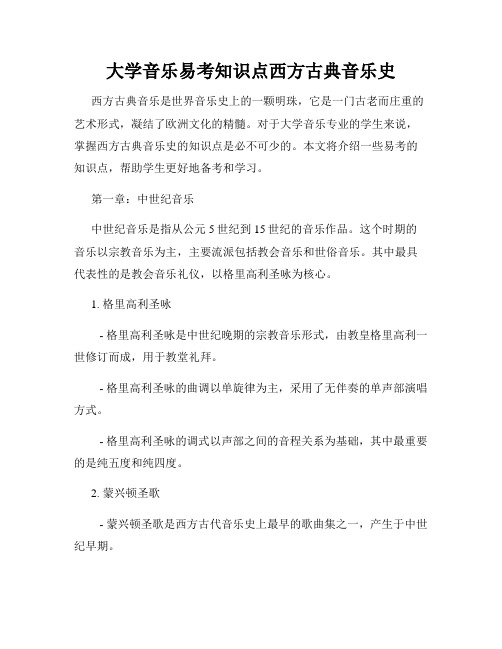
大学音乐易考知识点西方古典音乐史西方古典音乐是世界音乐史上的一颗明珠,它是一门古老而庄重的艺术形式,凝结了欧洲文化的精髓。
对于大学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掌握西方古典音乐史的知识点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将介绍一些易考的知识点,帮助学生更好地备考和学习。
第一章:中世纪音乐中世纪音乐是指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的音乐作品。
这个时期的音乐以宗教音乐为主,主要流派包括教会音乐和世俗音乐。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教会音乐礼仪,以格里高利圣咏为核心。
1. 格里高利圣咏- 格里高利圣咏是中世纪晚期的宗教音乐形式,由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修订而成,用于教堂礼拜。
- 格里高利圣咏的曲调以单旋律为主,采用了无伴奏的单声部演唱方式。
- 格里高利圣咏的调式以声部之间的音程关系为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纯五度和纯四度。
2. 蒙兴顿圣歌- 蒙兴顿圣歌是西方古代音乐史上最早的歌曲集之一,产生于中世纪早期。
- 蒙兴顿圣歌包含了大量的宗教诗歌,歌词内容涉及信仰、赞美和祷告。
- 蒙兴顿圣歌的曲调简单而庄重,采用了无伴奏的单声部演唱方式。
第二章:文艺复兴音乐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音乐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音乐风格呈现出了追求和声和人声多样化的特点。
以下是文艺复兴音乐的知识点:1. 马德里圣歌书- 马德里圣歌书收录了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期的一批宗教音乐作品,是文艺复兴音乐的重要代表。
- 马德里圣歌书的音乐特点是多声部的合唱和丰富的和声结构。
- 马德里圣歌书中的音乐作品主要分为圣诗和圣颂两类,歌词内容涉及赞美、祷告和宗教教义。
2. 麦诺特圣歌集- 麦诺特圣歌集是16世纪最重要的宗教音乐集之一,由佛蒙特勒修士创作和整理。
- 麦诺特圣歌集的音乐风格注重和声的平衡和和谐,且多用于教堂礼拜和宗教庆典。
- 麦诺特圣歌集中的音乐作品采用了多声部的合唱形式,歌词内容涉及信仰、教义和赞美。
第三章:巴洛克音乐巴洛克音乐时期是西方古典音乐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个时期的音乐作品具有复杂的和声结构和热情奔放的情感表达。
初中音乐西方音乐的发展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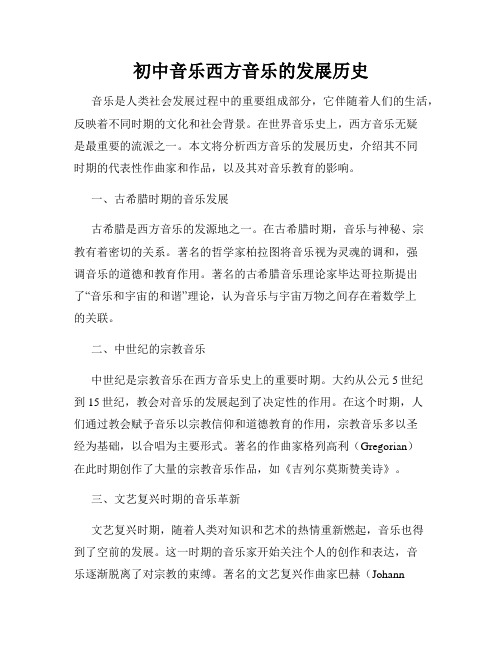
初中音乐西方音乐的发展历史音乐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反映着不同时期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在世界音乐史上,西方音乐无疑是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本文将分析西方音乐的发展历史,介绍其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曲家和作品,以及其对音乐教育的影响。
一、古希腊时期的音乐发展古希腊是西方音乐的发源地之一。
在古希腊时期,音乐与神秘、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将音乐视为灵魂的调和,强调音乐的道德和教育作用。
著名的古希腊音乐理论家毕达哥拉斯提出了“音乐和宇宙的和谐”理论,认为音乐与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数学上的关联。
二、中世纪的宗教音乐中世纪是宗教音乐在西方音乐史上的重要时期。
大约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教会对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人们通过教会赋予音乐以宗教信仰和道德教育的作用,宗教音乐多以圣经为基础,以合唱为主要形式。
著名的作曲家格列高利(Gregorian)在此时期创作了大量的宗教音乐作品,如《吉列尔莫斯赞美诗》。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革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类对知识和艺术的热情重新燃起,音乐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音乐家开始关注个人的创作和表达,音乐逐渐脱离了对宗教的束缚。
著名的文艺复兴作曲家巴赫(JohannSebastian Bach)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赋格曲》等至今仍是西方音乐的经典之作。
四、巴洛克时期的华丽音乐巴洛克时期是西方音乐史上最具特色的时期之一,它的特点是复杂的编曲和华丽的音乐表达。
这一时期的音乐既展示了作曲家的个人技巧,又表达了时代的荣耀和豪华。
代表作曲家包括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和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他们的音乐作品充满了激情、力量和表现力。
五、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创新古典主义时期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音乐发展时期,它以对称、平衡、规则为特点。
在这一时期,音乐开始注重对表现力和结构的细致研究。
浅谈西方音乐史中世俗音乐的发展

浅谈西方音乐史中世俗音乐的发展西方音乐史中世俗音乐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并经历了漫长而富有变化的历程。
在此过程中,世俗音乐在社会文化和艺术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塑造了西方音乐的面貌。
中世纪的世俗音乐主要是由民间流行歌曲和宫廷音乐所组成。
民间流行曲是通过口头传统流传下来的,通常是由普通人演唱和创作的。
这些歌曲通常讲述了爱情、战争、宗教和社会等各种主题,是人们生活经验的反映。
宫廷音乐则是在贵族社会和皇室宫廷中演唱和演奏的音乐作品,以优雅和高尚的格调而闻名。
宫廷音乐通常由专业音乐家创作和演奏,内容涵盖了各种主题,包括宗教、战争、政治和娱乐等。
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世俗音乐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世俗音乐的创作和演奏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推崇。
作曲家开始独立创作世俗音乐,并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
世俗音乐在这个时期的内容和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包括歌曲、舞蹈音乐、奏鸣曲等。
音乐家和歌手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他们在宫廷和市民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增加。
巴洛克时期是世俗音乐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
在这个时期,音乐开始变得复杂和技术化,作曲家开始探索更深入的音乐表达方式。
世俗音乐的形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如歌剧、室内乐和交响乐等。
巴洛克时期的世俗音乐充满了热情、戏剧性和表演性,对后世的音乐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主义时期是世俗音乐的又一重要阶段。
在这个时期,音乐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世俗音乐的表演和欣赏成为了社交活动的一部分。
作曲家开始创作更加严谨和精致的音乐作品,音乐的调性和结构得到了更加精确和完善的处理。
交响乐团和歌剧院的建立也为世俗音乐的演奏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浪漫主义时期是世俗音乐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的世俗音乐充满了激情、个性和表达力,作曲家开始追求个人的音乐创作风格,并通过音乐表达内心情感和情绪。
世俗音乐的形式和结构变得更加自由和灵活,作品常常以叙事性和戏剧性为特点。
这个时期的世俗音乐对后世的音乐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西方音乐史话(五)中世纪音乐——世俗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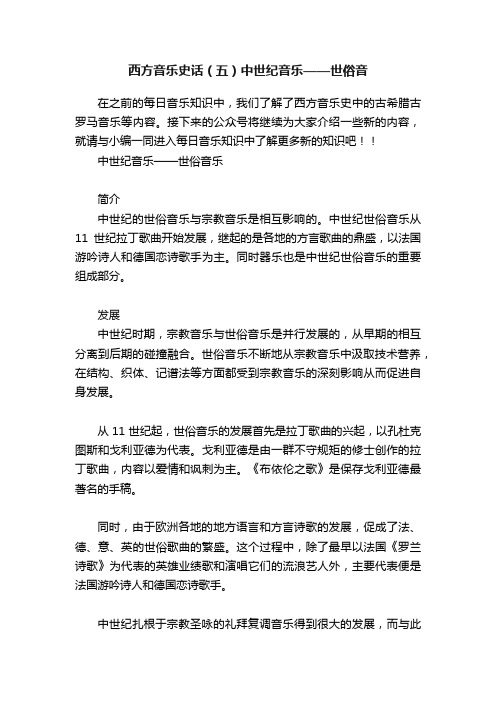
西方音乐史话(五)中世纪音乐——世俗音
在之前的每日音乐知识中,我们了解了西方音乐史中的古希腊古罗马音乐等内容。
接下来的公众号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新的内容,就请与小编一同进入每日音乐知识中了解更多新的知识吧!!
中世纪音乐——世俗音乐
简介
中世纪的世俗音乐与宗教音乐是相互影响的。
中世纪世俗音乐从11世纪拉丁歌曲开始发展,继起的是各地的方言歌曲的鼎盛,以法国游吟诗人和德国恋诗歌手为主。
同时器乐也是中世纪世俗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
中世纪时期,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是并行发展的,从早期的相互分离到后期的碰撞融合。
世俗音乐不断地从宗教音乐中汲取技术营养,在结构、织体、记谱法等方面都受到宗教音乐的深刻影响从而促进自身发展。
从11世纪起,世俗音乐的发展首先是拉丁歌曲的兴起,以孔杜克图斯和戈利亚德为代表。
戈利亚德是由一群不守规矩的修士创作的拉丁歌曲,内容以爱情和讽刺为主。
《布依伦之歌》是保存戈利亚德最著名的手稿。
同时,由于欧洲各地的地方语言和方言诗歌的发展,促成了法、德、意、英的世俗歌曲的繁盛。
这个过程中,除了最早以法国《罗兰诗歌》为代表的英雄业绩歌和演唱它们的流浪艺人外,主要代表便是法国游吟诗人和德国恋诗歌手。
中世纪扎根于宗教圣咏的礼拜复调音乐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与此
同时,非礼仪性的单声部世俗音乐也一直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由于他的表演和流传都是即兴性的,因而并没有宗教音乐那样的系统、规矩和受人重视,但这时出现的一些世俗音乐形式却成为日后与正统的宗教音乐相抗衡的强大力量。
西方音乐史完整版

晚期的古典主义音乐
总结词
晚期的古典主义音乐是西方音乐史上最后一 个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古典主义音乐的逐 渐衰落和浪漫主义的兴起。
详细描述
在晚期的古典主义音乐中,作曲家们开始尝 试突破传统形式的限制,探索更为自由和个 性化的表达方式。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包括 约翰·施特劳斯、安东·布鲁克纳和理查·瓦格 纳等,他们的作品在音乐史上留下了重要的 印记。
世俗音乐
流浪艺人
中世纪时期的街头艺人,他们表演的世俗音乐对后来的民间 音乐和艺术音乐产生了影响。
法国的香颂和意大利的麦地那
分别代表了法国和意大利的世俗音乐,这些音乐形式在当时 非常流行。
音乐理论
纽姆谱
中世纪早期的记谱法,用横线表示音 的高低,是现代五线谱的前身。
音阶与调式
中世纪的音乐理论家开始对音阶和调 式进行系统化研究,为后来的音乐发 展奠定了基础。
详细描述
法国巴洛克音乐在歌剧、室内乐和键 盘音乐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地位。吕利 的歌剧《阿尔西斯特》和拉莫的《和 声学》都是法国巴洛克音乐的经典之 作。
英国音乐
总结词
英国巴洛克音乐以其独特的旋律和丰富的和声而著称,代表作曲家有珀塞尔、普塞尔和塔利斯等。
详细描述
英国巴洛克音乐的代表作品包括珀塞尔的歌剧《狄多与埃涅阿斯》和普塞尔的《奥菲欧》等。这些作 品在旋律、和声和戏剧表现等方面都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
03 古典主义音乐
早期古典主义音乐
总结词
早期古典主义音乐是西方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标志着音乐从巴洛克时期的过度,逐渐走向了更为简洁、 清晰和优雅的风格。
详细描述
早期古典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包括约瑟夫·海顿、沃尔夫冈·阿马多伊斯·莫扎特和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等。这些作曲 家在创作中强调了旋律的优美和和声的和谐,同时也注重了形式的平衡和结构的清晰。
西方音乐史概述中世纪的音乐

中世纪的音乐中世纪(法 Mo yen a ge;德Mitte lalte r;意m edioe vo)开始时,西方世界政治和社会结构土崩瓦解,生活困苦,一派萧条,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漫长而迟缓的复苏。
然而,这个时期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却不容忽视。
音乐遗产亦很重要;虽然其思维方式及认识特点与今天相距甚远,但在其它一些重要方面,当代音乐却从中世纪音乐继承了大量财富。
1 中世纪一词的来源及其包括的年代“中世纪的”(Med ieval)这一形容词与其英语的名词,和其它语言中的对应词一样,都来源于拉丁语(诸如med ium a evum,media aeta s,med ia te mpest as),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认为自古代文明衰落至十五世纪文化、文学和艺术“复活”的整整一千年,仅仅是一首不值得称道的“哥特人”的黑暗插曲。
历史家虽然早已驳斥了这种偏见(可是这一观点由“黑暗时代”一词部分地保留下来),但是习惯上仍将这漫长的时期视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
通常公认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和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于土耳其人)为这一阶段的上下限。
可是,也有根据其他历史事件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因此其上限的确定分歧很大,有250年(野蛮民族开始人侵)或675年左右的(地中海海上贸易由于阿拉伯人的征服而陷于停顿,卡洛林王朝兴起)。
其下限的确定亦然,有的早至十四世纪初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萌发时期,亦有迟至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广泛传播时期,这还不包括特里维廉(Tr evely an)的有趣的观点,他竟然认为中世纪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末叶。
西方音乐的历史发展简况

西方音乐的历史发展简况1.中世纪音乐西方音乐的中世纪时期从公元5世纪一直到14世纪。
主要音乐形式是用于教堂礼拜歌唱的格里高利圣叹和赞美诗,中世纪后期复调音乐开始广泛传播,记谱法、唱名法和调式体系逐渐成熟。
2.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15-16世纪是西方音乐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
它的起点不是意大利。
面是英国和欧州大陆偏北地区。
声乐复调,尤其是无伴奏的多声部合唱是这一时期音乐的主要风格样式。
早期文艺复兴的主要乐派有布艮第乐派和佛兰德乐派。
代表人物是奥克冈和约斯堪。
主要成就是弥撒曲、经文歌和世俗复调歌曲。
16 世纪是文艺复兴音乐成就最高的时期,世俗音乐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法国尚松(歌曲)和意大利牧歌是其中的典范。
晚期文艺复兴音乐的中心逐渐转向意大利,罗马乐派的帕勒斯特里那的无伴奏声乐复调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音乐推向顶峰。
威尼斯以圣马可教堂为中心的宗教音乐发展了庄严宏大、带有器乐伴奏的合唱音乐,预示着欧洲音乐未来阶段发展的趋势。
3.巴洛克时期的音乐1600 -1750 年,西方音乐进入巴洛克时期,复调音乐达到巅峰,主调音乐正在兴起。
以歌剧、清唱剧、康塔塔等声乐体裁是巴洛克风格的标志。
歌剧产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经过蒙特威尔第以及众多作曲家的努力,于18 世纪前后发展成型。
巴洛克音乐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器乐的空前发展。
重要体裁有奏鸣曲、协奏曲、组曲等,提琴作为主导乐器取代了文艺复兴弹拨乐器的地位;管风琴、古钢琴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协奏曲以弦乐为中心,伴以键盘乐器“数字低音”的合奏。
科莱里、维瓦尔第是这一时期弦乐艺术最杰出的代表。
键盘乐领域,德国的管风琴和法国的古钢琴最为著名。
法国古钢琴学派大师库泊兰的音乐特点是典雅高贵,装饰细腻,体现了音乐上的“洛可可”风格。
巴洛克晚期,音乐转向德奥。
晚期巴洛克音乐代表人物是德国作曲家J.S.巴赫和亨德尔。
4.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18 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音乐进入“古典主义”时期。
古典主义时期只有半个世纪左右,影响却非常大。
(完整word版)西方音乐史

西方音乐史一.古代与中世纪音乐(一)古代音乐:西方音乐的源头:古希腊,“爱琴文化”.歌唱、抒情诗、戏剧.1.音乐论述:(1)四音音列:希腊著名音乐理论家—-阿里斯多赛诺斯。
(2)五度相生律(毕达哥拉斯律制):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
2.古希腊悲剧:(1)题材:神话、英雄传说、史诗。
(2)形式:合唱、独唱、对话交替出现。
(3)代表人物:“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戏剧艺术的荷马”索福克勒斯;“心理戏剧的鼻祖”欧里庇得斯。
3.乐器:(1)弦乐:里拉琴。
【颂扬阿波罗】(2)管乐器:阿夫洛斯管(竖笛)【敬奉酒神】4.乐谱:歌唱:字母器乐:符号《塞基洛斯歌》最完整的古希腊名作品。
(二)中世纪音乐:1.格里高利圣咏:(1)选编者: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2)适用场合:罗马教会礼拜仪式(3)形式:唱诵的经文。
(4)特征:音乐形式:无伴奏纯人声歌唱,单声部。
歌词:拉丁文. 节拍:无明显节拍特征.旋律:级进为主,跳进少。
情绪:肃穆超脱.2.多声部复调音乐:(1)西方最早的复调音乐:奥尔加农。
平行奥尔加农,平行奥尔加农的变体,自由的或反向的奥尔加农,花唱式奥尔加农,华丽奥尔加农。
(2)迪斯康特:(3)经文歌:无伴奏合唱复调音乐。
3.世俗音乐:法国游吟诗人,德国恋诗歌手。
拉丁歌曲,方言歌曲。
二.文艺复兴时期(一)马丁路德的宗教音乐改革:新形式圣咏合唱-—众赞歌。
(二)乐器:1。
波弦乐器:琉特琴、竖琴。
2。
弓弦乐器:维奥尔家族乐器(小提琴前身)3。
管乐器:短号、小号、笛、低音管、双簧管4。
键盘乐器:管风琴、击弦古钢琴、拨弦古钢琴。
三.巴洛克音乐(一)巴洛克:一种艺术风格。
特征:构思宏大、效果辉煌、充满活力、强调情感的表现.(二)蒙特威尔第1.代表作:(1)八册牧歌:《亚利安那的悲歌》《战争与爱情牧歌集》(2)三部歌剧:《奥菲欧》《尤里西斯的返国》《波佩亚的加冕》2.艺术成就:(1)意大利牧歌的奠基人;(2)写作有情感的旋律,拜托宗教舒服的新音乐倡导者;(3)提出“两种常规"思想;(4)《奥菲欧》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歌剧,歌剧艺术进入成熟发展时期.(三)A.斯卡拉蒂:现代歌剧缔造者。
西方音乐史—中世纪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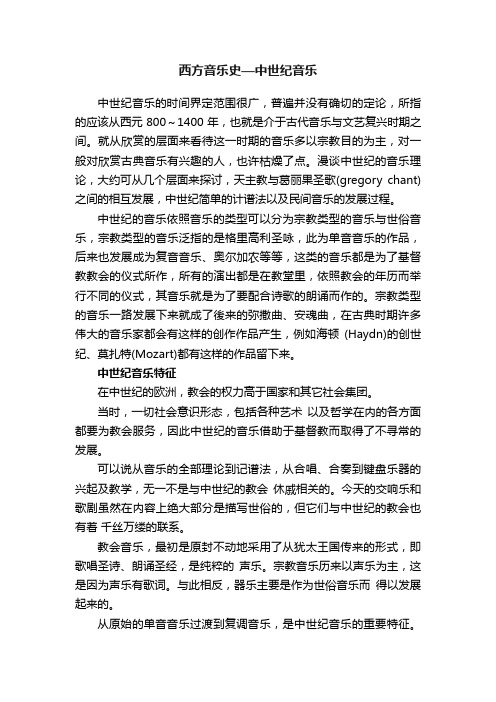
西方音乐史—中世纪音乐中世纪音乐的时间界定范围很广,普遍并没有确切的定论,所指的应该从西元800~1400年,也就是介于古代音乐与文艺复兴时期之间。
就从欣赏的层面来看待这一时期的音乐多以宗教目的为主,对一般对欣赏古典音乐有兴趣的人,也许枯燥了点。
漫谈中世纪的音乐理论,大约可从几个层面来探讨,天主教与葛丽果圣歌(gregory chant)之间的相互发展,中世纪简单的计谱法以及民间音乐的发展过程。
中世纪的音乐依照音乐的类型可以分为宗教类型的音乐与世俗音乐,宗教类型的音乐泛指的是格里高利圣咏,此为单音音乐的作品,后来也发展成为复音音乐、奥尔加农等等,这类的音乐都是为了基督教教会的仪式所作,所有的演出都是在教堂里,依照教会的年历而举行不同的仪式,其音乐就是为了要配合诗歌的朗诵而作的。
宗教类型的音乐一路发展下来就成了後来的弥撒曲、安魂曲,在古典时期许多伟大的音乐家都会有这样的创作作品产生,例如海顿(Haydn)的创世纪、莫扎特(Mozart)都有这样的作品留下来。
中世纪音乐特征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的权力高于国家和其它社会集团。
当时,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各种艺术以及哲学在内的各方面都要为教会服务,因此中世纪的音乐借助于基督教而取得了不寻常的发展。
可以说从音乐的全部理论到记谱法,从合唱、合奏到键盘乐器的兴起及教学,无一不是与中世纪的教会休戚相关的。
今天的交响乐和歌剧虽然在内容上绝大部分是描写世俗的,但它们与中世纪的教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教会音乐,最初是原封不动地采用了从犹太王国传来的形式,即歌唱圣诗、朗诵圣经,是纯粹的声乐。
宗教音乐历来以声乐为主,这是因为声乐有歌词。
与此相反,器乐主要是作为世俗音乐而得以发展起来的。
从原始的单音音乐过渡到复调音乐,是中世纪音乐的重要特征。
此外,中世纪音乐在理论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完成了对位法和线谱记谱法。
乐器的发明与制作也有了不小的进展,长号、小号和圆号等乐器在当时已广为流行,弓弦乐器(如维奥尔琴)也有了普遍的应用。
甘肃省考研音乐学复习资料西方音乐史发展脉络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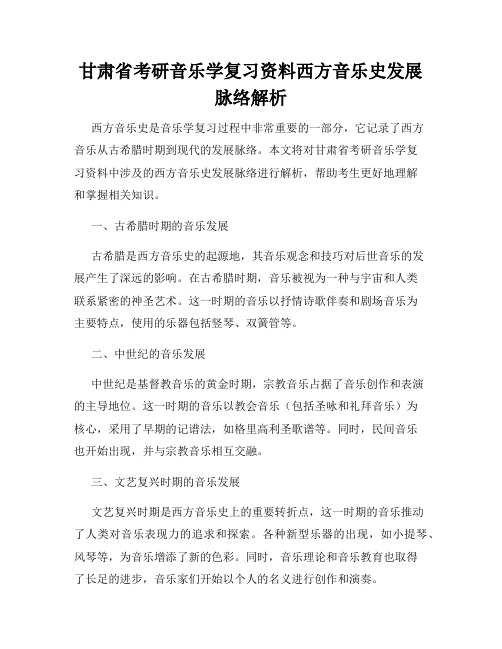
甘肃省考研音乐学复习资料西方音乐史发展脉络解析西方音乐史是音乐学复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记录了西方音乐从古希腊时期到现代的发展脉络。
本文将对甘肃省考研音乐学复习资料中涉及的西方音乐史发展脉络进行解析,帮助考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
一、古希腊时期的音乐发展古希腊是西方音乐史的起源地,其音乐观念和技巧对后世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古希腊时期,音乐被视为一种与宇宙和人类联系紧密的神圣艺术。
这一时期的音乐以抒情诗歌伴奏和剧场音乐为主要特点,使用的乐器包括竖琴、双簧管等。
二、中世纪的音乐发展中世纪是基督教音乐的黄金时期,宗教音乐占据了音乐创作和表演的主导地位。
这一时期的音乐以教会音乐(包括圣咏和礼拜音乐)为核心,采用了早期的记谱法,如格里高利圣歌谱等。
同时,民间音乐也开始出现,并与宗教音乐相互交融。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音乐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的音乐推动了人类对音乐表现力的追求和探索。
各种新型乐器的出现,如小提琴、风琴等,为音乐增添了新的色彩。
同时,音乐理论和音乐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音乐家们开始以个人的名义进行创作和演奏。
四、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发展巴洛克时期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之一,代表了音乐复杂技巧的巅峰。
巴洛克音乐强调对情感和情绪的表达,其特点包括复调性和装饰性的音乐风格,例如巴赫的管风琴曲和贝多芬的弥撒曲。
同时,巴洛克音乐也为后续音乐风格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五、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发展古典主义时期是西方音乐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它以清晰、简洁和对称的音乐特点为主导。
在古典主义时期,交响乐和室内乐成为了最重要的形式,作曲家们追求音乐的完美结构和和谐感。
莫扎特和海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
六、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发展浪漫主义音乐追求个人情感的直接表达,并注重音乐的想象力和情感冲击力。
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中充满了热情和情绪化的旋律,如贝多芬的交响曲和舒曼的钢琴作品。
西方音乐史(考研资料)

湘南学院音乐系2007——2008学年度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西方音乐史》复习提纲06音乐表演专用一、中世纪时期的音乐(476——1460年)1、格里歌利圣咏格里歌利圣咏(Gregorian Chant)是天主教音乐,它是公元6世纪教皇格里哥利一世在位时统一编订的。
格里歌利圣咏主要运用于日课(这是修道院僧人每天必做的“功课”)和弥撒(天主教、基督教为纪念耶稣受难而举行的仪式)之中。
格里歌利圣咏的基本功能是服从宗教礼拜活动。
音乐肃穆、节制,最大限度地排除世俗的感性欲念。
它是无伴奏的纯男歌唱的单声部音乐形式,以拉丁文为歌词,即兴式而无明显节拍特征,建立在单纯的自然音阶基础之上。
其旋律音调平缓,以级进和三度进行为主,偶有四、五度跳进,整个音乐音域较窄。
它的歌唱方式有四种:独唱、齐唱、交替歌唱、应答歌唱,各种歌唱方式根据礼拜进行的不同场合决定。
到公元11世纪时,除了米兰和西班牙外,欧洲其他地区都接纳它为仪礼中的圣歌。
2、奥尔加农奥尔加农(Organum)是9世纪至14世纪的复调音乐形式,根据其历史发展,可分为3种类型:a、平行奥尔加农(parallel organum)。
它是在格里歌利圣咏的上方式下方附加一个平行声部,构成四度、五度、八度音程的平行进行。
b、稍加变化的平行奥尔加农。
它的两个声部从同度开始,其中一声部上行进行,到两个声部构成四度时,再平行进行,最后两声部再回到同度。
c、华丽的奥尔加农(melismatic organum)。
大约在12世纪,奥尔加农的上声部越来越表现出流动性和装饰性,形成花唱式的华丽奥尔加农,它没有明显的节拍特征,活跃、华丽的上声部与下方缓、静止的圣咏声部形成鲜明的对比。
3、中世纪的游吟诗人游吟诗人(Troubadours)首先产生在11——13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Provence),它是游吟诗人的发祥地。
游吟诗人骑着马到处巡游,用奥克语(普罗旺斯方言)演唱坎佐(canzo)、清晨骊歌(alba)、西尔旺特(sirventes)、田园变歌(pastoarella)等体裁的歌曲,内容有爱情、时事、田园、讽刺等。
西方音乐史大一重点知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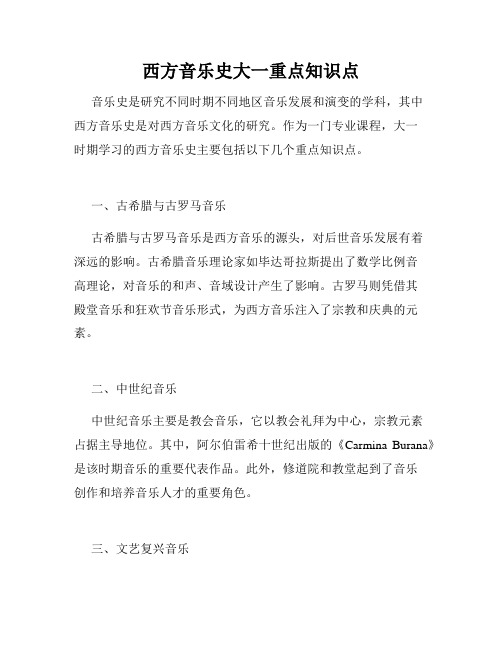
西方音乐史大一重点知识点音乐史是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音乐发展和演变的学科,其中西方音乐史是对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
作为一门专业课程,大一时期学习的西方音乐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点知识点。
一、古希腊与古罗马音乐古希腊与古罗马音乐是西方音乐的源头,对后世音乐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音乐理论家如毕达哥拉斯提出了数学比例音高理论,对音乐的和声、音域设计产生了影响。
古罗马则凭借其殿堂音乐和狂欢节音乐形式,为西方音乐注入了宗教和庆典的元素。
二、中世纪音乐中世纪音乐主要是教会音乐,它以教会礼拜为中心,宗教元素占据主导地位。
其中,阿尔伯雷希十世纪出版的《Carmina Burana》是该时期音乐的重要代表作品。
此外,修道院和教堂起到了音乐创作和培养音乐人才的重要角色。
三、文艺复兴音乐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艺术和思想迅速发展的时期,音乐同样受到了繁荣的影响。
16世纪的音乐家们开始探索以人的声音为中心的多声部和声技巧,拉塔尔第等人创作了大量合唱作品。
在音乐理论上,早期的音乐理论家奥凯农提出的音乐模式系统对后世音乐的调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巴洛克音乐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充满了复杂的装饰和华丽的表达方式,惠特尔和巴赫等作曲家是该时期的代表人物。
此外,伴随着巴洛克时期的歌剧和室内乐的发展,音乐家们开始注重表现情感和个人独创力,倡导个性化的演奏。
五、古典主义音乐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以对称和秩序为特点,节奏感强且条理清晰。
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曲家。
古典主义音乐以其优雅和谐的风格,成为继承巴洛克音乐并开创全新风貌的划时代作品。
六、浪漫主义音乐浪漫主义音乐是19世纪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强调对情感的表达和个人内心体验的呈现。
肖邦、舒伯特和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在这个时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此外,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音乐在浪漫主义时期也重新受到了重视。
七、现代音乐现代音乐是20世纪以来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对传统音乐的突破和创新。
西方音乐史概论

西方音乐史概论一、引言西方音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音乐传统之一,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多样的风格。
本文将带您了解西方音乐史的起源、发展和影响。
二、古典音乐时期1. 古希腊与罗马音乐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音乐与神秘信仰和宗教仪式密切相关。
我们将探讨这些文明对西方音乐发展的影响。
2. 中世纪音乐中世纪的基督教宗教音乐对后来的西方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将讨论这个时期的声部写作、吟唱圣歌和聚会流派等重要内容。
3. 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音乐的重要转折点。
人们开始研究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并开发出新的声部写作技巧。
本节中我们将学到关于前康塔承技法和多声部合唱风格等内容。
4. 巴洛克时期巴洛克音乐以其复杂的声部结构、装饰性的演奏方式以及大胆的形式创新而闻名。
我们将研究巴洛克时期的重要作曲家和他们的作品,并分析其风格特征。
三、古典时期与浪漫主义时期1. 古典主义音乐古典主义音乐注重形式和比例,追求清晰和对称。
我们将学习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等古典音乐巨匠以及他们对西方音乐发展的贡献。
2. 浪漫主义音乐浪漫主义音乐强调个人情感和表达,尝试使用更广阔的音域和奇异的和声技巧。
本节中我们将介绍肖邦、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等浪漫主义作曲家及其代表作品。
四、现代与当代音乐1. 印象派与20世纪初期印象派是20世纪初现代艺术革命的标志之一,也影响了当时的西方音乐。
我们将探讨德彪西、拉威尔和斯特拉文斯基等印象派作曲家及其创作的特点。
2. 新古典主义与现代音乐新古典主义是20世纪音乐中一种对传统音乐形式的回归。
同时,现代音乐也开始探索新的声响和技术。
本节中我们将了解巴赫、斯特拉文斯基和柴可夫斯基等重要作曲家对西方音乐的影响。
3. 当代音乐当代音乐包括民间音乐、流行音乐、爵士乐等多种风格,它们反映了当下社会的多样性和变迁。
我们将介绍几位当代重要作曲家并分析他们所处时代背景下的创作特点。
五、结语通过了解西方音乐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重要艺术传统的发展轨迹,以及各个时期和风格之间的联系与转变。
浅谈西方音乐史中世俗音乐的发展

浅谈西方音乐史中世俗音乐的发展西方音乐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而世俗音乐则是在中世纪开始发展,并在之后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世俗音乐是指非宗教性质的音乐,它反映了社会、政治、文化和个人生活,是人们情感和生活体验的表达。
在西方音乐史上,世俗音乐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和风格的变迁,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中世纪的世俗音乐在中世纪,世俗音乐主要分布在欧洲的农村和城市中,它吸收了古罗马、古希腊和东方的音乐风格,并结合当地的民间音乐和舞蹈节奏,形成了具有独特特色的中世纪世俗音乐。
这一时期的世俗音乐主要以歌曲形式流传,它们多以叙事的方式表达爱情、战争、农耕和生活等题材,成为中世纪欧洲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在中世纪,世俗音乐也与宗教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共同影响着当时的音乐创作和表演。
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音乐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音乐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世俗音乐发展的转折点。
在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开始摆脱对宗教音乐的依赖,世俗音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艺术形式。
这一时期的音乐家和作曲家们开始关注音乐本身的艺术性和技巧性,他们融合了古典文化的影响,创作出了大量的世俗音乐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也是音乐印刷术的发展时期,音乐作品的传播和保存得到了极大的便利,这也大大推动了世俗音乐的传播和发展。
巴洛克时期是世俗音乐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
在这一时期,音乐作品的形式和风格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世俗音乐成为当时贵族、市民和皇室园林游乐场所的重要演出节目。
这一时期的世俗音乐包括舞曲、歌剧、室内音乐等多种形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巴洛克时期的歌剧作品,它们结合了音乐、舞蹈和戏剧,成为了世俗音乐的一大创新。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很多知名的作曲家和音乐家,如莫扎特、巴赫、亨德尔等人,他们的音乐作品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音乐发展。
20世纪以后,世俗音乐得到了更多的发展和创新。
在这一时期,世俗音乐的创作和演奏形式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传统的音乐形式和风格得到了更多的挑战和改变。
西方音乐史之二——中世纪音乐(Middle?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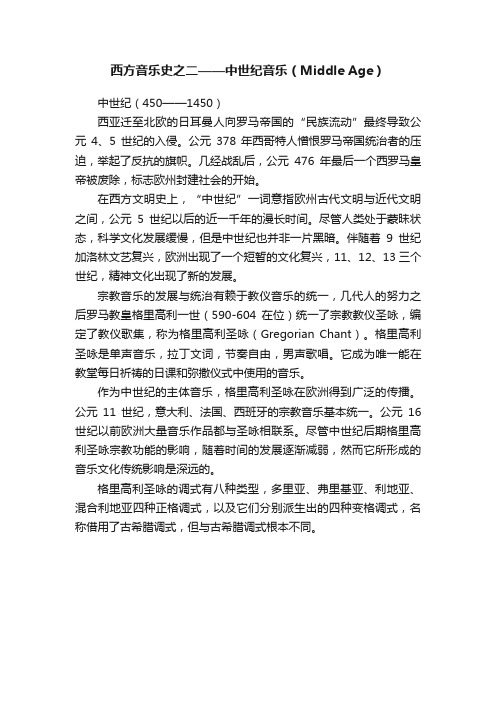
西方音乐史之二——中世纪音乐(Middle Age)
中世纪(450——1450)
西亚迁至北欧的日耳曼人向罗马帝国的“民族流动”最终导致公元4、5世纪的入侵。
公元378年西哥特人憎恨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压迫,举起了反抗的旗帜。
几经战乱后,公元476年最后一个西罗马皇帝被废除,标志欧州封建社会的开始。
在西方文明史上,“中世纪”一词意指欧州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之间,公元5世纪以后的近一千年的漫长时间。
尽管人类处于蒙昧状态,科学文化发展缓慢,但是中世纪也并非一片黑暗。
伴随着9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欧洲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文化复兴,11、12、13三个世纪,精神文化出现了新的发展。
宗教音乐的发展与统治有赖于教仪音乐的统一,几代人的努力之后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在位)统一了宗教教仪圣咏,编定了教仪歌集,称为格里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
格里高利圣咏是单声音乐,拉丁文词,节奏自由,男声歌唱。
它成为唯一能在教堂每日祈祷的日课和弥撒仪式中使用的音乐。
作为中世纪的主体音乐,格里高利圣咏在欧洲得到广泛的传播。
公元11世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宗教音乐基本统一。
公元16世纪以前欧洲大量音乐作品都与圣咏相联系。
尽管中世纪后期格里高利圣咏宗教功能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减弱,然而它所形成的音乐文化传统影响是深远的。
格里高利圣咏的调式有八种类型,多里亚、弗里基亚、利地亚、混合利地亚四种正格调式,以及它们分别派生出的四种变格调式,名称借用了古希腊调式,但与古希腊调式根本不同。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中世纪音乐早期的历史实际就是素歌的历史,这并非由于中世纪的人们完全沉迷于宗教而对世俗的事物丧失兴趣,而是因为教会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垄断了文化;因此,教会吸收了各类艺术的精华,更多的是创造了各类艺术的精华。音乐是宗教生活及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所有神职人员都必得实际参加歌唱;许多人还学习承自先人的音乐艺术(ars musica)理论知识,作为文科教育的初级科目之一。这时,统一教堂仪式的运动(八至九世纪时)导致了规定统一的礼拜歌曲曲目,宗教音乐也是在此时才成为历史的中心。这时有两个技术上的进步保证了曲调在流传和演唱时能够不走样,这两个进步在西方音乐史上都有深刻的影响:一是根据八个调式系统(这种调式系统直到十八世纪还在使用)对曲调进行的分类,一是以前只能帮助记忆的纽姆谱(neumes)逐渐发展为精确的音高记谱法(Pitch notation),其基本原则至今未易。随着素歌两种主要“方言”流派(高卢圣咏和莫萨挑布圣咏)的禁止使用,更重要的是从原来在口头流传时其歌词可以变动和相当自由,转向为依赖于写下来的歌词,从此,每次演唱时歌词(至少在原则上)可以保持不变了。
由于索莱姆(Solesmes)的本尼迪克特教团复兴了素歌,这种中世纪音乐最古老的主要形式为人们熟悉起来。其单旋律的本质、突出主调性的单纯的方式及其节奏的随意性(不管学者们在细节的诠释上有多么大的分歧)都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要想真正懂得曲调的形成、词曲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的曲调在特定庆典和常规宗教仪式中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则非专家而莫属。素歌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大多数中世纪音乐和听众之间的典型关系:修道院以及主教派教堂里的演唱纯属信仰的表达,根本就没有听众;一种基本观念由此产生,即音乐是供演唱者和礼拜仪式参加者听的,而不是供局外的听众欣赏的。
音乐史家在其著作的题目中涉及中世纪“的”音乐或中世纪“中的”音乐时,似乎是沿用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而通常避免给以精确的定义。然而在这些题目之下涉及的范围.可以上溯至基督教时代的开端,去推测新的宗教可能从犹太教堂继承了何种音乐成分,将何种音乐成分加以改革以适应新的需要,或是将何种音乐成分在它流传的过程中从异族的环境中直接吸收过来。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些充其量只是中世纪音乐的史前史(准备阶段),一直到九世纪,音乐才有了可供讨论的实体,理论著述也不再仅仅是古代音乐文献的翻版。上述两点都是八世纪西方教会建立高度统一的礼拜仪式的结果,而这一发展过程又与历史的趋向密切相关:即罗马教廷不再依赖遥远的东方帝国,而要寻求卡洛林王朝的支持。所以,将一般史学界提出的最晚时间,即公元675年左右,作为音乐史上可称为“拉丁中古时期”的上限,看来最为合适。“拉丁中古时期”一词是考虑到拜占庭及其有关的礼拜仪式而提出的,以便和大体上平行的“希腊中古时期”相提并论。
由于法国吟唱诗人的诗歌同各种现代文学的起源有密切的联系,它的音乐类型重新引起起了重视。人们的这种热情引起想去查明很多没有解决、甚或无法解决的语文学问题。这些诗人是否自己将他们的诗歌都用文字记载下来尚无定论,至于其音乐就更值得怀疑了。因为在十二世纪,大多数人都认为把曲调记录下来是很奇怪的想法。事实上,直至1250年左右,世俗歌曲根本就没有曲谱。即使到1250年左右,根据寥寥无几的现存手稿看来,其记谱方法也是不正规的。这种现象就导致人们认为旋律主要是由口头流传的,也使人们认为,与歌词相比,旋律居于次要地位,甚至可有可无(《意大利赞美诗》、《坎蒂加》和《自苔歌》等等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编集的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宗教性的大众唱歌集的手稿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些现存的修订版本已是二手材料,但有其历史价值;然而,试图重新演奏这些音乐的主要障碍仍是记谱问题。当时的记谱法精确地记录了歌曲的旋律,对于节拍却丝毫不曾提及,因此在“打谱”上有很大分歧。虽然许多比较简单的、大致一个音符对一个音节的曲调,在不考虑节拍的情况下,仍能令人清楚地领略其魅力,但另外许多成簇的装饰音群却无法探究,这是令人尤为遗憾的。
中世纪的音乐
中世纪(法 Moyen age;德 Mittelalter;意 medioevo)开始时,西方世界政治和社会结构土崩瓦解,生活困苦,一派萧条,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漫长而迟缓的复苏。然而,这个时期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却不容忽视。音乐遗产亦很重要;虽然其思维方式及认识特点与今天相距甚远,但在其它一些重要方面,当代音乐却从中世纪音乐继承了大量财富。
由于上述情况,素歌成为大多数音乐活动的主要内容便不足为奇了。为了与演唱圣咏时庄重的气氛相适应,音乐创作都按照教会的要求,对经文加以阐述和补充。“插入段”(trope)(其中当然包括更老的形式“继叙咏”[sequence]通过将新的歌词,甚或新的词曲与原有的结构精巧地交织或结合到一起。使得原有的曲调添加了节日的庄重气氛。与此类似,“音对音”平行进行的奥尔加农(organum,实际上是演唱教会曲调的一种特定的格式,而不是在此曲调上的即兴发挥)丰富了圣咏,使之在音响上更为丰满。在更富于艺术性的各种复调手法兴起之后,复调式唱法的“即兴上声部”(supra librum,从一些素歌歌集看来,这是一种视唱时机械地叠置的奥尔加农声部,甚至允许斜向或反向进行)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中新添声部的装饰性及其旋律和节奏的独立性带来记谱的要求,实际上,是由此产生了新的作曲法。新的声部逐渐发展,削弱了原先的教堂曲调的地位,使之再也不能被后作“主要声部”(Vox Principalis)——起码从音乐的角度看是如此;“定旋律声部”(tenor)从此仅指巴黎圣母院时期大型的奥尔加农中圣咏的持续音,但它在精神上和语音上仍然是整个复调结构的支柱。
3 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
教会的作用在音乐的保存上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存的所有非宗教音乐的混乱状况相比,这种作用尤为明显。首先是各种类型的拉丁文歌曲—大量的古代诗歌、挽歌、赞美歌、情歌、云游歌和单旋律歌曲—在九世纪至十三世纪间流传起来,数量越来越多。它们的分类是根据不同的题材和乐曲来源资料所属类型而定,但有个不容忽视的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有很高的文学水平。这只能归功于当时绝无仅有的文化杰出人物—教士、俗僧和修道士,甚至非正式教士(虽然将放荡的秽语和虔诚的忏海这两个极端看作是云游教士和非云游教士的形像是不现实的)。这就是音乐的理论和记谱法得以保存的土壤,对非宗教音乐,人们不予重视,不重视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在目前的所有资料中,曲调都是用极不精确的纽姆谱标记的,其作用充其量也只能对久已忘怀的曲调帮助提醒记忆而已。有的曲调重复用于不同的歌词,有的则以新词填入已有的(流行的)曲调,这都说明词曲的结合大多以方便为原则,而不考虑表现方面是否适合的问题,音乐只是一种可以随便放弃或者改变的工具。单旋律的孔杜克图斯大概要算是例外;但那时这个例外只用于它的后期的歌曲,这些歌曲已经引起对作曲家及作品的重视,同复调的孔杜克图斯以及巴黎圣母院时期的奥尔加农一起保存在具有音乐上的特殊性的手稿里。
4 节奏和经院哲学的音乐
规则的节奏律动在巴黎圣母院时期的复调音乐中已经确立,成为西方音乐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要素(称之为节奏模式[mode]、节拍[measure]或拍子[beat]),要想说清其历史进程中的因展关系是十分困难的。奥尔加农的诸上声部之间有着精确的时值要求,无疑,这主要是为了使得上声部中华丽多变的旋律线有机结合,以与定旋律声部的长持续音形成对比;其办法主要是使用不多几个节奏模式(modi或maneriae)的多次反复,这种记诸法是专为有一定节奏形式的素歌创制的、不能表达节奏变化。但是不容否认。其艺术上的成就超越了这些技术上的不足—节奏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取代定旋律声部而成为表现的基本要素,定旋律声部只是象征性地保留,其旋律上的主导地位由于其它声部的大大发展而不复存在。有关这一新趋势的现存最早文献是莱奥南为巴黎圣母院的礼拜仪式而作的二声部奥尔加农套曲,其时代正是圣母院开始建造的1163年前后,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在哥特式建筑征服了重力和空间的同时,莱奥南的作品及他的后继者佩罗坦的三部或四部奥尔加农征服了节奏。莱奥南和佩罗坦的名字出现在作曲者不署名的中世纪复调音乐文献中这一事实,说明了巴黎在艺术音乐中占据着领导地位,直至十五世纪之初。
在拉丁文歌曲流行的后期,各种民族语言的歌曲同时流行起来。这种歌曲以十二世纪初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吟唱诗人(trouba-dour)为其先导,吟唱诗人的题材主要是宫廷生活和骑士的爱情。
普罗旺斯的艺术传到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快也在法国北部吟唱诗人(trouvere)和德国的恋诗歌手(minnesinger)中引起了共鸣。这无疑是一种面向世俗听众的艺术,大多出自非教职人士之手,其中从最高阶层(包括如普瓦提埃的伯爵吉罕和纳瓦尔的国王提保)直至以智慧才能赢得参加宫廷生活资格的下层人物。由于带有宫廷的性质,这些诗歌有着显赫的署名,有时署名带有“拉佐斯”(razos),以说明诗歌产生的环境;但是诗歌作者对诗歌的曲调赋予多大影响尚不清楚。这个时知仍有证据表明同一首曲调可以配上不同的歌词:有时,表演的规则就是用前面的人用过的曲调填入新词答和;这就是“感兴诗”(sirventes)含义的一个方面,但在实践中绝不会拘泥于这唯一的歌曲类型。法国吟唱诗人歌曲由游唱艺人(Joglars或Jougleors)表演时,他们有时可能为缺乏音乐才能的主人提供曲调或改编曲调。
关于这种新型艺术的来源从来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来自民间、教会或阿拉伯,也有人认为是好多种成分结合的产物。从音乐角度来看,现存曲调与教堂音乐在曲式上可能有某种类似,但与各种教会调式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联系。一些例子可以证明有的曲调来自流行小调,或来自独唱与合唱交替伴舞的旋律(Kale-nda Maya和A I’entrada del tens clar是著名的例子);但是,由少数例证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而且流行曲调显然没有记下谱来(至少在八世纪之前,一所有音乐普遍如此),因此这种音乐的性质不为人知,可靠性就更差了。
1 中世纪一词的来源及其包括的年代
“中世纪的”(Medieval)这一形容词与其英语的名词,和其它语言中的对应词一样,都来源于拉丁语(诸如medium aevum,media aetas,media tempestas),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认为自古代文明衰落至十五世纪文化、文学和艺术“复活”的整整一千年,仅仅是一首不值得称道的“哥特人”的黑暗插曲。历史家虽然早已驳斥了这种偏见(可是这一观点由“黑暗时代”一词部分地保留下来),但是习惯上仍将这漫长的时期视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通常公认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和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于土耳其人)为这一阶段的上下限。可是,也有根据其他历史事件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因此其上限的确定分歧很大,有250年(野蛮民族开始人侵)或675年左右的(地中海海上贸易由于阿拉伯人的征服而陷于停顿,卡洛林王朝兴起)。其下限的确定亦然,有的早至十四世纪初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萌发时期,亦有迟至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广泛传播时期,这还不包括特里维廉(Trevelyan)的有趣的观点,他竟然认为中世纪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末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