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小说”《花腔》论文
花腔李洱读后感

花腔李洱读后感篇一花腔李洱读后感《花腔》这本书,读完后真的让我感慨万千!我觉得吧,这书就像一个神秘的迷宫,我在里面兜兜转转,一会儿觉得自己看懂了,一会儿又懵圈了。
李洱的文字啊,那叫一个花腔百出!他把历史、现实、人性啥的都揉在一起,搞得我脑袋都要炸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书太复杂,读起来费劲。
可我觉得,正是这种复杂,才让它有魅力啊!就像生活,哪有那么简单直白的?书里的人物,一个个都那么鲜活,好像就在我眼前蹦跶。
我读着读着,就仿佛跟着主人公们经历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冒险。
有时候我会想,要是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会怎么做?可能会吓得屁滚尿流吧,哈哈!说真的,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多面性。
那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啥花样都能玩出来,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花腔”?可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在生活中,难道就没有那么一点小心思,小手段?这书里的故事,一会儿让我愤怒,一会儿又让我悲伤,情绪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这难道不就是好书的魅力吗?它能把你的心紧紧抓住,让你跟着它的节奏起伏。
总之,读《花腔》这一路,真的是又累又爽,就像跑了一场马拉松,虽然累得要死,但到达终点的那一刻,又觉得无比满足!篇二花腔李洱读后感嘿,朋友们!今天我要跟你们唠唠《花腔》这本书。
刚开始读的时候,我心里直犯嘀咕:“这啥呀?咋这么乱呢?”可越往后读,我越发现,这乱中有序啊!李洱这家伙,真是个鬼才!书里的那些情节,就跟电影画面似的,在我脑子里不断闪现。
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们在命运的漩涡里挣扎。
也许有人会问:“这有啥好看的?”我想说,好看的地方多了去了!它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复杂。
你说这人吧,有时候善良得像天使,有时候又邪恶得像魔鬼。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是环境逼的,还是自己作的?我觉得吧,可能都有。
还有那些人物的命运,真是让人揪心。
他们一会儿被捧上天,一会儿又摔得很惨。
这难道就是人生?我不禁反问自己,如果是我,能承受得住这样的起起落落吗?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感觉自己都快精神分裂了。
《花腔》新论文

《花腔》新论摘要:《花腔》作为李洱的代表作,具有独特的审美魅力。
文本中,个体在历史面前无声地泯灭,历史在历史叙事的作坊中也悄然瓦解。
历史与个人在被言说的话语情境中丧失了主体性,并在这种被言说中不断地走向分裂与瓦解。
在这血流成河的历史深处,革命伦理的的暗流以其天然的暴力与血腥参与着历史的构造。
关键词:个体存在;历史叙述;缺席;革命伦理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13-01《花腔》的问世在新历史主义小说陷于沉寂之时掀起了新一轮的风波,作家李洱也因此在文坛获得声声赞誉。
无论是文体形式,还是多变的叙事视角,抑或是作者凭借“一本正经的书写葛任的历史”来戏仿历史、调侃历史的姿态都激起了研究者的浓厚兴趣。
诚然,阐释主体的认知差异必然造成文学作品在阐释层面的多义性与复杂性。
然而这正是经典作品的魅力所在。
下文将从两个不同的阐释角度挖掘作品的内在意蕴。
一、个体与历史的双重缺席与泯灭文本中,葛任因“与个人谐音”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个体存在的代名词。
就物理时间而言,个体的存在只此一次,一旦死去,便灰飞烟灭。
可是,他在叙述人居心叵测的转述中一次次地活过来,并且面目各异。
每个人都在依据自己的政治立场与现实处境来任意勾画葛任的轮廓,以自身狡黠的腔调为葛任命名。
他们扭曲葛任的最大目的无非是为其自身寻求存在于世的合法性并希冀在历史中为自己谋求一席之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三个正文叙述人还是副本叙述人“我”在各怀鬼胎的面目之下构成了同谋关系,他们合力“谋杀”了缺席的葛任,失语的葛任。
诚如福柯所言,“一个人在他去世时留下来的关于他的这一大堆乱杂的词语,在交叉错节中所操用的如此相异的语言,对此又应该赋予它们以什么样的地位呢?”或许,白圣韬早已一语成谶“对于葛任的任何理解都可能是曲解”。
在这段声音驳杂的历史中,作为个体存在的葛任始终未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是“懂得维护个人尊严的人”,在死亡的伴随下出生,在死亡的掩盖下远离政治,独居大荒山。
言说中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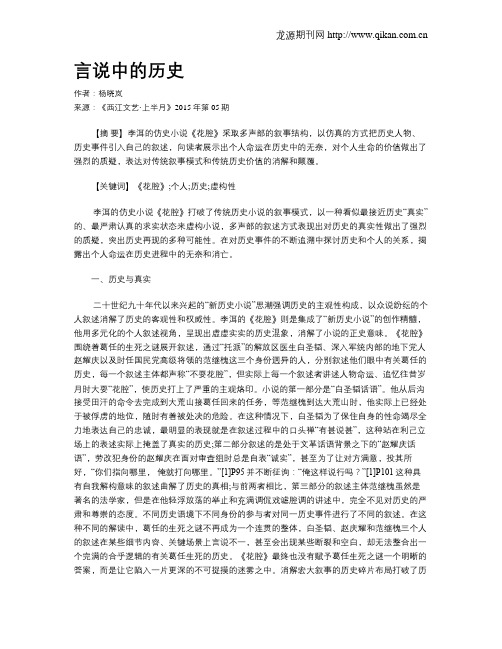
言说中的历史作者:杨晓岚来源:《西江文艺·上半月》2015年第05期【摘要】李洱的仿史小说《花腔》采取多声部的叙事结构,以仿真的方式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引入自己的叙述,向读者展示出个人命运在历史中的无奈,对个人生命的价值做出了强烈的质疑,表达对传统叙事模式和传统历史价值的消解和颠覆。
【关键词】《花腔》;个人;历史;虚构性李洱的仿史小说《花腔》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以一种看似最接近历史“真实”的、最严肃认真的求实状态来虚构小说,多声部的叙述方式表现出对历史的真实性做出了强烈的质疑,突出历史再现的多种可能性。
在对历史事件的不断追溯中探讨历史和个人的关系,揭露出个人命运在历史进程中的无奈和消亡。
一、历史与真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历史小说”思潮强调历史的主观性构成,以众说纷纭的个人叙述消解了历史的客观性和权威性。
李洱的《花腔》则是集成了“新历史小说”的创作精髓,他用多元化的个人叙述视角,呈现出虚虚实实的历史混象,消解了小说的正史意味。
《花腔》围绕着葛任的生死之谜展开叙述,通过“托派”的解放区医生白圣韬、深入军统内部的地下党人赵耀庆以及时任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范继槐这三个身份迥异的人,分别叙述他们眼中有关葛任的历史,每一个叙述主体都声称“不耍花腔”,但实际上每一个叙述者讲述人物命运、追忆往昔岁月时大耍“花腔”,使历史打上了严重的主观烙印。
小说的第一部分是“白圣韬话语”。
他从后沟接受田汗的命令去完成到大荒山接葛任回来的任务,等范继槐到达大荒山时,他实际上已经处于被俘虏的地位,随时有着被处决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白圣韬为了保住自身的性命竭尽全力地表达自己的忠诚,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叙述过程中的口头禅“有甚说甚”,这种站在利己立场上的表述实际上掩盖了真实的历史;第二部分叙述的是处于文革话语背景之下的“赵耀庆话语”,劳改犯身份的赵耀庆在面对审查组时总是自表“诚实”,甚至为了让对方满意,投其所好,“你们指向哪里,俺就打向哪里。
【VIP专享】《花腔》毕业论文

真实与虚幻――――李洱长篇小说《花腔》文本赏析200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长篇小说《花腔》被认为是2001- 2002年度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作者李洱。
首先,我们先讨论一下这部作品的题目――《花腔》。
花腔一词,在文本中被多次提及。
多是被采访者说自己“从来不耍花腔”。
顾名思义,“耍花腔”就是用虚假而动听的话骗人。
用二元论判断我们这个世界的事物很简单,非真即假。
也就是说除了真的就是假的。
花腔一词就像是真与假,虚幻与现实之间的面纱,让人们很难去判断。
文本中的人物确实没有耍花腔吗?我想每一位读者阅读文本后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答案。
作者在文本中独出心裁的采用了“@”和“&”两个符号将文本分为了两个层面。
“@”我们都知道在英语中就是“at”。
意思是“在。
”,也就是说文本中的角色是在场性的叙述。
因此“@”符号之下的内容我们可以看作是文本的正文,是用采访与被采访的口述形式叙写的。
包含了三个不同的叙述者:受田汗委派从延安去大荒山白陂镇执行特殊使命的白圣韬医生;曾打入国民党军统、后在文革时期沦为劳改犯的赵耀庆;以及曾在国民党军统任职、现为著名法学家的范继槐。
三人与葛任都有或亲或疏的关系,既是葛任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其历史创造的参与者和讲述着。
他们身份、阅历、与主人公的关系以及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各个不同,因而他们各自的叙述烙上了不同的腔调和色彩。
“&”呢,就是英语的“and”,意思是“和。
”也就是附加、附属、补充之意。
因此,“&”符号下的内容相对于“@”来说应被视为副本,是由主人公葛任后代对其生平的探寻,构成了整个作品文本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它由众多虚拟或经过作者精心改造编辑的各式引文组成,对理解主人公葛任的生平事迹、事件背景作了大量的补充和说明。
所引文章既有真实的历史资料,也有正文所涉及与葛任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人物的文章和言谈,并且这些人物既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文献又不乏小说家塑造之人物和杜撰之资料,同时副本还包括了小说中的“我”对相关人物及文献的考订和品评。
《花腔》的多重变奏:文本结构·语言艺术·叙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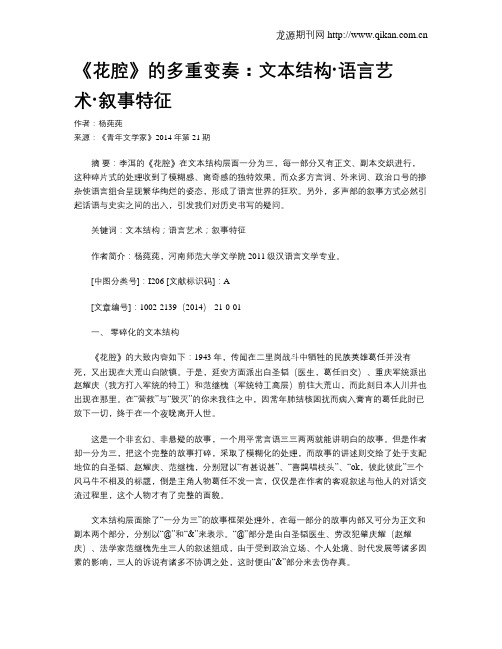
《花腔》的多重变奏:文本结构·语言艺术·叙事特征作者:杨莼莼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21期摘要:李洱的《花腔》在文本结构层面一分为三,每一部分又有正文、副本交织进行,这种碎片式的处理收到了模糊感、离奇感的独特效果。
而众多方言词、外来词、政治口号的掺杂使语言组合呈现繁华绚烂的姿态,形成了语言世界的狂欢。
另外,多声部的叙事方式必然引起话语与史实之间的出入,引发我们对历史书写的疑问。
关键词:文本结构;语言艺术;叙事特征作者简介:杨莼莼,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1-0-01一、零碎化的文本结构《花腔》的大致内容如下:1943年,传闻在二里岗战斗中牺牲的民族英雄葛任并没有死,又出现在大荒山白陂镇。
于是,延安方面派出白圣韬(医生,葛任旧交)、重庆军统派出赵耀庆(我方打入军统的特工)和范继槐(军统特工高层)前往大荒山,而此刻日本人川井也出现在那里。
在“营救”与“毁灭”的你来我往之中,因常年肺结核困扰而病入膏肓的葛任此时已放下一切,终于在一个夜晚离开人世。
这是一个非玄幻、非悬疑的故事,一个用平常言语三三两两就能讲明白的故事。
但是作者却一分为三,把这个完整的故事打碎,采取了模糊化的处理,而故事的讲述则交给了处于支配地位的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分别冠以“有甚说甚”、“喜鹊唱枝头”、“ok,彼此彼此”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标题,倒是主角人物葛任不发一言,仅仅是在作者的客观叙述与他人的对话交流过程里,这个人物才有了完整的面貌。
文本结构层面除了“一分为三”的故事框架处理外,在每一部分的故事内部又可分为正文和副本两个部分,分别以“@”和“&”来表示。
“@”部分是由白圣韬医生、劳改犯肇庆耀(赵耀庆)、法学家范继槐先生三人的叙述组成,由于受到政治立场、个人处境、时代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三人的诉说有诸多不协调之处,这时便由“&”部分来去伪存真。
别具特色的文体实验——李洱《花腔》的文体分析

别具特色的文体实验——李洱《花腔》的文体分析
王军亮
【期刊名称】《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8(009)003
【摘要】分析了李洱的<花腔>在整体结构和叙述手法上的创新;作者设计了三个不同的讲述者,使文章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结构模式,不同讲述者也构成了文章叙述视角的转换,同时,多个特殊历史时期话语的运用在丰富文章语言的同时也形成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总页数】3页(P72-74)
【作者】王军亮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2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
【相关文献】
1.韩少功小说文体观念与文体实验刍论 [J], 王青;姚海燕
2.对C.D.Lewis的The Last Words的文体分析——形式和功能文体分析比较 [J], 袁邦株;徐润英
3.饶舌的哑巴:怀疑主义者的青春期话语——李洱早期小说文体风格 [J], 魏天真
4.小说·历史·真实——李洱《花腔》与小说文体 [J], 魏天无
5.叙述嬗变与文体反讽——李洱长篇小说简论 [J], 孙谦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李洱《花腔》的多重叙事艺术 汉语言文学专业

李洱《花腔》的多重叙事艺术摘要:《花腔》是作家李洱的一部代表作,被认为是2001- 2002年度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入围第6届茅盾文学奖,首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
作品围绕主人公葛任为基本线索,以破解葛任的生死之谜为结构中心,描写了葛任囊括生活状况,对政治的渴求和爱情的萌发等方面的人生之路,结合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来描写其奔波流离的人生,引发了读者对于真实这一概念的质疑与思考。
大量的引文和三个当事人的口述,则构成了《花腔》独特的叙事艺术。
本文将分析《花腔》叙事层次的五个方面,以及《花腔》所蕴含的独特意义。
关键词:叙事策略、真相、耍花腔一.小说是一门结构的艺术作品《花腔》以寻找主人公葛任的生死为线索,以破解葛任的生死之谜为结构中心。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它具有独特的先锋性,在出版上一开始就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甚至出现了一些问题据说这部小说写在20世纪60年代“灯塔”工程。
李洱的小说创作本文通过对葛仁形象的分析,对葛仁形象进行分析跟踪和窥视个人生死的命运这幅画揭示了历史伦理对人性的危害。
他独特的对话方式他们创造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巨大的谜题,宏大叙事与历史的崇高进行了明确的解构。
在黑暗中在历史真相面前,我们对人生和历法有了深刻的理解历史的真相必须重新考虑。
同时《花腔》又是一部形式感非常强的小说,其表面结构是其主要特征。
其中有着数量众多的有关叙事的方法和技巧,小说在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了作者本人对主角“葛仁”在动荡不安的岁月中表现出的革命觉悟和热情的独到理解,而且还借此抒发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与其悲剧命运的反差,从而加深对历史主体对推动历史跌宕起伏发展的理解。
在一部小说中,结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小说是一门结构的艺术,小说美学的本体不是意象,而是结构。
结构是如何呈现和构造心灵世界的文化原型体制与文本叙事技巧的深层融合,是作为小说美学即小说叙事学的本体,在文化与文本两个层面的统一。
”【1】。
小说的每一个字都属于小说结构的一部分,结构又承载着作家对世界的理解和向往。
谈长篇小说《花腔》对“革命”的重新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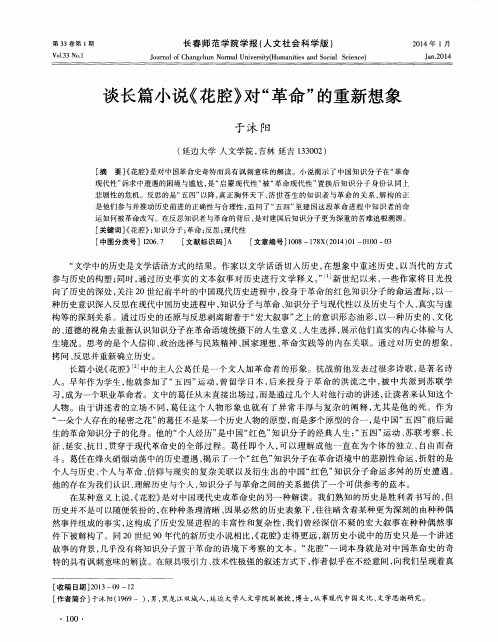
朵个人存在 的秘密之花” 的葛任不是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原型, 而是多个原型的合一 , 是中国“ 五四” 前后诞 生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化身。他的“ 个人经历” 是 中国“ 红色” 知识分子的经典人生: “ 五四” 运动 、 苏联考察 、 长
一
征、 延安 、 抗 日, 贯 穿 于现代 革命 史 的全 部 过 程 。葛 任 即个 人 , 可 以理 解 成 他 一 直在 为个 体 的独 立 、 自由 而奋
[ 收稿 日期 ] 2 0 1 3— 0 9—1 2 [ 作者简介 ] 于沐 阳( 1 9 6 9一 ) , 男, 黑龙 江双城人 , 延边 大学人文 学院副教授 , 博 士, 从事现代 中国文化 、 文学思潮研 究。
・
1 0 0・
正 发 生过 的历 史 本来 面 目。是在 虚构 的幌 子 下 , 以小 说 的方 式 解 构 、 背叛“ 胜利者” 描 述 的 历史 , 还 原 历 史 的 本真 , 是对 主 流历 史话 语 的权 威性 与 确定性 的挑 战 , 实 际上 对现 代 以来 中 国革命 道路 乃 至革命 方式 、 革命 手 段
历 史并 不是 可 以随便 装扮 的 , 在 种种 条 理清 晰 、 因果必 然 的历 史表 象下 , 往往 暗 含着 某种 更 为深 刻 的由种 种偶
然事件组成的事实 , 这构成 了历史发展进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 我们曾经深信不疑 的宏大叙事在种种偶然事 件下被解构了。同 2 0世纪 9 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相比, 《 花腔》 走得更远 , 新历史小说 中的历史只是一个讲述 故事的背景 , 几乎没有将知识分子置于革命 的语境下考察 的文本。“ 花腔” 一词本身就是对中国革命史 的奇 特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解渎。在颇具吸引力 、 技术性极强的叙述方式下 , 作者似乎在不经意间, 向我们呈现着真
花腔

《花腔》:李洱的历史诗学汪政在新历史主义小说思潮渐近沉寂之际,李洱却以其长篇新作《花腔》宣告了自己历史诗学的诞生。
为了更“接近”历史,为了让阅读建立起历史的期待视野,《花腔》将既成的具有常识性的历史史实大把大把地引进自己的叙述。
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乃至细节都与接受者已知的历史知识积累对缝合榫地重合在一起。
为了证明自己的叙述是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的,作品甚至动用了考据学的方式。
这样的努力应该说取得了作者预期的艺术效果,一种历史叙事的知识背景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一种历史阅读法的期待视野也由之先入为主地交到了读者那儿,而其后的一切变化与戏剧性的接受效应,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
这正是李洱《花腔》的狡黠之处。
《花腔》是对主人公葛任生平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段特殊经历的追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记叙的又是一桩历史疑案:“葛任事件”。
因此,作品采取转述而非呈现的方式就变得非常自然了。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即“有甚说甚”、“喜鹊唱枝头”和“OK,彼此彼此”,分别由三个人物白圣韬、赵耀庆和范继槐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而中间又夹以大篇幅的插叙,对讲叙中的内容进行补充、阐释并寻找旁证,这部分内容也是第一人称,其叙事人是作为整个“材料”的整理者和葛任的后人出现的。
因此,严格地说,《花腔》其实是由四个声部构成的。
除了插叙部分外,其他三个讲叙者实际上既是讲叙者,又是被叙者,他们互为镜象,又相对独立。
由于讲叙者的角色身份不同,时间跨度设计又很大,从而造成了整部小说斑驳陆离的文体特点。
至于插叙部分真假莫辨的引文和仿作更近于一种后现代的拼贴,几乎是各种文体的大杂烩。
小说曾经“征引”葛任的朋友徐玉升的《湖心亭之雪》,并评价说徐文“半文半白,亦中亦洋”,其实倒是可以用来概括《花腔》的特点的。
“葛任事件”,连同葛任本人,在小说的追忆中有没有水落石出,一直到最后都不能肯定。
当然,这并不是叙述的模糊乏力,而恰恰是李洱的刻意所为。
从叙述方式上讲,李洱显然倾向于认为历史是被讲述出来的,实在的历史可能只是一种虚幻。
众声喧哗中的探寻——评李洱长篇小说《花腔》的叙事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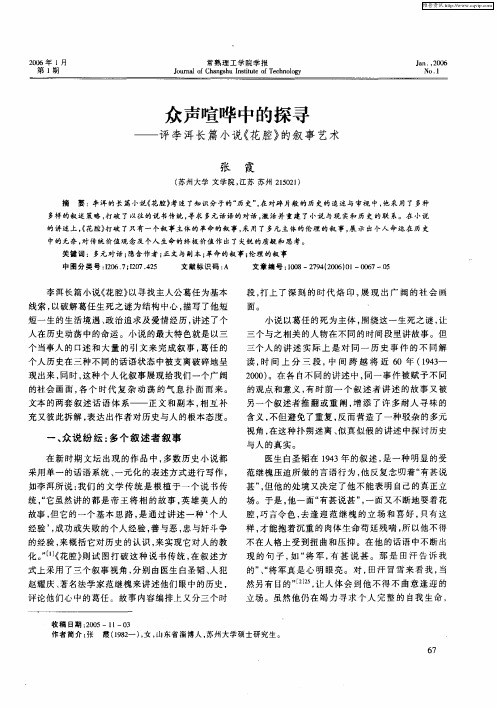
个人历 史在三 种不 同 的话 语状 态 中被支离 破碎地 呈
段, 打上 了深 刻 的 时代 烙 印 , 现 出 广 阔 的 社 会 画 展
现出来 , 同时 , 这种个 人 化叙事 展现 给我们 一个广 阔
20 ) 00 。在 各 自不 同的讲述 中 , 同一 事 件被 赋予 不 同 的观 点 和意义 , 时 前一 个 叙 述 者 讲 述 的故 事 又 被 有
另一 个叙 述者推 翻或 重 阐 , 添 了许 多 耐人 寻 味 的 增 含义 。 不但 避免 了重 复 , 反而 营造 了一 种驳 杂的 多元
场 。于是 , 他一 面“ 有甚说 甚 ” 一 面又 不断 地耍着 花 , 腔 , 言令 色 , 逢 迎 范 继槐 的立 场 和喜 好 , 巧 去 只有 这
经 验 ’成 功或 失败 的个人 经验 , , 善与 恶 , 与奸斗 争 忠
的经验 , 概括 它对历 史 的认识 , 实现它对 人的 教 来 来
中 图分 类 号 : 0 .; 0 .2 1 67 I 74 5 2 2 文 献 标 识 码 : A 文章 编 号 :0 8 7420 )1 0 7 5 10 —29 (06 0 —06 —0
李 洱长篇 小说 《 腔》 花 以寻找 主人公 葛任 为基 本 线索 , 以破解 葛任生 死 之谜 为结构 中心 , 描写 了他 短
样 , 能抱 着沉重 的 肉体 生命 苟延 残喘 , 以他不 得 才 所 不在人 格上 受 到扭 曲和压 抑 。在他 的话 语 中不断 出
文学,说到底就是文本——谈李洱的《花腔》

文学袁说到底就是文本谈李洱的《花腔》周明全 近两年,因为一个特别的缘故,所以我对近百部被大家公认的中国当代优秀小说进行了排列式的阅读。
坦率地说,不读便罢,一读读得我颇感莫名。
一些当初盛名灌耳的小说,而今看来也不过尔尔,想不通当初它怎弄起那么大的阵势。
不过其间也有例外。
譬如李洱的《花腔》,它竟再次刷新了我的阅读感受。
李洱让你首先想到的是,他不仅是个作家,更像是一个学者。
不是学者,写不出《花腔》这样奇特的文本。
他让我联想起美国的索尔·贝娄,那位终生盘桓于学院的象牙塔里、文质彬彬的老者,一位看似神经质的唠唠叨叨的写作者。
李洱与他似乎有着相同的方面。
那就是,都有着深潜于学院的经历,以及在写作上的共同癖性,即他们的写作,似乎都带着对当代颇前卫的文学以及语言艺术,似乎是在进行学术探讨一般的写作特征。
这种作家,人们通常称之为学者型作家。
文学的成熟,首先应该是特别重视文本的意义和价值。
而中国文学之不成熟,正是文学研究者甚至一般读者总是忽视小说文本的审美价值。
当下文坛,大家对文学的态度,太过浮躁,几乎没有谁会有耐心去认真对待一些有创造性的作品。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花腔》这样优秀文本的出现,它首要的意义,是象征着文学的纯正品格的出现。
但是这部具有纯正文学品格的小说,自2002年面世以来,按说获得的关注并不少,然而却一直没有人充分研究和关注它真正优异于其他小说的地方,至于对于文本的研究,也几乎无人提及。
对《花腔》来说,若不能抓住它在文本方面的贡献,就等于无法真正认清它的文学价值以及独特意义。
我们每年出版数千部小说,却未必能从中寻觅到一个有独特面貌的文本。
一个好文本、新文本,也似乎好多年才会出现一个,像天上掉馅饼一样。
李洱的《花腔》,正是这种不可多得的作品,一个精致的堪称完美的文本,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即所谓的先锋文学闹腾一场之后,在一地鸡毛的场地上,几乎是硕果仅存的可以继续谈论的一部小说。
一尧文本是一个客观存在文本是什么?“文本是文学活动的直接结果。
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诗学”——以《花腔》为例

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诗学”——以《花腔》为例
刘思谦
【期刊名称】《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3(36)1
【摘要】新历史小说是近十几年来我国文坛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
它的最初命名对应的是当代历史 (包括革命史 )题材小说 ,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似乎并无关系。
但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观察这一文学现象 ,同时立足于中国问题 ,不仅可以获得新的视域 ,而且有利于发现和总结新历史小说所内涵的历史诗学 ,探索文学叙事与历史的微妙关系。
为此 ,本刊组织了一组以阐释新历史小说之历史诗学为主的笔谈。
【总页数】9页(P108-116)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新历史小说;历史诗学
【作者】刘思谦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相关文献】
1.时代精神与英雄形象塑造——论革命历史小说与新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抗战英雄形象塑造 [J], 刘宏志
2.历史小说理论研究的新突破——评蔡爱国《历史的表情——当代历史小说的叙
事策略与精神旨归》 [J], 莫先武
3.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新典范——评祝春亭、辛磊的历史小说《大清商埠》 [J], 李满;
4.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新典范——评祝春亭、辛磊的历史小说《大清商埠》 [J], 李满
5.《花腔》中的历史诗学 [J], 杨海波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新历史主义小说《花腔》叙事浅析

第37卷第3期Vok37No.3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LANZHOU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20296Jun2021新历史主义小说《花腔》叙事浅析代东冉(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天津300270)[摘要]《花腔》作为一本新历史主义小说,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去解构历史,在时代背景与权力话语体系下,作;中不同叙述者的叙述受到了限定,视角、立场的差异构成了一场叙事的狂欢。
这部作;采用了顺叙、插叙、倒叙等多种叙述顺序,在相差巨大的时间节点上,以不同的叙述语言娓娓道来葛任之死的"真相”。
本文从《花腔》的叙述者、叙述时间和叙述话语三方面对其叙事进行详细分析。
[关键词]历史叙事;叙述者;叙述时间;叙述话语[中图分类号]12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9503(202903903593[收稿日期]2020-9-9《花腔》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叙事观念。
这部小说是以三个人的采访和对话为基点展开的,主要讲述了葛任之死的故事,其中还掺杂着“我”的一些叙述,每位叙述者都坚持本人叙述的真实性,但是综合几部分叙述对照,就能发现每位叙述者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叙述,真真假假,如雾里看花。
《花腔》引用了大量的回忆录、报纸、文章等资料,从个人化的角度去解读历史、解构历史,以倒叙、顺叙、插叙的叙述时间来叙述故事,通过虚构化、个人化、碎片化的叙述展现出葛任这个人生命的片段。
一、叙述者(一)多个叙述视角《花腔》以白圣韬、赵耀庆以及范继槐三个人的叙述“@”为主体,“我”的补充叙述“&”为副本,讲述了革命烈士葛任在二里岗战斗中牺牲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得到了葛任幸存的消息,不约而同地选择审问劝降和灭口的故事。
第一个叙述部分是在1773年由白陂至香港途中,由白圣韬向范继槐讲述的,白圣韬是一位精通粪便学的医生,是葛任年少的朋友,他曾和葛任一起去苏联访问,观察当时苏联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制。
花腔写历史 故事又新编——读李洱《花腔》,兼谈鲁迅与瞿秋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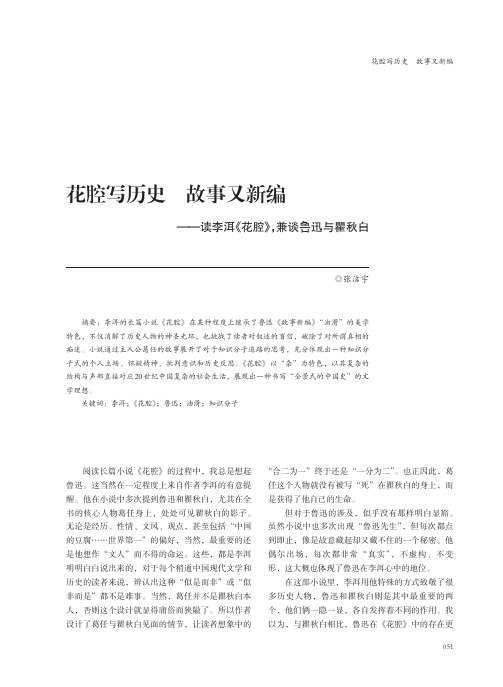
的豆腐……世界第一”的偏好,当然,最重要的还
到即止,像是故意藏起却又藏不住的一个秘密。他
是他想作“文人”而不得的命运。这些,都是李洱
偶尔出场,每次都非常“真实”,不虚构、不变
明明白白说出来的,对于每个稍通中国现代文学和
形,这大概也体现了鲁迅在李洱心中的地位。
历史的读者来说,辨认出这种“似是而非”或“似
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⑥问题的
题——“花腔”——做出了画龙点睛般的诠释。
“花腔”是包含了“油滑”的意味的。民间说
“耍花腔”的基本意思就是“用虚假动听的话骗
人”。在小说的第二部“向毛主席保证”中,阿庆
关键在于,在什么地方“点染”,在什么时候“信
口开河”。作家显然不会是为油滑而油滑,因此,
及 《理水》 与“油滑”问题,这绝不是随意为之,
“花腔”与“油滑”的联系是明显的。那些插
他暗示了小说对 《故事新编》 的历史观与叙事方式
科打诨、时空错乱的语言和细节,用鲁迅的话说,
的致敬与借鉴,甚至于,他是在借鲁迅之口点明
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叙事有时也有一
“油滑”的意义与效果,暗中对自己这部小说的标
中年之际就已充分表露的怀疑、绝望和虚无的情
话真说地耍花腔,还是真话假说地讲历史呢?这是
绪,到了他深居上海市井与革命文学漩涡中心的这
整部小说留给读者的最大悬念。
个时候,更得到了极大的爆发。他以一种对于历史
小说里也曾给出过“花腔”的“定义”,说
与现实统统看透的深刻与清醒的姿态,将古往今来
053
2021 年第 3 期
鲁迅。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作者李洱的有意提
任这个人物就没有被写“死”在瞿秋白的身上,而
迷雾中的探寻——论《花腔》的叙事交流模式

、
一
作者简介 : 杜仙茹 , 在读硕士 , 华侨大学文学院 2 0 1 4 级现 当代文学专业 。研究方 向: 当代小说及文艺思潮。 基金项 目: 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 目 。
・
1 41・
第1 1期
鸡 西 大 学 学 报
2 0 1 6丘
然不是, 细看范老的叙述不难发现同样的花腔, 如对于自己
特的叙述交流模式, 即一个异故事叙述者“ 我” 和三个作为 同故事叙述者的“ 亚故事叙述者” , 每个同故事叙述者的 叙 述发生在不同 历史时期, 独立成章且有相对应的固 定的 受 述者, 而“ 我” 则在他们的 叙述过程中通过副本对他们的 叙 述进行必要的补充( 辨伪) , 这样的叙述交流模式与所叙述 的内容一起, 极大地扩充了小说内涵, 从而使叙述交流模式 本身也具有了极深的意味。 潜在花腔: 不对等的叙述情境设置 依照普林斯定义 , 叙述者是指“ 铭刻在文本 中” 的“ 叙 述[ 故事] 的 人” , 而受述者则 是指与叙述者相对的“ 接受叙 述的 人” 。 …小说中 多重叙述者和受述者的安排能使读者 体悟到 不同的叙述情境。《 花腔》 的主体由三个并列的部 分组成 , 三个部分分别 由三名参与到葛任最后岁月的同故 事叙述者在不同的时间段完成( 他们都与葛任有着较为密 切的关系, 并被不同的政党派往大荒山执行刺杀葛任的任
信仰就是希望国家强盛, 早 日实现现代化。可是, 要强盛,
而侥幸存活的葛任不但什么都不是了, 如若回到延安, 还会 爱” 的名义下, 奔 要实现现代化, 首先得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 。对于 自己最 以叛徒论处。因而医生白圣韬就在这份“ 赴大荒山执行刺杀葛任的相关任务。而在国民党方面, 执 终借川井之手杀死葛任, 他这样说“ 这是大气候和 小气候决 定的……现在毙掉他, 其实是在成全他……我杀掉他, 他不 行与葛任相关任务的人员杨凤 良、 赵耀庆以及范继槐的出 就成为烈士了吗? ” 由于叙述者的地位以及讲述这段历史的 发点也是对于葛任的“ 爱” , 在他们相关的叙述 中, 这种 “ 爱” 溢于言表, 甚至连最后安排 日 本人川井杀死葛任的范 目的—— 自己的传记 , 所以在叙述过程中也就避免不了刻 继槐还这样说“ 天地良心 , 我是因为热爱葛任才这样做的 意的美化。 “ 花腔” 含义有二, 一种为带有装饰音的的咏叹调 , 另 呀” , 爱与死相连, 爱是死的前提, 死是爱的体现, 在特定的 种为小说中A圣韬所说的那样 , 即花言巧语, “ 巧言令色, 国 人之本能也。 ” 小说取名为《 花腔》 显然具有极强的反讽 意味, 在这种反讽之下的叙述情境设置便显得极富意味。 “ 人格担保仅仅是一种道德担保, 而道德却并非解决一切的 良药” , 所以尽管三个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都一再保证 自己所讲述的内容为真 , 但是由于其与受述者的特殊关系 以及叙述的内容对其 自身可能产生的影响, 因而在叙述之 前, 这些影响其叙述真实性的潜在要素便使其所叙述的内 容变成了可能性的“ 花腔” , 而这也使“ 我” 所苦苦追寻的真 实在一开始便染上了“ 花腔” 的色彩。
简谈《花腔》的历史叙述

简谈《花腔》的历史叙述作者:陈烨来源:《电影评介》2015年第08期李洱一直坚持着“知识分子写作”,一是他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另一点是他的小说一直致力于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和发展的探究。
《花腔》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自其面世,就在文学界和评论界引起很大的轰动和反响,直至今日,我们看他的《花腔》仍无法找出另一本小说将它们并置来谈其中的共性。
小说对历史的回顾并有给读者一个历史的真相,而是使历史更加扑朔迷离,进一步会使读者对过往历史类书籍中的历史产生一定的怀疑。
从小说的名字来看,“花腔”有着两层含义,本义是指基本的唱腔加花,成为一种特定的华彩腔调。
其引申义是比喻玩弄花招。
这两层意思在小说中白圣韬的讲述里都有涉及。
从文本来看,标题“花腔”既指小说的多声部叙述,各人叙述的真假难辨、虚实不分,另外从小说中出现的文类题材也能契合这一标题。
一《花腔》的叙述带有多声部特点。
三个主要的叙述者,他们的讲述构成了文本的主体部分“@”,还有一个总的叙述者,同时也是对于过去历史的整理记录者,他在主要叙述者的讲述过程中,随时插入与讲述的人物或事件相关的各种资料,构成小说的副本“&”。
小说的三个需要叙述者:白圣韬、阿庆(赵耀庆)、范继槐。
他们和历史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过共同的生活和交往经历,交情不浅,在处理葛任的事件中,他们却都是带着同样的使命——置葛任于死地。
三个人围绕这件事展开了自己的回忆和讲述。
而“回忆不仅是单纯地把往事再现出来,回忆也是重建,它本身就是一种图式活动,通过演绎和推理完成对过去事件的重建”。
“我们的回忆本身,就有重建过去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回忆总是立足于现在的需要才产生的”。
[1]小说中详细记载了三个人讲述故事的时间和地点:白圣韬于1943年从白陂到香港的逃亡路上对范继槐讲述;阿庆于1970年在劳改场对调查组讲述;范继槐是在2000年从京城到白陂市的火车上讲给白圣韬的后代白凌。
在小说的“卷首语”,总的叙述者就提醒读者:“讲述者本人的身份往往存在着前后的差异。
穿透花腔迷雾论文:穿透花腔迷雾管窥个人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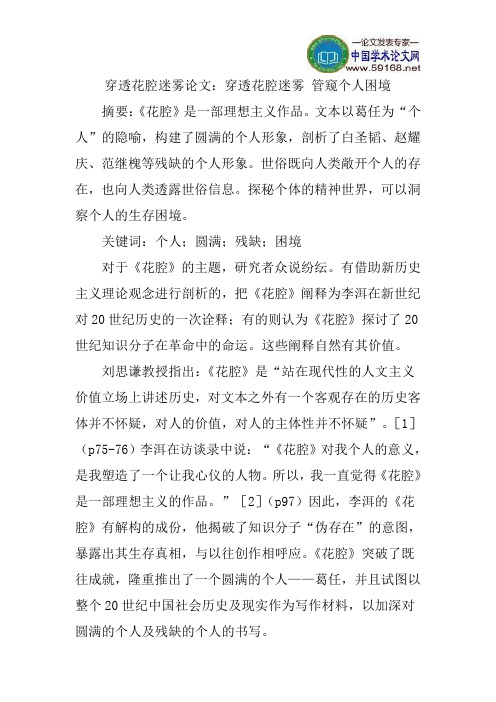
穿透花腔迷雾论文:穿透花腔迷雾管窥个人困境摘要:《花腔》是一部理想主义作品。
文本以葛任为“个人”的隐喻,构建了圆满的个人形象,剖析了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等残缺的个人形象。
世俗既向人类敞开个人的存在,也向人类透露世俗信息。
探秘个体的精神世界,可以洞察个人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个人;圆满;残缺;困境对于《花腔》的主题,研究者众说纷纭。
有借助新历史主义理论观念进行剖析的,把《花腔》阐释为李洱在新世纪对20世纪历史的一次诠释;有的则认为《花腔》探讨了20世纪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命运。
这些阐释自然有其价值。
刘思谦教授指出:《花腔》是“站在现代性的人文主义价值立场上讲述历史,对文本之外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客体并不怀疑,对人的价值,对人的主体性并不怀疑”。
[1](p75-76)李洱在访谈录中说:“《花腔》对我个人的意义,是我塑造了一个让我心仪的人物。
所以,我一直觉得《花腔》是一部理想主义的作品。
”[2](p97)因此,李洱的《花腔》有解构的成份,他揭破了知识分子“伪存在”的意图,暴露出其生存真相,与以往创作相呼应。
《花腔》突破了既往成就,隆重推出了一个圆满的个人——葛任,并且试图以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现实作为写作材料,以加深对圆满的个人及残缺的个人的书写。
一、圆满的“个人”——葛任“个人”是一种理念,是一个抽象名词,它当然会以“思想”的方式存在于各种思想性的文本中,供读者阅读、思考。
李洱则提供了“葛任”这个具有“隐喻”意义的形象,以葛任“行走的影子”的方式——实践的方式、外在的症候向读者敞开了个人的真相。
这些实践、这些外在症候可能是“羞涩”的,可能是“个人的秘密之花”,而且总是只属于个人的,它不属于公众,它有私密性的特征,它害怕为人窥破,似乎不应为外人所道,但“个人”又是那么顽强地向世人敞开着自己,使世人得以一窥庐山真面目。
少年时代,葛任与冰莹的恋爱自然而纯洁,从玩伴到恋爱,从结伴游玩到“定情物柳叶笛”的赠送,没有俗世金钱、地位等的纠缠和烦恼,只有纯情相伴。
先锋文学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重读《花腔》

因为葛任先生的死,因为爱的诗篇与死亡的歌谣总在一起唱响,我心中常常有着悲愤和绝望,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写作的继续,这悲愤和绝望又时常会变成虚无的力量。
虚无的力量是那样大,它积极的一面又是那样难以辨认,以致你一不小心就会在油腔滑调中变成恶的同谋。
我必须对此有大的警惕。
感谢《花腔》的主人公葛任先生,是他把自我反省的力量带给了我,并给了我一种面对虚无的勇气。
———李洱,《花腔》后记李洱《花腔》发表于《花城》2001年第6期,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多次再版,被部分批评家视为“先锋文学的集大成之作”譹訛。
问世以来,《花腔》一直被纳入“先锋文学”的框架中来理解,《花腔》的叙述旨趣,也确实流露出“先锋文学”的明显特征,“向历史真相接近,但最终这个真相又不可接近,所有的意义都产生在探索和叙述中”譺訛。
在表面上,《花腔》似乎是一部新历史主义的先锋典范譻訛,小说以多声叙述来表现历史之虚构,这无疑契合着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观点,“我将历史作品视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中的一种言辞结构”譼訛。
而李洱自己尽管在写作《花腔》前没有读过这类理论,但他以神似海登·怀特的口吻表示,“其实历史也是一种叙述方式”譽訛。
在《花腔》的《真实就是虚幻?》这一节中,叙述人举了一个剥洋葱的例子,“‘真实’就像是洋葱的核,一层层剥下去,你什么也找不到”譾訛。
然而,回顾《花腔》的接受史,笔者有一点疑虑:几乎所有关于《花腔》的评论,都内嵌着“先锋文学”的认知装置。
在这种阐释中,“先锋文学”不是一个供讨论的对象,而是给定的知识与认知的范式。
倘或,《花腔》真的仅仅是虚构、虚幻乃至于虚无的作品,真的是“什么也找不到”的对历史的怀疑,那么笔者难以读懂《花腔》后记。
“洋葱”辛辣,李洱这样的作家也流下了眼泪,“那一夜如此遥远,又如此迫近,似乎还要反复重现。
多年来,我无数次回到《花腔》的开头,回到那个大雪飘飘的夜晚……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的雪花,此刻从窗口涌了进来,打湿了我的眼帘”譿訛。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浅析“新历史主义小说”《花腔》摘要:随着西方“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传播,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国文坛作家们也把精力投入到“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中,李洱的《花腔》即是其中之一。
《花腔》讲历史的“真相”置于广泛的“虚无”之中,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开拓了私人话语空间,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念。
关键词:《花腔》;新历史主义;真相;消解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012-01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文坛上掀起一场颇具声势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思潮,李洱的《花腔》是其中的代表。
《花腔》运用消解的手法,将历史的“真相”置于广泛的“虚无”之中,用极富个性的叙事技巧和独特的个体价值体验,完成一次对历史真相和传统思想的消解。
阅读李洱的《花腔》,最初直观的阅读感觉是这个小说很像侦探小说和笔记小说。
小说的叙事框架别致有趣,在“我”设置的叙事结构中,安排三个故事讲述者,三个讲述者以各自的讲述演绎了自己的角色。
三个叙述者明明讲述的是同一经历,但不同讲述者那里,事件、人物的面貌大不相同。
小说的小字部分,有叙事人给读者提供的参考和线索。
使读者自己也参与到故事中来,用自己的观察、思考来追寻历史真相。
本文认
为这部小说有三个问题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思考,也正是在对这三个问题的探寻中,我们可以渐渐发现《花腔》对意识形态的某种解构与反叛,同时也可以以此为点来思考“新历史主义”的创作目的和先锋特色。
第一个问题——谁杀死了葛任。
其实在书中明确交代了是白区军统的高级特务范继槐串掇日本人
川井,杀死了葛任。
但是欲行杀人灭口之事的,不只是白区,苏区派出的白圣韬等人也有或者被迫有杀人动机。
这些人无一不是葛任的旧交,而且感情深厚。
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被不同的叙述者赋予了不同的内涵。
但“我们”有时并非真是从大局、整体来考虑的,往往还是归结于个人私利。
无论是范继槐还是田汗,他们都希望葛任继续做“民族英雄”或者为己所用。
葛任若配合范继槐,为国统区效力,可以使范继槐光荣地完成任务,以此获得加官进爵的筹码。
葛任若配合田汗,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地做“二里岗”牺牲的“民族精英”,既可得个人的美名,也可让田汗维护自己的利益地位。
第二个问题——个人(葛任)的选择与消失。
虽然葛任死于他杀,但他的死似乎有很大的自我选择成分。
他自己通过再次发表旧作(《蚕豆花》),主动“泄露”自己活在大荒山的信息。
而且阿庆说他“料事如神”,其实是葛任明白(预计)到几方人马的寻找。
既然如此,他肯定预料到自己“不合作”态度的下场——死。
但他不怕,甚至可以说是从容赴死。
叙事人没有给予真正权威的原因,只是做了揣测——葛任是在“向世界预告,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真实的生活其实才刚刚开始。
”作者也许只是在暗示,每一个读者作为独立、的个体,也应该像葛任一样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葛任”,很明显在谐音“个人”,他瘦弱、羞涩、忧郁,但也豪迈、忠诚。
他选择死亡,是一种抗争。
他也许正想通过一种试验似的方式看自己能否不属于某一阵营而作为作为“个人”,作为“自己”存在着。
他的消失似乎是一种必然,在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面前,“个人”必须归于胜利者的阵营,或者依顺胜利者的声音,否则只有“消失”,只有被遮蔽。
第三个问题——“花腔”与“油滑”。
“花腔”的原义是指中西皆有的一种发声唱法,以声调多转折、拖腔格外长为特点,也包括种种装饰音、急速的音阶等等。
后来,多用“耍花腔”比喻用虚假而动听的话骗人。
李洱的《花腔》,显然是用了“花腔”的引申义,但又不仅止于此。
在《花腔》中,曾出现多次的是“油滑”这个词。
作者虚实真假地用了鲁迅先生写《故事新编》的事,在鲁迅与葛任的书信来往中讨论写作中“油滑”的运用。
葛任的“油滑”。
葛任为人、为文都并不油滑,《花腔》里阐述的故事也很严肃的。
但葛任从容赴死的这个选择似乎又充满了游戏与实验的意味。
一切都在他预料之中,所以他不急不躁,也不配合。
几路人马为之懊恼、焦虑时,葛任却偏偏“淡定”地一意孤行。
他像
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耍了一次滑头,只不过这“油滑”的目的其实是“较真”。
传统的历史小说往往有一个经历传奇的英雄式主人公,他们中大多数都是通过对“崇高”的追求,为历史和社会的前进作出贡献。
但以《花腔》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却浓墨重彩的写出了历史的偶然性和个人可能拥有的选择性。
李洱在“反讽”、“复调”、“结构主义诗学”、“互文”等后现代主义的技术的运用中把真实变成一个扑朔迷离的虚幻概念,扩大了私人话语空间,使《花腔》的文本意义不是由意识形态话语加以确认的,而是提供了读者可以自由解释的话语空间。
这也正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意义之一,拥有了属于个人的历史观,在所谓的主流历史观下开拓了个人的历史视角和感性化思考,尽可能地让每个人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参考文献:
[1]刘玉山等.《花腔》:对“先锋”的再言说[j].小说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