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童历史小说的生存意识与逃亡意识
浅析苏童小说中的逃亡意识

浅析苏童小说中的逃亡意识摘要20世纪80年代,一种以独特的话语方式构成的小说文体新形式在中国一个接一个的登上文坛,从一开始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新颖独特的文学创作之路,并被大家广泛喜爱,在这期间,苏童,马原,余华就是当时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作家。
作为 80 年代后期的作家,苏童在文学形式上的创新已经显而易见,从创作内容到创作方式,同样的,在语言上我们也很容易看到有一些明显的表现形式上的创新,大胆超越传统,用奇异的语言冲击着读者的审美这些特点也奠定了他在“先锋作家”领域的地位。
苏童小说里的意识有很多,其中“逃亡意识”应该是最引人关注的,因为对于探讨苏童小说中的逃亡意识,对于当下处于改革中的中国有着深远的意义,的小说中所展现的逃亡主题反映的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普遍的焦虑、迷茫、和窘迫,这点和当时许多作家形成了共鸣,在改革开放己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人们原有对生存现实的态度,经济利益已经是无可替代时,信仰危机也就随之而来,用“逃亡”来面对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因此探讨苏童小说中人们当时迷失的状态也就为逃亡的主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素材关键词:逃亡先锋文学信仰危机一、逃亡的主题对于逃亡的主题,苏童是这么对读者说的:“逃亡好象是我所迷恋的一个动作,人只有恐惧了,拒绝了,才会采取这样—个动作,这样一种与社会不合作的姿态,才会逃,我觉得这个动作或姿态是—个非常好的文学命题,这是—个非常能够包罗万象的文学主题,人在逃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好多所谓的人生的价值和悲剧性的一面”[1],《1934 年的逃亡》中的陈文宝的儿子狗崽,作为新生一代,逃离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留下的也无疑就是老弱病残,《罂粟之家》中,“我”也看到家乡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神韵,随处可见的逃亡已经使这里蒙上了一层代表结束阴影;除了人为的因素,《米》中的五龙,是自然灾害是五龙背井离乡,不愿与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为伴就只能城市来对内心中家乡进行重建,自然灾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乡村的吞并已经是势不可挡,对于农村的青年人,即使怀着深深的乡愁也只能踏上对城市的探索之路。
毕业论文从黄雀记看苏童小说“逃离”主题之新变

从《黄雀记》看苏童小说“逃离”主题之新变摘要:《黄雀记》是苏童近年的作品。
苏童选取其惯用的“逃离”主题来贯穿全书。
《黄雀记》一方面延续了苏童以往的写作风格,另一方面在其主题表现形式和结局安排上,有着创新性。
研究其中的创新性,深化对“逃离”主题的认识,挖掘苏童写作上的创新。
关键词:《黄雀记》逃离失魂意象宿命论《黄雀记》是苏童最新的长篇作品,属香椿树街系列作品。
其创作风格较之前期有了很大的改变。
近年来,人们主要分三个方面来研究这部作品。
第一是研究其出现新的内容,如研究作品中的新意象、新现象、新的创作手法,是属于对比性的研究,如绳之捆绑——论苏童小说《黄雀记》中的“绳索”意象;第二是研究某一个主题在作品中的体现,如其孤独意识,是属于综述性的研究,如何处是江南——论苏童《黄雀记》的孤独主题;第三是对作品的解读,属于探索性的研究,如一场时代的失魂记——关于《黄雀记》的一种解读。
而本文主要研究此作品“逃离”主题表现的新方式,属于对比性研究。
苏童是我国先锋小说派的代表人物,其创作的作品在国内外都得到不少的好评,有些作品甚至被拍成电影,搬上荧幕。
通过细分,苏童作品可分为三类,其中“枫杨树故乡”类作品最受关注。
这类小说基本是以“逃离”为主题,而且表现形式各异。
而“香椿树街系列”则像一部斗争史,以“少年、暴力”作为主题。
逃离,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
其内部有着深层的思想内容,包含着民族文化组成的部分。
可以说,逃离是一个带有民族性的名词。
但是由于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在中西方的历史中,都未确立到最为准确的定义。
段义孚对“逃”则有这样的描述“一个人受压迫的时候,或者无法把握不确定的现实的时候,肯定对非常迫切希望迁往他处。
”[]p1据此,我们可以把“逃离”划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物理空间的更换变迁,而是精神意义的无根漂泊。
而苏童一直坚守”逃离“主题,文学史上对苏童有着这样的评论“对于苏童来说,逃遁是命中的劫数,是命运分派给他的第一主题,也是他小说的基本情调。
论苏童小说的死亡意识

037
作家杂志 Write品研究
冬天挥洒自己的一腔热情。梅珊, 她是 那种宁愿拼一个香消玉陨来换取刹那 光华的女人。她宁愿焚毁自己也不愿 在屈从中漫漫凋落, 她像是黑夜里一 朵妖娆的昙花, 散发出逼人的美丽。梅 珊在临死之前还在吟唱她的京剧, 一 字一句都是诉说: 叹红颜薄命生前就, 美满姻缘付东流。她挥舞水袖在风中 飘扬的身影如同俏丽的鬼魅在陈府翻 飞。
梅 珊( 《妻 妾 成 群》) 大 胆 而 任 性 , 对陈府、对陈佐千她有一种洞透了污 浊人生的反抗。她完全用一种自毁的 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和忧伤。她用 自己青春健康的躯体来嘲弄、祭奠陈 佐千的干枯的生命。她或许可以没有 爱情, 但不可以没有激情。她不可能不 知道那可怕的井是专门用来吞没反抗 者的灵魂的, 但她依然公开在飘雪的
忧伤, 也是对人的现实境遇和文化命 运的忧伤。
三 死亡具有其独特的审美意义 苏童和其他同代的作家一样在他 的小说之中, 我们也能看到苏童对于 死亡的惨烈和死亡清静的激烈描述的 场面。在这一点上苏童和余华他们一 样, 都对于死亡的场景有比较过于欣 赏化的描述。这手法在当代“先锋小 说 ”中 也 是 比 较 常 见 的 表 现 方 式 。例 如 在《罂 粟 之 家》中 对 于 沉 草 杀 死 哥 哥 演 义 的 描 述 , 作 者 写 到“ 他 抓 起 那 把 柴 刀 朝 演 义 脸 上 连 砍 五 刀 ”,“ 脚 下 流 满 一 汪 黑 红 的 血 ”; 在《一 个 礼 拜 天 的 早 晨》 中 ,“ 香 椿 树 街 的 人 们 来 到 路 口 , 看 见 水泥地上有一滩鲜红的血污, 血污的 旁边横陈着一辆熟悉的破旧的自行 车 。 ”“ 在 早 晨 , 九 点 钟 的 阳 光 下 , 那 块 肥 肉 闪 烁 着 模 糊 的 灰 白 色 的 光 芒 。”这 样 的 反 观 的“ 冷 叙 述 ”的 手 法 把 死 亡 的 审丑意义表现得是很鲜活的。 人的生命从一开始便无可挽回地 走向死亡。苏童向读者展示的这幅死 亡图画看来是够阴暗, 够恐怖了。但按 照存在主义哲学的解释, 人只有真正 领会和懂得死, 才真正领会和珍惜生。 畏死使人能够反省生存, 获得生命的 动 力 。死 亡 为 生 命 带 来 了 极 限 或 边 界 , 死亡与生命坚实而不可离异地交织在 一起。对死亡意识的关照, 有助于人们 对 生 命 的 重 新 塑 造 。“ 正 因 为 有 了 死 亡 意识的骇人提醒, 人的生命才获得了 一 种 吁 求 超 越 的 可 能 性 。”苏 童 打 破 了 传统文学对死亡意识的遮蔽, 使死亡 昭显出来。只有通过死亡意识震醒灵 魂后, 人才可能通过有限的生命获得 内 在 而 纯 正 的 高 度 ,“ 向 死 而 生 ”( 海 德 格 尔 语) , 是 人 类 生 存 的 一 种 必 然 状 态。
论苏童小说的逃亡主题

论苏童小说的逃亡主题一、本文概述Overview of this article苏童,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刻的主题内涵,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和学术界的关注。
他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触、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人性的深入探索而著称,尤其是他小说中的“逃亡”主题,更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解读。
Su Tong, one of the important writer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as won the attention of a wide readership and academia with his unique literary style and profound thematic connotations. His works are known for their delicate brushstrokes, unique narrative style, and in-depth exploration of human nature, especially the theme of "escape" in his novels, which has sparked widespread discussion and interpretation.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苏童小说中逃亡主题的内涵、表现形式及其文化意义。
我们将对苏童的创作背景进行简要介绍,以便更好地理解其作品中逃亡主题的来源和背景。
我们将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揭示苏童小说中逃亡主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包括人物逃亡的动机、方式以及逃亡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等。
我们将从文化、社会和心理等多个角度,对苏童小说中的逃亡主题进行深入解读,探讨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语境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This article aims to delve into the connotation, expressive form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eme of escape in Su Tong's novels. We will provid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u Tong's creative background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ource and background of the theme of escape in his works. We will reveal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theme of escape in Su Tong's novels through specific text analysis, including the motivations and methods of character escape, as well as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s during the escape process. We will delve into the theme of escape in Su Tong's novel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culture, society, and psychology, and explore its uniqu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ntext.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苏童小说的艺术魅力,同时也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欣赏和理解苏童的作品。
《黄雀记》:从叙事策略、逃亡与意象运用解析苏童的情感世界

《黄雀记》:从叙事策略、逃亡与意象运用解析苏童的情感世界最开始了解苏童其实是从电影开始的,看过巩俐主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章子怡主演的《茉莉花开》,才知道这些经典的影片都是改编于苏童的小说。
《黄雀记》也是一部非常优秀而且值得改编的小说,小说通过三个人十多年的人生际遇和变故,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小人物的生活现状,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等深刻的人生主题。
《黄雀记》在2015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现实内容为基础但是又充满了诗意的笔法,勾勒出一幅芸芸众生相。
小说中独具匠心的叙事策略、令人深刻的逃亡形象、蕴含深意的意象都值得称道,本文就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解析这本小说,更好地去理解苏童构建的情感世界,还有他高超的写作手法、表达的思想内涵。
1,时空交叉倒的叙事,构成了一个春、夏、秋“轮回”的情感世界。
叙事策略可以说是长篇小说的精髓和灵魂所在,纵观以往的长篇小说,通常采用的叙事策略都是连贯的线性结构。
比如《红楼梦》整体的叙事,从宝玉的前世,到宝玉出生在贾府,然后经历了荣华富贵到破落不堪的生活,最后绝望出家。
这样的叙事就是连贯的线性结构,也是很多长篇小说都会采用的结构。
苏童的《黄雀记》并没有采取这样的结构,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他另辟蹊径,用独特的叙事策略讲述了一段关于保润、柳生、仙女之间的情感故事。
(1)3个叙事时空,统一成一个完整的时间轴《黄雀记》整个故事分为3个相对独立的中篇,名字分别是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这个3个中篇联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时间轴,讲述了他们三个人12年的爱恨情仇。
这个3个中篇对应了3个季节的变化和交替,其实也是暗指时间的更替和主人公的不断成长。
在这3个叙事时空中,对应着3个主人公的叙事视角,以这个主人公的经历为侧重点。
“保润的春天”讲述了青春期的保润暗恋仙女,这里仙女和白小姐其实是一个人,只不过名字有一些变化。
后来柳生强暴了仙女,但因为仙女的报复,保润成了替罪羊进了监狱。
浅析苏童小说中的死亡主题

浅析苏童小说中的死亡主题师保亮死亡作为一种日益迫近的确定性的抽象存在,对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
王夫之说:“草木任生,而不恤其死;禽兽患死,而不知哀死。
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
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废天地之化。
故哀与患,人禽之大别也。
”由此可看,死亡问题,也有它属于人类的一面。
死苏童笔下的人物从小到老,从生到死,都是死亡这一主题的高手,那么,苏童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确立贯穿于这些小说中的死亡主题的?他笔下人物的死亡方式为何具有颓废耽美让人把玩不已的特点呢?本文正是基于这些困惑,试图去理清这些问题。
1 家族背景下人物的死亡许多人一辈子都生活在一条幽暗的巷子里,在殖民式的情绪中等待感恩节的来临。
苏童在1987年第5期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这篇小说中充满了灵气十足地情景和氛围,以及让人惊讶的想象和随之产生的另类幻觉,更重要的是由此交织而成的纷繁感悟,在逃亡的背景下,读者完全可以摒弃题目所带来的冲击力,因为逃亡既可以是发兴无端的,也可以是被迫的,苏童将小说题目故意虚化,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是对那个特殊时期的考量和显化。
1.1 对故土的诗意营造“祖母蒋氏在朝祠堂里走的时候手被汗湿透变得僵硬……而令人困惑的是陈宝年从她身上嗅到了一股牲灵的腥味。
”苏童志不在召唤一史诗般雄浑苍朗的格调,所以在破败的家族中,陈文治疯狂的野心侵蚀着他腐烂的身体,在有限的时间历程和无限的时间长河中,一个又一个家族只是事件或时间的标示,而不是存放个人生命价值的源泉。
作为家族的末代子孙,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写出了“那将是个闷热的夜晚……包围着深夜的逃亡者。
”在苏童笔下,“自从幺叔死后,罂粟花在枫杨树村绝迹,以后那里的长出了晶莹如珍珠的大米,灿烂如黄金的麦子。
”象征死亡和绝望的罂粟大块大块地消失,象征重生的大米小麦拔节生长,在上溯家族沧桑追忆父辈事迹的过程中,械斗与攻讦络绎不绝不知归路,而所有的这些在作者看来,是“为了表现人生世界的不确定性……我真正面临过死亡的威胁,所以长大后在小说中经常写到死亡,我作品中之所以弥漫着那么一种氛围,也许是因为与那个时期的经历有关。
试论苏童小说里的逃亡主题——以《米》为例

Vo1.35 NO.1
新 乡学 院 学报 Journal of Xinxiang University
2018年 1月 Jan.2018
试 论 苏 童 小 说 里 的逃 亡 主题
—
—
以 《米 》为 例
张子 晴
(西北 师 范大学 文 学 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收 稿 日期 :2017 09 11 作者简 介 :张子 睛(1996一 ),女 ,河南新 乡人 ,研 究方向 :现 当代 文学。
张 子 晴 :试 论 苏童 小说 里 的 逃 亡主 题
· 35 ·
孩 子 。
织云真切 、善 良的问候给五龙 的 IL,里 带来 了快乐 ,可 这
苏童最著名 的文本《妻妾成 群 》写 的并 非简单意 义 快乐马上被冯老板 的态度打破 了。冯 老板让织云 给五
一 、 逃 离 家 园 后 的 无 助
《米 》写 的是 五龙逃 亡 的故事 ,同 时也是 关 于追捕 者与逃亡 者 虚假 性 关 系 的命 题 。逃 亡 者 五龙 来 自农 村——枫杨树 乡 ,在 城市 兜兜转 转 后仍 然渴 望 回归家 乡 。“五龙”谐 音“乌龙”,逃 离家 园 的五龙最 终 回到 了 家 园,这一场逃 亡似 乎从未 开始 ,逃脱 了乡村 的灾难 , 又身 陷都市 的罪恶 ,所有 的一切 只是 子虚 乌有 的生存 游 戏 。
苏童 的写作 既没有启 蒙角度的叙 述压力 和意识形 态 的局限 ,也没有刻意 营造苍凉无力 的文化失 落感 ,他 进行 的似是一场无助 的写作 。他 穿越 充满罂粟 气息 的 南方 ,穿越 自己颓败谨慎 的童年 ,仓促 地来到 自己的文 学世界 ,悲壮 而满 足。这 似乎 是其 作 品中重 复 出现 的 “逃亡”主题 的原型 。苏童 在和林 舟 的访 谈 录 中说 ,人 只有恐惧 了,拒绝 了 ,才会采取这样 一个动作 。具体来 说 ,在“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 ”成长 的少年 ,似 乎喝醉 了酒 ,始终在逃亡 的路上 。
一场追逐人性的盛大逃亡_论苏童_我的帝王生涯_中的逃亡意识

A chase human grand getaway———Talk about the fugitive consciousness in Su Tong's "My career emperor"/Jingxin Shi一场追逐人性的盛大逃亡【摘要】纵观苏童的小说创作,透过他委婉哀伤的笔端,不难发现苏童对于“逃亡”有着欲罢不能的眷恋,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有想挣脱现状的逃亡情结。
在《我的帝王生涯》中,苏童通过主人公端白跌宕起伏的一生使逃亡意识得以彰显,因此,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主人公端白的逃亡史,一场挣脱人性束缚的大逃亡。
【关键词】孤独逃亡轮回Abstract :Throughout the creation of Su Tong's novel,through his sad euphemism written down,not difficult to find Su Tong to "escape"has unable to stop the attachment,works almost all the characters in the status quo on the run to break complex."My career emperor",the Su Tong ups and downs through the hero's life end so that the white flight to demonstrate awareness,so this work can be said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hero end of white flight,abigbreakescapehuman bondage.Key words :lonely flight cycle在苏童的作品中“逃亡”这个词并不陌生。
论苏童小说的逃亡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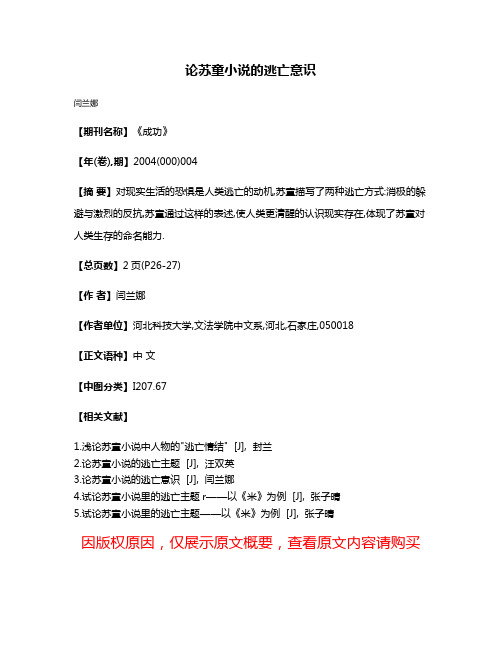
论苏童小说的逃亡意识
闫兰娜
【期刊名称】《成功》
【年(卷),期】2004(000)004
【摘要】对现实生活的恐惧是人类逃亡的动机,苏童描写了两种逃亡方式:消极的躲避与激烈的反抗,苏童通过这样的表述,使人类更清醒的认识现实存在,体现了苏童对人类生存的命名能力.
【总页数】2页(P26-27)
【作者】闫兰娜
【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河北,石家庄,05001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67
【相关文献】
1.浅论苏童小说中人物的"逃亡情结" [J], 封兰
2.论苏童小说的逃亡主题 [J], 汪双英
3.论苏童小说的逃亡意识 [J], 闫兰娜
4.试论苏童小说里的逃亡主题r——以《米》为例 [J], 张子晴
5.试论苏童小说里的逃亡主题——以《米》为例 [J], 张子晴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选修课论文(文学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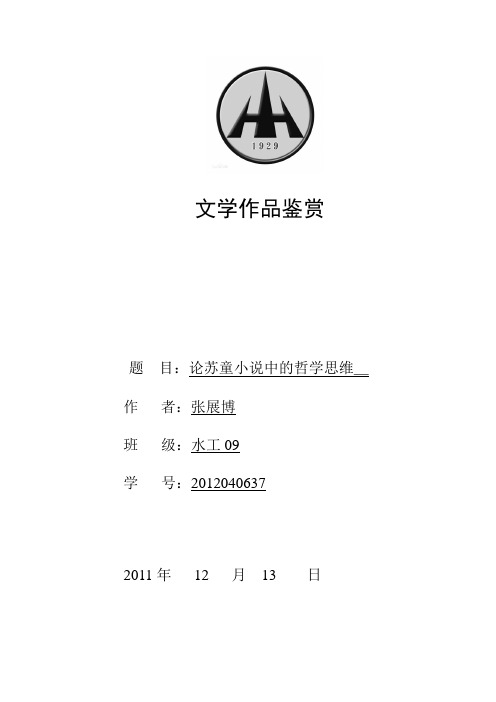
文学作品鉴赏题目:论苏童小说中的哲学思维_作者:张展博班级:水工09学号:20120406372011年12 月13 日论苏童小说中的哲学思维内容摘要:苏童的小说在语言、叙事结构和思想层面上都展现了别具一格的先锋意识。
这些意识集中地体现了苏童个人的哲学思维。
人们在苦难压迫下求取生存却始终挽救不了精神危机,苏童在其中寄寓了关于生存哲学的深刻思想。
小说中的人物在与现实的适应中的艰难深刻地揭露了进化论的悖论。
苏童在小说中极力渲染环境对人的心灵的深刻影响及“性”与罪恶的关系,展现了心理哲学的思维特色。
关键词:生存哲学进化论悖论精神家园心理哲学泛性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文革中青年一代在诗歌与小说领域的探索,但是直到80年代中期激进的实验才形成了强大的阵容和声势。
这期间,出现了众多的先锋派作家,像马原、莫言等。
苏童的小说也是先锋派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洋溢在苏童小说中的哲学思维尤为显得独特而颇具魅力。
生存哲学与迷茫人生人一生都在面对生存问题,每个人都渴望生存并获得健康、自由、幸福的人生。
人们不断在生活中挣扎,在物质与精神的世界游走。
人真的可以获得自己希冀的人生吗?苏童在小说中给予了否定:挣扎的结局是迷茫的结局。
在《妻妾成群》中,颂莲是一个接受了新思想的女大学生,与“五·四”时期大多“新青年”相反,颂莲这个“新女性”却走进了一个旧家庭,她几乎是自觉成为旧式婚姻的牺牲品,她的干练坚决成为她走向绝望之路的原动力。
在这个充满封建意识的家中,颂莲不得不做好适应的心理准备,她有清纯的气质和活泼的性格,却在这个家中不得不积累争风吃醋的经验。
为适应环境、求取生存而成为了牺牲品。
在小说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意识:人们拥有了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却往往在适应现实环境的过程中被现实的洪流所泯灭。
相反的,成为了无路可走的人。
另一类生存是逃亡的主题,是由受难的乡村逃亡理想的幸福之地——城市。
在苏童的相关小说中,逃亡首先表现在对固有生活环境的摆脱。
人性的悲歌和生存的逃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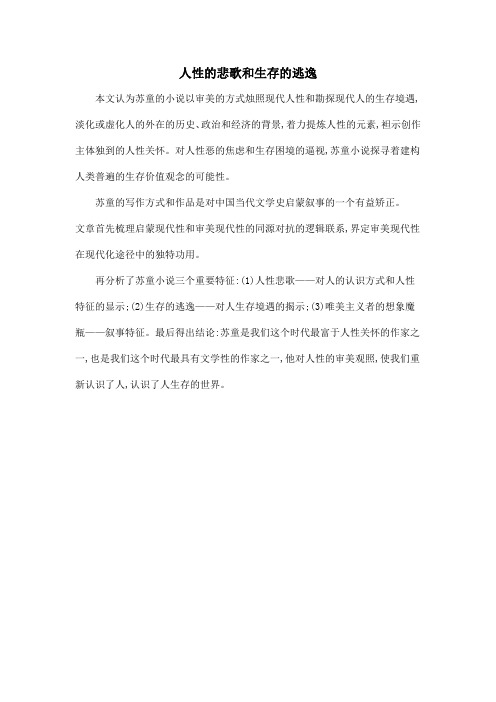
人性的悲歌和生存的逃逸
本文认为苏童的小说以审美的方式烛照现代人性和勘探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淡化或虚化人的外在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的背景,着力提炼人性的元素,袒示创作主体独到的人性关怀。
对人性恶的焦虑和生存困境的逼视,苏童小说探寻着建构人类普遍的生存价值观念的可能性。
苏童的写作方式和作品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启蒙叙事的一个有益矫正。
文章首先梳理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同源对抗的逻辑联系,界定审美现代性在现代化途径中的独特功用。
再分析了苏童小说三个重要特征:(1)人性悲歌——对人的认识方式和人性特征的显示;(2)生存的逃逸——对人生存境遇的揭示;(3)唯美主义者的想象魔瓶——叙事特征。
最后得出结论:苏童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富于人性关怀的作家之一,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文学性的作家之一,他对人性的审美观照,使我们重新认识了人,认识了人生存的世界。
孤独的灵魂 孤独的歌——论苏童小说的生存意识

孤独的灵魂孤独的歌——论苏童小说的生存意识导言:众所周知,苏童是我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主题广泛,内容丰富,尤以其独特的生存意识而闻名。
本文将以苏童小说中表现出的孤独主题为切入点,探究其作品中的生存意识,以期从中深入了解人的心灵世界,以及探寻现实中的个体生存境遇。
一、孤独的灵魂苏童小说中,孤独是其作品的主要主题之一。
孤独是人类固有的存在状态,每个人都会在某一时刻感到孤独。
苏童却将之当作一种灵魂的存在,其作品中的角色无一不是心灵深处的彷徨与孤独的集合体。
1.1 内心世界的孤独在苏童的小说中,人物往往存在着内心的孤独。
比如在《当岁月忽悠人》中,主人公阿会因为未能和心爱的人团聚,内心长久以来憋屈的情感使他感到深深的孤独。
这种孤独与外在环境无关,主要源于个体内心所承受的压抑和直接的心理冲突。
1.2 社会环境的孤独除内心的孤独外,苏童小说中描写了不同人的孤独与社会环境也密切相关。
比如在《木兰花》中,主角木兰花是一位多年在军中远离家乡的女性,她的孤独感源自于对家庭的思念,同时也是对战争和社会不公正的反思。
社会环境的孤独使得人们感到无法融入,在内心世界中找不到安身之处,从而陷入更深层次的孤独。
二、孤独的歌在苏童的小说中,孤独并非一种消极的存在,而是一种自我价值和意义的彰显。
孤独的歌指的是孤独者在面对孤独时所发出的呐喊与抗争。
2.1 内心世界的抗争苏童的作品中,主角常常通过内心世界的抗争来宣泄和彰显自我。
如《小镇》中,主人公支羽以寻找真情和美好生活为目标,通过与现实世界的艰难斗争来表达自我,与内心的孤独对抗,积极寻求解脱之道。
2.2 社会环境的抗争在社会环境的孤独中,苏童小说中的人物也有着自己的抗争方式。
他们坚守自我,通过实际行动来改变现实。
比如《活着活着就老了》中,老年主人公韩道汉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社会环境的孤独相对抗。
他们的抗争可以看作是一种对生命的坚守和尊重,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社会发出了一种生存的信号。
浅论苏童小说中人物的_逃亡情结_

经济研究导刊ECONOMIC RESEARCH GUIDE总第51期2009年第13期Serial No.51No.13,2009一苏童生于1963年,在湿漉漉的江南古城———苏州读完了小学、中学。
1980年他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
大学毕业后他又到了南京,在南京艺术学院当了一年的辅导员后,到《钟山》杂志社当编辑,现在是中国作协江苏分会的专业作家。
苏童的祖籍是扬中。
扬中是长江中心的一座孤岛,扬中县邑的构成乃至今日的繁华全是由于苏北农民迁徙的结果。
苏童的祖辈由扬中移居到古城苏州谋生,苏童自然也无法直接感受到扬中这一孤岛的独有情绪,可祖辈们的移民意识深深地渗进了苏童的血液和思维之中,使他无法摆脱对虚幻“故乡”的眷恋和描绘。
从1985年《石码头》的发表开始,随着《祖母的季节》、《青石与河流》、《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一九四三年的逃亡》、《丧失的桂花树之歌》、《故乡:外乡人父子》、《蓝白染坊》、《罂粟之家》等小说的相继面世,苏童小说就卓然自立了一个“枫杨树系列”。
这里几乎浸透了作者的全部灵性和追求,也呈现出了全部的矛盾和不安。
在这些小说中,逃亡似乎是苏童写得最多的,古老的枫杨树乡村总是与无法预料的灾祸联系在一起,滔滔的洪水,无情的饥荒,那片养育了苏童祖先的土地总像是一位年迈的老者,不堪重负。
从对文本的阅读来看,苏童对先人的传说与故事似乎是情有独钟,从表面上看,他以其独特的切入视角不经意地向人们讲述着祖辈、父辈们的经历。
但是,当他在记忆与梦幻之中重现先人的足迹时,自己紧跟着掉进了逃亡的陷阱。
苏童的叙述总伴随着一种逃亡意识,一种被追逐感,如同一个梦者。
二“多少次我在梦中飞越遥远的枫杨树故乡,我看见自己每天在逼近一条横贯东西的浊黄色的河流。
我涉过河流到左岸去,左岸红波浩荡的罂粟花卷起龙首大风,挟起我闯入模糊的枫杨树故乡。
”苏童经常用这样的叙述向人们展现历史,死亡的恐怖、灾难的冷酷、人生的艰难、历史的沉重、自然世界的灾祸如同一张无边的黑网笼罩着枫杨树故乡的人们。
论苏童小说的逃亡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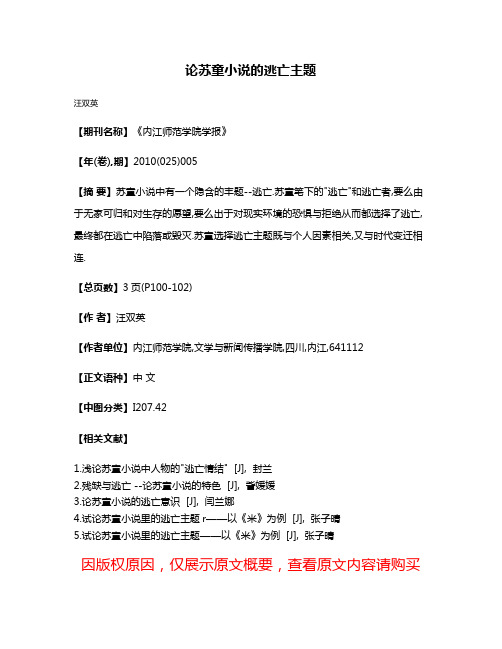
论苏童小说的逃亡主题
汪双英
【期刊名称】《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0(025)005
【摘要】苏童小说中有一个隐含的丰题--逃亡.苏童笔下的"逃亡"和逃亡者,要么由于无家可归和对生存的愿望,要么出于对现实环境的恐惧与拒绝从而都选择了逃亡,最终都在逃亡中陷落或毁灭.苏童选择逃亡主题既与个人因素相关,又与时代变迁相连.
【总页数】3页(P100-102)
【作者】汪双英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内江,64111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相关文献】
1.浅论苏童小说中人物的"逃亡情结" [J], 封兰
2.残缺与逃亡 --论苏童小说的特色 [J], 訾媛媛
3.论苏童小说的逃亡意识 [J], 闫兰娜
4.试论苏童小说里的逃亡主题r——以《米》为例 [J], 张子晴
5.试论苏童小说里的逃亡主题——以《米》为例 [J], 张子晴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浅论苏童小说中人物的“逃亡情结”

作者: 封兰
作者机构: 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泰州225300
出版物刊名: 经济研究导刊
页码: 221-222页
主题词: 移民意识;逃亡情结;枫杨树系列;苏童
摘要:苏童的祖辈由扬中移居到古城苏州谋生,祖辈们的移民意识深深地渗进了苏童的血液和思维之中,使他无法摆脱对虚幻“故乡”的眷恋和描绘。
苏童对先人的传说与故事似乎是情有独钟,从表面上看,他以其独特的切入视角不经意地向人们讲述着祖辈、父辈们的经历。
但是,当他在记忆与梦幻之中重现先人的足迹时,自己紧跟着掉进了逃亡的陷阱。
苏童的叙述总伴随着一种逃亡意识,一种被追逐感,如同一个梦者。
试图从小说人物命运的角度探寻苏童小说中人物的逃亡情结。
论苏童小说的逃亡主题

第25卷第5期(2010)内江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NEIJIANG NORM AL U NIVERSIT YNo.5Vol.25(2010)论苏童小说的逃亡主题汪 双 英(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12)摘 要:苏童小说中有一个隐含的主题 逃亡。
苏童笔下的逃亡!和逃亡者,要么由于无家可归和对生存的愿望,要么出于对现实环境的恐惧与拒绝从而都选择了逃亡,最终都在逃亡中陷落或毁灭。
苏童选择逃亡主题既与个人因素相关,又与时代变迁相连。
关键词:苏童;逃亡;逃亡者中图分类号:I207 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785(2010)05-0100-03苏童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因多部作品如∀1934年的逃亡#∀米#等而跻身于先锋派!作家的行列,并成为核心人物。
自1987年以来,苏童以他的三个中篇力作∀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令文坛瞩目。
而后又以两部长篇小说∀米#和∀我的帝王生涯#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苏童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红粉系列!、枫杨树系列!、香椿树系列!还有宫廷系列!小说四类。
与传统文学相比,苏童的作品多展现人性的丑恶、暴露世界的黑暗。
在他的小说里,其主人公大多因为自然灾害、现实环境等因素逃离家乡或历史,因而,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几乎可以看见一个隐含的主题,那就是逃亡!。
一苏童的祖籍是江苏扬中县,在他的父辈一代,举家从扬中迁居到苏州,作为移民后代的苏童,身上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无根!情结。
这种情结渗透到创作中就造成了一批逃亡者的出现。
正如苏童所说的:逃亡好象是我所迷恋的一个动作,人只有恐惧了,拒绝了,才会采取这样 个动作,这样一种与社会不合作的姿态,才会逃,我觉得这个动作或姿态是 个非常好的文学命题,这是 个非常能够包罗万象的文学主题,人在逃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好多所谓的人生的价值和悲剧性的一面![1]。
因而这种奔跑式的逃亡!执拗地缠绕在苏童的小说作品中。
论苏童小说的逃亡主题

33-40
第一节逃亡主题的社会历史内涵
33-36
1.苏童笔下的“逃亡”和其它先锋作家的共鸣
33-35
2.社会转型时期普遍的焦虑
35-36
第二节逃亡主题的文化心理内涵——孤独和虚无
36-40
结语
40-41
参考文献
41-43
论苏童小说的逃亡主题
内容提要
4-5
Abstract
5
引言
8-10
第一章逃亡主题和逃亡意象
10-20
第一节苏童笔下的“逃亡”和逃亡者
10-12
第二节逃亡意象的文本构成
12-20
1.以“飞”为核心意象的逃亡
12-14
2.以“铁路”为核心意象的逃亡
14-17
3.以“梦”为核心意象的逃亡
17-20
第二章逃亡主题的主导情节分析
20-33
第一节无助和恐惧——逃亡原因分析
20-25
1.无家可归和生存的愿望
20-23
2.对现实环境的恐惧和逃离的愿望
23-25
第二节流浪或自闭——逃亡方式分析
25-28
1.永不停息的流浪
25-26
2.消极的自闭和隐忍
26-28
第三节无望的挣扎——逃亡结局分析
28-33
1.终点又回到原起点
29-30
苏童《1934年的逃亡》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苏童《1934年的逃亡》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文档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谢谢!并且,本店铺为大家提供各种类型的经典范文,如诗歌散文、原文赏析、读书笔记、经典名著、古典文学、网络文学、经典语录、童话故事、心得体会、其他范文等等,想了解不同范文格式和写法,敬请关注!Download tips: This document is carefully compiled by this editor.I hope that after you download it, it can help you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document can be customized and modified after downloading, please adjust and use it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thank you!In addition, this shop provides you with various types of classic sample essays, such as poetry and prose, original text appreciation, reading notes, classic works, classical literature, online literature, classic quotations, fairy tales, experience, other sample essays, etc.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difference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format and writing of the sample essay!苏童《1934年的逃亡》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导语】:作者简介苏童,1963年1月生于江苏苏州,在苏州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大学期间开始学习写作,并在1983年发表小说处女作。
孤独中的生存理想_论苏童的小说

苏童的小说中写满了孤独,他用孤独倾诉着在现实生活的洪 流中苦苦挣扎的苦涩灵魂,充满悲伤,也带有诗意,同时他也用孤 独的心构筑了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一种不断的追寻的理想生存 信念。 就如顾城所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 光明”。
曹文娟(1985-)女,山东高密人 ,现读研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一
苏童曾说:“孤独的不可摆脱和心灵的自救是我们必须面对 的现实,我们和文学大师们关注这样的现实 ”。 因而在他的小说 中,孤独成为其创作的一个母题,孤独也使其小说散发出一种神 迷诡异的迷人气息。
小说中强烈的孤独感,首先源于苏童所塑造的形形色色的孤 独者。 《少年血》中的小拐,孤僻而古怪的独居者;《我的帝王生涯》 中的端白, 宫廷中享有最高权力却渴望能像鸟一样飞翔的燮王; 《妇女生活》中无法彼此理解的几代母女;《妻妾成群》中痛苦寂寞 无人可依的颂莲;《沿铁路行走一公里》以鸟引诱剑陪自己说话的 老严;还有《离婚指南》中的杨泊,《飞越我的风杨树故乡》中的幺 叔……他们挣扎于无法与他人进行交流的落寞与痛苦中,难以解 脱,孤独是他们内心最深切的体验。
文 学 界·文 学 评 论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李清霞论苏童历史小说的生存意识与逃亡意识历史发展是由一系列的偶然因素造成的,历史“就是一杯水已经经过沉淀,你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它看清它。
”!"苏童拾起历史的碎片,以自己独特的观照方式,缝补叠合,虚构重建了一个世界,他有时以历史观照现实,有时以历史还原现实,有时通过对历史的虚构表达某种理念,实现自己渴望表达的强烈欲望。
亚当・斯密认为,被别人所相信,劝服别人、教导别人的欲望,是我们有生以来最强烈的欲望之一。
人类所独有的语言能力,或许就是建立在这一本能之上的。
作家和艺术家恐怕是这类欲望最强烈的人群之一,作家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叙述劝服读者相信自己,阅读自己的文本,接受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而评论家的最强烈的欲望一是教导作家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创作,二是指导甚至强迫读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解读文学文本和作家。
评论家的话语强权要么使作家和读者成为他们的附庸,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要么成为自说自话式的批评,与创作和阅读严重脱节,目前的学院式批评就存在着评论家、作家、读者各行其是的现象。
新时期文学通过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等等言说之后,人们对过去的历史充满了好奇,不再满足于历史教科书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过去和历史的阐释,哪怕看到的是历史的碎片,哪怕看到的是局部的放大的真实,哪怕是阴暗、糜烂、丑陋的历史图景和瞬间,都满足了人们在特定时期重新解读历史的强烈愿望。
新历史小说应运而生,恰恰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
新历史小说解构了宏大叙事的诗意的历史文学模式,将现实主义的对生活的模仿转变为对历史的虚拟化、寓言化、偶然化的叙述,注重选取历史的瞬间或对历史的碎片进行重构,强调历史的细部真实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
苏童善于选择个体在生存范畴的历史,把历史的历时形态和完整外观打碎,从中找出人类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要素进行重构,揭示永恒人性和个体生命体验在历史长河中的冲突、矛盾和激荡。
《米》就是人的基本生存需求与人性的冲突所构成的生命寓言,米是人类生存和种族延续所需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五龙和整个种族无法割舍的永恒的情结,论苏童历史小说的生存意识与逃亡意识57评论米象征着生命永恒存在的梦想。
五龙是强硬生命意志的化身,他的一生除了对米表现出过迷恋、温柔、怜惜和珍爱之外,对自己的身体,对家人,对一切人和事,他都采取对抗的强硬的态度,他的生命是靠仇恨支撑着的,他用仇恨、暴力和变态的施虐来对抗贫穷、自卑、奴役、暴力、孤独,在对抗中他的身体一点点残疾直至彻底衰亡,他的生命在沉浮中发出呻吟、喘息、狂喜或痛苦的叫声。
苏童就是这样将欲望的人置于历史的情境和具体的偶然事件或灾难之中,让他们的生命本能得到尽情的释放。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是由英雄创造的,而人是受生命原欲所支配的,历史的发展与人的原欲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历史的某个瞬间,也许就是某个具体的生命主体的欲望在创造或改写着历史,某个生命瞬间的本能冲动就有可能改变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
陈宝年因为个体性欲的无法满足逃离家乡,从而创立了陈记竹器铺的招牌,使枫杨树的竹器加工手艺走向了城市,形成了规模生产,制造了一九三四年的竹匠的大逃亡,从而改写了枫杨树的历史,一个生命个体的本能冲动就这样影响着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历史发展。
人类童年的欲望总是那么简单,简单的欲望一旦进入社会就复杂起来,每一个简单欲望的实现,人类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都要经历一次感情或人性的危机,有时甚至是个体的生命。
陈宝年的欲望很简单,就是逃离丑陋的妻子、贫穷的农村,他的愿望实现了,引发了竹器加工业的繁荣,引发了枫杨树家乡的凋敝,他的冷酷与怪癖间接造成了蒋氏五个儿女死于瘟疫,小女人环子流产,并最终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苏童的小说几乎都与欲望有关,他写人的食欲、性欲、贪欲、权力欲、征服欲、复仇欲、毁坏欲等等,他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执著地探索历史的变迁与个体本能欲望的释放之间的神秘渊源,与个体的血缘、血气、血性之间的关系,男性个体生殖能力的旺盛与否,女性个体的血气是否旺盛,直接关系到该家族的生存、延续与强弱,中国是一个封建的宗法制国家,家国一体,家族的繁荣衰败不仅直接关系到一个种姓的存亡,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要研究中国历史就要研究中国的家族兴衰史,而性能力直接决定着家族的存亡,苏童醉心于营造某种历史,某种归宿,某种结论。
他写历史总是把性作为人的诸多欲望的核心,作为一切罪恶的源泉,性既生成人又毁灭人,既给人生的希望,又给人死的恐惧,性能力的丧失就意味着人生命的终结。
他思考和面对的是人的黑暗的一面,求知欲、自我超越的欲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的性欲、贪欲、征服欲、毁坏欲等人性黑暗隐密不为人知的层面,也在影响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人类历史上,英雄和枭雄同样在客观上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
《米》是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说《米》是“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我写了一个人具有轮回意义的一生,一个逃离饥荒的农民通过火车流徙到城市,最后又如何通过火车回归故里,五十年异乡漂泊是这个人生活的基本概括,而死于归乡途中又是整个故事的高潮。
”!"他用性本能解构了一切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性关系常常使不同阶级的男女的命运纠结在一起,织云作为一个性符号,将六爷、阿保和五龙这三个不同社会阶层的男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虚构的社会,演绎出一个爱恨情仇的悲剧故事,地主陈文治与女长工蒋氏的性关系,更加耐人寻味,小说反复渲染性与血气的密切关联,女人的血气像男人的性能力一样直接关系到生殖能力的强弱,关系到家族的繁衍,陈文治迷恋蒋氏旺盛的生殖能力,崇拜她的血气,蒋氏在失去所有儿女之后需要一个男人来实现她生命的价值,证明她旺盛的生殖能力,这时他们之间没有阶级对抗,有的是对性和生殖的共同的渴望。
生命本能就这样超越了社会关系和阶级对立。
苏童说:历史总是充满缺陷,人在历史中也总是充满缺陷,我们因此抓住了许多人类的尾巴,也因此发现了小说创作的巨大空间。
!"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对人对事的态度都有强硬的,陈宝年、祖母蒋氏、陈佐千、颂莲、五龙、织云等等,他们或暴力、或贪婪、或纵欲、或变态、或仇恨一切,它们的缺陷都是人最根本的缺陷,不是外力强加给他们的,或者说不是环境造成的,而是58他们自身或者宿命造成的。
祖母蒋氏被陈宝年认作灾星,原因很简单,就是她天生丑陋让陈宝年想折磨她、逃避她、利用她、占有她;织云从小就喜欢纸醉金迷的生活氛围,她为一件水貂皮的大衣就轻而易举地做了六爷的干女儿;“我”的姑母凤子和小女人环子,她们的悲剧源于天赋的美貌或风骚,他们成为男人实现贪欲或性欲的工具。
纵欲好色贪婪是男人的通病,男人的死亡和残疾似乎都与此有关,五龙强悍一生最终死于花柳病,陈宝年从妓院出来遭人暗算,儿子狗崽被小瞎子引诱导致纵欲和伤寒病发而死,小瞎子从十八岁到四十岁一直患有淋病,陈佐千、陈文治既性无能又性变态,性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也是罪恶之源。
这大概就是人的原罪吧,人被本能欲望所引诱,不断地毁灭他人、毁灭自身、毁灭世界,出于对这种生命本能的恐惧,有些生命个体开始逃避性的诱惑,米生不愿要孩子,陈佐千的儿子是同性恋,五龙杀死了8个可能给他染上性病的妓女。
然而,性就像吃饭一样是人类无法逃避、无法控制的,历史的发展也无法逃避人的性行为和性观念,性直接关乎到历史发展的进程,这是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新的解读,在苏童的叙事陷阱中,我们的确看到了性欲望在操纵、改变着历史,而这种叙述理念在传统历史叙事和宏大叙事中是不可想象的。
对生存困境的逃亡是生命救赎的一种途径。
当个体感觉到自身处于生存困境中孤立无援时,就会自觉地选择逃亡,“我”的祖父陈宝年婚后七天就义无反顾地逃离了让他预感到会给枫杨树带来灾难的、令他厌恶的、丑陋的灾星蒋氏,蒋氏是传统的社会规范和婚姻制度强加给他的,他所逃离的不只是一个丑女人,也不只是穷困,而是一种体制,一种文化,一种习惯,一种血缘,他渴望毁灭它、遗弃它、逃离它,但又被血亲所牵引、诱惑,出自本能地占有它、通过生命的繁殖延续它,出于对它的仇恨和厌恶折磨它,希望它自生自灭。
蒋氏穿破了8双草鞋去追赶抢走儿子的城里小女人环子,在长江边止步了、回头了,回到了失去生命创造力与精血的男人陈文治的没落的黑砖楼里,这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血气极旺的”、丑陋到美丽的女人(陈文治认为这个女人在生育时所表现出美丽激起了他强烈的性欲和占有欲)能否力挽狂澜为陈文治家传宗接代,改变这个家族衰亡的命运呢,“我”没有提及,只是坚信蒋氏的魂灵一定会回来。
蒋氏对陈宝年所隐喻的城市文明充满仇恨、恐惧和绝望,她逃进了象征着过去的黑砖楼,她的灵魂能得到安宁吗?1934年枫杨树村139个竹匠为逃避瘟疫、贫穷纷纷逃往城市,蒋氏由陈文治和三个强壮的女人抬进黑砖楼;七十年后在贾平凹笔下历史的瞬间再次闪现,夏天义死后清风镇竟然找不到四个抬棺材的壮年男子(《秦腔》),这是农村向城市的又一次迁徙,历史的循环在一个瞬间定格,农村凋敝的景象由此可见一斑。
逃离只是一个短暂的回避,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存困境,五龙为逃避灾难深重的乡村,为摆脱灾难与死亡的威胁,逃往城市寻觅富足的生活,他摆脱了饥饿的折磨,又陷入城市罪恶的深渊,人仿佛置身于生命永恒的轮回中无望地挣扎、逃离,时空的转换从未改变他们孤独绝望的生存困境和宿命。
五十年的轮回,火车将五龙带往喧嚣的城市,五龙又带着一车皮的米回归故里,他一生的奋斗、厮杀都是为了米,为了生存。
对现实生存困境和死亡的恐惧是人们逃亡的原因和内在动力,当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时,他就会下意识地逃亡,逃亡是一种生存的需要,无望的挣扎,陈宝年们在逃亡中满足了最简单的欲望,又陷入城市这个不断出产新的欲望的陷阱,他们不但没有在逃亡中得到灵魂的慰藉,还失去了原有的纯朴美好的人性,最终在欲望的泥淖中无法自拔,孤苦地走完自己悲剧的一生。
逃亡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现实生存困境,摆脱死亡的阴影,但是,陈宝年的逃亡在短暂的生命辉煌之后终结;五龙一生宿命般的轮回,从原点又回到了原点;颂莲逃进深宅大院,又陷入妻妾争斗的重围,花一样的生命被恐惧折磨成行尸走肉。
人们总是在逃亡、恐惧中挣扎,没有终点,人的灵魂永远找不到可供栖息的理想家园,逃亡、恐惧、孤独、死亡,是人类的宿命,人类的现实生存状态就是无处可逃。
这就是苏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瞬间或人类现实的生存处境,这就是他提供给我们的对人类生命过程的解释,欲望的人在欲望的深渊挣扎,找不到自我精神超越的桥梁,宿命般地走向毁灭。
丹尼尔・贝尔说:社会历史视野下一种开放的英雄主义59评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
!"苏童的新历史小说也试图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生存过程和状态进行艺术的、独特的、细微的解释,他迷恋那些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人,偏爱强硬的人生态度,钟情于那些强悍冷硬的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