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隐逸情结及其现实意蕴阐释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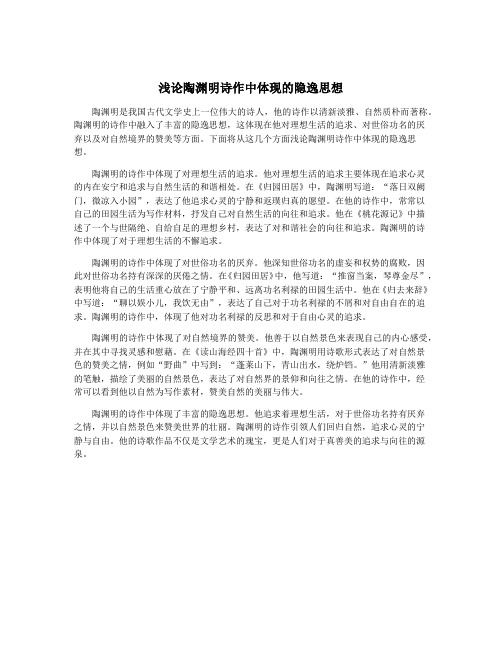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陶渊明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作以清新淡雅、自然质朴而著称。
陶渊明的诗作中融入了丰富的隐逸思想,这体现在他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对世俗功名的厌弃以及对自然境界的赞美等方面。
下面将从这几个方面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
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了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他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主要体现在追求心灵的内在安宁和追求与自然生活的和谐相处。
在《归园田居》中,陶渊明写道:“落日双阙门,微凉入小园”,表达了他追求心灵的宁静和返璞归真的愿望。
在他的诗作中,常常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写作材料,抒发自己对自然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他在《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一个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理想乡村,表达了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了对于理想生活的不懈追求。
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了对世俗功名的厌弃。
他深知世俗功名的虚妄和权势的腐败,因此对世俗功名持有深深的厌倦之情。
在《归园田居》中,他写道:“推窗当案,琴尊金尽”,表明他将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了宁静平和、远离功名利禄的田园生活中。
他在《归去来辞》中写道:“聊以娱小儿,我饮无由”,表达了自己对于功名利禄的不屑和对自由自在的追求。
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了他对功名利禄的反思和对于自由心灵的追求。
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了对自然境界的赞美。
他善于以自然景色来表现自己的内心感受,并在其中寻找灵感和慰藉。
在《读山海经四十首》中,陶渊明用诗歌形式表达了对自然景色的赞美之情,例如“野曲”中写到:“蓬莱山下,青山出水,绕炉铛。
”他用清新淡雅的笔触,描绘了美丽的自然景色,表达了对自然界的景仰和向往之情。
在他的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以自然为写作素材,赞美自然的美丽与伟大。
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了丰富的隐逸思想。
他追求着理想生活,对于世俗功名持有厌弃之情,并以自然景色来赞美世界的壮丽。
陶渊明的诗作引领人们回归自然,追求心灵的宁静与自由。
他的诗歌作品不仅是文学艺术的瑰宝,更是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与向往的源泉。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中国古代文学中,陶渊明被誉为“隐逸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诗作中充满了隐逸思想,体现了他对世俗的厌弃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本文将从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入手,深入探讨其背后的意蕴。
陶渊明的诗作中常常反映出他对世俗社会的失望和不满。
在他的诗中,对官场权谋、人情冷暖的揭露与批判随处可见,如《归园田居》中有“灵泉寺,僧舍幽,草鸟争鸣春色浮”之句,可见他对尘世的烦忧之情。
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点名道姓,但通过对官场腐败、人情沧桑的描绘,表现出他对世俗深处的不满和厌倦。
这种失望和不满推动了他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构成了他诗作中隐逸思想的基础。
陶渊明的诗作中表现出对自然和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他的诗歌中常常描绘田园风光,赞美田园生活的恬静与安逸。
在《饮酒》中有“田家少闲月,日暖厝蚁眠燕,时有落花至,迥如卷帘人”之句,表现出他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的倾慕。
他认为在自然之中,可以远离世俗之扰,享受心灵的宁静。
这种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的热爱,也成就了他诗作中强烈的隐逸主题。
陶渊明的诗作中还包含了对人生真理的追求和思考。
在《饮酒》中,有“人生寄一世,且得一心期,所以无故物,此外复何事”之句,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对内心世界的追求。
在孤独的隐居生活中,他更加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和追求精神世界的寄托。
在他的诗作中,对人生的意义和境界的探寻贯穿始终,这也是他隐逸思想的重要体现。
陶渊明的诗作中充满了对人情和友谊的感怀和赞美。
在他的诗中,朋友和门下弟子常常是他的知己和精神寄托。
在《归园田居》中,他写道:“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皆已极,陶然亦无多”。
可见,他对友情的珍视和对交心知己的赞美。
在他的隐逸生活中,朋友和门下弟子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坚持隐逸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
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了浓厚的隐逸思想。
他对世俗的不满和厌倦,对田园生活和自然的向往,对人生境界和真理的探索,以及对人情和友谊的感怀和赞美,构成了他诗作中丰富多彩的隐逸意蕴。
陶渊明的田园诗意与隐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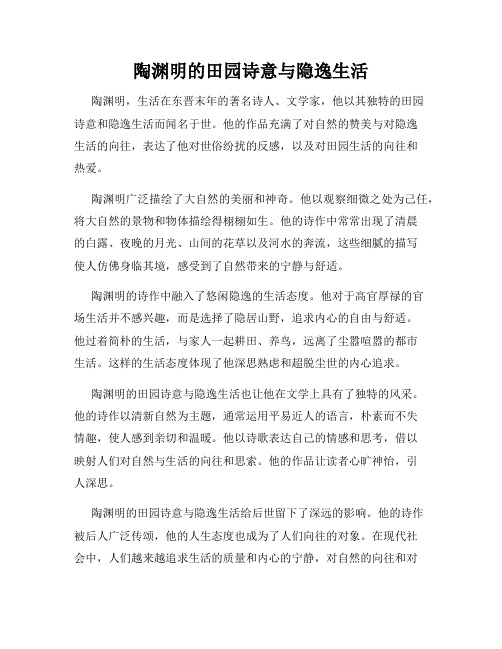
陶渊明的田园诗意与隐逸生活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的著名诗人、文学家,他以其独特的田园诗意和隐逸生活而闻名于世。
他的作品充满了对自然的赞美与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表达了他对世俗纷扰的反感,以及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热爱。
陶渊明广泛描绘了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
他以观察细微之处为己任,将大自然的景物和物体描绘得栩栩如生。
他的诗作中常常出现了清晨的白露、夜晚的月光、山间的花草以及河水的奔流,这些细腻的描写使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自然带来的宁静与舒适。
陶渊明的诗作中融入了悠闲隐逸的生活态度。
他对于高官厚禄的官场生活并不感兴趣,而是选择了隐居山野,追求内心的自由与舒适。
他过着简朴的生活,与家人一起耕田、养鸟,远离了尘嚣喧嚣的都市生活。
这样的生活态度体现了他深思熟虑和超脱尘世的内心追求。
陶渊明的田园诗意与隐逸生活也让他在文学上具有了独特的风采。
他的诗作以清新自然为主题,通常运用平易近人的语言,朴素而不失情趣,使人感到亲切和温暖。
他以诗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借以映射人们对自然与生活的向往和思索。
他的作品让读者心旷神怡,引人深思。
陶渊明的田园诗意与隐逸生活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诗作被后人广泛传颂,他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人们向往的对象。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的质量和内心的宁静,对自然的向往和对简朴生活的追求成为了社会潮流。
因此,陶渊明的思想和作品一直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灵的寄托和追求。
总之,陶渊明的田园诗意与隐逸生活表达了他对自然的赞美和对世俗生活的反思。
他以诗歌抒发内心情感,倡导简朴隐逸的生活态度。
他的作品深受后人喜爱,并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陶渊明的田园诗意与隐逸生活给予我们一种反思,让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态度,并在追求物质繁华的同时重视内心的宁静和平静。
从陶渊明诗歌看隐逸文人的济世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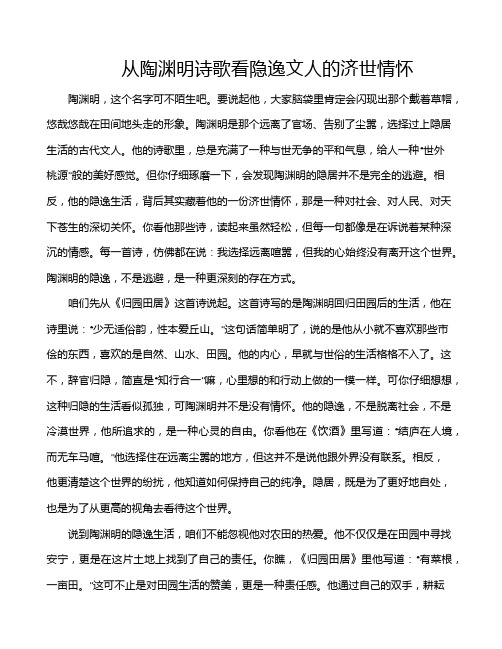
从陶渊明诗歌看隐逸文人的济世情怀陶渊明,这个名字可不陌生吧。
要说起他,大家脑袋里肯定会闪现出那个戴着草帽,悠哉悠哉在田间地头走的形象。
陶渊明是那个远离了官场、告别了尘嚣,选择过上隐居生活的古代文人。
他的诗歌里,总是充满了一种与世无争的平和气息,给人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美好感觉。
但你仔细琢磨一下,会发现陶渊明的隐居并不是完全的逃避。
相反,他的隐逸生活,背后其实藏着他的一份济世情怀,那是一种对社会、对人民、对天下苍生的深切关怀。
你看他那些诗,读起来虽然轻松,但每一句都像是在诉说着某种深沉的情感。
每一首诗,仿佛都在说:我选择远离喧嚣,但我的心始终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陶渊明的隐逸,不是逃避,是一种更深刻的存在方式。
咱们先从《归园田居》这首诗说起。
这首诗写的是陶渊明回归田园后的生活,他在诗里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这句话简单明了,说的是他从小就不喜欢那些市侩的东西,喜欢的是自然、山水、田园。
他的内心,早就与世俗的生活格格不入了。
这不,辞官归隐,简直是“知行合一”嘛,心里想的和行动上做的一模一样。
可你仔细想想,这种归隐的生活看似孤独,可陶渊明并不是没有情怀。
他的隐逸,不是脱离社会,不是冷漠世界,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心灵的自由。
你看他在《饮酒》里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他选择住在远离尘嚣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说他跟外界没有联系。
相反,他更清楚这个世界的纷扰,他知道如何保持自己的纯净。
隐居,既是为了更好地自处,也是为了从更高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
说到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咱们不能忽视他对农田的热爱。
他不仅仅是在田园中寻找安宁,更是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责任。
你瞧,《归园田居》里他写道:“有菜根,一亩田。
”这可不止是对田园生活的赞美,更是一种责任感。
他通过自己的双手,耕耘大地,播种希望。
这种看似简单的农耕生活,其实蕴含着对社会深深的关怀。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陶渊明没选择和世界对抗,他选择在平凡的田园中守护一份纯净。
桃花源记中的隐逸思想对现代人有何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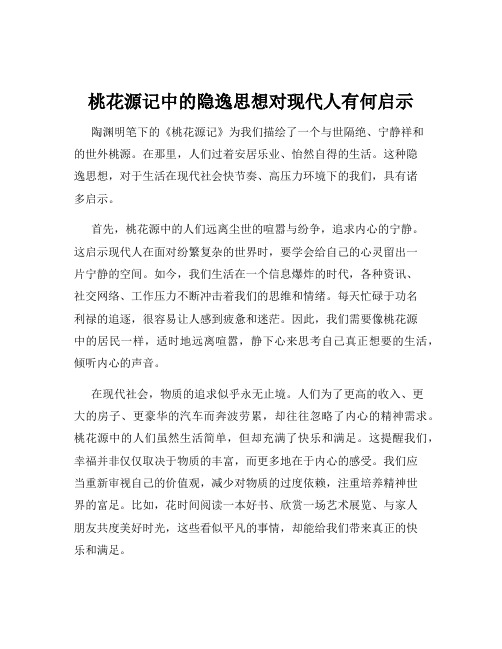
桃花源记中的隐逸思想对现代人有何启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宁静祥和的世外桃源。
在那里,人们过着安居乐业、怡然自得的生活。
这种隐逸思想,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快节奏、高压力环境下的我们,具有诸多启示。
首先,桃花源中的人们远离尘世的喧嚣与纷争,追求内心的宁静。
这启示现代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要学会给自己的心灵留出一片宁静的空间。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资讯、社交网络、工作压力不断冲击着我们的思维和情绪。
每天忙碌于功名利禄的追逐,很容易让人感到疲惫和迷茫。
因此,我们需要像桃花源中的居民一样,适时地远离喧嚣,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倾听内心的声音。
在现代社会,物质的追求似乎永无止境。
人们为了更高的收入、更大的房子、更豪华的汽车而奔波劳累,却往往忽略了内心的精神需求。
桃花源中的人们虽然生活简单,但却充满了快乐和满足。
这提醒我们,幸福并非仅仅取决于物质的丰富,而更多地在于内心的感受。
我们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减少对物质的过度依赖,注重培养精神世界的富足。
比如,花时间阅读一本好书、欣赏一场艺术展览、与家人朋友共度美好时光,这些看似平凡的事情,却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桃花源中的人际关系简单而和谐,邻里之间相互帮助、友好相处。
这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人际关系有时变得功利和冷漠。
然而,我们从桃花源中可以得到启示,努力营造真诚、友善、互助的人际关系。
在工作中,与同事合作共赢,而非勾心斗角;在生活中,关心邻里,互帮互助。
这样的人际关系不仅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也有助于缓解压力,增强内心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再者,桃花源中的人们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
他们依靠自然的恩赐生活,对自然充满敬畏和感激之情。
而现代社会中,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的过度扩张,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我们应当反思自己的行为,学会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隐士,其诗作中体现了浓郁的隐逸思想。
隐逸思想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是一种追求内心自由与宁静、远离尘世烦扰、追求自我完善与卓越、行持道德的人生哲学。
隐逸思想渗透在陶渊明的诗作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学风格,深受读者喜爱。
首先,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出隐逸的山水情怀。
山水自古以来就是士人们隐逸乐土,陶渊明的诗歌也是如此。
他的《桃花源记》就是一个隐逸的寓言故事,讲述了一个隐居在深山中的理想之乡,并以此批判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腐败。
他的诗歌中也融入了对山水的理解和热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饮酒·其三》)“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桃花源记》)这些诗句抒发了他内心对山水的向往和追求,反映出了他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其次,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出对清静的渴求。
陶渊明对于清静的追求可以从其诗作中得到明显的体现,清静成为他思想和行为处处呈现的特色。
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羁旅深山,愁闻空蝉,徘徊榆关”(《归园田居·其二》)的无尽孤独,甚至可以感受到他的隽永清寂,“野望千里,烟光袅袅。
”(《饮酒·其七》)这些深情的句子表达了他对平静、清闲的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此外,陶渊明诗作中还往往流露出对世俗的蔑视和对道德的关注。
他在《桃花源记》中对当时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批判,表现出了对世人的不满和对清高高洁的向往:“闻道无妻先隐泪,有妻空更试比年。
”(《归去来兮辞》)这一句诗表现出了他对于世俗婚姻制度的蔑视与调侃。
而《杂诗·其二》“是以嘉乡者,游避胜于市,退身卫其真,得非相之事。
”则表明了他坚持道德清高的主张。
总之,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了浓郁的隐逸思想,他一方面具有对山水的爱好和崇尚清静的追求,另一方面对世俗的蔑视和对道德的关注,体现出一种深沉的隐逸情结。
这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即便到现在,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和价值意义。
陶渊明论文人生经历论文:陶渊明的隐逸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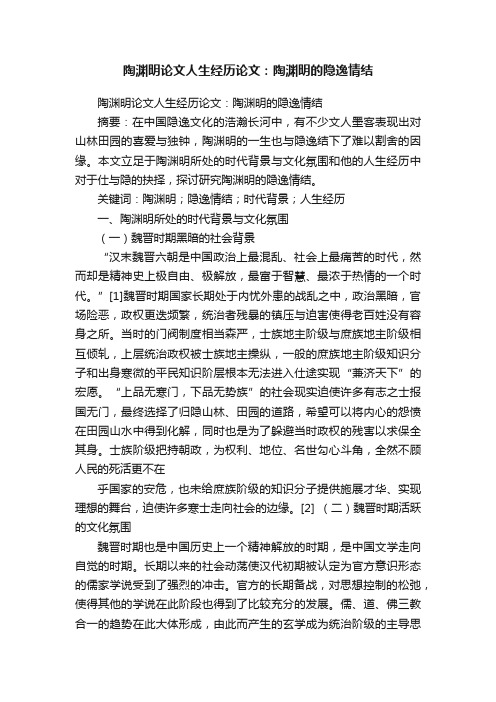
陶渊明论文人生经历论文:陶渊明的隐逸情结陶渊明论文人生经历论文:陶渊明的隐逸情结摘要:在中国隐逸文化的浩瀚长河中,有不少文人墨客表现出对山林田园的喜爱与独钟,陶渊明的一生也与隐逸结下了难以割舍的因缘。
本文立足于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氛围和他的人生经历中对于仕与隐的抉择,探讨研究陶渊明的隐逸情结。
关键词:陶渊明;隐逸情结;时代背景;人生经历一、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氛围(一)魏晋时期黑暗的社会背景“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1]魏晋时期国家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战乱之中,政治黑暗,官场险恶,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残暴的镇压与迫害使得老百姓没有容身之所。
当时的门阀制度相当森严,士族地主阶级与庶族地主阶级相互倾轧,上层统治政权被士族地主操纵,一般的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阶层根本无法进入仕途实现“兼济天下”的宏愿。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现实迫使许多有志之士报国无门,最终选择了归隐山林、田园的道路,希望可以将内心的怨愤在田园山水中得到化解,同时也是为了躲避当时政权的残害以求保全其身。
士族阶级把持朝政,为权利、地位、名世勾心斗角,全然不顾人民的死活更不在乎国家的安危,也未给庶族阶级的知识分子提供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舞台,迫使许多寒士走向社会的边缘。
[2] (二)魏晋时期活跃的文化氛围魏晋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精神解放的时期,是中国文学走向自觉的时期。
长期以来的社会动荡使汉代初期被认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官方的长期备战,对思想控制的松弛,使得其他的学说在此阶段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
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趋势在此大体形成,由此而产生的玄学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
玄学主张辨明析理,崇尚清谈,名士之风盛行。
时代的氛围使隐逸之风成为许多士大夫追求的生活方式和对人生的审美体验。
陶渊明《饮酒·其五》赏析:隐逸生活的诗意与哲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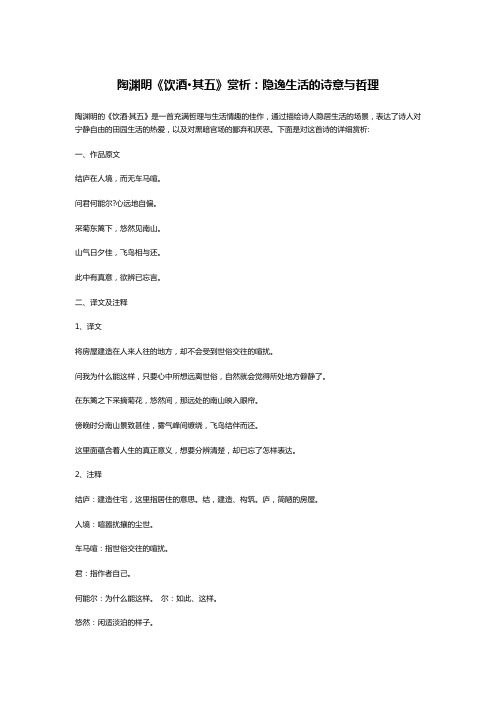
陶渊明《饮酒·其五》赏析:隐逸生活的诗意与哲理陶渊明的《饮酒·其五》是一首充满哲理与生活情趣的佳作,通过描绘诗人隐居生活的场景,表达了诗人对宁静自由的田园生活的热爱,以及对黑暗官场的鄙弃和厌恶。
下面是对这首诗的详细赏析:一、作品原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二、译文及注释1、译文将房屋建造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却不会受到世俗交往的喧扰。
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只要心中所想远离世俗,自然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
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
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
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想要分辨清楚,却已忘了怎样表达。
2、注释结庐:建造住宅,这里指居住的意思。
结,建造、构筑。
庐,简陋的房屋。
人境:喧嚣扰攘的尘世。
车马喧:指世俗交往的喧扰。
君:指作者自己。
何能尔:为什么能这样。
尔:如此、这样。
悠然:闲适淡泊的样子。
见:看见(读jiàn),动词。
南山:泛指山峰,一说指庐山。
山气:山间的云气。
日夕:傍晚。
相与:相交,结伴。
真意:从大自然里领会到的人生真谛。
相与还:结伴而归。
三、创作背景关于《饮酒二十首》的写作年代,至今尚无定论。
历来大致有六种说法:元兴二年癸卯(403年)说、元兴三年甲辰(404年)说、义熙十年甲寅(414年)说、义熙二年丙午(406年)说、义熙十二三年(416、417年)说、义熙十四年戊午(418年)说。
此诗为组诗之一。
这首诗大约作于公元四一七年,即诗人归田后的第十二年,正值东晋灭亡前夕。
作者感慨甚多,借饮酒来抒情写志。
四、作品赏析1、整体赏析“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诗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
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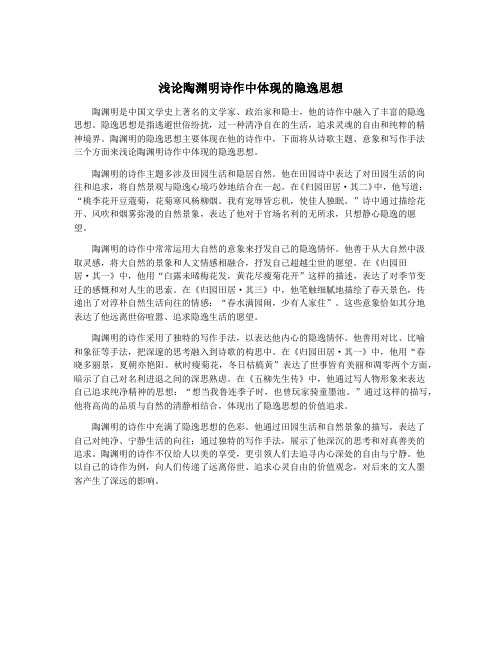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隐士,他的诗作中融入了丰富的隐逸思想。
隐逸思想是指逃避世俗纷扰,过一种清净自在的生活,追求灵魂的自由和纯粹的精神境界。
陶渊明的隐逸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诗作中,下面将从诗歌主题、意象和写作手法三个方面来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
陶渊明的诗作主题多涉及田园生活和隐居自然。
他在田园诗中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将自然景观与隐逸心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在《归园田居·其二》中,他写道:“桃李花开豆蔻菊,花菊寒风杨柳烟。
我有宠辱皆忘机,使佳人独眠。
”诗中通过描绘花开、风吹和烟雾弥漫的自然景象,表达了他对于官场名利的无所求,只想静心隐逸的愿望。
陶渊明的诗作中常常运用大自然的意象来抒发自己的隐逸情怀。
他善于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将大自然的景象和人文情感相融合,抒发自己超越尘世的愿望。
在《归园田居·其一》中,他用“白露未晞梅花发,黄花尽瘦菊花开”这样的描述,表达了对季节变迁的感慨和对人生的思索。
在《归园田居·其三》中,他笔触细腻地描绘了春天景色,传递出了对淳朴自然生活向往的情感:“春水满园闹,少有人家住”。
这些意象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远离世俗喧嚣、追求隐逸生活的愿望。
陶渊明的诗作采用了独特的写作手法,以表达他内心的隐逸情怀。
他善用对比、比喻和象征等手法,把深邃的思考融入到诗歌的构思中。
在《归园田居·其一》中,他用“春晓多丽景,夏朝亦艳阳。
秋时瘦菊花,冬日枯槁黄”表达了世事皆有美丽和凋零两个方面,暗示了自己对名利进退之间的深思熟虑。
在《五柳先生传》中,他通过写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追求纯净精神的思想:“想当我鲁连季子时,也曾玩家骑童墨池。
”通过这样的描写,他将高尚的品质与自然的清静相结合,体现出了隐逸思想的价值追求。
陶渊明的诗作中充满了隐逸思想的色彩。
他通过田园生活和自然景象的描写,表达了自己对纯净、宁静生活的向往;通过独特的写作手法,展示了他深沉的思考和对真善美的追求。
陶渊明情结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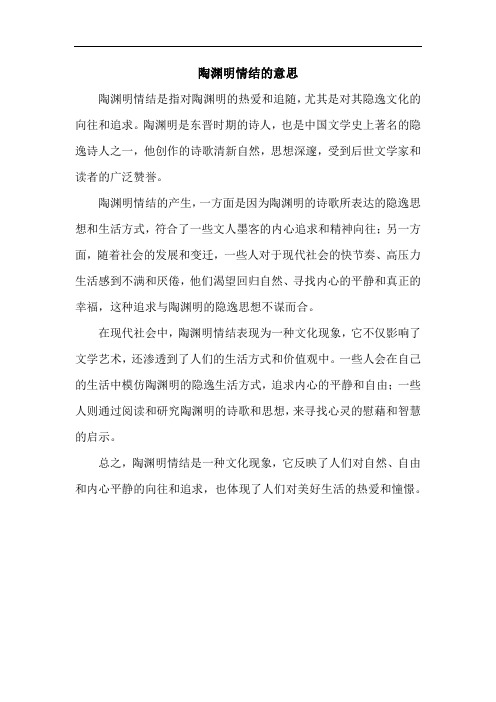
陶渊明情结的意思
陶渊明情结是指对陶渊明的热爱和追随,尤其是对其隐逸文化的向往和追求。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的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隐逸诗人之一,他创作的诗歌清新自然,思想深邃,受到后世文学家和读者的广泛赞誉。
陶渊明情结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陶渊明的诗歌所表达的隐逸思想和生活方式,符合了一些文人墨客的内心追求和精神向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一些人对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高压力生活感到不满和厌倦,他们渴望回归自然、寻找内心的平静和真正的幸福,这种追求与陶渊明的隐逸思想不谋而合。
在现代社会中,陶渊明情结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仅影响了文学艺术,还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中。
一些人会在自己的生活中模仿陶渊明的隐逸生活方式,追求内心的平静和自由;一些人则通过阅读和研究陶渊明的诗歌和思想,来寻找心灵的慰藉和智慧的启示。
总之,陶渊明情结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了人们对自然、自由和内心平静的向往和追求,也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憧憬。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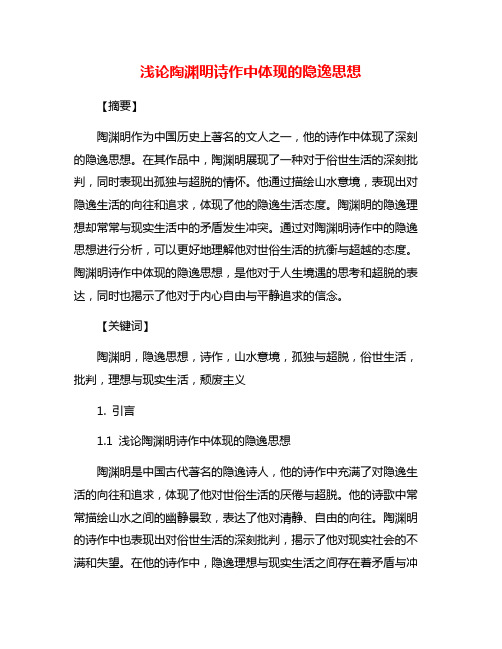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摘要】陶渊明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人之一,他的诗作中体现了深刻的隐逸思想。
在其作品中,陶渊明展现了一种对于俗世生活的深刻批判,同时表现出孤独与超脱的情怀。
他通过描绘山水意境,表现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体现了他的隐逸生活态度。
陶渊明的隐逸理想却常常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发生冲突。
通过对陶渊明诗作中的隐逸思想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对世俗生活的抗衡与超越的态度。
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是他对于人生境遇的思考和超脱的表达,同时也揭示了他对于内心自由与平静追求的信念。
【关键词】陶渊明,隐逸思想,诗作,山水意境,孤独与超脱,俗世生活,批判,理想与现实生活,颓废主义1. 引言1.1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陶渊明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隐逸诗人,他的诗作中充满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体现了他对世俗生活的厌倦与超脱。
他的诗歌中常常描绘山水之间的幽静景致,表达了他对清静、自由的向往。
陶渊明的诗作中也表现出对俗世生活的深刻批判,揭示了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失望。
在他的诗作中,隐逸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这种探讨也使得他的诗歌更加丰富和深刻。
通过对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以及他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和态度。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从多个角度来探讨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探寻其中的深层含义与意义。
2. 正文2.1 陶渊明的隐逸生活态度陶渊明的隐逸生活态度体现了他对世俗生活的不满和追求内心宁静的渴望。
在他的诗作中,隐逸是一种精神的寻求,是追求心灵的自由和内心的安宁。
陶渊明借助自然山水的清幽景致表达了对俗世烦扰的回避和对自然的热爱。
他将隐逸生活视为一种境界上的追求,通过超然脱俗的态度去抵制社会的纷扰和世俗的诱惑。
陶渊明认为,世俗的功名利禄与人的内在精神境界并无直接关系,而追求名利只会导致内心的烦躁和矛盾。
他选择了隐逸生活,将自己置身于深山幽谷之中,与自然为伴,与自己的内心对话。
陶渊明隐逸情绪及其现实意蕴阐释

、
陶渊 明政治理 想
解读陶渊明仕 与隐矛盾心理冲突出发点 当为
对他政治理想的认识 、 确定。历代论者多以陶渊明 为 “ 隐逸诗人之大宗”而认为 《 桃花源记 》中的乌 托邦便是陶渊明的政治理想。如果我们通览陶集 ,
把他的作品置于历史的大环境下来解读陶渊明 , 就 会发现 “ 仕而达 , 济天下”才是他的少年猛志 、 真
2 1 年 第 3期 00
陕西社会 主 义学院学报
鸲
口 武 宏 璞
【 摘 要】 陶渊明的的政 治理想并非 《 桃花源记 》
为
(8 ) 33 发生了令东晋人振奋的事情 , 谢安指挥东 晋八万军队击溃前秦三十万大军 , 并乘机收复大片
失地 ,大批将领崭露头角,建立了功勋。
中的乌托邦, 而是 “ 而达, 仕 济天下” 士志于道” 。“ 是历代士人的主导精神 ,隐逸诗人 多不能超然地融
希望你能够温和恭俭 , 能像孔仅那样成为有出息的
人。“ 按照陶渊明的愿望 ,孩子们应该超过乃父直 迫先辈陶侃、陶舍才是。他是按照家族史上陶侃、 陶舍的高大身影为孩子们量体裁衣” 。 特别是第九章陶公为了诫勉其子引用 “ 厉夜生
子”的典故 : 厉之人 ,夜半生子。其父遽取火而视 之 ,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由厉之人的 “ 汲汲然”
二 、陶渊 明仕 隐矛盾情 结 追踪
春秋后期 , 各诸侯国社会结构 、 政治格局急剧 变化 ,士之阶层骤然壮大。他们原本官事鞅掌、行 役在外而躬行勤勉 ,有着较强的重视个人才能和业 绩 的个体意识 ; 虽无| 叵产而有恒心,胸襟博大,志 于凭借 自己的才能和努力由社会 的下层步入社会
到陶公深感生命危机 ,“ 念将老也” 白首无成” 、“ , 为壮志难酬而郁闷不安。 读罢前三章 , 我们会深深 感受到陶公因 “ 憔悴有时” 慨暮不存”而焦灼伤 、“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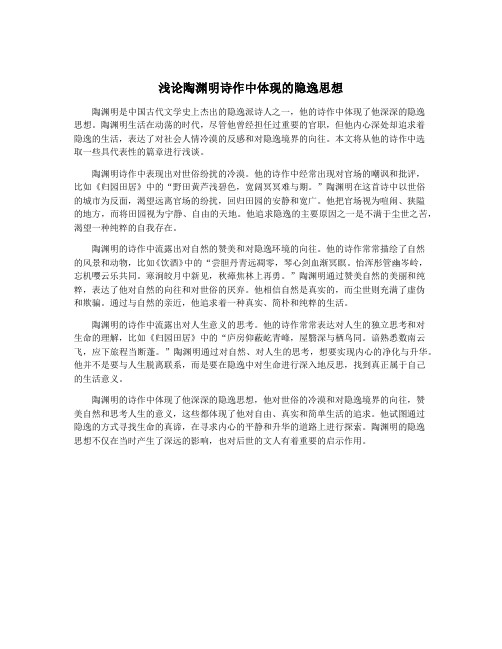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杰出的隐逸派诗人之一,他的诗作中体现了他深深的隐逸思想。
陶渊明生活在动荡的时代,尽管他曾经担任过重要的官职,但他内心深处却追求着隐逸的生活,表达了对社会人情冷漠的反感和对隐逸境界的向往。
本文将从他的诗作中选取一些具代表性的篇章进行浅谈。
陶渊明诗作中表现出对世俗纷扰的冷漠。
他的诗作中经常出现对官场的嘲讽和批评,比如《归园田居》中的“野田黄芦浅碧色,宽阔冥冥难与期。
”陶渊明在这首诗中以世俗的城市为反面,渴望远离官场的纷扰,回归田园的安静和宽广。
他把官场视为喧闹、狭隘的地方,而将田园视为宁静、自由的天地。
他追求隐逸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满于尘世之苦,渴望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
陶渊明的诗作中流露出对自然的赞美和对隐逸环境的向往。
他的诗作常常描绘了自然的风景和动物,比如《饮酒》中的“尝胆丹青远凋零,琴心剑血渐冥瞑。
怡浑彤管幽岑岭,忘机嘤云乐共同。
寒涧皎月中新见,秋瘴焦林上再勇。
”陶渊明通过赞美自然的美丽和纯粹,表达了他对自然的向往和对世俗的厌弃。
他相信自然是真实的,而尘世则充满了虚伪和欺骗。
通过与自然的亲近,他追求着一种真实、简朴和纯粹的生活。
陶渊明的诗作中流露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他的诗作常常表达对人生的独立思考和对生命的理解,比如《归园田居》中的“庐房仰蔽屹青峰,屋翳深与栖鸟同。
谙熟悉数南云飞,应下旅程当断蓬。
”陶渊明通过对自然、对人生的思考,想要实现内心的净化与升华。
他并不是要与人生脱离联系,而是要在隐逸中对生命进行深入地反思,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意义。
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了他深深的隐逸思想,他对世俗的冷漠和对隐逸境界的向往,赞美自然和思考人生的意义,这些都体现了他对自由、真实和简单生活的追求。
他试图通过隐逸的方式寻找生命的真谛,在寻求内心的平静和升华的道路上进行探索。
陶渊明的隐逸思想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后世的文人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隐逸派诗人,他生活在东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以其独特的隐逸思想和清新的诗风享有盛名。
他的诗作中体现了隐逸思想,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自然隐逸生活的向往。
本文将从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方面进行论述。
陶渊明的诗作中常常抒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之情。
他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政治流离和残酷战乱为背景,写出了许多感慨世事的诗篇。
例如《桃花源记》中写道:“至今事重悲咨嗟,管仲居然流汉家。
”他通过描绘桃花源中的安乐境地,表达了对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的不满,渴望远离尘世束缚、过上自由自在的隐逸生活。
陶渊明的诗作中常常表达出对自然的热爱和向往。
他以田园生活为题材,以诗人自身的情感体验,写出了许多关于自然的描写与抒发。
例如《归园田居》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是陶渊明对大自然美景的直接描摹,展现了他对自然世界的向往之情,希望在恬静宜人的自然环境中寻找内心的宁静和自由。
陶渊明的诗作中还充满了对宁静和自由生活的追求。
他反对官僚主义和权贵阶级的压迫,嘲讽附庸风雅的文人,强调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追求。
例如《归去来兮辞》写道:“归去来兮汉无事,挥手自兹去。
”这是陶渊明表达对尘世繁杂的厌恶和对自由隐逸的渴望,他希望能够摆脱现实的枷锁,追求内心的宁静和自由。
陶渊明的诗作中还反映了他对人生命运的思考。
他深入反思人生的真谛和意义,批判功利主义和权力欲的追求。
例如《读山海经》中写道:“阅之沉潜,错时终天。
”这是陶渊明对人生追寻的深思,他认为人生应该以追寻真理、探求内心的平静和宁静为重,而不是追逐权力和名利。
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了丰富的隐逸思想。
他以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自然的热爱为出发点,追求心灵的自由和宁静。
他呼唤人们远离尘嚣,寻求新的生活方式,提倡隐逸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
陶渊明的作品对后世诗人和文人的影响深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文化符号。
文学论文 浅析陶渊明的归隐情结

浅析陶渊明的归隐情结摘要:陶渊明追求的理想生活是符合人性自然状态的,那便是物质的富足与精神的自由闲适。
陶渊明决定彻底归隐时的心态很复杂,归隐后的田园生活并不那么美好,陶渊明只能以古圣先贤和委化任运来安慰自己了。
陶渊明辞官归隐,也是深知官场禁锢自由、戕害人性而厌弃功名的结果。
陶渊明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
陶渊明代表了隐逸文化的辉煌,陶渊明描写田园生活、表现隐逸情趣的诗文,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关键词:陶渊明;归隐;田园生活1.引言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
东晋末期南宋人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
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
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
陶渊明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鲁迅《隐士》),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
关于陶渊明的入仕与归隐,有人从政治方面入手,分析他入桓玄幕,任刘裕参军是为了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人从当时的社会思潮着眼,看出他的归隐与六朝隐逸之风有关;也有人从儒道哲学思想对他的影响考虑,得出他儒道互补或内儒外道等多种多样的结论。
本文无意以某种理论框架来衡量陶渊明,仅想就陶渊明诗作的分析,探究一下他入仕与归隐时的心态。
魏晋隐逸文化中, 陶渊明无疑是一颗最璀璨的明星。
陶渊明自称“幽居士”, 出生于“浔阳洪族”, 是东晋名将、大司马长沙郡公陶侃的曾孙。
到陶渊明时, 家道虽已中落, 但他仍有较好的出仕为官条件。
然而他“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 ,“闲居三十载”, 直到而立之年才勉强“投耒去学仕”, 几经仕而隐、隐而仕在的反复, 最终选择了“终死归田里”。
因此他与“隐”有关, 留给后人一个风神飘逸的隐士形象。
他的亦耕亦读、饶有情趣的生活方式, 卓然独立、超迈流俗的文化精神, 独树一帜、出类拔萃的创作成就, 获得后世士人的认同和仰慕, 成为中国隐逸文化史上一座不可企及的丰碑。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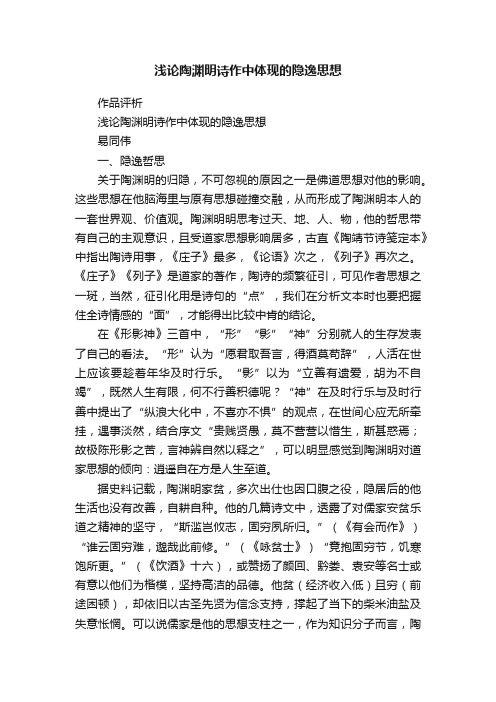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作品评析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易同伟一、隐逸哲思关于陶渊明的归隐,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是佛道思想对他的影响。
这些思想在他脑海里与原有思想碰撞交融,从而形成了陶渊明本人的一套世界观、价值观。
陶渊明明思考过天、地、人、物,他的哲思带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且受道家思想影响居多,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中指出陶诗用事,《庄子》最多,《论语》次之,《列子》再次之。
《庄子》《列子》是道家的著作,陶诗的频繁征引,可见作者思想之一斑,当然,征引化用是诗句的“点”,我们在分析文本时也要把握住全诗情感的“面”,才能得出比较中肯的结论。
在《形影神》三首中,“形”“影”“神”分别就人的生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形”认为“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人活在世上应该要趁着年华及时行乐。
“影”以为“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既然人生有限,何不行善积德呢?“神”在及时行乐与及时行善中提出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观点,在世间心应无所牵挂,遇事淡然,结合序文“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可以明显感觉到陶渊明对道家思想的倾向:逍遥自在方是人生至道。
据史料记载,陶渊明家贫,多次出仕也因口腹之役,隐居后的他生活也没有改善,自耕自种。
他的几篇诗文中,透露了对儒家安贫乐道之精神的坚守,“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
”(《有会而作》)“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
”(《咏贫士》)“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
”(《饮酒》十六),或赞扬了颜回、黔娄、袁安等名士或有意以他们为楷模,坚持高洁的品德。
他贫(经济收入低)且穷(前途困顿),却依旧以古圣先贤为信念支持,撑起了当下的柴米油盐及失意怅惘。
可以说儒家是他的思想支柱之一,作为知识分子而言,陶渊明有自己的儒家价值观,这与上文谈到的几点思想综合构成了陶氏哲思的主体。
二、农耕之乐陶渊明笔下的农耕不同于白居易笔下“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酸,他是累并快乐着。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隐逸,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们的一种特有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
而在中国文化史上,陶渊明被誉为“隐逸者的典型”,他的诗作中体现了深厚的隐逸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贯穿于他的生活方式,也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
在陶渊明的诗作中,不难发现他对隐逸的向往和追求,体现了他对自然、自由和内心世界的深刻思考。
下面就让我们从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入手,深入探讨这位文学大师的隐逸情怀。
陶渊明的诗作中表现出对自然的热爱和向往。
在他的诗中,常常出现对山水的描绘和对花草树木的赞美,如“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白帝城前一片水,山峡中间数峰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等等。
这些诗句不仅展现了陶渊明对自然景色的独特感悟,更表达了他对自然清幽、远离尘嚣的向往。
在陶渊明看来,自然是生命的源泉,只有与自然相处,才能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快乐。
他常常在自然中寻找隐逸的乐土,抒发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
陶渊明的诗作中流露出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
他认为人生应当追求真正的自由,并非是物质上的富足,而是心灵得到的解放。
在他的诗作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生活的厌倦和对现实的不满,如“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且乐生前欢,一死了之”,“丈夫何为者,日取一顷饥怡然”。
这些诗句中流露出的是陶渊明对物欲的淡泊和对金钱的不屑,他主张“乐天知命,尚自然,心怀天地” ,认为金钱地位不过是虚名,只有摒弃物欲,返璞归真,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他寻求隐逸生活,追求心灵的自由。
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出对内心世界的深刻思考和追求。
他并不仅仅追求物质上的隐逸,更是在追求内心世界的安宁和宁静。
在他的诗作中,我们经常能够感受到他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人生境遇的反思,如“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纵我不死,终归一尘土”等等。
这些诗句表现出陶渊明对时间流逝和生命无常的感悟,他在对自然、对自由的追求中,更多地是在寻找一种内心的出口,一种超脱的精神乐园。
陶渊明诗歌中所蕴含的归隐情结及人生态度

陶渊明诗歌中所蕴含的归隐情结及人生态度□王禹然【内容摘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和隐逸思想,在这句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众所周知,陶渊明是一个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田园诗人”。
本文针对陶渊明的古诗及个人的人生态度和隐逸思想进行深入探讨,通过陶渊明的诗来分析其人。
【关键词】田园诗歌;归隐情结;人生态度【作者单位】王禹然,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经济带来的利益纠纷和利益至上的现象,使得社会出现了各种不良思想,对人们的生活及其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分析陶渊明古诗中所蕴含的人生态度及隐逸思想,是为了利用传统文化中优良的思想文化,为大众宣传有益的人生哲理,更好地引导大众明确自身的追求,追求积极的生活态度。
一、陶渊明及其古诗研究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田园诗创作的第一人,田园诗在其作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所以,后人形象地称其为田园诗人或是隐逸诗人。
古代诗歌中田园诗是比较具有特色的一个门类,反映田园风光以及田园生活的诗歌都可以称为田野诗歌,这种诗从大体上都是表明诗人自身对宁静、安逸生活的向往,或是对脱俗生活的追求,表达出的诗境都非常的超出于世俗,体现出的都是平静的思想及心态,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不仅有对大自然的优美描写,也表达出了田园诗的思想中心。
从这些古诗中,可以读出其对世俗、对官场的厌恶,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在官场上沉浮多年,也没有同流合污,而是独树一帜,寄情山水,走出仕途的低迷,沉醉于田园生活中。
对陶渊明的归隐情结及人生态度的研究,能更好地解读其生活的历史背景,启发现代人们的生活。
二、古诗情感的转变———由积极出仕到向往隐逸“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陶渊明的田园诗隐逸生活与自然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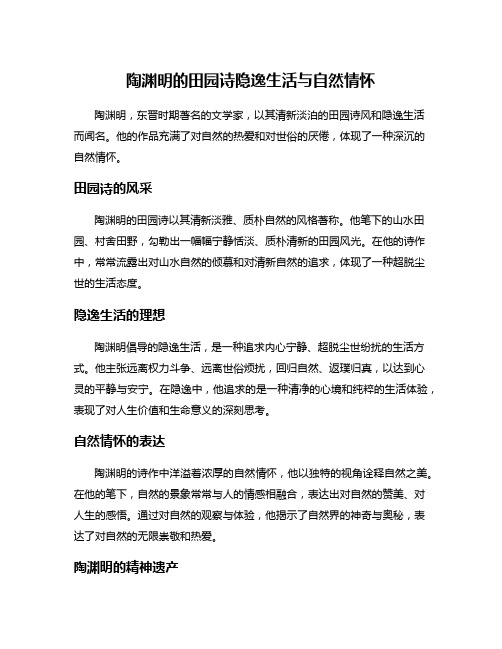
陶渊明的田园诗隐逸生活与自然情怀
陶渊明,东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以其清新淡泊的田园诗风和隐逸生活而闻名。
他的作品充满了对自然的热爱和对世俗的厌倦,体现了一种深沉的自然情怀。
田园诗的风采
陶渊明的田园诗以其清新淡雅、质朴自然的风格著称。
他笔下的山水田园、村舍田野,勾勒出一幅幅宁静恬淡、质朴清新的田园风光。
在他的诗作中,常常流露出对山水自然的倾慕和对清新自然的追求,体现了一种超脱尘世的生活态度。
隐逸生活的理想
陶渊明倡导的隐逸生活,是一种追求内心宁静、超脱尘世纷扰的生活方式。
他主张远离权力斗争、远离世俗烦扰,回归自然、返璞归真,以达到心灵的平静与安宁。
在隐逸中,他追求的是一种清净的心境和纯粹的生活体验,表现了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
自然情怀的表达
陶渊明的诗作中洋溢着浓厚的自然情怀,他以独特的视角诠释自然之美。
在他的笔下,自然的景象常常与人的情感相融合,表达出对自然的赞美、对人生的感悟。
通过对自然的观察与体验,他揭示了自然界的神奇与奥秘,表达了对自然的无限崇敬和热爱。
陶渊明的精神遗产
陶渊明的田园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人文内涵,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隐逸生活理念和自然情怀,激励着人们追求内心的宁静与深层的情感体验。
陶渊明的精神遗产,不仅体现在他的诗作中,更融入到人们对自然、对生活的理解与感悟中,成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
陶渊明的田园诗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独特的审美追求和情感表达方式,体现了对自然、对生命的热爱与感悟。
他的隐逸生活与自然情怀激励着人们追求内心的宁静与深层的情感体验,成为中国文化中一道璀璨的风景线。
陶渊明集读后感隐逸情怀生命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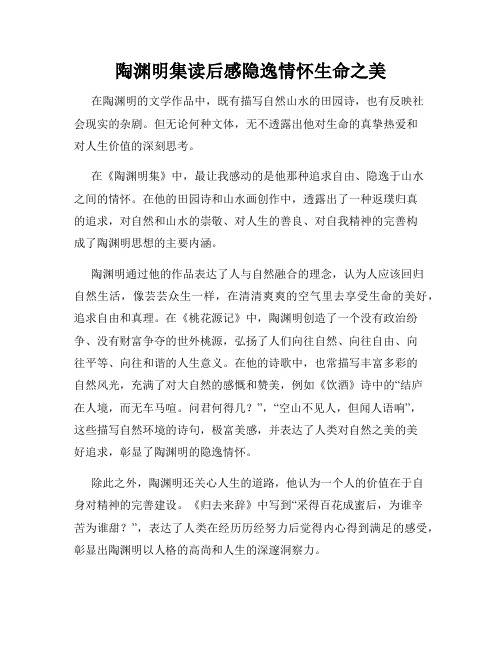
陶渊明集读后感隐逸情怀生命之美在陶渊明的文学作品中,既有描写自然山水的田园诗,也有反映社会现实的杂剧。
但无论何种文体,无不透露出他对生命的真挚热爱和对人生价值的深刻思考。
在《陶渊明集》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他那种追求自由、隐逸于山水之间的情怀。
在他的田园诗和山水画创作中,透露出了一种返璞归真的追求,对自然和山水的崇敬、对人生的善良、对自我精神的完善构成了陶渊明思想的主要内涵。
陶渊明通过他的作品表达了人与自然融合的理念,认为人应该回归自然生活,像芸芸众生一样,在清清爽爽的空气里去享受生命的美好,追求自由和真理。
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创造了一个没有政治纷争、没有财富争夺的世外桃源,弘扬了人们向往自然、向往自由、向往平等、向往和谐的人生意义。
在他的诗歌中,也常描写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感慨和赞美,例如《饮酒》诗中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得几?”,“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这些描写自然环境的诗句,极富美感,并表达了人类对自然之美的美好追求,彰显了陶渊明的隐逸情怀。
除此之外,陶渊明还关心人生的道路,他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在于自身对精神的完善建设。
《归去来辞》中写到“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表达了人类在经历历经努力后觉得内心得到满足的感受,彰显出陶渊明以人格的高尚和人生的深邃洞察力。
进一步,在陶渊明的读书笔记中,他不仅笔下山水,也涉及到了对人生、社会、感情等方面的思考。
他在阅读《孟子》时,深深地洞察了人性和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民主和宪政制度的要求;在阅读《观止》时,他对文学创作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更好地创作了他的文学作品。
尽管陶渊明已逝,但他的思想却感召了很多的灵魂。
我们也应该像陶渊明一样,珍惜人生、追求自由、关注社会、尊重自然;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体验生命的美好和生命的意义。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武宏璞[摘 要]陶渊明的的政治理想并非《桃花源记》中的乌托邦,而是“仕而达,济天下”。
“士志于道”是历代士人的主导精神,隐逸诗人多不能超然地融入田园山水恰是“士志于道”赋予了他们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现代生命观的重建。
[关键词]政治理想 士志于道 隐逸情结 人格重建纵观陶渊明一生,是“仕”还是“隐”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他,虽有暂时的心灵宁静得以拈笔舒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但“萧萧哀风失,猛气冲长缨”(《咏荆轲》)的积郁始终荡漾在他的心头,至死亦挥之不去。
一、陶渊明政治理想解读陶渊明仕与隐矛盾心理冲突出发点当为对他政治理想的认识、确定。
历代论者多以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大宗”而认为《桃花源记》中的乌托邦便是陶渊明的政治理想。
如果我们通览陶集,把他的作品置于历史的大环境下来解读陶渊明,就会发现“仕而达,济天下”才是他的少年猛志、真正理想。
门阀政治下的东晋王朝自建国之始就处于世族与世族、皇权与世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之中,战争乌云始终笼罩着建康。
太元五年(380)陶渊明“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薄,不就”[1],居闲于家。
陶渊明家乡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距都城建康不远,对围绕建康发生的各种政治变故的反馈当是颇及时准确的。
太元八年(383)发生了令东晋人振奋的事情,谢安指挥东晋八万军队击溃前秦三十万大军,并乘机收复大片失地,大批将领崭露头角,建立了功勋。
淝水之战五年后(389),那些崭露头角的人士已有了显赫的地位,隐居在家的陶公作《命子》,此篇没有丝毫的田园之思,是一篇管窥陶渊明心态的关键之作。
诗中陶公用了六章的篇幅叙述祖辈的武功、勋业,可谓津津乐道,特别强调了祖辈“德”方面的建树;第七章以下方始及“命子”之意,先感叹自己无才无德而无法追踪先辈的事业,偶一顾窥已见双鬓斑白,不禁惭愧顿生,怅惘不已;接着说:“我”之所以给你命名俨字求思,是因为“我”希望你能够温和恭俭,能像孔 那样成为有出息的人。
“按照陶渊明的愿望,孩子们应该超过乃父直追先辈陶侃、陶舍才是。
他是按照家族史上陶侃、陶舍的高大身影为孩子们量体裁衣”[2]。
特别是第九章陶公为了诫勉其子引用“厉夜生子”的典故:厉之人,夜半生子。
其父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由厉之人的“汲汲然”可以想见陶公自愧寡陋无成而“夙兴夜寐,愿尔斯才”的“汲汲然”。
望子成才之心如此殷切,恰见陶渊明对自己居于田园未能出仕的不满意。
淝水之战使许多士子彰显于世,这必将诱发了陶公“扶剑独行游”(《拟古》)的渴望、“猛志逸四海的”(《杂诗》)的壮志,陶公渴望有人赏识重用,从而获得“伊勋伊德”的功业。
从他盛赞陶茂“直方”、“惠和”、要求子俨“温恭朝夕”可以看出,陶公要求出仕的目的是在拥有自我发展空间的前提下,秉政务事,施惠于民,“达则兼济天下”。
此时他那“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咏荆轲》)的豪情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仕而达,济天下”。
“有志不获聘”的陶渊明于太元十六年(391)创作的《荣木》则更能表达他“仕而达,济天下”的渴望,诗序云:“《荣木》,念将老也。
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
”我们就可以看到陶公深感生命危机,“念将老也”、“白首无成”,为壮志难酬而郁闷不安。
读罢前三章,我们会深深感受到陶公因“憔悴有时”、“慨暮不存”而焦灼伤痛的心的跳动,也会随之而沉痛不已。
待读到第四首,我们便会豁然开朗:陶公前三章所营造的郁闷气氛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向命运低头了,你看,“四十无闻,斯不足畏”,不以岁月垂暮而放弃“仕而达济天下”之志;“脂我名车,策我名骥”,给“我”出仕的机会,给我“济天下”的舞台,“千里虽遥,孰敢不至”——陶公“仕而达济天下”之心可谓迫也。
清李广地评析为证:“人但知靖节之清高旷达,岂知其隐居求志如此哉”[3]!陶渊明先是因怀着“济天下”之志、无机会出仕而忧闷不已;出仕后因“济天下”之志未能“达”而积郁不安。
当他最终认识到“仕而达济天下”的理想于当时政治环境犹如水中望月之时,他便暂时放下这沉甸甸的理想,归于田园;需要指出的是,陶渊明不是笑着奔向田园的,而是带着一丝牵挂和遗憾,深埋在心底的遗憾伴随他直到终老。
在此后的田园生活中,他每每弹奏出与田园韵律极不合拍的音调。
这不合拍的音调恰显出了陶渊明迥异于其他的隐者和贵族的价值取向和心态,“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的,所以他伟大’。
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4]。
睿智于审时度势的陶渊明根本不会相信《桃花源记》中乌托邦的描述的实现,那只能算作他对生活的向往憧憬。
这一乌托邦的憧憬恰是他“仕而达,济天下”的理想无途以试而无奈悲吟的映像,也恰是他徘徊于仕与隐之间的心灵写照。
二、陶渊明仕隐矛盾情结追踪春秋后期,各诸侯国社会结构、政治格局急剧变化,士之阶层骤然壮大。
他们原本官事鞅掌、行役在外而躬行勤勉,有着较强的重视个人才能和业绩的个体意识;虽无恒产而有恒心,胸襟博大,志于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由社会的下层步入社会上层加入卿大夫的行列,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
他们甘以天下为己任,参与政治的意识非常强烈。
“士”便逐步由单纯的社会阶层升华为这一群体的人格理想,成了具有深层伦理道德涵义的生活范畴,与“君子”并论而称之为“士君子”。
《论语》中对士的修为有精确的论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泰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季氏》),“不仕无义。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
士人群体据德依仁、死守善道、见善思及的精神风貌与社会上层堕落的社会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精神风貌经孔子终生席不暇寐的总结、宣讲及其弟子的归纳整理、阐发提升而成为儒家思想的基础。
儒家后学大师孟子的“民贵君轻”理论对这一精神进行了更高境界的强化:“君有大过,反复之而不听,则移位”(《告子下》)。
这在提高“下则沦落为民、上则位达卿大夫”的“士君子”在国家行为中的地位的同时,对他们的境界也进行了更高的界定:甘以天下为己任,必要时不惜个人安危而与独夫民贼做斗争。
“儒家诸子频繁地讨论士君子的准则,在各种场合、从各个不同角度给‘士’、‘君子’、‘士君子’下定义,逐渐建立起其伦理价值生命观,应该说儒家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即建立在这种士君子的生命观上”[5]。
“士志于道”便成了士人的主导精神,“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以春秋战国为界,此前以崇拜上帝、上天为主;其后,以崇圣为主”[6]。
在崇圣文化的大背景下,历代士人无不饱受“先师遗训”的侵染,致力于“正心、诚意、修身”,以求成为“治国、平天下”之圣贤。
这一精神被东晋张载总结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
大部分士子终生劳碌于中央政权之外,穷经皓首而无途以酬壮志,便依外在的田园山水来减轻不能济天下的苦痛;一些士子在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在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然而他们权与势扩张引起了“圣”与“王”关系的恶化,造成“圣贤不得通其道”的郁愤。
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有着隐逸情结。
对隐逸情结的解读,历代论者多出于自我需要而注入感情色彩,强调他们冲淡飘逸的一面而未能感知出他们“志于道”的生命意识。
实际上,仕与隐的冲突过程恰是多数隐逸诗人壮志难酬之下、倍感生命危急而以田园山水来转换视觉、感觉却欲罢不能的心路历程,多数没有超然地融入田园山水。
关于隐逸行为的最早记载可追溯至《周易》。
《后汉书·逸民传》:“《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
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梁书·处士传》:“《易》曰:‘君子遁世无闷,独立不惧”。
隐士们能否都能做到“遁世无闷”,他们的生命追求是否就是“独立不惧”,这些记载无据可考。
下面我们通过对流传下来的较早隐逸作品的品析作以管窥。
据现存文献,最早的隐者遗作是《诗经》中的《卫风·考梁》、《陈风·衡门》、《小雅·鹤鸣》。
关于《考梁》已有定论:“这首诗创造了一个清谈闲适的意境,文字省净,……一种怡然自得之趣,流行于间”[7],细品诗作,隐者的确有“遁世无闷”的境界。
而《衡门》则没有这种潇洒,诗作二、三章用食鱼不必选择鲂鲤比娶妻不必选择贵族,显然渗透着丝丝求而不得的酸意,知足常乐的表述极不自然。
《鹤鸣》通篇用比兴的手法抒写招致人才为国所用的主张,细品诗中对隐居之地精炼细致的描绘及语气的殷切,可以肯定是隐者遗作。
从“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为玉”来看,这位隐士是关注现实、体察政治且希翼被征用的。
显然,《衡门》、《鹤鸣》中的隐士未能达到“遁世无闷”的境界。
隐居首阳山中的伯夷、叔齐是最早留下姓名和诗作的隐士,他们以株薇为食,及饿且死之际,做《采薇歌》。
且不说诗行之间流动着对“以暴易暴”的鄙视,就“我适安归兮” 所表达的对无归宿地的迷茫、对隐居生活的不满便足以见证诗人最终没有达到“遁世无闷”的境界,从最后一句“吁磋徂兮命之衰矣”更能读出隐逸的悲壮、凄凉、无奈。
仕隐话题在先秦诸子中也有着热烈的讨论。
《论语》多处涉及:“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邦有道,贫且戏焉,肚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
然而,孔子居于“礼崩乐坏”的无道之世却游说诸侯,积极求仕,周游列国而不辞风尘劳顿,寻求出仕的途径:“子曰:‘然,有是言也。
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
寥寥数语足可洞见孔子求仕心情的迫切,使他有关“无道则隐”的论说苍白无力。
庄子在《外篇·刻意》中,把士分为五类:平世之士、朝廷之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导引之士,其中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和部分导引之士都属于隐士。
“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在心境和精神状态上迥然有别:前者为被迫归隐,雕砺心志,崇尚品行,心怀怨愤,形容枯稿,忧愤至极时可导致赴渊而亡;后者为自觉归隐,徜徉于山水之间,心境平和,悠闲自在,重生养性。
庄周自认为属于后者,因为他多次自觉拒绝入仕。
但他终究没有达到“江海之士”的心境,因为“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的思想,与其说是追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更有人称《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刘鹗《老残游记》)。
仕与隐的冲突在屈原身上亦有所表现。
屈子一面高呼“世浑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一面悲歌“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均见《涉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