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袁宏道前期诗文理论述评
袁宏道提出的文学主张

袁宏道提出的文学主张
袁宏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文学领域中提出的主张
影响了数代文学人的创作思路和风格。
袁宏道主张文学应该以人为本,以人的情感、心灵体验为重点,表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塑
造真实、立体的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袁宏道的文学主张在当时是异常前卫和独特的,他认为文学是一种表
达人性的艺术,要表达人性就必须真实地反映人们的内心感受和情感
体验。
他反对过于抽象和理性化的文学创作方式,主张追求更加深刻、真实和生命力强的文学情感表达方式,并且提出了“以情感为主,以
语言为辅”的文学创作口号。
袁宏道在文学创作中强调语言的表达能力,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
有丰富、细腻的语言表达能力,通过精炼、恰当、有节奏的语言来传
递文学情感,让作品产生强有力的感染力、震撼力。
他同样也反对浮
华的语言和过于自我陶醉的文学创作方式,倡导朴实却真实的语言风
格和具有生命力的文学创作态度。
袁宏道的文学主张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界,很多作家和文艺工
作者都受到了激励和启发,不断尝试着寻找文学创作上更加真实、自然、立体的表达方式。
对于新时代的文学创作,袁宏道的思想启示仍
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总的来说,袁宏道提出的文学主张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文艺理论,他在文学表达角度的阐述打破了当时文学创作思维方式的局限,在情感表达和语言表达方面提出了全新的方法和思路,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创作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袁宏道《徐文长传》赏析-中国古典名家散文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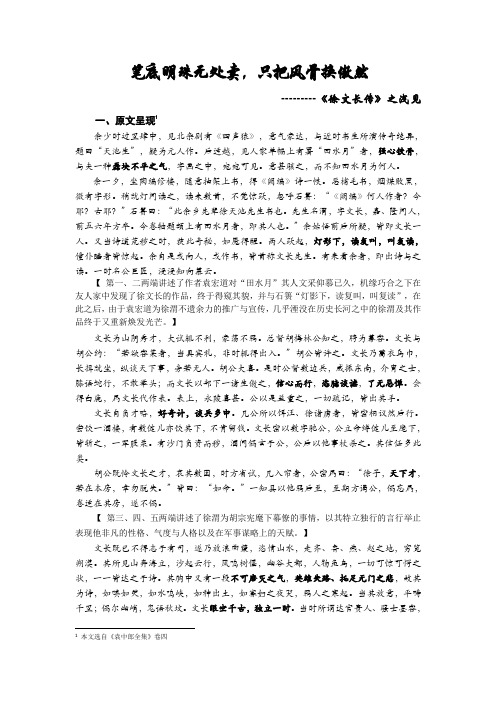
笔底明珠无处卖,只把风骨换傲然---------《徐文长传》之浅见一、原文呈现1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
后适越,见人家单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
意甚骇之,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
余一夕,坐陶编修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
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
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忽呼石篑:“《阙编》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篑曰:“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
先生名渭,字文长,嘉、隆间人,前五六年方卒。
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
”余始悟前后所疑,皆即文长一人。
又当诗道荒秽之时,获此奇秘,如魇得醒。
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
余自是或向人,或作书,皆首称文长先生。
有来看余者,即出诗与之读。
一时名公巨匠,浸浸知向慕云。
【第一、二两端讲述了作者袁宏道对“田水月”其人文采仰慕已久,机缘巧合之下在友人家中发现了徐文长的作品,终于得窥其貌,并与石篑“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在此之后,由于袁宏道为徐渭不遗余力的推广与宣传,几乎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的徐渭及其作品终于又重新焕发光芒。
】文长为山阴秀才,大试辄不利,豪荡不羁。
总督胡梅林公知之,聘为幕客。
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
”胡公皆许之。
文长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
胡公大喜。
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谈谑,了无忌惮。
会得白鹿,属文长代作表。
表上,永陵喜甚。
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
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
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
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
有沙门负资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
论袁宏道初度诗文及其交际性

论袁宏道初度诗文及其交际性高竞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摘要:初度作为一个极具特殊意义的日期,一直深受文人墨客创作的喜爱。
初度诗在明代已经蔚为大观,而寿序此时也已经脱离了寿诗,体例完备。
袁宏道作为拥有正常社交关系的文人,为他人而作的初度诗文自然也承担了交际的作用。
而根据创作对象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并且作品的表达方式和叙述手法也因为交际功能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关键词:袁宏道;初度诗文;社会交际从古至今,诞辰这一特殊日期,一直是人民表达对未来一年美好希冀的精神载体之一。
上至帝王将相,下及平民百姓,无不期盼自己长命百岁,因此“寿”在很多情况下也成为了衡量一个人幸福与否的标准之一。
在文学上,围绕生日展开的创作不胜枚举,早在《诗经》、《庄子》等先秦经典中便有精辟的论述,及至唐宋,寿诗寿词已然成为体例完备的文学体裁。
明代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初度诗,并且原本依附寿诗所作的寿序,此时也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成为赠序中的一类。
清人方苞于《张母吴孺人七十寿序》云:“以文为寿,明之人始有之”①,明代文人创作了大量寿序,如“归震川所作寿序,不下百篇”②。
不仅是归有光、黄宗羲、陈继儒这样的文人创作寿序,甚至连戚继光这样的军事家也参与过寿序的创作,足以证明寿序以及祝寿文化在明代的兴盛。
纵览袁宏道的创作生涯,现存的诗文集③中也出现了部分同生日有关的诗文创作,其中为他人生辰创作的诗作13首,为自己生日而作的诗作7首,以及寿序7篇。
为己而作的初度诗,属于自我记录,充分体现了独吟诗歌所拥有的抒情风格。
不一定必须有昂扬的风格和华美的文字,袁宏道更多描述了真实平易的生活场景、对生命历程的回顾以及个人情感浓厚的自我独白。
但显而易见,这类的初度诗是作者对自己人生的思考,并不具有与他人进行交际的功能。
而袁宏道为他人所作的初度诗文,多为酬唱应和之作,承担了诗人与初度者之间关系的艺术表达作用,目的是与人交流,因此指向性很高。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关于生日的文学创作,都可以简单归类为“寿文学”。
袁宏道小品文文学性赏析

袁宏道小品文文学性赏析
袁宏道是中国近代文学家、学者、艺术家,袁宏道以其独特的文学性格而闻名于世,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他的小品文也是十分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括《到西湖去》、《小花》、《三字经》等作品。
本文旨在从文学性角度,赏析袁宏道的小品文。
袁宏道的小品文,表现了其独特的文学性格。
他有一种淡淡的思想,不论在抒情还是夸张上,都有非常灵活的处理手法。
他多以小事为素材,比如《到西湖去》中他把游山玩水的过程用简单的语言描述出来,而且有着非常优美的语言从而展现出一幅古典的美景图景。
他在抒情上也善于把握,即使描述的是繁琐的现实,也能给人以淡然的感受,在他的文章中反复体现了“隐忍”、“温柔”的人生态度。
另外,袁宏道的小品文也非常有趣,他喜欢夸张、想象、玩笑,充满了讽刺意味。
他在《小花》中,既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田园秋色,又把它与同时期社会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行径比较起来,从而把人们从中引导出对压迫者的反抗性。
此外,他还有着幽默之处,比如《三字经》中的“静思”这一概念,他有几句诗将它表达得淋漓尽致,把静思比作一种虚拟的药丸,非常有趣却又发人深省。
从以上的分析看,袁宏道的小品文不仅聚焦于抒发情怀,而且也充满了讽刺、挖空等多种文学性表达手法,着实令人钦佩。
从文学性角度,他的作品可谓十分有价值,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经典杰作。
明朝诗人袁宏道,“公安派”三袁之一,看他写的诗文是怎么得来的

明朝诗人袁宏道,“公安派”三袁之一,看他写的诗文是怎么得来的袁宏道,明朝诗人,是明朝文学反对复古运动主将。
他既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学说,亦反对唐顺之、归有光摹拟唐宋古文。
他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
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称公安三袁,由于三袁是荆州公安县人,其文学流派世称“公安派”或“公安体”。
他说,"性灵",能导致文章的"趣"和"韵",而它们是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的。
他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指出,"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又说:"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
"拟宫词玉殿莲筹夜未央,内人传旨出昭阳。
朝来刚赴西宫约,莫遣经筵进讲章。
罗隐南王章甫小集斋中说旧事偶成珠楼曲曲贮仙娃,一带风窗十里沙。
记得中和门外路,女墙东去是他家。
罗隐南王章甫小集斋中说旧事偶成万瓦如鳞绣作堆,别山重见秃翁来。
晴川阁下南条水,一日同君荡几回。
天坛三首仙苑桃花朵朵香,曾于天上看霓裳。
刘郎老去风情减,闲把音容问太常。
天坛三首碧翁难道是无情,分合千年议不成。
不得宁居天亦苦,古来多事是书生。
天坛三首空坛深净驳琉璃,秃发簪冠老导师。
铜呇金涂秋草里,如今不似世宗时。
春江引溪潋潋,草茙茙。
野桃露滴珊瑚红,花气晓腥鱼子浪。
柳枝晴扇麦苗风,美人罗袖扑香蕊。
科斗旋旋丁子尾,百舌欲止复冲人,一声滴溜芳溪里。
郊外水亭小集清歌袅袅两妖童,尼酒题诗兴转工。
拾翠女来虚槛外,分蔬人立小畦中。
落花扑面都如雪,密树宜亭不碍风。
怪得夜来乡梦好,穿云直入武陵东。
放言效白三首贤愚富贵且凭他,山上髻鬟柳上蛾。
铁网试捞穿海月,渔舟任载过头波。
齐肩大士辞荤久,秃发中书感事多。
船上老郎江口女,咿哑容易得成歌。
戊戌初度禅灯滟滟雪玻璃,贝典将来戒小妻。
明朝文学家袁宏道的学说介绍

明朝文学家袁宏道的学说介绍袁宏道是明朝一位著名的文学家,那么你了解明朝文学家袁宏道的学说吗?以下是店铺为你整理的明朝文学家袁宏道的学说,希望能帮到你。
明朝文学家袁宏道的学说袁宏道是明朝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和理念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
他是明代反对复古文学运动的主要人物,在文学上反对写文章模仿秦汉,写诗词模仿唐代的做法,他认为写文章要跟自己的时代相连接不能只是一味地效仿前人留下的方法。
他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简单地说就是要表现出作家的个性和真情,而不要总拘束于一个套路上去效仿前人的做法。
袁宏道提出的性灵说跟李贽的“童心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认为出自于自己真情和个性的作家写出来的诗句才是真正的诗句,那些随自己率真的个性而做事情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从而来强调不是出自自己真情的诗句还是不要下笔了。
因此他们主张真正的作品应该既精美又充满诚意,那些既不精美又没有诚意的诗句是不能打动人的。
所以要求个人说自己想说的话,说别人不能说的话,说别人不敢说的话,这就包含了对儒家思想传统温柔敦厚的传教进行反抗。
他们认为文学创作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灵感是发自于自己的心,又蕴含在景象中。
对自己所看的景象有所触动,自己的心灵才会有所感悟,就有想袒露的情感,才能提起袖子把它写出来。
只要天下的聪明的文人学子知道心灵的表现是无穷无尽的,那表达的情感会越来越丰富,在文学上也会呈现出各种独特的风格,便能实现文学的改革与进步了。
明朝文学家袁宏道的简介袁宏道,湖北省公安县人,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曾担任过知县、稽勋郎中、博士等职位。
他家有三兄弟,不过人们都认为他是他们三兄弟中成就最高的人。
他是明朝反对复古文学的主要人物,他在文学上反对文章模仿秦汉,诗文模仿唐代的做法,他认为写文要真实,要与时俱进,不能总是停留在前人的基础上,不要总拘束于一个套路上。
袁宏道自小就非常聪明,善于写文章,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诸生了。
即使他当任过如此之多的职位,但他还是不太喜欢当官。
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歌创作主张

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歌创作主张袁宏道是明代的文学家,同其兄长袁宗道、弟弟袁中道并有才名,被称为“公安三袁”。
袁宏道在文学上反对拟古蹈袭,好诗应该任性而发,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歌创作主张。
本文从其《解脱集》中看“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歌创作主张。
在万历二十四年前后袁宏道逐渐对文坛的复古之气不满,故提出性灵说的主张。
在《答李子髯》中写道:“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
……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
”在他看来,复古的诗作不如民间的俚曲和俗曲,认为作诗不应该作茧自缚,模拟蹈袭。
而《解脱集》中收录的诗歌,是作者作于万历二十五年上半年游览吴越之作,此时他辞去吴县县令一职,摆脱了官场,使他的心性得以解脱,再加上与好友游览山水,更使他无拘无束地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这一时期的诗更能体现出他的诗歌创作主张。
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在《叙小修诗》中,他认为诗文应该抒发自己的性情,不应被固定的格式所束缚,如果不是从自己心中的“真”流露出来,就不应该下笔书写。
一、真诗在民间首先他认为能够抒发真性情的诗在民间。
他认为民间的诗歌正是无闻无识的真人之作,只有这种诗歌才算任性而发,才能充分表现人的真性情。
在他的《解脱集》中也写了不少具有民歌风味的诗歌。
如《江南子》其四:“湖蚕吐练光如水,桑娘夜织金阊里。
熟作绫绒生作纱,挑尽虫鱼与花蕊。
年年宫样换新机,一虫能作几般丝?父当解户兄塘长,官家头运五月时。
”从“湖蚕吐练”“桑娘夜织”“一虫”“几般丝”可以看出这首诗歌语言直白通俗、浅显易懂,表现手法和语调又似散曲和民歌。
正是这种直白通俗的手法,使作者能够直抒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通过这首诗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出这首诗歌揭露和控诉了明代社会的黑暗,勤劳的妇女没能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反而给她们自身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和灾难。
《横塘渡》与上一首诗在感情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横塘渡,临水步。
郎西来,妾东去。
……吹花误唾郎,感郎千金顾。
袁宏道《徐文长传》赏析-中国古典名家散文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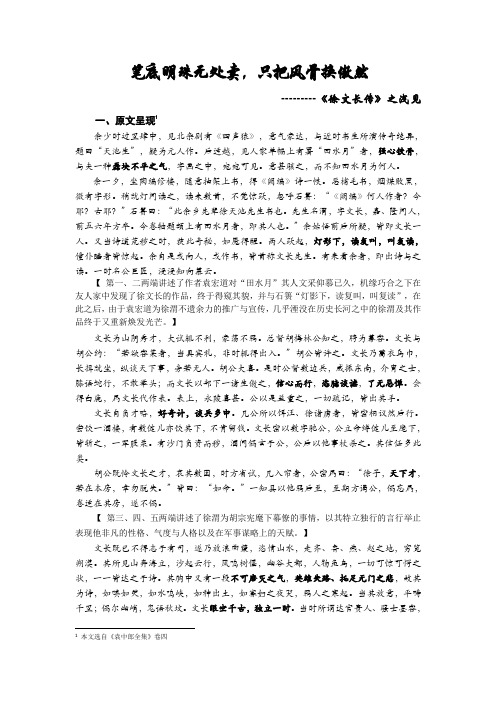
笔底明珠无处卖,只把风骨换傲然---------《徐文长传》之浅见一、原文呈现1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
后适越,见人家单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
意甚骇之,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
余一夕,坐陶编修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
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
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忽呼石篑:“《阙编》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篑曰:“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
先生名渭,字文长,嘉、隆间人,前五六年方卒。
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
”余始悟前后所疑,皆即文长一人。
又当诗道荒秽之时,获此奇秘,如魇得醒。
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
余自是或向人,或作书,皆首称文长先生。
有来看余者,即出诗与之读。
一时名公巨匠,浸浸知向慕云。
【第一、二两端讲述了作者袁宏道对“田水月”其人文采仰慕已久,机缘巧合之下在友人家中发现了徐文长的作品,终于得窥其貌,并与石篑“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在此之后,由于袁宏道为徐渭不遗余力的推广与宣传,几乎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的徐渭及其作品终于又重新焕发光芒。
】文长为山阴秀才,大试辄不利,豪荡不羁。
总督胡梅林公知之,聘为幕客。
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
”胡公皆许之。
文长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
胡公大喜。
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谈谑,了无忌惮。
会得白鹿,属文长代作表。
表上,永陵喜甚。
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
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
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
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
有沙门负资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
袁宏道《雪涛阁集序》的得与失

袁宏道《雪涛阁集序》的得与失赵 琼袁宏道在为江盈科所作的《雪涛阁集序》中提出“时使之也”的观点,批评当时文坛盛行的复古风气,自觉探讨诗文自《雅》至明代的流变,论证自己的文学思想。
但是,其同时表现出矫枉过正和机械性分析的弱点,在诗文流变的解读方面留下了遗憾。
一、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表达的思想主张袁宏道对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提出了批评,认为复古派扼杀了文学创作的生命力,其拟古之作仅仅是“剿袭模拟”的滥腐之辞。
他认为诗文的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进而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性灵说”。
在为江盈科《雪涛阁集》所作的序中,他探讨了诗文的流变方向,阐释其中缘由,并极力印证自己的思想。
《雪涛阁集序》前两段实际上是袁宏道对历代诗文发展的总结。
因为“《雅》之体穷于怨”,已经不足以寄托更深沉的感情,故《骚》生。
晋、唐后,诗从有情无事、诗体为虚发展为“诗之体已不虚”;文从有事无情、文体为实发展为“文之体已不能实”。
初唐以“流丽”矫正六朝骈丽,却失于“轻纤”;盛唐以“阔大”矫正之,却又滋生“阔而生莽”的问题;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又出现“因实而生俚”的问题;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却陷入境界狭小的泥沼,从而使诗道衰微。
至宋代,“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
《雪涛阁集序》的后半部分则着重强调拟古之害,并为江盈科的诗文作辩护,反驳时人提出的“近平近俚近俳”的异议。
通观全文,袁宏道想表达的主要是以下几层涵义:第一,以时间顺序叙述并概括自《雅》至近代(即明代)的文体与诗文特征,并用牡丹花和穿衣作比,与首句“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相呼应。
草木无情,之前人们推崇的鞓红鹤翎品种因时代审美的变化而被左紫溪绯品种所取代;一味模仿古人言辞,并以之为雅,就像在冬季里穿夏衣一样可笑。
自《雅》到明代诗文,中间经历的是一个下一代文人对上一代诗文流弊进行矫正,同时产生新的问题,再由后代创作者继续进行矫正的不断重复循环的“怪圈”。
毕业论文例文-从《解脱集》谈袁宏道早期的佛教态度及其原因

从《解脱集》谈袁宏道早期的佛教立场及其启事邱麟淳四川大年夜学文学与往事学院摘要:袁宏道是明末禅净双修的一名十分有影响力的佛教居士,但在《解脱集》中,存在多篇对佛教立场很不恭谨的诗文。
本文准备评论辩论袁宏道撰写《解脱集》时,对佛教的立场和这类立场发生的启事。
关键词:袁宏道佛教《解脱集》袁宏道是明末禅净双修的一名佛教居士,他的《西方合论》被藕益巨匠智旭支出《净土十要》。
《西方合论》是《净土十要》唯一支出的居士作品,掉掉落和尚的高度评价。
请抄写两则资料证实:“袁中郎少年颖慧,坐断一时禅宿舌头……复深化法界,归心乐国,述为西方合论十卷,字字从真实悟门中流出……”“《西方合论》:此书是袁宏道中郎居士所撰,气概澎湃,涵盖广阔,乃明末净土诸书中,最具气魄的一种。
”藕益巨匠和圣严法师均是空门中人,他们对袁宏道下如此赞语,那么袁宏道的行动也应在空门规矩内。
否则,就会如对李贽通俗:佛教界对他避而不谈,或许赞成其报答“人杰”,但对他的梵学著作,不作评价。
《西方合论》是袁宏道归心净土以后的作品:“西风不道禅心定,吹入山头环佩声。
”在参禅时写作的《解脱集》中,很多诗文,都显示了袁宏道对空门很不恭谨的立场。
如:“少年曾盗子胡狗,父母不容亲戚丑。
每到僧房索平平易近,更向佛头种葱韭。
读书十年未识字,持戒三生不时酒。
恁有通俗可笑人,逢着师尼便解纽。
”——《过云栖见莲池上人有狗丑韭酒纽诗戏作》袁宏道此诗是以莲池上人的旧韵作古诗。
当日,有禅者难莲池上人,说:“今居秽土求净邦。
还许出秽韵求净偈否?”乃出韵狗、丑、韭、酒、纽。
葱、酒、韭菜等物皆为佛家所忌的污秽之物。
莲池上人便以此秽韵做偈云:“万山无人纵鹰狗。
顽石高低尽遮丑。
糁遍苔痕白似毡。
压翻莆叶青如韭。
寒膏时煮竹炉茶。
洁体不陪金帐酒。
水晶城外一声梆。
玉关顿地开银纽。
”莲池上人此诗,确是以秽韵做净偈的榜样。
但袁宏道却拿此诗开起了打趣。
诗中句句犯戒,语涉不端,调戏僧尼。
如许的诗文在《解脱集》中极其罕见。
袁宏道小品文文学性赏析

袁宏道小品文文学性赏析
袁宏道,20世纪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他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他独创的小品文文学格调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一致好评。
本文从探讨袁宏道小品文的文学性来赏析他的小品文,探究他受到大众喜爱的原因,以期从中发现他的文学魅力,并向读者传播他优秀的文学风格。
袁宏道的小品文具有良好的文学性,他生动地描绘了生活中真实而又诗意的景象,描写出生活中温暖美好的一面,勾勒出社会现实和人生追求的真谛。
他的文字极富层次性与节奏感,文中穿插著寓言故事,把思想内涵深入浅出的表达出来,让人耳目一新,给人以打动心灵的触动。
袁宏道的小品文显示出他独特的文学手法,这些手法包括文学的艺术形式,例如虚拟的事、开放的描述性、小节的展开等,以及节奏之间的转折关系,如旋律式的叙述、对比性的对比、叠句式的叙述,使文章在表达思想的同时兼具艺术性。
此外,袁宏道小品文的文学性还体现在他的文体特点上。
他的文体多样,有现实主义的写实、新闻式的简洁、平实的叙事和社会现实的审视等。
他的语言朴实清新,内涵深刻,词句恰当而富有情调,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
最后,袁宏道小品文蕴含着浓厚的文化色彩。
他经常赋予文章有关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味道,这既打开了一扇通往民族文化的大门,又加深了人们对文化精神的思考和学习。
总之,袁宏道小品文文学性赏析显示出他的文学思想极具活力,他凭借一种独特的文学语言和技巧,向人们展示出现实生活的景象,表达了他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内涵。
他的文学,以其独特的文学手法和丰富的艺术形式,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袁宏道的小品文的文学性赏析,无疑是我们研究他的优秀文学风格的宝贵财富。
袁宏道小品文文学性赏析

袁宏道小品文文学性赏析本文以小品文的方式,记述了袁宏道与其友人在杭州生活时的琐事、轶闻。
从而反映出封建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丑态与陋习,以及袁氏兄弟作为具有自由思想的文学家对它们进行无情的嘲弄与抨击的强烈情感。
先是讲他的父亲对他的影响。
从幼年起,袁宏道就和弟弟一起被送到钱塘县城去读书。
那里书馆很多,如学富堂、学海堂、桂文堂等等,这些书馆都是当地名流的私塾,规模大,收藏多。
袁宏道兄弟俩就和许多同学混熟了,每天便结伴来回奔走于各个书馆之间,读诗文,谈古今,整天处于嬉戏玩乐的状态。
袁宏道一边读书,一边也学着老先生们写诗作文,将所学融会贯通后,再加上父亲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使他们的才能显露出来。
十岁那年,袁宏道随父亲去京师,居住了几年,见到了皇帝,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洗礼。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句话在袁宏道身上真正体现出来,使他终生难忘。
后来又跟随父亲的老师们遍游各地,饱览了祖国的壮丽山河,陶冶了心灵,获得了丰富的文化知识。
父亲的言传身教,使他终生受益,为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袁宏道一直不得志,虽然很有才华,但他经常参加科举考试却屡试不中。
随后,朝廷颁布了一项重要的法令:凡是二品以上官员子孙三代内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否则依律治罪。
这一法令使袁宏道失去了进入仕途的希望。
这样的经历让他彻底醒悟了,放弃了做官的念头,开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公安派”成员袁宏道作为其中的一个小群体,他与他的朋友们非常珍惜相聚在西湖边上的短暂时光。
他们是怎样度过这段快乐时光的呢?袁宏道早上刚醒来,便要去找朋友们一起游湖。
在游船上,他们看到绿水如镜,白鸥点点,只听到歌女们的轻歌曼舞。
岸上桃红柳绿,楼阁亭台,美不胜收。
在歌舞声中,吃着美味佳肴,谈论着最新的科场事件,这是多么惬意啊!有时,他们也在静静地思索,或低头吟咏,或仰头观望星空,抑或什么都不做,只是面对湖水,任清风拂过。
他们还有很多的兴致,比如玩骰子,用纸牌赌博,饮酒……在欢笑声中,又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袁宏道在苏州--读《袁宏道集笺校》有感

袁宏道在苏州--读《袁宏道集笺校》有感作者:曹炜芳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形成,得之于温和湿润的气候条件,得之于临海近湖、河网交汊的水环境,得之于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
最近笔者阅读了《袁宏道集笺校》[1](以下简称《笺校本》)中的《锦帆集》、《解脱集》以及《附录》等,深感有明一代,不应忘记诗坛公安派领袖袁宏道。
袁宏道,湖北公安人,生于明朝隆庆二年(1268),卒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
万历十六年(1588)考中举人,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登进士第,万历二十三年(1595)三月任吴县令,二年后乞归离职。
袁宏道在苏州虽然只有二年,即他自称“六百日县令”,但是在县令任上政绩颇好,与苏州文人学士来往甚密,著述甚丰,因而在政治、文学领域对苏州的影响不容忽视,下面就袁宏道在苏州的情况分别缕述。
一为政之清廉与否,能干与否,是考察一个官吏的重要依据。
袁宏道在吴令任内以仁为本、治绩超颖、清正廉明,正如他在长洲令任上的江盈科的诗中所说:“年俭迟君俸,官贫独我知。
痛民心似病,感事泪成诗。
不是催科拙,由来薄茧丝。
”“数叠铜符篆,一挥案牍尘。
”“德畏民无狱,道治鬼不神。
”[2]这也是袁宏道本人作风的写实。
明代苏州是国内重要的商业大都会,物阜民繁,是朝廷倚重的赋税大户。
但由于明末政治腐败,胥吏横行,朱紫其籍,浑水摸鱼,欺上瞒下,横征暴敛,使吴地民众备受煎熬。
袁宏道是三甲进士,根据明代成化年间诏令,选为吴县令。
袁宏道到任以后,首先整顿纳赋簿籍,对于田赋不符,数字可疑之处,便召吏诘问,甚至连诘十余处,使这些滑吏在事实面前只得“俯首曰弊”。
袁宏道将这些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胥吏根据有关法律进行惩处。
据统计,经过他的整顿,除去了额外之征总数达万万(石)。
袁宏道是一位诗人名士,他虽屡叹作令烦苦,向往历史上独往独来的名士生活,但他一旦作令,却是一位十分负责、办事认真的官吏。
袁宏道上任第二年(万历二十四年,即公元1596年)六月,苏州遭受特大水灾,袁宏道以吴县令到治下灵岩、阳山、天池、横山、穹窿、天平等地勘查灾情,并写下了很多咏景寄情的诗篇,但在有些地方如横山等。
袁宏道文艺思想中的真诗思想刍议

袁宏道文艺思想中的真诗思想刍议王志钢【摘要】本文论述了袁宏道的真诗思想及其直接理论源头,并对真诗思想中体现的文学发展思想及其理论不足以及竟陵派诗人对其理解、接受上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期刊名称】《兰州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32)003【总页数】2页(P3-4)【关键词】真诗;创作论;文学发展论【作者】王志钢【作者单位】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辽宁沈阳11002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5袁宏道的诗歌创作论崇真斥赝。
他主张诗人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哪怕艺术表现力不是很成熟、辞藻不富丽,也不要一味抄袭古人,因此提出了真诗思想。
(一)涵义何谓真诗?袁宏道解释说:“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
”[1]188真诗的特点有四:“真人”所作,任真情而成,创作过程中未被过分注重模拟的创作论等所缚,可以感人。
那么,何谓真人?他在《识张幼于箴铭后》中有如下表述:袁子曰:两者不相肖也,也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
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
[1]193据袁中郎的解释,真人就是“各任其性”“率性而行”之人。
显然,这还不是诗学层面对创作主体的一种划分,而类似《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鉴。
但是,从思维的同构性角度推察,“各任其性”“率性而行”引申到诗歌创作理论,似可推导出对不受拟古主义的创作论束缚的任情抒写的崇尚。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
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一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为野狐外道。
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
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之情欲,是可喜也。
[1]188袁宏道这段话不是仅强调只有民歌才可以传世,他是强调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有真情实感(所谓“真声”),不模拟剽窃、对唐人字仿句模。
谈袁宏道前期诗文理论述评

谈袁宏道前期诗文理论述评论文关键词:袁宏道诗文理论通变论文摘要:袁宏道是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
以他为核心的公安派文人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力主以心为师,“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观念。
他前期的诗文理论是其全部诗文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是反对摹拟,主张通变,一是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袁宏道,湖北公安人,生于明朝隆庆二年(1568年),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病卒。
中郎一生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不过短短二十几年,但他的诗文创作却相当丰富。
他文学创作的成熟与旺盛期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这段时间。
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中郎以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理论推开了晚明文学理论革新的大门,一扫王、李之云雾,对晚明文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郎的诗文理论并非一蹴而成的。
在万历二十二年之前,他虽然尚未形成自己的诗文理论体系和文学创作风格,但他在文学道路上已经颇有建树。
万历十一年,年少的中郎在县城读书期间结社城南,赋诗为文,初显身手于文坛。
他在读书之暇又赋诗为文,并集成一帙,现在《敝箧集》中收有当时的一些作品。
中郎的疏狂性情在此期间已经昭然可见。
万历二十三年,中郎赴吴县任职。
任吴县县令前后的这段时间,是中郎文学活动最为恣肆、最富革新精神的时期。
中郎虽然政务繁剧,但仍然忙里偷闲,与江盈科等友人的酬唱赠答、同游出行,还有其他文坛俊杰在他们周围推波助澜、摇旗呐喊,再与北京的兄长宗道遥相呼应,一起将文学革新运动推向巅峰。
此时的中郎已是:“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
”[1]而且无日不诗,进入他文学创作的鼎盛期,同时也进入他诗文理论的形成发展期。
这一时期,中郎有许多专论诗文理论的文章。
这些文章都是极力抨击当时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同时也提出了公安派自己的求变求新的文学主张。
一、反对摹拟,主张通变对于当时文坛的状况,中郎描述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
论袁宏道闲适思想的历史渊源

2014.02学教育20奶奶的故事“断顿儿的时候,每顿都要欠一点儿。
”每吃一顿都应该为了下一顿儿打算,正所谓“半饥半饱日子长”,这才是吃。
王一生是普通贫苦大众中的一员,他贫穷,会为了生计而忧愁,他的吃反映出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特点。
虽然贫穷,但他依然为生活奋斗,勇于面对困难,这是小人物王一生的坚持。
寻根文学产生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文化在文革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文人作家认识到应该重视中国的民族文化。
开始质疑什么是民族文化,这时的民族文化主流意识深受文革的影响,作家开始从民间或边远地区,那些不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地方进行创作。
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多含有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
《棋王》中的王一生深受道家哲学的思想,他的语言中蕴含着道德哲理。
棋呆子的棋艺深得一个捡垃圾的老者的真传,但这个老者宛如神仙。
来去无影,老者给他讲的不仅是棋道,更加是人生之道,“无为即是道,也就是棋运之大不可变,你想变,就不是象棋,输不用说了,连棋边儿都沾不上。
棋运不可悖,但每局的势要自己造。
棋运和势既有,那可就无所不为了。
”老者的话蕴含着道家的哲理,棋道即人生,也许生下来时的运气不是很好,家庭的贫苦或是身体的不健全,只要不放弃,去努力,去奋斗,自己去拼搏出一片广阔的未来,未来依然会色彩斑斓,这就是道家所说的“自己造”,在人生的道路中,只有自己是改变出路的那个绘画者。
王一生曾说过:“我迷象棋。
一下棋,就什么都忘了。
呆在棋里舒服。
就是没有棋盘、棋子儿,我在心里就能下,碍谁的事儿啊”,这是一种超脱的思想观念,即使再迫害性的文化,人们要是心灵反抗的话,也是无法侵入人的心灵深处的。
在道家哲学中,人们的精神状态被看作是理想人格的本质特征。
王一生酷爱下棋,将自己融入于下棋之中,在九人车轮战争中,对于王一生喝水的描述“把碗缓缓凑到嘴边儿。
这时下一个局号又报了棋步,他把嘴定在碗边儿,半晌,回报了棋步,才咽一口水下去,“咕”的一声儿,声音大得可怕,眼里有了泪花”。
袁宏道前期诗文理论述评

袁宏道前期诗文理论述评
梁新荣
【期刊名称】《新疆职业大学学报》
【年(卷),期】2008(016)002
【摘要】袁宏道是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以他为核心的公安派文人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力主以心为师,"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观念.他前期的诗文理论是其全部诗文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是反对摹拟,主张通变,一是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总页数】3页(P23-25)
【作者】梁新荣
【作者单位】新疆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新疆,伊宁,835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相关文献】
1.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述评 [J], 李斌
2.袁宏道游德山、桃源后的诗文风格及入世态度 [J], 武晓静
3.袁宏道《述怀》新诠——兼论袁宏道诗文笺注 [J], 刘硕伟
4.试论袁宏道前期的诗文理论 [J], 王承丹
5.华山与袁宏道诗文创作 [J], 孙瑜鑫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论文关键词:袁宏道诗文理论通变论文摘要:袁宏道是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
以他为核心的公安派文人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力主以心为师,“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观念。
他前期的诗文理论是其全部诗文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是反对摹拟,主张通变,一是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袁宏道,湖北公安人,生于明朝隆庆二年(1568年),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病卒。
中郎一生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不过短短二十几年,但他的诗文创作却相当丰富。
他文学创作的成熟与旺盛期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这段时间。
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中郎以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理论推开了晚明文学理论革新的大门,一扫王、李之云雾,对晚明文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郎的诗文理论并非一蹴而成的。
在万历二十二年之前,他虽然尚未形成自己的诗文理论体系和文学创作风格,但他在文学道路上已经颇有建树。
万历十一年,年少的中郎在县城读书期间结社城南,赋诗为文,初显身手于文坛。
他在读书之暇又赋诗为文,并集成一帙,现在《敝箧集》中收有当时的一些作品。
中郎的疏狂性情在此期间已经昭然可见。
万历二十三年,中郎赴吴县任职。
任吴县县令前后的这段时间,是中郎文学活动最为恣肆、最富革新精神的时期。
中郎虽然政务繁剧,但仍然忙里偷闲,与江盈科等友人的酬唱赠答、同游出行,还有其他文坛俊杰在他们周围推波助澜、摇旗呐喊,再与北京的兄长宗道遥相呼应,一起将文学革新运动推向巅峰。
此时的中郎已是:“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
”[1]而且无日不诗,进入他文学创作的鼎盛期,同时也进入他诗文理论的形成发展期。
这一时期,中郎有许多专论诗文理论的文章。
这些文章都是极力抨击当时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同时也提出了公安派自己的求变求新的文学主张。
一、反对摹拟,主张通变对于当时文坛的状况,中郎描述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
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2] 中郎认为时至今日古文已经凋敝,而那些复古学古摹古者,只是鹦鹉学舌,没有任何创造性,必然导致诗文走入死胡同。
在复古派食古不化的文学主张下,诗已不成诗,文也不成文,只是一些字拟句摹的复制品。
中郎对摹拟之风深恶痛绝,并对这一现象作出尖锐的批评,称这些复古者是:“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
”[3]因而他呼唤真文的出现来扫荡文坛摹拟之风,强调“真”的重要性,并认为文学创作和书画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贵在其真,也唯有真才能:“理虽近腐,而意则常新;词虽近卑,而调则无前。
”[4]只有不断变化、求真、求新才能使作品长存于世。
中郎反对摹拟,主张通变,认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
”[5]文学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现实生活并非停滞不前,永恒不变,而是不断变迁的。
因此,反映各个时代生活的文学也随着时代不断变化,这是规律所然。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
”[6][!--empirenews.page--] 中郎认为,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
[7] 通变是文学发展的规律,时代不同,文学的风格亦不同。
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产物,因而没有什么优劣高下之分。
那些字拟句摹的作品,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时代特色,缺乏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才是真正卑不足道的。
中郎在抨击当时复古现象的同时,从社会的、时代的立场,剖析文学变迁的过程,提出了新的见解。
他虽然极力反对复古,但并不笼统地排斥古人。
他主张从古人的经验中汲取有用的营养,批判的继承。
他在《叙竹林集》中说:“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
法李唐者,岂谓其机格与字句哉?法其不为汉,不为魏,不为六朝之心而已。
是真法者也。
”[8]中郎认为无论是画者还是诗者都不应以古人的法式为师,而应以现实生活为师,并学习古人求新求变的精神。
复古派不懂得“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的道理,因而止步不前,抄袭模拟,导致真文不传。
中郎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揭示出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
基于这个规律,明代的文学创作也应该“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创作属于自己时代的作品,而不是用一成不变的标准来苛求大家去复古。
也只有这样的创作精神才会让明代的文学有自己独特的时代烙印,和汉代散文、盛唐诗歌一样流传于世,一争高下。
中郎还认识到文学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一方面要顺着社会发展这个大潮流向前不断奔流,另一方面它也要在自身内部动力的推动下前行。
即随着文学自身的矛盾运动,不但文学的内容,而且文学的形式与语言也要有所变化。
“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
后之人有拟而为之者,终不肖也。
何也?彼直求骚于骚之中也。
”[9] 雅之变骚,是因为骚才能更好地抒发情感。
接下来,中郎以诗为例来阐述这个规律:“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
晋、唐以后,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辨说,有论叙。
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
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10] 诗最初的功能只是泛寄抒情,而社会不断的发展已使得单纯的泛寄抒情之诗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于是诗歌开始走向多元化,赠别、叙事等进入诗歌的题材领域。
文亦如此,也在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拓宽自己的领域。
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弃旧图新中不断发展的。
袁宏道对前后七子复古主张的猛烈抨击和力倡文随时变,既是对前后七子的针砭,也为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开辟了道路。
[1][2]下一页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摹拟,就意味着提倡独创。
中郎在否定文学复古运动的同时,提出诗文革新,强调作家要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并认为作品应是作家真实情感的流露。
这是前、后七子思想僵化、盲目尊古等理论所远远不及的。
他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一鲜明的文学观点,并以之为核心建立了一套旨在破除创作镣铐的束缚,充分展示作家自身主动性的诗文理论体系。
[!--empirenews.page--] 中郎主张为文应打破一切格套,既不受任何思想道德观念上的各种束缚,也不受古文的法度规则对文学创作的束缚,任主体情感自由抒发,表现作家自身独特的风格。
首先,在内容上,中郎强调文学抒写真性情。
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流露。
中郎提倡诗文创作必须抒写作家的性灵,表现内心的真实情感。
出自性灵者则为真诗。
要想性灵真,首先要做真人,进而强调文章不是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
他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
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
然予则极喜其疵处。
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11] 由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中郎主张诗人在创作上应该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即便创作手法或者艺术表现力还不够成熟,作品中多有疵处也无妨,反而会因为是本色独造语而更加有魅力。
对于什么是真诗,中郎也给出了答案:“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
”中郎认为复古派以传统的、陈旧的创作思路对作品进行了规范和限制,他们所摹写出来的情感不可能是真情实感。
而那些出于劳动人民之口的民歌时调没有礼教规范的约束,任情而发,故清新质朴,令人耳目一新。
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
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12] 这里提出,“真人”写“真声”的创作现象,以真实的情感抒写真实的心灵,这种诗歌才有价值。
在文学创作中,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家都崇尚真实。
中郎强调在文学创作中应注重自然本色,即真。
“真”是性灵说的重要内容,也是他论述较多、较详的内容。
他曾云:+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于唐?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
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
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
[13]他认为性灵不仅藏于主体心灵中,也隐于客体物体之中。
当心与境相交融的刹那,性灵就会激发出激情的火花。
这时创作主体只要跟随心的律动,以当时涌现的语言表述出来,就是最完美的诗歌,即真诗。
在那个模拟成风的时代,中郎再一次强调“真”的美学意义,并力倡大家写真诗,作真文。
中郎以尚真为精髓使公安派的文学革新运动具有了明确而丰富的内涵,使得以抒写真情为特征的晚明文学,具备了较为成熟完备的理论形态。
其次,在创作方法上,中郎主张信腕信口、率性而为。
如何在作品中表现诗人的真情?中郎认为,诗人的真情实感应该在作品中自然倾泻,而不需任何藻饰,应该是信腕信口,率性而为。
对此,他说:“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
”[14]又说:“不肖诗文多信腕信口。
”在文学语言的要求上,提倡语言本色自然,即不加任何修饰,自然流露性灵的本色语,反对陈词滥调。
他极力推举文之“露”、“本色”,在《叙小修诗》曾云: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
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15] 他认为在进行诗文创作时,情感跟随意境变化,文本语言跟随情感变化,作家只需担心不达其意,而不需太多考虑诗文措辞修饰等方面。
即使有“露”,也是前文中提到的多本色独造语的疵处,亦是佳处。
中郎如此强调自然与直露,是针对当时的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文坛风气而提出的。
晚明文人多为豪放不羁之士,文学观念也多激进之论。
以公安派为核心的文人对这种直抒胸臆、直露本色的风格很是推崇,同时他们也认同风格的多样化。
李贽曾云:性格清沏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
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
[16][!--empirenews.page--] 李贽认为创作是作家个性的自然流露,强调抒发心中之情感。
他打破旧传统、旧形式,让作品平民化、自然化。
深得李贽真传的中郎对同是疏狂之士的徐渭的欣赏也是基于他不拘世俗的独特风格,他在《徐文长传》中这样描述徐渭创作: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
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