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学诠释与宋儒对“文章之弊”的批评
诗学批评论文:宋诗诗学批评透析-文学批评论文-文学论文

诗学批评论文:宋诗诗学批评透析-文学批评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一、“宋人注宋诗”中注释者的诗学素养宋人注宋诗中的注释者偏重于诗学批评的一大原因在于,这些注释者本身亦擅长诗歌创作,并对注释的对象十分倾慕,且熟悉其创作风格。
任渊《黄陈诗集注序》云:“始山谷来吾乡,徜徉于岩谷之间,余得以执经焉”[2](P3)。
可知任渊青年时期曾经接受过黄庭坚的教导,因此对黄庭坚诗歌的创作风格非常熟悉。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的重要注释者赵次公也擅长诗歌创作。
宋人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题徐少章和注后村百梅诗》记载了赵次公遍和苏诗之事[3]。
苏轼之诗,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能将全集和尽,难能可贵。
王安石诗的注释者李壁(字季章),亦是当时诗文名家。
南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四《四灵诗》条云:“水心称当时诗人可以独步者,李季章、赵蹈中耳”[4]。
另外,真德秀在《故资政殿学士李公神道碑》中称:“其所自作,知诗者谓不减文公”[5]。
可见,李壁本人的创作特点近似王安石,因此在注释时对王安石诗创作特点的评论,往往能发表真知灼见。
宋人注宋诗的这些注释者,不仅本身具有较高的创作水平,并且对注释对象的创作成就与风格较为熟悉,因此他们首先对注释对象的诗学价值都予以较高的评价,其次将诗学批评重点放在创作特长方面,下文将对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宋人注宋诗”中注释者对宋诗价值的体认1.赵次公对苏诗的弘扬:苏诗之“不使事”与“自命新意”宋代有些学者对苏诗有一种成见,即认为苏诗喜欢炫耀学问、搬弄前代故事、套用前人语汇,创造力不强。
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
以押韵为工,始于韩退之而极于苏、黄。
……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
”[6](P3237)又云:“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
朱熹的圣经解释学

38宋明理学研究︵中英文︶朱熹的圣经解释学□ 陈乔见摘要:朱熹的解经学认为圣经(圣人之言)体现着融贯一致的天地之理,这是解经得以可能与必要的先验条件,也表明解经的目的是通过圣人之言把握天地之理。
就具体方法而言,朱熹一方面充分吸收汉唐注疏的训诂成果,但也认识到注疏学之陋,不足以理解圣人之意和天地之理;另一方面他与其他宋代学者一样强调义理之学,但却也十分警惕宋人好为高论新说的空疏之敝。
一方面主张随文(经)解义,另一方面也强调理会意味,切己体验。
虽说追求圣人原意和圣经本意是朱熹解经的首要目标,但他也认为有的解释未必是圣经本旨,却也是一极有价值之解释,因为它揭示了某种道理。
虽说朱熹具有强烈的圣经贤传意识,但他也认为对于以往错误的解释不应当由人情回护,而应辩其是非曲直。
在不疑与有疑、训诂与义理、原意与发明、善意原则与人性原则之间,朱熹总是保持着某种张力与平衡,使得解释成为一项既有规范亦不乏创造的意义活动。
关键词:朱熹 解释 圣经 圣人之心 天地之理作者陈乔见,中山大学哲学系暨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教授(广东 广州 510275)。
一、引言[见英文版第35页,下同]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宣称:实用主义是各种理论的公共走廊。
a仿其言,吾人可以说:诠释学是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公共走廊。
诠释学(德文Hermeneutik,英文hermeneutics,又译解释学、阐释学、释义学等)在西方发展颇为成熟,洪汉鼎先生如此概括:“综观西方诠释学的发展,我们一般可以区分两种诠释学:一是以方法论为主要取向的诠释学理论或解释理论(Interpretationslehre),其代表人物有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以及以后的埃米尼奥·贝蒂和汉斯·伦克(Hans Lenk)等;一是以存有论为主要取向的诠释学哲学,其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其后试图批判和综合哲学诠释学的哈贝马斯、利科和阿佩尔等。
儒学、经典与圣人之道-论北宋学者对儒、经、道关系的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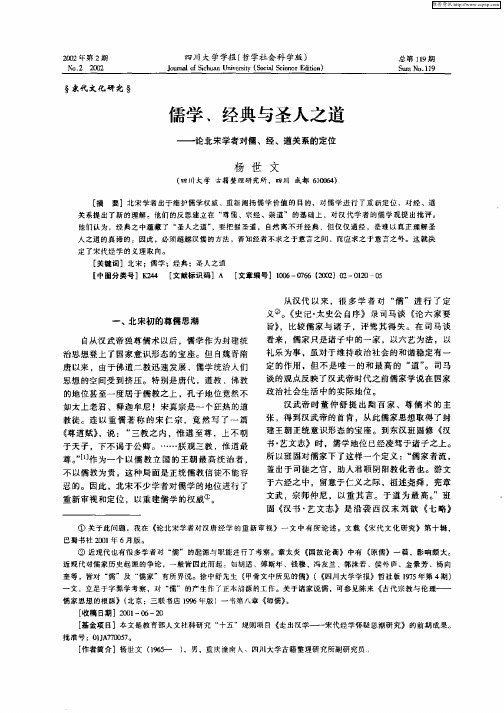
自从 汉武 帝独 尊儒 术 以后 ,儒 学作 为封 建统
治 思想 登上 了国家 意识 形 态的宝 座 但 自魏 晋 隋
唐 以来 ,由于佛道 二 教迅速发展 ,儒 学统治 人们
思想 的空 间受 到挤 压 。特 别是唐 代 ,道 教 、佛教
谈 的观 点反 映了汉武 帝 时代之前 儒 家学说 在 国家
[ 关键 词]北宋 ;儒学;经典 ;圣人 之道 【 中图分 类号 ]K4 [ 24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 6 06 ( O) 2 02 — 5 0 — 76 2 2 0 — 1 0 0 O 0
从汉 代 以来 ,很 多 学 者 对 “ ”进 行 了 定 儒
一
、
北宋 初的尊 儒 思潮
懦家 思想 的根源》 ( 北京 :三联书店 19 96年版)一 书第八章 《 师儒》 。
[ 收稿 日 ]20 — 6 如 期 01 0 一 [ 基金项 目]本 文是 教育 部人文社科 研究 “ 十五 规则项 目 《 走出汉学—— 宋代经学怀疑思潮研究》的前期 成果。
批 准号 :0 J 70 5 1A 70 7
近 现代 对儒家历史起源 的争论 ,一 般皆因此而起 。如胡适 、傅斯年 、钱 穆、冯友兰 、郭沫若 、候 外庐 、金 景芳 、杨 向
奎等 ,皆对 “ 及 “ 儒 儒家 有所界说。徐中舒先生 《 甲骨 文中所 见的儒》(《 四川大学 学报》哲社版 1 5 第 4 ) 9 年 7 期
一
文 ,立足于字豫学考察 ,对 “ 懦”的产生作 了正本清源的工作 。关 于诸家说儒 ,可参见陈来 《 代宗 教与伦 理—— 古
[ 作者简 介]杨世文 (9 5 16一
) ,男,重庆潼南人 。四川大学古藉整理研 究所副研究员。
杨慎对儒学的揭示与批判

杨慎对儒学的揭示与批判揭示理学和心学都存在的弊端杨慎说: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
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
故高远之弊,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
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于(而效)小,学而无用,世以俗学以之。
“尊德性而道问学”,本为《中庸》所谓,但宋儒中,朱熹主张以究理问学为主,提倡研读经传,一依圣贤遗教去做,有偏重于“道问学”的倾向,陆九渊讥评其支离破碎;陆九渊主张学者从经典中解脱出来,求诸本心,认为“学苛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有“尊德性”的倾向,朱熹斥责其尽废讲学。
自南宋朱、陆相争以来,两家之学渐成水火之势,“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
这对儒学发展影响甚大,诚如程敏政所说:“朱、陆之辨,学者持之至今。
…其流至于尊德性、道问学为两途,或沦于空虚、或溺于训诂,卒无以得真是之归。
此道所以不明不行。
”杨慎在这里则对朱、陆都进行了批评,指出陆学之弊在于“以空索为一贯”,趋简凭虚而入于禅,“学而无实”;朱学之弊在于“以杂博相高”,遗本溺心而流于俗,“学而无用”。
在他看来,“经学之拘晦,实自朱始”,“新学(此指象山心学)削经铲史,驱儒归禅”,两者对学术风气和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这样,杨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学。
对于当世流行的“道学”(即理学)和“心学”,杨慎亦持全面否定态度。
他说:“道学、心学,理一名殊。
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
更无高远亢(言)妙之说,至易而行难,内外一者也。
被之所行,颠倒错乱,于人伦事理大戾。
顾巾衣诡服,阔论高谈,饰虚文美观而曰:吾道民、吾心学,使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琢磨,以求所谓禅悟。
此其贼道丧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乱民之俦,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学、心学之有?”他认为儒学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内外一者也”,但承袭宋儒之学风而流行于明世的所谓“道学”、“心学”,尽管名称不一,形式有异,而其实都是只知“阔论高谈”、“虚饰文词”,只说不行,“教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着摸”的空洞无用之物。
陈澧文学思想综述

陈澧文学思想综述陈澧,晚清岭南著名学者,平生致力于经学研究,旁及历史、地理、金石、音乐、文学等,著有《声律通考》《汉儒通义》《东塾读书记》等著作,对近代广东学术发展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今人一般将陈澧视为经学家、思想家,对其诗文及文学思想则较少关注。
陈澧虽无专门的文论著作,但在大量的札记、书信、文评、序跋中,他的文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并且与他的经学思想相辅相成、互相辉映。
陈澧在经学上持汉宋调和的立场,其文学思想正如他的经学主张,“本之于经”的同时对当时文坛上的各种矛盾基本上持调和折中的立场。
作为汉宋兼采派经学家的代表人物,陈澧的文学思想在近代文论转型的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一、文论观点“本之于经”作为一名经学家,陈澧亦兼擅文学,其经学思想及其学术方法不知不觉向文学的领域延伸。
陈澧的文论观点皆“本之于经”,将《诗经口小雅》中“有伦有脊”一词作为作文指导法则,并将文学视为学术经世的手段之一。
对于作文之法,陈澧拈出了“有伦有脊”的原则,并且明确指出自己的文论观点“本之于经”:“昔时读《小雅》‘有伦有脊’之语,尝告山舍学者,此即作文之法,今举以告足下,可乎?伦者,今日老生常谈,所谓层次也。
脊者,所谓主意也。
夫人必其心有意而后其口有言,有言而其手书之于纸上,则为文。
无意则无言,更安得有文哉!有意矣,而或不止有一意,则必有所主,犹人身不止一骨,而脊骨为之主,此所谓有脊也。
意不止一意而言之,何者当先?何者当后?则必有伦次。
即止有一意而一言不能尽意,则其浅深本末又必有伦次,而后此一意可明也。
……虽然,伦犹易为也,脊不易为也,必有学有识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读书而非徒读文所可得者也。
仆之说虽浅,然本之于经,或当不谬。
”[1所谓“有脊”,是指文章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
所谓“有伦”,是指文章层次清楚、条理分明,也就是要求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然而,“伦犹易为也,脊不易为也”,如何才能做到文章“有伦有脊”?陈澧提出“必有学有识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读书而非徒读文所可得者也。
论《子不语》中袁枚的经学观念

论《子不语》中袁枚的经学观念孙全敏袁枚的《子不语》作为清代志怪小说,其受关注程度远不及《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但其中体现着袁枚的社会观念、人生观念和经学观念,是研究袁枚的资料之一。
本文立足于小说《子不语》的具体篇章对袁枚的经学观念进行分析,发现其中体现了袁枚批判汉学和宋学、不尊经学权威的经学观念。
袁枚是清代乾嘉诗坛的盟主,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
袁枚主张“独抒性灵”,其诗歌创作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其“性灵派”有创新之处,但也被当时很多学者所诟病。
袁枚同时也是一位小说家,他的志怪小说集《子不语》就是清代非常重要的文言小说之一。
但袁枚的《子不语》受关注以及受研究的程度远不及同时期的《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
从《汉书艺文志》将六艺类列于首位后,其中包含的经学在中国整个传统学术文化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国文士从小就要接受经学教育,并以此走入仕途。
袁枚“仆龀齿未落,即受诸经”就证明他从小接触经学。
但是,袁枚不是一味地继承经学,他对经学有着自己的思考。
袁枚自身的经学观点不仅在其诗集、文集中体现出来,其小说中也通过故事体现着经学观点。
袁枚从小接受经学的熏陶,对经学有着自身独特的想法,而且他对当时经学纷争有着自己的观点,与当时许多经学大家有着书信往来,一起探讨着经学问题。
袁枚在《与程蕺园书》与当时富有盛名的宋学家程鱼门就宋儒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
袁枚在文中直指程蕺园诸流以宋儒为尊的荒谬性,强调自己并非反对宋儒,而是主张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来评论宋儒宋学。
《答惠定宇书》和《答定宇第二书》中,袁枚反对汉儒唯经是从,认为“六经皆文”。
袁枚认为,注疏考据之学不如文学著作的创作。
袁枚与宋学家和汉学家都有书信来往,并没有加入其中一派。
一、批汉儒、反汉学袁枚对经学有着自己的观点,同时包容其他观点的存在,但是对汉儒持批判的态度。
《续子不语卷五》的《麒麟喊冤》一文写道,有一神殿名为“文明殿”,大殿两旁陈列了各种各样的书籍。
易简功夫――宋儒的经学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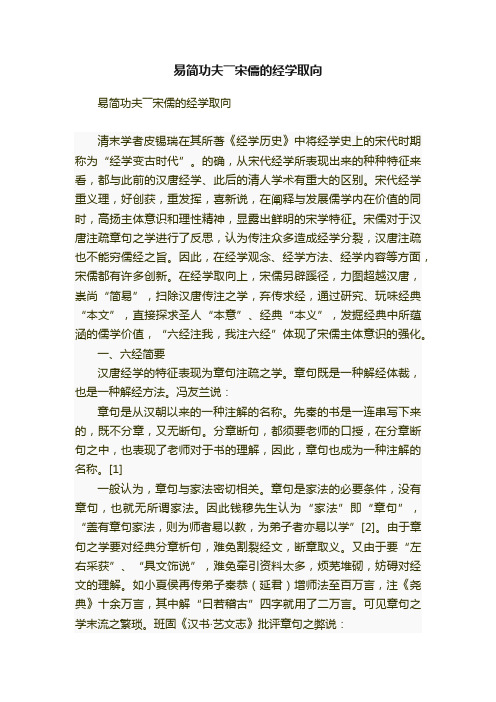
易简功夫――宋儒的经学取向易简功夫――宋儒的经学取向清末学者皮锡瑞在其所著《经学历史》中将经学史上的宋代时期称为“经学变古时代”。
的确,从宋代经学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来看,都与此前的汉唐经学、此后的清人学术有重大的区别。
宋代经学重义理,好创获,重发挥,喜新说,在阐释与发展儒学内在价值的同时,高扬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显露出鲜明的宋学特征。
宋儒对于汉唐注疏章句之学进行了反思,认为传注众多造成经学分裂,汉唐注疏也不能穷儒经之旨。
因此,在经学观念、经学方法、经学内容等方面,宋儒都有许多创新。
在经学取向上,宋儒另辟蹊径,力图超越汉唐,崇尚“简易”,扫除汉唐传注之学,弃传求经,通过研究、玩味经典“本文”,直接探求圣人“本意”、经典“本义”,发掘经典中所蕴涵的儒学价值,“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体现了宋儒主体意识的强化。
一、六经简要汉唐经学的特征表现为章句注疏之学。
章句既是一种解经体裁,也是一种解经方法。
冯友兰说:章句是从汉朝以来的一种注解的名称。
先秦的书是一连串写下来的,既不分章,又无断句。
分章断句,都须要老师的口授,在分章断句之中,也表现了老师对于书的理解,因此,章句也成为一种注解的名称。
[1]一般认为,章句与家法密切相关。
章句是家法的必要条件,没有章句,也就无所谓家法。
因此钱穆先生认为“家法”即“章句”,“盖有章句家法,则为师者易以教,为弟子者亦易以学”[2]。
由于章句之学要对经典分章析句,难免割裂经文,断章取义。
又由于要“左右采获”、“具文饰说”,难免牵引资料太多,烦芜堆砌,妨碍对经文的理解。
如小夏侯再传弟子秦恭(延君)增师法至百万言,注《尧典》十余万言,其中解“曰若稽古”四字就用了二万言。
可见章句之学末流之繁琐。
班固《汉书·艺文志》批评章句之弊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
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张之洞的经学思想

张之洞的经学思想作者:文丹来源:《教育文化论坛》2018年第02期摘要:张之洞是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同时师从鸿儒、8岁即读完四书五经,勤于治学,可谓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集于一身,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自汉代经学兴起以来,主要区分为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
两派壁垒森严,互相攻讦,今古文之争绵延数千年。
张之洞强调治经“以汉学为本”,从“文字训诂入手”精研经书。
自宋代始,理学立为正统学说,传统学术的重心转入对人心、人性、人欲的主观世界的探究,使儒学由孔、孟时代的伦理政治学演变成道德哲学,明清逐渐走向空疏清谈。
张之洞以汉学为宗,一贯反对空疏清谈而尊承孔儒“经世”之传统,主张“通经明理致用”。
通经明理致用最终“归于有用”,这种思想与张之洞尊承汉学“经世”之传统并行不悖。
关键词:四书五经;通经明理致用;汉代经学中图分类号:G529;G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8)02-0135-04DOI:10.15958/ki.jywhlt.2018.02.027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
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
清同治进士。
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时师从鸿儒、八岁即读完四书五经,勤于治学,可谓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于一身,在中国学术上特别是经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一、守古文经学、恶古文经学中国之学术以经学为主流。
自汉代经学兴起以来,主要区分为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
两派壁垒森严,互相攻讦,今古文之争绵延数千年。
张之洞早年所师从者,有如韩超、黄政钧、王含章、敖国琦、丁诵孙、童云逵、洪次庚、吕文节等,皆宗古文经学,这无疑给予张之洞以决定性影响。
张之洞恪守古文经学立场,而对今文经学深恶痛绝。
在《读聂氏三礼图札记》、《汪拔贡述学》以及《读书札记》、《輏轩语》、《劝学篇》等著述中,都表达了他的立场和观点。
张之洞强调治经“以汉学为本”,从“文字训诂入手”精研经书。
论王世贞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与反思(一)

论王世贞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与反思(一)作为“后七子”的领袖和七子派的集大成者,王世贞精通文学、史学和经学,思想灵活开放,不为传统和权威所。
在明中后期学术思想逐步解放的背景下,对宋儒、宋明理学及理学家文艺观念进行了广泛而直率的批评,对明代儒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反思。
爬梳和整理这些散见于浩繁卷帙中的批评言论,总结和探索其儒学思想的特点及成因,不仅有助于丰富学界对文学巨匠王世贞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七子派的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王世贞对理学家文艺观念的批评维护诗文的本体特征,是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重要目标。
嘉、万年间,“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现象仍然存在,唐宋派理学习气更是甚嚣尘上。
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重张复古大旗,试图遏制文学创作中过分谈道论理以致文辞为道理所束而塞不畅的现象。
《书曾子固文后》一文曾言:子固有识有学,尤近道理,其辞亦多宏阔遒美,而不免为道理所束。
间有塞而不畅者,牵缠而不了者。
要之,为朱氏之滥觞也,朱氏以其近道理而许之。
近代王慎中辈,其材力本胜子固,乃掇拾其所短而舍其长,其塞牵缠,迨又甚者。
(卷三)王世贞在此指出了曾巩诗文“为道理所束”的弊病以及与朱熹在文风方面的联系,并严厉批评了王慎中等唐宋派文人在学习曾巩时“掇拾其所短而舍其长”的做法。
对唐宋派的理学习气以及以、曾巩为榜样的问题在此不妨多说几句。
据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记载,王慎中曾“与龙溪王畿讲解王阳明遗说,参以己见。
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契合。
囊惟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
至是始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味长,而曾(巩)、王(安石)、欧氏(欧阳修)文尤可喜……但有应酬之作,悉出入曾、王之间。
”而唐宋派另一重要人物唐顺之更是如此。
他曾自述其诗是“率意信口,不调不格,大率似以寒山、《击壤》为宗”,而文则“大率所谓宋头巾气习”(卷六《答皇甫百泉郎中》)。
在给王慎中的信中又说:“近来有一僻见,以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曾巩),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邵雍)者。
阮元的经、文学思想与八股批评观

阮元的经、文学思想与八股批评观作者:江丹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03期摘要:乾嘉之际,阮元以显宦和学者的身份倡导实学,调和汉宋,从实学出发,阮元主张“以训诂求义理”的治学方法,认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强调通经致用,反对士子只习八股不为实学的不正学风,反对书院只课时艺,唯科考是从;从尊经立场出发,阮元认为骈文乃文章正宗,而八股文体源于骈文,其文体亦属正宗。
关键词:经学;汉宋之争;骈文;八股文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3.13阮元(1764-1849),字伯元,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
其人“博学淹通,早被知遇”。
一生官运亨通、历居要职,以学者、显宦一身二任,勤于治学,主持风会,以奖掖后进、刊刻书籍为事。
《清史稿》总结阮元一生学术功绩时言:历官所至,振兴文教……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祀许慎、郑康成,选高才肄业;在粤立学海堂亦如之,并延揽通儒,造士有家法,人才蔚起。
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诂》《皇清经解》百八十余种,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纪事、谈艺诸编,并为世重。
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阮元治学通博,龚自珍在《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中将其学问分为训故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九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和掌故之学等十种学问。
本文简论阮元基于尊经立场的经、文学思想,并阐述其基于经、文学思想的八股批评观。
一、以训诂求义理,“实事求是”之经学立场,反对书院八股教育清代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学者总结明亡教训,将明末游谈无根之心学末流所导致的空疏视为明亡的重要原因,提倡通经致用的实学,认为治学当明道救世。
到了乾嘉时期,清廷一方面文禁甚严,大兴文字狱,一方面“稽古右文”,倡导学术,专制与怀柔结合,加之学术本身的发展趋于纯熟,这就促使了乾嘉时期不问现实只重训诂考据的汉学之风大盛。
论汉学,宋学经典诠释之不同

·中国哲学·论汉学、宋学经典诠释之不同3蔡 方 鹿经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哲学与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经学的发展演变相适应,中国有两千多年注释儒家经典的传统,有许多关于诠释学的思想资料,并形成了较有代表性的若干诠释方法和理论。
汉学和宋学即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两大流派,它们分别对儒家经典做出了自己的诠释,而它们对经典的诠释又是与各自学派的性质和特点分不开的。
本文试就汉学和宋学经典诠释的不同加以探讨,并从经典诠释的角度进一步分析经学史上汉学与宋学各自学派的特征。
经学分为汉学和宋学两派,此说由清四库馆臣提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称:“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
”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章句集注〉提要》亦称:“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以偏重于考证或是偏重于义理来区分汉学与宋学。
其后,江藩在其《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中,亦将经学分为汉学和宋学两大派。
所谓汉学,是指在战国经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唐章句训诂注疏考证之学,它包括西汉今文经学、东汉古文经学、汉末融通今古文的郑玄之学、魏晋王肃之学、南北朝经学、隋唐经学等从西汉到唐代约一千一百年间的经学派别。
所谓宋学,指宋代义理之学(后延续到元明,亦包括清代宋学),它是以讲义理为主的经学派别,大体以理学诸派为主体,并包括了王安石新学、三苏蜀学以及当时讲义理的诸治儒家经学的流派。
汉学与宋学经典诠释之不同,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区分:一是就经典诠释所依傍文本的重心而言,汉学以五经系统为主,宋学则以四书系统为主;二是就经典诠释的方法而言,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三是从经典诠释的理论深度而言,汉学以经学诠释为主,宋学则在经学诠释的基础上加以哲学诠释;四是就儒家经学与宗教的关系而言,汉学以排斥佛、道二教为主,宋学则对佛、道二教既有排斥又有吸取。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笔记和考研真题详解(苏轼和北宋的文学理论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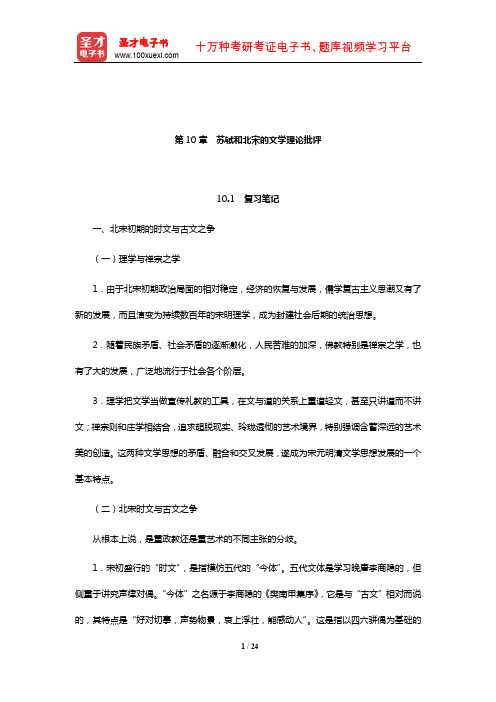
第10章苏轼和北宋的文学理论批评10.1 复习笔记一、北宋初期的时文与古文之争(一)理学与禅宗之学1.由于北宋初期政治局面的相对稳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儒学复古主义思潮又有了新的发展,而且演变为持续数百年的宋明理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
2.随着民族矛盾、社会矛盾的逐渐激化,人民苦难的加深,佛教特别是禅宗之学,也有了大的发展,广泛地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
3.理学把文学当做宣传礼教的工具,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重道轻文,甚至只讲道而不讲文;禅宗则和庄学相结合,追求超脱现实、玲珑透彻的艺术境界,特别强调含蓄深远的艺术美的创造。
这两种文学思想的矛盾、融合和交叉发展,遂成为宋元明清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
(二)北宋时文与古文之争从根本上说,是重政教还是重艺术的不同主张的分歧。
1.宋初盛行的“时文”,是指模仿五代的“今体”。
五代文体是学习晚唐李商隐的,但侧重于讲究声律对偶。
“今体”之名源于李商隐的《樊南甲集序》,它是与“古文”相对而说的,其特点是“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
这是指以四六骈偶为基础的一种偏重艺术形式美文体。
2.随着儒学复古主义思潮的深化,提倡古文的理论与实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开展了对西昆派诗文的激烈批评。
二、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和梅尧臣的“平淡”论(一)欧阳修及其理论1.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
是北宋前期文坛领袖。
2.欧阳修的理论:“穷而后工”(1)“穷”,主要是指政治上穷达之“穷”,而不是指生活上的穷困。
即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政治上不得志,受排挤、遭迫害,隐身江湖草野山林田园,借诗文来寄托其济世安民壮志,抒发对现实黑暗的怨愤不满以及种种忧思、苦闷、压抑、感慨之情。
(2)他在主张“道胜”的同时,又十分重视文的修饰。
“工”,就包含着他对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追求。
在内容和形式关系上,他既肯定内容的主导作用,又充分注意形式的重要性及其相对的独立性(二)梅尧臣及其理论1.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人。
马氏文通批评经传释词

马氏文通批评经传释词马氏文通是宋代末年儒学家,其学术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将南宋以来的经学发扬光大,同时采纳了理学的某些观点。
在经学方面,马氏文通批评了一些经传的释词,对“经传释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马氏文通批评经传释词的论点及其意义。
一、批评经传释词虚假歧义在经典中,有很多造成歧义的词语。
这些歧义可以是多义性的,也可以是语义相反的。
南宋以来,经学家们为了对经典进行解释,就采用了“经传释义”的方式,即用古文注释古文。
马氏文通认为,在这种方式下,解释经典的目的成为了体现注释者自身的学问和观点,而非真正恢复经典原意。
这种释义虚假和歧义的结果是使得我们更难以理解经典,也更容易对经典产生误解。
二、提倡经学精神马氏文通认为,解释经典的目的应该是尽可能恢复经典原意,而非注释者的意见。
他倡导的是经学精神,即真实、神圣、客观地去了解和传播经典。
在这种解释中,注释词汇的选用和翻译都应该顺应经典语境和前后衔接的逻辑关系,而不是根据注释者自身的观点加以解释。
三、呼吁经传文人审慎解释在马氏文通看来,经传释义的问题不只在于词汇的选择,还在于注释者的拥有自己的学说和观点后所持的主观性。
因为主观性原因,注释者可能会在解释中曲解真正的含义。
因此,他强调经传文人需要具备审慎解释的素养。
他们需要准确理解经典,尊重并兼顾经典各方面的信息,从而更好的发挥注释员的作用。
四、对于曲解传统观念诵偏口舌的责备马氏文通的另外一个观点是,许多注释者在解释经典时发生了诵偏口舌的现象。
因为他们的个人思想或实际需要,这些注释者倾向于错误解释部分信息或遗漏一些关键信息,导致在学术领域引起了误解。
因此,他警示注释者应当警惕自身的思想冲动,通过主动反思和讨论,客观地评估自己的观点的合理性。
马氏文通的这些论点对于今天的学术界仍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方面,我们仍然面对着经传释词虚假歧义的情况。
因为中文的多义和含糊性,我们很容易在阅读中理解出偏差的词义。
章太炎论宋明理学——以程朱陆王之辨为中心的检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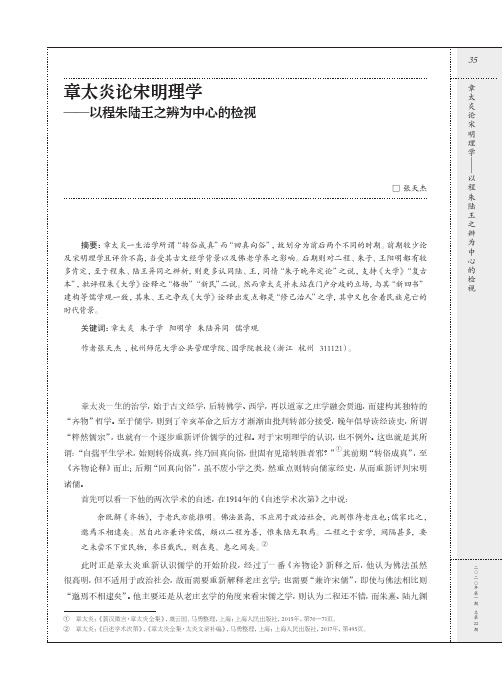
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
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许宋儒,颇以二程为善,惟朱陆无取焉。二程之于玄学,间隔甚多,要 之未尝不下宜民物,参㠯戴氏,则在夷、惠之间矣。b
此时正是章太炎重新认识儒学的开始阶段,经过了一番《齐物论》新释之后,他认为佛法虽然
前期的章太炎,对于宋明理学论断并不多,且比较杂乱,不同文献的指向也不一致,总的来说则 是以经史考据、小学,以及佛学、玄学的立场来看儒学,特别反对调和附会的汗漫学风,故而对以“朱 子晚年定论”调和朱陆的王阳明评价不高;而程、朱、陆等人能够吸收佛学而转出儒家的心性之学,使 得宋代理学攀得上魏晋玄学,故而特别维护程、朱,然亦评价不高,还对朱子被定于一尊多有批判。
结合这两篇自述,则可知章太炎在其自身的哲学建构完成之后,方才重新钻研宋明理学,并对程 朱、陆王之异同等问题,都作了较多的辨析,从而形成其重构儒学的新理念。b
一、前期之论宋明理学 [见英文版第41页,下同]
不过在讨论章太炎后期的宋明理学观点之前,先简要回顾一下其前期对于宋明理学的基本看法。 其前期相关的文献并不多,较为典型而笼统地论及儒学的文章有《论诸子学》:
检
本”,批评程朱《大学》诠释之“格物”“新民”二说。然而章太炎并未站在门户分歧的立场,与其“新四书”
视
建构等儒学观一致,其朱、王之争或《大学》诠释出发点都是“修己治人”之学,其中又包含着民族危亡的
时代背景。
关键词:章太炎 朱子学 阳明学 朱陆异同 儒学观
作者张天杰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学院教授(浙江 杭州 311121)。
a
瑕衅何为而不息乎?
宋儒《中庸》学之滥觞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看胡瑗的《中庸》诠释

Zh a n g Z a i a n d Two Ch e n g B r o t h e r s ,b u t h e h a s i n d e e d l e d t h e t h i n k i n g wa y f o r h i s g e n e r a t i o n . An d t h e
Ab s t r a c t : Ta k i n g
“ Ti a n Di Z h i Xi n g ’ ’a s t h e b a s i s o f“ Go o d n e s s ’ ’ a n d“ Xi n g Qi q i n g ’ ’ a s t h e a p p r o a c h
后 来张 、 程、 朱 子 等 道 学主 流 的论 说 方 向 。从 经 学 史 的 角 度 来 说 , 胡 氏 之 注《 中庸 》 , 则 明显 表 现 出 理 说 经 的 倾 向 。从 中我 们 可 以 看到 , 作 为 宋儒 《 中庸 》 学之滥觞 , 其 对《中庸 》 的诠释 , 其 内涵虽不及 后来张 、 程 等人 那 么丰 富 与 深 刻 , 但 无 疑 已经 引领 了一 代 人 的 思 考 方 向 , 其 意 义或 已在 内容 本 身 之 上 。 [ 关 键 词 ]胡 瑗 ; 《 中庸 》 ; 性; 情 [ 中 图分 类 号 ]B 2 4 4 [ 文 献 标 识 码 ]A [ 文 章 编 号 ]1 0 0 8 -1 7 6 3 ( 2 0 1 4 ) O 1 一O 0 2 7 一O 6
he ha s be g un t he ma i n d i r e c t i on o f a r gu me n t o f Zha n g Za i ,t wo Che ng Br o t he r s a nd Zh u Xi .Fr o m t h e hi s —
儒道与死生:宋儒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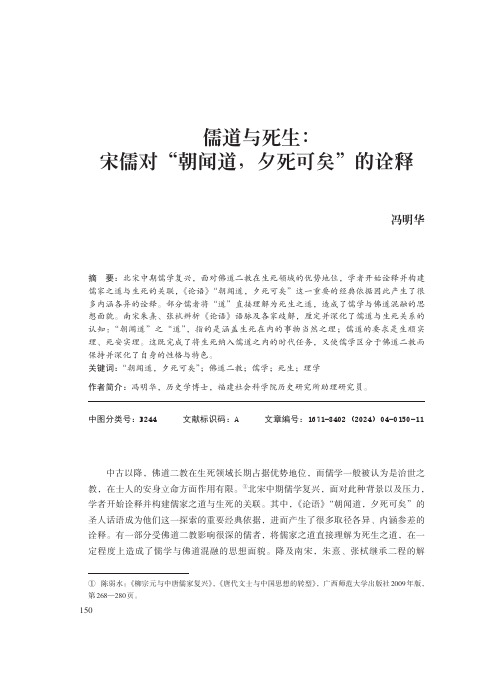
儒道与死生:宋儒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诠释冯明华摘要:北宋中期儒学复兴,面对佛道二教在生死领域的优势地位,学者开始诠释并构建儒家之道与生死的关联,《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一重要的经典依据因此产生了很多内涵各异的诠释。
部分儒者将“道”直接理解为死生之道,造成了儒学与佛道混融的思想面貌。
南宋朱熹、张栻辨析《论语》语脉及各家歧解,厘定并深化了儒道与生死关系的认知:“朝闻道”之“道”,指的是涵盖生死在内的事物当然之理;儒道的要求是生顺实理、死安实理。
这既完成了将生死纳入儒道之内的时代任务,又使儒学区分于佛道二教而保持并深化了自身的性格与特色。
关键词:“朝闻道,夕死可矣”;佛道二教;儒学;死生;理学作者简介:冯明华,历史学博士,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24)04-0150-11中古以降,佛道二教在生死领域长期占据优势地位,而儒学一般被认为是治世之教,在士人的安身立命方面作用有限。
①北宋中期儒学复兴,面对此种背景以及压力,学者开始诠释并构建儒家之道与生死的关联。
其中,《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圣人话语成为他们这一探索的重要经典依据,进而产生了很多取径各异、内涵参差的诠释。
有一部分受佛道二教影响很深的儒者,将儒家之道直接理解为死生之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儒学与佛道混融的思想面貌。
降及南宋,朱熹、张栻继承二程的解①陈弱水:《柳宗元与中唐儒家复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280页。
150《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释,辨析《论语》语脉及各家歧义,厘定并深化了儒道与死生关系的认知:“朝闻道”之“道”,指的是涵盖死生在内的事物当然之理;儒道的要求是生顺实理、死安实理。
这既完成了将死生纳入儒道之内的时代任务,又使儒学区别于佛道二教而保持并深化了自身的性格与特色,为士人在安身立命方面提供了新的思想与践行途径。
北宋中期的儒门分歧——文史之争

北宋中期的儒门分歧——文史之争北宋中期,儒学借古文运动而得以复兴,其中的代表人物从政治上分为两派:即旧党和新党。
但他们在对待史学和文学的态度上却划分的不是那么明显,而反倒彼此有重合之处。
其中新党反对史学和文辞之学,旧党中则有尊史而反文的,如朔学司马光一派,尚文史的如蜀学三苏一派,以及反对文史之学的,如洛学一派。
洛学之反文史,朔学之反对文辞之学,与政治上敌对的新党持相近态度。
我们可以看到,对待文学和史学的态度成为区分各新兴儒学学派的重要特征。
而从这种重合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北宋中期学术争斗的真实情况远较其表面层次复杂。
一、史学之尊贬北宋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儒学复兴运动,诸儒从文史入手,而上溯先秦诸子以至于古代经学。
史学历来是儒学中重要的领域。
在古文运动诸大家中,欧阳修是以史学著称的。
其他如古文运动早期人物孙复曾作《春秋尊王发微》,石介作《春秋说》,于五经中独重《春秋》一经,应该说他们都是尊重史学的。
同样作为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王安石则不喜史学,甚至反对史学。
王安石《答韶州张殿丞书》说: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
盖其所传,皆可考据。
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史。
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不,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栗,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耳。
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邪?从书中可知,王安石于三代以后之史,根本持怀疑态度。
《春秋》开后世史学之端,因此他于六经中最不喜《春秋》,曾经诋《春秋》为“断烂朝报”。
对史学的态度如何,正是元祐学术(旧党的学术)与王安石新学的一大歧异之处,重史学则多尊传统,倾向保守;否定历史则多变法,走向激进。
司马光之朔学可算作当时的史学一派,陈襄《熙宁经筵论荐三十三人品目》论司马光云:“以道自任,博通书史之学”,司马光组织编写了《资治通鉴》,他在当时是以名臣兼史家闻名于世的。
《士冠礼》“三服之屨”于“经末记前”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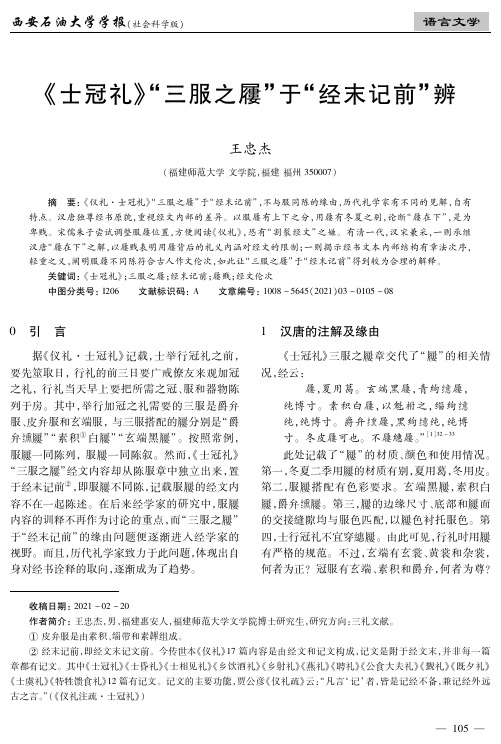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21-02-20作者简介:王忠杰,男,福建惠安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三礼文献。
①皮弁服是由素积、缁带和素鱢组成。
②经末记前,即经文末记文前。
今传世本《仪礼》17篇内容是由经文和记文构成,记文是附于经文末,并非每一篇章都有记文。
其中《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12篇有记文。
记文的主要功能,贾公彦《仪礼疏》云:“凡言‘记’者,皆是记经不备,兼记经外远《士冠礼》“三服之屦”于“经末记前”辨王忠杰(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摘 要:《仪礼·士冠礼》“三服之屦”于“经末记前”,不与服同陈的缘由,历代礼学家有不同的见解,自有特点。
汉唐独尊经书原貌,重视经文内部的差异。
以服屦有上下之分,用屦有冬夏之别,论断“屦在下”,是为卑贱。
宋儒朱子尝试调整服屦位置,方便阅读《仪礼》,恐有“割裂经文”之嫌。
有清一代,汉宋兼采,一则承继汉唐“屦在下”之解,以屦贱表明用屦背后的礼义内涵对经文的限制;一则揭示经书文本内部结构有章法次序,轻重之义,阐明服屦不同陈符合古人作文伦次,如此让“三服之屦”于“经末记前”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士冠礼》;三服之屦;经末记前;屦贱;经文伦次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645(2021)03-0105-08 0 引 言据《仪礼·士冠礼》记载,士举行冠礼之前,要先筮取日,行礼的前三日要广戒僚友来观加冠之礼,行礼当天早上要把所需之冠、服和器物陈列于房。
其中,举行加冠之礼需要的三服是爵弁服、皮弁服和玄端服,与三服搭配的屦分别是“爵弁纟熏屦”“素积①白屦”“玄端黑屦”。
按照常例,服屦一同陈列,服屦一同陈叙。
然而,《士冠礼》“三服之屦”经文内容却从陈服章中独立出来,置于经末记前②,即服屦不同陈,记载服屦的经文内容不在一起陈述。
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

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一、孔子删诗公案宋代兴起经学的怀疑学风,宋儒严格地强调纲常礼教,认为《诗经》中有大批“淫诗”,“若以圣人删定”,则借圣人之名传播“恶行邪说”[2],所以不能承认孔子按礼义标准删诗之事。
从此展开删诗说与非删诗说的论战。
当“五四”的狂飙过去,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中国学者冷静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检讨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重新肯定孔子的历史贡献。
孔子不是神圣,不是必须顶礼膜拜的偶像,却是对中国文化有卓越贡献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古文献整理专家。
在现代回顾孔子删诗的公案,其性质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实质上只是一位教育家和经他编选的一部教材的关系,一位古文献整理专家和他所整理的一部上古文献的关系。
这样,现代学者完全可以从新的角度来清理这一公案。
七十年代后期起,学者扩大了视野,开始在较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研究春秋时古文献和《诗经》流传的情况,研究孔子整理古文献的思想和方法,全面探讨《诗经》和孔子的关系,以此为题的专论达数十篇之多[8]。
由于以新角度、全方位地进行审视,使这一公案取得更大的进展。
总括近十余年的研究,基本认识如下:二、所谓“正乐”,即孔子自己所说的“《雅》《颂》各得其所”,按乐曲的正确音调校正音律,并进行篇章编次的调整,《雅》诗归于《雅》这一类,《颂》诗归于《颂》这一类。
《史记》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可见他确实按乐曲分类进行编订。
三、所谓语言规范化,即《论语·述而》所记“皆雅言也”。
从各地搜集来的传本,在当时只有抄本,十五《国风》又是土乐,其文辞必然古语、方言、俗语错杂。
孔子运用当时的“雅言”(标准语)进行语言规范化的处理,取得语言的统一。
这是作为教师的孔子,对用作教授学生的教材,必然要做的工作。
为了规范化,对某些文字和语法作必要的加工和改动,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通过以上考察,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孔子是否按礼义标准选诗。
——这个问题,只有从孔子对《诗》的内容的评价和他整理古文献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
宋代的儒学与经学

宋代的儒学与经学宋代儒学与经学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年代,这个时期儒学与经学在文化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后来的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儒学和经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而在宋代,则逐渐形成了儒学为主、经学为辅的文化主导格局。
下面将会从经学、儒学这两方面入手,探讨一下宋代儒学与经学的关系。
一、宋代经学宋代经学,主要包括了《易经》、《周易》、《尚书》、《礼记》等经典。
宋代经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对于经义的注释、研究、整理与发扬,在学理的范畴内形成了世所公认的柿崩学派、白学派、程学派等。
宋代经学的重心不再是以琐碎的注释为主,它更注重对经典内涵的研究,强调对经典精神和价值的挖掘,从而形成比较系统与完整的经学学派。
宋代经学的最大代表,是程朱理学。
这个理学体系是以程颐、朱熹为主要代表的,它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以“性”与“理”的相互关系为核心。
该理学体系对于宋代文化及明代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里,笔者特别要强调的是程学派的特点,因为这一学派的出现,使得经学的学习及传承,得以更加系统、完整和科学。
二、宋代儒学宋代儒学的兴盛归功于孔子思想的再现、补充和创造。
有人说:“宋代儒学,是对困扰自孔子以来的问题的继承和解决。
”对此,有两个方面需要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
1. 孔子思想的再现与创造孔子思想的再现,指的是对于孔子思想的纯粹再现,使其得以正本清源。
宋代儒学对于孔子思想的注释和解读,已经融入了自身的伦理价值观和社会理论,并且将孔子思想和文化融合在了一起。
宋代的儒学思想,以在《礼记》和《大学》中所体现的“中庸”为核心,注重人性、自我和道德的教育,强调人类社会的和谐与正义。
另一方面,宋代儒学又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思想,使其得以与当时的时代要求相符合。
例如,在《七十子》中,新儒家以“惟心”的学说,修正了“形神一体”的“老庄学派”,同时,又摈弃了“知行合一”的程学派,主张“心所欲,皆无不可”。
并且,宋代儒学很好地将“德”和“知”两个层次进行了升华,提出了“格物致知”的重要思想。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宋代经学诠释与宋儒对“文章之弊”的批评李丽琴导言“文章之弊”在宋代成为一个问题。
1一直以来,学界论及宋儒对“文弊”的讨论,或以“文艺排斥”定论,2或以“学士文人歧为文哲二途”为由,3对宋儒的“文弊”问题的讨论予以批评和否定。
4论及“文弊”问题的提出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理学家们从自己的哲学主张和理学倾向出发,5视文章为小伎,并由此否定了文学的社会作用与自身价值。
6但是,我们发现,即以朱熹而言,其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同时于文学有三大著作:《诗集传》、《韩文考异》和《楚辞集注》,又有千余首诗、十多首词行世,其间还不乏花间词手笔。
这样,仅以文哲分途解释宋儒的“文艺排斥论”,显然不够周全。
钱穆论及朱熹的《楚辞集注》时曾特意指出:“朱子一生最后绝笔,实为其修楚辞一段,此则后人少所述及,尤当大书特书,标而出之,以释后人群认为理学家则必轻文学之积疑。
”7那么,对于宋儒“文章之弊”的批评缘由,当作怎样的理解呢?我们注意到,宋儒所谓“作文害道”论的提出,8其关注点实在于“文”与“道”的关系问题。
程颐明言: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
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
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
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
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
9在程颐看来,“训诂之学”、“文章之学”与“儒者之学”是有分界的,“欲趋道,舍儒者1“文弊”在宋元时代成为一个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参查洪德《宋元人对理学文弊的批判和理学文学观的演变》,《殷都学刊》1(2004):65—73。
2周予同著:《朱熹》,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第4页。
3周予同著:《朱熹》,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第4页。
4按:郭绍虞、王运熙、顾易生、成复旺、张少康等先生的诸本批评史著作均持此见。
详参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81页;成复旺等著:《中国文学理论史》(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281—282页,第340页,第411页等;王运熙、顾易生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0页;张少康、刘三富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2—38页等。
5按:对此,学界常以“道学文艺”指称。
参王哲平《朱熹文学思想论略》,《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31. 3(2007):102;何寄澎《朱子的文论》,《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3)1215。
6按: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有学者已对这一问题作了全新的阐释。
如韩经太在其《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就理学家的「作文害道」作了崭新的阐释。
他指出, 「作为理学家而提出的‘作文害道’之论,与其说它反映了道学先生不了解文学价值(文章价值)的偏执,不如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文学主体意识的文化品格问题,此亦即上文提到的人文关怀精神问题。
」参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北京:中华书局,1997)47;莫砺锋在其《朱熹文学研究》一书中也肯定了朱熹在宋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参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4。
7钱穆著:《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04页。
8按:《二程语录》载程颐之答问云:问:作文害道否? 曰:害也。
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
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
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
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
”此诗甚好。
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
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见于[宋]程颐、程颢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9页。
)9[宋]程颐、程颢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7页。
之学不可”;而“文章”,已与“训诂”和“异端”一起,成为学者“趋于道”的障碍。
这里所谓“训诂”和“异端”,实乃经学内部释经方法和经意理解的方面。
宋初的经学诠释,沿袭的是汉唐的注疏训诂传统。
作为已经写定的文本范例,“经”似乎为既定的文字文化提供了强健的稳定性。
但是,在佛教盛行、文庙冷落的处境中,宋代经学不再能凭借其以往的理解和诠释方式向前发展。
宋儒荡弃师法家法,抛开传注,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通过对元典的重新阐释,以不同于汉唐经师的诠释方式去理解它们,穿越对这些经典文本的前理解和既定期待,发现其中的“它性”,尝试与现时的生命存在作直接的思维性沟通,开始了经学诠释的“新变”。
在诠释学的意义上,这一“新变”更意味着宋儒的性理之学对儒家形上智慧的复活,使儒家的仁义之道真正在本根深处与佛、老之学有所区别,而儒士也得以在精神最深处拥有真正能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据,即此完成儒学终极关切的构建使命。
在此,当我们在经学诠释的视域中思考宋儒的“文弊”观念时,我们发现,宋儒对所谓“文弊”的批评,不过是其经学诠释原则在文学观念上的一种反映而已。
宋儒依经明理,要求“格物穷理”,“精察其理之所自来”,其所强调的,是精察事物不可移易之定分,其所要求的,是对仁义道德之为儒士的终极关切的终极原因的探讨。
这是得“意”(significance)而不是得“义”(meaning)的问题。
1以朱熹而言,“圣人言语”所发明的这个“道理”就是“文意”;而正是这一“意”,“吾身也在里面,万物亦在里面,天地亦在里面”,“通同只是一个物事”——“理”!这是“得意”!这是诠释主体对所有那些深蕴于写定的“圣人言语”中的精神的内在理会!在这一过程中,诠释主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以一种更高的方式在自身中把握了“圣人言语”所发明的那个道理。
只有在诠释主体对所予以诠释的经学文本完成了历史性的自我渗透,实现了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之后,经学诠释学的使命才最终得以成就。
这里所谓之“文”,是针对“文”作为“道”之“显显者”的意义而言的。
2“道”、“经”、“理”等词语在此与儒士的终极关切相连、成为人和万物存在的终极基础,即已获得了超出其标志意义的含义,成为一种象征。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终极的儒家信仰的表述。
儒士作为一个群体,将自己的生命命定于“经”。
“经”作为“道”之“显显者”,其本身介入了“道”的神圣性。
但“经”本身不是“道”,那个超越一切的东西超越了“道”的每一种象征,“显1按:朱熹对“文义”与“文意”的理解有明确的区分。
《语类》三十六载:“因说子在川上章,问曰:今不知吾之心与天地之化是两个物事,是一个物事,公且思量。
良久乃曰,今诸公读书,只是去理会得文义,更不去理会得意。
圣人言语,只是发明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吾身也在里面,万物亦在里面,天地亦在里面,通同只是一个物事,无障蔽,无遮碍。
吾之心,即天地之心。
圣人即川之流,便见得也是此理,无往而非极致。
”(详参朱傑人等编:《朱子全书•朱子语类》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57页。
)2按:这是朱熹与弟子讨论程颐所谓“与道为体”的论题时提出的观念。
道本无体,但借着“物事”,可以“盛载那道出来”,但“物事”并不是本然的道之本体,其仅仅作为“显显者”,是道之本体的显现者。
(详参朱傑人等编《朱子全书·朱子语类》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54—1355页。
)显者”之得以显现的根据乃在于“道”本身。
这里隐伏着一种“模棱两可”的危险。
“经”,作为一种儒家信仰的象征,既具创造性,同时又是毁灭性的。
当“经”作为“道”之“显显者”出场,浸润万民,文以化成,儒士据以实现“己立立人”的理想目标,儒士的意义和价值世界得以在生活实践中彰显,儒士得以安然居住。
可是,“经”一旦丧失其终极关切的意义而沦为儒士的学术对象,或者更严重的是,沦为追名逐利的途径和工具,“经”仅仅是经,那么,这时的经就面临“恶魔化”的危险,经学信仰沦为“偶像崇拜”。
另一方面,当“经”仅仅是“经”时,“经”就作为一种客体或对象被转化为一种“神”。
这样一来,“经”便被符号化为一种终极,而真正蕴涵于“经”中的“道”的终极关切意义则消失了。
实际上,这意味着“实在本身的基础层次”的消失。
德国神学家蒂里希以为,“实在中的这个维度是所有其他维度和深度的基础,因此,它不是跟其他层次并列的层次,而是基本的层次,是其他所有层次的根底,是存在本身的层次,或者说是存在之终极力量。
”1失却了“道”的根底,“经”在其自身中变为终极。
“经”被等同于道本身而成了偶像,儒士对于“经”的信仰沦为“偶像崇拜”。
神圣的经书,当它们被推向道本身所有的无条件性和终极性时,就变成了恶魔。
此时此刻,那种为“文”所表征的终极不再是“道”,“经”(“文”)不再向我们传达它们起初传达和它们被创造出来用以传达的东西。
儒士无以安身立命!也就是在这里,产生了“文弊”作为一个问题的焦虑。
概而言之,宋儒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文章之弊”的问题予以批评。
一、文士“作文害道”:“文”之对象化宋儒对“文章之弊”所予以批评的较为极端的例子,可以程颐对人生“三不幸”的界定为证:人有三不幸:年少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势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2程颐将“有高才能文章”作为人生第三大“不幸”,明显表露出对“能文之士”的贬斥与讽刺。
此外,程颐以为,“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
”3程颐在此对“文士”的贬斥,以及将“知道者”与“文士”、“讲师”相区别,正是虑及“文士”“专务章句”、为文而文的对象化倾向。
1保罗·蒂里希:《文化神学》(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New Y 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p.59.)2[宋]程颐、程颢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43页。
3[宋]程颐、程颢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5页。
程颐以为,古之学者,因孔氏门人的系统传授,“由经以识义理”是可以做到的;而今之学者,在学统中断、道统不继的状况下,“都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
”1这是一切学术的绝对基设,否则,任何方式的“训诂”和“希古”,只能是“文章则华靡其词,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已。
经术则解释辞训,较先儒短长,立异说以为己工而已。
” 2所以,程颐以为,没有“识义理”的前提,学者就不具备通达圣人之道的可能,至多“只是说道”而“不知道”,不可能成为“知道者”。
与此相应的是,由于“不知道”,一方面,文士的文章之学仅只“悦人耳目”而已;另一方面,文士的“专务章句”、为文而文,实等同于玩物丧志,使他们从根本上丧失了“知道”的可能性前提,“文章之学”只能成为与释老“异端”一样的“害道”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