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医从文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是什么_鲁迅弃医从文的理由是什么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是什么_鲁迅弃医从文的理由是什么很多成功人士都转过专业,有些人甚至会退学。
鲁迅先生就曾经弃医从文,最后成为了著名的作家。
下面店铺给大家分析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希望能帮到大家。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1904年9月,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在这里,他遇到了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
一年半后,鲁迅退学,离开仙台,并最终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鲁迅为什么会弃医从文?鲁迅在散文《藤野先生》中写道:“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全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此后回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这一段话历来被用来解释鲁迅最终为什么会弃医从文。
鲁迅自己也在后来说过,他从那时认识到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精神的强健比身体的强健更重要,因为“一个精神匮乏的民族,无论他的身体有多么强壮,也不过是被砍头的对象和麻木的看客而已。
”但是且慢,中国的贫弱,中国人的被羞辱、被残杀,为什么没有激起青年鲁迅奋发向上,拼命要学好医学的激情?难道拿笔的就一定比拿手术刀的更爱国吗?肉体都消失了,精神又从何强健?我们不妨再从别的方面,寻找一下促成鲁迅在人生的重大的转折关口,做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的原因。
首先学医不是鲁迅最早的选择。
最初鲁迅打算上的是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专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弘文学院负责升学指导的老师就劝鲁迅改学医学,说,日本医学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也不逊色,而且医学比工学、农学的学校数量多,接收留学生没有限制,入学也比较容易。
可能是在好歹先上学的权宜之计的心理下,鲁迅来到了仙台医专。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作文是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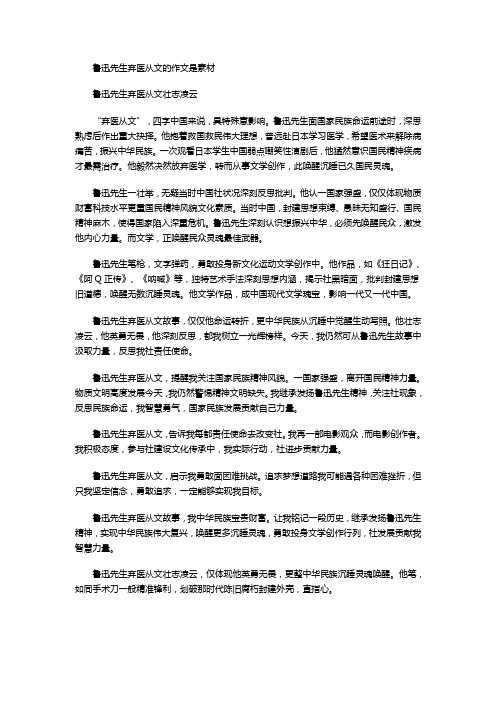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作文是素材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壮志凌云“弃医从文”,四字中国来说,具特殊意影响。
鲁迅先生面国家民族命运前途时,深思熟虑后作出重大抉择。
他抱着救国救民伟大理想,曾远赴日本学习医学,希望医术来解除病痛苦,振兴中华民族。
一次观看日本学生中国弱点嘲笑性演剧后,他猛然意识国民精神疾病才最需治疗。
他毅然决然放弃医学,转而从事文学创作,此唤醒沉睡已久国民灵魂。
鲁迅先生一壮举,无疑当时中国社状况深刻反思批判。
他认一国家强盛,仅仅体现物质财富科技水平更重国民精神风貌文化素质。
当时中国,封建思想束缚、愚昧无知盛行、国民精神麻木,使得国家陷入深重危机。
鲁迅先生深刻认识想振兴中华,必须先唤醒民众,激发他内心力量。
而文学,正唤醒民众灵魂最佳武器。
鲁迅先生笔枪,文字弹药,勇敢投身新文化运动文学创作中。
他作品,如《狂日记》、《阿Q正传》、《呐喊》等,独特艺术手法深刻思想内涵,揭示社黑暗面,批判封建思想旧道德,唤醒无数沉睡灵魂。
他文学作品,成中国现代文学瑰宝,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故事,仅仅他命运转折,更中华民族从沉睡中觉醒生动写照。
他壮志凌云,他英勇无畏,他深刻反思,都我树立一光辉榜样。
今天,我仍然可从鲁迅先生故事中汲取力量,反思我社责任使命。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提醒我关注国家民族精神风貌。
一国家强盛,离开国民精神力量。
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今天,我仍然警惕精神文明缺失。
我继承发扬鲁迅先生精神,关注社现象,反思民族命运,我智慧勇气,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告诉我每都责任使命去改变社。
我再一部电影观众,而电影创作者。
我积极态度,参与社建设文化传承中,我实际行动,社进步贡献力量。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启示我勇敢面困难挑战。
追求梦想道路我可能遇各种困难挫折,但只我坚定信念,勇敢追求,一定能够实现我目标。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故事,我中华民族宝贵财富。
让我铭记一段历史,继承发扬鲁迅先生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唤醒更多沉睡灵魂,勇敢投身文学创作行列,社发展贡献我智慧力量。
鲁迅选择弃医从文作文

鲁迅选择弃医从文作文
《鲁迅为啥弃医从文》
嘿,咱今天就来讲讲鲁迅为啥弃医从文这档子事儿。
你们知道不,鲁迅当年本来是学医的呢。
他呀,一开始是想着能当个好医生,救治好多好多人。
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有一天,鲁迅正在教室里上课呢,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吵闹。
他好奇地跑出去一看,原来是一群中国人在围观一个被日军抓住的中国人要被砍头。
那场面,真叫一个血腥啊!可气的是,那些围观的中国人脸上没有一点儿愤怒或者悲伤,反而是一脸的麻木,就好像在看一场无关紧要的热闹似的。
鲁迅当时就傻眼了,他心里那个难受啊,就别提了。
他就在想啊,这些人身体是没啥大毛病,可这精神上简直是病入膏肓啊!光靠医术能救得了他们吗?显然不能啊!
就这么着,鲁迅一拍脑袋,决定不干医生啦,他要拿起笔,用文字去唤醒这些麻木的人们。
他要像一个战士一样,用文章去战斗,去改变这个社会。
你看看,就这么一件事儿,让鲁迅做出了这么重大的决定。
从那以后啊,他就开始疯狂地写作,写出了好多好多厉害的文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哎呀,想想还真是感慨啊,要是没有这件事儿,说不定我们就看不到那些精彩的文章了呢。
鲁迅这一弃医从文,可真是太对啦!。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给你的启示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给你的启示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给你的启示1. 引言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一生经历和文学成就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其中,他从医生转型成为文学家的经历,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 从医生到文学家的转变鲁迅先生原本是一名医生,但在他年轻时就已经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了西方文学和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产生了深刻的反思。
他选择放弃医生的身份,全心投入文学创作之中,并成为了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3. 对个人的启示这一段经历给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鲁迅先生敢于放弃稳定的职业,选择追求内心的热爱。
这让我们意识到,生活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真正喜欢和热爱的事业。
他也告诉我们,追求梦想需要付出艰辛和代价。
他的文学创作中,每一部作品都蕴含了他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和对人性的直面。
这启示我们,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学家,需要对社会、人性有着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思考。
4. 对社会的启示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不仅在文学上具有重要意义,更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文学作品探讨了社会现实、人性弱点和道德困境。
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和人性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对这些问题的理性思考和探讨。
这其中的内容,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和学习。
5. 个人观点和总结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梦想时,我们需要有勇气和决心,同时也要有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思考。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扎实。
让我们一起铭记鲁迅先生的这段经历和他的文学成就,去思考他对我们每个人和整个社会所留下的重要启示。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经历给每个人都带来了深刻的启示,为我们树立了追求梦想和探索真理的榜样。
希望每个人都能从他的经历中汲取力量,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追求自己真正的梦想。
藤野先生中作者弃医从文的原因

藤野先生中作者弃医从文的原因作者弃医从文的原因是:要拯救国民的精神。
作者通过怀念藤野先生,赞扬藤野先生没有民族偏见的伟大性格和正直、热忱、高尚的品质,回顾了自己在日本求学时期探索救国道路和思想转变的过程。
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毅然地放弃了跟随生平最敬爱的老师一一藤野先生学习医学,摈弃了科学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改为从事文艺运动以拯救国民的精神为己任。
创作背景:
1902年4月,鲁迅22岁,鲁迅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理想,去留学,在东京的弘文学院补习日文。
1904年9月,转赴仙台,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毕业于爱知县立医学校的藤野先生以自己的高尚品质给鲁迅以极大的影响。
弃医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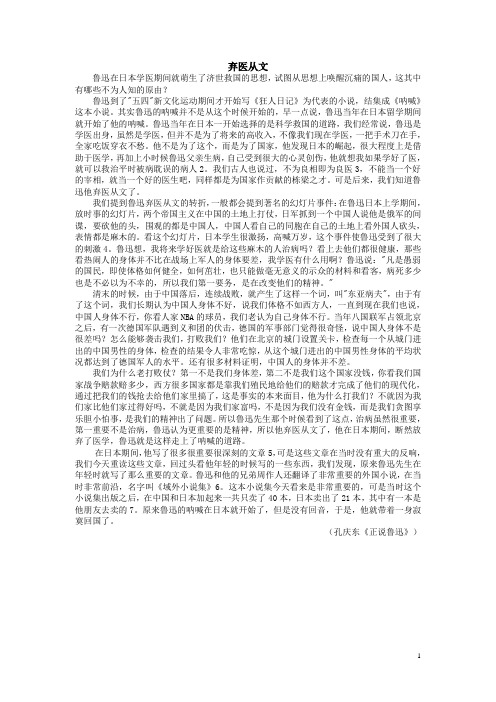
弃医从文鲁迅在日本学医期间就萌生了济世救国的思想,试图从思想上唤醒沉痛的国人,这其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原由?鲁迅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才开始写《狂人日记》为代表的小说,结集成《呐喊》这本小说。
其实鲁迅的呐喊并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早一点说,鲁迅当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了他的呐喊。
鲁迅当年在日本一开始选择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我们经常说,鲁迅是学医出身,虽然是学医,但并不是为了将来的高收入,不像我们现在学医,一把手术刀在手,全家吃饭穿衣不愁。
他不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国家,他发现日本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医学,再加上小时候鲁迅父亲生病,自己受到很大的心灵创伤,他就想我如果学好了医,就可以救治平时被病耽误的病人2。
我们古人也说过,不为良相即为良医3,不能当一个好的宰相,就当一个好的医生吧,同样都是为国家作贡献的栋梁之才。
可是后来,我们知道鲁迅他弃医从文了。
我们提到鲁迅弃医从文的转折,一般都会提到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在鲁迅日本上学期间,放时事的幻灯片,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日军抓到一个中国人说他是俄军的间谍,要砍他的头,围观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看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看外国人砍头,表情都是麻木的。
看这个幻灯片,日本学生很激扬,高喊万岁,这个事件使鲁迅受到了很大的刺激4。
鲁迅想,我将来学好医就是给这些麻木的人治病吗?看上去他们都很健康,那些看热闹人的身体并不比在战场上军人的身体要差,我学医有什么用啊?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第一要务,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清末的时候,由于中国落后,连续战败,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词,叫"东亚病夫",由于有了这个词,我们长期认为中国人身体不好,说我们体格不如西方人,一直到现在我们也说,中国人身体不行,你看人家NBA的球员,我们老认为自己身体不行。
弃医从文鲁迅作文

弃医从文鲁迅作文
嘿,朋友!今天我想跟你聊聊鲁迅先生那让人惊叹的弃医从文之路。
记得那时候,鲁迅先生远渡重洋,怀着治病救人的理想,一心扎进了医学的世界里。
在日本的那些日子,他可真是拼了命地学习。
有一回,鲁迅先生正在课堂上认真地听着老师讲解人体结构,那专注的劲儿,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了他和那些医学知识。
突然,老师放了一段关于中国人被日军砍头的影片。
周围的日本同学那冷漠的眼神,还有他们刺耳的嘲笑,像针一样扎在鲁迅先生的心上。
“这中国人,就该杀!”一个日本同学阴阳怪气地说道。
“哼,他们就是东亚病夫!”另一个同学跟着附和。
鲁迅先生的拳头紧紧握住,愤怒在他的眼中燃烧。
他望着屏幕上那些麻木不仁的同胞,心中一阵刺痛。
“我们学医,真的能救得了这样的国民吗?”鲁迅先生喃喃自语。
从那以后,鲁迅先生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不再只是埋头于医学书籍,而是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他常常和好友许寿裳一起探讨,怎样才能唤醒沉睡的国人。
“寿裳啊,我觉得光是治病救人的身体还不够,得唤醒他们的灵魂才行!”鲁迅先生皱着眉头说道。
“是啊,可这该怎么做呢?”许寿裳一脸疑惑。
“或许,文字能成为我们的武器!”鲁迅先生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就这样,鲁迅先生毅然决然地放下了手术刀,拿起了笔。
他要用文字去刺痛国人的麻木,去唤醒他们的良知。
如今回想起来,鲁迅先生的这一抉择,真的是太伟大啦!他用他的笔,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力量。
朋友,这就是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故事,是不是很让人敬佩呀?。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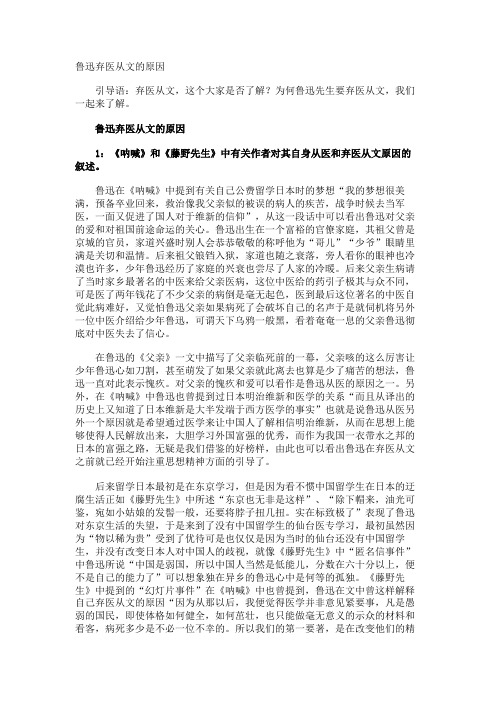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引导语:弃医从文,这个大家是否了解?为何鲁迅先生要弃医从文,我们一起来了解。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1:《呐喊》和《藤野先生》中有关作者对其自身从医和弃医从文原因的叙述。
鲁迅在《呐喊》中提到有关自己公费留学日本时的梦想“我的梦想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鲁迅对父亲的爱和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关心。
鲁迅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官僚家庭,其祖父曾是京城的官员,家道兴盛时别人会恭恭敬敬的称呼他为“哥儿”“少爷”眼睛里满是关切和温情。
后来祖父锒铛入狱,家道也随之衰落,旁人看你的眼神也冷漠也许多,少年鲁迅经历了家庭的兴衰也尝尽了人家的冷暖。
后来父亲生病请了当时家乡最著名的中医来给父亲医病,这位中医给的药引子极其与众不同,可是医了两年钱花了不少父亲的病倒是毫无起色,医到最后这位著名的中医自觉此病难好,又觉怕鲁迅父亲如果病死了会破坏自己的名声于是就伺机将另外一位中医介绍给少年鲁迅,可谓天下乌鸦一般黑,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鲁迅彻底对中医失去了信心。
在鲁迅的《父亲》一文中描写了父亲临死前的一幕,父亲咳的这么厉害让少年鲁迅心如刀割,甚至萌发了如果父亲就此离去也算是少了痛苦的想法,鲁迅一直对此表示愧疚。
对父亲的愧疚和爱可以看作是鲁迅从医的原因之一。
另外,在《呐喊》中鲁迅也曾提到过日本明治维新和医学的关系“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也就是说鲁迅从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希望通过医学来让中国人了解相信明治维新,从而在思想上能够使得人民解放出来,大胆学习外国富强的优秀,而作为我国一衣带水之邦的日本的富强之路,无疑是我们借鉴的好榜样,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在弃医从文之前就已经开始注重思想精神方面的引导了。
后来留学日本最初是在东京学习,但是因为看不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迂腐生活正如《藤野先生》中所述“东京也无非是这样”、“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
弃医从文的十大名人

弃医从文的十大名人1、孙中山。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小小的日本,竟打败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堂堂中国。
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空前苛刻的“中日马关条约”,中国不仅要付出巨额赔款,还要割让大片领土。
这一切都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
他下定决心,放弃行医,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救国救民的大业。
2、毛姆。
英国小说家、戏剧家,其作品《月亮与六便士》在国内备受欢迎。
他的作品常以冷静、客观乃至挑剔的态度审视人生,基调超然,充满讽刺和怜悯意味。
3、柯南道尔。
如果说柯南道尔这个名字你觉得陌生,那么福尔摩斯这个名字你不可能不知道。
柯南·道尔毕业于爱丁堡医科大学,由于对医务并不热衷,于1891年弃医从文,专门从事侦探小说写作,并成功塑造了福尔摩斯这一家喻户晓的人物。
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是柯南道尔笔下最成功也是侦探小说史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柯南道尔也被称为“世界侦探小说之父”,将侦探小说推向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4、知念实希人。
提到知念实希人这个名字,很多国内读者可能还不是十分熟悉。
他是日本新生代推理作家中的翘楚,2012年获得第四届福山推理文学新人奖,已经有几部作品的销量达到了百万级别。
知念实希人——左手做手术,右手写小说。
5、冰心。
现代著名女作家,她原是医科预备班的学生,后因身体不好,老师劝她改行,她弃医从文后,为现当代文坛留下了《给小读者》、《小桔灯》等诸篇充满爱心的美文。
6、渡边淳一。
1933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札幌医科大学毕业,医学博士。
毕业后留校任整形外科讲师,后弃医从文,著作有《失乐园》。
7、布尔加科夫。
前苏联作家。
1916年基辅大学医疗系毕业后被派往农村医院,后转至县城,在维亚济马市迎接了十月革命。
1918年回基辅开业行医,1920年弃医从文,开始写作生涯,著作有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1966)。
直到逝世,其他著作有剧本《莫里哀》(1936)、传记体小说《莫里哀》(1962)等。
鲁迅弃医从文选择之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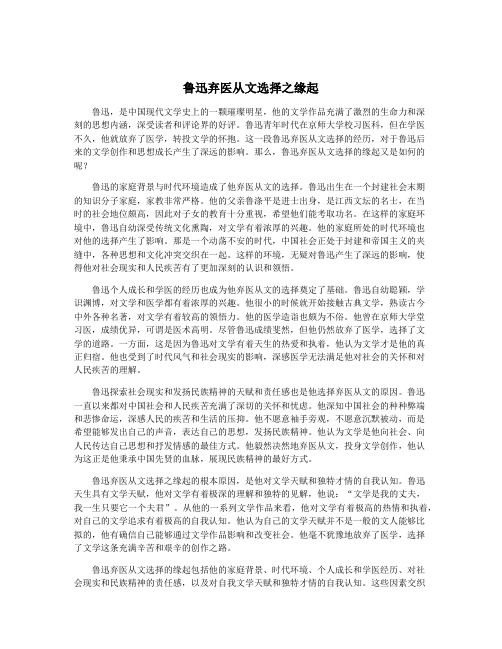
鲁迅弃医从文选择之缘起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他的文学作品充满了激烈的生命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深受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
鲁迅青年时代在京师大学校习医科,但在学医不久,他就放弃了医学,转投文学的怀抱。
这一段鲁迅弃医从文选择的经历,对于鲁迅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鲁迅弃医从文选择的缘起又是如何的呢?鲁迅的家庭背景与时代环境造成了他弃医从文的选择。
鲁迅出生在一个封建社会末期的知识分子家庭,家教非常严格。
他的父亲鲁涤平是进士出身,是江西文坛的名士,在当时的社会地位颇高,因此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希望他们能考取功名。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鲁迅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的家庭所处的时代环境也对他的选择产生了影响。
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封建和帝国主义的夹缝中,各种思想和文化冲突交织在一起。
这样的环境,无疑对鲁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他对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领悟。
鲁迅个人成长和学医的经历也成为他弃医从文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鲁迅自幼聪颖,学识渊博,对文学和医学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古典文学,熟读古今中外各种名著,对文学有着较高的领悟力。
他的医学造诣也颇为不俗。
他曾在京师大学堂习医,成绩优异,可谓是医术高明。
尽管鲁迅成绩斐然,但他仍然放弃了医学,选择了文学的道路。
一方面,这是因为鲁迅对文学有着天生的热爱和执着,他认为文学才是他的真正归宿。
他也受到了时代风气和社会现实的影响,深感医学无法满足他对社会的关怀和对人民疾苦的理解。
鲁迅探索社会现实和发扬民族精神的天赋和责任感也是他选择弃医从文的原因。
鲁迅一直以来都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疾苦充满了深切的关怀和忧虑。
他深知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悲惨命运,深感人民的疾苦和生活的压抑。
他不愿意袖手旁观,不愿意沉默被动,而是希望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思想,发扬民族精神。
他认为文学是他向社会、向人民传达自己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最佳方式。
鲁迅弃医从文选择之缘起

鲁迅弃医从文选择之缘起【摘要】鲁迅弃医从文选择之缘起,是因为他对医学的失望和对文学的热爱。
背景是在当时医学水平低下,鲁迅在医学方面遇到种种困难,决定放弃医生的身份。
之后,他开始了从医到文学的转变,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鲁迅选择从医到文学的动机是为了寻找出路和表达心声。
这一选择对他的影响深远,使他在文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
这个选择的意义在于展示了一个人在困境中的坚持和对理想的追求。
鲁迅弃医从文选择之缘起启示了我们要追随内心的信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追求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鲁迅, 弃医从文选择, 缘起, 背景, 医学, 文学, 动机, 影响, 意义, 启示, 历史价值, 时代意义1. 引言1.1 鲁迅弃医从文选择之缘起鲁迅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危机深重。
他目睹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残酷,感受到了人民的疾苦与无助。
他深知医治一己之病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决定通过文学作品来唤醒民众的觉悟,传播进步思想,推动社会改革。
从医到文学的转变并非易事,鲁迅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挫折。
他深信文学的力量,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
他的文学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现实的丑陋和人性的扭曲,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和讨论。
鲁迅弃医从文选择之缘起,不仅影响了他自己的一生,也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坚持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正义立场,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这一选择的背后蕴含着鲁迅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也反映了他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刻关怀和思考。
2. 正文2.1 鲁迅弃医从文选择之缘起的背景鲁迅弃医从文选择之缘起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其早年的医学学习经历。
鲁迅生于一家医学世家,父亲是著名的医生。
鲁迅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医学教育,也曾在京师大学堂学医。
鲁迅对医学并不感兴趣,更倾向于文学创作。
他在医学学习中并未取得出色的成绩,因为他更多时间都花在了文学领域的探索和创作上。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对中国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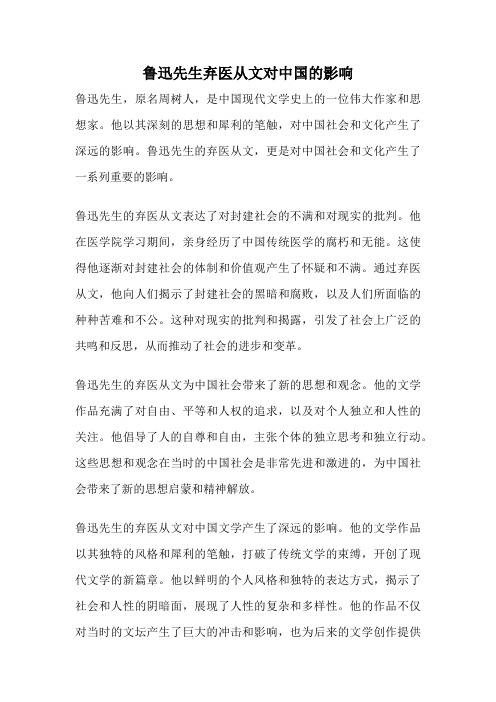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对中国的影响鲁迅先生,原名周树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作家和思想家。
他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犀利的笔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更是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影响。
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和对现实的批判。
他在医学院学习期间,亲身经历了中国传统医学的腐朽和无能。
这使得他逐渐对封建社会的体制和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通过弃医从文,他向人们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以及人们所面临的种种苦难和不公。
这种对现实的批判和揭露,引发了社会上广泛的共鸣和反思,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思想和观念。
他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自由、平等和人权的追求,以及对个人独立和人性的关注。
他倡导了人的自尊和自由,主张个体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
这些思想和观念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非常先进和激进的,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
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犀利的笔触,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束缚,开创了现代文学的新篇章。
他以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表达方式,揭示了社会和人性的阴暗面,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性。
他的作品不仅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也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对中国的影响还体现在他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关怀和呼唤上。
他在弃医从文中多次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忧虑和担忧,呼吁人们要关注民族困境,振兴中华文化。
他认为,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的崛起是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基础,因此他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号召人们要从文化上振兴民族,实现国家的崛起和富强。
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通过自己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引发了社会的反思和变革;他倡导了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思想,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他的文学作品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束缚,开创了现代文学的新篇章;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怀和呼唤,引发了人们对民族困境的关注和振兴中华文化的呼唤。
怎样认识鲁迅弃医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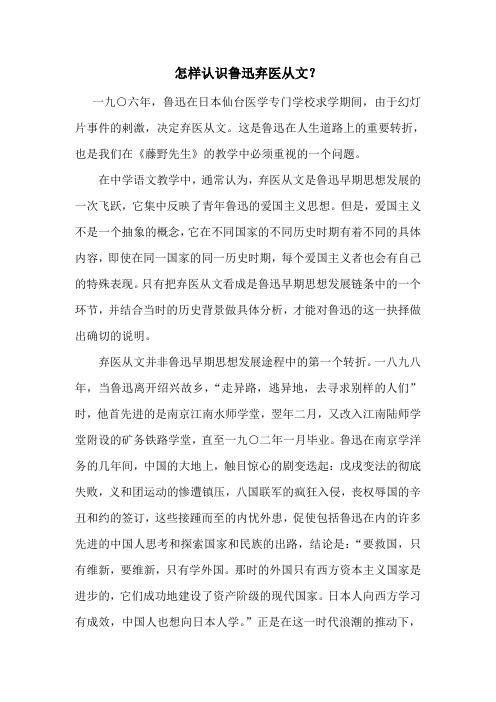
怎样认识鲁迅弃医从文?一九○六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期间,由于幻灯片事件的剌激,决定弃医从文。
这是鲁迅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也是我们在《藤野先生》的教学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通常认为,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它集中反映了青年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
但是,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即使在同一国家的同一历史时期,每个爱国主义者也会有自己的特殊表现。
只有把弃医从文看成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做具体分析,才能对鲁迅的这一抉择做出确切的说明。
弃医从文并非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途程中的第一个转折。
一八九八年,当鲁迅离开绍兴故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时,他首先进的是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二月,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直至一九○二年一月毕业。
鲁迅在南京学洋务的几年间,中国的大地上,触目惊心的剧变迭起: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义和团运动的惨遭镇压,八国联军的疯狂入侵,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的签订,这些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促使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结论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
”正是在这一时代浪潮的推动下,鲁迅于一九○二年四月到了日本。
当他知道日本的维新运动“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后,即决定弃矿从医。
尽管鲁迅此举的动机不无幼稚之处,但他做出这一抉择的出发点是爱国主义,则是确定无疑的。
这种爱国主义的实质,是“对于维新的信仰”,它是当时的维新浪潮冲击青年鲁迅所激起的一朵浪花。
给新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之前,改良运动的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除旧布新”、“保种自强”,代表了那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
弃医从文的事件概括

鲁迅早年学医是为了想单纯地通过提高国民的身体素zhi质从而使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后来,鲁迅先生发现一个国家想要强大起来,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觉悟,否则就算再强壮,也只有落得像牛一样被奴役的悲惨命运,所以,鲁迅先生才弃医从文,为的就是从思想上解放中国人。
具体经过:日本留学期间,鲁迅与其老师藤野严九郎的朝夕相处,对其走上文坛产生过重要影响。
藤野毕业于爱知县立医学校(今名古屋大学),在鲁迅入学前的两个月他才升格为教授。
藤野说话时有家乡福井县的口音,鲁迅听着不习惯,却觉得亲切。
决心弃医从文的鲁迅最后向藤野提出了退学申请。
《藤野先生》就是鲁迅对仙台时期生活的回忆。
后来,藤野才知道曾经的中国留学生周树人成为了作家鲁迅,并将自己的故事写入了散文。
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

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鲁迅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评论家、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人。
为什么鲁迅要弃医从文呢?以下就是店铺做的整理,希望对你们有用。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汪先恩):适逢世界读书日,又重读了一遍《阿Q正传》,愈觉自己多少沾有阿Q式毛病,也多少潜藏着抢“宣德炉”和“秀才娘子宁式床”的革命心态,好像每个社会都有抱怨“枪毙不如杀头好看”的芸芸看客,更有阿Q式的替死鬼,社会浑浊时多一点,清明时少一点。
文短而意深,可谓不朽之作。
细读鲁迅的作品,可以揣摩这位留日前辈为何弃医从文。
有所顾忌的时候,要么匿名,要么假名,要么改名。
鲁迅喜欢改名和用假名,本名周樟寿,18岁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的笔名“鲁迅”盖过所有真假名。
他赶上了第一次留日潮。
1894年甲午战败,天朝被再次警醒,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向西方学习,以夷为师。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主张向引进西方制度成功的日本派遣留学生,理由是省钱省力。
1896年清政府选派戢冀翚、唐宝锷等13人赴日留学,开启了留日先河,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筑波大学前身)校长嘉纳治五郎培养,为此他特为清国学生设立预科学校,即相当于高中的三年制弘文学院(始称亦乐书院)。
浙江省的周树人经过严格选考,1902年2月被公派到弘文学院留学。
1902年夏留日学生为614人,到1904年增到1454人,其中有不少“速成班”的学生,速成班的学生三个月或半年就修业,有些是走过场,所以鲁迅非常看不起他们,玩不到一块。
1904年夏季,鲁迅毕业,面临升学,费用是个大问题。
由于四年制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现东北大学医学部)免除考试又免除学费,很有吸引力,于是他于1904年9月到仙台,呆了一年半,学了些解剖学等基础课程,1906年3月辍学,离开仙台。
关于离开仙台的原因,他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披露了两点:一是从幻灯中看到日俄战争中华人的麻木不仁,二是受到同学歧视。
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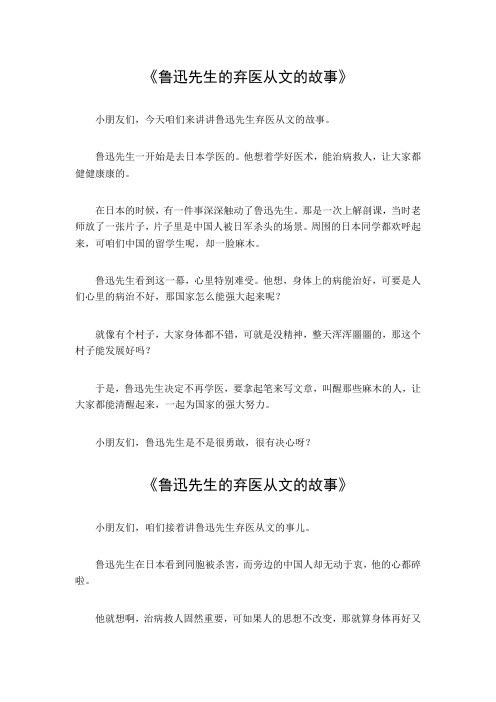
《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的故事》小朋友们,今天咱们来讲讲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故事。
鲁迅先生一开始是去日本学医的。
他想着学好医术,能治病救人,让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件事深深触动了鲁迅先生。
那是一次上解剖课,当时老师放了一张片子,片子里是中国人被日军杀头的场景。
周围的日本同学都欢呼起来,可咱们中国的留学生呢,却一脸麻木。
鲁迅先生看到这一幕,心里特别难受。
他想,身体上的病能治好,可要是人们心里的病治不好,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就像有个村子,大家身体都不错,可就是没精神,整天浑浑噩噩的,那这个村子能发展好吗?于是,鲁迅先生决定不再学医,要拿起笔来写文章,叫醒那些麻木的人,让大家都能清醒起来,一起为国家的强大努力。
小朋友们,鲁迅先生是不是很勇敢,很有决心呀?《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的故事》小朋友们,咱们接着讲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事儿。
鲁迅先生在日本看到同胞被杀害,而旁边的中国人却无动于衷,他的心都碎啦。
他就想啊,治病救人固然重要,可如果人的思想不改变,那就算身体再好又有啥用呢?比如说,一个人总是胆小怕事,不敢面对困难,就算身体没病,能做成大事吗?鲁迅先生觉得,要用文字的力量,像一把锤子一样,敲醒大家沉睡的心灵。
所以他果断地放弃了医学,开始写文章。
他写的文章就像一把把火炬,照亮了人们前进的道路。
小朋友们,咱们要向鲁迅先生学习哟!《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的故事》小朋友们,让我再给你们讲讲这个故事。
鲁迅先生当初满怀希望去学医,想着能救很多人的命。
可是那次看到的场景,让他明白,更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思想。
就好像一个房子,外表看着挺好,可里面的人都迷迷糊糊的,这房子能住得舒服吗?鲁迅先生决定用文字当武器,去战斗。
他写的文章,有的像警钟,让人警醒;有的像春风,给人温暖和希望。
小朋友们,鲁迅先生的故事是不是很激励人呀?。
鲁迅选择弃医从文作文

鲁迅选择弃医从文作文
《鲁迅为啥弃医从文》
嘿,你们知道不,鲁迅当年为啥放着好好的医不读,非要跑去搞文学呀!这可得从一件事儿说起。
那时候鲁迅在日本学医呢,成绩还不错哦。
有一天,他们在上一堂解剖课,那场面,啧啧,可真是有点吓人哩。
老师在上面认真地讲着,同学们也都聚精会神地听着。
突然,鲁迅看到旁边一个日本同学对着中国人的尸体标本露出了一种轻蔑的笑,嘴里还嘟囔着一些难听的话,大概就是说中国人怎么怎么不行之类的。
哎呀呀,这可把鲁迅给气坏了呀!他心里那个窝火呀,就想着,我们中国人身体生病了可以靠医术来治,可这思想上的病咋办呀!这时候他就开始琢磨了,光靠治病救人好像不行嘞,得从根本上改变大家的思想才行。
就是这么一件事儿,让鲁迅意识到,文字的力量也许比手术刀更强大。
他觉得自己要用笔杆子去敲醒那些麻木的国人,让他们觉醒,让他们知道要为国家的命运去抗争。
于是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学医,走上了从文的道路。
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却改变了鲁迅的人生轨迹呀。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不停地写呀写,用他那犀利的文字去批判社会的黑暗,去呼唤人们的觉醒。
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那个黑暗的时代。
到现在,我们提起鲁迅,还是会被他的精神所感动。
他当初的那个选择,真的太重要啦!这就是鲁迅为啥弃医从文的故事,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呀!。
鲁迅弃医学文作文200字

《鲁迅为啥弃医从文》篇一嘿,你们知道不,鲁迅当年为啥放着好好的医不读,非要跑去搞文学呀!这可得从一件事儿说起。
那时候鲁迅在日本学医呢,成绩还不错哦。
有一天,他们在上一堂解剖课,那场面,啧啧,可真是有点吓人哩。
老师在上面认真地讲着,同学们也都聚精会神地听着。
突然,鲁迅看到旁边一个日本同学对着中国人的尸体标本露出了一种轻蔑的笑,嘴里还嘟囔着一些难听的话,大概就是说中国人怎么怎么不行之类的。
哎呀呀,这可把鲁迅给气坏了呀!他心里那个窝火呀,就想着,我们中国人身体生病了可以靠医术来治,可这思想上的病咋办呀!这时候他就开始琢磨了,光靠治病救人好像不行嘞,得从根本上改变大家的思想才行。
就是这么一件事儿,让鲁迅意识到,文字的力量也许比手术刀更强大。
他觉得自己要用笔杆子去敲醒那些麻木的国人,让他们觉醒,让他们知道要为国家的命运去抗争。
于是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学医,走上了从文的道路。
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却改变了鲁迅的人生轨迹呀。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不停地写呀写,用他那犀利的文字去批判社会的黑暗,去呼唤人们的觉醒。
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那个黑暗的时代。
到现在,我们提起鲁迅,还是会被他的精神所感动。
他当初的那个选择,真的太重要啦!这就是鲁迅为啥弃医从文的故事,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呀!《鲁迅的选择》篇二嘿,咱今天就来讲讲鲁迅那弃医从文的事儿。
当年啊,鲁迅远渡日本去学医,想着学好了医术回来救治咱中国人的身体呢。
那时候的他呀,可真是一门心思都在医学上。
他每天认认真真地学习,就盼着能早点成为一个厉害的医生。
可是呢,有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有一次,他在课堂上看到了一张片子,上面是一个中国人被日军抓住砍头,而旁边一群中国人却麻木地看着,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这可把鲁迅给惊到了,他心里那个难受呀,就别提了。
他突然意识到,光治好身体有啥用呀,要是这精神上还是麻木的,那国家怎么能好起来呢?于是乎,鲁迅就一拍脑袋决定了:咱不弃医了,咱从文!他要用笔杆子来唤醒这些麻木的灵魂,让大家都醒醒,都起来抗争。
弃医从文的故事6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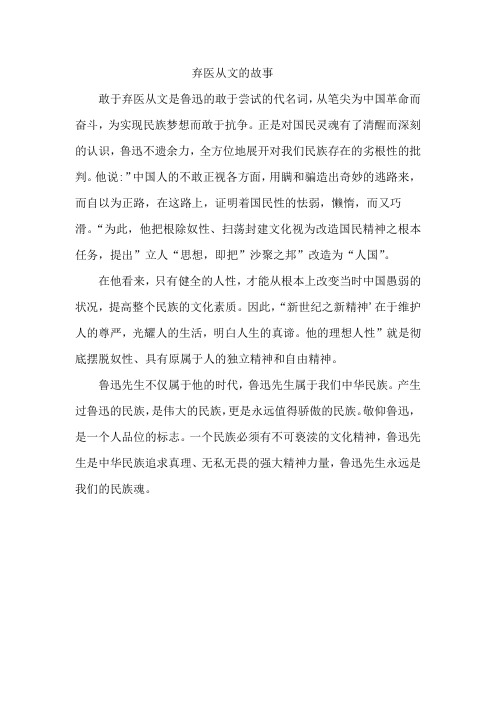
弃医从文的故事
敢于弃医从文是鲁迅的敢于尝试的代名词,从笔尖为中国革命而奋斗,为实现民族梦想而敢于抗争。
正是对国民灵魂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鲁迅不遗余力,全方位地展开对我们民族存在的劣根性的批判。
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为此,他把根除奴性、扫荡封建文化视为改造国民精神之根本任务,提出”立人“思想,即把”沙聚之邦”改造为“人国”。
在他看来,只有健全的人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中国愚弱的状况,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因此,“新世纪之新精神'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光耀人的生活,明白人生的真谛。
他的理想人性”就是彻底摆脱奴性、具有原属于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
鲁迅先生不仅属于他的时代,鲁迅先生属于我们中华民族。
产生过鲁迅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更是永远值得骄傲的民族。
敬仰鲁迅,是一个人品位的标志。
一个民族必须有不可亵渎的文化精神,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追求真理、无私无畏的强大精神力量,鲁迅先生永远是我们的民族魂。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弃医从文:鲁迅的言说策略□ 吕晓英 下面这段鲁迅的思想轨迹几乎家喻户晓:1905年,二十四岁的鲁迅在日本仙台的医学校里,看了中国人做看客又做刀下鬼的幻灯片,当鲁迅看到一名同胞即将被日本人斩首示众,而画面中“许多久违的中国人”竟表情麻木时,他猛然醒悟,“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于是,鲁迅毅然选择了退学,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承担起了呼唤民众的重任,最终成为伟大的文学家。
而在这次顿悟之前,他原本真是打算做医生的。
这便是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
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被几代人解读着,毫无异议。
正如周海婴先生所说的,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也把这个特别“革命化”了的鲁迅形象以知识普及的形式传播给了一代代中国人。
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鲁迅形象也还保留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特征。
这个“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体现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价值,而他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则被大大地简化了。
弃医从文发生在1905年,鲁迅第一次将其披露给公众是17年后的1922年底,在他给自己第一部小说所作的长篇序言《〈呐喊〉自序》中,即当鲁迅作为新文学作家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他第一次回顾他作为作家的成长史时。
《〈呐喊〉自序》无疑是鲁迅作为作家第一次回顾自己创作历程的文本。
在请名家写序或请朋友写序或自己写序之间作出选择,这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策略”,选择的结果已包含着对“序”的某种期待。
而且“自序”又显然是最能“随心所欲”地实现期待的。
《〈呐喊〉自序》作为鲁迅给自己第一部小说所作的长篇序言,作为一个极富经营性的文本一定蕴藏许多值得深究的“策略”。
1 鲁迅重提弃医从文是为了凸显自己是一个启蒙者的形象,为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再次回归启蒙立场,重新启动一直未能如愿的文化启蒙,重拾启蒙梦想而立此存照。
尽管,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弃医从文的说法在数十年来,被研究者引用不辍,目为定论,是最具权威性的,但是,坦率地说,将鲁迅弃医从文这一重大的人生抉择仅仅归因于这一“画片”,或称“电影”“幻灯片”的刺激,确实失之简单。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通过文学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是潜藏在鲁迅心底的一种长久的意识和一贯的观念。
考察鲁迅1922年以前的一些文化活动,足以证明鲁迅是有着启蒙情结的。
众所周知,早在1902年,鲁迅就已与许寿裳探讨了关于国民性的思考。
1903年6月,留学生“拒法”“拒俄”运动期间,为配合斗争,鲁迅在《浙江潮》第五期发表编译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飘飘大旗,荣光闪烁,于铄豪杰,鼓铸全身,诸君诸君,男儿死耳!”小说盛赞斯巴达人民的复仇精神,慷慨激昂,政治激情澎湃。
这是鲁迅第一次用这种寄情于文的独特的思想方式参与革命,反映了鲁迅开始有意识地用自己熟悉的文笔作武器进行战斗,并注重在思想意识上鼓舞士气,参与革命。
开始筹办《新生》杂志后,仅1907年,他就在留学生刊物《河南》上先后发表四篇长文:宣传进化的《人之历史》、强调科学改造社会的《科学史教篇》、鼓吹改造人心再造精神的《文化偏至论》和崇尚文学中的“斯巴达之魂”的《摩罗诗力说》,那时的鲁迅,激情飞溅,文气浩荡,寄意高远,神往生命之自由。
这同样证明他已开始有意识地用思想启蒙的方式进行战斗。
即使在鲁迅看上去似乎真的平静自处,“甘于虚无”的“沉默”阶段(1909-1917),我们仍能从鲁迅1912年至1917年的日记中看到他内心埋藏着对几乎所有国民(包括知识阶层本身)生存境状的强烈不满,显露着鲁迅内心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生命牵挂。
这个“沉默”中的人其实心怀着对于悲苦人间的某种难以割舍的情愫。
周建人说:鲁迅在归国初期,眼见陈腐古国、破败故家中,人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黑暗、残酷之事,内心震惊,但仍然尽自己的薄力想努力改变,而并不见效果时,则深为叹息。
“并且常对我说,不管压力多大,要顶得住;不管冤屈多深,要受得了,千万不能自暴自弃,要奋发和自爱。
”①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我们,对鲁迅来说,麻醉自己,放弃自己的真正追求、向往是一件艰难,而且极难以被他自己所真正认可的事情。
只要时机成熟,鲁迅终究要实施自我救赎,重归启蒙立场,再拾启蒙梦想的。
然而鲁迅是需要借力的,要在合力中才能显现出中坚的本色,而这一条件,需要到五四时期才有转机。
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护法”,中国社会都在同一个位置上打圈子,始终没有一个向前进的曙光,当时的志士们更多看重的似乎是政治制度,对于文化思想的变革并没有足够的意识。
要直到“新文化运动”,直到围绕着《新青年》的“新文化”集体形成以后才有改观。
鲁迅才真正找到了适合自己“呐喊”的场所。
当他感到启蒙时机成熟时,他便放下手头的古碑,开始摇旗呐喊。
所以,也就难怪那个时代,鲁迅写散文,写得很随意,很放松。
可是写小说非常紧张,每写一部又有非常强的用意。
他写小说就是为了救国,启蒙那些麻痹的人们,至此小说也就成了一个被夸大了的文学形式。
事实上,从他的小说创作初衷来看,鲁迅就更倾向于做一个思想家,而作为艺术家的意念显然要淡薄得多。
他后来回忆说,当他开始从事小说创作的时候,小说还不能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因而“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②就是说,他不是冲着做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梦想,而是怀着思想批判和社会改良的志向走上小说创作之路的。
就这样,鲁迅怀着强烈的启蒙文学观开始了小说创作,并率先把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等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推到小说表现的中心位置上,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因而其叙事实践主要是有针对性地改造中国旧小说的说书人的虚假的全知全能外视角和“大团圆”的故事中心结构,使小说能在被他视作文学艺术的生命的“真实”和深广的层面上“为人生”和改良人生。
五四时期诗人和作家们对思想启蒙有一种自觉和自动的选择。
鲁迅的说法或许最有说服力,他在1933年谈起自己怎么做起小说来时,依然满怀深情地说:“说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③。
在五四时期,正因为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思想启蒙已被广大文学家普遍接受,自觉从事启蒙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作家们共同的文学追求。
一种话语形成之后,人们之所以遵从它,有时候并不是刻意为之,更多的情况下是无意识地对它予以接受和遵从。
五四时期广大作家都有“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启蒙主义的创作目标,也就是说他们的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即“说什么”和“怎么说”基本上遵从了这种蕴藏着启蒙主义文化内涵的“语码”。
在启蒙话语形成之后,这一话语对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必然会产生的潜移默化的规约作用。
弃医从文的蕴意无疑极其吻合这一文学主潮。
当“启蒙和拯救”成了“五四”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神圣”的栅栏时,这道栅栏就已为知识分子的立言圈定了疆域。
鲁迅笔下的“将令”就是对这道栅栏的命名,所谓的“听将令”也就是倾听中心话语的指令。
当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在刊物报纸上发表后很快获得空前的反响时,也就是因听将令而呐喊的他迅速地被尊为“主将”的时候。
于是乎,无论从自身的启蒙情结出发,还是为了迎合时代的潮流,鲁迅已决计让自己再次重新拿起“文艺启蒙”的武器,而且从此终其一生。
于是乎,在自己的小说将要结集出版之际,他郑重其事地写下颇费思量的自序,几乎是以小说笔法来传达这段十七年前的往事,其用意便是要为自己再次回归启蒙立场这一行动,为自己作为启蒙者再度出山立此存照。
从1922年重新构成过去的事件这个侧面上来看,重要的是鲁迅为什么单单挑出幻灯片事件来叙述。
而且,只看《呐喊》的序言的叙述时,仿佛觉得鲁迅的幻灯片事件之前对文学漠不关心,对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毫无知觉。
但在别的资料中我们则能够看出鲁迅在仙台学医之前就对文学十分感兴趣,很早就觉悟到对中国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性。
《呐喊》序言的叙述隐蔽了这些实情,从而体现了一种叙述的效果。
也就是说,形成了一个以幻灯片事件为契机而弃医从文的生动的故事。
一个平常的故事,一段一般的回忆就这样被高度地神圣化了。
2 当鲁迅以启蒙者的形象再度出山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主潮又反作用于他,使他的人生追求更贮满诗意,使他的人生之路豁然开朗。
1922年的鲁迅,已从寂寞中站起,他犹如一个在高度的沉静中久经思考而终于胸有成竹的战士,他的记忆力已复苏,他的自我意识已重建,这复苏和重建的结晶便是即将结集出版的《呐喊》。
鲁迅要在《呐喊》出版之际郑重其事地几乎是以小说的笔法写下一个颇费思量的自序,以此把《呐喊》打扮齐整,漂漂亮亮地送给新潮社。
鲁迅重提弃医从文,便是为了弥补《呐喊》文本上的不足,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引向创作小说的本事上。
我们先来看看接纳《呐喊》的新潮社的出版宗旨。
在“五四”时期蜂起的各种文化社团中,新潮社算得上是创办较早的一家,也是很有影响的一家。
它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与师长们的《新青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成犄角之势,与旧势力、旧传统、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新潮社同人们的出版活动熔铸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文化使命意识,“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被确定为出版物应采用的三“原素”。
如果以此出版宗旨来观照《呐喊》中十几篇小说,冷暖自知的鲁迅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文本是有某些先天不足的,即某些篇目与社会时代所应表达的公认的五四主题有距离。
在此我们无须回避,这也是一些鲁迅研究专家们早有论述的。
《呐喊》中的十四篇小说从表现的主题或思想的取向看,可以分两类,一类是社会性论题,即与国家前途、大多数人生存相关的话题,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处于文化或舆论的中心,是知识阶层特别关心并力图给予解答的时代课题,如《狂人日记》展开的是反封建专制、揭露家庭制度与礼教的弊害;《孔乙己》《白光》表现科举制度的罪恶、旧读书人的末路;《药》《阿Q正传》《风波》都涉及到辛亥革命及以后的社会现实,都沉重地表现了民众的不觉悟、麻木等精神创伤,即国民性问题。
《端午节》写知识分子软弱、模糊、逃避的人生和精神状态;《故乡》和《头发的故事》情况比较复杂,既有社会性、时代性的话题,又有个人化的话题,都涉及国民麻木,改革艰难的思想。
以上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取向几乎都体现了“五四”时期的时代主题和人文关怀,与新潮社的出版宗旨极为契合。
而另外一类作品就不是这样了。
其话题明显表现了个人性、一己性,与社会、时代虽有一些联系,但不是全社会共同关注,大家一看即知的时代主题或热点。
如《一件小事》是叙事者从一件小事对自我“越来越看不起人”的思想的反省,这篇作品具有某种个人的道德思想反省的倾向,作品虽然也迎合了“五四”时期一部分知识者在劳动者面前自我忏悔的时代思潮,但从鲁迅个人经历来看,思想的指向却在个人的某种或某方面的思绪与感受,作品叙事构成的“意义”,近于散文的个人性质而不具备小说的普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