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
适合朗诵的短诗歌(通用12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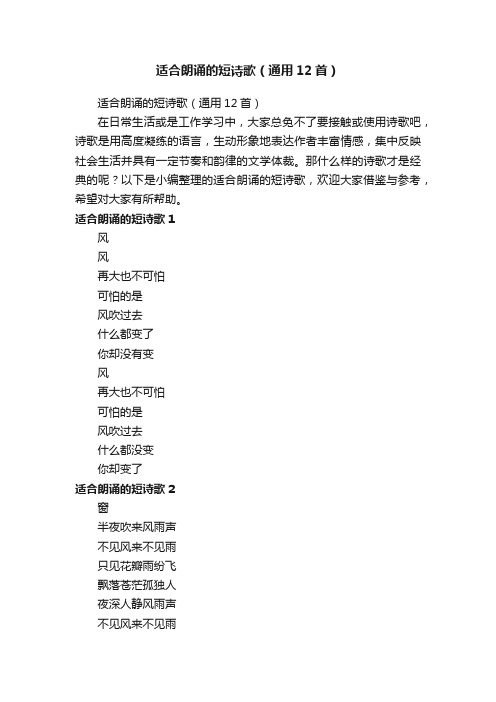
适合朗诵的短诗歌(通用12首)适合朗诵的短诗歌(通用12首)在日常生活或是工作学习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诗歌吧,诗歌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
那什么样的诗歌才是经典的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适合朗诵的短诗歌,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适合朗诵的短诗歌1风风再大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风吹过去什么都变了你却没有变风再大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风吹过去什么都没变你却变了适合朗诵的短诗歌2窗半夜吹来风雨声不见风来不见雨只见花瓣雨纷飞飘落苍茫孤独人夜深人静风雨声不见风来不见雨只见树摇呼吸声飞舞花瓣寂寞心适合朗诵的短诗歌3小时候的那张画小时候在一张白纸上画画涂涂画出了大大的太阳小房子还有小树看了又看笑容里塞满了幸福长大了在一张白纸上涂涂改改呆呆地握着笔颤抖真不知道画什么一路走来垃圾桶里满是纸团小时候在一张白纸上涂涂画画画出了大大的太阳小房子还有小树看了又看荡漾出幸福的阳光适合朗诵的短诗歌4再别康桥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桥的柔波里,我甘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适合朗诵的短诗歌5一棵开花的树作者:席慕容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於是把我化做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心适合朗诵的短诗歌6梦中的诗歌一场梦穿越了神的时空我是你复活的天行者经过艰难险阻追寻从未追寻过的梦未曾见你的面容你的形象是沙漠的风推动我学习学习那现实中学不会的武工游戏般的与恶魔拼杀杀到现实中永飞不到的天宫团结的心把师徒拧成股绳鞭策着邪恶迎来你沙漠般的面孔终结这梦结局的完美我爱你那现实中的燕子那梦中爱情我已用你紧握的锥子完成你的现实和梦当我施展完梦中的功夫又看见你的回眸适合朗诵的短诗歌7寻找诗歌这是春天鸟语爆绽枝头诗人我在阳光下寻找你隔世的那首诗歌沿着爬满青藤的篱笆肥胖的蜜蜂们吟唱而来彩色的蝴蝶翩跹舞来我寻找的心情就像一朵迟开的花朵留下孤独的.影痕和浅浅的哀叹也许这是你传递信息诗人在温柔且动人之处不露声色它教我正视一切并以平和的语气默诵线装古书里的绝句现在我抱着这枚哲理的果核置身在春天里诗人在你回望篱笆和鸟语的时候能不能告诉我那首诗歌飘逝的方向适合朗诵的短诗歌8音乐与诗歌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是因为多年前的今天,是两颗星陨落的日子一个是从逆境中登上巅峰的音乐家《英雄》和《命运》磅礴壮丽一个是从悲伤中离尘的诗人《春天,十个海子》划痛心际有人说,音乐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那么,诗歌可是苦难中暂短的欢愉?音乐似流动的诗,诗如静止的音乐音乐在诗中,诗在音乐里行云流水,平平仄仄它们都用心灵跳舞有谁分得清,哪个属于音乐哪个属于诗歌呢?如果说,音乐是镇痛剂它给了贝多芬生的勇气那么,诗歌呢?诗歌在路上。
查找现代诗歌

著名经典古诗诗歌1. 《登鹳雀楼》-作者:王之涣-原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登幽州台歌》-作者:陈子昂-原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3. 《悯农二首·其一》-作者:李绅-原文: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4. 《旅夜书怀》-作者:杜甫-原文: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5. 《咏鹅》-作者:骆宾王-原文: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春望》-作者:杜甫-原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7. 《清明》-作者:杜牧-原文: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8. 《静夜思》-作者:李白-原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9. 《芙蓉楼送辛渐》-作者:王昌龄-原文: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10. 《绝句》-作者:杜甫-原文: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11. 《春夜喜雨》(节选)-作者:杜甫-原文: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2. 《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作者:李商隐-原文: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13. 《山居秋暝》(节选)-作者:王维-原文: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14. 《将进酒》(节选)-作者:李白-原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15. 《关雎》-作者:佚名(出自《诗经》)-原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关于诗经的诗歌

关于诗经的诗歌1、《卫风硕人》先秦·佚名硕人其颀,衣锦褧衣。
齐侯之子,卫侯之妻。
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
四牡有骄,朱幩镳镳。
翟茀以朝。
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施罛濊濊,鳣鲔发发。
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2、《关雎》先秦·无名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3、《蒹葭》先秦·无名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4、《桃夭》先秦·佚名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5、《氓》先秦·佚名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送子涉淇,至于顿丘。
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
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
淇水汤汤,渐车帷裳。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
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
淇则有岸,隰则有泮。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6、《采薇》先秦·佚名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精选10首适合朗诵的经典诗歌

精选10首适合朗诵的经典诗歌
1.《登鹳雀楼》 -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春晓》 - 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静夜思》 -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4.《登高》 -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赋得古原草送别》 - 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6.《悯农》 - 李绅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7.《登鹳雀楼》 -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8.《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 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9.《登鹳雀楼》 -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0.《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 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以上是10首适合朗诵的经典诗歌,每一首都有其独特的韵味和意境,可以让人们感受到诗歌的美好与深远的意义。
精美诗歌12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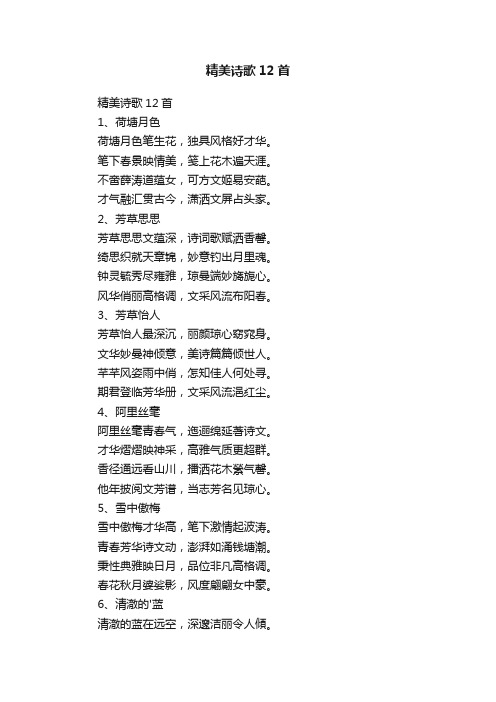
精美诗歌12首精美诗歌12首1、荷塘月色荷塘月色笔生花,独具风格好才华。
笔下春景映情美,笺上花木遍天涯。
不啻薛涛道蕴女,可方文姬易安葩。
才气融汇贯古今,潇洒文屏占头家。
2、芳草思思芳草思思文蕴深,诗词歌赋洒香馨。
绮思织就天章锦,妙意钓出月里魂。
钟灵毓秀尽雍雅,琼曼端妙旖旎心。
风华俏丽高格调,文采风流布阳春。
3、芳草怡人芳草怡人最深沉,丽颜琼心窈窕身。
文华妙曼神倾意,美诗篇篇倾世人。
芊芊风姿雨中俏,怎知佳人何处寻。
期君登临芳华册,文采风流浥红尘。
4、阿里丝毫阿里丝毫青春气,迤逦绵延著诗文。
才华熠熠映神采,高雅气质更超群。
香径通远看山川,播洒花木縈气馨。
他年披阅文芳谱,当志芳名见琼心。
5、雪中傲梅雪中傲梅才华高,笔下激情起波涛。
青春芳华诗文动,澎湃如涌钱塘潮。
秉性典雅映日月,品位非凡高格调。
春花秋月婆娑影,风度翩翩女中豪。
6、清澈的'蓝清澈的蓝在远空,深邃洁丽令人傾。
虽有阴霾能蔽掩,纵归柳杨映花红。
诗文尽占高格调,一腔情怀奏凯声。
他年寻看丽人榜,粉面桃花在笺中。
7、雪琼白洁雪何妖娆,冬占北国最琼妙。
翩飞来临似万蝶,縈枝披树挂银桃。
迎来送往殷勤意,赠情送意志趣高。
寒风吹摧无悔意,伴梅随稥胆节豪。
映日照月修真缔,吟诗著文送俏娇。
8、墨妍(凌波仙子)文秀琼颜西湖春,绮香光彩照世人。
娇韵风采高格调,凌波栖水不沾尘。
翘首仰望中天月,俯身浇汲芳华馨。
网间闪耀靓丽影,曲院风荷罩颀身。
9、星空独月人间多少悲欢事,尽在欲言又止中。
历尽劫波应回首,陶然一笑叙平生。
情仇爱恨寻常事,悲欢离合儿女情。
总为青春多珍重,携羽尘间待花红。
10、溪水清清溪水清清花露红,心花绽开在诗中。
初春将至君可待,却非去年杨柳风。
天地流转四时变,百花争艳却寒冬。
文坛驰骋结硕果,诗坛繁华待君耕。
11、倚窗望月倚窗望月好钗珺,纤心柔肠著诗文。
玉手挽来天边月,妙思吟动天边云。
菡荷洁丽照倩影,琼颜载梦织绮魂。
它年定登名媛册,娇颜才华天下闻。
12、醉雨轩醉雨轩中数红颜,诗精文透最可观。
诗歌诗词大全

诗歌诗词大全一、《书·知行》
洋洋说容易书究竟重,那少年读书究竟深。
目标若明腾空剑正弯,少年拼搏心遥神近。
莫言希望没有未来,必须今天争取永恒。
无论地位高低皆应学,努力拼搏勇攀高峰。
二、《静夜雪》
星光晨曦夜色静,白雪染尽林峦青。
灯火幽处空山凝,月华彩云伴清冥。
树梢如列猿声箫,波涛如簇鹤踪隐。
宁静无事难住美,冰冷夜雪照心深。
三、《声声慢》
古今逢春催愁添,千里落笔情似天。
落日空山复何事,滴泪洒青衫心酸。
声声慢何处子,客舟已过凉州边。
遥想江南何时返,只是归梦不在今。
四、《西江月》
西江月夜轮归清,灯山花月立芳青。
沙堤风月籁竹安,芦花流水醉潇湘。
春思恋船动人心,月明烟柳照渔灯。
两岸路多无限远,重叠此夕西江秋。
五、《秋实》
秋实今宵看叶落,此时江湖万木枯。
枫叶飞舞风里去,一片秋色带伤愁。
残阳满山当行色,叶渐零落两岸秋。
秋实将尽梦犹在,夕阳归去故国愁。
每日一首诗歌

每日一首诗歌
1. 《春日》
春日暖阳照,花开满园香。
风轻拂柳绿,云淡映山苍。
2. 《夏夜》
夏夜清凉爽,星空万里长。
蝉鸣声声远,蛙鼓阵阵忙。
3. 《秋思》
秋风吹落叶,飘零满地黄。
思念随云去,远隔重山长。
4. 《冬雪》
冬雪纷纷落,银装素裹妆。
天地一色白,清净无尘霜。
5. 《友情》
友情似海深,相隔万里心。
携手共进退,同舟共济难。
6. 《爱情》
爱情如花开,芬芳满枝头。
心心相印处,情深意更浓。
7. 《思乡》
思乡情切切,归心似箭飞。
遥望故乡月,照我归家路。
8. 《奋斗》
奋斗在路上,汗水洒征程。
不畏艰难险,只为梦成真。
9. 《珍惜》
珍惜眼前人,莫待成追忆。
时光不等人,一去不复返。
10. 《感恩》
感恩遇贵人,携手共前行。
知恩图相报,友谊永长存。
古诗诗歌大全100首

古诗诗歌大全100首1、《望庐山瀑布》唐代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黄鹤楼闻笛》唐代李白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3、《凉州词二首·其一》唐代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4、《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唐代李白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5、《雁门太守行》唐代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6、《早冬》唐代白居易十月江南天气好,可怜冬景似春华。
霜轻未杀萋萋草,日暖初干漠漠沙。
老柘叶黄如嫩树,寒樱枝白是狂花。
此时却羡闲人醉,五马无由入酒家。
7、《逢入京使》唐代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8、《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唐代杜牧翠岩千尺倚溪斜,曾得严光作钓家。
越嶂远分丁字水,腊梅迟见二年花。
明时刀尺君须用,幽处田园我有涯。
一壑风烟阳羡里,解龟休去路非赊。
9、《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唐代杜甫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
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
10、《蜀道难》唐代李白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11、《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唐代韩愈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12、《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13、《江畔独步寻花·其六》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14、《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5、《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适合朗诵的诗歌(精选18首)

适合朗诵的诗歌(精选18首)适合朗诵的诗歌篇11.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翻译:在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送走了旧年迎来了新年。
春风把暖洋洋的暖气送入屠苏酒,天刚亮时,家家户户都取下了旧桃符,换上新桃符,迎接新春。
2.同张将蓟门观灯唐孟浩然异俗非乡俗,新年改故年。
蓟门看火树,疑是烛龙燃。
翻译:在外地的风俗跟家乡的风俗是不一样的,新年与旧年也不同。
在蓟门看烟火,怀疑是烛龙起来了。
3.庾楼新岁唐白居易岁时销旅貌,风景触乡愁。
牢落江湖意,新年上庾楼。
翻译:年岁销蚀着旅人的容貌(也就是说在外漂泊的人易老),眼前的景象出动了我的乡愁,身在江湖尽是失意不得志,新年的时候上庾楼。
4.元日宋辛弃疾老病忘时节,空斋晓尚眠。
儿童唤翁起,今日是新年。
翻译:生了很长时间的病都往了时节了,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去睡觉,小孩子来叫我起床了,说今天是新年了。
适合朗诵的诗歌篇2《南方的夜》作者:冯至我们静静地坐在湖滨,听燕子给我们讲南方的静夜。
南方的静夜已经被它们带来,夜的芦苇发着浓郁的清热。
我已经感到了南方的夜间的陶醉,请你也嗅一嗅吧这芦苇中的浓味。
你说大熊星总象是寒带的白熊,望去使你的全身都感到凄冷。
这时的燕子轻轻地掠过水面,零乱了满湖的星影。
请你看一看吧这湖中的星相,南方的星夜便是这样的景象。
你说,你疑心那边的白果松总仿佛树上的积雪还没有消融。
这时燕子飞上了一棵棕榈,唱出来一种热烈的歌声。
请你听一听吧燕子的歌唱,南方的林中便是这样的景象。
总觉得我们不象是热带的人,我们的胸中总是秋冬般的平寂。
燕子说,南方有一种珍奇的花朵,经过二十年的寂寞才开一次。
这是我胸中觉得有一朵花儿隐藏,它要在这静夜里火一样地开放! 适合朗诵的诗歌篇3《老师》平凡的人,平凡的手架起一座知识的桥梁走过冬的严寒走过夏的酷暑培养出莘莘学子一只粉笔指点知识王国的迷津一块黑板记下比海还深的真情一个讲台映照着园丁浇灌鲜花的艰辛三尺教鞭挥向通往理想境界的途径我们是繁星您是月亮把优美动听的故事“讲给”我们听让我们能进入美好的梦境清晨的阳光是您那灿烂的微笑不管我们失败还是胜利不管我们后退还是前进您,都会用微笑鼓励我们再接再厉老师慈祥的母亲老师千万颗童心的梦想老师祖国赋予您特殊的使命让您把一棵幼小的禾苗培养成祖国的栋梁老师我要您那慈祥的面容永不变老老师我要您那明亮的眼睛永远不黯淡老师我要您那乌黑的头发永不变白老师我要您那疲劳的双手变的轻松老师我要为您歌唱,为您祝福老师您是我最敬佩的人!老师是开启智慧的敲门砖,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金钥匙,更是我们生活航程中的引路人。
中国著名诗歌精选

以下是中国著名诗歌精选:
1、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2、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白《将进酒》
3、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登高》。
儿童诗歌、经典诗歌

儿童诗歌、经典诗歌1. 《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哇,这就像小朋友们的眼睛,那么明亮!你看,星星在天上眨呀眨,是不是在和我们打招呼呢?2. 《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那大白鹅游在水上的样子,多像一艘小船呀!难道你不觉得很可爱吗?3. 《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春天的早晨多美好啊,小鸟的叫声就像是在唱歌!你喜欢春天的早晨吗?4. 《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那月光就像妈妈的温柔,洒在地上。
你有没有在看到月亮时想起自己的家乡呢?5. 《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农民伯伯种地多辛苦呀,就像我们努力学习一样!我们可不能浪费粮食哦!6. 《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妈妈的爱就藏在那细细的线里,多温暖呀!你感受到妈妈的爱了吗?7. 《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那黄河奔腾的气势,就像我们勇往直前的决心!我们要不断向上攀登呀!8. 《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那孤独的渔翁,多像在坚守自己的信念!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坚持呢?9. 《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那纷纷的细雨,是不是也勾起了你的思绪呢?10. 《山村咏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那小小的村庄,就像一幅美丽的画!真让人陶醉呀!我的观点结论:儿童诗歌和经典诗歌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它们简单易懂又充满真情实感,能让我们感受到美好和温暖,应该让更多的小朋友去接触和喜爱它们。
古代诗歌大全

古代诗歌大全1、江南汉乐府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敕chì勒lè歌北朝民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qióng庐lú,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3、咏鹅(唐)骆宾王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风(唐)李峤qiáo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5、静夜思(唐)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6、登鹳雀楼(唐)王之焕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7、春晓(唐)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8、鹿柴(zhài)(唐)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现代诗歌(56首)

现代诗歌(56首)现代诗歌(精选56首)现代诗歌(精选56首)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
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
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现代诗歌,希望对你有帮助!1、《乡愁》作者:余光中XXX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呵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呵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2、《一切》作者:XXX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解释一切都带着一切迸发都有少焉的宁静一切出生都有冗杂的回声3、《天问》作者:余光中水上的霞光呵一条接一条,何故都没入了暮色了呢? 地上的灯光呵一盏接一盏,何以都没入了夜色了呢? 天上的星光呵一颗接一颗,何以都没入了曙色了呢? 我们的生命呵一天接一天,何以都归于永恒了呢? 而当我走时呵把我接走的,究竟是怎样的天色呢? 是暮色吗昏昏?是夜色吗沉沉?是曙色吗耿耿4、《再别康桥》作者:XXX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桥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XXX,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5、这也是一切——答XXX的《一切》作者:XXX不是一切大树都被风暴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断翅膀。
古代诗歌大全

古代诗歌大全古代诗歌大全1、《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村居》清·高鼎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扬柳醉青烟。
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4、《所见》清·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5、《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6、《赠刘景文》宋·苏轼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7、《山行》唐·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8、《回乡偶书》唐·贺知章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9、《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0、《赋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1、《宿新市徐公店》宋·杨万里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12、《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3、《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14、《夜书所见》宋·叶绍翁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
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
15、《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6、《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7、《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全部诗歌大全

全部诗歌大全
1、《登鹳雀楼》
——李白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望庐山瀑布》
——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赤壁之战》
——杜甫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长江一发,平天下。
”
5、《寒食》
——杜甫
食暖还寒日萧萧,炊香闻更胜满座。
枇杷汤沾白粥,翠菜豆腐香荤饭。
6、《山行》
——李商隐
两山相对出翠微,一水中分碧溪溯。
绿槐高处连晚景,白鹭飞下拂乱枝。
7、《春晓》
——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常见诗歌分类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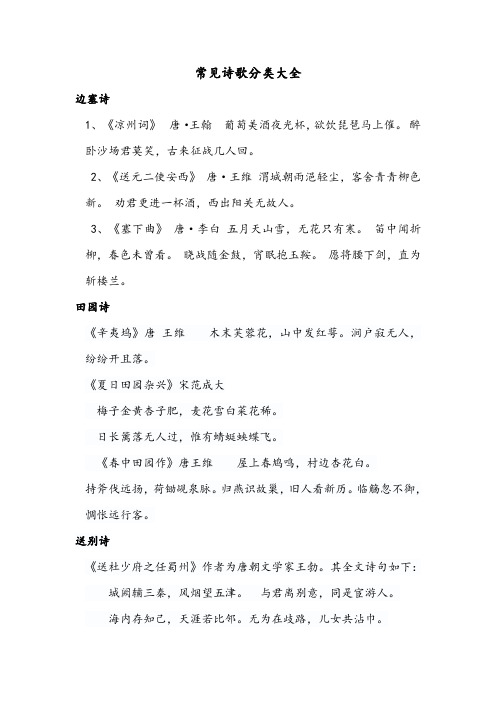
常见诗歌分类大全边塞诗1、《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2、《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3、《塞下曲》唐·李白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田园诗《辛夷坞》唐王维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夏日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春中田园作》唐王维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
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
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
临觞忽不御,惆怅远行客。
送别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作者为唐朝文学家王勃。
其全文诗句如下: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芙蓉楼送辛渐》作者为唐朝文学家王昌龄。
其全文诗句如下: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别董大》作者是唐代文学家高适。
其全文诗句如下:千里黄云白日昏,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哲理诗王之焕《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杜甫《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朱熹《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思乡诗1、<夜雨寄北>唐·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2、<泊船瓜洲>宋·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3、<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童趣诗1、《幼女词》唐·施肩吾幼女才六岁,未知巧与拙。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诗歌,现实与语言之旅——王家新2008年11月7日(2008-12-23 08:48:00)标签:杂谈分类:素材在通向黄山的路上夜里九点,从黄山屯溪机场出来后,参加“2008帕米尔诗歌之旅”的中外诗人乘车前往黟县,正好我和从美国来的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及他的夫人、诗人布伦达•希尔曼(Brend Hillman)坐在一辆中巴的最后一排,车在黑暗中行驶,我们便一路上谈了起来。
哈斯可不是一般的诗人,他是美国第八位桂冠诗人(1995—1997年度),多次全美图书奖、普利策奖的获得者。
但他却是那种一见就让人感到很亲切和温暖的人,“你看上去真像是弗罗斯特啊”,在北京初次一见面,我就禁不住这样对他说,他笑了:“早就有人告诉我这个了”。
碰巧的是,和弗罗斯特一样,哈斯也出生于旧金山,生长于加州北部。
我不曾访问过旧金山,但我曾在那里的海湾机场转机逗留过,在强烈的阳光和发蓝的深邃大气中,我看到远山的积雪闪耀。
而这,也正是眼前这位诗人给我带来的感觉。
我难忘那近一小时的轻声交谈。
因为我特别喜欢米沃什的诗,而哈斯是米沃什在美国最主要的译者,所以在车上我主要就问他这个。
他说他的翻译是和米沃什一起合作的结果。
他们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并且住在相邻的街区。
一谈起米沃什,哈斯的脸上就放光(即使在黑暗中,我也感到了那光亮)。
在他的神情和语调中,有着对一位伟大诗人的崇敬,又有着友人之间的那种友情和默契。
一次他们译完一首诗,都感到非常满意,米沃什像个孩子似地嚷嚷了起来,“啊啊,你怎么没告诉我你喜欢这首诗?”讲到这里,哈斯笑了起来。
我想到米沃什在中国的译者、诗人张曙光访美时,曾到伯克利访米沃什不遇,他只是登上了伯克利校园里的钟楼,从那里眺望米沃什不止一次描写过的加利福尼亚海湾。
咳,曙光当时真应该去找哈斯呀!他译米沃什时,主要依据的正是哈斯那杰出、优异的译文!我更多地明白了为什么米沃什的诗在英语世界那么有影响了。
伟大的诗歌有赖于伟大的翻译。
或者说,伟大的翻译照亮了伟大的诗歌,使它在人们面前熠熠生辉。
“诗歌如何回应现实”清晨,在一阵喳喳的鸟声中醒来。
推开窗户:静谧的竹林、带雾气的山丘……用一位诗人后来的话说,好一幅前工业社会的图景!我们住在黟县(据说这是中国内地人口最少的一个小县)城边上一座传统徽式风格的山庄里,这里如此安静,刚从北京来,我的耳朵都有些不适应了。
诗会的主题是“诗歌如何回应现实”。
住在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的所在,欧阳江河说这是一个“现代性”被减缓、被过滤的地方。
但我想现实完全可以有着不同的读解。
我们坐着旅游专线的小飞机而来,来到这里喝着进口咖啡看远山,难道这一切和“现代性”就没有关系?这一切,也许正是“现代性”的产物。
这也印证了美国纽约派诗人罗恩(Ron Padgett)在会上所说的:现实具有欺骗性。
的确,说到“现实”,首先引起的就是困惑。
布伦达在发言中坦承“如何回应现实”这样的话题让她很困惑,她说英语中“现实”(reality)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源是“给予的事物”,柏拉图则认为现实是幻影。
这样的“现实”是很难获知的。
在今天,诗人们不能不生活在一个悖论的世界上。
他们只能把自己边缘化(她称之为“英雄主义式的边缘化”),把晦涩作为拯救。
她这个开场白引起了哈斯的反响。
和一些中国批评家往往把现实看作是重大的社会现象的看法很不一样,他说有看得见的现实,但也有看不见的现实,我们呼吸的空气,包括胃里的细菌是不是现实的一部分?人类就像发明上帝一样发明了现实这个词。
但现实应有所限定,不然它就会超出诗的表达能力。
他还引用了米沃什在《诗的六讲》中的一句诗:“现实,我们能对它做什么?它在词中的什么地方?”这样的发问真是耐人寻味。
会议主持人西川则作了一些解释。
他说在中国传统中,人们一般是用儒家的眼光读诗,用道家的眼光看画。
而这些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和动荡的世界上,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更是困扰着中国的诗人们。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诗会的主题是“诗歌如何回应现实”。
我理解这种用意。
但是正如加拿大诗人蒂姆•利尔本(Tim Lilburn)所说,我们最好还是离开关于现实的宏大叙事,回到个人的现实、语言的现实。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现实感”都很不一样。
比如当我说“杜甫是一位现代诗人”时,我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里、什么样的现实中呢?因此我赞同哈斯的建议:让“经验”“感受”这类词加入我们的讨论。
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我们当然不能不关注现实,但诗的写作与其说是来自对现实的回应,不如说来自对个人经验的挖掘。
诗是“经验”的生长、转化和结晶。
不过这一切,反而印证了这个话题的有效性。
它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来自西班牙的诗人胡安(Juan Carlos Mestre)用激越的声调宣称:诗人的现实,不是现实的现实。
他要致力于“语言的乌托邦”,以唤回诗的尊严。
而早些年曾提出“拒绝隐喻”的于坚,在发言中也来了句隐喻:现实是果酱。
这可能来自他早上往面包上抹果酱时的灵感吧。
但如果我们这个会是在东北的某个地方开,席间端上来一锅热腾腾的酸菜炖肉(里面可能还有大虾、海参、冻豆腐什么的),那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一锅“东北乱炖”!困境和难度这次交流最多的,是和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Tomaz Salamun)。
我们一见面,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近,后来我们开会时坐在一起,吃饭时也往往坐在一起。
萨拉蒙在东欧和美国都挺有影响,他的诗被美国诗人查尔斯•西米克等人译成英文,他自己也经常在美国大学教授创造性写作,他和许多诗人都是朋友,比如近些年来为中国诗人所关注的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
说到扎加耶夫斯基,我说到我的一次经历:去年访美期间我在哈佛大学旁边的书店挑了一本他的英译诗选,到柜台付钱时,年轻的男店员眼睛一亮“你也喜欢他的诗?”说着,他从自己的背包中掏出了同样一本诗集,说他上下班的路上就读它!听我这样说,萨拉蒙两眼直放光,“好!好!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告诉给扎加耶夫斯基!”是啊,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一个诗人呢?!但是,对一个诗人的压力也永远存在着。
我听萨拉蒙讲了他的经历,那几乎和文革后期以来北岛、芒克他们的经历是同一个故事。
因此,他会在会上这样说:写作的压力到处都有,很难说在某个国家感到的多,在另外的国家感到的就少,天知道?!写作是一种历险,仿佛被鲸鱼吞了进去,仿佛是在梦中,但又是清醒的……借用策兰的一句话,这才是我从“深海听到的词”!因为它越过生活的表层,深入到写作的内里。
写作不仅是有压力的,它本身就应该是“困难的”。
因此我在会上谈到了“写作的难度”问题。
说真的,我担心的不是人们关不关心现实,而是在一个让人“坐不住”的时代,我们的写作能否保持深度和难度的问题。
因为会上的中外诗人不时地提到策兰,因为策兰对欧美一些后现代诗人和语言诗派诗人影响甚大,我谈到策兰的语言实验,比如策兰《低水》一诗中的“一个沙吧/立在一个小小的/不可通航的沉默前。
”“沙吧”(sand bar)显然是策兰杜撰的一个词。
“吧”是人们交流、谈话的所在,而这个吧却是用“沙”垒成的,且立在“一个小小的/不可通航的沉默前”!这真是显现出一种罕见的思想深度。
那些内里贫乏却热衷于玩语言游戏的“先锋派”们能写出这样的诗吗?正因为有策兰这样的诗人,我感到我们的一些话是不是说得太轻易了?我们的写作是不是太雄辩、太聪明,或太流畅了?而策兰的诗让我高度认同,就在于它既是对难度的挑战,但同时又是对难度的显现和保持。
他的一些诗,正如杜甫晚期的诗,把一种写作的难度提升到一个令人惊异的程度。
我的这些谈论,引起了与会一些诗人的反响。
布伦达在她送给我的诗集上这样写到:“我喜欢你的诗和你关于写作的难度的思想,我说,更困难!”也许,正因为这种难度,才对一个诗人构成了真正的激励。
诗会期间,萨拉蒙一下子送我了他四本英译诗集,并对我说:“家新,你一定要到斯洛文尼亚来!你知道吗?里尔克的杜依诺城堡,就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是吗?我的眼一亮,我仿佛已看到了那座立于悬岩之上、迎向狂风和大海的古堡,如一个艰难的星座,在茫茫时空中为我们再次升起。
诗歌的“漂流瓶”诗会第二天,来自美国的安妮•沃尔德曼(Anne Waldman)便提出要朗诵。
她是金斯伯格当年的朋友和小伙伴,现在被视为“后垮掉”代表性诗人。
诗人们聚会而不朗诵诗,在她看来太奇怪了,于是大家同意了她的提议。
晚上,山庄庭院的烧烤花园里,安妮第一个站起来朗诵,她读(准确地说是“表演”)的是一首《给虚无上妆》的长诗。
发蓝的夜色中,那女巫一样尖叫、燃烧的声音,甩动的长发,还有不时飘来给朗诵者“上妆”的烧烤的白烟,真把我们给看傻了(我瞄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哈斯,他干脆把头仰到藤椅后面,养神去了)。
我们的邻座,本来是一桌大声喧哗的本地人,似乎也被镇住了,最后居然走过来向我们敬酒。
安妮的诗,包括她那一路垮掉/后垮掉诗人的诗,就个人口味来说,我其实并不怎么欣赏,但她的朗诵真的很吸引人。
尤其是后来她在另一个场合朗诵的一首和动物保护有关的诗,使我受到很深感动。
她的朗诵伴随着她儿子创作的音乐,音乐中居然还不断出现了濒临灭绝的海牛的鸣叫声。
这不仅让我体会到诗人内心中的那种哀痛,也让我领略到诗歌朗诵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魅力。
遗憾的是,似乎大多数中国诗人只会“念诗”而不会“朗诵”(用于坚的话说,“念”字带着一个“心”字,所以他只“念”而不“朗诵”)。
我这个人天生嘴笨,而且带口音,每次上台“朗诵”总像是被押赴刑场一样,但我多么希望其他中国诗人在这方面有更勇敢、更富有创意的尝试!但是中国诗人的诗,用萨拉蒙等人的话来说,也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他们为此甚至多少有些惊讶。
在来中国之前,他们似乎只知道北岛。
这次他们深入到“腹地”中来了。
一些与会中国诗人的作品英译,如西川、于坚、欧阳江河、宋琳、蓝蓝等人的诗都受到赞誉,蓝蓝的《风》(“风吹走他的内賍亲人的地平线。
/风把他一点点掏空。
/他变成沙粒一堆粉末/风使他永远活下去——”),我就听到布伦达很兴奋地一再谈起。
哈斯也专门找到我谈我的那些诗。
他说一些西方人读中国诗只是了解一些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但这次他们面对的是“作为艺术的诗”。
他喜欢《尤金,雪》、《田园诗》,说这种写法很奇妙,而且很有深度,尤其是诗片断《冬天的诗》、《变暗的镜子》,他说对他来说它们“完全是新的”,他从未读到过这样的诗。
他甚至用了一个词:brilliant。
因此他们十分关心中国诗歌的翻译、出版情况。
他们说中国现在这些诗人的诗完全应该在美国出版,不仅汉学界,美国读者和诗人们也会很感兴趣的。
但问题就在这里:谁来翻译和出版呢?在美国有志于中国现当代诗的人本来就很少(似乎汉学家们都去翻译小说、研究电影了),更没有什么真正有影响的诗人和出版社加入到这种翻译、出版中来。
而诗歌翻译最好经过诗人尤其是优秀诗人之手,否则它只能在汉学界打转,谈不上真正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