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墙纸》与十九世纪的女性主义
浅析《黄色墙纸》中的女性主义

“ 黄 色墙 纸 ” 这 一意 象 , 委婉 表述其 女性 主义思 想 。
1 女 主 人公 的 生存 处 境
同当 时许 多 作 品 中 的女 性 角 色 一 样 , 小 说 的 女 主人公 没有 姓名 , 相反 , 如她 的堂 弟 堂 妹 , 甚 至 约 翰 的妹妹 都有 名字 。这是 吉尔 曼 的有 意 为 之 , 因为 她 要 塑造 一个 全新 的女 性形 象 。女性 历来 都非 性 别 中
bo d i e s t h e i d e o l o g y o f pa t r i a r c h l a s o c i e t y. He r ”i ns a n i t y ”i s i n e f f e c t h e r s e e k i n g o f s e l f - i d e n t i t y a n d p u r —
s ui ng o f ̄e e d o m. By d e p i c t i n g t h i s f e ma l e i ma g e, Gi l ma n t ie r d t o s h o w r e s i s t a n c e a g a i n s t t he pa t ia r r c h a l s o c i e t y wh i c h c a us e d de p r e s s i o n t o f e ma l e s a nd e v e n f e mi n i ne wr it i n g, a n d b r o k e t h e t r a d i t i o n a l b i n a y r 0 p— p o s i t i o n o f g e n d e r a n d i d e n t i t y. Ke y wo r ds: Gi l ma n; T h e Ye l l o w Wa l l p a pe r ; i n s a n i t y; f r e e do m; g e n de r ; i d e n t i t y
《黄色墙纸》的女性主义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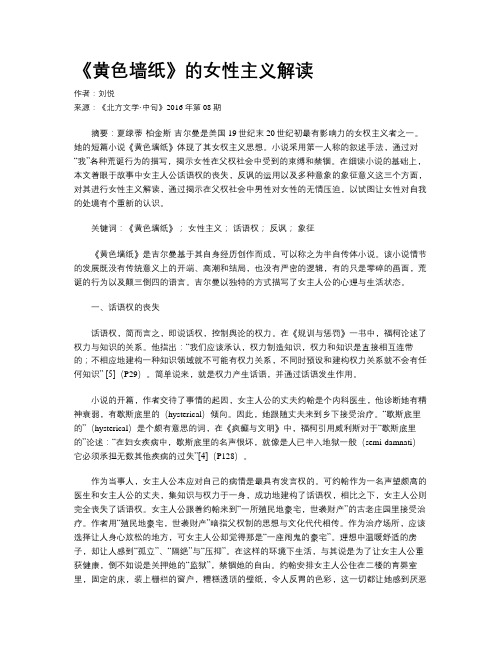
《黄色墙纸》的女性主义解读作者:刘悦来源:《北方文学·中旬》2016年第08期摘要:夏绿蒂·柏金斯·吉尔曼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之一。
她的短篇小说《黄色墙纸》体现了其女权主义思想。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通过对“我”各种荒诞行为的描写,揭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受到的束缚和禁锢。
在细读小说的基础上,本文着眼于故事中女主人公话语权的丧失,反讽的运用以及多种意象的象征意义这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女性主义解读,通过揭示在父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无情压迫,以试图让女性对自我的处境有个重新的认识。
关键词:《黄色墙纸》;女性主义;话语权;反讽;象征《黄色墙纸》是吉尔曼基于其自身经历创作而成,可以称之为半自传体小说。
该小说情节的发展既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开端、高潮和结局,也没有严密的逻辑,有的只是零碎的画面,荒诞的行为以及颠三倒四的语言。
吉尔曼以独特的方式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心理与生活状态。
一、话语权的丧失话语权,简而言之,即说话权,控制舆论的权力。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论述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
他指出:“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5](P29)。
简单说来,就是权力产生话语,并通过话语发生作用。
小说的开篇,作者交待了事情的起因,女主人公的丈夫约翰是个内科医生,他诊断她有精神衰弱,有歇斯底里的(hysterical)倾向。
因此,她跟随丈夫来到乡下接受治疗。
“歇斯底里的”(hysterical)是个颇有意思的词,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引用威利斯对于“歇斯底里的”论述:“在妇女疾病中,歇斯底里的名声很坏,就像是人已半入地狱一般(semi-damnati)它必须承担无数其他疾病的过失”[4](P128)。
作为当事人,女主人公本应对自己的病情是最具有发言权的。
黄色墙纸文体学分析

对《黄色墙纸》的文体学分析摘要:《黄色糊墙纸》是吉尔曼的代表作,它揭示了女性是如何在重重围城中挣扎的,从而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及婚姻家庭对女性的束缚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本文的主体部分将从文体学角度出发研究和分析小说特色,即语言描述和修辞应用。
一、引言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出现了一位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她就是夏洛蒂·波金斯·吉尔曼。
她的短篇小说《黄色糊墙纸》已经成为妇女文学中的一个小小的“经典”。
小说通过一位已婚妇女“我”从轻微的精神抑郁到彻底疯癫的精神发展历程,给我们描绘了生活在围城中女性的渴望、矛盾以及自我分裂的痛苦挣扎。
从而揭示了女性由于从身体到思想的被禁闭而走向精神崩溃的悲剧性命这,并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以厦婚姻家庭生活对女性的束缚进行了质疑和批判。
长期以来,女性一直没有自己的语言,正如女权主义批评家所比喻的那样,“向来在努力偷盗语言”。
女权主义者西苏认为语言是控制着文化和主体思维方式的力量,要推翻父权制的控制,就要从语言的批判开始:“每一件事都决定于语词:每一件事都是语词,并且只能是语词……我们应该把文化置于它的语词中,正如文化把我们纳入它的语词中一样……任何政治思想都必须用语言来表现,都要凭借语言发挥作用,因为我们自降生入世便进入语言,语言对我们说话,施展它的规则……甚至说出一句话的瞬间,我们都逃不脱某种男性欲望的控制。
对于如何摆脱父权制话语的控制,建立自己的象征秩序,英美女性主义激进派强调改造现存的语言,甚至要用以女性为中心的语言体系取代父权制的旧语言体系;而美国女作家吉尔曼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以她的近似日记的短篇小说《黄色糊墙纸》竖起了一面女权主义的旗帜。
她不仅是要描写妇女的真实处境,而且设计出一种反抗父权制的叙述策略:钻进父权制话语内部对之进行颠覆。
二、文体分析的性质和内容文体学的任务不在于列举若干文体的题目,而在于观察和描述若干种主要文体的语言特点,其目的在于使学者能够更好的了解他们所表达的内容和在恰当的场合分别使用他们。
从哥特式风格分析《黄色墙纸》中的女权主义

- 253 -校园英语 / 文艺研究从哥特式风格分析《黄色墙纸》中的女权主义哈尔滨师范大学/齐欢【摘要】《黄色墙纸》是著名女性作家吉尔曼的文学作品,小说记述了自己产后的一段产后生活经历以及对婚姻态度变化。
《黄色墙纸》是一部哥特式小说,充满刺激与悬疑,哥特式风格广泛应用于女权主义作家的小说之中,通过《黄色墙纸》这一小说反映了19世纪末期男性权威的影响下,女性权利的缺失以及给女性带来的痛苦经历,在压迫之下,女性开始反抗男性权威,寻求自我的过程。
【关键词】女权主义 哥特式 女性地位一、作者个人经历及当时社会背景吉尔曼是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中重要作家,是19世纪末最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之一。
“吉尔曼的家族中不乏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先进思想者,她的姨婆莉叶·毕秋·斯托是大力呼吁废除黑奴制度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作家”,吉尔曼在24岁时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但是这次婚姻吉尔曼并不幸福。
产后的吉尔曼身体和精神状态每况愈下,《黄色墙纸》这一作品正是根据吉尔曼的婚姻生活为原型,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现社会及家庭带给女性的痛苦和创伤,她甚至暗下决心终生不嫁,全身心投入到追求女性平等运动中去。
离婚之后,她独自带女儿生活,靠写作和演讲维生,家族和感情经历的影响让她反对性别歧视并争取平等自由的权利,呼吁社会更多的关注女性。
玛格丽特·富革力是一位高度关注女性地位和女性发展的19世纪女知识分子,她在1845年写出了美国第一部妇女问题专著《十九世纪妇女》,论述两性平等对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益处。
她说我们会摧毁一切专制的堡垒,我们将打通所有的道路,让她们像男性那样自由的对女性开放。
二、《黄色墙纸》中的哥特式色彩《黄色墙纸》是一部典型的哥特式小说,小说中充满大量的恐怖的元素。
小说开篇提到“我”对租期为三个月的房子的印象,一座殖民时期的大楼,四周空旷,高高的院墙,紧锁的大门,给人阴森恐怖的气氛。
“我”所住婴儿室的窗户上安着栅栏,房间有种难闻的味道。
谈《黄色壁纸》中的“我”的困境与出路——论夏洛蒂·吉尔曼的女性主义观

1引言——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女 权主义文 学批评 ( e nsLt a r c m) 2 Fmii i rr Ci i 是 0世纪 6 t e y ts i o 年代 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高潮 的社会背景 中诞生的一种新的文学 批评 观念与行为 , 是女权 主义在文化领域 , 尤其是文学活动领域延 伸的产物。 美 国女权 主义者 艾德里安娜 ・ 里奇 ( d en Re ) : 没有 A r ne i 说 “ i h 日益发展 的女权主义运动 ,女权主义的学术活动就不会迈出第一 步。”1 挪威学者托里 ・ [3 1 1 2 莫依 ( o l o ) 直接地说 : 女权主义 T r i 更 i M “
文 研究 ■ 化
谈《 黄色壁纸 》 中的 “ ’ 我’的困境 与 出路
— —
论 夏 洛 蒂 ・ 尔曼的女 性 主 义观 吉
王 燕
河北 . 定 保 0 10 ) 70 1
( 河北农 业大 学外语 学院
中图分类号:1 6 10 0 0 - 3 - 2 1 7 — 8 4( 0 9) 4 2 1 0
3《 黄色壁纸 > 中的 “ 我”的困境
《 黄色壁纸 》 发表 于 19 8 9年 , 小说 采用 “ 第一人称”的叙事视 角, 女主人公没有 名字, 意指 “ 不单仅 某一个孤立 、 我” 封闭的女性 个体, 而是指 代任何一位女 性群体中女性 意识 已觉醒个体女性 , 弗 吉尼亚 ・ 伍尔夫在她 的 《 一个 自己的房间 》 中说道 : 那 么, “ 这就是 我 , ……或是别的你所喜欢 的名字— —完全没有关系。 作者 叫我 ” 将虚实结合 ,描绘 出了有神经抑郁 的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挣扎 的困境 。那么 “ 我”的困境到底是如何一点点逐步形成的呢? 文 中以第一人称妻子 的口吻叙 述了夏天她产后不久 ,丈夫约 她和孩子到一乡村别墅休养 。 “ 那是一所殖民豪宅 , 世袭财产 ” 隐 , 约透露着其象征着父权制社会 的历史 积淀根深蒂固 , 也侧面解 这
黄色的墙纸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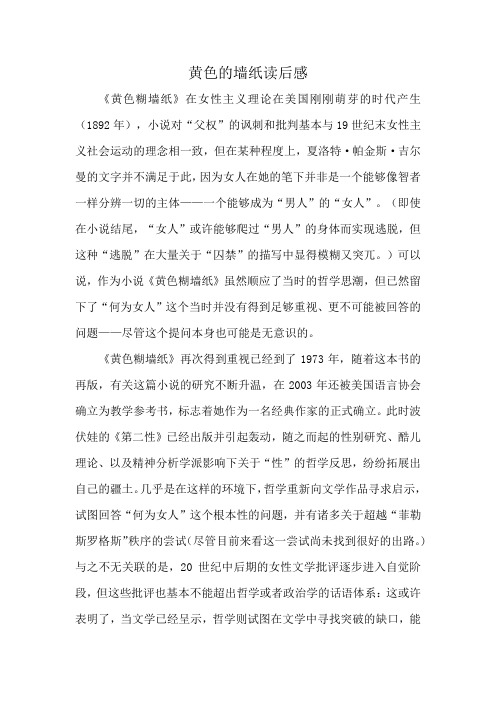
黄色的墙纸读后感《黄色糊墙纸》在女性主义理论在美国刚刚萌芽的时代产生(1892年),小说对“父权”的讽刺和批判基本与19世纪末女性主义社会运动的理念相一致,但在某种程度上,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文字并不满足于此,因为女人在她的笔下并非是一个能够像智者一样分辨一切的主体——一个能够成为“男人”的“女人”。
(即使在小说结尾,“女人”或许能够爬过“男人”的身体而实现逃脱,但这种“逃脱”在大量关于“囚禁”的描写中显得模糊又突兀。
)可以说,作为小说《黄色糊墙纸》虽然顺应了当时的哲学思潮,但已然留下了“何为女人”这个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更不可能被回答的问题——尽管这个提问本身也可能是无意识的。
《黄色糊墙纸》再次得到重视已经到了1973年,随着这本书的再版,有关这篇小说的研究不断升温,在2003年还被美国语言协会确立为教学参考书,标志着她作为一名经典作家的正式确立。
此时波伏娃的《第二性》已经出版并引起轰动,随之而起的性别研究、酷儿理论、以及精神分析学派影响下关于“性”的哲学反思,纷纷拓展出自己的疆土。
几乎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哲学重新向文学作品寻求启示,试图回答“何为女人”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并有诸多关于超越“菲勒斯罗格斯”秩序的尝试(尽管目前来看这一尝试尚未找到很好的出路。
)与之不无关联的是,20世纪中后期的女性文学批评逐步进入自觉阶段,但这些批评也基本不能超出哲学或者政治学的话语体系:这或许表明了,当文学已经呈示,哲学则试图在文学中寻找突破的缺口,能否突破也许仍需证实,但毕竟文学已经提供了新的视野。
《黄色糊墙纸》塑造了一个由于精神失常而受丈夫“监禁”的女性形象,而在受到男性统治的过程中,失常陷入更为强烈的疯癫。
笔者认为,疯癫在此并非是一个偶然的设定,或者仅仅是作者吉尔曼对自身经验的投射,它自身有更深刻的哲学内涵。
从文本的表层叙述逻辑看,这种疯癫与对男性“恐惧症”(phobia)不无联系。
《黄色墙纸》语言层面的女性主义解读

语言文字
《 黄色墙纸 》语言层面的女性主义解读
徐婧 西南交通 大学外 国语 学院 60 3 10 1
4这种话语方 式 ,一方面 ,正好表 明了 《 黄色墙 纸 》是美 国著名 女 权运 动 先驱 及作 家—— 夏 种气 味煞是可怕 ”。 【1 洛特・ 吉 尔曼 (8 0 1 3 ) 帕・ 1 6 .9 5 的代 表作 。小 说通过描 写一位患 女 主人公 思维混乱不 清 、逻辑 错乱 的精神 病状 ,符合其人物 精神抑郁症的知识 女性 ,受 到丈夫 的控 制 ,在男权婚 姻家庭 形象 ,而另一方面 ,这也是 已确定的传统 的语言规则和方式
另一位 法国女性主义者 西苏在其 《 美杜莎 的笑声 》中主张 , “ 妇女必须写 自 :必须写妇 女 ,把妇女写震 颤性谵妄症般 歪歪扭扭 地在队列里来 回走 动” ,
“ 散乱 的线 条像 斜 向飘 逸的波纹 ,形成恐怖 的光 影” , “ 一
她看来 , “ 言是控制 文化和主体 思维方式 的力量 。任何 思 长 串的伞 菌含苞 待 放 、发 芽抽 蕊 ,延绵 不 断地盘 绕着 ”。 语 这些 有着哥 特风格 的怪诞 比喻和描 写 ,反应 出了女 主人 5 想都必 须用语 言来表现 ,凭借语 言发挥作用 ,要推翻父权 制 1’
里备受压抑的经历 ,批判 了不平 等 的夫 妻关系 ,揭露 了父权 相反 的话 语形式 ,是 对 已经确 立的理性 的 、强调逻辑性 的权 制文化这一 “ 囚笼”对女性身 心的摧残 。该作 品现在 已成为 威话语 ,即男权主义话语 的有力挑战 。 再 者 , 《 色墙 纸 》通 篇都 是 以第 一人 称 的角度 进行 黄 英语世 界 国家最受评论 家瞩 目的名 篇之一 。 自1 9 年 首次出 82 版后 , 《 黄色墙纸 》在欧洲各 国引起广泛 关注 。尽管 现已是 的叙述 ,讲 述了女主人 公受到 男权 制度婚姻压 迫的经历 。这
国内外《黄色墙纸》女性主义研究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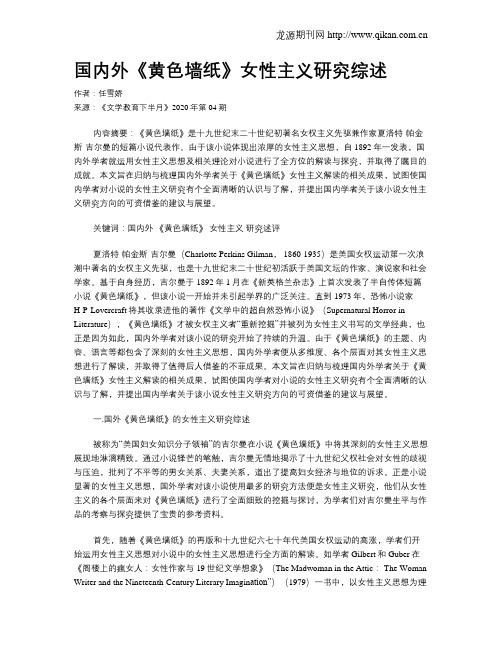
国内外《黄色墙纸》女性主义研究综述作者:任雪娇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20年第04期内容摘要:《黄色墙纸》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著名女权主义先驱兼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短篇小说代表作。
由于该小说体现出浓厚的女性主义思想,自1892年一发表,国内外学者就运用女性主义思想及相关理论对小说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与探究,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本文旨在归纳与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黄色墙纸》女性主义解读的相关成果,试图使国内学者对小说的女性主义研究有个全面清晰的认识与了解,并提出国内学者关于该小说女性主义研究方向的可资借鉴的建议与展望。
关键词:国内外《黄色墙纸》女性主义研究述评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是美国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中著名的女权主义先驱,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活跃于美国文坛的作家、演说家和社会学家。
基于自身经历,吉尔曼于1892年1月在《新英格兰杂志》上首次发表了半自传体短篇小说《黄色墙纸》,但该小说一开始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直到1973年,恐怖小说家H·P·Lovercraft将其收录进他的著作《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小说》(Supernatural Horror in Literature),《黄色墙纸》才被女权主义者“重新挖掘”并被列为女性主义书写的文学经典,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内外学者对该小说的研究开始了持续的升温。
由于《黄色墙纸》的主题、内容、语言等都包含了深刻的女性主义思想,国内外学者便从多维度、各个层面对其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解读,并取得了值得后人借鉴的不菲成果。
本文旨在归纳与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黄色墙纸》女性主义解读的相关成果,试图使国内学者对小说的女性主义研究有个全面清晰的认识与了解,并提出国内学者关于该小说女性主义研究方向的可资借鉴的建议与展望。
一.国外《黄色墙纸》的女性主义研究综述被称为“美国妇女知识分子领袖”的吉尔曼在小说《黄色墙纸》中将其深刻的女性主义思想展现地淋漓精致。
《黄色墙纸》的存在主义解读_外国文学论文【精品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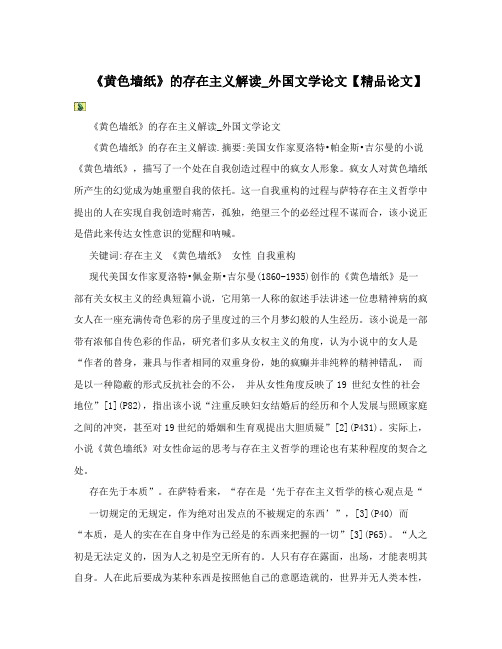
《黄色墙纸》的存在主义解读_外国文学论文【精品论文】《黄色墙纸》的存在主义解读_外国文学论文《黄色墙纸》的存在主义解读.摘要:美国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小说《黄色墙纸》,描写了一个处在自我创造过程中的疯女人形象。
疯女人对黄色墙纸所产生的幻觉成为她重塑自我的依托。
这一自我重构的过程与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提出的人在实现自我创造时痛苦,孤独,绝望三个的必经过程不谋而合,该小说正是借此来传达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呐喊。
关键词:存在主义《黄色墙纸》女性自我重构现代美国女作家夏洛特•佩金斯•吉尔曼(1860-1935)创作的《黄色墙纸》是一部有关女权主义的经典短篇小说,它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讲述一位患精神病的疯女人在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房子里度过的三个月梦幻般的人生经历。
该小说是一部带有浓郁自传色彩的作品,研究者们多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认为小说中的女人是“作者的替身,兼具与作者相同的双重身份,她的疯癫并非纯粹的精神错乱,而是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反抗社会的不公,并从女性角度反映了19 世纪女性的社会地位”[1](P82),指出该小说“注重反映妇女结婚后的经历和个人发展与照顾家庭之间的冲突,甚至对19世纪的婚姻和生育观提出大胆质疑”[2](P431)。
实际上,小说《黄色墙纸》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与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也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之处。
存在先于本质”。
在萨特看来,“存在是‘先于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是“一切规定的无规定,作为绝对出发点的不被规定的东西’”,[3](P40) 而“本质,是人的实在在自身中作为已经是的东西来把握的一切”[3](P65)。
“人之初是无法定义的,因为人之初是空无所有的。
人只有存在露面,出场,才能表明其自身。
人在此后要成为某种东西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造就的,世界并无人类本性,因为世界并无设定的人类本性的上帝”[4](P34)。
存在主义强调人的自我选择,自我构建,是因为并没有什么既定规范来限制人所应该具有的特性。
《黄色墙纸》

二、带栏杆的幼儿室
三、黄色墙纸
19世纪女性的社会地位
小说中女主人公被限制在房间之中,没有丈夫 的“指导”就不能随意活动;她只能在内心反对她医生 丈夫的“疗养”,因为她知道她的反对意见只会被忽略。
在那个年代,女性的职责还是局限于每天晚上 为归来的丈夫提供一个温暖、舒适的避风港,被置 于从属地位。
而男性不仅扮演着掌控的角色女性的健康、 孕产、精神崩溃和治疗 状况,以及女性主义和 性别关系。
墙纸中的女人不仅代表 着主人公自我意识的投 射,同时也代表着所有 受到束缚而无法实现自 我的女性。
这部小说也可以被看 做是对于神经衰弱的 一个丰富的记录。
由于黄色墙纸的刺激,表面 上看主人公疯了,实际寓意 是她最终战胜了婚姻和社会 的束缚。 只要付出巨大的 决心和努力,女性终将获得 完全的自由和解放。
从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角度解读《黄色墙纸》

2019年第10期学术专业人文茶趣收稿日期:2019年9月19日。
从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角度解读《黄色墙纸》郑芳(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桂林)摘要:《黄色墙纸》是女权运动的经典之作。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文体学,从文本中的词语和隐喻这两个方面,分析吉尔曼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并描述女性试图摆脱婚姻、家庭束缚的渴望。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体学;隐喻;男权社会Abstract:《The Yellow Wallpaper 》is a classic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By means of feminist stylistics,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criticism against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further depict women's desire for running away from the bond-age of marriage and family.Keywords:Feminist stylistics;Metaphor;Patriarchy1引言夏洛蒂•铂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是美国19世纪、20世纪之交伟大的女权主义者,还是个优秀的作家。
她将小说作为她宣扬女权主义思想的有力工具,揭露现存制度的荒谬不合理,歌颂妇女在创造性劳动中的重要作用,并传达妇女历来被压抑、忽视和排斥的心声(陈姝波,1995)。
吉尔曼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因与丈夫缺乏共同语言,产后患上了精神忧郁。
为此,她去咨询了当时著名的神经学专家米切尔医生(S.Weir Mitchell )。
后者对她采取了“疗养”法(rest cure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一贯采用的治疗方法,但是这种“疗养”法不但没有改善吉尔曼的精神状况,反而让她陷入几乎疯癫的状态,而《黄色墙纸》则是吉尔曼在这种疯癫的状态下完成的一部短篇杰作。
从《黄色墙纸》浅析吉尔曼的女性主义意识

从《黄色墙纸》浅析吉尔曼的女性主义意识作者:张晓晓来源:《大观》2017年第02期摘要: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7.3-1935.8.17),是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妇女运动的著名理论家。
她的《黄色壁纸》表现了女性主义者对于这个社会以及人生的深刻思考,表现了意识觉醒萌芽的女性对独立和自由的渴望。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提出的女性主义观点对当时和现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和学习。
关键词:女性主义;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女性主义观点;黄色壁纸一、作者背景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1860—1935)是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妇女运动的著名理论家。
吉尔曼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历任女性主义先锋作家、《先驱》月刊出版人、社会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演讲人、商业艺术家等多重职业。
吉尔曼曾入罗得岛设计学院,此外,所受其他正规学校教育不多,但其祖母家族中女性先驱辈出。
[1]她先后经历过两次婚姻,产后引发的抑郁症困扰终身,大部分作品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
在患乳癌三年后,吉尔曼于加州帕萨迪纳自杀,那正是其短篇代表作《黄色壁纸》的诞生地。
吉尔曼童年十分凄苦,父亲抛弃了吉尔曼的母亲家境十分贫寒,少女时期的她就表现出高度的自主自强。
吉尔曼结婚后育有一女,家务和琐事使她几近精神崩溃,后带着女儿离婚,开始从事著作和演讲。
而后再婚,但婚后仍然奔走于演讲和著述的事业中,关注妇女问题,倡导妇女的经济独立。
这在当时的女权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而确定了她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的地位。
二、对男权社会的谴责《黄色壁纸》几乎就是作者本身的写照,这部作品以半自传的日记形式写成,表现了吉尔曼在生下女儿之后,强烈的产后忧郁症状使她遇上了许多生活的困境。
此小说讲述了一名患有抑郁症的妻子被丈夫以“关爱的”形式软禁锢在家里,接受与外界隔绝的休养渐渐精神崩溃的过程。
夏洛蒂.吉尔曼《黄色墙纸》的结构主义解读-最新文档

夏洛蒂.吉尔曼《黄色墙纸》的结构主义解读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妇女运动的领导者。
其短篇杰作《黄色墙纸》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讲述了一位美国中产阶层知识女性因产后失调患上轻微的精神抑郁症,在一所阴暗的、恐怖的老房子里接受她的丈夫―― 一位内科医生所谓的“休息治疗”的经历。
如同女性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一样,在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女性通常都处于被支配的的地位。
而《黄色墙纸》就是一部关于一位知识女性受到压抑导致身体衰弱以及心情苦闷直至成为“疯女人”的作品,它所表现出来的妇女痛苦经历和女性反抗精神,对我们解读19世纪末女权状况有着重要意义。
对于《黄色墙纸》的解读,传统的方法是从作者生活背景、历史背景及新历史批评理论的方面,去把握小说的主题思想、写作特色、历史意义。
本文尝试以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方法对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即从内部结构透视、探求作品的深层意义结构。
一结构主义及其二元对立原则1 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哲学思潮。
它是20世纪下半叶最常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
广泛地讲,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
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 (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
结构主义的出现,帮助人们从生活混乱的表象中,揭露隐藏其中的完整结构,但亦因这简约化的结果,造成结构主义把“文本”作了过多的解读,而让学者创造出许多并不存在的意义与结构。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场广义的革命。
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强调。
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
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
国内外《黄色墙纸》女性主义研究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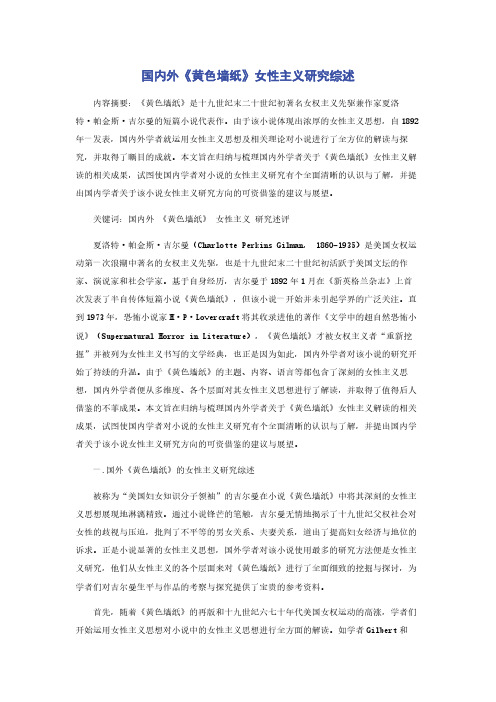
国内外《黄色墙纸》女性主义研究综述内容摘要:《黄色墙纸》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著名女权主义先驱兼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短篇小说代表作。
由于该小说体现出浓厚的女性主义思想,自1892年一发表,国内外学者就运用女性主义思想及相关理论对小说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与探究,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本文旨在归纳与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黄色墙纸》女性主义解读的相关成果,试图使国内学者对小说的女性主义研究有个全面清晰的认识与了解,并提出国内学者关于该小说女性主义研究方向的可资借鉴的建议与展望。
关键词:国内外《黄色墙纸》女性主义研究述评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60-1935)是美国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中著名的女权主义先驱,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活跃于美国文坛的作家、演说家和社会学家。
基于自身经历,吉尔曼于1892年1月在《新英格兰杂志》上首次发表了半自传体短篇小说《黄色墙纸》,但该小说一开始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直到1973年,恐怖小说家H·P·Lovercraft将其收录进他的著作《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小说》(Supernatural Horror in Literature),《黄色墙纸》才被女权主义者“重新挖掘”并被列为女性主义书写的文学经典,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内外学者对该小说的研究开始了持续的升温。
由于《黄色墙纸》的主题、内容、语言等都包含了深刻的女性主义思想,国内外学者便从多维度、各个层面对其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解读,并取得了值得后人借鉴的不菲成果。
本文旨在归纳与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黄色墙纸》女性主义解读的相关成果,试图使国内学者对小说的女性主义研究有个全面清晰的认识与了解,并提出国内学者关于该小说女性主义研究方向的可资借鉴的建议与展望。
一.国外《黄色墙纸》的女性主义研究综述被称为“美国妇女知识分子领袖”的吉尔曼在小说《黄色墙纸》中将其深刻的女性主义思想展现地淋漓精致。
在迷茫中前行由《黄色墙纸》中的象征看夏绿蒂伯金斯吉尔曼对女性自由的探索

参考内容三
基本内容
基本内容
人生规划教育,一个看似陌生但实际上对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概念。我 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面对着种种挑战和选择,人生规划教育的重要性 也因此日益凸显。它不仅帮助学生找到他们的兴趣和目标,还教会他们如何在生 活的大海中航行,勇敢面对风浪。
基本内容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人生规划教育还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它需要我们持 续的探索和改进。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人生规划教育并不仅仅是帮助学生 设定职业目标。它更是一种全面的教育,的是个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他们的兴趣、 技能、价值观和人生目标。
基本内容
最后,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的反馈和改进。人生规划教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它需要我们不断地评估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收集学生的反馈、观察他们的行为 和评估他们的成果来了解我们的教育是否有效,并根据需要做出调整。
基本内容
总的来说,人生规划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和努力。 然而,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用心去引导学生走向成功的人生 之路,我们就能在探索中不断前行,为每一位学生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好未来。
基本内容
然而,尽管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限制,主人公并没有放弃对自由的追求。她通 过不断地探索、反抗和思考,最终找到了通往自由的道路。这其中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她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而是与社会、与他人紧密相连的。因 此,她不能仅仅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而忽视他人的感受和需要。这种认识使她开 始并理解其他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从而建立起与其他女性的和团结。
基本内容
首先,国外学者对吉尔曼在《黄色墙纸》中所展现的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深 入的分析。他们认为,吉尔曼通过小说中的女性角色,表达了对当时社会对女性 的歧视与压迫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同时,他们也指出,吉尔曼的女性主义思想不 仅仅是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更是对未来社会的展望。
《黄墙纸》的女性主义视角品评

《黄墙纸》的女性主义视角品评摘要:《黄墙纸》是女性主义者吉尔曼的代表作。
文中通过描写妇女受到丈夫的控制以及男权影响的痛苦经历。
揭露了性别歧视和压迫,批判了不平等的夫妻关系,探讨了女主人公的女性意识觉醒和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象征含义,从而揭示了父权制文化对女性身心的摧残。
关键词:黄墙纸;话语权;女性主义;象征意象文章编号:1812-2485(2007)12-0029-009作为美国19世纪末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夏洛蒂·珀·吉尔曼竭力摆脱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努力实现作为女性的自我价值。
她为了争取独立,从事写作事业,不仅使自己成为著名的小说家,还同时扮演着诗人、演说家、社会评论家和记者这些社会角色,成为当时争取独立的女性的典范。
她在美国社会新秩序日益完善的19世纪末所写的《黄色墙纸》(TheYellow Wallpaper)便是一部体现女权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品。
《黄墙纸》描述了一个美国中上阶层女性因产后失调而患上轻微的精神抑郁症。
身为医生的丈夫带她住进一所殖民时期的老房子进行“休息治疗”。
这种休息治疗使她不得照看自己的孩子,不得离开,不得写作,不得做任何她喜欢做的事情。
她几乎被囚禁在一间育婴室里,她惟一可做的就是坐着看墙纸。
渐渐地,她似乎从孩子们撕得乱七八糟的墙纸上看出了图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似乎看到了牢笼里关着的一个女人。
当她认出了那个女人就是她自己时,她疯了。
丈夫在他的现实世界中如鱼得水,然而妻子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中。
她想象力丰富,忧愁而敏感。
可能是浪漫美丽的遐思,可能是灰暗阴森的冥想,这一直为丈夫公开嘲笑并严加提防。
他的这种家长制作风体现在对妻子的不屑的嘲讽、严厉的警告和亲热的诱骗中。
他的男权思想固执的认为妻子身染重症,必须治疗。
而一直以来所接受传统思想的妻子也不断强化自己的这种病态意识,乖巧听话地积极配合着丈夫。
然而整日的沉睡并没有平静纷繁的思绪,反而在不断的压抑和无意识反抗下变得烦躁沮丧又神经质。
《黄色墙纸》与吉尔曼的女权主义表达

作者: 李颜伟[1] 梁茜[2]
作者机构: [1]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天津300072 [2]天津大学文法学,天津300072
出版物刊名: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页码: 20-21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4期
主题词:�黄色墙纸》 吉尔曼 新女性观念 女权主义 生存困境
摘要: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女权主义先驱,其女性思想的形成与其本人的生活经历以及该时期美国新女性观念等进步主义思想的滥觞有着直接的联系。
吉尔曼的经典短篇小说《黄色墙纸》正是其女权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这个短篇里,她以真实的亲身经历为素材,结合虚幻荒诞的故事情节,并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通过对"我"从抑郁到疯癫的近景描写,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自传性质,体现了作家本人,对美国社会嬗变时期女性整体生存困境和精神煎熬的控诉,以及对于男女平等、女性独立与自我实现等现代两性关系与女性观念的倡导。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黄色墙纸》与十九世纪的女性主义摘要本文从女性主义作家夏洛蒂·泊金斯·吉尔曼的《黄色墙纸》出发,通过对文中的人物和情节的分析初步探讨十九世纪女性主义思潮的内涵,最后提出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黄色墙纸》,女性文学,女性主义1作品介绍《黄色墙纸》是美国十九世纪的女性文学作家夏洛蒂·泊金斯·吉尔曼的成名作。
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一名中上阶层的知识女性,因为患有轻度抑郁症而被丈夫约翰安排到一处偏僻的房子中“修养”。
身为医生的丈夫给“我”开出的处方竟然是禁止“我”做任何与思考有关的事情(譬如写作),也不准“我”四处走动,只让“我”整日呆在一个糊有黄色墙纸的房间里。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丈夫还指派了他的妹妹——珍妮对“我”进行“看护”。
珍妮是一个尽职的女管家,她时刻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并把这些如实地报告给约翰。
囚徒般的生活使“我”的精神十分压抑,“我”渐渐对墙壁上的黄色墙纸产生了幻想。
“我”发现墙纸的图案后面隐藏着许多女人,她们试图爬出墙纸,却总是被墙纸上的图案所阻止。
最后“我”决心帮助墙纸中的女人爬出来,并把自己幻想成被困在墙纸中的无数女性的一员,进而把墙纸撕裂,把房门锁起来,在房间中四处爬动。
匆匆赶来的约翰被“我”的怪异行为吓得晕倒在地,“我”就从他身上爬了过去。
[1]2人物形象2.1 “我”的丈夫——约翰约翰同“我”的哥哥一样,是一名出色的医生。
他十分爱“我”,把“我”称为“亲爱的”、“小傻瓜”、“小姑娘”、“幸福的小天鹅”,让我服用各种补品,并且禁止“我”进行任何体力和脑力劳动,甚至不让“我”动纸笔。
表面上看,他对“我”的关心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然而实际上他只是把“我”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
这可以从他对“我”的某些诉求的反应看出。
“我”提出要搬到楼下的房间里,想要有一间自己的小屋,但是他却以“那间房间放不下两张床”为由拒绝了(在十九世纪,妇女确实没有自主选择房间的权利[2]);“我”渴望写作,但是遭到约翰的反对,因为他认为“编造故事的想象力和习惯必然会把我的神经衰弱引向一种兴奋的幻想状态”而不利于“我”的病情,并且让“我”“用意志去控制这种倾向”;“我”提出要把墙纸换掉,约翰却说“更换了墙纸后,接着要更换的就是粗笨的床架,然后是上了闩的窗户,然后是楼梯前的那扇门,等等等等的东西”,后来此事也不了了之。
不难发现,约翰并没有认真考虑“我”的种种要求,而是武断地从自己的想法出发为“我”指定居住环境和疗养方法。
他并未把“我”置于平等的地位,而是把“我”当成自己的附属品,当成一具没有思想和灵魂但是可以与之共同生活的行尸走肉。
约翰以及同为医生的“我”的哥哥象征了十九世纪的父权势力,他们不认可女性的社会和家庭地位,认为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女性不能有自己的工作、思想和言论。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取了种种或明显或隐蔽的措施,如在经济上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文化上掌握发言权等。
1929 年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在其发表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2]。
“有钱”指的是要有自己的经济来源,“一间自己的房间”指的是要有独立的思想。
在男性作家的作品漫天飞舞的十九世纪,女性作家进行创作不仅要有创新的精神(以避免成为男性话语的附和者),更要有非凡的勇气。
在《黄色墙纸》作者生活的十九世纪,女性写作确实被视为一种疯癫的行为,多萝西就曾说过“即使自己一周不睡觉也不会作出这么疯癫的行为”[3],可见当时女性作家的创作面临着多么巨大的物质和思想上的阻力。
而根据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话语权意味着权力,只有充分地广播自己的话语才能确立自己的权力[4],被剥夺了话语权(写作权)的女性自然没有社会地位。
约翰和“我”的哥哥正是通过对“我”施加严密的控制(把“我”软禁在房间里,不让“我”思考)来使“我”成为一个“失语者”,以达到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目的。
2.2 “我”的小姑——珍妮“我”对珍妮的描述是这样的:“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孩啊,对我又是那么地体贴周到”、“她是一名出色而热情的女管家,她没有其他的奢望,只想做一名称职的女管家”。
但是“我”必须把自己写作的手稿隐藏起来,不让她看到。
她还仔细地向约翰报告“我”的种种情况。
珍妮代表了那一类主动接受统治的妇女,她们从未对自己的命运产生过怀疑,认为自己从属于男性是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
在她们的观念里,女性就应该在家里从事家务劳动,就应该对男性言听计从,也不能有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思想。
在父权社会里,女性已经被无意识地当成了囚犯、孩子[2],她们没有自己的天地,没有写作、工作的权力,只能被动地接受男性的安排,在父权主义的“保护伞”下小心谨慎地做好“分内事”,不敢抬头看一下外面的天空。
有时候,她们甚至沦为父权势力的帮凶,就像小说里的珍妮一样,对“我”这一类敢于怀疑、敢于反抗的新女性施加严密的监视。
这是十分可悲的。
试想,连革命的意识都没有,又怎么可能为自己争得解放?2.3 “我”“我”是一个从一开始听从丈夫到渐渐产生怀疑最后奋起反抗的女性。
和小姑珍妮不同,“我”虽然也身处父权主义的包围,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经常有写作的冲动。
因为丈夫约翰对“我”很好,一开始“我”对自己那些原本合理的要求(如更换房间、墙纸、写作等)产生了愧疚感。
但是长久的单调生活以及种种权利的被剥夺最终使“我”开始怀疑这一切的合理性,“我”开始对黄色墙纸进行观察,想从里面找出“我”想要的答案,即女性屈从于男性统治的原因。
渐渐地,“我”发现墙纸后面隐藏着一个个女人,她们在“摇动图案”,试图爬出墙纸,却被墙纸上的图案“倒转过来”,以至“眼珠都泛白了”。
“我”看到墙纸上有一个个头颅,那正是无数企图爬出墙纸的女人留下的。
“我”终于明白黄色墙纸上的图案是阻碍女性获得自由的罪魁祸首。
“我”感到自己是她们当中的一员,于是“我”打算帮她们——也帮自己爬出墙纸。
“我”象征了在父权主义统治下敢于反抗的新女性。
约翰企图用甜言蜜语以及通过把“我”限制在小房间里,阻止“我”进行写作等措施来迫使“我”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但是“我”并未简单就范。
“我”生病的事实其实也是一种掩饰,在维护女性自身独立思想的举动不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情况下,“我”只能通过“生病”这一借口来为自己的勇敢行为寻求一种存在方式。
最终“我”还是胜利了,约翰看到在地上爬行的“我”吓得晕了过去,“我”则从他身上爬过,但是那时“我”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3故事情节《黄色墙纸》中值得注意的情节主要有三个:1)故事开头约翰给“我”安排的疗法;2)故事高潮“我”撕毁黄色墙纸;3)故事最后“我”从约翰身上爬过。
3.1 无声的谋杀——约翰的疗法约翰的疗法主要包括:①让“我”服用各种补品;②限制“我”的自由,让“我”整天呆在房间里;③禁止“我”思考、写作和表达自己的意见;④派妹妹珍妮对“我”严加看护。
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三点。
约翰假借关心“我”的名义让“我”不要动脑子,还要“我”用意志控制自己的言行,其实质在于剥夺“我”的独立思想,使“我”成为一具没有反抗意识、不能自主思考的行尸走肉。
他对“我”说不允许“我”写作是为了“我”的健康考虑,但其实际用意在于使“我”丧失话语权,进而失去权力。
前面提到,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中,“话语即权力”,女性丧失了话语权之后,也就无从表达自我,只能被动地接受男性作家强加给她们的种种角色:贤妻、良母、悍妇、荡妇[2]等等,久而久之她们也就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错误地认为“女人本该如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约翰的疗法可谓十分毒辣,具有“杀人于无形”的效果。
他要谋杀的不是“我”的肉体,而是“我”的灵魂。
3.2 无畏的反抗——撕毁黄色墙纸黄色墙纸那错综复杂的图案下面隐藏着另一幅图景:无数女性被囚禁在父权制设定的条条框框里,“卑微地、无声无息地爬行着,总也逃不出父权制森严的围墙[5]”。
“我”发现墙纸是囚禁女性的牢笼后,就下定决心撕毁墙纸。
“我”撕毁黄色墙纸的行为象征了觉醒的女性意识对男权的反抗。
由于墙纸上的图案正是父权社会用来束缚女性的工具,墙纸的消失也就意味着女性终于挣脱了枷锁,获得了真正的解放。
3.3 艰难的胜利——“我”从约翰身上爬过约翰代表了十九世纪的父权势力,他最终晕倒在地象征了父权势力的统治在觉醒的女性的反抗下土崩瓦解。
故事的最后“我”从约翰身上爬过更是进一步把这种胜利推向高潮——强大的父权统治倒下了,女性越过父权社会的阻碍,获得了新生。
4总结吉尔曼的《黄色墙纸》以锐利的笔调无情地揭示了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种种隐蔽的压迫,歌颂了勇于反抗的新女性形象,展望了女性意识必将觉醒、女权必将取得与男权同等地位的光辉前景。
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三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我”的丈夫约翰、“我”的小姑珍妮还有作为“精神病人”的“我”。
约翰是父权势力的代表,珍妮是被动接受统治的旧女性,“我”则是用于反抗的新女性。
作品还通过约翰的疗法、“我”撕毁黄色墙纸的举动以及“我”从晕倒的约翰身上爬过三个情节分别寓示了男权社会为防止女性意识的觉醒而编织的严密的控制网络、新女性对于旧的性别秩序的反抗以及“性别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事实。
今日的社会与十九世纪相比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女性的权利已经得到法律、道德的保障并已广为公认,女性在现代社会中也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在某些领域,针对女性的偏见依然存在,如女性不擅长于逻辑推理、不宜成为领导者等种种论调,有些甚至深入人心,成为社会潜意识的一部分。
对此,我们要加以警惕。
在争取女性的自身权利方面,《黄色墙纸》给我们的启示有:1.女性在经济上要独立。
小说中“我”不能自由选择居住的环境,根本原因在于“我”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
为了实现经济独立,女性必须接受教育,参加工作。
2.女性在反抗时要坚决,要警惕“甜蜜的牢笼”。
小说中约翰给“我”提供了种种优越的物质条件,但是这些并不是“我”真正需要的;相反,它们使“我”疯狂。
因此,广大女性必须同男权主义做最坚决的斗争,直至最后的胜利。
3.女性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一方面,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要让自己的大脑成为男性话语的跑马场;另一方面,要敢于抛开男性已经建立的种种文学秩序,要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风格。
参考文献1. 夏洛特·P·吉尔曼and 吴其尧, 黄色墙纸.名作欣赏, 1997(03): p. 112-120+111.2. 刘建, 试论《黄色糊墙纸》中“疯女人”的形象意蕴.琼州大学学报, 2005(04): p. 60-61+70.3. 李靓, 《黄色墙纸》中的疯癫涵义.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01): p. 82-85.4. 洪流, 规训权力与反抗权力——吉尔曼《黄色墙纸》的权力机制解析.外国文学, 2006(03):p. 59-64.5. 徐冻梅, 《黄色糊墙纸》中的象征意象释读.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06): p.3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