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的轻与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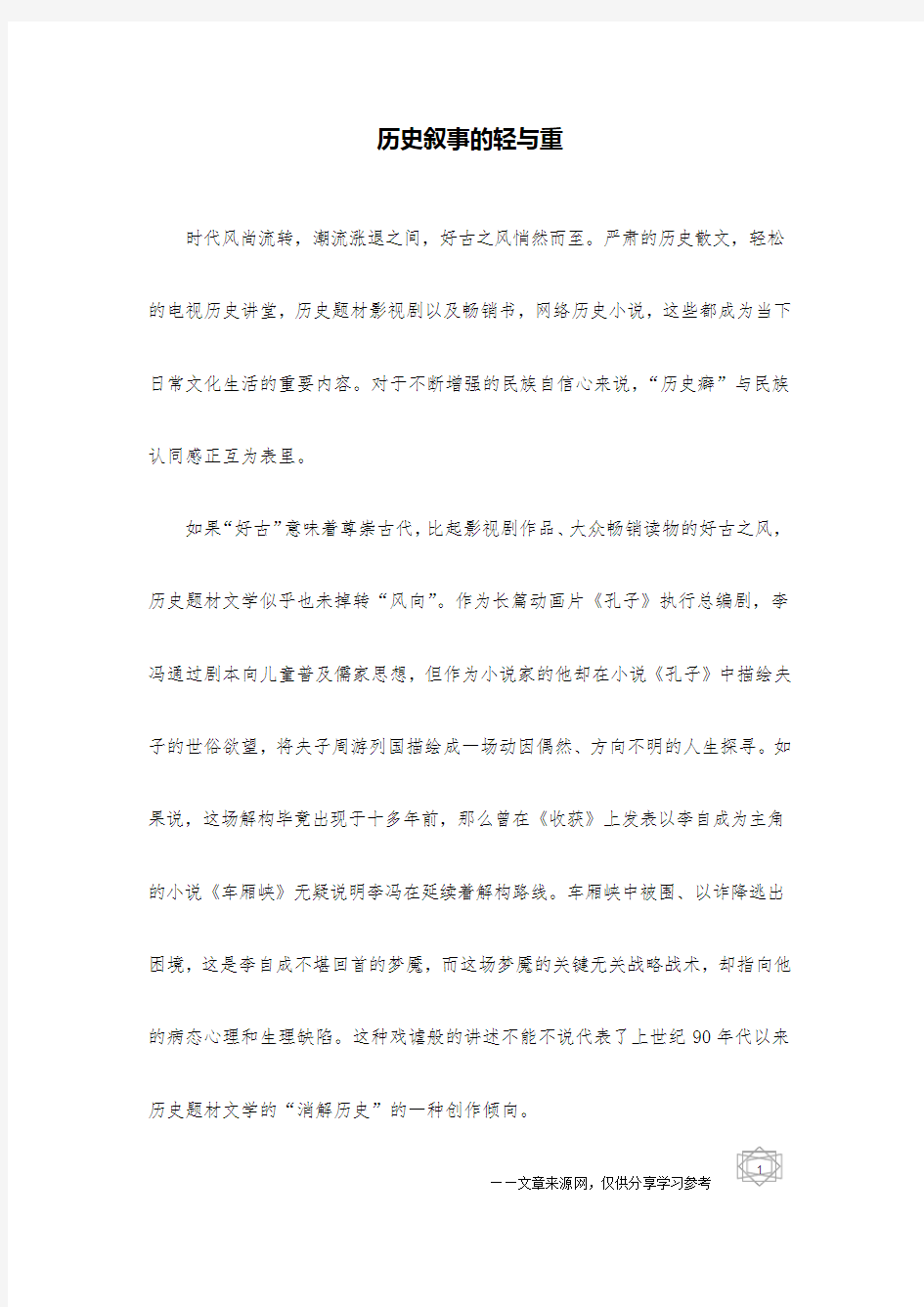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历史叙事的轻与重
时代风尚流转,潮流涨退之间,好古之风悄然而至。严肃的历史散文,轻松的电视历史讲堂,历史题材影视剧以及畅销书,网络历史小说,这些都成为当下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对于不断增强的民族自信心来说,“历史癖”与民族认同感正互为表里。
如果“好古”意味着尊崇古代,比起影视剧作品、大众畅销读物的好古之风,历史题材文学似乎也未掉转“风向”。作为长篇动画片《孔子》执行总编剧,李冯通过剧本向儿童普及儒家思想,但作为小说家的他却在小说《孔子》中描绘夫子的世俗欲望,将夫子周游列国描绘成一场动因偶然、方向不明的人生探寻。如果说,这场解构毕竟出现于十多年前,那么曾在《收获》上发表以李自成为主角的小说《车厢峡》无疑说明李冯在延续着解构路线。车厢峡中被围、以诈降逃出困境,这是李自成不堪回首的梦魇,而这场梦魇的关键无关战略战术,却指向他的病态心理和生理缺陷。这种戏谑般的讲述不能不说代表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题材文学的“消解历史”的一种创作倾向。
在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故乡相处流传》中可以看到类似的解构历史的叙事。在有意彼此戏仿的四段叙述里,曹操袁绍争战,朱元璋移民,太平天国失败……互相说明着历史的重复与历史生活的残暴。可以说,在他们的历史题材写作中,主导作家的不是历史意识而是“非历史意识”。“非历史意识”,并非没有历史意识,恰恰是要摆脱历史的沉重,凭借思辨获得一种力量,以期轻盈一跳占据批判的高地。在此类写作中,叙述指向抽象观念的普泛性,具体历史场景自然无关紧要,历史事实就更不再拘泥。
这种轻盈的叙述,有人认为缘起鲁迅《故事新编》。毕竟,鲁迅开了时空交错的写作先河,在《起死》中让死了500年的汉子复活跟庄周大捣其乱,在《理水》中让大禹时代的文化人口口声声“古貌林”……《故事新编》炉火纯青,幽默而富于批判性,笔调却轻盈无比。在这一点上,当代“故事新编”延续了叙事上的轻盈,一个个从事实拘泥中逃离出来。确实,在“非历史意识”这一点上,两者无疑有共通之处。不过,鲁迅《故事新编》作为一种小说化的文明论,他的批判指向是具体的,比如《起死》对“无是非”、“无特操”的批判,《理水》对空谈的批判和对实干的赞扬。当代“故事新编”的反叛却是抽象地拒绝历史,其
“逃离历史现场”的路径比较单一,很难跳脱用权利、情欲等人生欲望去重新解释历史的新叙事牢笼。从历史现场逃出来后要奔向哪里?他们更是不予回答——这是解构的特权,正像李冯小说《孔子》中那一趟艰苦而又荒谬的流浪旅途背后折射出的迷茫感。在这些小说中,轻盈的叙事透露出的正是后现代的主要特征:消除历史深度。《故乡相处流传》让小说人物批评历史:“历史从来都是简单的,是我们自己把它闹复杂了!”轻盈正成为一种纯质的轻。
有理论家曾将当代历史学模式归纳出三类:滑稽模仿,对同一性的分解,摧毁认知主体。三双“鞋子”做得很好,当代历史题材文学很可以舒舒服服穿上其中一双,完全不必削足适履。《故乡相处流传》中四段叙述最能体现当下历史题材文学的“滑稽模仿”特征,《车厢峡》则用人的欲望消解了农民运动的沉重,而所有这些都透露出一种否定性特征。可以说历史题材文学的创作倾向与当代历史学模式是异质同构的。
“轻”小说的出现当然有其合理性,正是对以往之“重”的反拨。不必多加追溯,2016年“茅盾文学奖长篇历史小说书系”出版,这些创作大体可以视为“重”的一端。此系列中最出色的三套——姚雪垠《李自成》、徐兴业《金瓯缺》、
刘斯奋《白门柳》——恰好可以代表90年代以前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倾向和成绩。仅就篇幅来说,这三套书就够“重”了,《李自成》300万字,《金瓯缺》120万字,《白门柳》130万字。但上述小说之“重”更在于,和90年代后“去历史化”、“非历史意识”的后现代历史叙述之“轻”迥然不同,这些大部头恰恰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意识。姚雪垠赋予失败的农民运动领袖李自成和高夫人以应时而动的时代使命与个人优秀品质;徐兴业刻画两宋之间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马扩,要从不屈不挠的主人公以及广大保家卫国的普通民众身上凸显出中华的“民族魂”;刘斯奋选择明末士人群体来描绘,是要“寻找和表现那些代表积极方面的、能够体现人类理想和社会进步的东西”,并找到了“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我国早期民主思想的诞生”。这类历史叙事背后,正是对应着一种“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
有人曾将其时代的历史意识分成三种:纪念碑式的,好古的,批判的。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是找出古代的伟大并尊崇之。好古式的历史意识则专注于从古以来就存续着的东西,认为这些载体体现着家族、城市、民族的精神。这种“好古”在上述小说中也不无体现。《金瓯缺》开头精细地描绘街道、饭店场景以及闹元
宵的节令习俗,渲染出大宋都城东京之繁华。《白门柳》则记述了大量的士人日常生活场景,比如黄宗羲寻觅稀见版本古书、钱谦益和柳如是品藻诗句、董小宛与冒辟疆煮茶等,由此展现明末清初的生活氛围与文化人心态。同时,这些历史小说无不具有更高目标:对所描绘历史时期、历史事件进行批判性反思,正所谓“批判的历史意识”。姚雪垠曾坦言,要在小说中检讨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既要成为一个小说家,更要肩负起历史学家的责任。徐兴业通过刻画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三任帝王的不同性格,描绘宋朝文臣武将在外患面前迥然相异的表现,自然而然揭示出传统文化的正负两面渗透到个人身上的深刻印记。而刘斯奋的小说以钱谦益为第一主角,揭露这样一位深具影响力的读书人在新旧政权更替之际的婉曲隐秘心态,更是以文化批判为创作主旨。
当然,以上创作并非完璧,艺术成就与历史判断都有其可商讨之处,但这些小说因其针对具体历史语境处理题材,无不沉重起来。提出这三种历史学模式的作者是针对他的时代来谈论来批判的,因为他害怕这种沉重变成压垮当代人的重负,可是,他的批判到了20世纪就发展成了一种拒斥: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被滑稽模仿所代替,虔敬好古的历史意识变成了对同一性的分解,重审往昔不公正
的批判性变成了对认识主体的彻底摧毁。这些历史题材文学,自觉不自觉地反叛“沉重”的前辈作品,形成解构之“轻”的新向度。
所谓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当下盛行的好古之风未尝不可视为新一轮的反拨征兆。小说《孔子》的消解圣人与动画片《孔子》的尊孔教化,即使有着“为文学”与“为稻粱”的区别,也不能不说其中透露出李冯等作家应时而变的思考转向。在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上,成名作家进一步的沉淀,有学术背景的新生代作家的出现,大量网络写手的忘我写作,这些也许预示着新的纪念碑式的文学样式不久将会破茧而出。
我们期待,我们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