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英第一课 第二课和第四课翻译
高级英语第一,二课的课后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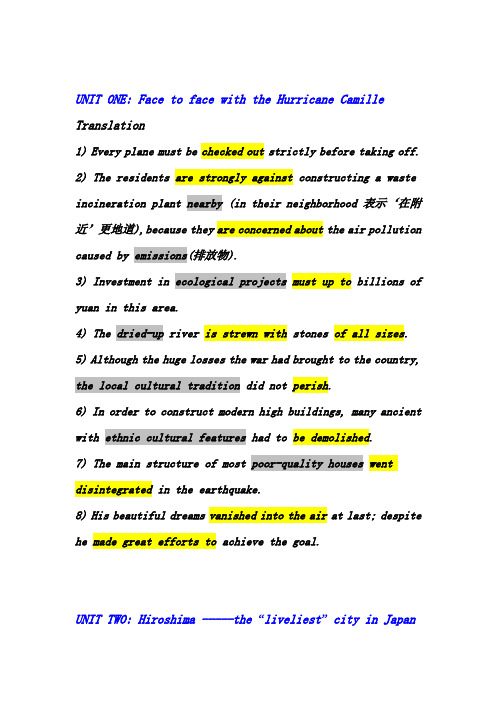
UNIT ONE: Face to face with the Hurricane Camille Translation1) Every plane must be checked out strictly before taking off.2) The residents are strongly against constructing a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 nearby (in their neighborhood 表示‘在附近’更地道),because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air pollution caused by emissions(排放物).3) Investment in ecological projects must up to billions of yuan in this area.4) The dried-up river is strewn with stones of all sizes.5) Although the huge losses the war had brought to the country, the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 did not perish.6) In order to construct modern high buildings, many ancient with ethnic cultural features had to be demolished.7) The main structure of most poor-quality houses went disintegrated in the earthquake.8) His beautiful dreams vanished into the air at last; despite he made great efforts to achieve the goal.UNIT TWO: Hiroshima -----the “liveliest” city in JapanTranslation1) There is no one in the hall.The meeting must have been put off.2)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looks very much like UFO.3) As for the northerners, Sichuan dialect sounds much the same as Hubei dialect.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tell one from the other.4) The very sight of the monument reminds me of my good friend who was killed in the battle.5) He was so deep in thought that he was oblivious of what his friends were talking about.6) What he di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her.7) She couldn't fall asleep as her daughter's illness was very much on her mind.8) I have had the matter on my mind for a long time.9) He loves such gatherings at which he rubs shoulders with young people and exchange opinions with them on various subjects.10) It was only after a few minutes that his words sank in.11) The soil smells of fresh grass.12) Could you spare me a few minutes?13) Could you spare me a ticket?14) That elderly grey-haired man is a coppersmith by trade.。
高级英语1第三版课文翻译及单词

高级英语(第三版)第一册课文译文和词汇张汉熙版Lesson 1 Face to Face with Hurricane Camille迎战卡米尔号飓风约瑟夫.布兰克小约翰。
柯夏克已料到,卡米尔号飓风来势定然凶猛。
就在去年8月17日那个星期天,当卡米尔号飓风越过墨西哥湾向西北进袭之时,收音机和电视里整天不断地播放着飓风警报。
柯夏克一家居住的地方一-密西西比州的高尔夫港--肯定会遭到这场飓风的猛烈袭击。
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三州沿海一带的居民已有将近15万人逃往内陆安全地带。
但约翰就像沿海村落中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不愿舍弃家园,要他下决心弃家外逃,除非等到他的一家人一-妻子詹妮丝以及他们那七个年龄从三岁到十一岁的孩子一一眼看着就要灾祸临头。
为了找出应付这场风灾的最佳对策,他与父母商量过。
两位老人是早在一个月前就从加利福尼亚迁到这里来,住进柯夏克一家所住的那幢十个房间的屋子里。
他还就此征求过从拉斯韦加斯开车来访的老朋友查理?希尔的意见。
约翰的全部产业就在自己家里(他开办的玛格纳制造公司是设计、研制各种教育玩具和教育用品的。
公司的一切往来函件、设计图纸和工艺模具全都放在一楼)。
37岁的他对飓风的威力是深有体会的。
四年前,他原先拥有的位于高尔夫港以西几英里外的那个家就曾毁于贝翠号飓风(那场风灾前夕柯夏克已将全家搬到一家汽车旅馆过夜)。
不过,当时那幢房子所处的地势偏低,高出海平面仅几英尺。
"我们现在住的这幢房子高了23英尺,,'他对父亲说,"而且距离海边足有250码远。
这幢房子是1915年建造的。
至今还从未受到过飓风的袭击。
我们呆在这儿恐怕是再安全不过了。
"老柯夏克67岁.是个语粗心慈的熟练机械师。
他对儿子的意见表示赞同。
"我们是可以严加防卫。
度过难关的,"他说?"一但发现危险信号,我们还可以赶在天黑之前撤出去。
" 为了对付这场飓风,几个男子汉有条不紊地做起准备工作来。
课后翻译高级英语第一册(10,12)第二册(1-4课)

第四课第四课Para 23 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把东西南北联在一起的伟大全球联盟来对付这些敌人,以确保人类享有更为丰硕充实的生活呢?能是否愿意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呢?动呢?Can we forge against these enemies a grand and global alliance, North and South, East and West, that can assure a more frui ul life for all mankind? Will you join in the historic effort?Pare 24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上,只有少数的几代人能在自由面临极大危险的时刻,被赋予保卫自由的任务。
在这一重任面前,我不退缩;我欢迎这一重任。
我认为我们中间不会有人愿意与别人或另一代人调换位置。
我们从事这一事业的那种精力,信念和献身精神将照耀我们的国家和一切为此出力的人们。
这一火焰所发出的光芒将真正照亮这个世界出的光芒将真正照亮这个世界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world, only a few genera on have been granted the role of defending freedom in its hour of maximum danger. I do not shrink from this responsibility; I welcome it. I do not believe that any of us would exchange places with any other people or any other genera on. The energy, the faith, the devo onwhich we bring to this endeavor will light our country and all who serve it, and the glow from that fire can truly light the world.Para25 因此,美国同胞们,你们要问的不是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是你自己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高英1翻译Uunit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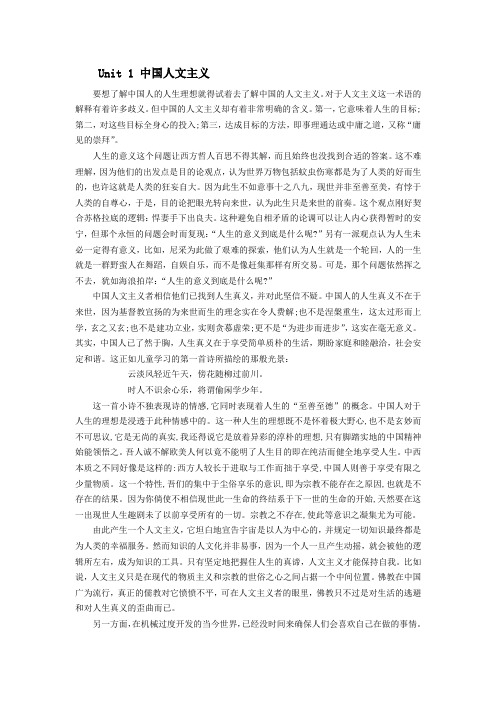
Unit 1 中国人文主义要想了解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就得试着去了解中国的人文主义。
对于人文主义这一术语的解释有着许多歧义。
但中国的人文主义却有着非常明确的含义。
第一,它意味着人生的目标;第二,对这些目标全身心的投入;第三,达成目标的方法,即事理通达或中庸之道,又称“庸见的崇拜”。
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让西方哲人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始终也没找到合适的答案。
这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目的论观点,认为世界万物包括蚊虫伤寒都是为了人类的好而生的,也许这就是人类的狂妄自大。
因为此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现世并非至善至美,有悖于人类的自尊心,于是,目的论把眼光转向来世,认为此生只是来世的前奏。
这个观点刚好契合苏格拉底的逻辑:悍妻手下出良夫。
这种避免自相矛盾的论调可以让人内心获得暂时的安宁,但那个永恒的问题会时而复现:“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另有一派观点认为人生未必一定得有意义,比如,尼采为此做了艰难的探索,他们认为人生就是一个轮回,人的一生就是一群野蛮人在舞蹈,自娱自乐,而不是像赶集那样有所交易。
可是,那个问题依然挥之不去,犹如海浪拍岸:“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中国人文主义者相信他们已找到人生真义,并对此坚信不疑。
中国人的人生真义不在于来世,因为基督教宣扬的为来世而生的理念实在令人费解;也不是涅槃重生,这太过形而上学,玄之又玄;也不是建功立业,实则贪慕虚荣;更不是“为进步而进步”,这实在毫无意义。
其实,中国人已了然于胸,人生真义在于享受简单质朴的生活,期盼家庭和睦融洽,社会安定和谐。
这正如儿童学习的第一首诗所描绘的那般光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一首小诗不独表现诗的情感,它同时表现着人生的“至善至德”的概念。
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理想是浸透于此种情感中的。
这一种人生的理想既不是怀着极大野心,也不是玄妙而不可思议,它是无尚的真实,我还得说它是放着异彩的淳朴的理想,只有脚踏实地的中国精神始能领悟之。
高级英语课文翻译(上册)

第一课超级摇滚巨星——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他们告诉我们些什么?摇滚乐是青少年反叛的音乐。
一—摇滚乐评论家约翰·罗克韦尔由其崇拜的人即可知其人。
——小说家罗伯特·佩恩·沃伦1972年6月中旬的一天,芝加哥圆形露天剧场里观众如潮,群情激昂,狂摇猛摆。
台上,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正在演唱“午夜漫步人”。
演唱结束时评论家唐·赫克曼在现场。
他说:“贾格尔抓起一个装有半加伦水的罐子沿着舞台前沿跑动,把里面的水往前几排狂热的听众身上洒。
他们蜂拥地跟随他,热切地希望能淋上几滴这洗礼的圣水。
”1973年12月下旬的一天,大约一万四千名尖声叫喊的歌迷在华盛顿市外的首都中心剧场嘈杂地涌向台前。
美国的恐怖歌星艾利斯·库珀正要结束自己表演。
他借助断头台假装结束自己生命来结束表演。
他的“头”落人一个草篮中。
“啊!”一个穿黑衣服的女孩惊呼道,“啊,太了不起了!”十四岁的迈克·玻利也在场,但他的父母并不在。
“他们觉得他令人恶心,”迈克说,“他们对我说,‘你怎么能忍受那种东西?’”1974年1月下旬的一天,在纽约州尤宁代尔的拿骚体育馆里,鲍勃·狄伦和乐队正在为音乐会上用的乐器调音。
场外瓢泼大雨中,摇滚乐迷克利斯·辛格正等着入场。
“这是朝圣,”克利斯说,“我应该跪着爬进去。
”你是如何看待所有这些溢美之词与英雄崇拜?当米克·贾格尔迷们把他视为至高的神父或神明时,你是赞成他们还是反对他们?你和克利斯·辛格一样对鲍勃·狄伦怀有几乎是宗教般的崇敬吗?你认为他或狄伦步入歧途了吗?你是否嫌艾利斯·库珀表演恶心而不接受他?还是你莫名其妙地被这个怪异的小丑吸引,因为他表现了你最疯狂的幻想?这并非是些随便问问的问题。
有些社会学家认为,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能说明你在想些什么,社会在想些什么。
换句话说,可以说明你和社会的态度。
高级英语第三版第一册课文翻译重点

高级英语第三版第一册课文翻译重点第一篇:高级英语第三版第一册课文翻译重点Lesson 1 Face to Face with Hurricane Camille迎战卡米尔号飓风约瑟夫.布兰克小约翰。
柯夏克已料到,卡米尔号飓风来势定然凶猛。
就在去年8月17日那个星期天,当卡米尔号飓风越过墨西哥湾向西北进袭之时,收音机和电视里整天不断地播放着飓风警报。
柯夏克一家居住的地方一-密西西比州的高尔夫港--肯定会遭到这场飓风的猛烈袭击。
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三州沿海一带的居民已有将近15万人逃往内陆安全地带。
但约翰就像沿海村落中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不愿舍弃家园,要他下决心弃家外逃,除非等到他的一家人一-妻子詹妮丝以及他们那七个年龄从三岁到十一岁的孩子一一眼看着就要灾祸临头。
为了找出应付这场风灾的最佳对策,他与父母商量过。
两位老人是早在一个月前就从加利福尼亚迁到这里来,住进柯夏克一家所住的那幢十个房间的屋子里。
他还就此征求过从拉斯韦加斯开车来访的老朋友查理?希尔的意见。
约翰的全部产业就在自己家里(他开办的玛格纳制造公司是设计、研制各种教育玩具和教育用品的。
公司的一切往来函件、设计图纸和工艺模具全都放在一楼)。
37岁的他对飓风的威力是深有体会的。
四年前,他原先拥有的位于高尔夫港以西几英里外的那个家就曾毁于贝翠号飓风(那场风灾前夕柯夏克已将全家搬到一家汽车旅馆过夜)。
不过,当时那幢房子所处的地势偏低,高出海平面仅几英尺。
“我们现在住的这幢房子高了23英尺,'他对父亲说,”而且距离海边足有250码远。
这幢房子是1915年建造的。
至今还从未受到过飓风的袭击。
我们呆在这儿恐怕是再安全不过了。
“ 老柯夏克67岁.是个语粗心慈的熟练机械师。
他对儿子的意见表示赞同。
”我们是可以严加防卫。
度过难关的,“他说?”一但发现危险信号,我们还可以赶在天黑之前撤出去。
“ 为了对付这场飓风,几个男子汉有条不紊地做起准备工作来。
综合教程第二版何兆熊主编 高英1-7单元课文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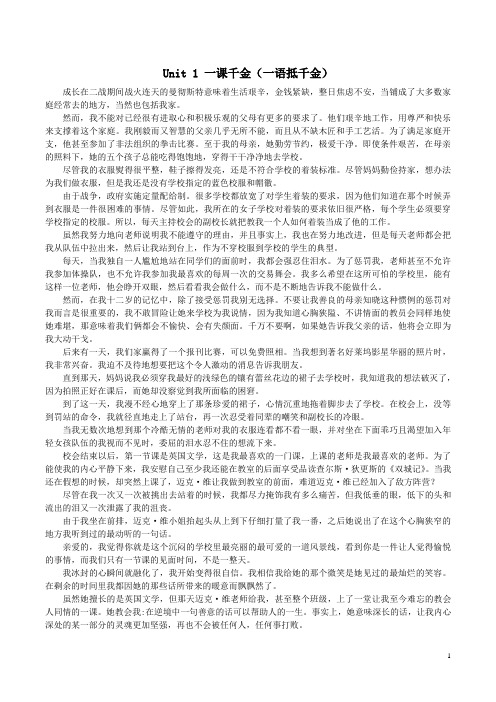
Unit 1 一课千金(一语抵千金)成长在二战期间战火连天的曼彻斯特意味着生活艰辛,金钱紧缺,整日焦虑不安,当铺成了大多数家庭经常去的地方,当然也包括我家。
然而,我不能对已经很有进取心和积极乐观的父母有更多的要求了。
他们艰辛地工作,用尊严和快乐来支撑着这个家庭。
我刚毅而又智慧的父亲几乎无所不能,而且从不缺木匠和手工艺活。
为了满足家庭开支,他甚至参加了非法组织的拳击比赛。
至于我的母亲,她勤劳节约,极爱干净。
即使条件艰苦,在母亲的照料下,她的五个孩子总能吃得饱饱地,穿得干干净净地去学校。
尽管我的衣服熨得很平整,鞋子擦得发亮,还是不符合学校的着装标准。
尽管妈妈勤俭持家,想办法为我们做衣服,但是我还是没有学校指定的蓝色校服和帽徽。
由于战争,政府实施定量配给制。
很多学校都放宽了对学生着装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弄到衣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尽管如此,我所在的女子学校对着装的要求依旧很严格,每个学生必须要穿学校指定的校服。
所以,每天主持校会的副校长就把教我一个人如何着装当成了他的工作。
虽然我努力地向老师说明我不能遵守的理由,并且事实上,我也在努力地改进,但是每天老师都会把我从队伍中拉出来,然后让我站到台上,作为不穿校服到学校的学生的典型。
每天,当我独自一人尴尬地站在同学们的面前时,我都会强忍住泪水。
为了惩罚我,老师甚至不允许我参加体操队,也不允许我参加我最喜欢的每周一次的交易舞会。
我多么希望在这所可怕的学校里,能有这样一位老师,他会睁开双眼,然后看看我会做什么,而不是不断地告诉我不能做什么。
然而,在我十二岁的记忆中,除了接受惩罚我别无选择。
不要让我善良的母亲知晓这种惯例的惩罚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我不敢冒险让她来学校为我说情,因为我知道心胸狭隘、不讲情面的教员会同样地使她难堪,那意味着我们俩都会不愉快、会有失颜面。
千万不要啊,如果她告诉我父亲的话,他将会立即为我大动干戈。
后来有一天,我们家赢得了一个报刊比赛,可以免费照相。
高英1-4课课后句子翻译

Lesson One1.This picture brings back many pleasant memories of her Spanish holiday.2.News and weather forecasts reports are staples of radio programmes.3.By mere accident Tom met in a bar his long-lost brother who was thought to have been killed in action duringthe war.4.Bill intuited something criminal in their plan.5.They think that obsessive tidiness in factory is a bad sign .6.Y esterday his mother sold several years’ worth of paper and magazines.7.His heartening speech impelled us to (work with) greater efforts.8.Those who enjoy pulling off a miracle often fail.9.As language students we should have a sense of nuances of plain words and expressions.10.The rude behavior of Mrs. Taylor’s adopted son is driving her into a nervous breakdown.11.I like to see films in general, and American Western and horrors in particular.12.In some sense Mary saw in her aunt a surrogate of her mother.13.My father never equivocated, and he always gave some brief but poignant opinions.14.Though he disabled, he never tries of helping people.15.In any country, those who are remiss in their duty must be severely punished.16.Awareness of the fact that the child was in danger impelled the policeman to action.Lesson 21. A. The chances are that they will be held up by traffic on their way to the airport.B. the plane takes off at 6:35. 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y couldn’t make it.1.Another popular notion which is in fact a misconception is that expensive clothes invariably raise one’s status.2.Can you imagine what kind of life a man has lived who aspires to excellence and abhors mediocrity?3. A copy of our latest product catalogue will be sent free of charge if you will fill up the form on the reverse ofthis card and post it.4.It will be an absurdity, if not a catastrophe. If half of the population of this city abandons their posts and goesin for business.5.Because they want their kids to be somebodies, some well-intentioned parents exercise enormous pressureson their children and the results all too often prove the reverse.6.The revered professor predicted that these brilliant young people would surely make their way in thescientific-technical realm in a few years.7.Many writers have quitted writing stories because, as they say there is no market for them. Y et Lessing sticksand she would go on even if there reall y wasn’t any home for them but a private drawer.8.Satire under his pen is only a means to an end, a form to expose social evils.9.It seemed no body at the party, not even the reporters, made special note of the general’s absence which mighthave aroused the suspicion of his rivals.10.During the first months in the strange land, the new arrivals had to take menial jobs refused by the natives andwork like slaves to make a living. Later, having saved enough money, most of them set up small businesses.11.Intellectual sluggards may get rich but they can never make good in the academic field.12.Schools should make prodigious effort to inculcate the students with a sense of justice and the love of truth.13.Y esterday she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her cousin in sian to the effect that the latter would arrive today by thenight train instead of the morning train he had mentioned in his letter.14.All her relatives were under no illusion that her husband could be one of the three lucky survivors in therecent plane crash.15.In the we st many people remain single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tie themselves down (to be tired down) toresponsibility.16.If nothing interferes the school sports meet will be held as scheduled.17.With V incent playing baseball is a means to an end, the best way to get acquainted with those stars.Lesson Three1.These gifts had got thoroughly mixed up and needed to be sorted into three different sets.2.The Security Council would take issue with the proposals put forward by the warring states.3.Because of repeated defeate d the enemy troops’ morale sank low and their discipline broke loose.4.In a bid to host the Olympic Games, what really counts is not the winning but the spirit to compete and takepart.5.In designing the office building, du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eople who will work inside it.6.The well-groomed young man is impatient to wait for the bride to arrive and the wedding ceremony tostart.7.For several weeks, the city was in a turmoil. The rebels had surrounded the City Hall, hailing stones,wielding sticks, and shouting slogans.8.After the success of the experiment, for several days, he indulged himself in the luxury of sleeping late andgetting up late.9.I’m not the type of person who thrives on city life. I am more accustomed to (the ) life in the peacefulcountryside.10.Having weathered wind and rain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se buildings of European style are barelyrecognizable as they were.11.Before the interviews, the hoary -headed father patted him on the shoulder in an extremely reassuringmanner and wished him every success.12.Som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 Monore doctrine means that European nations should no longer interferewith American nations or try to acquire more territorie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13.As a remedy for the blight of mediocrity , our society should show greater respect for excellence ineducation.14.The young mother lamented that it was her own lack of concern that had driven her boy from the house thatnight.15.His enthusiasm ebbed away when he learned how troublesome it was to go through the red tape in order togo abroad for further studies.16.As prices are skyrocketing, workers are determined to go on strike, regardless of its consequences.17.It is absurd to wear a pair of torn blue jeans at such a formal dinner.18.The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of intellectuals should entitle them to higher salaries.Lesson Four1.John remained motionless without even blinking, because he knew who the chairman remark was leveledat /against.2.The message was delivered to the wrong department owing to a mistake on the part of a clerk.3.It seems that in every attack Dickens makes upon society he always points to a change of spirit rather thana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4.Before they covered 2 km in the desert, the explorers had walked themselves dizzy and exhausted.5.After their seizure of the city, the enemy troops started to despoil all the buildings.6.He had wandered in the unsavory areas of London and seen for himself the appalling living conditions ofthe poor.7.Conrad points to a danger that is already appa rent in his friend’s writing, that of alienating his charactersfrom their social context.8.The circumstances of her childhood are not easy to establish; these were facts she herself wished to forget.9.These pages tell at least as much, if no more was jeopardized.10.Whenever an important decision is made, they defer to (the opinion of) their department head.11.As he had made bad investments, his fortune was jeopardized.12.All the staff members must be alert to the danger of fire.13.He is a person who will stand up for what he thinks right, no matter what the cost to himself.14.The highest award he w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st testifies to his musical talent.15.The peasants in that poverty-stricken area worked hard to try and wrest a living from the soil.16.He spoke in such a round-about way that we found it hard to fathom his real motives.17.In the darkness of night, an indescribable fear overlook him when he moved on alone in the jungle.18.The local department responsible for the Hope Project has collected contributions of about 2million yuan.。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第一课迎战卡米尔号飓风小约翰。
柯夏克已料到,卡米尔号飓风来势定然凶猛。
就在去年8月17日那个星期天,当卡米尔号飓风越过墨西哥湾向西北进袭之时,收音机和电视里整天不断地播放着飓风警报。
柯夏克一家居住的地方一—密西西比州的高尔夫港——肯定会遭到这场飓风的猛烈袭击。
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三州沿海一带的居民已有将近15万人逃往内陆安全地带。
但约翰就像沿海村落中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不愿舍弃家园,要他下决心弃家外逃,除非等到他的一家人一—妻子詹妮丝以及他们那七个年龄从三岁到十一岁的孩子一一眼看着就要灾祸临头。
为了找出应付这场风灾的最佳对策,他与父母商量过。
两位老人是早在一个月前就从加利福尼亚迁到这里来,住进柯夏克一家所住的那幢十个房间的屋子里。
他还就此征求过从拉斯韦加斯开车来访的老朋友查理?希尔的意见。
约翰的全部产业就在自己家里(他开办的玛格纳制造公司是设计、研制各种教育玩具和教育用品的。
公司的一切往来函件、设计图纸和工艺模具全都放在一楼)。
37岁的他对飓风的威力是深有体会的。
四年前,他原先拥有的位于高尔夫港以西几英里外的那个家就曾毁于贝翠号飓风(那场风灾前夕柯夏克已将全家搬到一家汽车旅馆过夜)。
不过,当时那幢房子所处的地势偏低,高出海平面仅几英尺。
“我们现在住的这幢房子高了23英尺,,’他对父亲说,“而且距离海边足有250码远。
这幢房子是1915年建造的。
至今还从未受到过飓风的袭击。
我们呆在这儿恐怕是再安全不过了。
”老柯夏克67岁.是个语粗心慈的熟练机械师。
他对儿子的意见表示赞同。
“我们是可以严加防卫。
度过难关的,”他说?“一但发现危险信号,我们还可以赶在天黑之前撤出去。
”为了对付这场飓风,几个男子汉有条不紊地做起准备工作来。
自米水管道可能遭到破坏,他们把浴盆和提俑都盛满水。
飓风也可能造成断电,所以他们检查r手提式收音机和手电筒里的电池以及提灯里的燃料油。
约翰的父亲将一台小发电机搬到楼下门厅里.接上几个灯泡。
并做好把发电机与电冰箱接通的准备。
那天下午,雨一直下个不停.乌云随着越来越猛的暴风从海湾上空席卷而来。
全家早早地用r晚餐。
邻居中一个丈夫去了越南的妇女跑过来。
问她和她的两个孩子是否能搬进柯夏克家躲避风灾:另一个准备向内陆带转移的邻居也跑来问柯夏克家能否替他照看一下他的狗。
不到七点钟,天就黑了.,狂风暴雨拍打着屋子。
约翰让大儿子和大女儿上楼去取来被褥和枕头给几个小一点的孩子。
他想把全家人都集中在同一层楼上。
“不要靠近窗户!”他警告说,担心在飓风巾震破的玻璃碎片会飞来伤人。
风凶猛地咆哮起来?屋子开始漏雨了……那雨水好像能穿墙透壁,往屋里直灌。
一家人都操起拖把、毛巾、盆罐和水桶,展l开了一场排水战。
到八点半钟,电没有了。
柯夏克老爹便启动了小发电机。
飓风的咆哮声压倒了一切。
房子摇晃着,起居室的天花板一块块掉下来。
楼上一个房问的法兰西式两用门砰地一声被风吹开了。
楼下的人还听到楼上其他玻璃窗破碎时发出的劈劈啪啪的响声。
积水已经漫到脚踝上了。
随后,前门开始从门框上脱落。
约翰和查理用肩膀抵住¨,但一股水浪冲击过来。
撞开了大门,把两人都掀倒在地板上。
发电机泡在水里,电灯熄灭了。
查理舔了舔嘴唇,对着约翰大喊道:“这回可真是大难临头了。
这水是成的。
”海水已经漫到屋子跟前?积水仍不断上涨。
“都从后门到汽车上去!”约翰提高嗓门大叫道。
“我们把孩子2们一个个递过去,数一数!一共九个!”孩子们从大人手上像救火队的水桶一样被递了过去。
可是汽车不能发动了?它的点火系统被水泡坏了。
水深风急。
又不可能靠两只脚逃命。
“回屋里去!.'约翰高声喊道。
“数一数孩子们。
一共九个!”等他们爬着回到屋里后。
约翰又命令道:“都到楼梯上去!,,于是大家都跑到靠两堵内墙保护的楼梯上歇着。
个个吓得要命,气喘吁吁,浑身湿透。
孩子们把取名为斯普琪的一只猫和一个装着四只小猫仔的盒子放在楼梯平台上。
斯普琪心神不定地打量着自己的幼仔,邻人的那条狗已蜷起身子睡着了。
狂风就像在身边呼啸而过的列车一样发出震耳的响声,房屋在地基上晃动移位。
一楼的外墙坍塌了,海水渐渐地漫上了楼梯。
大家沉默无语?谁都明白现在已是无路可逃.死活都只好留在崖子里了。
查理。
希尔对邻家的妇女和她那两个孩子多少尽了一点责任。
那妇女简直吓昏了头。
她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连声叫道:“我不会游泳,我可不会游泳啊r“不会游泳也不要紧?”他强作镇定地安慰她道,..一会儿便什么都过去了。
”柯夏克老奶奶伸出胳臂挽住丈夫的肩膀。
把嘴凑到他的耳边说,“老爷子,我爱你。
”柯老爹扭过头来也回了一句“我爱你,,一一…说话声已不像平日那样粗声粗气的厂。
约翰望着海水漫过一级一级的台阶,心里感到一阵强烈的内疚。
都怪他低估了卡米尔号飓风的危险性,一直认为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决不会发生。
他两手抱着头,默默地祈祷着:“啊.上帝,保佑我们度过这~难关吧!”不一会儿,?阵强风掠过,将整个屋顶卷入空中,抛向4()英尺以外。
楼梯底层的几级台阶断裂开来。
有一堵墙眼看着就要倒向这群陷入进退维谷境地的男女老少。
设在弗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国家飓风中心主任罗伯特.H.辛普森博士将卡米尔号飓风列为“有过记载的袭击西半球有人居住地区的最猛烈的一场飓风”。
在飓风中心纵横约70英里的范围内,其风速接近每小时200英里,掀起的浪头高达30英尺。
海湾沿岸风过之处,所有东西都被一扫而光。
19 467户人家和709家小商号不是完全被毁,便是遭到严重破坏。
高尔夫港一个60万加仑的油罐被狂风刮起,摔到3.5英里以外。
三艘大型货轮被刮离泊位,推上岸滩。
电线杆和20英寸粗的松树一遇狂风袭击便像连珠炮似的根根断裂。
位于高尔夫港以西的帕斯克里斯琴镇几乎被夷为平地。
住在该镇那座豪华的黎赛留公寓度假的几位旅客组织了一次聚会,从他们所居的有利地位观赏飓风的壮观景象,结果像是有一个其大无比的拳头把公寓打得粉碎,26人因此丧生。
柯夏克家的屋顶一被掀走,约翰就高喊道:“快上楼一一到卧室里去!数数孩子。
”在倾盆大雨中,大人们围成一圈,让孩子们紧紧地挤在中间。
柯夏克老奶奶哀声切切地说道:“孩子们,咱们大家来唱支歌吧!”孩子们都吓呆了,根本没一点反应。
老奶奶独个儿唱了几句,然后她的声音就完全消失了。
客厅的壁炉和烟囱崩塌了下来。
弄得瓦砾横飞。
眼看他们栖身的那间卧室电有两面墙壁行将崩塌,约翰立即命令大伙:“进电视室去!”这是离开风头最远的一个房间。
约翰用手将妻子搂了一下。
詹妮丝心里明白了他的意思。
由于风雨和恐惧,她不住地发抖。
她一面拉过两个孩子紧贴在自己身边,一面默祷着:亲爱的上帝啊,赐给我力量,让我经受住必须经受的一切吧。
她心里怨恨这场飓风。
我们一定不会让它得胜。
柯夏克老爹心中窝着一团火,深为自己在飓风面前无能为力而感到懊丧。
也说不清为什么,他跑到一问卧室里去将一只杉木箱和一个双人床垫拖进了电视室。
就在这里,一面墙壁被风刮倒了,提灯也被吹灭。
另外又有一面墙壁在移动,在摇晃。
查理.希尔试图以身子撑住它,但结果墙还是朝他这边塌了下来,把他的背部也给砸伤了。
房子在颤动摇晃,已从地基上挪开了25英尺。
整个世界似乎都要分崩离析了。
“我们来把床垫竖起来!”约翰对父亲大声叫道。
“把它斜靠着挡挡风。
让孩子们躲到垫子下面去,我们可以用头和肩膀把垫子大一点的孩子趴在地板上,小一点的一层层地压在大的身上,大人们都弯下身子罩住他们。
地板倾斜了。
装着那一窝四只小猫的盒子从架上滑下来,一下子就在风中消失了。
斯普琪被从一个嵌板书柜顶上刮走而不见踪影了。
那只狗紧闭着双眼,缩成一团。
又一面墙壁倒塌了。
水拍打着倾斜的地板。
约翰抓住一扇还连在壁柜墙上的门,对他父亲大声叫道:“假若地板塌了,咱们就把孩子放到这块门板上面。
”就在这一刹那间,风势稍缓了一些,水也不再上涨了。
随后水开始退落。
卡米尔号飓风的中心过去了。
柯夏克一家和他们的朋友都幸存下来了。
天刚破晓,高尔夫港的居民便开始陆续返回家园。
他们看到了遇难者的尸体一一密西西比沿海一带就有130多名男女和儿童丧生一海滩和公路上有些地方布满了死狗死猫和死牲畜。
尚未被风刮倒的树上结彩似地挂满被撕成布条的衣服,吹断的电线像黑色的实心面一样盘成一圈一圈地散在路面上。
那些从外面返回家乡的人们个个都是慢慢地走动着,也没有谁高声大叫。
他们怔住了,呆立当地,不知该怎么才能接受眼前这幅使人惊骇的惨景。
他们问道:“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上哪儿去呢?”这时,该地区的一些团体,实际上还有全美国的人民,都向沿海受灾地区伸出了援助之手。
天还没亮,密西西比州国民警卫队和一些民防队便开进灾区,管理交通,保护财物,建立通讯联络中心,帮助清理废墟并将无家可归的人送往难民收容中心。
上午十时许,救世军的流动快餐车和红十字会志愿队及工作人员已开往所有能够到达的地方去分发热饮料、食品、衣服和卧具了。
全国各地的数百个城镇募集了数百万美元的捐款送往灾区。
各种家用和医疗用品通过飞机、火车、卡车和轿车源源不断地运进灾区。
联邦政府运来了440万磅食品,还运来了活动房屋,造起了活动教室,并开设了发放低息长期商业贷款的办事机构。
在此期间,卡米尔号飓风横扫密西西比州后继续北进,给弗吉尼亚州西部和南部带来了28英寸以上的暴雨,致使洪水泛滥,地塌山崩,又造成111人丧生,最后才在大西洋上空慢慢消散。
第二课马拉喀什见闻一具尸体抬过,成群的苍蝇从饭馆的餐桌上瓮嗡嗡而起追逐过去,但几分钟过后又非了回来。
一支人数不多的送葬队伍——其中老少尽皆男性,没有一个女的——沿着集贸市场,从一堆堆石榴摊子以及出租汽车和骆驼中间挤道而行,一边走着一边悲痛地重复着一支短促的哀歌。
苍蝇之所以群起追逐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死人的尸首从不装进棺木,只是用一块破布裹着放在一个草草做成的木头架子上,有四个朋友抬着送葬。
朋友们到了安葬场后,便在地上挖出一个一二英尺深的长方形坑,将尸首往坑里一倒。
再扔一些像碎砖头一样的日、干土块。
不立墓碑,不留姓名,什么识别标志都没有。
坟场只不过是一片土丘林立的荒野,恰似一片已废弃不用的建筑场地。
一两个月过后,就谁也说不准自己的亲人葬于何处了。
当你穿行也这样的城镇——其居民20万中至少有2万是除开一身聊以蔽体的破衣烂衫之外完全一无所有——当你看到那些人是如何生活,又如何动辄死亡时,你永远难以相信自己是行走在人类之中。
实际上,这是所有的殖民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础。
这里的人都有一张褐色的脸,而且,人数书如此之多!他们真的和你意义同属人类吗?难道他们也会有名有姓吗?也许他们只是像彼此之间难以区分的蜜蜂或珊瑚虫一样的东西。
他们从泥土里长出来,受哭受累,忍饥挨饿过上几年,然后有被埋在那一个个无名的小坟丘里。
谁也不会注意到他们的离去。
就是那些小坟丘本身也过不了很久便会变成平地。
有时当你外出散步,穿过仙人掌丛时,你会感觉到地上有些绊脚的东西,只是在经过多次以后,摸清了其一般规律时,你才会知道你脚下踩的是死人的骷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