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小说
政治小说的名词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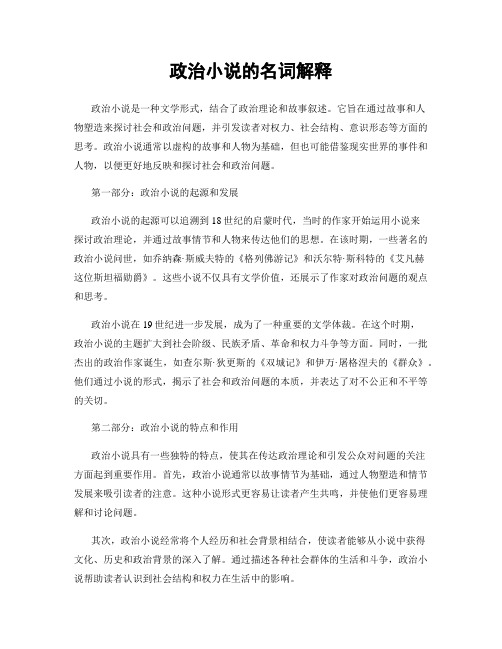
政治小说的名词解释政治小说是一种文学形式,结合了政治理论和故事叙述。
它旨在通过故事和人物塑造来探讨社会和政治问题,并引发读者对权力、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思考。
政治小说通常以虚构的故事和人物为基础,但也可能借鉴现实世界的事件和人物,以便更好地反映和探讨社会和政治问题。
第一部分:政治小说的起源和发展政治小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时代,当时的作家开始运用小说来探讨政治理论,并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来传达他们的思想。
在该时期,一些著名的政治小说问世,如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和沃尔特·斯科特的《艾凡赫这位斯坦福勋爵》。
这些小说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展示了作家对政治问题的观点和思考。
政治小说在19世纪进一步发展,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
在这个时期,政治小说的主题扩大到社会阶级、民族矛盾、革命和权力斗争等方面。
同时,一批杰出的政治作家诞生,如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和伊万·屠格涅夫的《群众》。
他们通过小说的形式,揭示了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本质,并表达了对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关切。
第二部分:政治小说的特点和作用政治小说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使其在传达政治理论和引发公众对问题的关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首先,政治小说通常以故事情节为基础,通过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来吸引读者的注意。
这种小说形式更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并使他们更容易理解和讨论问题。
其次,政治小说经常将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相结合,使读者能够从小说中获得文化、历史和政治背景的深入了解。
通过描述各种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斗争,政治小说帮助读者认识到社会结构和权力在生活中的影响。
第三部分:政治小说的经典例子政治小说有很多经典的例子,每一部都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以下是一些广为人知的例子:1. 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部小说描述了一个极权主义社会,通过创建虚假的现实世界和对人们思想的控制来探讨权力和个人自由的问题。
作品简介范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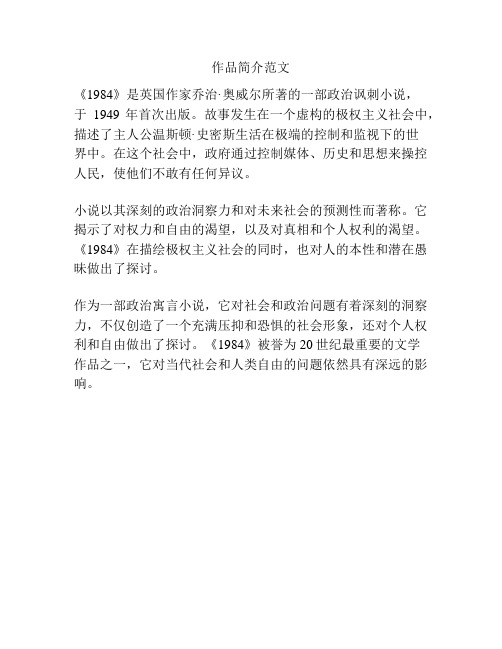
作品简介范文
《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所著的一部政治讽刺小说,
于1949年首次出版。
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极权主义社会中,描述了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生活在极端的控制和监视下的世
界中。
在这个社会中,政府通过控制媒体、历史和思想来操控人民,使他们不敢有任何异议。
小说以其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和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性而著称。
它揭示了对权力和自由的渴望,以及对真相和个人权利的渴望。
《1984》在描绘极权主义社会的同时,也对人的本性和潜在愚昧做出了探讨。
作为一部政治寓言小说,它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不仅创造了一个充满压抑和恐惧的社会形象,还对个人权利和自由做出了探讨。
《1984》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
作品之一,它对当代社会和人类自由的问题依然具有深远的影响。
高中政治新课标课外必读书目

高中政治新课标课外必读书目
1.《人民的名义》
- 作者:周梅森
- 内容简介:该小说描绘了一场惩治腐败的斗争,展示了中国
为了实现党的纪律和规矩、为了全党严守纪律创造的艰辛过程。
通
过主要人物侯亮平的行动和思考,阐述了中国反腐败的决心和坚持。
2.《局外人》
- 作者:艾伯特·加缪
- 内容简介: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对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观持
反叛态度的男子梅尔朗·泛鲁索的故事。
通过揭示主人公在社会中
的孤立和与社会的冲突,书中呈现出了对传统权威的质疑和对个体
自由的探索,启发我们思考规则与自由的关系。
3.《1984》
- 作者:乔治·奥威尔
- 内容简介:这本小说想象了一个极权社会的未来世界,通过
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的视角,描绘了国家对思想、权力和个人自
由的极度控制,以及对的严重限制。
通过这个反乌托邦的故事,书
中引发了对权力与个体自由、的反思。
4.《宣言》
- 作者: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 内容简介:这是一份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的政治宣言,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的政治纲领。
通过阐述阶级斗争、资
产阶级剥削和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共产主义
思想的根源和政治目标至关重要。
以上是建议的高中政治新课标课外必读书目,希望能够拓宽你
的政治视野,培养你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考能力。
阅读这些书籍
将对你的学业与未来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风声》读书笔记:政治悬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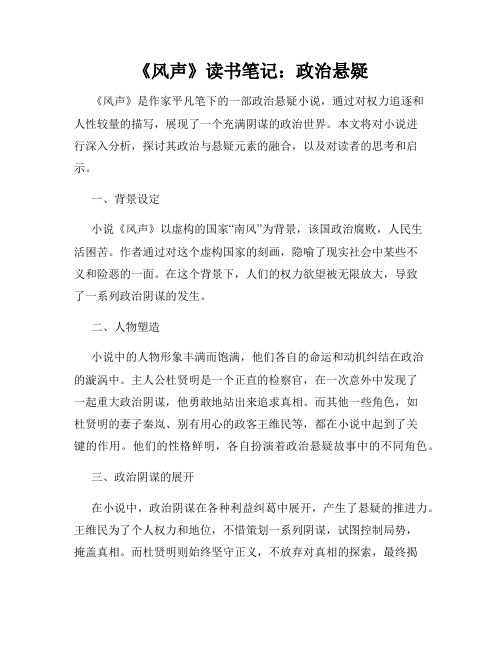
《风声》读书笔记:政治悬疑《风声》是作家平凡笔下的一部政治悬疑小说,通过对权力追逐和人性较量的描写,展现了一个充满阴谋的政治世界。
本文将对小说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政治与悬疑元素的融合,以及对读者的思考和启示。
一、背景设定小说《风声》以虚构的国家“南风”为背景,该国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
作者通过对这个虚构国家的刻画,隐喻了现实社会中某些不义和险恶的一面。
在这个背景下,人们的权力欲望被无限放大,导致了一系列政治阴谋的发生。
二、人物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丰满而饱满,他们各自的命运和动机纠结在政治的漩涡中。
主人公杜贤明是一个正直的检察官,在一次意外中发现了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他勇敢地站出来追求真相。
而其他一些角色,如杜贤明的妻子秦岚、别有用心的政客王维民等,都在小说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他们的性格鲜明,各自扮演着政治悬疑故事中的不同角色。
三、政治阴谋的展开在小说中,政治阴谋在各种利益纠葛中展开,产生了悬疑的推进力。
王维民为了个人权力和地位,不惜策划一系列阴谋,试图控制局势,掩盖真相。
而杜贤明则始终坚守正义,不放弃对真相的探索,最终揭开了一个个谜团。
作者通过政治阴谋的揭示,引发了读者对现实政治的深思。
四、权力的腐败与悲剧小说中展现了权力的腐败与悲剧。
政治权力的欲望使得一些人置道德和良知于度外,不择手段地追逐自己的利益。
人们葬送了自己的良知和正义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伤害。
小说以此来警示读者,让人们深思权力的本质和对个人命运的操控。
五、对读者的思考和启示在阅读《风声》的过程中,读者不仅可以享受到悬疑情节的刺激,还能够对政治与人性进行深入思考。
作为当代社会的一员,我们常常身处于权力的角逐中,而小说中呈现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形象地展示了权力对人性的诱惑和腐蚀。
通过对这些情节和人物的观察和反思,读者应该能够提高对权力的判断力和警觉性。
六、结语《风声》是一部政治悬疑小说,通过对政治权力的追逐和阴谋的揭示,展现了一个充满政治与悬疑元素的世界。
官场小说合集目录

官场小说合集目录一、官场小说简介官场小说是一种以官场为背景,以政治、权力、人性为主题的小说。
通过描述官员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人际关系等,展示了官场的生态和各种政治斗争。
官场小说不仅反映了社会现实,还深入探讨了权力对人性的影响和政治道德的问题。
二、官场小说合集目录1、《官场之绝色诱惑》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市领导的办公室里。
女秘书的诱惑、下属的陷阱、情人的纠缠,所有的一切都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官场百态图。
2、《权力之巅》这是一部描绘权力斗争的官场小说。
主人公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市长,他面对各种权力的诱惑和挑战,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最终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3、《官场之狼》这是一部揭露官场黑暗面的小说。
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官员,他在官场上经历了各种黑暗和腐败,但最终选择了正义,揭露了真相。
4、《官场之舞》这是一部描写官场生态的小说。
主人公是一个女官员,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在官场中一路高升,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权力和利益的诱惑。
5、《权力游戏》这是一部以政治斗争为主题的小说。
主人公是一个高官的儿子,他通过自己的智谋和手段,在政治斗争中一路高升,最终成为了权力游戏的赢家。
三、总结官场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类型,通过描述官场生态和政治斗争,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性的复杂。
这些小说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还能够让读者深入了解官场的规则和生态,提高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理解。
一、引言自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逐渐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这类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官场生活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
本文将探讨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的演变、特点以及意义。
二、官场小说的演变自上世纪80年代起,官场小说开始崭露头角。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包括二月河的《落霞》、《康熙大帝》等。
这些作品大多以历史为背景,描绘了封建王朝的兴衰,对官场生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官场小说开始现实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张平的《天网》、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等。
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地位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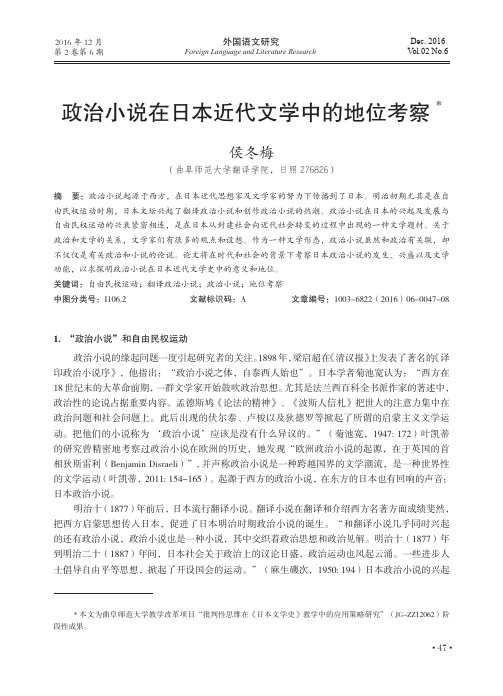
2016年12月第2卷第6期外国语文研究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Dec. 2016V ol.02 No.6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地位考察*侯冬梅(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日照276826)摘 要:政治小说起源于西方,在日本近代思想家及文学家的努力下传播到了日本。
明治初期尤其是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日本文坛兴起了翻译政治小说和创作政治小说的热潮。
政治小说在日本的兴起及发展与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衰紧密相连,是在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文学题材。
关于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文学家们有很多的观点和设想。
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政治小说虽然和政治有关联,却不仅仅是有关政治和小说的论说。
论文将在时代和社会的背景下考察日本政治小说的发生、兴盛以及文学功能,以求探明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地位。
关键词:自由民权运动;翻译政治小说;政治小说;地位考察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6-0047-081. “政治小说”和自由民权运动政治小说的缘起问题一度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他指出:“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
日本学者菊池宽认为:“西方在18世纪末的大革命前期,一群文学家开始鼓吹政治思想。
尤其是法兰西百科全书派作家的著述中,政治性的论说占据重要内容。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把世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上。
此后出现的伏尔泰、卢梭以及狄德罗等掀起了所谓的启蒙主义文学运动。
把他们的小说称为 ‘政治小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菊池宽,1947: 172)叶凯蒂的研究曾精密地考察过政治小说在欧洲的历史,她发现“欧洲政治小说的起源,在于英国的首相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并声称政治小说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文学潮流,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运动(叶凯蒂,2011: 154-165)。
新世纪政治小说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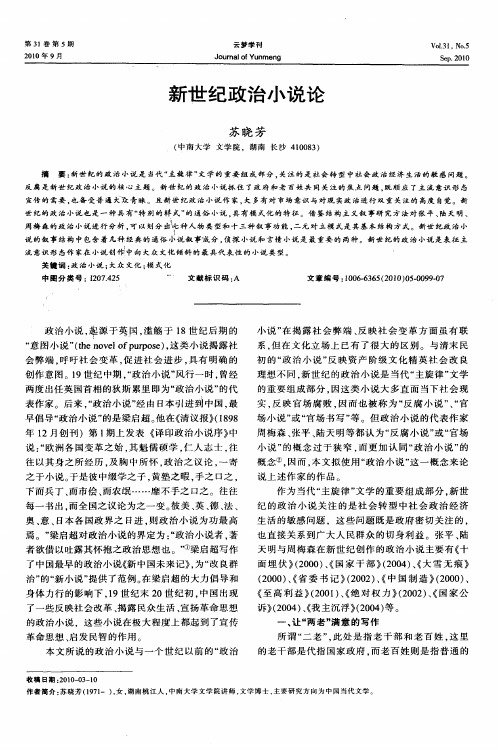
下而兵 丁 、 而市 侩 、 而农 氓 … …靡 不手 之 口之 。往 往 每一书 出 . 而全 国之议 论 为之一 变 。 彼美 、 、 、 、 英 德 法 奥、 、 意 日本各 国政 界 之 日进 , 政 治小 说 为功 最 高 则 焉 。” 启超对 政治 小说 的界定 为 :政 治小 说者 , 梁 “ 著 者欲借 以吐露 其怀 抱之 政治思 想也 。” 梁 启超 写作 ④ 了中国最早 的政治 小说 《 中国未来 记》 为“ 良群 新 , 改 治 ” 新小 说” 的“ 提供 了范 例 。 在梁启 超的 大力倡 导和
理 想不 同 , 新世 纪 的政 治小 说是 当代 “ 主旋 律 ” 文学 的重要 组成 部 分 , 因这 类小 说 大 多直 面 当下社 会现
创 作意 图 。l 9世纪 中期 ,政治 小说 ” “ 风行 一时 , 曾经
两 度 出任 英 国首 相 的狄 斯 累里 即为 “ 治小说 ” 政 的代 表作 家 。后来 ,政治小 说 ” 由 日本引进 到 中 国 , “ 经 最
作为 当代 “ 主旋 律 ” 学 的重 要组 成部 分 . 文 新世 纪 的政 治 小说 关注 的是 社 会转 型 中社 会 政 治 经济 生 活 的敏感 问题 ,这 些 问题既 是政 府 密切 关 注 的 ,
也 直 接关 系 到广大 人 民群 众 的切 身利 益 。张 平 、 陆
天 明与周 梅 森在新 世 纪创 作 的政 治 小说 主要 有《 十
“ 意图小 说 ”ten v l f up s ) 这类小 说 揭露 社 ( o e o p ro e . h 会 弊端 . 吁社 会 变革 , 进社 会 进 步 , 呼 促 具有 明确 的
小 说 ” 揭 露 社 会 弊端 、 映社 会 变 革 方 面虽 有 联 在 反 系 , 在文 化立 场上 已有 了很大 的区别 。与清末 民 但 初 的“ 治 小 说 ” 映资 产 阶级 文 化 精 英 社会 改 良 政 反
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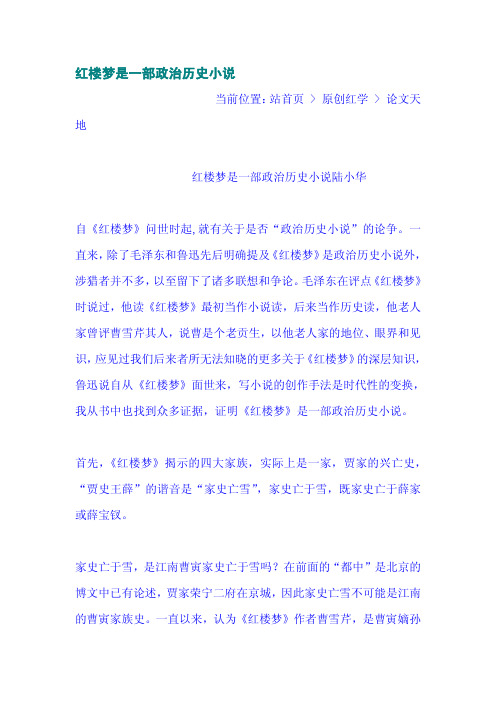
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当前位置:站首页>原创红学>论文天地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陆小华自《红楼梦》问世时起,就有关于是否“政治历史小说”的论争。
一直来,除了毛泽东和鲁迅先后明确提及《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外,涉猎者并不多,以至留下了诸多联想和争论。
毛泽东在评点《红楼梦》时说过,他读《红楼梦》最初当作小说读,后来当作历史读,他老人家曾评曹雪芹其人,说曹是个老贡生,以他老人家的地位、眼界和见识,应见过我们后来者所无法知晓的更多关于《红楼梦》的深层知识,鲁迅说自从《红楼梦》面世来,写小说的创作手法是时代性的变换,我从书中也找到众多证据,证明《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
首先,《红楼梦》揭示的四大家族,实际上是一家,贾家的兴亡史,“贾史王薛”的谐音是“家史亡雪”,家史亡于雪,既家史亡于薛家或薛宝钗。
家史亡于雪,是江南曹寅家史亡于雪吗?在前面的“都中”是北京的博文中已有论述,贾家荣宁二府在京城,因此家史亡雪不可能是江南的曹寅家族史。
一直以来,认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是曹寅嫡孙子而成桎梏,从而为贾家南北争论留下了伏笔,其实曹雪芹是不是江宁织造曹寅的嫡传孙子,值得再认真推敲,我认为不是,在《因为曹雪芹》中已涉及,此文不累!《红楼梦》第一回的楔子,对曹雪芹的来历和作用已有明确脂批,卒年应该定得下来,况且曹雪芹早年曾写过《风月宝鉴》,是其弟棠村作的序,曹雪芹有弟弟是明确的,跟江南曹寅家联系不上,我一直怀疑《红楼梦》里的龄官是曹雪芹和棠村的母亲,通过贾蔷砸了那只关押“金顶玉豆”的鸟笼的情节,暗示是放鸟外养,曹雪芹俩兄弟是不归宗的贾家人,既姓曹,应该是随母姓而已。
《红楼梦》第一回中空空道人就更奇怪了,《石头记》由空空道人定名,空空道人是在《石头记》上改朝代、地名和官衔的人,且从《石头记》到《风月宝鉴》到《金陵十二钗》到《情僧录》到《红楼梦》,最后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且问空空道人不是脂砚斋?到是谁是脂砚斋?其实,空空道人到过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石归山下无灵气!石已终,脂来悼念石头!《红楼梦》第十三回,在“若不早毁此物”此物指(“风月宝鉴”)处,脂砚斋有批语曰:凡野史俱可毁,独此书不可毁。
二十本红色经典书籍推荐3篇

二十本红色经典书籍推荐第一篇:政治史类人民的名义《人民的名义》是著名作家周梅森的代表作之一,该书通过小说的形式揭示了现今社会腐败现象的真相,揭露了权力的背后隐藏的利益和钱财交易,以及扶贫、反腐与改革的艰辛和复杂。
这本书引爆了整个社会,也掀起了整个国家的大反腐浪潮。
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李之仪在明朝中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反映了三国时期各种军阀间的政治争斗和战争,它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经典巨著。
水浒传《水浒传》是明代施耐庵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一群穷苦百姓在十二人的带领下,因为忍受不了官吏和地主的欺压,便组成了“梁山好汉”,打击豪强,反抗封建统治。
这部小说描绘了中国封建社会饱受苦难百姓的反抗,表现了封建制度中矛盾的激化和复杂的情感,也是中国小说经典之一。
红楼梦《红楼梦》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创作的古代章回小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
该书的故事围绕大观园展开,描绘了贾家和其他官僚家庭之间的复杂情感与人际关系,以及它们在封建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
第二篇:文学类红颜《红颜》是萧红早期的代表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该书以革命军阀北伐为背景,通过反复出现同名“红颜”描写了故事的主线和两位男性的所作所为,向读者展现了一幅独具特色的革命历史画卷。
围城《围城》是钱钟书创作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一对新婚夫妇在有名无实的城墙中挣扎以及他们与外界之间的矛盾与疏离,直接反映了当时官僚主义下的中国社会及文化现状,是中国现代文学之一的代表作。
梦里花落知多少《梦里花落知多少》是作家三毛的代表作之一,一部以沙漠为背景的纪实性小说。
小说以细腻的笔调描写了三毛在西班牙经历的一段恋爱故事,也描绘了三毛所感悟到的生命真相、沙漠和人性的深层奥秘。
格列佛游记《格列佛游记》是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所创作的一部著名的幽默小说,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它以现实和幻想相结合的方式,讽刺并揭示了当时英国封建社会中的各种弊端,是一部深刻而幽默、妙趣横生的文学作品。
大棋局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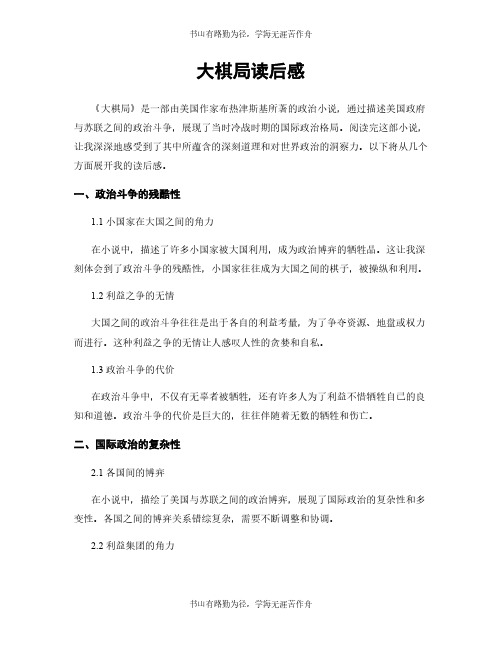
大棋局读后感《大棋局》是一部由美国作家布热津斯基所著的政治小说,通过描述美国政府与苏联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现了当时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
阅读完这部小说,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其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和对世界政治的洞察力。
以下将从几个方面展开我的读后感。
一、政治斗争的残酷性1.1 小国家在大国之间的角力在小说中,描述了许多小国家被大国利用,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小国家往往成为大国之间的棋子,被操纵和利用。
1.2 利益之争的无情大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往往是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为了争夺资源、地盘或权力而进行。
这种利益之争的无情让人感叹人性的贪婪和自私。
1.3 政治斗争的代价在政治斗争中,不仅有无辜者被牺牲,还有许多人为了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良知和道德。
政治斗争的代价是巨大的,往往伴随着无数的牺牲和伤亡。
二、国际政治的复杂性2.1 各国间的博弈在小说中,描绘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政治博弈,展现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各国之间的博弈关系错综复杂,需要不断调整和协调。
2.2 利益集团的角力除了国家之间的博弈外,利益集团之间的角力也是国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协调,影响着国际政治的格局和走向。
2.3 战略与谋略在国际政治中,战略和谋略是至关重要的。
各国需要制定合适的战略来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也需要运用巧妙的谋略来应对各种挑战和考验。
三、权力的游戏3.1 权力的诱惑在政治斗争中,权力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许多人为了追逐权力而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原则和道德。
3.2 权力的腐蚀权力的过度集中往往会导致腐败和腐蚀。
在小说中,描绘了许多角色因为权力而走向堕落和毁灭。
3.3 权力的责任拥有权力的人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滥用权力,更不能为了私利而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权力的行使需要慎重和谨慎。
四、历史的教训4.1 历史的重演在小说中,许多政治事件和人物都是取材于现实历史,这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历史的重要性和教训。
著名政治讽喻小说:The stifling horror world.doc

著名政治讽喻小说:The stifling horrorworld著名政治讽喻小说:The stifling horror world《1984》是一部极具预言性质的政治讽喻小说,描绘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惧的泯灭人性的极权主义社会。
在这个被称为大洋国的极权主义社会里,你说的每一句话,发出的每一个声响都会被监听;只要有一点光线,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监视,人性被扼杀,自由被剥夺,思想被钳制,而历史每时每刻也在被伪造。
那里的人类生存状态,永远警示着人们不要走进这黑暗的悲剧。
(选自图书介绍)作者简介乔治奥威尔(1903 1950),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社会评论家。
他一生颠沛流离,但始终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记录着他所生活的时代,致力于维护人类自由和尊严,揭露、鞭笞专制和极权主义,并提出了超越时代的预言,因此他被尊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选自图书介绍)Plot SummaryIn 1984, there were three superstates in the world --- Oceania, Eurasia and East Asia. The three countries were not peaceful together. There were continual outbreaks of wars and each country was controlled highly with centralized rules. Each country used extreme means like rewriting history and language, using monitoring screens to control people s thoughts and instinct and maintain extreme personal worship of leaders.Winston Smith, the protagonist, was a member of the Outer Party in Oceania where there was only one party, English Socialism (Ingsoc in Newspeak). He worked in the records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Truth in the history of falsification. Smith had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believed in the existence of objectivity. He hated himself in the report of the Ministry in the event oftampering with history. He doubted his own real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perception of people s thinking. In a sober environment, Winston dialogued and debated with himself in his diary to confirm his view of the world.Later he fell in love with another party member Julia, who doubted about the party s preaching too. So they became th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Ocean States leader, Big Brother, let the police take Smith into prison. In the prison, he was severely tortured and eventually his brain was washed. Finally, Winston Smith had a purity thought.Excerpts1. Double think means the power of holding two contradictory beliefs in one s mind simultaneously, and accepting both of them.2. But if thought corrupts language, language can also corrupt thought.3.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RecommendationThis book described a totalitarian society Oceania , where morals decayed, regardless of good and evil, thought was muzzled, history was tampered with, and freedom was forbidden. Life was poor and the whole world was hateful. Let us know something about the darkness of politics. Although it is a fantasy society, it is like an alarm, knocking and shocking the world. It called on people to recover conscience, reason, and common sense, and with the resistance to wake up the world.本文为原创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本文作者:GU L.J. 公众号:一起阅读。
晚清政治小说的时空想象

1 新的叙述起点与新的国家想象
以梁启 超 为代 表 的先 进 知 识 分 子 们 认 为 中 国
活幸福 ; 街上人来人往 , 止文明, 举 衣着得体 , 们 人 素质高到警察 都没有必要存在 ; 女子地位大大 提 高, 她们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成绩 。国人既不妄 自 菲薄 , 也不夜郎 自大 , 他们 经常纪念过 去 的苦难 。
开设帝国大 电厂 , 验 出一种金属原质 , 试 制成 “ 电 翅 ” 绑在人 的背 上 , 能 飞 行 , 眼千 里 。当 时西 , 就 转
第3卷 O
第1 期
东 华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会科 学版 ) 社
Vd. N0 _13O .1 M a . 011 r2
2 1 年 3月 01
J RNAL OF E T C N OU AS HI A I T T E OF T C NS I UT E HN OG OL Y
特别热 衷 于创作 政治小 说 , 以新 的叙 述起 点 建立 新 的 国家 想象 。 晚清政 治小 说 的叙 述 起 点 在 时 间上 多 着 眼 于
“ 觉世” 的功能超过 了“ 传世 ” 。吴趼人的《 新石 头 记》 大量描写 的未来新世界 , 设想 了在一个文明发
达 的环境 里 , 由姓 东方 的父 子 五人 管 理 , 国家是 开 明专制 之 国 。万 国和平会 在北 京举 行 , 中国皇 帝 发 表演讲 ; 食讲 究 科 学 搭 配 , 消 化 、 美 容 ; 们 饮 益 益 人 使 用 助听器 、 望远镜 。军事 演 习简 直与 今 天 的现 代
这些建 立 在 新 叙 述 起 点 上 的未 来 想 象 , 文 学 的 使
弱小 的主要 原 因 是 旧小 说 的 长 久毒 害 , 而 “ 们 进 他 推论 , 假如 说对 于 中国人面 临 现代 世 界手 足无 措 这
关于官场的经典小说有哪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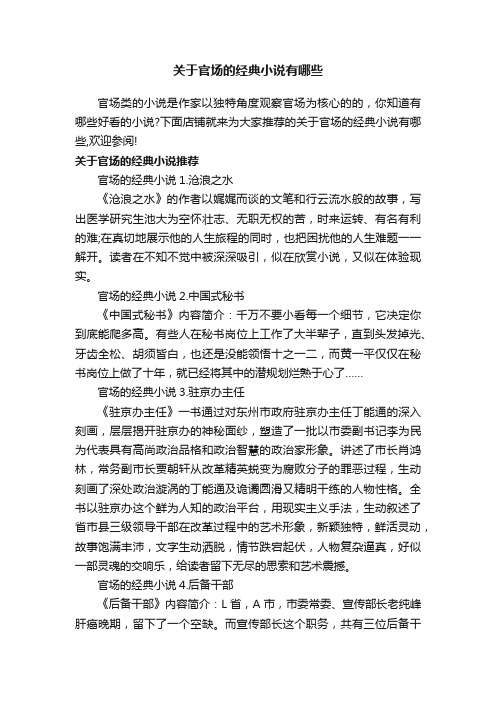
关于官场的经典小说有哪些官场类的小说是作家以独特角度观察官场为核心的的,你知道有哪些好看的小说?下面店铺就来为大家推荐的关于官场的经典小说有哪些,欢迎参阅!关于官场的经典小说推荐官场的经典小说1.沧浪之水《沧浪之水》的作者以娓娓而谈的文笔和行云流水般的故事,写出医学研究生池大为空怀壮志、无职无权的苦,时来运转、有名有利的难;在真切地展示他的人生旅程的同时,也把困扰他的人生难题一一解开。
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深深吸引,似在欣赏小说,又似在体验现实。
官场的经典小说2.中国式秘书《中国式秘书》内容简介:千万不要小看每一个细节,它决定你到底能爬多高。
有些人在秘书岗位上工作了大半辈子,直到头发掉光、牙齿全松、胡须皆白,也还是没能领悟十之一二,而黄一平仅仅在秘书岗位上做了十年,就已经将其中的潜规划烂熟于心了……官场的经典小说3.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一书通过对东州市政府驻京办主任丁能通的深入刻画,层层揭开驻京办的神秘面纱,塑造了一批以市委副书记李为民为代表具有高尚政治品格和政治智慧的政治家形象。
讲述了市长肖鸿林,常务副市长贾朝轩从改革精英蜕变为腐败分子的罪恶过程,生动刻画了深处政治漩涡的丁能通及诡谲圆滑又精明干练的人物性格。
全书以驻京办这个鲜为人知的政治平台,用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叙述了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在改革过程中的艺术形象,新颖独特,鲜活灵动,故事饱满丰沛,文字生动洒脱,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复杂逼真,好似一部灵魂的交响乐,给读者留下无尽的思索和艺术震撼。
官场的经典小说4.后备干部《后备干部》内容简介:L省,A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老纯峰肝癌晚期,留下了一个空缺。
而宣传部长这个职务,共有三位后备干部可能“出线”:李听梵、梁吾周和张嘉缑。
李听梵是省里下派的女干部,梁吾周是市委党校第一副校长,张嘉缑是市报总编辑。
三个人中,李听梵因为父亲“贪污受贿事件”,又拒绝了省委宣传部长穆天剑的非分要求而出局。
于是,梁吾周和张嘉缑围绕着这个位子,开始四处活动,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红与黑》赏析

红与黑(斯丹达尔)【思想内容】·作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与斯丹达尔其他作品一样,《红与黑》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被称为“政治小说”。
·它通过于连个人奋斗的悲剧,揭露了王政复辟时期封建贵族、天主教会和资产阶级各种势力的反动本质,再现了当时法国的社会风貌。
第一,《红与黑》暴露了上层社会贵族统治阶级的贪婪、狡诈与庸俗无能。
第二,讽刺了资产阶级金钱万能、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本质。
第三,《红与黑》揭露了教会的虚伪贪婪与势利,暴露了天主教会的黑暗和欺骗性。
总之,斯丹达尔在《红与黑》中,通过于连所接触的各阶层社会的生活,形象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势力与第三等级反复辟势力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实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作为一部政治小说,它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对上层阶级的揭露与批判是非常深刻而无情的。
【人物形象】于连: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无权和受压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形象。
他的爱憎、追求和最后失败的命运,对于这一时期被排斥于政权之外的中下层资产阶级青年是典型的。
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为出人头地而敢于冒险的英雄主义热情。
在于连身上,同时存在着反抗性与妥协性这两种看来对立的性格,构成性格的复杂性。
当环境对他有利,他就妥协;环境对他不利,他就反抗。
·他的反抗性产生于社会对他的压制,基于个人向上爬的野心。
于连对于使他这样的平民被剥夺了上升机会的现存制度是不满的,他蔑视贵族阶级合法的权威,憎恶教会的虚伪卑鄙。
·但是,他反抗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的,他主要谋求个人的出路,追求个人的飞升。
因此,其性格便自然具有软弱的一面。
正是这性格的软弱,导致了他常常与统治阶级妥协,为实现自己的美梦而甘愿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
【艺术特色】《红与黑》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在艺术上取得突出成就,表现出鲜明特色:第一,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抓取典型材料,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
政治小说——晚清文坛的奇异之葩

[ 键词] 政治小说; 日 梁启超; 发生 关 本; 中图分 类号 : 0 . I 62 2 文 献标识 码 : A 文章编 号 :6 2 6 0 2 1 ) 2 0 2 一O 1 7 —8 1 ( 0 0 0 - 0 3 2
语文 学刊
21 0 0第 2期
政治 小 说
晚清 文坛 的奇 异之 葩
。 赵 宇 华
( 宁工程技 术大 学 基 础教 学部 , 宁 葫 芦 岛 1 5 0 ) 辽 辽 2 15
[ 摘 要 ] 政治小说, 是梁启超从 日 本引进的一种文学形式, 他所介绍的政治小说, 是借小说家言, 以发起
广 铁 肠 之 《 间 莺 》《 中梅 》藤 田 鸣 鹤 之 《 明 东渐 史 》 矢 花 、雪 , 文 ,
野 龙 溪 之《 国 美谈 》 _ 。 经 等 】 ]
梁 启 超 肯 定 了 小 说 对 推 动 明 治 维 新 的作 用 , 指 出 , 并 这 些小 说 的 作 者 都是 一 些 活 跃 于 日本 政 坛 的 政 治 家 , 们 “ 他 寄 托 书 中之 人 物 , 以写 自己 之 政 见 , 不 得 专 以小 说 目之 ” 固 。文 章最 后 还 表 明 了 与 同 道 一 起 创 作 小 说 的 愿 望 : 呜 呼 !吾 安 “ 所得如施耐庵其人者 , 日夕 促膝 对 坐 , 与 指 天 画 地 , 黄 今 相 雌 古 , 纳欧亚 , 吐 出其 胸 中所 怀 块 垒 磅 礴 错 综 繁 杂 者 , 一 一 熔 而 铸 之 , 质 于 天 下 健 者 哉 之 后 , 了宣 传 君 主 立 宪 政 治 和 以 为
国民 的政 治 思 想 、 励 其 爱 国精 神 为 宗 旨 的 , 力 主 为他 的政 治 思 想服 务 的 。 它适 应 了 时代 的要 求 与 人 们 的心 声 , 激 是 获得 了 同道 人 的 支持 。但 由于政 治 形 势 的 险 恶 , 以文 学改 革 社 会 是 不 能 在 短 时 间 内见 效 的 。 随 , 梁启 超 在 日本 居 留 时 间 , 启 超 的 思 想 发 生 了很 大 梁 的 改 变 ,又 自居 东 以来 , 搜 日本 书 而 读 之 , 行 山 阴 道 上 , “ 广 若
励志政治小说推荐

励志政治小说推荐励志政治小说推荐湖南卫视一部《人民的名义》拉开了21世纪中国的政治小说,受全民关注,可见人民之心。
那么,除了《人民的名义》之外,还有哪些政治小说值得一读?今天,给大家推荐五本让你读得畅快淋漓的小说!1《国画》王跃文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历史背景上,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从省市机关的政治生活到中国农村的乡村选举,许多小说对此都有着相当真切的反映,王跃文的《国画》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部。
《国画》出版后,“人民网”就其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讨论,除了叫好声外,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甚至被媒体冠上了“现代官场现形记”的称号。
官场是一种敏感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它不仅是政治生活的聚集点,也是各种社会力量交汇、交错乃至交锋的中心地带,其本身就是一个言说不尽的地方,是社会的热点、兴奋点。
2《省委书记》陆天明陆天明的小说或剧本有相当一部分涉及敏感的反腐题材或是社会现实题材,从创作到出版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困难。
有人劝他不要再写这类题材的作品,而是写一些主旋律,爱情题材或是戏说历史题材的作品不是更好?他认为这样是挺好,但重要的是文学应该有自己的灵魂或品格,领导或长官喜欢,一味粉饰太平的作品永远不会成为主旋律。
主旋律不是为领导歌功颂德,也不等于长官意志。
为了人民,国家的利益,而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去批判丑恶,弘扬正气的作品才是主旋律。
《省委书记》是第一部全面表现当代高层政治生活和高层政治人物的长篇小说。
在这部小说中作家以史家的气魄、恢宏的气势、悬念迭出的笔法,在雄浑厚重的底色上,大胆地进入“省委书记”这一鲜为知的领域,成功地塑造了以省委书记贡开宸为代表的三代省委书记形象,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他们面对信念、事业、良心、家庭、情感、挫折和失误所表现出的激情和英雄主义悲壮。
3《二号首长》黄晓阳与以往官场小说和各种充斥坊间的厚黑学不同,《二号首长》表达出的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是根本的为官之道,是阳谋。
沉重的主题和精妙的语言——解读周梅森的政治小说《绝对权力》

作者: 谢金生
作者机构: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出版物刊名: 当代文坛
页码: 14-16页
主题词: 周梅森;政治小说;《绝对权力》;主题;语言特点;政治思想;语境;人物性格
摘要:把周梅森的《绝对权力》看作是一部政治小说无疑是十分准确的。
梁启超曾对政治小说作如下定义:“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怀抱之政治思想也。
”周梅森在《绝对权力》中十分鲜明地揭示了当今社会尤其是官场中的种种阴暗面,作者对当今政治状况的深刻思考也体现了政治小说的内涵。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耿传明--------------------------------------------------------------------------------《江汉论坛》2007年第1期本文共分5页:[1] [2] [3] [4] [5]摘要:晚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新小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标志,文学担负起了一个时代先行者的角色。
政治小说是这个时期人们宣传政治主张、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载体,它与时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时代政治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
政治的文学化与文学的政治化成为中国文学由传统步入现代的一个突出表征,浪漫主义政治和浪漫主义文学具有一种同源关系。
关键词:晚清新小说;文学政治;社会心态变异;理性主义的激情化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1-0114-06 一1900年的“庚子之变”是晚清社会变迁的分水岭,慈禧太后在守旧派彻底失败之后,也不得不倡言改革了,由此开启了历史上所谓的晚清新政时期。
由清廷启动的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酿成了一种朝野上下“咸与维新”的时代风气,由此维新、变革、改造社会等等成为时代的主导话题,求新、求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由此,引发了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
首当其冲的是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由于清廷开始倡导西学,而受到冷落,更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而遭受沉重打击。
庚子之前讲西学的人除了为数不多的“康党”之外,并不多见,而庚子之后则风气大变,士人阶层几乎全都卷入到如火如荼的兴西学热潮中,连旧学大家如桐城派古文学家吴汝纶也作出这种预言:“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
”①朴学大师孙诒让也对自己所治的旧学作出这样的反省:“救焚拯溺,贵于开悟国民,讲习科学。
不佞曩昔所业,固愧刍狗已陈,屠龙勿用。
”②由此,自命代表“西政之本源”的政治法律书籍成为时代的畅销书,如此相应的是“法政学堂”等新学堂遍地开花,成为新的“官员养成所”。
但这些并没能缓解失去了传统“晋身之阶”的士人心中的焦虑和惶恐。
诚如时人所言:“庚子重创而后,上下震动。
于是朝廷下维新之诏以图自强。
士大夫惶恐奔走,欲副朝廷需才孔亟之意,莫不问新学。
虽然,甲以问诸乙,乙以问诸丙,丙还问诸甲,相顾错愕,皆不知新学之意何云。
于时联袂城市,徜徉以求苟合,见夫大书特书曰‘时务新书’者,即麋集蚁聚,争购尤恐不及。
而多财善贾之流,翻刻旧籍以立新名,编纂陈简以树诡号,学人昧然得鱼目以为骊珠也。
朝披夕吟,手指口述,喜相告语,新学在是矣,新学在是矣!”③在这种急功近利心态下所接受的新学,显然会大失其原味。
与此相应的是对西学的推崇引发的对新的政治趋向的追求,仿行西方,进行立宪,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要求。
《东方杂志》这样报道:“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合异口同声。
”④在这种趋势之下,守旧派已成为为大众所不喜的人物,许珏因为上书反对立宪,招致的反应是:“朝野哗然,以为阻挠立宪,非愚则狂。
”⑤西学的兴盛培养起新一代读书人对“理性”的崇拜,即相信只有“公理”才具有判断一切的权威性,而公理也就是来自于西方的物竞天择、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这类出自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真理,这种空前“崇理”的风气对于推动革命是大有助力的。
孙中山先生对庚子前后人们心态的变化感触颇深:“当初之失败也,(庚子之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
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人交游也。
唯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
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受这种“崇理”思潮影响最大的当推新式学堂里的青年学生,这与遍及学校的革命党的宣传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变革时代,“时势权力”与实存权力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有力量,因为它掌握了人心的指向。
实存权力可以管束人的身体,但管束不了人心。
人心所向决定着历史前进的方向。
在公理信仰者看来,公理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发展趋势。
它之所以不可抗拒,是因为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正如邹容所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万人百千万思想也,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人人虽各有思想也,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
”⑥由此,这种崇拜公理的进步主义信仰成为时代的强势主导话语。
这种时代强势话语是为要求变革的不同政治派别所共享的,康梁君主立宪派和孙中山同盟会之间的不同并不在于对这种公理的见解上有所不同,而在于实现公理的方式途径以及对实现成本、代价的考虑等不同而已。
这种对于天演公例、世界公理的信仰构成了时代文学政治话语的核心。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考察法国大革命兴起的根源时说道:“旧制度消亡的真正原因仅仅在于它赖以为基础的传统之削弱,在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之后,旧制度再也找不到更多的拥护者,于是它就像一个根基遭到破坏的建筑那样天然坍塌了。
”⑦返观清王朝的覆亡也是如此,支撑旧的制度的文化信仰在理性主义文化的冲击下人心丕变、土崩瓦解,是导致清王朝灭亡的深层原因。
理性主义的抽象性、逻辑性以及一理万殊的普适性使它在扫荡经不起理性验证的历史遗规、传统习俗时极具杀伤力,几可使旧信仰、旧习俗毫无还手之力,从“新小说”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种现代公理的威力。
晚清“新小说”发源于梁启超1902年11月在日本横滨创刊的《新小说》杂志,梁启超不仅意识到了小说对于改良群治的重要性,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创作了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
其主要目的是要借小说来“发表政见,商榷国计”。
这部小说的影响主要不在于它是对新中国的未来的畅想曲,而是在于他对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的彻底消解:他在小说中将专制政体视为“一件悖逆的罪恶”,因为“任他甚么饮博奸淫件件俱精的强盗,甚么欺人孤儿寡妇狐媚取天下的奸贼,甚么不知五伦不识文字的夷狄贱族,只要使得着几斤力,磨得利几张刀,将这百姓像斩草一样杀得个狗血淋漓,自己一屁股蹲在那张黄色的独夫椅上头,便算是应天行运圣德神功太祖高皇帝了!”这种对于传统政体合法性的彻底否定,正是来自于一种理性主义的彻底性。
只是出于一种代价、成本的考量,梁启超后来才主张一种“无血的破坏”,但公理主义信仰使他不可能真正排斥革命,他只是一个策略意义上的“政治保守派”,并非西方意义上那种致力于自由与秩序的考量的经验主义的改革者。
晚清新小说的公理崇拜除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之外,还深受中国传统的大同主义的影响,康有为的《大同书》在理念上的彻底性是令现代人都瞠乎其后、瞠目结舌的。
他对于新社会的构想是一种唯理主义的演绎式思维,《大同书》可以说是一个把理性进行到底的范例。
但现实中的康有为还是把应然和实然区分开来的,所以他的《大同书》虽早就写出,但一直不愿公之于世,因为担心此书一出导致的结果将会是血流成河,他没有完全取消理念与现实的分野,因此只能成为一个理论和实践两分的改革者。
他认为:“理想乃是将来的缩影,而实际必须符合目前的境遇。
”⑧这当然也是他迅速为时代抛弃的原因。
公理主义在革命时代起着类似于革命的“发动机”的关键作用,它煽动起人们的热情和梦想,呼唤人们主动参与到历史创造之中。
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它迅速地推动了晚清士风的转换,即由“名士”向“志士”的转变,使得创造历史的英雄主义成为时代的主调。
实则吸引晚清理性主义者的并不是“理性”自身,而是从对理性的信仰中生发出来的激情和创造新世界,使自己留名千古、铜像巍巍的使命感。
这种激情化的理性崇拜和英雄主义的使命感使他们排斥对其信仰的理性本身进行任何理性的反思,因此它沉浸在自己的信仰之中,除了信仰之外再不考虑其他,并拒绝任何批评,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视为必须剪除的敌人。
由此它不仅违背了理性必须从正反双向进行才能发展存在的本质,而且取消了对理性的任何限制,走向一种唯理主义。
这种公理崇拜可说是催生出了现代中国第一代可称之为“理念人”的现代知识分子,但这种理念人只是将传统静态的“天理”代之以进化的“公理”而已,尚未领会真正的理性思考的真谛。
公理至上填补了传统信仰退位留下的空缺,满足了现代人追求政治自由的需要,但由于这一需要完全排斥了其他的需要,则可能会导致一种新的绝对主义的公式化的思维方式。
政体、国体在传统专制时代都是不容人置喙的问题,到了清末新政时期,则成为人人都可以置喙的热门话题。
人人都可以自由设计选择政体、国体,这种政治上的开放、自由可以说是空前的,传统束缚至此已完全失效。
旅生的《痴人说梦记》开篇就是写现代的读书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常规:书中的宁孙谋是康有为的化身,他首先要做的是“要做一部书,人皆晓得十三经要读的,殊不知道经书,早被秦朝一把火烧尽了,其余多半是后人伪造。
我想出许多证据,在肚子里尚未写出,趁着日长无事,要做成这部书,免得那些迂儒,谈三皇,说五帝,弄得浑身束缚,一样事都做不成功。
……我做这部书的意思,是要先将读书人第一个照例的念头打断,你道好不好?”他的朋友听到他的这番高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挣脱了常例束缚的读书人,或主君主立宪、或主革命暴动、或主海外殖民——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建立理想国。
政治选择的不同也决定了小说想象模式的差异:君主立宪派的《新中国未来记》,在虚拟的倒叙式叙述中仍在延续与革命派的激烈辩论,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痴人说梦记》则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小说的代表,他们都钟情于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建立一个文明极致的模范新社会,其理想越高超、彻底,也就离现实越远。
如后来鲁哀鸣的《极乐地》等等也是如此。
革命党小说则多在现实背景下展开理想,表现出一种写实和浪漫相结合的倾向,崇高的理想通过斩草除根式的革命彻底性表现出来,这可以《黄绣球》为代表。
源于唯理主义的革命最为反对的是从“枝节上的推求”,即零碎的、渐进的改革,而追求根本性的变革、理念上的彻底性。
如《黄绣球》用了两个比喻来表达这种彻底性:一个比较常见,即房子要倒了,是修理它还是拆掉它彻底重建,革命者的选择显然是后者。
即不拆旧房子建不起新房子。
第二个比喻是花和蚂蚁的比喻:黄通理问两个儿子:“譬如一棵花,种在地上,花上爬了些蚂蚁,这便怎样?难道就把花掐了不成?”那大的说:“这与花何害?只要将蚂蚁除去便是。
”小的则说:“不然,好好的一朵花,固然不能掐去,但是蚂蚁除了又有。
就算这枝花上除去,他又爬到那枝花上去了,除之不尽,劳而无功,不如寻着蚂蚁的窠,或是掘了他的根,或是把种的花移种在好地上去,叫蚂蚁无从再爬,然后我们的花才能开得枝枝茂盛,年年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