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力的双重治理:对人主体生命的隐性统治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导言: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权力、知识和主体的研究为后续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福柯的思想围绕着权力实践、知识形成和主体解构展开,从而对现代人的社会存在和政治权力有了新的理解。
本文将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出发,以及他的“人之死”概念为线索,探讨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
一、知识考古学的历史视角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的研究,对西方的知识形成和权力实践进行梳理,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
他将知识视为一种权力实践的产物,通过历史的视角,追溯各种知识形态的出现和转变过程。
福柯认为,知识不仅限于科学理性的范畴,还包括诸如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知识形式,这些知识形式的出现和发展,既受到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也与权力实践息息相关。
在福柯看来,知识考古学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知识形成的历史变迁,更为重要的是,它暴露了知识背后的权力运作。
他指出,知识的产生和传播都与特定的权力机构和机制相连,通过这些机制,某些知识形态得到推广和强制实施,而其他形态则被边缘化或排斥。
这种权力运作使得知识成为一种社会政治控制的工具,进而影响和塑造了主体的认识和行为方式。
二、权力知识与主体解构福柯将权力和知识作为主体解构的关键要素,认为主体是权力和知识的受托者和生产者。
他以权力知识的交织关系为出发点,分析了权力如何通过知识的生产和运作来约束和操控主体的思想和行为。
福柯提出了“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的概念,认为通过对生命的控制和规训,权力得以深入主体的内部,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和法律的监管,将主体纳入到自己的支配之下。
福柯关注的“人之死”概念是他主体解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人的生命和死亡被权力所制约,权力通过生命的规训和控制来塑造主体的行为和身份。
福柯研究了人类历史上关于人之死的不同实践和观念,揭示了生命权力如何通过技术、医学等手段对主体进行干预,从而影响主体的自由和身份认同。
福柯论技术治理

福柯论技术治理作者:刘永谋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03期摘要:从技术治理的视角看,福柯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一是区分技术、规训技术和人口技术等三种技治技术;二是“知识纪律化过程”;三是专家政治研究;四是技术反治理;五是作为反治理措施的自我技术。
福柯对技术治理的批判具有反科学主义、历史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特征,对于研究技术的治理与反治理之间的平衡颇有启发。
由于对技术的理解过于宽泛,福柯的批判显得有些混乱,尤其是他将局部反抗、生存美学和自我技术作为反抗的出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导致无法找到人类彻底解放的方向。
关键词:福柯;技术治理;技术反治理;专家政治中图分类号:B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22)03-0009-14技术治理是当代社会公共治理领域的普遍趋势。
所谓技术治理,指的是将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运用于社会运行当中的治理活动。
技术治理是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重要议题,有时他称之为现代“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e)研究。
总体而言,他对技术治理持极端的批判态度,详细地对各种技术治理所用的治理技术进行过不厌其烦地批判。
并且,他试图寻找某种“反治理术”以对抗技术治理。
福柯对技术治理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当代社会治理的基本趋势,更好地运用和控制技术治理,为社会福祉服务。
一、批判科学运行原则“技术治理二原则”是不同形式技术治理模式都坚持的基本立场,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运行原则,即运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运行当代社会。
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是知识—权力主导政治和公共治理活动的社会,依赖科学技术知识来维持其权力秩序,因而实际上是技治社会。
对此,福柯的批判是指:现代社会坚持的科学运行原则,实际上是依据知识—权力的权力治理,而不是依据客观真理的治理,只是名之为真理的权力运作。
(一)知识—权力即技术治理福柯讨论的现代科学技术虽然涉及的学科门类众多,但均在权力—知识的范围内,即在与现代权力“共生”的知识谱系之中。
当代生命政治学的三种范式

摘要:生命政治学已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热门话题。
肇始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当代生命政治学已形成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其一是以福柯为代表的生命权力范式展现出资本主义的治理力量,其二是以齐泽克为代表的生命安全范式体现出美国主导的霸权力量,其三是以奈格里、哈特为代表的生命潜能的范式呈现出诸众的自治力量。
从学理层面上明晰当代生命政治学的不同范式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生命政治学的理论。
与此同时,厘清当代生命政治学的不同范式可以透视到生命政治学的生产性的内在线索,这为我们找到生命政治的解放指明了道路。
关键词:生命政治学;生命权力;生命安全;生命潜能中图分类号:B1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20)01-0096-07作者简介:刘茜(1991—),女,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当代生命政治学的三种范式刘茜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米歇尔·福柯在法兰克福学院的讲座中提出了“生命政治”一词,从而开启了生命政治的理论视阈。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受到大批哲学家的关注,尤其以激进左派阿甘本为代表的生命政治学,重新打开了关于生命政治研究的新格局,生命政治学进而也成为当代哲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
福柯作为最为代表性的生命政治学家,但是将生命政治等同于福柯的思想则规避了生命政治学的当代意义,从而造成我们对生命政治学的理解模糊和片面。
事实上,当代生命政治学已经呈现出三种不同范式:第一是以福柯为代表,从生命权力视角出发所构建的治理力量;第二是以齐泽克为代表,从生命安全视角出发所展现的霸权力量;第三是以奈格里、哈特为代表,从生命潜能视角出发所形成的自治力量。
这三种范式共同构筑了生命政治的理论内涵。
如果我们只是从福柯、阿甘本的视角去理解生命政治学,将不利于我们对生命政治学的全面理解,甚至造成对生命政治学的误读。
从生命权利到生命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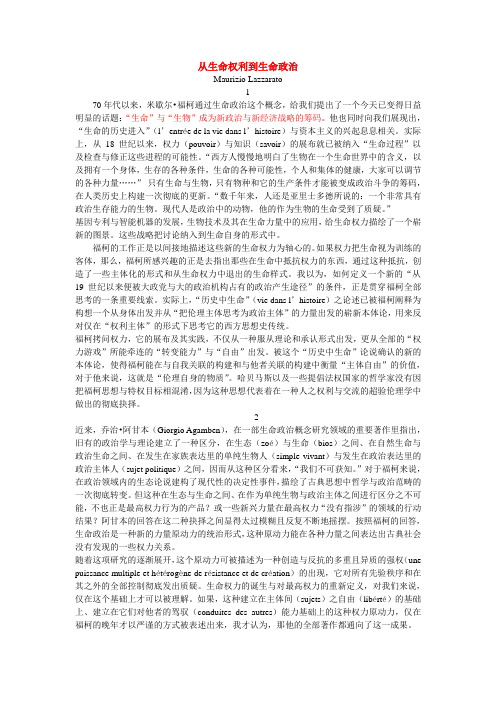
从生命权利到生命政治Maurizio Lazzarato170年代以来,米歇尔•福柯通过生命政治这个概念,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今天已变得日益明显的话题:“生命”与“生物”成为新政治与新经济战略的筹码。
他也同时向我们展现出,“生命的历史进入”(l’entrée de la vie dans l’histoire)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息息相关。
实际上,从18世纪以来,权力(pouvoir)与知识(savoir)的展布就已被纳入“生命过程”以及检查与修正这些进程的可能性。
“西方人慢慢地明白了生物在一个生命世界中的含义,以及拥有一个身体,生存的各种条件,生命的各种可能性,个人和集体的健康,大家可以调节的各种力量……”只有生命与生物,只有物种和它的生产条件才能被变成政治斗争的筹码,在人类历史上构建一次彻底的更新。
“数千年来,人还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非常具有政治生存能力的生物。
现代人是政治中的动物,他的作为生物的生命受到了质疑。
”基因专利与智能机器的发展,生物技术及其在生命力量中的应用,给生命权力描绘了一个崭新的图景。
这些战略把讨论纳入到生命自身的形式中。
福柯的工作正是以间接地描述这些新的生命权力为轴心的。
如果权力把生命视为训练的客体,那么,福柯所感兴趣的正是去指出那些在生命中抵抗权力的东西,通过这种抵抗,创造了一些主体化的形式和从生命权力中退出的生命样式。
我以为,如何定义一个新的“从19世纪以来便被大政党与大的政治机构占有的政治产生途径”的条件,正是贯穿福柯全部思考的一条重要线索。
实际上,“历史中生命”(vie dans l’histoire)之论述已被福柯阐释为构想一个从身体出发并从“把伦理主体思考为政治主体”的力量出发的崭新本体论,用来反对仅在“权利主体”的形式下思考它的西方思想史传统。
福柯拷问权力,它的展布及其实践,不仅从一种服从理论和承认形式出发,更从全部的“权力游戏”所能牵连的“转变能力”与“自由”出发。
生命政治反抗资本统治的三重原则——从奈格里的激进政治解读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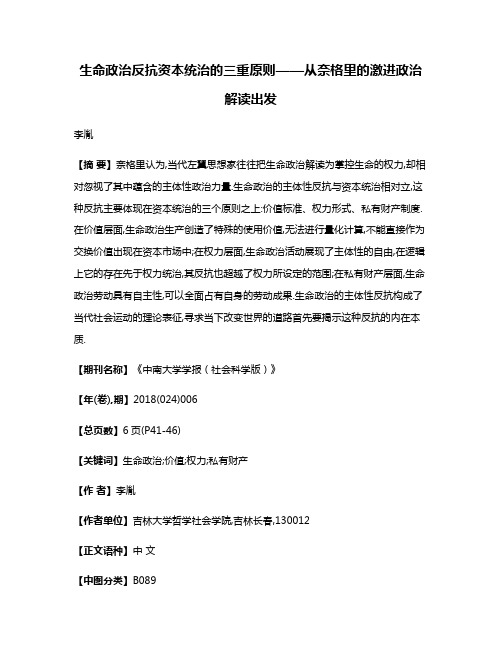
生命政治反抗资本统治的三重原则——从奈格里的激进政治解读出发李胤【摘要】奈格里认为,当代左翼思想家往往把生命政治解读为掌控生命的权力,却相对忽视了其中蕴含的主体性政治力量.生命政治的主体性反抗与资本统治相对立,这种反抗主要体现在资本统治的三个原则之上:价值标准、权力形式、私有财产制度.在价值层面,生命政治生产创造了特殊的使用价值,无法进行量化计算,不能直接作为交换价值出现在资本市场中;在权力层面,生命政治活动展现了主体性的自由,在逻辑上它的存在先于权力统治,其反抗也超越了权力所设定的范围;在私有财产层面,生命政治劳动具有自主性,可以全面占有自身的劳动成果.生命政治的主体性反抗构成了当代社会运动的理论表征,寻求当下改变世界的道路首先要揭示这种反抗的内在本质.【期刊名称】《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8(024)006【总页数】6页(P41-46)【关键词】生命政治;价值;权力;私有财产【作者】李胤【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089在当代左翼的政治哲学中,生命政治构成了一个核心话题。
学术界往往侧重于从权力统治的视角出发来解读生命政治。
在这一视角下,生命政治被视作一种掌控生命的权力,也正是这样一种控制生命的外在力量,构成了当代左翼批判的绝佳样本。
然而,这里同时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困境,那就是基于这一视角的思想仅仅只能停留在批判的认识论层面,它无法继续为批判之后的变革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与同时代的左翼理论家不同的是,奈格里还将生命政治解读为“生命本身的力量,可以反抗并寻求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1](36)。
奈格里的这一解读内含一个重大的突破,即他从权力统治的视角转向了被统治者的主体性视角,进而阐发了一种新的理解生命政治的思想路径。
在新的视角下,生命政治作为一种主体性的“政治”力量,体现在与统治结构的对立关系当中,它能够为反抗统治提供内在动力,为社会关系的变革提供可能性,而同时代的思想家则普遍忽视了这种被统治视角下的反抗形式。
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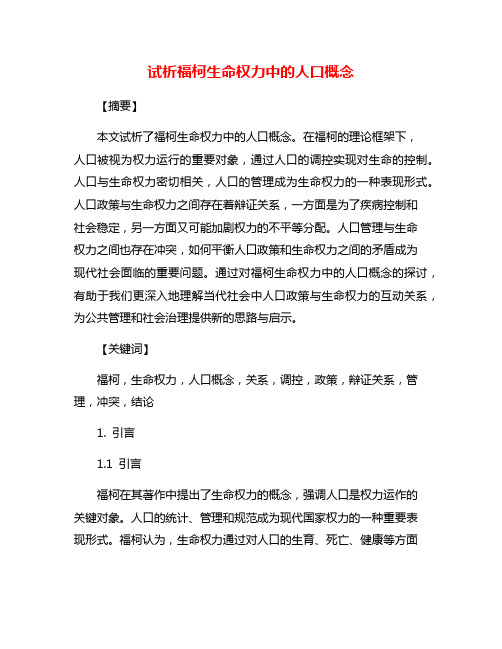
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摘要】本文试析了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在福柯的理论框架下,人口被视为权力运行的重要对象,通过人口的调控实现对生命的控制。
人口与生命权力密切相关,人口的管理成为生命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人口政策与生命权力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一方面是为了疾病控制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又可能加剧权力的不平等分配。
人口管理与生命权力之间也存在冲突,如何平衡人口政策和生命权力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通过对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代社会中人口政策与生命权力的互动关系,为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与启示。
【关键词】福柯,生命权力,人口概念,关系,调控,政策,辩证关系,管理,冲突,结论1. 引言1.1 引言福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生命权力的概念,强调人口是权力运作的关键对象。
人口的统计、管理和规范成为现代国家权力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福柯认为,生命权力通过对人口的生育、死亡、健康等方面进行监视和控制,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管理。
人口因此成为生命权力调控的核心对象。
人口与生命权力的关系紧密相连,人口的数量、质量、分布以及结构都受到生命权力的影响。
生命权力通过各种手段对人口进行干预和控制,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人口对于生命权力而言不仅是被统计和管理的对象,同时也是其行使权力的主要对象之一。
生命权力中的人口调控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对人口进行调整和管理,以实现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
人口调控包括生育政策、移民政策、卫生政策等方面的措施,旨在控制人口数量和结构,以满足社会发展和权力运作的需要。
人口政策与生命权力的辩证关系体现在政策既要保障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又要维护国家的长期利益和社会的稳定。
在实践中,人口政策常常受到生命权力的影响和制约,需要在人口管理和生命权力之间寻求平衡和调和。
人口管理与生命权力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个体权利与集体权益、国家利益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矛盾。
人口管理往往涉及到对个体生活和自由的限制,引发社会对权力运作的质疑和抵制。
这次第怎一个“罪”字了得--论莫言《蛙》的批判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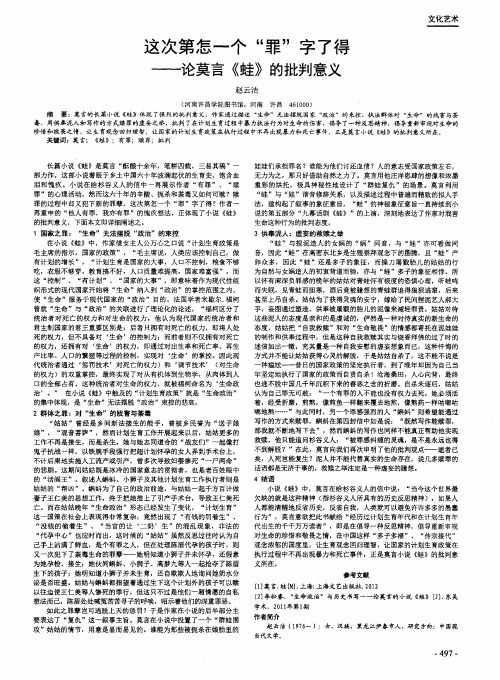
毒、 用供奉泥人和写作的方式赎罪的虚妄之举,批判 了 在计划生育过程中暴力执法行为对生命的伤害,倡导 了一种反思精神,倡导重新审视对生命 的 珍惜和敬畏之情,让生育观念回归理智,让 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过程 中不再 出 现暴力和死亡事件 ,正是莫言小说 《 蛙》的批判意义所在
关 键词 :莫 言 ; 《 蛙 ; 有 罪; 赎罪 ;批 判
长 篇小说 《 蛙》是莫言 “ 酝酿十余年 ,笔耕 四载 ,三 易其稿 ”一 部力作 ,这部小说着眼于乡土 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 育史,饱含血 泪 和愧疚 。小说在给 杉谷义人 的信 中一再展示作 者 “ 有 罪”、 “ 赎 罪 ”的心理活动 ,然而这六十年的辛酸、扼杀和荼毒又 如何可赎 ?赎 罪 的过程 中却又犯下新的罪孽 ,这次第怎一个 “ 罪”字 了得 ?作者一 再重 申的 “ 他人有罪 ,我亦有罪 ”的愧疚想法,正体现了小说 《 蛙》 的批判意义,下面本文 即详细阐述之 1国家之 罪: “ 生命 ”无法摆脱 “ 政治”的束控 在 小说 《 蛙 》中,作家借 女主 人公万心之 口说 “ 计划生 育政策是 毛主席 的指示 ,国家的政策 ”, “ 毛主席说,人 类应 该控 制自己,做 有计划 的增长 ”, “ 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大事,人 口不控 制,粮食 不够 吃 ,衣服不够穿 ,教育搞不好 ,人 口质量难提高,国家难 富强 ”,而 这 “ 控制 ”、 “ 有计划 ”、 “国家的大事”,即意味着作为现代性组 织形式 的现代 国家开始将 “ 生命 ”纳入到 “ 政治”的掌控 范围之 内, 使 “ 生命 ”服务于现代 国家的 “ 政治 ”目的。法 国学者米歇尔. 福柯 曾就 “ 生命 ”与 “ 政治 ”的关联进行了理论化的论述 , “ 福柯 区分 了 统 治者对死 亡的权力和 对生命 的权力 ,他 认为现代 国家 的统治者和 君主制 国家 的君王重要 区别是 :后者只拥有对死亡的权 力,即将人处 死 的权力 ,但不具备对 生命 ’的控制力;而前者则不仅拥有对死亡 的权力 ,还拥有对 生命 的权力,即通 过对出生 率和死亡率 、再生 产 比率 、人 口的繁殖等过程的控制,实现对 生 命’的掌控 。因此现 代统治者通过 ‘ 惩罚技术 ’对死亡的权力)和 ‘ 调节技术 ’ ( 对生命 的权力 )的双重掌控 ,最终实现了对从有机体 到生物学 ,从 肉体到人 口的全部 占有 。这种统治者对生命 的权力,就被福柯命名为 生命政 治 ’。” 在 小说 《 蛙》中触及的 “ 计划生育政策 ”就是 “ 生命政治” 的集中体现 ,是 “ 生命 ”无法摆脱 “ 政治”束控的悲哀 。 2群体之罪 :对 “ 生命 ”的戕害与荼毒 “ 姑姑” 曾经是 乡间新 法接生 的能手 ,曾被乡 民誉 为 “ 送 子娘 娘 ”、 “ 观音菩萨 ”,然而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起来 以后 ,姑姑更 多的 工作不再是接生 ,而是杀生,她与她志同道 合的 “ 战友们 ”一起像打 鬼子抗战一样 ,以铁腕手段强行把超计划怀 孕的女人弄到手术 台上 , 不计后果地实施人工流产或引产,曾多次导致妇婴惨死 “ 一尸两命 ” 的悲剧 。这期间姑姑既是冰冷的国家意志的贯彻 者,也是 老百姓 眼中 的 “ 活阎王 ”。叙述人蝌蚪、小狮 子及其他 计划 生育工作执行者则是 姑姑的 “ 帮凶 ”。蝌蚪为了 自己的政 治前途 ,与姑姑一起千方百计做 妻子王仁美的思想工作,终于把她 推上了引产手术 台,导致王仁美死 亡 。而在姑姑晚年 “ 生命政治 ”形态 已经 发生了变化 , “ 计划生育 ” 这一国策在社会上表现得非常复杂,竟然 出现 了 “ 有钱 的罚着生 ”、 “ 没钱 的偷着 生”、 “ 当官的让 二奶 生 ”的混 乱现象 ,非法的 “ 代孕 中心 ”也应时而出,这时候的 “ 姑姑 ”虽然反思过往时认为 自 己手上沾满了鲜血,是个有罪之人,但在 处理陈眉代孕 的孩子时 ,则 又一次犯下了荼毒生命的罪孽一一她 明知道 小狮子并未怀孕 ,还假意 为她孕检、接 生;她伙同蝌 蚪、小狮子 、高梦九等人一起抢夺 了陈眉 生下的孩子;她 明知道小狮 子并未生 育,还 自欺欺人地询 问她奶水分 泌是否旺盛。姑姑与蝌蚪都 指望着通过生 下这个计划外 的孩子可 以赎 以往迫使王仁 美等人惨 死的罪行,但这 只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 自私 想法而 已,陈眉处处喊冤苦苦寻子的呼唤 ,昭示着他们的深重罪恶。 如此之罪孽 岂可逃脱上天 的惩罚 ?于是作家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主
论生命权宪法保障

论生命权宪法保障近年来,我国侵害生命的重特大事故和事件不断发生,正在催生这样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民共识: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越大的灾难需要有越深刻的反省,越应该让我们懂得生命的宝贵和尊严。
从这些表述当中,一项至高无上而又长期未在国内得到应有关注的权利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生命权。
一、什么是生命权生命权就是指人对自己生命所享有的权利,活的权利。
生命权的主体客体均为人自身,具有高度同一性。
生命权的内容应包括生命存在权、生命安全权和生命自主权。
生命存在权即保持人的生命按照自然规律延续的权利,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
生命安全权指人有权生活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其生命不受各种危险的威胁。
生命自主权指为免除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患有不治之症的垂危病人有权选择安乐死。
二、生命权宪法保障的理论基础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它们的最高法律即宪法中以各种方式规定了生命权,通过宪法保障生命权。
联合国也在其各种权利公约中一再强调保障人的生命权。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先后有85个国家通过制定新宪法或修改宪法规定了生命权。
宪法保障生命权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潮流。
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后,有的学者主张从人权一词推导出生命权,更有学者建议在宪法上明确规定生命权。
为什么生命权需要宪法的保障?生命权的宪法保障以宪法学的相关理论为其理论基础。
(一)公权利论世界各国民法(例如我国《民法通则》)一般都规定了生命权,为什么我们仍需要宪法来保障生命权?这主要是因为规定在宪法上的生命权与规定在民法上的生命权的性质不同,宪法生命权与民法生命权的功能也不同。
公法与私法在法学界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一直被视为对法的一种基本分类。
相应地,又通常把权利分为公权与私权,或公权利与私权利。
公权利是指私人主体在公法上的权利,私权利是指私人主体在私法上的权利。
二者的功能也不同,公权利反映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对抗国家的;而私权利反映的是市民与市民之间的关系,是用来对抗其他私法上的主体的。
文化研究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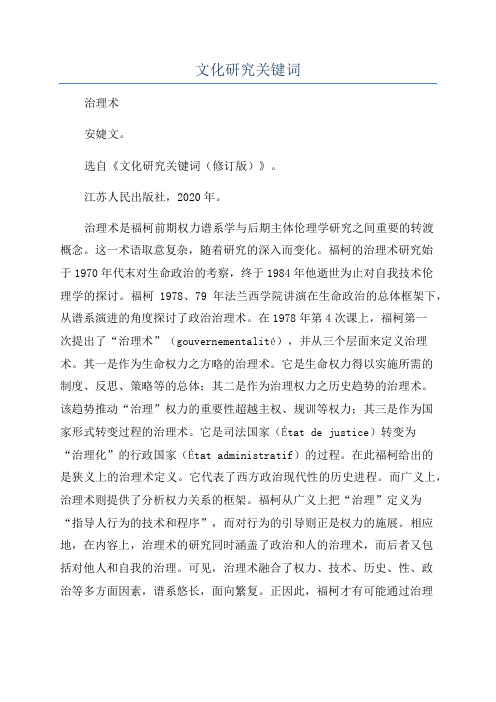
文化研究关键词治理术安婕文。
选自《文化研究关键词(修订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
治理术是福柯前期权力谱系学与后期主体伦理学研究之间重要的转渡概念。
这一术语取意复杂,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变化。
福柯的治理术研究始于1970年代末对生命政治的考察,终于1984年他逝世为止对自我技术伦理学的探讨。
福柯1978、79年法兰西学院讲演在生命政治的总体框架下,从谱系演进的角度探讨了政治治理术。
在1978年第4次课上,福柯第一次提出了“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并从三个层面来定义治理术。
其一是作为生命权力之方略的治理术。
它是生命权力得以实施所需的制度、反思、策略等的总体;其二是作为治理权力之历史趋势的治理术。
该趋势推动“治理”权力的重要性超越主权、规训等权力;其三是作为国家形式转变过程的治理术。
它是司法国家(État de justice)转变为“治理化”的行政国家(État administratif)的过程。
在此福柯给出的是狭义上的治理术定义。
它代表了西方政治现代性的历史进程。
而广义上,治理术则提供了分析权力关系的框架。
福柯从广义上把“治理”定义为“指导人行为的技术和程序”,而对行为的引导则正是权力的施展。
相应地,在内容上,治理术的研究同时涵盖了政治和人的治理术,而后者又包括对他人和自我的治理。
可见,治理术融合了权力、技术、历史、性、政治等多方面因素,谱系悠长,面向繁复。
正因此,福柯才有可能通过治理术的研究,将控制技术与自我治理的主体化实践结合起来。
福柯最终将治理术定义为统治他人的技术与自我技术的结合。
狭义上的治理术代表了政治现代性的历史进程。
在谱系学意义上,政治治理术是一种“历史元叙事”,从国家理性开始赋形,经由古典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最终发展而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形式。
福柯将治理术的源起追溯至希伯来牧领权力(pouvoir pastoral)。
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_张翔

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张 翔*内容提要:在德国的宪法理论中,基本权利被认为具有/主观权利0与/客观法0的双重性质。
除了作为个人权利的性质外,基本权利被认为是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客观价值秩序0,是对国家权力产生直接约束力的法律。
这一理论构成了对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德国建构了一套严密的基本权利保障体系。
这一理论对中国宪法的基本权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本权利 主观权利 客观法 客观价值秩序在当代德国宪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基本权利被认为具有/主观权利0和/客观法0的双重性质。
在/个人得向国家主张0的意义上,基本权利是一种/主观权利0。
同时,基本权利又被认为是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客观价值秩序0,公权力必须自觉遵守这一价值秩序,尽一切可能去创造和维持有利于基本权利实现的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基本权利又是直接约束公权力的/客观规范0或者/客观法0。
112在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之下,德国的宪法理论与实践构筑了一个精致严密而井然有序的基本权利保障体系,使得国家权力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在以人格尊严为核心的基本权利基础上得以整合。
双重性质理论构成了德国对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的基本框架,对于我国正在建构中的基本权利理论体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笔者在本文中尝试大致梳理这一理论的基本脉络,并初步探讨其对于解决中国基本权利问题的启发。
一、基本权利双重性质理论的起源(一)语词起源/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0实际上起源于德文中/Recht 0一词的多义性。
作为名词的Recht 在德文中有两个基本含义:一为/法0,二为/权利0,122为了保证法律概念的规范与严格,德国人在使用Recht 一词时往往在其前加上/客观的0或/主观的0修饰,以明所指。
subjektives Recht(主观权利)就*112122参见5新德汉词典6,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932页以下。
Robert Alexy:5作为主观权利与客观规范之基本权6,程明修译,5宪政时代6第24卷第4期。
论福柯的身体政治思想_伍小涛

第33卷第4期学报(社会科学版)Vol.33No.4 2015年7月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Jul.2015论福柯的身体政治思想伍小涛(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贵州贵阳550028)摘要:福柯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身体政治思想家。
他的身体政治思想包罗万象,对日常生活的疯癫、疾病、性的历史建构,对身体规训、身体统辖、身体治理的政治论述,对权力和话语的身体铭刻,无不显示福柯身体政治思想的深度和幅度。
而其思想的基石,是当时最为盛行的新自由主义。
关键词:福柯;身体政治;新自由主义中图分类号:B5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15)04-0019-08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5.04.04A Study of Foucault’s Political Thoughts on Human BodyWU Xiao-tao(Department of Sociology,Party School of Guizhou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Guiyang,Guizhou,550028,China)Abstract:Foucault is one of the greatest political thinkers on human body in the world.His body political thought covers and contains everything,such as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madness,disease,and sexuality in dai-ly life;political discourse on physical discipline,body control and treatment;and discourse of power and physi-cal inscription.All these have demonstrated the depth and broadness of Foucault’s political thought on human body.The cornerstone of his ideology is the most prevalent one-new liberalism.Key words:Foucault;political ideology of body;new liberalism正如福柯自己所写道:他的作品构筑了一部“身体史”,一部关于身体当中最具有物质性和生命力的东西如何被贯注的历史[1]72。
2021年《安全生产法》详细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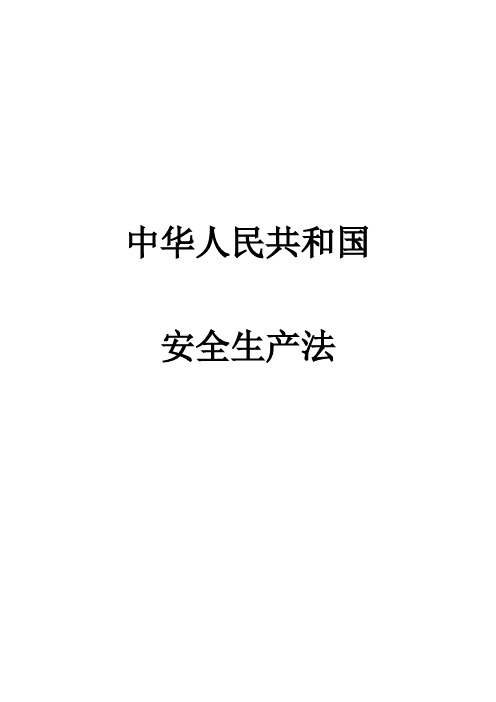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目录第一章总则 (1)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 (6)第三章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 (18)第四章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21)第五章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27)第六章法律责任 (32)第七章附则 (46)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条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与政府监管责任,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机制。
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本行业、领域的特点,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履行本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安全生产义务。
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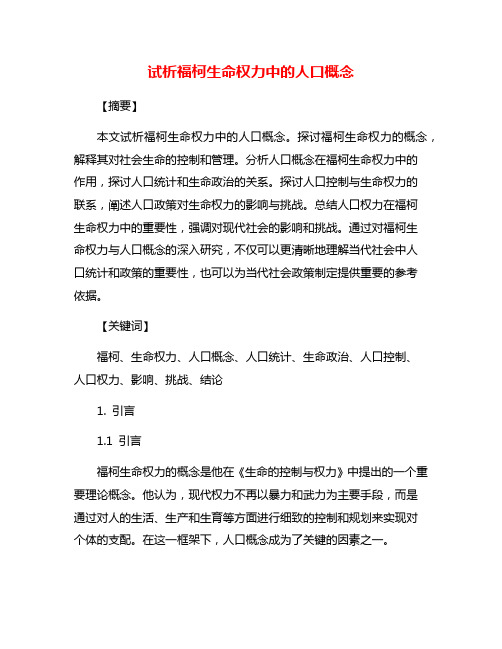
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摘要】本文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探讨福柯生命权力的概念,解释其对社会生命的控制和管理。
分析人口概念在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作用,探讨人口统计和生命政治的关系。
探讨人口控制与生命权力的联系,阐述人口政策对生命权力的影响与挑战。
总结人口权力在福柯生命权力中的重要性,强调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挑战。
通过对福柯生命权力与人口概念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当代社会中人口统计和政策的重要性,也可以为当代社会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福柯、生命权力、人口概念、人口统计、生命政治、人口控制、人口权力、影响、挑战、结论1. 引言1.1 引言福柯生命权力的概念是他在《生命的控制与权力》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
他认为,现代权力不再以暴力和武力为主要手段,而是通过对人的生活、生产和生育等方面进行细致的控制和规划来实现对个体的支配。
在这一框架下,人口概念成为了关键的因素之一。
人口概念在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作用是指,人口数量、结构和分布等因素成为了生命权力运作的基本对象。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的控制和管理不再仅限于对个体或群体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对人口的统计、分类和管理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
人口控制与生命权力的联系则是指,通过种种手段和措施对人口进行控制和规划,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调控。
这种控制不仅限于对人口数量的管理,还包括对人口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和规范。
人口权力的影响与挑战是指,尽管人口管理和生命政治可以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秩序和稳定,但也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
个体权利的受限、社会不公平和不平等等。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解决。
2. 正文2.1 福柯生命权力的概念福柯生命权力的概念主要涉及到对人的生存、生活和生殖的控制与管理。
福柯认为,权力并非只是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而是贯穿于社会各个方面,包括个体的生命和身体。
他强调社会机制通过生命的统计、分析和管理来实现权力的控制和影响。
宪法与生命权利保护人民生命尊严与健康

宪法与生命权利保护人民生命尊严与健康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人民的生命权利的保护。
而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旨在确保人权的实现与保障。
本文将探讨宪法与生命权利的关系,以及宪法如何保护人民的生命尊严与健康。
1.生命权利在宪法中的地位与意义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赋予了人民基本的权利与自由。
其中,生命权利作为人权的核心,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宪法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有生存和自由发展的权利。
这意味着国家应该保护人民的生命,确保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
2.生命尊严的保护宪法保护人民生命尊严的核心理念是尊重和保护人的人格尊严。
宪法规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
这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国家都有责任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
无论是对人身安全的侵害,还是社会或经济条件的不利影响,国家均应采取措施予以保护。
此外,宪法还规定,人民有享受健康与环境的权利,国家应当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提供医疗和环境保护等服务。
3.健康权利的保护宪法保护人民健康权利的核心是确保人民享有医疗保健的权利。
国家应当制定政策和法律,保护人民的健康权益。
同时,国家应当加强医疗卫生体制建设,提高人民的医疗服务水平。
宪法还强调了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重要性,国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公共卫生工作,提供必要的预防和健康服务。
4.宪法的保护机制与现实挑战宪法的保护是通过法律和司法机构来实现的。
法律明确规定了对侵害生命权利的行为进行惩治,并为受害人提供救济措施。
而法院则负有保护人民生命权益的法律责任。
然而,在实践中,宪法保护生命权利面临一些挑战。
例如,缺乏足够的法律保护力度、执行不力、知识普及不足等问题,都可能导致生命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护。
综上所述,宪法在保护人民的生命尊严与健康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宪法赋予了人民生命权利的保护,确保人民的生存和健康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
然而,为了更好地实现宪法的保护,需要进一步加强法律保护力度、加强知识普及、完善法律执行机制等。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浅谈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人权和主权的关系问题日益突出。
各国学者对于人权究竟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还是冲破国家界限的全球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本文从人权与主权的概念和性质,以及二者关系的发展阶段入手,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最低限度人权高于主权的合理性。
【关键词】:人权主权人权普遍性最低限度人权【正文】:一、人权和主权的概念和历史进程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也就是公民个体基于自己的需求对国家进行请求的权利。
是人类社会最高形式和最具普遍性的权利。
其产生的基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改变了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国家和个人之间发生了各种法律联系,这种联系的核心是人权。
广义的人权在国家和法律出现之前就有了。
但以自由、平等、人道为其重要内容与特征的狭义的人权,是近代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出现后才有的。
人权源于人的本性。
这种本性包括两个方面,即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的自然属性。
所谓社会属性是指,人是生活在各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
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①所谓人的自然属性,即人性。
它包括三个基本的要素。
首先,人性是指人的天性。
人的生命不受肆意剥夺,人的人身安全不受伤害,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的思想自由不受禁锢,人的最低生活得到保障,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都是人的天性和本能。
其次,人性是指人的德性。
人是一种有伦理道德追求的高级动物,这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根本点。
再次,人性是指人的理性。
人通过理性,可以认识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规律,并据以改造世界。
同时,人还可以通过理智,克制自己不去做那些不合情不合理的事情。
主权的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是由法国学者博丹首先提出,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至上的权力。
之后,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将国家主权观念延续至国际社会,重点从国际法角度突出了主权的对外性质。
生命权力能否切中现实生命生命政治的文明面及其当代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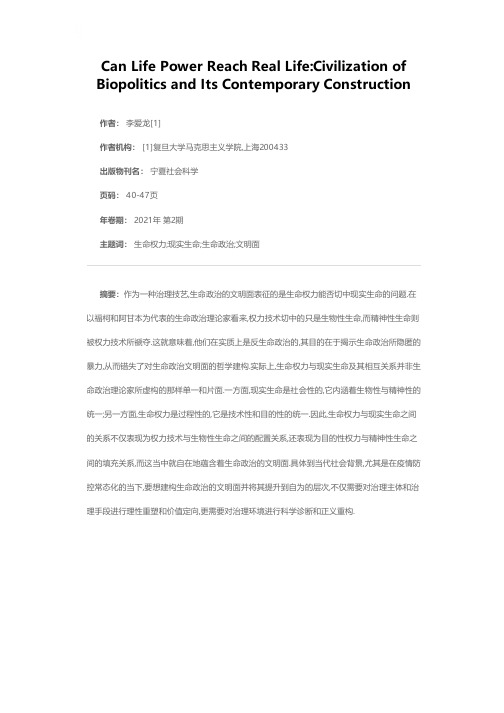
Can Life Power Reach Real Life:Civilization of Biopolitics and Its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作者: 李爱龙[1]
作者机构: [1]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出版物刊名: 宁夏社会科学
页码: 40-47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2期
主题词: 生命权力;现实生命;生命政治;文明面
摘要:作为一种治理技艺,生命政治的文明面表征的是生命权力能否切中现实生命的问题.在以福柯和阿甘本为代表的生命政治理论家看来,权力技术切中的只是生物性生命,而精神性生命则被权力技术所褫夺.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实质上是反生命政治的,其目的在于揭示生命政治所隐匿的暴力,从而错失了对生命政治文明面的哲学建构.实际上,生命权力与现实生命及其相互关系并非生命政治理论家所虚构的那样单一和片面.一方面,现实生命是社会性的,它内涵着生物性与精神性的统一;另一方面,生命权力是过程性的,它是技术性和目的性的统一.因此,生命权力与现实生命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为权力技术与生物性生命之间的配置关系,还表现为目的性权力与精神性生命之间的填充关系,而这当中就自在地蕴含着生命政治的文明面.具体到当代社会背景,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要想建构生命政治的文明面并将其提升到自为的层次,不仅需要对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进行理性重塑和价值定向,更需要对治理环境进行科学诊断和正义重构.。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生命权力的双重治理:对人主体生命的隐性统治作者:程远航来源:《学理论·下》2020年第08期摘要:在传统君王绝对统治权力之后,福柯提出的生命权力模式展开了两极运行机制:规训权力对人肉体惩戒规范的微观治理以及生命权力从整体人口调节的宏观治理。
由此形成的生命权力运行机制与传统君王的外部统治从个体和整体两方面的规范治理进入人自身内部,表面是对人主体价值更好实现的防范调整,然而是一种隐藏在牧领式关心下的隐形统治,双重治理机制使得生命权力统治人的主体性深入到生活各处,从而使人毫无意识地丧失生命的主体性而无能为力。
这种缺失人主体性的生命权力政治,需要在人的生存价值和“类本性”的寻求中得到恢复和重塑自我。
关键词:规训权力;生命权力;主体生命;隐性统治中图分类号:B0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8-0058-03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确立的“生命政治”揭示了在18世纪下半叶现代社会存在的一个现实:尽管以追求自由、财富、安全等名义,所有人的生命生活都与权力秩序紧密联系起来。
福柯认为18世纪前的社会是以君主国家主导统治权力。
这种统治权力主要是借助法律和惩罚保护公民权利主体,以一种否定性的掌握绝对“生杀大权”将生命与权力联系起来,呈现出“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力形式。
这种统治权力虽然与生命有所联系,但完全遵从君主的权力统治地位趋向于强迫压制性的消亡生命的手段。
所以说这算不上确切的生命政治权力。
随着君主社会到民主社会的转变,封建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过渡,“我们可以说‘让’人死或‘让’人活的古老权力已经被‘让’人活或‘不让’人死的权力取代了。
”[1]116自杀不再是篡夺君主权力的犯罪,而是个人在控制自己生命权力的私人死亡权力的展现。
这种转变源于现代社会政治权力不再以君主统治为主导,而是以管理生命为主导。
由此福柯的“生命政治”延伸出肉体惩戒微观治理的规训权力以及人口调节宏观治理的生命权力两极。
福柯将传统君主统治权力作为前社会存在的前提,从规训权力开始探究生命与权力的关系,最后落脚在生命权力中,这三种权力模式完整地构成了权力技术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生命政治概念。
这三种权力模式不是在时间顺序上绝对地替代过程,而三种模式共存在社会进程中,只不过现代社会从关注国家权力转变到关注治理技艺。
在生命政治中对个体行为的规训和从总体调节人口生命活动的权力技术都使得生命被纳入知识和权力的控制网中,成为权力密切关注的对象。
生命政治在福柯那里主要被看作一种现代形态的治理技艺在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两极运行机制中实现了对人主体权力的布控。
一、生命权力的两极运行机制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力对人的社会身体进行一种积极的引导教化从而维持社会个体生命良好的活动秩序的权力统治。
这种权力统治形式,一方面包含治理国家政治活动的传统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包括治理个体自身活动与社会整体关系间的身体政治问题。
生命权力的治理技术是一种追求普遍的善的牧领权力。
就像牧领权力不仅要照顾羊群的整体,还要关注到每一个个体的情况,其中个体与整体的关注是同等重要的。
就像这种持续监视和看守的牧领权力一样,生命权力保留牧领权力的看管服从的核心要素。
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是一种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对生命权力的运用的新的权力技术,主要形成个体的微观规训权力和整体的宏观人口调节的生命权力两种权力形式。
与个体密切相关的规训权力是为使人肉体的某些能力得到提高进行的以肉体为核心的一些训练活动,同时通过这些活动教化人达到规训的目的。
规训权力不再像传统统治权力那样具有君主绝对的权力中心,也不会突出体现法律对活动规范的强制作用。
规训权力不针对法律主体和权利主体,而是对具有劳动能力的肉体的人借助纪律和教导规范进行规训。
“为了重新控制细节,开始了最初的适应:权力机制对个体的适应,通过监视和训练——这就是惩戒”,是规训权力最初容易实现的一部分[2]273。
这种规训权力在学校、工厂、医院、军队以及监狱等社会机构中得到突出显现,其中对人通过监视、锻炼、训练等教化活动,制定标准规范奖罚体系促进个人进行有利于团体构建的积极活动。
这与“使人死”的传统统治权力有根本区别,是一种“讓人活”的生命延续,规训的目的是让肉体很有力量。
因此,规训权力通过惩戒肉体实现的是一种个人化的解剖政治学。
与此相对的整体的大众化的生命权力形式是一种生命政治学,以人口和生命为中心关注到作为物种繁殖基础意义上的人口的质量问题。
生命权力也同样没有传统统治权力的绝对中心,权力的行使由国家机构人员、生活学家、公共卫生学家等专业领域人士承担。
福柯引入“人口”一词来说明生命权力也不再关注个体人的肉体活动,而是关心整体的人口的生命质量。
这里的人口不是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个体,也不是具有主体权利的社会集合体,而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具有人种概念的生物性群体。
所以生命权力不关注个体活动,而是把个体都放置在人种的群体中从概率统计的角度探究整体的出生率、死亡率、整体健康水平以及寿命等生命质量问题。
借助信息技术进行安全调控,从而实现人口总体平衡和整体安全的目的。
福柯认为“生命政治学干预的是一些人是普遍的而另一部分人是偶然的整个整体现象,”[2]267与规训权力的纪律规范不同,是一种通过概率风险预估的调节机制,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
福柯认为作为个人肉体的规训权力和人口安全调控的生命权力形成了生命权力展开的两极运行机制,也构成了两个系列“肉体系列—人体—惩戒—机关;和人口系列—生活学过程—调节机制—国家。
”[2]273虽然这两种机制分别从个人细节的控制和总体大众的调节的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在不同层面展开权力形式,但二者也不会相互排斥而是可以通过某个中介连接起来,共同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由民主社会”的诉求。
规训权力从微观个人角度控制教化人的活动,生命权力从整体的人口调节人种的宏观问题,这样就不难发现福柯引入生命政治的两个运行机制是在通过一种权力逻辑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机制,但在生命权力的统治下其实质仍然是对人主体的一种双重统治。
二、双重治理对人主体生命的隐性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权力的政治统治与传统君主的绝对统治有很大不同,君主的统治权力具有至上性不容置疑,其权力行使以一种否定性禁止人做什么活动;而生命政治权力的两极权力形式是以一种积极的肯定方式教化人们能够做什么活动。
福柯引入生命政治的两极运行机制绝不是赞颂资本主义社会在生命权力的统治下实现了人的自由和平等,构建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而是通过剖析生命权力形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对人的双重治理。
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这两种权力形式到19世纪结合在一起,形成既是解剖学又是生物学;既是个体化又是整体化的,既是微观的又是宏观的生命权力,从而使得资产阶级的生命政治权力“承担了整体生命的责任,包括肉体的一极和人口的一极”[2]277,完全占有统治人类生命本身。
当这种生命权力得到滋生的可能性就会以不可思议的扩张形式,在技术和政治上“安排生命,使生命繁殖,制造生命,制造魔鬼,制造无法控制和具有毁灭性的病毒”[2]277,以一种隐形的方式逐渐达到对人主体性生命的完全控制。
生命权力的双重治理对人主体生命的隐形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以“生”的形式和种族主义中以“死”的形式得到实现。
首先,在福利国家中规训权力对人主体生命活动的统治得到突出的体现。
福利国家承担起管理人民健康的责任,需要通过设置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引导人们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环境的构建。
福利国家可以理解是通过国家的福利政策引导对国民的肉体进行规范矫正从而将其整合进有效的社会控制系统中提高国家的实力。
“在20世纪开始时,在欧洲和北美的民族国家及其许多殖民地,两大由政府资助的生命政治策略逐渐形成”[3]69,像卫生方面的城镇规划、污水管道系统以及一些卫生防疫讲习班等活动,通过外部的硬件条件以及内部国民主体习惯的教化,以健康为中介将有关适于社会的健康卫生道德观念灌输给每个个体。
福利国家中的卫生统治是借助国民普遍关心健康卫生问题,通过设立巡讲机构以及基础设施实现国家对个人卫生的监管,这是从微观方面对人的生命活动进行规范和教化实现对生命的管制。
在福利国家中蕴含一种以“让人活”为目的运行的规训权力机制。
另外,在生命权力中也保留的“让人死”的一部分,这部分是通过种族主义实现的生命权力统治。
福柯认为,“在规范化社会中,种族,种族主义,这是接受把人处死的条件。
在国家按照生命权力的模式运转之后,国家杀人的职能就只能由种族主义来保证。
”[2]281种族主义挂上一种进化论思维使战争和民族歧视冠以科学的合理性,使得在种族主义下按照生命权力的模式运转可以光明正大地排斥其他民族。
“种族主义与国家的职能相联系,后者被迫利用种族、种族的清洗和种族的纯洁来行使它的统治权。
”[2]282种族主义体现为主流种族对其他种族的排斥以及国外与其他种族的战争,这在本质上形成了对生命的强制压迫,构成了对他人生命的侵犯。
福柯认为,纳粹是新权力机制发展的顶端。
在纳粹主义中杀人的权力被放大逐渐丧失了控制,使得杀人的权力不仅限制在国家中还蔓延给予到一系列相关人中。
福柯认为,以纳粹为代表的种族主义不是20世纪的特有现象,而是西方社会进入现代之后出现的“生命的国家化”趋向的内在延伸。
这也从宏观人种的角度实现生命权力对人主体生命的控制。
由此看来,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整这两种生命权力机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实现从头到尾地对生命的控制。
通过对这两个权力机制的分析,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表面是追求自由平等,但实质仍是对人的操控并且通过生命权力控制人的生命,使其权力控制更为彻底。
生命权力通过微观的肉体规训和宏观的人口调整,使得生命权力统治深入到生活各处,对人的主体性生命进行全面的隐性统治。
福柯通过权力逻辑的分析,引出的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宏观统治深入个体生活的微观统治的事实。
福柯希望关注到生命政治下被生命权力彻底征服而失去主体性生命的人,希望能够在人的生存美学中重新找到人的主体地位。
三、人在类存在的本性中恢复主体自我福柯通过分析生命权力的微观肉体的规训权力和宏观人口调节的生命权力这兩种机制揭示了在生命政治下权力统治的无处不在,以一种“非生命”的形式对人的主体生命进行隐性统治,表达了福柯在生命权力统治下对人主体生命存在的悲观理解。
福柯对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两种权力统治形式的分析确实很透彻,深刻揭示出现代社会生命政治权力统治下存在的主体性缺失问题。
但面对这种事实,我们要如何应对?如何重新建构具有主体性的生命存在,在生命权力面前如何处理人与权力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福柯相对比较消极,在他对生命政治的分析下常常会形成生命权力的彻底统治而人无法反抗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