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复仇
鲁迅《复仇》读后感(范文大全)

鲁迅《复仇》读后感(范文大全)第一篇:鲁迅《复仇》读后感鲁迅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终生都在追求理想的完美、人格的完美、道德的完美。
他论敌的议论,总是锋芒毕露,直入对手骨髓。
在《复仇》、《复仇(其二)》两篇散文诗中,鲁迅复仇的矛头却直指百姓——那些他一心想唤醒、想拯救的人。
鲁迅的这种“复仇”精神,是对愚昧百姓“怒其不争”。
面相觑,慢慢走散”,这时,干枯而立于旷野的男女则反过来赏鉴路人的干枯与死亡,而且因为生命的飞扬而大喜。
《复仇(其二)》这首散文诗所写的故事情节和细节,均取材于《新约全书?马可福音》,但鲁迅竭力把神之子手足被钉的痛楚,同玩味着神之子被钉杀的可悲悯可诅咒的人们的欢喜,作了鲜明而强烈的对照,这就使宗教神话故事获得了新的意蕴。
在散文诗的主体部分,一共八次出现了“神之子”的字样,反复渲染耶酥是“神之子”,到散文诗的结尾,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说出了他是“人之子”。
人们钉杀的是“人之子”,而“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这是文章真正的意蕴所在。
《复仇》表现了他对庸众的几乎没有复仇的复仇,是鲁迅式的黑色幽默,《复仇(其二)》则借用宗教神话故事,表现先觉者在被他希望拯救的庸众迫害的大痛楚中,以对庸众的悲悯和诅咒来作为复仇,他痛得“柔和”和“舒服”,都因为这玩味——复仇之故。
这种复仇当然更没有复仇意味,只是牺牲自己以期庸众将来的醒悟。
第二篇:《复仇》读后感对麻木者的复仇——读鲁迅《复仇》(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鲁迅写完第一篇《复仇》之后,继续写了同名的另一篇散文诗《复仇》(二)。
作品借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表现了对社会上麻木者的反抗,其意比前一篇《复仇》更深了一层。
耶稣,是救世的先觉者,他的努力就是为了解除为奴的同胞的苦难。
为救同胞苦难而被拘捕,而被送上十字架,而被钉杀。
在耶稣被钉杀的时候,耶稣一直为之奋斗的同胞们不但不给予丝毫的理解和同情,相反,却对耶稣百般的戏弄、辱骂、讥诮,鉴赏耶稣的痛苦。
鲁迅复仇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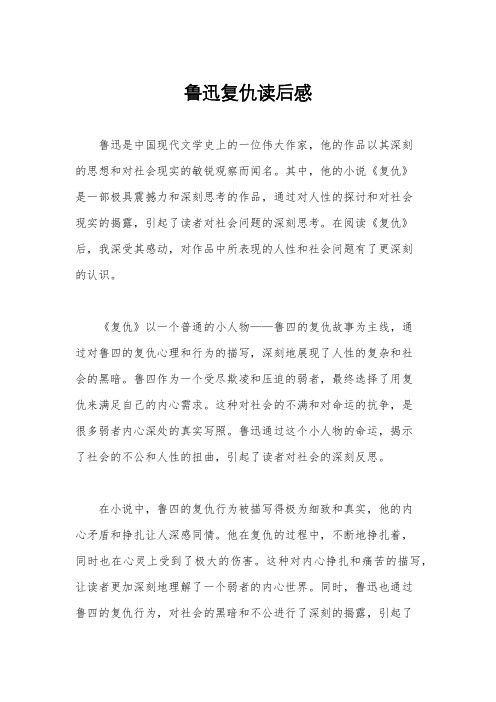
鲁迅复仇读后感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作家,他的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和对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而闻名。
其中,他的小说《复仇》是一部极具震撼力和深刻思考的作品,通过对人性的探讨和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引起了读者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
在阅读《复仇》后,我深受其感动,对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性和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复仇》以一个普通的小人物——鲁四的复仇故事为主线,通过对鲁四的复仇心理和行为的描写,深刻地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黑暗。
鲁四作为一个受尽欺凌和压迫的弱者,最终选择了用复仇来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
这种对社会的不满和对命运的抗争,是很多弱者内心深处的真实写照。
鲁迅通过这个小人物的命运,揭示了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扭曲,引起了读者对社会的深刻反思。
在小说中,鲁四的复仇行为被描写得极为细致和真实,他的内心矛盾和挣扎让人深感同情。
他在复仇的过程中,不断地挣扎着,同时也在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这种对内心挣扎和痛苦的描写,让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一个弱者的内心世界。
同时,鲁迅也通过鲁四的复仇行为,对社会的黑暗和不公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引起了读者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
除了对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深刻揭露,鲁迅在《复仇》中还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细节的描写,展现了其高超的文学功底。
鲁四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成功,他的内心世界和复仇行为都被描写得非常细致和真实。
同时,鲁迅对社会现实的描写也非常细腻,通过对细节的描写,展现了社会的种种不公和黑暗。
这种对人物形象和社会现实的描写,使整个作品更加生动和有力,引起了读者对作品的深刻思考。
总的来说,《复仇》是一部极具震撼力和深刻思考的作品,通过对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引起了读者对社会的深刻反思。
鲁迅通过对鲁四的复仇故事的描写,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黑暗,引起了读者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
同时,鲁迅在作品中对人物形象和社会现实的描写也非常成功,使整个作品更加生动和有力。
《复仇》无疑是一部值得反复品味的作品,它对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深刻揭露,将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引发读者对社会的深刻思考。
鲁迅复仇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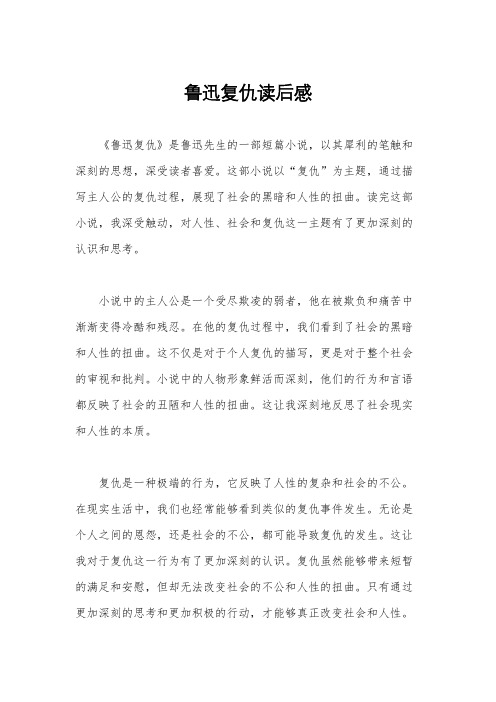
鲁迅复仇读后感《鲁迅复仇》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短篇小说,以其犀利的笔触和深刻的思想,深受读者喜爱。
这部小说以“复仇”为主题,通过描写主人公的复仇过程,展现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
读完这部小说,我深受触动,对人性、社会和复仇这一主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
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受尽欺凌的弱者,他在被欺负和痛苦中渐渐变得冷酷和残忍。
在他的复仇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
这不仅是对于个人复仇的描写,更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审视和批判。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活而深刻,他们的行为和言语都反映了社会的丑陋和人性的扭曲。
这让我深刻地反思了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本质。
复仇是一种极端的行为,它反映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不公。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类似的复仇事件发生。
无论是个人之间的恩怨,还是社会的不公,都可能导致复仇的发生。
这让我对于复仇这一行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复仇虽然能够带来短暂的满足和安慰,但却无法改变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扭曲。
只有通过更加深刻的思考和更加积极的行动,才能够真正改变社会和人性。
在读完《鲁迅复仇》之后,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和文学成就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他以犀利的笔触和深刻的思想,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让人深受触动。
他的作品不仅是文学的经典,更是对于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深刻思考。
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和人性,从而更好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
总之,读完《鲁迅复仇》之后,我对于复仇、社会和人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
这部小说不仅是文学的经典,更是对于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深刻思考。
通过阅读这部小说,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和人性,从而更好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阅读这部小说,从中汲取力量,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鲁迅复仇》课件

鲁迅的作品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揭示和抨击,挑战当时的社会观念和体制。
四、鲁迅复仇的方式
文学创作和思想倡导
鲁迅通过他的大量文学作品和思 想倡导,表达对社会的复仇。
作品选介和实例解读
介绍鲁迅的经典作品,《狂人日 记》等,解读其中的复仇意义。
鲁迅的创作风格和理论追求
探讨鲁迅的写作风格和他对文学 和社会的理论追求。
四五运动和文化运动是鲁迅创作的背景和时代背景,对其复仇意义产生影响。
鲁迅的政治立场和主张
鲁迅积极参与政治,呼吁民主革命,致力于改革现代社会。
三、鲁迅的复仇意义
不同于报复,鲁迅的复仇意味着
鲁迅通过文学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批判,追求正义和改革。
鲁迅在痛苦中自我超越和净化
鲁迅通过作品反思自己的人生和生活,实现心灵的自我净化和超越。
五、鲁迅复仇的意义和启示
鲁迅的影响和地位
鲁迅的作品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史,对后代作家和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鲁迅的复仇对当代文化和精神的启示
探讨鲁迅的复仇精神对当代文化和精神的启示,尤其在当前社会背景下。
如何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精神
提出如何继承和发扬鲁迅的复仇精神,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六、结论
鲁迅的复仇对当代人的意义和价值
《鲁迅复仇》PPT课件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其作品被广泛传播和研究。 本次演讲旨在探讨鲁迅复仇的含义与意义。
一、引言
• 鲁迅简介 • 鲁迅的创作背景和意义 • 本次演讲的主题和目的
二、背景分析
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
鲁迅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面临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阶段。
四五运动和文化运动
总结鲁迅的复仇意义,对当代人的思考和行动产生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第十讲鲁迅与复仇

三、《复仇》 三、《复仇》解读:鲁迅笔下的看客
1、 看客群像:
《狂人日记》 里“一路上的人”、《孔乙己》中的酒客 们、《祝福》里听祥林嫂讲阿毛故事的“男人”“女人” 们、《药》里开头在刑场上游动的“几个人”、“一 堆人 ”“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横肉的人”,《示 众》中“挟洋伞的长子” “十一二的胖孩子”等。
三、《复仇》 三、《复仇》解读:文本细读
如何复仇? 如何复仇?
“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 拥抱或杀戮之意”。借以摆脱被看、被围观、 被赏鉴的尴尬的也是危险的处境。 他们将这种姿态保持“至于永久” 以生命为代价——“圆活的身体,已将 干枯”。
三、《复仇》 三、《复仇》解读:文本细读
“复仇”的结果。 复仇”的结果。
鲁迅 与 《复仇》 复仇》
焦点问题:
1、鲁迅的生平经历概况及思想发展情况; 2、鲁迅创作成就及其作品中“看客”群体形象特征; 、鲁迅创作成就及其作品中“看客” 3、《复仇》对国民精神的揭示。 、《复仇》
一、生平经历概况 (1881-1936) 1881-1936)
出身: 小康坠入困顿” 出身:“小康坠入困顿” 求学: 逃异地,走异路,寻求别样的人们” 求学:“逃异地,走异路,寻求别样的人们” ———“幻灯片事件” 弃医从文 ———“幻灯片事件” 精神界战士的“摩罗诗力” 精神界战士的“摩罗诗力” 战斗的呐喊 十字路口的彷徨 思想的飞跃 鞠躬尽瘁——民族魂 鞠躬尽瘁——民族魂 ——
精巧的构思 奇崛的意象和文思 细腻而尖新的描写 复沓而有力的语句 铸成了强烈的感觉和思想的冲击力。
四、思考与讨论
1. 《复仇》中两次写到“永 复仇》 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 的大欢喜中”,其用意有何 不同? 2. 依你所见,诗中二人有此 处境,应“毫无动作”呢, 还是或相爱、或相杀,“照 所欲而行的为是”呢? 3. 联系现实生活,“看客” 是否仍然存在?
鲁迅的复仇观-文档

鲁迅的复仇观本文将讨论以下两个问题:1、将鲁迅从日本留学到厦门工作这个时期的复仇观划分成以下三个部分:1)基于民族层面的复仇观;2)遭遇挫折的改革者的复仇观;3)遭遇了背叛的献身者的复仇观,并考证它们的变化因由。
2、探寻这三种复仇观的渊源。
早期文学活动时的复仇观(1903年-1909年)提及鲁迅在这个时期的复仇观,首先要涉及到《摩罗诗力说》(1908年)一文。
鲁迅在早期的文学活动中,主要是突出介绍象拜伦、雪莱那样改革的先行者对专制的反抗和不媚俗的精神。
伴随着他们的反抗之声和行动的是,在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出现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先行者和诗人。
鲁迅期待通过介绍他们的思想能够唤醒中国人的觉醒。
在《摩罗诗力说》的基调中并不存在着复仇。
但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的第八节中提到了波兰诗人斯洛伐斯基的“报复之声”,并介绍了“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的《死人之祭》中囚徒之歌,他在这里把重点放在了复仇上。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复仇的内容。
“欲我为信徒,必见耶稣马理,先惩污吾国土之俄帝而后可。
俄帝若在,无能令我呼耶稣之名。
”“渴血渴血,复仇复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报矣;即不如是,亦报尔!”这是针对沙皇的民族压迫,表明了被压迫民族波兰人的复仇观,迸发出民族的复仇感。
“如上所言报复之事,盖皆隐藏,出于不意,其旨在凡窘于天人之民,得用诸术,拯其父国,为圣法也。
”为了将祖国从外族的压迫中拯救出来,各种形式的复仇,即便是通过欺骗和卑劣的形式,也可以被看成是神圣的法则。
只是《摩罗诗力说》并不赞许那些不问含义和目的的复仇。
“凡厥中勇士,等是见放于人群,顾复不离亚历山大时俄国社会之一质分,易于失望,速于奋兴,有厌世之风,而其志至不固。
普式庚于此,已不与以同情,诸凡切于报复而观念无所胜人之失,悉指摘不为讳饰。
”鲁迅认为,普希金彻底地揭露了当时俄罗斯社会中出现的拜伦式的英雄“诸凡切于报复而观念无所胜人之失”的先天缺陷。
换句话说,《摩罗诗力说》一文并不推崇那些不问内容的复仇,他所要颂扬的复仇是针对被压迫民族的专制以及它们的实施者,即基于民族层面的复仇。
鲁迅复仇的艺术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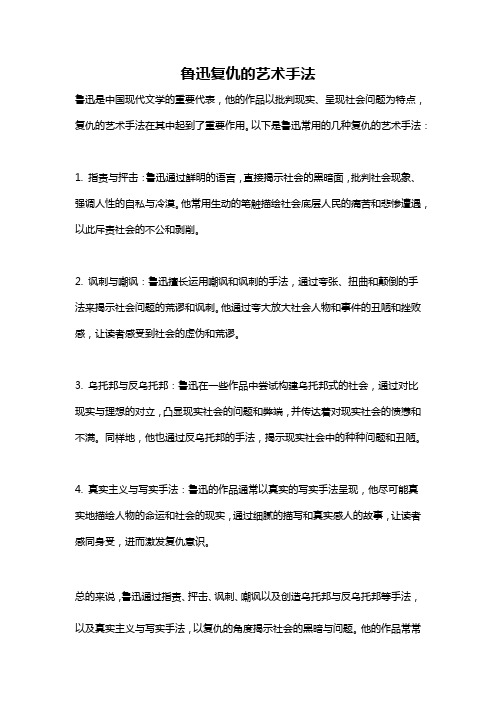
鲁迅复仇的艺术手法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以批判现实、呈现社会问题为特点,复仇的艺术手法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下是鲁迅常用的几种复仇的艺术手法:
1. 指责与抨击:鲁迅通过鲜明的语言,直接揭示社会的黑暗面,批判社会现象、强调人性的自私与冷漠。
他常用生动的笔触描绘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和悲惨遭遇,以此斥责社会的不公和剥削。
2. 讽刺与嘲讽:鲁迅擅长运用嘲讽和讽刺的手法,通过夸张、扭曲和颠倒的手法来揭示社会问题的荒谬和讽刺。
他通过夸大放大社会人物和事件的丑陋和挫败感,让读者感受到社会的虚伪和荒谬。
3.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鲁迅在一些作品中尝试构建乌托邦式的社会,通过对比现实与理想的对立,凸显现实社会的问题和弊端,并传达着对现实社会的愤懑和不满。
同样地,他也通过反乌托邦的手法,揭示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和丑陋。
4. 真实主义与写实手法:鲁迅的作品通常以真实的写实手法呈现,他尽可能真实地描绘人物的命运和社会的现实,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真实感人的故事,让读者感同身受,进而激发复仇意识。
总的来说,鲁迅通过指责、抨击、讽刺、嘲讽以及创造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等手法,以及真实主义与写实手法,以复仇的角度揭示社会的黑暗与问题。
他的作品常常
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人文关怀,对社会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控诉。
鲁迅《复仇》读后感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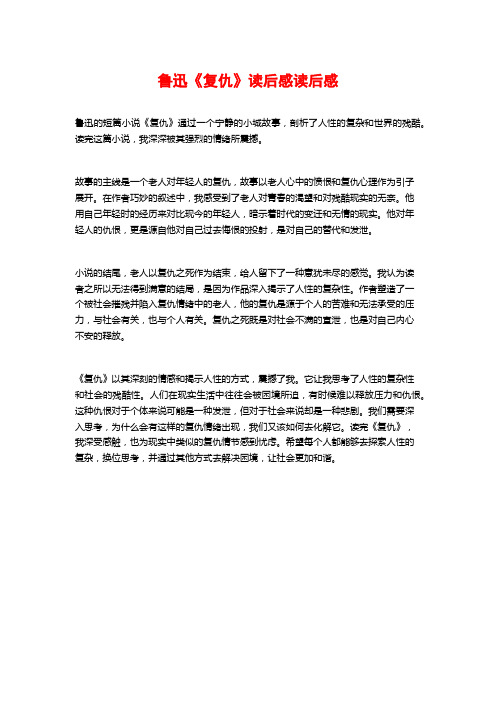
鲁迅《复仇》读后感读后感
鲁迅的短篇小说《复仇》通过一个宁静的小城故事,剖析了人性的复杂和世界的残酷。
读完这篇小说,我深深被其强烈的情绪所震撼。
故事的主线是一个老人对年轻人的复仇,故事以老人心中的愤恨和复仇心理作为引子
展开。
在作者巧妙的叙述中,我感受到了老人对青春的渴望和对残酷现实的无奈。
他
用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来对比现今的年轻人,暗示着时代的变迁和无情的现实。
他对年
轻人的仇恨,更是源自他对自己过去悔恨的投射,是对自己的替代和发泄。
小说的结尾,老人以复仇之死作为结束,给人留下了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我认为读
者之所以无法得到满意的结局,是因为作品深入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
作者塑造了一
个被社会摧残并陷入复仇情绪中的老人,他的复仇是源于个人的苦难和无法承受的压力,与社会有关,也与个人有关。
复仇之死既是对社会不满的宣泄,也是对自己内心
不安的释放。
《复仇》以其深刻的情感和揭示人性的方式,震撼了我。
它让我思考了人性的复杂性
和社会的残酷性。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被困境所迫,有时候难以释放压力和仇恨。
这种仇恨对于个体来说可能是一种发泄,但对于社会来说却是一种悲剧。
我们需要深
入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复仇情绪出现,我们又该如何去化解它。
读完《复仇》,
我深受感触,也为现实中类似的复仇情节感到忧虑。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去探索人性的
复杂,换位思考,并通过其他方式去解决困境,让社会更加和谐。
鲁迅复仇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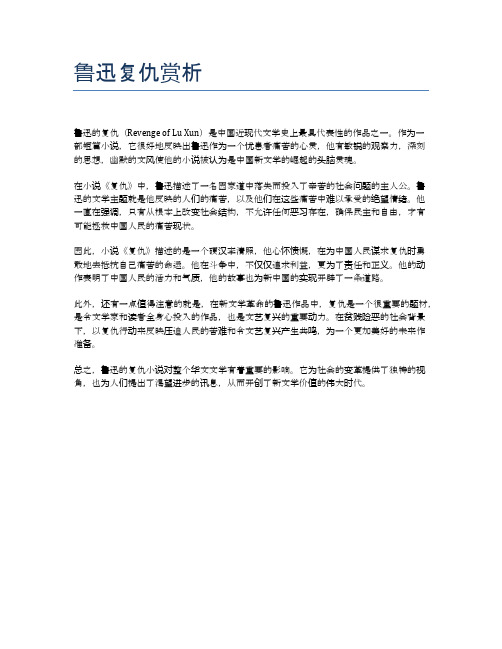
鲁迅复仇赏析
鲁迅的复仇(Revenge of Lu Xun)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作为一
部短篇小说,它很好地反映出鲁迅作为一个忧患者痛苦的心灵,他有敏锐的观察力,深刻
的思想,幽默的文风使他的小说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的崛起的头脑灵魂。
在小说《复仇》中,鲁迅描述了一名因家道中落失而投入了辛苦的社会问题的主人公。
鲁
迅的文学主题就是他反映的人们的痛苦,以及他们在这些痛苦中难以承受的绝望情绪。
他
一直在强调,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不允许任何恶习存在,确保民主和自由,才有
可能拯救中国人民的痛苦现状。
因此,小说《复仇》描述的是一个硬汉李清照,他心怀愤慨,在为中国人民谋求复仇时勇
敢地去抵抗自己痛苦的命运。
他在斗争中,不仅仅追求利益,更为了责任和正义。
他的动
作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活力和气质,他的故事也为新中国的实现开辟了一条道路。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新文学革命的鲁迅作品中,复仇是一个很重要的题材,是令文学家和读者全身心投入的作品,也是文艺复兴的重要动力。
在贫贱险恶的社会背景下,以复仇行动来反映压迫人民的苦难和令文艺复兴产生共鸣,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作
准备。
总之,鲁迅的复仇小说对整个华文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
它为社会的变革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为人们提出了渴望进步的讯息,从而开创了新文学价值的伟大时代。
孤独者从愤激到冷峻的复仇——鲁迅《复仇》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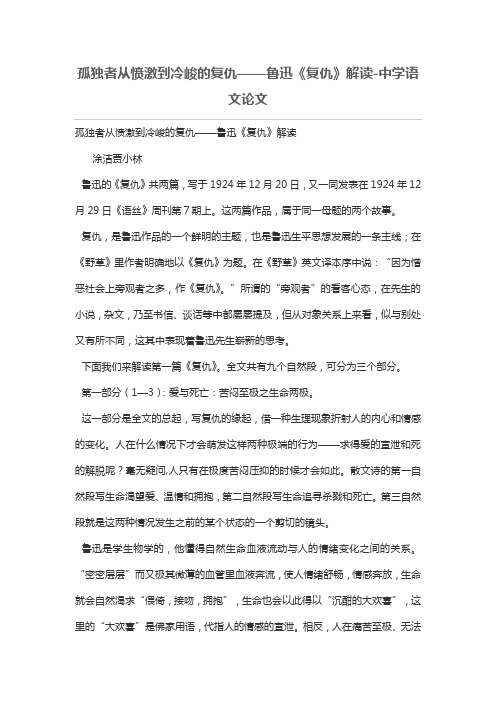
孤独者从愤激到冷峻的复仇——鲁迅《复仇》解读-中学语文论文孤独者从愤激到冷峻的复仇——鲁迅《复仇》解读涂洁贾小林鲁迅的《复仇》共两篇,写于1924年12月20日,又一同发表在1924年12月29日《语丝》周刊第7期上。
这两篇作品,属于同一母题的两个故事。
复仇,是鲁迅作品的一个鲜明的主题,也是鲁迅生平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在《野草》里作者明确地以《复仇》为题。
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
”所谓的“旁观者”的看客心态,在先生的小说,杂文,乃至书信、谈话等中都屡屡提及,但从对象关系上来看,似与别处又有所不同,这其中表现着鲁迅先生崭新的思考。
下面我们来解读第一篇《复仇》。
全文共有九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1—3):爱与死亡:苦闷至极之生命两极。
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起,写复仇的缘起,借一种生理现象折射人的内心和情感的变化。
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萌发这样两种极端的行为——求得爱的宣泄和死的解脱呢?毫无疑问,人只有在极度苦闷压抑的时候才会如此。
散文诗的第一自然段写生命渴望爱、温情和拥抱,第二自然段写生命追寻杀戮和死亡。
第三自然段就是这两种情况发生之前的某个状态的一个剪切的镜头。
鲁迅是学生物学的,他懂得自然生命血液流动与人的情绪变化之间的关系。
“密密层层”而又极其微薄的血管里血液奔流,使人情绪舒畅,情感奔放,生命就会自然渴求“偎倚,接吻,拥抱”,生命也会以此得以“沉酣的大欢喜”,这里的“大欢喜”是佛家用语,代指人的情感的宣泄。
相反,人在痛苦至极、无法发泄的时候,就会因为苦闷抑郁而血脉瘀滞喷张,急于找到一个突破口,以“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这是情绪发泄的一种极端方式;结果便以“冰冷的呼吸,淡白的嘴唇”示人,使“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
这里“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就是生命的死亡,佛家说,死亡是人的生命的终极宣泄,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谓之“永远”。
从《复仇》看鲁迅对于启蒙的态度及其抗争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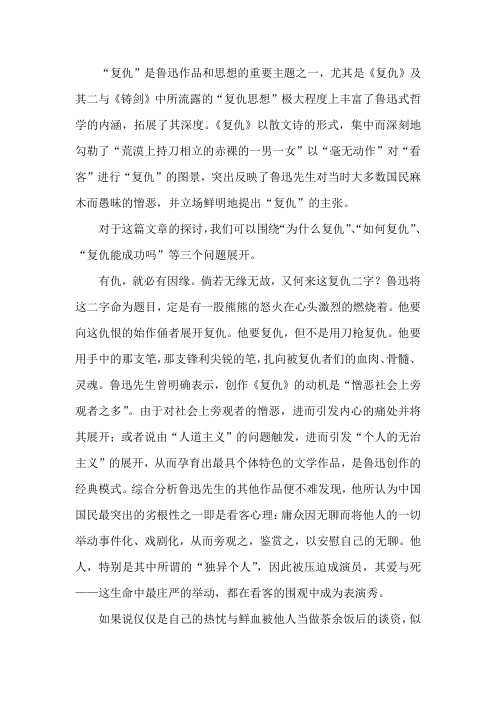
“复仇”是鲁迅作品和思想的重要主题之一,尤其是《复仇》及其二与《铸剑》中所流露的“复仇思想”极大程度上丰富了鲁迅式哲学的内涵,拓展了其深度。
《复仇》以散文诗的形式,集中而深刻地勾勒了“荒漠上持刀相立的赤裸的一男一女”以“毫无动作”对“看客”进行“复仇”的图景,突出反映了鲁迅先生对当时大多数国民麻木而愚昧的憎恶,并立场鲜明地提出“复仇”的主张。
对于这篇文章的探讨,我们可以围绕“为什么复仇”、“如何复仇”、“复仇能成功吗”等三个问题展开。
有仇,就必有因缘。
倘若无缘无故,又何来这复仇二字?鲁迅将这二字命为题目,定是有一股熊熊的怒火在心头激烈的燃烧着。
他要向这仇恨的始作俑者展开复仇。
他要复仇,但不是用刀枪复仇。
他要用手中的那支笔,那支锋利尖锐的笔,扎向被复仇者们的血肉、骨髓、灵魂。
鲁迅先生曾明确表示,创作《复仇》的动机是“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
由于对社会上旁观者的憎恶,进而引发内心的痛处并将其展开;或者说由“人道主义”的问题触发,进而引发“个人的无治主义”的展开,从而孕育出最具个体特色的文学作品,是鲁迅创作的经典模式。
综合分析鲁迅先生的其他作品便不难发现,他所认为中国国民最突出的劣根性之一即是看客心理:庸众因无聊而将他人的一切举动事件化、戏剧化,从而旁观之,鉴赏之,以安慰自己的无聊。
他人,特别是其中所谓的“独异个人”,因此被压迫成演员,其爱与死——这生命中最庄严的举动,都在看客的围观中成为表演秀。
如果说仅仅是自己的热忱与鲜血被他人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似乎并不达到值得让人复仇的地步,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男一女所反映的现实主体吧。
他们有温热的血,有锋利的武器,有异于常人的姿态,有不破不立的胆识。
哪怕他们不是完全的“革命者”,也一定是“先驱者”。
在那个时代,先驱者是在无边黑夜中探求光明的人,是为国为民而战斗牺牲的人。
而当他们英勇就义前回眸凝望自己所奉献一切的山河大地时,却发现自己的奋斗被自己致力于救赎的人当做作秀,自己的鲜血不过是自欺欺人而一厢情愿的狂欢,感染不到“看客”分毫,这世界一如自己投入战斗前一般沉沦,又如何能不怒其不争、哀其不醒,又如何能不想要“复仇”?至于复仇的方法,可以说是“兵不血刃”而“一针见血”的。
诗意与旋律——鲁迅散文诗《复仇》《复仇(其二)》赏析

诗意与旋律——鲁迅散文诗《复仇》《复仇(其二)》赏析鲁迅散文诗《《复仇》(其二)》原文与赏析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认为上帝之子是以色列的国王。
兵丁们给他穿上紫袍,戴上荆冠,庆贺他;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他,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他自己的衣服。
看哪,他们打他的头,吐他,拜他……他拒绝喝混有没药的酒,但想清楚地思考以色列人如何对待他们的上帝之子,并对他们的未来感到更加永久的同情,但讨厌他们的现在。
各方都是敌对的,可怜的,被诅咒的。
丁丁叮的一响,指甲尖穿透了他的手掌。
他们要钉他们的上帝之子,所以甜蜜的人,让他的痛苦软。
丁丁一响,指甲尖穿透脚背,碎了一根骨头,疼痛也穿透了心脏。
然而,他们自己钉死了他们的上帝之子,并诅咒人们,这使他在痛苦中感到舒适。
十字架竖起来了;他悬在虚空中。
他没有喝掺了没药的酒。
他想清楚地思考以色列人如何对待他们的上帝之子,并对他们的未来感到更加永久的同情,但讨厌他们的现在。
过路的人辱骂他,祭司长和经学家戏弄他,还有两个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戏弄他。
看哪,和他同钉的……各方都是敌对的,可怜的,被诅咒的。
在手脚的痛苦中,他沉思着可怜的人民钉死上帝之子的悲哀,以及被诅咒的人钉死上帝之子的喜悦,而上帝之子即将被钉死。
突然,断骨的巨大痛苦穿透了内心,他陷入了巨大的喜悦和悲悯。
他的腹部起伏不定,一波怜悯和诅咒的痛苦。
遍地都黑暗了。
“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你为甚么离弃我?!)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
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析】《复仇》与《复仇(其二)》,是《野草》中命意比较明白的两篇。
鲁迅曾解释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
”又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竟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
复仇〔其二〕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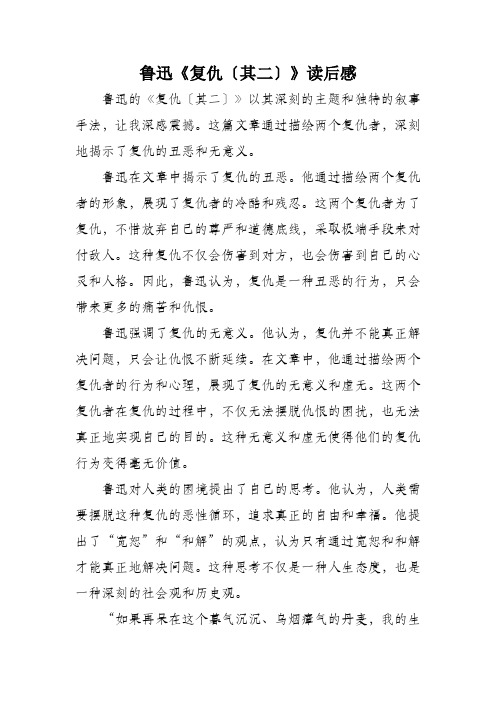
鲁迅《复仇〔其二〕》读后感鲁迅的《复仇〔其二〕》以其深刻的主题和独特的叙事手法,让我深感震撼。
这篇文章通过描绘两个复仇者,深刻地揭示了复仇的丑恶和无意义。
鲁迅在文章中揭示了复仇的丑恶。
他通过描绘两个复仇者的形象,展现了复仇者的冷酷和残忍。
这两个复仇者为了复仇,不惜放弃自己的尊严和道德底线,采取极端手段来对付敌人。
这种复仇不仅会伤害到对方,也会伤害到自己的心灵和人格。
因此,鲁迅认为,复仇是一种丑恶的行为,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和仇恨。
鲁迅强调了复仇的无意义。
他认为,复仇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会让仇恨不断延续。
在文章中,他通过描绘两个复仇者的行为和心理,展现了复仇的无意义和虚无。
这两个复仇者在复仇的过程中,不仅无法摆脱仇恨的困扰,也无法真正地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种无意义和虚无使得他们的复仇行为变得毫无价值。
鲁迅对人类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他认为,人类需要摆脱这种复仇的恶性循环,追求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他提出了“宽恕”和“和解”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宽恕和和解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这种思考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深刻的社会观和历史观。
“如果再呆在这个暮气沉沉、乌烟瘴气的丹麦,我的生命和一切的一切都将萎靡。
”这句话表现了主人公对环境的厌恶,暗示着复仇的必要性。
“年,美国花旗集团董事长杰米·戴蒙,从他的事业之父、人生之师那里听到了一个震惊的通知——让他离开公司。
把他驱赶出公司的,是桑迪·威尔——让花旗集团成为美国第一大金融集团的人。
”这句话揭示了主人公的复仇动机,描绘了他决心复仇的背景。
“去死,去睡就结束了,如果睡眠能结束我们心灵的创伤和肉体所承受的千百种痛苦,那真是生存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
”这句话揭示了主人公内心的痛苦和绝望,为复仇做了铺垫。
“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
”这句话提出了关于“高贵”的定义,暗示着主人公选择反抗而不是忍受。
鲁迅《野草》散文集:《复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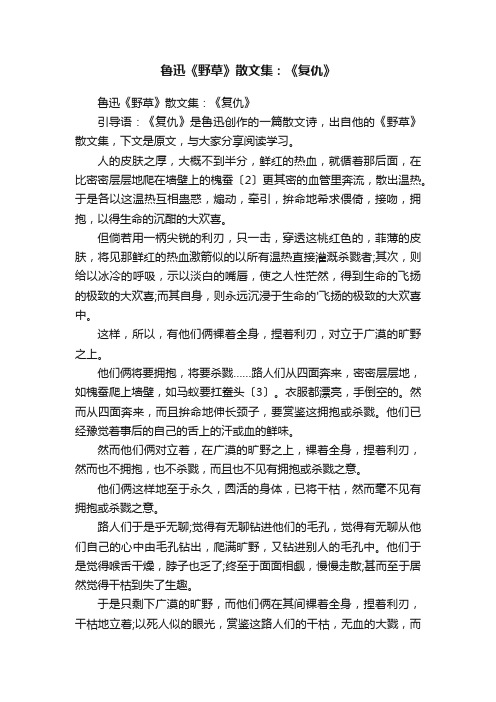
鲁迅《野草》散文集:《复仇》鲁迅《野草》散文集:《复仇》引导语:《复仇》是鲁迅创作的一篇散文诗,出自他的《野草》散文集,下文是原文,与大家分享阅读学习。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2〕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
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鲞头〔3〕。
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
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拚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
他们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然而他们俩对立着,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
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注解】〔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七期。
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
又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致郑振铎信中说:“不动笔诚然最好。
《鲁迅 复仇》6

《这样的战士》:无物之阵消磨战士的生命和价值。
小结:先驱者不能从他人(群众、敌人)获得存在 的价值和意义。
(2)人与自我的关系
《影的告别》:自我彷徨于无地。 《过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 小结:自我是无可归依的存在。 2、反抗绝望:鲁迅精神的精髓 《死火》:“我不如烧完”的哲学。 《影的告别》:“我不如在黑暗中沉没”的哲学。
1、1893年,鲁迅的祖父因科举案入狱。 “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象王子一样
2,化时津变控的旦段家时、但子起人制时巧,思候革1在9是都,民庶候妙当想,失1—中1,不我出民,获然强下望年—国一如就版”就得要制次。辛,薛旦 了 恨 社 , 会 成 “ 庶 革亥“绥我,这“发功说民命革只之家我个这生,点的就命要《庭感社个有革新地又爆建鲁发到会儒名命事方会发立迅生这了家的政情去一,一生变不。思东府,了下1个平9故是”想西就但”子1政史3后一的出是,发—年府料,个强现不待展—袁,汇人人制了知到起革世就编们住一”不它来命凯一(就的方,觉“”。复定第把社搞它间搞。这用四辟我会得在又得个儒辑,看,很最跑很革家)对成从厉初到凶命思》社叫那害阶儒的一想天会 “在—1“如《至12— 在—2—《…… 《—《在—1…2“小《…牺-《小…反在—…小总你如—总-群、、、、、、《中—群果死于—中——复……影—复中—…群结复…牲过结…对中—…结而的果—而众《 1反 1《 1娜国 革 众 显 火 “ 8内国 革 9内 仇 我 但的 薛 仇 国 革 但 众 : 仇 我 上 客 : 凡 , 国 革 但 : 言 反 显 内 言9,野9抗1野1拉11,命,得》还3山 ,命山》所我 告绥》,命我,自》所场》先有如,命我先之抗得山之-年年草年绝草走-“。-觳:要完 “。完:说对 别之:“。对-我:说,:驱一置“。对驱,,觳完,尤--辛辛》,望》尤尤后只觫“反造 只造先的人 》《先只人是先的如我者人身只人者我是觫造我其亥亥鲁:的的怎其其要,我抗要觉话说 觉要说无觉话果是不的无要说不为为,为《 《:鲁《是革革迅鲁主主样是是建他不”建者,话 者建话可者,显谁能主边建话能自了他自上 上“迅上中命命的迅题题》中中立们如,立的常时 的立时归的常得,从张际立时从己希们己海 海我生海国爆爆祖精::国国一就烧倒一孤与, 孤一,依孤与慷我他,的一,他和望就和漫 漫不平漫的发发父神个个的的个看完是个独所却独个却的独所慨从人得荒个却人别光看别语语如史语,,,因的体体,,政了”真政和想总 和政总存和想,哪(了原政总(人明了人》 》》在料--11科精人人--永99--府滑的的府群的拣 群府拣在群的他里群赞,府拣群的的滑的黑汇永永11举髓的的远33,稽哲,,众不那 众,那。众不们来众和无,那众设到稽设暗编远远年年案精精是就剧学但就的同些 的就些的同就,、,可就些、想来剧想中(是是袁袁入神神戏一。。我一麻,光 麻一光麻,看我敌是措一光敌,罢。,沉第戏戏世世狱困困剧定知定木至明 木定明木至了往人促手定明人是?是没四剧剧凯凯。境境的用道用,于些 ,用些,于悲哪)其的用些)两两”辑…的的复复——看儒这儒看何的 看儒的看何壮里获前了儒的获样样的)…看看辟辟——客家“家客已说 客家说客已剧去得进,家说得的的哲》但客客,,人人。思所思的如出 的思出的如;?存的这思出存。。学天我。。对 对失失想以想鉴此, 鉴想,鉴此在,是想,在。津的社社去去控反控赏,然 赏控然赏,的得怎控然的人反会会存存制抗制消则而 消制而消则价了样制而价民抗变变在在庶之庶解我偶 解庶偶解我值反的庶偶值出,革革根根民故民了已不 了民不了已和对悲民不和版却失失本本”””先在留 先”留先在意,哀”留意社不望望依依,,,觉意 觉,意觉义是呵,意义《《过。。据据“与“者, 者“,者。促,“,。呐呐是的的这小这的就 的这就的其我这就喊喊与焦焦个鬼个价露 价个露价奋于个露》》黑虑虑儒截儒值出 值儒出值斗是儒出序序暗。。家然家和阎 和家阎和的以家阎上上捣思不思意王 意思王意,我思王说说乱想同想义并 义想并义独所想并过过。的。的。不 。的不。有感的不::强强反 强反叫到强反不不制制对 制对喊者制对愿愿一一, 一,于为一,将将方方“ 方“生寂方“自自搞搞小 搞小人寞搞小己己得得鬼 得厉反而厉反想想害害不 害不生害不,,的的乐 的乐人的乐传传时时意 时意并时意染染候候的 候的无候的给给,,话 ,话反,话别别就就来 就来应就来人人会会。 会。,会。。。发发发既发生生生非生有有有赞有名名名同名的的的,的东东东也东西西西无西 ——内山完造《上海漫语》
复仇(其二)-鲁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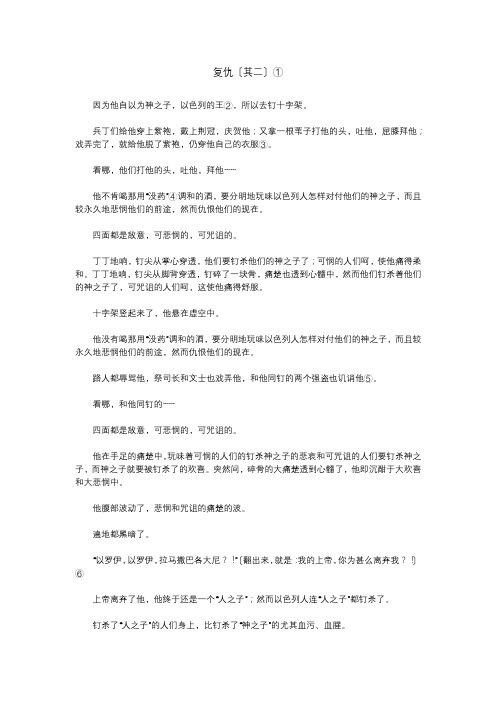
复仇〔其二〕①因为他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②,所以去钉十字架。
兵丁们给他穿上紫袍,戴上荆冠,庆贺他;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他,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他自己的衣服③。
看哪,他们打他的头,吐他,拜他……他不肯喝那用“没药”④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
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他们要钉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悯的人们呵,使他痛得柔和。
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然而他们钉杀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咒诅的人们呵,这使他痛得舒服。
十字架竖起来了,他悬在虚空中。
他没有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路人都辱骂他,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也讥诮他⑤。
看哪,和他同钉的……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
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
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
他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楚的波。
遍地都黑暗了。
“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你为甚么离弃我?!〕⑥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
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注释】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七期。
文中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是根据《新约全书》中的记载。
②以色列的王:即犹太人的王。
据《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十五章载:“他们带耶稣到了各各他地方(各各他:翻出来,就是髑髅地),……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鲁迅《复仇》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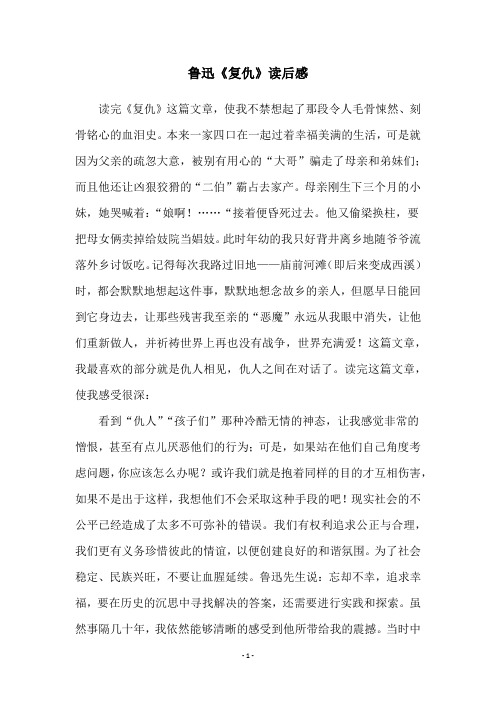
鲁迅《复仇》读后感读完《复仇》这篇文章,使我不禁想起了那段令人毛骨悚然、刻骨铭心的血泪史。
本来一家四口在一起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就因为父亲的疏忽大意,被别有用心的“大哥”骗走了母亲和弟妹们;而且他还让凶狠狡猾的“二伯”霸占去家产。
母亲刚生下三个月的小妹,她哭喊着:“娘啊!……“接着便昏死过去。
他又偷梁换柱,要把母女俩卖掉给妓院当娼妓。
此时年幼的我只好背井离乡地随爷爷流落外乡讨饭吃。
记得每次我路过旧地——庙前河滩(即后来变成西溪)时,都会默默地想起这件事,默默地想念故乡的亲人,但愿早日能回到它身边去,让那些残害我至亲的“恶魔”永远从我眼中消失,让他们重新做人,并祈祷世界上再也没有战争,世界充满爱!这篇文章,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仇人相见,仇人之间在对话了。
读完这篇文章,使我感受很深:看到“仇人”“孩子们”那种冷酷无情的神态,让我感觉非常的憎恨,甚至有点儿厌恶他们的行为;可是,如果站在他们自己角度考虑问题,你应该怎么办呢?或许我们就是抱着同样的目的才互相伤害,如果不是出于这样,我想他们不会采取这种手段的吧!现实社会的不公平已经造成了太多不可弥补的错误。
我们有权利追求公正与合理,我们更有义务珍惜彼此的情谊,以便创建良好的和谐氛围。
为了社会稳定、民族兴旺,不要让血腥延续。
鲁迅先生说:忘却不幸,追求幸福,要在历史的沉思中寻找解决的答案,还需要进行实践和探索。
虽然事隔几十年,我依然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他所带给我的震撼。
当时中国积弱的状况,表面上安定团结,其实危机暗伏。
鲁迅借闰土的遭遇控诉黑暗势力;借凡卡的命运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对穷苦儿童天性压抑的罪恶;他怀着拯救人类灵魂的热忱,诅咒和抗议造成这些不幸的根源——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在《故乡》里抒发难以抑止的悲愤,呼唤传统美德和高尚品格的回归;在《孔乙己》里讽刺麻木愚昧的国民劣根性;在《药》里揭示封建医道和“人血馒头”的惨痛事实;在《明天》里哀叹世间少有不被“吃人者”糟蹋致死的“药”……读罢鲁迅全集,字里行间总会涌动着一股久违的浩气。
鲁迅复仇优秀课件

鲁迅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民族 精神重建的思想动力,也是现代 文学的源头。
他所思考、所感到焦虑的问题, 至今仍然缠绕着我们,警示着我 们。
民主问题【反封建专制,争人权民主,但同时 又提出不迷信民主,防止民主异化——任个人 而排众数——不迷信“民主”】
科学观【科技发展必然极大地改变世界,他又 提出不是科技发达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人的 素质就提高了。他甚至怀疑科学、物质文明无 节制的极大发展,可能会构成对人生的一种威 胁。科学要发展,但要注意人性之全,以人为 本。——剖物质而张灵明—关注人的精神灵魂】
2021/7/1
5
鲁迅主要作品:
小说集:
《呐喊》(1922)、《彷徨》 (1926)、《故事新编》(1936)。 散文集:
1927年北京北新书局初版 散文诗集 《野草》;1928年北京未名社初版《朝 花夕拾》(《旧事重提》)。
杂文集:
《坟》、《热风》、《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 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 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 文 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 部杂文集。
描摹看客的形态、目的 揭示看客的深层心理动机 表达作者内心的愤慨、憎恶、无奈
——为“复仇”做铺垫
阅读思考第6—9段
1、被看者如何“复仇”?
“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 杀戮之意”
“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 干枯,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被看者如何复仇?
——被围观者拒绝被迫演出。借以摆脱 被看、被围观、被鉴赏的尴尬的危险 的处境。
——精神麻木、无爱心,甚至残忍、健忘、 无特操、无“迷信”的一群“看客”。
鲁迅 复仇

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 五、第二部分:看客来了
也不同于作者同时期所写的“随笔”……
他人特别是其中的所谓“独异个人”,因之被迫成为表演者,其庄严神圣的爱与死,都在无聊看客的围观中成为作秀。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注: “大欢喜”:佛家语,此指宗教般的欢欣,极言其喜。
四、第一部分:热血与生命之力
至第四段点明其二人之间两种关系的 极端状态:
或“爱”,则互相拥抱,或“杀”, 则互相杀戮。
注:即生命力发扬的两种极端形态。
五、第二部分:看客来了
以现代观念衡量,此二人或相爱、或相杀,乃完 全为其个体生命力所驱动的个人行为,无关于他 者。
三、鲁迅因何而“复仇”?
“复仇”的复杂内涵
“庸众”因“无聊”而将他人的一切举 动“事件”化、“戏剧”化,从而“旁 观”之,“赏鉴”之,以慰其无聊;他 人特别是其中的所谓“独异个人”,因 之被迫成为表演者,其庄严神圣的爱与 死,都在无聊看客的围观中成为作秀。 而被赏鉴者欲摆脱此一地位,则只有 “毫无动作”,使路人“无戏可看”, 以此向看客们“复仇”!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
镜子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论》:“空
前的民族英雄”
《复仇》文本详析
一、焦点问题
为何“复仇”? 今天,还需要鲁迅式
的“复仇”吗?
二、散文诗,怎样读?
本文是《野草》中的一篇重要作品。 《野草》的基本特点是其“独语”性 不同于作者的“杂感”类作品…… 也不同于作者同时期所写的“随笔”……
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 七、复仇! 愤激还是无奈?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复仇导语:我们这里的“复仇”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文章(《复仇》),二是指我们的话题——终极发挥——是复仇的。
因为我们愿意从鲁迅的《复仇》中读出“复仇的终极发挥”。
我们将捋一捋鲁迅写作该文时的心理反应和身外环境,主要依据是他老先生前后的言论和一些显然的事实;接着将尽量不带感情地引述一些时人的感受;其中,加以可能被认作狂妄的评点,把“复仇”推向极致——一个哲学的归宿。
像大多数鲁迅的散文诗一样,《复仇》的篇幅不大(内涵可能是无穷的),该文的出笼,当然应该自1881年9月25日始。
其实这本不值得一说。
真要说的话,鲁迅之生,以及生之生,倒可以推演整个人类的本初了。
也不见得。
我们关注的是他的经历,以及对于经历的思维感触。
很明显的是,“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使幼年的鲁迅“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这一点很关键,许多人都指出了。
大凡思想家,总要游离于人世的,生活的变动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东渡日本,参加革命,激扬心志,驰骋文字。
我们当然愿意寻找与“复仇”主题相关的瞬间,也就摸着了《摩罗诗力说》的情感心弦。
“如斗剑之士,转辗于众目前,使抱战栗和愉快而观其鏖扑。
故无流血于众之目前者,其群祸矣;虽有而众不之视,或且进而杀之,斯其为群,乃愈益祸而不可救也!”浪漫主义引发了欧洲大革命,旗帜之一是“个性主义”。
也许个性主义和民主主义挂不上钩,许多人也争吵不息。
毫无疑问,鲁迅选择了她。
中国需要主义,即使是极端的。
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见得多了,不仅失望,而且麻木(拿破仑之后的欧洲浪漫派人士们也多是这样)。
于是去钞古碑,于是去看星星(《呐喊自序》)。
新文化运动的肇端大概是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吧?甚或更早。
1917年起了一个小波澜,1919年时才起了几个大波澜。
风火了好一阵子(据说倒是可以挖掘历史意义的)。
鲁迅一开始就没抱多少信心,但毕竟有希望。
“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呐喊自序》)。
我们也可以猜想,鲁迅有过惊喜,这是肯定的。
他能够感受到浪漫主义的气息,也感觉到了群众运动的力量。
但鲁迅还不至于没有回忆的能力。
回忆是令人心酸的。
会不会是“辛亥革命现象”呢?鲁迅心中有疑虑,疑虑往往使人有活下去的信念,活下去是需要运动的。
《呐喊》就是疑虑烟雾中的运动。
彷徨不幸而至,这是可以预见的。
新文化阵营马上就分裂了。
原因很多,错综复杂。
人在柔弱的时候,容易结合(可能暗地里还有互啮);得势了以后,思想就会出错。
鲁迅并没有得势,或者说不想得到势,思想也没有出错。
应该说,从一开始,鲁迅就对新文化不满意。
这是理想道路的分裂。
他试图扭转,按照自己的标准。
许多人都在依着自己的标准扭转着。
这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在分裂中新生。
鲁迅的思想分裂了。
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分裂的,也正在分裂着。
从一种不着边际的视角上看,精神院的长期顾客们才不至于精神分裂,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思想,或间歇性没有思想——针对间歇性精神病人来说。
有思想就存在着精神分裂。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思想分裂是正常的变态。
鲁迅的与众不同在于他更变态。
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权且把我们当作“辞可达意主义者”吧)。
正像公认的那样,这一时期的杂文是“奋斗的”、“激昂的”、“充实的”、“积极的”;而其散文(诗)则是“黑暗的”、“虚无的”、“堕落的”、“沮丧的”;日记倒是琐碎的,显示着为人的无奈;书信则更情感化,细腻的不得了。
多面的人生大概才是典型的人生吧。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鲁迅的家庭生活。
兄弟失和彻底破碎了鲁迅对传统和谐美执著的最后一块阵地;孝敬母亲却是无争的,虽然有时也有无奈;与朱安女士的法律关系还得维系;宋景先生激昂着鲁迅的现代性追求。
还有一些别的因素,生计所迫,女师大学潮,诸如此类,共同形成了鲁迅写作《复仇》的背景及环境。
现在,我们大体上描绘了一个时期以来鲁迅的生境图画。
我们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但不能忽视环境对人生的影响。
生活是需要理由的,说话也不是空穴来风。
当下有许多人要踏倒鲁迅,孰不料正是鲁迅的存在才给与他们说话的理由,乃至于作为过程的生活。
顺便说一下,为什么是鲁迅而不是别人给我们以说话权利呢?这应当是有趣而又值得深思的事。
鲁迅自己说《野草》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野草〉英文译本序》),可见他对这个集子的喜爱。
“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些措辞也就含糊了” (《〈野草〉英文译本序》)。
这句话又暗示我们,对于《复仇》,大可以含糊的去理解。
这就是朦胧,就是象征。
大凡象征主义者是喜爱含糊的,越含糊越好,以至于成为颇不讨人爱的神秘主义者。
这也是研究象征派“家”们所关注的。
需要提及的是,鲁迅在这一时期,翻译了日本学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这里有一条学术渊源线索,即弗洛伊德的原欲观念祟入鲁迅的头脑中(很显然是扭曲的),至于说“象征”精神,中国古来有之,最大的获益也就是见识了另一种方式而已。
“血”的意象的塑造应当是最成功的。
其具有象征意味最为不争。
万圣的爱和凶暴的杀戮都汇集于血。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
它奔流,它沸腾。
它汩汩作响,怂恿着人性的骚动。
这是毋庸讳言的。
人类赞美血及相关的火、光和红色,就因为这些喻体至少代表了生的力量和希望。
我们要看到,在冠冕堂皇的盛装下面是炼狱般的原欲——这个据说为弗洛伊德所俘获的撒旦。
鲁迅大概不甘这样地生,“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
当“杀戮”被发现的时候,却也是这样的酣畅流离。
人类运命的第二个“生”被发现了。
我们同样要看到,在獠牙青面的画皮里面,也竟然蒙着一个出水芙蓉的爱——这个上帝心尖的肌跳。
血的意象成为人类永恒的主题,以皮肤为界分隔着拥抱和杀戮。
善和恶在这里降生,却是难产之后的阵痛。
鲁迅思考善恶美丑很久了,并似乎已经有了明朗的认识。
但时不时要孤立自己,体味孤寂的悲哀。
也许他根本就是无意识。
“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竟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
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
”(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信)这段话给后人许多启示。
显然,这是鲁迅有意识时说的话。
“凡是人,只要他血管里流着热血,就都有他的爱憎。
有所爱的都希求偎依、拥抱、接吻,有所憎的甚至会发生杀戮。
……但是,也有一种人是专门冷漠地赏鉴别人的相爱或相杀的。
正是为了惊醒这些无聊的看客,鲁迅描写了一对男女,持刀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上,……并不拥抱,更不杀戮……让看客被自己的麻木无聊所杀戮。
这种‘复仇’,显然并不能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旁观者既不能因此而觉悟,复仇者也给自己招致了不必要的麻烦。
”显然,吴小美的这段论述出自于现实关怀的立场,并不为过。
从实际状况考虑(包括已解释出来的鲁迅创作的本意),这是完全站的注脚的。
但同时也许是“象征主义的尴尬”(可参见T•E•休姆著名的论文《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
“烈士被庸众所疏远和虐待,成了孤独者;但这孤独者这只能从拯救庸众、甚至为他们牺牲中,才能获得自己生存的意义,而他得到的回报,又只能是被他想拯救的那些人们关进监狱、剥夺权利、殴打甚至杀戮。
”李欧梵提出“独异个人”与“庸众”对立的看法,试图与鲁迅靠近。
应当说,这是成功的,至少在民主层面上获得了普遍的认可。
当然也是现实关怀的,——一种破坏“诗的张力” 的因素(可参看著名的艾伦•退特的论文《论诗的张力》)一个时期以来,“模糊的东西” 不被人们所认好,往往也被人们归咎为神秘主义的特质。
比较清楚的是,许多人搞“清晰的东西”,即求真心态作祟的贴近当事人、为善心理运作的心仪受难者,搞得多了,不免圆滑;见得多了,也不免滑稽,于是才萌生了“模糊的东西”。
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把“模糊的东西”理解作一种终极的发挥,就像梦魇时的沉酣,又如仰望夜空时的心旷神怡。
我们也只能以类比的方法隐喻之。
可以肯定的是(当然我们也愿意这样),就是“模糊的东西”是人们心理的追求之一,汲汲于实的心灵需要终极发挥带来的松弛。
这也是我们可以用来骗人的理由之一。
(四)在准备投入火热的生活之前,我们有义务作一番已然的交代。
“有”与“无”的相依相伴为历史的最终基底,“实”与“虚”的天衣无缝演绎人性的满足与虚根,祈祷和享受缘于宗教性质的原罪,阴阳结合始为和谐的无极,天地匹配方为自然的亘久,坚白互融却为理性的深渊。
请大家不要为生活的玄虚所迷茫,美妙的纱幔可能已经打开。
鲁迅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野草题辞》)在这里,我们不想贴近鲁迅,而权把他当作人类的代言人。
从“为了什么而死”到“不为什么而生至死”,应当是人类生活的典型范式。
即使有不少人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其血液流动的沟渠里必然是幽灵的穿梭。
历史的理由在于身份认同的终极追求,背后是平静的生活,不管是做作者,还是鉴赏者,乃至于杀戮者。
生活中总有一些不喜欢的东西,可能具有民族性。
令人难堪的是,往往说不清楚这些是什么东西。
总之是一种感觉。
这才想到血的流淌,聆听着血流的潺潺。
感觉转移了,反而有了“饥饿”的意念,于是才在物质世界中寻找填补。
这样思想脉络的人可能不多,鲁迅却是超绝的一个。
感觉的外化当然是清晰的,无怪乎人们想到“孤独者”对“庸众”的“复仇”。
这本不是什么失误,却不免缺乏了物质的内敛。
我们把“孤独者”内敛为喜怒无常的无边昊天,把“庸众”内敛为固若金汤的冷铁壁墙,“复仇”则是流淌的血了。
在皮下的时候警醒了上帝的原罪,在皮上的时候喷薄为撒旦的印象画。
在终极的“无地”,却发挥为“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
鲁迅的《复仇(其二)》作于1924年的年底,因为五四的退潮和兄弟的反目,他那时的心境颇为落寞,这样落寞的心境与《圣经》中耶稣受难的故事共鸣,就形成了这篇短文悲愤阴冷的色调。
这篇短文对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描写,采用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兵丁们的钉杀、路人的辱骂、祭司长和文士的戏弄和被同钉的两个强盗的讥诮,构成了四周无尽的敌意,而耶稣则是在这无尽的敌意中,也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被钉杀的悲哀和就要被钉杀的欢喜。
耶稣自以为是神之子,要拯救以色列,然而却受到以色列人的钉杀,这是他感到悲哀的原因;因为要拯救以色列而被以色列人钉杀,他于是对他们的现在怀着仇恨,然而能以自己的被钉杀来反证他们的血腥,却也体味到一种反抗的欢喜。
所以他拒绝“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他要以自己绝对的反抗企图唤醒他们,从而体认到自己对他们的将来所怀着的悲悯,然而钉杀在继续,敌意与蔑视也不断地增加,他终于在碎骨的大痛楚中,在遍地的黑暗中,喊出“我的上帝,你为甚么离弃我”的绝望,在这样的痛苦的喊声中,他由神之子而变成了人之子,肉体毁灭所带来的痛楚超过了精神的痛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