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诗人李煜描写春花秋月的人间古诗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诗人李煜描写春花秋月的人间古诗李煜南唐元宗(即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莲峰居士,汉族,生于金陵(今江苏南京),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铜山区),南唐最后一位国君。
接下来小编会给大家分享一首关于李煜的古诗词。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五代: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雕栏通:阑)【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译文这年的时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往事知道有多少!昨夜小楼上又吹来了春风,在这皓月当空的夜晚怎能忍受得了回忆故国的伤痛。
精雕细刻的栏杆、玉石砌成的台阶应该都还在,只是所怀念的人已衰老。
要问我心中有多少哀愁,就像那不尽的春江之水滚滚东流。
注释此调原为唐教坊曲,初咏项羽宠姬虞美人死后地下开出一朵鲜花,因以为名。
又名《一江春水》、《玉壶水》、《巫山十二峰》等。
双调,五十六字,上下片各四句,皆为两仄韵转两平韵。
了:了结,完结。
砌:台阶。
雕栏玉砌:指远在金陵的南唐故宫。
应犹:一作“依然”。
朱颜改:指所怀念的人已衰老。
君:作者自称。
能:或作“都”、“那”、“还”、“却”。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创作背景此词与《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均作于李煜被毒死之前,为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这时李煜归宋已近三年。
太平兴国三年,徐铉奉宋太宗之命探视李煜,李煜对徐铉叹曰:“当初我错杀潘佑、李平,悔之不已!”大概是在这种心境下,李煜写下了这首《虞美人》词。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人物介绍李煜(937年8月15日―978年8月13日),南唐元宗(即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莲峰居士,汉族,生于金陵(今江苏南京),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铜山区),南唐最后一位国君。
李煜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修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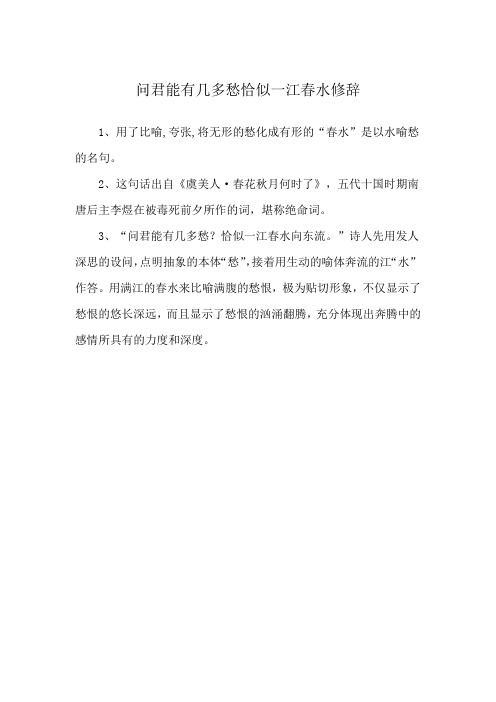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修辞
1、用了比喻,夸张,将无形的愁化成有形的“春水”是以水喻愁的名句。
2、这句话出自《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在被毒死前夕所作的词,堪称绝命词。
3、“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诗人先用发人深思的设问,点明抽象的本体“愁”,接着用生动的喻体奔流的江“水”作答。
用满江的春水来比喻满腹的愁恨,极为贴切形象,不仅显示了愁恨的悠长深远,而且显示了愁恨的汹涌翻腾,充分体现出奔腾中的感情所具有的力度和深度。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全诗翻译赏析及作者出处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全诗翻译赏
析及作者出处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句话是什幺意思?出自哪首诗?作者是谁?下面小编为同学们整理出这首古诗词的全文翻译及全文赏析,提供给同学们。
希望能对同学的古诗词的学习与提高有所帮助。
1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出自五代李煜的《虞美人·春花
秋月何时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雕栏通:阑)
1全文赏析《虞美人》是李煜的代表作,也是李后主的绝命词。
相传
他于自己生日(七月七日)之夜(“七夕”),在寓所命歌妓作乐,唱新作《虞美人》词,声闻于外。
宋太宗闻之大怒,命人赐药酒,将他毒死。
这首词通过今昔交错对比,表现了一个亡国之君的无穷的哀怨。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三春花开,中秋月圆,岁月不断更替,人生多幺美好。
可我这囚犯的苦难岁月,什幺时候才能完结呢?“春花秋月何时了”表明词人身为阶下囚,怕春花秋月勾起往事而伤怀。
回首往昔,身为国君,过去许许多多的事到底做得如何呢,怎幺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据史书记载,李煜当国君时,日日纵情声色,不理朝政,枉杀谏臣……透过此句,我们不难看出,这位从
威赫的国君沦为阶下囚的南唐后主,此时此刻的心中有的不只是悲苦愤慨,多少也有悔恨之意。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苟且偷生的小楼又一次春风吹拂,春花又将怒放。
回想起南唐的王朝、李氏的社稷——自。
请简要赏析尾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妙处。

请简要赏析尾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妙处。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中国古代诗人陆游的一首名作,这句话非常有诗意,感受到季节的变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多种感情的交织。
这句话妙处在于:
一、对比生动
以“几多愁”对比“江春水”,一个表示苦涩,一个表示婉转,这样的对比很生动,突出水如人情,也突出了心中的悸动。
二、境界深刻
句中使用“恰似”,而非“就是”,表达了一种更深刻的境界。
“问君能有几多愁”,一般不会有特定的答案,但却可以感受到对愁问的理解,以及和江流之间的共情。
三、寓意深邃
句中的“流”是指什么,也许有无数的可能性:可能是一句长话短说,
也可能表达爱情、友谊、家庭等等;可能也代表着一种精神上的放荡和流浪。
而无论如何,“东”字却温暖而深邃,不失为句中一个隐含的寓意。
尾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词凝神,情有可原,充满了思考和情感的力量,因此,在古典名句中仍占据一席之地。
南唐后主李煜断头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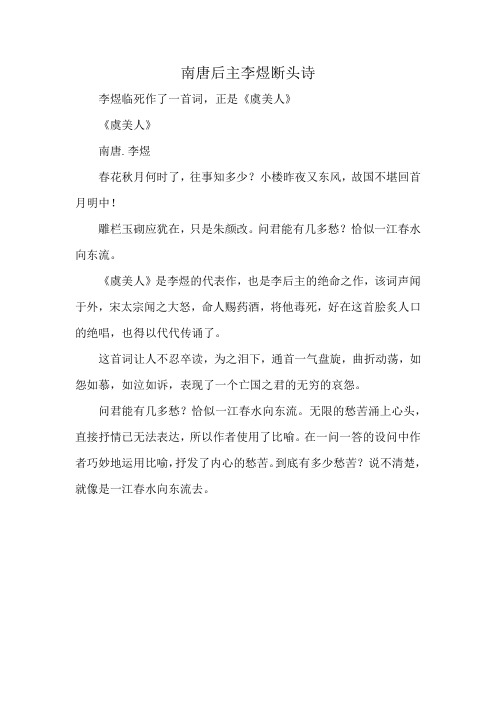
南唐后主李煜断头诗
李煜临死作了一首词,正是《虞美人》
《虞美人》
南唐.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是李煜的代表作,也是李后主的绝命之作,该词声闻于外,宋太宗闻之大怒,命人赐药酒,将他毒死,好在这首脍炙人口的绝唱,也得以代代传诵了。
这首词让人不忍卒读,为之泪下,通首一气盘旋,曲折动荡,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表现了一个亡国之君的无穷的哀怨。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无限的愁苦涌上心头,直接抒情已无法表达,所以作者使用了比喻。
在一问一答的设问中作者巧妙地运用比喻,抒发了内心的愁苦。
到底有多少愁苦?说不清楚,就像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去。
春花秋月何时了整首诗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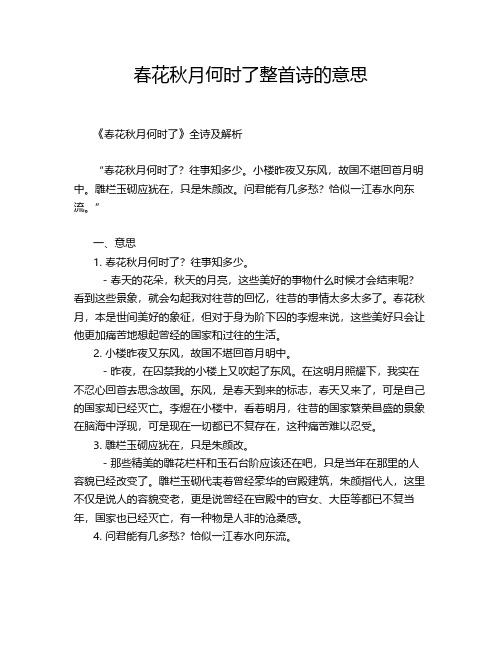
春花秋月何时了整首诗的意思《春花秋月何时了》全诗及解析“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意思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 春天的花朵,秋天的月亮,这些美好的事物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看到这些景象,就会勾起我对往昔的回忆,往昔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春花秋月,本是世间美好的象征,但对于身为阶下囚的李煜来说,这些美好只会让他更加痛苦地想起曾经的国家和过往的生活。
2.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 昨夜,在囚禁我的小楼上又吹起了东风。
在这明月照耀下,我实在不忍心回首去思念故国。
东风,是春天到来的标志,春天又来了,可是自己的国家却已经灭亡。
李煜在小楼中,看着明月,往昔的国家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脑海中浮现,可是现在一切都已不复存在,这种痛苦难以忍受。
3.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 那些精美的雕花栏杆和玉石台阶应该还在吧,只是当年在那里的人容貌已经改变了。
雕栏玉砌代表着曾经豪华的宫殿建筑,朱颜指代人,这里不仅是说人的容貌变老,更是说曾经在宫殿中的宫女、大臣等都已不复当年,国家也已经灭亡,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沧桑感。
4.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 要问我心中有多少忧愁?就像那滔滔不绝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去。
这是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忧愁。
江水滔滔,连绵不绝,就如同李煜心中那无尽的愁绪,无法断绝,难以排遣。
二、衍生注释1. 春花秋月:这是自然中非常美好的景象,春天百花盛开,秋天明月皎洁。
在诗词中常常被用来表达美好的时光或者象征着时光的流转。
这里李煜用这两个意象,更多的是一种反讽,美好的事物对他来说却是痛苦的源泉。
2. 故国:指李煜曾经统治的南唐。
南唐在李煜在位时被宋朝所灭,李煜被俘,从一个国君沦为阶下囚。
他对故国有着深深的眷恋和不舍。
3. 雕栏玉砌:雕绘的栏杆,玉石砌成的台阶,这是形容宫殿建筑的精美豪华,代表着李煜曾经拥有的富贵和权力。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翻译、理解性默写、简答及答案【部编版高一必修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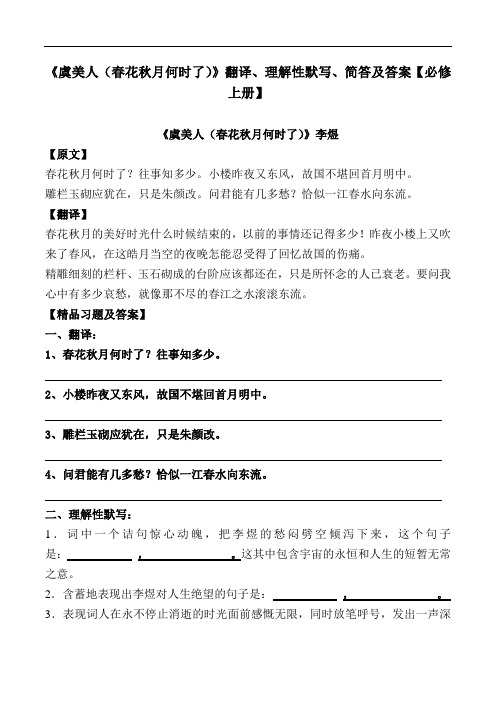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翻译、理解性默写、简答及答案【必修上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煜【原文】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翻译】春花秋月的美好时光什么时候结束的,以前的事情还记得多少!昨夜小楼上又吹来了春风,在这皓月当空的夜晚怎能忍受得了回忆故国的伤痛。
精雕细刻的栏杆、玉石砌成的台阶应该都还在,只是所怀念的人已衰老。
要问我心中有多少哀愁,就像那不尽的春江之水滚滚东流。
【精品习题及答案】一、翻译:1、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3、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4、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二、理解性默写:1.词中一个诘句惊心动魄,把李煜的愁闷劈空倾泻下来,这个句子是:,。
这其中包含宇宙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无常之意。
2.含蓄地表现出李煜对人生绝望的句子是:,。
3.表现词人在永不停止消逝的时光面前感慨无限,同时放笔呼号,发出一声深沉的浩叹的句子是:,。
4.直接抒发亡国之恨的句子是:,。
5.用对比手法,反衬出人生无常的句子是:,。
7.用比喻、夸张、设问手法写出愁思的多与深广的句子是:,。
这与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简答:1.“春花秋月”本是美好事物,作者为什么希望它结束呢?2.讨论:“往事知多少”中的“往事”具体指什么?换句话说,李煜到底在怀念什么?3. “小楼昨夜又东风”中的“又”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4.词的最后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感情?【参考答案】一、翻译:1、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翻译:春花秋月的美好时光什么时候结束的,以前的事情还记得多少!2、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翻译:昨夜小楼上又吹来了春风,在这皓月当空的夜晚怎能忍受得了回忆故国的伤痛。
关于愁的诗句飞花令

关于愁的诗句飞花令1.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就像李煜的愁绪如那无尽的江水,流淌不息。
你说,咱生活中那些烦恼事儿,是不是也像这江水一样,有时多有时少呀?2.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李白这愁得头发都那么长啦!哎呀,那咱有时候发愁,是不是感觉头发都要愁白几根呢?3.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李清照的愁连小船都载不动,这得多愁呀!咱要是遇到特别难的事儿,那愁绪会不会也这么重呢?4.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这离愁就像乱麻一样,怎么也理不清楚。
好比和好朋友分别时,那心里的愁绪不就是这样嘛!5.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想借酒消愁反而更愁,这多无奈呀!就像有时候我们想逃避烦恼,却发现根本躲不掉,是不是?6.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把愁心寄托给明月,多有意思的想法呀!我们不也会把心里的愁跟别人倾诉嘛。
7.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那雨丝就像愁绪一样细密,真的好形象啊!下雨的时候,会不会也让你想起一些发愁的事儿呢?8.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这离愁随着距离越来越远还越来越多,就像那春水一样绵延不绝。
就好像和家人分别后,那思念和愁绪是不是也一直萦绕心头呢?9.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思念带来的愁绪两个人都有,真的好贴切呀!当你和喜欢的人不能在一起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闲愁呢?10.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等真正知道了愁的滋味,却又不想说了。
这不就是我们有时候的状态嘛,心里有很多愁却不知道怎么表达。
我的观点结论:愁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种情绪,这些诗句把愁描绘得如此生动形象,让我们更能感受到古人的情感,也让我们对自己的愁绪有了更深的理解。
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诗词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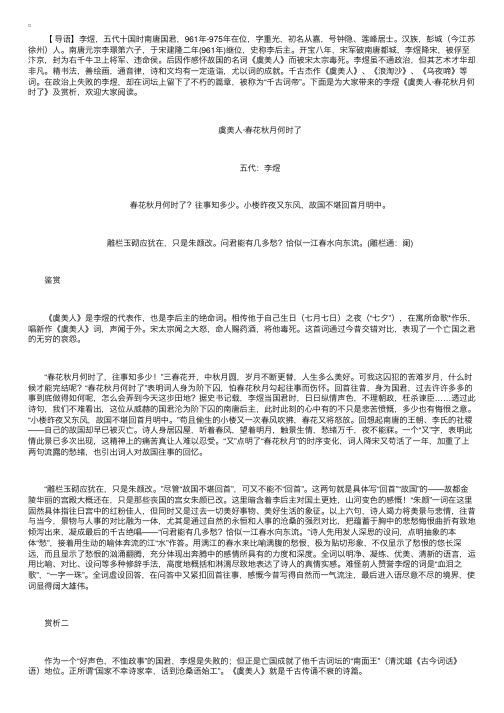
【导语】李煜,五代⼗国时南唐国君,961年-975年在位,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
汉族,彭城(今江苏徐州)⼈。
南唐元宗李璟第六⼦,于宋建隆⼆年(961年)继位,史称李后主。
开宝⼋年,宋军破南唐都城,李煜降宋,被俘⾄汴京,封为右千⽜卫上将军、违命侯。
后因作感怀故国的名词《虞美⼈》⽽被宋太宗毒死。
李煜虽不通政治,但其艺术才华却⾮凡。
精书法,善绘画,通⾳律,诗和⽂均有⼀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
千古杰作《虞美⼈》、《浪淘沙》、《乌夜啼》等词。
在政治上失败的李煜,却在词坛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被称为“千古词帝”。
下⾯是为⼤家带来的李煜《虞美⼈·春花秋⽉何时了》及赏析,欢迎⼤家阅读。
虞美⼈·春花秋⽉何时了 五代:李煜 春花秋⽉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楼昨夜⼜东风,故国不堪回⾸⽉明中。
雕栏⽟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多愁?恰似⼀江春⽔向东流。
(雕栏通:阑) 鉴赏 《虞美⼈》是李煜的代表作,也是李后主的绝命词。
相传他于⾃⼰⽣⽇(七⽉七⽇)之夜(“七⼣”),在寓所命歌*作乐,唱新作《虞美⼈》词,声闻于外。
宋太宗闻之⼤怒,命⼈赐药酒,将他毒死。
这⾸词通过今昔交错对⽐,表现了⼀个亡国之君的⽆穷的哀怨。
“春花秋⽉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三春花开,中秋⽉圆,岁⽉不断更替,⼈⽣多么美好。
可我这囚犯的苦难岁⽉,什么时候才能完结呢?“春花秋⽉何时了”表明词⼈⾝为阶下囚,怕春花秋⽉勾起往事⽽伤怀。
回⾸往昔,⾝为国君,过去许许多多的事到底做得如何呢,怎么会弄到今天这步⽥地?据史书记载,李煜当国君时,⽇⽇纵情声⾊,不理朝政,枉杀谏⾂……透过此诗句,我们不难看出,这位从威赫的国君沦为阶下囚的南唐后主,此时此刻的⼼中有的不只是悲苦愤慨,多少也有悔恨之意。
“⼩楼昨夜⼜东风,故国不堪回⾸⽉明中。
”苟且偷⽣的⼩楼⼜⼀次春风吹拂,春花⼜将怒放。
回想起南唐的王朝、李⽒的社稷——⾃⼰的故国却早已被灭亡。
诗⼈⾝居囚屋,听着春风,望着明⽉,触景⽣情,愁绪万千,夜不能寐。
虞美人高中课文原文

虞美人高中课文原文虞美人高中课文原文虞美人此词一反寻常怀人念运词的凄恻,极淡远清疏之致地表情达意,为这类题材词作境界的开拓作出了贡献。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虞美人高中课文原文,欢迎来参考!虞美人作者: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注释①此调原为唐教坊曲,初咏项羽宠姬虞美人,因以为名。
又名《一江春水》、《玉壶水》、《巫山十二峰》等。
双调,五十六字,上下片各四句,皆为两仄韵转两平韵。
②了:了结,完结。
③砌:台阶。
雕阑玉砌:指远在金陵的南唐故宫。
应犹:一作“依然”。
④朱颜改:指所怀念的人已衰老。
⑤君:作者自称。
能:或作“都”、“那”、“还”、“却”。
赏析此词大约作于李煜归宋后的第三年。
词中流露了不加掩饰的故国之思,据说是促使宋太宗下令毒死李煜的原因之一。
那么,它等于是李煜的绝命词了。
全词以问起,以答结;由问天、问人而到自问,通过凄楚中不无激越的音调和曲折回旋、流走自如的艺术结构,使作者沛然莫御的愁思贯穿始终,形成沁人心脾的美感效应。
诚然,李煜的故国之思也许并不值得同情,他所眷念的往事离不开“雕栏玉砌”的帝王生活和朝暮私情的`宫闱秘事。
但这首脍炙人口的名作,在艺术上确有独到之处:“春花秋月”人多以美好,然后作者却殷切企盼它早日“了”却;小楼“东风”带来春天的信息,却反而引起作者“不堪回首”的嗟叹,因为它们都勾发了作者物是人非的枨触,跌衬出他的囚居异邦之愁,用以描写由珠围翠绕,烹金馔玉的江南国主一变而为长歌当哭的阶下囚的作者的心境,是真切而又深刻的。
结句“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以水喻愁的名句,含蓄地显示出愁思的长流不断,无穷无尽。
同它相比,刘禹锡的《竹枝调》“水流无限似侬愁”,然后稍嫌直率,而秦观《江城子》“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则又说得过尽,然后反而削弱了感人的力量。
可以说,李煜此词所以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在很大程度上,然后正有赖于结句以富有感染力和向征性的比喻,将愁思写得既形象化,又抽象化:作者并没有明确写出其愁思的真实内涵——怀念昔日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而仅仅展示了它的外部形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问君能有几多愁下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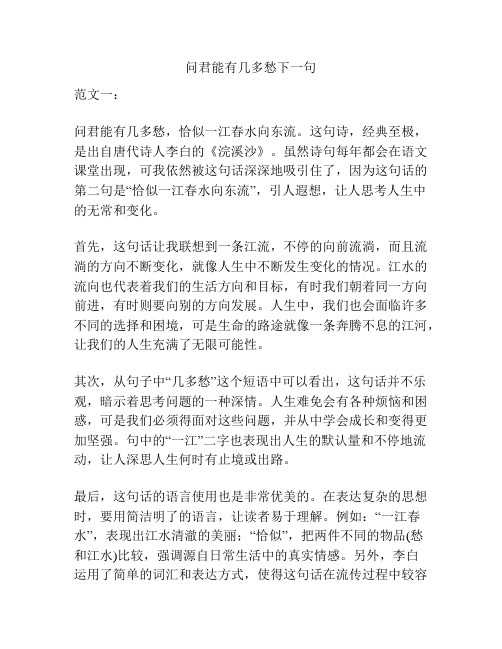
问君能有几多愁下一句范文一: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句诗,经典至极,是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浣溪沙》。
虽然诗句每年都会在语文课堂出现,可我依然被这句话深深地吸引住了,因为这句话的第二句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引人遐想,让人思考人生中的无常和变化。
首先,这句话让我联想到一条江流,不停的向前流淌,而且流淌的方向不断变化,就像人生中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
江水的流向也代表着我们的生活方向和目标,有时我们朝着同一方向前进,有时则要向别的方向发展。
人生中,我们也会面临许多不同的选择和困境,可是生命的路途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无限可能性。
其次,从句子中“几多愁”这个短语中可以看出,这句话并不乐观,暗示着思考问题的一种深情。
人生难免会有各种烦恼和困惑,可是我们必须得面对这些问题,并从中学会成长和变得更加坚强。
句中的“一江”二字也表现出人生的默认量和不停地流动,让人深思人生何时有止境或出路。
最后,这句话的语言使用也是非常优美的。
在表达复杂的思想时,要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让读者易于理解。
例如:“一江春水”,表现出江水清澈的美丽;“恰似”,把两件不同的物品(愁和江水)比较,强调源自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情感。
另外,李白运用了简单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使得这句话在流传过程中较容易被人们接受。
在我看来,这句话非常经典,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发掘人生价值和意义。
正如上文所述,人生就像一条江流,不断的前行,充满变化和无尽的可能性。
我们要善于去享受人生的过程,处理和解决任何问题,并不断地改善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出色的人。
范文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人生的波澜起伏,无论是人生高峰还是低谷,我们都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梦想。
“几多愁”,这句话有两种不同的感情,一种来自于豪放,一种则是淡雅幽深。
它描绘了人们情感的矛盾和内心的波折,也使我们想起人生中的变化和困难。
正如诗中所说,“恰似人生中波澜起伏,我们也会经历高峰和低谷。
李清照武陵春原文及赏析

李清照武陵春原文及赏析李清照武陵春原文及赏析《武陵春》这首词是公元1135年(宋高宗绍兴五年)李清照避难浙江金华时所作。
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词意写的是暮春三月景象,当做于绍兴五年三月。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李清照武陵春原文及赏析,欢迎阅读。
原文:武陵春李清照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翻译:恼人的风雨停歇了,枝头的花朵落尽了,只有沾花的尘土犹自散发出微微的香气。
抬头看看,日已高,却仍无心梳洗打扮。
春去夏来,花开花谢,亘古如斯,唯有伤心的人、痛心的事,令我愁肠百结,一想到这些,还没有开口我就泪如雨下。
听人说双溪的春色还不错,那我就去那里划划船,姑且散散心吧。
唉,我真担心啊,双溪那叶单薄的小船,怕是载不动我内心沉重的忧愁啊!赏析:这首词是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作者避难浙江金华时所作。
当年她是五十三岁。
那时,她已处于国破家亡之中,亲爱的丈夫死了,珍藏的文物大半散失了,自己也流离异乡,无依无靠,所以词情极其悲苦。
首句写当前所见,本是风狂花尽,一片凄清,但却避免了从正面描写风之狂暴、花之狼藉,而只用“风住尘香”四字来表明这一场小小灾难的后果,则狂风摧花,落红满地,均在其中,出笔极为蕴藉。
而且在风没有停息之时,花片纷飞,落红如雨,虽极不堪,尚有残花可见;风住之后,花已沾泥,人践马踏,化为尘土,所余痕迹,但有尘香,则春光竟一扫而空,更无所有,就更为不堪了。
所以,“风住尘香”四字,不但含蓄,而且由于含蓄,反而扩大了容量,使人从中体会到更为丰富的感情。
次句写由于所见如彼,故所为如此。
日色已高,头犹未梳,虽与《凤凰台上忆吹箫》中“起来慵自梳头”语意全同,但那是生离之愁,这是死别之恨,深浅自别。
三、四两句,由含蓄而转为纵笔直写,点明一切悲苦,由来都是“物是人非”。
而这种“物是人非”,又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变化,而是一种极为广泛的、剧烈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的变化,无穷的事情、无尽的痛苦,都在其中,故以“事事休”概括。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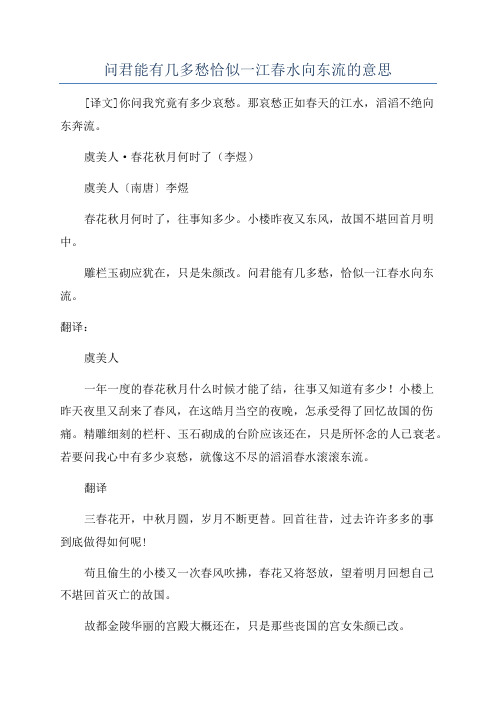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意思[译文]你问我究竟有多少哀愁。
那哀愁正如春天的江水,滔滔不绝向东奔流。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煜)虞美人〔南唐〕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翻译:虞美人一年一度的春花秋月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往事又知道有多少!小楼上昨天夜里又刮来了春风,在这皓月当空的夜晚,怎承受得了回忆故国的伤痛。
精雕细刻的栏杆、玉石砌成的台阶应该还在,只是所怀念的人已衰老。
若要问我心中有多少哀愁,就像这不尽的滔滔春水滚滚东流。
翻译三春花开,中秋月圆,岁月不断更替。
回首往昔,过去许许多多的事到底做得如何呢!苟且偷生的小楼又一次春风吹拂,春花又将怒放,望着明月回想自己不堪回首灭亡的故国。
故都金陵华丽的宫殿大概还在,只是那些丧国的宫女朱颜已改。
问君你能有多少哀愁,那过往的哀愁好像一江春水浩浩荡荡地流走了。
赏析:《虞美人》是李煜的代表作,也是李后主的绝命词。
相传他于自己生日(七月七日)之夜(“七夕”),在寓所命故妓作乐,唱新作《虞美人》词,声闻于外。
宋太宗闻之大怒,命人赐药酒,将他毒死。
这首词通过今昔交错对比,表现了一个亡国之君的无穷的哀怨。
“春花秋月何时了?”这一问,问得离奇。
“春花秋月”那可是美好的景色啊!人们是多么期盼年年花好,岁岁月圆的景色。
可是,此时词人偏偏言:“何时了?”繁花似锦、明月当空该什么时候了结呢?这一问充分地描绘出了词人对“春花秋月”的厌倦和对人生近乎绝望的心态。
这一问,问得干脆,这一问,非失落感达到极点而不能出。
这一问,亡国之事,悲愤之思蜂拥而至。
在这种痛苦感情的挤压下,很自然地想到往事。
“往事知多少”句就如顺水之舟漂流而下。
“往事”,在这里指他在江南南唐国做君主的时候。
那时候“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
别殿遥闻箫鼓奏”;那时候“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
李煜《虞美人》欧阳修《踏莎行》阅读答案对比赏析

李煜《虞美人》欧阳修《踏莎行》阅读答案对比赏析【阅读理解题目】:虞美人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踏莎行欧阳修候馆梅残,溪桥柳细。
草薰风暖摇征辔。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
楼高莫近危栏倚。
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1)欧阳修诗文向来注重炼字,请简要赏析欧阳修词开篇两句“候馆梅残,溪桥柳细”中“残”与“细”二字的妙处。
(2)“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化用了《虞美人》中的哪两句?试比较两者在修辞手法和表达效果上的异同。
【参考答案】:(1)“残”写出了梅花之凋零,“细”写出了柳条之初生。
“残”“细”既交代了作者出行的时间——初春时节,又浸透着浓郁的凄凉之意,饱含着离别的浓浓愁情,为整首词奠定了感情基调。
(2)化用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修辞手法相同:都运用了比喻的手法,都以水喻愁,将满腔愁绪比作江水,表现愁绪之多,绵延不断。
抒情效果不同:欧阳修词借迢迢春水表达了渐行渐深的离愁别绪,画面真切,意境优美;李煜词则借一江春水表达了国恨家仇的忧伤情感,境界开阔,意境深远。
[赏析]《虞美人》全词以问起,以答结;由问天、问人而到自问,通过凄楚中不无激越的音调和曲折回旋、流走自如的艺术结构,使作者沛然莫御的愁思贯串始终。
“春花秋月”是多么美好,作者却殷切企盼它早日“了”却;小楼“东风”带来春天的信息,却反而引起作者“不堪回首”的嗟叹,因为它们都勾起了作者物是人非的感触,衬出他的囚居异邦之愁。
下片前两句,一“在”一“改”道尽了几多物是人非的酸楚与哀伤。
结句“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以水喻愁的名句,含蓄地展示出愁思的长流不断,无穷无尽。
《踏莎行》这首词上片写行者的离愁,下片写行者的遥想即思妇的别恨,从游子和思妇两个不同的角度深化了离别的主题。
全词以优美的想象、贴切的比喻、新颖的构思,含蓄蕴藉地描写出一种“迢迢不断如春水”的情思,一种情深意远的境界。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全文翻译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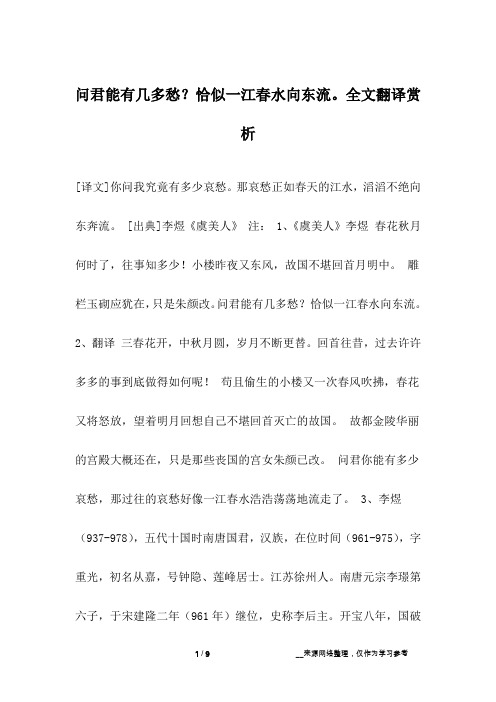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全文翻译赏析[译文]你问我究竟有多少哀愁。
那哀愁正如春天的江水,滔滔不绝向东奔流。
[出典]李煜《虞美人》注: 1、《虞美人》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2、翻译三春花开,中秋月圆,岁月不断更替。
回首往昔,过去许许多多的事到底做得如何呢!苟且偷生的小楼又一次春风吹拂,春花又将怒放,望着明月回想自己不堪回首灭亡的故国。
故都金陵华丽的宫殿大概还在,只是那些丧国的宫女朱颜已改。
问君你能有多少哀愁,那过往的哀愁好像一江春水浩浩荡荡地流走了。
3、李煜(937-978),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汉族,在位时间(961-975),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
江苏徐州人。
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于宋建隆二年(961年)继位,史称李后主。
开宝八年,国破降宋,俘至汴京,被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
后为宋太宗毒死。
李煜虽不通政治,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
李煜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
内容主要可分作两类:第一类为降宋之前所写的,主要为反映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题材较窄;第二类为降宋后,李煜因亡国的深痛,对往事的追忆,富以自身感情而作,此时期的作品成就远远超过前期,可谓“神品”.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皆成于此时。
此时期的词作大都哀婉凄绝,主要抒写了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对“往事”的无限留恋。
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千古词帝”.对后世影响亦甚大。
他继承了晚唐以来花间派词人的传统,但又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意境,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
李煜文、词及书、画创作均丰。
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古人emo的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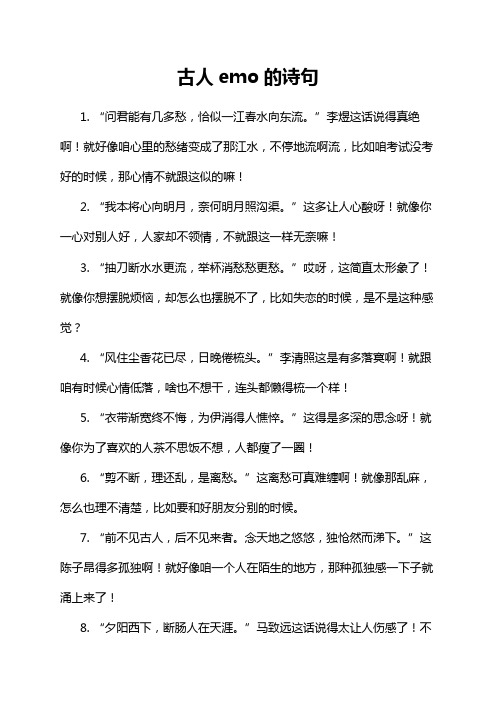
古人emo的诗句1.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这话说得真绝啊!就好像咱心里的愁绪变成了那江水,不停地流啊流,比如咱考试没考好的时候,那心情不就跟这似的嘛!2.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这多让人心酸呀!就像你一心对别人好,人家却不领情,不就跟这一样无奈嘛!3.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哎呀,这简直太形象了!就像你想摆脱烦恼,却怎么也摆脱不了,比如失恋的时候,是不是这种感觉?4.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李清照这是有多落寞啊!就跟咱有时候心情低落,啥也不想干,连头都懒得梳一个样!5.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得是多深的思念呀!就像你为了喜欢的人茶不思饭不想,人都瘦了一圈!6.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这离愁可真难缠啊!就像那乱麻,怎么也理不清楚,比如要和好朋友分别的时候。
7.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陈子昂得多孤独啊!就好像咱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那种孤独感一下子就涌上来了!8.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这话说得太让人伤感了!不就像在外漂泊的人,看着夕阳,心里那个难受劲儿嘛!9.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李清照这一连串的词,把那种孤独凄凉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像咱有时候一个人在家,感觉冷冷清清的。
1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张继这诗里满满的都是愁绪啊!就好像咱晚上睡不着,心里有事的时候,那感觉不就来了嘛!我觉得这些古人 emo 的诗句真的很能引起我们的共鸣,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当时的心情,也让我们对自己的情绪有了更深的理解。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者:徐春霞来源:《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10期摘要:在中国文艺传统里,一致认为苦痛比快乐更容易产生诗歌,往往好的诗歌产生于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发泄和表现,这种思想在古代是老生常谈的,也是当代中国文评里的重要概念。
“愁怨说”包含了钱先生的重要思想,就是写文章应该抒发真实情感,勿弄虚作假,无病呻吟。
关键词:怨愁说赋愁诗悲剧论[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09)-10-0007-02大家熟知的李煜一句诗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水向东流。
”这里的“愁”用“一江春水向东流”来形容,把这种抽象的情绪得以物化、动化、具体化,水有多深,愁就多深,水是流动不止的,愁也是无法计量的。
《论语•阳货》里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里的“怨”表达了在忧患中的写作以达到“舒郁”和“解愠”的目的。
也可以说,一个人潦倒愁闷身处困境可借“诗可以怨”来著书作诗以舒愤、以获得愁闷的排遣和心灵的慰藉与补偿,能使他和艰辛冷落的生涯妥协相安。
钱先生提倡抒写生活本质的真实,使抽象转化成具体,适当的比喻能把难以表达的情感完全表达出来。
钱先生喻愁拟愁,举出了一些例子:《全三国文》卷一九曹植《释愁文》:“愁之为物,惟恍惟惚,不召自来,推之勿往”;《海录碎事》卷九《圣贤人事部》下载庾信《愁赋》:“功许愁城终不破,荡许愁城终不开!何物煮愁能得熟?何物烧愁能得然(燃)?闭户欲推愁,愁终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全宋词》七四三页徐俯《卜算子》:“柳外重重迭迭山,遮不断愁来路”;薛季宣《浪语集》卷一一《春愁诗效玉川子》:“逃形入冥室,关闭一已牢,周遮四壁间,罗幕密以绸,愁来无际畔,还能为我添幽忧。
”[1]钱钟书先生认为,这些赋愁诗的拟喻可谓是“侔色揣称”,描摹物色,恰到好处:“写忧愁无远勿至,无隙亦入,能以无有入无词。
运思之巧,不特胜‘忧来扣门’,抑且胜于《浮士德》中之‘忧愠’有空必钻,虽重门下钥,亦潜自匙孔入宫禁;或乌克兰童话之‘忧魅’,小于微尘,成群入人家,间隙夹缝,无不伏处;然视‘忧来骚足’,尚逊诙诡。
”[2]林东海《诗法举隅》受到钱钟书的启示,将喻愁诗中比拟的动态化形象细细加以区分,一一条列为:愁可以“量”:如庾信诗:“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愁可以“载”:如辛弃疾词:“明月扁舟去,和月载离愁”;(李清照《武陵春》:“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石孝友《玉楼春》:“春愁离恨重于山,不信马儿驮得动。
”)愁可以“抛”:如白居易诗:“惟留花香楼前看,故已抛愁与后人”;愁可以“割”,如刘子翚诗:“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割断愁”;愁可以“剪”:如李后主词:“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愁可以“引”:如钱珝诗:“引愁天末去,数点暮山清”;愁可以“洗”:如元刘秉忠诗:“一曲清歌一杯酒,为君洗尽古今愁”[3]。
这些愁,这些恨,这些怨,都是无形的,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没有点创造性思维,是难以形容的。
这些无生命的愁与有生命的人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人在哪里,愁也在哪里,睁不开,更是摆不脱。
用各种形象,赋予“愁”情以生命,使之生命化、动态化,因此我们可以借用亚里士多德评荷马的话来说明:“用有生命之物来作无生命之物的隐喻,所有这些地方都因为它们那种行动的效果而显得很出色。
”[4]愁情何事、何处、何时不生?但这不是一般愁情,唯独“暝色起愁”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黄昏的时候,如钱钟书所说:“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黄昏时分,触绪纷来,所谓‘最难消遣’。
”[5]许瑶光《雪门诗钞》卷一《再读四十二首》第十四首云:“鸡栖于桀下牛羊,饥渴萦怀对夕阳。
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将息是昏黄”,钱钟书称赞许瑶光于“暝色起愁”之情“大是解人”[6]。
司马相如《长门赋》:“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韩偓《夕阳》:“花前洒泪临寒食,醉里回头问夕阳:不管相思人老尽,朝朝容易下西墙”;赵德麟《清平乐》:“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云:“愁因薄暮起”;皇甫冉《归渡洛水》云:“暝色起春愁”。
钱先生认为这些可以解释为日暮增愁之故。
“暝色起愁”之成为人类的一种共同心理,盖白昼思绪旁逸,或有它托,惟薄暮万籁将寂,若鸟归黄昏,思绪纷来,愁端复起也。
钱先生以宋玉《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结合《高堂赋》“长吏隳官,贤士失志,愁思无已,太息垂泪,等高怀远,使人心瘁”道出了“伤高怀远”的意境。
围绕着“伤高怀远”这一意境,钱先生认为能“曲传心理”者要数李峤《楚望赋》,该《赋》云:“非历览无以寄杼轴之怀,非高远无以开沉郁之绪。
……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故夫望之为体也,使人惨悽伊郁,惆怅不平,兴发思虑,震荡心灵。
其始也,惘兮若有求而不致也,怅乎若有待而不致也。
……精回魂乱,神苶志否,忧愤总集,莫能自止。
”李《赋》被钱钟书看重,就因为它登临感伤的原因和心理活动的过程,于浪漫主义‘企慕’可谓揣称工切矣。
诸如此类,还有“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之思,也有“悔教夫婿觅封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之思,有“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之愁,也有“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愁。
种种愁思的原因钱先生都一一辩析:“客羁臣逐,士耽女怀,孤愤单情,伤高望远,厥理易明。
若家近‘在山下’,少‘不识愁味’,而登陟之际,‘无愁亦愁’,忧来无向,悲出无名,则何以哉?虽怀抱犹虚,魂梦无萦,然远志遥情已似乳壳中函,孚苞待解,应机枨触,微动几先,极目而望不可即,放眼而望未之见,仗镜起心,于是惘惘不甘,忽忽若失。
”[7]真是望之感人深矣,而人之激情至矣!日落黄昏也愁、等高临渊也愁,见月看花也伤心落泪,忧国忧民,真可谓“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人类既然有如此多的愁思苦情,不言诗何以展其志?不藉文何以抒其愤?钱先生得出一个结论:“诗可以怨”。
在《诗可以怨》那篇讲稿中,他论及了司马迁说“人皆意有所郁结”而“发愤所为作”,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记事,最后把《诗三百篇》都归于“怨”。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只说“舒愤”而著书作诗,目的是避免“姓名磨灭”、“文彩不表于后世”,着眼于作品在作者身后起的功用,能使他死而不朽。
钟嵘说:“使贫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强调了作品在作者时的功用,能使他和艰辛冷落的生涯相安;或者可以说,一个人潦倒贫困,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
随着后世文学体裁的孳生,这个对创作的动机和效果的解释也从诗歌而蔓延到小说和戏剧。
我们知道“蚌病成珠”的成语,说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那么作者的文笔也是愁思痛苦的流露。
珍珠是痛苦的产物,那么那些“发愤而为作”的诗词、小说、戏曲、音乐就如珍珠一样,痛苦形成。
《送孟东野序》是收入旧日古文选本里给学僮们读熟读烂的文章,韩愈一开头就宣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历举庄周、屈原、司马迁、相如等大作家作为“善鸣”的例子,然后隆重地请出主角:“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
”一般人认为“不平则鸣”和“发愤而为作”涵义相同;事实上,韩愈和司马迁讲的是两码事。
司马迁的“愤”就是“坎壈不平”或通常所谓“牢骚”;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快乐在内。
其实韩愈曾比前人更明白地规定了“诗可以怨”的观念,那是在他的《荆潭唱和诗序》里。
韩愈提出了“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的结论。
为什么有“难工”和“易好”的差别呢?盖诗言志,欢愉则其情散越,散越则思致不能深入;愁苦则其情沉着,沉着则舒籁发声,动于天会。
故曰:诗以穷而后工,夫亦其境然也(《国粹丛书》本《张苍水集》卷一《曹云霖诗序》)。
陈兆伦说得更简括:“‘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词易好。
’此语闻之熟矣,而莫识其所由然也。
盖乐主散,一发而无余;忧主留,辗转而不尽。
意味之浅深别矣”(《紫竹山房集》卷四《消寒八咏•序》)。
我们还可以举一些西方浪漫诗人的名句:“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8]。
有位诗人用散文写了诗论,阐明一切“真正的美”都必须染上“忧伤的色彩”,“忧郁是诗歌里最合理合法的情调”[9]。
近代一位诗人认为“牢骚”宜于散文,而“忧伤宜于诗”,“诗是关于忧伤的奢侈”[10]。
没有人愿意饱尝愁苦的滋味——假如他能够避免;没有人不愿意作出美好的诗篇——即使他缺乏才情;没有人不愿意取巧省事——何况他并不损害旁人。
既然“穷苦之言易好”,那末,要写好诗就要说“穷苦之言”。
不幸的是,“憔悴之士”才会说“穷苦之言”,而说出来必然经历过“销魂与断肠”。
可是事实上,往往一些诗人企图不通过代价而写出好诗来。
比如小伙子作诗“叹老”,大阔佬作诗“嗟穷”,好端端过着闲适日子的人作诗“伤春”、“悲秋”。
难怪李贽读了司马迁“发愤所为作”那句话而感慨说:“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而不作矣。
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也。
虽作何观乎!”(《焚书》卷三《序》)。
其实“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但是却牵涉到很多的问题。
如,古代评论诗歌,重视“穷苦之言”,古代欣赏音乐,也“以悲音为主”[11]。
人类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无论古今中外,处处都有“愁和怨”来作梗:触景兴怀,感时伤世,有愁添愁,有怨生怨,忧思无绪,愁出无名,怨也说不清理还乱。
所以很多诗文都喜欢编结“愁怨”,赋愁写愁,赋怨写怨,比比皆是,可以供写一部悲剧观的诗歌史、文学史了。
钱先生就提出了“愁怨说”来大做文章,由“愁”而“悲”,由“悲”而“愤”,离娄察毫,条分缕析,最后上升到“悲剧论”的理论高度。
注释:[1][2]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焦氏易林》,第562页。
[3]《诗法举隅》第54页,60-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6月版。
[4]《西方文论选》上卷第9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6月新1版。
[5][6]《管锥编》第一册《毛诗正义》,第101页。
[7]《管锥编》第三册《全上古三代文》,第877-878页。
[8]雪莱《致云雀》;凯尔纳《诗》;缪塞《五月之夜》。
[9]爱伦坡《诗的原理》和《写作的哲学》,《诗歌及杂文集》(牛津,1945)177又195页。
[10]弗罗斯特《罗宾逊诗集序》又《论奢侈》,普利齐特《近代诗人评传》(1980)129又137页引。
[11]《管锥编》第三册《全上古三代文》,第946-9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