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与章学诚
戴震义理之学的形成及确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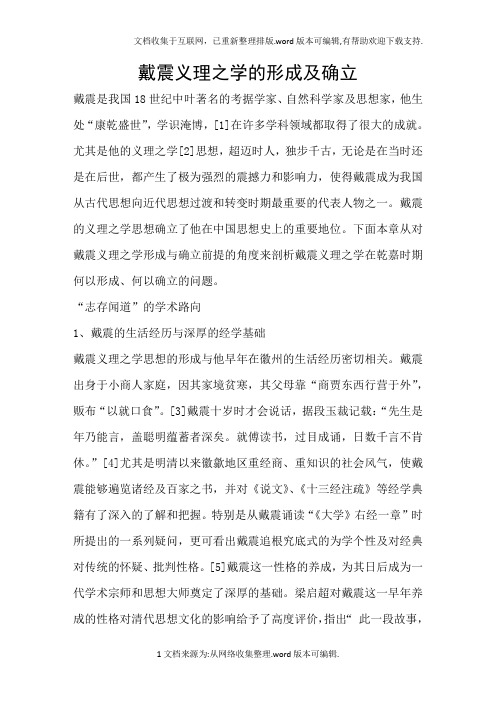
戴震义理之学的形成及确立戴震是我国18世纪中叶著名的考据学家、自然科学家及思想家,他生处“康乾盛世”,学识淹博,[1]在许多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尤其是他的义理之学[2]思想,超迈时人,独步千古,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使得戴震成为我国从古代思想向近代思想过渡和转变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确立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下面本章从对戴震义理之学形成与确立前提的角度来剖析戴震义理之学在乾嘉时期何以形成、何以确立的问题。
“志存闻道”的学术路向1、戴震的生活经历与深厚的经学基础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形成与他早年在徽州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戴震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因其家境贫寒,其父母靠“商贾东西行营于外”,贩布“以就口食”。
[3]戴震十岁时才会说话,据段玉裁记载:“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深矣。
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
”[4]尤其是明清以来徽歙地区重经商、重知识的社会风气,使戴震能够遍览诸经及百家之书,并对《说文》、《十三经注疏》等经学典籍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把握。
特别是从戴震诵读“《大学》右经一章”时所提出的一系列疑问,更可看出戴震追根究底式的为学个性及对经典对传统的怀疑、批判性格。
[5]戴震这一性格的养成,为其日后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和思想大师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梁启超对戴震这一早年养成的性格对清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
[6]18—20岁期间,戴震曾随其父经商于江西、福建等地,一边教书以维持生计,一边研读经书。
20岁时与同乡同学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汪梧凤、方矩、金榜等人,师从婺源经学名儒江永,学习礼经、推步、音声及文字之学。
在江永诸弟子中,由于“惟震能得其全”,故江永对戴震极为器重,引为忘年之交。
这一时期,戴震在经学、自然科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29岁,戴震补为休宁县学生,受汪梧凤之聘至不疏园,于是,不疏园成为“好学之士日夜诵习讲贯”之所,也成为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术活动中心。
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及其哲学的形上学追求——以戴震、章学诚、钱大昕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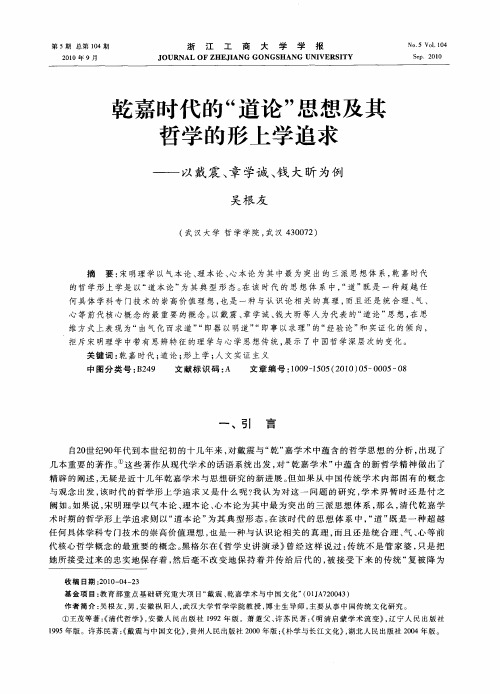
6
一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21 0 0年
种现 成 的材料 , 由精 神加 以转化 。 接 受 过来 的 遗产 就 这样 地 改 变 了 , 那 而且 那 经 过加 工 的 材料 因而
就更为 丰富 , 同时也就保 存下 来 了 。 ¨ 乾 嘉 时代 的思想 家们 通 过 以“ ” 核 心概 念 的哲 学 或 思想 体 ” 道 为 系, 将前代 分别 以理 、 以心 、 以气为核 心 概 念 的哲 学 体 系 , 成 了 自己体 系 内的一 个 部 分 。 中 以戴 震 变 其
何 具体 学科 专 门技 术 的 崇高 价值 理想 , 也是 一种 与认 识论 相 关 的真 理 , 而且 还 是 统合 理 、 、 气 心 等前代 核心 概念 的 最重要 的概 念。 以戴震 、 学诚 、 章 钱大 昕 等人 为 代表 的“ 论 ” 想, 思 道 思 在 维方 式上表 现 为“ 由气化 而求道 …‘ 即器 以 明道 …‘ 即事 以求理 ” 的“ 经验论 ” 实证 化 的倾 向 , 和 拒斥 宋 明理 学 中带有 思 辨特征 的理 学 与心 学思想传 统 , 示 了 中国哲 学深 层次 的变化 。 展 关 键词 : 嘉 时代 ; 论 ; 乾 道 形上 学 ; 文 实证 主义 人
中 图 分 类 号 :2 9 B 4 文献 标识码 : A 文 章 编 号 :0 9 10 ( 0 0 0 — 0 5 0 10 —5 5 2 1 )5 0 0 —世纪初 的十几年 来 , 0 0 对戴 震 与“ ” 学 术 中蕴 含 的哲学 思想 的分析 , 乾 嘉 出现 了
几本 重要 的著 作 。 些著 作从 现代 学术 的话 语系 统 出发 , “ 这 对 乾嘉 学 术 ” 中蕴 含 的 新哲 学精 神 做 出 了
驳章学诚“戴震不解史学”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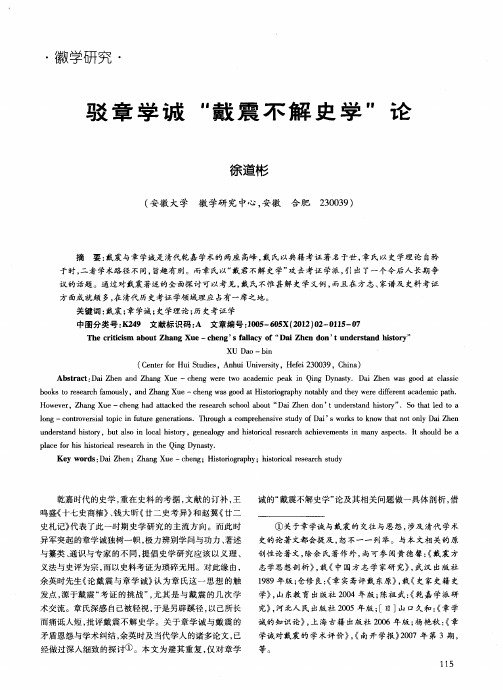
方 面成就颇 多, 清代 历史考证学领域理应 占有一席之地 。 在 关键词 : 戴震 ; 学诚 ; 章 史学理论 ; 史考证 学 历
中图分类号 : 2 9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0 5 6 5 2 1 )2 0 1 - 7 K4 A 10 - 0 X(0 2 0 - 15 0
史的论著文都会提及 , 不一一 列举 。与本文相 关的 原 恕
与纂类 、 通识与专家 的不 同 , 倡史学 研究应该 以义理 、 提
义法与史评 为宗 , 而以史料考证为琐碎无用 。对此缘 由,
创 性论 著文 , 除余 氏著作 外 , 尚可参 阅黄德 馨 : 戴 震 方 《 志学思想剖 析》, 《 国方志 学 家研 究》, 汉 出版社 载 中 武 18 9 9年版 ; 仓修 良: 章 实斋评戴 东原》 载《史家史籍 史 《 , 学》 山 东教 育 出版 社 20 , 0 4年版 ; 陈祖 武 : 乾嘉 学派研 《 究》 河北人 民 出版社 2 0 , 0 5年版 ; 日] 口久和 : 章 学 [ 山 《
paef ihs r a r er eQn y at. l r s ioi l e ac i t i D n s c oh t c s hnh g y
Ke r s Da h n;Z a g Xu y wo d : i e Z h n e—c e g h n ;Hi o ig a h s r r p y;h s rc e e c t d t o iti a r s a h su y o l r
・
徽 学研 究 ・
驳 章 学 诚 ¨ 震 不 解 史 学 ¨ 论 戴
论章学诚的学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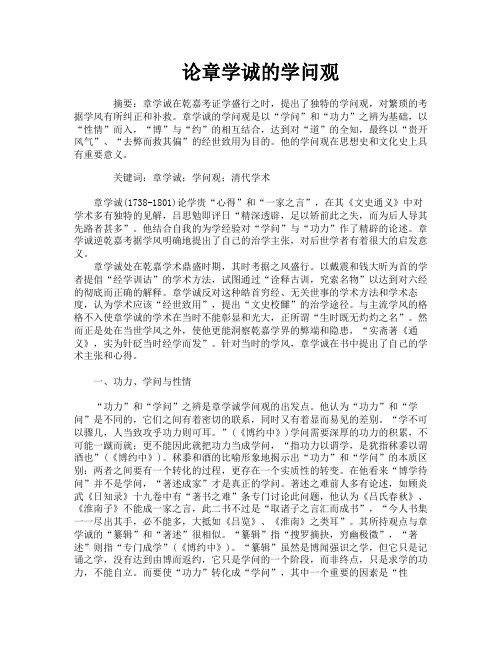
论章学诚的学问观摘要:章学诚在乾嘉考证学盛行之时,提出了独特的学问观,对繁琐的考据学风有所纠正和补救。
章学诚的学问观是以“学问”和“功力”之辨为基础,以“性情”而入,“博”与“约”的相互结合,达到对“道”的全知,最终以“贵开风气”、“去弊而救其偏”的经世致用为目的。
他的学问观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章学诚;学问观;清代学术章学诚(1738-1801)论学贵“心得”和“一家之言”,在其《文史通义》中对学术多有独特的见解,吕思勉即评日“精深透辟,足以矫前此之失,而为后人导其先路者甚多”。
他结合自我的为学经验对“学问”与“功力”作了精辟的论述。
章学诚逆乾嘉考据学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学主张,对后世学者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章学诚处在乾嘉学术鼎盛时期,其时考据之风盛行。
以戴震和钱大昕为首的学者提倡“经学训诂”的学术方法,试图通过“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以达到对六经的彻底而正确的解释。
章学诚反对这种皓首穷经、无关世事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认为学术应该“经世致用”,提出“文史校雠”的治学途径。
与主流学风的格格不入使章学诚的学术在当时不能彰显和光大,正所谓“生时既无灼灼之名”。
然而正是处在当世学风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学界的弊端和隐患,“实斋著《通义》,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
针对当时的学风,章学诚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心得。
一、功力、学问与性情“功力”和“学问”之辨是章学诚学问观的出发点。
他认为“功力”和“学问”是不同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
“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
”(《博约中》)学问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当成学问,“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博约中》)。
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和“学问”的本质区别: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更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转变。
在他看来“博学待问”并不是学问,“著述成家”才是真正的学问。
语言学概论02任务参考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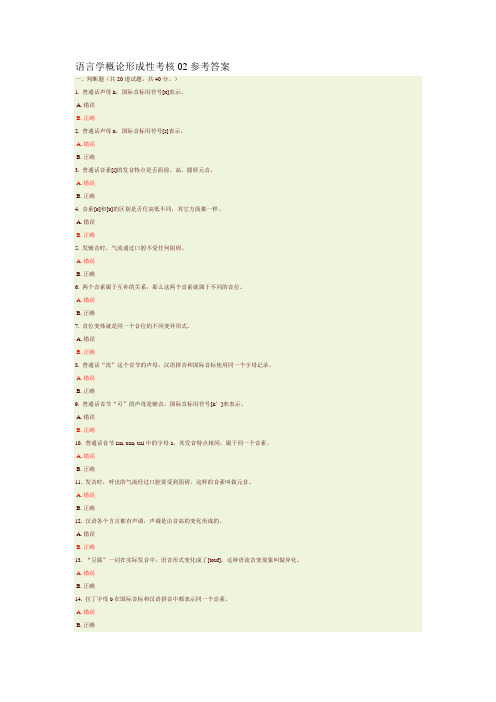
语言学概论形成性考核02参考答案一、判断题(共 20 道试题,共 40 分。
)1. 普通话声母h,国际音标用符号[x]表示。
A. 错误B. 正确2. 普通话声母x,国际音标用符号[s]表示。
A. 错误B. 正确3. 普通话音素[i]的发音特点是舌面前、高、圆唇元音。
A. 错误B. 正确4. 音素[o]和[u]的区别是舌位高低不同,其它方面都一样。
A. 错误B. 正确5. 发辅音时,气流通过口腔不受任何阻碍。
A. 错误B. 正确6. 两个音素属于互补的关系,那么这两个音素就属于不同的音位。
A. 错误B. 正确7. 音位变体就是同一个音位的不同变异形式。
A. 错误B. 正确8. 普通话“洗”这个音节的声母,汉语拼音和国际音标使用同一个字母记录。
A. 错误B. 正确9. 普通话音节“可”的声母是辅音,国际音标用符号[k’]来表示。
A. 错误B. 正确10. 普通话音节ian. uan. uai中的字母a,其发音特点相同,属于同一个音素。
A. 错误B. 正确11. 发音时,呼出的气流经过口腔要受到阻碍,这样的音素叫做元音。
A. 错误B. 正确12. 汉语各个方言都有声调,声调是由音高的变化形成的。
A. 错误B. 正确13. “豆腐”一词在实际发音中,语音形式变化成了[touf],这种语流音变现象叫做异化。
A. 错误B. 正确14. 拉丁字母b在国际音标和汉语拼音中都表示同一个音素。
A. 错误B. 正确15. 口腔中最为灵活的发音器官是舌。
A. 错误B. 正确16. 音素根据发音特点可以分为两类,普通话的声母就是由辅音充当的。
A. 错误B. 正确17. 普通话音位[p]和[t]的区别是发音方法不同。
A. 错误B. 正确18. 在发音器官中,唇、舌头、软腭、小舌、声带等是能够活动的,是主动发音器官。
A. 错误B. 正确19. 两个音素具有对立的关系,它们就属于同一个的音位。
A. 错误B. 正确20. 一个音素的发音特点是双唇、浊、鼻音,这个音素用音标[m]表示。
戴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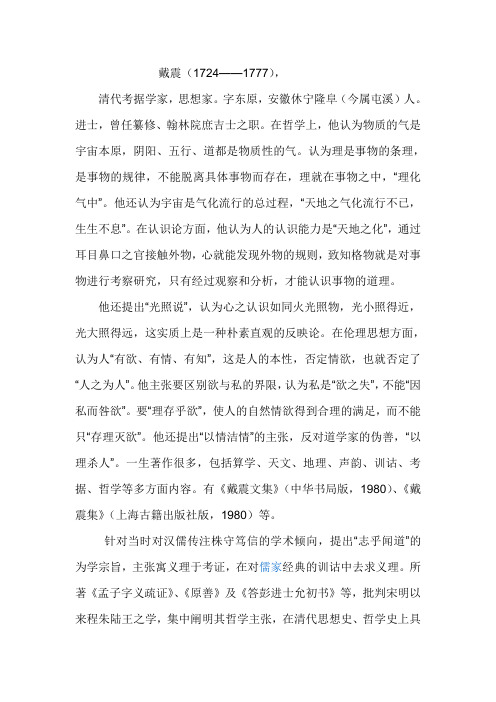
戴震(1724——1777),清代考据学家,思想家。
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属屯溪)人。
进士,曾任纂修、翰林院庶吉士之职。
在哲学上,他认为物质的气是宇宙本原,阴阳、五行、道都是物质性的气。
认为理是事物的条理,是事物的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理就在事物之中,“理化气中”。
他还认为宇宙是气化流行的总过程,“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
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天地之化”,通过耳目鼻口之官接触外物,心就能发现外物的规则,致知格物就是对事物进行考察研究,只有经过观察和分析,才能认识事物的道理。
他还提出“光照说”,认为心之认识如同火光照物,光小照得近,光大照得远,这实质上是一种朴素直观的反映论。
在伦理思想方面,认为人“有欲、有情、有知”,这是人的本性,否定情欲,也就否定了“人之为人”。
他主张要区别欲与私的界限,认为私是“欲之失”,不能“因私而咎欲”。
要“理存乎欲”,使人的自然情欲得到合理的满足,而不能只“存理灭欲”。
他还提出“以情洁情”的主张,反对道学家的伪善,“以理杀人”。
一生著作很多,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考据、哲学等多方面内容。
有《戴震文集》(中华书局版,1980)、《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0)等。
针对当时对汉儒传注株守笃信的学术倾向,提出“志乎闻道”的为学宗旨,主张寓义理于考证,在对儒家经典的训诂中去求义理。
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及《答彭进士允初书》等,批判宋明以来程朱陆王之学,集中阐明其哲学主张,在清代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书中提出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见解。
认为理就是条理,而宋明理学家的所谓理,不同于儒家经典中的理。
指出:“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
”抨击程朱“以理为气之主宰”是“诬圣乱经”。
痛斥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是“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是“以理杀人”。
与之针锋相对,他提出了“欲,其物;理,其则也”的命题,认为“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
章学诚的知识论—搜狗百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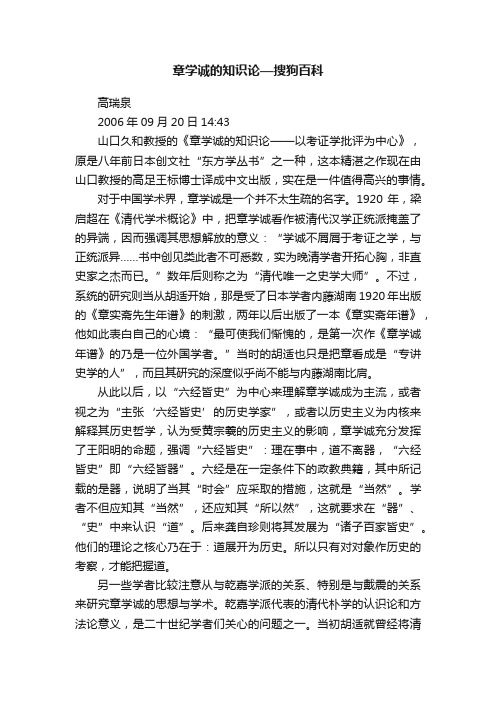
章学诚的知识论—搜狗百科高瑞泉2006年09月20日14:43山口久和教授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评为中心》,原是八年前日本创文社“东方学丛书”之一种,这本精湛之作现在由山口教授的高足王标博士译成中文出版,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对于中国学术界,章学诚是一个并不太生疏的名字。
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章学诚看作被清代汉学正统派掩盖了的异端,因而强调其思想解放的意义:“学诚不屑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书中创见类此者不可悉数,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
”数年后则称之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
不过,系统的研究则当从胡适开始,那是受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920年出版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刺激,两年以后出版了一本《章实斋年谱》,他如此表白自己的心境:“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学诚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学者。
”当时的胡适也只是把章看成是“专讲史学的人”,而且其研究的深度似乎尚不能与内藤湖南比肩。
从此以后,以“六经皆史”为中心来理解章学诚成为主流,或者视之为“主张‘六经皆史’的历史学家”,或者以历史主义为内核来解释其历史哲学,认为受黄宗羲的历史主义的影响,章学诚充分发挥了王阳明的命题,强调“六经皆史”:理在事中,道不离器,“六经皆史”即“六经皆器”。
六经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政教典籍,其中所记载的是器,说明了当其“时会”应采取的措施,这就是“当然”。
学者不但应知其“当然”,还应知其“所以然”,这就要求在“器”、“史”中来认识“道”。
后来龚自珍则将其发展为“诸子百家皆史”。
他们的理论之核心乃在于:道展开为历史。
所以只有对对象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把握道。
另一些学者比较注意从与乾嘉学派的关系、特别是与戴震的关系来研究章学诚的思想与学术。
乾嘉学派代表的清代朴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二十世纪学者们关心的问题之一。
当初胡适就曾经将清代汉学的精神称之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进一步将之比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
章学诚与戴震

读 史 札记 ・
章学诚 与戴震
陶 清
章学 诚 (78 l 1 , 实斋 , 江会 稽人 。 自幼 13一 8 )字 0 浙
酷嗜史学 , 纵览群书 , “ 于经训 未见领会 , 而史部之 书 , 乍 接于 目, 便似夙所 攻习者” 。章学诚 的历史理论研 究 ,
在历史观念和史学方法上贡献甚 巨, 如提出“ 经皆史 ” 六 的历史观念 、 经世致用” “ 的治学宗 旨、 即器明道 ” “ 的治
“ 史学义例 , 校雠心法 , 皆前人从未 言及”垒, 则 ( 不无辟芜 )
依章学诚 , 还原历史 实际当“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 付诸章学诚对戴震 的批评则是先褒后 贬 、 欲扬 还抑 : 戴 “ 君学 问, 见古 人大体 , 深 不愧 一代 巨儒 。而心术未 醇 , 颇 为近 日学者之 患 , 故余作 《 陆篇》 之。 ⑧ 可见 , 朱 正 ” 章学 诚批评戴震源起于对戴震“ 心术未醇 ” 的指责 , 忧患则 其
16 2
・
章学诚 与戴 震 ・
指戴震 的考据 学和部分哲学著 述 , 水经 注》 《 善》 如《 、原
等 ; 口授之 言” “ 指戴震与当时学者或从学者 的学问讨论
史 空间和长时段 的历 史 时间 中 , 尚总是 一种偏 颇 ; 时 而 于偏颇 中识得其中的恒久不变者 , 才是治 史者应 有的历 史 意识 和见 地 。因此 , 于立 志 于通 经 明道 的学 者 来 对 说 ,义理必须探索 , “ 名数必须考 订 , 文辞必 须娴 习, 皆学 也, 皆求道之资 , 非可 执一 端谓 尽道 也 。君子 学 以致 而
通方 ” “ ,史识 ” 阙失 , 因此 , 誉 者既非 其真 , “ 毁者 亦失 真
章学诚经学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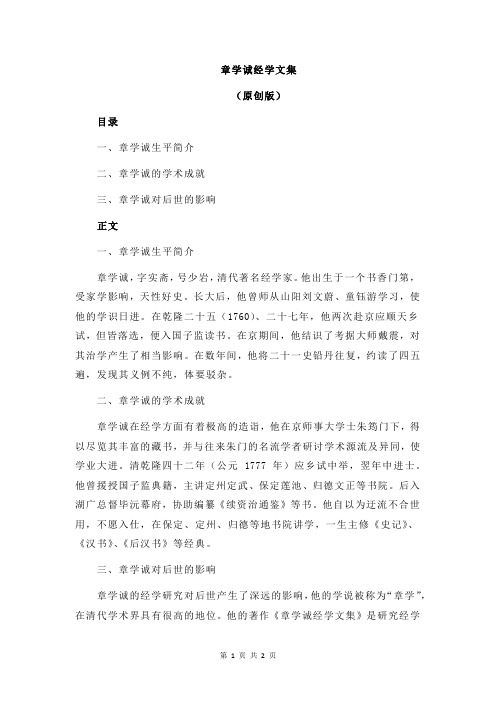
章学诚经学文集
(原创版)
目录
一、章学诚生平简介
二、章学诚的学术成就
三、章学诚对后世的影响
正文
一、章学诚生平简介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清代著名经学家。
他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受家学影响,天性好史。
长大后,他曾师从山阳刘文蔚、童钰游学习,使他的学识日进。
在乾隆二十五(1760)、二十七年,他两次赴京应顺天乡试,但皆落选,便入国子监读书。
在京期间,他结识了考据大师戴震,对其治学产生了相当影响。
在数年间,他将二十一史铅丹往复,约读了四五遍,发现其义例不纯,体要驳杂。
二、章学诚的学术成就
章学诚在经学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他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门下,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使学业大进。
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 1777 年)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
他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
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
他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在保定、定州、归德等地书院讲学,一生主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经典。
三、章学诚对后世的影响
章学诚的经学研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学说被称为“章学”,在清代学术界具有很高的地位。
他的著作《章学诚经学文集》是研究经学
的重要资料,对后世的经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时,他在书法、诗词等方面也有一定造诣,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由故训以明理义”——戴震哲学方法论思想的新阐释

戴震“由故训以明理义”的哲学方法论不仅引起清代中期哲学的一个转向,而且还建立了清代汉学家哲学的典范,从而推动了中国哲学史上概念范畴意识的发展。建立新的典范的人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具体研究方面,他的空前的成就对以后的学者起着示范作用;一是他在该学术领域之内留下许多工作让后人接着做,从而逐渐形成新的研究传统。考据学思潮虽然酝酿已久,但是,自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后,经学考证才开始发生革命性变革,从而奠定了清代学术的大局,从这个意义上讲,清代学术的范式是由顾炎武确立的,顾炎武的经学研究方法由戴震继承下来,即成为“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经学方法论,从经学史的角度看,戴震与顾炎武是一致的。但是,从哲学史的角度讲,戴震与顾炎武的思想还是有距离的。顾炎武反对脱离经学讲义理之学,反对脱离典章制度讲性与天道,以经学代理学的背后实际上是要以朴学代理学,取消义理之学的独立性。戴震虽然强调训诂、考据对义理之学的基础性和工具性价值,但从来没有想取消义理之学的独立地位,而且,突出义理之学的优先性是他一贯的学术宗旨,《孟子字义疏证》就是戴震在对经典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的义理之学。
《孟子字义疏证》从形式上看更象一部字典,实际上是讲概念范畴的,上卷专门解说理,中卷解说天道、性,下卷解说才、道、仁义礼智、诚、权。他在每个范畴标题下都标明了条数,以此说明这是采取了考据学的方法,这也是他在书名中用“疏证”的用意所在。在中国哲学史上,以范畴为核心来阐释哲学思想并非是戴震首创,南宋朱熹弟子陈淳的《北溪字义》已开先河,此书上卷阐释了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下卷阐释了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不过此书的目的在于阐释、推广朱熹的理学思想,其思维方式与宋儒无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则是以实证分析的方法来阐释其哲学思想,而非宋儒主观体证、形上体悟的方法。虽然孟子字义疏证所提到的范畴都是宋儒提到过的,但戴震以新的方法将其重新概念化,赋予新的内涵,重新概念化的过程正是科学革命(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标志,许多学者依照戴震的这一典范继续进行哲学研究,较有影响的有焦循的《论语通释》、阮元的《性命古训》、陈澧的《汉儒通义》、黄以周的《经义比训》,刘师培的《理学字义通释》、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他们都是以训诂考据为工具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大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意识的发展。吴派领袖惠栋曾作《易微言》,其方法、体例皆与《孟子字义疏证》同,但其影响远远不如后者,而且其所论范围也仅仅局限于易学,钱穆称“当时吴派学者实欲以此夺宋儒讲义理之传统,松崖初发其绪而未竟。”[12]可谓知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戴震确立了清代汉学家哲学研究的典范。
余英时:打天下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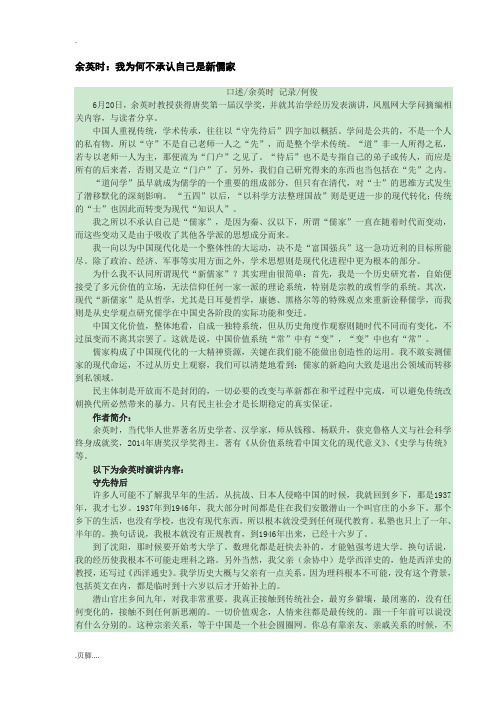
余英时:我为何不承认自己是新儒家口述/余英时记录/何俊6月20日,余英时教授获得唐奖第一届汉学奖,并就其治学经历发表演讲,凤凰网大学问摘编相关内容,与读者分享。
中国人重视传统,学术传承,往往以“守先待后”四字加以概括。
学问是公共的,不是一个人的私有物。
所以“守”不是自己老师一人之“先”,而是整个学术传统。
“道”非一人所得之私,若专以老师一人为主,那便流为“门户”之见了。
“待后”也不是专指自己的弟子或传人,而应是所有的后来者,否则又是立“门户”了。
另外,我们自己研究得来的东西也当包括在“先”之内。
“道问学”虽早就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只有在清代,对“士”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五四”以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则是更进一步的现代转化;传统的“士”也因此而转变为现代“知识人”。
我之所以不承认自己是“儒家”,是因为秦、汉以下,所谓“儒家”一直在随着时代而变动,而这些变动又是由于吸收了其他各学派的思想成分而来。
我一向以为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大运动,决不是“富国强兵”这一急功近利的目标所能尽。
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实用方面之外,学术思想则是现代化进程中更为根本的部分。
为什么我不认同所谓现代“新儒家”?其实理由很简单:首先,我是一个历史研究者,自始便接受了多元价值的立场,无法信仰任何一家一派的理论系统,特别是宗教的或哲学的系统。
其次,现代“新儒家”是从哲学,尤其是日耳曼哲学,康德、黑格尔等的特殊观点来重新诠释儒学,而我则是从史学观点研究儒学在中国史各阶段的实际功能和变迁。
中国文化价值,整体地看,自成一独特系统,但从历史角度作观察则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不过虽变而不离其宗罢了。
这就是说,中国价值系统“常”中有“变”,“变”中也有“常”。
儒家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大精神资源,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做出创造性的运用。
我不敢妄测儒家的现代命运,不过从历史上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的新趋向大致是退出公领域而转移到私领域。
戴震志传文、碑传文论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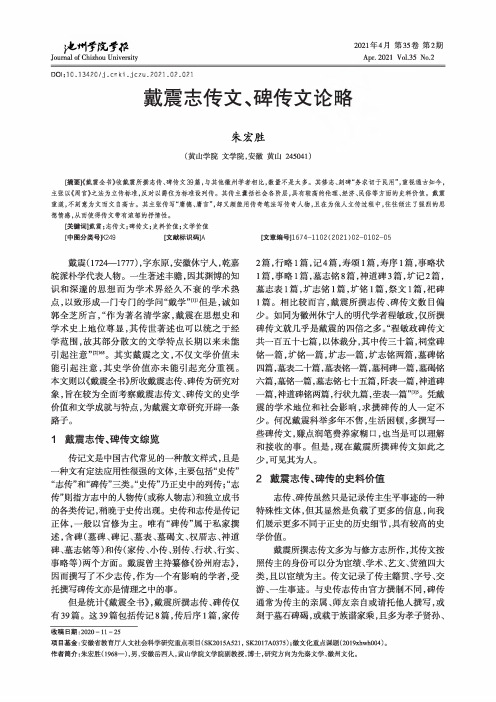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21)02-0102-05
戴震(172—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乾嘉 皖派朴学代表人物。_生著述丰赡,因其渊博的知 识和深邃的思想而为学术界经久不衰的学术热 点,以致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戴学”妙但是,诚如 郭全芝所言,“作为著名清学家,戴震在思想史和 学术史上地位尊显,其传世著述也可以统之于经 学范围,故其部分散文的文学特点长期以来未能 引起注意”叩‘。其实戴震之文,不仅文学价值未 能引起注意,其史学价值亦未能引起充分重视 。 本文则以《戴震全书》所收戴震志传、碑传为研究对 象,旨在较为全面考察戴震志传文、碑传文的史学 价值和文学成就与特点,为戴震文章研究开辟一条 路子。
主张以《周官》之法为立传标准,反对以爵位为标准设列传。其传主囊括社会各阶层,具有较高的伦理、经济、民俗等方面的史料价值。戴震
重道,不刻意为文而文肖高古。其主张传写"庸德、庸言”,却又颇能用传奇笔法写传奇人物,且在为他人立传过程中,往往倾注了强烈的思
想情感,从而使得传文带有郁的抒情性。
[关键词]戴震;志传文;碑传文;史料价值;文学价值
2戴震志传、碑传的史料价值
志传、碑传虽然只是记录传主生平事迹的一种 特殊性文体,但其显然是负载了更多的信息,向我 们展示更多不同于正史的历史细节,具有较高的史 学价值。
戴震所撰志传文多为与修方志所作,其传文按 照传主的身份可以分为宦绩、学术、艺文、货殖四大 类,且以宦绩为主。传文记录了传主籍贯、字号、交 游、一生事迹。与史传志传由官方撰制不同,碑传 通常为传主的亲属、师友亲自或请托他人撰写,或 刻于墓石碑碣,或载于族谱家乘,且多为孝子贤孙、
104
池州学院学报
【觅经记】戴震:皖派终成,以经翼理(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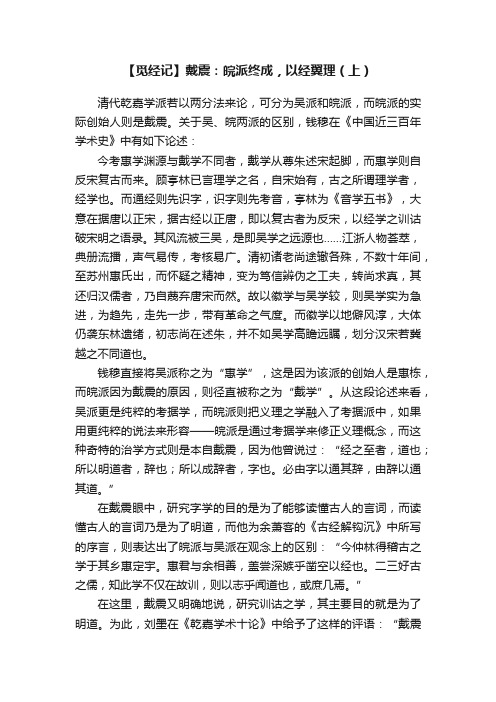
【觅经记】戴震:皖派终成,以经翼理(上)清代乾嘉学派若以两分法来论,可分为吴派和皖派,而皖派的实际创始人则是戴震。
关于吴、皖两派的区别,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如下论述:今考惠学渊源与戴学不同者,戴学从尊朱述宋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
顾亭林已言理学之名,自宋始有,古之所谓理学者,经学也。
而通经则先识字,识字则先考音,亭林为《音学五书》,大意在据唐以正宋,据古经以正唐,即以复古者为反宋,以经学之训诂破宋明之语录。
其风流被三吴,是即吴学之远源也……江浙人物荟萃,典册流播,声气易传,考核易广。
清初诸老尚途辙各殊,不数十年间,至苏州惠氏出,而怀疑之精神,变为笃信辨伪之工夫,转尚求真,其还归汉儒者,乃自蔑弃唐宋而然。
故以徽学与吴学较,则吴学实为急进,为趋先,走先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
而徽学以地僻风淳,大体仍袭东林遗绪,初志尚在述朱,并不如吴学高瞻远瞩,划分汉宋若冀越之不同道也。
钱穆直接将吴派称之为“惠学”,这是因为该派的创始人是惠栋,而皖派因为戴震的原因,则径直被称之为“戴学”。
从这段论述来看,吴派更是纯粹的考据学,而皖派则把义理之学融入了考据派中,如果用更纯粹的说法来形容——皖派是通过考据学来修正义理概念,而这种奇特的治学方式则是本自戴震,因为他曾说过:“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
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
”在戴震眼中,研究字学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读懂古人的言词,而读懂古人的言词乃是为了明道,而他为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中所写的序言,则表达出了皖派与吴派在观念上的区别:“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定宇。
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经也。
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
”在这里,戴震又明确地说,研究训诂之学,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明道。
为此,刘墨在《乾嘉学术十论》中给予了这样的评语:“戴震比吴派高出一层的,就在于能够超越‘故训’之上‘闻道’。
”戴震何以有着这样的思想?按他自己的解释,他在年轻之时就已做如是想。
从来前贤畏后生——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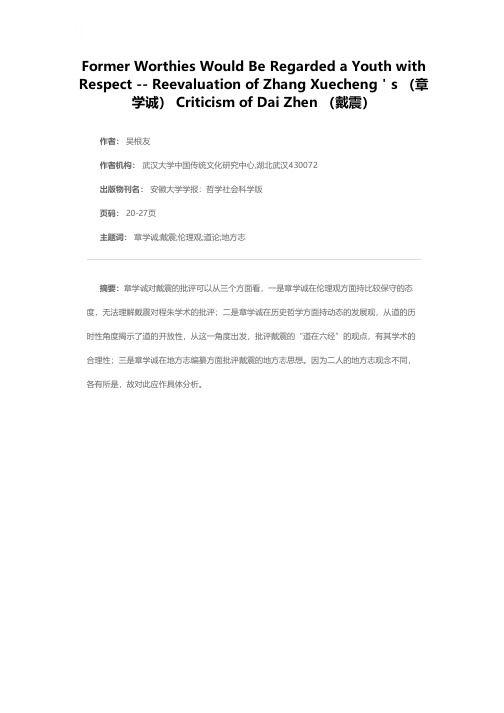
Former Worthies Would Be Regarded a Youth with Respect -- Reevaluation of Zhang Xuecheng's (章学诚) Criticism of Dai Zhen (戴震)作者: 吴根友
作者机构: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出版物刊名: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20-27页
主题词: 章学诚;戴震;伦理观;道论;地方志
摘要: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章学诚在伦理观方面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无法理解戴震对程朱学术的批评;二是章学诚在历史哲学方面持动态的发展观,从道的历
时性角度揭示了道的开放性,从这一角度出发,批评戴震的“道在六经”的观点,有其学术的
合理性;三是章学诚在地方志编纂方面批评戴震的地方志思想。
因为二人的地方志观念不同,
各有所是,故对此应作具体分析。
隐喻型的章学诚和转喻型的戴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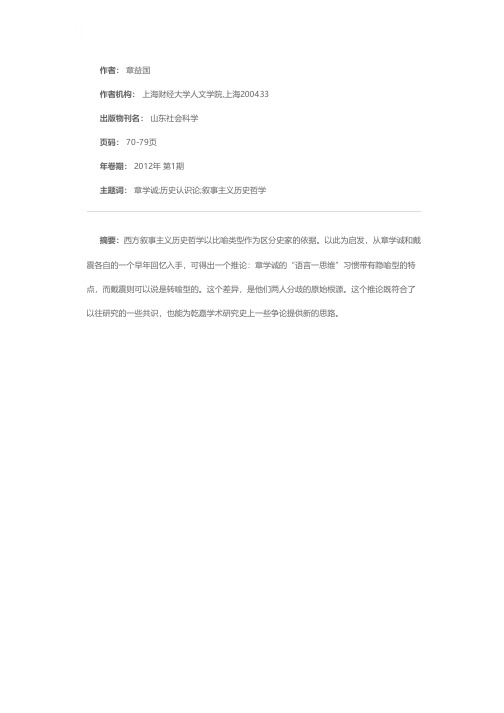
作者: 章益国
作者机构: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433
出版物刊名: 山东社会科学
页码: 70-79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1期
主题词: 章学诚;历史认识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
摘要:西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以比喻类型作为区分史家的依据。
以此为启发,从章学诚和戴震各自的一个早年回忆入手,可得出一个推论:章学诚的“语言一思维”习惯带有隐喻型的特点,而戴震则可以说是转喻型的。
这个差异,是他们两人分歧的原始根源。
这个推论既符合了以往研究的一些共识,也能为乾嘉学术研究史上一些争论提供新的思路。
从来前贤畏后生_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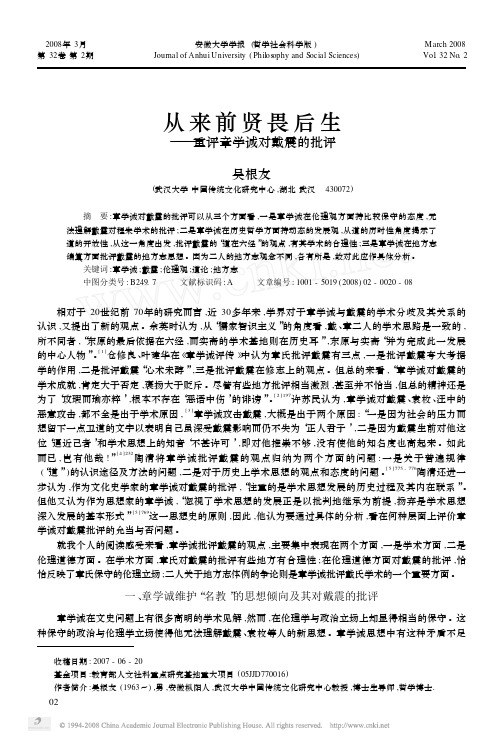
2008年3月第32卷第2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 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March2008Vol.32No.2从来前贤畏后生———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吴根友(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2)摘 要: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章学诚在伦理观方面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无法理解戴震对程朱学术的批评;二是章学诚在历史哲学方面持动态的发展观,从道的历时性角度揭示了道的开放性,从这一角度出发,批评戴震的“道在六经”的观点,有其学术的合理性;三是章学诚在地方志编纂方面批评戴震的地方志思想。
因为二人的地方志观念不同,各有所是,故对此应作具体分析。
关键词:章学诚;戴震;伦理观;道论;地方志中图分类号:B24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8)02-0020-08相对于20世纪前70年的研究而言,近30多年来,学界对于章学诚与戴震的学术分歧及其关系的认识,又提出了新的观点。
余英时认为,从“儒家智识主义”的角度看,戴、章二人的学术思路是一致的,所不同者,“东原的最后依据在六经,而实斋的学术基地则在历史耳”,东原与实斋“并为完成此一发展的中心人物”。
[1]仓修良、叶建华在《章学诚评传》中认为章氏批评戴震有三点,一是批评戴震夸大考据学的作用,二是批评戴震“心术未醇”,三是批评戴震在修志上的观点。
但总的来看,“章学诚对戴震的学术成就,肯定大于否定,褒扬大于贬斥。
尽管有些地方批评相当激烈,甚至并不恰当,但总的精神还是为了‘攻瑕而瑜亦粹’,根本不存在‘恶语中伤’的诽谤”。
[2]197许苏民认为,章学诚对戴震、袁枚、汪中的恶意攻击,都不全是出于学术原因,[3]章学诚攻击戴震,大概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社会的压力而想留下一点卫道的文字以表明自己虽深受戴震影响而仍不失为‘正人君子’,二是因为戴震生前对他这位‘逼近己者’和学术思想上的知音‘不甚许可’,即对他推崇不够,没有使他的知名度也高起来。
章学诚笔下的戴震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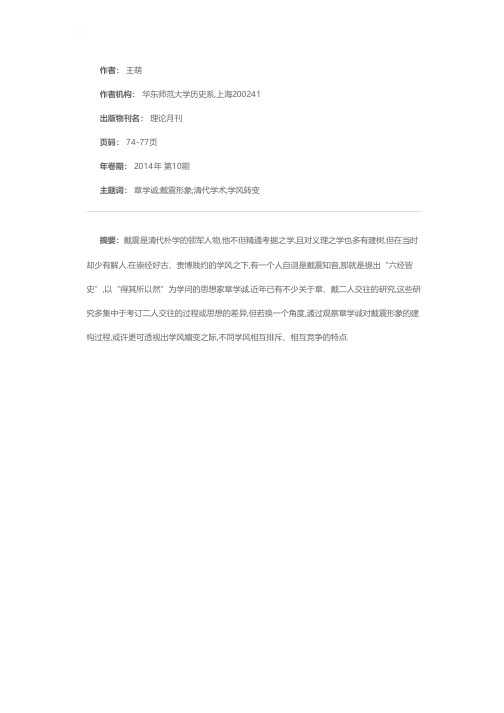
作者: 王萌
作者机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241
出版物刊名: 理论月刊
页码: 74-77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10期
主题词: 章学诚;戴震形象;清代学术;学风转变
摘要:戴震是清代朴学的领军人物,他不但精通考据之学,且对义理之学也多有建树,但在当时却少有解人.在崇经好古、贵博贱约的学风之下,有一个人自诩是戴震知音,那就是提出“六经皆史”,以“得其所以然”为学问的思想家章学诚.近年已有不少关于章、戴二人交往的研究,这些研究多集中于考订二人交往的过程或思想的差异,但若换一个角度,通过观察章学诚对戴震形象的建构过程,或许更可透视出学风嬗变之际,不同学风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的特点.。
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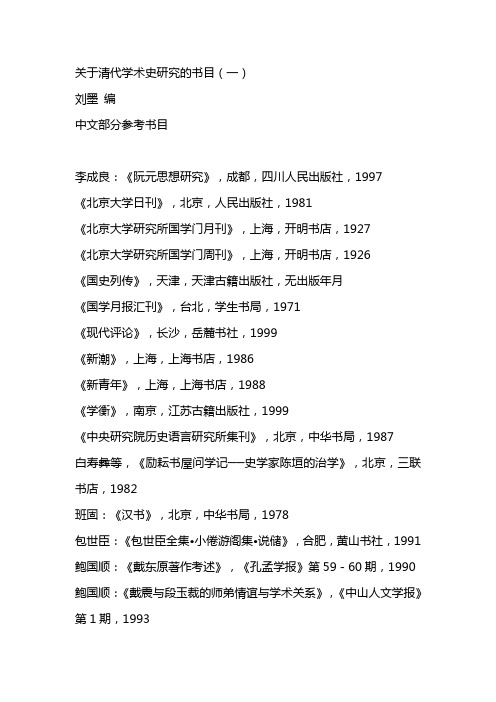
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书目(一)刘墨编中文部分参考书目李成良:《阮元思想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北京大学日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海,开明书店,1927《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上海,开明书店,1926《国史列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无出版年月《国学月报汇刊》,台北,学生书局,1971《现代评论》,长沙,岳麓书社,1999《新潮》,上海,上海书店,1986《新青年》,上海,上海书店,1988《学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87白寿彝等,《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北京,三联书店,198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8包世臣:《包世臣全集•小倦游阁集•说储》,合肥,黄山书社,1991 鲍国顺:《戴东原著作考述》,《孔孟学报》第59-60期,1990鲍国顺:《戴震与段玉裁的师弟情谊与学术关系》,《中山人文学报》第1期,1993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组编:《清史论文索引上编》(1644~1840),北京师范大学油印本,1973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综合性图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蔡可园:《清代七百名人传》,上海世界书局,1937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94岑溢成:《诗补传与戴震解经方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岑溢成:《训诂学与清儒训诂方法》,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博士论文岑仲勉:《考据举例》,《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1944柴德赓:《王西庄与钱竹汀》,《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79 陈旦:《清儒治文字学之派别及其方法述略》,《国学丛刊》第1卷第2期,1923陈登原,《中国文化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陈第:《毛诗古音考》,台北,艺文印书馆,1967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想史》,齐鲁书社,1989陈恒嵩:《五经大全纂修研究》,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北京,中华书局,1997 陈澧:《东塾丛书》,台北,华文书局,1970陈澧:《东塾读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陈澧:《东塾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陈美延等编:《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陈平原、王枫主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陈平原等编,《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陈其泰:《清代公羊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陈寿熊:《读易汉学私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陈新雄:《古音学发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87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初编》、《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陈智贤:《清儒以说文释诗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7陈柱:《清儒学术讨论集》(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陈祖武:《中国学案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程克雅:《乾嘉学者以例释礼解经方式比较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崔述:《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香港,存萃学社,1978 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第二编,香港,崇文书店,1971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第三编,同上,1972 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第四编,同上,1973 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第五编甲集、乙集,同上,1974存粹社编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香港:存粹社 1978年戴逸:《汉学探析》,《清史研究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北京,中国人大学出版社,1992戴震:《戴震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4邓广铭主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三联书店,1955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北京,中华书局,199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书原因之研究》,台北,华正书局,1983 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杜联喆、房兆楹:《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北京,中华书局,1959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北京,中华书局,1988杜维运:《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台北,学生书局,1989杜维运:《清盛世的学术工作与考据学的发展》,《大陆杂志》1964年第28卷第9期杜维运:《学术与世变》,台北,环宇出版社,1971杜正胜、王泛森主编:《新学术之路》,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 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中国文化》,1995年第2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樊克政:《中国书院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方苞:《方望溪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方东树:《汉学商兑》,北京,三联书店,1998方诗铭、周殿杰:《钱大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方以智:《方以智全书•通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方中履:《古今释疑》,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费海玑:《钱竹汀传记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傅斯年:《傅斯年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高在旭:《戴东原哲学析评》,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0高正:《清代考据家义理之学》,《文献》1987年第4期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2000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耿云志编:《胡适研究丛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耿云志等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北京,三联书店,1993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1994耿志宏:《惠栋之经学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古国顺:《清代尚书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古国顺:《清代尚书著述考》,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5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顾颉刚:《清代汉学家治学精神与方法》,《广播周报》第106期,1936顾颉刚编,《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顾颉刚主编:《古籍考辨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55顾燮光:《梦碧簃石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学林出版社,2001管敏义主编:《浙东学术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884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杭世骏:《道古堂外集》,补史亭刊本,1788何炳松:《何炳松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何冠彪:《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1何冠彪:《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 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何佑森:《近三百年朱子学的反对派》,《幼狮学志》第16卷第4期,1981何佑森:《清代汉宋之争平议》,《文史哲学报》第27期,1978 何泽恒:《焦循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贺长龄、魏源编:《清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贺岳僧:《清代汉宋学之争》,《时代精神》第8卷第3期,1943 洪亮吉:《洪亮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侯外庐等人:《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97侯外庐等人:《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980 胡楚生:《清代学术史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胡楚生:《清代学术史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胡槐植:《戴震师友记》,《徽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3、4期,1991年第1-4期,1992年第1期胡朴安:《戴先生所著书考》,《安徽丛书》第六期内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0 胡适:《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胡适:《章实斋年谱•齐白石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黄道庸:《清代学术思想之史的发展过程》,《学习生活》第3卷第1期,1942黄建斌:《清代学术发展史》,台北,幼狮书店,1974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期(1997)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黄侃:《量守文钞》,收入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1,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价》,《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1年第11期黄启华:《乾嘉考据学兴起后些线索──兼论顾炎武钱大昕学术思想的发展关系》,《故宫学术月刊》,第8卷第3期黄忠慎:《惠周惕诗说析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994黄宗羲:《南雷文定》,四部丛刊本惠栋:《春秋左传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惠栋:《后汉书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惠栋:《惠氏读说文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惠栋:《九经古义》,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惠栋:《九曜斋笔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惠栋:《松崖笔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惠栋:《松崖文钞》,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惠栋:《易汉学》,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惠栋:《易例》,台北,艺文印书馆,1967惠栋:《周易述》,台北,成文书局,1976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江藩:《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江弘远:《惠栋易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 江声:《六书说》,北京,中华书局,1985江声:《尚书逸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江永:《算学》,四库全书本姜广辉:《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蒋天枢:《陈寅恪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蒋天枢:《全谢山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32蒋元卿:《校雠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蒋致中:《牛空山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焦循:《雕菰集》,丛书集成初编本焦循:《论语补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焦循:《论语通释》,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1金荣奇:《庄存与春秋公羊学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瞿兑之:《汪辉祖传述》,民国丛书第三编,上海书店柯维卿:《戴震孟子学研究》,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孔立:《清代文字狱》,中华书局,1980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来新夏:《清代考据学述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编》,台北,文光图书公司,1965李调元:《淡墨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台北,明文书局,1985李纪祥:《明末清初儒学之发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上海,上海书店,1996李开:《戴震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李铭皖、谭钧培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李瑞良:《中国目录学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李威熊:《中国经学发展史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李新霖:《清代经今文学述》,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77李洵:《清代全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李耀仙:《廖平学术论著选集》,成都,巴蜀书社,1989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长沙,岳麓书社,199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饮冰室文集》卷四十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上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廖千慧:《焦循论语学研究》,台湾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廖秀珠:《钱大昕及其十驾斋养新录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林聪舜:《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变迁与发展》,台北,学生书局,1990 林丽容:《民初读经问题初探(1912-1937)》,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林美珠:《方东树汉学商兑研究》,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林明波:《清代许学考》,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60 林明波:《清代雅学考》,《庆祝高邮高仲华先生六秩诞辰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68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6林庆彰主编:《明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同上,1996林庆彰主编:《乾嘉学者研究论著目录》,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林庆彰主编:《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林庆彰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 林尹:《中国学术思想大纲》,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凌廷勘:《校礼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凌廷堪:《礼经释例》,北京,中华书局,1985刘蕙孙:《清代的考据之学》,《中国文化史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刘梦溪:《传统的误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刘梦溪主编:《现代中国学术经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香港,崇文书店,1971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1期,1930刘盼遂:《王石渠先生年谱附伯伸先生年谱》,《女师大学术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刘起釬:《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刘巍:《钱穆与胡适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整理的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刘寅生、房鑫亮等编:《何炳松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刘寅生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柳曾符等选编:《柳诒征史学论文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卢文弨:《群书拾补》,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台北,广文书局,1978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6陆谦祉:《厉樊榭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逯耀东:《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吕思勉:《经子解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吕思勉:《论学集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罗炳绵:《清代学术论集》,台湾,食货出版社,1978罗冈、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罗焌:《诸子学述》,长沙,岳麓书社,1995罗振玉:《清朝学问源流概略》,《东亚》第3卷8—9期,1930 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2000:5)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1999:11)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马叙伦:《清人所著说文之部目初编草稿》,《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6马一浮:《马一浮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毛子水:《适之先生对学术界的影响》,《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5)梅文鼎:《历算全书》,四库全书本孟森:《明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牟润孙:《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牟钟鉴:〈《明代思想史》与明代思想研究〉,《中国文化》,第10期(1994:8),页173-8。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论戴震与章学诚《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余先生1976年初版的旧作。
该书在1996年曾由余先生亲手作了增补,虽则问世至今已经三十余年,然仍不失为了解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
本书的成书目的的照余先生自云“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尚未见有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检讨” “我同时也想借此展示儒家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 。
概而言之,即通过对戴东原和章实斋学术思想的分析从而理解儒家何以何以从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证。
余先生提到,在他之前的一些学人,认为清学“既不能’经虚涉旷’则已无积极的思想内容科研,甚至不免是中国哲学精神过程中的一次逆转” ,因而他们的新儒学都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 。
但在余先生看来,“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中。
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
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 。
这大概便是余先生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对儒学采取一直“广阔而动态的看法”的前提下,余先生开始了本书的论述。
全书内篇共分八章,除去前两章的引言和末两章的后论及补论外,以戴、章二人分别各为两章的论述中心。
儒家本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前代学人也多有提及。
余先生在此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儒家智识主义”。
书中“道问学”约等于智识主义,“尊德性”则约等于“反智识主义”。
明清之际,儒学主流由理学转入考据,即从“尊德性”层次转入“道问学”层次,这可称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
这种现象的产生,余先生主要从“内在理路”(inner logic)进行分析。
关于“内在理路”,笔者下文还将详论。
余先生从程、朱与陆、王相争,王阳明最后不得不重订《大学》古本,欲“复旧本”以“复见圣人之心”悟到“所争者仍在义理之是非,而所采用之方法正是考证辨伪。
这里清楚地透露了考证学兴起的思想史的背景” 。
书中随后引用的一段材料十分清晰的凸显出此处转变的脉络,孤引之如下: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
如六书、九数、典章、制度之学是也。
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
如义理之学是也。
由此可知清代考证的兴起乃有儒学自身内部的原因。
盖因“尊德性”发展到了极端不免流入“反智识主义”,各家各持己说不相上下,于是不得不征诸古本以定是非,走上“道问学”的道路。
二者是儒学的两个方面,有其儒学内部的联系,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并不均衡。
书中章学诚是作为与戴震相抗衡的角色出现。
余先生首先指出,这乃是出于后人的见解。
在戴、章身处的时代里,时人均认为章学诚远远不能与戴震相提并论。
然在章学诚自己的内心深处,“确引东原为同道,而且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和东原在学术上分庭抗礼” ,并就此一点展开了详细论述。
实斋之所以自认自己能与东原并立乃在于他提出了与时人(包括戴东原)迥异的两个观点:一是经、史不应有高下之分,因为二者殊途同归,皆是入道的途径;再则是学问从入之途不限于考据一端,从“观其大意”入手,也能通于道。
进而言之,章氏在清初“经学即理学”纲领的笼罩下开创性地提出了“六经皆史”,这一理论经过章氏多年的建设已成论证充分的完善系统。
因而有了“六经皆史”的有力支撑,章氏遂有信心以“文史校雠”与其时“经学训诂”的领袖——戴东原相抗。
然“实斋岁自视甚坚……但并世学人,包括他的桓谭——邵晋涵在内,却未必能同意实斋这种自我评价” 。
所以他作《朱陆》篇,指出“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此即指东原;而后撰《浙东学术》,“显然是要为自己在宋、明以来的儒学传统中找一个适当的位置。
这和《朱陆》篇认定东原之学系承朱子数传而后起,意思全相一致” ,由此一来,“南宋有朱、陆,清初有顾、黄,这才能衬托出乾隆时的戴、章并峙”,即从学术史上为自己的学说找寻脉络,以加强其在时人眼中的真实性。
这即是本书关于章学诚的基本论述。
戴东原的心态相对实斋而言稍显复杂。
在论及章氏作《朱陆》、《浙东学术》二文所采取的以“性情”划分学者的理论时,余先生引入了“狐狸”与“刺猬”说。
此说源自古希腊残句“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英人柏林借用这句话来分别一切思想家与作家,柏林的说法简而言之,即刺猬型学者的生活、行为、观念都贯穿在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之中,狐狸型的人物则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其行为、观念大抵是离心而非向心,对各种经验和外在形象采取一种严肃的就事论事的态度。
章学诚自然属于刺猬型的人,而“东原则以’刺猬’而深具’狐狸’的本领,而且一开始便被’狐狸’误认作同类,成为群狐之首……不过,通东原一生论学的见解观之,则东原虽偶有与’狐狸’敷衍妥协之处,而最后并没有丧失他自己的‘刺猬’立场” 。
对处于18世纪的戴东原而言,考证是一种职业,因而“我们在讨论东原与考证学的关系时,不能不特别把他对纯学术的兴趣和职业上的兴趣加以分别” 。
一个人的形象一旦固定,则此“形象”常常会反过来束缚住他。
东原性本偏爱义理,在时人眼中却是以考证闻名,所以他难以(几乎不能)与考证派公然决裂,因此东原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比实斋要大。
他作《绪言》(后更名为《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诸篇论性,篇成喜不自禁。
然而却在反复修改,加入许多经典根据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上。
自然,余先生也承认“清末以来的政治影响说——清代的文字狱——是有根据的”,但当他秉着“我之所以强调’内在理路’,是因为它足以破除现代各种决定论的迷信”“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这样的观点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明清之际一切外在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变动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所投射的影响,本书全未涉及” 。
因而,如果单从本书来看,“内在理路”对于儒学传统的转换表述得极为清楚,逻辑明晰,这不免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儒学传统在明清之际的转变即是由于儒学自身的内在特性所决定。
虽然这或许不是余先生的本意,但本书的确向读者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是不容否认的。
依笔者看来,余先生采用此种写法自有其现实关怀,但书中对“内在理路”的依赖程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使得此书显得有些证据有余而说服不足了。
本书的另一个“内在理路”是对戴、章二人的心理分析。
余先生在《引论》中提到“以前研究东原与实斋的学者对他们两人论学的心理背景还不曾做过有系统的发掘,这却是本篇所要特别加以注重的所在”。
这或许来自余先生的老师——钱穆教授的教导,钱先生曾说: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
换言之,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悟到其人之学。
故研究中国学术史,必特别注重其学者之人格,即学者其人之本身。
心理分析虽有其客观性,却也有其局限性。
书中对戴、章二人大量的心理分析,尤其是对二人学术交涉重要关节的心理分析,有时不免使人产生疑问。
如余先生在论及为何章学诚晚年要做《浙东学术》追认自己于“浙东学派”时,他指出“从心理层次看,实斋十分需要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他自己的后盾,不然他将无法与承朱子之学数传而起的戴东原相匹敌”,此说暂不论对否,余先生随后给出的证据颇有可商榷之处:一是《浙东学术》篇云“梨洲虽与亭林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流长”。
余先生认为此语有夸大之嫌,因为顾氏之学上宗朱子,下有东原也是源远流长,何谓黄氏之学在传承上优于顾氏呢?二是同篇亦云“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有卓也”。
余先生认为,浙东学派的学人并未有一个明显的史学传统,实斋此言显夸大了。
据此,余先生指出,实斋之所以对浙东学术进行夸张,乃在于其内心孤愤,欲为自己寻一有力学术源流为依托以于东原抗衡。
笔者以为,余先生此说未免有些不太恰当。
首先对第一条论据而言,顾氏实其并没有明确师承。
梁启超说“亭林既老寿,且足迹半天下,虽不讲学,然一时贤大夫,乐从之游” “说亭林是清代经学之建设者,因为他高标’经学即理学’这句话,成为清代经学家信仰之中心……其纯以经学名家,而且于后来经学家学风直接有关系者,或者要推阎百诗,其次则胡朏明和万充宗” 。
而黄氏的师承关系则相当明了,上接刘宗周、王守仁,下开万氏兄弟,师承确比顾氏更长。
在《朱陆》篇中,实斋所溯清的实是东原在学术传统上的源流,而非确切的师承,而在《浙东学术》篇中,他则直云“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这一直接的师生传承了。
两文虽都旨在辨明学术源流,但对源流的取向实异;再则实斋言“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有卓也”,其主要目的仍是强调不可空言不切于事,这个观点贯穿《文史通义》全书,在《浙东学术》中亦言之“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与大雅也”等等。
况且从“此其所以卓也”这一句来看,只是本之实斋一贯思想所得出的结论,也并非反常的赞扬。
至于对浙东史学的夸大之嫌,在叶瑛对《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篇的注中云:王、刘皆言性命,至黄、万、金则究于史,王守仁称’六经皆史’已有究于史之意。
我们或可称实斋此句不那么严谨,但若说他有意夸张则未免过于苛刻了。
陈寅恪在《<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
王船山亦有类似的名言“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 。
大凡欲构成一系统者,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局限。
余先生为了完善其“内在理路”的逻辑系统而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入手,或不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因而在论述过程中反被心理分析所束缚,某些不是很顺畅的解释也似有强为之说的意味,这就造成了本书的一点小瑕疵了。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言及清代学术,章末论曰:“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
此说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亦有提及::“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
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端见焉。
他的论点即是说清儒有一套“科学”的考据方法,不是空言著述,以“复古为解放”。
这与余先生所提“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极为类似。
梁启超将明清之际儒学传统的转变同西方“文艺复兴”相比较,对笔者而言实是一个莫大的启发。
然在笔者看来,二者之间还有一点绝相类似,即儒家从“尊德性”到“道问学”中的“人之发现”。
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对于人之天性的禁锢是众所周知的。
陆王心学则讲究“心即理”“德性之知,不假见闻”,初看起来似乎很重视人的能动力,其实若从较深的层次考察,就会发现其具有一种余先生所谓的“反智识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