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教”到“三教合一”
研学资料——朝代主流思想

各朝代主流思想春秋战国主流思想:百家争鸣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等等原因:乱世中,有人选择转身离去,有人选择拯救这个世界。
这其中,则诞生了许多家学派,称之为诸子百家。
1.政治因素。
当时的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
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
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的学说思想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
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机会。
2.科技因素。
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
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3.文化因素。
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兴起。
4.学术自由因素。
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
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5.竞争。
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
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秦朝主流思想:法家思想代表人物:李斯原因:秦国之所以强盛,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
因为法家的政策立竿见影、效率极高,所以秦国较为推崇法制。
1.铁律制人:虽然从效果上来说,肯定是儒家“以仁义道德约束百姓思想”更好,但是其境界高远,在战国时代,是十分不切实际的。
法家因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抛弃仁义,从人性最恶的角度,来构建整个价值体系。
君王不担心臣子不忠,而让他不得不忠;不怕万民作乱,而让其无法作乱。
2.举国体制:极端的竞争,需要极权体制。
秦国像要争霸,那争霸必须成为举国目标。
君王的理想,必须彻底贯彻在每一位国民之上。
国民可能有他独有的理想,但是在秦国霸国梦之下,都被无情碾压。
三教整合的原因及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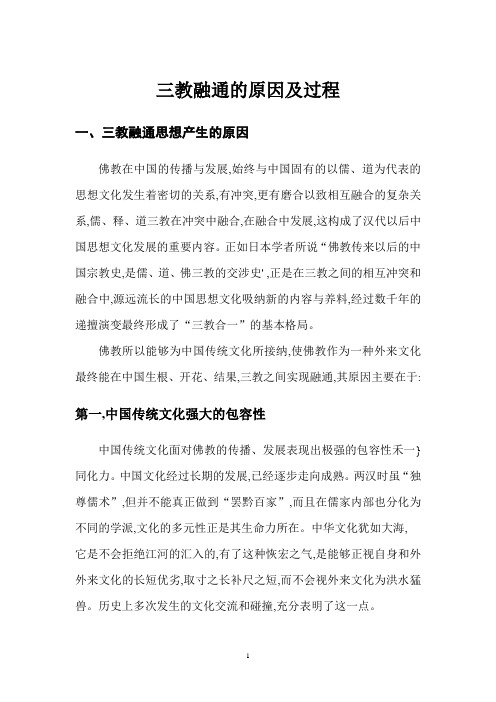
三教融通的原因及过程一、三教融通思想产生的原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有冲突,更有磨合以致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儒、释、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正如日本学者所说“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 ,正是在三教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融合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吸纳新的内容与养料,经过数千年的递擅演变最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
佛教所以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使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最终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三教之间实现融通,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禾一}同化力。
中国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
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黔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
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
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佛教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外来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十分注意依附迎合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努力调和与儒、道思想矛盾的同时,不断地援儒、道入佛,并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一致性,从多方面拉进三者之间距离,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从而使儒、释、道三教关系趋于融合。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双方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三教融通的表现一、三教融通关系论说佛教初传之时,中土的人们对它了解甚浅,常把它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混为一谈,并用儒家观点阐释佛陀。
论三教合流及中国当代社会思想

论三教合流及中国当代社会思想自1966年到1976年文革以降,左倾错误导致我国思想混乱,“除四旧”,“划清界线以示清白”等等,摧毁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信仰价值体系,当代中国人心中已经缺失了心中的信仰,道德沉沦。
改革开放,是自1978年以来的既定国策,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使得我国的经济实力猛涨,中华民族强势崛起。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社会矛盾也很突出。
其突出的表现在,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且固化,贫富差距拉大,道德滑坡。
欲挽大厦于将倾,救社会于崩溃之边缘,实应立足于我国之传统思想的传承。
然而我们却不能行那外儒内法之道,更不能独尊儒术,还需从儒,释,道三家合流处着手。
所谓“三教合流”从佛教在东汉时期进入中国以后,就有所谓三教,即儒、释、道三家。
儒教就是以孔丘为主的儒家思想,道教就是以老子为主的道家的一部分思想,佛教则是以释迦牟尼为主的思想。
“三教”的说法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
“三教合流”的说法据说由南北朝时期的医学家、道家学者陶宏景较先提出。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教的分合是贯穿近二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一股重要的流,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
对于此种现象,学者多以三教合一统而论之。
然而,从三教并立到三教合一,则有一个过程。
元明间“三教合一”一词的出现可以说是三教间关系已经具有内质的演变。
三教概念的发展,可以分几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阶段,唐宋是一个阶段,元明清是一个阶段。
最初的阶段里,虽然有三教的连称,不过彼此是独立的,当然相互间都有影响,儒、道、佛三者之所以相提并论,则是偏重于它们社会功能的互补。
中间的阶段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主要在于彼此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树一帜。
只有最后的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
其中,第二阶段是在继续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亦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大。
《西游记》传统价值观:孙悟空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

《西游记》传统价值观:孙悟空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西游记》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同时也是一部充满智慧和思想的作品。
其中,孙悟空这个角色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传统价值观,即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
本文将从儒家、佛家和道家三个方面论述孙悟空的思想,并说明他是如何将这三种思想融合在一起的。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强调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
而孙悟空虽然是个猴子,但他却具备了儒家思想所崇尚的许多品质。
首先,他对待师长极为尊重,从师傅菩提祖师到师父唐僧,孙悟空一直表现出顶礼膜拜的态度,体现了孝敬师长的儒家观念。
其次,他具备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始终保护师父唐僧等团队成员不受恶势力的伤害,展现了仁义的儒家思想。
此外,孙悟空还具备智慧和诚信,他为了拯救人间的众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表现出智勇双全的儒家理念。
佛家思想注重人生的解脱和慈悲心肠。
孙悟空在西游取经的过程中,不仅帮助师父唐僧克服了困难,也帮助了许多遇难众生。
这体现了佛家思想中关于拯救有情众生、消除众生苦难的观念。
孙悟空的慈悲心肠不仅体现在对待众生的态度上,还表现在对待敌人上。
他对敌人常常采取宽容态度,甚至帮助恶魔和妖怪走上正途,体现了佛家思想中的慈悲观念。
此外,孙悟空通过修行,最终达到了身心的解脱,并在五行山下守护师父唐僧,展示了佛家修行的境地。
道家思想强调顺应自然和追求自由自在。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体现了道家价值观的多个方面。
首先,他以身体灵活、变化多端的特点展示了顺应自然的道家思想。
他可以变化成各种形态,操纵风云雷电等自然元素,表现出追求自然自由的态度。
其次,孙悟空并不愿受人约束,追求心灵的独立和自由。
他不服从天庭的限制,为了反抗天命,与诸多神仙争斗,表现出了道家思想中追求自由自在的一面。
孙悟空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并不仅体现在他个人形象和行为上,还体现在他对待众生和社会问题上的态度。
他以宽容和智慧对待各种不同种族的生灵,强调平等互助,展现了儒家和佛家的教诲。
宗教闲谈之三教合一

浅谈“三教寺”与“三教合一”

浅谈“三教寺”与“三教合一”作者:张龙平来源:《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07期摘要:白佛山是山东东平的重要旅游景区,三教寺位于山中,是我国北方最早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寺院,给我们研究儒、佛、道的流传提供了宝贵资料。
关键词:三教寺三教合一【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09)-07-0071-01白佛山,又名危山、金螺山,当地人称白虎山,位于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东平镇焦村正北边,东面与县城相接,西边与美丽的东平湖遥遥相望,南邻大清河,北依群山,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佛山因石窟造像群而闻名全国,石窟群位于南山腰向阳处,其中最大的一尊为隋代释迦牟尼雕像,也被人称为“齐鲁第一大佛”。
石窟下方茂密的林木中掩映着一座建筑古朴、雄伟壮观的寺院——三教寺。
三教寺始建于金大定七年(1167),最初名为“三教堂”。
寺内主殿里面共有三尊塑像,菩提树下悟道的佛陀释迦牟尼像居中,右边是“文宣玉”、人间万世师表的孔子像,左边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太上老君”老子像。
这座三教寺是我国北方最早的“佛教、儒教、道教”三教合一的建筑。
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6-前486年),原名乔达摩悉达多,佛教创始人。
“佛”是梵文“佛陀”的音译的简称,意思是“大彻大悟的人”。
释迦牟尼最初的说教内容是“四谛”,即“苦、集、灭、道”四种真理。
人们通过修行、断惑、涅槃,成为阿罗汉意为“不生”,不再坠入因“造业”产生的生死轮回。
“四谛”后来成为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
释迦牟尼还提出了“八正道”之说,即正见、正定、正言、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欲。
此外,佛教要求其徒众终身尊“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宣扬一切生命在灵魂上平等;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修行得到解脱,早期的佛道不设神庙,不主祭祀,不拜偶像,传教用语通俗易懂,并且不排斥低级“种姓”的人入教,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他所创立的思想、行为模式潜移默化为道德标准,随着佛教徒的数量的猛增,佛教势力越来越大,名声越来越响。
儒释道三教合一

天干地支和阴阳对应表天干地支和五行对应表地支和生肖对应表四季和五行的对应十神表儒释道三教合一,殊途同归中国本土的三大圣人:儒家的孔子、道家的老子、佛家禅宗的六祖慧能。
代表了中国儒、释、道三家。
儒家是讲入世的,勇猛精进,百折不挠,它的精义是“工作”。
佛家是讲出世的,似空非空,云空家的学说便是最为快捷的解决方法。
那里不但有医治你身体疾病的中药,而且有着医治你精神创伤的良方。
佛家,讲求慈悲入定,求“治心”。
侧重于人生出世观,虽然是“泊来品”,但几千年来,传入中国以后,经中国人的改造,早以融进了种种中国元素。
它像一家“百货店”,各种商品应有尽有。
你不妨也进去看看,也许能得到不少有用的东西,也许你还能发现,人世间找不到的东西或情感,在那里都能找到。
当你在精神空虚的时候,也许在那里会找到自己精神的寄托。
四,论修养;儒家,讲“修身,齐家,治世,平天下”讲的是重视现世的修为。
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就是说人们要先懂得生活,再谈论死亡。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治天下”。
道家,言“养生,遁世,穷万物”。
讲的是穷尽变化。
老子为人们讲述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让人们效法天道,顺应自然,在自然之道中学习为人处世之道。
佛家,悟“见性,救世,通万有。
”讲的是“缘起性空“四大皆空。
从“空性”中去追求人生的不空。
五,觅智慧;儒家讲的智慧是德行智慧。
通过仁、礼、乐的教化,修身实践,尽心知性而知天。
道家言的智慧是心灵智慧。
在自然无为中寻求和谐的处世之道。
佛家悟的智慧是解脱智慧。
是无漏的大智慧。
无执无欲,破茧出脱,直悟生命的本质。
六,殊途同归;嵩山少林寺有一处供奉了佛陀、老子、孔子,三位教主的大殿。
殿中有一对联;百家争理,万法一统。
三教一体,九流同源。
在殿边的小室山上还有一副对联;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
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
精辟地点明了三教殊途同归的本质特点。
七,精神盛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礼仪之帮,并非是专一宗教信仰的国家,是有着56个民族共存,和谐相处,充满着宽容、融洽、共进的社会。
道教在三教合一中的演化

道教在三教合一中的演化摘要: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三教为了各自的发展,都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吸融其他二教。
道教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不同的发展时期从各个层面吸佛纳儒,有力的推动了三教合一的形成和发展。
本文通过搜集、采用一些道教经典等材料,以及对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归纳了道教在推动三教合一的过程中自身的发展与演化。
关键词:道教三教合一演化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自汉末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形成之后,中国文化由汉武帝时代以来的儒家一统天下,逐渐演变为儒、释、道三元共轭的格局,这种特殊的多元文化结构一直维系到近代。
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互相交涉,经过多次斗争又相互影响,最终趋归融合,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至今。
继承先秦道家兼容并蓄之学风的道教,更是大幅度的融摄、吸收佛、儒二家之学建构起自家庞大而驳杂的思想体系。
道教以中华本土传统信仰为基础,广泛的吸收融合诸家文化之精华,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也各有不同:一、汉魏两晋时期:这一时期是儒释道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三家的基本情况是儒学的历史最长,但需要根据心得形势进行必要的改造,佛教刚入中国,尚未站稳脚跟,道教刚刚建立,各方面都较幼稚原始,三家要忙于自己的事务,彼此的直接冲突较少,相反,儒学为了改造需要从别的思想来汲取营养,佛教为了在中国生根立足,需要迎合迁就儒道,道教为了自己的建设,需要向儒释汲取必要的养料,而主要表现为对儒家思想的吸收。
这一时期,随着道教被一些最高统治者接受,传播于世胄高门,大批高级士族人士加入道教,成为它的信徒,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天师世家,大批高级士族的涌入,必然会将他们的思想带入道教中来,所以这一时期道教的代表人物丹阳葛洪提出了以神仙养生为主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
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纲常名教结合,建立了一套长生成仙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
葛洪曾在《抱朴子》中说:“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
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

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作者:郭福军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8年第07期摘要:从历史沿袭的角度来看,从三教并立到三教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
在元代至明代期间,三教合一一词开始出现,这表明儒教、佛教、道教三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内在的转变。
本文从“三教合流”类型的视角探讨与分析“三教合流”现象,旨在理清在传统儒家社会中是如何对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行处理的,从而为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正确处理宗教关系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三教平等;三教同归;三教同源前言:儒释道中的“儒”是指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也被称之为儒教,曾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其基本占据主流思想体系的地位,对于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东南亚等地区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发展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儒释道中“释”是指今天尼泊尔境内的乔达摩·悉达多所创立的佛教,也被称之为“释教”,是三大宗教之一。
儒释道中的“道”是指在我国东周时期的黄老道依据《老子》、《庄子》所创立宗教,其为中国本土宗教。
在中国道教是根,儒教是茎,佛教是叶与花,所以儒释道本就是一家,同气连枝。
一. 三教平等三教平等是儒教立场的三教合流。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儒教主要具有两大代表集团,其一就是封建帝王,其二就是学识渊博的儒士。
两大代表集团虽然在身份与地位上不同,但是在处理三教关系的时候说持有的观点具有相似性,那就是三教平等,但是二者之间所侧重的点却存在不同,帝王关注的是宗教在封建统治中的作用,所以其更加关注三教之间的平衡,而儒士,尤其是唐朝中期以后的儒士,一般都是将辟佛老作为自己的任务与使命,但是在生活中却又暗自通晓佛老,这在更深层次之上实现了三教之间的融合。
从封建帝王统治的视角来看,儒释道三者各有所长,所以三教应该和谐共存、相互制衡,最终服务于封建社会的统治,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在封建帝王的心中始终坚持三教平衡。
其中儒教的功能在于治世,是封建君王实施封建统治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儒教可以确立起封建社会的礼仪规范以及道德标准,从而使得普通民众自觉的按照这一意识形态规规矩矩的接受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遵守封建统治制度。
“三教融合”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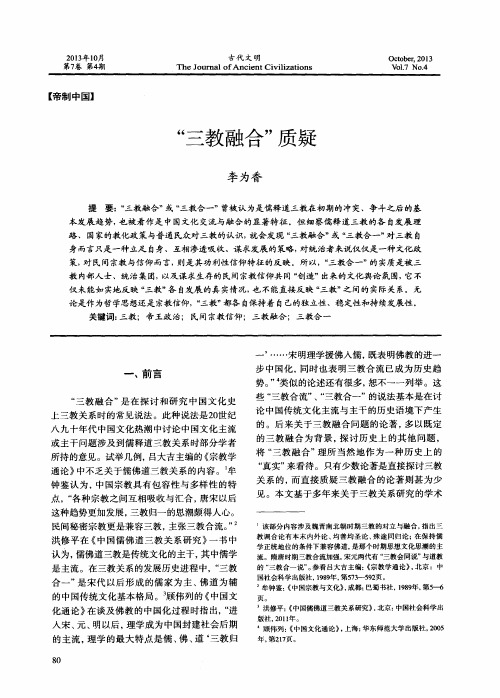
2 0 1 3 年l 0 月
所持的意见。试举几例, 吕大吉主编的 《 宗教学 通论》 中不乏关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内容。 牟
钟 鉴 认 为 ,中 国宗 教 具 有 包 容性 与 多 样 性 的 特 点 ,“ 各 种 宗教 之 间互 相 吸 收与 汇 合 , 唐 宋 以后 这种 趋势 更 加发 展 , 三教 归一 的思 潮 颇得 人 心 。
势。 ” 类 似 的论述 还 有 很 多 , 恕 不一 一 列举 。这 些 “ 三教合 流”、 “ 三教合 一 ”的说 法 基 本 是在 讨 论 中 国传 统 文化 主流 与 主 干 的历 史语 境下 产 生
“ 三教融合 ” 是 在 探 讨 和 研 究 中 国 文 化 史 上 三 教关 系 时 的 常见 说 法 。此 种 说 法 是2 0 世 纪 八 九 十年 代 中 国文化 热 潮 中讨论 中 国文 化 主流 或 主 干 问题 涉 及 到儒 释 道 三 教关 系 时部 分 学者
版社 , 2 0 1 1 年。 顾伟列 : 《 中国文 化通论 》 , 上海 : 华 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2 0 0 5 年, 第2 1 7 页。
史, 质疑长期 以来学术界对 “ 三教融合” 的普遍 用法 , 探讨 的主要 问题则是 “ 三教融合 ” 与 “ 三 教合 一” 如何被各种社会群体创造 出来 ,并对 三教 融合与合一的说法作进一步 的澄清 ,提示
古 代 文 明
三教合一的看法

三教合一的看法三教合一是指佛教、道教和儒教三教的合一。
它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味着这三个思想体系具有相通之处,可以和谐融合,形成一种新的教义和宗教体系。
对于三教合一的看法,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首先,支持三教合一的观点认为,这一合一可以促进各个教派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宗教和谐发展。
在中国的历史上,佛教、道教和儒教相互渗透、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点,形成了一个多元化、兼收并蓄的宗教文化体系。
例如,佛教弘扬了慈悲、舍己为人的精神,道教倡导自然和谐的思想,儒教强调礼仪和道德规范。
将这些思想合一,可以使人们在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中得到更全面的满足。
其次,三教合一可以促进宗教与现代社会、科学进步之间的对话与融合。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逐渐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宗教信仰也面临着挑战。
通过将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合一,可以使宗教的思想体系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与科学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相结合,使宗教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发展和传承。
此外,三教合一也有助于解决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在中国的历史中,佛教、道教和儒教之间曾经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互相排斥对方的观点和信仰。
通过三教合一,可以弥合不同宗教之间的分歧,增进宗教间的理解与合作,推动宗教的和平共处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然而,还有一些人对三教合一持有不同的观点。
他们认为,佛教、道教和儒教作为不同的教派,各自有着独特的信仰体系和思想传承。
三教合一可能会模糊它们之间的区别,使得宗教信仰变得模糊不清。
此外,三教合一也存在对于教义的选择与折中,可能损害各教派信徒的权益和利益。
对于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保留各教派的独特性和优势,与之形成互补的关系来解决。
可以对三教的核心价值进行整合,形成新的教义和宗教体系,同时也要保持教派之间的独立性和多样性。
综上所述,三教合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和讨论。
虽然一些人支持将佛教、道教和儒教三教合为一体,但也有人持保持各教派独立性的观点。
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卢飞宏

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中华武学思想文化探索研究)中国在五千余年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灿烂辉煌,从先至明清中国思想界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展现了数千年恢弘浩瀚的思想文化画卷。
从先时期的百家争鸣到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统治地位的确立。
从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到唐朝佛学的鼎盛发展,又到宋明理学的兴起,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借鉴和融合,直到最后明清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确立,让人们徜徉在卷帙浩繁的思想文化史中。
中国文化具有连续性、独立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及统一性,它是在相当大的地域围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华夏五千年文明,留下了灿烂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它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儒释道三教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三教合一文化对中国社会、哲学、思想、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对周边国家文化也有深远的影响。
在当今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融合中,研究探索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传统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激活中华思想文化的生命力,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教合一”文化的历史形成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要容和主流意识的,主体是儒道释三教,而其三教融合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
在历史发展中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各有传承,相互融合,统贯着社会、学术与文化的命脉。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涵,它们从相互尊重到相互对立和斗争,到相互借鉴和吸收,再到相互包容和融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
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是中国历史中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各种传统文化和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产物,历史上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重要作用,有其存在合理性和必然性,是中华民族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文化。
三教合一 殊途同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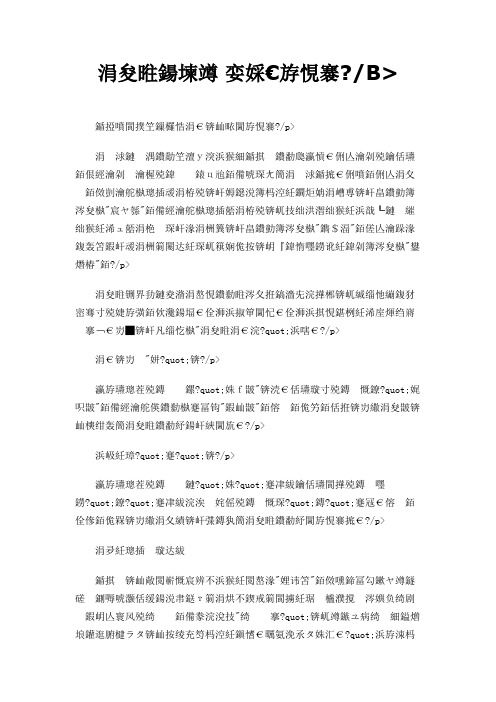
三教合一殊途同归儒释道三教合一,殊途同归中国本土的三大圣人:儒家的孔子、道家的老子、佛家禅宗的六祖慧能。
代表了中国儒、释、道三家。
儒家是讲入世的,勇猛精进,百折不挠,它的精义是"工作"。
佛家是讲出世的,似空非空,云空未必空,以出世观行在世事,它的精义是"睡眠"。
道家在出世和入世之间,行云流水,顺其自然,其精义是"生活"。
三教虽然有着不同的教义和思想体系,但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同化,从某种角度而言,已经是"三教一体"了。
一,说"气";孔子讲的是要树"正气";老子说的是修炼"清气"。
佛家悟的是心平"和气"。
正、清、和,这三气,显示了三教的异同归途。
二,谈"心";孔子讲的是要有"正"心;老子道的是自然"炼"心;佛家求的是修行"明"心。
正、炼、明,这三心,反映了三教的异途同归。
三,讲学说;儒家,注重修己治人,重在"治世"。
几千年来一直被历代封建君王捧之为治国之道,被百姓视之为精神和道德的粮食。
仿佛似"粮食店",一日没粮会感到腹中饥饿,水米不进,恐怕就会饿死。
"五四运动"中提出打倒这个孔家粮食店,改吃外国的洋面包,可是中国人的胃口就是不适应,到头来还是喜欢自己的馒头、大米饭。
道家,讲究宁静阴柔,重在"治身"。
如同中草药,当人们面对生死、得失、烦扰,喜怒、哀乐,要想消除心中的愤懑、抑郁时,道家的学说便是最为快捷的解决方法。
那里不但有医治你身体疾病的中药,而且有着医治你精神创伤的良方。
佛家,讲求慈悲入定,求"治心"。
侧重于人生出世观,虽然是"泊来品",但几千年来,传入中国以后,经中国人的改造,早以融进了种种中国元素。
三教合一新论

21 0 0年 1 0月
武 汉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 会 科 学 版 ) 社
J o u a i fS i & Te h ( o il ce c iin . fW h n Un .o c. c . S ca in eEdto ) S
Vo1 2, .5 .1 NO
宗 、 学 与 外 道 、 家与 居俗 的 中 国佛教 诸 宗 派 , 内 出
土化 了的 佛 教 。古 代 “ 化 ” “ ” “ 教 ” 教 之 教 与 宗 之 “ ” 教 尚无 明确 的 区分 , 而 习 惯 上也 将 三 家 笼 统 故
地 称 为 “ 教 ” “ 教 合 一 ” 有 关 中 国文 化 基 本 三 。 三 是
度 上 具 有 了其他 两 家的 某 些 要 素 或 特 征 ; 家 经 过 长 期 的 磨 合 , 同 构 建 了 中 华 民族 赖 以 安 身 立命 的精 神 家 三 共
园 ; 家作 为 一 种 深 厚 的 文化 积存 和现 实 的 精神 力 量 , 同 融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有 中 国特 色社 会 主 义 建 设 三 共
解 呢?
一
既 反映 了中国文 化 转 化 外来 文化 的心 胸 和智 慧 ,
也充 分 体现 了佛 教 在 异 质文 化 环 境 中具 有积 极 、
主 动的 灵活适 应能 力 。
道家 和道 教对 儒佛 因素 的吸 收பைடு நூலகம்利 用促 成 了
、
三 教 各 合 其 一
自身 形 态 的 发 展 演 变 。 道 家 在 先 秦 “ 家 争 鸣 ” 百 中 是儒 家 的对立 面 , 汉之 后虽 然也 一度受 到重 视 , 入
三教融合过程与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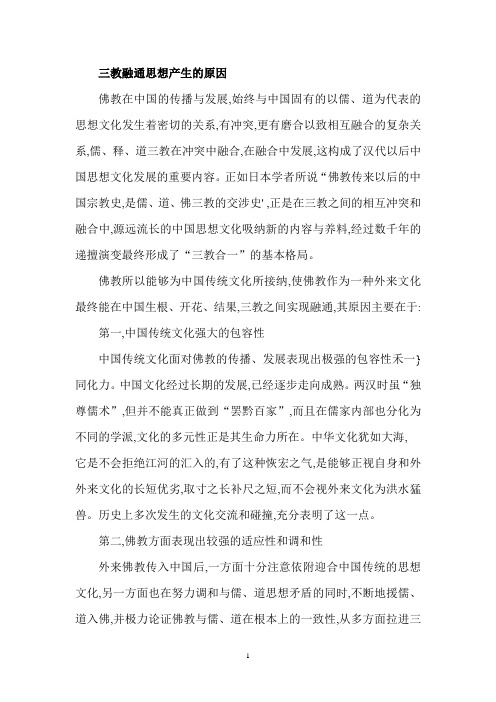
三教融通思想产生的原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有冲突,更有磨合以致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儒、释、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正如日本学者所说“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 ,正是在三教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融合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吸纳新的内容与养料,经过数千年的递擅演变最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
佛教所以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使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最终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三教之间实现融通,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禾一}同化力。
中国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
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黔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
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
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佛教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外来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十分注意依附迎合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努力调和与儒、道思想矛盾的同时,不断地援儒、道入佛,并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一致性,从多方面拉进三者之间距离,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从而使儒、释、道三教关系趋于融合。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双方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三教融通的表现一、三教融通关系论说佛教初传之时,中土的人们对它了解甚浅,常把它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混为一谈,并用儒家观点阐释佛陀。
如袁宏《后汉纪》中介绍说:佛者,汉言觉,将以觉悟群生也。
王通“三教可一”思想简论

王通“三教可一”思想简论道教和佛教不断发展兴盛,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佛道二教的严峻挑战。
为了解决三教纷争的问题,各派学者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是这些观点都不是站立在儒学的立场上提出来的。
王通自幼受儒学熏陶,勤奋好学,以振兴儒学为己任。
将其“中道”的观点,合理地运用到了如何处理三教关系上面,明确地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
这是第一次在儒学的立场,吸收和借鉴佛、道两家的思想,兼容并蓄,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
这种观点也对后世的宋明理学家在处理三角关系上有所启示。
标签:王通;中道;儒释道;三教可一王通(584—617年),字仲淹,隋河东郡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人。
出身世宦和儒学家庭,自幼受儒学熏陶,勤奋好学。
20岁曾上《太平策》,隋文帝未用。
后居于河汾之间,以授徒著述为业。
其著书多拟六经,有《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世称《王氏六经》,早已遗失不存。
现存《中说》十卷,由其子记述编纂,旨在光大儒学。
在历史的长河中,王通是一位长期不受重视的儒家学者,然而,被冷落往往是先驱者的命运。
王通之所以不受重视,是因为他的思想过于超前,他在儒学改造还不成熟的隋代,就提出了儒学改造的课题,并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佛学和道家,从“三教可一”观念出发大量吸收了佛学和道家思想,构建了融合儒释道的思想体系。
王通一生致力于推崇周公、孔孟之道,在儒家思想走向没落的危急关头,王通走在世人的前面,他的思想为儒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韩愈、李翱以及后世的宋明理学都起到了启蒙和引导作用。
王通的“三教可一”论正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而吸收佛道两家思想对儒家进行改造,显示了儒家的未来发展,也预示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未来走向。
一、王通时代的三教关系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天人感应”的思想,为当时汉朝的大一统的局面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从实际上使得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统治思想,成就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
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卢飞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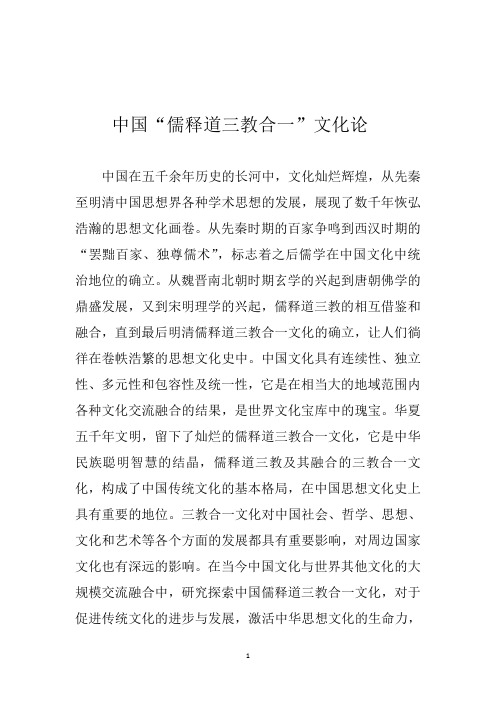
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中国在五千余年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灿烂辉煌,从先秦至明清中国思想界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展现了数千年恢弘浩瀚的思想文化画卷。
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到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统治地位的确立。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到唐朝佛学的鼎盛发展,又到宋明理学的兴起,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借鉴和融合,直到最后明清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确立,让人们徜徉在卷帙浩繁的思想文化史中。
中国文化具有连续性、独立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及统一性,它是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华夏五千年文明,留下了灿烂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它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儒释道三教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三教合一文化对中国社会、哲学、思想、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对周边国家文化也有深远的影响。
在当今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融合中,研究探索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传统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激活中华思想文化的生命力,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教合一”文化的历史形成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和主流意识的,主体是儒道释三教,而其三教融合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
在历史发展中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各有传承,相互融合,统贯着社会、学术与文化的命脉。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内涵,它们从相互尊重到相互对立和斗争,到相互借鉴和吸收,再到相互包容和融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
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是中国历史中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各种传统文化和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产物,历史上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重要作用,有其存在合理性和必然性,是中华民族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文化。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三)
在区分三教和三教合一时,有一条界限是需要分明的,即站在佛、道的宗教立场上说三教一家,和以三家观念统一到一个宗教形态之中是有着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后者也可说是前者观念发展的结果。
纵观从三教到三教合一观念的变化,可以察看到中国社会的一些发展动态。首先,自唐以后,无论是从外在的政治统一,还是内在的专制集权程度,都甚于以往的朝代,而且是一代甚于一代。这种专制集权的大一统社会政治体制的不断加强,愈来愈需要更为一致的含有宗教形态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于是三教合一的呼声也越加强烈,包括象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统治者的极力提倡[35]。其次,鉴于自春秋至秦汉思想趋向一致所形成的传统,三教在长期并存的过程中,内质上通过交流,彼此的认同越来越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教的真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要的条件。如余英时先生指出:“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的”[36]。又如元代全真教主王哲(重阳)在山东等地组织“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三教七宝会”等等,表明在新道教的内部,三教合一的因子更为成熟,“大量儒释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为入明以后道教的一大特色”[37]。这种现象也在当时上层建筑中各个领域内泛现,如“‘三教圣人’在元代戏剧及其它著作中就突然出现了”[38]。再次,由于十三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的瓦解,使中国佛教再也难以吸收与中国文化异质的东西,这对加速与其它二家的同化,反而成了有利因素。最后,中国民众在宗教上一向是兼容并收的,儒、道、佛诸家的内容都早已司空见惯,三教合一把这些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调和起来,推陈出新,民众是乐于其成的。这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会条件。
至隋唐两宋,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陈寅恪先生谓:“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14]。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但客观上却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并反映了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的需要。如唐“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15]。三教在唐宋时频频进行的廷争,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16],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认同。如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17]。甚至从唐时起“中医药学是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18]。冻国栋先生也通过对《唐崔暟墓志》等史料的考释,认为:“儒、释、道兼习乃是隋唐时代士人及其家族的普遍趋向”[19]。同时,“中唐以后,天子生日举行有关三教的传统性活动──三教讨论”,致使“中唐产生了三教一致的思想”[20]。不过由于这些辩论的主题方向往往是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框架下展开的,目的是为了皇朝的“鼎祚克昌”和“天下大定”[21],故三教连称在唐代,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因为“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22]。思想上的融会贯通必定会见诸于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如在《旧唐书》中,“三教”一词共出现24次,比除了《新唐书》之外的其它二十二史中此词所出现的次数加起来的总和还多。可谓彼时之三教连称,系时风所趋,深入人心。武则天时编纂《三教珠英》,参加者皆为一时之选,如“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23],这些人俱是少读经书,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此当然也会给三教在文字表达中的频率高低带来影响。
在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帝王的崇佛,以及佛教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生气和丰富内涵,使佛教成了三教的中心。梁武帝在其《述三教诗》中说他自己“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最后达到“至理归无生”[13]的认识,非常形象地突出了佛教盖过其它二教的吸引力。这可以说是该时期三教关系的一个特点。
(二)
从统合的角度看,“三教合一”的含义无疑要比“三教”更进一步。关键在于对“合一”的理解。如果将“合一”视作儒、道、佛三家的内在义理上,特别是在道德标准取向上走向融合的一种趋势,当然可以,但此至少在明代之前是称为“三教合流”或“三教归一”的。其实一般现在的学术著作中在说三教合一时,也就是这个意思。
三教在社会上的客观存在是三教概念出现的基础,不过三教概念的提出却是社会意识发展变化的结果。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形成是在两汉之间,虽然“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2],但三教概念的出现和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三国之前人们的论著中是没有“三教”一词的。《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3]。以及“牟子作《理惑论》,论儒佛思想之一致;道安以《老子》语解《般若经》;这些可以说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见”[4]。以后“暨梁武之世,三教连衡”[5],三教一词出现在文献上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作为强大的社会存在已经无可置疑。时人于佛儒、佛道、儒道之间的互补共通之处,分别有很多的建议论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6]。如孙绰在《喻道论》中云:“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7]。明僧绍则认为“佛开三世,故圆应无穷;老止生形,则教极浇淳”,所以“周孔老庄诚帝王之师”而“释迦发穷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8]。王治心先生就张融、顾欢等人“道同器殊”思想阐述道:“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来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释教道教之分。……这些都是六朝三教同源的意见,这种意见,影响于后世亦非常之大”[9]。此外,作为体现此类理念的人物在当时也大量出现,著名的如道士陶弘景既著“《孝经》、《论语》集注”,又“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10]。还如沙门昙度“善三藏及《春秋》、《庄》、《老》、《易》。宋世祖、太宗并加钦赏”[11]等等,当时诸如此类的人物是很多的。存在决定意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12]。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出现了“三教”的概念。
林兆恩的“三一教”,是以公开标榜三教合为一教作宗旨的,其它一些民间宗教里也有以此为旗帜的,此可见诸于那些民间宗教的经典“宝卷”。如《销释悟性还源宝卷·留三教经品》云:“自今慈悲来找你,才留还源三教经”;《开心结果宝卷》中有《三教菩萨品》;《混元红阳临凡飘高经》亦有《取三教圣人品》等[30]。此表明明清二代有更多无名有实的三教合一宗教组织,即是上述那些活跃在当时的五花八门民间宗教。对此明末清初时的颜习斋看得很清楚,他说:“大凡邪教人都说‘三教归一’或‘万法归一’”[31]。在这些民间宗教所奉行的宝卷里,三教之间的原有差别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正如安娜·塞德尔所说 ,“这些佛──道经文起源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世俗圈子中,在那里,两个宗教在教义上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32]。事实确是这样,如罗教创始人罗清在其《五部六册》中的《破邪显证钥匙卷·破不论在家出家辟支佛品第一》里就进一步说明:“一僧一道一儒缘,同入心空及第禅。似水流源沧溟瀇,日月星辰共一天。本来大道原无二,奈缘偏执别谈玄。了心更许何谁论,三教原来总一般”。酒井忠夫先生曾对《五部六册》引文进行考证,发现其中不仅有《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等佛经,还有《道德经》、《悟真篇》等道教典籍和儒家的《大学》、《中庸》等[33],说明这些所谓宝卷完全是三教合一的。大体上说,这些宝卷“全是邪教名目而假充如来佛经以欺人者”[34],也就是说民间宗教如果在崇拜形式上还往往显示着佛教色彩的话,但其所主张的现世人们行为准则,却是儒家的忠孝仁义等伦理,如其中《销释孟姜忠烈贞节贤良宝卷》、《二十四孝报娘恩》、《节义宝卷》等等。
(一)
“三教”,指的是儒、道、释三家[1]。三教概念的发展,可以分几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阶段,唐宋是一个阶段,元明清是一个阶段。最初的阶段里,虽然有三教的连称,不过彼此是独立的,当然相互间都有影响,儒、道、佛三者之所以相提并论,则是偏重于它们社会功能的互补。中间的阶段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主要在于彼此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树一帜。只有最后的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其中,第二阶段是在继续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亦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大。
论“三教”到“三教合一” 作者:严耀中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教的分合是贯穿近二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一股重要的流,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对于此种现象,学者多以三教合一统而论之。然而,从三教并立到三教合一,则有一个过程。元明间“三教合一”一词的出现可以说是三教间关系已经具有内质的演变。今将这种演变分阶段具说之,希方家指正。
三教合一概念在明代的提出,必定是当时的社会中已经有了合三教为一教的某种实际形态存在,哪怕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社会上确存在三教形态上的共一。如到了明代,三教共同崇拜的神祗日益流行,其中最盛的是关帝信仰,约成书于明中期的《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称关羽君临三界,“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再如晚明的林兆恩甚至创立以儒为主体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三一教”,宣称要通过“炼心”、“崇礼”、“救济”等手段,“以三教归儒之说,三纲复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后世”[28],甚至“立庙塑三教之像:释迦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为儒童菩萨塑西像,而处其末座。缙绅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29]。实行了三教在信仰崇拜体系上的合一。从而使三教合一概念的内涵有了质的飞跃。
不论是魏晋还是隋唐,三教的并提,都可以说有着以下的意味:第一,表明作为社会的意识力量,儒、道、释各有影响范围,可以说三分天下,虽然其间常有高低先后之争。第二,所谓三教归一、三教一家之类的说法,不论是出于那一家之口,无一不是从维护社会道德,有利政治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认为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24]。这种“一”致被强调的结果,实际上是将儒家理念作为三教的取舍标准,故反对三教并提的一方,也是以佛、道二家不具备能与儒家等量齐观的社会功能作为一条重要理由,认为三者在道德趋向上仍未一致,甚至还有所牴牾。不过在魏晋,乃至隋唐,反对方始终不是社会主流意见,至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未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纳。第三,三教仍然各自保持着独立的形态,不过相互间在观念和思想方式上,不断地进行交流和融合,一定程度上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加深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第四,由于自南北朝起玄学的消退和经学的东山再起,尤其是王通、韩愈等人对新儒学的发展,一直到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学主导社会意识的动能日益强大,促使三教在隋唐之后朝儒家倾向的势头也愈来愈明显[2模糊,古人极少用三教合一这个词,至少是明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使用过此词。作者曾请友人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通过电脑光盘检索,三教合一之称在整个《四库全书》中只出现过八次,且全都是在元代以后。也就是说,在明代之前,只有三教的概念,而根本没有三教合一概念的流行。或者说,明代以前的人们,尚未认识到三教在外在形态上有合一的可能性。当然,明代人所说的“合一”,仍可分二个层次。其一依然是以往“三教归一”、“三教一家”的那层意思,即主要指三家在道德价值观念上的一致性。如顾宪成在《明故礼部仪制司主事钦降南阳府邓州判官文石张君墓志铭》中云:“东溟管公倡道东南,标三教合一之宗。君相与质难数百言,管公心屈”[26]。不过,从明代一位监察御史陆陇其所云,“今人言三教合一,岂非朱子之所叹然。又有谓三教不可合而各有其妙,不妨并存者,则又是以不合为合,尤巧于包罗和会者也”[27]。陆氏所谓三教的两种合一,其区别正是表现于外在形态上,即当时人们确有主张将三教混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