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的邪恶”与“盲从的犯罪”
阿伦特论“平庸的恶”

阿伦特论“平庸的邪恶”W2/Gt&徐贲©中间思想文化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U!$©中间思想文化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63从二次大战结束到1975年去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整个的政治哲学生涯中始终不能忘怀专制的邪恶问题。
六十年代初,她对极权专制邪恶的看法由于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克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事件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她因此而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由原先为《纽约客》所写的五篇报道修改而成)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邪恶”一说。
她对专制邪恶的关注也逐渐从对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统治形态转移到对专制制度下个人道德判断的政治批判,进而提出了一个至今对我们仍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那就是,专制制度下的个人负有怎样的道德责任?S}JGiR©中间思想文化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AnuK阿伦特在她五十年代初出版的《极权主义之源》一书中,将纳粹和斯大林主义这样的极权专制界定为“激进的邪恶”。
激进的邪恶是极端的邪恶,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原创的邪恶。
纳粹统治下的灭犹行动,斯大林统治下的集中营,是激进邪恶的最集中体现。
在阿伦特看来,激进的邪恶有三个特征:不可罚、不可恕和不可知。
她写道:“集中营是进行改变人性试验的实验室,……为了证明没有不可能的事,极权统治却无意中发明了既无法惩罚也无法饶恕的罪行。
当不可能的(罪行)成为可能的时候,它也成为不可罚、不可恕的极恶。
极恶是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懦怯这些邪恶动机来解释的,因此,对极恶既不能用恨去复仇,也不能用爱去容忍,或用友情去宽恕。
”〔注1〕A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BJw 阿伦特提出的关于极端邪恶的三个特征并不属于同一范畴,前两个特征是关于“我们如何对待邪恶,”第三个则是关于“邪恶是什么。
”前面的两个特征可以用普通人对大恶的一般看法来映证,后一特征则必须在道德哲学中才能得到说明。
何谓平庸之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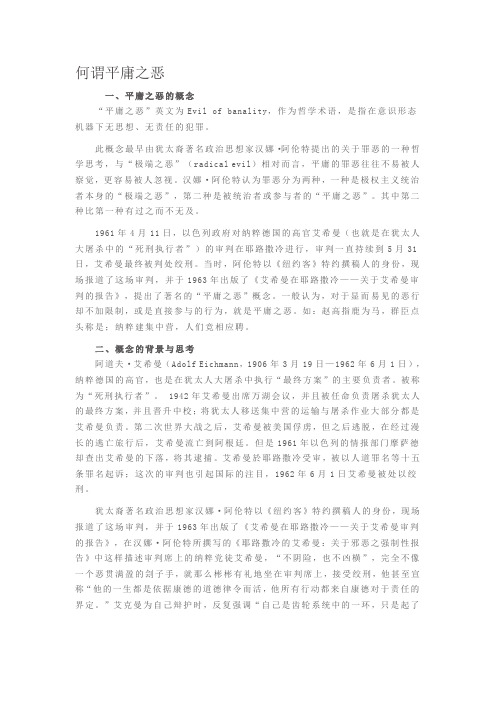
何谓平庸之恶一、平庸之恶的概念“平庸之恶”英文为Evil of banality,作为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此概念最早由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关于罪恶的一种哲学思考,与“极端之恶”(radical evil)相对而言,平庸的罪恶往往不易被人察觉,更容易被人忽视。
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
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
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纳粹德国的高官艾希曼(也就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死刑执行者”)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一直持续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
当时,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
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
如:赵高指鹿为马,群臣点头称是;纳粹建集中营,人们竞相应聘。
二、概念的背景与思考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
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并且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艾希曼负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
但是1961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却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逮捕。
艾希曼於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在汉娜·阿伦特所撰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中这样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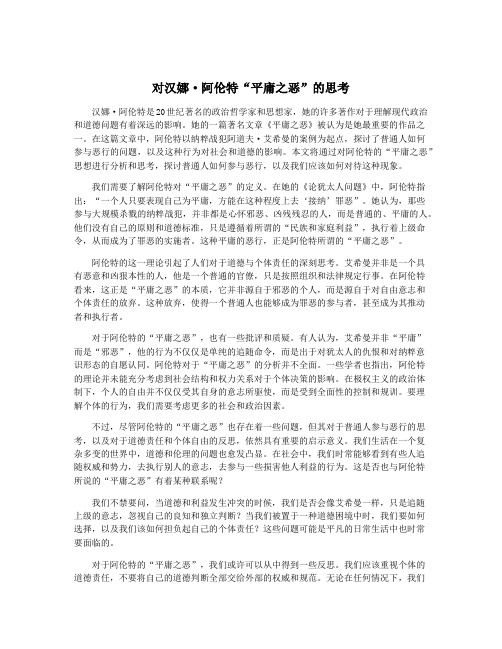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她的许多著作对于理解现代政治和道德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
她的一篇著名文章《平庸之恶》被认为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阿伦特以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案例为起点,探讨了普通人如何参与恶行的问题,以及这种行为对社会和道德的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思想进行分析和思考,探讨普通人如何参与恶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现象。
我们需要了解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定义。
在她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阿伦特指出:“一个人只要表现自己为平庸,方能在这种程度上去‘接纳’罪恶”。
她认为,那些参与大规模杀戮的纳粹战犯,并非都是心怀邪恶、凶残残忍的人,而是普通的、平庸的人。
他们没有自己的原则和道德标准,只是遵循着所谓的“民族和家庭利益”,执行着上级命令,从而成为了罪恶的实施者。
这种平庸的恶行,正是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
阿伦特的这一理论引起了人们对于道德与个体责任的深刻思考。
艾希曼并非是一个具有恶意和凶狠本性的人,他是一个普通的官僚,只是按照组织和法律规定行事。
在阿伦特看来,这正是“平庸之恶”的本质,它并非源自于邪恶的个人,而是源自于对自由意志和个体责任的放弃。
这种放弃,使得一个普通人也能够成为罪恶的参与者,甚至成为其推动者和执行者。
对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也有一些批评和质疑。
有人认为,艾希曼并非“平庸”而是“邪恶”,他的行为不仅仅是单纯的追随命令,而是出于对犹太人的仇恨和对纳粹意识形态的自愿认同。
阿伦特对于“平庸之恶”的分析并不全面。
一些学者也指出,阿伦特的理论并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对于个体决策的影响。
在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下,个人的自由并不仅仅受其自身的意志所驱使,而是受到全面性的控制和规训。
要理解个体的行为,我们需要考虑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
不过,尽管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其对于普通人参与恶行的思考,以及对于道德责任和个体自由的反思,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平庸的恶-素材

平庸的恶艾希曼是个恶名昭彰的纳粹罪犯,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他认为他的一切行为只是在执行命令。
他真诚地信奉着纳粹的思想,坚定地相信领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因此在执行命令时,也是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执行。
在他的心目中,并未将犹太人当作人,而只是杀人机器所需要吞噬的原料。
在他执行任务之时,他已非正常之人,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正常人的情感,而是异化成为一台机器。
他按照体制或者制度的指令,机械而无情地杀死犹太人。
只要这种制度不改,将谁放到那个位置上,都会执行杀人的命令,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
因此艾希曼所犯下的罪愆,并非个人的罪愆,而是制度之罪,是纳粹那种邪恶的思想或者主义带来的罪愆。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她的著名观点,认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极端之恶,而是平庸的恶,是在邪恶体制之下,每个小人物都可能犯下的恶。
艾希曼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从其法庭上的表现来看,他也是一个彬彬有礼之人。
他也不愚蠢,喜欢康德的哲学,并自称以康德哲学来作为自己行事准则。
他为人夫为人父,恪守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在家人的眼里完全可能是个完美的儿子、丈夫或者父亲。
如果将他放到一个正常的社会,他会是个守法的好公民,也许还会是社会的中坚。
不幸的是,他生于乱世,生于一种极其邪恶的制度之下,他没有成为好公民,而是成为了杀人的艾希曼。
而这,正是当时整个德国人的缩影,每个德国人都可能成为艾希曼。
艾希曼这种小人物何以会有着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彻底放弃了思考的权利,以制度之思想代替了自己的思考。
他们完全将自己当成了所服膺制度中的一颗螺丝钉,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与这个制度步调一致,就是让这个制度完美地运转,从不去思考这个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思考这个制度的合理性。
在电影中,汉娜·阿伦特重复了她老师海德格尔的话,思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而只是让我们能够判断善恶与美丑。
最后,她提出,思考能带来力量。
平庸的邪恶

平庸的邪恶
曲柏杰律师
.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阿伦特提出的关于罪恶的一种哲学思考,与独裁者的“极端之恶”不同,平庸的罪恶往往不易被人察觉,更容易被人忽视。
平庸的邪恶,是因平民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
比如中国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号称不关心民主权利,不关心外部世界,不关心人类命运的奴民。
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或是接受当局洗脑,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非大奸大恶。
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它们拒绝思考,它们行尸走肉,它们假装无辜,它们麻木不仁,它们屈膝下跪,它们与鬼立约,它们用沉默纵容暴行,它们是独裁恶政的最忠实拥趸,最坚定盟友,也是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培育的僵尸魂灵。
汉娜·阿伦特《关于平庸的恶》

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后记)本书是一个审判报告,主要资料来源是分发给耶路撒冷媒体的庭审记录的副本。
除了检察方的公诉书以及辩护方的概括否认答辩外,审判记录没有公开出版,也很难找到。
法庭用语为希伯莱语;分发给媒体的材料已被申明“是未经校正和修改的现场同声翻译的记录”,因此“难免会有文体上的缺憾和语言错误。
”除了用德语进行的庭审,我自始至终使用的都是英文文献;当审判中使用德语时,我自认为可以轻松胜任翻译工作。
除了检察长的开庭报告以及最后的判决,其翻译不是现场的同声翻译、而是在庭外准备的外,这些记录中没有一件是绝对可信的。
唯一的权威性版本是官方的希伯莱语记录,而我没有利用。
但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由官方提供给记者供其使用的,而且就我所知,在官方的希伯莱语记录和译本之间,还没有发现严重的出入。
德语的现场同声翻译相当糟糕,但据说英语和法语翻译是可信的。
下面这些庭审材料的可靠性――只有一件除外――均无可置疑,它们也都是由耶路撒冷官方提供给媒体的:1)警察对艾希曼的提审记录。
德语,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曾经给艾希曼看过,他还亲手做过改动。
它和审判记录堪称最重要的档案材料。
2)检察机关提交的档案材料,以及检察机关提供的“合法材料”。
3)16个证人的宣誓证词。
这些证人最初是辩方邀请的,但后来检察机关也部分地采用了他们的证词。
这16个证人是:埃里希·冯·迪姆·巴赫-齐拉维斯基,理查德·贝尔,库尔特·贝歇尔,霍斯特·格雷尔,维廉·霍特尔博士,瓦尔特·豪朋库森,汉斯·尤特纳,赫伯特·卡普勒,赫尔曼·克鲁梅,弗兰茨·诺瓦克,阿尔弗雷德·约瑟夫·斯拉维科,马克斯·默顿博士,阿尔弗雷德·西克斯教授,埃贝哈德·冯·塔登博士,爱德蒙德·法思梅尔博士,奥托·温克尔曼。
【第三讲】平庸的恶

她并不是卷入了和一 个人的纷争,而是卷 入了与整个世界的纷 争。 被从头到脚浇上大雨而没有一把雨伞
O ‚真正伟大的爱情就像文学杰作一样不同寻常。‛
——巴尔扎克
在平时劳动和消费的活动中,人们 仅仅是维持肉体的生存,“被完全扔给 了他自己”从而造成人们互相之间的隔 绝。但在公共空间及其交谈中,大家从 自己的角度发表各自的看法,使得不同 种类的事物、不同视角的观点得以呈现, 这才是生命的一种真正的开放。勇于在 众人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勇于冲破喉 管的气流而“出声”,这样一次又一次 “站出来”的做法才体现了人的尊严。而 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随时准备回应别人 对自己的批评,勇于面对和敢于“接招”, 不把“私下”掌握的真理认定为唯一的真 理。
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 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追寻真理:站出来与接招
O 阿伦特把这样一些意趣不同的人们集合在一起,相当
于小型公共空间的演习。在阿伦特看来,在平时劳动 和消费的活动中,人们仅仅是维持肉体的生存,"被 完全扔给了他自己"从而造成人们互相之间的隔绝。 但在公共空间及其交谈中,大家从自己的角度发表各 自的看法,使得不同种类的事物、不同视角的观点得 以呈现,这才是生命的一种真正的开放。勇于在众人 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勇于冲破喉管的气流而"出声", 这样一次又一次"站出来"的做法才体现了人的尊严。 而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随时准备回应别人对自己的批 评,勇于面对和敢于"接招",不把"私下"掌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平庸之恶的无法抵抗性
O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并且强调专业化的社会,
解读“平庸之恶”

解读“平庸之恶”作者:王楠单棣斌许存岳婷来源:《科教导刊》2017年第07期摘要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把普通人不假思索地服从邪恶命令的行为称为“平庸之恶”,这种行为的存在给社会带来了危机和伤害。
“平庸之恶”从心理学解释是一种消极极端的服从行为,其产生原因可以从“米尔格拉姆实验”中寻求答案,即个体在负面权威的影响下自我意识丧失的一种服从行为。
通过这种分析,可以给我们的社会管理、维稳处突、打击违法犯罪等工作提出有效建议。
关键词服从平庸之恶权威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7.03.067服从是人由于外在强制力或他人影响而做出的遵照、顺从行为。
积极的服从给我们带来了秩序、规则、凝聚力和工作效率。
但是社会行为中也存在一种消极的极端的甚至恐怖的服从,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把这种服从称之为“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
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
1 “平庸之恶”现象2014年3月,昆明火车站广场发生的暴徒砍人事件,造成了29人死亡的惨剧。
暴徒中唯一的女性帕提古丽·托合,在羁押期间已怀有身孕,这样的情况,本应在家享受即将成为母亲的喜悦,应该是最具有爱和温情的角色,却在极端宗教势力的蛊惑下,在上级组织的命令和安排下,将刀砍向无辜的群众,去发动所谓的“圣战”行动。
9·11事件之后,美国心理学家对施行暴行的恐怖分子进行研究之后,深感不安的指出:“那些令人吃惊、引人注目的大多数自杀式恐怖分子几乎都源于普通民众。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普通人变成了恐怖分子呢?如何解释那些极端的宗教信徒心甘情愿地为所谓“纯正伊斯兰国”献出自己的生命并戕害别人的性命呢?恐怕也应该从心理学上寻找内在的原因。
平庸之恶——精选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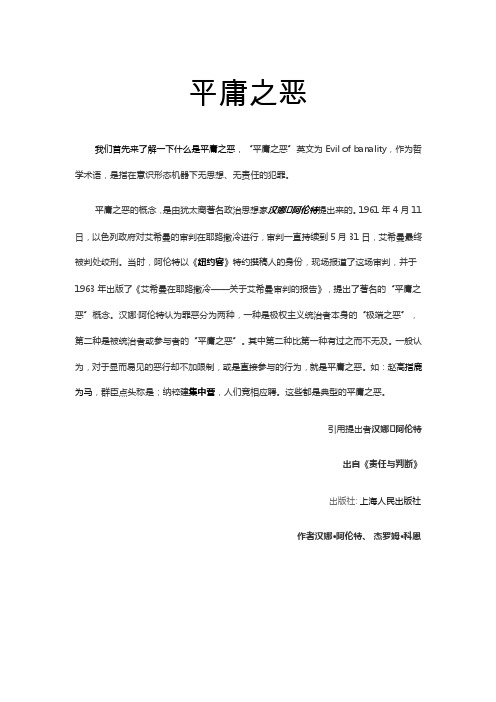
平庸之恶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平庸之恶,“平庸之恶”英文为Evil of banality,作为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平庸之恶的概念,是由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
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艾希曼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一直持续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
当时,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
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
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
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
如:赵高指鹿为马,群臣点头称是;纳粹建集中营,人们竞相应聘。
这些都是典型的平庸之恶。
引用提出者汉娜·阿伦特出自《责任与判断》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作者汉娜•阿伦特、杰罗姆•科恩西方有句谚语:“没有一滴雨会认为是自己造成了洪灾。
”因为雨是造成洪灾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雨就成了那点恶?为什么没人在自身上找找原因呢?如洪水的主要原因主要有山区植被被滥伐,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加剧,河床加深,泄洪能力衰弱等原因。
世纪六十年代,阿伦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组题为《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的系列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富有启示性的观点,即像艾克曼这种组织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具有的只是“平庸的恶”。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艾克曼负责驱逐在德国的犹太人,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以及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吉卜赛人去死亡集中营。
一九四四年三月在德国已经溃败的情况下,艾克曼到了布达佩斯,组织向奥斯威辛的运送。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起,他和他的部下经常每天把一万人送到指定地点。
“神人之恶”与“平庸之恶”

“神人之恶”与“平庸之恶”作者:朱国良来源:《杭州(上半月)》 2014年第8期我们会不明就里,不经意间传播某些可怕的谣言,或天真地相信某些无据的说法。
文朱国良又一个“神医”被揭穿了把戏。
近日的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曝光了杭州红枫园背后的“神医”杨中武团队,不计其数的民众被其骗走了上亿的血汗钱,更有人因为耽误治病而失去生命。
近些年来,一大批“神棍”混迹于迷信和养生之间,靠“ 模糊养生术” 甚至“ 邪恶养生术”发家致富、飞黄腾达。
不妨先梳理一下这类骗术的特征,看看他们究竟有怎样的神通,能屡屡得手。
首先,“神医”大多重视包装,荣誉满墙,亮瞎人眼。
那些名目繁杂、收费不菲的荣誉称号评选,真可谓是“神医”产业的上游,为“神医”行骗作出了不小贡献。
其次,造噱头,给自己搞一个名头来行骗。
除此之外,“神医”还擅长团队作战,一大群托儿假冒病患身份现身说法,制作视频、网站、书籍、杂志。
这年头,隔三差五从犄角旮旯里会冒出个“大师”。
可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些“大师”,而是甘心在这些个“大师”面前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弟子们和热捧者。
其实,连我这个外行都看得出,所谓“神医”明显违背科学规律,他们却装得煞有其事。
有人说,这只是一场熟人之间的游戏。
事情怕是没那么简单。
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这一著名概念。
本意是说,因为扭曲的服从,一味执行上级错误命令,从而犯下罪恶。
制造“平庸的恶”的人,往往平素浅薄,他们自愿放弃独立思考和冷静判断的能力,放弃对抗虚假邪恶的权利,心甘情愿依附于非正义的体系。
一些“大师”的门下弟子,我看就属于一种“平庸的恶”。
他们是一群平庸的人,要么因为无知而可怜,要么因为有意而可恶。
他们不是元凶,只是帮凶,可如果越来越多的公众上当受骗,白花花的银子拱手奉上,“平庸的恶”就可能成为“极端的恶”。
心理学家米尔格朗曾做过一项试验。
他请一群助手们来到一间房子,那里有一名学生被绑在椅子上。
只要答错问题,助手们就要轮流电击学生。
平庸之恶—刘盛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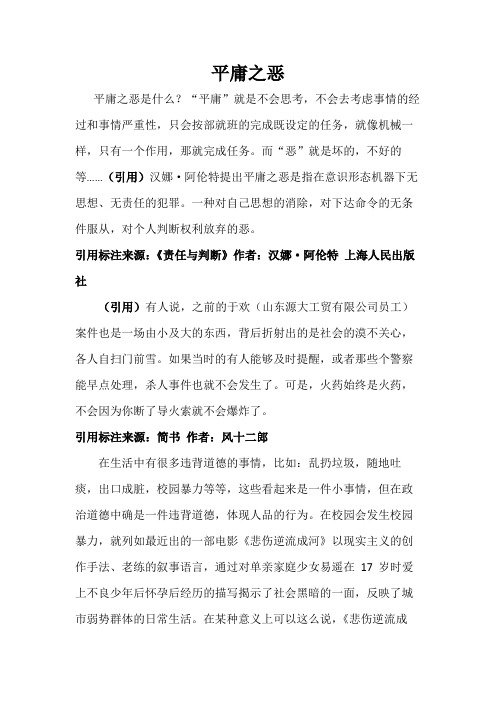
平庸之恶平庸之恶是什么?“平庸”就是不会思考,不会去考虑事情的经过和事情严重性,只会按部就班的完成既设定的任务,就像机械一样,只有一个作用,那就完成任务。
而“恶”就是坏的,不好的等……(引用)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引用标注来源:《责任与判断》作者:汉娜·阿伦特上海人民出版社(引用)有人说,之前的于欢(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员工)案件也是一场由小及大的东西,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的漠不关心,各人自扫门前雪。
如果当时的有人能够及时提醒,或者那些个警察能早点处理,杀人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
可是,火药始终是火药,不会因为你断了导火索就不会爆炸了。
引用标注来源:简书作者:风十二郎在生活中有很多违背道德的事情,比如: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出口成脏,校园暴力等等,这些看起来是一件小事情,但在政治道德中确是一件违背道德,体现人品的行为。
在校园会发生校园暴力,就列如最近出的一部电影《悲伤逆流成河》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老练的叙事语言,通过对单亲家庭少女易遥在17 岁时爱上不良少年后怀孕后经历的描写揭示了社会黑暗的一面,反映了城市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悲伤逆流成河》是一种慢性毒药,是青春文学中的一朵恶之花,它将这么多丑恶的东西以温柔甜蜜伤感忧郁的煽情的方式无形中侵入年轻人的纯洁的灵魂,这绝对是中学生不宜的。
(引用)在旧社会也有很多例子,列如:元朝的《窦娥冤》以弱小寡妇窦娥,在无赖陷害、昏官毒打下,屈打成招,成为杀人凶手,被判斩首示众。
临刑前,满腔悲愤的窦娥许下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
果然,窦娥冤屈感天动地,三桩誓愿一一实现。
这样的故事展示了下层人民任人宰割,有苦无处诉的悲惨处境,控诉了贪官草菅人命的黑暗现实。
这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等之恶,使得社会的大恶出现。
被误读与滥用的概念

被误读与滥用的概念作者:魏英杰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3年第30期阿道夫·艾希曼,第三帝国党卫军中校,负责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兵站指挥官,对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负有重要责任。
1960年,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抓获,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审。
学者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报道这场大审判,并据此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
这本书有着一个极富争议性的副标题: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这个概念,旨在审视艾希曼这类人的行为动机及其作用。
她关心的是,在第三帝国极权体制下,人的良知是如何一步步泯灭的。
这是继阿伦特在《极权主义》中提出“极端的恶”之后所进行的哲学思考。
如今,这一概念已广为人知,成为一个经典论断。
经典即权威,而这有时并不是什么好事。
伴随着“平庸的恶”一词的流传,误读变得越来越难以避免。
在国内,这一术语首先遭遇的是误译。
目力所及,国内各种译作除把这个概念译成“平庸的恶”之外,还有平庸的邪恶、平庸之罪、恶的平庸性、罪恶之肤浅性,以及罪恶的平庸性等多种译法。
不同的译法,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包括误读。
到底哪一种译法更符合阿伦特原意?阿伦特在致犹太学者肖莱姆的信中称: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
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
阿伦特对恶的重新定义,来源于她对艾希曼的近距离观察。
在她看来,艾希曼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并且缺少这种想象力。
他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
这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
但时下有些人,似乎并没有完整地理解阿伦特的上述观点,导致这一概念被不加节制地滥用。
阿伦特当年提出这一概念,针对的是第三帝国这种极权体制,审视的对象是像艾希曼这类背负罪责的纳粹分子。
这其中,“平庸”指的是思考的匮乏,而不是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恶”指的是广义上的邪恶,或者干脆说是助纣为虐式的作恶,而不是一般职务行为或失德言行。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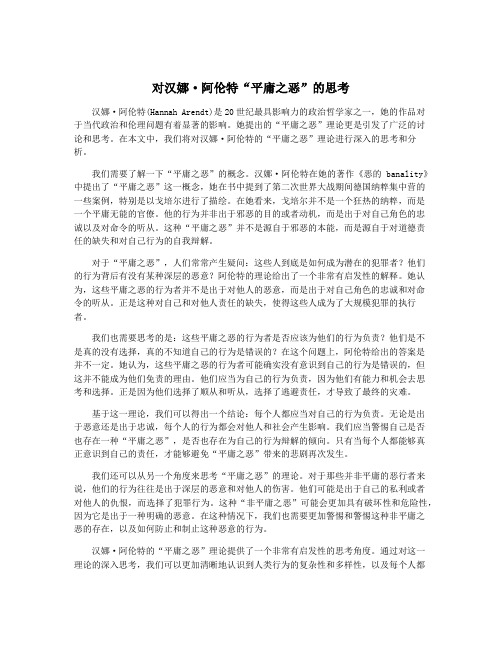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她的作品对于当代政治和伦理问题有着显著的影响。
她提出的“平庸之恶”理论更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在本文中,我们将对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理论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平庸之恶”的概念。
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著作《恶的 banality》中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概念,她在书中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集中营的一些案例,特别是以戈培尔进行了描绘。
在她看来,戈培尔并不是一个狂热的纳粹,而是一个平庸无能的官僚。
他的行为并非出于邪恶的目的或者动机,而是出于对自己角色的忠诚以及对命令的听从。
这种“平庸之恶”并不是源自于邪恶的本能,而是源自于对道德责任的缺失和对自己行为的自我辩解。
对于“平庸之恶”,人们常常产生疑问:这些人到底是如何成为潜在的犯罪者?他们的行为背后有没有某种深层的恶意?阿伦特的理论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解释。
她认为,这些平庸之恶的行为者并不是出于对他人的恶意,而是出于对自己角色的忠诚和对命令的听从。
正是这种对自己和对他人责任的缺失,使得这些人成为了大规模犯罪的执行者。
我们也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平庸之恶的行为者是否应该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选择,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阿伦特给出的答案是并不一定。
她认为,这些平庸之恶的行为者可能确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们免责的理由。
他们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有能力和机会去思考和选择。
正是因为他们选择了顺从和听从,选择了逃避责任,才导致了最终的灾难。
基于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无论是出于恶意还是出于忠诚,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对他人和社会产生影响。
我们应当警惕自己是否也存在一种“平庸之恶”,是否也存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倾向。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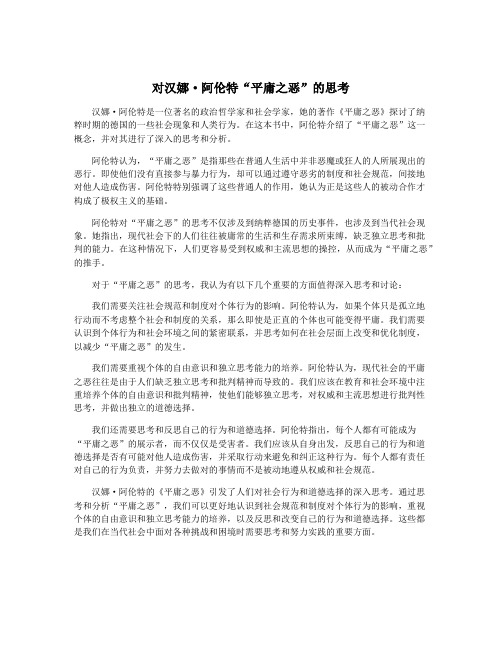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汉娜·阿伦特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她的著作《平庸之恶》探讨了纳粹时期的德国的一些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
在这本书中,阿伦特介绍了“平庸之恶”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是指那些在普通人生活中并非恶魔或狂人的人所展现出的恶行。
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暴力行为,却可以通过遵守恶劣的制度和社会规范,间接地对他人造成伤害。
阿伦特特别强调了这些普通人的作用,她认为正是这些人的被动合作才构成了极权主义的基础。
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思考不仅涉及到纳粹德国的历史事件,也涉及到当代社会现象。
她指出,现代社会下的人们往往被庸常的生活和生存需求所束缚,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受到权威和主流思想的操控,从而成为“平庸之恶”的推手。
对于“平庸之恶”的思考,我认为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方面值得深入思考和讨论:我们需要关注社会规范和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阿伦特认为,如果个体只是孤立地行动而不考虑整个社会和制度的关系,那么即使是正直的个体也可能变得平庸。
我们需要认识到个体行为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思考如何在社会层面上改变和优化制度,以减少“平庸之恶”的发生。
我们需要重视个体的自由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阿伦特认为,现代社会的平庸之恶往往是由于人们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而导致的。
我们应该在教育和社会环境中注重培养个体的自由意识和批判精神,使他们能够独立思考,对权威和主流思想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做出独立的道德选择。
我们还需要思考和反思自己的行为和道德选择。
阿伦特指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平庸之恶”的展示者,而不仅仅是受害者。
我们应该从自身出发,反思自己的行为和道德选择是否有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并采取行动来避免和纠正这种行为。
每个人都有责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努力去做对的事情而不是被动地遵从权威和社会规范。
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引发了人们对社会行为和道德选择的深入思考。
人人都可能是作恶者《被掩埋的巨人》政治哲学解读

Oct. 2020Vol. 23 No. 42020年10月第23卷第4期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Xi 9 an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文学艺术研究】人人都可能是作恶者:《被掩埋的巨人》政治哲学解读高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西安710071)摘要:《被掩埋的巨人》是作家关注局部战争和冲突世界,对人类战争与和平、民族融合与民族仇恨等宏大主题试图做出理性思考,在遥远古代荒蛮大地上展开的文学想象与政治讽喻。
小说情节看似魔幻,却再一次书写个 体命运在战争屠杀面前的无力挣扎与抗争悲剧。
小说文本与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话语互文解读,小说中的高文 徒有骑士之名,既无青春勇武的骑士体格,亦无诚实高贵的骑士品质;只知恪尽职守,愚忠效命,是又一个艾希曼式 的“无思之人”,犯下“平庸的恶”之罪责。
小说讲述一个无关于时代,无关于地域的寓言:人人都可能是作恶者,彰显小说家的个体反思与人文关怀。
关键词:政治寓言;阿伦特;无思;平庸的恶;普通人中图分类号:110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 - 777X(2020)04 - 0026 - 07石黑一雄2015年出版的《被掩埋的巨人》,被 誉为“三十三年文学生涯中最具奇幻、冒险色彩并 极富雄心壮志的一本书”⑴。
小说出乎意料地选取 后亚瑟王时代的英格兰,人住在地下洞穴、受食人兽威胁、被精灵女巫迷惑、为果腹之食与栖身之所而抗争。
小说主人公是一对年老的不列颠夫妇:艾 克索(Axl)和比特丽丝(Beatrice ),他们同村庄里其他人一样,患上了失忆症,隐约感觉曾有个儿子,踏上寻子之路。
路途艰难跋涉,他们先后遇到撒克逊 骑士维斯坦(Wistan)、小男孩埃德温(Edwin)和暮 年骑士高文(Gawain),并逐渐发现失忆与恶龙魁瑞格(Querig)有关。
不列颠人曾在亚瑟王领导下征服 了包括撒克逊在内的众多部落与村镇,实行血腥屠杀,并得梅林法师相助,差遣骑士驯服恶龙吐雾以 蒙蔽记忆。
关于学会独立思考为题的议论文五篇精选

关于学会独立思考为题的议论文五篇精选议论文,又叫说理文,是一种剖析事物,论述事理,发表意见,提出主张的文体。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学会独立思考为题的议论文五篇精选相关模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关于学会独立思考为题的议论文五篇精选(一)可以确定地说,思考乃是人的天赋。
因为人们只要悉心搜索自己童年的印记,往往都会有这样一个原创的提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个很容易却又很难回答的问题,于是对此问题,大人的回答也就往往大同小异,或者说“你是从妈妈的胳肢窝里来的”,或者说“你是从妈妈的屁股里出来的”。
这些带点旁敲侧击或者敷衍了事的的回答,童年的人们则是似懂非懂却认认真真地记下来,直到他们成人,在时间中体会那种荒唐。
这里的发问,即是思考,当然它还仅是萌芽阶段的思考。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头脑”逐渐在科学的意义上成熟,思考反而消失了。
常规一点的,自由自在地长到四五岁,进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望断秋水,只为一个理想,一个未经验证的理想,也就是说未曾成熟思考过的未来。
大学出来,关进单位,又十有八九发出“理想在哪里”的感叹,工作,无非“为稻粱谋”而已。
非常规一点的,读到半路,甩手不干了,去寻找各种各样生活的路,但究其根本,也无非是跟着别人,去求得钱途而已。
大家殊途同归,一样地,被动地生活。
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思考似已变得毫无必要。
中国人是世界是网民最多的国家,2006年网民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地成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中国网民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的。
中国网民光顾最多的网站是哪一个?百度搜索。
搜索好啊,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找游戏,问百度;找论文,问百度;传情意,上百度……搜索已成为一种生活。
而在搜索引擎逐渐强大的同时,是思考的日益衰弱,人们都在寻找答案,不是从自己这里,而是从别人那里;小到日常生活问题,大到人生理念的构设。
“我思故我在”,人们在反复引用这句名言的同时抛开了思考。
但是既然我们的大脑已经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已经失去了个体生命的尊严,又何妨爽爽快快地把生命的代理权交给世界上的某一个人?这人们似乎又并不愿意。
平庸之恶无罪三辩稿范文

平庸之恶无罪三辩稿范文英文回答:In the depths of dark, tortuous alleys and interwoven paths, lies the murky shadows of complacency, where the insidious evils of banality lurk. This phenomenon, aptly termed "the banality of evil," unfolds when individuals, ensnared in the labyrinthine web of conformity and bureaucratic machinery, commit heinous acts, often in the name of "duty" or "obedience." They become mere cogs in a soulless system, their humanity eclipsed by a chilling indifference and mindless adherence to orders.Hannah Arendt, the enigmatic philosopher, coined this term in her seminal work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disquieting account of the trial of the Nazi war criminal, Adolf Eichmann. Arendt, through her rigorous analysis, sought to unravel the psyche of those who, like Eichmann, willingly participated in the Holocaust. She argued that they were not necessarily malicious or driven bypathological hatred, but rather ensnared in the seductive embrace of banality.Arendt's thesis has garnered profound resonance not only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Holocaust but also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the annals of history, we bear witness to countless examples of individuals committing heinous acts, driven not by malice, but by the allure of conformity and the allure of obeying authority. The infamous Milgram experiment, conducted by the social psychologist Stanley Milgram, serves as a poignant illustration. In this paradigm, participants willingly administered what they believed to be painful electric shocks to an unseen individual simply because they were instructed to do so by an authority figure.This disturbing experiment underscores the profound power of authority and the insidious pull of conformity. In its wake, we are left to grapple with the unsettling truth that ordinary individuals, in the grip of banality, are capable of perpetrating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vils.中文回答:平庸之恶无罪三辩稿。
高考作文理论素材积累之平庸之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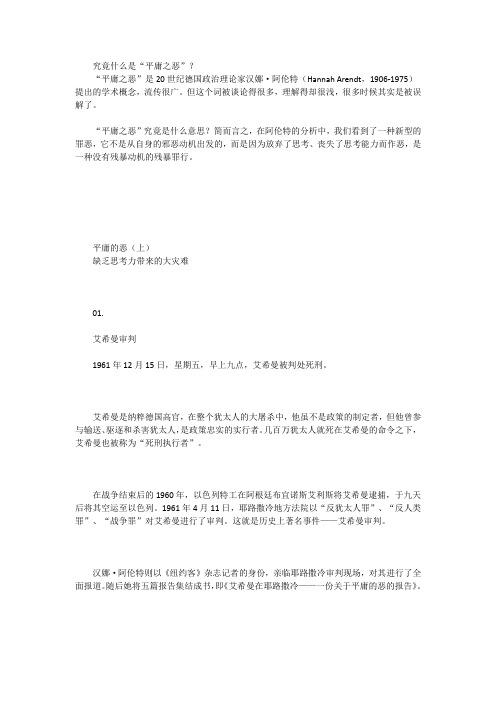
究竟什么是“平庸之恶”?“平庸之恶”是20世纪德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提出的学术概念,流传很广。
但这个词被谈论得很多,理解得却很浅,很多时候其实是被误解了。
“平庸之恶”究竟是什么意思?简而言之,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平庸的恶(上)缺乏思考力带来的大灾难01.艾希曼审判1961年12月15日,星期五,早上九点,艾希曼被判处死刑。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高官,在整个犹太人的大屠杀中,他虽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但他曾参与输送、驱逐和杀害犹太人,是政策忠实的实行者。
几百万犹太人就死在艾希曼的命令之下,艾希曼也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在战争结束后的1960年,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将艾希曼逮捕,于九天后将其空运至以色列。
1961年4月11日,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以“反犹太人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对艾希曼进行了审判。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事件——艾希曼审判。
汉娜·阿伦特则以《纽约客》杂志记者的身份,亲临耶路撒冷审判现场,对其进行了全面报道。
随后她将五篇报告集结成书,即《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通过这次审判,阿伦特对“恶”的问题有了全新视角的思考,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恶”的理论。
也因为这本书的出版,使阿伦特陷入巨大的争议,以至于在后期她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捍卫自己的立场。
在阿伦特看来,“平庸的恶”具有着双重指向:一方面是指艾希曼身上的“不思考”性;另一方面是指犹太人自身的“不思考”性,犹太人要为自身的命运承担着责任。
02.艾希曼的“平庸的恶”如前面所述,在集中营和灭绝营里,纳粹分子对犹太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气氛恐怖至极。
或许大多数人会认为,作为纳粹负责人的艾希曼一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魔鬼,是绝对极端的冷血者。
汉娜·阿伦特对“平庸的恶”的哲学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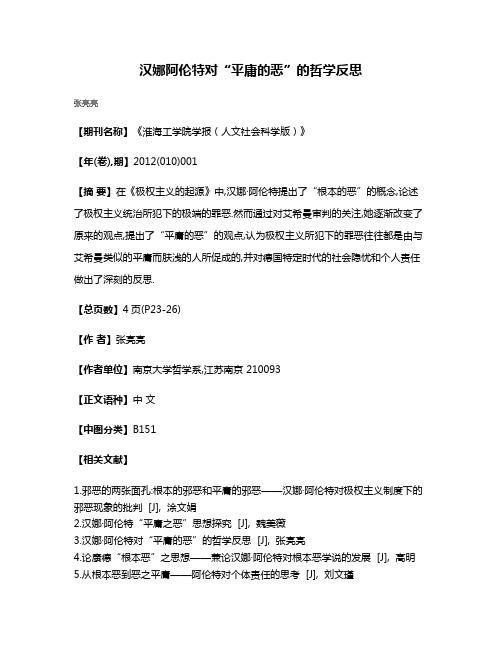
汉娜阿伦特对“平庸的恶”的哲学反思
张亮亮
【期刊名称】《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10)001
【摘要】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根本的恶”的概念,论述了极权主义统治所犯下的极端的罪恶.然而通过对艾希曼审判的关注,她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观点,认为极权主义所犯下的罪恶往往都是由与艾希曼类似的平庸而肤浅的人所促成的,并对德国特定时代的社会隐忧和个人责任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总页数】4页(P23-26)
【作者】张亮亮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151
【相关文献】
1.邪恶的两张面孔:根本的邪恶和平庸的邪恶——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制度下的邪恶现象的批判 [J], 涂文娟
2.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思想探究 [J], 魏美薇
3.汉娜·阿伦特对“平庸的恶”的哲学反思 [J], 张亮亮
4.论康德“根本恶”之思想——兼论汉娜·阿伦特对根本恶学说的发展 [J], 高明
5.从根本恶到恶之平庸——阿伦特对个体责任的思考 [J], 刘文瑾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平庸的邪恶”与“盲从的犯罪”——关于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正当性”的思考卢建平[摘要] 汉娜•阿伦特将纳粹战犯艾希曼的罪恶定义为“平庸的邪恶”,这一论断为当今国际刑法中“上级命令不免除责任”的原则确立了法理基础,也为现代各国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正当性”思考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涵义。
对于“盲从的犯罪”进行追究,是建设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平庸的邪恶;法令行为;正当性Abstract:The Banality of Evil put forward by Hannah Arendt to analyse the behavior of Adolf Eichman under the Totalitarian Regime can also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to the principl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some actions ordered by laws or legitimate authorities in criminal matters.Key Words:banality of evil;superior orders;legitimacy一、阿道夫•艾希曼案件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又译艾克曼,1906-1962)是纳粹德国战争罪犯,1932年加入党卫军,曾先后在党卫军保安处柏林总部和奥地利、捷克等国任职,主管犹太人事务,1939年起在德国中央保安局犹太处工作。
1942年1月,德国决定对犹太人实施“最后解决”计划,即以大规模屠杀的方式消灭犹太人,而艾希曼被指定负责执行这一造成数百万犹太人死亡的计划。
德国战败后,艾希曼被美军俘虏,并被关在战俘营里,但他的真实身份并没有暴露。
1946年初,他逃出战俘营,在汉堡以南的一个地方当了4 年伐木工人。
1950年5月,在原纳粹党卫队成员的帮助下,艾希曼经奥地利逃往意大利,并于同年7月从意大利逃往阿根廷。
在阿根廷,他化名里卡多•克莱蒙特(Ricardo Klement),取得了身份证件和工作许可证。
1952年,艾希曼的妻子及其3个孩子也来到阿根廷与他会合。
同年,他在梅塞德斯—奔驰汽车公司在阿根廷的一个工厂得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色列政府和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在到处寻找艾希曼的下落,以便将他绳之以法。
后来,以色列情报部门终于侦察到他化名藏匿在阿根廷的确切消息。
1960年5月11日晚,艾希曼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被绑架,同年5月20日,他被伪装成一位生病的以色列政府官员,用飞机送回了以色列。
以色列总检察长指控艾希曼犯有战争罪、反犹太人罪和反人道罪,以及参加犯罪组织罪等15项罪行,并向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提出起诉。
艾希曼被指控的具体罪行包括:杀害数百万犹太人;使数百万犹太人置于可能死亡的状态下;使犹太人的生理和心理遭受严重伤害;禁止和干扰犹太妇女怀孕和生育;基于种族、宗教和政治理由迫害犹太人;与屠杀有关的对犹太人财产的抢劫;强迫数十万波兰人离开家园;从南斯拉夫驱逐1,4万名斯洛文尼亚人;将数以万计的吉普赛人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参加党卫队和国家秘密警察组织,等等。
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于1961年4月11日开庭审理此案。
艾希曼首先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
他认为,第一,以色列检察机关指控他的罪行是在以色列成立之前,在该国领域以外所犯的,而且受害人也不是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法院对这种行为没有管辖权。
第二,对他进行绑架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对于被以非法方式带到法院的被告人,法院不能对他进行审判和处罚。
第三,他在战争期间的行为是代表国家实施的,属于国家行为,根据国际法,一国法院对外国的国家行为不能行使管辖权。
第四,对于被指控的犯罪,他认为他只是负有“协助和唆使”的责任,他只是一个奉命行事的执行者,而从未实施过任何具体的犯罪行为。
“我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恶魔,而是错误舆论的受害者” 。
对于艾希曼的辩解,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一一予以驳斥。
1961年12月11日,法院对于艾希曼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裁定被告的15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处被告死刑。
艾希曼不服判决,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1962年5月29日,最高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同日,艾希曼向以色列总统本-茨维提出赦免的请求。
同年5月31日,本-茨维总统驳回艾希曼的请求。
几小时后,艾希曼被执行死刑。
艾希曼案件因为其中的管辖权争议、对犯罪嫌疑人的非法逮捕(绑架)的事实等引起国际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国际法学或国际刑法学上的著名案例。
然而,法学界所津津乐道的多是法律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如实体法上的管辖权问题、程序法上的公正问题等,这无疑限制了案件讨论的意义。
对于艾希曼所犯罪行的性质、他为什么会犯这样的罪行、时隔这么多年再来审判艾希曼等会有什么样的意义的探讨,似乎已经超出了法学家的研究范围。
不过,当代著名女性思想家、当时任美国《纽约客》杂志记者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从她特有的视角撰写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赋予这场讨论以全然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对当今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
汉娜•阿伦特在该书中提出的“平庸的邪恶”的观点不仅仅是现代政治哲学中的真知灼见,也使人们对艾希曼的第三、第四个辩解理由(“代表国家的行为”与“奉命行事”)给予高度重视,对于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正当性”思考给予了新的启示。
二、汉娜•阿伦特关于“平庸的邪恶”汉娜•阿伦特在二战期间饱受极权专制之苦,为此,从二战结束一直到1975年去世,她始终在思考的就是极权专制的邪恶问题。
五十年代初期她出版了《极权主义之源》一书,将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等极权专制界定为“激进的邪恶”。
激进的邪恶是极端的邪恶,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原创的邪恶。
纳粹统治下的灭犹行动,斯大林统治下的集中营,是激进邪恶的最集中体现。
在阿伦特看来,极权邪恶是对人类的犯罪。
那么这种对人类的犯罪又是什么样的人在具体执行的呢?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阿伦特即向美国洛克菲乐基金会申请,要求以《纽约客》杂志记者的身份前往见证。
她在信中写道:“你会理解我为什么要报道这次审判;我没能亲眼见证纽伦堡审判,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些人活生生的是什么样子,这也许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在被告人玻璃亭里的艾希曼,是一个看上去彬彬有礼的绅士;他在种族屠杀中犯下弥天大罪,而他的动机却是极其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忠于职守。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邪恶不在于他犯下了普通的罪行,而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极权统治将人变为多余的“伟大事业”,并毫无保留地将体现这种伟大事业的法规当作最高的道德命令。
从根本上说,他所体现的邪恶平庸指的是无思想,甚至无动机地按照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的和法律的责任。
邪恶的艾希曼并不是另一世界中的“妖魔鬼怪”,而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中的熟悉人物。
正如凯诺文(Margret Canovan)所说的,“要表述那种在极权主义非人力量面前的自暴自弃和自我矮化为二脚动物,实在没有比‘平庸’二字更确切的了”。
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是一个纳粹制度中人,也是一个纳粹制度的运作者。
他成为邪恶的化身,不是因为他具有什么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理想或思想能力;恰恰相反,他在邪恶当道时为虎作伥,是因为他失去了判断是非的思维能力。
不是原罪形式的人本性恶或人本质恶使人和社会陷入大恶。
使人陷入专制之恶的是人自己的不思想,人自己的丧失道德判断能力和各种形式的逃避政治责任。
在极权体制中的各层次的体制运作者,上至各级首长,下到普通成员,无不以执行上级决定、命令为最高行为规范。
在这个体制中,邪恶不是每个运作成员个人邪恶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自上而下、自动丧失“政治责任”的集体之恶。
“平庸的邪恶”对于解说极权政治体制的形成、发展乃至衰亡都是极其精辟的。
正是因为有了无数个艾希曼式的“平庸的邪恶”,所以也才酿造出了希特勒的“激进的邪恶”;而又是希特勒的“激进的邪恶”引发了艾希曼式的“平庸的邪恶”。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艾希曼的辩解同样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的“盲从”仍然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一种典型的“搭便车”的行为。
因此,极权体制的集体之恶并不能勾销平庸之辈的个别之恶,“元凶”的责任要追究,但是“帮凶”也不能放过。
这正是国际刑法中“上级命令不免除责任原则”得以确立的法理基础。
三、国际刑法中的“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艾希曼受到指控的罪名是国际犯罪,也即严重侵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或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是侵犯和伤害人类,因而阿伦特认为,应该给艾希曼定罪的不仅是遭受苦难的犹太人,而是全人类。
人类历史上的国际刑事审判正是建立在对上述价值或利益的共识基础之上的。
这种共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显然是模糊的,因为那时连最权威的国际法学者如奥本海都认为,“只有在没有政府命令的情况下实施的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方可构成战争罪行。
如果武装部队成员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是遵照政府命令实施的,他们就不是战争罪犯,也不能由其敌人予以惩罚……” 上级命令是合法的辩护理由。
然而1945年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8条规定,“被告是遵照其政府或长官之命令而行动之事实,不能使其免除责任;但为法庭认为合于正义之要求时,将于刑罚之减轻上加以考虑。
”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认为,任何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人,无论其罪行是否根据上级命令所犯的,都应被视为战犯而受到审判。
但对于因服从上级命令而犯有罪行的人,法庭在量刑时应该结合执行命令者的地位层次考虑该人如果违抗命令可能产生的危险,该人是否存在不执行命令的道德选择。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实践表明,上级命令不免除责任的原则基本上得到了正确的适用。
一方面,主要的战争罪犯没有能够以执行上级命令的理由逃脱其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一般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也没有由于执行上级命令参加侵略战争而普遍地受到起诉和惩罚。
纽伦堡审判结束以后,上级命令不免除责任原则在国际刑法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确立起来。
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纽伦堡原则》第4项明确指出:“依照政府或其上级命令行事的人,如果他能够进行道德选择,不能免除其国际法上的责任。
”1993年《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7条第4款和1994年《联合国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6条第4款分别规定,被告人执行政府或上级命令而犯罪,不得免除其刑事责任,但如果法庭认为考虑上级命令的理由符合正义原则,可以斟酌减刑。
1996年《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法典草案》第5条也作了相同的规定。
1998年在罗马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33条就“上级命令和法律规定”作了如下规定:銆€“(一)某人奉政府命令或军职或文职上级命令行事而实施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事实,并不免除该人的刑事责任,但下列情况除外:1、该人有服从有关政府或上级命令的法律义务;2、该人不知道命令为不法的;和3、命令的不法性不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