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自尼采以来的存在意识的递嬗
尼采的哲学思想的论文

尼采的哲学思想的论文尼采是德国哲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他的很多哲学观点在教育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践行。
以下是店铺精心整理的尼采的哲学思想的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尼采的哲学思想的论文篇一略论尼采的历史哲学思想摘要:尼采认为历史的价值在于促进现实的个体生命的成长,人需要历史,但过量的历史会损害生活。
历史对于三种人是必需的,同时历史也有三种形式。
后期,尼采提出了永恒轮回的思想,认为世界历史就是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
在个人的历史作用的问题上,尼采鼓吹杰出个人的作用。
尼采的历史观主要涉及历史评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价值论。
关键词:历史;永恒轮回;非历史的;超历史的本文浅析尼采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哲学。
他毕生关注历史问题,以历史意识的现实性所据有的生活意义为对象,将目光放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上,自觉地投身到他所要把握的某一历史瞬间中去,以便了解在今天什么才是关键所在。
尼采早期的历史哲学思想集中于《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一书中,主要讨论历史的价值和无价值的问题,即历史价值的标准问题。
贯穿于其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历史不是一种纯知识、纯科学,历史也不是一概给人以力量的教育因素;历史应服务于生活;只有从生命的视角才能追问历史的价值和无价值,只有已经懂得生活并为自己的行动做好充分准备的人才需要历史。
因此,历史是为了生活、行动和为生命服务的愿望,而不是知识欲。
研究历史如果过分尊重历史,以至使生命、生活萎缩退化,那便颠倒了生命与历史的关系,二者之间,生命是目的,历史是手段,历史是为生命、生活服务的,而不是相反。
尼采判断历史利弊的标准很明确,那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现实的个体生命的成长。
在这一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尼采认为人不仅仅是吃、喝、拉、撒、睡,夜以继日,日复一日,同时还“忙于他们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1]。
与没有历史的动物相比,人总要追溯自己的过去,“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留恋过去”[2]。
20世纪德国尼采传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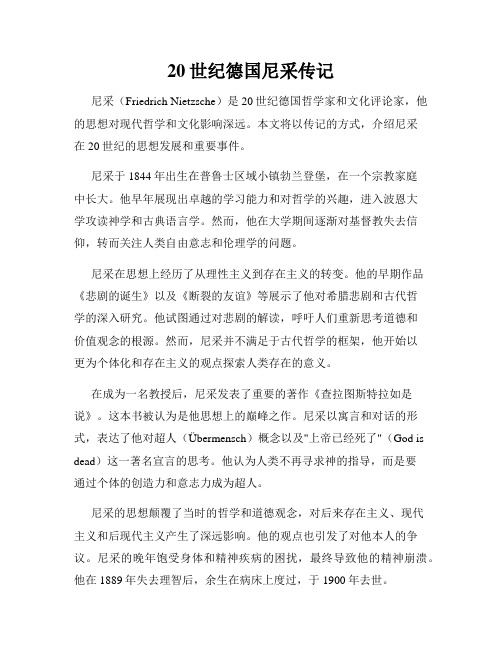
20世纪德国尼采传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是20世纪德国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他的思想对现代哲学和文化影响深远。
本文将以传记的方式,介绍尼采在20世纪的思想发展和重要事件。
尼采于1844年出生在普鲁士区域小镇勃兰登堡,在一个宗教家庭中长大。
他早年展现出卓越的学习能力和对哲学的兴趣,进入波恩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语言学。
然而,他在大学期间逐渐对基督教失去信仰,转而关注人类自由意志和伦理学的问题。
尼采在思想上经历了从理性主义到存在主义的转变。
他的早期作品《悲剧的诞生》以及《断裂的友谊》等展示了他对希腊悲剧和古代哲学的深入研究。
他试图通过对悲剧的解读,呼吁人们重新思考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根源。
然而,尼采并不满足于古代哲学的框架,他开始以更为个体化和存在主义的观点探索人类存在的意义。
在成为一名教授后,尼采发表了重要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这本书被认为是他思想上的巅峰之作。
尼采以寓言和对话的形式,表达了他对超人(Übermensch)概念以及"上帝已经死了"(God is dead)这一著名宣言的思考。
他认为人类不再寻求神的指导,而是要通过个体的创造力和意志力成为超人。
尼采的思想颠覆了当时的哲学和道德观念,对后来存在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的观点也引发了对他本人的争议。
尼采的晚年饱受身体和精神疾病的困扰,最终导致他的精神崩溃。
他在1889年失去理智后,余生在病床上度过,于1900年去世。
尼采的作品成为哲学和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
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尽管在生前他并不被广泛接受,但他在20世纪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在学术界和社会中被重新评价和接纳。
总结起来,尼采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对哲学、存在主义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尽管他的思想在当时并不被广泛接受,但他的作品在后世得到了许多学者和思想家的重视。
浅谈尼采

浅谈尼采20世纪西方美学的源头实际上是尼采。
他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他颠覆传统,杀死了上帝,一个孤独的哲人以及一个漂泊的诗人。
理性精神在他的哲学中是被唾弃与斗争的对象,他眼中闪耀着的是强大而深刻的意志之光。
他以他热情与真诚的态度,在人生的道路上切身地探索着,伴随着鲜血淋漓的伤痛,直到身心俱损,对至高无上之精神的追求从未停止过脚步。
以往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曾像他一样如此贴近生命的本真,他为人类非理性主义开创了新纪元。
在他后面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都是站在了他宽厚而强韧的肩膀上。
他是个恶魔,而却又是个真实的血肉之躯。
尼采出生于1844年10月15日,1947年7月,尼采的父亲死于脑软化症。
数月后,年仅2岁的弟弟又夭折。
当时尼采才5岁,亲人接连的死亡,使这个天性敏感的孩子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阴暗面,铸成了他忧郁内倾的性格。
后来他自己回忆说:“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
这往往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殿堂里,我在那里找到了真实的快乐。
”父亲死后第二年,尼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瑙姆堡,从此便生长在一个完全女性的家庭里。
正因为如此,他对生命的感悟更加透彻和深刻,加上其天生喜欢思索的性格,造就了他非同一般的人生经历。
尼采孤僻敏感,与现实格格不入,他虚构了一个理想的世界。
“飞向未来,飞得太远,恐惧抓住了我,……只有时间与我同行……”“人类的话进不了我的耳朵。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他认为最为重要的著作,“距人和世界的彼岸六千英尺”“这是我对人类的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财产”。
尼采仿佛高高地俯视着现实世界的种种,这个自大自恋且如此智慧的哲学家,带给人类的确是前所未有的颠覆与震撼。
在精神寄生虫们依附于苏格拉底等古代大师的十九世纪,尼采却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学说表示异议,这当然是需要超群的勇气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西方世界,尼采发现基督教约束了人性,腐蚀了人心,因此他重估一切价值,不仅对基督都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斥之为“最要命、最蛊惑人心的谎言”,而且还发出惊天动地之语:“上帝死了!”无疑这需要更加非凡的勇气。
尼采的思想 [试论尼采的永恒轮回思想]
![尼采的思想 [试论尼采的永恒轮回思想]](https://img.taocdn.com/s3/m/ca601f2df61fb7360a4c657a.png)
《尼采的思想 [试论尼采的永恒轮回思想]》摘要:在尼采的众多思想中,永恒循环思想是最受争议的,多数学者都把其与“宗教轮回”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我们更易于从中不难解读出永恒轮回思想另一的思想渊源,东方神话中的凤凰在浴火中重生的典故给予了尼采以强烈的灵感,凤凰是东方神话中的一种神鸟,是人世间的一种幸福之鸟,佛经中称之为迦留罗,永恒轮回思想在尼采的多种著述中均有叙述,本文仅以《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一文为例,来简要的阐述下尼采是怎么样表达这个思想的,以及这个思想的主要内容,永恒轮回思想不是尼采众多思想中的一个孤立的思想,它与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学说、价值重估思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永恒轮回思想的提出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世纪的神学宗教思想及古希腊的传统流变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表达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新的诉求,永恒轮回在尼采看来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万物均在轮回,轮回是不可否定的本文在简要阐述永恒轮回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及传统哲学、宗教神学等思想影响的的基础上,简单地介绍了其思想的渊源。
同时并以查拉斯图特拉与侏儒的对话为例,尝试性地为读者解读了尼采永恒轮回思想的形成脉络。
永恒轮回思想的提出,突出表达了尼采肯定轮回、热爱现实生活、反对虚无主义的精神理念。
一、永恒轮回的思想渊源(一)时代背景任何思想的来源无不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深深的联系在一起,没有哪一个思想来自作者的偶发奇想,无不深深的打上时代的烙印。
弗里德利希・威尔海姆・尼采,(1844―1890)生活于19世纪中晚期,当时正是自然科学兴盛的时期,人们深受自然科学领域三大发现的影响,哲学这门古老的学问更难逃其宿命。
尼采直接把能量守恒定律作为其永恒轮回思想的依据,尼采认为,权利意志其总量是恒定的,它不会永远停滞于某一状态中,除了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以外,别无它物。
“你们知道‘世界’在我看来是什么吗?我可以在我的镜子里把它指给你们看吗?世界就是:一种巨大无匹的力量,无始无终;一种常驻不变的力量,永不变大变小,永不消耗,只是流转易形,而总量不变;……一个奔腾泛滥的力量的海洋,永远在流转易形,永远在回流,无穷岁月的回流,以各种形态朝汐相间,从最简单的涌向最复杂的,从最净的、最硬的、最冷的涌向最烫的、最野的、最自相矛盾的,然后再从丰盛回到简单,从矛盾的纠缠回到单一的愉悦,在这种万化如一、千古不移的状态中肯定自己,祝福自己是永远必定回来的东西。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对人类存在和道德的思考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对人类存在和道德的思考引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创作的一部重要著作。
本文将探讨尼采在这本书中对人类存在和道德的思考。
人类存在的超越与自我解放尼采认为,人类应该超越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束缚,追求个体的自由和解放。
他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超越现有文化、偏见和权威,发现自身真正的潜能。
•尔斯谟主义:尼采提出了"尔斯谟主义"(Ubermensch)的概念,指代一个能够超越常规道德标准、创造自己价值观念的新型人类。
•"上帝已死":尼采宣称上帝已经死去,并呼吁人们摆脱依赖神权和宗教,找到自己生命意义与幸福感的来源。
道德与善恶观念尼采对传统道德观念持批判态度。
他认为传统道德标准是由强者为了控制弱者而制定的,遵守这些道德准则只会导致个体的虚假与拘束。
•主奴道德:尼采将传统道德分为"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
主人道德是基于力量与优秀的评判标准,而奴隶道德是以温良、谦逊和服从为原则。
•重新定义善恶:尼采认为善恶不应被绝对化地定义,而是因人而异。
他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自行确定自己的价值观念,并活出真我。
静默超越与永劫回归尼采认为超越传统价值观念需要静默和内省,以及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反思。
•静默超越:尼采相信通过内心沉思和自我发现,个体可以达到一种超越常规思维的境界,并实现自我的解放。
•永劫回归:尼采提出了"永劫回归"(Eternal Return)的概念,意味着每一个历史瞬间都会无限重复。
他认为只有接受历史的无常与重复,才能真正超越宿命和拥抱生命。
结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展示了尼采对人类存在与道德的独特思考。
他主张个体应该超越传统标准,通过自我解放和重新定义善恶来创造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价值观念。
同时,超越需要个体的静默超越和对历史的回归接纳。
尼采的这些思想仍然对现代世界有着深远影响,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
尼采哲学思想内涵浅析论文(共3篇)

尼采哲学思想内涵浅析论文(共3篇)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第1篇:尼采哲学思想浅析一、叔本华及尼采尼采所处的时代人们高扬理性关注物质生活,认为理性和科学技术能给人带来终极幸福。
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在遇到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之后开始瓦解,叔本华将世界本质看做是生命意志,每个个体都被生命意志支配,个体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整个生命受伟大的生命意志的控制,于是摆脱生命意志枷锁唯一的出路就是结束生命。
叔本华自身的学术观点不够彻底,但是深受叔本华思想影响的中国清代学者王国维就以亲身经历贯彻了叔本华的思想,他自杀了。
尼采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其整个哲学思想的基调也是悲观的,但是他称自己的哲学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尼采将虚无主义分为两类,即积极的虚无主义和消极的虚无主义。
缥缈消极的虚无主义是现代人在否认一切价值观念之后表现出的一种无所适从和自我沉沦的状态,一切旧传统价值遭到否认之后处于彻底的价值虚空之中,丧失信仰无人管束做什么都可以的失控儿童。
而积极的虚无主义则是指在批判一切传统价值之后重新建立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重塑现代人的价值观,在对一切旧价值感到失望之时,身处绝境却不自暴自弃,起身反抗从而克服虚无主义,这种反抗精神在尼采思想中就表现为高扬生命活力的酒神精神和权利意志。
其积极的虚无主义使他认识到生命本身的悲剧性质,即能够自由运用理性思索整个宇宙的人生命却是有限的,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宇宙之间的张力使人必须承认自身的悲剧性。
但同时,在认识到个人是被伟大的生命意志所控制之后,应该勇敢地面对悲剧的人生,用顽强的生命力来战胜掌控一切的生命意志,这也就是尼采与叔本华最大的区别所在。
二、尼采对理性的批判尼采对理性批判的靶子首先对准的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他强烈地批判苏格拉底以来欧洲历史上的理性主义。
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这句话成为后世理性主义的开端,这里知识就是理性的代表,苏格拉底认为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对外部世界和内在心灵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最终才能得出对人类有用的知识。
浅谈对尼采及其思想的主观认识

浅谈对尼采及其思想的主观认识梅源2016440148一、尼采对于现代思想的影响为便于快速理解尼采,首先,我们先简述一下尼采对于现代思想的影响,这样也会对以下的内容有宏观的把控。
尼采对于现代思想的一般影响主要表现在一下几方面:(一)尼采从基督教信仰的崩溃,提出“上帝已死”的事实,站在人的个性、可能性和可塑性的立场上,推导出传统价值应当被重新估计的结论。
(二)尼采揭露了传统文明的弊病,强调自我意识的重要性。
(三)尼采揭示出科学的非理性来源和具有局限性的事实,明确的提出人的心理存在无意识领域。
(四)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创始人之一,他强调哲学中探求人生意义的重要性。
二、尼采与理性主义哲学回顾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哲学思考的重心经历了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移。
泰勒斯以世界的始基是水的命题开始了最早的哲学探讨,以此揭开人类哲学本体论的篇章。
现代西方哲学对于人的研究主要由两方面开展。
一方面是由马克思所开辟的宏观社会学,重点揭示人的实践本性;另一方面是尼采所开辟的微观心理学,重点揭示个体的人的非理性本性。
在尼采看来,19世纪末哲学的堕落,莫过于依附权势,迎合民众的迷信。
而尼采(原名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作为一个哲学家,对此事嗤之以鼻的,他认为,哲学家必须是精神上的强者。
精神的强者出于内在的丰满和强盛,与一切相嬉戏,玩弄至今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藐视至高无上者。
1因此,尼采备受争议,普遍认为他是极端的唯心主义者,这背离近代理性唯物主义。
但是随着哲学的发展,近代理性主义也受到批判。
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于近代理性主义的批判,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性主义立场的本质在于把逻辑思维提升到至高地位,而逻辑思维不过是人与外界联系的一种工具。
这样,理性主义的统治下,把人类生存的意义归结为依靠工具掌握和支配外部世界,迷信科学、热衷知识,从而忽视内心生活。
第二,理性主义假定世界具有逻辑本性,倘若并非如此,理性主义就把它视为虚假的现象世界,而断定其背后还有一个真实的本体世界。
《尼采》的读后感范文

《尼采》的读后感《尼采》的读后感范文当细细品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想,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
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尼采》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尼采》的读后感1尼采(1844-1900),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的生命已经俨然站立在二十世纪的地平线上;而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尼采是最不能忽略的人物,同时也是最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由于观点与立场的不同,人们对其毁誉不一,对他的思想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仅如此,尼采的思想由于采取了独特、强劲、充满隐喻和矛盾,甚至是“疯癫”的独白形式,因此常常遭到误解,以至于波达赫说,“尼采的生平和著作是近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受到最严重曲解的现象”。
笔者认为,凡是那些对尼采思想的褒扬抑或是极力的批判,都可以不加理会。
作为一名读者,最重要的是你从其中汲取到了什么。
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尼采,你只需要你心中的尼采。
在读了丹尼尔的《尼采传——一个特立独行者的一生》与尼采的《瞧,这个人》、《快乐的智慧》、《偶像的黄昏》、《善恶的彼岸》、《人性的、太人性的》、《查拉图斯特如是说》等著作后,我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重估一切价值体系。
尼采说,“人们既不相信我的话,也不了解我,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业将我事业的伟大性和我同时代的渺小性之间的悬殊,明白地表现出来了。
”于是他便允诺去完成最后一件事——“改良”人类。
正如他所说的“我没有建立新的偶像,我只希望旧的偶像们了解所谓赋有人类双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打倒偶像非常接近我的工作,打倒偶像然后对一切价值体系重新评估。
”对一切价值体系重新进行评估,这是对现代性与一切业已存在并且牢不可破的社会意念、价值体系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批判和颠覆。
这场重估运动成了尼采思想和“文明”之间的针锋相对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浅谈尼采主要的哲学思想

浅谈尼采主要的哲学思想浅谈尼采主要的哲学思想反传统主义者尼采,其学说的影响无论是在世界各国还是在中国都很强烈的。
从近代起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形成了三次“尼采热”(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抗日战争时期,1985一1989年间)。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尼采的思想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
尼采的思想深受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
他先是追随叔本华,后是扬弃了叔本华,以自己的“强力意志说”来代替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强调发挥人的创造性活力和生命本能。
他高呼“上帝死了”主张“用铁锤从事哲学”。
他提出“打倒偶像”,反对以苏格拉底和基督教为代表的欧洲理性派哲学传统,及其孕育的“强力意志”相悖的“奴隶道德”(全增瑕主编《西方哲学史》第417页)。
他大胆提倡“重估一切价值”,以使人的生命充盈的“主道德”代替以往的使人堕落、屠弱的“畜群道德”或“奴隶道德”,以现实世界的“超人”代替彼岸世界的“上帝”或“救世主”以及个性被泯灭的“末人”。
一、强力意志尼采强力意志论一直可以追溯到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但是尼采扬弃了叔本华全面否定生命的悲观主义思想,强力意志实现的是对人性的肯定,对人生存价值的认可,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强力意志,强力意志是人的本质特性。
生命意志的目标不是求生存,而是求强力具有强力意志的人是自由之人、智慧之人、自主之人。
人在创造中成其为人,只有具有强力意志的主体才是自由的艺术创造的主体,才是生存有价值、有意义的人。
生命是一种自我扩张、自我延伸、不断上升的过程,强力意志是一种自我肯定的意愿,一种自我超越的意愿,人要成为自己的主人、命运的主宰,就必须有强力意志。
人出生就是走向死亡,这是人的宿命的悲剧,而通过艺术创造可以实现对这种宿命苦难的升华,可以避免这种痛苦,从而拯救人类悲剧性的命运,这是一种古希腊式的逃避痛苦、消极对待的方式,而尼采认为,强健的生命渴求痛苦,从生命本体的高度和不可知的悲剧命运力量的抗争,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柏拉图与尼采的“嬗变”——丹托艺术定义思想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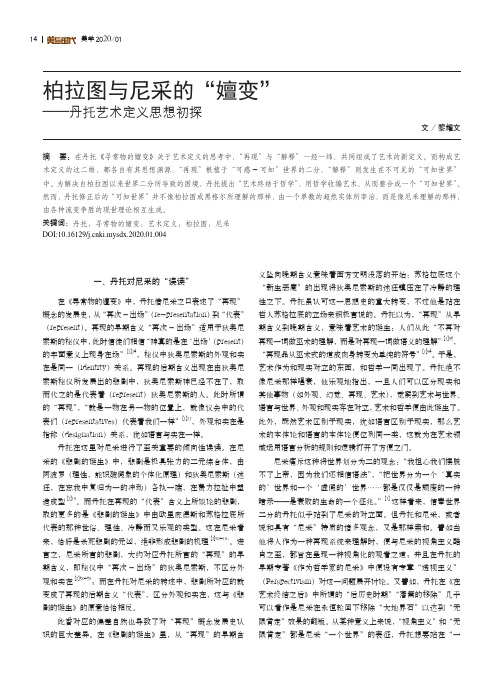
14美学2020/01一、丹托对尼采的“误读”在《寻常物的嬗变》中,丹托借尼采之口表述了“再现”概念的发展史,从“再次-出场”(re-presentation)到“代表”(represent)。
再现的早期含义“再次-出场”适用于狄奥尼索斯的秘仪中,此时信徒们相信“神真的是在‘出场’(present)的字面意义上现身在场”[1]24,秘仪中狄奥尼索斯的外观和实在是同一(identity)关系。
再现的后期含义出现在由狄奥尼索斯秘仪所发展出的悲剧中,狄奥尼索斯神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代表着(represent)狄奥尼索斯的人。
此时所谓的“再现”,“就是一物在另一物的位置上,就像议会中的代表们(representatives)代表着我们一样”[1]21,外观和实在是指称(designation)关系,犹如语言与实在一样。
丹托在这里对尼采进行了至关重要的倾向性误读。
在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悲剧是极具张力的二元综合体,由阿波罗(理性,能识破假象的个体化原理)和狄奥尼索斯(迷狂,在忘我中复归为一的冲动)各执一端,在费力拉扯中塑造成型[2]19。
而丹托在再现的“代表”含义上所谈论的悲剧,取的更多的是《悲剧的诞生》中由欧里庇德斯和苏格拉底所代表的那种世俗、理性、冷静而又乐观的类型。
这在尼采看来,恰好是杀死悲剧的元凶,绝非形成悲剧的机理[2]90-107。
进言之,尼采所言的悲剧,大约对应丹托所言的“再现”的早期含义,即秘仪中“再次-出场”的狄奥尼索斯,不区分外观和实在[2]58-59;而在丹托对尼采的转述中,悲剧所对应的就变成了再现的后期含义“代表”,区分外观和实在,这与《悲剧的诞生》的原意恰恰相反。
此番对应的偏差自然也导致了对“再现”概念发展史认识的巨大差异。
在《悲剧的诞生》里,从“再现”的早期含义坠向晚期含义意味着西方文明没落的开始:苏格拉底这个“新生恶魔”的出现将狄奥尼索斯的迷狂镇压在了冷静的理性之下。
丹托虽认可这一思想史的重大转变,不过他是站在哲人苏格拉底的立场来积极言说的。
尼采永恒轮回思想研究

尼采永恒轮回思想研究摘要尼采说:“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与快慰;就算人生是场梦,我们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要失掉梦的情致和乐趣。
”永恒轮回之说印证了生命流向的单一性,一旦流逝,便永不复返,这么看生命,是残酷的,也是美丽的,但即使绚丽如此,我们也不必太多在意,就像是部落之间的一次战争,千万人死去,也丝毫改变不了世界本来的面目。
尼采以非科学性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生命,对于这一伟大学说,后人研究从未停止,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永恒轮回概念的现世意义。
以期为相关理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尼采;永世轮回;哈姆莱特;生成概念引言从科学的角度上看,尼采的永恒循环说是难以成立的,但从哲学信仰的角度看,永恒循环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与寄托,在此意义上,尼采把它称之为“肯定生命的最高公式”。
可是“永恒”与“超越”的二律背反也使得尼采不得不进行如同铁笼困兽般的抗争之中。
还有学者从生存论的意义上来考察永恒轮回,认为尼采提出这一思想的着眼点人的生命及人的责任,具有伦理倾向。
永恒轮回表明任何事物都是无穷无尽地重复出现,因而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是对永恒事物及生命的无限责任,责任本身就赋予了行为本身巨大的价值。
也有研究者认为应把尼采放到西方哲学历史之中去弄懂尼采,永恒轮回是尼采对欧洲哲学虚无主义传统的批判,这一批判首先直指基督教神学思想,即其所谓的罪与罚、得救—和解这类谎言,因为永恒中并没有正义、和解,只是同样的轮回;其次,尼采的矛头针对传统理念论哲学的“超越”态度,即感性世界的生活是应该否定的,只有理念世界是永恒的、真实的,尼采要破除这千年积习,使之颠倒;再次,永恒轮回指向人世间的永生、永死,世间万物及人永不能超越这个生死的轮回,所以,并没有永恒的超越。
一、概述尼采的永恒轮回概念棋子受规则束缚,可能的步骤是有限的,因此由之构成的棋局也是有限的,只要局数够多,必将出现相同的棋局。
尼采与近现代人类存在哲学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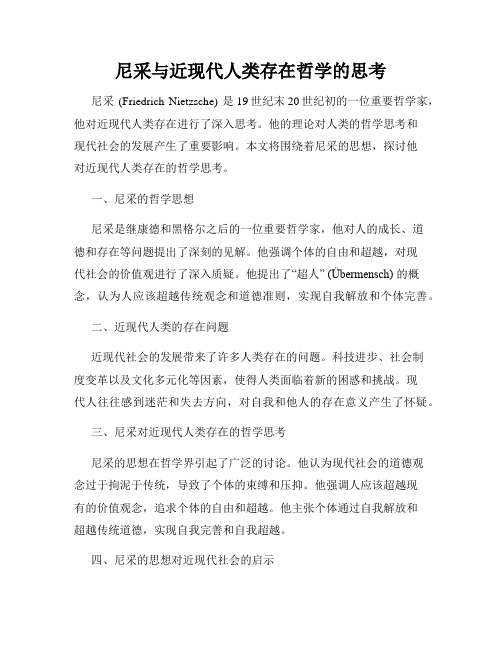
尼采与近现代人类存在哲学的思考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重要哲学家,他对近现代人类存在进行了深入思考。
他的理论对人类的哲学思考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将围绕着尼采的思想,探讨他对近现代人类存在的哲学思考。
一、尼采的哲学思想尼采是继康德和黑格尔之后的一位重要哲学家,他对人的成长、道德和存在等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他强调个体的自由和超越,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入质疑。
他提出了“超人” (Übermensch) 的概念,认为人应该超越传统观念和道德准则,实现自我解放和个体完善。
二、近现代人类的存在问题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人类存在的问题。
科技进步、社会制度变革以及文化多元化等因素,使得人类面临着新的困惑和挑战。
现代人往往感到迷茫和失去方向,对自我和他人的存在意义产生了怀疑。
三、尼采对近现代人类存在的哲学思考尼采的思想在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道德观念过于拘泥于传统,导致了个体的束缚和压抑。
他强调人应该超越现有的价值观念,追求个体的自由和超越。
他主张个体通过自我解放和超越传统道德,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
四、尼采的思想对近现代社会的启示尼采的思想对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的思想提醒人们重视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思考,超越传统的道德准则,追求自我完善和超越。
在当代社会,人们往往被现有的社会价值观念所束缚,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方式,追求个体独立和自由。
五、结语尼采对近现代人类存在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他的思想对于当代人们审视自身存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面对现代社会的困扰和挑战时,我们应该从尼采的思想中汲取智慧,超越传统的价值观念,追求个体的自由和自我完善。
通过重新审视自身的存在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适应和拥抱现代社会的发展。
论文(尼采的意志哲学述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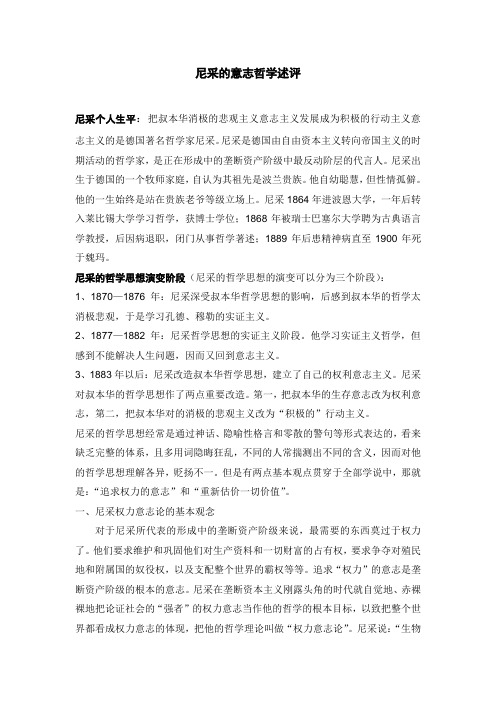
尼采的意志哲学述评尼采个人生平:把叔本华消极的悲观主义意志主义发展成为积极的行动主义意志主义的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
尼采是德国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的时期活动的哲学家,是正在形成中的垄断资产阶级中最反动阶层的代言人。
尼采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牧师家庭,自认为其祖先是波兰贵族。
他自幼聪慧,但性情孤僻。
他的一生始终是站在贵族老爷等级立场上。
尼采1864年进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获博士学位;1868年被瑞士巴塞尔大学聘为古典语言学教授,后因病退职,闭门从事哲学著述;1889年后患精神病直至1900年死于魏玛。
尼采的哲学思想演变阶段(尼采的哲学思想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870—1876年:尼采深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后感到叔本华的哲学太消极悲观,于是学习孔德、穆勒的实证主义。
2、1877—1882年:尼采哲学思想的实证主义阶段。
他学习实证主义哲学,但感到不能解决人生问题,因而又回到意志主义。
3、1883年以后:尼采改造叔本华哲学思想,建立了自己的权利意志主义。
尼采对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作了两点重要改造。
第一,把叔本华的生存意志改为权利意志,第二,把叔本华对的消极的悲观主义改为“积极的”行动主义。
尼采的哲学思想经常是通过神话、隐喻性格言和零散的警句等形式表达的,看来缺乏完整的体系,且多用词隐晦狂乱,不同的人常揣测出不同的含义,因而对他的哲学思想理解各异,贬扬不一。
但是有两点基本观点贯穿于全部学说中,那就是:“追求权力的意志”和“重新估价一切价值”。
一、尼采权力意志论的基本观念对于尼采所代表的形成中的垄断资产阶级来说,最需要的东西莫过于权力了。
他们要求维护和巩固他们对生产资料和一切财富的占有权,要求争夺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奴役权,以及支配整个世界的霸权等等。
追求“权力”的意志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的意志。
尼采在垄断资本主义刚露头角的时代就自觉地、赤裸裸地把论证社会的“强者”的权力意志当作他的哲学的根本目标,以致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权力意志的体现,把他的哲学理论叫做“权力意志论”。
尼采的思想三阶段

尼采的思想三阶段作者:叶水涛来源:《七彩语文·教师论坛》2021年第03期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说的都是“思”——“我思”。
帕斯卡尔说人的本质在“思”,人因思考而有生活的意义;笛卡尔说人因“思”而存在,并以“思”证明自己的存在。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说的也是“思”。
人之所思,或对外物,或对自身。
对外物之“思”,旨在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对自身之“思”,重在对人生意义的拷问。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诗的语言和隐喻、象征的手法,提出了人生思想三阶段的学说。
人的一生中,思想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尼采认为是“骆驼”。
“骆驼”的角色,忍辱负重,一步一个脚印,辛苦奔走于途。
以此暗喻人生最初的历练——有如“骆驼”,驮着沉重的辎重,行走在炎热干燥的沙漠之中。
干渴、饥饿、劳累,还有无穷的远方,没有任何诗意的浪漫,有的是对生理极限的考验,同时接受考验的还有心理承受能力。
“骆驼”阶段的特质无疑是忍耐、克制、坚持不懈,而不在思想锋芒的咄咄逼人,也不在成功的喜悦和欢乐。
何谓忍耐?埋头苦干、坚韧不拔,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执着地完成人生赋予的任务。
尼采告诉我们,“骆驼”是人生的必然阶段,但不是随遇而安,从此得过且过。
在经历艰难困苦的磨炼以后,这段时期的任务履行完毕,尼采告诫我们要义无反顾地、坚决地告别“骆驼”阶段。
我们在“骆驼”阶段经受了各种苦难,但培养了吃苦耐劳、执着前行的精神。
“十年面壁图破壁。
”接受“骆驼”的命运,并非欣赏“骆驼”的身份。
“骆驼”是沉默的——负重跋涉,默默行走于万里沙漠中。
“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说这话的是鲁迅,他被称为“中国温和的尼采”。
就在这艰难困苦的旅途中,“骆驼”会突然变身为“雄狮”。
尼采认为,雄狮是勇猛善战的动物,它敢于在沙漠中向巨龙挑战。
巨龙身上每一片金黄色的鳞甲都闪烁着光辉,它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价值。
尼采生存哲学优秀读后感心得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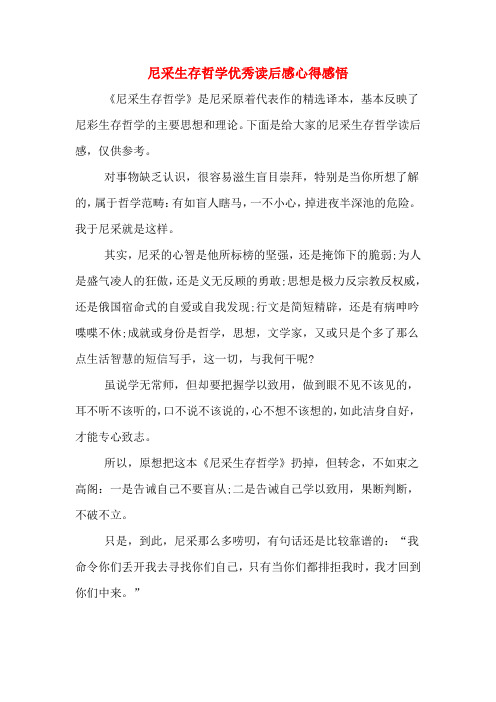
尼采生存哲学优秀读后感心得感悟《尼采生存哲学》是尼采原着代表作的精选译本,基本反映了尼彩生存哲学的主要思想和理论。
下面是给大家的尼采生存哲学读后感,仅供参考。
对事物缺乏认识,很容易滋生盲目崇拜,特别是当你所想了解的,属于哲学范畴:有如盲人瞎马,一不小心,掉进夜半深池的危险。
我于尼采就是这样。
其实,尼采的心智是他所标榜的坚强,还是掩饰下的脆弱;为人是盛气凌人的狂傲,还是义无反顾的勇敢;思想是极力反宗教反权威,还是俄国宿命式的自爱或自我发现;行文是简短精辟,还是有病呻吟喋喋不休;成就或身份是哲学,思想,文学家,又或只是个多了那么点生活智慧的短信写手,这一切,与我何干呢?虽说学无常师,但却要把握学以致用,做到眼不见不该见的,耳不听不该听的,口不说不该说的,心不想不该想的,如此洁身自好,才能专心致志。
所以,原想把这本《尼采生存哲学》扔掉,但转念,不如束之高阁:一是告诫自己不要盲从;二是告诫自己学以致用,果断判断,不破不立。
只是,到此,尼采那么多唠叨,有句话还是比较靠谱的:“我命令你们丢开我去寻找你们自己,只有当你们都排拒我时,我才回到你们中来。
”从以上几段文字来看,不正是应验了他所说的吗?难道他真乃神人。
是在用阴谋还是阳谋让我们发现自己,检验自己吗?都不是。
这句话倒让我想起了一名算命先生的话,他说:“母在父先亡”,那么,是母在,父先亡呢?还是母在父先,亡。
其实,尼采所命令的人心中,都包含了宗教信仰和自我发现两个元素,“命令寻找自己”,便开启了人心中这两个元素的缠斗,而不管过程如何,其中的元素“自我发现”都会被另一个元素排拒绝,当然不管结果怎样,人的“自我发现”也都不会被消除;尼采代表的是“自我发现”,其实,他早已在你们心中,只是换了种说法,好像最后他就回到“你们中来了”。
这只是他的心理把戏罢了。
无论如何,对尼采,最后,礼毕,解散。
有评论说读《尼采生存哲学》是一次走近大师的心灵之旅:或许会改变你的一生。
哲学是人生观的学问:哲学是心灵的完善:哲学是生命的诗。
浅谈尼采的哲学思想

一、尼采及其哲学思想的初步认识寄语:哲学是人生观的学问。
哲学是心灵的完善。
哲学是生命的诗。
或许这是一次走进哲学大师的心灵之旅,或许会改变我的一生!在我以前的印象中,我把尼采看作是一个自诩为“太阳”的狂者,一个看破一切,对任何人任何事“不屑一顾”的顽固的老头子。
我觉得他是一个狂人,一个敢于以不同于他人的理解方式表现自己的人生态度和表达自己思想的狂人。
我并没有太多的心思去分析这样一个狂人所散发出的独特的哲学的花香,至少我认为现在的我还没有资格作一个能够闻到这种花香的蜜蜂。
我只是在书中去寻找并搜索花香所飘散的路径,追求对尼采的哲学思想有一个比较简单而理性的认识。
当然,不能仅仅建立在我读完关于尼采哲学思想的一本书(《尼采成功意志学》)后乱谈一点不负责任的话——我还不敢说对他能有什么评价,毕竟我认为我还没有达到一个学者评价一个哲学大师的水平。
所以,我同时也参看了被称作“存在哲学大师”的马丁·海德格尔的《尼采》。
海德格尔和一切存在主义者都把尼采看作是为他们开拓了道路的人。
海德格尔的《尼采》我也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
他对尼采的哲学思想有比较系统的分析。
我不敢说我已经完全看懂了,也承认我现在还不能完全依照海德格尔的思维去分析一个德国老头子的满纸带着嘲讽口气却很深奥的哲学思想。
不过,在看《尼采成功意志学》的同时参看海德格尔的《尼采》,用海德格尔著作中的一些我能够理解的东西,帮我渐渐有一点理解尼采的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学说。
二、从尼采的生平谈点感想如果说在读一位哲人的著作之前不了解哲人的生平或者说他的人生际遇或轨迹,我们很难说服自己在读著作的时候能真正把心融入哲人的思维中去。
尼采,德文名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尼采1844年出生在一个新教牧师家庭。
尼采早期宗教思想的形成及其现代启示

尼采早期宗教思想的形成及其现代启示尼采早期的宗教思想主要涉及到异端主义、消极主义、基督教的崩塌以及道德的矛盾。
尼采认为,现代社会中宗教思想迅速崩溃,而这种崩溃是由于基督教之间的宗教分裂引起的。
因此,尼采早期的宗教思想颇具贡献,对于今天的宗教研究和文化思考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首先,尼采认为宗教的消极性质是很明显的。
宗教是对于责任和道德规范的逃避,是因为人们害怕面对现实而产生的一种幻象。
通过信仰来避免现实中的痛苦和不幸,是一种低劣而懦夫的行为。
因此,尼采认为,宗教的消极性质一直占据了它的主导地位。
而这种消极性质的表现是,宗教强调教条主义,对于知识和文化的隔离,对于思想和行为的约束,以及对于模糊和虚伪的哲学观点。
例如,基督教的“约束”思想以及天主教的“教条主义”等等,都是宗教消极性质的典型代表。
其次,尼采认为,宗教的稳定性和封闭性会限制个人的发展。
个人的价值不应该被宗教要求、规章和约束所束缚,而应该追求自由和创造力。
宗教社群的束缚让个人失去了自由、创造力和个性。
因此,尼采认为,宗教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会压抑人们的天赋才能。
例如,伊斯兰教的禁欲主张以及某些神秘宗教的禁止人们思考等等,都是宗教稳定性和封闭性的典型代表。
第三,尼采认为宗教教义的“超人”和“无神论”是道德观察上的矛盾。
宗教追求统一和平庸,却忽略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而无神论则追求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却忽略了道德的规范。
因此,尼采认为,宗教和无神论是道德观念的矛盾。
例如,康德在其伦理学中强调了道德自治和道德命令,但忽视了人性的直觉、天性和个性,因此不符合真正的道德观点。
第四,尼采认为,宗教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宗教能够给人需要的力量和信念,能够在现实中带给人温暖和安慰。
例如,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和伊斯兰教的人道主义等等,都是宗教积极义的典型代表。
第五,尼采的宗教思想对于今天的宗教研究和文化思考有一定的启示。
尼采的宗教思想中包含了众多的生命哲学、文化哲学和形而上学思想。
【2018最新】尼采生存哲学读后感作文word版本 (2页)

【2018最新】尼采生存哲学读后感作文word版本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尼采生存哲学读后感作文说实话,看这书绝对是对自己精神的挑战,真庆幸我没有崩溃,而且能在此提起拙笔,感叹一下自己的愚见。
尼采那“上帝已死”的呼声宣称必须将以宗教信仰为基准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彻底摧毁。
他提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体系,主张以人自身作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
他那颠覆性的思想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们。
书中有尼采的很多关于道德的观点,最为强烈的是批判宗教性的“奴隶式道德”。
以此同时,尼采还提出了“超人”的英雄主义的哲学人生观。
中西方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关于“道德”,两者就差别甚大,然而,关于“超人”这一说,中西方却有着相似之处。
尼采主张个性张扬,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意志去开发创新人生,享受努力奋斗的成就,即使是失败,只要永远在奋斗,也是最有价值的自我实现。
他的英雄主义,不难让我们想起中国《周易》中的伟大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同尼采的生存哲学和主张一样,强烈的影响或改变了许多名人的思想和生活。
对我们常人来讲,又何尝不是值得再次品味和重读的励志箴言呢!很少有人,甚至没有人能再及尼采,但至少,我们,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的远些。
[ 尼采生存哲学读后感作文 ]相关文章:1. 关于学会生存作文的作文五篇2. 适者生存作文3. 独立生存作文4. 有关于生存的作文5. 依赖与生存作文。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摘要:尼采哲学问世以来,一直散发着巨大的精神魅力,吸引着无数卓有才识的后学为之耗尽心血。
尤其是它的关于存在者的主体性问题,更是一百多年来众多哲人关注与探究的焦点所在。
存在者整体如何进行自我超越,主体的现代性如何展开,这些命题如何解决,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哲人对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关键词:尼采;存在意识;新贵族;善与恶;存在者整体一、引言自康德这个来自德意志哥尼斯堡的矮个子以来,西方精神中再也难有与之并驾齐驱的高等人类了,如果有的话——在一百年以后还能被人类当作规范的话,那一定是尼采无疑了。
这个以超人,酒神,新贵族自命的伟大精神,这个深刻的构成了现代精神的巨大英魂,至今还被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读者当作其思想的源泉,在意识的幽暗中摸索前进,他以及他的思想到底具备了什么魅力能让一百多年来的众多生灵如此痴狂?其人其思以语言为媒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现代精神?或许我们久历爱憎的摩荡,已经对所谓的“思想影响大众”的说法疲惫不堪,甚至于如是存想:既然是终归一死,既然是身后虚无,既然是不增不减,终古如此,那么所有的追问又有什么意味呢?或者又如海德格尔所说:“哲学的一切根本性问题必定都是不合时宜的……哲学本质上是超时间的,因此它属于那种极少的一类事物,这类事物的命运始终不能也不可能在当下现今找到直接反响。
”[1]难道思想仅仅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行为,而与极少数的他人相涉?《维摩诘经》文殊师利云:“乃至不可说,不可说,是真入不二法门。
”你明明知道这种追问在很大程度上是荒诞无谓的举动,但你还要处心积虑地一直向下做去,难道这不是一种平庸的权力欲在作怪?或许你在苦心积虑的将一些追问记述下来以后对这些文字的遗留再也难有鲜活的印象,它们让你迷失,并且由于你的轻率与冷淡,它们也会很快迷失,难道这也是生命的必要?幸好还有一点可以确证:你正是看到了诸如“回响”、“积极的虚无主义”之类的文字,你的痛苦才减轻了许多,有时也会像一个高傲的人,自挹自足,“物无贵贱” [2],没有太深的成见,没有太多的忿戾,虽然敏感矛盾,毕竟没有沉沦下去。
尼采说:“做一个高超的人。
”你的痛苦虽然有一部分是增长于文字,但是毕竟整个的痛苦确是由于文字祓除的。
佛家要人“持戒,信行,忍辱”,其言虽可,但也希求报偿,可是当你连报偿都不需要时——我说的这种报偿也包括对高等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你的人生还能剩下什么呢?当下你的存想是:是佛家式的还是尼采式的,痛苦是要减轻还是加重?而这种欲求及其对象不是一种更为荒诞的报偿吗?二、新贵族历史是循环的吗?自从黑格尔、马克思以其辩证逻辑(其核心为矛盾观)确立进步史观以来,富有创造力的一批后进的德国哲人们便纷纷提出了异议。
假如历史被认为在曲折中前进、盘旋式的上升的话,那么人们就只能在进步的自我幻设中踽踽前行了,待个体的活力耗散殆尽后,历史便会呈现出一片荒芜的景象,个体还能有何作为呢?个体的可能性还剩多少?这一切都表现为一种可恶而邪恶的本源。
为什么历史是决定论的模式而不能在偶然性中催发个体的活力?1900年前后,德国的两位民间哲人——尼采和斯宾格勒就以不同的侧面给出了相似的回答,这就是轮回和循环。
一提起这两个名词,多数人都会立刻想到一种典型的东方思维形式——佛家的轮回说。
几百年来,一种西方流行的理论,一直认为轮回说不过是没落的贵族阶级在其文化分崩离析之际而做出的无耐的回应而已,甚至于日本的永田广志在其《封建制意识形态》中也毫不客气的将日本贵族的疲沓无力、风流自伤归咎于过度享乐的倦怠感与佛教相合流的结果。
然而尼采和斯宾格勒的学说甫一问世,立刻就获得了巨大而持久的反响,并且人们对他们持说甚切的贵族理想也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与最大限度的谅解。
照此观彼,其间的反差何其之大。
西方人一贯以中心自居,隐然自命为他者的标准,即便是东西方共同的命题也要千方百计地削弱彼方的效力。
其间的滋味,确实令人难堪。
在西方,自由主义方兴伊始,就有歌德等人对之表示了深沉的忧虑。
歌德写道:人类变得将更加聪明,更加机灵,但是并不变得更好、更幸福和更强壮有力。
我预见会有这么一天,上帝不再喜欢他的造物,他将不得不再一次毁掉这个世界,让一切从头开始。
1853年托克维尔看到民族政治的到来不可避免,因此他在研究民主的本性时,并不关注如何避免民主政治的思想,而是关注如何将它的危害减至最低的思想。
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把民主政治视为蛮族的入侵。
布克哈特则以恐怖的心情注视着民主政治的袭来。
比这更早一点的是斯坦达尔在1829年写下的话。
他以冷静的客观态度看待此事:“在我看来,在一个世纪之内自由将扼杀艺术的感觉。
那种感觉是非道德的,因为他把我们引入歧途,一如爱情的狂热,引入懒散和夸张…..两院制将遍行世界,给美术以致命的打击。
统治者们不会去建造可爱的教堂,而将他们的主要兴趣放在美洲的投资上,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发生政变时去哪里安享生活。
”[3]显然,这种忧虑还是带有很深的复古怀旧的情调的。
这是一种悠远的乡愁。
虽然仅仅是在情感上对那些遥远的古典形式的强劲有力、凝重和谐投注了巨大的热情,并且也没有进行学院式的学理探究,但是这些已经足够了,能够把理念投入到生命整体当中,难道不比创立一套很快就会僵死的概念体系更有意味?降至尼采、马克思的时代,隐忧就变成了批判,“佛教源自最高等级……基督教运动乃是退化运动…….它憎恨一切高贵者和统治者,为此它需要一种诅咒高贵者和统治者的象征……并且诅咒精神。
”[4]而根源于基督教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等等则更是众暴寡、弱凌强的群氓思维的体现。
众多的庶民抟聚在一起,“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多数的名义发泄着破坏毁灭的沴气,数十百年以后,渐行渐渍,人类的生活将更加庸陋丑恶,高贵的精神将沦丧无余。
大地上呈现一片莽苍的景象,哪里还有归宿?那里还有方向?尼采和斯宾格勒都转而诉求于新贵族的这个概念,而马克思则将之诉诸于阶级斗争的概念,一则向后,一则向前,共同引领了此后一个世纪的思想风潮。
新贵族理想诉诸于古典、观相、艺术、主体、精神等概念,而阶级斗争则倾向于数理、分析、技术、客体、物质之类的概念,一为精英,一为大众,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在反对新教徒的泛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
资本主义何以成为可能?何以具有如此邪恶的生命力?是缘于科技主义的煽惑?还是邪恶而恐怖极点的现代统治技术的综合效用?亦或故伎重演将之归咎于人性、欲望的循环?以海德格尔、雅斯贝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学者,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多数将之归结为全面性技术统治的实现所致。
卡夫卡的作品就展示了这种精细绵密的权力控制模式对社会人生各个层次的整体控制的图景。
在现代社会里,个体已难以施展其作为个体的权力,个体的主体性空间已被挤占无余。
在“发了狂一般的运作技术和相同的肆无忌惮的民众组织” [5]面前,“如果有一天技术和经济开发征服了地球上的最后一个角落;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任何一个事件在任何时间内都会迅即为世人所知;如果人们能够同时…体验‟法国国王的被刺和东京交响乐会的情景;如果作为历史的时间已经从所有民族的所有此在那里消失,并且仅仅作为迅即性、瞬刻性和同时性而在;如果拳击手被奉为民族英雄;如果成千上万的群众集会成为一种盛典,那么,就像阎王高居于小鬼之上一样,这个问题仍会凸显出来,即:为了什么?走到哪里?还干什么?”[6]个体在这台疯狂运转的统治机器面前,还能有何反击之力?个体只能放弃抵抗,成为众多他者中的一员,福柯的《规则与惩罚》、《疯癫与文明》、《性经验史》就从发生学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统治理念如何借助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之类的概念获得道义上依据的过程,并且指出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持久地精心预设的谋略。
统治阶级有计划通过各种交流手段(如教育、媒体等)对个人的思维、脾性进行规训,使之成为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稳定的一员,使之虽自知沉沦却无力反抗……这就是现代,诸神逃遁,大地毁灭,世界趋向黑暗,人类渐次群众化,“那种对一切具有创造性和自由的东西怀有恨意的怀疑在整个大地上已经达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各民族已处于丧失其最后的精神力量的危险中。
”[7]所以对贵族精神的颂扬似乎就变得有些必要了。
毕竟,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群之间的对立总是在少数上层与多数下层之间展开的,既然多数人的泛民主主义会带来如此严重的灾变,那么重新回到少数人的立场就成为首要而唯一的选择了。
但是这样一来,新贵族的理念不就显得庸陋乏味了吗?历史有必然性吗?为什么要非此即彼,而不能有其他选择吗?难道刚才你对占据必然性地位的进步史观的反对就是为了重树新贵族的主导地位而铺路吗?多言者躁,“多言数穷”,难道话语一旦增多,话语的魅力就必然散失吗?也许,新贵族仅仅是极少数人的梦呓,它本身也不可能获诸现实,并且它本身也不会变得明晰,获得赋形,但是以此为机缘构建起精神内心世界的宽广前景却是大有可为的。
三、超越善与恶每当读书阅世之余,也即当你开始反思的时候,是否也会想到——像先哲们所陈述的那样,一切意念终归不过是造作而已。
善与恶?当人类还和其他生物一样终日游食时,头脑中会有如此明晰的概念吗?是与非?它们的概念不是一直在变动吗?甚至是虚无,以及虚无之虚无。
所有的“无尽缘起”,不也是一种造作吗?当然,这仅仅是东方的思维,西方的哲人是绝少作如是观的,他们太过于执著,以至于明知其不可却偏要坚持下去,以痛为乐,以反为正,以体验剧烈的矛盾冲撞为最高享受。
二者虽然在认识论上是等量齐观的,但是在态度和价值趋向上却是迥然不同的。
尼采说:“自尊者和独立者若被人同情就会感到万分委屈,与其被人同情倒不如被人憎恨。
”[8]这乃是一种求恶的意志。
其渊源可以上溯到黑格尔那里,他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谈到“…否认的东西的无比巨大的力量‟:…这是思维,纯粹自我的能力……柔弱无力的美之所以憎恨知性,就是因为知性硬要它做它所不能做的事情。
但精神生活不是由于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
精神只有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
精神是这样的力量,不是因为它作为肯定的东西而对否定的东西根本不加理睬。
犹如我们平常对某种否定的东西只说虚无的或虚假的就算了事而随即转身它向不再闻问的那样,相反,精神所以是这样的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
‟可见就连德国唯心主义也敢于把恶思考为属于存在之本质的东西。
”[9]而尼采则对之评述道:“德国哲学的意义(黑格尔):挖空心思地构想出一种泛神论,并不认为恶、谬、苦是反对神性的论据,这种伟大的首创精神已经被存在的各种权力(诸如国家等等)滥用了,似乎它已经认可了正在台上的统治者的合理性。
”[10]显然,黑格尔和尼采已经敏锐地触及到人类意识的幽暗一面,幽暗到似乎隐隐有一种毁灭与作恶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