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璠_河岳英灵集_诗学思想述略_张海明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https://img.taocdn.com/s3/m/9b9fe2cac0c708a1284ac850ad02de80d5d80647.png)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河岳英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提要臣等谨案,河岳英灵集三巻,唐丹阳进士殷璠编。
自常建至阎防二十四人,诗二百三十四首。
仿锺嵘诗品之体,姓氏之下各着品题。
虽不显言次第,然篇数无多,而分上中下巻,其人又不甚叙时代,毋亦隐寓锺嵘三品之意乎?《通考》作二巻,盖误也。
其序谓:“爰因退迹,得遂宿心”。
盖不得志而着书者,故所録多淹蹇之士,所论多感慨之言,而序称名不副实,才不合道,虽权压梁窦,终无取焉,其宗旨可知也。
凡所品题类多精惬,张谓条下称其《代北州老翁答湖上对酒行》,而集中但有《湖上对酒行》,疑辗转传冩有所脱佚矣。
唐人搃集存于今日者,不过毛晋所刋七八种,稽其时代,盖莫古于是编。
以盛唐之人选盛唐之诗,见闻既切,工拙易明,其所品定固终胜后来之寻声而索者也。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河岳英灵集目録巻上常建李白王维刘眘虚张谓王季友陶翰李颀髙适卷中岑参崔颢薛据綦毋潜孟浩然崔国辅储光羲王昌龄贺兰进明巻下崔曙王湾祖咏卢象李嶷阎防叙曰: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称尽善,高听之士,或未全许。
且大同至于天宝,把笔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贿赂者,中间灼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岂得逢诗辑纂,往往盈帙。
盖身后立节,当无诡随,其应诠拣不精,玉石相混,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
论曰:昔伶伦造律,盖为文章之本也。
是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
宁预于词场,不可不知音律焉。
孔圣删《诗》,非代议所及。
自汉魏至于晋宋,高唱者十有馀人,然观其乐府,犹有小失。
齐梁陈隋,下品实繁,专事拘忌,弥损厥道。
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或须避之,纵不拈二,未为深缺。
即“罗衣何飘飘,长裾随风还”,雅调仍在,况其它句乎?故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
而沈生虽怪,曹王曾无先觉,隐侯言之更远。
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
殷璠《河岳英灵集》的文学批评论(一)

殷璠《河岳英灵集》的文学批评论(一)【内容提要】天宝末年,丹阳进士殷璠,以其卓越的识见,严肃的精神,完成了李白的未竟之志,选编了一部很有特色的盛唐诗歌选本一一《河岳英灵集》。
和《文选》的编者萧统一样,他也旨在通过选本来体现自己的文艺观点,开展文学批评。
尤其选诗的标准、范围、题材、特征以及发展路向等,在众多的“唐人选唐诗”版本中独树一帜,唱响了那个时代的“盛唐之音”,历千年洗练依然魅力不衰,同样称得起是“河岳英灵”之作。
【关键词】殷璠;《河岳英灵集》;盛唐之音;文学批评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诗人们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光辉的艺术成就,争奇斗胜,呈现出一派缤纷壮丽的色彩,这就是人们所称颂的诗歌的“盛唐气象”1]。
这个艺术史上的不寻常现象,不只是后之来者回望那遥远的艺术史的高峰而景仰赞叹,就是身当其时的诗人,也对展现在面前的崭新鼎盛景象,感到欢欣振奋。
天才横溢的李白就曾引吭高歌:”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冥。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古风》其一]。
他赞美同时代的诗人像秋天夜空中灿烂闪烁的群星,光辉四射。
他也曾有志对这一代的诗歌进行删述,以冀永传。
但又自叹“吾衰竟谁陈!”深恐这一千秋大业无人交付。
所幸李白的希望没有落空,天宝末年,“丹阳进士”殷璠,以卓越的识见,严肃的精神,完成了这一事业,得遂李白的未竟之志。
这就是殷璠及其编选的《河岳英灵集》。
一殷璠,丹阳(今江苏丹阳县)人,生卒年不详,大致生活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
他选编的《河岳英灵集》,是一本很有特色的盛唐诗歌选本。
殷璠和《文选》的编选者萧统一样,也是通过选本来体现自己的文艺观点,进行文学批评的。
他在《河岳英灵集·序》中坦言:“璠虽不馁,窃尝好事。
常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
爰因退迹,得遂宿心。
粤若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三十五人,皆河岳英灵也。
此集即以河岳英灵为集。
”2]这既说明了编选诗集的初衷,也点明了诗集名称的由来。
殷璠《河岳英灵集》诗学思想述略

殷瑶《河岳英灵集》诗学思想述略
《河岳英灵集》,清代殷墦所著,是一部记述晋、陕间山川名胜的纪游之作。
此书在写作上是承袭《容斋随笔》的体例。
其书前半部分记述晋人山水景物,后半部记述秦人及陕西各地名胜。
这是殷墦为自己家乡所作的一部纪游之作。
在其创作上,虽有对前人作品的继承,但更多的是一种自出机杼的创新和探索。
他在对《容斋随笔》及其他笔记作品有了初步研究之后,便以自己所熟悉、掌握的历史资料为基础,把目光投向了晋陕交界一带。
其书中有不少描写晋人山水景物的篇章,与《容斋随笔》中许多记游之作相较,确已别有一番风貌和特色。
这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中也是很少见的一种现象。
这说明殷墦不仅善于利用前人作品来。
从殷璠《河岳英灵集》诗学旨趣论盛唐诗学之文质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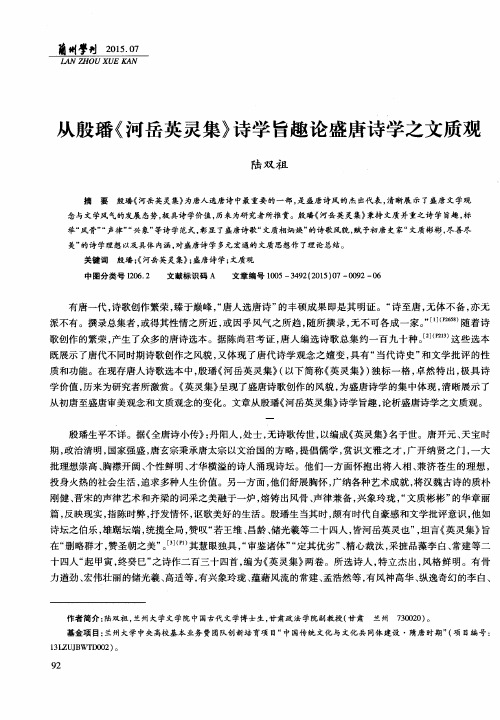
质和功能。在现存唐人诗歌选本中, 殷瑶《 河岳英灵集》 ( 以下简称《 英灵集》 ) 独标一格 , 卓然特出, 极具诗
学 价值 , 历来 为研究 者所 激赏 。《 英 灵集 》 呈 现 了盛 唐诗 歌创 作 的风貌 , 为 盛唐 诗 学 的集 中体 现 , 清 晰展 示 了 从 初唐 至盛 唐审美 观念 和文 质观 念 的变化 。文章从 殷瑶 《 河 岳英灵 集 》 诗学 旨趣 , 论析 盛唐诗 学 之文质 观 。
9 2
王维等 , 有情深境幽、 神闲意惬 的綦毋潜 、 张谓等 , 有声律宛然、 发调清新的刘奋虚 、 李颀等 , 有警策博雅、 省净
鲜 静 的祖 咏 、 李 嶷等 。而所选 诗歌 , 乐府 、 五古 、 五律、 五绝 、 五排 、 七古 、 七律、 七 绝无 体不 备 。边塞 游侠 、 咏物
L N ZH oU XUE KAN
从殷瑶 《 河 岳 英灵 集 》 诗 学 旨趣 论 盛 唐 诗学 之 文 质 观
陆双 祖
摘
要 殷瑶 《 河岳英灵集》 为唐人选唐诗 中最 重要 的一 部 , 是 盛唐诗 风的杰 出代表 , 清晰展 示 了盛 唐文 学观
念与文学风 气的发展 态势 , 极具诗学价值 , 历 来为研 究者所推 赏。殷瑶《 河岳英灵 集》 秉持 文质 并重之诗 学 旨趣 , 标
由此可见殷瑶的兴象说虽然继承了陈子昂的兴寄说但他却侧重于对文学本体的关照批评的重心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之前极具社会政治伦理色彩的批评即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反思转向了以文学为本位的艺术审美观照强调诗人的主体性强调意象的感发性强调诗歌的形象性和审美性同时强调诗语的新奇凝练性强调诗意的隽永深远性等等
确卅 警羽 2 0 1 5 . 0 7
殷瑶生平不详 。据《 全唐诗小传》 : 丹阳人 , 处士 , 无诗歌传世 , 以编成《 英灵集》 名于世。唐开元 、 天宝时
殷璠河岳英灵集唐诗选评研究的中期报告

殷璠河岳英灵集唐诗选评研究的中期报告1.引言殷璠河岳英灵集,是一部收录了许多唐代各地诗人的作品的选集。
本报告旨在对殷璠河岳英灵集唐诗选进行评析研究,在探索其文学价值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唐代文学的深厚魅力。
2.概述2.1 殷璠河岳英灵集的背景和特点殷璠河岳英灵集是唐代晚期的一部诗歌选集,以河岳为主题,汇集了许多当时的文人墨客的作品。
这一作品以诗歌形式表达了对河山之美的赞美,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的风貌。
2.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殷璠河岳英灵集唐诗选进行评析,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学价值和时代特色,并通过对诗人背景和作品风格的研究,更好地理解唐代文学对后世的影响。
3.文学价值的探索3.1 殷璠河岳英灵集的艺术风格殷璠河岳英灵集的诗歌作品大多采用豪放洒脱的风格,通过独特的词藻和形象描写,展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景色和河山美景的赞美之情。
这一艺术风格彰显了唐代文人的思想境界和审美追求。
3.2 诗人的背景与作品在殷璠河岳英灵集中,可以看到许多著名的唐代诗人,如杜甫、李白、王之涣等。
他们的作品既表达了个人情感,又对社会给予了独立的思考和批判。
通过对诗人背景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作品,并深入理解唐代的文学氛围。
4.时代背景的剖析4.1 殷璠河岳英灵集与唐代文化殷璠河岳英灵集的创作背景是唐代,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期。
在这个时代,文人墨客们纷纷涌现,他们的作品反映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迁。
4.2 唐代文学对后世影响的展望通过对殷璠河岳英灵集唐诗选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唐代文学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开创了文学的新境界,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5.结论殷璠河岳英灵集唐诗选的研究,对于理解唐代文学的重要性和深厚魅力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诗歌艺术风格、诗人背景和作品的研究,以及对唐代文化和时代背景的剖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唐代文学对后世的影响。
这种研究不仅可以拓宽我们的文学视野,还可以启迪我们对现代文学的创作和理解。
《四库提要》之《河岳英灵集》探析

摘要:结合相关史料与工具书从《四库提要》之《河岳英灵集》文本出发分析作者、书名、职官、卷数、篇数、收录诗人、版本问题、书籍评价有关内容,并提出有待考证的问题。
关键词:殷璠;河岳英灵集;四库提要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专选盛唐诗歌,是唐人选唐诗中十分重要的一种。
编选者首创评、选结合之体例,表达了自己对于诗歌的见解。
该集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深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该集的研究主要在诗集间的比较研究、版本研究、音律研究、诗论研究四个方面,而从《四库提要》之《河岳英灵集》文本着手进行研究的极少。
现在笔者拟从这一角度对该集作者、书名、职官、卷数、篇数、收录诗人、版本问题、书籍评价进行浅探。
同时提出值得研究的问题,以期为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一、作者1. 关于殷璠:《提要》这样介绍殷璠:“唐殷璠编。
璠丹阳人,《序》首题曰‘进士’,《书录解题》亦但称‘唐进士’,其始末则未详也。
”[1]原始文献中有两部对殷璠有所介绍。
一是文渊阁《四库全书》:“唐丹阳进士殷璠”;[2]二是《书录解题》:“唐进士殷璠” [3]此外,其他类书、诗文评等类书籍中也可以查找到相关线索。
如“《河岳英灵集》唐丹阳进士,殷璠撰” [4] “殷璠次为《丹阳集》与开元进士萧颕士同年生也” [5] “《河岳英灵集》首标“唐丹阳进士殷璠集”《全唐诗》小传:璠,丹阳人,进士。
它无所考。
” [6] “殷璠:《全唐诗》小传:‘璠,丹阳人,處士。
’序有丹阳进士,‘退迹诸语’璠似又非處士。
” [7]依此,我们可以得知殷璠为唐时丹阳进士,傅璇琮认为“殷璠的治所在今江苏镇江” [ 8]查找《旧唐书》、《新唐书》、《唐才子传》等史书均未提及殷璠生平,辅以类书、诗文评类书籍查找亦大同小异,在现代学者的研究中亦是未有新获。
由此,殷璠可能出生在开元年间,并活跃于开元、天宝年间。
为江苏镇江人,为进士,为官官位应该比较低。
2. 书名《提要》中提到《河岳英灵集》·三卷对照原始文献,这与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一百八十六集部三十九总集类一、《新唐书》卷六十、《宋史》卷二百九、《文献通考》下册卷二百四十八、《直斋书录解题》(下)卷十五、《玉海》卷五十九中提到的是一致的。
殷璠_河岳英灵集_的诗歌批评方法及其意义_卢燕新

诗句 进
‘
追溯 其 所 叙 评 者 诗 风 形 成 的 个 人 及 社 会 原 因
。
、
品评
。
如 引 常 建诗 并 评 曰
’
,
“
:
至如
,
松际
是 为 了 表 明 其对遴选 者 的 情感 态 度 露微 月
,
清 光 犹为 君 此例 十数 句
, ’
又
‘
山 光 悦鸟 性
。
潭影空
值 得关 注 的 是
一
体例
、
,
使 该集凸 显 出
玉 台 新咏》
、
或注 重 论 析 诗 人 风 格 主 要 特 点
。
或 论述 诗 人 风 格
珠英 学 士 集 》
。
《
国 秀 集 》 等选 本 所不 具 备 的 诗歌 的 文 学 史 意 义
批评 功 能 品 论 诗人诗 风时
《
,
《
河 岳英 灵 集 》 也 常 常采 用
时
,
,
《
河 岳 英 灵集 》 在 叙 评 诗 人 人 心
,
’
,
,
并可 称 警策
’ ,
然
‘
一
篇 尽善
,
常 常 追 溯 诗 歌史 现 象 或 选 择 相 同 相 近 的 文 士 者
。
‘
战 余落 日 黄
,
军 败鼓 声 死
, ‘
今与 山 鬼邻
”
以 比 较 论析
如 叙孟 浩 然 云
。
“
,
余常 谓 祢 衡 不 遇
自
河岳 英 灵 集 》 的 诗 学 思 想
从《河岳英灵集》看殷璠“雅调”旨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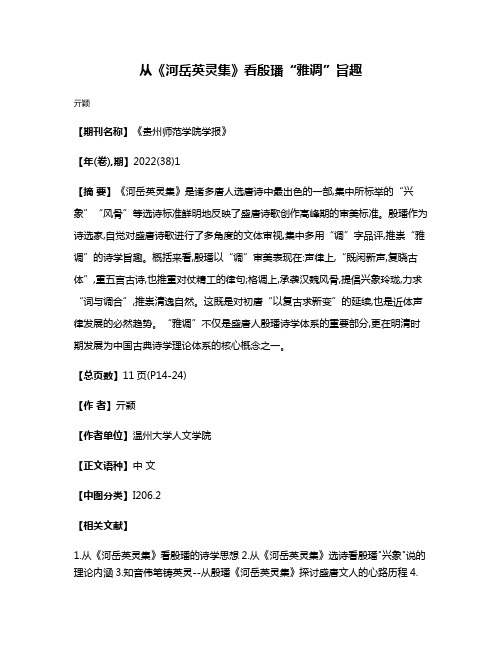
从《河岳英灵集》看殷璠“雅调”旨趣
亓颖
【期刊名称】《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2(38)1
【摘要】《河岳英灵集》是诸多唐人选唐诗中最出色的一部,集中所标举的“兴象”“风骨”等选诗标准鲜明地反映了盛唐诗歌创作高峰期的审美标准。
殷璠作为诗选家,自觉对盛唐诗歌进行了多角度的文体审视,集中多用“调”字品评,推崇“雅调”的诗学旨趣。
概括来看,殷璠以“调”审美表现在:声律上,“既闲新声,复晓古体”,重五言古诗,也推重对仗精工的律句;格调上,承袭汉魏风骨,提倡兴象玲珑,力求“词与调合”,推崇清逸自然。
这既是对初唐“以复古求新变”的延续,也是近体声律发展的必然趋势。
“雅调”不仅是盛唐人殷璠诗学体系的重要部分,更在明清时期发展为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
【总页数】11页(P14-24)
【作者】亓颖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相关文献】
1.从《河岳英灵集》看殷璠的诗学思想
2.从《河岳英灵集》选诗看殷璠"兴象"说的理论内涵
3.知音伟笔铸英灵--从殷璠《河岳英灵集》探讨盛唐文人的心路历程
4.
从殷璠《河岳英灵集》诗学旨趣论盛唐诗学之文质观5.由《河岳英灵集》看殷璠对陶渊明的接受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殷璠的兴象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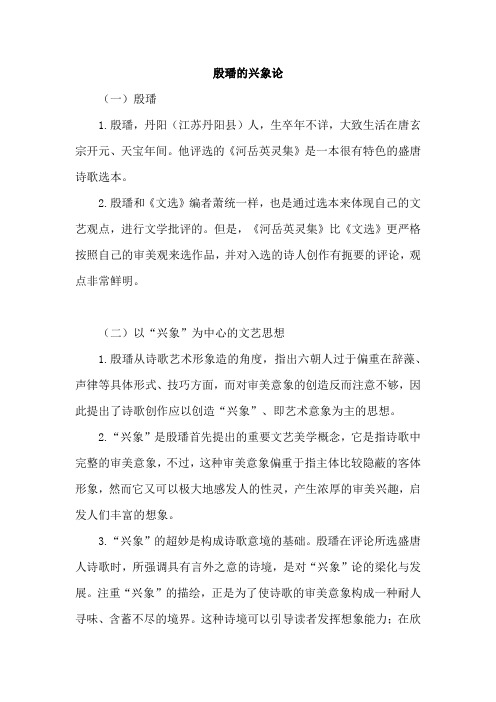
殷璠的兴象论(一)殷璠1.殷璠,丹阳(江苏丹阳县)人,生卒年不详,大致生活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
他评选的《河岳英灵集》是一本很有特色的盛唐诗歌选本。
2.殷璠和《文选》编者萧统一样,也是通过选本来体现自己的文艺观点,进行文学批评的。
但是,《河岳英灵集》比《文选》更严格按照自己的审美观来选作品,并对入选的诗人创作有扼要的评论,观点非常鲜明。
(二)以“兴象”为中心的文艺思想1.殷璠从诗歌艺术形象造的角度,指出六朝人过于偏重在辞藻、声律等具体形式、技巧方面,而对审美意象的创造反而注意不够,因此提出了诗歌创作应以创造“兴象”、即艺术意象为主的思想。
2.“兴象”是殷璠首先提出的重要文艺美学概念,它是指诗歌中完整的审美意象,不过,这种审美意象偏重于指主体比较隐蔽的客体形象,然而它又可以极大地感发人的性灵,产生浓厚的审美兴趣,启发人们丰富的想象。
3.“兴象”的超妙是构成诗歌意境的基础。
殷璠在评论所选盛唐人诗歌时,所强调具有言外之意的诗境,是对“兴象”论的梁化与发展。
注重“兴象”的描绘,正是为了使诗歌的审美意象构成一种耐人寻味、含蓄不尽的境界。
这种诗境可以引导读者发挥想象能力;在欣赏过程中实现再创造。
(三)创作出有言外之意的“兴象”的诗歌1.殷璠认为应当有“风骨”(1)他评高适诗说:“多胸臆语,兼有气骨。
”又说崔颢的诗:“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
”论陶翰的诗:“既多兴象,复备风骨。
”这些対于风骨的理解,大体和钟所说的“建安风力”,以及刘勰论建安诗的“慷慨多气”是一致的。
(2)殷璠对“风骨”的理解还有另一方面的含义,即是指超然物外、避世隐居那种仙风道骨般的飘逸之气。
2.殷璠认为“兴象”超远的作品,应当具有“神来,气来,情来”之妙(1)“神来”,是要求“兴象”塑造必须以神似为主,而达到形神并重之妙。
(2)“气来”,是要求“兴象”具有生机盎然的特点,表现描写对象内在的生命活力,昂扬的精神状态。
(3)“情来”,则是强调“兴象”中应寄寓有作者充沛的、强烈的感情,能够感染读者,它是幽远深厚的、又是非常自然真实的。
孔子诗教观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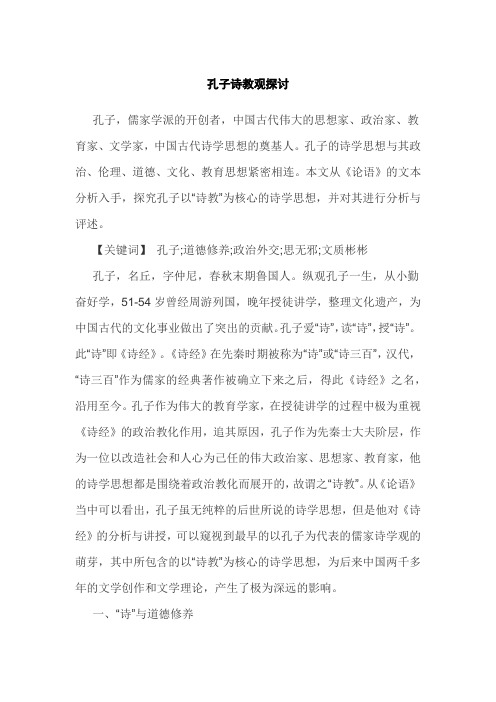
孔子诗教观探讨孔子,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奠基人。
孔子的诗学思想与其政治、伦理、道德、文化、教育思想紧密相连。
本文从《论语》的文本分析入手,探究孔子以“诗教”为核心的诗学思想,并对其进行分析与评述。
【关键词】孔子;道德修养;政治外交;思无邪;文质彬彬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
纵观孔子一生,从小勤奋好学,51-54岁曾经周游列国,晚年授徒讲学,整理文化遗产,为中国古代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孔子爱“诗”,读“诗”,授“诗”。
此“诗”即《诗经》。
《诗经》在先秦时期被称为“诗”或“诗三百”,汉代,“诗三百”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被确立下来之后,得此《诗经》之名,沿用至今。
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学家,在授徒讲学的过程中极为重视《诗经》的政治教化作用,追其原因,孔子作为先秦士大夫阶层,作为一位以改造社会和人心为己任的伟大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诗学思想都是围绕着政治教化而展开的,故谓之“诗教”。
从《论语》当中可以看出,孔子虽无纯粹的后世所说的诗学思想,但是他对《诗经》的分析与讲授,可以窥视到最早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诗学观的萌芽,其中所包含的以“诗教”为核心的诗学思想,为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诗”与道德修养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的重视源于儒家,孔子崇尚道德,孔门四科中“德行”科注重弟子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完善。
孔子大约从30岁开始收授弟子,在他的教育生涯中,诗礼乐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被视为达到最高人格境界的途径。
如何进行道德修养?《论语·泰伯》中记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指出了道德修养的三个层面,首先应该先学诗,而后以礼来立身,最后用音乐完善人性。
礼乐文明的创立者是周公姬旦,“礼乐”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是社会秩序和谐的标志。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礼乐文化无法适应变革时代的社会要求,礼坏乐崩的局面开始出现,如何对待周代的礼乐文明,也是先秦百家争鸣的议题。
论殷璠《河岳英灵集》对唐诗选本的编辑学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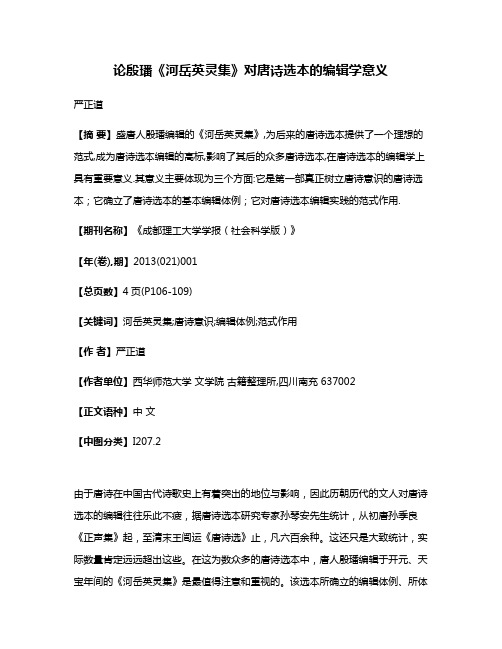
论殷璠《河岳英灵集》对唐诗选本的编辑学意义严正道【摘要】盛唐人殷璠编辑的《河岳英灵集》,为后来的唐诗选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成为唐诗选本编辑的高标,影响了其后的众多唐诗选本,在唐诗选本的编辑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其意义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它是第一部真正树立唐诗意识的唐诗选本;它确立了唐诗选本的基本编辑体例;它对唐诗选本编辑实践的范式作用.【期刊名称】《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21)001【总页数】4页(P106-109)【关键词】河岳英灵集;唐诗意识;编辑体例;范式作用【作者】严正道【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所,四川南充 637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由于唐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与影响,因此历朝历代的文人对唐诗选本的编辑往往乐此不疲,据唐诗选本研究专家孙琴安先生统计,从初唐孙季良《正声集》起,至清末王闿运《唐诗选》止,凡六百余种。
这还只是大致统计,实际数量肯定远远超出这些。
在这为数众多的唐诗选本中,唐人殷璠编辑于开元、天宝年间的《河岳英灵集》是最值得注意和重视的。
该选本所确立的编辑体例、所体现的编辑思想和原则以及编辑理论与实践所达到的高度,都为后来的唐诗选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成为唐诗选本编辑的高标,影响了其后的众多数唐诗选本,因而在唐诗选本的编辑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第一部真正树立唐诗意识的唐诗选本唐诗意识是编辑者对唐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独特地位与价值的判断,可以说它就是唐诗选本的灵魂,而第一部真正体现并树立这种意识的唐诗选本就是《河岳英灵集》。
从武德初到开元、天宝,唐诗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嬗变发展,已经完全摆脱了齐梁诗歌的影响,自铸新风,盛唐气象隐然形成,如殷璠所说“武德初,微波尚在。
贞观末,标格渐高。
景云中,颇通远调。
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1]然而在殷璠之前,尽管已经有人编辑出了各种诗歌选本,包括通代和断代的,但能够准确反映唐诗这种创作实践的却几乎没有,说明当时的一般编辑者或者缺少识力,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唐诗的独立价值,或者意识到了但无法准确把握并通过选诗表达出来,进而树立全新的唐诗意识。
殷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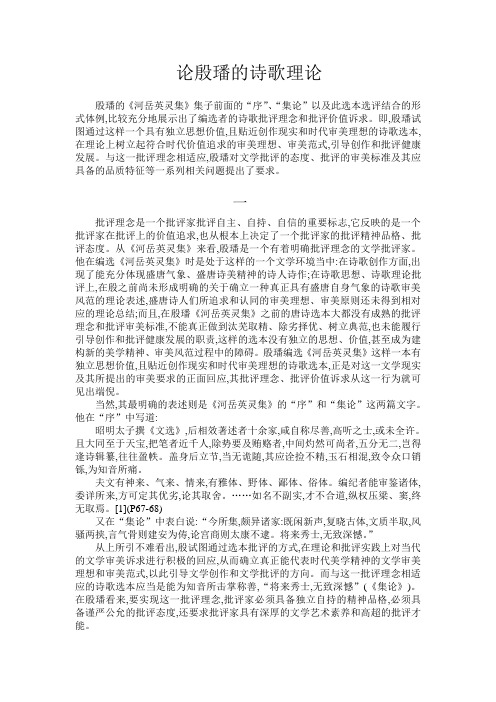
论殷璠的诗歌理论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集子前面的“序”、“集论”以及此选本选评结合的形式体例,比较充分地展示出了编选者的诗歌批评理念和批评价值诉求。
即,殷璠试图通过这样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价值,且贴近创作现实和时代审美理想的诗歌选本,在理论上树立起符合时代价值追求的审美理想、审美范式,引导创作和批评健康发展。
与这一批评理念相适应,殷璠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批评的审美标准及其应具备的品质特征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提出了要求。
一批评理念是一个批评家批评自主、自持、自信的重要标志,它反映的是一个批评家在批评上的价值追求,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批评家的批评精神品格、批评态度。
从《河岳英灵集》来看,殷璠是一个有着明确批评理念的文学批评家。
他在编选《河岳英灵集》时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文学环境当中:在诗歌创作方面,出现了能充分体现盛唐气象、盛唐诗美精神的诗人诗作;在诗歌思想、诗歌理论批评上,在殷之前尚未形成明确的关于确立一种真正具有盛唐自身气象的诗歌审美风范的理论表述,盛唐诗人们所追求和认同的审美理想、审美原则还未得到相对应的理论总结;而且,在殷璠《河岳英灵集》之前的唐诗选本大都没有成熟的批评理念和批评审美标准,不能真正做到汰芜取精、除劣择优、树立典范,也未能履行引导创作和批评健康发展的职责,这样的选本没有独立的思想、价值,甚至成为建构新的美学精神、审美风范过程中的障碍。
殷璠编选《河岳英灵集》这样一本有独立思想价值,且贴近创作现实和时代审美理想的诗歌选本,正是对这一文学现实及其所提出的审美要求的正面回应,其批评理念、批评价值诉求从这一行为就可见出端倪。
当然,其最明确的表述则是《河岳英灵集》的“序”和“集论”这两篇文字。
他在“序”中写道: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称尽善,高听之士,或未全许。
且大同至于天宝,把笔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贿赂者,中间灼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岂得逢诗辑纂,往往盈帙。
盖身后立节,当无诡随,其应诠捡不精,玉石相混,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
《河岳英灵集》选评李颀诗及其诗歌史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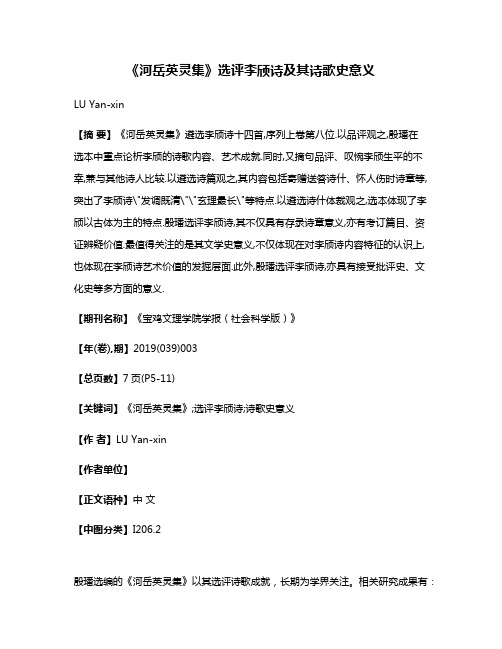
《河岳英灵集》选评李颀诗及其诗歌史意义LU Yan-xin【摘要】《河岳英灵集》遴选李颀诗十四首,序列上卷第八位.以品评观之,殷璠在选本中重点论析李颀的诗歌内容、艺术成就.同时,又摘句品评、叹惋李颀生平的不幸,兼与其他诗人比较.以遴选诗篇观之,其内容包括寄赠送答诗什、怀人伤时诗章等,突出了李颀诗\"发调既清\"\"玄理最长\"等特点.以遴选诗什体裁观之,选本体现了李颀以古体为主的特点.殷璠选评李颀诗,其不仅具有存录诗章意义,亦有考订篇目、资证辨疑价值.最值得关注的是其文学史意义,不仅体现在对李颀诗内容特征的认识上,也体现在李颀诗艺术价值的发掘层面.此外,殷璠选评李颀诗,亦具有接受批评史、文化史等多方面的意义.【期刊名称】《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9(039)003【总页数】7页(P5-11)【关键词】《河岳英灵集》;选评李颀诗;诗歌史意义【作者】LU Yan-xin【作者单位】【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殷璠选编的《河岳英灵集》以其选评诗歌成就,长期为学界关注。
相关研究成果有:李珍华、傅璇琮合著《河岳英灵集研究》、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下文称王《注》)、拙文《〈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1]《殷璠〈河岳英灵集〉的诗歌批评方法及其意义》[2]《论〈河岳英灵集〉选诗与品评相结合的编集体例》[3]等等。
然而,已有的成果对殷璠所遴选的悲怨诗人,如李颀等,尚有待于深入研究。
李颀为盛唐名家,是殷璠心目中的“英灵”。
在《河岳英灵集》中,无论是选诗数量,还是品评内容,抑或是编集排序,李颀都是这部选本中值得关注的诗人。
一、《河岳英灵集》评李颀诗及其特点殷璠评李颀曰: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秀,杂歌咸善,玄理最长。
至如《送塈道士》云:“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
”又《听弹胡笳声》云:“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
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
高中语文 2022年江苏省淮安市楚州中学高考语文适应性试卷(5月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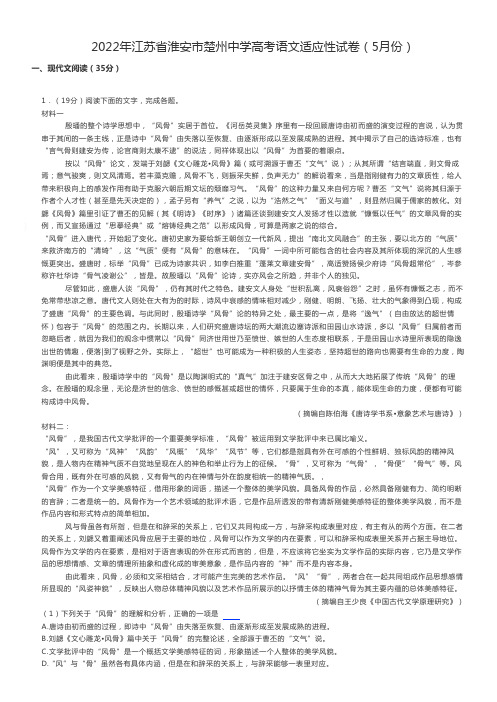
2022年江苏省淮安市楚州中学高考语文适应性试卷(5月份)一、现代文阅读(35分)1.(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殷璠的整个诗学思想中,“风骨”实居于首位。
《河岳英灵集》序里有一段回顾唐诗由初而盛的演变过程的言说,认为贯串于其间的一条主线,正是诗中“风骨”由失落以至恢复、由逐渐形成以至发展成熟的进程。
其中揭示了自己的选诗标准,也有“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官商则太康不逮”的说法,同祥体现出以“风骨”为首要的着眼点。
按以“风骨”论文,发端于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或可溯源于曹丕“文气”说);从其所谓“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的解说看来,当是指刚健有力的文章质性,给人带来积极向上的感发作用有助于克服六朝后期文坛的颓靡习气。
“风骨”的这种力量又来自何方呢?曹丕“文气”说将其归源于作者个人才性(甚至是先天决定的),孟子另有“养气”之说,以为“浩然之气”“面义与道”,则显然归属于儒家的教化。
刘勰《风骨》篇里引证了曹丕的见解(其《明诗》《时序》)诸篇还谈到建安文人发扬才性以造就“慷慨以任气”的文章风骨的实例,而又宣扬通过“思摹经典”或“熔铸经典之范”以形成风骨,可算是两家之说的综合。
“风骨”进入唐代,开始起了变化。
唐初史家为要给新王朝创立一代新风,提出“南北文风融合”的主张,要以北方的“气质”来救济南方的“清绮”,这“气质”便有“风骨”的意味在。
“风骨”一词中所可能包含的社会内容及其所体现的深沉的人生感慨更突出。
盛唐时,标举“风骨”已成为诗家共识,如李白推重“蓬莱文章建安骨”,高适赞扬侯少府诗“风骨超常伦”,岑参称许杜华诗“骨气凌谢公”,皆是。
故殷璠以“风骨”论诗,实亦风会之所趋,并非个人的独见。
尽管如此,盛唐人谈“风骨”,仍有其时代之特色。
建安文人身处“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之时,虽怀有慷慨之志,而不免常带悲凉之意。
唐代文人则处在大有为的时际,诗风中哀感的情味相对减少,刚健、明朗、飞扬、壮大的气象得到凸现,构成了盛唐“风骨”的主要色调。
《河岳英灵集》在唐诗学史上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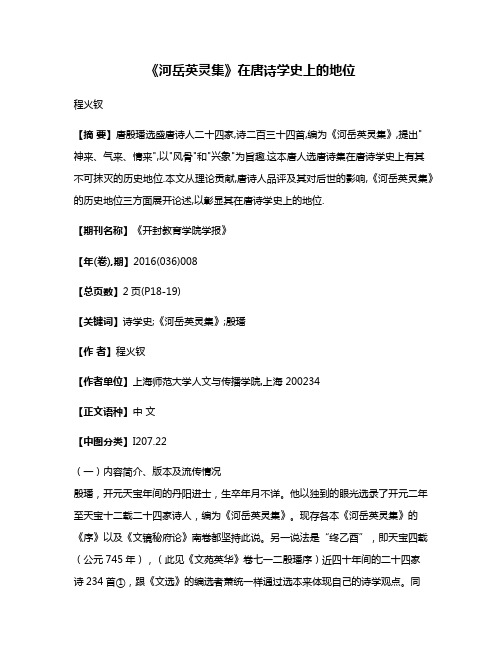
《河岳英灵集》在唐诗学史上的地位程火钗【摘要】唐殷璠选盛唐诗人二十四家,诗二百三十四首,编为《河岳英灵集》,提出"神来、气来、情来",以"风骨"和"兴象"为旨趣.这本唐人选唐诗集在唐诗学史上有其不可抹灭的历史地位.本文从理论贡献,唐诗人品评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河岳英灵集》的历史地位三方面展开论述,以彰显其在唐诗学史上的地位.【期刊名称】《开封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36)008【总页数】2页(P18-19)【关键词】诗学史;《河岳英灵集》;殷璠【作者】程火钗【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2(一)内容简介、版本及流传情况殷璠,开元天宝年间的丹阳进士,生卒年月不详。
他以独到的眼光选录了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载二十四家诗人,编为《河岳英灵集》。
现存各本《河岳英灵集》的《序》以及《文镜秘府论》南卷都坚持此说。
另一说法是“终乙酉”,即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此见《文苑英华》卷七一二殷璠序)近四十年间的二十四家诗234首①,跟《文选》的编选者萧统一样通过选本来体现自己的诗学观点。
同时,他对入选各家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作了简洁评价,不乏精辟之见,齐艺术观点和选诗标准在《序》与《集论》中都已表露无遗。
《河岳英灵集序》中说诗选共分两卷,至宋代不少人沿用此说法,如宋刻本(国图藏本有清季振宜题款,另一种有清莫友芝校)。
但从明代开始,却著录成三卷,如明嘉靖刻《唐人选唐诗》六种本。
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是三卷,致使之后大多数人都以为是三卷。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也都著录为两卷,而明代毛晋、清何焯都曾有手抄本为两卷本。
因此,有学者认为今本三卷是后人“推测其意似以三卷分上中下三品,并非编著者原意”。
《河岳英灵集》版本繁多,目前,宋刻本、明善本、汲古阁本、日本文正本和清代几个版本在国图都有留本,通行的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收入《唐人选唐诗(十种)》中。
殷璠《河岳英灵集》诗学思想述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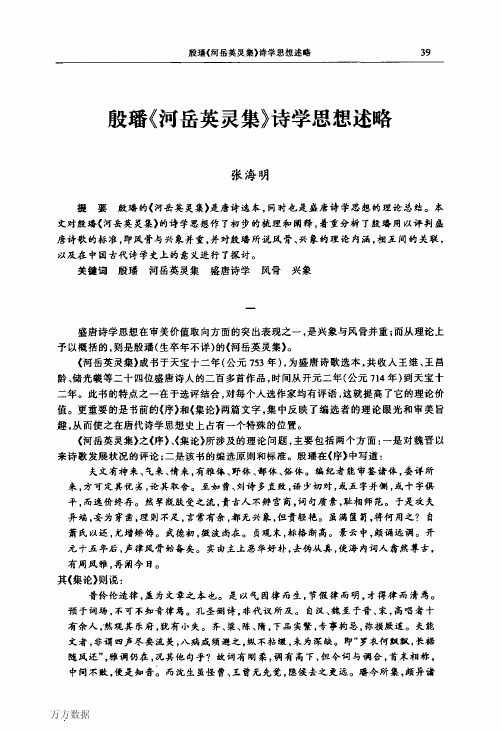
殷瑶所谓声律、风骨兼备,其实也就是《河岳英灵集》的主要人选标准。《集论》说得非 常清楚:“瑶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 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这正可为声律、风骨兼备作一注脚。同时,它很容易令人想到杜 甫“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的主张;而诗“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云云,也与
。
杜甫:(戏为六绝句)。
万方数据
42
《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
规律有着深人了解的理论家,刘勰并没有像大多数复古主义者那样,将质朴文风与华美文 风截然对立,或用文学的政教功能去否定文学的审美功能,而是尽可能将二者统一起来, 从而既肯定了文采的必要性,同时又避免了为形式而形式的偏颇。刘勰之所以标举风骨, 就是为了从理论上阐明诗文之美不独在声律辞藻,作品所表现所情志以及由此所产生的 感染力才是更为根本的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心雕龙・风骨)中,刘勰并投有明确将风骨与壮美风格联系起来, 尽管他所用的某些比喻不无刚健的意味,但若就刘勰的本意而言,提出风骨绝不是为了倡 导壮美文风。这不难由《风骨)全文的基本思想看出,也可以从他举的两个例子一一司马 相如的<大人赋)和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得到证实o。 钟嵘<诗品・序》提到的“风力”,也与刘勰所说风骨相关。<诗品・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诗有三义焉:一日兴,二日比,三日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 事,寓意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昧之者无极,闻之 者动心,是诗之至也。”钟蝾此论所可注意者有三:一是他以“风力”为诗之主干,以“丹采” 为诗之润饰,这与刘勰说的“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以及取譬鹰隼、雉鸡正相一致;二是 钟蝾认为兼备“风力…‘丹采”的诗作,能够令读诗者砰然心动,回昧无穷,这也与刘勰不谋 而合;三是钟嵘将“兴”与“风力”联系起来,虽然在表述上尚欠明朗,但可以断定是将“兴” 视为诗歌“风力”的重要根源。这一点尤具特殊意义,因为钟蝾与刘勰的一个重要差异,是 他专论五言诗,所以他只讲“风力”而不及“骨力”,应该说,就纯粹的文学作品而论,以兴为 文学审美要索的基本构成,较之刘勰所说情志,无疑更加确切。 回溯刘勰、钟嵘所说风骨及相关概念的意义在于更好地认识唐人对此思想的继承与 发展。显然,当陈子昂感慨“文章道弊五百年”而提出恢复“汉魏风骨”时,他实际上是把风 骨作为矫正绮靡文风的有力武器,希望借此改变“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文学创作现 状;当杨炯批评龙朔文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时,他所不满的也正是上官仪等人的诗作 “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缺乏能够感染人打动人的思想情感。所以,在标举风骨以强调作 品内窖性因素这一点上,初唐诗家与刘勰等人的看法并无不同。 初唐诗家对风骨范畴的发展,主要是使先前潜在的壮美意味明朗化,从而丰富了风骨 的内涵。这或许与初唐诗文创作的实际情况相关:一方面,从初唐四杰开始,边塞诗逐渐 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而边塞诗正以刚健豪迈、雄浑壮阔为基本特色。无论是诗 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还是边塞大漠荒原的自然景物,乃至沙场征战的金戈铁马,都为 壮美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也促成了诗人对壮美风格的偏爱。另一方面,既然那种单纯 追求形式技巧的诗作具体表现之一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那么壮美理所当然地成为救 治文风萎弱的良方,而陈子昂对东方虬(修竹篇)的称誉:“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 有金石声”,也就自然被视为优秀诗作必备的特征。换句话说,从矫正绮靡文风的角度来 看,充实的内容和刚健的风格,与风骨便有了一种天然的联系。 此外,初唐诗家尤其是四杰对于诗歌创作中感兴的重视,似乎也和风骨不无关联。因 为从根本上说,诗歌之壮美风格的形成,首先得力于作者强烈的感受和浓郁的情思,至于 相应的表现形式,那是第二位的。故王勃(山亭思友人序)道:“思飞情逸,风云坐宅于笔
《河岳英灵集》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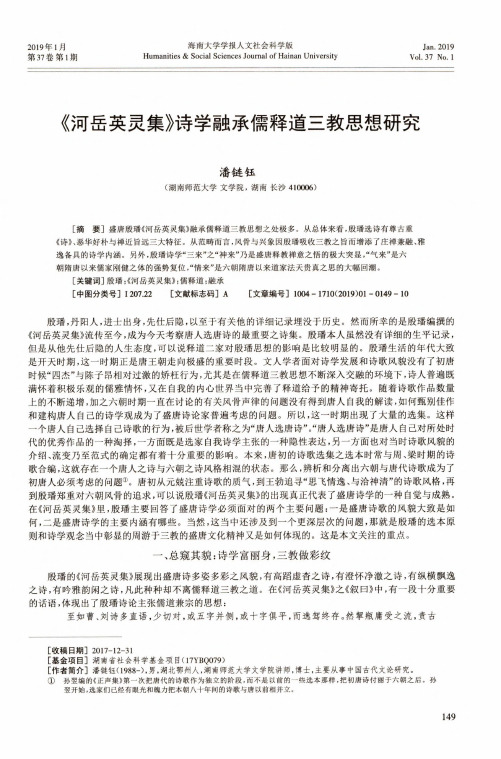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2019年1月第37卷第1期Jan. 2019Vol. 37 No. 1《河岳英灵集》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潘链饪(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06)[摘要]盛唐殷墙《河岳英灵集》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之处极多。
从总体来看,殷皤选诗有尊古重《诗》、恶华好朴与禅近旨远三大特征。
从范畴而言,风骨与兴象因殷皤吸收三教之旨而增添了庄禅兼融、雅逸备具的诗学内涵。
另外,殷皤诗学“三来”之“神来”乃是盛唐释教禅意之悟的极大突显,“气来”是六朝隋唐以来儒家刚健之体的强势复位,"情来”是六朝隋唐以来道家法天贵真之思的大幅回潮。
[关键词]殷舔;《河岳英灵集》;儒释道;融承[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 - 1710(2019)01 - 0149 - 10殷躋,丹阳人,进士出身,先仕后隐,以至于有关他的详细记录埋没于历史。
然而所幸的是殷躍编撰的 《河岳英灵集》流传至今,成为今天考察唐人选唐诗的最重要之诗集。
殷躋本人虽然没有详细的生平记录, 但是从他先仕后隐的人生态度,可以说释道二家对殷躍思想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殷皤生活的年代大致 是开天时期,这一时期正是唐王朝走向极盛的重要时段。
文人学者面对诗学发展和诗歌风貌没有了初唐 时候“四杰”与陈子昂相对过激的矫枉行为,尤其是在儒释道三教思想不断深入交融的环境下,诗人普遍既 满怀着积极乐观的儒雅情怀,又在自我的内心世界当中完善了释道给予的精神寄托。
随着诗歌作品数量 上的不断递增,加之六朝时期一直在讨论的有关风骨声律的问题没有得到唐人自我的解读,如何甄别佳作 和建构唐人自己的诗学观成为了盛唐诗论家普遍考虑的问题。
所以,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选集。
这样 一个唐人自己选择自己诗歌的行为,被后世学者称之为“唐人选唐诗”。
《河岳英灵集》及传世版本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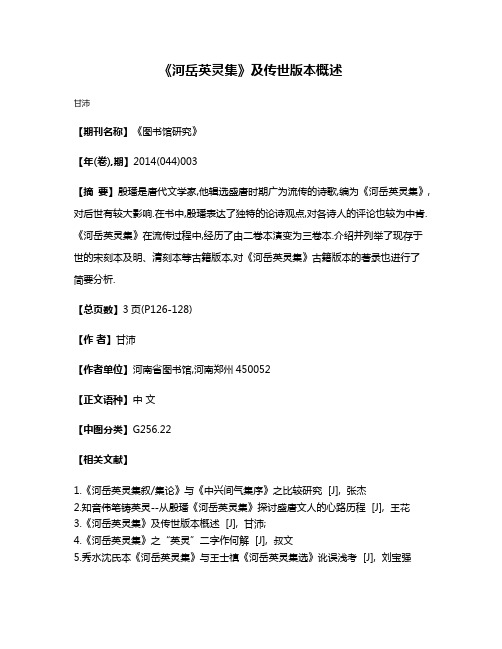
《河岳英灵集》及传世版本概述
甘沛
【期刊名称】《图书馆研究》
【年(卷),期】2014(044)003
【摘要】殷璠是唐代文学家,他辑选盛唐时期广为流传的诗歌,编为《河岳英灵集》,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在书中,殷璠表达了独特的论诗观点,对各诗人的评论也较为中肯.《河岳英灵集》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由二卷本演变为三卷本.介绍并列举了现存于世的宋刻本及明、清刻本等古籍版本,对《河岳英灵集》古籍版本的著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
【总页数】3页(P126-128)
【作者】甘沛
【作者单位】河南省图书馆,河南郑州45005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6.22
【相关文献】
1.《河岳英灵集叙/集论》与《中兴间气集序》之比较研究 [J], 张杰
2.知音伟笔铸英灵--从殷璠《河岳英灵集》探讨盛唐文人的心路历程 [J], 王花
3.《河岳英灵集》及传世版本概述 [J], 甘沛;
4.《河岳英灵集》之“英灵”二字作何解 [J], 叔文
5.秀水沈氏本《河岳英灵集》与王士禛《河岳英灵集选》讹误浅考 [J], 刘宝强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专题08 论述类文本阅读专训(2)-2022年高考语文一轮复习之现代文阅读(学生版)

论述类文本阅读专训(2)(学生版)时间:40分钟分值: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唐人选唐诗中有的选录杜诗,有的并不选录杜诗,这种情况是杜甫研究的重要命题,以杜甫同时代作家作品为收录范围的三种诗选,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和主潮,《箧中集》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动向,这些是当时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
杜诗亦在这三部诗选入选范围之内,却都先后意外落选。
原因何在?《河岳英灵集》(殷璠)是被认为最能代表盛唐诗歌理想的诗选,盛唐诗坛重要人物基本入选其中。
杜甫当时诗歌创作数量也不少,却没有引起诗坛和殷璠的注意、除了进入长安较迟、年资不深这一客观因素之外,主要原因应是杜诗本身的问题,即其内容、艺术风格和当时主流风尚并不一致。
如深受今人赞美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借写景而喻时事,乃至“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
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的高自标置,反而不如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人的即景写实、淡定优雅,杜诗“沉郁顿挫”风格不太符合殷璠气象高华、“风骨”与“声律”兼备的要求。
从安史之乱爆发到终老于江湘,正是杜甫创作高峰,在杜诗佳作不断涌现之时诞生的两部诗选《箧中集》和《中兴间气集》中却仍难觅杜诗踪影,原因何在? 元结于《箧中集》序虽称“尽箧中所有,总编次之”,其实并非没有严格的入选标准。
元结序主张“雅正”,肯定入选作者“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元结文学思想明显是盛唐“别调”,并非主流,正好和杜甫比较接近,然细审之,杜甫其人其诗并不完全吻合其选人、选诗之标准。
杜甫曾为左拾遗,并非“正直无禄位”“忠信而久贫贱”者,且杜诗主题与单纯歌咏个人苦难也不一致,他们关注个人疾苦,而杜甫则忧国忧民,杜诗虽歌咏个人苦难,但往往推己及人,这种精神正是杜甫超越《箧中集》诸子之处。
据卢燕新考察,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选诗标准为“体壮风雅,理致清新”“朝野通取,格律兼收”。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殷《河岳英灵集》诗学思想述略张海明提 要 殷的《河岳英灵集》是唐诗选本,同时也是盛唐诗学思想的理论总结。
本文对殷《河岳英灵集》的诗学思想作了初步的梳理和阐释,着重分析了殷用以评判盛唐诗歌的标准,即风骨与兴象并重,并对殷所说风骨、兴象的理论内涵,相互间的关联,以及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殷 河岳英灵集 盛唐诗学 风骨 兴象一盛唐诗学思想在审美价值取向方面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兴象与风骨并重;而从理论上予以概括的,则是殷(生卒年不详)的《河岳英灵集》。
《河岳英灵集》成书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为盛唐诗歌选本,共收入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位盛唐诗人的二百多首作品,时间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到天宝十二年。
此书的特点之一在于选评结合,对每个入选作家均有评语,这就提高了它的理论价值。
更重要的是书前的《序》和《集论》两篇文字,集中反映了编选者的理论眼光和审美旨趣,从而使之在唐代诗学思想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河岳英灵集》之《序》、《集论》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魏晋以来诗歌发展状况的评论;二是该书的编选原则和标准。
殷在《序》中写道: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
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
至如曹、刘诗多直致,语少切对,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而逸价终存。
然挈瓶肤受之流,责古人不辨宫商,词句质素,耻相师范。
于是攻夫异端,妄为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
虽满箧笥,将何用之?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
武德初,微波尚在。
贞观末,标格渐高。
景云中,颇诵远调。
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人翕然尊古,有周风雅,再阐今日。
其《集论》则说:昔伶伦造律,盖为文章之本也。
是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
预于词场,不可不知音律焉。
孔圣删诗,非代议所及。
自汉、魏至于晋、宋,高唱者十有余人,然观其乐府,犹有小失。
齐、梁、陈、隋,下品实繁,专事拘忌,弥损厥道。
夫能文者,非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纵不拈缀,未为深缺。
即“罗衣何飘飘,长裾39殷《河岳英灵集》诗学思想述略DOI :10.15990/j .cn ki .cn11-3306/g2.2003.02.004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
将来秀士,无致深惑。
不难看出,如何认识和评价齐、梁以来诗歌的格律化倾向,是殷讨论问题的切入点。
这是极其自然的,格律问题所以成为唐代诗家一直关注的对象,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与唐诗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格律化是近体诗得以成熟的必由之径,舍此之外别无它途;但另一方面,过分追求格律化,为形式而牺牲内容,则必然会妨碍诗歌的健康发展。
以是之故,从初唐到盛唐,格律始终是诗家谈论的热门话题,当然也就成为唐代诗学的重要内容。
至于殷所论,如果孤立地看,似乎不过是折衷调和,但实际上更应看作是对先前观点的一种超越。
无论是他对诗歌声律的有限度的肯定,还是他对过分强调声律的批评,都与初唐人有所不同。
具体些说,相对于初唐四杰,殷对诗歌声律的肯定要明确得多,他公开承认“预于词场,不可不知音律”;而相对于上官仪、元兢等人,殷又不是那么琐碎细微。
“夫能文者,非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纵不拈缀,未为深缺”。
殷的态度是颇为通达的。
他有一些表述我们似曾相识,如:“故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
”这与钟嵘《诗品序》所说“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确实如出一辙。
然而,从钟嵘到殷,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已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回环。
正是在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础上,殷对魏晋以来诗歌发展的状况作了概述。
如果说他对齐、梁文学的看法仍沿袭了初唐诗家的观点,那么对于入唐以后诗歌的发展,殷则作出了自己颇有见地的评判:“武德初,微波尚在。
贞观末,标格渐高。
景云中,颇诵远调。
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殷在此指出:唐代诗歌由初唐到盛唐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逐渐克服齐、梁诗风的负面影响,由单纯追求声律到转向注重格高调远,最后达到声律和风骨并重的过程。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殷此论的意义在于准确地勾勒出这一时期诗歌发展不同阶段各自的特征;而从诗学思想的角度来说,则可以看作是殷对初唐以来诗歌审美价值取向的一个总结。
我们知道,初唐魏徵曾提出合南北文学之长、宫商词义并重的主张①,令狐德也希望能够形成一种“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的新的文风②,但在当时,这还仅仅是一种理想,直到进入盛唐阶段以后,这一理想才真正落实成为现实的存在。
所以,殷《河岳英灵集》的出现是一个标志,它表明由初唐开始的诗风的嬗变至此已告一段落,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盛唐诗歌的确呈现出了新的风貌。
殷之所以将入选作品的年代限定在开元二年到天宝十二年之间,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时段内的作品最能代表这种新的风貌。
二殷所谓声律、风骨兼备,其实也就是《河岳英灵集》的主要入选标准。
《集论》说得非常清楚:“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
”这正可为声律、风骨兼备作一注脚。
同时,它很容易令人想到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的主张;而诗“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云云,也与40《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杜甫所说“别裁伪体亲风雅”不无相通①。
这种相通相似当然并非偶然,它恰好说明声律与风骨并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时代共同的审美取向。
不过,声律、风骨兼备尚不能完全概括盛唐诗歌的特色,也不是殷用以选择评判诗作的所有标准,在殷对具体作家的评论中,与声律、风骨兼备相似的还有另一种表述,那就是兴象、风骨并重。
如评陶翰诗:既多兴象,复备风骨。
兴象与风骨并举,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但兴象具体当作何解,其与风骨、声律又是什么关系,殷并未加以界说。
这就需要我们对之进行分析,探求上述诸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各自的理论内涵,并结合唐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合理的解释,以期更好地认识殷的诗学思想及其在唐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意义。
先看风骨。
好诗须有风骨,这在初唐诗学思想中已有所强调,如杨炯《王子安集序》称龙朔初载文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谓“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而四杰等人的创作也如闻一多《唐诗杂论》所说由“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风格趋于开阔壮大。
这表明随着对六朝绮靡文风批判的深化,风骨开始成为初唐人有意追求的诗学理想。
但风骨一词却非唐人的发明,作为一个专门的文论术语,风骨可以追溯到齐、梁时期的刘勰。
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中,“风骨”单列一篇,其重视程度于此可见。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刘勰说得很清楚:“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
”风骨是构成优秀诗文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足以决定文章的高下成败。
那么,刘勰为什么将风骨摆到如此重要的位置呢?从《风骨》篇全文来看,刘勰所说的风骨,大抵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风骨是作者情志的外在表现,是作品能够对读者产生影响的关键。
用刘勰的话说,风骨是“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
这就是说,风骨之于诗文的作用恰如翅膀之于征鸟,是其得以广为传播并影响后世的根本原因。
由于《文心雕龙》兼论文笔,所以刘勰又将风骨一分为二,风指文学性(抒情性)作品所特有的艺术感染力,而骨则指实用性(论证性)作品所特有的逻辑说服力。
第二,就风骨与作品形式的关系而言,风骨是作家选择相应形式的出发点,也是文辞章法的内在结构。
刘勰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这表明在刘勰看来,风骨对于作品的形式因素具有决定意义,或者说,形式技巧的运用必须遵从表现风骨的原则。
第三,风骨与文采共同构成作品的审美要素。
对此刘勰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夫翟备色,而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
文章才力,有似于此。
若风骨乏采,则鸷聚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
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如果将文采视为诗文外在的美,那么风骨便是诗文内在的美,只有风骨而无文采或只有文采而无风骨,都不免于缺憾,理想之作应该是风骨与文采兼备。
由此看来,风骨所以在《文心雕龙》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原因主要在于刘勰对当时文学现状的态度:一方面,刘勰承认由质朴到华美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视文学的发展而要求退回到古代,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对于当时文坛出现的片面追求声律辞藻的弊病,刘勰又深感不满,希望能有所矫正。
作为一个对文学史和文学创作、鉴赏41殷《河岳英灵集》诗学思想述略42《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规律有着深入了解的理论家,刘勰并没有像大多数复古主义者那样,将质朴文风与华美文风截然对立,或用文学的政教功能去否定文学的审美功能,而是尽可能将二者统一起来,从而既肯定了文采的必要性,同时又避免了为形式而形式的偏颇。
刘勰之所以标举风骨,就是为了从理论上阐明诗文之美不独在声律辞藻,作品所表现所情志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感染力才是更为根本的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心雕龙·风骨》中,刘勰并没有明确将风骨与壮美风格联系起来,尽管他所用的某些比喻不无刚健的意味,但若就刘勰的本意而言,提出风骨绝不是为了倡导壮美文风。
这不难由《风骨》全文的基本思想看出,也可以从他举的两个例子──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和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得到证实①。
钟嵘《诗品·序》提到的“风力”,也与刘勰所说风骨相关。
《诗品·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意写物,赋也。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钟嵘此论所可注意者有三:一是他以“风力”为诗之主干,以“丹采”为诗之润饰,这与刘勰说的“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以及取譬鹰隼、雉鸡正相一致;二是钟嵘认为兼备“风力”“丹采”的诗作,能够令读诗者砰然心动,回味无穷,这也与刘勰不谋而合;三是钟嵘将“兴”与“风力”联系起来,虽然在表述上尚欠明朗,但可以断定是将“兴”视为诗歌“风力”的重要根源。
这一点尤具特殊意义,因为钟嵘与刘勰的一个重要差异,是他专论五言诗,所以他只讲“风力”而不及“骨力”,应该说,就纯粹的文学作品而论,以兴为文学审美要素的基本构成,较之刘勰所说情志,无疑更加确切。
回溯刘勰、钟嵘所说风骨及相关概念的意义在于更好地认识唐人对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显然,当陈子昂感慨“文章道弊五百年”而提出恢复“汉魏风骨”时,他实际上是把风骨作为矫正绮靡文风的有力武器,希望借此改变“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文学创作现状;当杨炯批评龙朔文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时,他所不满的也正是上官仪等人的诗作“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缺乏能够感染人打动人的思想情感。
